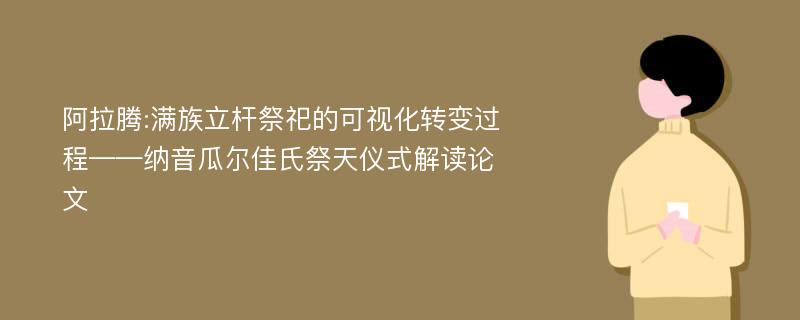
摘要:立杆祭祀是满族春秋大祭的重要内容,其缘起及所祭神灵,研究人员持不同观点。通过纳音瓜尔佳氏祭天仪式细节的解读,可揭示满族立杆祭与北方游牧民族相关祭祀的内在联系。在萨满前往他界旅行的框架内,立杆祭纳入游牧民族祭天内容,并以祭祀牲猪的方式将其可视化,从而使具巫术性质的祖宗观念转变为一种宗教信仰。
关键词:满族;天祭;立杆祭
对满族“立杆祭”或“还愿祭”之起源及所祭神灵,满学研究者众说不一。定宜庄认为,杆祭习俗起源于神树崇拜,满族建国之后才将杆祭纳入民族共同体,其要素大多来自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新满洲”祭祀仪式,从中可以找到从神树崇拜过渡立杆祭祀的某些特点。该祭祀适应了满族从森林渔猎到定居农耕的变迁过程,伴随满族社会变化及萨满文化发展,从祭祖演变为祭天,成为满族初兴时期统治者的思想武器。[1]其后张杰将不同学者的观点总结为以下两种:其一,祭天说。如,张佳生在其《满族文化史》中提出:“在满族,将杆子立在祭天仪式中代表神位,人称神杆。在某些地区还保留着以树祭天的记忆。”[2]其二,祭乌鹊说。如,阎崇年《满洲神杆及祀神考源》认为:“满洲神杆及奉祀之神,缘起于满洲先民祭祀神树及其栖食之神鸟——乌鹊,每年春秋,乌鹊群噪,设肉、米于斗中以享之。尔后缘习成礼,岁时祀享乌鹊。”[3]张杰则通过分析堂子祭神演变与满族起源传说,并结合赫哲族习俗认为,满族祭祀的神杆应为“祖宗杆”,即祭祖,而非前述的“祭天”与“祭乌鹊”。[4]这几种观点,似乎强调定氏观点的不同侧面,并未展开实质性分析。然而,定宜庄有关从祭祖演变为祭天,进而成为满族统治者思想武器的观点更具启发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纳音瓜尔佳氏,隶属于正黄旗佛满洲,今冠以汉字“关”为姓。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修谱时,记述本氏族“祭祀规则”,编纂谱书,1937年续修谱书时将其印刷成册。本谱书现收藏于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及农安县等地关氏成员家中。[5]138纳音瓜尔佳氏祭祀分为前日的白日祭祖、白日祭神、夜晚祭神及次日的院心祭神等几个部分。
巴菲特投资法则中就有非常重要一条:如果股票因“非经营性”因素大幅下跌,那是绝佳的投资机会。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大股东股票质押爆仓是否牵涉到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如果股价只是被大势拖累,那投资者可以观察,可以等待,但更要看到这也许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瓜尔佳氏院心祭神仪式需要事先准备的器具及食物类有以下几种。
昔年满族人家,院心均有影壁,设立祖宗杆子(满语名曰索拨力棍),上有锡拉碗。目下无影壁者居多。祭祀时,先砍一杨木杆,长约七尺,粗二寸余。木杆头,用刀砍如锥形,用谷草一束,绑于杆梢上。新碾小米半斗,净水一大碗。在风门里横放高桌一张,上摆三盅净水,一碟小米。(1)纳音瓜尔佳氏祭祀流程均出自何晓芳,张德玉:《满族历史资料集成》(民间祭祀卷),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
解剖心肝,用膛血涂抹杆子顶部的做法,使人觉得繁琐。因为完全可以用杀猪时放出的血液,涂抹杆子顶部。这一繁琐程序可以用牺牲动物种类解释。如上所述,此时牺牲物的原型为羊。游牧民宰羊,通常在羊肚上划开口子后伸进手掐断动脉,羊血留在腔体内部,在开膛之前,血液不会流出来。于是,仿照此类情景,杀猪也开膛之后用胸膛里血液涂抹杆子顶部。当然,膛血与心肝等内脏发生关联,不排除从中汲取某种生命力的考虑。接下来,祭祀礼仪将关注祭肉的解剖顺序及生熟的分别。达哈拉即肚囊肉一块置于方盘内;肠、肚、心、肝、胆为一组,除胆囊不能食用外,其余则留出一部分后,投入锅内。梭子骨可代表动物的关键之处。骨头部分亦取一部分,其余都被投入锅内。这样,留下来没煮的部件皮、头、部分内脏、肚囊肉及带骨肉,被重新构建造型。
主祭人率族中人,二次行礼已毕,仍旧将碟内之米、盅内之水扬之,水盅扣放。次将高桌抬到院心影壁地方,遂将祖宗杆子搭在桌上,木尖向南,将锅放在三块石上,用木柈燃着,烧水,以备煮肉需用也。
先将猪皮放妥,次将猪首摆于猪皮底下,再摆脖圈,刀口向上。其大梁骨、二乌叉、后乌叉,均以头骨向下,所留大小肠、心、肝等均放于当中,左右两块肋条肉、前后四只腿,均骨头向下摆之,将猪尾尖割一小截,放于供桌上,余剩猪尾连于猪皮之上也。
设齐,主祭人率同族人在桌里向外行叩首礼,起身将碟内小米摄三摄扬于外。次将东头盅内之水亦扬于外,将盅扣放,二人抬桌至院心。随行大锅一口,方盘内放尖刀两把、笊篱一把、铁勺子一把、刷帚一把、水瓢、肉墩等物至房门外西边。地放寸板,上放方盘相连,用板凳一个,上放木杆一根,架起,用毯子一条,搭于杆上(满语名曰蒙古波,即今之帐房也)。
于我个人,2016年春天至今,一直是病痛的。更准确地说,这种病痛是从2011年开始的。完全不怪别人,是自己在治疗胃病时,无意识地吃错了药,导致了抑郁症及伴生的胃炎、窦性心律不齐等等。那段时间,头晕、心悸、情境障碍、四肢发软、意识模糊和混沌,等等,使得我九死一生。至2017年夏天,这种症状稍微缓解。但到秋天,又罹患轻度萎缩性胃炎。有人说,这是很常见的病,还有的说,这是不死的癌症……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无关紧要,萎缩性胃炎会癌变,这才是真的。
摆设齐整,将猪抬至桌上,其猪牝牡均可。猪首向南,蹄向西,而杀猪之人跪一单腿。杀完,将猪血盆放在高桌上,候血凝结,取血三勺,倒于锅内,遂将猪之四蹄割下,四梢挑开,将皮剥下。其猪首解下,不剥皮,用火烧烤。猪皮剥完,上祭毕,亦火烤之。先取肋肌肉两条,次解前两腿里面肉两条,放于锅内。再解后两腿里面肉两条及哈拉巴,放于盘内。如牡猪,将猪鞭子取下,放在供桌上,接解达哈拉。
接着开始牲猪处理程序。牲猪“牝牡均可”,说明该程序与动物繁衍并无关联。猪首向南,蹄向西,与宫廷祭祀做法一致,“司俎太监等转猪首向西,置于包锡大桌上省之。司俎太监二举银里木槽盆接血,列于高案上,猪气息后,转猪首向南顺放。”[6]祭祀向南,与前一节扬米、扬水及族人行礼方向一致。从单纯操作角度看,猪被“抬至桌上”,宰杀牲猪时“跪一单腿”,显得不太得力。该姿另有他意,根据场景设置判断,牺牲动物原型并非是猪,而是羊。宰羊一般放在地上,单腿跪地便于操作。宰杀后将血盆放在高桌上,虽然在等候血液凝结,但也可理解为在供献。取血三勺,意味着多数。割下猪蹄、挑开四梢、剥下猪皮,与宫廷内“司俎等即于院内去猪皮”相同,[6]都属于异于寻常的宰杀方法。在本氏族前一天的祭祖、祭神及背灯祭等环节中,牲猪都以煺毛的方式处理,剥皮模仿了羊皮的处理方式。在游牧民的祭祀仪式中,羊皮被剥下来后留作他用,与祭祀活动毫无关联。而猪皮,不论在平日,还在前日所举行的祭祀环节当中,都在煺毛后与猪肉一起食用。猪皮从猪身上剥下,必须经过去毛处理才能食用。去毛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火烤,然而,烧烤去毛的程序并不是单纯的料理过程,而是被视为祭祀仪式的关键环节,其中蕴含着特定意义。结合祭祀场所空间的建立及祭祀人、族人的行为方式就可知道,此时牺牲动物正在某种场景中接受某种历练。在历练中,火烤是一项重要内容,使人联想拣选萨满候选人的历练。萨满候选人必须经历阴间磨难,才能获得萨满本领,成为正式萨满,如,上刀山下火海等。根据雅库特人神话,“有一群精灵把未来的萨满带到地狱,将他关在一间屋子里长达三年。就在那里,他接受了入会礼:精灵割掉他的头,放在一边(因为新萨满必须亲眼观看自己被大卸八块),然后把她的身体剁成碎片,再将碎片交给掌管各种疾病的精灵。”[8]955虽然不能将这里的牺牲物直接看作被拣选的萨满,但在经历某种特殊的程序之后才能进入一种新状,二者思维模式是一致的。
至心肝处,见有膛血,一人手拿祖宗杆子,而解猪之人将心血掏出,抹在杆子尖上,约有尺余即可。唯达哈拉解下,再由当中取五寸长、三寸宽肉一条,放于方盘,其余置于锅内,次将肠、肚、心、肝取出,猪胆放在高桌上,煮肝肺各一叶,猪心半块,留大肠半截,小肠一根,猪肚半截,其余碎油、小肠等放于锅内,再将猪首脖圈内之梭子骨剔出煮之。大梁骨由前数之,取三根断一块,取两根断一块,左边腰子一个,左边肋条骨,由前头取三根,右肋取两根,一并放于锅内,其余之肉,以备摆件子之需也。
其中,影壁为永久性设施,无需临时准备。祖宗杆子,即“索拨力棍”,满语称subarhan,蒙古语称suburga,语义为“塔”。在瓜尔佳氏族人心中,“祖宗杆子”并非一根“杆子”,而是复杂的设施,祭祀活动是围绕着“塔”展开的。有了“塔”,萨满便可援之攀到各层次的“天”。 “锡拉”,满语称siltan,是指杆子,锡拉碗即杆上之碗,并非碗,而是hiyase“斗”。祭祀时砍的杨树木杆,尺寸无定则,临到堂子祭祀时,“于洁净山内,砍取松树一株,长二丈,围径五寸,树梢留枝叶九节,余皆削去制为神杆”。[6]木杆顶部砍成锥形,使其显“塔”状。谷草一束,绑在杆梢上,便于其中撒米。新碾小米半斗,强调“新”字,与农业祭祀有关。净水一大碗,涉及到水。据伊利亚德研究,每种与水联系都意味再生,水能增强创造潜能。[7]风门里摆高桌一张,表明祭祀空间的边界在大门处,空间范围此时包括了整个院落。三盅净水之“三”表明多数,一碟小米代表种子或新收获的谷物。
主祭人,多为氏族萨满,担任祭祀活动主持任务,由其率领族人,通过礼仪程序实现与超自然力量的交流。在祭祀活动中,萨满不进入失神状态,通过礼仪程序完成与神灵的交流。由于家萨满受过专门训练,能熟知繁琐的程序,展现权威的力量。主祭人及族人从桌里向外叩首,说明高桌在该空间中处于境界的位置,向外扬去碟里的小米,意味着神灵在境界之外。在宫廷祭祀里,此礼节被分为两次进行,“司俎满洲进,向前立,捧米碟洒米一次,祷祝祭天毕,又洒米二次。”[6]向外扬出东头盅内的水,扣放水盅,强调水已不存在,避免盅里进入异物。“二人抬桌至院心”时,空间范围发生变化,与神灵交流的通道被临时关闭。由此大锅、方盘、笊篱、铁勺、刷帚、水瓢及肉墩等与牺牲动物有关的器具才得以出现。各种器具搁置于房门外西边,于是神圣空间就被扩大到整个院落范围。寸板放在地上,上放方盘,是在复原野外原始场景。用板凳、木杆及毯子搭成的设施,族人将其称为“蒙古波(包)”。宫廷祭祀与此一致,“离神杆石稍远西北方设红漆架一,架上覆以红毡”。[6]经过布置,建立游牧民野外祭祀场景。
煮熟的猪肉切成片状,而肠、肚、碎油等剁碎之后熬煮。在宫廷里,“司俎等向东列坐于木盘后,颈骨供于高案西边所设银碟内,胆贮于东边所设银碟内,细丝小肉成后盛小肉丝二碗,各置箸一双,稗米饭二碗,各置一杯,从东向西,饭肉相间以供。”[6]在超自然空间里,作为牺牲物的猪被“碎成万段”。如上所述,只有在他界里被这样处置以后,牺牲物或萨满才能得到新生,候补萨满才能变成正式萨满或获治病救人的本领。方盘里放置两个瓷盆,显示前来接受牺牲物的神灵来自东西两个方向。在阿尔泰语系民族萨满信仰中,除最高的“长生天”外,还有99尊“天”。其中,东方的天为44尊黑色的天,属于恶天,西方的天为55尊白色的天,属于善天。(2) 参见道尔吉·班扎罗夫:《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 (第十七辑),1965年。先捞三下,置于东头盆内,意味着东方的神灵被优先祭奠,然后才是西方神灵。下面程序亦遵循同样原则,先东后西,且祭献供品的数量显出薄厚:东方的是大梁骨及三根肋条,西方的则为达哈拉,在主祭人或族人的心目中,东方神灵居上。当然,除东西方向的神灵外,还有南方的神灵,而该神灵的地位最高,东西方的神灵为次级职能神。从性质上看,本环节祭祀仪式除了主神以外,还关注各方神灵,亦可算作过渡程序。
越秀把孩子捆绑在背后,把丈夫的尸体就地埋了,又把狗皮道人和五趾上人埋在一个坑里。越秀再去拖丈夫那个同伴时,听到有人说话,赶紧背着儿子跑了。
将肉煮熟时,成块肉用刀片之,肠、肚、碎油等物放于菜墩上剁碎,放于锅内煮一小时。二人抬一方盘,上放瓷盆两个,用笊篱先捞三下,置于东头盆内,次捞三下,置于西头盆内,将锅内剁碎之肉捞尽,两盆分盛之。各盆放筷子一双,再将大梁骨、三根肋条,放于东头盆内,骨梢均向北。将梭子骨肉剔净,放于供桌上。其屋内煮饭之时,有先有后,先捞一大碗,放于东头,次捞一大碗,放于西头,各碗放小木匙一个。末后,将达哈拉扣于西头盆上,各肉盆浇三勺汤,均供献于桌上。
主祭人率族人行礼及抛撒米、水的仪式,虽然看似仍在原地执行,但由于场景已经重新设置,在空间上与前一仪式并不相同。将高桌抬到院心影壁处,将祖宗杆子搭其上面,祭祀重心便集中到杆子。杆尖向南,意味着祭祀对象位于南方,是本次祭祀的主要方位。三块石头垒起的临时锅灶,在显示此处是游牧世界“蒙古波”外面空间。
仪式进入摆件程序。虽然程序用预留部件摆出造型,但注重摆件的先后顺序。放好猪皮后,以猪头、脖圈、大梁骨、前腿、后腿的顺序,从头部开始渐次往后摆设。造型部件不够齐全,但能显示全猪形状。这与宫廷处置方法基本相同,“先以颈骨连精肉取下,并择取余肉煮于红铜锅内,余俱按节解开,列于银里木槽盆内,置首于前,以皮蒙盖其上,南向,顺放于包锡大案上,肠脏修整后亦贮于木槽盆内,以盛血木槽盆横放于盛肉木槽盆之前”。[6]从“刀口向上”“骨头向下摆之”来看,此时牲猪是仰面躺在桌上的。这让人联想被拣选的萨满前往阴间期间,躺在帐篷里数日不动的情景。如,雅库特萨满在前往地狱的旅程中,躺在帐篷里,“毫无知觉,几乎没有生气,长达三天至九天”。[8]955猪尾巴尖割取小截放在供桌上,象征猪并不齐全,虽然身体大部分已经来到场地,但尚有部分仍未到达。通过此手法,显示猪在途中,或象征猪的不完整,需要超自然力量将其补全,等待神灵最后添补。在此显示出一种矛盾,明知猪身大部分已在锅里,但将猪尾一部分切除后供在桌上,以此象征猪体的不完全。
祭品摆齐,主祭人率领行叩首礼,毕,仍将小蝶米摄三摄扬之,将第三盅水扬出,毕,再将杨木杆拿来。此等方法,情因昔年各族院心均有影壁,前设一松木杆,上有锡拉碗,敬盛诸物之用,今砍一杨木杆,系从全办理,以做致祭之用品。遂将猪尾梢,扫小蝶米于草把上。一切零物,摄三摄肉,三匙饭,亦放于草把上绑好。次将梭子骨,宽面向下,套于杨木杆上,将此杆暂绑于高桌腿上而立之,等候送骨头之时,一并送之也。
生产区负责下辖大队生产管理安排和协调工作,配合供应贸易部调度,一部分运送新洋分公司仓储中心烘干入库,一部分直接由苏垦米业调拨销售,一部分大华种业烘干收购,一部分大队烘干种子自存,流程规范标准有序,场头周转顺畅。
祭品摆齐后,意味着主要祭祀活动正式展开。主祭人率众叩首,扬米、扬水。此行为可视为犒劳各种禽兽神灵。在《尼山萨满》中,尼山萨满携带大酱前往阴间索取依赖儿子的灵魂时,将大酱当做赏物。[9]这礼节要重复进行,是场景及对象变换的缘故。虽然场地看似并未变换,但搬来木杆时,空间已发生变化。至于杆子的材质,虽然之前为永久性的松树木杆,而当下为临时性的杨树木杆,但性质未曾发生变化。猪尾梢及小蝶米被置草把,先前准备的物品于是显示其用处——一件器具或身体部件总能够发挥不止一种功能,或者说可尽量使其发挥更多功能。除尾梢外,其他零碎肉屑及饭食都被绑在草中。套在木杆上的梭子骨,其宽面朝下,表明牺牲的头是朝外朝上的。木杆祭祀结束后与猪骨一同送走,显示由木杆的临时性特征而发生的文化变迁。
祭毕,先将锅内汤取出,下留两瓢,将东盆肉、东盆饭放于锅内,加上作料,众人食用。如若剩饭,送与外人吃,不准拿入屋内。端西头肉盆先行,拿饭碗人随后行之。用二人抬汤盆到屋,放在正房西炕西北角。西炕放一方盘片肉,其猪首、猪皮及蹄在外烤好,随肉拿至屋中煮熟,将骨头剔净,候众人吃毕,名曰送骨头。先将炕、地扫净,猪肉锅刷净,一人拿杨木杆,并门上草把,送于江河边或野外均可。唯有骨头,抛在影壁后,刷锅水及所有尘秽,弃于门外可也。
(2)实践教学环节不能满足工程化要求。目前数据库实践课程教学主要采用验证式的实验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比较注重学生单个技能的培养,对数据库技术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综合应用缺乏系统的讲解与训练,致使学生能理解基本概念,却无法在具体项目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进行综合设计及开发。
祭祀仪式进入收尾阶段。虽然“祭毕”,但与神灵的交流并未结束,族人分享东边盆子里供奉东方神灵的肉及饭,西边盆子里的肉及饭则供献居于西北日落方向的祖灵,也可以理解为未曾动用过的食物供献给祖宗。猪头、猪皮及猪蹄烤好之后在屋内锅里熬煮。这些部件在游牧民祭祀中的处置比较随意,因而进一步说明,瓜尔佳氏祭祀活动中的猪是游牧民祭祀活动的羊之变体。将骨头剔净,原本涉及狩猎民或游牧民祭祀禁忌,游牧民在日常饮食习惯中亦严格遵守。禁止丢弃食物被视为一种美德,在更深层次观念中,这人类与“动物之主”建立良好关系有关。根据猎人和游牧民有关与超自然存在之间的互惠关系,人类只有小心对待,动物才被食用后返回人间。因此,不论是狩猎民,还是游牧民,都十分留意动物骨头的干净与完整。骨头被抛影壁处,与此处最接近“动物之主”有关,只有这里才能通往他界。接下来扫净屋内和刷净锅碗,都在强调对动物的尊重,以便牺牲物在他界传达人类的善行。杨树木杆,原本是永久性设立的松树木杆,但由于环境变迁,祭祀方式亦发生变迁,在祭祀结束后将其处理。门上的草把,是举办祭祀活动之前用来告知他人的标志,自然被认为其中已经附着来源不明的超自然存在,同样祭祀活动结束时予以毁弃。在藏传佛教庙会上,事先会准备被当作“象征、征兆”的草把。该草把在查玛跳神过程中一直竖立在会场,等仪式结束就会将其烧掉,以去除聚集于其中的晦气。瓜尔佳氏祭祀的草把与藏庙上的草把出于类似的思维模式。
定宜庄指出,立杆祭是在满族建国之后的产物,其源头在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一带“新满洲”的树祭。其实祭树是广泛存在于北方民族当中的祭祀仪式,都是一种对于打破均质空间里的标志物所倾注特别情感的行为。纳音瓜尔佳氏立杆祭祀仪式内容更多源于游牧民族类似的祭祀活动,如,大树祭祀、天神悬杆祭祀、敖包祭祀等。类似祭祀活动是北方民族相通的祭祀模式,在中国古籍里亦多有记载。在这种祭祀模式下,各民族依据所处生态环境及生计活动方式,选择不同的物质材料,形成各具特色的祭祀礼仪。纳音瓜尔佳氏的院心祭神即立杆祭便是在萨满前往他界旅行的框架内,添加适合于自身生计活动的内容而形成的。通过祭杆时场景的设置、牲猪的处理及摆设等一系列方式,立杆祭使原本不可视的萨满旅程变得具有可视性且可操作化,完成族人对于愿景的构建。
村小组代表大会应该制定并通过章程(村规民约),这是村自治的基础,关系到全体村民利益。因此在制定的时候,应最大限度听取村民意见,并保证顺利实施。村民小组代表大会还可以聘请一名专业的法律顾问,为其提供法律指导和帮助,进一步规范权力行使。
参考文献:
[1]定宜庄.神树崇拜与满族的神杆祭祀[J]. 北方民族,1989,(1).
[2]张佳生.满族文化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575.
[3]阎崇年.满学论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64.
[4]张杰.清代满族萨满教祭祀神杆新考[J].社会科学辑刊,2003,(5).
[5]何晓芳,张德玉.满族历史资料集成(民间祭祀卷)[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
[6]允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G]//刘厚生.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41-214.
[7]Mircia Eliade.PatternsinComparativeReligion. New York: Seed & Ward, Inc.1958: 188-189.
[8]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M].吴晓群,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9]荆文礼,富育光.尼山萨满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388.
TheVisualTransformationProcessofManchu’sRodSacrifice:InterpretationofNayinGuardian’sSacrificialCeremony
ALTA
(Institute of Manchu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The pole ritu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nchu Spring and Autumn Festival. The origin of the festival and the spirit of the sacrifice, the researchers hold different view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ails of Nayin Guardian’s rituals, it can reveal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nchu pole festival and the sacrifices of the northern nomad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haman’s travel to the world, the pole festival is included in the nomadic sacrifices and is visualized in the way of sacrificing the pigs, thus transforming the ancestral concept of witchcraft into a religious belief.
Keywords:Manchu; nomadic sacrifices; the pole ritual
收稿日期:2019-04-30
作者简介:阿拉腾(1962-),男(蒙古族),内蒙古锡林郭勒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8BMZ045)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19)01-0140-05
标签:祭祀论文; 满族论文; 木杆论文; 萨满论文; 杆子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满语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MZ045)论文; 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