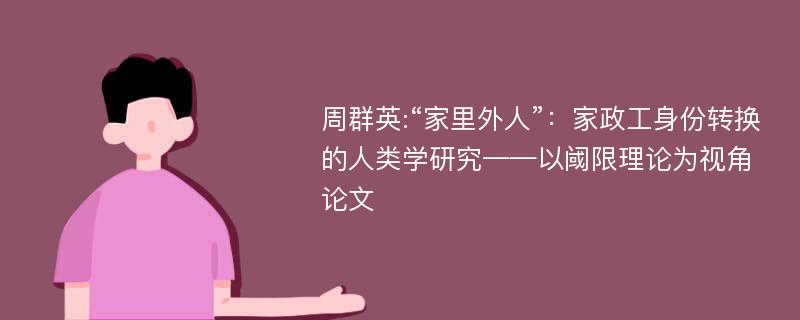
摘要:中产阶级和家政工因家务分工而相遇,她们在家庭功能上相互补充文化上相互分离。家庭成为身份转换和阶层划分的微观政治场域。本研究提出“雇主为什么不敢得罪保姆、她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怎样的转换、阶层边界如何划分?”的问题。研究发现:既养又育的工作特性使家政工成为“阈限人”,其身份转换为“家人”;阈限主体从“家务分工”和“育儿风格”两方面界定阶层边界,构建家政工“外人”的等级秩序。研究得出:尽管“交融”是周期性和暂时性的,地位逆转的阈限并没有消解社会结构的等级,但却有缓和阶层矛盾、实现社会结构有序运行的功能,即使这种改变发生在道德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关键词:家里外人 家政工 身份转换 阈限
一、研究缘起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城市女性为缓解“贤妻良母”的性别规范与职场女性面临的“照料危机”(crisis in care)间的冲突,通过雇佣保姆分担家务。家政行业门槛低、就业机会多成为农村女性进城打工的首选。中产阶级和家政工因为家务劳动而相遇。在中国,农村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象征方式上都保持比城市落后的他者地位。[注]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人口流动被视为一场从贫穷和边缘进入到现代和中心的运动。[注]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建》,袁长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页。流动人口被视为城市社会秩序的外来者和威胁者。[注]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45页。“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通常从事家政、小商贩、工人等职业。家政女工因为农民和性别的双重弱势使她们成为流动人口中的“二等公民”,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弱势群体。媒体关于家政工虐待婴儿和老人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对家政工的恐慌。个别家政工的越轨行为延伸为行业的道德缺陷,家政服务被污名化,家政工被塑造为“道德缺陷”的流动人口。
然而,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不一致的客观事实。雇主描述说,她们“不敢得罪阿姨”“对阿姨就像‘家里人’一样”“我很尊重她”“一定要对她好”“我买礼物给她”“主动给她涨工资”等被主流社会界定为“弱势群体”和“道德缺陷”的家政工,在家庭场域中如何与雇主互动?雇主为何不敢得罪她?家政工的社会地位真低吗?在什么情境下家政工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转换?劳雇双方在家庭微观场域形成了怎样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中,双方分别采取什么策略和行动?后现代学者近年来打破了研究者价值中立的迷思,强调研究和写作必须从特定的文化与社会情境出发。[注]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第417页。基于这样的立场,本文聚焦于家政工的工作场域(即家庭内部)和互动过程,引入阈限理论探究家政工的身份地位转换,指出既养又育、家务分工和育儿风格是家政工“家里外人”身份地位的生成机制,进而指出,中产阶层和社会底层间的地位高低和权力强弱在特定的场域内互为转换,底层身份地位的逆转有助于阶层矛盾的缓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即使这种改变发生在道德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中青家政[注]遵从学术惯例,调查所在公司和文中所有人名均已做匿名处理。是一家全国家庭服务百强企业,公司成立于1994年。笔者调查所在的西直门店坐落在西直门北大街45号某小区的底层,于2008年成立并单独运营。服务内容包括家务料理、育婴早教、月子护理、病老陪护、涉外服务、小时工等。笔者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是访谈。访谈地点在包括公司的门店和员工宿舍。被访者的选择通常是笔者先和公司王老师[注]“老师”是家政工对公司工作人员的称呼。王老师从西直门店成立之初便加入,已在此工作10年。沟通,由她推荐不同类型和工作时长的访谈对象。被访者一是保姆,包括住家保姆、非住家保姆、固定日工和临工[注]笔者访谈的临工包括两种:一种是利用休假时间接临时活的家政工,另一种是秋收后进城找活的临时工。,尤其以前两种类型为主;二是雇主,以教师、医生、公务员、白领等中产者为主;三是家政工公司工作人员。需要指出的是,家政工是学术界的表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她们常常被称为“保姆”或“阿姨”,三种表述方式在本文中通用。虽然被访者在不同阶段照顾过老人或做过家务保洁,甚至在周末休息时偶尔接份“临工”,但目前从事的工作以育儿为主,即育儿家政工或“育儿嫂”。
倘若让我俩教语文和数理化,不说胜任,还算凑合,教农业技术?乖乖!简直是擀面杖吹火!事已至此,别无他法,我们赶紧买了几本农业方面的书,也正经八百地认真备课写教案,还预先分好工:我教《农机具管理和使用》,巴克夏教《农作物栽培》。我知道来上课的肯定不少。因为报上曾刊登了某地致富后,城市姑娘下嫁农村的消息,把这儿的小伙子的心撩拨得痒痒的。
二、阈限理论:考察家政工身份转换的重要视角
回顾和梳理家政工相关研究,其分析路径有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和情感劳动等。劳动关系视角关注全球化背景和城市化进程中劳雇双方的不平等,并同时融入权力、性别、阶层、城乡、种族等理论视角。[注]Emily Abel and Margaret Nelson,eds.,CirclesofCare:WorkandIdentityinWoman’sLives,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朱影:《西方女性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页;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第5-10页。有论者认为家政工因性别弱势,受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被迫入行。[注]Emily Abel and Margaret Nelson,eds.,CirclesofCare:WorkandIdentityinWoman’sLives,p.6.蓝佩嘉对雇主与家政工的研究表明二者间存在明显的种族和阶层界限。[注]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第3-60页。国内学者从“问题—解决”范式出发,指出家政工在结构社会存在诸多问题,从结构(赋权)和个体(增能)两方面提出应对策略。“问题”论者指出“处于失语状态的保姆们”面临诸多不公,其根源是公共支持系统的缺失。[注]杨书:《“消费的城市”与“边缘”的“她们”》,《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马丹:《北京市家政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张琳:《人口新常态背景下农村家政女工生存与发展现状调研》,《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赋权”论者揭示家政工的权益受到挤压,主张完善法律和制度以保障其合法利益。[注]郭慧敏:《家政女工的身份与团结权政治》,《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6期;郭慧敏:《城市妇女住房权:被挤压的空间诉求》,《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5期;王竹青:《论家政工的劳动权利》,《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6期。“增能”论者关注家政工的专业技能和社会网络,主张提升其技能和重构其社会支持网络。[注]李春霞:《内生性社会网络:成因、影响与差异》,《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李春霞:《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社会网络的建构分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中药材品种繁多,目前北柴胡、荆芥、桔梗等含挥发油的药材共选育出了225个优良新品种,其中已有164个新品种得到了推广。中药材品种审定、鉴定、认定或登记工作正逐步走向管理科学、严谨、可靠的规范化轨道,但也存在对于新品种的种类界定不明确,驯化自野生、引种自其他地区、农家品种、育成品种兼顾不足等问题[23]。所以,有必要制定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相关政策法规,确保药用中药材品种一致,从而有效减少中药挥发油的质量差异。
通过本文研究成果的试点、探索、改进,辅助某市级供电企业初步构建配网主动运维检修工作机制,有效降低了配网故障事件发生、提升了供电服务质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果说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视角主要关注家务劳动的经济意义,那么,持“情感劳动”视角的学者强调家务劳动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注]朱影:《西方女性研究》,第55页。情感劳动概念最早由亚莉·霍奇斯柴德提出,她指出服务业的劳动者将情感出卖给资方,资方通过组织规则来管理和操纵劳动者的情感。[注]亚莉·R·霍奇斯查德:《情绪管理的探索》,徐瑞珠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47-55页。苏熠慧分析了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及其内部张力,指出情感劳动的维系是需要条件的,当不同主体的育儿理念与知识发生冲突时,当劳动关系存在不平等和冲突时,情感劳动难以维系甚至瓦解。[注]苏熠慧:《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转换机制》,《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许捷认为家务劳动中感情与道德投入的价值长期被低估,“保姆荒”暴露了市场失灵要求重新评估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注]许捷:《“保姆荒”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分析》,《学术交流》2011年第7期。
下面是贾女士的一日工作安排:
对于家有幼儿且无老人帮忙的中产家庭来说,即使对保姆存在诸如道德缺陷、照顾不周等忧虑,从家政公司聘请阿姨的安排仍不失为最佳次优方案。雇主希望可以在工作的同时,让孩子在母亲不在场的状态下仍享有关怀和照顾。事实上,中产家庭雇佣阿姨照顾小孩或钟点工料理家务已成为刚性需求。理想的保姆被期待无微不至照顾孩子生活的同时能将爱、情感与温暖投注在孩子身上。保姆被寄予“母职”的期望,可以从道德、知识和能力各方面培养孩子。[注]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而这些正是在这类职位的体系中对社会职位的担任者的要求。[注]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94-95页。为了确保照护工作的品质,雇主以“策略性手段”建构保姆“家里外人”的角色。一方面通过营造“家一般”氛围的策略,接纳保姆为“家人”,通过“虚拟亲人”的身份掩盖不平等的雇佣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家务分工”和“育儿风格”有意识构建隐形的阶层差异和公私界限,小心翼翼地使用雇主权威,打造保姆“外人”的角色。
我在小说中加入了卡莱尔在德克萨斯州考古并挑战了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关于人类大陆迁移是从亚洲穿过白令海大陆桥到达北美洲的学说,这是有寓意的。他们对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不感兴趣,既乐观又自信的他们只想每一代、每一日都重新起步向前走。以这样的思想背景去观照美国的传统,必须脱开中国人“慎终追远”“毋数典忘祖”的历史之思想习惯,才能把握美国式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场战争的一切偶然与必然。
阈限理论经由“过渡仪式”展现出来,是对前工业社会仪式的时空结构及功能的阐释,被普遍接受为身份地位转化的社会机制。过渡仪式分为“分隔—边缘—聚合”三阶段发展模式。阈限主体在分隔和聚合阶段具有清晰的结构位置。边缘阶段呈“阈限”特征,即通过者的社会地位差异被搁置,他们的身份地位变得模糊,在分类上非此非彼或既此又彼。[注]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仪式》,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页。特纳发展了阈限理论,指出阈限是“模棱两可”的状态和过程,它处于正常或日常的文化和社会状态或过程之间,是结构间的缝隙。在阈限阶段,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各种规范与准则统统失效。[注]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人类学关键概念》,鲍雯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7页。阈限主体借助仪式,颠覆正常社会结构中必须遵守的行为与规范,人们暂时处于平等的“交融”状态中,是“卑微与神圣、同质与同志的混合体”。[注]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仪式中出现“合法化的失礼(licensed disrespect)、规定性的无礼(prescribed immodesty)”式场景。由此,特纳提出了“反结构”概念,指阈限主体暂停社会结构赋予的身份象征,如财产、地位、级别等,他们原先的世俗标签被“剥去”,通过者之间“达到绝对平等”。[注]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109页。也就是说,经由阈限,人们获得共融的体验,这是一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得以建设并经历的过程。[注]潘忠党:《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特纳对阈限阶段的重视、对交融概念的阐释成为仪式理论的重要特色。特纳进一步指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结构,在结构中个人受角色、关系和规则的束缚,有结构就有结构性对立,就会有冲突和不满。身处低位的人试图抗争,高位者也需要释放。在结构性社会中,仪式具有了“净化”结构的作用。阈限阶段的身份混同、结构倒置及高位者纡尊,经过短暂的交融和反结构状态,社会得以重新整合人群,再次回到秩序和结构中。从结构到反结构,再回到结构之中,由此从象征上强化结构,社会结构和秩序得到恢复与重建。
对宏观劳动关系的关注隐喻了对家庭领域微观权力互动关系的忽略。有论者从劳动过程视角分析雇主的控制与家政工的抵抗。[注]苏熠慧:《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社会》2011年第6期。有论者论述家务劳动过程中双方累积了较多不满情绪。雇主抱怨家政工“技能差”“责任心不够”“干活偷懒”等,她们被描述为道德缺陷的客体。[注]冯小双:《转型社会中的保姆与雇主关系——以北京市个案为例》,孟宪范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47页。家政工则认为雇主“挑剔”“看不起保姆”“视为外人”等。[注]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
尽管过渡仪式关注前工业社会,但结构与交融现象普遍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中,特纳就此拓展了阈限理论,使它走出了人生阶段转折等仪式场域,成为解释身份转换、社会冲突和社会运行的有力工具。
《论语》中的恕和忠关系紧密,常以忠恕并提或并列。忠恕的目的是仁,是仁的内容,行恕的目的是体现忠。《论语》指出:“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意是指,孔子讲:“曾参呀!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曾子说:“是的。”孔子走了出去,别的学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先生的学说就是忠和恕罢了。”很清楚,忠恕已成为《论语》道德准则的核心内容。
三、“家里外人”:家政工的身份转换
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引入特纳的阈限理论来讨论家政工的身份地位。毋庸置疑,家政工在明确定义的文化分类(betwixt and between)中处在法律、社会和结构所指定的低阶层位置,但在阈限阶段(雇佣过程中),这种区别与等级消失或同化了,世俗社会结构里的社会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家政工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转变。家政工与雇主形成一个阈限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按等级排位的组织结构,而是超越了等级的、年龄的、亲属位置的混合体。[注]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0页。
(一)阈限与交融:保姆“家人”身份的生成
家庭微观场景中,阈限主体包括保姆和雇主。保姆入住雇主家,进入非常不同的生活状态;雇主因为保姆的帮助从照料危机的无序进入有序状态。保姆和雇主都从原来的结构位置中撤离出来。[注]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95页。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意味着家政工承担了妻子和母亲的部分职责。对职业女性来说,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意味着让渡了部分妻子和母亲的义务。于是,保姆和雇主都离开了与原位置结构相关的价值观、规范、情感以及技术,被剥离了过去的思考、感觉和行动习惯。[注]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105页。
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文化产物,“儿童观念”在20世纪经历了从经济上“无用”到情感上“无价”的社会建构过程。[注]薇薇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王水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社会对儿童的重视也蕴涵着他们对儿童教育的新观念。[注]奥维·洛夫格伦:《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7页。家庭围绕孩子来组织,给予孩子重要的地位。[注]菲利普·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沈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父母们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兴趣花费在儿童教育方面。由于对儿童和教育的双重重视,有关孩子的活动被区隔为生活和教育。父母掌握教育孩子的权力,保姆主要负责生活照料。事实上,保姆每天长时间与孩子接触,为确保孩子的干净整洁,给他们换尿布,训练他们上厕所,给他们擤鼻涕,把他们脸上的食物擦净,陪他们午睡,等等,这些有关卫生、便溺、饮食、作息都带有教育意义,各自责任的边界很难界定。[注]沈奕斐:《个体家庭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266页。概言之,教育和生活互相融合,教育孩子融入在日常生活中。
我姓贾,我感觉多数客户(访谈中,家政工用“客户”一词描述雇主。)期望保姆可以帮助孩子养成规律作息、健康饮食、干净卫生等好习惯。以前有个雇主将孩子的作息要求贴在孩子房间的门上,要求保姆严格执行。我最长的一家干了2年,客户家有姥姥、爸爸和孩子,妈妈在外地工作,回来得少。孩子上幼儿园,主要由姥姥接送,我偶尔也接送。孩子上学我主要做家务搞卫生,孩子放学我主要是陪孩子。爸爸要求孩子规律作息,我每天的时间安排是固定的,每天都差不多。(BJ20181106)
概言之,如果说劳动关系视角强调了关系的不平等,却忽略了劳雇双方的情感投入,这能化解劳动过程中的劳资矛盾,即使她们双方的情感投入脆弱不堪。劳动过程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劳雇双方的控制与抵抗,忽略了劳动过程的交融与隔阂。情感劳动容易被误认为劳动过程的“相敬如宾”,从而忽略了劳动过程的张力与冲突。无论哪种视角都隐喻了家政工在结构上处于“低下”或“边缘”的位置,家政工被建构为弱势群体。
图1贾女士日常工作流程图
从贾女士的工作流程图可以看出,作为住家保姆,她的工作内容以孩子回家为分水岭。孩子上学期间,她主要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中午有三小时的午休时间。孩子回家后,贾女士全方位陪伴孩子。晚饭前,贾女士陪孩子做游戏、读绘本、讲故事。晚饭后,每日给孩子洗澡。临睡前,陪孩子温习压腿压胳膊等舞蹈基本功。孩子爸爸工作忙、经常加班,顾不上教育孩子。姥姥担任了事实上的“家庭主妇”角色,负责照看家庭、指挥保姆。贾女士肩负照料者与教育者双重角色。对贾女士来说,两难的处境是既要把饭菜做得营养可口,又要监督孩子晚餐不能多吃,因为孩子胖且贪吃,这原本是属于母亲的职责。既养又育的工作特性混淆了保姆和母亲的身份特征,她们既是保姆也是妈妈,或者二者皆不是。
如果说家政工在世俗社会结构中有清晰的位置,但在家庭微观互动场景中,家政工被部分或完全地与文化上规定的有序的状态和地位领域隔开,不属于任何一种明确的文化类别,失去了社会模式的固定位置,她们的身份无法被定义[注]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黄剑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7页。,是处在“门槛之处的人”。
在下面刘女士的案例中,低位的保姆扮演了教育者和协调者的角色,本应承担教育职责的父母,因为老大说“你们越护着他(指老二),我就越整他”,不得已出让了教育孩子的权力。刘女士从尽到照顾好老二的职责出发,越俎代庖扮演了教育老大和平衡兄弟关系的角色。
我的客户是医生,她家两儿子。我负责照顾二宝。大宝7岁,刚上一年级,他欺负二宝,抢玩具、打他、掐他、推他。父母为了照顾老大的情绪,纵容老大,看到小的受欺负也不吭气、不作为。二宝哭闹不止,我很为难。客户认为是我没有照顾好老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家里房子小,也没有空间把兄弟俩分开。不得已,我开始当她妈的面教育大宝。刚开始,宝妈不高兴,说“你不能这么说我们老大,老大也是我们的宝”。我说“你们默许大的欺负小的,不干涉不教育,影响了我的工作,要么我教育老大,要么你们另请阿姨”。后来宝妈默许了我教育大宝。老大开始并不听我的,后来我两个孩子一样疼,协调兄弟俩的关系。现在兄弟俩能稍微玩一小会儿了。(BL20181107)
刘女士教育不在其教育职责范围内的老大,雇主默许了刘女士的行为,育儿情境中出现雇主顺从保姆的“合法化的失礼”或“规定性的无礼”等场景,高位的雇主无奈接受了保姆从“照顾者”转换成“教育者和协调者”的身份转换。雇主与保姆犹如进入了“公共域”,结构社会的规范与准则失效,个体等级秩序消失,伴随身份的权力义务区别也消失,母亲与保姆平起平坐,暂处平等的“反结构状态”(anti-structure)中,是“卑微与神圣、同志与异质的混合体”。[注]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100页。
阈限状态结构上的简单性被它文化上的复杂性所抵消。[注]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第102页。潘毅指出,工人是“主动的、灵活的、策略性的行动者”。[注]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0页。作为社会能动者(social agents),家政工身份的“阈限性”意味着其社会地位不再是结构性的,相反,通过“教育者”与“协调者”的角色重新定义了保姆的身份与地位,保姆具有了“母亲”的部分属性,拥有了与“母亲”身份相匹配的社会地位,进而获得社会地位的暂时性提升。[注]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第186页。
此外,家政公司从身份转换与知识重构两方面对家政工进行培训。[注]苏熠慧:《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转换机制》,《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在培训中,培训者有意唤起家政工的“母亲”身份,让她们通过换位思考,将劳雇关系转换为家人关系,通过“想象”照顾自己孩子的情境来对待客户家的孩子,将“情感投入”与日常工作融为一体。[注]王斌:《女性社会工作与情感劳动:一个新议题》,《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4期。培训师成功的唤起了家政工的“母亲”身份,她们主动将“母爱”融入育儿工作,“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疼”,这种移情模糊了保姆与母亲的区别。无论是家政公司的关系营造还是保姆的移情,都彰显了家政女工被裹挟进入情感劳动之中。
对幼儿来说,母亲与保姆的身影重叠难辨。在孩子的认知里,“有奶便是娘”,保姆就是妈妈,妈妈就是保姆。保姆和妈妈的身份差异被消解,她们的地位差异被搁置。正如洛夫格伦指出,中产阶级中母亲角色常由雇佣的人扮演,孩子跑到保姆那里去擦鼻涕,从那里获得安慰、关注乃至责备。[注]奥维·洛夫格伦:《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第101页。周女士是教师,平时工作很忙,经常性加班,她说:
我闺女15个月了,她走路早,语言发育一般,从一岁开始会叫妈妈,现在只会叫妈妈和爸爸,她叫阿姨“妈妈”,叫我也是“妈妈”。我觉得她叫阿姨“妈妈”是有意识的,因为如果阿姨在厨房,我在客厅,她会从客厅一路叫“妈妈”跑到厨房拍门。日常生活中,有时孩子不小心磕碰一下,她也会到阿姨那里寻求情感上的慰藉,要求阿姨摸摸或者亲亲。可能,在她心里,阿姨就是妈妈吧,毕竟,我白天上班,经常加班,陪伴她的都是阿姨。(GY20181001)
在孩子眼里,家政工“母亲”身份被放大,遮蔽了劳动者的身份。对于雇主来说,相比不断更换保姆照顾孩子,她们更倾向于雇佣能够和孩子长期相处的阿姨。保姆身份的阈限性和“(保姆)母亲—孩子”的依恋关系给予家政工举足轻重的家庭地位。雇主很容易屈服于照顾孩子的保姆,因为保姆既有能力行善也有能力作恶。道格拉斯认为,分类不清晰或矛盾的东西在文化上是不纯洁的,不洁来自对界限的逾越,隐喻了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破坏,“阈限人”因为似是而非的身份被归因为“潜在的危险”。[注]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174页。化解危险的路径以消解雇主权威、弱化劳雇关系或涨工资为代价。比如,雇主常常扮演谦卑的角色利用周末或休假煮饭给保姆吃、或通过“姐妹”“阿姨”或“某妈”等“虚拟亲属称谓”营造一种“虚拟亲属关系”来消解劳雇阶层的地位差异、或通过“涨工资”留住或满足阿姨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重要两点是:首先,“家人”身份的生成并不否认劳动过程中双方微妙的摩擦与冲突。雇主(包括准雇主老人)和阿姨育儿理念和方法的冲突很容易冲击家政工“家人”的身份而凸显其“劳动者”的身份。事实上,在日常工作中,家政工难以将客户想象成“家人”,而是理性地当作一项工作看待。劳动关系中出现的各种不平等瓦解了家政工的“家人”身份,日常矛盾转换为劳动冲突。家政工“家人”身份在具体情境中动态地建构与瓦解。其次,地位逆转具有周期性和短暂性特征,存在某种按照文化所规定的时间点和阶段性。特纳指出,阈限包括阶段和状态,阈限行为有重新回归结构,并确定结构中身份和地位的趋势。[注]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167页。因此,保姆努力形成一种新的身份模式社会归属感并不意味着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完全超越社会结构的阴影,尤其在面试阶段和雇佣关系结束阶段,保姆的社会地位重新回归既定社会结构当中。
(二)结构的边缘:“外人”身份的构建
家庭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对个体来说,家庭是一种自我认同(family identity)。[注]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与终结》,吴咏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页。不同家庭成员对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家庭”认同是不同的,家庭具有伸缩性。家庭自我认同意识不仅决定了家庭的边界,是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基础,而且直接影响人们在家庭内外的互动行为。家庭成员可以在空间上彼此分离,在心理上彼此认同,可见,家庭的认同显然和居住不是同一个概念。[注]沈奕斐:《个体家庭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第133页。人类学家对“家庭”(family)和“家户”(household)进行界定:家庭主要涵盖亲属关系(kinship),家户泛指共同居住(propinquity/common residence)的各成员。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具有同居共财的生活和生产单位,而家户则包括所有共同居住的亲属和非亲属。[注]俞金晓:《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杨懋春认为,家户指“所有一起生活和吃饭的人,包括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如雇工”。[注]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10页。保姆被雇主雇佣并嵌入到雇主的家庭关系之中,她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雇主家庭的惯习与规范,与雇主组成临时性“家户”,是“家庭”的外人。
家庭观念与阶层观念之间存在联系。[注]菲利普·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第331页。家在传统中国社会被当作是国家的一种象征以及正当(等级)关系的基础。[注]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的白人妇女因水土不服乳汁稀薄,无法哺育子女,她们雇佣本地乳母,但与之保持距离。欧洲人抱怨中国仆人“不诚实”和用“腐败和不卫生的方式做事”。人类学者克里佛(James Clifford)形容佣人是“驯化的外人”,身处家庭私人生活内部,担任“街头”与家庭的中介,是性别、阶级与种族区隔的看门人,他们的存在表明界线的逾越,凸显了她们“家中的外人”的吊诡位置。[注]李贞德:《性别、身体与医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8-241页。欧洲家庭依赖本地保姆维持家务运作和养育孩子的同时,猜忌保姆的道德操守和生活习惯,将保姆排斥在家庭亲密关系之外。
家政工习惯用“上户—下户”来描述她们的就职过程。根据阈限理论,结合家政工劳动过程所呈现的情境性特征,“上户”是家政工正式劳动过程的开始和进行,可以理解为“阈限”,“下户”可以分解为“雇佣前和雇佣结束”,家政工的就职过程可以用“雇佣前—雇佣中—雇佣结束”三阶段动态地表示。“上户”作为社会状态分野的临界点,把“雇佣前后”视为世俗的结构社会,把“雇佣中”视为“反结构”的阈限时期。结构社会存在组织结构、有彼此差别的存在形式;反结构社会没有组织结构,或仅有基本的组织结构的共同体,阈限主体处于平等融洽的“交融”状态。劳雇双方的社会差异与阶层界限透过家庭场域的微观互动循环地被模糊与跨越、界定与强化。
清代法律中,奴仆身份的人被当作贱民,他们与主人及其亲属的从属关系反映了他们地位的不平等,刑法典规定以犯罪者身份而不是罪行本身来判定处罚。[注]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第117-118页。仆人与家庭成员间社会地位上的巨大鸿沟冲击了日常生活的亲密性,重新定义了身份差异与阶层界线。男性精英轻视和嘲讽来城市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村妇女,城里人可能出于保护工作机会、维持社会阶序以及文化优越感而滋生出对乡下女人的偏见。[注]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杨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62页。母亲雇主面对一种情绪上的两难困境:她们希望保姆爱自己的小孩,同时对“孩子—保姆”间的情感依赖忧心忡忡,解决之道是发展出阶层化的母职劳动分工。[注]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第145页。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当代城市中产家庭:雇主一方面要权衡以何种策略和程度接纳家政工成为“家里人”;另一方面,她们认为,雇主和保姆两种社会类别必须划出界限,无论是社会的还是象征的。[注]奥维·洛夫格伦:《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第106页。
工作内容的安排象征了社会角色的区隔和社会地位的分化。雇主从“家务分工”和“育儿风格”两方面构建隐形的阶层差异和公私界限。在家务分工方面,雇主通常将日常家务诸如换洗尿布、整理玩具、打扫卫生、洗晾衣物等肮脏及失序意义的工作,分配给保姆承担,自己负责传递家庭成员情感的工作,最明显的是辅导功课、亲子阅读和接送上下学。
铎铎妈育有两个孩子,女儿(老大)小时候由阿姨照看,姥姥主要做家务。现在姥姥负责接送老大上下学,阿姨照顾儿子(老二)。铎铎妈说,面试时对阿姨的工作内容有明确要求。比如,下班回家后我带孩子,陪孩子读绘本、做手工或画画,和孩子聊天,了解她在学校的情况;安排阿姨洗衣服、擦地板、整理玩具、收拾屋子。周末我送孩子去早教中心,阿姨在家大扫除。(GH20181105)
航航妈说,辅导功课是家长负责的,阿姨管不了学习的。首先她不懂,其次孩子也不会听她的。接送也主要是我们,因为这也是和老师沟通的“黄金五分钟”,老师的安排布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主要通过接送时与老师交流获知的。(GZ20180915)
Park和Stearns提出的颜料光学叠加原理:即不起化学作用的各种颜料混合后,混合物的吸收和散射系数符合颜料光学叠加原理。根据这一思想,可以得到混合颜料的吸收和散射系数与其配比关系为:
2017年,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镇江市先后有两批共5个村入选省特色乡村建设试点,分别丹徒区世业镇世业村还青洲、世业村永茂圩、先锋村一组、句容市天王镇唐陵村东三棚、茅山风景区管委会李塔村陈庄。
以上三位中产女性借由区分“妇职与母职”工作中的“日常”与“精神”面向,创造出阶层化的象征秩序,凸显母亲的重要性,通过雇主的规范构建“外人”的阶层关系,保姆扮演结构性局外人(structural outsiderhood)与结构性低地位(structural inferiority)角色。母亲有意识地通过规定(分配)保姆的工作内容与之产生某种形式的分工,即保姆承担“吃喝拉撒”等生活照顾,母亲在“情感和教育”等事务上亲力亲为。此时的重点不在于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时间的长短,而是这些时光承载的象征和道德价值。[注]薇薇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第113页。这反映了中产阶层的家庭观和教育观:家庭情感的强度并不是与在一起的时间成正比,而是一种精神上彼此从属的感觉更为关键。父母关注子女的教育、教养和情操,父母之爱是代际关系的主导。家庭象征安全、和睦、舒适与温暖。雇主化身为“道德母亲”,负责孩童教育的权威角色。保姆矮化为“保洁女工”,负责维护整洁有序的家庭环境。雇主与保姆的关系在地理上亲近但在地位上分化。
在钻进机构抵达限幅机构预定位置时,对接锁合组件能够实现限幅机构与钻进机构的锁定,从而使得限幅机构与钻进机构进行随动,保证后续的钻取采样作业顺利进行。
母亲与保姆阶层化的象征秩序不仅体现在工作内容上的分工,还蕴含在育儿风格上的区别。父亲的育儿风格较为宽松,允许甚至鼓励孩子去探险,尽量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年轻父母的育儿风格,正如美国学者Sharon Hays提出的“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概念,认为养育孩子应该以孩子为中心、专家引导、高度情感灌注、密集劳动投入,以及大笔花费支出。[注]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第148页。保姆为了规避孩子受伤的风险与责任,给孩子提出诸多约束,如不能爬高,不能跑远,怕摔跤怕受伤。这一点与老人的育儿风格不谋而合。访谈中,43岁的河南籍阿姨高女士说:
邹女士有两个孩子,老大已经上初中,老二是“二孩政策”放开后所生。她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和中层领导,工作繁忙。面试时邹女士将工作内容说得很清楚,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带孩子,二是做饭,三是家务活。家务活不是硬性规定的,能干多少干多少。但阿姨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好孩子。(GZ20111125)
此外,温室气体还与土壤的有机质、氮的形态(硝态氮/铵态氮)、pH等有关[32]。如透光抚育温带帽儿山红松林会降低其非生长季CO2、CH4和N2O的排放通量,增加其CO2排放与土壤温度、含水量、铵态氮的相关性[16]。刘泽雄等在对闽江河口湿地冬季CO2排放量时发现,其与土壤pH值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3]。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党和政府对于加强信息整合建设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在我国党校图书馆建设“三大文库”以及“四大专题数据库”的引领下,当前我国许多党校图书馆都在加强特色信息数据库建设,有代表性的像安徽党校图书馆的“区域经济与文化信息数据库”、上海党校图书馆的“重要发展战略信息数据库”,这些都取得良好的反响,我国许多党校图书馆在硬件条件上、系统以及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在实际建设进程中,一些图书馆在图书以及信息资源上出现重复建设、相似度高的问题,而且一些图书馆由于缺乏信息整合平台、信息数据集中性不高,存在难以实现深度挖掘与研究分析信息的问题。
殷明突然又惊醒了。他惊坐起来,呆呆的望着四周,有些发懵,这是在哪里?白净素洁的床单,光线明亮的楼房,设计雅观的墙壁。殷明望着其他的床躺着的病人,又望望自己身上穿着的蓝白相间的衬衣,才明白这是医院。不一会儿,便有一位护士进来了
我不习惯照顾老人,老人比较闷,和她们没有共同语言,老人喜欢聊天,我和她们聊不到一块儿。我喜欢照顾孩子,孩子每天都有进步,看着高兴,但照顾孩子操心重,安全第一。在回答如何平衡带孩子与做家务的关系时说,家务活只能在客户接过孩子时才能干,一边带孩子一般干家务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有危险。我不敢让孩子离开视线,怕他磕着、碰着、扎了、摔了。再说,厨房有开水、火、刀具,这些都是危险品。(BG20181018)
高女士说育儿工作是“忌讳”孩子受伤的。孩子受伤隐喻了保姆工作的不称职。在这里,“忌讳”可以理解为“禁忌”。禁忌是所有掉落在已经建立的范畴之外的事物,是在概念体系中找不到位置的事物。家政工需要严守禁忌,小心翼翼地避免孩子受伤的情形发生。如果保姆不能远离孩子受伤的禁忌,将遭受来自雇主阶层的不满和同伴群体的嘲笑。雇主阶层(父母)可以跨越这种禁忌,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鼓励孩子探索世界。可见,禁忌虽不能导致社会分层,但却起到了维护已经存在的分层的功能。
张女士来自山西运城,初中文化,曾在广州的工厂待过,由老乡带入家政行业。她说北京的雇主很和气,也好沟通。入户第一周,主要是熟悉客户的需求,比如饭菜的咸淡、抹布的分类、家人的作息等。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只了解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对客户的其他事情一律不过问,从不打听家里的各种事。
1.绩效审计的概念。绩效审计也称3E审计,是对一个组织利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的评价。经济性是指以最低的资源耗费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出,就是节省的程度;效率性是指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包括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取得一定的产出或者是以一定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就是支出是否讲究效率;效果性是指多大程度上达到政策目标、经营目标和其他预期结果,就是是否达到目标。
张女士通过“不过问”和“不打听”表达了“局外人”的姿态。调查发现,家政工往往觉得自己介于“家庭成员”和“雇佣者”之间,有时候像雇主的好朋友,有时候又像个外人,当自己与某些家庭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时,又会遭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嫉妒(BX20181029)。特纳认为在当代的西方社会,交融的价值十分显著地体现在弱势群体中,与根植于过去的结构不同,他们强调自发性、即时性和存在性,所以他们自发从社会结构中分离出去,而他们离开的这一社会秩序又是与地位密切联结。[注]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231页。
对中产阶级来说,家既是向外展示的橱窗,也是抵制外部世界的庇护所。家具有私人领域和庇护所的双重功能。[注]奥维·洛夫格伦:《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第104页。家务雇佣关系挑战了内与外、公与私的界限。内外隐喻在性别体系的构建中具有象征作用。在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中,“内”与“外”之间既彼此分隔又相互交织。“内外”不仅仅表现为由“门窗”等实体的有形空间界线,它更是通过亲属、角色所展现的象征性文化界线。对内外的遵从实际是建立和维系不同身份、角色之间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异。[注]罗莎莉:《儒学与女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0-86页。高彦颐认为内外界限是“一种协商性的分隔”,空间的内外划分确实发挥了约束社会角色的作用,逾越内外界限会受到惩罚,即使逾越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注]高彦颐:《闺熟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陈为坤关注在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间游走的女性角色。对于保姆来说,公共空间既被视为女性追求自由的平台,也被当作她们遭受歧视和压迫的地方。[注]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第15-20页。公私理念同样适用于个人家庭。对于雇主和保姆来说,作为亲密圈的家庭(family)与作为实际住所的“家”(home)都呈现断裂的状态。一方面,雇主“私密生活”的家庭成为保姆的“公共领域”的职场,进入家庭的保姆是位置不正确的“他者”。[注]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第202页。另一方面,“家”是理解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决策的关键。家政工为了获得免费的住处与食物,与没有血缘关系的雇主同吃同住,形同“虚拟家人”,却不得不与自己的亲人两地分隔。保姆与雇主通过“空间距离的近”与“社会距离的远”同构了保姆“外人”的社会身份、角色及地位。家庭异化为身份转换和阶层划分的微观政治场域,雇主和劳工同时在其中确认和挑战彼此的差异与地位。
四、家政女工、阶层关系与社会秩序
中产阶级和家政工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中产阶级依靠保姆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保姆出卖劳动力换取薪资和食宿。既养又育的工作特性混淆了保姆和母亲的角色,她们既是保姆也是母亲。雇主与保姆犹如进入了“公共域”,彼此间形成某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和平等关系,世俗的级别之分和地位之分消失了,伴随身份的权力义务区别也消失了。[注]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第96页。结构社会的规范与准则统统失效,阈限主体暂处平等的交融状态中。[注]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第100页。保姆“母亲角色代理人”身份模糊了阶层界限,社会关系必须重新划分与界定。阈限主体从“家务分工”和“育儿风格”两方面区隔阶层差异,构建保姆“外人”的身份角色与阶序等级。社会生活是动态辩证的过程,交融具有周期性和短暂性特征,阈限主体有重新回归结构,并确定结构中身份和地位的趋势。家政工“家里外人”身份的生成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消弭“底层女性”的污名,尤其在面试环节和冲突性事件中。
家庭观念、性别权力与阶层等级间存在联系。家庭和阶层通过共同的道德相似性和对生活方式的认同,将靠近的人联合起来。[注]菲利普·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第332页。即使家政工与雇主在同一屋檐下“同吃共爨”,但她们间的差异性和等级性愈发显著,精神距离取代了物理距离。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中,社会文化期待职业女性能完美兼任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产阶层雇佣底层女工应对照料危机,她们豁免家务劳动是以家政女工的参与为基础的。“性别平等”的实质以阶层不平等为代价。[注]沈奕斐:《个体家庭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第262页。中产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获得源于底层女性的权力让渡而非男性。女性化的家务劳动解放中产女性的同时,维护了性别从属关系。[注]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第163页。雇主与劳工在家庭场域互动的延伸,是公共领域不可消解的性别秩序与阶层冲突。[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特纳指出,阈限作为一种社会安排,具有实现社会结构有效运行的功能。尽管“交融”具有即时性、周期性和暂时性特征,阈限主体的身份转换与地位逆转并不能消解结构的秩序与差别,但她们在阈限中积极地参与到某种结构中去,尽管这种结构是幻想的、虚拟的。交融让低位的阈限者在某个时间段里合法地以另一种命运方式经历不同的“释放”(release),作为个体的通过者在阈限阶段地位提升了。在情感层面,没有什么能够像过度的或暂时的被允许的越轨行为那样,为阈限者带来极大的满足感。阈限被认为有着特殊的力量,能够将社会结构变得纯粹。此外,阈限的周期性特征冲刷前一阶段结构关系里积存的不良情绪和矛盾纷争,结构被交融净化,周而复始。阈限的最终效果是为结构等级中不同阶层提出和解,阶层间有可能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包含着结构与交融先后承继的辩证过程。
“OutsidersinFamily”:AnAnthropologicalAnalysisoftheStatusTransformationofDomesticWork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shold Theory
ZHOU Qunying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the middle class and domestic workers meet, and they functionally depend on but culturally distrust each other. The family becomes the micro-political field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hierarchy. Therefore, problems such as “Why employers do not dare to offend their domestic workers? How have their status been changed? And how are the hierarchical boundaries divided?”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job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raising and breeding make the nanny a “threshold person”, whose identity is transformed into a “family member”.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construct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and public and private boundaries from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arenting style” jointly maintain the hierarchical order of the nanny “outsider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the “combination” is cyclical and temporary, the threshold of status reversal does not eliminate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 but it has the function of alleviating the hierarchical contradictions and realizing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even if this change occurs on the moral level rather than the economic level.
KeyWords: outsiders in family; domestic workers;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threshold theory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重大委托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调查”子课题“百村社会治理调查”(18@ZH011);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治理智库项目“大学生就业心理动态研究”“新中国70年中国家庭变迁研究”。
作者简介:周群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讲师,博士(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陈沛照
标签:阈限论文; 保姆论文; 家政论文; 雇主论文; 结构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重大委托项目"; 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调查"; 子课题"; 百村社会治理调查"; (18@ZH011)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治理智库项目"; 大学生就业心理动态研究"; "; 新中国70年中国家庭变迁研究"; 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