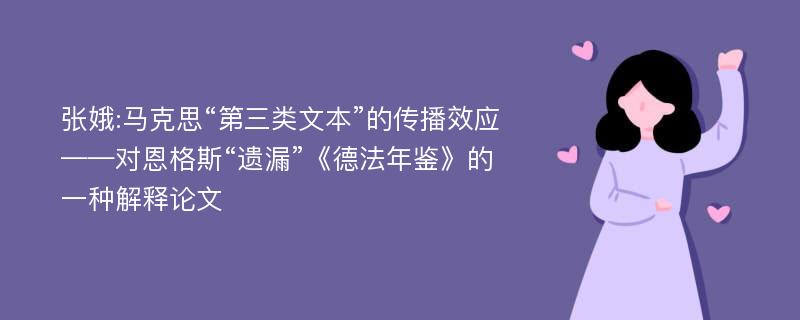
[摘 要] 以思想与现实的粘合度为依据,马克思的文本可以被划分为四类,报刊文章属于“第三类文本”。“第三类文本”与其他文本相比,兼具思想形成价值和传播价值,文本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判断其价值的重要指标。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发表文章的思想价值,但恩格斯晚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到马克思一生参与的众多报刊时,却“遗漏”了《德法年鉴》。可能的解释是他考虑到《德法年鉴》传播效应缺失而进行了取舍。因为《德法年鉴》在传播之初遭遇“夭折”致使其社会效应大大减弱,未能充分发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引领作用,从而影响了恩格斯对其价值的评判。
[关键词]马克思;“第三类文本”;恩格斯;《德法年鉴》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创办、主编和参与的报纸达15家,为100多家报纸撰稿①参见童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人民报刊的思想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5期。,撰写了大量报刊文章来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报刊创作在马克思思想萌芽、发展以及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以报刊为思想阵地与现实持续互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自身的世界观建构,并充分发挥了其思想传播的社会效应。学界过去大多将研究马克思思想演变的注意力集中于著作、手稿或书信中,对报刊文章的考察也主要侧重于思想内容的深度挖掘,而相对忽视“报刊”这一载体内含的传播效应。从文本及其思想史的深度“耕犁”角度出发,需要对作为“第三类文本”的报刊文章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价。恩格斯晚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及马克思一生参与的报刊活动,却“遗漏”了被当今学界高度评价的《德法年鉴》。笔者尝试解释恩格斯“遗漏”《德法年鉴》的可能原因,揭示报刊文章作为“第三类文本”兼具思想形成价值与传播价值的独特性,强化“第三类文本”双重价值,从而为进一步深入探讨马克思“第三类文本”重要作用提供一条新路径。
一、“第三类文本”的划分依据及其思想形成与传播效应
马克思一生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①据学者统计,在马克思长达50 年的写作生涯中,根据已知文献资料统计发现,马克思拥有独著1660部(篇),合著314部(篇),书信3099 封(参见聂锦芳:《马克思著述知多少——从“书志学”方面进行的清理、考证与统计》,《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这些数字在凸显马克思思想文献资料的丰富性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其研究工作的复杂性。,涵涉著作、笔记、手稿与书信等不同形式的文本,它们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依据,是打开马克思思想宝库的锁钥。由于马克思写作这些文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尽相同,利用文本分类学的方法,将不同文本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相对低迷的复合肥需求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经销商纷纷调整自身产品结构,以保证整体的利润空间。对此,刘真表示,许多经销商青睐有较大利润空间的特种新型肥料产品,但这些产品多应用于果蔬等经济作物,受需求量的影响,复合肥仍是大田作物区经销商的主要利润来源。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的文本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划分方式。其一,有学者将马克思的文本分为四类:“第一类文本”是马克思的“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第二类文本”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第三类文本”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第四类文本”是“拟文本”,即由后人重新建构起来的马克思读书过程中所做的批注。②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导言”第12—13页。其二,有学者也将马克思的文本分为四类,但把“第一类文本”界定为马克思本人创作、修订并出版的著作,“第二类文本”界定为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著作,“第三类文本”指认为后来的马克思研究者整理出版的文本,而“第四类文本”则是马克思的各种译文版本。③参见周嘉昕:《文本、历史与问题——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视域中的“青年马克思”》,《教学与研究》2018 年第1 期。其三,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文本应该被划分为这样四类:“第一类文本”是马克思个人已经发表的“自主公开文本”;“第二类文本”是马克思准备发表但实际未发表的“类公开文本”;“第三类文本”是马克思向他人公开却未发表的“亚公开文本”;“第四类文本”是指马克思未完成和未向他人公开的“非公开文本”。④参见何怀远:《理解马克思与文本类型置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的文本学方法之一》,《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在进行文本划分之前,该学者区分了两种文本——“研究文本”与“认同文本”,“研究文本”是指马克思本人创作的文本,而“认同文本”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文本,“研究文本”内含于“认同文本”之中。该学者认为,对“研究文本”进行四种文本类型的划分“对我们研究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心路逻辑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何怀远:《理解马克思与文本类型置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的文本学方法之一》,《学术研究》2006年第1 期)。笔者以为,以公开发表或向他人公开与否作为划分“研究文本”的依据与其说对理解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有所裨益,倒不如说对理解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形成与传播价值有所裨益。因为文本是否公开更为凸显的是其社会影响而非马克思自身思想的形成理路,就这一意义而言,这种划分方式与第四种划分方式存有共通之处。其四,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文本应该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文本”为“成熟性文本”,即完整的、成型的纯理论著作;“第二类文本”是“生成性文本”,即为纯理论著作写作所做的笔记、手稿;“第三类文本”是“应用性文本”,即报刊文章。⑤参见王广:《马克思报刊文章的文本归属与学术价值》,《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6 期。
这四种划分方式所依据的标准各不相同:第一种以文本思想的完成度为标准,第二种以创作、出版的承担者为标准,第三种以文本是否公开发表或是否向他人公开及其组合为标准,第四种则是以“思想与现实”的关联度为标准进行划分。这些划分方式本身既无优劣之分,也非对立冲突关系,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与关注点不同而已。笔者倾向于赞同第三种划分方式⑥笔者虽然赞同这一划分方式,该划分方式本身仍存在一定局限,如马克思的书信并未被纳入文本划分范围之中。恩格斯晚年曾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谈道,他和马克思“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从恩格斯的论述来看,书信和报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着相同的作用,但这类书信只是马克思留下的书信的小部分,将其同报刊一起归为“第三类文本”不太恰当。笔者认为,书信与现实的粘合度介于“第一类文本”和“第三类文本”之间,将其单独划分为“第四类文本”更为合适。,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创见并非静坐于“书斋”产生的学问,而是关注现实并发脉于实践的思想结晶,但文本的呈现方式有直接(或显性)反映现实与间接(或隐性)反映现实之分,用“思想与现实”的粘合度来划分文本能够更好地体现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和文本表现形式的差异性。
由于不同的译者存在的翻译目标不尽相同,所使用的翻译策略自然也就存在着差异。(方梦之2013:47)。林语堂为了想西方读者更好的译介中国文化,传递中国传统思想,作为二战时期西方人的“精神寄托”,无论是选材、译中处理,林语堂都考虑了西方读者的审美需求、可接受度。为了更好地译介中国文化、传递中国传统思想。林语堂在翻译中国典籍时,运用各种策略和方法以便西方读者更好的接受中国文化。同时,林语堂的读者意识使得他在进行书籍的翻译、编撰时更费心思,体现了他灵活的翻译策略。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才能向海外各国人民讲述好“中国故事”。
9月27日上午,水利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过程与控制重点实验室举行揭牌仪式。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出席并讲话,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共同为实验室揭牌。
评价之四:马克思实现了传统哲学从本体论到生存论的根本性变革。马克思通过建构生存论的提问方式,摆正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不再拘泥于传统哲学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追问,将目光投向了“人的自我分裂”问题;他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以及最终解放,其视域从致力于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转向人以对象性实践活动不断生成自身的过程,从而实现了哲学的根本性变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人”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在场者而非蛰居世界之外的抽象物,从而澄明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历史的进步成了人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人不再是臣服于世界的被动存在,变为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主动存在。哲学从本体论追问转向生存论关切,实现了根本性变革。
二、 对《德法年鉴》文本思想价值的肯定性评价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作为“第三类文本”自然也具备思想形成价值与传播价值。透过马克思1843年写给卢格的信,可以窥见他写作这两篇文章的核心关切:一是关注“人的理论生活”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 页。,二是影响同时代人。马克思认为,要实现这一关切,必须以“宗教”和“政治”问题为出发点,因为它们是德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德法年鉴》的办刊方案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阐明了该报刊的发展方向,指出《德法年鉴》要为人类自由做出应有贡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法年鉴》将对其他报刊、书籍进行评述或评介,并关注政治问题、介绍有思想的人物和有价值的学说。所以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将论述的中心议题确认为“宗教批判”与“政治解放”,从而“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第9页。。
学界对这两篇文章的思想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虽然观点各异,但均给予了较高评价。具有代表性的四个肯定性评价是:
强生公司从全部召回的3500万瓶泰诺速效胶囊中,发现8瓶含有氰化物。这8瓶胶囊均来自于芝加哥地区。警方推断凶手是在药店买了胶囊后,把胶囊拆开混入毒物后重新装好,再偷偷放回货架的。
评价之一:马克思完成了“两大转变”,即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一表述最初由列宁提出,后被学界普遍认为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达到的思想高度。尽管也有学者对列宁的“两大转变论”提出质疑:一种观点认为,“两大转变论”拔高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马克思在此时并没有彻底完成向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如果这里的唯物主义是指一般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这个转变又有什么意义呢?”①孙要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三个经典命题的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 期。。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此时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性质有待商榷,它离真正的实现彻底转变仍有一定距离,但并未否定马克思开启思想转变的客观事实。②参见赵家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历史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 期。这两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后者。马克思此时虽未完成彻底转变,但开始转向一般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仍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言,马克思此时转向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一种形态,并未创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无法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方法和方向指引,也不能对历史发展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但对马克思自身思想的发展而言,这种转向标志着马克思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迈出了一大步。“两大转变论”对马克思语境中“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具体所指缺乏清晰论述,是引发质疑的关键。“共产主义”一词因语境差异,具有内涵上的差异性。马克思曾经批判过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他在写给卢格的信中谈到:“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第7—8 页。,并因此拒绝将消灭私有制与实现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在马克思充满论战性的报刊文本中,由于论敌、批驳对象以及马克思本人使用的术语复杂交织,如果不明晰“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涵与现实指向,可能会出现对“两大转变”理解的分歧。
对于恩格斯“遗漏”《德法年鉴》的原因,可以排除以下三种解释:
报刊文章作为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是思想与现实直接碰撞的结果,因而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相比,兼具思想形成价值与传播价值。报刊文章的产生取决于“双主体”的共同作用,是一种传播导向型文本。文章的撰写者必须考虑受众的需求与接受能力来进行创作,因而读者本身也间接地构成这一文本建构的主体。读者兴趣、阅读能力等因素的差异性,必然对报刊文章产生不同类型的文本需求。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报刊文本包含了消息文字文本、报刊特写文本、报刊通讯文本和报刊评论文本等类型。①参见谢晖:《新闻文本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278页。在这些文本类型中,马克思的报刊文章以报刊评论文本居多,以论战性或评论性的文章为主,并被倾注鲜明的个人风格——敏锐的洞察力、生动的表现形式以及晦涩的哲学话语。他在《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中指出,《莱比锡总汇报》是为了传达“政治事实”,《莱茵报》却“主要是满足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人的要求”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3页。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主编时曾表明,哲学以前拒绝利用报纸,因为报纸致力于新闻报道,与哲学对“宁静孤寂”“自我审视”的追求格格不入。而面对报纸对哲学肆无忌惮地攻击,他认识到哲学必须利用缜密的思维逻辑以回击其他报纸的肤浅之见,从而实现哲学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19—221页),而这正是《莱茵报》与众不同的地方。马克思致力于传播“政治思想”,他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不仅具备传播价值,而且承载思想形成功能。马克思传达“政治思想”的坚定性并没有随着《莱茵报》的停刊而结束,它贯穿马克思一生所有的报刊活动。
评价之三:马克思完成了唯物史观的最初表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尽管《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并未对其进行准确阐释,但他的表述却比转向一般的唯物主义前进了一步。恩格斯晚年在回顾他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时曾表明,《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就已经概括出“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的观点。这一说法遭到了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的质疑,认为恩格斯并未确切转达马克思的思想,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更接近这一表述。为了回应巴加图利亚的质疑,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在《德法年鉴》中完成了唯物史观的最初表述①参见段忠桥:《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表述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还是在〈德法年鉴〉》,《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因为他阐明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天国”与“尘世”的关系,而天国的幻象正是尘世生活的映现,国家必须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虽然他此时并未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现实描述以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关系澄清都是对唯物史观思想的初步阐释。
“第三类文本”的价值彰显同马克思的革命家、哲学家的双重身份密不可分,革命的使命决定了其“第三类文本”具备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目标导向,而哲学的功底又使其能够将思辨的“批判”具体化到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之中。马克思与现实的持续互动,使他不断萌生新思想,又将这些思想以报刊为媒介向社会传播。他以报刊为理论阵地,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以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提供方向指引,这也决定了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是思想形成与思想传播过程的统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俗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去帮助他人,不但能提高个人在社会上的人格魅力,而且可以缓和当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社会冷漠”,构建社会和谐的大环境,让旁观者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
这四种代表性的评价切入点各不相同:第一种主要关注马克思世界观层面的初步转变,第二种侧重于马克思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批判的彻底性,第三种挖掘的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轨迹,而第四种则是在与传统哲学的比较中评价马克思此时达到的思想高度。这些评价尽管切入点具有差异,对《德法年鉴》文本思想价值肯定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却存在共通之处,即都是以强调《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发表的两篇文章的重要性为前提的。令人疑惑的是,既然《德法年鉴》在当代拥有如此高的评价,为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列举了许多马克思生前从事的报刊活动,却并未提及《德法年鉴》呢?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总结、回顾并高度赞扬了他的一生。在证明马克思首先是革命家时,恩格斯列举了马克思所参与的丰富的报刊活动:“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 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 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列举的报刊中,有很多被当今学界关注较少的刊物,如《前进报》《纽约每日论坛报》,但对学界评价甚高并认为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德法年鉴》却并未被恩格斯提及。那么,他究竟出于何种原因“遗漏”了《德法年鉴》?
三、 缺乏思想传播:被恩格斯“遗漏”的一种解释
1.7.4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血红细胞(CRBC)测定 按照Yang等[11]方法,通过向小鼠注射SRBC激活巨噬细胞,并在处死小鼠后,分离腹腔巨噬细胞,与鸡血红细胞(CRBC)悬液混合孵育,在载玻片上固定病染色后观察计数。计100个细胞,其中巨噬细胞的个数即为巨噬细胞百分率。受试样品组的巨噬细胞百分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方可判定该项实验结果阳性。
评价之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几乎可与《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有学者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敏锐性”和“独断性”使人联想到《共产党宣言》④参见[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3页。;有学者指出,它具有政治论辩的明决性,可以媲美《共产党宣言》⑤参见[意]帕·陶里亚蒂:《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转引自秦水等译:《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年,第47 页。陶里亚蒂甚至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就思想的深度,论述范围的广度,文体的力量而论……都达到了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高度”([意]帕·陶里亚蒂:《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转引自秦水等译:《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47页)。笔者不完全赞同陶里亚蒂的观点。《德法年鉴》中的两篇文章就政治论辩的明觉性而言,确实可与《共产党宣言》相媲美,但认为其在思想深度、论述广度和文体力量方面均已达到《共产党宣言》的高度,可能存在夸大之嫌。因为此时的马克思并未完全挣脱黑格尔的思想框架,未能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更未彻底发现人类社会存续的内在规律,其达到的思想高度与唯物史观创立之后的《共产党宣言》仍具有一定差距。。这种“敏锐性”“独断性”以及“政治论辩的明觉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此时虽未将资本主义作为批判的核心对象,也未喊出“消灭私有制”的响亮口号,但同《共产党宣言》一样,他已将无产阶级视为解放主体,将斗争目标确立为人类解放。在这一最终目标的引领下,马克思对现实的德国制度展开猛烈批判,主张“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页。。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犀利的笔触与《莱茵报》时期大不相同。为了同新书报检查制度周旋,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必须在尽可能地表达自身观点的同时躲避严格的审查制度,致使其批判显得“缩手缩脚”。但他十分厌恶这一做法,希望“大刀阔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离开德国到达巴黎后,由于法国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马克思便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批判,表达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强烈愿望,这种坚定的政治立场以及批判的彻底性与《共产党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处。
排除第一种解释:恩格斯并不熟悉《德法年鉴》,因而未提及。这种解释之所以应该排除,首先是因为恩格斯曾在仅出版一期的《德法年鉴》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虽然那时他还并未开启与马克思长达40年的合作。其次,恩格斯在1844年回顾德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历史时,曾称《德法年鉴》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8页。,表明了他对刊物价值的认可。最后,恩格斯曾在其他回忆马克思的传记性文本中谈及《德法年鉴》及其涵盖的文本,证明他对这一刊物较为熟悉。马克思逝世后,他撰写了两篇关于马克思的回忆性传记,一篇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另一篇是《马克思·亨利希·卡尔》。在写于1892年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为了尽可能详尽的含括马克思公开发表的所有著作,他提及《德法年鉴》并列举了其中的两篇文章。既然恩格斯知悉《德法年鉴》的存在,也对该报刊上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较为熟悉,那么便不存在因为不熟悉而“遗漏”《德法年鉴》的情况。
排除第二种解释:恩格斯认为《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思想价值不高,因而未提及。笔者认为,这一解释并不成立。原因在于,恩格斯晚年曾对《德法年鉴》上文章的思想价值给予肯定。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指出,他在曼切斯特通过经验性观察得出的结论——经济事实构成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阶级对立形成的基础,而阶级对立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里就已经将其概括为:“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2页。所以在恩格斯看来,《德法年鉴》中马克思虽未对唯物史观进行完整准确的阐释,其唯物史观思想却已具雏形。这是对《德法年鉴》思想价值的充分肯定。
排除第三种解释:恩格斯既知晓《德法年鉴》,也承认其具备思想价值,只是无意“遗漏”。马克思一生写下不计其数的报刊文章,因而《德法年鉴》在列举时被无意间“遗漏”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一解释不具有十足的说服力。《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草稿中,恩格斯并未提及马克思的报刊活动,只是称赞作为工人运动领袖的马克思在创建国际工人协会与推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中做出的卓越贡献。然而在正式讲话中,恩格斯新增了马克思参与的报刊活动,并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视为这些活动影响力的“顶峰”,凸显了其在马克思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从正式讲话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每一时期列举一种刊物,并按时间先后顺序有规律地排列。然而通过查阅马克思的报刊资料可以发现,不同的时间段都存在两种以上的刊物,如与《莱茵报》同时期的《特里尔日报》,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同时期的《改革报》等,这表明恩格斯列举的刊物并非随意选择而是有意为之,故不存在无意“遗漏”《德法年鉴》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恩格斯知晓《德法年鉴》,也承认其思想价值,他并非无意“遗漏”而是在选择刊物时进行了取舍。首先,从纵向时间轴来看,所有的报刊中《德法年鉴》传播产生的社会效应并不凸显。以《莱茵报》和《新莱茵报》为例,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至少34篇文章,抨击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唤醒了民众的反抗意识;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近250 篇文章,指引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据恩格斯晚年回忆,《新莱茵报》在出版后的一年里虽几经查禁,其影响力却与日俱增。1848 年9 月,该报发行了约5000 册,当1849 年5月被查禁时,报纸征订用户已达6000人,而当时影响力较大的《科隆日报》仅有9000 名订户。恩格斯不无自豪地说,“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2 页。。与《莱茵报》和《新莱茵报》不同,《德法年鉴》在1844年2月仅出版一期便因各种原因最终“夭折”③关于《德法年鉴》缘何出版一期就“夭折”的原因,学界目前有较为统一的认知。《曼海姆晚报》曾在1844年4 月7 日刊登了一则消息:来自莱茵省的可靠信息,《德法年鉴》停刊的起因是企业无力支付出版费用及其他外部困难。这则消息虽对《德法年鉴》停刊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却并没有打消人们的疑惑,各种质疑与诽谤络绎不绝。4 月20日,为了回应当时各种各样的诽谤,马克思在《总汇报》第111 号(特刊)上刊登了一则《声明》:瑞士出版社因为经济原因退出导致《德法年鉴》停刊。与马克思的《声明》相比,恩格斯晚年的解释产生的影响力更大。他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指出:“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在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393 页)学者们综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释,大多将《德法年鉴》的停刊归因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原因,二是普鲁士政府的高压政策,三是马克思与卢格的观点分歧。在这三方面原因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与卢格的观点分歧才是导致《德法年鉴》停刊的最终决定因素,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黄楠森等(参见[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0—104页;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无论是发表文章的数量还是产生的社会影响力,都无法与这些报刊相比。其次,从横向时间轴来看,巴黎的《前进报》①这一报纸是指由德国人亨·伯恩施泰因1844年1 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刊,并非1876年出版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已经明确作者归属的文本中,马克思发表在《前进报》中的文章似乎并不多见,只能找到两篇文章——《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和《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如果马克思确实在1844—1845 年间从事《前进报》的编辑与撰稿工作,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那么缘何留存下来的文本如此之少?对于这一问题,恩格斯晚年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的回顾性论述或许可以解惑。在对马克思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行尽可能全面梳理的过程中,恩格斯有这样一句表述:“1844年在巴黎报纸‘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未署名)。——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1848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上发表的一些署名和未署名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400—403 页)。根据恩格斯的表述,我们或许可以知悉马克思在《前进报》中发表的文章之所以没有被保存下来,重要原因就在于多数文章均未署名,无法辨别其真正归属,因而后来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时未被归入其中。《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也存在同样的情形。正因如此,《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即使在现在看来发表马克思文章数量较少的《前进报》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也被恩格斯视为马克思报刊活动的代表性刊物。与《德法年鉴》同属于1844年,恩格斯却选择了前者而非《德法年鉴》。这就说明,他在选择1844年的代表性刊物时进行了取舍,而解开“遗漏”谜团的关键在于理清恩格斯做出这一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笔者认为,恩格斯之所以没有选择《德法年鉴》并不是因为这两篇文章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缺乏足够的价值,而是出于对其现实影响力的考量,思想传播受阻致使社会效应缺失可能是他并未提及《德法年鉴》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于1843年10 月—12 月写作了《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2月出刊,他在《德法年鉴》这一理论阵地坚守了约4个月。《前进报》于1844年1月创刊,直到7月底马克思才在该报刊发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驳斥卢格署名“普鲁士人”发表贬低工人运动的言辞并澄清读者将“普鲁士人”认定为马克思的猜测。尽管马克思接触《前进报》的时间晚于《德法年鉴》,但他直到1845年2月被迫离开巴黎一直都在从事《前进报》的编辑与撰稿工作。在这段时间内,马克思虽然不是名义上的主编,却在编辑部内取得了与主编贝尔纳斯同等重要的地位。《前进报》每周出版两次,到1844年底,订阅用户已经超过800 位,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力,恩格斯称其为“共产主义报纸”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8页。。而《德法年鉴》的命运则截然不同,它只出版一期就已“夭折”,这仅有的一期也被普鲁士政府大量没收③《德法年鉴》出刊后,便被普鲁士政府扣上“预谋叛国和侮辱国王”的大罪,遭到封禁与没收。《曼海姆晚报》曾在1844年4月7日刊登的一则消息:《德法年鉴》印刷3000 册,在巴黎当地售出300多册(尽管该报称几乎每个来到巴黎的德国人都“人手一份”,但笔者认为销售仅300 多册的杂志,其思想产生的实际影响仍然不大),约300册在缴税时被巴伐利亚税卡扣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8页)。学界对于《德法年鉴》流入社会的具体数量存在一定争议: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指出,《德法年鉴》在德国被禁,“数百本杂志在边境被查封”(参见[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英国哲学家大卫·利奥波德曾在书中写道,《德法年鉴》“印刷了1000册且似乎有约800册被当局没收”([英]大卫·利奥波德:《青年马克思——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刘同舫等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德法年鉴》总共印刷了3000册,大概三分之二的报刊在德法边境被普鲁士政府没收(参见萧灼基:《马克思青年时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1页;夏鼎铭编著:《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报刊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页;李义天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第1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也有学者指出,《德法年鉴》一共印刷了2000册,有三分之一被没收(参见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3》,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由于时代变迁,我们无法考证《德法年鉴》被没收的具体数目,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确实被大量没收,最终导致马克思想要传达的思想并未传播到工人运动中或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因而思想未得到有效传播。恩格斯认为,在马克思的所有身份(哲学家、革命家、科学家等)中,革命家的身份占据首要位置,因为马克思始终渴望打破资本主义的统治桎梏进而求得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在列举马克思参与的报刊创作之前,恩格斯语重心长地感慨:很少有人像马克思“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2 页。。这一表达并未出现在悼词草稿中,却被恩格斯同列举的报刊活动一起增加至正式讲话中。借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卓有成效”可能是恩格斯选择报刊的标准,《德法年鉴》由于马克思工作时间短且思想并未得到有效传播,从而与其他报刊相比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无法体现马克思革命家身份的典范定位,所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并未提及。
“第三类文本”无论是写作动机还是写作旨趣都与现实紧密相连,它的产生是对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也是指引现实运动的主要思想阵地,因而思想传播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构成衡量这类文本价值的重要指标。恩格斯晚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遗漏”《德法年鉴》可能是考虑到其传播效应强弱的问题。这启示我们,由于报刊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我们在评价马克思“第三类文本”的价值时应做出更加全面的考量,既要考察它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涵,也要关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的大众化倾向以及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功能。
The Spreading Effect of Marx’s “the Third Type of Texts”: An Explanation for Engels’s “Omission” of the German-French Yearbook
ZHANG E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dhesion between thought and reality, Marx’s text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nd his newspaper articles belong to the third type of texts. Compared with other texts, the third type of texts has the significance in showing how his thoughts were formed and spread, and the social effect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text dissemin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determine its value. Academics at home and abroad spoke highly of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Marx’s articles published in Germany-France Yearbook, but when Engels mentioned in his speech at Marx’s tomb in his later years that Marx participated in contributing articles to and editing man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he “omitted” the Germany-France Yearbook.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omission” is that when he selected the works to mention, he took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Because its “death in infancy” caused its social effect to be greatly weakened, the German-French Yearbook fail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us influenced the evaluation of its value by Engels.
Key words: Marx; the third type of text; Engels; Germany-France Yearbook
张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310028)。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About the author:ZHANG E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210028).
标签:马克思论文; 恩格斯论文; 文本论文; 年鉴论文; 思想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