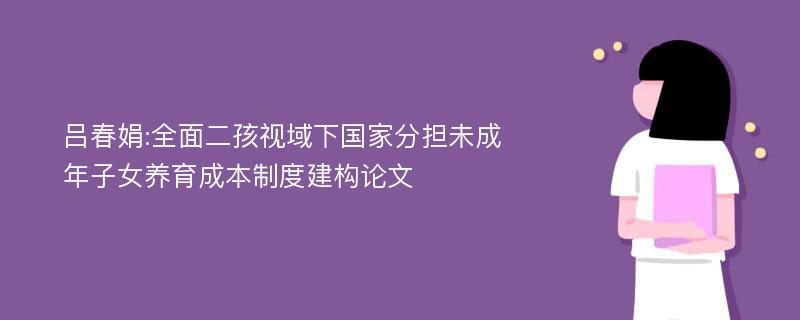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转型,未成年人养育成本日渐攀升,尤以城市最为明显。因传统观念与国家的立法政策均将未成年人养育的负担交给家庭内部,导致家庭对昂贵的养育成本不堪重负。虽然全面二孩立法推行已逾3年,但是人口的出生率并未达到我国人口规划的目标,其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养育分担制度的设计缺位,养育成本的不断上扬成为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严重桎梏,而表象之后则是家庭内部养育重担沿袭传统的女性为主方式,职业女性陷于养育重任与职业发展平衡的困境。反观域外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颁行激励人口增长的未成年人养育成本分担制度。基于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重要的劳动力与纳税人之故,加之国际公约也有国家负担未成年人养育责任之立法,正视当前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的事实,立法构建国家分担未成年人养育成本的制度则属当下亟需之策。
关键词:全面二孩;养育成本;国家分担;制度建构
一、引言
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该规划提出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的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 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2018年新生儿出生更是跌破1 500万。近年来,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也已连续低于1.5。总和生育率的不断走低使得我国人口数量中少儿人口从1990年的31 659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22 958万人,少儿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26.7%降到2016年的16.6%[1]。少儿人口数量的下降,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未成年人①养育成本的逐渐提高,远远超出一个正常家庭能够负担的程度。对养育成本过高的忧虑导致民众不愿意多生,而这背后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普遍只有一个孩子时,人们会把所有希望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养育孩子会变得奢侈化,让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此外,在近些年低生育率下,中国老龄化迅速加剧,社会和家庭的经济与心理负担不断加重。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的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2]。上海妇联发布的调查报告(1)根据上海妇联发布的“十三五”上海妇女发展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在45岁以下的已婚女性中,半数以上(54.2%)的人明确表示“一个就够了,不想要两个”,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仅为15.1%。不想要二孩的原因中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排第一位(58.2%),中低收入女性首肯经济压力大的比重更高达(80%以上);排第二位的是无人照看孩子(29.5%),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女性因孩子照看问题而不打算生育两孩的比重最高,达41.2%[3]。恰好也应证了这个事实:即由于宏观层面国家对家庭养育责任缺乏足够的支持,职业女性倾向于推迟生育或者要承担更多生育后重新就业的困难,由此那些已经生育一个子女后成功地重新就业的女性对选择生育二孩时更加谨慎或者望而却步则在必然之中。
我国立法一直以来均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与教育义务,立法与养育责任的承担通常在家庭私领域以及女性承担主要责任的传统观念高度契合,政府在未成年人养育责任中的角色长期呈边缘性甚或缺失。因此,全面二孩视域下未成年人养育成本的社会化趋势愈来愈明显,随之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性议题,与未成年人相关的福利政策法律法规也因此需要相应转型。对此,我国个别地方率先出台鼓励生育的文件,辽宁省颁行《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在全国首次明确对生育二孩家庭给予奖励;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月子中心、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构,加快培养月嫂和育儿嫂,满足二孩抚养的需求[4];湖北咸宁为二孩孕母提供免费孕期保健服务,在职二孩母亲可以弹性选择具体工作地点时间,并在住院分娩、幼儿园保教费、住房等方面加大对二孩家庭的支持与保障力度[5]。基于地方为激励人口增长的先行示范措施,本文正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养育成本的分担现状,结合未成年人养育成本分析,力求构建国家分担未成年人养育成本的制度,以期对提振我国人口增长有一定助力。
二、全面二孩视域下未成年人养育成本构成分析
美国学者哈威·莱宾斯坦(Harrey Leibenstin)于19世纪50年代将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分析方法应用于人口学研究,该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中国。莱宾斯坦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一书中将父母生育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从怀孕开始到孩子出生,并成长到生活自立时为止的期间内父母花费的所有抚养费用(包括衣食住行的支出)、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其他支出;间接成本是指父母为抚养和培育一个新增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和带来收入的机会,又称为机会成本[6]。具体如下:
一是养育未成年人的直接经济成本。因通货膨胀及消费上涨因素的影响,加之一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形成的“精养”独生子女观念,很多育龄夫妇不得不在生育二孩之前考虑养育子女的经济成本。因为已经育有学前儿童的家庭,势必会因新成员的加入而增加额外支出。首先,就新成员的“衣、食”而言,婴幼儿所需食品及进食时间与成年人不同,又需考虑营养,几乎很难与其照顾者共食,不仅食品本身需要特别准备,有些协助进食的辅助器材需额外购买,而且婴幼儿体型的变化非常快速,对营养的需求相应较高。婴幼儿的衣服也跟大人的尺寸不一样,很难与家中其他成年人共享。其次,就是各种高昂的早教与教育费。中国新闻网根据接受采访某中等城市的一个中等家庭,将育儿分为婴幼儿阶段(0~3岁)、幼儿阶段(3~6岁)、童年阶段(6~12岁)、青少年阶段(12~18岁)。四个阶段中,奶粉、衣服玩具、幼儿园加早教费用、特长费用、课外辅导、旅行等费用共计62万~70万不等[7]。上述高昂的费用绝大多数均为父母自行负担,因此,生育二孩对家庭消费而言增加了一笔巨大的支出。
二是养育未成年人的时间成本。养育子女不仅需要经济实力,更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优生更要优育的理念倡导父母陪伴儿童的成长,从婴儿时期的陪伴到儿童时期各种亲子班、特长班、兴趣班活动等都需要父母花费时间去完成。在当下职业领域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育儿所需时间与职业发展的冲突使得很多育龄夫妇在考虑生育二孩时退却。
三是养育未成年人的工作机会成本。除整个孕期本身会影响工作外,职业女性生育后回归职场不可避免面临由于产假期间疏远岗位信息所导致的知识资本的相对落后,基于此因,很多职业女性会考虑工作机会成本而无热情生育二孩[8]。有人对上海市部分0~3岁婴幼儿家庭育儿现状与需求进行问卷调查并进一步研究发现:同样情况下,相对于男性,女性的育儿机会成本更大;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母亲在职业发展上存在明显差异,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育儿机会成本更大;生育二孩对职业女性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升职加薪受到限制(53.1%)、再就业困难(42.5%)、更早遭遇职场“天花板”(41.5%)、被迫放弃工作(35.6%)、应聘时遭受歧视(31.7%)等[9]。需要我们深思的是,如果“幼有所育”主要由家庭来承担,而“老有所依”由国家来包办,那么这样的制度可能影响未来生育率发展趋势,则社会福利财政亦会受到低生育率的影响。
焊接结果:试验焊缝完成48h后,检测焊缝表面,均无裂纹产生。然后解剖磨制断面,用40倍放大镜观测断面裂纹,板厚32mm的钢板不预热,板厚50mm的钢板预热80℃均无裂纹产生。斜Y坡口焊接裂纹试验结果如表6所示。
最后,《儿童权利公约》第27条具体明确儿童成长的生活水平,要求“签约国应依照国内之条件,在财力许可范围内,支持父母以及其他对儿童负有责任者,完成此项责任时所必须之适当措施。必要时特别针对营养、衣服,以及住所,提供必要之物质援助与支持措施。”由此得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使得儿童取得政策上的个人地位,也使家庭隐私与国家权力间的界线被重新划分[10]。
1.亲职假、儿童津贴制度
课程考核以思辨能力考核为主,即通过适当增加主观题来考察学生对解题思路和方法的掌握程度,提倡采用开放式答案,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来阐述观点。此外,学习是动态发展的,不能仅凭期末考试一锤定音,因此,要准确反映学生真实的学习效果,需构建以过程性评价为基准的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
四是养育未成年人的风险成本。除了上述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之外,女性主要承担育儿责任无疑增加了其在婚姻存续期间的风险成本。中国传统女性角色被解构的同时,原先角色中的保护设定也被解构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婚姻法律中财产归属条文的明晰化,法律规则呈现出保护弱者趋向保护强者。如果女性放弃参与社会生产,放弃自我发展,在婚姻变故中更易沦为弱者。因缺乏有效、共通的社会公序保护机制,女性经济自立、社会地位自强则显得尤为重要,故而很多女性优先选择提升自我,获得婚姻家庭中的抗风险能力。反之,如果女性专注于育儿,无形增加婚姻存续期间的风险成本,基于此,很多职业女性优先选择提升自我,进而才考虑是否承担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责任(2)风险成本的规避另具文在婚姻家庭法的设计中撰写。本文论述国家需要分担的主要是前三类养育成本。。
我国《宪法》《婚姻法》以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均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抚养费包括生活费、教育费以及医疗费三部分。因此,无论是立法的安排,亦或传统观念的认知,养育儿女是父母天经地义的义务与责任,政府乃至国家只有在一些家庭陷入困境时才有福利政策的帮助与救济。显而易见,一以贯之的观念与立法使得当前育儿成本的负担现状将育龄家庭置于低迷的生育意愿之中。
信息技术与聋校数学教学的整合优化了数学课堂教学方法。现代信息技术的实践应用,使聋校传统的数学教学成为了一种开放性、综合性的教学形式。聋生新知识的获取变得全方位立体化了,有效地促进了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情感的激发;教学中强调了聋生的学习过程和自身的体验,实现了对聋生思维方法的引导,加强了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互动[4]。
通过观察创造性地使用几何中的全等证明法,显然是对解析几何的一种新思路的尝试,这道看是无从下手的解析几何题就被转化成了一道其貌不扬的初中平面几何题。
三、国家分担未成年人养育成本理由证成
(一)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的劳动力与纳税人
选取2016年1月~2017年1月本院接收的异位妊娠大出血输血治疗患者40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平均年龄(26.68±1.76)岁;平均孕周(8.99±1.06)周。根据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将其分为两组,各20例。无不良反应组为无输血不良反应或无感染的患者,不良反应组为有输血不良反应或感染者的患者。比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就上述两种倾向而言,国家尽可不干预倾向之理论基本与我国一直以来的立法及政策一致,显然不利于当下我国提振生育率的规划目标。相较于前者,市场失灵倾向更有助于化解当下我国生育率低迷的国情。因为它采纳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养育未成年人是父母的投资行为,换言之,未成年人是父母的投资财产,具备公共财产之特性,即具有非敌对性和非排他性。非敌对性是指该财产具有不可分割性,此处消费的边际成本是零;非排他性仅指无法排除他人使用,此处的“他人”是指没有养育未成年人的人。进一步而言,这些没有养育未成年人的人在年老时无论是否付出代价,均可以享用未成年人成年后带来的收益,从而使得养育未成年人者无法向未养育未成年人者收取受益的代价。此时,未成年人的“非排他性”特征(3)日常生活的非排他例子则是代价非指金钱,例如:某班体育课,只要有一人去器材室借到排球(篮球),全班都可以顺利上体育课,那些没有借球的人即可说是没有付出代价(借球),也可以享受结果(顺利上课)的人。非常明显。养育未成年人行为是一种“外部经济”行为,即父母培养未来的劳动力与纳税人,但却不能排除他人享用成果,所以,“养育子女”存在有外部经济,父母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逐渐升高,而养育子女的效益却不断受到挑战。反之,“不养育未成年人”这个行为是“外部不经济”的。具体而言,当国家提供的公共财产与福利措施越完善,传统上所担心的没有子嗣而导致的不良后果(成本)并不用自行承担,没有生养子女的个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时间)赚取经济所得,若一旦步入老年,即可能因缺乏家庭功能而有较大的概率需要国家援助,该经济行为因有部分成本不必自行负担,必将发生外部不经济现象。假如老年保障的成本持续集体化,而抚育后代的成本仍然个体化,必然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称结果。所以,国家应有相应立法,将“育儿”与“养老”政策协调起来[10]。
未成年人照顾服务市场其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损失无法衡量,因为他关涉未成年人的健康与生命,而且,信息不对称现象在未成年人照顾市场尤其容易发生。由于劳务的购买者不是劳务的实际使用者,虽然未成年人是直接接受服务的主体,但因行为能力受限,缺乏辨识力去了解或反应照顾品质的好坏,父母也无法时刻在照顾现场监督,这也恰是母亲优先选择来照顾子女的原因,女性照顾子女与职业发展的冲突自然产生,此时国家有义务负起定期评鉴托幼机构,并公布结果或者监督儿童照顾服务的工作这类义务。另一方面,国家也有义务提供某些补助,引导父母使用高品质的未成年人照顾服务[2]。与此同时,未成年人是国家经济的创新劳动力源泉,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多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所以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有数十年的滞后期。创新和创业是中国经济提升的动力,但低生育率会弱化这种动力。由于人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在30岁左右达高峰后快速下降,人口越年轻的国家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就越旺盛。分析表明,老龄化不仅减少年轻人的比例,也减少他们的创新动力,让整个经济患上老年病[11]。
综上,因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的劳动力与纳税人,理所当然未成年人就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相应养育未成年人的责任不应全然落在家庭,而有必要由国家来分担,这些介入或者共同承担的预设化为行动之后,除了义务教育作为国家承担的积极性的措施之外,育儿假、育儿津贴、未成年人照顾服务等均须提上日程[10]。
经30天长时间验证测试,系统各模块工作正常,设备能长时间连续稳定工作,无数据丢失报错情况;无线模块室内传输距离远、穿透性强,是普通Wifi信号的4~5倍;网页、微信客户端能实时读取传感器信号,同时也能通过发送命令控制开关热水器、净化器、照明设备等;Xbee无线通讯模块具有自组网功能,能实现多个模块同时工作并进行数据传输,设备扩展性好.
(二)《儿童权利公约》成员国承担儿童养育责任立法表征
2.儿童照顾服务
首先,《儿童权利公约》第18 条第1款规定:“为保证与提升本公约所揭示之权利,签约国应给予父母与法定监护人在担负养育儿童责任时予以适当之协助,”此条明确了国家与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以及国家应积极协助父母的必要性。第2与第3款强调“缔约国应确保发展育儿机构、设施和服务,确保就业父母的子女有权享受他们有资格得到的托儿服务和设施”。
其次,《儿童权利公约》亦清楚规定一般儿童的一系列权利,诸如第24条的健康权,第26条的福利权,第28条的受教育权以及第29条规定的社会参与权。其中公约第26条所规定的福利权是指儿童享有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津贴、福利服务、就业服务、住宅等福利权益,由此可看出儿童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儿童基本人权的内涵范围。
根据滑坡变形破坏形态与特征,结合现场勘察成果,选择该滑坡的最危险断面为Ⅱ-Ⅱ,Ⅱ-Ⅱ工程地质剖面图如图2所示.
我国于1990年加入该公约,成为缔约国之一,理应遵守公约的规定。但就公约第18条在我国的落实来看,我国目前对父母与法定监护人的协助,多局限于父母对儿童有高风险行为,或者父母外出谋生计的留守儿童以及其他困境儿童,针对一般儿童的父母缺乏必要的协助。我国将儿童照顾责任交由家庭承担,唯有家庭功能受损、不完整时,才由国家介入的“补充原则”,与《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对父母与法定监护人之适当协助”仍有差距。进而,就公约第26条而言,综观我国当前实施的关于儿童的各项福利服务措施,主要将资源集中在保护弱势儿童,缺乏对一般儿童给予普惠性的基本保障,因此,国家层面推动普惠性儿童福利制度,实乃落实国家分担养育成本的具体策略。最后,就公约第27条儿童的生活水平规定而言,我国依旧将儿童养育成本交给家庭内部承担,儿童养育责任基本交由家庭完成,还没有打破家庭私领域与国家权力间的界线。
显然,基于我国人口结构老化严重的国情,提振生育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虽然儿童养育成本社会化并不足以完全提振生育率,但也不能直接引伸出养育儿童的负担主体仅限于家庭,不需国家分担之结论。结合前述,儿童就是社会公共财产,如果生养子女的外部经济效益愈大,就表示国家更应当分担愈大的养育责任,而非由家庭独自承担,最直接最具体的措施则是降低父母的育儿成本与提高父母育儿的效益。
四、域外典型国家分担未成人养育成本的立法
(一)瑞典未成人养育成本分担的立法述评
瑞典为北欧典型的福利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遭遇少子化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早在1930—1940年代期间,政府和立法者提倡“全新家庭”的理念。该理念强调国家有照顾儿童的责任,从而促使父母得以自由就业。1970年代以来,瑞典即在该理念的主导下,着重于性别平等目标的达成,建构了亲职假、儿童津贴、托育服务公共化等儿童照顾制度[12]。
2018年11月7日,商务部联合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供销合作总社印发了《城乡配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印发有利于落实《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初步建立起高效集约、协同共享、融合开放、绿色环保的城乡高效配送体系,确定全国城乡高效配送示范城市50个左右、骨干企业100家左右”的主要目标;有利于指导各地对开展城乡高效配送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有利于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与模式创新发展;也是检验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动成果的重要依据。
卢春泉的投资理念一直很明确,“就是顺应国家战略,重点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有些外界炒得很火的概念,像比特币什么的,我们看都不看。”
瑞典于1974年设立亲职假制度,提供了亲职、妊娠与临时性亲职三种津贴。亲职假早在1974年就规定为6个月,期间所得为离职前收入的80%。其特殊性在于不仅母亲可以申请,父亲亦拥有申请离职的法定权利。该权利的确保在于强调男性参与儿童的照顾责任,进而对性别平等有决定性的影响。另外,瑞典还向家中育有0到12岁儿童的受雇父母提供每年120天的临时性亲职假。至于临时性亲职津贴,则以家中有0到12岁生病之儿童的父母为对象,该津贴亦与收入相关,以协助其照顾生病之儿童。儿童津贴是瑞典政府于1948年为刺激生育率而引进的措施。2008年开始,凡家中育有2个以上的儿童时,每位儿童可获得每月100欧元的补贴。除此之外,还制定了失能儿童照顾津贴,针对因照顾失能儿童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如全职工作改为部分工时工作),以及因照顾所衍生的额外成本给予相关补贴。针对单亲家庭(大多为女性),瑞典政府根据家庭收入、家庭人数、住宅成本和规模予以发放住宅津贴。针对父母离异的儿童,如果父母不能履行抚养义务,社会保险机构先行保证对每名儿童每个月最高可给付125欧元。假如父母未能履行该义务,则积累为国家的债权[12]。
2.儿童照顾服务
1992 年日本政府修订了《育儿、看护休假法》,该法充分保障男女两性职工照顾儿童的休假权,雇主不得加以拒绝,也不能因此辞退职工,而且休假重返工作岗位的职工,其工龄必须连续计算,国家承担女职工育儿假期间的保险费。《育儿、看护休假法》规定女性可享受14周产假,同时也鼓励男性在子女出生后8周内休假,且该假期不算在育儿假内;特殊情况下,育儿假可延长至子女满18个月。政府为家庭提供儿童津贴、育儿津贴等货币援助,以减轻育儿经济负担[13]。
显然,瑞典的立法皆以男女两性在法律上的平等作为主要的考量原则。故儿童养育成本分担立法与政策强调协助女性充分就业,以建构友善女性的职场环境。通过法律以及政策,使得女性得以与其子女、就业、以及公共生活融洽共处,从而避免相较男性有更为困难的抉择[12]。瑞典的儿童抚养分担政策凸显“去家庭化”的模式特点,既对提升生育率起到了积极效果,也对女性就业率的提升起到了积极效果。具体表现为:瑞典总和生育率从2000 年的 1.56 升至 2015年的1.92,女性就业率也一直维持在55%左右的较高水平[13]。
(二)日本未成人养育成本分担的立法述评
1.亲职假,儿童津贴制度
为了保证家中有儿童的父母得以就业或求学,瑞典政府向1到12岁儿童提供相关的托育服务。1970年代初期,免费的日间托育是针对6岁儿童,以作为小学入学的衔接课程,此后日间托育延伸至1岁以上的儿童[12]。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新理念的引进与对话,自1980年代起,瑞典在儿童照顾政策的调整上,采取时间与收入并重的调整,藉以鼓励父职的参与和照顾责任的分担。在1994年,瑞典增加了1个月的带薪父职假,以要求父亲积极参与儿童照顾工作。该假期不得转移,若家中父亲未使用该假期,将丧失该权利。2002年带薪亲职假进一步延长为16个月,同时规定父母亲各有8个月,其中2个月不得移转,以强化父职参与儿童照顾意愿。2008年瑞典在既有的亲职假给付制度中引进性别平等奖金,以鼓励公平分担亲职假的父母。而瑞典地方政府亦提供每位儿童300欧元的儿童照顾津贴,鼓励父母的其中一人留在家中照顾1到3岁的儿童,以取代公共日间照顾措施[12]。
家国关系在近代福利国家强调的社会资本视野下,主要有两种倾向,其最为典型的当属国家尽可不干预家庭倾向,该倾向下,国家视家庭为私领域,家庭有高度自治权,父母与子女密不可分,国家赋予家长自由裁量权,决定子女居住地点、托育方式、教育、宗教信仰等。唯有在家庭功能缺失或者紧急情况下,国家才介入。另一则是市场失灵倾向,该倾向主张未成年人是未来的劳动力与纳税人,因此未成年人是具有外部性的公共财产,国家必须通过政策分担养育未成年人的责任,具体措施为育儿假、普惠性的育儿津贴与儿童照顾服务;与此同时,在儿童照顾服务市场,因信息不对称之故,父母选择照顾服务存在盲点,国家必须负起生产资讯或服务的责任。具体表现在儿童照顾、儿童教育、儿童服务机构的监督与评价等方面[10]。
与此同时,为了提振生育率,政府发放“育儿休假奖励金”“企业内托儿补助金”以及“育儿休假人员复工程序奖励金”等物质奖励,帮助企业减轻负担,从而推动企业积极主动落实育儿休假制度,设立企业职工子女保育设施,促进女性再就业。另外,日本厚生劳动省将每年的10 月定为“工作与家庭思考月”,评选和表彰“家庭友善企业”和“推进均等兼顾企业”,普及促进女性兼顾家庭与工作的政策[14]。
为了保障男女两性平等就业权利从而有效发挥女性的职业能力,使之更好地协调家庭生活和职业发展,日本政府于1985年6月颁布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该法旨在促进男女两性就业机会公平,禁止企业因女性结婚、妊娠或生育作为理由而予以辞退。同时还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来处理女员工与雇主的纠纷。同年,日本政府还相继制定了《劳动者派遣法》《雇用法实施规则》《女子劳动标准规则》等规定。2007年,日本政府对《计时工劳动法》进行修订,以此改善雇用环境,推动短时间劳动者的充分就业,从而发挥女性工作能力。
美院严苛的成规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艺术家的个性。1885年离开美院后,谢洛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出国后,谢洛夫目睹了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众多艺术家的作品,为他们对“人性之美”和“现实生活”的炽爱所折服。前人作品中的这种情感表达对谢洛夫的影响在他此后的作品中逐渐有所显现。而幼时家庭的艺术氛围则幻化为谢洛夫笔下不时出现的节奏、韵律和灵动的音乐气氛,令其早期作品具备了独树一帜的诗意情怀。此外,年轻的谢洛夫曾寄寓在阿布拉姆采沃和多莫特坎诺沃,那两段欢乐时光也促成了他早期肖像作品中鲜明的抒情格调。
对于儿童福祉之理念,从生存权的维护,扩展到人权发展之保障。此精神具体展现在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定儿童的基本权益应予以保障,除明释儿童权利的实质内涵之外,更强调政府的适时介入。
⑧严格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在资金管理方面,严格依照《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利科技专项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和“资金审计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设立专户、对“948”项目资金进行管理,拨付项目引进资金必须与项目的进度、项目合同的要求相一致。
儿童照顾服务方面,日本政府先后颁行“天使计划”(Angel Plan)和“新天使计划”(New Angel Plan)。在儿童养育的公共设施提供方面,不断完善育婴室、母子生活支援设施、儿童寄养设施等。设立保育所,提供儿童课后服务以及短期照料支持服务等。努力推行“将等待入托儿童降为零的战役”,从而解决3岁以下幼童入托到保育所的紧迫问题。日本政府每年增设公营保育所数量的同时,也鼓励私营保育所的设立,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改善保育设施,从而延长保育时间。推广多样化保育模式,诸如休息日保育、临时保育、夜间保育等模式,以便有效解决幼童入托与入园的现实问题,从而为儿童的养育构筑一个良好社会环境。日本政府为鼓励代际之间的支持,刻意与企业合作,逐渐推出“老人给孙子孙女‘交学费’不用缴税”政策和“带孙子假”。与2000年前后相比,201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小幅上升到1.46。育龄女性各年龄段的生育率都有上升,尤其35~39岁升幅更大[13]。
显然,日本的立法不仅在于构建男女性别平等,共同承担家庭责任,而且在雇佣方面予以全方位立法,确保女性在就业机会、报酬等方面与男性有平等机会。国家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旨在于消除女性生育时对机会成本的忧虑。在儿童照顾服务方面,可谓举措全面,尤其“再家庭化”的政策助推隔代抚养的社会风尚。
五、我国从国家层面分担育儿成本的立法建构
我国女性从事无酬工作的时间很长,承担较重的家庭照顾工作。据调查,当女性没有工作时,照顾儿童的比例达81.7%;务农的女性照料儿童占比64.8%[15]。但近年来,经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于我国乡村振兴、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6]。因此,从女性就业、从事无酬工作的比重来看,我国更需要构建友善女性的职场环境和两性平等的育儿责任分担机制。对此,可借鉴前述瑞典和日本两国在未成人养育责任分担立法与政策方面的成熟经验。
(一)完善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律,推进男女就业报酬平权
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是应对当下紧急之需的上策。在就业促进法中明确界定“就业性别歧视”概念,明确平等就业权、同职同酬的具体内容。同时,制定统一且具有预防歧视的处罚标准,如产后复职与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等,以加强对就业歧视受害人的保障,从而敦促用人单位遵守相关法律规范,以消弭职场中对女性的就业歧视[17]。
(二)增设《儿童养育法》,明晰国家分担儿童养育责任的内容
1.立法中明确育儿假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问题[18]。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也是对十九大报告中“幼有所育”的积极回应。借鉴前述国家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的产假规定,为更好地协助与促进父母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进男女两性平担育儿责任,需要规定富有弹性的育儿假,可以借鉴瑞典[19](4)自2014年1月1日后出生的孩子,带薪或最低收入补贴的育儿假都可以在孩子12周岁前用完,但只有96天在孩子4岁以后可用。在此之前出生的孩子,父母可以在孩子8岁以前或者在其一年级结束前用尽育儿假。并且,育儿假的时长以日而非周或者月来计算以增强其使用的弹性,可以休全天、休半天、休1/4天或者1/8天来累积计算。例如,可以在八小时工作中每天减少工作一小时,作为1/8 的休假。为人父母的雇员可以连续休假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休假,最多一年可分成三个阶段休假。在孩子未满一岁以前,父母可同时休最多30 天的带薪休假。照顾孩子的休假,不仅是在孩子出生后的两年里,还包括了孩子平时生病时,所以育儿假法规定,父母享有每年每个孩子最多60 天的生病照顾休假时间,期间享有临时的每月3000瑞典克朗的照顾津贴。的做法,在立法中规定,全国亲职假统一为6个月,期间为全薪休假,6个月中1个月为父职假,不可以转移给母亲。育儿假的时长是以日而非周或者月来计算以增强其使用的弹性,可以休全天、休半天、休1/4天或者1/8天来累积计算。例如,可以在8小时工作中每天减少工作1小时,作为1/8的休假。为人父母的雇员可以连续休假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休假,最多1年可分成三个阶段休假。在孩子未满1岁以前,父母可同时休最多30天的带薪休假(5)目前我国各地陆续都有男性陪产假的立法,7-30天不等,期间为全薪。。除此之外,育儿假应规定孩子出生后的2年内,包括孩子平时生病时,父母共享有每年每个孩子最多60天的生病照顾假,期间父母为半薪休假。另外,鉴于我国当前女性生育年龄偏大的现状,怀孕风险也同时增加,建议增设妊娠假,根据具体情况赋予怀孕期间有风险的孕妇15至30天不等的假期,在此期间可根据单位的具体情形领取一定数额的津贴。
2.规定普惠式的育儿津贴
我国《民法总则》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均将未成年人年龄规定为未满18周岁,结合前述国家的经验以及我国辽宁湖北两省的做法,国家实施普惠式的家庭或者儿童津贴,给付对象从0岁到18岁,甚至于18岁以上限制行为能力者,只要属于二孩,无论年龄,符合资格,均予给付,该津贴属于全民性的家庭或儿童津贴,应由国家财政承担。但就我国目前财力而言,财务可行性是考虑重点,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以学前孩童优先,再逐步扩张受益对象到 18 岁(6)我国台湾地区根据2018年官方公布的数据,台北每胎奖励20000元,还享有育儿津贴、5岁幼儿的幼儿园补助、孕前健康检查、孕期唐氏症筛检、儿童医疗补助等不同津贴;高雄市每胎6000元;第三胎以后每胎另有育儿津贴、托育补助等。整个台湾地区对生育二孩及三孩呈递进的奖励。参见2018全台生育补助及育儿津贴总整理: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6107-2018%E5%85%A8%E5%8F%B0%E7%94%9F%E8%82%B2%E8%A3%9C%E5%8A%A9%E5%8F%8A%E8%82%B2%E5%85%92%E6%B4%A5%E8%B2%BC%E7%B8%BD%E6%95%B4%E7%90%86%EF%BC%81/?page=1最后访问日期2018-07-18.。普惠性的育儿津贴可以作为国家承担儿童养育责任的积极表现,在财政因素无法显著突破的情况下,也可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同时联结“育儿”与“养老”两个制度目标,即在老年给付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增加“育儿津贴”,其水准可以参照老年津贴,设定于最低或基本的经济安全[10]。
3.明确国家提供公共性的儿童照顾服务
1990年代之前,我国曾经较为完善的托儿所体系有效地化解了母亲在家庭与职业之间的矛盾,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事业单位逐渐剥离了其对员工子女托育的社会责任,也就是人的再生产责任,单位体制下的托育服务体系全面瓦解,由此,人的再生产成本完全回归到家庭中来,形成高度依赖家庭内部的儿童照顾模式。全国妇联公布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70%的家庭将“无人照料幼儿”列为不愿意生育的首要原因[20]。即便是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我国很多家庭对公共的托育服务也有很大需求。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婴幼儿养育的成本加重,无形加剧了家庭育儿的焦虑,而此焦虑恰是发生在育儿的父母尤其女性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权明显减弱、社会提供的家政服务质量无法保证之际,加之家庭因二孩的出生导致支付能力大大降低,从而使得育儿责任回归家庭成为束缚女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桎梏。除了城市女性,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也随着城市化的趋势普遍参与到非农社会劳动中来,单位对员工的理想期待是24小时随时待命,与此同时,“职业经理人式育儿模式”[21]与“丧偶式育儿模式”(7)主要是指父亲角色的缺失,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承担了双亲的角色。等过度精细化的育儿模式的出现,使得女性面临家庭与社会对其传统规范的双重要求进一步彰显。公共托育服务成为民众刚性的、迫切的、重要的民生需求。我国《2009—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早就提出: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为各类人才平衡家庭责任和工作创造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新时代的“幼有所育”之要求,但客观情况则是托育的公共服务基本缺失,不免成为家庭尤其是女性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基于此,亟需重新定位 “幼有所育”。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的趋势加快,社会公众对于托幼保健、儿童教育和医疗等相关的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儿童照顾愈加超越家庭领域,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政策性议题[22]。假如强调儿童照顾服务的市场化与商品化,可能造成服务购买者、照顾者、被照顾者三方皆输的结果[23](8)结果则是:第一,市场生产不足且价格昂贵,一般家庭无法负担;第二,照顾工作者受到剥削,而多数从事这类工作者是女性;第三,照顾服务品质不佳使得老人或者儿童未得到理想的照顾。。2016年1月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明确了“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具体策略,即给生育家庭提供托育服务,可以适度缓解女性的家庭压力,从而让女性释放出更大的社会劳动潜能,有效减弱职场的性别歧视,推动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业的发展。
关于公共托育服务机构的性质、设立条件、类型、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对机构以及从业人员的监督等也需详细予以建构,鉴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再详述。
参考文献
[1]赵周华.少子化、老龄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6):43-53.
[2]黄文政,梁建章.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问题[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4):129-136.
[3]上海妇联.上海妇女发展需求调查分析[J].中国妇运,2015(5):29-31.
[4]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辽政发([2018]20)[EB/OL].(2018-07-25)[2018-10-10].http://www.ln.gov.cn/zfxx/zcjd/201807/t20180703 3273240.html.
[5]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咸宁市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EB/OL].(2018-08-02)[2018-10-10].http://www.xianning.gov.cn/xxgk/wjzl/201808/t20180802 1062092.shtml.
[6]Harvey,Leeibenstein,H.Econon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nmic Growth[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147.
[7]为了“富养孩子”不愿生二孩?爸妈们这么说[EB/OL].(2018-07-28)[2018-08-03].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7-28/8582215.shtml.
[8]应译.全面“二孩”如何让女性就业“软着陆”[J].中国就业,2015(12):10-11.
[9]张苹.落实生育新政需重视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N].中国人口报,2017-08-14(003).
[10]郑清霞.育儿责任分担的探讨与推估——国家vc.家庭[J]东吴社会工作学报,2007(5):95-135.
[11]王淑云,郑清霞,王正.儿童津贴之合理性与可行性研究[J].台大社工学刊,2012(6):45-92.
[12]黄志隆.儿童照顾政策与福利体制的路径变迁:瑞典、德国与美国之比较[J].东吴社会工作学报,2013(1):1-34.
[13]杨菊,杜声红.部分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探索,2017(2):137-146.
[14]吕卫清,李亚芬.日本促进女性就业经验对解决我国“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歧视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9):16-18.
[15]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编著.中国家庭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69.
[16]孙俊芳.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制度环境与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基于江苏省 597 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西部论坛,2019(6)网络首发版.
[17]刘小楠.港台地区性别平等立法及案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3.
[18]杨菊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改革思路:中国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研究[J].社会科学,2018(9):89-100.
[19]何霞.瑞典消除就业性别歧视立法与实施机制研究刘小楠,王理万主编[C]//反歧视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1):80-82.
[20]全国妇联.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报告[EB/OL].(2016-12-28)[2018-12-02].http://education.news.cn/2016-12/28/c 129422869.htm.
[21]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18(2):79-90.
[22]邓锁.从家庭补偿到社会照顾: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路径分析[J].社会建设,2016(3):28-36.
[23]傅立叶,王兆度.照顾公共化的改革与挑战——以保姆托育体系的改革为例[J].女学学志:妇女性别研究,2011(12)::79-120.
ConstructionoftheSystemofSharingtheCostofRaisingChildreninViewofaComprehensiveTwo-ChildPolicy
LVChun-juan
(Law School,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Lanzhou 73002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cost of raising a child is increasing,especially in city.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and the state rules all attribute the cost of raising a child to the family,making the family be overwhelmed by the raising cost.Although two-child law has taken effect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population birth rate has not reached the target of China's population planning.The primary reason is the lack of design of a state cost-sharing system for child-raising.The rising cost of parenting has severely held back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childbearing age group.Along with female-based parenting tradition,the working women are often trapped in a dilemma of balancing between the parentingjoband career developments.However,in other countries,as early as in the 1970s,the cost sharing system of raising children was introduced to encourage population growth.Considering the minors would be the important labor force and taxpayers in the future,coupled with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bout the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pbringing of minors,a state cost-sharing system of child-raising is an imperative policy to adopt.
Keywords: Two-child policy;child-raising cost;state share;system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G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19)04-075-09
* 收稿日期:2019-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两孩政策’视域下分担未成年人养育成本的制度设计”(17XFX019)。
作者简介:吕春娟(1972—),女,甘肃陇西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婚姻家庭法、人权法。①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的界定,“为本公约之目的,未成年人系指18 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 岁。”与此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未成年人是指18周岁以下的公民。因此,本文未成年人与儿童为同等意思,表述不同则是为了前后语言搭配协调。
(责任编辑:郭海明)
标签:儿童论文; 家庭论文; 国家论文; 未成年人论文; 成本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两孩政策’视域下分担未成年人养育成本的制度设计”(17XFX019)论文; 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