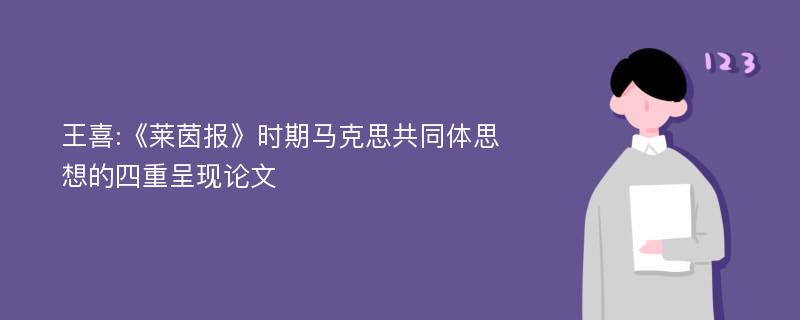
[摘要]《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体现在其对国家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矛盾的现实切近,其中包括共同体的公共舆论空间诉求、特殊私利批判、运行逻辑反思以及自由理性期待。马克思通过批评颠倒了制度与人、个体与类之间关系的书报检查令,阐明了自由报刊之于建构公共舆论的意义;通过批判特权者利益亵渎法的普遍性的林木盗窃法案,指出理性国家不能沦为私利工具;通过揭示地区贫困问题中管理机构的官僚本质,提出消除管理贫困是消除地区贫困的根本进路;通过批判基督教国家观,指出国家的建构基础是自由理性而非宗教精神,国家应当是自由个体与理性国家互为生成的“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关键词]马克思;《莱茵报》;共同体;自由理性
1841年夏,青年黑格尔派的两位成员因普鲁士的封建专制而陷入困境,一是鲍威尔因批判福音书而被解除波恩大学的教职;二是卢格因出版的《哈雷年鉴》面临或接受政府检查或迁至国外的去留两难。普鲁士渐趋强化的反动政策使马克思在大学寻求教职的希望破灭,但也现实地推动了他从之前的“咖啡馆的争论”转向社会政治斗争,从而真正“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使“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1]75。而《莱茵报》在科伦的发行,恰逢其时地成为马克思的实战阵地。从1842年4月、5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0月移居科伦担任主编,到1843年3月17日因报刊面临查封发表退出申明,这便是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莱茵报》时期。如果说博士论文是马克思通过自由意志表达独立个体脱离共同体定在的诉求,那么《莱茵报》时期的系列政论则是其从书报检查、特殊私利、官僚制度、宗教精神等问题对普鲁士国家共同体进行的反思,进而指向一种思想自由、普遍平等、个体自由与国家理性相互建构的“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共同体的公共舆论空间诉求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一边是英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腾飞,一边是德国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破土般的挣扎。直至19世纪40年代,面对封建政治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持续束缚,德国公众强烈呼吁政治思想自由。迫于民众压力,普鲁士政府在1841年末至1842年初通过颁布新的书报检查令,用伪装的自由主义敷衍民众诉求,以期缓解社会情绪。为揭穿普鲁士封建专制的骗局,争取真正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舆论自由,马克思撰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作回应。其中,马克思从书报检查制度与新闻出版自由的矛盾对普鲁士国家共同体的“合法权威”进行了质疑与反思,并表达了对“自由报刊”所代表的共同体内部公共舆论空间的诉求。
书报检查令以主观态度为客观真理设限,在虚伪的自由中颠倒了制度与人、个体与类的关系。
其一,“书报检查令”以“严肃和谦逊”等内容之外的主观态度限制客观真理的探讨。一方面,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而“谦逊”则是内容之外的东西,是一种主观的态度。真理像是光亮,它无需也很难“谦逊”,而“谦逊”恰是对作为结论的真理的畏惧。“谦逊”作为一种主观态度具有强烈的个体性,但真理是为大家所有的普遍的东西。总的说来,精神的谦逊是以理性的姿态来呈现,是以事物的本质特征去注解事物本身所呈现的普遍的思想自由,而“书报检查令”藉“谦逊”之名进行的自由标榜恰是对思想自由的束缚。如同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它以一种官方的指令将精神的丰富化约为单一,从而遮蔽了“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的事实[1]111。另一方面,真理是检验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而“严肃是肉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种虚伪姿态”[1]111,112。所谓“谦逊”和“严肃”,它们的概念本身也存在着背反,如笑可笑之物本身即是严肃,而谦逊地对待不谦逊又恰是最大的不谦逊,到底是严肃还是诙谐,谦逊还是不谦逊,结果取决于书报检察官的脾气。总之,这种对真理探讨的主观规定是对真理客观本质的亵渎,它无视认知主体之间的差异而落入了抽象理解的窠臼之中。究其实质,这不过是普鲁士封建政权用“法律的形式”作为掩饰,以政府的命令替换了真理,以当权者的威权绑架了社会成员在真理探讨中的主体性。
其二,“书报检查令”以宗教原则混同政治原则、以追究倾向的法律钳制思想,在立法形式与法律内容的矛盾中沦为政治工具,消解了个体之间的权利平等。马克思指出:“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1]118而新的书报检查制度却以“不许攻击宗教”的规定混淆政治原则与宗教原则。它要求一种外在的“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取代“道德和良好习俗”,以“外表的现象、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替代“作为道德的道德”,从而在对“宗教良心”的强化中弱化了“道德良心”,使公众作为精神主体的自为存在受到贬抑。新检查令以“倾向”而非“行为”作为判断依据本身就是一种对公民名誉与公民生存的侮辱与危害,因为“倾向”本身不能构成法律所应有的客观标准,因而由此做出的裁决便是逸出事实之外的“诛心之论”。而且,谁是追究的主体?主观“倾向”如何判断?马克思指出,追究思想的法律源于追求实利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恰是建立在无思想和不道德的基础之上。在这种国家观的指导之下,书报检查机关以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独占者自居,臆造了一套同人民根本对立的、反国家的、追究倾向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当政集团作为追究的主体,在对追究倾向的法律的工具化利用中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这种法律本身也就成为了权力优越性转为思想优越性的基轴。
其三,“书报检查令”赋予了书报检查官指摘新闻出版界的权力,在限制新闻出版与鼓励检查官履职的悖谬中导致了人与制度、个体与类之间的倒错。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令”自身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一是“新闻出版被剥夺了批评的权利,可是批评却成了政府批评家的日常责任”[1]122,二是“检查令要求对官员阶层无限信任,而它的出发点却是对非官员阶层的无限不信任”[1]124。具体而言,这种矛盾体现在,一方面检查令禁止人们使用侮辱他人的词句,杜绝败坏他人名誉的判断,禁止作者怀疑个别人、怀疑整个阶级的思想;而另一方面书报检查官却每天都在通过行使所谓的检查权力,以臆测行为动机的方式对人作出侮辱性的、败坏名誉的判断,并将全体公民分成恶意的、可疑的和善意的、不可疑的两类,要求人们尊重以任性的制度、信任有缺陷的书报检查制度及其检查官等。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的存在源于警察国家对其官员所抱有的“虚幻而高傲”[1]133的观念。就制度与人的关系而言,“书报检查令”作为特殊的、反国家的东西却以国家法的形式出现,它不是对“主观思想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维护,而是以检查官代替上帝充当“心灵的法官”对个体倾向进行审判;[1]122,123就个体与类的关系而言,书报检查官身兼“原告、辩护人和法官”多职,公众的智慧与良好愿望遭遇着善恶、信疑的粗暴臆测,湮灭在他们看似的无所不能之中。可见,在现有的报刊、书报检查、书报检查官以及最高书报检查机关的关系下,整治书报检查制度从而使普鲁士的作者获得真正的、更多的自由,其根本办法在于废除这一制度而非更换检查人员。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三篇论文,它揭示了特权者的片面的物质利益对国家理性与法的僭越。针对普鲁士政府提交省议会的林木盗窃法草案,马克思指出,若将未经许可进入森林捡拾枯枝的行为论以盗窃罪,“必然会把一大批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1]243。人的权利屈居幼树的权利之下,是林木所有者特殊私利的张扬,是等级制度下国家理性与法在私人利益中的堕落。
辩论中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不同诉求是不同等级精神的映射。譬如,诸侯等级的代表认为报刊应是上流社会的刊物,而新闻出版自由是各国人民以粗野而冒失的语言对高贵的亵渎,束缚了真实而高尚的精神发展;骑士等级的代表将个人特权与个人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以“自由可能产生恶,因此,自由是恶的”[1]166为逻辑,以“人类不成熟”为借口反对新闻出版自由,认为报刊只能以一种被监管的姿态依附并服从于政治权力;城市等级的代表虽然肯定新闻出版自由,却将其归结为行业自由,于是自由从目的本身沦为行业牟利手段,从而抹杀了作者蕴含于作品中的自由意志。马克思认为只有农民等级的代表真正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新闻出版的内在诉求,即人类精神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新闻出版应遵循这一规律推动其自由发展,也只有尊重个体将自身成就告诉他人的权利才能防止人类精神的停滞与腐化。而且,赞扬的价值源于对指责权利的珍视与尊重,基于人类精神发展规律的新闻出版行业应当成为一个既能摆脱国家政治权力的束缚,亦能杜绝商业投机的矮化,真正实现独立自由发展的社会领域。
在“动物崇拜”的逻辑下,林木所有者一边在其等级内部(大小林木所有者之间)贯彻平等,一边对等级之外的林木管理条例违反者坚持“不平等的公理”,显然,这与国家理性相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所承载的是全体人民的自由与利益,国家的行事手段应符合其自身的理性、普遍性与尊严,作为被告的捡拾枯枝者的权利、生活条件和财产应成为国家运用其手段的观照对象。然而,特殊私利一出场便消解了国家理性,它狡猾地“把自己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1]261。当林木所有者以“意志自由”为由要求对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的处置权,并要求对代表其特殊利益的护林官员的终身任命,这无非是将“林木所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1]267。结果,不是国家观念点化、充实私人利益的空虚灵魂,而是国家自身沦为牟取私人利益的手段。整个国家制度与各种行政机构堕化为一种工具性存在,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而“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的“耳、目、手、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盗窃林木者偷了林木所有者的林木,而林木所有者却利用盗窃林木者来盗窃国家本身”[1]277。
国家理性不能沦为封建等级制度下私人利益的工具。马克思以“精神的动物王国”喻指封建制度,揭示其作为“分裂的人类世界”的本质。他指出,动物世界中的唯一平等不过是特定种的动物内部的平等,正如“自然界在猛兽的胃里为不同种的动物准备了一个结合的场所、彻底融合的熔炉和互相联系的器官”,而在实行单纯的封建制度的国家中人类亦是实行着“按抽屉来分类”的等级制度,这便是“原始形式的动物宗教”,是“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的所谓“动物崇拜”[1]248,249。
从新闻出版自由的意义、自由报刊的本质与功能出发,马克思指出了公共舆论之于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意义。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之于整个自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且同其他形式的自由之间相互影响,如果新闻出版自由受到指责,那么其他自由亦不过泡影,甚至整个自由都如同虚设。自由报刊作为“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1]329,呈现出本质上的人民性与功能上的公共性双重特征。这种“人民性”是指“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1]153。自由报刊既是人民实现斗争形式观念化(即实现物质斗争、血肉斗争以及需要、欲望、经验的斗争转向思想斗争、精神斗争和理论、理智、形式的斗争)的重要平台,是人民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解救的指引,也是人民进行自我精神审视、生成智慧的重要条件;而人民的心声正是报刊的活力源泉,民众的承认是其赖以生存的条件。而自由报刊的公共性则体现在它之于管理机构与被管理者的沟通意义,它超越官方与私人的单边利益,在两相差异中有沟通,同单方利益有距离。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由于既不以官僚前提作为出发点,也不同私人利益相纠缠,自由报刊兼具“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双重特质[1]179。从而,在这个既公共又独立的中介领域内,管理机构和管理对象可以超越从属关系而在其基本权利范围内对对方的原则和要求展开平等的批评。作为社会舆论的制造者,自由报刊是可以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的“国家精神”;作为社会舆论的产物,自由报刊是源自于现实又流回现实的“观念的世界”。总之,自由报刊承载着公共舆论对国家共同体内部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建构。
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共同体的特殊私利批判
针对现实政府“书报检查法令”对理性国家“新闻出版法律”的背离,马克思指出了自由报刊建构公共舆论空间之于共同体的意义。“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1]134,135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引用了塔西佗《历史》中的这句话作为结尾,并继续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为争取这种公共的“幸福”进行辩护。
法律是一种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其价值在于维护人民的普遍利益,而不应为特权者的任性所亵渎。正是在这种应然的普遍性的规约之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1]176。林木盗窃法却暴露出特权者的任性对法的普遍性的亵渎。何种行为构成事实层面的盗窃林木,捡拾枯枝同其有何区别?前者是擅自对他人财产作出“判决”,或直接侵害树木本身,或偷窃已经砍伐的树木,从而导致一种财产剥离的结果;后者“只是执行财产本性本身所作出的判决”[1]244,因为落下的树枝已经逸出树木的占有之外。而“说真话”是法律的普遍义务,即法律必须按照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而不是相反,因此,如果将捡拾枯枝的行为混同盗窃林木,那么穷人便将成为“撒谎的”法律的牺牲品。马克思指出,林木盗窃法是贵族的“习惯法”,是特权私利对法的工具化利用。特权者的习惯同法的普遍性相抵牾,其习惯法势必同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对立,而“当特权者不满足于制定法而诉诸自己的习惯法时,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1]248,249。这里的“法的人类内容”是指人民的普遍利益,是包括了“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在内的人的利益;而所谓“法的动物形式”,则是特定的种的平等,而非类的平等,是一部分人利益的张扬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遮蔽:它强调以是否符合“我的利益”来评价某项法律规定的好坏,而如果“纯粹从法理幻想出发,也应该适用于被告,那就是多余的、有害的、不实际的”[1]247,248。林木盗窃法正是林木占有者所要求的“法的动物形式”。本应代表全省利益的等级议会却接受了特权者的任务而放弃了整个莱茵省,它为确保林木所有者的利益不惜毁灭“法和自由的世界”。它不仅认可以林木盗窃罪论处捡拾枯枝的行为,且在条文中规定受雇于林木所有者的护林官员具有告发、估价的权利,林木占有者自身作为惩罚主体享有罚款的权利。可见,在“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牺牲法的原则”与“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之间,“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1]288。从而,特权变成了法,一种特殊利益的法。
BIM运维平台支持对空间进行在线划分与管理,精准化管理每个房间,计算每个房间的数据(面积、租户/部门、人员、能耗、成本),同时可以精细化管理每个员工的卡座,灵活统计每个部门的使用空间及成本,最终为管理员提供最佳的空间优化方案。
马克思在对等级特性与普遍自由、新闻出版法与书报检查令、新闻出版自由与行业自由的比较中阐释了“自由”是新闻出版的应有内涵。马克思指出:“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1]167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识性期待与普遍性价值,正如“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1]163,特权者的特殊自由不能凌驾于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之上。马克思指出,新闻出版自由代表的是一种“普遍权利”,而书报检查制度却是检查官对公众的权利,是检查制度对新闻出版界的权利,它导致了类与种的关系颠倒,使“反对精神的自由”比“精神的自由”享有更多的权利。这种颠倒也恰恰揭示了国家法律与政府法令在“自由”问题上的矛盾:在新闻出版法中作为惩戒者的“自由”,却在书报检查令中遭遇怀疑而沦为受惩者;在新闻出版法中“自由”因滥用而被惩罚,而在书报检查令中“自由”因被施加“滥用”之名而受到惩罚。可见,新闻出版所追逐的自由却在书报检查制度中被驱逐。诚然,与行业自由一样,新闻出版自由是作为“种”的自由归属于“类”的一般自由,但新闻出版本身最为根本的自由并不指向成为某种“行业”。正如书报检查之于新闻出版是一种外部不自由,那么以物质工具对其进行度量便是内部不自由,因为新闻出版作为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方式,它以一种“不知道尊重个人、只知道尊重理性”的姿态实现“人类自由”[1]196。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看出,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相对于普通前置胎盘患者来说,面临的威胁更大,可能导致的不良妊娠结局与不良新生儿结局的概率更高。另外,在一般资料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高龄产妇、孕次和产次较高的产妇其发生凶险型前置胎盘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临床上对于此类前置胎盘产妇要给予特别关注。
对比2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研究组肺部感染1例、发热1例,总例数2例,参照组患者肺部感染2例、静脉血栓1例、发热3例、压疮1例、颅内感1例,总例数8例,数据对比X2值为4.2667,p值为0.0388,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6.25%低于参照组患者发生率25%,组间对比统计学意义存在(P<0.05)。
三、《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共同体的运行逻辑反思
马克思通过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归因揭示了“官员理智”与“市民理性”的对立,指出社会现实是“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两相勾连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用当事人的意志取代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来解释一切是人们研究国家状况时容易走上的歧途。面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普遍贫困,普鲁士政府作为管理机体对其持漠视甚至否认态度,并在行动上只是意欲“尽量减轻”而非将其“消除”,而作为被管理机体的葡萄种植业经营者则以其现实的困窘诠释了贫困从个别走向普遍的事实,他们用“实际的证据”同官方摆出的所谓证据进行对照,指出官僚歪曲事实的狂妄自大以及自私自利的执意偏狭。具体而言,“官员指摘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利益缩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利益”[1]372,这便是“官员理智”与“市民理性”的对立。马克思指出,“官员理智”不过是对“世界的现实景象和官僚在办公室所设想的世界景象之间的矛盾”[1]372的掩饰,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经常性”贫困,是从“几乎不为人所觉察”逐渐走向“登峰造极”的历史性结果,是“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交互生成的结果,因此,国家管理机构不能回避其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贫困状况的责任,亦如其无法否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内。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组文章的写作缘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对《莱茵报》记者彼·科伦布茨报道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责难,马克思通过广泛收集材料为其进行辩护,揭示了国家制度运行与社会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源于政府管理工作的贫困,而政府管理工作的贫困则源于官僚制度的贫困。如果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发现了私人利益同国家理性与法之间的罅隙,那么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他开始在国家理性之外寻求一种具有客观本性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来审视国家制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对立,这便是“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1]377。
其次要加强监管,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学校监护为辅的监护制度,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家长进行教育和引导,探索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有效模式。
马克思基于对普鲁士封建国家运行原则的分析,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源于管理工作的贫困,并提出废除官僚制度是消解管理机构与管理对象之间等级对立的根本进路。官僚制度是普鲁士封建国家组织体系与运行原则的集中反映,它在本质上是等级制度,它将公民“分为管理机构中的积极的、自觉的公民和作为被管理者的消极的、不自觉的公民”[1]374。面对被管理者的贫困现实,深植于官僚本质的管理机构,在自身范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以回避其应担的责任。他们将摩泽尔河地区的贫困归咎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归咎于子虚乌有的葡萄种植者私人生活的“挥霍无度”,归咎于同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却拒绝承认行政当局自身的税收因素。[1]373可见,面对社会现实与管理制度的矛盾,管理机构不是对管理工作本身进行变革,而是设法对管理对象进行调适,即要求所辖地区的居民将自己的生活安排适合于现有的管理制度。在他们看来,“管理工作是为这个地区而存在,而不是这个地区为管理工作而存在”[1]376,正是这种倒错的制度逻辑现实地加剧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
冲砂系统的开挖与常规的地下隧洞开挖有区别的,坡积体段管棚灌浆处理形成了封闭裂隙,加强基岩的完整性,达到提高岩体强度和刚度的。在开挖过程中明显出现砂砾石形成整体现象,加上临时支护及时,未出现大量塌方现象,说明该隧洞的坡积体段施工方法可靠。
马克思立足于事实材料与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交互分析,揭示出摩泽尔沿岸地区的贫困源于普鲁士官僚制度下的政府管理工作的贫困。因此,废除官僚制度才是消除贫困问题的根本方法,而以作为第三方因素的自由报刊对管理机构与被管理者进行沟通是消除等级对立的重要进路,这是马克思反思普鲁士封建国家共同体的重要结论。
四、《〈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共同体的自由理性期待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是《莱茵报》与《科隆日报》论战的始幕。该论战起于《科隆日报》政治编辑海尔梅斯对《莱茵报》政治立场的攻击,他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普鲁士书报检查机构应严禁青年黑格尔派批判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的报刊言论。针对海尔梅斯的基督教国家观,马克思立足哲学世界化的现实意义,在梳理哲学与宗教、政治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主义国家观。
海尔梅斯认为宗教是建构国家的基础与最为必要的条件。对此,马克思指出,正如“拜物教远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1]212,宗教精神不能视同政治国家的理性原则。无论是历史维度还是逻辑层面,宗教同国家合法性之间都没有必然联系:一是偶像崇拜者的心灵需要在宗教上求得满足,但粗野的感性欲望可能使其反过来砸碎宗教偶像;二是“存在的事实”无法推出“存在的权利”,即不能以某些国家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就认定宗教是国家的基础;三是宗教并非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因,从古希腊极盛时期的宗教排斥,到古罗马衰亡时期亚历山大亚学派的诞生,都历史地证明了宗教意识的发展程度与民族兴衰之间不存在绝对相关性;四是宗教并不懂得制度之间的差别,因而并不能判定制度的好坏。正如基督教既存在于共和政体的国家,亦存在于君主专制或者君主立宪的国家。马克思指出,不同政体有着不同的制度规范,国家制度是否合理的判断依据不是宗教,而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即“不应该根据宗教,而应该根据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1]226。
(2)造液厂房、净化厂房为384 m×(24 m+24 m)×21 m(25 m)大型钢筋混凝土排架柱、预应力屋架结构联体厂房,防腐方法与电解厂房类同。
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人世的智慧,而宗教则是一种来世的智慧,因此哲学比宗教更切近现世王国,即国家。不同于宗教神权以神性泯灭人性,哲学以合乎人性为指向,以自由理性观照国家。而且,超越了从前哲学家基于本能或个人理性的构想,现代哲学从整体观念出发,认为国家是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的庞大机构,国家法律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1]228如果说基督教国家只是教徒践履教义的联合,那么自由理性的现代国家则是“有道德的个人自由地联合”[1]215,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1]217。这种“教育”旨在通过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建构“合乎理性的公共的存在”,其中,“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1]373。
五、结语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生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文本线索而言,如果说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呈现了植根于道德神学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博士论文彰显的是基于意识哲学的个体自由张扬,那么《莱茵报》时期系列文章则是政治哲学转向下的个体与共同体关系审视[2]。马克思通过对国家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矛盾的现实切近,从公共舆论环境、物质利益关系、制度运行逻辑等维度对现存的普鲁士政治国家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应当根据自由理性来建构一种个体与共同体互为共在的“联合体”。诚然,《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中不乏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印记,彼时他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亦未深入触动社会经济关系,但马克思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提出了“哲学世界化”的命题并引导理论研究观照社会实践,这一时期他对民众贫困的关切、对官僚国家的不满,以及对人民自由与国家理性之间合理关系的探求成为其反思黑格尔理性国家观、转向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真实起点,[3]为共同体问题的研究推进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立足新闻出版自由强调公共领域之于民众与管理机构的沟通意义,并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区分国家理性与私人利益,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厘清了葡萄种植者与地方行政人员之间的立场差异,马克思看到了国家理性同私人利益之间的勾连,这为其后批判“虚幻的共同体”提供了现实材料与论理依据,他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思考,亦为其共同体思想演进的社会哲学向度延展提供了重要支点。《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指出国家应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并提出个体自由与国家理性的双向互动是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基础,初步彰显了“真正的共同体”关于“自由”“共在”的基本价值蕴含,这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淑梅.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J].哲学研究,2009(6).
[3]张亮.在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夜——《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再考察[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Four Dimensions of Marx's Community Thoughts in the Period ofRheinische Zeitung
WANG Xi
(School of Marxism,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Dongguan,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Marx's community thoughts in the period ofRheinische Zeitungare embedded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reason of state’ and ‘social life’,which includes the demand of public opinion space in the community,the criticism on special self-interest,the reflection of running logic,and the expectation of liberty and rationality.Marx explained the significance of free newspapers in constructing public opinion space by criticizing the censorship which rever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people,individual and mankind.He raised that rational state shouldn’t be descend to a tool for private interest through the criticism of Act of Wood Steal in which indicated the universality of law was profaned by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vileged.By revealing the bureaucratic essen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poverty regions,he proposed that abolishing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was the fundamental access to abolish regional poverty.He criticized the christian views of country and pointed out that a country should be based on liberty and rationality rather than religious spirit,and it should be an association of free individuals through mutual education 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ree individuals and the rational state.
Keywords:Marx;Rheinische Zeitung;Community;Liberty and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9)06-0047-07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19.06.008
[收稿日期]2019-05-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YJC71008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17ZDA001);广东医科大学科研基金博士启动项目“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研究”(B2017049)。
[作者简介]王喜(1986-),女,法学博士,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禚丽华
标签:马克思论文; 自由论文; 国家论文; 普鲁士论文; 书报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长白学刊》2019年第6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YJC71008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17ZDA001)广东医科大学科研基金博士启动项目“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研究”(B2017049)论文; 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