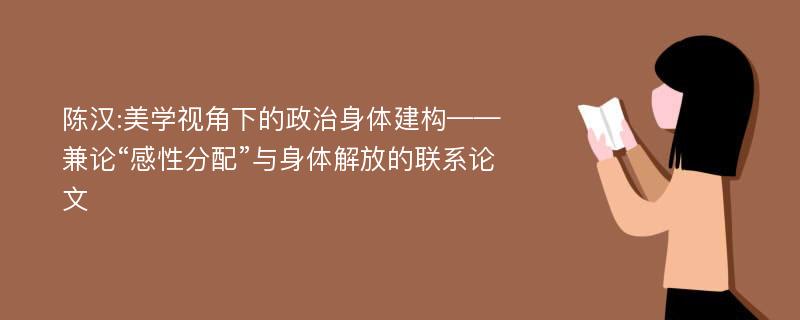
●文学研究
摘 要:在福柯等人的著作中,“政治身体”是理解政治观念与合法性变迁的重要概念。中世纪至近代以来的统治者利用多种视觉与艺术再现手段,诉诸崇高与神秘美学效果的营造,达成对臣民视觉经验和身体感受方式的控制,以期实现神圣化国家的统治目的。分析政治身体的美学建构方式,为解读政治与美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向度。朗西埃从政治身体建构的美学机制中,挖掘出潜藏在身体美学中的政治解放潜能,通过打破感性的既有分配格局,赋予身体平等参与和分享审美经验的权利,从而消解和抵抗“治安”对身体的规训。
关键词:政治身体; 美学建构; 感性分配; 身体美学
考察身体在漫长历史中的存在景况,可发现身体始终处于西方政治与哲学争论的中心。无论是从政治神学的角度出发对政治身体、国王神迹(the royal touch)的讨论,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兴起背景下对性之本质的不同主张,笛卡尔对心身二元论的提倡,还是近代科学观念对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冲击,包括临床医学的诞生对疾患与身体关系的重塑,社会生物学以遗传解释性格差异的理论,身体都是理解和探究最广义政治变化的核心隐喻和重要切入口。
身体的历史不只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也是权力规训身体的历史,新的“身体——对象的联结”(body-object articulation)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产生。身体为权力关系所干预和利用,所谓的“身体”就是一个被制造的、观念堆叠的产物,是一种人为的“拟制”(fiction),提供了支撑统治者身份和形象的综合、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中世纪以降,围绕王权的拟制身体形象逐渐衍生出了“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二分的社会共有意识,这一新变化也预示着政治与美学通过身体建立联系的可能。
渗沥液A/O系统O池为好氧处理工艺,O池的曝气量与除臭风量及加盖密封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在方案确定前对曝气量进行了实地监测,依据实际运行的曝气量乘以1.2倍的安全系数,确定除臭系统的风量,以保证加盖后的O池在运行过程中处于微负压状态。
一、国王的两个身体——“政治身体”概念的缘起
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Early Modern),欧洲各地涌现出大量表明人体脆弱和不完美的证据。受限于当时由一个个强大威严的君主统治的封国、公国构成的稳定连续的封建专制结构,政治理论家、神学家必须弥补教权、王权的至高无上与主教、君王个人身体存在诸多缺陷这一现象之间的罅隙,逐渐发展出“国王的两个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这一概念:
“国王同时具有两个身体,即自然身体(Body natural)与政治身体(Body politic)。他的自然身体(若依其自身考量)是一具肉体凡胎,受制于由自然或意外导致的各种病痛疾患,以及婴儿期与衰老期的愚昧呆痴,和其他人的自然身体一样具有种种缺陷。但他的政治之体不是可见可触的肉身,而是由政制和治理构成(consisting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其构成之目的为指导人民,以及管理公共福利,并且,此身体完全免于自然之体可遭受的幼年、老年以及其他自然败坏和能力不足,为此,国王在其政治之体里面所作之行为,不因其自然之体的任何无能力而导致无效或失败。”[1]77
肖像是对某人的一种再现,国王最重要的无生命的代表则是他的画像。用17世纪波尔—罗亚尔的逻辑学家的话来说,“恺撒的画像即恺撒”。损坏或冒犯国王的艺术再现,即被等同于攻击绝对君主制的核心要素——政治身体本身。国王的艺术再现与他的自然身体同生共存,对这一观念的普及倡导最力者当属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截至1715年,路易十四的统治行将结束之际,已有不下700件各色围绕国王的绘画和雕塑作品。[2]100在画面中,路易十四通常全身披挂盔甲、手握权杖、表情坚毅抑或端庄随和,将理想化的描绘与写实的细部融会在一起。国王肖像画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常规元素与非常规元素并置,国王身着加冕礼袍,配之以王权的标准物品:王冠、权杖和宝剑,并且,有女神站立在国王身旁,往往还有宗教神话传说中的怪物,被国王踩在脚下。[8]38
“对君主宗教仪式般的加冕典礼正是这个类神性政治身体的象征,它将君主与其他所有凡夫俗子分离开来。”[2]92于是,国王成为了同时具备神圣的权威和世俗权力的唯一一人。“小写的国王,指那个膝盖会因痛风而肿大的那个真实的个人,那个血肉之躯,被全然转变为他的‘形象’,成为了一种‘再现’,成为了大写的国王,代表尊荣、威严与政治身体。”[3]222路易十四本人认识到了国家权力的这种双重性,他的名言“朕即国家”正是绝对君主制(absolutist monarchies)个人化的生动体现。
探究政治身体的形象化及法理化建构过程,成为了众多学者集体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既有霍布斯、洛克这样的古典政治哲学家,也有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米歇尔·福柯等思想史学者。福柯曾就此直言:“我们关注的是‘政治肉体’(body politic),把它看作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4]30这种国家形象再现方式的比喻性转变,暗含着一种权力的组织和支配逻辑的变化——权力意图将民众纳入国家建立合法性基础(legitimacy)的过程之中,让民众介入,成为政治身体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由于政治身体的形成是公众共同参与的结果,在阅兵及庆典仪式之外,大规模的公开处刑对暴力的正当化与合理化,使得政治身体成为了完全依赖视觉再现的存在。
课堂1:老师声音清晰,但是紧张,后稍好。准备教学材料充分,讲故事学习单词,较好,但是节奏缓慢。问题太难,提示较少,没有介绍强调具体的事例或语言点,给学生做笔记。(2006年10月9日)
二、政治身体的美学建构——视觉再现与观念形塑
罗马帝国时期的统治者们充分吸收了利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技术:凯旋的将领往往让士兵扛着大型的人物宣传画,用图画向民众描绘攻城略地的场景;奥古斯都在位期间让人塑造了大量的青铜半身像;图拉真建造的纪念柱,柱身浮刻着皇帝的赫赫功勋;提图斯、君士坦丁则建立了庆祝胜利的凯旋门。但这一时期的造型艺术与古希腊相比,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古希腊的艺术品追求造型效果、宏大效果与纪念碑效果,没有或者少有情节,缺乏叙事性和戏剧性;罗马和基督教艺术重图解,重叙事——错觉效果,追求戏剧和电影的动感。”[9]63不论在表现方式上有何差别,被雕刻的身体这一视觉符号在政治身体的威严面前毫无地位,创作者不需要精确地如实还原,观看者也不被要求见证它的纯正性,而只需要在塑造的人物、事件的崇高前为之颤栗,进而向权力屈服。
借助公开地、艺术化的再现方式,利用登基加冕、葬礼和节庆日等仪式典礼、包括艺术作品赞助制度、盛大的阅兵游行、竖立大型纪念碑和雕塑,政治身体的塑造被带入国家的正常运作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政治身体观念的形成不但仰赖不同的思考方式(ways of thinking),同时,也意在调动多方面身体感觉的参与,汇聚各种感官的共同作用。下面试对几种通行的方式进行分析:
(一)肖像画
整合层。在该层将数据接口作为基础,对原始数据进行基础处理,主要处理对象为冗余数据、重要数据、失真数据等,在此层主要为保证数据的真是有效。
所以,伟翔把工资奖金交给我,我都当那是他欠我的。我会说:“别当是你养我,我为你付出的远远比这几个钱多得多。”
当一副图像超出写实的意涵而具有了象征性时,就“有能力指向别处、远方、指向象征性的他者,能与观者建立联系,并进而在不同的观者之间建立联系”[7]42。与此同时,“只要图像向自身之外的别的事物开放,就有其神圣之处”[7]43。
当路易十四无法接见来宾时,国王的肖像画就被置于御座厅中代替国王,履行其作为公共人物的职责,路易是国王的化身,而他的画像则是君主制本身的再现。除此之外,“路易十四的视觉形象见诸绘画作品、青铜制品、石料制品、挂毯(并鲜见诸蜡笔画作品、搪瓷制品、木料制品、赤陶制品以及腊制品)”[8]19。这种日常生活随时随地被政治意象填充,从路易有“太阳王”之喻可见一斑,政治身体被呈现为一种显而易见、可触可感的物质实体,而且是一个能够进行多重、无限再现的整体,就像太阳一样,拥有无远弗届的笼罩范围。
政治身体与自然身体的二分,一方面承认了国王身体本身具有自然的残缺特性,是不完美的,但同时却又创造出一个拥有神秘意味的、水火不侵、永恒不灭的政治身体,从而回避了教权、王权对自然身体的依赖所内涵的脆弱性。
在罗马帝国,直至帝制时代后期,在公开场合展示肖像依然受到严格的管束和限制。起初只有故去的显胄才有被画成肖像的资格,后来在世的权贵也拥有了这一特权,但只限男性公民,女性肖像和半身像的出现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正如画像的权利,最初属于贵族身后的特权,直到共和时代的晚期,方才给予普通公民。”[7]10
(二)雕塑/纪念碑
以人物立像来彰显统治者的尊贵与权威,其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古典时期,雕塑、绘画与颂歌一样,都表现了当时兼顾精神与肉体的贵族审美理想。据希腊史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记载,第一尊为奥林匹克竞赛优胜者塑造的雕像出现于公元前536年。“无论是为在奥运会上夺冠的青年贵族塑造的、通常被称为‘阿波罗塑像’的立像,还是埃伊纳神庙山墙上那些有着轻描淡写的强健体魄和骑士风度的塑像,都与品达罗斯那种贵族——英雄化的、带有含蓄古风的颂歌风格相呼应。”[9]41无一例外的,这些雕像表现的都是充满竞赛精神的理想男性,而且都是有着贵族气质和健美体魄的人物类型,它们不求逼真,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尽可能地表现人体,阐释人体美。批评家博德曼如此评论帕特农神庙的饰条——人体的形象“被理想化,而不是写实化;同时也不是将神拟人化,而是将人予以神化”。[10]291僭主(Tyrant)们则借用这一艺术形式,在公民广场和神庙前为自己立像,用以宣扬功绩,树立军功卓著的统治形象。
护理干预后,干预组患者无抑郁、轻度抑郁、中度抑郁相比常规组要多,而重度抑郁患者明显少于常规组,组间各指标差异较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患者护理后的抑郁程度情况如表1所示。
政治身体类似于一种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但其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神学的概念被使用,与“正当性”、“证成性”这些现代政治哲学的术语有很大的区别。在西方世界的早期语境中,合法性(legitimacy)一般指国家权力的法理基础。按照马克思?韦伯对国家的社会学定义,国家被视为社会内部一种对合法暴力拥有垄断权的组织机构,韦伯创造了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政权的合法性来源进行了分类,把合法性定位在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来源的感受之上。[5]22韦伯提出了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卡理斯玛型和法理型,以及与之相对的三种支配形式(form of domination),即官僚制、家长制和卡里斯玛制,分别依靠遵从首领权力的传统习俗、正式程序的制度沿袭、领袖的超凡禀赋,授予其不同的合法性基础。但这三种理想支配类型,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往往是交错重叠的,维护法制的基本权威,以君主的个人魅力吸引追随者的认可和服从,弘扬传统的礼节仪式强化人们对权威的认同,实际运行中的权威往往有着多重的合法性基础。政治身体可被视作与合法性具有某些共通意涵的概念,如果要把国家表现为一个有机体,对国家的身体化再现就是维持国家权威这一假象的关键,亦即让远离统治核心区域的广大民众产生一种错觉,即国家就是真实存在、可触可感的一具身体。
借助对“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和“纪念碑”(monument)这两个概念内涵层次的说明,或可从另一侧面理解政治身体的视觉符号化、显身式再现。这两个词都源自拉丁文monumentum,本意为提醒和告诫,“纪念碑性”指的是一种纪念的状态和内涵,更多地关注纪念碑符号层面上的象征纪念功能,以及这一功能的历史延续,但一座纪念碑即使丧失了仪式层面的纪念功能和教育意义,依然可以作为由物质材料构成的建筑物而存在。如同政治身体关系到王权的延续、统治的权威、合法性的赋予一样,纪念碑性也和集体记忆的承续以及政治和宗教义务有关。巨型建筑和雕像的建造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它们所使用的石料和砖块也尽可能地增强建筑的永久性。“可以说,三个基本元素——可视性、永久性和纪念性——共同构成了它们的纪念碑性。”[11]24
纪念碑性的本质不仅仅限于建筑的外形和表明功能,而在于可以内化(internalization)礼仪规章、道德规范、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雕塑和纪念碑所显现的是对权力的公开展示,使得这些人造物具有重大的、超乎它们实用价值的意义。“只有一座具备明确‘纪念性’的纪念碑才是一座有内容和功能的纪念碑,‘纪念碑性’的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意义。”[12]5纪念碑是政治性的建筑物,就像国王的身体不单纯只是一具拥有新陈代谢功能的生物性肉体。“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12]5
(三)集会/游行
“政治“(politic)这一概念直接源自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一个城邦即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富有强烈包容性的、积极参与和相互竞争的公民组成的政治社团”,[13]22公民空间位于其中心地位。“在古希腊,公共的即政治的,和私人的即个人的或者家内的领域之间,不可能有明确的对立存在。”[13]23希腊的政治活动具有直接和参与性的特点,公民大会(Ekklesia)及其举行的议事厅和户外剧场,正是这一特点的最好体现。
随着燃料乙醇和食品加工中伴生的液体副产品产量增加、果蔬种植规模化伴生的鲜基饲用资源增加,加上环保要求趋严、饲料成本上升,促进了液体农副产品、鲜基地源饲料和发酵液体饲料的应用和推广,液体饲料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1]。
Image(意象)的原初意涵指的是人物或肖像,始自13世纪,其词义可追溯至拉丁文词源imago(这一词演变后带有幻影、概念、观念等义),同imitate(模仿)的词义演变存在着某种关联。但语词的应用往往附加着歧义和模糊效果,“image这个词蕴含了一种极为明显的张力——在‘模仿’(copying)的概念与‘想象、虚构’(imagination and the imaginative)概念二者之间”[6]270。对Image(人像或肖像)这个英文词实体意涵的考察,围绕着“模仿”、“想象、虚构”这两重概念出现了无限衍义的现象,“这两重概念——就其整个形塑过程而言,皆属于心理概念(mental concept),其中包含了相当早期的意涵:设想不存在的东西或明显看不见的东西”[6]270。
由表2可知,干预后全院及各临床科室日均领药次数和领药时间均较干预前大幅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其中,全院日均领药次数降幅为53.4%,全院日均领药时间降幅为74.5%。这说明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改善领药过于频繁、领药耗时长的现象。由于妇科为新设立科室,故无干预前数据,但干预后其日均领药次数和领药时间数据表明优化后的流程可良好地适用于新增设科室。
广场与议事厅,赋予了政治身体的展演一个仪式性的空间。空间的改变则映射出社会对个人身体的监控和管理,使个人与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能通过空间的改变而大幅缩小,甚至达到合而为一的最高境界。“所谓的议事厅,就是一个大型的聚会场所。”[14]42罗马帝国的议事厅结构长而高,四周围绕着裙房,大厅两端有亮光,窗户正好开在裙房屋顶与议事厅相接之处的上方,庄严的氛围与议事人员肃穆的着装、庞大的数量相匹配,平添对帝国与皇帝的崇敬之情。“罗马空间的几何学规训着身体行动,并且发出命令,命人观看并遵守。”[15]129当恺撒在外与高卢人作战时,他派人在罗马广场西侧修建了一个新广场,名义上说是为了提供额外的空间备处理法律事务之用,实际目的则是提醒罗马人恺撒那缺席的在场,让人感受到皇权令人敬畏的存在。
国王触摸仪式成为了王权神圣性的一种强有力象征。在登基过后两天,路易十四就施行了首次国王触摸礼,有3 000名患者获得了国王的恩赐。“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触摸过35万人:这只是个保守的估计。可以说,这些人完全表明了其对神圣王权的信仰。”[8]175触摸仪式之后,假若出现了暂时性的病情消退,或罕有的痊愈案例,那么民众对国王创造奇迹能力的信仰就有了正当理由,国王借此获得了道义的信任、信仰上的支持与个体魅力形象的提升,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随之建立起来。
因应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动员与宣传,特别是身体的调动与训练,在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于原来仅为征发赋税及维持治安之对象的人民,为了促其转化为主动致力于国家发展的‘国民’,须逐步进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16]258一方面,纳粹试图从一战军事与精神的双重挫败中,重新构筑起强健的雅利安男性形象;另一方面,激化起排犹浪潮以清除犹太人——这一潜藏在德国政治身体内部的隐秘威胁。党卫军和冲锋队的设置,希特勒青年团的建立,塑造出“武装的身体”(armoured body)的军事化身体统御方式。同时,一系列连续不断的节日庆典,以及相伴的游行庆祝活动,渲染出热闹、特殊的气氛,增加游行的声色,提醒公民们国家取得的成就。“为期数周的准备,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及壮观的游行活动,试图赋予国家纪念活动以引人注目的重要性,以此建立一种‘我们’的感觉,从而让公民们相信他们是这一伟大尝试的一部分。”[17]35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身体被置换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念。通过公开场合激情澎湃的演说,唤起民众参与的热情;不定时举行的阅兵仪式、大众的集会和游行,壮观的场面对力量的展示,让尚未认同这一组织的旁观者印象深刻。“这些游移在街道和公共广场上,进行示威、游行、请愿、讲演和国民大会的身体,它们的存在和装扮,以及激情的诉求和集体情绪沸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经常使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在急遽的时间内变成一个深受各方关注的政治或社会文化空间。”[18]192但政治身体的再现受多方因素的制约,身体的力量(the power of body)不是一个固定空间所能全然框限。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内,身体所蕴含的能量一经释放,可以使一个原本平凡的空间变为一个极具政治张力的地带,这也为冲破政治身体设置的界限预留了可能。
翻开大蒜史,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许多物种中,就有“大蒜”。晋惠帝逃难时,就曾从民间取大蒜佐饭。《太平御览》记:“成都王颖奉惠帝还洛阳,道中于客舍作食,宫人持斗余粳米饭以供至尊,大蒜、盐、豉到,获嘉;市粗米饭,瓦盂盛之。天子啖两盂,燥蒜数枚,盐豉而已。”
(四)仪式/观念
权力系统总是依赖某种社会规则及其集体意识(consciences collective),而“社会规则又能借助仪式行为嵌入身体,社会权力关系也随着这些嵌入过程被内化”。[19]28在日耳曼人征服过程中兴起的国家,由于王权被引入了合法的基督教仪式,对基督教意识形态的虔诚、对既定的教会和王室组织结构的认同,连同对国王神圣性的确信不疑,一道构成了普通民众的集体心态和共同情感。“这种情感把神异世界与生活世界、个体追求与社会需要、历史记忆与公共秩序等连接起来,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一部分。”[20]528流行于中世纪11世纪到18世纪期间的英法国王以手触摸为患者治病现象,正是权力借助仪式、观念、信仰与民众互动的最好例证。
在许多世纪里,英法盛行着一种观念,国王被认为拥有超凡的治病能力,依照传统仪式,国王仅仅通过以手触摸患者,就能治愈瘰疬病。这一遍及整个欧洲的由一种思想和情感运动所促生的治病仪式,有其漫长的演化历史。在王权与教权界限模糊的时段内,由于基督教精神支配权的确立,王权的神圣性与神秘性被纳入基督教精神形态,国王被视为神圣之人,被人们认为拥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这些超自然特性是由意义极其明确的仪式来表现的,登基仪式、涂油礼、圣餐礼在宗教礼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希伯来所有礼仪中,涂油礼是一个基本的要素,它构成了一个人或物由俗入圣的正常步骤。”[20]51加冕典礼确立了王权神授这一概念,圣油使国王具有了基督形象,而加冕典礼使其具有了神圣性。西欧的君主们继承了长期存在的尊崇习俗,被烙上了神圣的印记。由于中世纪的人们习惯于以一种极为世俗而实际的方法来想象宗教事务,此世与来世的生活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圣化礼内容的一切都具有治病能力”。[20]59-60
观看者的参与是政治身体再现得以成功的关键。1662年,路易十四在杜伊勒里宫的广场前,举行了骑兵竞技表演,在其回忆录中,国王特别强调了这一登基以来首次娱乐活动的政治意义。此后,路易十四每经过一座城市,都要举行凯旋般的入城仪式,这种仪式起源于中世纪末期。通过定期的对一些城市的政事巡防,以使平头百姓得以分享国家的壮丽和国王的荣耀。
民众对“国王神迹”的信仰,源于对神圣王权超自然性的信念。随着17、18世纪英法两国革命的爆发,两位国王被公开斩首,显示出政治身体的虚构性质(artificial body politic)。国王被揭露为只不过是一介凡人(natural body),其后再造政治身体的诸多尝试总是显露出空洞的一面,政治身体概念也逐渐被代议制政府、共和主义思想所取代。但通过身体的教养操弄民众的感官,调动多种艺术形式增强美学再现的效果,塑造臣属于权力体系的身体展布格局,成为各类统治者追求的共同目标。正视这种规训力量的存在,并评估它对身体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剖析其运作的美学机制,以寻求一种解放的可能,这是朗西埃为我们指明的方向。
三、感性分配——身体美学与政治解放
在法国思想家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看来,“治安”(police)和“寡头制”(olgarchy)构成了分析当代政治的重要概念,与这两个概念相对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和民主。“政治一般被看作一系列的程序,从而实现集体的聚集并就一些问题达成一致,(它指的是)权力的组织、地位和角色的分配,以及使得这一分配变得合法化的体系。”[21]46典型的观点将政治简化为科层制官僚化的行政体系以及经济管理,朗西埃则拒绝这种做法,他直接倾向于把社会视作一个等级秩序进行分析,分配体系被“治安”(the police)代替,“治安秩序”(police order)被用来指称所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包括议会的立法、政策的制定(policy-making)、行政命令、司法判决,以及市政设施维护、公共安全保障和经济的规划。
“治安”这一概念的引入,朗西埃意在指涉社会组织,泛指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划分与分配。“‘治安’这个用语往往会让人想到基层警察、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警棍攻击与秘密警察的审问。”[21]46但朗西埃马上给予提醒,如同福柯对治理术的一系列分析,作为一种治理(gouvernment)的技术,治安在17、18世纪即已出现。“治安包括所有事情,任何治安秩序都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也制造了等级),而且还决定着‘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由此它也决定了一个物质秩序)。”[22]248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分配,职位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安排,商业运行的管理,都属于治安所统辖秩序的一部分。
治安似乎成为了一个广泛的、无所不包的空间,事实上,朗西埃认为尝试从否定的角度出发,去构想一个存在于治安秩序控制之外的纯粹自由领域(outside)是不可行的。现实主义的做法,是承认人们生活于治安秩序之中,如同追问最好政体一般去分析既有治安秩序的变化和差异,基于社会分化和宰治的进程,具体地聚集于那些被排除于政治参与之外的人所处的位置(a part that has no part)。治安是一个具有“反思性”(reflexivity)的概念,旨在探索一种从压迫性的社会强力中“解放”个体及社会的方式。这一解放的关键,在于对身体(bodies)的特定安排。
任何社会阶级成员,都或多或少有着自己特定的政治利益,但一旦将问题扩展到公民权利的正当施行,关涉到自身政治诉求的表达,则往往受制于原子化的个人在权力场中所处的位置关系。治安即是对社会角色的分配,作为对身体的部署方式,治安“定义的是对做事的方式、存在的方式以及说话的方式的分配”[23]78,任何治安秩序都决定了社会中权势地位的归属。“治安首先便是界定行动的方式、存在方式与说话方式分配的身体秩序,并且确认那些身体依其名称被指派到某些位置或任务上。”[21]48治安秩序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感性的分配/划分(distribution/partition of the sensible)”,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决定外观秩序,通过感知能够理解的秩序运作的方式。“与其说治安是身体的‘规训化’,毋宁说它是管控身体出现的规则、职业的形态,以及这些职业所分配到的空间的性质。”[21]48治安不只决定了社会地位的配置,它还可以凸显或抑制社会中的某一个群体,决定着这群人是否可以发声、可被理解(intelligibility)。在治安秩序中没有位置,意味着被流放至体系的边缘,成为无法被感知、注意到(unintelligible),没有参与既定秩序资格的人(those who “do not count”/“have no part”)。
从政治到治安的转移,表明了朗西埃对政治的基本观点:所有的社会秩序都以等级和统治为特征,秩序和体制建设(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都意在使治安秩序所预设和施行的不平等自然化,并赋予其正当性。破坏治安秩序的感知分配,最终揭发秩序的纯粹偶然性,建立民主的政治参与机制,探寻接受所有言说者皆为平等的可能,便是朗西埃政治美学诉诸的核心目标。朗西埃指出的,是一条通过美学分析转化为政治行动和实践,最后达至政治解放的道路。这一道路奠基在一个美学观点之上——只有拥有了作为感知先决条件的可感性,主体性才能被看到、听见,才能被其他社会成员关注到。当一个社会中某些被认为不可感知的元素,通过表达异见(歧义dissension),向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秩序发出挑战时,民主政治就开始了。政治行动便是某种意义上的审美行为(aesthetics),不但需要重构意义可被感知的条件,必要时还要打乱既有的身体分配格局。可感性的分配即是政治对抗的起点,这种对抗正是为了打破固有的标准,这个标准奠定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基础(principle of propriety),但在寻求平等的感性的分享/分配面前,这个标准建立的社会共同秩序显然是可疑的。
3.1.2 配合施用生物肥料。生物肥料又称生物菌肥,是人们利用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制成。其性质与其它肥料不同,本身不含有大量元素,主要以微生物生命活动的产物来改善植物营养条件,抑制某种病害发生,发挥土壤潜在肥力的作用,从而获得农作物的增产效果。
“政治是一种重新塑造了可被感知事物的行为。”[24]115对可感性(the sensible)的分享,以及在可感性中分配位置,都源自治安(the police)划分等级体系的功能。在朗西埃对政治美学的分析中,审美的参与成为了政治行动的基础,旨在重构视觉和听觉的感觉倾向,以此迎来身体和政治的解放。
四、结语
尽管所身处的社会现实与政治情境发生了改变,但政治身体的建构依然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与政治的集权时代不同的是,今日统治者的物质身体已不再是政治身体想象所围绕的核心,围绕国家与公民身体控制权的斗争仍将持续下去。政治身体的演变方式也并非是直白简单、线性叙事地,从原始向文明、从开放转向封闭、从统一转向多元(或称碎片化),以及从绝对主义向民主化的发展。相反,政治身体愈发地成为了一种感性重新配置的场域,无论是在公民个体之间,还是在公民与统治者之间,以视觉符号为媒介的再现始终处于与不断变化的性别、文化和政治观念的对话之中。对于艺术风格的探寻也日益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美学的,即是政治的。
政治身体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美学于其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指出了政治解放的潜在可能。巴赫金对中世纪狂欢节的描述,以及这种节庆日中出现的各类怪诞的身体装扮,就深切体现出与身体有关的美学能量一经释放,就会给统治权力和官方文化带来严肃的挑战。众声喧哗,多元并存和角力的现象,才是身体所处的实际境域。在权力与身体的缠斗交锋中,关注视觉和图像材料的应用,从崇高感的建立和感性分配的角度,拓展政治美学,特别是身体美学的边界,正是剖析身体美学政治维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康托洛维茨. 国王的两个身体[M]. 徐震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身体图景:艺术、现代性与理想形体[M]. 萧易 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3]Marin,Louis. The Portrait of the King[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4]福柯.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 刘北成、杨远婴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赵鼎新. 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M].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17.
[6]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7]雷吉斯·德布雷. 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M]. 黄迅余、黄建华 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彼得·伯克. 制造路易十四[M]. 郝名玮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豪泽尔. 艺术社会史[M]. 黄燎宇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0] John Boardman,JasperGriffin,Oswyn Murray.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1]巫鸿.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12]巫鸿.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 李清泉、郑岩 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3](英)克里斯托弗·罗.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M]. 晏绍祥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4] Richard Krautheimer. 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Architecture[M]. New York:Viking-Penguin,1986.
[15]理查德·桑内特.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 黄煜文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6] 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17]彼特沃克. 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M]. 张洪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18]黄金麟.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 [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9]克里斯托弗·乌尔夫. 社会的形成[M]. 许小红 译. 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12.
[20]马克·布洛赫. 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M]. 张旭山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21]雅克·朗西埃. 歧义:政治与哲学[M]. 林淑芳,刘纪蕙,陈克伦等 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22]Foucault. Omnes et Singulatim:Towards a Criticism of Political Reason [R].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Stanford University,10 and 16 October,1979.
[23]让·菲利普·德兰蒂. 朗西埃:关键概念[M]. 李三达 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24]Jacques Rancière. Dissenting Words: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Rancière”[J]. D.Panagia(trans.)Diacritics30(2):115.
ConstructingtheBodyPoliticfromthePerspectiveofAesthetics——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and Physical Liberation
CHEN H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Among the works of scholars such as Foucault, “Body politic”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ideas and changes in legitimacy. The ruler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 used a variety of visual and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to achieve control over the visual experie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way they feel in the body. These mean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sublime and mysterious aesthetic effects, attempt to reach the goal of sanctifying the country.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body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From the great role of aesthe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ody politic, Rancière discovers the potential for political liberation contained in somaesthetics. Rancière believes that by breaking the existing patter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and giving the body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and share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equally, it can weaken and resist the discipline of "the police".
Keywords:the body politic;aesthetics construct;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somaesthetics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408(2019)01-0035-07
收稿日期:2018-12-06
作者简介:陈汉(1992— ),男,云南曲靖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后人类与身体美学研究。
标签:身体论文; 政治论文; 国王论文; 这一论文; 王权论文; 《昭通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兰州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