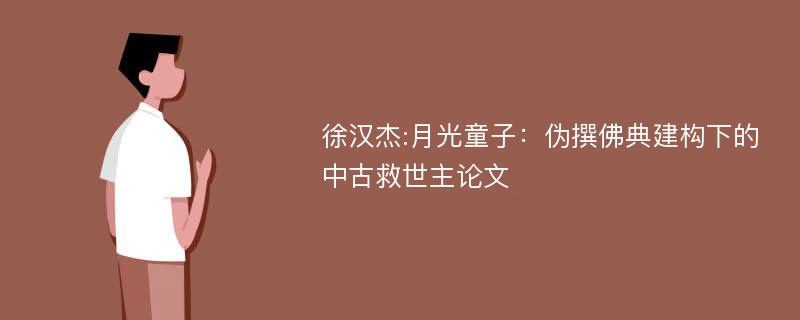
[摘要]中古中国流行的月光童子出世为圣君的观念是在借鉴了译经中的未来佛弥勒形象后,通过中国本土伪撰的佛典塑造出来的。根据这些伪撰佛典的叙述,月光童子将在释迦佛入灭后下生人间作转轮圣君。因此中古时期的统治者经常以月光童子自居,以此来说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另外,月光童子信仰得以产生并被世人所接受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末法”和“无佛”思想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 月光童子; 伪经; 王权; 末法
中国的中古时代(3至9世纪),佛教极度兴盛,整个社会上至帝王公卿下到庶民奴婢都沉浸在浓厚的宗教狂热之中。当时的绝大多数统治者也意识到了利用佛教信仰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统治,特别是在解释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上,佛教的观念逐渐代替了中国原有的“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和“君权神授”等学说。因此,一些统治者甚至不惜以伪造佛典的手段来制造信仰。
中古时期流行的月光童子信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伪撰佛典的建构下,月光童子被塑造成了一位终结乱世的圣君。最早注意到月光童子这一形象的学者是荷兰的许理和(Erik Zürcher),1982年他在《通报》上发表了一篇PrinceMoonlight:MessianismandEschatologyinEarlyMedievalChineseBuddhism(《月光童子:中国中世早期佛教的救世主义和末世论》)的长文,文中许氏对中古时代早期的道教和佛教的救世主观念的特征、发展过程及相关资料作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考察,他认为早期佛教文献中出现的救世主月光童子形象是道教终末论影响的产物[1]155-121。不过,许氏关心的仅仅是佛教文献中的救世论和末世论,对于月光童子圣君形象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并没有做过多的讨论。之后古正美的《齐文宣与隋文帝的月光童子信仰及其形象》一文,重点讨论了北齐文宣帝高洋和隋文帝杨坚对佛经中月光童子的圣君形象的利用[2]。尽管古氏的研究已经不只局限在宗教观念本身,而是开始将月光童子信仰与历史事件相结合,但是她过分强调了帝王们对佛王传统的利用,却忽视了统治者能够有效利用月光童子信仰的现实基础。其实,月光童子信仰的出现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它的产生及其流行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弥勒信仰、末法思想等因素是分不开的,而统治者能够利用这种信仰维护统治的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招标投标活动程序完备,但因投标单位数量过多造成一定的混乱,严重影响投标秩序。对于一个投资不大、规模较小的建设项目来说,多家单位竞争致使中标率低,有的甚至只有2%,这就造成了很多单位和个人在估计自己不中标的情况下,抱着恶意竞标、浑水摸鱼、搅乱市场的心态参加投标,给招标投标市场制造了一定的混乱。
从图1可见,1) 在350 nm波长处生物总碱的吸光度随小檗碱标准溶液浓度升高而升高,即二者间存在线性关系,其回归方程为y=0.022 4x+0.009 7(R2=0.999 4),即小檗碱溶液浓度为7.712~38.56 μg/mL时与吸收度有良好的线性关系。2) 随着小檗碱含量(C)升高,峰面积(A)呈上升趋势,二者间存在线性关系,其直线回归方程为A=0.025 2C-0.100 2(R2=0.999 9)。表明,小檗碱含量在48.2~867.6 μg与峰面积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资料,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采用ROC曲线分析Netrin-1联合Kim-1预测AKI的价值,获得最佳截断值。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利用COX回归性分析确定AK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从弥勒到月光:佛教救世主观念的文本考察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宗教都存在一个末世的概念,不过这些宗教的缔造者们并没有让信众完全陷入末世的绝望之中。末世来临时,他们总会制造出英雄人物把人们从末世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如犹太教的摩西(Moses),基督教的耶稣(Jesus),伊斯兰教的马赫迪(Mahdi),琐罗亚斯德教(袄教)的沙西安(Saoshyant),摩尼教的密特拉(Mitra),道教的李弘等都是传说中的救世主。
在佛教的世界中,最广为人知的救世主当属未来佛弥勒。东汉安世高译《大乘方等要慧经》可能是最早提到弥勒的汉文佛典,不过此经主要讲述释迦佛为弥勒述说菩萨的不退转八法,并没有出现弥勒净土与未来成佛的预言。弥勒的未来佛形象得以在中国确立与所谓“弥勒六经”(分别是西晋竺法护《弥勒下生经》、东晋失译人《弥勒来时经》、后秦鸠摩罗什《弥勒大成佛经》和《弥勒下生成佛经》、刘宋沮渠京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唐义净《弥勒下生成佛经》六部弥勒类佛典)的翻译与传播密不可分。弥勒,本名阿逸多,弥勒为其姓,义译为慈氏,他出生于婆罗门之家,后成为佛弟子,追随释迦牟尼修行。弥勒在释迦之前先行入灭,往生兜率天宫。释迦预言,弥勒将会在他灭度56亿年后,再次下生阎浮提,并托生于翘头末城的大臣修梵摩家中。在经历了出家修行,弥勒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道,以三会说法度无量无边众生,使释迦时代未能得道者度脱。
弥勒信仰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弥勒次补释迦的未来佛形象在印度本土就已确立。而弥勒信仰传到中国后则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异,在弥勒译经中(成佛后的)弥勒与转轮王本是一组对应组合:即弥勒佛是精神世界的最高领袖。转轮王是世俗世界的最高领袖,转轮王为弥勒佛的下生做供养准备,但是弥勒信仰传到中国后则出现了弥勒佛即是转轮王的说法,康乐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影响[3]130-137。这种弥勒即是转轮王的说法在历史上经常被统治者利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武则天在篡位时期对这个理论的使用。她一方面伪造《大云经(疏)》,宣扬自己就是弥勒菩萨下生[4]卷183薛怀义传,4742,另一方面又自封“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4]卷6则天皇后本纪,124,宣扬其为转轮圣王,为取代李唐王朝制造理论。可见弥勒的未来佛形象在中国经常被用来充当圣君出世的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文佛典中除弥勒经典之外还存在一类讲述月光童子事迹的佛典也出现了释迦佛的授记。不过,此类经典的授记主角已不再是弥勒而是月光童子。根据《开元释教录》记载,这类佛典四译一失,除《失利越经》已阙,现存四译,分别是三国吴支谦(?)译《佛说申日经》①,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月光童子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申日儿本经》,隋代那连提耶舍译《佛说德护长者经》(又名《尸利崛多长者经》)四经。这类佛典主要讲述了王舍城大姓富豪申日因信奉外道,欲设计用毒饭和火坑陷害释迦佛。月光童子栴罗法为使其父申日不入魔道,试图劝他放弃,申日不听,最后释迦施展法术,破解了申日的诡计,他本人也在佛陀的开悟之下被彻底感化,皈依佛教的故事。作为同本异译的四经,在叙述申日加害释迦佛,月光劝父的情节基本相似,但颇有意思的是《申日经》和《德护长者经》两部佛典在月光童子劝父的基本情节之外又增加了释迦佛对童子的授记。据《申日经》云:
当出世为圣君的月光童子佛典虽然都伪撰于中国本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凭空产生的。许理和(Erik Zürcher)在考察中古早期道家对佛教的影响时,就注意到了《首罗比丘经》中对道教末世弥塞亚主义的吸收与继承。[1]许氏的研究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这里我们不想再单独讨论具体某部月光童子佛典的源头,然而在对比了多部月光童子佛典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其实都多少受到了弥勒译经的影响。为方便讨论我们将两类佛典的相似之处列于下表:
《德护长者经》云:
(佛言:)“又此童子,我涅槃后,于未来世护持我法,供养如来受持佛法,安置佛法,赞叹佛法。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名曰大行,能令大隋国内一切众生,信于佛法种诸善根。”[5]第14册,849中栏
企业要想实现新发展,就必须加强对权利合理分配工作的重视。在公司制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必须合理开展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配工作,才能保障股东的应有效益。通过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可以加快问题解决速度。
在《申日经》和《德护长者经》的释迦佛授记中,释迦预言了在他入灭后,月光童子将接替他成佛,护持佛法,这种情况与弥勒经典宣扬的弥勒将接替释迦作佛极其类似。这类佛典也接受了“转轮王即佛”的观念,文中不仅提到月光童子将要“作佛”,而且还说其当出任“圣君”。与弥勒下生阎浮提翘头末城不同,《申日经》中的月光童子当出任“秦国”圣君,《德护长者经》则表示他将作“阎浮提大隋国”的国王。毫无疑问,不管是“秦国”还是“大隋国”,其实都是指代中国。
另一方面,除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少数几人外,中古时期的帝王大多热衷于发展佛教事业。北魏初年,僧人法果为道武帝拓跋珪创立了当今皇帝即为现世如来的政教结合政策[8]卷114释老志,3293,北魏文成帝时,昙曜等人在云冈、龙门等地开凿了多身“帝王如来身”的大石佛,使“皇帝即如来”的观念第一次反映到了佛教造像之中。不久,“皇帝即如来”的观念也传到了南朝,梁武帝开始以“皇帝菩萨”的身份进行统治⑧。此后,这种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帝王所接受,但是帝王们热衷的“皇帝即如来”观念与中古社会上流行的“末法”和“前不值释迦,后不遇弥勒”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长期处于“法灭”和“无佛”的危机意识之中也是极不利于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北齐文宣帝高洋、隋文帝杨坚和武则天等人才会以月光童子自居,通过篡改佛典来标榜自己就是当世如来。可见出世为圣君的月光童子佛典虽然都是在中国本土伪撰的,但从它们背后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却是真实的。
在这些“译经”之外,中古时期还流传着一部预示月光童子即将出世的伪经——《首罗比丘经》②。此经又名《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宋后不传。幸运的是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了此经的若干写本,使我们又能见其面目③。其经文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以首罗比丘与五百仙人二人间的问答展开,五百仙人预言了月光童子即将出世,并为首罗比丘解答了月光童子出世前后的种种迹象。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君子国国王、大臣、宰相、一切士官并及国内人民在五百仙人的带领之下来到“蓬来山海陵山闵子窟”中拜见月光童子,听童子说法的情景。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前面经文内容的引申,其中多次出现了“法王欲待,圣君欲下”,“月光童子欲出,圣成(城)欲现”等宣扬月光出世的字句,很明显是在呼应前经,不过第三部分的经文结构零散,语意混乱,其中又有咒语及相关行法、谶言等的混入,因而显得条理不甚明晰。此外,在中古时期流通的《法灭尽经》④、《般泥洹后诸比丘经》⑤等伪经中同样也提到了月光童子的出世。
月光童子从坐而起,赞叹佛已而白佛言:“设我来世得作佛时,令我国土一切人民无有恶心皆应质朴。有诸恶国人民刚强五浊贱世,我愿于中而开化之。……佛告阿难:“我般涅槃千岁已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受我经法兴隆道化。秦土及诸边国,鄯善、乌长、归兹、疏勒、大宛、于填及诸羌虏夷狄,皆当奉佛尊法普作比丘。”[5]第14册,819上栏、中栏。
佛经中的情节佛经类别释迦佛授记新佛的下生时间佛出世时的人寿佛出世后为国王说法的情形迦叶的涅槃“弥勒六经”佛常言:“佛去后当有弥勒来。”《弥勒来时经》弥勒佛却后六十亿残六十万岁当来下。《弥勒来时经》尔时人寿极长无有诸患,皆寿八万四千岁。《弥勒下生经》是时蠰佉王闻弥勒已成佛道。便往至佛所,欲得闻法。……将八万四千众,往至佛所,求作沙门。尽成道果得阿罗汉。《弥勒下生经》(佛告迦叶:)大迦叶,亦不应般涅槃,要须弥勒出现世间,所以然者。……弥勒如来当取迦叶僧伽梨着之。是时迦叶身体奄然星散。《弥勒下生经》《申日经》(伪撰部分)佛告阿难:“我般涅槃千岁已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我(佛)般涅槃千岁已后《德护长者经》(伪撰部分)(佛言:)“我涅槃后……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般泥洹后诸比丘经》(佛涅槃)千岁之后,三百岁中人寿百八十岁《法灭尽经》寿命延长,诸天卫护,月光出世。《首罗比丘经》(君子国国王率)大臣并及人民随从大仙有五万七千人,去君子国七千余里,到蓬莱山中,海陵山下闵子窟所,见月光童子向者所说,汝若不信,但看迦叶石像,是吾出世记耳。
从上表可知,与弥勒经典一样,《申日经》和《德护长者经》两部月光童子佛典都出现了释迦佛的预言。《申日经》和《般泥洹后诸比丘经》甚至还为月光童子的出世加上了一个时间期限,这与弥勒经典宣扬的弥勒当在释迦入灭56亿年之后成佛极其类似,只不过与弥勒相比,月光童子出世时间要来的更短。在《弥勒下生经》中提到了弥勒下生时人寿当有“八万四千岁”,巧合的是《般泥洹后诸比丘经》和《法灭尽经》中也出现了月光童子出世时人寿的相关表述。弥勒成佛后,《弥勒下生经》记载了蠰佉王带领众人前往佛处听其说法的情节,而《首罗比丘经》中同样也出现了月光童子出世后君子国国王率大臣和人民拜访月光童子的情景。另外,迦叶作为将释迦佛衣钵传至弥勒的中间人,释迦佛曾告诫他必须在弥勒出世后再入涅槃,有意思的是,在《首罗比丘经》中我们也能找到迦叶的入灭与月光童子出世之间的联系。综上所述,不难推测当为圣君的月光童子佛典即便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但也是吸收了不少外来弥勒译经的结果。换句话说,即未来佛弥勒其实是月光童子的母胎。
二、从文本到现实:月光童子信仰与中古中国的王权塑造
月光童子的救世主形象是通过中古时期的伪撰佛典塑造的,但这并不影响月光童子信仰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作用。相反,大多数伪撰佛典的产生都带着作伪者的某种目的,因此它们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实来得更加直接。
予(道安)生不辰,值皇纽绝,猃狁猾夏,山左荡没。避难濩泽,师殒友折。……然天竺圣邦,道辽远,幽见硕儒,少来周化。先哲(释迦)既逝,来圣(弥勒)未至。进退狼跋,咨嗟涕洟[7]卷10,368。
兴宁三年(365)四月五日,凿齿稽首和南。……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日月虽远,光景弥晖;道业之隆,莫盛于今。岂所谓月光道寂,将生真土;灵钵东迁,忽验于兹乎?……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逸响,重荡濯于一代矣[6]卷12,639-640。
僧佑在其另一部著作《出三藏记集》中著录的《佛钵记》一经后有注云:“或云《佛钵记》,甲申年大水及月光菩萨出事”[7]卷5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225。《佛钵记》也是一部中国撰述的伪经,其文本早已失传,但从僧祐的注文中我们大体可以猜测其内容也应当与月光出世有关。可见当时“月光出世”与“佛钵降临”已是一对固化组合,因此信中提到的“月光”毫无疑问也是指月光童子。而信中所说的肃祖明皇帝其实就是晋明帝司马绍,司马绍是东晋历史上的第二位皇帝,他本人笃信佛教,在位期间广修塔庙,大力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同时他还平定了王敦之乱,协调地方势力,对稳定东晋王朝的局势至关重要。习凿齿的意思很明确,他认为司马绍的出现正是应验了月光童子降临中国,佛教必将得到重振。当然光从此信还不能看出司马绍本人是否宣扬自己是月光童子下生,但习凿齿把司马绍比作月光童子这一现象,至少能反映出此时月光出世为圣君的观念已经流行,而且月光童子的形象也已开始用来为帝王的统治服务。
因为月光童子有出世为圣君的形象,所以这个称谓在当时对于一般人来说又是极其敏感的。如北魏熙平年间(516-518),刘景晖参与了王买等人领导的叛乱后被擒,群臣在朝堂上讨论对其如何处置的问题。廷尉卿裴延儁认为应当把刘景晖处死,但正崔纂不同意,他认为刘景晖只是一个9岁小儿,并不具备叛乱生事的能力,他只是被别人利用,才会与叛乱者一道来蛊惑民众。而且 “月光童子”这一头衔也并非出于刘景晖本人的意思,而是被那些渴求邀功的奸吏们无端加上的[8]卷111刑罚志,3141。不难推测奸吏们为刘景晖加上“月光童子”这一头衔,很可能是想加重他的罪孽,从而获得更大的功劳。因为按照佛典的意思,月光童子的出现代表着将有新君出世。
W4#=0.6(0.6415,0.1279,0.7428,0.1056,0.0961)+0.4(0.2509,0.2159,0,0,0)T=(0.4853,0.1631,0.4457,0.0634,0.0577)T
此后,利用“月光童子”之名来塑造王权正统的事例依然不少,甚至还出现了在统治者主导下伪撰或篡改月光童子佛典的现象。北齐天保八年(558)北天竺乌场国人那连提耶舍译出《月灯三昧经》十卷[9]卷6,419。此经主要讲述释迦佛为月光童子解说一法速得菩提、三昧四十义、入三忍法等教义。在那连提耶舍译本之前,《月灯三昧经》至少已有两译。据《大正藏》编纂者考证,藏中NO.640《佛说月灯三昧经》很可能是刘宋先公译本。此译本又名《文殊师利菩萨十事行经》[9]卷12,713,主要讲述了释迦佛为文殊师利童子解说布施、持戒清净、立忍辱等菩萨行十事,相当于那连提耶舍译本的第六卷。但与那氏译本不同,先公译本的主角是童子身的文殊师利菩萨而非月光童子。藏中NO.641《佛说月灯三昧经》亦是《月灯三昧经》之异译。《大正藏》的编者认为此经的译者很可能是东汉的安世高,不过此经只有正宗分,其内容旨趣略同那氏译本中的第五卷后半部分。
那么同本异译的两经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不同的主人公呢?如果了解那连提耶舍的译经遭遇,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天保七年(557)那连提耶舍来到邺城,高洋对其极其礼遇。从天保八年(558)至天统四年(568),他共译出佛经七部,《月灯三昧经》就是其中之一[9]卷6,419。然而,那氏的译经场景耐人寻味,据《开元释教录》记载高洋“勅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昭玄都瞿昙般若流支、长子沙门达摩阇那(齐言法智)及居士万天懿传语。”[9]卷6,421古正美指出高洋派遣如此多人监督那氏翻译《月灯三昧经》,而且译成后又向群臣宣告“此乃三宝洪基”,是由于他想以月光童子的形象统治北齐,所以那氏才会把此经的主角从文殊师利童子偷换成月光童子[2]174-175。
古氏的这个说法我们比较认同,而且此说在北齐宗室赵郡王高叡留下的《定国寺塔铭碑》中也得到了印证。此碑刻于天保八年(558),碑中有“月光童子戏天台之旁,仁祠浮图绕嵩高之侧。行藏比于幻化,出没放于净土”[10]卷20的记载。月光童子与天台山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但仅看碑文内容很难搞清两者的关系。幸运的是,《首罗比丘经》中保存了首罗比丘和五百仙人之间的一段对话,似乎能帮我们解答这个疑问:
1.3 标本采集 标本采集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四版)和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推荐的标本采集方法[3]。
首罗问大仙曰:“月光出世当用何时?”
车牌定位采用自制的训练数据集,而Yolov2采用的是VOC 2007和VOC 2012数据集聚类得到的5个初始框。以上两个数据集中目标种类繁多,因此得到的初始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为更好地适应车牌结构的特殊性,需要在自制的车牌数据集中重新进行聚类,选取合适的初始框。本文运用k-means++进行真实框的无监督聚类。
《首罗比丘经》云:
从《首罗比丘经》的描述来看,这里的天台山很可能就是找寻月光童子的路标。高叡是高欢(高洋父)之侄,自幼被高欢抚养长大,北齐建立后,封赵郡王,深受文宣帝高洋信任。《定国寺塔铭碑》中所提到的月光童子,其实寄托着高叡希望月光童子出世,创建人间净土的美好夙愿。这与他修建定国寺塔庙的初衷也是一致的,而这个出世的月光童子很可能就是指文宣帝高洋。巧合的是,同样是在天保八年(558),高叡被高洋调回邺都委以重任[12]卷13高叡传,171。可见,高叡刊刻此碑必定与高洋宣扬月光童子信仰有关。我们甚至怀疑,高叡广修塔庙的举动,也是为了配合刚从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手上夺得政权的高洋借佛之名塑造王权的政治活动。
北齐灭亡后,那连提耶舍入隋,为隋文帝杨坚译经。众所周知,杨坚的皇位是依靠宫廷政变从年幼的北周静帝手上夺来的,他本人又笃信佛教,在位期间他经常借佛教之力制造图谶,为新建的隋杨政权增加理论依据。有意思的是,为了配合隋文帝的统治需求,那连提耶舍同样选择了在月光童子身上动刀。开皇三年(583),那连提耶舍为杨坚译出《德护长者经》两卷[5]历代三宝记:卷12,第49册,102下栏,经中又出现了释迦佛对月光童子的授记。隋人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就《德护长者经》出现佛授记的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又《德护长者经》如来记云:“月光童子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脂那国内作大国王,名为大行。彼王能令脂那国内一切众生住于佛法种诸善根。”震旦脂那,盖梵楚夏耳。此称末者,正法既灭去佛渐遥,通言末法。……昔魏太武毁废之辰,止及数州弗湮经像。近遭建德周武灭时,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圣教灵迹削地靡遗,宝剎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凡经十年不识三宝,当此毁时即是法末。所以人鬼哀伤,天神悲惨。慧日既隐,苍生昼昏。天启我皇乘时来驭,君临亿兆化被万邦,庶政咸新典章斯革,轻刑薄赋减役省徭,二十进丁两床输匹,含齿戴发俱喜泰平。既清廓两仪,即兴复三宝[5]第49册,107中栏、下栏。
开皇中,费长房曾入大兴善寺协助那连提耶舍译经,因此他对那氏的译经意图应该相当清楚。他在这段话中指出《德护长者经》中的“震旦脂那”即是指中国,“佛法末时”即是按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隋文帝的出现使得社会风气一改从前,国家轻徭薄赋,佛教三宝复兴,就如同佛法末时下生于脂那国来拯救世人的月光童子一样。另外,那氏还在《德护长者经》中还描述了大行王供养佛钵,抄写经卷,广造佛像,带头出家受菩萨戒的举动,与之后隋文帝的行径也完全吻合。毫无疑问那连提耶舍译出《德护长者经》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隋文帝塑造王权正统,而且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隋文帝,他篡改佛经的举动比北齐时来得更加猖獗。
隋文帝之后,借助“月光”之名塑造王权的事件依然没有断绝。长寿二年(693)天竺僧达摩流支为武则天译出《宝雨经》十卷,经中又出现了释迦佛的授记。据《宝雨经》云:
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曰月光……佛告天(子)曰:“……我涅盘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位居阿鞞跋致,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尔时月光天子从佛世尊闻授记已,踊跃欢喜,身心泰然,从座而起,遶佛七匝,顶礼佛足,即舍宝衣严身之具,奉上于佛。”[5]卷1,第16册,284中栏、下栏
在达摩流支译本之前《宝雨经》已有多个译本问世,《大正藏》中所收梁代曼陀罗仙译《宝云经》和梁代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译《大乘宝云经》都是此经异译,但这两部早出的《宝雨经》异译都没有出现月光天子这一形象。敦煌发现的英藏S.2278号达摩流支译《宝雨经》写经题记有“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监译”几字,薛怀义是武则天的男宠,他为武则天的篡位制造过诸多符谶,在《宝雨经》译出之前,他曾与法明等人伪撰《大云经(疏)》,“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4]卷183薛怀义传,4742,因此《宝雨经》中的这段话很可能也是薛怀义等人有意编造的结果。不难推测,月光天子的原型应当也是月光童子,但此经的翻译者似乎是为了配合武则天的称帝行为,而把经中月光天子的性别改成了女性。
总之,在伪撰佛典的建构下,月光童子被塑造成了一位转轮圣君,不少统治者也意识到了利用月光童子信仰能够稳固自身统治,于是他们又开始以月光童子自居。同时,由于统治者的加入,在世俗权力的干预下越来越多的月光童子佛典被制造了出来,这无疑使得月光童子信仰更加深入人心。
对照组:应用生物敷料进行创面修复,敷料包含微量元素、类黏蛋白、胶原纤维等,首先对创面进行清理和止血,顺延创面边缘将无生物活性或是焦痂的坏死组织进行清除,经电凝进行止血,应用经稀释后的碘伏进行清洗,用无菌纱布包扎,每隔2天更换一次纱布。
三、从伪造到真实:月光童子佛典背后的社会现实
写到这里几个疑问也因此产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月光童子被塑造成了释迦佛的继承者?而且这种伪撰的观念在中古时期为什么又会轻易被世人接受并流传开来呢?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再次回到这些月光童子原典之中。据《申日经》云:
佛告阿难:“我般涅槃千岁已后,经法且欲断绝,月光童子当出于秦国作圣君。”[5]第14册,819中栏
(五百仙人曰:)“古月末后,时出境阳,普告诸贤者:天台山引路游观,至介斧山,又到闵子窟列鲁薄。”[11]104-105
可见月光当在释迦入灭后弥勒未生前出世作佛(圣君)的观念已经成为这些月光童子佛典的固定模式。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涉及月光童子出世的时间问题时,按照《申日经》的说法是在佛涅槃“千岁已后”,《般泥洹后诸比丘世变经》则说是在佛涅槃“千岁之后,三百岁中”⑥。不管是千岁还是千三百岁,月光童子的出世明显比弥勒下生的时间要来得短,更容易盼得。而且按照中古世人对佛灭日期的认识⑦,经中所说月光童子出世时间基本就在中古这个时段,因此月光童子佛典的出现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对新佛出世的期盼,填补了他们对“前不值释迦,后不遇弥勒”的无佛时代的恐惧,所以这种中国本土伪造的观念很容易就被世人所接受了。
《法灭尽经》云:
在先前探讨其他大地震,如1999年集集(中国台湾)、2007年托科皮亚(智利)和2008年汶川(中国)地震的研究中(Wu and Wu,2007;Wang et al,2011),固定台站的高速GPS数据不能得到,但根据临时GPS台网或InSAR观测记录,很好估计出了强震台站的静态同震位移。因此,将已知的同震位移作为参考,研究经验基线校正是否能够得到改进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建议对选择时间参数的判据做修定,以便最终的位移与GPS参考值最接近。我们的结果表明,使用GPS参考值可明显改善由强震记录恢复位移过程(图8),为研究地震破裂过程提供更精确的有用低频波形数据。
佛告贤者阿难:“吾般泥涅后,法欲灭时……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与吾道,五十二岁。”[5]第12册,1118下栏,1119上栏、中栏
《德护长者经》云:
(佛言:)“又此童子,我涅槃后,于未来世护持我法,供养如来受持佛法,安置佛法赞叹佛法。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名曰大行。”[5]第14册,849中栏
《宝雨经》云:
(佛告月光天子:)“我涅盘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位居阿鞞跋致,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5]卷1,第16册,284中栏
佛教认为在佛陀入灭后,佛法将经历正法、像法、末法三个逐渐衰微的阶段。上述引文提到的“法且欲断绝”、“释迦朽故之法”、“法欲灭时”、“佛法末时”等词毫无疑问都是在宣传佛教的末法观。可见按照这些佛典的意思,月光童子出世时正好处于佛教的末法时代。
那么月光童子的出世为什么总会与佛教的末法思想联系起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中古中国的社会现实作一个考察。佛教的末法思想起源于印度,但随着佛教的传入,末法思想也被介绍到了中国,而月光童子佛典流行的中古时期正好是社会上末法思想最为兴盛的时候,这在一些当时留下的造像记和写经题记中可以得到印证。如云冈第11窟北魏太和七年(483)造像记云:“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积,生在末代,甘寝昏境,靡由自觉,微善所钟。”[13]25-26北齐天保十年(559)的《房绍兴造像记》云:“尹自然无始,物生在中,咸归雕洛。天长地久,终致消灭。”[10]卷21在敦煌写经中,亦有不少体现末法意识的题记。如S.4528《仁王般若经》东阳王元荣写于北魏建明二年(531)的题记云:“佛弟子元荣,既居未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是以身及妻子奴婢六畜,悉用为畀(毗)沙天王布施三宝。”上博15号(3317号)《法华经文外义》比丘惠袭写于西魏大统十一年(545)的题记云:“比丘惠袭于法海寺写说,流通末代不绝也。”当然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甚至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写经造像之风其实也是末法思想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在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佛教末法观念在现世得到了应验,更使得世人深信此说。
不过佛教在提出了佛法将会衰亡的末法概念之后又指定了弥勒的下生来终结末世,重振佛法。因此,生活于被末法思想笼罩的中古时期的人们一直在期待着弥勒的降临。如北凉昙无谶译《优婆塞戒经》的《出经后记》云:“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将来之世,值遇弥勒,初闻悟解,逮无生忍。”[7]卷9,341北凉《白双且塔铭文》云:“(弟)宗亲捨身受身,值遇弥勒,心门(意)解,获其果愿。”[14]184这些材料都表达了时人对弥勒下生的期待。然而弥勒下生人间需要很长时间,不管是《阿含经》中所说的“将来久远”、“三十劫”,还是《弥勒上生经》中所说的“五十六亿万岁”,对普通人来说都太过漫长。所以在对弥勒期盼的同时,当时的人们又普遍存在一种“前不值释迦,后不遇弥勒”的无奈之感。据释道安的《道地经序》云:
最晚至四世纪,月光童子的圣君形象已经被中国社会所接受了。关于当时的月光童子信仰我们在东晋兴宁三年(365)习凿齿写给释道安的信中是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僧祐的《弘明集》保存了此信,信中说:
这里道安所说的先哲就是指释迦佛,来圣则是指弥勒菩萨,可见道安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就是处于释迦已逝弥勒未至的“无佛”时期。而且世人对“世不值佛”的恐惧在当时的造像记中也有所表现,如北魏正光五年(524)刊刻的《刘根四十一人造像记》云:“生于千载之下,进不值鹫岩(释迦)初轩,退未遇龙华(弥勒)宝驾。”[15]164东魏武定七年(549)的《兴化寺高岭诸村造像记》云:“生遭季运,前不值释迦初兴,后未遭弥勒三会,二圣中间日有□叹。”[16]卷2,3037上栏
讨论到这里,我们再次把视角回归到月光童子佛典上来。据《法灭尽经》云:
吾涅盘后法欲灭时……诸天护卫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与吾道……如是之后数千岁,弥勒当下世间作佛[5]第12册,1118下栏,1119上栏、中栏。
(1)依据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在施工现场,制定相应的工序、要点,完成相应的观测工作,并且每一项观测任务都落实到个人。
《宝雨经》云:
佛告天(子)曰:我涅盘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位居阿鞞跋致,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天子!汝于彼时住寿无量,后当往诣覩史多天宫,供养、承事慈氏菩萨,乃至慈氏(弥勒)成佛之时,复当与汝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5]卷1,第16册,284中栏。
首罗比丘稽首问曰:“明君出世,法则云何?土境何以?疆场阔硖(狭)?”大仙答曰:“卅六国,疆场如是。”首罗问曰:“当化之时,万民有百调之名次,复输之太平治化,当用几载?”大仙答日:“当五十二载,为欲显释迦朽故之法。”[11]104
那么疑问也由此产生,在《申日经》和《德护长者经》为什么会出现月光童子将下生到中国为圣君呢?作为此经的同本异译,竺法护译的《月光童子经》和求那跋陀罗译的《申日儿本经》中又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段释迦佛授记呢?而且即便是都存在佛授记的《申日经》和《德护长者经》两经在处理如此敏感地名时为什么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呢?这些现象都是极其不正常的,唯一的解释是《申日经》和《德护长者经》两经的佛授记并非译自梵本,而是经文在汉译的过程中人为窜入的结果。
见义勇为的精神应该提倡,但是我们也应尊重客观规律。按照人的自然生理规律,处于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原本就是弱者,他们不像成年人那样有自立的能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首先要思考的命题不是救人,而是“自救”。因此,我们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而应通过智取的方法“见义巧为”,在保证自我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再去救别人。
四、结语
中古时期月光童子信仰虽然已经被当作了一般的佛教信仰受到世人认可,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不管是经典文献还是信仰模式,月光童子信仰都是脱胎于佛教的弥勒信仰。与宋后“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的局面不同,中古时期世人对弥勒的崇拜完全盖过了除释迦牟尼佛之外的任何菩萨,这点从当时留下的佛教造像和文献记载上都能反映出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月光童子信仰得以流行与中古社会上极为兴盛的弥勒信仰是分不开的。
1003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by 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 and cardioembolism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1 segment occlusion: a single 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对普通民众来说,弥勒能够终结末法,拯救众生脱离苦海,是他们期待的救世主。而对于帝王来说,利用弥勒下生宣扬弥勒治世能够更好的维护自身的统治。其实前面提到的北齐文宣帝高洋、隋文帝杨坚及其武则天等人除了利用月光童子信仰之外,他们同时也都利用过弥勒信仰,以转轮王的姿态实行统治。但是根据佛教的理论,弥勒的降生又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段,这是利用弥勒信仰的帝王们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伪撰的月光童子佛典的出现正好解决了弥勒长久不下生的问题,出于这点的考虑,因此中古时期的帝王们才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月光童子。
注释:
① 智昇在《开元释教录》卷17《别录中删略繁重录》(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70页)中云:“《申日经》一卷。右一经,与《大乘藏》中《月光童子经》文同名异。父名‘申日’,子号‘月光’,约此不同,立经名别。《长房录》云:‘《申日经》,吴代优婆塞支谦译’者,谬也。”他认为《申日经》与《月光童子经》文同名异,故译者也应当是竺法护。《大正藏》在编写时依据《开元录》的意见在《申日经》下加了译者竺法护之名,不过其编写者可能也注意到了把此经寄于法护之下漏洞颇多,因此经题下又加上了“《开元录》中无法护译,恐是支谦误为法护”的注文。经后又有按语,云:“《开元录》:此经四译一失,法护译中虽有《月光童子经》,亦名《申日经》者,自是一经有二名耳,非别有《申日经》是法护译者。藏中既有《月光童子经》,为法护译,斯已矣!此何更有《申日经》为法护之译耶?则未知此经是谁之译?又何据谓之法护译耶?今以录中有云:‘支谦译中有《申日经》一卷,云与《月光童子经》同本异译。今捡寻文句,二经不殊,故不双出云云。’则藏中必有支谦所译《月光童子经》,亦名《申日经》者。今诸藏皆无,恐此经即是,而误安法护之名耳。如是,则四译还具矣。冒陈瞽言,以俟来哲。”可见《申日经》的译者不管是支谦还是竺法护皆非定论。释章慧在《<申日经>经本定为与经题考》(《中华佛学研究》第8期,民国93年)一文中指出今本《申日经》可能并非之前各经录学家所见的《申日经》,因此今入藏的《申日经》与支谦译出的本子到底有多大联系,其实已无从考察。而且此经在言及申日子劝父的情节时,皆用“旃罗法”之名,但经末的发愿与释迦佛授记中却改称“月光童子”,从这两种不同的用词习惯来看,我们甚至认为《大正藏》中的《申日经》很可能不是一人一时之作。
② 《首罗比丘经》最早被隋代的《法经录》著录,入疑伪部,之后《仁寿录》、《内典录》、《大周录》、《开元录》、《贞元录》等经录都沿袭此说。
③ 《大正藏》第85册根据英藏S.2697号敦煌写经对其作过一个录文,可惜S.2697号卷首残缺,因此部分经文未被录出。之后白化文发表了《<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校录》(《敦煌学》第十六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一文,他以BD5926号(重26,北8274)为底本,参照现存其它卷号录出全本。杨梅的博士论文《4-8世纪中国北方地区佛教谶记类伪经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附录中亦附有《首罗比丘经》录文,她在白氏录文的基础上再做修订,是目前较好的本子,下文涉及的《首罗比丘经》文本多取杨录。
④ 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把《法灭尽经》录为失译佛经,《法经录》则把它当作伪经。撫尾正信在《法滅盡經について》(《龍谷論叢》創刊號,1954年)一文中对此经文本做过系统研究。从其经文内容看,我们也倾向于它是在中国撰述的伪经。
⑤ 《般泥洹后诸比丘经》最早收于《法经录》的伪经部,经文本不传世,幸而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发现S.2109.3号为此经的写本,同卷还抄写有《法灭尽经》一卷。
⑥ 此经录文见刘屹《月光与弥勒:一对中国佛教末世组合的固化与离散》(收入孙英刚主编《佛教史研究》第1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7年)一文。
4.教学重难点:掌握处理旅游者投诉的程序。能够根据旅游者投诉的现场的情况,正确分析旅游者的投诉心理,并以《旅游法》为准则,合理运用相应的技巧进行处理。
⑦ 关于中古世人对佛陀诞辰时间的认识可参考刘屹的《穆王五十二年佛灭说的形成》(《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一文。
⑧ 关于梁武帝“皇帝菩萨”思想的形成可参看藤堂恭俊的《江南と江北の仏教─菩萨戒弟子皇帝と皇帝即如来观》(《仏教思想史》,1981年第4期)、颜尚文《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及政策之形成基础》(《台湾师范大学学报》第17期,1989年)和《梁武帝受菩萨戒及舍身同泰寺与“皇帝菩萨”地位的建立》(《东方宗教研究》第1期,1990年)等论文。
[参考文献]
[1] Erik Zürcher: PrinceMoonlight:MessianismandEschatologyinEarlyMedievalChineseBuddhism [J]. T’oung Pao, 1982,68.
[2] 古正美. 齐文宣与隋文帝的月光童子信仰及形象[M]//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 台北: 商周出版社, 2003.
[3] 康乐. 转轮王观念与中国中古的佛教政治[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1分. 1996.
[4] (后晋)刘昫. 旧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5] (日)高楠顺次郎, 主编. 大正新修大藏经 [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1972.
[6] (梁)僧祐. 弘明集校笺 [M]. 李小荣, 校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7] (梁)僧佑. 出三藏记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8] (北齐)魏收. 魏书:修订版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9] (唐)智昇. 开元释教录 [M]. 北京:中华书局, 2018.
[10] (清)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11] 杨梅. 4-8世纪中国北方地区佛教谶记类伪经研究 [D].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12] (唐)李百药. 北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2.
[13] 员小中. 云冈石窟铭文楹联 [M]. 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 2014.
[14] 王毅. 北凉石塔 [M]//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 文物出版社, 1977.
[15]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编.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册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16] (清)陆耀遹, 纂. 金石续编[M]//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4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MoonlightBoy:AMedievalSaviorundertheConstructionofForgedBuddhistScriptures
XU Hanjie
(InstituteofDunHuangStudie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00)
Abstract: Imitating the future image of Buddha Maitreya in the translated scriptures, the popular idea of moonlight boy born as a saint in medieval China was shaped by the forged Buddhist scriptures written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se forged Buddhist narratives, moonlight boy will be rotating emperorson the earth after the death of Sakyamuni Buddha.Therefore, the rulers of the Middle Ages often regarded themselves as moonlight boys to illu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regime.In addition, the belief of moonlight boy was produced and accepted by the people,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ailing thought of “Dharma ending” and “no Buddha”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Keywords: moonlight boy; forged scriptures; emperor’s power; Dharma ending
[中图分类号]:[G 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9)02--0095--09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9.02.014
[收稿日期]2018-09-20
[作者简介]徐汉杰,男,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国佛教史。
【责任编辑张晋海】
标签:童子论文; 月光论文; 弥勒论文; 佛典论文; 释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