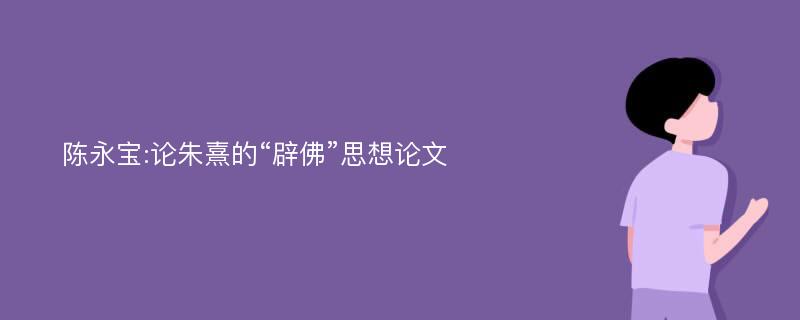
摘要:唐末宋初的辟佛运动,导致两宋时期的佛教内部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呈现出以智圆、契嵩、宗杲等大德高僧采用不同的方式浸染儒典的现象。一般认为,这种背景对朱熹早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于这种判定,自然离不开北宋时期“儒与佛合”的杂糅现象。需要指明的是,这种现象最终导致了朱熹既要区分佛老与儒家的杂糅现实,又需要完成“融道佛儒”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不应只将朱熹的“辟佛”简单理解为二程的“反佛”,以免对其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因此,对朱熹辟佛思想的过程与结论需要进行重新的梳理。
关键词:朱熹;辟佛;禅宗;使命
唐末宋初儒家提出“辟佛”思想时,佛教徒就儒者提出的挑战,给予了相应的回击,这种回击不单表现为以“佛学”对抗儒者,还表现为以“儒家经典”对抗“诸儒的抨击”。佛教徒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是否存在“误解”,这里暂且不论,但至少说明在两宋时期,儒家经典已经对“佛教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融合儒道思想较深的禅宗,相较于其它宗派,其影响的程度更强。在这种背景下,两宋禅宗中的智圆、契嵩、宗杲及其弟子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过来对两宋儒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刺激。总之,两宋时期儒佛二学呈现出既相互交融又“各正性命”的焦灼状态,这是朱子理学发展史中不能被忽略的历史因素。
2.选人视野的广阔性。实行竞争性选拔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选贤任能”,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选拔上来。竞争性选拔干部给所有层面的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平台。从报名参加竞聘的干部来源上看,所属单位和岗位都各不相同,丰富了源头活水,保证了干部来源的广泛性;从干部所属的层面上看,竞争性选拔特别是公开选拔使各个层面的干部都能参与进来,特别是赋予了广大基层干部以宝贵的机会,从而能够有效地优化干部队伍结构。
本文从理学的发展脉络中来探讨朱熹的辟佛问题。朱熹的辟佛思想既不是“完全反对、不加任何肯定”的反佛,也不是“皇子夺嫡式”的正统之争的灭佛。只有回到两宋的真实背景,才能清晰理解朱熹的辟佛本意。否则,对朱熹的辟佛问题的理解,极易滑入“反佛”“灭佛”这一非此即彼的思路之中。用这两种思路来诠释朱熹理学,既存在割裂两宋理学发展脉络的风险,又存在以己之思掩盖朱熹理学真实历史使命的问题。朱熹是两宋思想发展史中完成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家,若将他的辟佛诠释成“反佛”或“灭佛”,则明显误解朱子思想本义。实际上,朱熹的辟佛思想多表现为“辟禅”。他在文本里对“佛”的诠释,多同于“禅”的含义。只有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朱熹辟佛的主要目标指向。这一点与二程和张横渠的辟佛思想明显不同。因此,朱熹辟佛思想真正内涵是朱子理学研究中需要澄清的问题。基于此,笔者尝试通过梳理朱熹辟佛思想的背景,挖掘其历史原因,揭示其历史作用,从而厘清其发展脉络。希望通过本文的爬梳,能展示出朱熹辟佛的真正意图,以有助于学者理解朱熹理学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朱熹“辟佛”的背景
两宋时期,佛教内部出现了以儒家经典为理论支撑来诠释禅宗“明心见性”的现象,这在佛教徒对《孟子》与《中庸》的注疏中最为常见。当代学者对这种现象的解读带来的疑问是:到底是北宋时期《孟子》的思想影响了禅宗然后产生了“明心见性”的思想,还是禅宗影响了北宋学者然后产生了对《孟子》“尽心知性”思想的重视?这个问题导致当代学者在研究两宋理学(儒家)问题时产生了一定的思维困扰而无法正确理解儒佛关系。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北宋时期理学思想发展中佛儒二门的内在关系。
禅宗在两宋时期的衰落,导致佛教内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于是,两宋时期的佛教呈现出“释者儒家化”的样态。洪淑芬指出:
智圆、契嵩、宗杲虽因不同的因素而浸染儒典,也因不同的目的而提出调和思想,但他们站在不同的时空参与宋代儒学之进展,却也是不争之事实。浸润在宋初儒学复兴之发端期,智圆的调和论充满了忧患意识,也以儒家的治世之道怀着高度的期待与尊重。处于北宋中期排佛鼎盛的契嵩,其会通思想除了力捍佛法命脉之外,也具体响应了当代诸儒的抨击,举凡入善成治的外王事功,或内圣本体的会通,都有精彩的发挥。到了南宋,理学兴起,心情本体思想大作,宗杲的圆通思想,除了有禅法特殊的禅观旨趣外,也呼应理学家形而上学的思想模式。[1]581
这里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的儒佛二门复杂的内在关系。可以说,两宋时期展现出来的儒佛杂糅,是当时的一种社会常态。朱熹在抨击程门诸弟子及陆氏门人的时候,也常以“杂佛老”[2]2556、“近禅”等语词来形容他们的思想,例如,他曾说,“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2]2556。可见即使是以“儒学”为宗旨的“辟佛”的程门后学,也难逃佛教思想的干扰。
目前在国际上,人体睡眠状况与相关疾病的研究已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用,涉及的学科包括神经科学、耳鼻喉、口腔、心血管、肾脏、血液、内分泌等诸多专业,并和医学影像学科、医学工程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相结合,已发展成与高科技融为一体的新型边缘交叉学科-睡眠医学。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充足的睡眠是国际公认的健康标准之一。国际儿科学界对睡眠质量与儿童身心健康的关系更为关注,睡眠医学必将成为21世纪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
南宋初年,除了儒门内部与佛教纠缠不清外,儒、释、道在士大夫与皇族的共同影响下,呈现出三教共存的更为复杂的样态。宋光宗曾说:“以佛修心, 以道养生, 以儒治世, 斯可也。其惟圣人为能同之, 不可不论也。”[3]60493宋光宗这里明显有主张三教共存的倾向。皇权的干预导致儒释道杂糅混合的现象,成为我们理解朱子辟佛问题的一个历史参照。墨子说:“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4]156-157可见,“三皇”的统治理念势必让南宋的儒释道三教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于理学的发展之中。于是形成不同于汉唐时期对儒家或佛教的偏重,也不同于五代十国时代崇佛、灭佛的极端,宋朝对待儒佛交融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朱熹自己也认为,“(佛学)旧尝参究后,颇疑其不是。及见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后年岁间渐见其非”[2]3040。关于朱熹辟佛的语录,黎靖德主编的《朱子语类》(一百二十六卷)中存有大量的记载。这里需要点明的是,“辟佛”与“反佛”“灭佛”不一样。“辟佛”是既批判又保留,也可以说成是“批判性的继承”或“扬弃”,是一个选言判断①参见:叶公超《重编国语辞典:第一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331页)。辟,动词性的意思有:除去、开拓、搥胸、退避。因此,辟佛也可以诠释为包含“去除弊端、开拓新义”等义。纵观朱熹传世文本,可推测其“辟佛”绝不等于“反佛”或“灭佛”。;“反佛”是认为佛教思想全部无用,是一个全称判断;“灭佛”是认为佛教思想不光无用,而且有害,必须加以除之。三个概念中,“辟佛”更接近朱熹所提倡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因此,在看待朱熹的辟佛问题时,必须要把这三个概念做一个清晰的区分,方能了解朱熹本意。
儒佛的交涉,不管是智圆尊儒复古的情怀,或契嵩抗衡儒学的护法行动,还是宗杲儒佛交游下的思想合流,都为宋学带来不同阶段的发展成果。儒佛彼此的“挑战”与“响应”,促进了宋学的发展,也为佛儒交涉史写下精采的扉页。[1]1
因此,对两宋儒佛的关系,不能简单停留在“对抗”这一简单维度上,以“崇”或“辟”,甚至以“反”或“灭”的态度来看待佛教问题。同时,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也不能只把它们单纯理解为“尊佛”或“排佛”。
两宋的佛教出现了不同于传统佛教主张以“空性”为法门进而达到“出世”境界的新思潮。一般看来,“出世”成为佛教信徒为摆脱“入世”烦恼而找到的解决良药。然而两宋时期的佛教思想中,“入世”的思想一度成为两宋高僧追求的“成佛之道”。积极的“入世”观在智圆、契嵩和宗杲的影响下,成为两宋佛学发展中的一朵奇花。佛教发展中出现的“尊儒复古”运动,也从侧面刺激了两宋儒学的发展,对朱熹儒学体系的形成及完善更是贡献巨大。洪淑芬指出:“宋学的开展与儒学的复兴,其因多端,除了有学术自身的发展变化之轨则外,宋儒的自觉及朝廷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此外,佛教的刺激以及佛教僧侣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之事实。”[1]583-584在这种情况下,她进一步得出结论:“佛教对宋代学术的影响力,除了开理学之先声外,上起宋初的儒学复兴下至南宋理学家的成熟,都与佛教密不可分。佛教对宋学的影响可说如影随形,无所不在。”[1]584洪淑芬的结论并非她一人独有。钱穆也曾指出:“契嵩治学著书之主要宗旨,则在援儒卫释。其思想理论,多可与后起理学家言相呼应。”[5]39
当然,两宋佛教发展的新取向有其历史发展的源由,而并非只是佛教内部的研究转向。洪淑芬说:
就宋初“尊儒复古”之学风而言,这个时期的儒学复兴以对抗五代以来“文衰道弊”之风为主。因此,提倡宗经载道之文是当时尊儒复古之学者的任务,而藉由儒家的“仁义五常”来重建社会秩序也是他们(智圆、契嵩和宗杲)的共识。所以,这个时期的“道论”,主要以“五常”为论述核心,“文论”则以“文道合一”为理想,两者的目的都在于经世致用及拯衰救弊。[1]585
(4)期末考试:调整考题分布,增加实践操作的分值,侧重于考察同学们对Access数据库操作的综合掌握能力,同时兼顾基本的理论知识。
佛教的干预并非是佛教徒的“鸠占鹊巢”,而是北宋早期儒者本身无法担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当时“儒学之风气未开,投身于此儒学运动的朝臣大儒并不多,故无法形成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1]584-585。于是,佛门之中展开的同步的尊儒复古运动[1]586的重要性便被凸显出来。
佛教的“入世”,除了儒学衰微,另外两个原因也值得注意:一是韩愈的灭佛运动的刺激。韩愈在《论佛骨表》和《原道》中提出的“佛不足事”[6]614及“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6]19等言论,对智圆等人主张的佛教“入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二是佛教本身的衰微。钱穆指出:
南北朝隋唐,是佛学的全盛时期。武则天以后,禅宗崛兴。直到唐末五代,佛学几乎全归入禅宗。五代时代永明禅师,……是唐末五代惟一的大师。……然而佛学盛运,到他时代也近衰落了。……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到了包罗和会的时期,似乎便在宣告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之衰竭。[5]1
佛家的势微决定了它本身需要从儒学经典中寻找复兴之道,这就是前面谈到的“援儒卫释”。
因此,两宋佛教与之前的佛教相比,具有明显的“入世”特征。这种“入世”并非如隋唐五代时期以单纯的佛理来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入世,而是通过引进儒家的经典等来达到“援儒”入世。因此,我们对这一阶段辟佛理论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到存世文本中的“辟佛”部分,紧抓“佛儒的异”,而忽略“佛儒的融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合”不等于“同”,在根本思想的理解上,二者的分歧是一定存在的,这也是朱熹辟佛的原因之一。于是,朱熹对佛教问题的思考,学者常习惯于用“辟佛”来简单概括,这明显不够全面。
两宋思想家中关于儒佛问题的处理绝非如现在理解的那样清晰,界限的模糊是两宋时期的历史常态。忽略这个因素,在讨论两宋儒佛问题时,便容易导致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对两宋思想的研究中,朱熹的思想较为突出,极易被后世学者所关注。于是,对朱熹理学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比较,及朱熹的“辟佛”观念的由来,将成为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二、朱熹“辟佛”的由来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感觉,我只是天黑就睡,天亮便起。我房子的门有些锈了,我怕它割破我的手让我患上破伤风,所以我每次都是跳窗出去。我的父亲就埋葬在窗下,我每次出门都要踩我父亲一下,真是很对不起他。但我是故意将他埋在这里的,一来他永远睡得比我更接近大海,二来我踩着他的坟更容易爬窗。胡来胡去的爸妈曾经来找过我爷爷说这事,说胡生这么做有点不孝。爷爷说:胡说,孩子他不踩在父辈的身上,难道要像有些人那样,把脚踩在后辈的身上吗?
三君子本人受佛教的影响很深。为了说明这一点,陈来指出:
朱熹与佛教的渊源显然与其恩师刘子翚有关,“刘子翚与佛老之徒过往颇多,这既引起了朱熹的好奇,也给他带来了接触二氏的机会”[7]35。陈来指出:“刘子翚早年曾留意佛老,后读儒书,……刘子翚对青少年朱熹影响较大,在朱熹看来,刘子翚的‘为学次第’就是‘为己之学’的门户。”[8]31由于受到刘子翚的影响,青年朱熹对佛教颇有兴趣。陈来曾用“泛滥释老”[8]33来形容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他说:“留意佛老之学,是这个时期(绍兴十七年,朱熹18岁)朱熹思想的特征之一。”[8]34陈来进而判定:“朱子对二氏的留心在得举之前从三君子学时即已开始。”[8]34
刘元城曾语白水以方外之学,“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影响更大的是刘子翚对二氏的态度。……刘子翚曾习禅定,又见长庐清了,“儒与佛合”是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8]34
陈来这里基本道出了朱熹早年与佛教的关系是源自三君子,而非其父朱松。从这一段引文来判定,我们很难得知朱松本人是否受佛教影响,但其向朱熹传授儒学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在朱松逝前,朱熹的主要思想还是以儒学为主。朱松逝后,朱熹从学三君子时才产生倾佛的意向。这一点,从朱熹自己的回忆中也可见端详:
也就是说,朱熹的辟佛观念,不是他接触李延平之后的事情,而是他自小学习儒学以来一贯的主张。只不过在刘屏山的影响下,他“不反对以佛老为入道门户或入道之助”[8]40。
从这个材料中我们至少可以得知,朱熹的生平早期确实存在着佛学倾向。但陈来认为,“朱学一派竭力否认朱熹曾师尊释氏”[8]34,他给出的例证是夏炘和汪应辰的论辩。陈来指出:
汪应辰尝师宗杲,好禅学,夏氏谓朱子委婉其辞,亦有其理。但夏氏以为朱子于释氏并无“师其人”之实迹,则又属一偏。盖朱子必不会无中生有,且李侗与罗博文书明言“渠《朱子》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年谱》),故“师其人,尊其道”确有其事。[8]34
陈来的判断在朱熹与汪应辰书信中得到了应证。朱熹说:“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所得。”[7]1295这也就是说,朱熹的“师尊释氏”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可以说,在遇到李延平之前,他的佛学基奠就已经开始。陈来指出:“朱子留心禅学,始于在病翁刘屏山家遇道谦,时十五六岁。至见延平后一二年间悟禅学之非,已二十五六岁,但19岁以前,因举业所迫,当止于一般留心而已。而用力参究,应在得举之后至24岁拜见延平之间。”[8]37即使我们抛出朱熹与道谦之间的关系不谈,单从朱熹以佛理取士的事例来看,佛学对朱熹早期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末保皇派、革命派都在华侨聚居地创办报刊传播政治思想。革命党人黄馥生回忆在缅甸向华侨筹款,“回溯缅甸华侨从1906年在仰光组织中国同盟会以来,至1923年为止,整整十七年时间捐款不断”。[18]华侨踊跃捐款,得益于革命派在南洋地区的宣传。“革命党人为了揭露保皇会的阴谋,唤醒华侨,在仰光创办《觉民日报》”。[19]1908年,《时事画报》发起童谣征文,征文时间仅短短两月,投稿者中除广东本地读者外,也有来自南洋的读者。[20]仅凭署名虽无法判断“南洋”读者的真实身份,但至少可以见出南洋华侨对岭南报刊的认可与参与。
实际上,朱熹近佛思想与刘子翚(刘屏山)“儒佛合”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说:“刘屏山认为儒之道可以包容佛老,两者并非截然对立。换言之,志为己之学与求入道门径,并非尽辟二氏而后可。在这一点上朱熹无疑受到了屏山的影响。”[8]35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对佛学的理解并不是“信仰式”理解。从与道谦禅师的交往来看,朱熹对佛教并无明显的好感,而只是年少时求学兴趣而已。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2]2620所以,朱熹的佛学积淀,应不同于玄奘、六祖慧能式的“真心求法”,而是一种“格物致知”式的现实求道。只有厘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清楚朱熹在遇到李延平后,思想上有如此“重大的转变”。
实际上,朱熹对佛学的亲近并不代表对儒学的背弃。即使他早期亲近佛学的倾向,但是他的儒家思想依然起着作用。陈来指出:“如果以为朱熹当时已背弃孔孟,完全沉溺佛老之中,也是片面的,至少无法解释这一事实:何以朱熹拜见李侗后,虽言语未契,却能依李之说将禅学搁置一边,转而专意圣贤之书。”[8]37我们也能从朱熹的语录中发现一些端倪。朱熹说过:“某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戳直戳,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2]2616又说:“某今且劝诸公屏去外务,趱功夫专一去看这道理。某年二十余已做这功夫,将谓下梢理会得多少道理。”[2]2621所以,陈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一时期,朱熹也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儒者之学。”[8]40为了论证这个判断的准确性,陈来接着指出:
通过环境数据检测,可以为监测方提供数据,评价对应的环境质量现状,进而为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因此,检测公司(或监测站)高效的、提供准确的环境监测数据处理至关重要[2].环境监测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质量管理和人才素质等均会影响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朱熹曾说“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释老者十余年”。朱熹十四五岁即“有志于古人为己之学”,便“觉得这物事是好物事。心便爱了”,“十六岁便好理学”,“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由此可见,朱熹是把出入释老作为求道的一个途径。[8]40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2]2620
目前职业院校学生普遍存在的学习积极主动性不高、缺乏学习热情。《导基》虽然是一门基础性学科,以浅层基础理论知识为主,但应对筛选性资格考试,学习与记忆起来还是有点枯燥,并容易混淆。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形成立体化互动教学模式,教学手段不再单一,可以激起学生们兴趣,增加学生学习热情,让学生积极参与互动教学学习中。
需要指出的是,“泛滥释老的结果是对朱熹这一时期的人生态度造成了某种消极的影响”[8]40, 导致他“从心性修养下手,寻求一个‘安心’的自在境界”[8]40。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参究二氏的结果并没有使他感到真有所得”[8]41。这种失落的情绪在《题谢少卿药园诗》得到展现:
小儒忝师训,迷谬失其方;
朱熹转引明道“性用”说,意在指出佛教在道德本体上有悖伦理纲常。程明道曾说: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能寻到这样的线索,即他的辟佛的对象,主要是直指禅宗。在这里,朱熹在道德本体上对禅宗下了否定的判定。他甚至指出:“儒之不辟异端者,谓如有贼在何处,任之,不必治。”[2]3040显然,辟佛的最终目的,在于他维护周礼的决心。“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杨墨,正道不明,而异端肆行,周孔之教将遂绝矣。譬如火之焚将及身,任道君子岂可不拯救也。”[2]3039-3040在朱熹的思想里,儒释二门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别。于是,我们需要将朱熹的辟佛与二程、张横渠的辟佛思想相区隔,避免混为一谈。
古庙之战打响后,团救护队的五个女兵,在汪队长的带领下,一直跟随着一连。李晓英,马国平不仅认识,在工作中还有过接触。她既是护士,也是颇有几分才气的宣传员,是“连部五花”中的“花王”。
洪淑芬指出:“宋代是儒者排佛极剧之时期,也是士人参禅学佛极深之时代。在儒佛频繁的交涉中,不但促进了彼此思想的融合,佛教徒也实质担任着推动宋学之发展的重要角色。”[1]1在儒佛的交汇中,“辟佛”与“反佛”“灭佛”的界限由清晰逐渐走向模糊。除了上文所谈到的士大夫阶层与佛教团体的纠缠不清,佛教内部也出现了佛教儒家化,或对佛典进行儒学式诠释的倾向。北宋的智圆、契嵩,两宋交际的宗杲、道谦,都表现出融合儒佛的努力:
三、朱熹“辟佛”的内容
朱熹的辟佛思想是为了维护儒家“道统”而不可不辩的结果。关于辟佛,朱熹指出以下几个原因:
(一)禅宗为“盗用之学”,非印度真佛
第一,朱熹认为禅宗为杨墨之传,而非最初传入中土之佛教。他指出:“孟子不辟老庄而辟杨墨,杨墨即老庄也。今释子亦有两般:禅学,杨朱也;若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则自是假,今无可说辟。然今禅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试看古经如《四十二章》等经可见。”[2]3007关于杨朱,孟子曾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11]500在这里朱熹将“禅学”直接判定为“杨朱之学”。深谙孟子思想的朱熹,用杨朱来形容禅宗,可见其对禅宗的蔑视之情。
第二,朱熹认为禅宗有偷老子、列子之学,以扩充己意之嫌。“(佛经)大抵多是剽窃老子列子意思,变换推衍以文其说。”[2]3010在朱熹看来,中华之地流传之禅宗,非天竺之佛教,也非汉魏之佛教,而是老子思想与列子思想的变种。朱熹说:“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说耳目口鼻心体处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为十八戒。初间只有《四十二章经》,无恁地多。到东晋便有谈议,如今之讲师作一篇总说之。”[2]3008又如:“列子言语多与佛经相类,觉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2]3008朱熹反复强调:“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添月益,皆是中华文土相助撰集。”[2]3010“佛书分明是中国人附益。”[2]3038也就是说,朱熹认为,两宋时期在中华之地流通的禅宗,非真佛教,而为佛教中的“伪学”。
本文从不同角度对广西与东盟国家跨境贸易发展及跨境人民币结算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同时,选取当年累计出口额、当年累计进口额及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等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运用协整检验、构建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等分析方法,对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ln(crmb)与广西—东盟进出口贸易ln(ix)、ln(ex)三个指标变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第三,朱熹指出:“道释之教皆一再传而浸失其本真。”[2]3009在这里,朱熹对佛教本义未加评论,将批判目标直指禅宗,突出禅宗之非。他指出:“初来只有《四十二章经》,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其后达摩来又说禅,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论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说假。’”[2]3038这里的唐人,多指韩愈、李翱等人。晚唐的辟佛说,在这里被朱熹继承。事实上,禅宗传至北宋,其基本教义和修行法门确实不同于天竺佛教。
(二)禅宗的空性说,有悖纲常
第一,朱熹指出“顽空”“真空”之说,如死灰槁木,断人伦根脉。朱熹认为:“有所谓‘顽空’、‘真空’之说。顽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则能摄众有而应变,然亦中是空耳。今不消穷究他,伊川所谓‘只消就迹上断便了。他即逃其父母,虽说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断之矣。”[2]3008又说:“及达摩入来,又翻了许多窠臼,说出禅来,又高妙于义学,以为可以直超径悟。而其始者祸福报应之说,又足以钳制愚俗,以为资足衣食之计。遂使有国家者割田以瞻,择地以居之,以相从陷于无父无君之域而不自觉。”[2]3009
第二,朱熹认为,禅宗多重寂灭,而忽略人世。“论释氏之说,如明道数语,辟得极善。见行状中者。它只要理会个寂灭,不知须强要寂灭它做甚?既寂灭后,却作何用?何况号为尊宿禅和者,亦何曾寂灭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点检,喜怒更不中节。”[2]3008这也就是说,虽然智圆、契嵩、宗杲等人主张“援儒卫佛”的入世之道,但禅宗的终极目的仍为“寂灭”的离世之法。尘世、人世在禅宗看来,仍为“虚空”,而非“实有”,这与儒家本义相矛盾。
(三)禅宗的教旨,废周礼,灭法度
第一,朱熹指出,禅宗的祭祀方式和工夫论,有违周礼。其以“劝善”方式进行的宣传,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使百姓放弃周礼。在朱熹看来,追随孔孟,回到五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与现实追求,而周礼便是维系这一追求的现实方法。禅宗劝说百姓废除“牲祭”,自然让坚持回归五代理想的朱熹所不容。“夷狄之教入于中国,非特人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干庙所以塑僧像,乃劝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庙宇中,亦必有所谓劝善大师。盖缘人之信向者既众,鬼神只是依人而行。”[2]3038“牲祭”是自周代以来儒家供养祖先的一个典型标志,这是维护周礼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朱熹看来,禅宗劝其“不用牲祭”,表面为劝其以不杀生为德,实则为尽破坏周礼之行。《论语·阳货》中,宰我想要修改周礼的“三年之丧”,曾被孔子视为“予之不仁也!”[11]253禅宗欲想除去“牲祭”的作法,这种明显违反周朝的礼法,自然被朱熹所反对。他曾说:“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势如何拗得他转?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难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2]3041这里,朱熹认为自己的辟佛方向与欧阳修是一致的,他认为“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2]3038。
第二,禅宗对礼仪法度的挑战。朱熹曾举一例:
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为不善,一旦因读佛书,稍稍收敛,人便指为学佛之效,不知此特粗胜于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学佛者,全不曾见得力,近世李德远辈皆是也。今其徒见吾儒所以攻排之说,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为然者。如果是不以为然,当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伪作韩欧别传之类,正如盗贼怨捉事人,故意摊赃耳。[2]3039
配合饲料和血液饲养对菲牛蛭碱性磷酸酶(AKP)的影响见图2。配合饲料组肠道AKP活力显著高于血液组(P<0.05),AKP活力分别为(148.317±8.144)U/mg prot.和(18.664±1.627)U/mg prot.;配合饲料组嗉囔AKP活性稍高于血液组,差异性不显著(P>0.05),AKP活力分别为(14.333±1.154)U/mg prot.和(6.333±0.577)U/mg prot.。
释氏自谓识心见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为其于性与用分为两截也。圣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无不本于此。故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由其性与用不相管也。[2]3039
休药期是指从停止用药到允许动物和产品上市前的这段时间,通过制定严格的休药期制度,能保证动物体内的药物在规定时间内完全降解消除。动物养殖中,不同的动物种类、年龄、用药剂量、用药方法,所制定的休药期存在一定差异。而很多养殖户在动物上市前,不注重休药期制度,依然在饲料中添加兽药和兽药添加剂,导致许多新产品上市后体内的药物不能完全降解,残留超标。
一为往瘖病,望道空茫茫。[9]226
四、朱熹“辟佛”的使命
传统儒家思想的回归,是两宋时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需求。钱穆谈到,“在此形势下,时代需要有新的宋学之出现”[12]1,可以说,
宋代的学术发展,一言以蔽之即儒学复兴。然而,宋代的儒学复兴在不同的阶段又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因而也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成就。例如宋初的尊儒复古运动、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王安石的新学以及理学萌芽、南宋中期理学的成熟等,都是儒学复兴下的具体成果。[1]583
儒家的“入世”理念相较于佛教的“入世”探索,具有先天的优势。单从这一点来看,它比佛教更易为统治阶层接受。因此,在北宋统治阶级内部,虽士大夫阶层信佛者众,但主张治世理念的多为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对佛教理论的反省,成为北宋儒者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张横渠首先以天命观对佛教提出质疑。他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欤!”[13]19他接着用人性论来指出:“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虚空之大。此所以语大语小,流遁失中。其过也,尘芥六和;其蔽于小也,梦幻人世。”[13]19
修建麻石水电站扩建工程可充分利用水能资源,并有利于与上游洋溪、草头坪水电站联合协调运行,可增加电站的有效电量及有效容量,同时扩建工程还有利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因此,麻石水电站扩建工程的建设十分必要。
程明道提出了“释氏无实”[14]138的思想,他指出:“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危害尤甚。”[13]138他的理由是:“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14]139程伊川也认为:“佛逃父出家,便绝人伦,只为自家独处于山林,人乡里岂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贱所轻施于人,此不惟非圣人之心,亦不可为君子之心。”[14]139他的理由是:“释氏自己不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而谓他人不能如是,容人为之而己不为,别做一等人,若以此举率人,是绝类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为死生,其情本怖死爱生,是利也。”[14]139
二程与张横渠的激烈批评,侧面证实了北宋时期儒佛冲突现象十分普遍。虽然二程与张横渠表现出强烈的反佛意愿,但未能避免程门后学受佛教的浸染。朱熹讲学时多谈到:“程门诸公亲见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说,多入于释氏。”[2]2556他甚至说“游杨谢三君子初皆学禅。后来余习犹在,故学之者多流于禅。游先生大是禅学”[2]2556。因此,再次划清儒佛的界限,厘清儒家道统,成为朱熹的历史使命。不同于张横渠、二程“卫儒反佛”,朱熹的方式较为温和,我们可以将他的历史使命诠释为“融儒佛道”。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单把朱熹的“辟佛”理解为二程氏的“反佛”,那么对朱熹的理解就未免过于狭隘了。
朱熹的辟佛是有侧重的。他指出:
佛教初入中国,只是修行说话,如《四十二章经》是也。初间只有这一卷经。……后来达摩入中国,见这般说话,中国人都会说了,遂换了话头,专去面壁静坐默照,那时亦只是如此。到得后来,又翻得许多禅底说话来,尽掉了旧时许多话柄。不必看经,不必静坐,越弄得来阔,其实只是作弄这些精神。[2]3035
从这一段的文字来看,朱熹主要是反对佛教里的禅宗,其辟佛也多为辟禅。如其言:“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以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2]3014
佛教的禅宗化在北宋时期已经十分明显,钱穆认为:“到唐末五代,佛学几乎全归入禅宗。”[5]1禅宗对两宋士大夫有极强的影响,朱熹辟佛的核心即为禅宗。同时,佛教的禅宗化及“入世”的现实追求,混杂着佛寺与民争利现实问题,这都导致朱熹必须捍卫儒家正统思想,走上辟“禅”之路。朱熹指出,
释氏自谓识心见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为其于性与用分为两截也。圣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无不本于此。故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由其性与用不相管也。[2]3039
统计180枚鸡蛋的图像特征参数值发现,无论是G分量图像还是B分量图像,当蛋黄的面积与周长比大于65时,双黄鸡蛋被检出的概率为95.7%,因此这种情况判定为双黄鸡蛋。
实际上,朱熹一直所坚守的,是以儒学为底线,以佛道为参考。护儒家之正统,行不偏倚之中庸。张立文就指出:
儒、释、道三教长期的冲突、融合,各教内部逻辑地出现了三教融合的趋势。……儒、释、道三教融合趋势成为三教的共识。作为新儒学者,他们既认同三教融合的趋势而出入佛老,各取佛老之长而补己之不足,而又批判佛老,划清界限,延续儒学特质。[15]58
张立文的总结应该是最能反映朱熹的历史使命。陈来也指出:“朱熹是把出入释老作为求道的一个途径。在他看来佛老的心性修养也是‘为己之学’……他主要是从心性修养下手,寻求一个‘安心’的自在境界,他从这个角度理解‘为己之学’,并肯定儒与佛老合。”[8]40-41维护二程儒学正统思想为朱熹的主要任务,这也是朱熹坚持“辟佛”的主要目的。
五、结语
程朱理学发展到朱熹的阶段,“儒、释、道三教融合,是三教自身内在的需要”[15]64,朱熹自然是“三教学术的内在逻辑发展趋势”[15]64中的集中点。张立文指出,在这一时期,“儒教必须吸收佛道逻辑思维、终极关切和宇宙生成理论,以补形而上之道的不足”[15]。这也就是说,朱熹的辟佛思想,既为维护儒家正统思想,又要坚持兼容并包和“理一分殊”的思想原则。朱熹的太极、理、性等本体论思想与佛教的本体论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似并不能掩盖朱熹反对禅宗“性空”的本体论及“默坐澄心”的方法论。这也是朱熹一贯主张的“道问学”工夫论的方向。
除此之外,南宋都城临安及其周边信佛者众,庙产与民争利的情况多为常见,这为主张民生思想的朱熹所不容。同时,孝宗、光宗对佛教的怀柔政策也为朱熹所不满,遂导致他辟佛之念愈发激烈。但从其一生游历山水而书写的诗歌方面来看,他与佛教多有渊源。因此,对朱熹的辟佛问题,必须全面对待,方能避免曲解原意。
参考文献:
[1] 洪淑芬.儒佛交涉与宋代儒学复兴——以智圆、契嵩、宗杲为例[M].台北:大安出版社,2008.
[2]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 赵眘.原道论:第499册[M]//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第57 卷:二氏部.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88.
[4] 吴毓江.墨子校注: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M].北京:九州岛出版社,2011.
[6]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9] 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叶公超.重编国语辞典:第一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
[1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
[13] 张载.张子全书.林乐昌编校[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
[14]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 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明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OnZhuXi'sThoughtof"CriticizingBuddhism"
CHEN Yongbao1,2
(1.Marxist College,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China;2.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Xinbei Taiwan 24205, China)
Abstract:The "Criticizing Buddhism" Movement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ong dynasty, led to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side Buddhism during the two Song dynasties. These changes presented themselves in the form of a phenomenon where Zhiyuan, Qisong, Zonggao and other eminent monks got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lassics in different ways. Generally speaking, this background exerted some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Zhu Xi's early thoughts. Such judgment naturally ca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mixture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at needs to be pointed out is: this phenomenon eventually led to Zhu Xi's historical missio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Buddha and Confucianism, and to complete the integration of "Taoism,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people are supposed not to simply take Zhu's "Criticizing Buddhism" as two Cheng's "Anti-Buddhism", so as not to make too narrow an understanding of Zhu Xi's thought of Buddhism. Therefore, the process and conclusion of Zhu Xi's thought of "Criticizing Buddhism" need to be re-combed.
Keywords:Zhu Xi; thought of "Criticizing Buddhism"; Zen Buddhism; mission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9)01-0001-08
DOI:10.3969/j.issn.1004-2237.2019.01.001
收稿日期:2018-06-07
课题项目:中共三明市委宣传部基金项目(H160037);三明学院课题项目(17YG08S)
作者简介:陈永宝(1984-),男,吉林舒兰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朱子理学、伦理学。E-mail:cyblcz@163.com
[责任编辑邱忠善]
标签:朱熹论文; 佛教论文; 思想论文; 禅宗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宋论文; 元哲学(960~1368年)论文;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共三明市委宣传部基金项目(H160037) 三明学院课题项目(17YG08S)论文; 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辅仁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