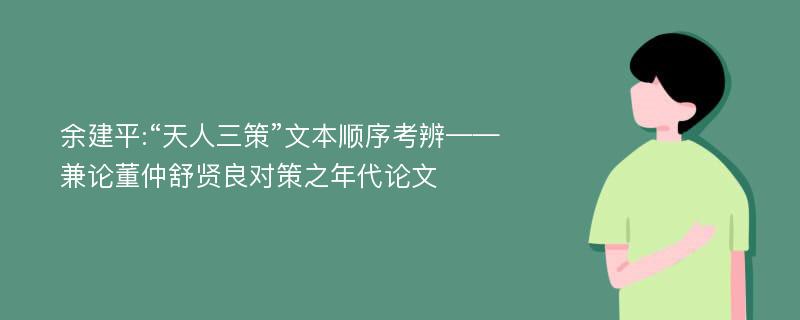
[摘 要] 历代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年代问题有很多争论,但研究者对“天人三策”之间的文本关系却疏于考察。“天人三策”并不是三篇具有内在连续性且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文本。第一、三对策应创作于建元四年、五年之间,而第二对策则要晚至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初。班固在三篇对策间加入“天子复册之”之文,造成三策具有时间递进关系的假象。
[关键词]董仲舒 天人三策 文本顺序 对策年代
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年代,《史记》和《汉书·武帝纪》未记其事,《汉书·董仲舒传》虽记其事,但未载具体的年代。《史记》《汉书》关于董仲舒事迹的记载又相互矛盾,这更增加了判断董仲舒参与贤良对策年代的难度。历代考证董仲舒贤良对策年代的研究成果甚多,其中有影响者,有“建元元年说”“元光元年五月说”和“建元年间说”数种。
如果只到问题4结束,将来可能会有不少学生认为,倒序相加法就是等差数列求和公式推导的专用方法,需要通过问题4-1帮助学生厘清这里的逻辑关系,需要让他们回顾思考用倒序相加法求和的其他问题.事实上,前面复习函数时有例子:已知函数则f(-2015)+…+f(-2)+f(-1)+f(0)+f(1)+f(2)+…+f(2016)=______.能用倒序相加的原因是另外,高二排列组合一章中也有例子:这也能用倒序相加法求和,因为组合数前面的系数是等差数列,且组合数有性质倒序后对应相等.
一、董仲舒对策年代诸家之说
“建元元年说”由司马光提出。《通鉴考异》曰:“《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令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於《纪》。”[1](P13-14)司马光并未直接说董仲舒对策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而是依据《董仲舒传》“抑黜百家”“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的记载,再比对《武帝纪》,只有建元元年举贤良这一记载符合。这一说法颇显无奈。司马光“建元元年之说”的影响很大,苏舆、[2](P479)张大可[3](P39-45)等人皆主此说。
“建元元年说”面临两个难点。其一,董仲舒第二策“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而汉兴(前206 年)至建元元年是67年,这是难以解释的。苏舆认为这是“浅人妄加数字”,[2](P492)张大可认为这是“六”与“七”在流传中的讹误,[3](P40)但仅仅以讹误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二,第二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悦德归谊”,据《史记》《汉书》,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康居之通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后。但近来有学者指出,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4](P3044)在司马相如作《喻巴蜀檄》前已有唐蒙使夜郎归谊之事,而此檄文恰有“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之语。[4](P3044)司马相如去蜀作檄文在元光元年(前134年)后,那么康居归谊之事应在元光元年前。[5](P85)这条史料对“元光元年五月说”有很重要的价值,但与“建元元年说”冲突。主“建元元年说”的学者认为,“夜郎康居”4个字也许是后人窜入。[3](P42)这种解释很无力,因此“建元元年说”并不可信。
集装箱水上“巴士”,指船舶按“五定班列”方式完成两港口或港区间集装箱的内支线运输,是港口集装箱集疏运的一种水水中转模式,以下简称水上“巴士”.深圳港水上“巴士”主要有基于东部盐田港的驳船支线,及基于西部蛇口和赤湾港的华南公共驳船快线.盐田港,地处深圳东部,海运优势明显,但就开展驳船业务而言,其地理位置远不如深圳西部港.深圳西部港,地处珠江入海口,东江、西江、北江在此汇流入海,通过珠江三角洲水网,与泛珠三角各大城市相通,为水上“巴士”提供了良好的地域优势.
综合以上4点可以看出,第一策和第三策前后逻辑连贯,衔接紧密,应是武帝在较短时间内下发的策文,董仲舒的对策也应是在相应的时间内完成的,而第二策与第一策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应是不同时间的文本。
成祖明另提新说,认为董仲舒对策在建元年间。[10](P137)他详细说明了诏举贤良和策问贤良之间的区别,认为从皇帝下诏书征召贤良到皇帝下策策问贤良,是一个前后递进的过程,中间有一段时间差。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初下诏举贤良,等各地的贤良文学汇集到京师,皇帝再下策发问,此时可能已经过了一年之久。他认为,建元二年(前139年)的政治形势与建元元年相比已有很大变化,窦太后重创了想要大展身手的武帝和儒生。董仲舒完成第一对策应是在这次政治风暴稳定扭转之时,此时已是建元三年(前138年)底、四年(前137年)初了。成祖明还认为,从皇帝制策到贤良对策,在较短时间内并不可能完成,董仲舒的第二、三对策,可能从建元四年一直延续到建元六年(前135年)。成祖明对诏举贤良和策问贤良的区分很有启发意义,他将制策和对策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认为董仲舒对策应是在建元四年到建元六年间,也很有参考价值。但他认为武帝在建元元年下诏征召贤良文学,而董仲舒却在建元四年对策,中间相隔两三年之久,这显然不合常理,并且他没有对三策之间的文本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其在确定对策年代时面临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
要解决董仲舒对策年代的问题,需综合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在史书无明确年代记载的情况下,对董仲舒的对策文本应作更细致的分析解读。以往学者虽然关注到“七十余年”“夜郎、康居归谊”等文本细部问题,但对三篇对策的文本关系仍缺乏细致的分析。其二,董仲舒对策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完成的,认真分析武帝朝的政治文化背景对判断董仲舒对策的年代很有帮助。其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与《史记·儒林列传》关于董仲舒事迹的记载相比,主要增加了董仲舒的三篇对策,因此综合考察天人三策的流传过程以及班固存录诏令奏议的原则,有助于我们判断董仲舒对策的年代。
二、天人三策的文本关系
董仲舒将阳与德、阴与刑联系起来,并认为王者应任德教而不任刑,这是对阴阳与王教关系极具创新性的阐发。因此,武帝第三策引述“阴阳”很可能是针对董仲舒第一对策关于“阴阳”的阐发而言。
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其次,三篇对策的前后顺序并不一定如班固《董仲舒传》般排列,这可从武帝的策与董仲舒对策的文本关系看出。
临床药物剂量可以根据理想体质量、总体质量、瘦体质量计算得出。但目前关于产妇的全麻药物剂量的最佳计算方法尚无共识。研究[2]认为,根据瘦体质量计算的丙泊酚诱导剂量不足以引起意识丧失;而总体质量更适用于肥胖患者[3]。本研究采用总体质量来计算产妇的诱导剂量。
其一,武帝在第三策中提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9](P2513)(以下所引武帝策及董仲舒对策皆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句中有“故”字,从上下文语气可以推断,武帝是在解释他为什么在上策问“天人之应”及唐虞、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事。以上诸事皆见于武帝第一策: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9](P2496)
用作牙膏凝胶剂,可替代进口的牙膏用增稠剂、触变剂(如Veegum,Laponite)。试验表明,使用国内蒙脱石含量大于97%、白度为82的高白膨润土,牙膏膏体细腻、挺括,膏体即时稠度为21 mm,灌装后挤出光泽性好。50 ℃连续放置3个月后,剖开膏体,色泽不变,没有结粒和干嘴现象,膏体表面光滑细腻。
文中提到虞舜至桀纣,王道陵夷大坏之事,这岂不就是第三策的唐虞、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事。“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岂不就是第三策的“天人之应”。反观武帝第二策,并不见“桀、纣”和“天人之应”的记载。因此,第一策和第三策有明显的前后衔接关系,而与第二策的联系则较为疏远。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9](P2523)
董仲舒的这三道对策被后人尊称为“天人三策”,因为他在策中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立太学、养士选官等一系列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建议。这三个对策如此重要,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有逻辑连贯性的整体,很少有人对它们之间的文本关系提出质疑。但从上文的考证中可以看出,三策之间并不是那么严密整饬,第一和第三对策前后衔接,确实有内容的前后相继性,但是第二对策被编排在中间,则完全破坏了第一、三对策的联系性,反而使三者的关系显得散乱、无逻辑。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於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於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於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
上述学者在考证时,均注意到了第一对策的“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和第二对策的“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并以此判断董仲舒对策的年代。这是用文本细读作考证的佳例,但有两个问题常被忽略,董仲舒这三篇对策是不是同一时间所作?它们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吗?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陈长琦在《董仲舒生卒考》一文中说:“详察班固所记董仲舒三道对策,其中有明显捏合之痕迹。……笔者个人认为,这三策不可能为同年所上,而是班固在编写时误把它们排在一起的。”[11](P139)陈长琦已注意到三策非同一时间所作,并提出史家误排的问题。这一观点极富启发性,但他只提出了这一推测,对三策文本的异质关系以及史家如何误排等问题并没有作详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证。
此外,武帝在第三策言:“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9](P2514)所谓的“大道之极”“治乱之端”均是指董仲舒在第一对策劝武帝扫除周秦以来之弊,兴教化,以崇五帝三王之道。董仲舒虽然在第二对策提出了兴太学、举孝廉等建议,但谈不上是“大道之极”,武帝的第三策其实是针对董仲舒的第一对策而言。
排练厅的低台是用红色地毯铺了面的,并不大,但因着王爷瘦,又是坐着,所以那低台仿佛在他身后空而寂寥地延伸了一大片过去。
其三,武帝在第三策中提到:“今子大夫明於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虖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欤?”[9](P2513-2514)“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是武帝抱怨董仲舒对策之无条理而使其不明目眩也。董仲舒在第三对策也承认:“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9](P2514-2515)他因此更换了一种书写方式,在每段之前先列武帝之策文,再接以自己的对策,如“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无所殊……”[9](P2515)仔细分析董仲舒的前两篇对策,第一对策与武帝策的对应关系较为漫散,武帝首问帝王之道日以扑灭的问题,之后又问“受命之符”“灾异之变”“性命之情”,而董仲舒的对策并没有直接回答武帝关于“帝王之道”的提问,却据《春秋》讨论灾异之缘起,后再论道与帝王之间的关系,逻辑较为散乱。反观董仲舒的第二对策,武帝的问与董仲舒的对一一对应,并不存在“条贯靡竟,统纪未终”的问题。因此,武帝第三策关于“条贯靡竟,统纪未终”的责问,应是针对董仲舒的第一对策而言。
其四,武帝在第二策中提到:“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於文系而不得骋欤?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欤?”[9](P2507)武帝提到的“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显然并不是针对董仲舒一人而言,更像是对百余待诏贤良的进一步策问。班固在第二对策前有一衔接语“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曰”。[9](P2506)观班固之辞,武帝似是在看到董仲舒第一对策后,因觉其对不同凡俗而紧接着发出第二策。但观武帝第二策之内容,他对这百余多贤良的对策是很不满的,所以才有“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之语。从这个角度看,班固将董仲舒的第二对策放在第一对策后,语气颇显隔阂,上下衔接并不通畅。
“元光元年五月说”最早由洪迈提出。《容斋续笔》卷六《汉举贤良》曰:“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6](P288)王先谦亦持此说。[7](P1152)周桂钿详考诸家之说,肯定了“元光元年五月说”。[8](P1019)主要证据有:其一,《汉书·武帝纪》有诏贤良的记载;其二,汉兴至元光元年为74岁,与“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符合;其三,夜郎“悦德归谊”在建元六年后,元光元年与之没有冲突;其四,董仲舒对策后,任江都相,《春秋繁露·止雨》曰:“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2](P438)江都王二十一年即元光二年(前133年),说明仲舒元光二年在江都相任上,两条史文相合。[5](P85)“元光元年五月说”虽较“建元元年说”合理,但仍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班固在《董仲舒传》明言:“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9](P2525)这里的逻辑关系很清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州郡举茂材孝廉”“立学校之官”都由董仲舒倡言,是在对策之后;而《汉书·武帝纪》“置五经博士”和“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分别在建元五年(前136年)和元光元年十一月,这两个时间点都在元光元年五月前,因此“元光元年五月说”也不可信。
三、天人三策之流传及编纂
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著录“天人三策”,不知是没有看到还是不够重视,受史料限制,只能存疑。武帝第一策曾提到:“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9](P2498)武帝鼓励贤良文学直言极谏,即使有“不正不直,不忠不极”之言,也仅限皇帝知道,对策内容并不会被漏泄出去。[12]董仲舒之对策经武帝批阅后,很可能藏于中央秘府档案中,外人不可能轻易得见。陈苏镇认为,“天人三策”可能于昭、宣时期才开始在民间流传。[13](P224)《汉书·杨恽传》载,宣帝时杨恽报孙会宗书曰:“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师古注曰:“引董仲舒之辞也。”[9](P2896)《汉书·董仲舒传》载“天人三策”言:“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9](P2521)二者文本极为相似,杨恽所引当从“天人三策”来,可见宣帝时“天人三策”已经开始在民间流传。
《董仲舒传》末载班固语:“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9](P2525-2526)这段话含有丰富的信息。一是《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9](P1727)班固所看到的“百二十三篇”,指的就是《汉志》所载董仲舒的著作,其中便有董仲舒的“上疏条教”,“天人三策”应在其中。《艺文志》乃据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而成。刘向在校书时应该参考了当时中央秘府之档案即所谓“中书”,以及当时民间流传之董仲舒著作即所谓“外书”,最后确定的这百二十三篇可能是汇合中、外书的成果。刘向在校定董仲舒之对策时不太可能完整保留原始材料之“时间信息”,如武帝何年何月何日所下之策,以及董仲舒何年何月何日对策。这些原始信息在文书中当然重要,但一旦文书转化为子书,这些信息则显得累赘、繁琐,很可能会被删除,贾谊《新书》就是一个例子。[14](P27-36)《新书》有部分篇章从贾谊奏议而来,但奏议之原始信息已被完全删削掉了。二是这些著作以“篇”为单位,“天人三策”很可能是其中的三篇,而不是一篇,这可从贾谊的《新书》得到侧面印证。《新书》的部分篇章实为贾谊的奏议,一篇言一事,班固删削整合贾谊的多篇奏议而成《汉书·贾谊传》所载之《陈政事疏》。[14](P27-36)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很可能也是分开的三篇,只不过班固并没有像对贾谊的奏议一样整合三者,而是在三策间加“复册之”以营造三者为一有机整体的印象。三是班固只是“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董仲舒传》中,“掇”字有选择之意,“天人三策”因影响深远而被班固选中。
班固所面对的很可能是三篇无时间信息、被删除掉文书原始格式的对策,而这三篇策与对策在词句、语气等方面又非常相似。班固在编排时,很可能误将第二道对策编入本有紧密联系的第一和第三对策间,并以“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曰”,“于是天子复册之”等词句来衔接前后之策,从而造成三策具有时间连续性且为一个系统整体的假象。
四、董仲舒对策年代考论
辨别清楚第一、三策与第二策的关系,对于确定董仲舒对策的年代有重大意义。以往学者因先入为主,认为三篇对策应有紧密的联系且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因而在确定年代的时候,总是面临一些无法解释的难点。如将其定为建元元年,无法解释“临政七十余年”和“夜郎康居归谊”的问题,将其定为元光元年前后,却无法解释“置五经博士”“州郡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前的矛盾。
董仲舒的第一和第三对策应是在建元四年至建元五年之间,而第二对策应在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初之间。为什么将董仲舒对策的年代确定在建元四年至建元六年之间?这要从武帝朝政治文化背景的分析入手。
高祖刘邦戎马倥偬建立汉朝,所依靠的是一群知识水平不高、无法提供文化制度建议的武官,而这批人在汉初一直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李开元称其为“军功受益阶层”。[15]武帝即位时,跟随刘邦打下汉朝江山的功臣已经陆续凋零,但其子孙仍把持着公卿要职,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而从汉初开始,为稳固江山需要陆续设立的诸侯王,虽因七国之乱力量大为削弱,但仍不可小觑。在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势力制衡下,汉初皇帝想要有所作为还是比较困难的。加上汉初黄老之学盛行,无为而治虽然让历经战乱而初创的帝国得以休养生息,但承秦以来的政治、文化等弊端也一直被忽视。贾谊曾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9](P2222)并主张更改秦以来风俗之流弊,以礼义教化天下。但在周勃等军功大臣的阻止下,文帝并没有接受贾谊的建议,贾谊本人也郁郁而终。
武帝即帝位时虽然年少,但必然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很不满,因此一开始就想要有一番大的变革。建元元年冬十月,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9](P155-156)文帝曾因日食向天下征召贤良方正,以补其政之弊,这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建元元年初并不见日食灾异,武帝主动诏丞相、御史等人举贤良,其实是想从民间征集人才来充实皇帝身边的人才储备,打破军功阶层把持朝廷要职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武帝想要在文化制度上有一番大的改革,知识水平并不高的军功集团无法提供建议,而从全国征召的贤良文学则能帮助其实现改制度、易服色的宏伟理想。是年,武帝用安车蒲轮征召鲁申公、议立明堂就是明证。可惜的是,建元元年初的这次举贤良并不成功,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9](P156)这些所举的贤良或治申、商刑名之学,或为战国纵横之术。刑名法术很难提供文化制度上的建议,战国纵横之术也与专制中央集权格格不入,因此武帝同意了卫绾罢黜这些人的建议。
建元二年初,因御史大夫赵绾建言勿奏事窦太后,儒生以及需要儒生助其实现明堂辟雍等计划的武帝,和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开始了正面冲突,此事最终以赵绾和王臧的自杀而告败。虽然经过建元二年的重大打击,武帝培养自己人才的打算并没有放弃,严助等人就是例子。《汉书·严助传》载:“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於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于是严助诘责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9](P2776)严助只是中大夫,但因为是武帝身边的近臣,所以可以当面诘责太尉田蚡,并只身持节赴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9](P2776)是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4](P1134)武帝取得了军事、外交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成祖明认为,严助平定闽越之乱一事不仅一举扭转了武帝内政上的被动,也激发了武帝在内政外交上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10](P138)此说很有道理,建元二年与窦太后的冲突虽然是一次严重的挫折,但武帝在建元年间并没有沉寂,而是抓住机会为他以后的文治武功作准备。《史记·大宛列传》:建元中 “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4](P3157)可见,北征匈奴的战略在建元年间就已谋划。
建元年间,帝国境内并不平静,可以说是灾异频仍,《汉书·武帝纪》载:
(建元二年),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蚀之。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病虫害的防治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在茄子的生长过程中,病虫害的防治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如果病虫害不能及时的预防和治理会感染大面积的茄子,影响茄子的产量和质量。在茄子的病虫害防治中,主要有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两种。生物防治就是采取一些生物措施对病虫害进行防治,进而保障茄子的质量。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九月丙子晦,日有蚀之。
为有效治理食品药品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该局实施食品医药企业诚信“积分制”,对负面积分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开曝光。近3年来共公开曝光食品医药“黑名单”64家,食品药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明显减少。
首先,根据汉代的文书创作、传递流程,董仲舒这三篇对策应该不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10](P140)《汉书·董仲舒传》:“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屮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9](P2524)董仲舒推说灾异,草稿未及上奏,便被主父偃窃取。此外,《汉书·师丹传》:“又(师)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9](P3506-3507)《汉书·朱云传》:“云上书自讼,(陈)咸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9](P2914)这些例子皆可说明,汉人上书一般都会先打草稿。奏文草创之后,又经一番修改而定稿,稿成后经尚书传递给皇帝,皇帝批复,再下发给上书者,如此往复,是一个很费时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董仲舒的三篇对策很可能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完成的。成祖明认为:“因为董仲舒的每一策并非像后世的科举考试,需要当场交出答卷,而是用对策的形式参与国家重大方针的研议,需要时间逐字逐句斟酌研思……而汉代公文上呈和下发还需要经过尚书等部门处理、传递……加上朝廷众多事务延搁和其时武帝耽于游猎,一些现实可行的建议到了武帝那里,也需进一步研议实施,这些都会延搁时日。……从第一策到第三策持续了较长时间是很有可能的。”[10](P140)其说颇中肯綮。
(五年)五月,大蝗。
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9](P158-160)
日食、水灾、星变、蝗灾、旱灾等灾异相继出现。灾异中的日食往往会得到人君的特别关注,它们被认为是上天告诫人君不德的征兆。文帝曾在即位二年,因日食发布罪己求贤之诏书:“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灾孰大焉!”[9](P116)文帝认为,人主不德,上天就会以日食来警告人君,人主想要消除灾异,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项是“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9](P116)少年即位的武帝在面对如此频繁的灾异时,必然心生戒惧,因而有意向有贤德之名的文帝学习,下诏罪己并求贤良。因此如果将武帝的第一策放在建元三年九月日食之后,就可以理解了。成祖明认为,武帝第一策的策问重点是“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而这也是为什么董仲舒对策开门见山便是“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云云,围绕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学说展开的原因。[10](P140)《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可为武帝建元三年举贤良增一佐证:“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4](P2748)建元中很可能就是指建元三年,此时武帝征召过贤良,只是《武帝纪》未载,董仲舒参与的很可能就是这次贤良对策。
汉太初元年以前以十月为岁首,九月发生的日食,实已临近建元三年岁末。而从武帝作策到董仲舒对策,文书写作和传递必然耗费一段时日,可能到建元四年初董仲舒才完成第一对策,因此“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也就可以理解了,此时距汉初刚好70年左右。董仲舒第三对策的时间与第一对策应不会相距很久,从武帝第三策的“故”“既已”等词可以判断,[9](P2513-2514)武帝在看到董仲舒的第一对策后不久,应该专门为董仲舒另发了策。
一是抓牢组建工作,夯实党组织基础。组建党的组织是搞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发展党员工作又是组建党的组织的关键点和基础。首先,要始终抓住发展党员工作不动摇,把一线生产能手培养成中层骨干,把中层骨干培养成入党积极分子,把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成合格党员。要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工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创新党组织设置模式,全面推进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的“全覆盖”。积极落实十八大报告精神,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
董仲舒在第三对策中回应武帝的策:
(3)表现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物联网发展中出现包括EPC系统在内的新的信息技术系统,通过利用对畜牧产品进行归类,对每一个产品进行唯一代码的编写,以代码的形式实现物品信息资源在互联网共享的新型平台操作,对于畜牧产品的信息流通起到重要的推广传播作用,另一方面,在产品流通中起到监管作用。2006年,有学者提出应用RFID技术、二维码技术以及相关组件技术,构建起猪肉可追溯系统,对生猪养殖及其肉制品实施全程质量监控。之后该系统不断应用、健全、完善,目前已实现让消费者购买猪肉制品后可追溯肉品生产全过程的目标,有效保证了猪肉制品的质量安全[3]。
盐城市区饮用水源生态净化工程库区生态堤防设计……………………………… 朱冬舟,陆惠萍,仓基俊等(14.26)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和建元元年卫绾罢退申韩刑名、苏张纵横之术相呼应,正中欲有一番大改革,想要立明堂辟雍、改制度、易服色的武帝的心怀。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在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从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可以推测,董仲舒的第三对策应就是在建元四年至建元五年之间完成的。他在完成第一和第三对策后,很可能被任命为中大夫。此事有一些佐证,《汉书·晁错传》曰:“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9](P2299)《汉书·严助传》:“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9](P2775)晁错和严助在对策后分别被任命为中大夫,可见对策高第而为中大夫应是当时的惯例。董仲舒的对策既得到武帝的肯定,那么像晁错、严助一样被拔擢为中大夫的可能性便很大了。
第二策则较为特殊,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辨清皇帝诏贤良和策贤良的区别。皇帝下诏征召贤良与皇帝下策策贤良是前后不同的过程,《汉书·谷永传》有清晰的记载:“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太常阳城侯刘庆忌举永待诏公车。对曰:‘陛下秉至圣之纯德……’”[9](P3443)建始三年(前130年)因日食地震同发,成帝于是下诏征召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谷永在举中。他在对诏中劝成帝注意后宫女祸,并提出选拔贤才、宽法缓刑等建议。班固言:“对奏,天子异焉,特召见永。”[9](P3450)这说明谷永之对在各郡所征召之贤良中较为突出,因此引起成帝之注意。班固又曰:“其夏,皆令诸方正对策,语在《杜钦传》。”[9](P3450)《杜钦传》确实有载:“其夏,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9](P2673)两相对照,可知成帝于建始三年冬下诏征直言之士,其后众人条对灾异之原因,当年夏天成帝再将众人召至白虎殿,令其对策。下诏征贤良在前,而下策策贤良在后,两者是前后相续但性质并不同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重审武帝的第二策,策中言“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似是针对已完成对诏但还未对策的贤良而言。此时之贤良还未对策,并没有因对策之高低而被授予相应官职,因此策中称他们为“待诏”。待诏是说他们仍处于待皇帝策问的阶段,董仲舒只是待诏者之一。董仲舒在完成第一、三对策后,再次被人举荐而参加贤良对策的可能性很大。晁错曾对文帝之策言:“平阳侯臣窋、汝阴侯臣竈、颍阴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昆邪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昧死再拜言……”[9](P2291-2292)晁错已为太子家令,而被曹窋等人举荐,仍可参加贤良对策,董仲舒的情况应该类似。班固将董仲舒的第二对策置于一、三对策之间,又用“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曰”[9](P2506)连接上下文,造成了三策前后相续的假象。
第二对策的时间要稍晚,文中的“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可以帮助我们定位年代。《汉书·西南夷传》:建元六年,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从巴苻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9](P3839)可见夜郎归谊之事在建元六年。而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4](P3044)司马相如去蜀作檄,在通夜郎之后不久,其檄文提到的“康居西域,重译请朝”显然在此之前。董仲舒很可能受唐蒙通夜郎之事的感发而在第二对策中提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事,所以董的第二对策应是在建元六年之后所作。
此外,董仲舒在第二对策言: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於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9](P2513)
在这个场景下,Graham拍摄了一系列照片。有的照片中Dylan显得更小一些,有的是拳击手套更模糊,还有的是或多或少挡住了模特的脸。这一张是所有要素的最佳组合状态。在对背景的虚化处理上,Graham选择的大光圈也十分恰当,这样的效果的确很有戏剧感。另外,色彩的处理很好地加强了整个画面的氛围,同时也让多种不同的光源在画面里显得和谐统一。
董仲舒向武帝建言,岁使有司贡二人,则天下之士可得而官。班固认为:“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9](P2525)另据《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9](P160)文中之“初”字正好与“皆自仲舒发之”形成对应。由此可推测,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其实就是受董仲舒对策的启发。这样董仲舒第二对策的年代就可确定,是在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初。在完成第二对策后,董仲舒由中大夫升迁为江都相,这也是为什么班固说“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9](P2523)据《春秋繁露·止雨》,董仲舒在江都易王二十一年,[2](P438)即元光二年在任,也是一证。
五、班固存录诏令奏议的原则
以往有些学者在判断董仲舒对策年代时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汉书·武帝纪》关于举贤良的记载。他们认为,《武帝纪》在建元元年、元光元年五月分别有诏举贤良的记载,而董仲舒的对策又是如此重要,班固绝不会在武帝的本纪中漏过,因此董仲舒对策不是建元元年就是元光元年五月。这其实是一个思维误区。
班固在《汉书》中存录诏令奏议时有一些基本原则:当他觉得臣民的奏议非常重要时,会在其本传中录下这些奏议,并在奏议之前附上皇帝的诏令。而当他觉得皇帝的诏令非常重要时,则会直接录在皇帝本纪中。如果他觉得皇帝的诏令和臣民的奏议都非常重要,则在皇帝本纪中简单记录,而在大臣本传中详列诏令奏议的正文,这样皇帝的本纪不至于太过臃肿,而大臣本传不至于太过简洁。
班固在编撰《武帝纪》时,大致以诏令的日月排列,并将一些重要的诏令和事件简洁编排。建元元年武帝刚即位,因是首次诏举贤良,所以可以被列入本纪。建元元年征召鲁申公议立明堂之事,象征着武帝要更改制度,向上古圣王学习,因此也被列入本纪。建元三年严助持节平定闽越之乱,是武帝对征服四夷的开端,也具有象征意义,因此也被写入本纪。
从班固的存录原则看,他并没有漏掉董仲舒的建议,《武帝纪》建元五年有“置五经博士”的记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有“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记载。皇帝本纪并不适合介绍“置五经博士”和“郡国举孝廉”的详细过程,因此班固在《武帝纪》简洁记下董仲舒对策被武帝采用这一结果,而在《董仲舒传》中详列武帝的策和董仲舒的对策,这是很正常的。《汉书·严助传》称严助被举贤良,《汉书·武帝纪》就没有记载严助在何年对策。上文引用过《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邓公在建元中被举贤良之事,而《汉书·武帝纪》也没有关于建元中举贤良的记载。班固在《严助传》中说:“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9](P2775)武帝雄才大略,内建制度,外立武功,国家多事,因此亟须从帝国境内征召能服务于自己的人才。这些多为平民而被征召的贤良无疑是武帝最佳的人选。这些人跟随在武帝身边,外难丞相御史等大臣,内为武帝提供政策建议,深得武帝的信任。班固说武帝“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武帝纪》中可见的举贤良记载却并不多,这说明班固在武帝本纪中只是选择其较关键者存录而已。
六、结 语
其二,武帝在第三策中曰:“今子大夫明於阴阳所以造化,习於先圣之道业。”[9](P2513-2514)如果按照班固的三策排列顺序,董仲舒应在第二对策中对“阴阳”有所阐述,武帝才可能有此说。但是遍查董仲舒的第二对策,并不见关于“阴阳”的论述,而在第一对策中,董仲舒曰:
对“天人三策”文本顺序的再思考,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年代问题。以往将董仲舒对策年代定于某一年的看法,其实有根本的逻辑问题。董仲舒对策应是在数年之间完成的,很可能是建元四年至元光元年初之间。对董仲舒对策年代的确定,又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武帝即位初期的史实。窦太后在建元二年对儒生的打压并没有让武帝消沉,相反,武帝在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之间,对外征服闽越、西南诸夷,内立五经博士,兴孝举廉,以广选官之路,为之后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储备了大量的人才。董仲舒的对策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注释:
一般情况下,患者在服用药物之后,会对自身的代谢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对标本中的条件带来变化,使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得不到有效保障。此外,药物自身的一些特性也会给检验结果带来较大的影响。主要机制为:①药物根据本身的作用以及不良反应等影响检验的结果;②通过药物的物理性质影响检验的结果;⑨通过药物的化学机制影响检验结果。
[1](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M].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张大可.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4).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近年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许多质疑高校思政课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杂音和谬论,比如“思政课取消论”、“思政课非意识形态化”、“思政课无用论”等。一些人认为,把思政课作为高校学生的必修课是没有必要的。一些人认为,高校开设思政课无可厚非,但应该摒弃以灌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流的思政课,代之以介绍世界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还有一些人主张,思政课没有多大的用处,不如把思政课的时间用在专业课的学习上。这些观点对思政课的误解、歪曲甚至抹黑,在当代大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是思政课建设面临的问题之一。
[5]刘国民.董仲舒对策之年辨兼考公孙弘对策之年[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3).
[6](南宋)洪迈撰,孔凡礼整理.容斋续笔[C]//.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5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7](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成祖明.诏策贤良文学制度背景下的“天人三策”[J].历史研究,2012(4).
[11]陈长琦.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12]汉人对于臣民之对策及奏事有严格的保密规定。董仲舒在家中应留存着对策的草稿,但这些草稿也不可能轻易示人。《汉书·孔光传》:“时有所言,辄削草槀,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服虔注曰:“言已缮书,辄削坏其草。”见(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354页.)奏书因多涉国家之重大事务,或有对皇帝直言极谏之言,并不适合公开传布。师丹就曾因奏事草稿漏泄而被弹劾大不敬,后被哀帝借机免除大司空之位。董仲舒虽然并没有像孔光一样删削奏书草稿,但注意奏书内容之保密,不使其在社会公开流传当是一定的。
[13]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M].中华书局,2011.
[14]余建平.贾谊奏议的文本形态与文献意义[J].文学遗产.2018(3).
[15]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TheResearchontheTextualSequenceof“ThreeCeofHeavenandMan”——Also on the Writing Time of Dong Zhongshu’s XianliangDuice
YU Jian-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A lot of debates were made on the writing time of Dong Zhongshu’s Duice, with the negligence on the textu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ThreeCeofHeavenandMan”. They were not written at the same time and without internal continuity. The first and third Duice should be created between the fouth years and fifth year of Jianyuan, and the second Duice should be created between the sixth year of Jianyuan and the beginning of Yuanguang. Ban Gu added the text of “the emperor gives Ce again” among the three Duice, making the illusion that the three Duice were created in the same period.
Keywords:Dong Zhongshu; “ThreeCeofHeavenandMan”; text order; Duice
[收稿日期]2018-07-12
[作者简介]余建平(1989-),男,江西上饶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6-005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5
标签:董仲舒论文; 对策论文; 武帝论文; 贤良论文; 元年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汉代哲学(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论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