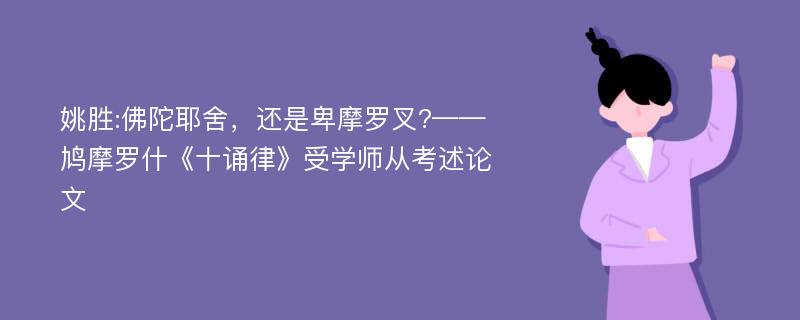
内容提要:关于鸠摩罗什《十诵律》受学于何人,最早的两部文献《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前者说是佛陀耶舍,而后者则认为是卑摩罗叉,学界对此也尚无定论。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部文献各自《鸠摩罗什传》的相关文本、佛陀耶舍与卑摩罗叉二人的译经活动以及鸠摩罗什与二人的心性异同,对鸠摩罗什《十诵律》师从人物进行考述,并做出了可靠结论。
关键词:十诵律 鸠摩罗什 佛陀耶舍 卑摩罗叉
“ (鸠摩罗什,Kumārajīva) 及还龟兹,名盖诸国…… 后从佛陀耶舍(Buddhaya as) 学《十诵律》(Sarvāstivādavinaya)。”
——僧祐:《出三藏记集》
“什还国……从卑摩罗叉(Vimalāk a) 学《十诵律》。”
基于环境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及Arthur Stamps的天际线美学评价理论,归纳得到城市天际线美学评价要素体系(表1),为下文进行定量评价奠定基础。以下将结合天津海河沿岸天际线实例,探讨城市天际线定量评价的实现途径。
——慧皎:《高僧传》
鸠摩罗什,五胡十六国前后秦时期僧人,出生于龟兹,父亲为天竺人,母亲为龟兹人。现存最早关于鸠摩罗什的历史文献,当属南朝齐、梁时期的两部,一是僧祐编纂的《出三藏记集》(又称《僧祐录》),①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 版。另一是稍后慧皎编纂的《高僧传》,②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1 版。《高僧传》卷十四“序录”(第524页) 写道:“沙门僧祐撰《三藏记》(作者按:即《出三藏记集》),止有三十余僧,所无甚众。”《出三藏记集》一共32 篇僧传,加上附传一共记有49 人。汤一介在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绪论”中说,“所有三十二僧传几全为《高僧传》所采录。”再往后,还有唐朝编纂的《晋书·艺术传》。③《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 版,1993年10月第5 次印刷。晚于僧祐但早于慧皎的还有宝唱编纂的《名僧传》,此书现已不存,尚有日本僧人宗性抄录的《名僧传抄》,保留了目录及部分内容。④宝唱撰,宗性抄,《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134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另,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 曾于1925年影印此书。
国内最早关注鸠摩罗什研究的,首推汤用彤,其于1938年初版、此后数次再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为“鸠摩罗什及其门下”。①本文所据版本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 版,2016年6月第2 版。陈寅恪对《高僧传》尤其是其中的“鸠摩罗什传”十分关注,有《读书札记》。②陈寅恪:《读书札记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9月第1 版,2015年7月第3 版。吕澂对中国佛学思想体系、宗派及其流变做过全面而系统的分析。③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 版。梁启超也对中国佛学思想、体系、经译等问题有过深入研究。④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6月第1 版。该书曾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作为《饮冰室专集》中的一种出版,1989年为影印版。近年,黄先炳、纪赟分别有博士论文对《高僧传》进行了研究。黄先炳对《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和《名僧传》做了充分、深入的比较研究。⑤从《名僧传抄》情况来看,“ 《名僧传》收录传主四百二十二人,其中超过半数,即二百二十四人见于《高僧传》正传,另有近三成即一百一十二人见于附传。”黄先炳:《〈高僧传〉 研究》,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博士论文,第46页。纪赟对《高僧传》作者思想观念、写作背景、文献资料、史料源流等做了系统研究。⑥纪赟:《慧皎〈高僧传〉 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2006年博士论文,2009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与传统研究方法和视角不同的是,陆扬从文化背景、叙述方式和历史心理学的角度,对鸠摩罗什传做了阐发。⑦陆扬:《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中国学术》第2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3月第1 版。Yang LU,Narrative and Historicity in the Buddhist Biographie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The Case of Kumarajiva,Asia Major,third series,vol 17,no.2 (2004),pp.1-43.陈楠发现元代藏文文献《红史》中有关于鸠摩罗什的记载,可与汉文史料对照。⑧陈楠:《鸠摩罗什生平事迹新证——汉藏文献记载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在研究综述方面,有黄夏年、桑荣、张开媛三人分别对前人研究成果做了梳理。⑨黄夏年:《四十五年来中国大陆鸠摩罗什研究的综述》,《佛学研究》,1994年第3期。桑荣:《鸠摩罗什研究概述》,《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张开媛:《1995年以来国内鸠摩罗什研究综述》,《邯郸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纪赟、陆扬则分别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做了介绍,后者尤其提到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鸠摩罗什生平包括生卒年份的关注。⑩纪赟:《慧皎〈高僧传〉 研究》,“引言,第二节 研究综述”,第10~21页。陆扬:《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一、研究现况与问题”,第30~32页。
再看第1 句“沙门法显以义熙二年从外国还,得《僧祇律》《弥沙塞律》二部,止获胡文,未得宣译。”我们知道,法显乘船返国抵达青州长广郡的时间是“义熙八年”(412年) 无疑。此处记为“义熙二年(406年)”,似乎明显有误。不过,相同的记载却还见于《出三藏记集》卷三“弥沙塞律”:“法显以晋义熙二年还都,岁在寿星,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七月,有罽宾律师佛大什来至京都……时佛大什手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至明年十二月都讫。”④《出三藏记集》卷三“弥沙塞律”,第120页。此即《名僧传抄》所引文字最后一句“宋景平元年,沙门佛驮什与智胜共出《五分律》”的详解。将《出三藏记集》这句话遮掉“义熙二年”,而连贯地看“法显……还都,岁在寿星,众经多译”一句,就能发现,这句话讲的是法显回到南京道场寺译经的情况。岁在寿星,即当年为丙辰年。据《法显传》“跋文”、①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第1 版,第153页。《摩诃僧祇律私记》②《中华律藏》第2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 版,第341页。《法显传校注》附录(六),第169页。、《出三藏记集》卷三“婆粗富罗律”③《出三藏记集》卷三“婆麤富罗律”,第119页。可知,法显于义熙十二年(416年) 岁次寿星十一月,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共译《摩诃僧祇律》,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出三藏记集》卷八“六卷泥洹经记”记载法显与佛驮跋陀于义熙十三年至十四年在“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译定《方等大般泥洹经》。④《出三藏记集》卷八“六卷泥洹经记”,第316页。同书卷二“大般泥洹经……佛游天竺记”(此为法显自天竺携回的经录) 记载“右十一部……沙门释法显……归京都,住道场寺,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共译出。其‘长’、‘杂’ 二《阿含》、《綖经》、《弥沙塞律》、《萨婆多律抄》,犹是梵文,未得译出。”⑤《出三藏记集》卷二,第54~55页。综合这些记载来看,《出三藏记集》“法显以晋义熙二年还都,岁在寿星,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二年”之前脱一“十”字,即法显以晋义熙十二年还都云云,而非“以晋义熙二年”。且,“众经多译”讲的应当是在义熙十二年至十四年间,有多部经书译出的情况,而非指十二年当年。⑥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对此“义熙二年还都”深感困惑:“ 《出三藏记集录》卷三有‘法显以晋义熙二年还都’ 之语……其为谬误,无庸赘言……”足立喜六为此还专门做了一个对照表(略),考证“义熙元年”、“义熙二年”之误。其困惑不解之原因正在于没有准确把握《出三藏记集》“义熙二年还都,岁在寿星,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的上下文意,没有意识到“义熙二年”就是“义熙十二年”之漏。[日] 足立喜六著,何建民、张小柳译《〈法显传〉 考证》,贵阳:贵州出版社,2014年3月第1 版,第234、235页。《名僧传抄》“沙门法显以义熙二年从外国还,得《僧祇律》《弥沙塞律》二部,止获胡文,未得宣译”,此处“义熙二年”亦为“义熙十二年”之误。
可以说,鸠摩罗什研究已是汗牛充栋,其中众人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鸠摩罗什的生平、思想以及译经等方面。不过,笔者发现,对于“鸠摩罗什《十诵律》受学于何人”这一问题,尚无定论。除伯希和、鎌田茂雄①伯希和撰,富安敦整理,张广达等译,《关于鸠摩罗什札记》,《西域文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第1 版。Paul Pelliot,Notes sur Kumārajīva,Antonino Forte and Federico Masini(eds.),A Life Journey to the East.Sinological Studies in Memory of 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Kyoto,2002,pp.1-19.[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Essays,volume 2]。鎌田茂雄:《中国佛教史》(「中国仏教史」) 第二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6月1日初版。该书有中文译本,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0月第2 版。与黄先炳有所考察之外,其他人则或回避,或虽涉及但未作分析,或径称受学于某人而未论述理由。②塚本善隆:《肇论在佛教史上的意义》(「仏教史上における肇論の意義」),《肇论研究》,京都:法藏馆,1972年,第138、139页。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 版,第260、262页。鸠摩罗什《十诵律》到底受学于佛陀耶舍还是卑摩罗叉,为何《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对此记载截然不同? 解决这个问题,实有必要,这也是本文的主旨。
一、《出三藏记集》的相关记载自相矛盾
廖:大凡某种学问成了体系,也就有了述史钩沉者.中国远古之文明可谓早已斑斓纷呈.三代以降,除匠作农桑之技外,更有天地玄黄之理、物化医算之明.但在大多数文人墨士眼中、看到与想到的只是驭民安邦之策、翰墨文华之流.故修史立典者,莫不以帝王政事为先、择儒林吏业为要.天文星象、河川地理、矿冶衣食,大多是系挂在这一核心之上.这些知识仅仅是在长期的积累与发展中,形成了最广义之“科学”——学问、体系化知所应具备的面貌与要素,以及丰富的内容,但并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概念.因而当然也不可能有自成体系的科学史.
“你看那边,是不是还是昨天那俩人?”虽然感冒了,精神不佳,但一点也不影响王施凯扫视四周,一眼就看到了路口徘徊的黑衣人。
最近对这一问题考察较多的是黄先炳,兹录其文如下:
黄先炳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实,不仅《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关于鸠摩罗什受学《十诵律》师从佛陀耶舍的记载有出入,《出三藏记集》自身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载就有自相矛盾之处。
鸠摩罗什于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401年2月8日) 抵达后秦都城长安,国主姚兴待之以国师礼,请入西明阁、逍遥园,并使沙门僧、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翻译佛经。鸠摩罗什在临终③《出三藏记集》没有记载鸠摩罗什的卒年,《高僧传》则记载为弘始十一年(409年),唐代《广弘明集》所收的僧肇撰《鸠摩罗什法师诔》记载为弘始十五年(413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该诔文是伪作。伯希和、汤用彤、塚本善隆、鎌田茂雄、陈世良(《鸠摩罗什年表考略》,《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期) 等对鸠摩罗什卒年多有考证,但目前仍未确证,尚有争议。笔者在此提供两条材料,或有益于讨论。其一,在本节我们会知道,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二年(410年) 开始着手翻译《昙无德四分律》,十四年译毕,十五年出《长阿含》。佛陀耶舍恐未通晓华语,故而所出二经由竺佛念翻译,道含笔受。若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鸠摩罗什尚在世,以其与佛陀耶舍之关系,为何不亲自与耶舍共译? 或说佛念只是翻译《长阿含》而未参与翻译《四分律》,则僧肇《长阿含经序》(《出三藏记集》卷九,第336、337页) “请罽宾三藏法师沙门佛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四年讫。十五年。岁在昭阳奋若。出此《长阿含》讫。凉州沙门佛念为译”(以“。”号为句读),如果佛念没有参与《四分律》,此《长阿含经序》完全不需要提及《四分律》一事。其二,《出三藏记集》“道生法师传”:“竺道生……钻仰群经,斛酌杂论,万里随法,不惮险远,遂与始兴慧睿、东安慧严、道场慧观,同往长安从罗什受学,关中僧众咸称其秀悟。义熙五年还都,因停京师。”此处义熙五年即弘始十一年(409年),道生此时离开长安,或许即为鸠摩罗什去世之后。前曾跟众僧告别,感喟自己“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在此应当说,《十诵律》的翻译,殊为不易,过程跌宕曲折,本文需要赘述一下。
据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录·萨婆多部〈十诵律〉》云:昙摩流支得书,方于关中共什出所余律,遂具一部,凡五十八卷。后有罽宾律师卑摩罗叉来游长安,罗什先在西域,从其受律。罗叉后自秦适晋,住寿春石涧寺,重校《十诵律》本,名品遂正,分为六十一卷,至今相传焉。
卷十四第一“鸠摩罗什传”卷十四第二“佛陀耶舍传”沙勒国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什进到沙勒国……诵《阿毗昙》《六足诸门》《增一阿含》至沙勒国,罗什后至,从其受学《阿毗昙》《十诵律》,甚相尊敬什随母东归,耶舍留止龟兹 及还龟兹,名盖诸国地点未明 后从佛陀耶舍学《十诵律》
从这两段我们可以发现,《出三藏记集》一说鸠摩罗什是随其母回到龟兹之后才从佛陀耶舍受学《十诵律》,又说是回到龟兹之前。而且,从两篇传文内容上来说,也无法得出鸠摩罗什跟随佛陀耶舍“学过两次”《十诵律》的信息,而只能是一次。同一部书的两篇传文,而且两篇传文一前一后紧挨在一起,却自相矛盾,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我们再对《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各自“鸠摩罗什传”的相关内容做一个简表,进行比较分析一下。
《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七岁 亦俱出家 亦俱出家九岁 进到罽宾,遇名德法师槃头达多 随母渡辛头河至罽宾,遇名德法师槃头达多年十二 其母携还龟兹 其母携还龟兹至月氏北山,有一罗汉见而异之 时什母将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罗汉见而异之什进到沙勒国,顶戴佛钵 什进到沙勒国,顶戴佛钵什於沙勒国诵《阿毗昙六足诸论》、《增一阿含》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诵《阿毗昙》
续表
《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时有莎车王子……什亦宗(须利耶苏摩)而奉之,亲好弥至顷之,随母进到温宿国及还龟兹,名盖诸国 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年二十 受戒于王宫后从佛陀耶舍学《十诵律》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有顷,什母辞往天竺又从须利耶苏摩谘禀大乘于龟兹帛纯王新寺得《放光经》,始披读(遇魔)于是留住龟兹,止于新寺。后于寺侧故宫中。初得《放光经》,始就披读(遇魔)后于雀梨大寺读大乘经(遇魔) 复闻(魔声)停住二年,广诵大乘经论 停住二年,广诵大乘经论后往罽宾,为其师槃头达多具说一乘妙义 俄而大师盘头达多不远而至西域诸国伏什神俊,咸共崇仰 西域诸国,咸伏什神俊
很明显,两书在“鸠摩罗什传”内容的基本脉络是别无二致的,对于“鸠摩罗什受学《十诵律》”的时间,也都是在返回龟兹之后,只是二者在师从人物上有所分歧。①关于鸠摩罗什师从须利耶苏摩学习大乘的时间,以及关于鸠摩罗什折服盘头达多的地点,二书记载也是有差异的。信息有限,无法做进一步分析,殊为遗憾。《高僧传》在其“佛陀耶舍传”中记载鸠摩罗什“从佛陀耶舍受学,甚相尊敬。什既随母还龟兹,耶舍留止”,但未明言受学内容。
显然,《高僧传》在编纂时,一是在“鸠摩罗什传”中将罗什受学《十诵律》的师从人物由“佛陀耶舍”改成了“卑摩罗叉”,二是将“佛陀耶舍传”中鸠摩罗什从佛陀耶舍受学的内容也做了删除。
这样一来,本文就必须将考察焦点投射至卑摩罗叉了。卑摩罗叉,何许人也?
二、《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对卑摩罗叉、佛陀耶舍相关活动的具体记载
正如前引黄先炳文所述,我们从《高僧传》“卑摩罗叉传”中就能得知,卑摩罗叉在龟兹以“弘阐律藏”闻名,“四方学者競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出三藏记集》虽然没有“卑摩罗叉传”,但在“鸠摩罗什传”里也写道:“初,什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与《高僧传》不明言鸠摩罗什从佛陀耶舍受学内容所不同的是,《出三藏记集》明确地说鸠摩罗什在龟兹随卑摩罗叉学习过律。
随着我国汽车市场的不断发展,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攀升,汽车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为汽车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势必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
想要让学生的家长不担心学生的学习成绩,那么就需要教师能够先给学生安排合理的时间,要让学生学会合理地分配自己的业余时间,能够让学生学习足球技巧和学习理论知识两个都不耽误,并让学生在成绩稳定的情况下,和学生家长协商,适当参加足球活动,并让学生家长能正确地看待体育教学,了解体育教学的重要意义。还可以向学生家长介绍足球的价值,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培养学生之间的团结力,是学生发展“德、智、体、美、劳”方面的重要基础。
我们现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关于卑摩罗叉和佛陀耶舍二人的相关记载列表如下:①《出三藏记集》有“鸠摩罗什传”和“佛陀耶舍传”,而无“卑摩罗叉传”。《高僧传》三传都有,皆在卷二“译经中”里,“鸠摩罗什传”第一,“卑摩罗叉传”第四,“佛陀耶舍传”第五。
《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卑摩罗叉罽宾律师卑摩罗叉来游长安,罗什先在西域,从其受律(“萨婆多部《十诵律》六十一卷”)卑摩罗叉……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競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卑摩罗叉传”)【A】(鸠摩罗什) 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鸠摩罗什传”)初,什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鸠摩罗什传”)初,什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鸠摩罗什传”)佛陀耶舍【B】 佛陀耶舍……后至沙勒国……待遇隆厚。罗什后至,从其受学《阿毗昙》《十诵律》,甚相尊敬(“佛陀耶舍传”)罗什后至(沙勒国),复从舍受学,甚相尊敬(“佛陀耶舍传”)【C】 及还龟兹,名盖诸国……后从佛陀耶舍学《十诵律》(“鸠摩罗什传”)
从上表,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除了“ 《十诵律》受学师从”之外,其他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假如我们将【C】 移至【A】,并将【B】的《阿毗昙》与《十诵律》删去,《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关于卑摩罗叉和佛陀耶舍二人的记载,也就基本一致了。
收付实现制,又称“现收现付制”或“现金制”,指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为标志来确定本期收入和支出的会计核算基础。凡在当期实际收到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均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支出;凡是不属于当期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均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支出。
学界已认定《高僧传》相关僧传源自于《出三藏记集》,因此可以说,晚出的《高僧传》在叙述鸠摩罗什受学师从时,将佛陀耶舍改成了卑摩罗叉。退一步说,《高僧传》相关僧传即便不是直接出自《出三藏记集》,二者也有着共同的材料来源。也就是说,《高僧传》不大可能是因为“不为《出三藏记集》所知的”史料来源而进行的更改。①还有一种可能是,《高僧传》的更改承袭于《名僧传》,但由于《名僧传》无存,《名僧传抄》又没有相关内容,因此只能存疑。
上面提到,伯希和、鎌田茂雄与黄先炳对鸠摩罗什《十诵律》受学师从做过考察。伯希和虽有分析但并未得出明确结论,实际上相当于调和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关于鸠摩罗什《十诵律》受学师从记载的矛盾,推测“鸠摩罗什很可能先是从佛陀耶舍进修,而后中断并改从卑摩罗叉受业。”③伯希和:《关于鸠摩罗什札记》,《西域文史》,第7~9页。鎌田茂雄也分析了这个问题,认为应当是师从卑摩罗叉。④鎌田茂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234、235页;中文译本在第274、275页。
那么,为什么在“ 《十诵律》受学师从”这个问题上,《高僧传》不仅不像其他内容一样直接采用《出三藏记集》“受学于佛陀耶舍”的记载,而是要另起炉灶,改作“受学于卑摩罗叉”呢?!②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佛陀耶舍和卑摩罗叉在二书中的分量似乎大有不同,相对于《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明显增大了卑摩罗叉的分量。要考察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卑摩罗叉、佛陀耶舍二人后来在长安的活动。
三、卑摩罗叉、佛陀耶舍在长安的活动
《出三藏记集》虽未明言罗什从卑摩罗叉受的是何律,但这段文字置于论《十诵律》传来汉地的因缘,所以当是指《十诵律》无疑。《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所载之汉地外国律师名单中,鸠摩罗什之名字即排在卑摩罗叉之后,则更说明鸠摩罗什传《十诵律》乃师承于卑摩罗叉。《高僧传》卑摩罗叉传亦载罗什曾随之受律事,时传主‘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竟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至于佛陀耶舍,《高僧传》载他亦是罗什之师,曾应姚兴之请,诵出《昙无德律》,并于稍后译为汉语。这与《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录》‘昙无德《四分律》’ 条所载一致。《十诵律》与《四分律》各有师承,《出三藏记集》经录所言甚明,独译经师列传中混淆。这种混淆尚非独见于鸠摩罗什传,佛陀耶舍传亦然,卷十四本传云:‘ (耶舍) 后至沙勒国,……罗什后至,从其受学《阿毗昙》《十诵律》,甚相尊敬。’ 慧皎亦察觉此误,所以《高僧传》佛陀耶舍传仅载‘罗什后至,复从舍受学,甚相尊敬’,不载所学包括《十诵律》。”①黄先炳:《〈高僧传〉 研究》,第84页。黄文此后继续写道:“前文已述僧祐是律师,以弘演《十诵律》为业,按理他记载《十诵律》的师承当不会有差误,此或说明译经师列传另有执笔人。”
1.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与处理。采用均数及标准差及配对样本均数的t检验,计算PBL教学前后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差异是否有显著性(P<0.05)。采用非参数检验(秩和检验),计算PBL教学前后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比例情况是否有显著性差异(P<0.05)。
鸠摩罗什于弘始三年抵达长安,开始译经活动。其时,“经法随传,律藏未阐”。继鸠摩罗什之后,罽宾人弗若多罗也抵达长安。弗若多罗备通三藏,而以戒节见称,专精《十诵律》,鸠摩罗什对他颇为推崇,十分尊敬。弘始六年(404年) 十月十七日,始译《十诵律》,由弗若多罗诵读梵语,鸠摩罗什译成华文。然而不幸地是,翻译工作刚刚进展至三分之二①《高僧传》“弗若多罗传”,第61页。不过《高僧传》“昙摩流支传”慧远致昙摩流支书写作:“ 《十诵》之中,文始过半,多罗早丧。”,《出三藏记集》“萨婆多部《十诵律》六十一卷”作:“始得二分,馀未及竟而多罗亡”,同卷庐山慧远致昙摩流支书也说“始备其二,多罗早丧”。或许弗若多罗诵《十诵律》梵文,鸠摩罗什译为华语,只是过半,尚未及三分之二。,弗若多罗患病,奄然离世。弘始七年(405年) 秋,以律藏闻名的西域僧昙摩流支抵达长安。庐山僧慧远知晓昙摩流支擅律,寄书于他,希望他能继续弗若多罗未竟之业。昙摩流支随即与鸠摩罗什合作开展并完成了《十诵律》的翻译。不过,鸠摩罗什虽然觉得译文繁冗,不够完善,却未及删修,以至有临终之憾。《十诵律》译本的完善,最终是卑摩罗叉完成的。
在氢医学蓬勃发展的近十年,氢气产品层出不穷、种类繁多,按照氢分子应用于人体的途径,可分为饮用氢水、吸氢气、氢水沐浴、氢食品以及氢化妆品等几大类别。富氢水是使用最普遍、获取途径最方便、效果非常明显的氢产品。富氢水的生成方法目前基本有物理法、化学法和电化学分解法。
《出三藏记集》没有卑摩罗叉的传记。《高僧传》本传记载,卑摩罗叉是罽宾人,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競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后来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大弘经藏”,又欲使“毗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前往长安。佛教经典分为“三藏”:经、律、论。毗尼,为梵语,就是“律”的意思。显然,在《高僧传》中,卑摩罗叉不论是在龟兹,还是前往长安,都是以弘扬律藏为己任的。而且,卑摩罗叉“弘律”,是与鸠摩罗什“译经”相对应的。卑摩罗叉于弘始八年(406年) 抵达长安,后于鸠摩罗什去世之后离开,出游关东,最后留驻寿春石涧寺。《高僧传》云其在此“律众云聚,盛阐毗尼”。
关于卑摩罗叉在长安之时的情况,《高僧传》则没有明确记载,也没有关于卑摩罗叉在长安与鸠摩罗什合作译经的直接记载。但是《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所译《十诵律》为五十八卷,最后一诵是关于“明受戒法”的,称为《善诵》。卑摩罗叉离开长安之后,将《十诵律》携出,在石涧寺重校将其扩为六十一卷,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意即《律诵》。②《出三藏记集》“萨婆多部《十诵律》六十一卷”(第117页):“罗叉後自秦适晋,住寿春石涧寺,重校《十诵律》本,名品遂正,分为六十一卷。”梁启超先在《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篇中说卑摩罗叉在寿春石涧寺“补译最后一诵”(第156页),继在同书“佛典之翻译”篇中说是“增改最后一诵”(第239页),后在同书“说四阿含”篇中表述为“罗叉续成罗什之十诵律”(第271页)。后二者意思差不多,前者可能为一时之误。随后,卑摩罗叉前往江陵辛寺,夏坐期间开讲《十诵律》,一时求理者聚集如林。《高僧传》盛赞道,“律藏大弘,(卑摩罗) 叉之力也!”在叙述卑摩罗叉于江陵辛寺开讲《十诵律》时,本传用了“既通汉言”这么一句表述。“既”字表明,卑摩罗叉此时已经通晓汉语,能够在开讲中“善相领纳,无作妙本,大阐当时”。这是在将鸠摩罗什所译五十八卷本《十诵律》增益至六十一卷之后。也就是说,在鸠摩罗什去世之前,卑摩罗叉很可能并不通晓汉语,因而无法协助鸠摩罗什删修《十诵律》。
根据《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佛陀耶舍传”记载,鸠摩罗什听说佛陀耶舍已至姑臧,劝姚兴迎之,未果。在姚兴命其译经时,鸠摩罗什趁机再次进言姚兴邀请佛陀耶舍。鸠摩罗什说:本人虽然能通诵经文,但并不善于把握其中的义理,弘宣法教,需要文义圆通,只有佛陀耶舍能够深刻理解经义,每一句话再三审度其详,然后下笔,使得细微之处也不致忽略,这样才能流传千载,信仰不绝。这回姚兴听从了鸠摩罗什的建议。
佛陀耶舍抵达长安之后,先是翻译《十住经》(与鸠摩罗什一道),然后于弘始十二年(410年) 至十四年(412年) 译出《昙无德律》(即《四分律》) 四十卷,十五年(413年) 译出《长阿含经》,由佛陀耶舍诵出,凉州僧竺佛念口译,僧道含笔书。①《出三藏记集》卷三“昙无德四分律”,第118页。关于竺佛念与佛陀耶舍共译《四分律》的问题,下文考证《名僧传抄》有记载可资佐证。佛陀耶舍善解《毗婆沙》,号大毗婆沙。鸠摩罗什去世之后,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五年(413年) 离开长安,返回罽宾。
关于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译经的记载还见于《名僧传抄》。该书卷第十八(第九页下) 有一段记载,一共5 句,②宝唱撰,宗性抄,《名僧传抄》,《卐续藏经》,第134 册,第18页。涉及五个时间节点,其中第2、3 句与鸠摩罗什和佛陀耶舍有关。
在本文中,作者在探讨接受理论视角下看文化缺省的翻译策略时,主要考虑了两个主要方面,分别为采用文化置换让读者体会到感同身受,以及采用保持异国情调让读者进行一次思想漫步,能够在书本中体会到异域风情。两个方面下又分别有满足其需求的翻译方法来进行翻译。杨先生更注重行文的流畅和自如的表达,而荣先生则在处理文化缺省时更偏向使用一些异化的手法或是通过直接介绍给读者本文化中没有的文化现象来丰富读者的认知。两人的译本各有千秋。
1 义熙二年 沙门法显以义熙二年从外国还,得《僧祇律》《弥沙塞律》二部,止获胡文,未得宣译2 义熙九年 有弗若多罗至长安与童寿共出《十诵律》3 到十二年 佛陀邪舍与佛共出《四分律》4 其年 佛驮跋陀又出《僧祇律》5 宋景平元年 沙门佛驮什与智胜共出《五分律》
为论述方便,我们不按数字顺序进行分析。先看第5 句“宋景平元年(423年),沙门佛驮什与智胜共出《五分律》。”这一句在《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都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此处没有问题,五分律即“弥沙塞律”。③《出三藏记集》卷三“弥沙塞律”,第120页。《高僧传》卷三“译经下·佛驮什传”,第96页。
式中,[A]是一个N阶矩阵,完全由传输系统的散射系数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传输系统有多个正特征值,式(3)中最大的特征值对应着最大的传输效率,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at]就是传输天线阵列最优的激励分布。
在1933年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1933年《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一文后,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开始着重“综合的工作”,撰写《唐诗杂论》,以诗论诗,相继发表了《类书与诗》《贾岛》《宫体诗的自赎》《四杰》和《孟浩然》五篇文章,依朱自清说:“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9]闻一多在清代朴学考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条理唐代诗歌,他的《唐诗杂论》可谓是“顶峰上的顶峰”。
再看第4 句“其年,佛驮跋陀又出《僧祇律》。”此处“其年”当为前文之“十二年”,从上下文意来看,也就是“义熙十二年(416年)”。法显于义熙九年(413年)夏“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⑦《法显传校注》,第148页。《出三藏记集》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罗,于道场寺译出《泥洹》、《摩诃僧祇律》……”⑧《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第576页。《高僧传》记载基本相同,但未写明《摩诃僧祇律》的翻译时间。⑨《高僧传》卷三“法显传”,第90页;卷二《佛驮跋陀罗传》,第73页,卷三《法显传》,第90页。不过从上文《出三藏记集》卷三《婆粗富罗律记》、《摩诃僧祇律私记》记载可知,《名僧传抄》此处记载没有问题。
再看第3 句“到十二年,佛陀耶舍与佛共出《四分律》。”按照文意,似乎此处“十二年”为“义熙十二年”(416年)。然而,从《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我们已经得知,佛陀耶舍翻译《四分律》的时间是弘始十二年(410年),至弘始十四年(412年) 完毕。也就是说,《名僧传抄》中的“到十二年佛陀邪舍……出《四分律》”中的“十二年”当为“弘始十二年”,而非从上文文意延伸出来的“义熙十二年”。另,文中“与佛陀邪舍共出《四分律》”的有一“佛”字,此处当为“竺佛念”。据《出三藏记集》卷三“昙无德四分律”、卷十四“佛陀耶舍传”,《高僧传》卷二“佛陀耶舍传”所载,佛陀耶舍译《四分律》及《长阿含》时,系由佛念译为秦言。恐佛陀耶舍并不通晓华语。佛念即竺佛念,《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均有传,与佛陀耶舍共译《四分律》与《长阿含》之前,曾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 与昙摩难提共译出《中阿含》与《增一阿含》。弘始十五年(413年),佛陀耶舍译出《长阿含》之后,即“辞还外国”,返回罽宾。
每年汛期来临之前,对县及乡镇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人员、责任人、监测人员、预警人员、村负责人进行山洪灾害专业知识培训,明确各自职责,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意识,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应急反应和指挥组织能力,熟悉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的运行操作流程,确保指挥系统正常、有效运转。培训分期分批举办,培训主要内容为山洪灾害成因及特点、山洪灾害防御形势、山洪灾害防御基本知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运行操作流程等。
最后看第2 句“义熙九年,有弗若多罗至长安与童寿共出《十诵律》。”义熙九年,即弘始十五年(413年),此年当为争议中的鸠摩罗什去世的时间。前文已知,弗若多罗去世时间为弘始六年(404年) 十月之后,弘始七年(405年) 秋昙摩流支抵达关中之前。在弗若多罗去世后,与鸠摩罗什续译《十诵律》的是昙摩流支。译毕未及削删,鸠摩罗什既而去世。显然,《名僧传抄》此处与童寿共译出《十诵律》的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是弗若多罗,而应是昙摩流支。然而新的问题是,如果说弗若多罗与鸠摩罗什只用了顶多一年的时间,就将《十诵律》的翻译完成了一半有余,而之后的不到一半,昙摩流支与鸠摩罗什却花了八年时间(以鸠摩罗什卒于弘始十五年计算)! 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如果类似第5 句那样,此处义熙九年也是弘始九年(407年) 之误的话,文意或可通顺。昙摩流支于弘始七年秋抵达长安,经过与远在庐山的慧远书信往来之后,开始着手续译《十诵律》,并于弘始九年译毕。卑摩罗叉抵达长安之后,虽未直接参与《十诵律》的翻译工作,但在鸠摩罗什去世之后,对《十诵律》进行了完善,了却了鸠摩罗什的临终遗憾。
至此,我们用表格将《名僧传抄》这五句话在不打乱语序的情况下,稍做处理,意思就明了了。
南朝译经 南朝年号 北朝年号 北朝译经沙门法显从外国还(都),得《僧祇律》《弥沙塞律》二部,止获胡文,未得宣译义熙 (十) 二年(416年)1 2 弘始九年(407年)弗若多罗 (昙摩流支)至长安,与童寿共出《十诵律》
续表
南朝译经 南朝年号 北朝年号 北朝译经3 弘始十二年(410年)佛陀耶舍与佛 (念) 共出《四分律》佛驮跋陀出《僧祇律》其年(义熙十二年)4沙门佛驮什与智胜共出《五分律》宋景平元年(423年)5
《名僧传抄》这五句话所在目录题为“律师”,从上下文来看,也是介绍律部源流及传至汉地的翻译情况。五句之中,三句为南朝译经活动,两句为北朝译经活动。此段文字恐为源自《出三藏记集》的各种译律信息之杂糅,同时也将时间给搞错乱了。
从卑摩罗叉、佛陀耶舍在长安的活动来看,卑摩罗叉参与过《十诵律》的翻译,而佛陀耶舍则无。这个意味,就已经相当明显了。①陈寅恪在此处案云:“什公与弗若多罗、昙摩流支所译为十诵律,而耶舍所译为四分律……似仍应作‘卑摩’ 而不作‘耶舍’ 为是”。《读书札记三集》,第49、50页。作者按:陈氏札记恐误。
四、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心性相近,不类卑摩罗叉
《出三藏记集》没有“卑摩罗叉传”。《高僧传》卷二中,“鸠摩罗什传”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和“卑摩罗叉”三传。这三传传主均“专精律藏”。②《名僧传》目录,佛陀耶舍与鸠摩罗什分列“卷二‘外国法师’”第一、二,而卑摩罗叉、昙摩流支则分列“卷十八‘律师’”第一、二,弗若多罗位于“卷十九‘外国禅师’”第一。《名僧传》如此分类,鸠摩罗什、佛陀耶舍与其他三人之差异,可见一斑。“卑摩罗叉传”之后,才是“佛陀耶舍传”。而且,《高僧传》对“佛陀耶舍”的评价,与前三位差别甚大! 我们可以再做比较看看。
弗若多罗:“少出家,以戒节见称,备通三藏,而专精《十诵律》部。”
昙摩流支:“弃家入道,偏以律藏驰名。”
卑摩罗叉:“沉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节成务。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倾之,闻什在长安大弘经藏,欲使毗尼胜品,复洽东国。”
佛陀耶舍:“年十三出家……至年十五,诵经日得二三万言……至年十九,诵大小乘经数百万言。然性度简傲,颇以知见自处,谓少堪己师者,故不为诸僧所重……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读诵为务,手不释牒。”
从《高僧传》对四人的评价就能看出,“专精律藏”的三位,都有“克己坚韧,律己修身”的性格,而佛陀耶舍则偏向于“智慧超群、博闻强记、风流倜傥、不拘一格”。佛陀耶舍的情况,不类此律师三人,而与鸠摩罗什相近!①陆扬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或许是论文研究主旨差异,他在此处并未展开。《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第4 节“神童鸠摩罗什”:“在僧祐与慧皎笔下,佛陀耶舍的生平除了出生没那么神奇之外,可以说与鸠摩罗什十分相像。”(《中国学术》第23 辑,第51页)。此后,在该文第10 节“作为史学作品的《鸠摩罗什传》”,陆扬再次提出:“除了在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的那些例子外,我们如果对照玄畅所撰的〈诃梨跋摩传〉中的《成实论》作者诃梨跋摩的形象,或者《付法藏因缘传》中马鸣的形象,就会发现僧祐、慧皎笔下的鸠摩罗什或多或少有这两位佛教智者的影像。”(《中国学术》第23 辑,第87、88页)。不过陆扬在此处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鸠摩罗什传”的自身意义以及传记作者的写作意图,而非进行史学考证。
《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在其本传开篇,都突出讲述了佛陀耶舍的一段经历。佛陀耶舍本出身“外道”世家,出家后,常随师远行,于旷野遭遇老虎,师父意欲躲避,而耶舍却颇有胆识:“此虎已饱,必不侵入,俄而虎去。”这与鸠摩罗什在龟兹新寺读经遇魔的遭遇十分相似。“(鸠摩罗什) 初得《放光经》。始就披读。魔来蔽文,唯见空牒。什知魔所为,誓心踰固。魔去字显,仍习诵之。复闻空中声曰:‘汝是智人,何用读此。’ 什曰:‘汝是小魔,宜时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转也。’”都是魔障,只不过一个是老虎,一个小魔。而与佛陀耶舍“虎去前行,果见余残,师密异之”相对应。鸠摩罗什也有折服其师盘头达多,其师“礼什为师”的故事。
这种与佛陀耶舍相似的“灵异”故事,在“鸠摩罗什传”还能找到很多。比如,佛陀耶舍初至沙勒国时,本不受过往欢迎,但太子称之“法子”,遂留宫中供养,待遇隆厚。而鸠摩罗什尚在胎中时,其母忽自通天竺语之外,“难问之辞,必穷渊致,众咸叹之”。罗汉达摩瞿沙曰:“此必怀智子”。当然,鸠摩罗什的神迹更多,更为神通广大。②在龟兹有吕光破龟兹获鸠摩罗什回师山下夜遇大雨,在凉州有吕光中路得福地、姑臧大风奸叛自定、吕篡讨段业必败、吕篡不斩胡奴头则胡奴斩吕篡头、中书监病死,在长安则有发“经信则舌不燋烂”誓等。汤用彤对鸠摩罗什在龟兹和凉州时“阴阳术数,无所不验”的六事有归纳。《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205页。
再比如,佛陀耶舍“至年十五,诵经日得二三万言……至年十九,诵大小乘经数百万言。”而鸠摩罗什同样“年七岁,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
更有,二人都擅用法术。《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记载:当鸠摩罗什邀请佛陀耶舍前往姑臧,而其为龟兹国人滞留不得前往,佛陀耶舍遂取清水一钵,以药投水中,念咒语数十言,与弟子洗足,即夜行数百里,龟兹国人追赶不及。鸠摩罗什则有:后秦姚兴逼其别有家室之后,诸僧多有效仿。鸠摩罗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这段故事前两书未载,但见诸《晋书·艺术传》。③《晋书·艺术传》“鸠摩罗什传”,第2502页。
如果说,上述两人身怀特异功能的故事过于离谱,那么关于二人心性、旨趣相类的记载,则真实得多。鸠摩罗什在沙勒国时,“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围陀舍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厉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什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伦匹者。”佛陀耶舍则是“性度简傲,颇以知见自处,谓少堪己师者,故不为诸僧所重。但美仪止,善谈笑,见者忘其深恨。年及受戒,莫为临坛,所以向立之岁,尤为沙弥。乃从其舅学五明诸论,世间法术,多所通习。”二者何其相似乃尔!①纪赟在《慧皎〈高僧传〉 研究》中提到,北朝佛教史传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对而言,南朝则十分发达,而其中的一大特点是,别传大量出现以及别传中掺杂了大量荒诞不经的传说,作者也并不在意是否真实可靠。同书第六章为“ 《梁传》中的神异与法术研究”,对《高僧传》中大量乃至反复出现的因果报应、灵异、母子神异、巫术、咒语做了分析。《高僧传》中关于“鸠摩罗什”和“佛陀耶舍”性情和灵异方面类似甚至雷同的记载,与佛教传记同史学传记在编纂目的上有着根本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得考虑,《高僧传》对同一流派或同一源流的高僧,采取了类型化的处理,这既是“人以群分”的客观结果,恐怕也使作者有意为之。纪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
特点 佛陀耶舍 鸠摩罗什博闻强记年十三出家……至年十五,诵经日得二三万言……至年十九,诵大小乘经数百万言。……恒以读诵为务,手不释牒年七岁,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不惧魔障本出身“外道”世家,出家后,常随师远行,于旷野遭遇老虎,师父意欲躲避,而耶舍却颇有胆识:“此虎已饱,必不侵入,俄而虎去。”(鸠摩罗什) 初得《放光经》。“始就披读。魔来蔽文,唯见空牒。什知魔所为,誓心踰固。魔去字显,仍习诵之。复闻空中声曰:‘汝是智人,何用读此。’ 什曰:‘汝是小魔,宜时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转也。’”折服其师 “虎去前行,果见余残,师密异之”折服其师盘头达多,其师“礼什为师”天生异象佛陀耶舍初至沙勒国时,本不受过往欢迎,但太子称之“法子”,遂留宫中供养,待遇隆厚鸠摩罗什尚在胎中时,其母忽自通天竺语之外,“难问之辞,必穷渊致,众咸叹之”。罗汉达摩瞿沙曰:“此必怀智子”傲视群侪性度简傲,颇以知见自处,谓少堪己师者,故不为诸僧所重。但美仪止,善谈笑,见者忘其深恨。什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伦匹者。为性率达不厉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多习外道年及受戒(二十七岁才受戒),莫为临坛,所以向立之岁,尤为沙弥,乃从其舅学五明诸论,世间法术,多所通习。在沙勒国时,“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围陀舍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
续表
特点 佛陀耶舍 鸠摩罗什擅使法术当鸠摩罗什邀请佛陀耶舍前往姑臧,而其为龟兹国人滞留不得前往,佛陀耶舍遂取清水一钵,以药投水中,念咒语数十言,与弟子洗足,即夜行数百里,龟兹国人追赶不及。在龟兹有吕光破龟兹获鸠摩罗什回师山下夜遇大雨,在凉州有吕光中路得福地、姑臧大风奸叛自定、吕篡讨段业必败、吕篡不斩胡奴头则胡奴斩吕篡头、中书监病死,在长安则有发“经信则舌不燋烂”誓等。(汤用彤对鸠摩罗什在龟兹和凉州时“阴阳术数,无所不验”的六事有归纳)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归纳出,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有以上“博闻强记”、“不惧魔障”、“折服其师”、“天生异象”、“傲视群侪”、“多习外道”、“擅使法术”等七大共同点,可见二人更多的是亦师亦友,性情相合,惺惺相惜。①汤用彤也持类似看法,《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200页。
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与其说鸠摩罗什受学《十诵律》师从佛陀耶舍,莫若说师从卑摩罗叉。另一方面,《高僧传》对于鸠摩罗什、佛陀耶舍,以及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五人传记的内容记述和个人评价,也是《高僧传》作者慧皎本人对这五人思想观念的体现。虽然《高僧传》取材于《出三藏记集》,但在涉及鸠摩罗什律学师承的问题上,慧皎并不认可《出三藏记集》的记载,无法认同鸠摩罗什受学《十诵律》是师从一个性情和修为都与之颇为相似的佛陀耶舍,更何况《出三藏记集》自己关于鸠摩罗什受学《十诵律》的时间就自相矛盾,因而将其师从改换为一位戒律修持更为令人敬仰的卑摩罗叉。②正如前文已提及的,出《出三藏记集》之外,《高僧传》的史源还可能包括《名僧传》,因而也就不能排除《名僧传》就已做此修改而为《高僧传》所承袭的可能。
余 论
一方面,从《出三藏记集》关于鸠摩罗什受学《十诵律》师从佛陀耶舍的记载,有时间上的自相矛盾之处这一点来看,另一方面,也从佛陀耶舍、卑摩罗叉各自在长安活动,佛陀耶舍与卑摩罗叉二人的各自所译经卷,以及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心性相近而不类卑摩罗叉等等情况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鸠摩罗什受学《十诵律》师从卑摩罗叉而非佛陀耶舍判断,是可靠的。
当然,鸠摩罗什在沙勒国也跟从佛陀耶舍学习过。《出三藏记集》“佛陀耶舍传”记载:“罗什后至,从其受学《阿毗昙》……甚相尊敬。”后来,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曾发感喟:“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翮于此,将何所论!”迦旃延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称“议论第一”。鸠摩罗什的自信,颇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气。佛陀耶舍同样擅论,“善解‘毗婆沙’ ……既为罗什之师,亦称‘大毗婆沙’”。或可说鸠摩罗什从佛陀耶舍所学当为论藏,即“阿毗昙”。
总而言之,在小学教育中针对科学课堂进行创新教学,对于学生开发学生大脑,提升综合素质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教师要注重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快乐高效的学习科学。
鸠摩罗什与佛陀耶舍,性虽相近,习却相远。佛陀耶舍性度简傲、通习外道,俱在二十七岁受具足戒之前,之后未见有大噩。而鸠摩罗什在二十岁受具足戒之后,却遭逢两次被逼破戒。①两次被逼破戒事,《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本传有详细记载。此外还有一次似乎是主动犯戒,仅见诸《晋书·艺术传》本传(第2501、2052页),不过未知史料来源。以至鸠摩罗什自叹:虽新经、诸论多所传出,却“累业障深”。而佛陀耶舍也在得知他被逼以妾媵之后,感叹:“罗什如好绵,何可使入棘中乎!”②此一感叹,无法得出“对其行为无比反感”的判断。伯希和:《关于鸠摩罗什札记》,《西域文史》第十辑,第12、13页。
对于鸠摩罗什,《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本传在其早年就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当鸠摩罗什母亲带着他从罽宾返回龟兹,途经月氏北山时。有一罗汉见而异之。谓其母曰:“常当守护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正可才明俊义法师而已。”优波掘多普渡众生,而法师只能解经说法,信仰大乘佛教的僧祐和慧皎两位作者采用这个典故,恐怕是因为对于大乘佛教信仰而言,优波掘多与法师堪称云泥之别吧。
“至三十五不破戒”这个伏笔,不仅是鸠摩罗什命运的伏笔,也是后人研究鸠摩罗什的魔碍。鸠摩罗什生年未见诸史籍,卒年颇有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鸠摩罗什第一次破戒,在三十五岁之前还是之后”的理解不同。反过来,这一理解又被用于论证鸠摩罗什的卒年。有人认为,鸠摩罗什大弘经藏,即为普渡众生,即为优波掘多,其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为吕光所逼受龟兹王女第一次破戒,应该就是在三十五岁之后。
《名僧传抄》附“名僧传说处·第二”也有一条关于鸠摩罗什破戒的记载:“梦释迦如来以手摩罗什顶曰:“汝起欲想,即土(生) 悔心”。可惜《名僧传》已佚,只余下宗性摘抄的寥寥数语,也就无从得见其详。③宝唱撰,宗性抄,《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134 册,第27、28页) 此处记有七条说处:1.罗什见《中》《百》二论始悟大乘事;2.梦释迦如来以手摩罗什顶曰:“汝起欲想,即土(生) 悔心事;3.罗什三藏译《法华》等经论三十八部二百九十四卷事;4.汉土三千徒众从罗什法事;5.罗什临终众僧告别曰事;6.罗什烧身之后舌犹存事;7.《涅槃》后分宋地无缘事。第7 事并非宗性抄自“鸠摩罗什传”,而是抄自“昙无忏(谶) 传”。《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本传均有相关记载。“道场寺慧观志欲重求后品(《涅槃》后分) ……宋元嘉中,启文帝资遣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遂卒。普临终叹曰:‘《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矣!’”陆扬:《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中国学术》第23 辑,第38页,注17;《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昙无谶传”,第580页;《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第80页。
作者简介:姚胜,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本文获黄先炳博士惠赠博士论文电子版,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标签:佛陀论文; 高僧论文; 长安论文; 佛教论文; 二年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佛学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