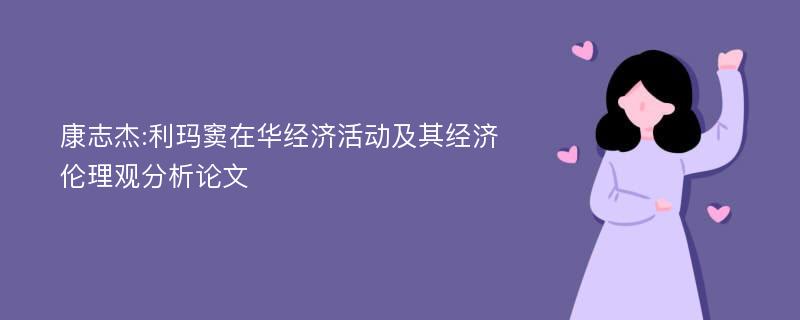
摘要: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以及所做的贡献,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关于利玛窦在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伦理观的研究,学界所论不多。利玛窦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其生活状况、经济活动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秉持“量入为出”“谨慎地消费每一个铜板”的原则,探索出适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支出原则。他“受俸不做官”,开传教士供职朝廷之先河,体现了“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传教理念。
关键词:利玛窦;经济活动;经济伦理观
耶稣会士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及历史地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但是,作为一名传教士,利玛窦是天主教来华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其在华活动,除了广交士大夫朋友,“以学术辅传教”,还忙于教务活动,其中购置教产是教务活动中的重中之重。天主教的经济活动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玛窦一直谨慎处理。本文主要对利玛窦的经济活动、经济伦理观进行了分析,例如分析其在财务支出中秉持“量入为出”“谨慎地消费每一个铜板”的原则,在不动产交易中按照民间规则订立契约,并依法交纳房税的做法,等等,由此展现出利玛窦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利玛窦及其同伴面临传教经费短缺的难题
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士罗明坚(P.Mich.Ruggier)、利玛窦(P.Matth.Ricci)进入中国内陆,他们“领到葡王的津贴,乘坐葡国的商船,先在中国边境的葡萄城内(澳门)暂住,由葡商引导来到中国;以后又由广州进入肇庆”[1]221。
深入内陆而逐渐远离澳门的形势,导致内地传教士领取经费十分困难。1582年之前,罗明坚已先后四次潜入内陆打探,经费花费不少;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正准备由广州赴肇庆,遇葡国商船在台湾海峡遭巨风沉海,路费难以凑齐,幸得澳门——葡萄牙富翁威加(Caspar Viegas)捐资,两人才于1583年9月10日抵达肇庆[2]。可见,早期进入内陆的耶稣会士在资金不足时,只能向澳门的葡萄牙人求助,“他们的命运紧紧与葡商相联”[1]221。
弹丸之地的澳门是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的通道与跳板,但两地(澳门与大陆)传教士的生存环境完全无法同日而语:长驻澳门的神职人员能够轻松得到传教经费及生活津贴,优渥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潜心学习语言①如罗明坚在澳门学习中文时曾得到官员的周济,[法]裴化行(H.Bernard).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M].萧浚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88。记曰:(罗明坚初到澳门)“人人争先恐后地来看西僧……竟有低级的官员到罗明坚那里去拜会,并且给与金钱的周济。”罗明坚在澳门时还曾得到一位意人的三百元葡国银洋资助(详见上书199页注释35)。;而深入腹地的传教士则没有这种“好运”,他们的资金仍然需要通过澳门获得,但显然不如驻澳门或毗邻澳门的沿海城镇那样便捷,此种态势透过利玛窦发往欧洲的信件(1585年)可略见端倪:
这个(肇庆)会院计有12口人,其中包括佣人和学生,后者帮助我们学习语言。一切生活费都由葡萄牙商人奉献我们,印度亚欧总督甚至葡萄牙国王都照顾我们[3]77。
本文研究EP去除厚度的控制方法,实现了超导铌腔表面去除厚度的实时监测,避免了化学抛光速率随反应时间增加而降低,从而去除厚度不能精确控制的缺点。这对以后的试验和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导,也为后期超导铌腔渗氮后的EP操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房屋是人类生存的基体与寄托,西方传教士一踏入中土,首要任务是购置房产,或用于传教,或用于居住,这类房产的主要功能是“自用”,如利玛窦、罗明坚定居广东肇庆后,第一要务就是购地建房,地基选好,但经费短绌,罗明坚只好折回澳门求援。而欧洲的商船未归,挨到次年春,罗明坚才携款重返肇庆,直到两年后,教堂修建工程才最终在肇庆东关崇宁塔旁峻工。这座中国内地第一座教堂,利玛窦给了一个颇具东方色彩的名字——“仙花寺”①“仙花寺”后被地方官府强夺,利玛窦以“易地而居”的方式,获准将传教点迁到韶州。。但好景不长,罗明坚、利玛窦花费重资历尽千辛万苦修建起来的教堂及会院,被两广总督刘继文侵占。罗明坚无奈又折回澳门,利玛窦于1589年北上韶州,继续其福传事业。
利玛窦北上之后,更加谨慎行事,他把带来的三棱镜、地图、自鸣钟、天象仪器以及各种奇巧物品摆出,任人观看,并将所带贵重物品,赠送给相关的地方官员。有关修建教堂事宜方面,在教堂的规模、样式等方面,尽量不太出格。万历十七年(1589年),利玛窦在韶州建教堂及住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南昌以六十两银买房做教堂;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利玛窦的同事李玛诺(P.Emman.Diaz)又以一百两银买一较大的房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利玛窦等在南京建教堂,澳门耶稣会为此筹集了约九百两银子,作为购买南京房屋及北上的费用②《利玛窦资料》,第2卷,第91页,注2;转引自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利玛窦三次到南京,前两次利玛窦为短暂逗留。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利玛窦第三次到南京,住城南承恩寺,随后买下了城西户部官员刘斗墟的宅院,并在厅中建一个祭台,奉天主圣像于其中,这是南京最初的天主教堂。。他在南昌发出一封信函,述说了教会的经济境况:
我们必须要获得总督或帝王每年一次的汇款,有它,我们才能维持生活,因为,直到现在他所给我们的不够支付,这是神父所知道的,勉强地只足以维持韶州会院我们四位会士的生活;现在又增加了这个新会院,又添了两个人,神父就很能了解我们需要的是多少了,还有,我们必须在新会院里建造圣堂[3]164。
这封救援函是利玛窦向驻澳门的同会孟三德发出的。随着北上进程加深,传教路线的延长,利玛窦深切感到,从澳门获取资金的艰辛,一年一次的领取经费,常常让内地传教士陷入窘境。受财力限制,利玛窦不得不买房充作教堂及会院,他想亲自建造一座像样的教堂,但力不从心。
受既有研究的启发,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文尝试聚焦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研究和批判,特别是马克思对地租这一纠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焦点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和解答,来发现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性理解的推进和深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提供一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的新的阐释模式。
耶稣会士受葡萄牙保教权资助,通常从澳门登陆进入内地,越向腹里深入,经费获取越发困难。如明朝末年在江西传教的苏如望神父,“传教初期不为人们所解,除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外,还受到外教人、邻居们以及士人们的欺凌”③参见[法]费赖之(Le.P.Louis Pfister,S.J.):《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第69页。苏如望神父(1566-1607),1595年来华,卒于南昌。。贾宜睦神父的境况更加悲惨,他于1637年来华,传教于江南,“当时由于中国的连年内战,使来自澳门的接济中断了;神父不愿接受教友们的资助,常使他因三餐不继,极度衰弱,以致卧床不起”④参见[法]费赖之(Le.P.Louis Pfister,S.J.):《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第278-279页。贾宜睦(P.Jér.de Gravina,1603-1662),意大利籍耶稣会士,1637年来华。。
对于结构安全性,各风机基础方案均应满足结构受力、长期变形、稳定、刚度等要求,保证各基础方案的技术可行性。对于单桩基础,结构较为简单,桩长相对较短,单根钢管桩重量很大,荷载传递明确,基础整体承载能力相对较好,但是基础抵抗变形和极限荷载的能力相对较差,一般需要大直径和较大厚度的钢管桩;对于多桩基础,结构相对复杂,桩长相对较长,抗倾覆弯矩能力强,基础刚度大,抗变形能力强,钢管桩的直径小,对结构受力和抵抗水平位移较有利。
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生存状况不及广东,曾经一度陷入拮据,幸“苏如望(P.Jean Soerio)神甫携金至”[4],才解决了急需资金的难题。中国修士钟巴相,得力于无语言障碍,不断奔波于各地,“冒生命危险,去澳门领到钱财及其他必需物品,发放于不同的传教点”[5],以维持教务正常运转。
尽管利玛窦做了“以学术辅传教”“耶儒文化调和”的种种尝试,但天主教信仰仍不能被中国大多数民众所接受,从而导致如同罗明坚所言:“此处教区仿佛是一颗嫩弱的苗芽,被微风一吹,便能置于死地。”[1]233教务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是外来资金时常受阻,而内陆固定的经济来源渠道又没有形成,传教经费极度匮乏。
二、以信仰为中心,以节俭为基点:利玛窦的支出原则
传教事业刚刚起步之时,外来经费进入中国内地困难重重,中国教会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作为传教团队的领头羊,如何拓展教务,节约每一个铜板,同时又不违反信仰原则,是利玛窦时常面临的问题。为了使教会正常良性运作,利玛窦在传教实践中探索出适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支出原则。经过打拼,至明末,“十三省三十处皆有天主堂。”⑤参见(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49,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918页。关于明末各地教堂的数量及地理分布,可参见方豪:《明末各省天主堂所在地名表手抄稿两种》,载李东华编《方豪晚年论文辑》,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50页。。
(一)持守纯正信仰,拒绝廉价馈赠
肇庆是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教的起点,因为身着僧服,当地官绅按照中国传统施舍,但利玛窦没有接受。他说:“我们本来会很容易地从官吏那里获得寺田中的某些地租,但神父们觉得最好是不要接受这种地租。”[6]利玛窦拒绝“廉价的馈赠”,是防止官绅将天主教神父与佛教僧侣混淆,从而为传教事业扫清障碍。
(二)“量入为出”与“人弃我取”的支付原则
自北上以来,利玛窦与他的同事们谨慎小心买房、建堂,随着传教事业的拓展,建堂买房的支出也逐渐增大。如前所述利玛窦在南昌传教期间做的一次房产交易就相当成功,“房子位于城中很好的地段,与布政使衙门毗邻,只有六十两银子的价钱就能买下来”[7]209。天主教置产与佛、道教不同,其宗教性用地需要选择交通便利、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利玛窦此番在南昌购房,就是综合了房源的区域位置、周边的人文环境以及教会的经济能力等多种要素,最终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满意的回报。
随着传教事业向中国腹地的深入,传教士购置教产增多,面对距离澳门遥远经费获取困难的现实,利玛窦支出经费更加小心谨慎。1599年初,利玛窦到南京,先购一小宅,用做与士大夫聚谈之所,但狭小的空间难以满足教务的发展,经过交涉,至四月,又实现了一笔不动产交易:
40年,铸就了一座雄厚的经济实力之城,同时又是一座古今辉映的文化之城。苏州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不足3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7万亿元,列全国第七;人均GDP由634元增加到15.9万元,列全国第三,超过葡萄牙等国家。与强大经济硬实力相得益彰的是,苏州又是一座古今辉映的文化之城,不仅是罕见的“双遗产”城市,还是全国唯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2014年,苏州因其在平衡经济发展与传承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出色成绩获得李光耀世界城市奖。
结合表3可以看出,于七律、七绝之上除高山仰止的杜甫、李白外,最为推崇的当属李商隐(七绝中与王昌龄选数差距不大,可并列)。
利玛窦用“一半费用买下闹鬼”的房子,是抓住了卖方对“灵异”事件极度恐惧,急于抛售现房的难得商机,成功的交易得力于利玛窦在经济活动中的才干与权变①天主教观念中对中国的神鬼说不予认同,这应该是利氏愿意用低价购入鬼屋的根本原因。。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初在顺承门(今宣武门)租房,不久看中一套宅子,“有大小近四十间屋子,价钱也不贵,但据传闻,这所空宅子闹鬼,按中国迷信的说法,这会给住户带来不幸”[7]390。利玛窦凑足了六七百两银子,毫不犹豫地将其买下,1605年8月27日,迁入新居。利玛窦再次把握住了卖方急于出手“闹鬼”房宅的机会,低价购入。
南京、北京两次购房,故事情节极为相似,均体现出利玛窦“人弃我取,非择而取之也”[9]100的支出策略与原则。在利玛窦所处的时代,外来经费进入内陆常常受阻,教会内部的自养体系尚没有建立,利玛窦所有的教务支出,必须精打细算,为了节省开支,买房时不得不讨价还价,甚至以低价购置“闹鬼”的房子,其谨慎节用的经济伦理观,为后辈树立了样板。
(三)恪守“文契存证”和交纳税款的游戏规则
房产、地产是制度型宗教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利玛窦率领的传教团队进入中国内陆以后,购置不动产成为教务活动的重中之重。而民间的不动产交易,除需要中人、保人,还要求向地方官府交纳一定的费用,由此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文书。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土,也按照交易规则,如在南京买房,“文契存证”俱全②参见庞迪我:《奏疏》,载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第100页。遗憾的是,利玛窦当年的“文契存证”已无法找到。,如此操作可避免不必要的民事纠纷,从另一侧面也展现出利玛窦所秉持的“契约精神”。
高铁会促进民航票价的稳定,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竞争,有利于价格的均衡。高铁有效改善了民航运输业的垄断性,有利于促进民航降低票价,优化服务。高铁的运营,可以采取针对老年乘客的特殊服务策略,更多地考虑老人的感受,也可以进行早高峰晚高峰和其余时间的差别定价,可以针对女性旅客开设女性候机室等来优化服务[2]。
购置不动产需要交纳税金,利玛窦买下北京闹鬼的宅子后,按照中国法律到本城一大官处盖章(办手续),发现之前的房主没有交税。这些税款需要利玛窦补交,于是他请官员帮助,最后获得了免税,官方为此宅颁发了永久免税的证明[7]391。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5月18日,同事庞迪我、熊三拔上书万历皇帝,请求赐利子坟地。5月22日奉旨照准,交户部尚书办理。6月14日,礼部吴道南复奏:宜加优恤。6月17日,神宗交吴道南疏于叶台山。6月19日钦赐墓地:在北京阜城门外之栅栏。
三、利玛窦“受俸不做官”,开传教士供职朝廷之先河
服用抗血小板药物(如阿司匹林)、抗凝药物(如华法林)后应注意观察皮肤有无瘀斑和出血点,有无鼻腔出血、牙龈出血、黑便、血尿、月经量明显增多或有异常的阴道出血及严重的头痛等情况,如出现上述情况,应及时就诊或立即咨询心脏专科医生。如需进行有创操作(如拔牙或组织活检),请告知医生您正在服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
为朝廷服务并得到相应的报酬,这一小小的“角色错位”,使第一位定居北京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的身份多多少少具有一些世俗化的色彩。关于定居北京之后遇到的特殊情况,严守耶稣会会规的利玛窦在1605年7月26日致总会长的信函中作了汇报:
上帝的意志明显促成了我们进入并居住于京城,我常常默念此一意志,使自己在这么大的困难中鼓起勇气。我父您可以想象,外国人人数这么少,还要摧毁生活着数以百万计偶像,碰到了多少障碍!按照帝国的法律,我们向皇上朝贡之后,赏给我们银子,然后就得遣返回国,至多赐给我们京城一官半职,得受某一衙门的约束,我们的传教事业就会受到严重障碍。官员们就是按照这个意思上奏皇帝,请求他至少把我们赶出京城,只是皇上不肯。另一方面,皇帝想要我们做官,我们表章上去力辞,不仅不要当官,也拒绝官员待遇……不过,我们还是保留了待遇,并无官职,这就避免了任何官儿的干扰。所以,中国人都知道我们在征集教徒,还招别的人,但谁也不敢碰我们[1]469。
享有经济待遇但又拒绝加官进爵,是利玛窦明智的抉择,但生活在一个把天主教视为异端的国度之中,洋人领俸遭到官员的批评,利玛窦的信函反映了这一现状:
最近有这么一件事:有位大官说要取消皇上给我们的恩俸,因为他说享受俸禄而不任职是违反中国律法的;我就传话给他说,请他明示其意图,如果确实,我要去觐见皇上辞别,明言我远离故土已经三载。这个威胁果然奏效,他通知我说月俸将继续给我,阴历年底他将与同僚商议。从此,再也没有人谈及此事[1]469。
利玛窦实为西方传教士中受“俸”第一人,对此中西文献均有述说,《明史》记曰:
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留居不去。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①参见《明史》卷三二六。。
作为开拓者,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教的历程充满着磨难和艰辛,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却是圆满的,他得到了一般外国人难以享受的待遇。利玛窦离世后朝廷赐地以及中国天主教第一处公墓的修建,表现出中国高层对来自异邦的传教士的尊重和认可;他们的才华也得到士大夫的欣赏,清初著名学者尤侗赞誉利玛窦的诗文即是例证:
(利玛窦)可以绝对地在京居留,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更确定的支持,那就是奉皇帝之命,从他的国库支付给神父们一笔足够的俸禄,用来供养他们自己和四个仆人,这笔俸禄每季收到②参见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28页。曾德昭,原名谢务禄,1613年来华(利玛窦去世仅3年),在南京传教时引发教案,被逐回澳门,后又潜回内陆,在中国传教数年,跑遍半个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情况极为熟悉,因而述说利玛窦在京情况可信。。
进入宫廷的利玛窦、庞迪我,因拥有特殊技能,成为京城的特殊人物,他们是皇宫钟表师,有固定的收入又可以“征集教徒”,广传福音,“钟表师”终于把天主教信仰送到了中国皇帝的身边。
从购置不动产签订契约,到置产后的交税,说明逐渐深入中国之后的利玛窦如鱼得水,他深深了解中国社会的生存之道,了解中国民间不动产交易的规则,而之后地方政府给予北京南堂的“永久免税”的优惠,说明利玛窦已经成功地在中国社会建构起一张有效的人际关系网络。
利玛窦逝后所获殊荣的原因是效力朝廷有功,正如其同事庞迪我在《奏疏》中所说:“三十八年,玛窦病故,迪我等具奏,陈谢圣恩,多年豢养”,申明“食禄有年”的特殊身份[9]74;顺天京兆王应麟为利玛窦撰写的墓碑铭文曰“上命礼部宾之,遂享大官(光禄寺)廪饩”。经过中西同仁的努力,神宗终于钦赐房地共四十八间,周围墙垣二十亩③顺天京兆王应麟撰“利玛窦墓碑铭文”,载[法]费赖之(Le.P.Louis Pfister,S.J.):《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第51页(“利玛窦神父传略·附”)。。中国天主教第一座公墓由此奠基④参见“钦敕西儒葬地居舍碑文清漳王应麟”,载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233页:文献记曰:“上震悼,赐地二十亩,在阜城门外滕公珊栏。”这块墓属于官田,有“房地共四十八间,周围墙垣十二亩。”关于利玛窦去世后朝廷赐房地,不同版本文献记载不一:如《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三)记“三十八间”,墙垣“二十”(第1324页)。。此后,栅栏墓地成为葡萄牙保教权系统传教士的安息之处,著名耶稣会士汤若望、龙华民、安文思等,也长眠于此。
田铭拒接范青青的电话,但范青青直接找上门,堵住他:“我今晚约你看星星。”范青青偏着头对着他笑,笑得胸有成竹。田铭不语。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P.Alvare de Semedo)著《大中国志》记载: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阜城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①(清)尤侗:《外国竹枝词》,清嘉庆8年(1804)养素楼刻本,第25页。康熙年间,尤侗的《西堂文集》印行,并收入《四库全书》。因为文集中未收《外国竹枝词》,故嘉庆年间将这一百多首外国竹枝词重新刻印出版,未分卷。。
1601年是利玛窦在华事业的转折点,是年利子定居北京,一道来此的有西班牙籍会士庞迪我(P.Did.de Pantoja)等。值得关注的是,利玛窦定居北京的身份是宫廷钟表修理师,而不是传教士。利玛窦进京后曾得到朝廷大员的帮助,吏部给事中曹于汴亲笔写了一份奏章,请皇帝正式批准这二位神父留在北京。皇帝并没有直接做出批复,而是让太监转告庞迪我和利玛窦,从此可安心住在北京。而且此后官方每月给他们相当8个欧洲金币的津贴。按庞迪我的话来说,这已足够他们日常的花销[10]。
(2)株洲段河岸沉积物中绝大部分重金属元素(Ba、V、Cr、Mn、Co、Ni、Cu、Zn)均表现为轻微的潜在生态风险,但重金属Pb存在很强的生态风险,平均值达183.40,尤其是ZU沉积柱中更是表现出极强的生态风险是湘江株洲段河岸沉积物中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的主要贡献因子.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单方面的认为自身地位受到威胁,欲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抑制中国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无疑是为他们敲响了警钟。所以,为维护本国的霸权地位,巩固自身在经济上的话语权,美国不得不向中国发起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中美贸易战。
诗下有文字补充:
利玛窦始入中国,赐葬阜城门二里沟,曰利泰西墓。天主堂有自鸣钟、铁琴、地球(仪)等器。国中玫瑰花最贵,取蒸为露,当为香药。[11]
(利玛窦)非常便宜地买下三幢宽敞、方便的住宅,作为南京耶稣会院的新会院,之所以购得房屋,是传说这些房子闹鬼,没有人愿意住在里面。而恰在此时,郭居静神父(Cattance)和其他耶稣会士带着行李,通过冰冻的运河,从北方来到南京。但是,郭居静不得不继续他们的行程,利玛窦为了筹集传教经费,曾为购房子讨价还价,最终以大约一半的费用买下了闹鬼的房子[8]。
诗与文均生动地表现了利玛窦离世之后,其影响犹在的历史事实。
进驻北京的西方传教士获得朝廷优渥,始于元代,当年进入汗八里的传教士曾受到朝廷青睐,他们“由中国国库支付很宽厚的衣食津贴,并获准就在汗八里宫墙外修建一座教堂”[12]。但利玛窦与元朝定居北京的传教士情况不同,利玛窦获得俸禄是因为服务于朝廷而元代传教士只纯粹传教;利玛窦与后继者汤若望等人接受“官职”也不同,他是“受俸不做官”,并由此开启了西方传教士接受中国朝廷俸禄之先河。
利玛窦服务朝廷的目的是“意专行教,不求利禄”,为传教赢得便利,这种思路影响其后继者,以至世纪后半期,支持适应政策的最富创造力的耶稣会士越来越多地在北京的朝廷供职,以求得皇帝的赞助与保护[13]。
制度型宗教需要依靠经济支撑来保证传教机器的运转,这种格局对传教士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即在涉足经济活动中做到清贫守节。关于来华耶稣会士这种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游走的生存格局,明清之际的教会文献已有明确述说:
1.2.4 BrdU掺入法检测细胞增殖 按罗氏公司BrdU掺入法检测细胞增殖试剂盒方法进行。即将转染的细胞接种于96孔板中;次日加入标记的Brdu,培养4 h后加入FixDenat试剂,室温孵育30 min,固定细胞;弃去FixDenat,加入抗Brdu的植物过氧化物酶工作液,室温孵育90 min后PBS缓冲液洗涤,加入100 μl/孔底物缓冲液,变色后加入25 μl/孔 H2SO4(1M)1 min后,在涡旋仪上震荡2 min;测定波长450 nm处各孔的光吸收值。
危害玉米健株生长最主要的地下害虫有地老虎、蝼蛄、金针虫的,其主要危害就是此类地下害虫会吞噬玉米的种子,啃食玉米的根茎部,造成苗株无法发芽或者苗株在生长初期变黄死亡,田间出现缺苗现象,若不加以管控,严重些会导致田间整片没有苗株生长。
图8给出了微通道分支数n=3,质量流率=3g/s,热流密度分别为25、35、45、55W/cm2时热沉热应力云图。
西士修规,绝财第一,日用薪水,俱仰给九万里外修会,定有常俸。但越海而来,屡遭失缺,不得不减缩用度,节啬衣食,置薄产以备空乏[14]。
来华耶稣会士们身揣“技艺”,远离欧洲导致生活拮据,接受俸禄可缓解经费的压力。从社会经济视角检视,获得朝廷俸禄,的确“逐渐削弱了他们对澳门的依赖”。但是,天主教传教修会的经济体制否定了“私产”的合法性[15118,他们奉行“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②“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本是道学、佛学讲求的境界,朱光潜先生曾用这句话评价弘一法师,此后天主教神职也用这句话自我激励、鞭策。的原则,俸禄归属教会,且有专人负责。在“17世纪90年代,耶稣会士从徐日昇的节俭作风中有所获益,徐日昇合理地管理钦天监同事的俸禄”[15]128。如果是俸禄之外的“赏赐”,且数额巨大,修会有更为严格的制度:耶稣会士罗德先(Bernard Rhodes)曾两次为康熙皇帝治病,因医术精湛,康熙“以价值二十万法郎的金元宝数锭送至法国耶稣会院。这是中国皇帝给外国传教士最大的一笔赏赐,资金存入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利息专供法国耶稣会使用;耶稣会解散后,作为留给北京会士的经费;1813年,北京耶稣会士全部亡故,传信部遂把该款划归北京的法国遣使会士”③ 参见[法]高龙鞶(Aug.M.Colombel,S.J.):《江南传教史》(Histo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第二册,周士良译,台湾,辅大书坊,2013年,第406页。耶稣会士罗德先所获巨款交给修会的情况,详见第十五章第二部分。。由此可见,耶稣会有着严格的财务管理体制,而来华耶稣会士严格遵循“减缩用度,节啬用度”的规则,实由利玛窦开创。
四、绪余及结语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批来华耶稣会,在华活动经费主要依靠葡萄牙王室资助,但由于17世纪信仰新教的荷兰崛起,并迅速投入海外殖民活动,澳门的天主教经济一度遭到打击,法国著名汉学家荣振华对此有一段评说:
传教区的经济形势从来也不是光辉灿烂的。其形势有时会变成灾难性的。例如在1603年7月29日,当葡萄牙水手们正在城内愉快地庆祝他们即将起航时,三条荷兰船在澳门港口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夺取了装有杜卡托(ducat,威尼斯古金币——译者)和正准备出航的船只,这些金币是用来支付在日本的122名耶稣会士,254名教理师和190个教堂费用的。当时便下令遣返半数教理师、传道员和仆人,把分散在各村庄的司铎们重新集中到城市,到处(在中国如同日本一样)都尽最大可能压缩开支[16]。
“不测风云”常因政治、军事、商业以及宗教等复杂因素引发,此为大航海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传教士一旦受“风云”突变之影响,经费开销就会吃紧,日子就有些难熬了。在传教经费紧张,天主教不动产的格局尚没有形成的形势下,利玛窦、庞迪我终于以钟表修理师的名义定居北京,此为西方传教士供职朝廷、领受俸禄之滥觞。
接受俸禄的传教士是传教团队中的精英,也是中国天主教会的中坚力量,起着联络地方传教会的作用。至于接受朝廷的“俸禄”,具体到传教士个人略有不同:第一批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等人“受俸不做官”,他们远离澳门,受俸可以减轻教会的经济负担;汤若望、南怀仁属于第二批来华的耶稣会士,此时经过利玛窦等前辈们的努力,全国已有数个传教站,教会不仅有来自欧洲的固定经费,而且还有信徒的资助;至于康熙年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他们则可以直接从国王路易十四那儿得到活动经费。总体上说,来华传教士的经济状况随着天主教影响的扩大而逐渐呈现好转的趋势,而不断有传教士进入宫禁,不仅可利用高层的人脉关系声援地方教会,其所得俸禄,特别是皇帝的“犒赏”,既可补充教会经费之不足,也可以借此“为传教的工作谋便利”[17]。
“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传教理念,使传教士在神圣与世俗,绝财与财富的关键点上,找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平衡点”,如此教会才能在良性的轨道上运作。利玛窦之后,地方的传教士在购置不动产时,均遵守置产立契,依法交税之准绳;在教务支出上秉持收支平衡、量入为出之原则;而供职朝廷的传教士则要恪守“俸禄充公、专人管理”之法规。中国天主教经济生活中的种种不成文的“规矩”,以及传教士必须持守“神贫”的经济伦理理念,均可溯源于开教先锋利玛窦。由此看来,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也是一位称职的传教团队管理者和精明的理财专家。
参考文献:
[1]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M].萧浚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罗光.利玛窦传[M].台北: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2:41.
[3]利玛窦全集:第三册[M].罗渔,译.台北: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台湾光启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
[4]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全二册[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35.
[5]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M].梅乘骐,梅乘骏,译.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60.
[6]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M].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09.
[7]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M].文铮,译;梅欧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8]ANDREW C.ROSS,A VISION BETRAYED.The jesuits in Japan and China 1542-1742[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4:136.
[9]庞迪我.奏疏[M]//钟鸣旦等.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
[10]张铠,庞迪我与中国[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71.
[11]尤侗.外国竹枝词[M].清嘉庆8年(1804)养素楼刻本:25.
[12]赫德逊.欧洲与中国[M].王尊仲,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128.
[13]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M].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330.
[14]无名氏.敬一堂志·田房[M]//钟鸣旦,杜鼎克,王仁芳.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3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13:581.
[15]柏里安.东游记耶稣会在华传教史,1579-1724[M].陈玉芳,译.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4.
[16]荣振华,方立中,热拉尔·穆赛,布里吉特·阿帕乌.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M].耿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92-393.
[17]魏特.汤若望传:第一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9:174.
Matteo Ricci's Economic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the Analysis on His View of Economic Ethics
KANG Zhi-jie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relevant studies on the status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famous Jesuit Matteo Ricci in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but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his economic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his view of economic ethics.As one of the first Jesuits entering China,Ricci's living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secular society.With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living within your means”and“consume every copper coin carefully”,he explored principles of expenditu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urches.He received the official salary without being an official,which was the first time for missionaries to serve i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embodied the missionary conception“doing the enterprise of worldliness with the spirit of aloofness”.
Key words Matteo Ricci;economic activities;economic ethics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9)03-0123-06
收稿日期:2019-02-19
作者简介:康志杰(1954-),女,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玲玲)
标签:耶稣论文; 利玛窦论文; 天主教论文; 传教士论文; 澳门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论文; 基督教史论文;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湖北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