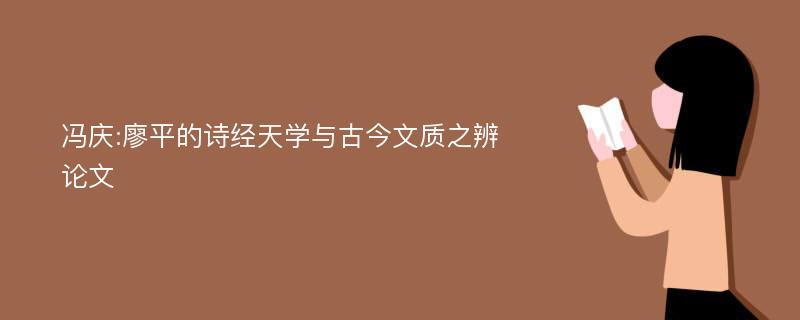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子·人间世》
近代经学大师廖平的思想有所谓“六变”,其中,前三变发生于晚清,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历史潮流密切相关;后三变发生于民国,与新文化运动、“五四”等思潮平行发生。廖平“六变”当中,“一变”为平分今古,其代表作为《今古学考》;“二变”为“尊今抑古”与“素王改制”,代表作为《知圣篇》(后多次修改);“三变”为使《王制》《周礼》分属“小统”、“大统”,进而论“大地制度”之说,代表作是《地球新义》《古今学考》《皇帝疆域图》等;“四变”是分天-人、内-外之学,代表作是《孔经哲学发微》等;“五变”是依先小后大、先人后天之序排列六经,并以《楚辞》《周礼》《王制》等为其传,兼倡文字始于孔子之说,代表作为《大学中庸演义》《文字源流说》《五变记笺述》《四益诗说》;“六变”是以五运六气解《诗经》《易》,代表作为《易诗合纂》(后改为《〈诗经〉经释》和《〈易经〉经释》)。
n——与隧道半径和土质条件有关的影响系数(对于黏性土,n取0.35~0.85;对于砂土,n取0.85~1.00);
在其后三变阶段,廖平对《诗经》的解读逐渐推进,将《诗经》之学视为处理“六合之外”的“天学”,也就是超出“人学”、以“神游”为导向的学问。这类通过解读古典诗歌文本切入“天学”问题的著作,包括《〈楚辞〉新解》(1906)、《〈诗经·国风〉五帝分运考》(1913)、《四益诗说》(1914)、《〈楚辞〉讲义》(1914)、《〈诗经〉天学质疑》(1914)、《〈诗纬训纂〉序》(1918)、《〈诗经异文补释〉跋》(1919)和《〈诗经〉经释》(1930)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大部分完成于民国初年,与“新文化运动”草创酝酿直至“五四”的时间段基本重合。近年来,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为名目,诸多学术思潮以“借古人翻后人”的姿态浮出水面。然而,同样相隔百余年,相比起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陈独秀、胡适等近现代思想家所获得的广泛关注,廖平于“新文化运动”普遍开展期间延续晚清经学问题意识所进行的诸多探索,却甚乏关注。在不熟悉廖平的人看来,他的学术意义局限在“近代”,局限在其晚清“平分今古”所获得的赞誉和因倡导“六经皆孔子所作”而获得的“言绝恢怪”(章太炎语)形象之上。迄今为止,谈论廖平的人们大多关注其早年的今-古学考论与《春秋》《王制》研究,或是探讨其对康有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少有人愿意评骘廖平在辛亥革命的政治大变局之后,逐渐由“今”返“古”、开启后“三变”的核心理路,其后期“天学”的内在机理更是几乎无人问津。
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直至今天,廖平苦心孤诣打造的“天学”一直遭到知识界的冷落,其原因是什么?通过回到历史语境,思索前人看待“天学”的方式,我们或许能够从正反两方面更好地审视中晚年廖平这一思想立场可能具备的现实意义,甚至在古典经学日益复兴、而现代性话语依然推动时代前进的“新时代”的语境中,发现其既坚守传统、又开辟未来朝向的苦心孤诣,为当下的思想和文化建设提供别样的智慧。
问:我从来不相信保健品,朋友读《养生三记》,说挺好的,我借来读,有一点动心,就想去彭祖补品屋看看。那天我和朋友一起去的,她买了一些东西,我买了麦绿素和补氧胶丸。妹妹是乙肝携带者,她吃了麦绿素,感觉乏力和肝区不适的症状没有了。父亲总头疼,吃了补氧胶丸,脑筋清爽,头不疼了。我很认可这些产品,我没有病,只是成天坐办公室,有时提不起精神,睡眠也不太好,可不可以吃麦绿素?
“时势”中的“天学”
在经学凋敝、新文化畅行的现代中国,新派学人或海外汉学家视廖平学说为敝屣,这也不难理解。但是,深谙经术、捍卫中华文明尊严的儒者、国学家们也反感廖平,原因可能在于,廖平用离经叛道的某些手段来捍卫经学,最后反而让经学真正走向了“终结”。廖平捍卫经学却最终导致经学终结的这种“二律背反”,5 同上,第253—254页。[Ibid., 253-54.]其实源于章太炎的“盖棺定论”。在章太炎为廖平所写的墓志铭中,一副古怪的图景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一方面,廖平“言甚平实,未尝及怪迂也”,其为人孝顺而“雅素”;另一方面,廖平又“智虑过锐,流于谲奇”,以至于到了晚年“杂取梵书及医经形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导致“其徒稍稍传君说,又绝与常论异”。6 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ZHANG Taiyan, LIU Shipei, 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shi lun (On China’s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100.]这无异于说,廖平尽管为人处事平实雅素,但智识上的强烈偏好压倒了他对儒家正统经义的持守,使得他的学说显得“超常”“绝俗”。因此,廖平晚年杂糅多家学说的“天学”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廖平本人天性“智虑过锐”。
钱穆怪廖平太“新”,冯友兰嫌廖平太“旧”,列文森则觉得廖平根本“无用”。取此三家之说,或可看出,廖平“天学”的“罪状”大致包括不遵儒学家法而奇谈怪论、不应时势规律而盲目守旧、不鼓吹政治实践而消极无为等。在新文化冲击之下渴望保守经义正统的儒者不会喜欢嗜好发明、变幻无常的廖平的学说;积极求变的新派学者也不想聆听廖平的“旧瓶新酒”;政治上渴望变革的人则必然把廖平著作视为遗老呓语抛诸脑后。廖平的“天学”也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构成了一些论者所谓的“经学的终结”,甚至被后世评传作家用黑格尔来比附,认为其“用否定的形式包容了一切经学的发展”,“又不自觉地指出了摆脱经学的现实道路,这就是从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中,去寻求解决现实矛盾的时代理论”,当然,在今天的人看来,这种“理论”违背“起码的历史常识”,进而显得“天方夜谭”。4 黄开国:《廖平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55—257页。[HUANG Kaiguo, Liao Ping pingzhuan(Liao Ping’s Biography),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5, 255-57.]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廖平的“天学”“非考据、非义理、非汉、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得其要领”,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24页。[QIAN Mu, 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shi(xia)(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I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724.]这是在指责廖平本人的“家法”不正,过于新异,无法让后世学人循序渐进、登堂入室。冯友兰则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廖平后期思想“若以历史或哲学视之,则可谓无价值可言……牵引比附而至于可笑,是即旧瓶已扩大至极而破裂之象也”,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第1041页。[FENG Youlan, Zhongguo zhexue shi (xi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47, 1041.]这是在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批评廖平太过保守,即便有“变通”意识,渴望让儒家经义在现代焕发生机,也做得左支右绌、笨拙不堪。汉学家列文森则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廖平“一生一事无成”,其“理论体系之所以稀奇古怪,就在于它与任何可设想的行为都毫无关联……只能充当一个历史的观看者而不是行动家”,3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74页。[Joseph R.Levinson, Rujiao Zhongguo jiqi xiandai mingyu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rans.ZHENG Dahua, REN Ji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274.]这是在指责廖平未曾或者无法用有效的手段,让儒学变成一种激发实际政治“行动”的思想力量。
廖平主张应当先入“人学”,再入“天学”,这是初学者们通过进入君子状态,再逐步切近圣人思想的次序。“天学”的重要性,在于为后世留下可以作为理想的至高想象法门,提供“人学”得以朝向的目的,决定其应当采取的形式;“人学”的重要性,则在于通过成熟周详的政教礼仪考察,对现实进行规范,进而实质上推动文明整体的发展。这样一来,“天学”与“人学”、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也就得到了明确:
Analysis of mechanics performance of container building with holes under horizontal load
余闻庄生有言,圣人之所以駴世,神人未尝过而问焉,次及贤人君子亦递如是。余学不敢方君子,君之言殆超神人过之矣,安能以片辞褒述哉?以君学不纯儒,而行依乎儒者,说经又兼古今,世人猥以君与康氏并论,故为辨其妄云。9 章太炎、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100—101页。[ZHANG Taiyan, LIU Shipei, 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shi lun (On China’s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100-1.]
章太炎将廖平“不纯儒”而又“行依乎儒者”的态度与康有为类比,与其说是要真诚表达对廖平的敬重,不如说是为了顺势攻讦其多年论敌:康有为可谓“言必称儒”而“行不依乎儒者”之典范。重要的是,章太炎提到庄子笔下“神人”“圣人”“君子”的人品等级,显然是在暗讽廖平晚年引佛道诸子入经学的思路,其实只是“不接地气”的玄想——在圣人、君子治理政事之时,“神人”理应不要过问,廖平的言论“超神人”,当然也就根本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就此暗讽内在的逻辑来看,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廖平的思考确实具有一种高明玄妙的向度。或许,如果廖平不执着于孔子作为素王制作五经的立场,不刻意要用经学来囊括诸子百家之学,那么,强调“六经皆史”、而诸子之学则应当自成体系的章太炎,10 王锐:《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7—146页。[WANG Rui, Zhang Taiyan wannian xueshu sixiang yanjiu (Studies on Zhang Taiyan’s Academic Thought in His Late Year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137-46.]或许会愿意承认廖平作为一个纯粹“证解”“参会”之人的高明之处。
章太炎或许反对的是廖平杂糅经、子的态度。毕生投身政治事务,到了晚年,章太炎把经学、读经也视为一种政治教化手段,尤其推重《孝经》《儒行》《丧服》《大学》四篇,“对于涉及抽象问题论辩的经书他并不提倡”。11 同上,第215页。[Ibid., 215.]而这些强调实践、伦理、制度的经典教育,在廖平后期分天人之学的框架里,只是“人学”范畴。晚年廖平于其“人学”则较少用力,而是把时间用于援引《列》《庄》,俯仰《诗》《骚》,将纬书、《山海经》《淮南子》和《黄帝内经》当中那些近乎神话的表述纷纷视为指涉星宿分野、气运周游的象征符号,以此构建“天学”谱系,磅礴浩荡而不着边际,在人间世“乘物以游心”,自然被目为“超神人”。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境内水系纵横交错。然而,近年来偷采、滥挖河砂不仅造成砂石资源日益枯竭,破坏了江河的生态环境,而且严重影响了河道安全和防汛安全。为了强化河道采砂管理,江西省政府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非法采运砂石资源依法严打,维护了采砂秩序,保障了河势稳定。
经学四教,以《诗》为宗,孔子先作《诗》,故《诗》统群经,孔子教人亦重《诗》。《诗》者,志也。获麟之前,意原在《诗》,足包《春秋》《书》《礼》《乐》,故欲治经,必从《诗》始。……使学者读《诗》,明本志,而后孟子“以意逆志”之效明,孔子重《诗》之教显。21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一,第201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1, 201.]
抛开新“时势”的催迫不谈,从儒学、经学内部而言,如果不在经、史、子、集之间确立显著边界,不遵守“家法”,贸然立说,肯定会带来强烈的思想震荡,进而直接影响到政教人心的秩序。“天学”不能为近代以来诸多眼界卓绝的学者所接纳,或许和“敬鬼神而远之”的祖训密切相关。廖平难道不知道这个祖训?难道他不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高明的“神人”应当节制自己的“智虑”,表达对“家法”的适当虔敬?他难道不是在《知圣篇》里就说过“至孔子时,先圣开创之功已毕,但用文教,已可长治久安,故力绝神怪,以端人心,而正治法”吗?(尽管他又补上一句“云‘不语’,则实有神怪可知”。)12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一,舒大刚、杨世文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8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1, eds.SHU Dagang and YANG Shiwe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208.]
小统《春秋》和大统《尚书》共同构成“人学”,《王制》是《春秋》传,《周官》是《尚书》传。群经得以在一个整体系统中彼此呼应,处理不同层次的问题。在廖平看来,今古家法之差异不在于经义的对错真伪之别,而在于各自所要经营的政治状态在规模和层次上有别。同样,“人学”和“天学”也是不同的“学术分工”,并不彼此抵触扞格。廖平显然不会承认“六经异义”,因此,他会踵续郑玄、朱熹等大儒的问题意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化解群经内在的各种冲突。为了能够让体系更为圆融,援引诸子百家、佛道医术进入经学充当“润滑剂”,也就成了必须的工作。
主今文者,为西汉博士派;主古文者,为东汉古学派。博士主小统,但言现在,求合时尚。后世开通世界,圣制无闻。……古学主大统,胶执训故,剖析文字,而昧于经国之大体。……“王伯”为小,“皇帝”为大,版图明察,政治乃利设施。“王伯”世局,治以《春秋》;“皇帝”世局,治以《书经》。13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二,第566—567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2, 566-67.]
其实,廖平并非不守经学家法,而是重新规定了经学的整体范畴:今文经学重视《王制》《春秋》,在廖平的体系里构成“小统”;古文经学重视《周礼》《尚书》,则构成了“大统”。“小”“大”之别的本质在于治理版图有“王伯”与“皇帝”两种规模,也就应当有两种相应的制度:
章太炎、钱穆和冯友兰所不解的——也是列文森嗤之以鼻的——正是在于,廖平紧紧抱着这样一个作为整全系统的“经学”不放,而不愿意单纯凭靠子学、史学和器物之学锻造新时代的“国学”,遑论像“五四”新青年那样,吸纳西方的历史哲学,重新改造中国国民性。和崇尚“六经皆史”的章太炎相比,廖平坚信作为全体的“经”始终高于“史”,哪怕在晚清民国的“时势”当中亦然如此。换句话说,廖平坚持要用经学的学术立场来全方位重新解释这一古今大变革的“时势”,而不是像其他同代人那样,让“时势”左右古典学术的内在文明尺度。这反而是在捍卫“家法”,而非一手要促成“经学瓦解”。实际上,某些保守主义者持守“家法”的旧说陈见,不愿接纳新知之可能性,而把应对世道时势的任务拱手让于史、子、集之学甚至西学,想必才是导致百年来经学凋敝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廖平反而显得格外“新潮”。
“天学”的意图与志趣
经学家廖平并非墨守家法,而是积极促进经学的自我疗养,开辟出新的治经方案以响应“时势”。在这方面,廖平最典型的文本当属其“第三变”时期的《地球新义》。这部著作毫无疑问充满了维新变法时期的时代色彩,但与同代学人将西人学说视为横向移植之核心、将中华传统视为格义脚注的做法相比,《地球新义》引入儒道小大二统之说,重新诠释《诗》《易》中的气运变化之理,将西方天文地理学说引入作为《尚书》《周礼》的脚注,着实提供了一种超出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视野、富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图景想象方略。为了能够更好地引导出经学体系“放眼世界”的想象力,廖平将“思无邪”中的“邪”解为“邑牙声”,即“涯”14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八,第130—131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8, 130-31.]——《诗经》的心法从“思无邪”变成“思无涯”,进而变成“其知也无涯”,于是,《诗经》也就将成为熟读诗书的有志之士想象未来世界的重要“智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球新义》也是廖平诗经学、亦即其“天学”体系之下的重要著作,其核心问题意识,当然正是“开眼看世界”。因此,指责廖平与时代脱节,这是说不通的。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人们首先会问:廖平虽然有志用华夏经学智慧全面化解“世界历史”,但却“有心无力”,给出的方案显得格外笨拙:试问熟悉西方科学的人,有多少会相信《诗经》的作者——不管他是不是孔子——已经认识到大地是圆球状、甚至知道包含美洲、澳洲在内的“大九州”15 同上,第65—67页。[Ibid., 65-67.]的存在?不仅如此,通过训诂诠释,把“思无邪”的义理换成“思无涯”,这不就瓦解了古典诗教敦风化俗的旨趣吗?廖平此举又显得像西方那些用语文学方法对古代经典进行“人文阐释学”的新派启蒙哲人,其做法看上去既损害了传统《诗》教匡正世道人心的功能,又无法真正给出“科学”“现代”的世界视角,最终,其应者自然寥寥。
进而,在排除了廖平落后于“时势”的嫌疑后,我们又产生了新的疑惑:廖平是否是在“强制阐释”、硬要把古典经义与现代问题囫囵吞枣地融贯在其学说当中?也许我们还不能太早下判断,因为,廖平“天学”在其整体经学框架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义法,尚未完整呈现在我们面前。
廖平把《诗经》视为“天学”,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儒家教化的基本立场;相反,他其实将敦风化俗的任务交托给了“人学”,并且严格限定了这两种学说的应用范围。廖平强调,《诗经》应当在经典序列当中具有更高的位格,作为“人学”的《春秋》《礼》《书》学,则构成走进《诗》学的前期准备。在《续论诗序》中,廖平就指出:“欲读《诗》必先读《书》,欲知《诗》必先习《书》。由《春秋》而求《书》,由《书》然后可知《诗》。《春秋》《尚书》人事之说既已精熟,则诗词起兴,自能解《诗》之义例。”16 同上,第331页。[Ibid., 331.]在进入《诗》之前,渴望自我实现君子修养的人,应该先从“人学”的《礼》《春秋》《书》中学懂“人事”。唯有经历了“人学”、成为君子,才会对政治事务会有更加练达深刻的体会,进而才能往上走,进入真正而非模拟的“起兴”。
这种诗学“起兴”的目的,不再是伦理教化意义上的“敦风化俗”,而是为了开辟出更高层次的智识修养与洞察万物秩序规律的宏阔视野。这就要提及廖平区分“人学”和“天学”的根本标准,那就是“行”“知”之别:“‘人学’重在行,必俟诸百世以后;‘天学’首在知,洞悉于寸心之间”。17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二,第574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2, 574.]“行”对应的是“人事”,“知”对应的是“义例”。
唯有理解了廖平关于“人事”与“义例”——亦即“人学”与“天学”——的区分,才能理解他为何会在“天学”中安置那些在史学家看来“怪诞”“不经”的内容:“义例”通向的是“寸心之间”的知识,并非对具体政治现实事件的记录,进而也就不是“历史材料”,更不是服务于当前政治伦理教化的行事策略;那些“以事说诗”者“或以为美,或以为刺”,均是受到《毛诗序》的不当影响,忽视了“孔子所传、子夏所授、先师所习,皆在义例,而不在时事”18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八,第327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8, 327.]的常识。
进而,廖平也就可以合乎情理地反驳那些对他无视史实、凭一己臆想强解经文的质疑。廖平会说:孔圣人也许无法用科学手段获得关于地球、天体与宇宙万物的切实可靠的知识,但是,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在于他能如同邹衍那般“验小推大”,19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一,第249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1, 249.]根据现实事物的规律展开哲学推理,“由人性以推物性……更由人类以推鬼神,由六合以内以推六合之外”。20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八,第525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8, 525.]“小球”、“大球”对应中国、世界,“大九州”包含美洲、澳洲,这些当然并非圣人考索实物后的经验判断,而是建立在对自然天道整全把握之上的理性推论。这种理性具有诗性“起兴”的特征,是具备比君子更高智慧的“圣人”的秘密心法。
的确如此。古之圣人在看到浩瀚汪洋时,当然会去想象在九州大地之外,还有着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秩序。在仰观天象时,发现星宿系统有大小相套的秩序,自然会想到根据这种秩序为人间世提供“分野”。这种具有宇宙整全解释意图的自然秩序观,并不仅仅存在于《诗经》《易》等经书当中。诸如《庄子》、纬书、《山海经》《楚辞》中关于“六合之外”的描述,在廖平看来,都体现着这种渴望在人间政治世界与天道自然秩序之间建立起稳定关联的“起兴”。“起兴”不是一种随意的想象,而是“天学”之教的真实所指,是一种古代圣人的诗性立法智慧。
正因为其针对的对象有“圣人”和“君子”的品性差异,“天学”之教和“人学”之教也就有着显著的区别。把《诗经》视为“人学”,当然引申出“温柔敦厚”的世俗教化层次;把《诗经》视为“天学”,则意味着要提供一种面向未来“圣人”的内在心性修炼。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廖平指出,《诗经》作为“孔子之教”之根本意义,在于使人“明志”:
不过,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方面,大型公立医院管理者并不是完全束手无策的。福建省立医院院长朱鹏立向《中国医院院长》强调,国内医院管理者在优化院内就医流程上,其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透过章太炎这位守“家法”、应“时势”还重视政治“实践”的近代大学者之眼,我们大致摸透了廖平“天学”在同辈和后世学人眼中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高”得太过分,以至于与那个以救亡和启蒙为主旋律的时代彻底脱节,显得虚无缥缈。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人间世》)
《诗经》是孔子教化之始,“与《春秋》虚实不同”,因为“盖《春秋》名分之书,不能任意轩轾;《诗》则言无方物,可以便文起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凡纬说、子书非常可骇之论,皆《诗》《易》专说”。22同上。[Ibid.]“言无方物”,不具体对应的政治史实,也就不提供具体的政治伦理方略和规劝;“便文起义”,则是为了通过文学诗句“断章取义”,把那种圣人通过《诗经》真正表达的沟通天人的立法“心志”,从字里行间剖析琢磨出来。
发菌阶段,菌丝体适宜弱光下生长,黑暗条件也可,光线太强反而不利于菌丝生长。出菇阶段,要有足够的散射光。
必须回到廖平对“孔经哲学”的整体理解,才能理解“便文起义”通向何种心志状态。在《四益诗说》中,廖平解《乐纬·动声仪》“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时,强调“诗人”乃是“作《诗》之人,指孔子”,“感而后思”则是一种“哲学思想”,23 廖平:《诗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LIAO Ping, Shi shuo (On Poetr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35.]这就把《诗》学的境界彻底拔高到了“哲学”——普通人不可能、也不会关心的“思想”之学:
不是每一种选择都需要坚持,不是每一种坚持都能够成功,不是每一种经验都可以复制,不是每一种努力都得到回报。人生成功的要素,除了能力、努力、毅力和激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找准奋斗的方向,找到适应的平台,发挥自己的长项,创造不凡的业绩。
哲学名词,大约与史文事实相反。惟孔子空言垂教,俟圣知天,全属思想,并无成事……今以性道定静归入天学,《大学》从修齐入手,方有余力研究国家天下事理,一切玄妙空谈,俟诸异日。24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二,第655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2, 655.]
教师培训者是教师的“教师”。从个人视角出发,教师培训者的结构优化,包括培训者队伍来源类型优化和培训者自身素质优化。群体性知识或公共知识和教师个体性知识是教师知识的两个重要来源,教师培训者的队伍构成对应就应包含教育科学理论知识丰富的高校专家和一线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小学教师。教师培训者还应提升自身素质,如掌握和熟练应用隐性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策略,教师个人知识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引导、建设能力以及根据教师个人知识形成规律而进行培训课程设计和实施能力。
选取2017年1月~2018年3月在蛟河市天岗镇中心卫生院接受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108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4例。其中,观察组男29例,女25例,年龄60~75岁,平均年龄(67.9±5.1)岁,病程6~23年,平均(13.8±2.4)年;对照组男30例,女24例,年龄60.5~73岁,平均年龄(67.5±5.3)岁,病程5~24年,平均(13.6±2.5)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原来,《诗》教的“便文起义”,就是孔子的“空言垂教”,其传授的内容乃是“性道定静”。此处之“性”,即“生之质”,在注解《诗纬》时,廖平引用《翼奉传》云:“诗之为学,性情而已”,重要的是,这一学问的修炼,要求能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25 廖平:《诗说》,第33页。[LIAO Ping, Shi shuo (On Poetry), 33.]作为性情之学的《诗》学,与天文历法、音律之学是一以贯之的。这样的学问,正对应着西方的古代天文学、数学、和声学等,并最终通向关于宇宙万物自然秩序的形而上学。26试比较吴寿彭先生翻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时自觉或不自觉回忆起的诸多中国诗学资源:“宇宙自然与诸天就依存于这样一个原理。而我们俯仰于这样的宇宙之间,乐此最好的生命,虽其为欢愉也甚促……以为觉醒,以为视听,以为意想,遂无往而不盎然自适,迨其稍就安息,又以为希望,以为希望,以为回忆,亦无不悠然自得。……是以思想所涵若云容受神明,毋宁谓禀持神明,故默想〈神思〉为唯一胜业,其为乐与为善,达到了最高境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5页)[Aristotle,Xingershangxue(Metaphysics), trans.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275.] 《诗经》在这个意义上也就通向“天道”,其所要求的治学心性,也就必然是“定”“静”,由此而来的运思方式,也就是“格致”或“静观”,亦即《中庸》所谓“至诚”“至道”“至圣”“至德”之学,“《中庸》三言‘及其至也’,至人在圣人之上,与真人同归。”研读《诗》文,开辟“神游思梦、上征下浮”27 廖平:《诗说》,第57页。[LIAO Ping, Shi shuo (On Poetry), 57.]可兹对比的是,在廖平此说之前不久,鲁迅在早年诗学作品《摩罗诗力说》(1908)中以“神思宗”喻指西方乌托邦主义,还借屈原“上征”之语形容国民整体的文明进化。见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33页。[ZHAO Ruihong, Lu Xun〈Moluoshi lishuo〉zhushi·jinyi·jieshuo (Notes on Lu Xun’s “On the Power of the Satanical School of Poetry”),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21, 33.]的运思法门,追求《庄子》所谓“至人”之“进境”,28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二,第547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2, 547.]以“知天”为目标——这种与西人所谓形而上学志趣一致的治经态度,就是所谓“天学”或“孔经哲学”的实质内涵。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与后来的新文化人与新儒家相比,廖平的差异在于坚信经学通向至高沉思的“哲学”可能。因此,他不愿把形而上的维度拱手让出,任由中国学术一头扎进“六经皆史”的实证主义。29 刘小枫《六绎圣人赞》,载《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LIU Xiaofeng,“Liu yi shengren zan” (Six Interpretations of Saints’ Praise), in Zhe yidai ren de pa he ai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6.]又见李长春《廖平经学与中国问题》,载曾海军编:《切磋六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LI Changchun, “Liao Ping jingxue yu Zhongguo wenti” (LIAO Ping’s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Chinese Problem), in Qiecuo liu ji (Six Episodes of Learning), ed.ZENG Haijun,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6.]“天学”在这个意义上是廖平为古典经学智慧量身定做的一片“无何有之乡”的土地。唯有少数有哲学天赋的人,能够徜徉于其中,“‘质诸鬼神’,参赞化育,统诸道释各教”——这一切都“非数千万年后,《尚书》世界既已统一,不能见诸实行”。30 廖平:《诗说》,第64页。[LIAO Ping, Shi shuo (On Poetry), 64.]这样一来,廖平的问题意识显然并非其他同代学者那样被迫响应“家法”“时势”和“行动”的呼唤,而是要保守住能够唤起主动创造新时代之力量的那种唯一的、根本的因素——圣人之心的运思方式,保守住经学中最为宝贵的文明遗产,亦即少数圣人凭借“神思”和“上征”,为一切现实变局重新立法的“哲学”。
说到这里,廖平“天学”的基本志趣已经得到了澄清。但是,问题在于,后世学者瞧不起廖平的,正是他这种“圣人立法”的死脑筋:全世界都开始“走出中世纪”,走出“形而上学”的“迷信”,积极拥抱科学实证精神和历史进步意识,怎么还会有人觉得必须要靠维持少数圣人的神秘形象才能捍卫中华文明?如果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又何必需要近乎“封建迷信”的“天学”作为基础呢?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局势之下毅然投身政治革命的章太炎,不就将“六经皆史”的精神革命持续进行下去、甚至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风气吗?众多中国学人都知道廖平具有深厚学养和极高见识,那么,他们为何不愿意尝试去接受廖平“天学”的形而上学旨趣?这或许和民国以来的中国“时势”密不可分:近百年来面对“世界历史”所遭遇的屈辱和危机,怎么能容许有志之士把宝贵时光消耗在揣摩“天学”的悠然奥渺状态当中呢?
“天学”与文明大义
对于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学人来说,面临“现代性”时表现出危机意识,简直成了一种“惯例”。中国知识精英中的多数人则横向移植了这种意识。正是因为相信这种危机感应当为所有“现代人”分享,西方人列文森才会觉得廖平是一个异类,将他那“不材”的“天学”视为出于宗教体验般的“幻想”:“他把光明和纯洁归于天,而把黑暗和杂质留给了地。天是他的归宿所在。……为了摆脱尘世的黑暗与污浊,廖最终还是陷入了升天的幻想……”这样一来,廖平几乎成了一个向往超验彼岸生活的厌世者,与西方某些仅仅享受内在体验的修士或哲人一般无二。在列文森的西方之眼看来,廖平的唯一历史意义,可能就是启发了康有为的改制立宪思想;廖平本人则“脱离社会活动,专注于内在志向,在日益增加的幻想中离开了他曾与康有为和梁启超共同信守的今文或公羊儒学”,儒学在他那里,不再能够承担起在现代语境中指导实践的光荣使命。31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277—282页。[Joseph R.Levinson, Rujiao Zhongguo jiqi xiandai mingyun (Confucianism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277-82.]
熟悉西方思想史的人不难想到,这种评价曾经被用在一种思想潮流之上,那就是德意志浪漫派。进步诗人海涅就曾挖苦大施勒格尔“不理解使当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把棺装着过去时代僵尸的那些诗歌吹得天花乱坠”。32 海涅:《浪漫派》,薛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Heinrich Heine, Langman pai (Die Romantische Schule), trans.XUE Hu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111.]在启蒙精神席卷整个欧洲、甚至尝试为全球立法的关键历史时刻,浪漫派选择与现实历史进程保持距离的态度,倡导回到“中世纪”,回到“传统形而上学”。显然,廖平与浪漫派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朝“过去”看,都显得“不合时宜”。列文森或许正是想到了西方思想史上的这类不合时宜者,便将廖平视为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对应物”。其实,列文森的大前提和海涅一样:凡是不愿意积极回应现代性启蒙进程、不愿意发生“现代转向”的思想,都是“空想”。但问题在于,浪漫派实际上的确也开辟出了一条回应现代性的道路,甚至为后世如海德格尔这样的激进思想家“批判性地”继承,进一步发挥为“后现代”的思潮,影响深远。如果说不可低估浪漫派的现实意义业已是西方思想研究的共识,那么,廖平立足于中国文明根脉所提供的“人学-天学”方案可能具有的现实意义,或许也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浪漫派的思想因海德格尔与法国激进思想家的评述而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有复兴趋势,甚至正在悄悄推动新一轮的“历史大势”。我们今天若听信列文森一面之词,视廖平学说“无用”而抛诸脑后,会不会“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天学”或许是表达圣人之心的“微言”之学,但当廖平琢磨《诗》《易》时,是不是依然渴望着为现实中的国族寻求一种“大义”?在《地球新义》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如何凭借“天学”思维,积极走进“大九州”的世界。但是,“大九州”学说依然是“人学”范畴,相比之下,“天学”则始终“不能骤企,惟当深知其理,自有卓尔而立之时”。33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二,第577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2, 577.]如果说我们今天普遍的历史任务与百年前一样,是应对越来越多的现代性风险,那么,必然不可能得到普遍接受、充其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的“天学”,又如何提供“大义”、迎接“历史的检验”呢?
蒙文通曾在《廖季平先生传》中评骘先师之“天学”:
《鲁迅小说》总字数(tokens),据antconc统计,为122,971个(不含标点),单字(types)3051个。频度最高100字依次是:“的、了、一、是、不、他、我、有、在、来、也、这、人、说、着、子、里、上、去、大、得、然、到、个、么、们、看、时、便、就、那、而、还、又、出、没、你、要、道、但、自、她、都、家、和、只、见、起、地、为、下、头、以、可、阿、过、于、天、小、面、很、却、后、老、想、样、回、知、多、生、之、什、好、些、已、己、中、眼、经、走、前、两、似、事、太、年、四、所、心、声、几、十、从、三、吃、无、手、话、气、对”。
晚年来学者,悉诏以小大天人之说,语汪洋不可涯矣,闻者惊异,则益为奇语以嘲之,非沉思不易得其根荄,故世鲜能明其旨要之所在。……尝谓治经如蚁穿九曲,吾遇盘根错节,沉思每忘寝食,豁然有会,顿化腐朽为神奇,不笑不足以为道。世盖有疑之者,而亦未尝不震其精神闳肆也。34 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MENG Wentong, Jingxue jueyuan (The Origin of Confucian Classic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199.]
进入廖平的“天学”,必须“沉思”以至于“忘寝食”,最终在“闳肆”精神中止于“笑”。显然,这种状态并非多数人、甚至并非多数学者所能达到。重要的是,蒙文通指出,
六变之论皆由礼启,然变者枝末,不变者其根实也。并世学者从其不变者而屡变之,言人人殊,先生亦屡变不一定,乃不善学者即先生之变以求之,邃迷罔莫从钻仰。35 同上,第200页。[Ibid., 200.]
这也就启发我们看到,廖平虽然一生“六变”,晚年大谈“六合之外”,但其却有着不变的“根实”,那就是“礼”——人间世道的基本伦常尺度。我们不要忘了章太炎眼中那个“孝子”和“雅素”之人——廖平本人无时无刻不坚持着中国人的基本伦理尺度,以身作则彰显“礼”之精神,致力于学术,邦无道则隐,从未被新旧交替的“大势”所裹挟而迷失自我,作出不明智的政治选择。
“礼”属“人学”,与“天学”何干?也许应当这样理解蒙文通的话:作为“根实”的“礼”,其实是廖平运思中的最终落脚点和“人文关怀”。廖平其实相信,如果“天学”维度得不到安顿,“人学”也就显得缺乏高维度的目的论,遑论“礼”教?但如若“天学”失去了“人学”的坚固基石,也将失去其重要的现实关怀。唯有这样,才能理解什么是廖平的“平分天人”——这并不意味着“天学”应当与“人学”脱离,而是说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这就和海德格尔与后现代主义者截然不同——他们相信只需以“人”统“天”,让“形而上学”服从于“实践哲学”,即可获得“诗意的栖居”。36 刘小枫:《海德格尔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页。[LIU Xiaofeng, Haidegeer yu Zhongguo (Martin Heidegger and China),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11.]
2)节能项目投资收益明显。“十二五”期间中国海油开展了650个节能技改项目,累计投入17.53亿元,年收益9.74亿元,平均投资回收期仅1.8年,经济效益明显。
章太炎显得和钱穆看法一致,都不喜欢廖平的“怪”。问题在于,在钱穆眼里,章太炎也是一个“立论怪诞”的新派学者,幸好其大多数思想影响不太大,“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7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92页。[QIAN Mu,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ba)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8),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392.]这也启发我们回想起来,“杂取梵书及医经形法诸家”,并非廖平一个人的专利,而是在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近代思想家乃至于章太炎本人的文辞中俯拾即是的特征。其实,大凡智术高卓之古人,倾心佛老诸子,旁采众长,并非什么不为人所容的事情,司马迁、董仲舒、韩愈、苏轼、王夫之等,莫不于经学儒术之外博采他山之石,这并不妨碍他们列席醇儒宗谱。但即便是博采众家之长、甚至曾在《原儒》中大声疾呼“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为术士”8 章太炎:《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姜玢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39页。[ZHANG Taiyan, Gegudingxin de zheli: Zhang Taiyan wenxuan (The Philosophy of the Revolution: Selected Works of Zhang Taiyan), ed.JIANG Yan,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1996, 339.]的章太炎,也无法接受晚年廖平“出儒术外”的“谲奇”,以至于在墓志铭中将廖平比附为“超神人”,给予这样一段带有“敬而远之”感情色彩的评价:
故先文明而后野蛮者,此为经说之递降,为孔子推极于大同之世,而想象其郅治之隆,勒为成书,以为后王法。而先野蛮而后文明者,此为人群进化必不可逃之定率,实中外之所同然。……荀卿曰: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于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能属于礼义,则归之王、公、士大夫。……人禽之别,端在于礼,由是进化之程序,始可得而言。37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八,第515—516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8, 515-16.]
孔子的立法根基由“天学”的推演机制所提供,是一种朝向未来的积极哲学规划。走进《诗经》,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圣人的“哲学”之心,进而明白,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文明,并非业已湮没的上古实存,而是需要我们去共同实现的未来理想。“人学”则在这个意义上才具有现实意义——否则,人们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感到“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华夏文明古代如此光辉,却还是最终在历史的“伟力”作用下走向衰败,既然如此,坚守礼法经义又有何用?《春秋》《尚书》如果只是古之史料,没有其他资源沟通其与“天道”的整全秩序,那么其中的“法”和“礼”也就决计不会对不可知也不可测的未来产生价值规范作用;在古文明史就此失效后,当然只有凭借具体处境下通过偶在经验和历史理性生成的实践智慧,才能帮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为了避免这种失却传统智慧依据的“无根”状态,经学大师廖平会认为,只有继续坚守通达圣人之心的“天学”,华夏文明才会在现代语境中获得目的论的奠基,“人学”才会获得权威并发挥现实感召力,礼乐文明的香火才能在一切新时代的变局中得以延续。
西方进入“现代”以来,以历史的、实践的理性取代形而上学关于万物整全秩序的自然理性,颇类似中国古人所云的以“权”胜“经”。即便如此,西方依然有一些明哲如施特劳斯、洛维特等试图通过重新调整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缔造出能够为后世师法的新精神体系。同样面对着“世界历史”所提出的复杂艰巨的思想难题,廖平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尝试制作“天学”,显然绝非仅仅出于“智虑过锐”的哲人天性,而是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旨在为中华文明的未来崛起提供既能与西方的进化论历史哲学与地缘政治意识分庭抗礼,又不与传统自然-宗法秩序决然割裂的理论进路:
西人每笑中人自以其国为天下者,实由秦始作俑。邹子虽有周礼海外大九州之说,不能夺也。西人又谓中国不进化,由战国至今二千年,文明程度未能大进,中儒亦深信其说。……所谓夏、殷、周即三世之符号,文明程度以渐而推,继长增高,此一定之势也。……儒家者流,谨据经之明文,必欲行三年于当时,人民爱亲之心未能及此,故有名无实。儒家之无德行事,躐等凌次也。墨与儒同出孔子,乃坚持三月,以久丧为非,合人情,因时宜,所以墨学大行,儒学反绌。然使人尽从墨说,则有层次无完全,百千万亿世后,无以为进化之准则。墨行于当时,儒垂于后世,一始一终,并行不悖。38 同上,第570页。[Ibid., 570.]
认为中国封闭自大、无所进变,是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固有偏见,并在清末透过西学的传入影响到中国读书人看待中国的视角。为了对此有所回应,通过引入“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的三世质文损益说,廖平为中华文明的“开放”视野和“进步”意识找到了凭据。廖平依据质文循环损益之说,将晚清托“墨学复兴”之名广纳西方现代学说的思潮视为与儒家同样源出圣人之心的“权宜之计”,将其安放在进化之初的位置,确立其必要性的同时,又以其无法推动“进化”为由,保守住了儒家经学虽然“有名无实”,但能朝向“后世”的崇高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儒学不再是复古之学,而是朝向未来的“新文化”之学。
在早年的《知圣篇》中,廖平早已阐明了他解决中西文明冲突问题的“质文相救”义法,并预先揭示了作为“天学”的《诗经》经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地质勘查管理司、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沿海11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有关地质勘查单位,沿海有关城市人民政府,原武警黄金部队有关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部室和直属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鲁商”二字即“文质”,“文质”即中外、华洋之借字。中国古无质家,所谓质,皆指海外,一文一质,谓中外互相取法,为今之天下言之,非古所有。……《诗》以《鲁》为文。《商》为质。(文主中国,即六歌之《齐》;质主海外,即六歌之《商》)至新周合文质,乃为极轨,所谓“文质彬彬”也。孔子因旧文而取新义,其意全见于《诗》。《诗》者,天经之始基也。39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一,第201、205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1, 201, 205.]
百达翡丽于北京开幕十周年之际,宣布其世界时腕表东八区代表城市将从 2019 年起回归“北京”,以向历史致敬!
在“质文相救”义法当中,儒家“无德行事”导致礼教虚文日积的弊端将为“因时宜”的墨家(西学)之“质”所救;而墨家(西学)“有层次无完全”的实践功利主义又将为未来之“文”所救。最后,廖平告诉我们,《诗经》当中正体现着孔子“质文相救”的义法,也是揭示“文质彬彬”理想境界的核心经典。的确,“天学”需要“人学”的积淀,但若要让《春秋》《书》《礼》呈现出在当代的重要规范性意义,必须在《诗经》中找到“文质彬彬”的理想范式。“天学”在这个意义上,提供的是让“人学”在当代产生效用、继续“进化”的思想蓝图。
廖平绝非食古不化,也绝非要刻意引发“经学的瓦解”,毋宁说,他渴望开辟出中国学术的新一轮气象升平,荡除时弊、重整人心的同时,推进“实事求是”的学术积淀:“西学日精,中学则日坏。……愿中外各去骄心,实事求是,既有导师,则不似从前之自辟蹊径,苦无印证,彼此会通,形神交尽。”40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卷八,第586页。[LIAO Ping, 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 vol.8, 586.]通过在历史危机时刻号召“改文从质”,廖平指出了中国学术应当分为“权”“经”二端,其中,积极学习现代知识是为“权”,保守圣教遗风是为“经”:“学人之事,官吏主之;教人之事,师儒主之……百僚当北面,师考其养育富强文明之治功;师儒一如该国,立校讲学”——相比起汲汲于治国理政,儒者经师的任务更应当是通过普及华夏之“文”——礼乐秩序,使“西人渐染华风”,在未来某一天服膺于中华文教之广博精深。41 同上,第352页。[Ibid., 352.]要让这种“文”之教化得以传承普及,处于民族危难历史时刻之中的向学青年也就必须走进“天学”、俯仰《诗》《易》之理,驰骋“六合之外”,想象天下秩序,在积极吸收西学、促进国家富强文明的同时,保守圣人之心,保守礼乐文明的形而上基础,为来日走向“世界”、走向“大同”的“理想制度”做好准备。这就是“天学”作为经学,同时作为新时代青年实践哲学的大义。
余论
廖平之所以是《诗经》研究谱系中一个不受重视的人物,42 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20页。[HONG Zhanhou, Shijing xue shi (Hist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620.] 提及廖平时寥寥数语带过,并认为其在“阐申大义方面更无可举述”;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XIA Chuancai, Shijing yanjiushi gaiyao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7.]丝毫未论及廖平。大概和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史之学延续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路径,重视历史考据和起源性辨识的思路有关。无论“信古”还是“疑古”,都将古典学问视为“古”之“遗产”,仅仅作为凝聚国内民心以求“自保平衡”的“幻象”铺垫。43 章太炎:《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第275、276页。[ZHANG Taiyan, Gegudingxin de zheli: Zhang Taiyan wenxuan (The Philosophy of the Revolution: Selected Works of ZHANG Taiyan), 275, 276.]直至今日,《诗经》研究的主要趋势一方面是古史辨-神话人类学进路,或是继续“疑古”,或是通过诉诸“先民”的“抒情”力量而为一种先于诗教的“文学性”提供奠基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强调温柔敦厚的伦常诗教,但由于切断了孔子诗学可能具有的“天学”维度,显得像是在单纯“宣教”,而无应对当代时势的灵活意识。可以说,是一百多年来踏入“现代性”旅程的历史紧迫感带来了这两种《诗经》的解释方向,而其共同丢失的,恰恰是那“天学”背后积极投射未来理想政治的意涵。这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的研究发展来说,显得格外遗憾。如果我们意识到西人文艺美学思想背后总是站立着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不断沉思“未来”的大哲学家,那么,也就没有理由任由中国的文艺传统继续在“时势”中随波逐流,而应当回过头去挖掘文明温床内在蕴藏的“哲学”珍宝,重视其中沟通古今、灵活变通的经权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经学还是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实证史学的角度出发),借助廖平的提示,找回“天学”的可能性,为“人学”的发扬光大提供心智修养上的宽裕空间,显得尤为必要。在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一家独大的时代,“天学”的再次显现,可能需要一系列否定性的论说方式来凸显:在仅存僵化习俗、不存通变理想的“家法”之外,在只有被动接受、没有立法心志的“时势”之外,在短视冒进、而非审慎熟虑的“行动”之外,通向整全自然的“天学”方会显现其面容。在“左”和“右”、激进与保守依然争执不休的今天,廖平的名字虽然几乎已被学林所遗忘,但其在古今文质交替之际沉吟所得的“天-人之学”的调和方案,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为有心人提供一条入门蹊径,一窥古典天人秩序,为新时代的中国开辟自然与历史汇通的思想之路。
Bibliography 参考文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
[FENG Youlan.Zhongguo zhexue shi (xi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I).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47.]
海涅:《浪漫派》,薛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Heinrich, Heine.Langman pai (Die Romantische Schule).Translated by XUE Hua.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HONG Zhanhou.Shijing xue shi (History of the Book of Songs).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黄开国:《廖平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
[HUANG Kaiguo.Liao Ping pingzhuan(LIAO Ping's Biography).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5.]
李长春《廖平经学与中国问题》,载曾海军编:《切磋六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
[LI Changchun.“Liao Ping jingxue yu Zhongguo wenti” (LIAO Ping’s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Chinese Problem).In Qiecuo liu ji (Six Episodes of Learning).Edited by ZENG Haijun.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6.]
廖平:《廖平全集》(巴蜀全书版),舒大刚、杨世文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LIAO Ping.Liao Ping quanji (Bashu quanshu b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Bashu quanshu Edition]).Edited by SHU Dagang and YANG Shiwen.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诗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Shi shuo (On Poetry).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Levinson, Joseph R.Rujiao Zhongguo jiqi xiandai mingyun (Confucianism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Translated by ZHENG Dahua, REN Jing.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
[LIU Xiaofeng. Zhe yidai ren de pa he ai (Ti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6.]
——:《海德格尔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Haidegeer yu Zhongguo (Martin Heidegger and China).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MENG Wentong.Jingxue jueyuan (The Origin of Confucian Classics).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QIAN Mu.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shi (xia)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II).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 Zhongguo xueshu sixiangshi luncong (ba)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s 8).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王锐:《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WANG Rui.Zhang Taiyan wannian xueshu sixiang yanjiu (Studies on ZHANG Taiyan’s Academic Thoughts in His Late Years).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XIA Chuancai.Shijing yanjiushi gaiyao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Book of Songs).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Aristotle.Xingershangxue(Metaphysics).Translated by WU Shoupeng.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章太炎:《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姜玢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ZHANG Taiyan.Gegudingxin de zheli: Zhang Taiyan wenxuan (The Philosophy of the Revolution: Selected Works of Zhang Taiyan).Edited by JIANG Yan.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1996.]
——、刘师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LIU Shipei.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shi lun (On China’s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
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ZHAO Ruihong.Lu Xun 〈Moluoshi lishuo〉zhushi·jinyi·jieshuo (Notes on LU Xun’s “On the Power of the Satanical School of Poetry”).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摘要:廖平于新文化运动至“五四”时期开展的诗经学研究被他本人视为“天学”,构成其后期学说的核心内容。然而,廖平的同代和后世学人大多认为“天学”或是有违经学“家法”,或是脱离“时势”需求,或是于现实“无用”。通过回到廖平本人后期思想转变的意图和志趣,发现其对圣人哲学精神的继承,明确其响应中华文明危机的问题意识和通过“改文从质”达到“文质彬彬”的义理构想,“天学”之于新时代的真实意义方能得到揭示。
关键词:廖平;天学;经学;哲学;诗经
LIAO Ping’s Cosmological Hermeneutics o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ry- Material Statuses
FENG Q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LIAO Ping invents a cosmological hermeneutic on The Book of Song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o fulfill his later teaching about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However, most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believe that this hermeneutic goes against the orthodoxical doctrine of classical reading, or beyond the historic demand, or away from the secular practicability.Returning to the intention and interest of LIAO Ping’s later thoughts can help to reveal his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consciousness of the crisi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LIAO Ping’s philosoph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ry-material status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illustrate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his cosmological hermeneutic for now and the future.
Keywords: LIAO Ping; cosmological hermeneutic;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Confucian philosophy; theBook of Songs
trustvision@163.com
Notes on Author: FENG Qing, born in Chongqing, PhD,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ngaged in research on comparative aesthetics,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y of ideas.
*投稿日期 Submitted Date: Mar.8, 2019; 接受刊登日期 Accepted Date: Apr.22, 2019.
作者简介:冯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讲师,学术兴趣集中于比较美学、文艺理论与思想史。
标签:章太炎论文; 经学论文; 中国论文; 诗经论文; 孔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