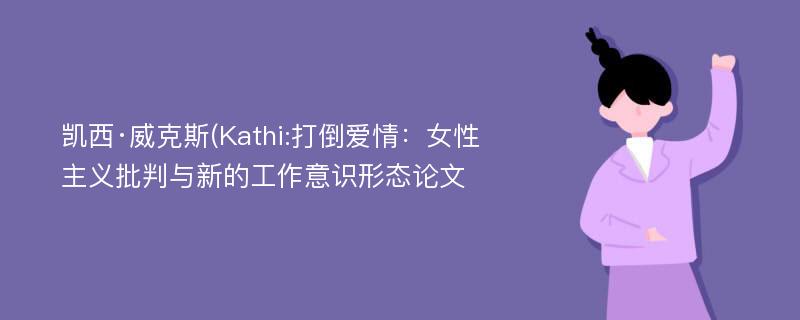
摘 要:文章借鉴了1970年代女性主义对爱情与罗曼司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对“大众忠告作品”(popular advice literature)的批判,这些作品试图引导员工在工作中去发现爱和幸福。在异性恋父权制资本主义的语境下(1)advice literature指的是向统治者建言献策的作品,这里指的是向大众提供忠告和建议的作品。另,原文斜体字翻译为中文时用黑体。——校者注,浪漫爱的意识形态不仅像过去一样把家务劳动指派到妇女头上,还被用来劝诫所有雇佣工人,让他/她们与工作结成更亲密的关系。
关键词: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 幸福; 爱;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工作伦理
过去一般认为,“爱”和“工作”分别在各自性别化的领域内运作。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内,我们坠入爱河,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当我们迈入雇佣工作的公共领域,我们就来到了经济合同的世界,用劳动换取收入。至少一般故事里是这么说的。19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向这一制度模式和社会想象发起了有力挑战。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私人家庭其实是经济体系中一个被遮蔽的组成部分,并且将家庭视为对于生产性劳动来说必不可少的再生产性劳动的首要中心,同时也将其视为一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工资得以分配给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人或出局者。女性主义由此证明:工作和家庭这两个领域并非彼此独立自主,而是互相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对雇佣劳动的批判也得到了修正,从而让这些批判适用于家务劳动和家庭内再生产关系。举例来说,1970年代“家务劳动有偿化”的提倡者把有偿劳动的经济当成一个镜头,透过它去反思家庭这个机构:他们将许多在家庭环境中进行的活动称为“工作”,以此让家务劳动变得和生产性工作一样引人瞩目(其中一种方法是强调家务劳动理应得到薪水),但与此同时,她们又强调家务活动没什么好热烈庆祝或肃然起敬的(这毕竟只是工作)。就这样通过各种方式,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成功地将此前一直无人关注的家庭、婚姻、异性恋爱情和罗曼司置于学术批判的耀眼强光下,并且去对抗意识形态的神秘化(mystification)、自然化(naturalization)、个体化和浪漫化的种种模式,而这些模式一直是让这些制度远离批判的挡箭牌。
班主任工作漫长琐碎繁杂,到了期末,最头痛的事莫过于写期末评语了。有些老师老老实实一个个地手写,耗时长而且费脑;有些老师就把学生分成几类,只需要几个模板套话一抄,也省了很多事,但太不尊重学生个性了。还惊见网上传有某老师把评语写成诗歌,整齐押韵,清新激情,但这对老师本人的文才要求太高,是不可模仿学习的。针对此现象,在长期的班主任工作中,秉着尊重学生个性与事实的原则,我想到了对期末评语的尝试改革,开展了一次“发现你我之美”的主题班会。
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方式——如通过揭示家庭与工作之间紧密而非对立的关系,利用各自独立的两个领域(家庭和工作)的模型并将其打破——的早期发展时,我们虽然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今天我们生活在新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批判性方法。这个新时代或许可以简单概括为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过渡的时期。当代后福特主义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种不同的雇佣关系以不同方式都具有了传统的女性工作形态的特征。正如很多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所发现的,女性主义者所阐述的女性劳动的环境,在今天已经成为普遍的工作环境。举例来说,试想一下,过去在许多产业工作(industrial job)中一向泾渭分明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包括心灵和灵魂的劳动(labors of the heart and soul),都在后工业生产中融为一体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灵活性、照看性、情感性、充满合作精神和沟通意识的女性化模式现在成了理想员工的特征,福特主义时代女性的工作在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中可能已经变成了主流,而非补充。
这些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是,员工的主体性被越来越多地折叠进或融合进“员工”这一身份认同之中。为了将工作塑造成身份认同的核心,必须首先在自我与工作的关系之中重塑自我。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由于模仿家庭内照看性劳动的缺乏边界,在当代经济中,过去用来区分工作与非工作时间、空间、行为和关系的公认边界已经被打破。带薪工作及其价值前所未有地支配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平均只能活27 350天”,一份职场成功学指南宣称,“其中有10 575天用于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一个现实,即“生活和工作在本质上是相连的,不是两回事,而是一回事”。过去,人们认为“冷酷世界”(工作)和“温暖港湾”(家庭)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而在当下这颠三倒四的时期里,这两个领域日益搅在一起,并随之产生了一些有趣也令人不安的后果。1990年代末,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发现,很多人颠倒了对于工作和家庭的情感投入,结果是很多人(在工作场所)工作时感觉是在家里,而在家里时则感觉是在工作(工作场所)。[1]最近,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在她的新书《与工作的亲密关系》(Work’sIntimacy)中写到,许多员工与工作产生更为亲密的关系,并且用罗曼司式的叙事去传达他们对于工作的热爱,以及从工作中得到的幸福。[2]
最后提到的这种趋势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为今天的管理话语似乎已经对爱和幸福着了魔。时髦的管理和职业咨询公司告诉我们,工作中的爱和幸福对老板和员工都有好处,为了获得这种情感重建和情绪规训,员工——这些管理和咨询公司没完没了地重复,只有员工能做到——所需要的不过是“单纯的狂热”。他们鼓吹做自己爱做的事,学会用十个简单步骤来爱上工作。与你的工作坠入爱河,甚至学会爱上你最痛恨的工作,工作的未来是美好的。史蒂夫·乔布斯,这波浪潮中最励志的人物,他那段最常被引用的名言,可谓这类作品的高度凝练:
工作占据了你的大部分生命,所以,想真正得到满足就必须选择一份自己认为很棒的工作。而从事一份很棒的工作,首先必须热爱这份工作。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继续寻找。别急着将就。全心全意去寻找,找到的一刻就会豁然开朗。并且,与其他美满关系一样,还会一年更比一年好。所以,继续寻找,不要停下,直到找到它。[3]
听力材料的篇幅长度,语速的快慢程度,音量和语音的清晰程度,是否存在不同的口音,句子的长短,材料的类型已经材料的主题都会在不同程度影响听者对材料的主观理解。听力材料中的内容熟悉程度也是影响其听力的理解的重要的因素。学生普遍反映如果听力材料涉及金钱,财务或者管理方面的内容,在背景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帮助下,他们听力的兴趣大增,听力理解能力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学生提及听力材料若涉及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交流,比起专业的学术的讲座更易于理解,更能激发其听力的热情。
正如德光美亚(Miya Tokumitsu)所言,“幸福,爱,激情与自我实现,这些就是今天的职业美德”[4]。
除了实现让不平等关系神秘化的经典意识形态功能,女性主义者发现,“爱与幸福”的话语还遮蔽了经济动机和经济效益,并对此进行了探索。一般认为,作为起源于私人家庭且以传统形象出现的浪漫爱,与属于公共领域的经济利益和竞争是截然相反的。这种浪漫叙事长久以来把婚姻呈现为一种非经济的关系,将无薪的家务工作编码为非工作、一种“爱的劳动”,这种劳动维系着家庭的完整,使其成为无情世界中的补偿性理想和避风港湾。弗里丹试图揭示无薪但幸福的家庭主妇这一形象的虚幻,正如莎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所言,这种表征意味着“用幸福的表象掩盖劳动的痕迹”[12-13]。1970年代一句激进的女性主义标语,很好地概括了浪漫爱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当作工作招聘的伪装机制:“以你投入他的怀抱为开始,以你踏入他的厨房而结束”。因此,如费尔斯通所描述的,浪漫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不断强化劳动分工的文化工具,这种分工对性别-阶级体系是根本性的。
如果说新教式的工作伦理可以被理解为资产阶级反复宣传、灌输给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当下“工作中的爱与幸福”的话语则无疑在专业人士和管理阶层中获得了强烈共鸣。不过,当这种工作伦理作为不容置疑的价值观在美国文化中越来越广泛地传播时——也包括雇主、公职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这项强制性热爱工作、享受幸福的“使命”,恐怕越来越像文化脚本和规范理念一样充满霸权意味。它宣称员工将在工作中获得有意义的快乐,但实际上未必如此;它并不符合多数雇佣关系的真实情况,尽管如此,这些都不能阻止贯穿于工作中的“爱与幸福”之理念形成一套更为广泛的文化标准,让一波又一波的雇员深受影响。为了在这样的劳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勉强保住(就甭提保持领先了)一份工作,我们必须或多或少地去适应这些不断影响着劳动等级制的职场情感规则和情感期待。这究竟意味着雇员是用深度伪装的变身效果(transformative effects)去满足老板对“幸福员工”的期待,还是仅做做表面功夫表示认同(“深度伪装deep acting”和“做表面功夫surface acting”这两个概念是霍克希尔德提出的)[6],取决于这位员工在职场角逐中的具体位置。不过,由于劳动与资本的力量平衡在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中的转变——这让雇主能够游刃有余,对越来越多希望持续就业的未来员工而言,就得在热爱工作和在工作中获得幸福方面多多下功夫了。
再一次,女性主义对爱的分析为我们研究主体性重建的计划提供了关键方法。毕竟传统的异性恋父权制女性范式不是将爱情视作女性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看作女性的本质所在。波伏娃在提出,“爱你的工作”话语可能会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并且重新归纳了一般所认为的如下差异:即男性仅仅将爱情视作生活中的“消遣”(occupation),而女性则视其为“生命本身”。对费尔斯通笔下的那些女人来说,没有爱情与幸福的人生根本算不上人生,她们不断索取爱情,为的是证明自己作为女人存在的意义。于是,渴望浪漫爱被想象为深植于女性的主体性结构之中,女人们除了被稳稳地安置起来以外什么都不需要,婚姻和家庭就足以确保这一点。正如波伏娃所描述的,这些寻找爱情和婚姻的女性“如此热忱地选择被奴役,对她们来说,仿佛这就是自由的表达”[11]。毕竟,“最为优雅的社会控制形式”,基普尼斯在她那本充满争议的《反对爱情》中提醒我们,“是那些伪装成个体的需求和满足感的东西,它们与个人心灵的结合如此紧密,以致任何与之对立的冲动都显得像是不招人爱而产生的焦虑”[9]。以此类推,谁不想在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更多的爱与幸福?尤其是当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工作糊口的时候。培养对工作的深厚爱意,并且让这种爱意堪比老套观念中女性对浪漫爱的向往,这或许已经够野心勃勃了,但它只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一长串结构—主体—基础—调节程序链上的一环。在这里也一样,目标据说是在充分展现个体自由的同时,创造出——如德光在解读那句福音般的“做自己喜欢的事”的规训功能时所说的——“热烈拥抱自己被剥削事实的劳动力”[4]。
现国内外基于上述基本原理的钢性钻孔弹模计已有近十种,其中美国的Goodman钻孔千斤顶最为常用。但由于Goodman千斤顶承压板纵向弯曲、钻孔孔壁与承压板曲率不匹配等问题,实测弹模值严重偏小。针对其不足,长江科学院岩基所基于Goodman钻孔千斤顶,研制了CJBE75/91-II型新型钻孔弹模计,增大了承压板刚度,加大了变形测量范围,提高了位移测试精度,其最大变形量测量范围为15 mm,位移传感器精度可达千分之一毫米[14]。
不过,在这些作品所提倡的情感和情绪管理中,还有更多特殊的主体化模式值得研究。实际上,他们指导员工去培养的是一种投入和疏远并存的复杂心态:爱且只爱工作,但不要在某个特定的雇佣关系上过于投入,而是像不断配对拆对重新组合的婚姻那样,准备好一生一世工作。这显然是不稳定就业环境中的生存秘笈;目标不是爱老板,爱公司,甚至不是爱你的职业,而是达到一种情绪上的灵活和情感上的温顺心态。做一个敢冒险的人,别再守着安乐窝,一位作者这样建议,毕竟,“太多安全感对你的创造精神有致命危害”。我们不能把雇佣关系误认为是照护关系;相反,我们应该期待并欢迎那种暂时、不稳定、根本无法让我们全情投入的工作。职场励志文学似乎就是靠教人“爱上恋爱”和“因为有能力感受幸福而幸福”来赚钱。这些作品描绘的爱情和幸福,并不是依附于某个特定对的情感活动,而是一个存在于主体内部的源泉,理论上是绝世而独立的。爱可能与浪漫情侣分道扬镳,但不会与其他对象相结合。爱和幸福总是延迟到来。在“对幸福的期待中,”艾哈迈德发现,我们希望“与和它相关的一切产生联系”[12]。宾客利描述了这类作品如何将幸福等同于追求幸福的行动能力。[14]漂浮于时空中的爱情和幸福,是无限的资源。与之接近的理念类似于某位作者称之为“情感忍者”的存在,这些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以有利自己的方式运用情感。或者读者可以将眼光放回自己身上,把工作看成一种“自爱”的行为,把我们感受幸福的能力当作幸福的源泉。因此,他们建议大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有生产性的个人”这一身份认同上来。最终,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是否深爱工作,而是把自己包装成爱工作的人,或至少沾一沾那些爱工作的人周身散发的光芒。
一、作为企业宣传的意识形态
任何批评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将耳熟能详的东西变陌生。女人都应该体验的浪漫爱究竟是何物?特-格蕾丝·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带着她那“优雅的天真”(cultivated naiveté)进行了思考:是歇斯底里、不顾一切,抑或狂暴迷乱?[10]若想对这一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势必要与那些关于爱的普遍常识保持一定距离。不过,相比“什么是爱”,更紧迫的问题是爱如何运作以及它产生何种效果:爱如何激活性别化的主体,它服务于何人的目的与利益?“爱情这个现象”,费尔斯通问到,到底是“如何运作的?”[5]我们应该期待着陷入爱情,然后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召唤;我们要认清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如何运作,服务于何种目的。女性主义者通过以下方式将浪漫爱和幸福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作为宣传手段,作为神秘化,作为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和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我们会发现,每种方式都为“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话语提供了批判性研究的路径。
将爱与幸福的意识形态描述为一种类似于宣传的东西,可能是这里面最缺乏说服力的表述。假设统治阶级的观念与整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则主导阶层可被描绘为一个统一群体,主动且有意识地将他们自身的利益伪装成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费尔斯通将浪漫主义描述为“男性权力的工具”,由此引出了“工具性权力”(instrumental power)(2)Instrumental power一般形容个体因其位高权重,拥有高于他人的权力,而这一权力从根本上又用来增强及维系他们的权威。 这一略显呆板的因果关系范式,[5]这种模式在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中频频出现。当然,这并不是这类研究中最强有力的版本,也不能代表197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准,但这个粗糙的意识形态批判仍与我的研究颇有关联。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道“爱你的工作并且感到幸福”的命令,个中原理十分简单明了:就是让你多卖力。管理大神(gurus)会告诉你,爱与幸福是能量、专注力和动力的无尽源泉。我们怎么才能爱上并享受工作呢?典型的回答是:再多承担些责任,再多些参与,再多学些技能,再多考些证书,让游戏不断升级。幸福地工作“是一种能让你最大程度地展现实力和激发潜力的思维模式”,正如反复提到的那样,“与生产力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雇主们可以放心,“幸福感对生意大有好处”。在这种形式下,所有的忠告都只不过是在重复宣传的模式:有意四处传播某种思想,以便达到有利于自己的效果。浏览相关文献,就能看出许多颇为拙劣的灌输手法了。
二、爱与幸福之谜
我们转向更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女性主义者将其用在对“浪漫爱和幸福”意识形态批判中,重点聚焦于它的神秘化功能。根据这些理论,至少有两个重要事实被遮蔽了: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异性恋罗曼司意识形态掩盖了父权制下的不平等。激进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流行的爱的版本,已经被政治性地用来作为掩饰男性与女性之间压迫关系。这一深刻的洞察力对我们今天的研究颇有帮助,因为“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这套话语在掩盖阶级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包括雇佣合同中双方达成的虚假平等,以及驱使着员工辛勤劳作的权力关系——方面十分有效。实际上,浪漫爱的语言为合同双方承诺了一个格外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然后,这一纽带能让那些在管理上被认定为下级身份的成员热切服从,而他们获得的奖赏是可以沾沾自喜地沉溺于那美妙诱人、明确无误的“我们”二字所传递的归属感中。西蒙娜·波伏娃——19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者最推崇的思想家——绝妙地将这些被管理者比拟为恋爱中的女人形象。[11]事实上,关于“工作中的爱与幸福”的作品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坚持利益一致性,让雇主和员工都能从情绪改造和情感训练中平等受益。为了兑现这种“互惠”主张,典型的作法是,将爱与幸福所带来的健康——作为某种不容置疑的中立价值被推销给读者——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放在一起不断进行强调,仿佛是在有些人认为值得赞赏的生产效率增长有益于组织的收益,而不是其人力资源时,可以以此来证明这种互惠的观点。
尽管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过去付出了诸多努力来促进各国会计准则的一致性,但仍然困难重重,仍有诸多问题等待商讨与解决,在这个漫长的协商过程中大大阻碍了全球经济发展效率与资本流通,而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菲利斯·莫恩(Phyllis Moen)和派翠西娅·勒林(Patricia Roehling)称之为“职业奥秘”(career mystique)的早期版本——这个奥秘理想化了福特主义雇佣合同——依赖家庭内的“女性奥秘”在其背后的隐形物质支持和意识形态掩护,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对这种奥秘进行了有力地揭露。现如今,新版本的“职业奥秘”歌颂理想的后福特主义雇员的情感投入和企业家精神,它依赖于另一种众所周知的“女性奥秘”,这种奥秘赞美浪漫爱的幸福狂喜,将其视作女性满足感的本质。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她的杰作《性别辩证法》(TheDialecticofSex)中批判了“女人为爱情而活,男人为工作而活”的老生常谈,[5]但这句话现在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现在人人都得热爱工作。这样一来,在异性恋父权制资本主义的语境下,源自不同领域的浪漫爱的意识形态,那种理想化和女性化的爱情模式,不仅继续用来给女人指派家务,还被用来维系员工与雇佣工作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
作为所有工作形式中最有代表性的范式,雇佣工作不可能因为爱而神奇地转变为“非工作”。不过,也不是说“工作中的爱与幸福”就不能被用来淡化作为创收活动的带薪工作所具有的经济上的理由。纯粹的工具性理由——用劳动换收入的经济交换——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立足,这是资本主义工作意识形态所导致的最主要后果,因为新教工作伦理宣称辛勤工作是被拣选的基督徒的身份标志。这些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的新形式——或许还有它们的目的,是将作为创收工具的带薪工作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去工具化(deinstrumentalize),把经济上的不得不然重新编码为个人自由。当下的这类作品坚称,金钱既不是工作中爱与幸福的源泉,也不是衡量它们的标尺。这类作品的作者能够同时锁定管理者和员工(而且尽可能让我们认同于后一范畴),尽力强调经济之外的动机和奖励。“过去,工作对我们来说就是谋生”,一位作者说,“渐渐地,工作的目的是寻找快乐”。令雇主高兴的是,金钱不一定是员工从事漫长而艰辛劳动的重要动机。更高的报酬并不能让员工更加幸福;金钱买不来爱。这种唯利是图的经济算计,这种小市民锱铢必较的心态,与真正的爱和真实的幸福毫无关系,也不应有关系。爱并不要求报酬;爱是无穷无尽的个人资源。实际上,按他们提出的一些说法,带薪工作的工具性应该被反过来看待:那些忠告作品告诉读者,工作不是为了支撑生活,同时还指导他们如何为了更有效地工作而调整生活。一位作者甚至催促那些爱上工作且将要获得幸福的员工学习有效打理自己的钱财,这样就不会有财务上的担忧让他们分心,或影响他们无法享受工作了。
当这些书的作者试着提出(哪怕是拐弯抹角地),一份工作有哪些特质值得读者去爱、去感到幸福的时候,往往就会变得很尴尬。尽管很明显,这些书主要针对的是高收入工作者,但作者都会尽量广撒网,不管是分享经验还是提出建议,都尽可能让自己的文字适用于所有员工。现在,一般可能会认为,工作的本质——薪资水平,每日劳作的愉快与痛苦,特别是其所输出的社会价值——决定这份工作是否可爱,员工能否从工作中得到幸福。但这些作者在这些问题上却一带而过,随便给点敷衍了事的意见。举例来说,一位作者讨论当工作侵犯了员工的道德准则时,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才分析到一半就不了了之了。除了建议他们培养自我意识、遭受磨难后进行自我保护,作者还重点建议当事人调整好心态,从出色完成工作、做一些有价值的小事中寻找意义,尽管可能只是一天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善意行为。我们必须培养出一种我们正在造福世界的感觉,因为相信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有积极影响,能够最大化我们工作时的信念。必须对异化说不:“不许再说你的公司毫无意义或者我的工作毫无意义”,我们就是自己工作之社会价值的仲裁人:“是否有意义,在于我们的选择。”
三、个体化和去政治化
或许正是因为费尔斯通讨论的主要范畴——性别-阶级——将性别置于与阶级等量齐观的位置,她提供的一些工具也的确可以用来分析经济上的等级制。有趣的是,费尔斯通还声称“浪漫主义的发展程度,与女人从其生物学特性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是正相关的”[5]。过去,经济上的强迫和严格的性别规范足以维持(再)生产性劳动的性别体制,但是,随着“性别阶级的生物学基础的崩溃,男性至上的权力只有靠人为的制度或夸大旧有的制度来维系了”[5]。因此,正如费尔斯通以其标志性的嘲讽口吻所形容的那样,“看来我们得帮帮她了,小伙子们!”再给她来一剂意识形态的迷魂药吧。[5]
Three randomized trials have indicated a participation rate for FIT approximately 60%,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FOBT[9-11], while the reported overall participation rate in the FIT studies ranges widely from 17%-77%[8-12].
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这一意识形态,还通过阻碍集体主义的形成、破坏团结的方式,将雇佣关系去政治化。所有教我们从工作中得到爱和幸福的方法都有个最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建议我们远离其它社会关系。停止“过度社交”,一位作者忠告说,别把时间花在“耗光你能量的人”身上,相反,要学着与这些“分心的事”一刀两断。团结于是被重新编码为一种病态,且并非巧合的是,同时也被视为女性化的相互依赖。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所提出的这种深度的个体化,比方说建议员工将个人情感和判断力集中在如下方面:让自己随时都能找到下家。
怀化学院于2016年启动MOOC建设,笔者团队负责建设生物工程基本技术实验(一)MOOC。生物工程基本技术实验(一)是生物工程专业实验课程体系改革的产物,涵盖了生物化学实验、微生物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中的大部分内容,包括生物工程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技术:溶液的配制、培养基的配制和灭菌、显微镜的使用和显微摄影术、细胞培养、细菌的培养制片和形态观察、微生物计数和大小测量、细菌染色、植物组织破碎、滴定、离心、分光光度技术、过滤和超滤、制作标准曲线、酶活力测定、离子交换层析、SDS-PAGE等,拟通过17个实验项目完成这些基本实验技术、实验方法的教学和训练任务。
不过这种作品的企图实际上在如下两个方面更为复杂。这种话语中的理想员工必须既是个人化的又是网络化(networked)的:这个快乐的员工,或者说这个有能力且决心在工作中获得幸福和成功的员工,就像那些书里常说的,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总体来讲,这些作者熟知情感研究——尤其是关于情感如何在生产性能量(productive energies)的传播中流通和积累的情感研究部分。幸福员工的“涟漪效应”是人类情绪中一种正面的、“超个体性的结果”,一种“用能量和幸福去影响周边人”的方式。在一个充满不稳定性的劳动力市场中,我们必须一直让自己具有受聘价值,就算我们——暂时和临时地——得到了工作,维持社会关系网也至关重要。一方面,我们被要求对自己的个人情况全权负责;而另一方面,又如管理大神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所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名片盒的大小”,社会关系网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更准确地说,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这套话语鼓励(生产性的)协作,不鼓励(反抗性的)团结。
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方法来研究乔布斯提出的“寻找工作”和“寻找爱”之间的异同:“遵从你的内心”,他表示,“当你找到的时候就会豁然开朗”[3]。先跳(leap),再看——这可不行。关于坠入(fall)爱河的观念在1970年代引发了女性主义者不小的兴趣。牵扯到爱情,判断力就失灵,这意味着在通常人们所强调的理性的主导、自利和独立意志等原则遭遇了有趣的例外;而鲁莽行为和消极心态的混合物倒成了解放生产活动的关键。费尔斯通这类理论家很容易就将童话式爱情或霍曼贺卡(3)霍曼贺卡,在北美十分流行的贺卡连锁品牌,标志性的设计就是浪漫风格的爱心、花朵等。式的浪漫给打发掉了。这种极致的浪漫主义,这种对具有特权的种族和阶级的美化——在这里面,爱情和工作被想象成互不相干的东西,这样,浪漫爱就不会被经济上的计算玷污了——是女性主义者的首要标靶。费尔斯通撕开浪漫主义理想化的面纱,将这种“爱情诡辩”认定为支撑劳动性别分工的另一种方式:“是用来巩固性别阶级的文化工具”[5]。并且,这些“诡辩”将其它亲密关系的实践病态化,这也为白人至上和异性恋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不过费尔斯通的焦点集中在她称之为性别-阶级的问题上,没有进一步追问下去。
四、作为主体化的意识形态
说完了忠告文学的宣传模式、神秘化以及去政治化功能,接下来,沿着阿尔都塞的思路,我们与其将“工作中的爱与幸福”的意识形态看作出售观念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现象,不如将其视为带有存在论意义的主体建构筹划。为了开始探究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工作中的幸福”和“工作的满足感”这个更老话语之间有何区别。工作的满足感一般被描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状态,而且主要决定于所处境况,而幸福的源泉则植根于个体员工的内心。基于此,“因……而满足”和“在……中感到幸福”之间的区别,经常被描绘为“制造同意”和“制造渴望”之间的区别。“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计划旨在培养对工作的密切渴望,把握这个概念最好从生命政治,而非传统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或至少要知道,关注焦点应该集中在情感与能量——对有机体——的改造,而不仅是改变想法、提高自觉性或塑造心态。
为了处理工作变革的新疆界以及为其提供支持的意识形态,我决定从另一个角度探究当代经济。我不是要基于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带薪工作模型,并用其去探索私人化的家庭空间中劳动的性别分工,而是借用女性主义对所谓“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研究,去更好地理解我们对工作的迷恋,以及我们在其中创造并投入情感的身份认同。为了这个特定目的,我想从一系列广泛、大量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将焦点集中在“什么是私人领地(personal terrain)”这个问题上。我将借鉴女性主义者对“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种异性恋爱情与罗曼司叙事的批判,以此来研究“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这套管理话语。这套关于带薪工作的罗曼司话语并不负责将家务劳动美化成爱的劳动——虽然它在关于家庭生活的更大话语中会如此;毕竟,带薪工作在今天已经成为(一般所承认为)工作的典型代表。相比之下,描写“工作中的爱与幸福”的流行文学,向读者推销了对于带薪工作的主观认同。“爱与幸福”与它们在传统的浪漫情侣或异性恋父权制小家庭之内的位置,保持着既相互纠缠又彼此远离的关系,因此能够与带薪工作重新建立关联。这些文学将“爱与幸福”宣扬成帮助雇主获得更高生产力的关键。常见的“爱与幸福”的文化修辞还被当作一种路径,通往幻想中蕴含着意志和能量的巨大宝藏;同时也被当作一柄杠杆,让雇主把这些能量撬动到生产活动中去。
在进行实际的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教学以及课后的网络学习进行一定的结合。例如,在进行课堂教学时教师仅仅将该部分课程的主要概念进行一定的介绍,使得学生对该部分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课后再根据自身的喜好在网络上对相关的知识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学习。这就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中的学生的学习方式,将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学习的效率,而教师可通过设计具有专业针对性的实验内容,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斯迪维·杰克逊(Stevi Jackson)指出,1970年代关于爱与罗曼司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当下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相对来说受到了忽视,尽管这些深具历史影响力的洞见来之不易。[7]在我进一步将这些观点重新关联、进入“带薪工作”的研究领域之前,首先来回顾一下这样的批判理论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勇敢地把异性恋浪漫爱的意识形态看作女性“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8]尽管她知道自己将被指责为“对感性和美好情感的不可饶恕的背叛”。到了劳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出版那本充满争议的《反对爱情》(AgainstLove)时,她发现,对爱情说不,更可能被认为是悲剧,而不是背叛。[9]同理,我怀疑如今若是跳出来反对热爱工作,就会让人看起来像个可悲的失败者,而不是造反英雄。“生怕‘爱’受到威胁而深感焦虑,”费尔斯通敏锐地发现,“这对认识其政治上的意义也有启发”[5]。今天,因为无法在工作中享受“爱与幸福”而引发的焦虑、羞耻、被边缘化和被排除在外的感受,既是浪漫爱文化具有文化权威的证明,也是新一波工作精神(ethos of work)已被自然化的结果,因此,任何无法顺应这种局面的人,都属于个体缺陷。拒绝培养合格工作情绪的“摇头族”(naysayer)被人们看作“不快乐的人”,而非“煞风景的人”。可怜啊,他们体会不到美好的感受,再想一想,无人与你分享这些意义非凡的(工作)关系,是多么孤单寂寞。更糟的是,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社会里,不能从工作中感受到爱与幸福的人,可能会被贴上“闯入者”(interloper)的标签,无权作为这个想象性阶层中的一员去享受更广泛的文化资源。如果说“爱”——不管爱的对象是什么——是一个众所周知让人难以批判的对象,对工作的爱则更让人难以把握,因为它将一个备受珍视的价值观包进另一个不容置疑的信仰结构之中——即,工作伦理将工作抬高为人的本质需求、道德责任和目标本身。最后,“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话语就这样与批判隔了两层保护。
五、坠入(falling)还是跳入(jumping)?
显然,这种爱的深度个体化概念,与新自由主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主体理念形成了强烈共鸣。关于工作中的爱与幸福的作品,至少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你在工作中能否获得幸福,根本取决于你自己。要学会蓄积深厚的抗击打能力,不要总是表现出惨兮兮的样子,一位作者这样建议,正如另一位作者解释的,“幸福指数由你自己决定”。艾哈迈德巧妙地描述了“为自己的幸福负责”的主张是如何被转化成“不负责任的唯我论”的:这是一种“避开一切阻碍自己获得幸福的自由”。[13]这些作者建议我们摆脱“员工心态”,“精心培养企业家精神去对待工作”。而另一位作者则表示,“记住,你所追寻的财富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人才市场里’”(对雇主来说,额外的好处就是这个刺激生产力的方法相对便宜:“由于重点放在了个体而不是职场上,因此机构执行起来也更简单、便宜、灵活”)。这些作者所谈论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主体,正如伊姆雷·塞曼(Imre Szeman)所指,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主体”,能很好地适应因为当下资本积累模式而不断增长的不稳定性。[14]爱与幸福的正面情绪是资源,可以让个体进一步推进他们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是手段,正如萨姆·宾客利(Sam Binkley)在阐释这类作品的关键信息时所言,个体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解放自身,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独立自主、野心勃勃的行动者,这样才最有机会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逃出生天、蒸蒸日上。
除了掩盖不公平、模糊爱情和工作在经济上的工具性外,“爱与幸福”的意识形态还通过将经验个体化的方式,将“爱与幸福”去政治化。爱的语言与个体人物之间肯定会产生强有力的共鸣。爱是私密的、个人的,不是公共的、政治性的;普遍认为,爱情是一种独一而本真的情感,我们很难将其与需要广泛分享经验的领域联系起来,更别说让其服从于管理上操控了。费尔斯通阐释了异性恋夫妇的浪漫概念是如何私密化(privatize)和个人化(individuate)女性的,她们被洗脑得如此成功,以致于“对自己的阶级普遍性视而不见”[5]。阿特金森认为,女性缩进异性恋夫妇关系中——用她的话说是放下武器、投靠敌营——是女性之间团结的失败。[10]
我们在这里借用她的洞见来强调一个事实:一个员工越因为有其他谋生手段而较少地被迫为钱工作,他就越有可能换到不同的或更好的职业,也就是说,一个员工越不顺从多数人都必须面对的典型环境,其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越有可能被浪漫化。再次重申,辨认出隐藏在“热爱你的工作,找到幸福”的建议背后的主体化过程很重要,它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经济需求不太紧迫,或因职业资本层次较高而能抗住高压管理的员工,这种建议也更容易在他们中间引起共鸣,尽管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老板希望“网撒得更大”。
乍一看,有些没大没小为老不尊,可细细一想,却又忍俊不禁。一个家庭中,有了严厉认真的老妈,其实还必须有个幽默护短的老爸。这叫互补调和,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然而,按照费尔斯通的说法,女性总是处于太过不稳定的境况,无法等待机会去坠入爱河。如果说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存在意义的证明”,同时也是她们在经济上的支撑,那么“女人可负担不起一时冲动的爱情”。费尔斯通指出,男人可以沉迷于坠入爱河的浪漫幻想,但对女人来说,将爱情交给“命运”或“运气”往往要危险得多。史蒂夫·乔布斯引用了坠入爱河的概念,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另一位在职场励志题材颇有名气的撰稿人——用了稍微更具鼓励性的“向前一步”这个表达,[15]而大部分“工作中的爱与幸福”作品给出的则是更接近主动跳入(jumping)的建议。一位作者让我们明白,热爱工作可不是罗曼蒂克式的犯傻,“更多的是要脚踏实地和吃苦耐劳”。“与你的工作坠入爱河是要付出心血的”,另一位作者警告大家,“良好的关系”,哪怕最美满的婚姻,“都需要工作”。不过,相比于德光批为阶级自恋(class narcissism)的流行语“做自己所爱的事”——因为这会让那些不太可爱的工作被视而不见,“爱自己所做的事”这种观念在拥有特权的职业领域之外,会让更多人有所认同。也许你运气不好,没法做自己爱做的事,但你可以“振作起来”,学会爱上本职工作,并从中得到快乐。从这方面看,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于找到那个乔布斯让我们坚持寻找的“唯一”的梦幻工作,而在于定下心来,爱你手头的工作。为了不让艰难去爱上勤劳的努力听着太让人泄气,这种爱上工作的冷静方法也有其美好的一面:为了“爱上工作”而做的“工作”本身,就能让你提神醒脑和充满力量。努力工作会带来幸福,而幸福会让人更加努力工作。
如果计算主义成立,本文所关心问题的答案也就显而易见。即如果AI与人类智能本质上就是一类东西,那么关于人工智能AI能不能超越人类艺术家之类的问题压根无须讨论,答案几乎直接蕴含在计算主义主张里面。无论艺术活动看起来多么玄虚,也无非是人的意识活动之一,而意识活动的本质在于计算,那么拥有更强计算能力的AI在原则上必然会超越人类,无论是围棋还是艺术活动。AI当然可以成为艺术家,并且借助计算力的优势赶上并超过人类艺术家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六、帷幕后面的山峰
这些话语所提及的主体化过程是雄心勃勃的。再看一遍乔布斯的训诫吧:“工作占据了你的大部分生命,所以,想真正得到满足就必须选择一份自己认为很棒的工作。而从事一份很棒的工作,首先必须热爱这份工作。”[4]换句话说,既然工作消耗掉太多的时间和能量,我们就只好相信这是份好工作;若想相信这是份好工作,就只好爱上它。逃不出去,就干脆完全陷进来。这一理念把既无法避免又令人艳羡的带薪工作变成了整个世界和目的本身,是源源不断的主体性投入与身份认同的对象,是希冀与渴望。工作与生活之间残留的边界也将在这种规训的敌托邦(dystopia)中消失殆尽。
当然,这种不需要管理者各种形式的压迫就能做到“全情投入”的员工——每个雇主的梦想——也的确是白日做梦罢了。这个再主体化的规划里至少有两处瑕疵,有两处地方让该规划遭遇了分析上的问题。工作中的爱欲幸福之类的话语的第一个问题非常明显:没有几样工作是真正值得一做的;作者们让我们去追求的那些东西,大部分雇佣形式根本就无法满足。正如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敏锐地观察到的,“我们的经济模式破坏的正是它赖以存在的心理属性(psychological attribute)”[16]。在当代经济语境下,“工作中的爱与幸福”的承诺,正是劳伦·勃兰特(Lauren Berlant)称之为“残酷的乐观情绪”的实证,因为你渴求的对象恰恰“阻碍了你去实现最初吸引你的目标”[17]。
如果说在工作中得到爱与幸福的第一个阻碍来自外部的结构性力量,第二个则来自于这种作品内部被我称之为“述行性调整”(performative adjustment)的计划。毫不奇怪,这些作者提出建议的目的是帮助大家适应现状。写到员工的地方绝不会出现“宁可不要……”等字眼——这些不愿做事的员工会被当成奇闻异事来说,更别提对既有的雇佣模式积极提出异议了。这类作品以一种最粗糙的形式为主体进行调整,以便适应(表面上)滴水不漏的结构。这些作品不是号召我们“接受工作但心怀不满”(take this job and shove it),而是要“干一行爱一行”(take this job and love it)。一位作者建议,与其质问老板能为你做什么,不如把注意力放在你能干好什么上。“抱怨工作一点儿用都没有”,另一位作者则宣布,“不如好好审视一下自己”。
这种适应筹划的述行性维度代表了这类作品的一个明确特点。为了实现情绪和情感的调整,我们需要好好练习。想感受自由,先自由行动。我们可以做到充满希望,乐观向上,坚韧不拔,甚至成为宝贵财富;秘诀就是提前排练,扮演我们希望成为的样子。不过,尽管大多数作者都会放弃主体的本质主义概念,转而寄希望于主体的社会化建构,但他们不一定会放弃在社会决定论方面下功夫。“去做”和“成为”之间,原本最好被视为高度复杂和漫长的相辅相成关系,现在却被简化成一份相对直截了当的功利主义行动指南。一位作者建议说,有了这些方法,员工就能被重塑为一名生产英雄,一个名副其实的“爱的机器”。最终,这些文本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自我调节的简化程序,在这个程序中,述行性被化约为个体有意进行自我塑造的表现。这些号称能让人们深入钻研、重构及重新指导主体情感结构的生命政治筹划,其实就是指导人们在表面装装样子,然后进行情感劳动。
七、打倒爱情!
为了更好地反击这波职场浪漫主义风潮,我准备借鉴“拒绝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后者产生于1970年代“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所倡导的“拒绝工作”,重点是反对那种将工作视为社会生活之最高目标和绝对核心的意识形态,提出对工作伦理的“拒绝认同”(disidentification)。拒绝工作可以被理解为双重过程:既要进行反工作(antiwork)批判,又要展开后工作(postwork)想象力。这种拒绝既包括对当下工作组织的批判,又包括建立一个不同未来的主张。
我们让这种拒绝思想来应对“工作中的爱与幸福”作品,拒绝的第一步就是对那些让你进行情感重构或情感调节的指令说“不”。虽然认识到,我们这样的个体除了在最坏的情况下做最好的选择之外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就像阿特金森在描述女性签下婚姻的一纸合同时所说的那样,“通过与敌人融为一体,来弥补定义上和政治上的损失”[10],但能明确认识到这种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也不可谓不是收获。或许尤其重要的是,要明白这种对灵活性和顺应能力的赞美,对自力更生和无穷创意的歌颂,都是为了批量生产出能接受这种不稳定环境和超强工作压力的员工——这已经逐渐成为当代雇佣关系的专有特色。拒绝的一个方式是坚持对雇佣劳动观“重新工具化(reinstrumentalization)”。这也是1970年代家务运动有偿化的提倡者所倡导内容的一部分,“想要更多微笑?给更多钱。对于破坏微笑的治愈效果来说,没有什么比钱的威力更大了”。费尔斯通(并非完全开玩笑的)为妇女解放所提出的建议是“抵制微笑”,这可以被重新认定为反工作行动主义。那些宣称“对工作感觉还好”但实际上却把幸福感,尤其是爱,留给生活中其它领域的员工,可能会被描述成艾哈迈德形容女性主义者时所说的“情感怪物,远离幸福”的形象,她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好好加以培养的拒绝形式。
拒绝的第二步,是始终保持开放心态,去看待那些不强制生活服从于工作并且对工作和生活进行另类组织的模式。即使是1970年代最激烈的批评家,也至少会用一只眼睛关注着更好的未来。在费尔斯通看来,浪漫爱被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腐化了,但她也表达了希望,即在另一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去感受爱。不过,在费尔斯通的判断中,贬低爱情的不光是性别-阶级的不平等;问题还在于对象选择范围的狭窄:爱仅限于浪漫爱的(男女)伴侣关系、家庭制度,以及——在当下语境中——带薪工作的制度。费尔斯通在她研究浪漫爱的文章尾声处问道:“为什么所有的兴奋快乐都被集中起来,被导入人类经验的世界中一条狭窄而无人知晓的小巷,而其它那么多地方都被荒废掉了?”[5]就我们能将自己“爱情体系中的情感贫困”归咎于“爱情在资本体制下的被剥夺”来说,在处理拒绝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这一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借用费尔斯通的术语,将其视为把爱和幸福“再度扩散(rediffusion)到……我们生命的所有领域”的运动。
这种对“再度扩散”——借用费尔斯通的术语——爱与幸福的号召,不应与如下主张相混淆:重新把爱与幸福固定在私人家庭中这个传统机构。相反,将她们限制在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和玛丽·麦金托什(Mary McIntosh)所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反社会的家庭”里,反而会产生相反效果,因为这种贫乏可怜的社会形式会“把周遭一切养分全部吸干喝净,让其它机构营养不良,发育迟缓”[18]。相比之下,我们若将爱情重新构想为一种革命力量,或许就能从中得到灵感与指引,其所产生的能量也将参与到政治变革的运动中。在詹尼佛·纳什(Jennifer C. Nash)最近从事的对第二波黑人女性主义关于爱与政治文献的处理中,可以找到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纳什解读出,黑人女性主义者的爱情-政治并不是在个体化和去政治化的浪漫爱模式中去思考爱情的,而是将爱视为一种更具包纳性的共同情感和关怀行为,后者指向某种未来可能出现的激进可能。纳什借鉴文献中的观点指出,在一些黑人女性主义的政治传统里,爱被作为一种差恒情感上关联的模式而得到认识和实践,能够激发新形式的社会团结和政治组织。黑人女性主义政治从私人空间和老套的异性恋罗曼司中解放出来,证明一些人已经着手,其他人也能学习,去培养爱的新形式,这种形式能够让大家团结起来,追求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共居方式。[19]
如何应对长期存在的过度看重工作的伦理命令所出现的新情况,我就刚才的思考做一个总结。拒绝“工作中的爱与幸福”话语的一个方法,就是坚持不断将我们与工作之间的关系重新编码,这样爱与幸福就可以在其它空间、以其它目的被重新塑造或重新定位。作为结束,我将引用西尔维娅·费德里希(Sylvia Federici)在1970年代“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中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拒绝工作”所包含的“重新工具化”和“再度扩散”的双重步骤:“我们想要把工作的归于工作,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最终重新发现‘爱为何物’”[20]。
网课是一个更新潮的东西,它是在互联网的发展下形成的,通过网络的连接,将老师上课的视频录下来,通过视频的方式演示,还可以随时返回,重复观看。这种学习方法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一种十分受欢迎的方法,尤其是在大学时期,许多学生要自学去考试考证,但又不能耽误自己平时的专业课,所以网课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既能随时观看,又能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学习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长短,是很方便的,但这种学习方法需要自己有很好的自控能力,能够抵挡住外界的诱惑,专心学习。
【参考文献】
[1]HOCHSCHILD A. 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1997.
[2]GREGG M. Work’s intimac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1.
[3]JOBS S.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Jobs says[EB/OL].(2005-06-14).http:∥news.stanford.edu/2005/06/14/jobs-061505/.2005.
[4]TOKUMITSU M. Do what you love: And other lies about success and happiness[M]. New York: Regan Arts,2015.
[5]FIRESTONE S.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70.
[6]HOCHSCHILD A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l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7]JACKSON S. Love and romance as objects of feminist knowledge[M]∥Women and romance: A reader. New York: NYU Press,2001:254-64.
[8]WOLLSTONECRAFT M.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M].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1992.
[9]KIPNIS L. Against love: A polemic[M]. New York: Pantheon,2003.
[10]ATKINSON T-G. Amazon odyssey: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the political pioneer of the women’s movement[M]. New York: Links Books,1974.
[11]BEAUVOIR S. The second sex[M]. New York: Vintage,2012.
[12]AHMED S. Killing joy: Feminism and the history of happiness[J].Signs,2010(3): 571-94.
[13]AHMED S.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rham[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14]SZEMAN I.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new common sense[J].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2015,114 (3): 471-90.
[15]SANDBERG S. Real happiness at work: Meditations for accomplishment, achievement, and peace[M]. New York: Workman,2014.
[16]DAVIES W. The happiness industry: How the government and big business sold us well-being[M]. New York: Verso,2015.
[17]BERLANT L. Cruel optimism. Durham[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
[18]BARRETT M, MCINTOSH M. The anti-social Family[M]. New York: Verso,1982.
[19]NASH J C. Practicing Love: Black Feminism, Love-Politics, and Post-Intersectionality[J]. Meridians,2011,11(2):1-24.
[20]FEDERICI S. Wages against housework[M]∥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 new edition. Cheltenham, UK: New Clarion Press,1995:187-94.
DownwithLove:FeministCritiqueandtheNewIdeologiesofWork
Kathi Weeks, Compiler: LI Wensi, Proofreader: WANG Xingkun
Abstract: This essay draws on 1970s feminist critiques of the ideologies of love and romance to develop a critique of the popular advice literature that directs employees to find love and happiness at work. The author argues that, under heteropatriarchal capitalism, the ideology of romantic love is being harnessed not only to continue to assign domestic work to women, but to recruit all waged workers into a more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work.
Keywords: 1970s feminism; happiness; love; Marxist feminism; work ethic
作者简介: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杜克大学教授,从事性、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
编译者简介:李闻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从事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
校者简介: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批判理论与文化理论相关的研究。
① 本文编译自《女性研究季刊》第45辑(Women’sStudiesQuarterly)2017年秋冬3-4号刊第37-58页刊登的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的《打倒爱情:女性主义批判与新的工作意识形态》(DownwithLove:FeministCritiqueandtheNewIdeologyofWork),感谢作者授权。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6- 0016- 10
[责任编辑 林雪漫]
标签:工作论文; 幸福论文; 费尔论文; 斯通论文; 爱与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杜克大学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