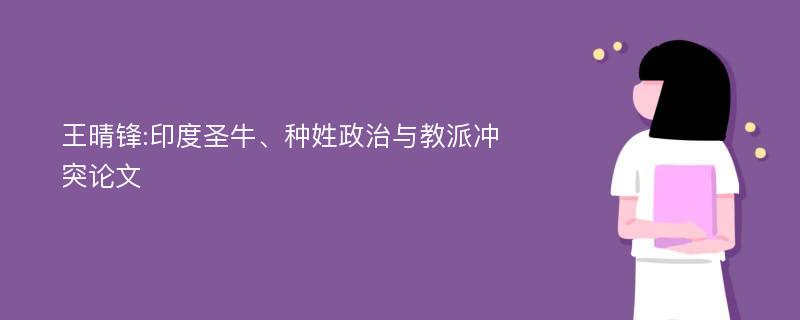
摘要:印度圣牛在精神与物质、象征与生计、宗教与经济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婆罗门放弃吃牛肉、崇拜母牛并成为严格的素食主义者是婆罗门教与佛教争权夺利的结果。在不杀生伦理、生灵等级观和圣牛信仰之基础上,原先无贵贱高下之分的饮食实践产生了阶序性差异,并通过宗教外衣逐渐结构化。与食物阶序相对应,种姓阶序的顶端是婆罗门、中间是非婆罗门,底端则是“不可接触者”。由此,饮食实践成为种姓政治的外显标志。在历史和现实中,圣牛还成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教派冲突的持续来源,不同族群策略性地利用经济效用和宗教权利进行自我争辩。在母牛成为印度教之核心象征物的今天,它将继续成为政治动员、唤醒宗教情感和民族主义的工具。
关键词:印度圣牛 屠牛禁令 印度教特性 种姓政治 教派冲突
母牛在印度教社会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数世纪以来,母牛一直在印度次大陆被广为崇拜,它构成了印度教文化传统之核心,母牛保护也成为一项文化传统。母牛在印度教徒的神圣宗教仪式和世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它不仅承载着与神进行联通的功能,同时也在生计、母性、财富象征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环境的变迁促使作为文化象征的母牛发生地位的变化,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圣牛观,最终使禁止宰牛和避免食牛肉成为文化禁忌。印度圣牛观涉及复杂的种姓政治,而屠牛禁忌背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更是频频引发教派冲突。本文试图从印度政府颁布的“最严屠牛禁令”作为切入点,探讨圣牛观产生的现实政治,包括饮食阶序与种姓阶序之间的对应、圣牛信仰导致的教派冲突以及神圣宗教权利与世俗护牛逻辑之间的关系等。
阮小棉悄悄加了罗漠的qq。他真坦荡,qq的名字就是罗漠,头像是那个很像三毛的圆鼻头小子。一点也不像他呀,他那么成熟,她想。
一、“圣牛情结”:从最严屠牛禁令谈起
印度教徒占全印人口的80%,由于印度教的主体性地位,印度很多邦都将母牛视为神圣的,并立法禁止屠宰母牛。2015年3月3日,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领导下的马哈拉斯特拉邦政府通过一项法律,将禁止屠牛的范围扩大到公牛、阉牛以及年老衰弱、对农业生产无用的牛。不仅如此,它还禁止贩卖和食用牛肉以及以任何形式占有牛肉,甚至将牛运输到其他邦进行屠宰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这被认为是印度历史上最严厉的禁牛令之一。在通常情况下,很多邦除了母牛之外,其他类型的牛是允许被屠宰的,而且农民在缺乏资金时可以将牛转卖给他人,尤其是将不再产奶或无法耕地的母牛卖给屠户,这样穷苦的村民不必再饲养这些年迈体衰的牛。而如今,这些行为都将遭到禁止。任何人贩卖或占有牛肉将面临5年监禁和200美元的罚款。[注]Stephanie March, “India′s government hints at national ban on cow slaughter; beef exporter warns of job losses,”ABCNews,31 Mar 2015, http://www.abc.net.au/news/2015-03-31/india-beef-industry-turmoil-ban-killing-cows/6360912.
在印度,屠牛禁令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它由来已久,并且一直争议不断。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较为强盛的邦,通常执行严格的屠牛禁令。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古吉拉特邦就立法禁止屠宰母牛。1979年,禁牛法令进一步扩大,它明令禁止屠宰15岁以下的公牛和阉牛,该条例得到印度最高法院的确认。1994年,古吉拉特邦再次修改法律,将禁令无差别地扩展至所有牛。又如,马哈拉施特拉邦正式立法禁止屠牛的历史也已有近四十年。早在1976年,《马哈拉斯特拉邦动物保护法》(The Maharashtra Animal Preservation Act)全面禁止屠宰母牛。1995年,湿婆神军党(Shiv Sena)政府通过修正案,试图将禁止范围扩大至水牛,但是未得到印度中央政府的批准。2004年,在印度人民党的支持下,下议院通过了《防止残暴对待母牛法案》(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ows Bill),这项非约束性的决议旨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屠牛,它甚至建议依照《防恐条例》(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2002)严厉惩处违反屠牛禁令者。人民党政府积极推动屠牛禁令在国家层面正式立法,但由于各种反对意见以及政权更迭,终未能实现。2014年,以纳伦德拉·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执掌中央政府后,情势发生了变化,保守势力利用其职权积极推动立法,以期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宰杀母牛。马哈拉斯特拉邦只是这种权力政治背景下的一个缩影,禁牛法案在该邦被搁置了近20年后,如今印度人民党同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执政,那么通过严厉的屠牛禁令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通过应用单井效益评价体系,将采油井分为无效井、效益井(表1),有针对性地采取“治、关、调、堵、包”等措施[2],注重对有效、高效井的保护。该体系运用“三线四区”模型(图1),模型综合了单井、单元、区块、油田的投入和产出,对比产出效益与运行、操作和完全成本,将各级对象划归到无效益区、增量无效区、边际贡献区和利润区。
印度的肉食品行业通常由穆斯林主导,而畜牧业则由阿希尔(Ahirs)等种姓的印度教徒控制。在圣牛问题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水火难容。印度教徒在情感上憎恶任何食牛肉或宰杀牛的行为,因为它与印度教的核心价值观相冲突。而在穆斯林的日常饮食结构中,牛肉是基本的食物。穆斯林还从事贩卖牛肉的生意,每年隆重举行的古尔邦节大量屠宰、献祭动物,其中牛肉是重要的供奉物。在前现代时期,尽管印度教徒对穆斯林屠牛、食牛肉的行为表示遗憾,但他们选择了克制和宽容,理解屠宰和活物献祭是穆斯林需要履行宗教义务。大多数穆斯林也感恩这种宽宏大量,并尽可能地不去伤害印度教徒的圣牛情感。因此,在英国殖民统治初期,教派冲突较为少见。然而,19世纪之后,印度教徒(尤其是中产阶级)逐渐对宗教差异不再像以前那样宽容,他们不愿意对宗教权利作出让步。对此,马修·格罗夫斯(Matthew Groves)认为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有四个原因[注]Matthew Groves, “Law, Religion and Public Order in Colonial India: Contextualising the 1887 Allahabad High Court Case on ‘Sacred’ Cows,”SouthAsia:JournalofSouthAsianStudies,vol. 33, no.1, 2010, pp. 95. :首先,当时“新教徒式”的宗教改革席卷整个印度,它呼吁回归基本教义,并通过宣教与皈依吸纳新的信徒。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内部变得更加同质化,而两者之间的界限则更加分明,不同教派的信徒之间日益难以彼此和解与妥协。其次,穆斯林精英嫉妒印度教的“暴发户”在各个行业和公共部门占据要职,并且其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与日俱增。再次,早在1870年,旁遮普锡克教的库卡派(Sikh Kuka)开始组织母牛保护运动。1882年,婆罗门教的改革者、哲人达耶难陀·娑罗斯瓦蒂(Dayanand Saraswati)在旁遮普创建“母牛保护协会”(Gaurakshini Sabha),使母牛成为印度教的象征,该协会竭力反对穆斯林宰牛。此后,印度各邦掀起母牛保护运动的浪潮,它经常夹杂着强烈的反穆斯林情绪。19世纪80、90年代,母牛保护运动成为一系列严重教派骚乱的重要原因。此外,母牛保护者还采取一些新的举措,诸如:为老弱病残的牛提供庇护所,专门成立准政治组织以制止屠牛行为,还采用暴力威胁和经济抵制等挑衅性的方式对抗穆斯林。最后,英国殖民政府对印穆关系采取所谓的“中立政策”。
当前,我国北京、广东、河北等省市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划针对个人消费端的、政府牵头的碳普惠机制。结合各地特点,它们涵盖的低碳行为方式、采用的核算方法、激励机制及商业模式也各有不同,见表1。在民间层面,以支付宝旗下的“蚂蚁森林”为代表的各类碳普惠产品也受到公众关注。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它对很多事物并不存在同质性的、单一的价值标准。不同的宗教—政治—经济共同体对牛的态度呈现为一种“神圣—世俗”的连续统[注]Prodipto Roy, “The Sacred Cow in India,”RuralSociology,vol. 20,1955, pp.9. ,它的一端是完全世俗的、理性的和实用主义的立场,另一端则是极其神圣的、非理性的和非经济性的立场,中间还有许多不同程度的温和派。很多印度教徒禁吃牛肉,视牛为圣物,印度教的领袖也竭力倡导母牛保护运动。例如,2009年9月30日至2010年1月17日,一些宗教领袖从印度教圣地库茹柴陀(Kuruksetra)出发,进行一场为期108天行程25 000公里的徒步远征,旨在传达这样的信息,即保护母牛就是保护印度的灵魂。[注]Govindasamy Agoramoorthy and Minna J. Hsu, “The Significance of Cows in Indian Society between Sacredness and Economy,”AnthropologicalNotebooks,vol. 18, no. 3, 2012, p.9.他们敦促印度中央政府立法禁止屠牛,并承认母牛是印度的“国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印度公民都严格遵循母牛神圣不可违犯性的原则。违反食牛肉禁忌的通常是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诸如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和阿迪瓦斯(Adivasis)[注]阿迪瓦斯,即印度的土著部落,他们主要聚集于中东部的偏远山地,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等,他们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牛,不认为母牛是神圣的,也并不忌讳吃牛肉。他们中的很多人避免食牛肉或不杀牛是迫于印度教徒的压力。尤其是穆斯林群体,他们是屠宰业的主导者,最为强烈地反对圣牛观。即使在印度教徒中,大量低种姓群体也吃牛肉,达利特(Dalits)[注]达利特,即所谓的“贱民”。本文涉及的“贱民”“不可接触者”和“达利特”均指同一类人,他们被长期剥夺合法权利,被高种姓视为“非人”,属于印度宪法中的“表列种姓”。以处理动物尸体、剥死牛皮为生,而且牛肉比羊肉、鸡肉等更为廉价和富有营养,因而成为他们获取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由于屠牛禁令威胁到许多民众(尤其是低种姓)的生计和生活方式,因而遭致非印度教徒和达利特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政府以狭隘的教派之见立法保护母牛,违背了公共利益,饮食习惯是受印度宪法保护的个人基本权利,屠牛禁令不仅违反了公民的民主权利,而且将导致经济灾难。
二、饮食阶序与种姓政治
在圣牛保护的问题上,印度教其实并不是反经济理性的。相反,早期护牛运动的理由恰恰是经济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关于圣牛保护的经济性解释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1878年,王公巴韦(Acharaya Bhave)曾绝食要求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立法禁止屠牛。1881年,雅利安社(Arya Samaj)的创建者达耶难陀·娑罗斯瓦蒂发起母牛保护运动,很快得到正统印度教徒和改革者的响应,也得到锡克教、耆那教的支持。护牛运动形成了一个泛印度教的共同体身份,它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通常是高种姓,很多是显赫的律师、富裕的商人和地主、学校教师以及王公、首领等,其对象则是英国人、穆斯林以及“不可接触者”。由于护牛运动引发的暴力往往采取教派主义的形式,因此经常遭致殖民政府的压制。1889年,达耶难陀·娑罗斯瓦蒂撰写的Gokarunanidhi由雅利安社员杜尔迦·普拉萨德(Durga Prasad)翻译成英文《仁慈之海》(The Ocean of Mercy),该宣传册成为护牛运动的基础性文本,对此后的护牛话语产生了深远影响。
印度教徒的素食主义观与母牛的神圣性、不杀生或非暴力伦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杀生”或“无杀念”与轮回转世、因果报应有关,遁世修行者将不杀生的教义运用于饮食实践,并视之为比婆罗门教的活物献祭具有更高的德性。最初,不杀生是禁欲苦行者信奉的原则,后来在佛教与耆那教的影响下被大众接受,婆罗门教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严格践行素食主义。也就是说,婆罗门放弃食牛肉是出于一种生存策略的考虑。[注]B. R. Ambedkar, “Untouchability, the Dead Cow and the Brahmin,” In D.N. Jha, eds.,TheMythoftheHolyCow,New Delhi: Navayana Publishing, 1999, p. 198.婆罗门不仅摒弃吃牛肉的传统,还进而弃绝食肉,成为彻底的素食者。如果不成为严格的素食者,婆罗门教无法重新赢回被佛教争夺走的信徒。动物献祭原先是婆罗门教的核心仪式,在农业社会里,大肆宰杀对农业生产极为实用的牛以及婆罗门祭司的饕餮之欲显然无法赢得贫苦大众的心。为了动摇并取代佛教的至尊地位,婆罗门废止了吠陀教的一些传统习俗,它甚至必须在饮食禁忌上更胜一筹。因此,婆罗门教彻底摒弃了食肉习俗和活物献祭的仪式。用比姆拉奥·安贝德卡(Bhimrao Ambedkar)的话说,“这是以极端主义击败极端主义。这是右派战胜左派的策略。打败佛教的唯一手段是比佛教徒更进一步,成为素食主义者”[注]B. R. Ambedkar, “Untouchability, the Dead Cow and the Brahmin,” p. 202. 。在拥护印度教的笈多王朝时期,杀牛成为一项死罪,并公开禁止出于献祭目的屠杀母牛。婆罗门放弃食牛肉、开始母牛崇拜并成为严格的素食者是婆罗门教与佛教争权夺利的结果。素食成为高种姓的符号和工具,它彰显着素食主义伦理的优越性。不杀生的伦理最终通过特定时期的权力斗争使原先并无贵贱高下之分的饮食习惯产生了阶序性差异,并通过宗教的外衣而迅速结构化。一旦婆罗门将母牛尊为圣物,而被边缘化的群体继续吃牛肉,那么他们便被排除在种姓之外沦为“贱民”,遭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和疏离。
目前,国家和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要求高校通过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方法和考核方式等途径深化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从而形成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1],使高校学生的创新思维、创业意识和创业实践能力明显增强,投身创业的学生显著增加。
印度独立后,依然存在种姓政治的仪式性差异,随着印度宪法废除种姓制度以及各类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实施,现实中的种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达利特与非达利特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不杀生的道德伦理下,素食的高种姓与食牛肉的达利特形成鲜明的对比。杀牛和食牛肉继续影响着种姓关系,甚至成为种姓冲突的来源。对高居种姓阶序顶端的婆罗门而言,维护圣牛的光环,就是维护自身的优越性。食牛肉禁忌还涉及日常生活中的“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例如,2012年,海德拉巴奥斯马尼亚大学(Osmania University)的达利特学生公开宣称他们的饮食权,反对不许食牛肉的禁令,并发表一项政治声明,捍卫达利特与穆斯林的饮食习惯。[注]Jahnabi Barooah, “Osmania University Beef Festival Leads To Violence,”TheHuffingtonPost,Apr. 17, 201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4/17/beef-festival-osmania-university_n_1432303.html但是对低种姓和达利特而言,反对屠牛禁令并不是反对母牛的神圣性,这与穆斯林群体有所不同。作为一种社会象征系统,禁食牛肉的饮食伦理背后隐含着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不公正性,食牛肉是污秽和贱民的标识,成为违法犯罪和非道德的行为。在这里,饮食习惯产生了道德阶序,它不再仅是象征性的文化规范,而是进入政治系统,成为社会冲突和种姓战争的重要来源。这便是饮食实践的政治意义。
有些低种姓为了提高他们的种姓地位而遵从、模仿婆罗门的习俗,包括放弃吃牛肉改食素,由此进阶成为“再生种姓”,这个过程被称为“梵化”(Sanskritisation)。在历史和现实中,很多非婆罗门阶层放弃了食牛肉的传统。婆罗门曾是印度最庞大的食牛肉群体,因为牛是珍贵的,非婆罗门不会仅仅为了获取食物而宰牛,通常是在履行宗教义务等特殊情况下才会这么做;而作为祭司的婆罗门却有大量机会吃到新鲜的牛肉。如今,婆罗门的饮食习惯已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他们不仅放弃吃牛肉,还彻底放弃食用任何肉类,成为严格的素食者。贱民吃的通常是死牛肉,这并不违法,也没有违背不杀生的伦理,因此,他们继续沿袭这种做法。但是,既然可接触者能够摒弃食牛肉的习俗,为何“贱民”不跟着效仿婆罗门而同样弃食牛肉呢?安贝德卡认为,一方面,这种效仿的代价过于高昂,极端贫困的达利特无法承受,因为死牛肉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对达利特而言,处理死牛既是特权,也是义务。既然无法避免处理死牛,他们也一如既往地不在意以牛肉作为食物。[注]B. R. Ambedkar, “Untouchability, the Dead Cow and the Brahmin,” p. 207.
三、圣牛信仰与教派冲突
本文进行夜间灯光处理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来自NGDC(隶属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公开发布的第四版全球DMSP-OLS夜间灯光产品(V4DNLTS),均可在NGDC的官方网站下载。第二部分数据为辐射定标灯光图像,该图像用于饱和及内部校准的参考灯光,来自NGDC另外发布的辐射定标灯光图像系列。第三部分数据为石油/天然气燃烧矢量图层,同样来自NGDC公开的全球数据库。第四部分为国家及其行政区域地图,来自DIVA-GIS项目网站(http://www.diva-gis.org/Data)。
从近代早期以来,正统印度教徒崇敬母牛,并禁止肆意杀害它。如今,全印大多数邦和联邦属地制定了禁止屠牛的严格法律,这使很多人难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牛肉。在印度,很多非印度教徒对母牛持世俗态度,食牛肉者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它包括印度教的低种姓和达利特(约占45%)以及穆斯林(13.4%)、基督徒(2.3%)等,估计有60.7%的印度人吃牛肉。[注]Anand Teltumbde, “The Holy Cow,”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vol.50,no.14,2015,pp.11.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少高种姓的年轻人也不忌讳吃牛肉。因此,尽管存在各种限制杀牛、食牛肉的禁忌,印度仍然是世界第七大牛肉消费国。严酷的屠牛禁令违背了大多数印度人的意志,对穆斯林和其他非印度教徒而言,屠牛禁令是印度教专制统治的象征,圣牛成为文化排斥、政治压制的工具。饮食禁忌也成为教派冲突的来源,宗教情感与教派政治糅合在一起,变得错综复杂。
除了马哈拉施特拉邦之外,有些邦(如哈里亚纳邦等)甚至考虑将杀牛等同谋杀罪,将判处终身监禁。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而言,严格的屠牛禁令实乃合情合法之举,但它可能与纳伦德拉·莫迪在竞选时承诺为民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相抵触。根据相关报道,2015年,印度出口牛肉24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超过巴西的200万吨和澳大利亚的150万吨。这三个国家占全世界牛肉出口量的58.7%,而印度占23.5%。超过80%的印度牛肉销往亚洲市场,其中越南是印度牛肉最大的消费国。[注]N. H. Zuberi,“Ban on cow slaughter in India: FPCCI optimistic about market opportunity,”BusinessRecorder,November 04, 2015. http://www.brecorder.com/agriculture-a-allied/183:pakistan/1243095:ban-on-cow-slaughter-in-india-fpcci-optimistic-about-market-opportunity/印度的禁牛令将使成千上万人失去工作,直接牵涉的行业包括屠宰业、牛肉的进出口贸易和皮革制造业等。马哈拉施特拉邦每月被宰杀的牛只达30万头,大量从事养牛业及其交易的人们将因此受严重影响。[注]M.N. Parth, “Indian state's ban on cattle slaughter is driving farmers to ruin,”LosAngelesTimes,July 28, 2015. http://touch.latimes.com/#section/-1/article/p2p-84087656/在全球化市场下,他们已经受到激烈竞争,屠牛禁令更是令他们雪上加霜。
在殖民统治时期,屠牛成为社会动乱和教派冲突的重要来源,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最初,为了尊重地方性传统与宗教实践,同时也为了避免麻烦,东印度公司主动回避印度本土的宗教问题,采取“不干涉”的自由放任政策,交由印度人自行处理。但当局很快发现,宗教管理与维持公共秩序密是密不可分的,当他们不得不介入宗教事务时,便要求行政官员严格按照当地的习惯法来处理。19世纪中期,英国人在冲突解决机制中又引入公平观念,即不仅要保护人们自由崇拜的权利,也要进行积极干预,以确保宗教自由不会导致不同教派之间相互践踏权利。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殖民当局很难做到在不同教派之间保持权利均衡。例如,在一些争议性公共事件的司法裁定中,殖民当局质疑母牛作为宗教对象的地位。1887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在关于圣牛的案件中认为,根据《印度刑事法》(Indian Penal Code,IPC),母牛并非宗教“圣物”。这实际上破坏了殖民当局宣称的“宗教中立”原则,激发了印度教徒保护母牛的大众情绪,并持续引发骚乱。到了19世纪末,随着印度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英国殖民统治者在穆斯林群体中找到了忠实而强有力的支持者。殖民者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政治的或策略性的,由于英国人也屠牛、食牛肉,他们发现穆斯林精英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个人品质(无畏、正直等)都比高种姓的印度教徒(严格素食、柔弱等)更加意气相投。因此,殖民政府声称的宗教“中立政策”更多地仅是形式,在实际处理印度教徒-穆斯林的关系时,很难说是没有偏见的。[注]Matthew Groves, “Law, Religion and Public Order in Colonial India: Contextualising the 1887 Allahabad High Court Case on ‘Sacred’ Cows,” pp. 99-100. 殖民当局为维护统治秩序,以“法治”为名,通过纵横捭阖的手腕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斗争,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
19、20世纪之交,受印度教徒支持的母牛保护运动爆发大范围的教派冲突,并不断推动着屠牛禁令的法律生成。在强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感的驱使下,母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象征性意义。印度非暴力运动的传奇领袖莫罕达斯·甘地曾说:“如果有人问我印度教最重要的外在表现是什么,我会说是母牛保护的观念。”[注]Govindasamy Agoramoorthy and Minna J. Hsu, “The Significance of Cows in Indian Society between Sacredness and Economy,” p. 5. 20世纪50年代中期,立法禁止屠牛在制宪会议中引起广泛争论。当时一项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母牛保护的法案被提交到印度议会,经过激烈地讨论后最终被拒绝。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强烈反对这项提案,认为它违背了世俗主义的国家理念。[注]Subrata Kumar Mitra, “Desecularizing the Stat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ndia after Independence,”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History,vol. 33, no. 4, 1991, pp.770-772. 在印度宪法中,有一部分是“国家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它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但为政府在制定法律时确立了基本原则。其中第48条“农业与畜牧业组织”规定:“政府应尽力以现代和科学的方法组织农业和畜牧业,尤其是采取措施保护和改良品种,并禁止屠宰母牛、牛崽以及其他产奶和抗旱的役畜。”宪法的这种表述在本质上是一种折衷,因为它对禁止屠牛的规定仅是一种“指导性原则”[注]Daphne Barak-Erez, “Symbolic Constitutionalism: On Sacred Cows and Abominable Pigs,”Law,CultureandtheHumanities,vol. 6, no. 3, 2010, pp. 425.。也就是说,它只是鼓励地方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立法,但并没有进行强制性规定。对该政策的理解与实施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由各邦的立法会议自主决定。实际上,印度的大多数邦都立法禁止屠牛。但是,各邦禁止杀牛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通常会根据母牛的使用价值区别对待,例如,某些邦可以宰杀垂死挣扎、羸弱不堪的母牛。不同的邦关于禁止宰杀的牛种也存在差异,诸如是否包含公牛、水牛等。尽管如此,印度教的护牛主义者希望颁布全国性的禁牛法令,使母牛保护真正成为一项国策。
印度教的食物禁忌不仅区分了素食者和肉食者,而且还严格区分了食牛肉者和非食牛肉者。这样便产生了印度教的饮食阶序,即素食者、肉食者(非牛肉)和食牛肉者,是否食牛肉将“可接触者”(其他印度教徒,无论是素食者还是肉食者)与“不可接触者”区别开来。素食对应的是洁净,它是高尚的饮食方式,食牛肉则是亵渎神明的行为。素食者是高贵的,食牛肉者是低贱的。这种饮食阶序建立在不杀生伦理、生灵等级观以及圣牛信仰的基础上。[注]Shraddha Chigateri, “‘Glory to the Cow’: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Food Hierarchy in India,”SouthAsia:JournalofSouthAsianStudies,vol. 31. no. 1, 2008, pp.11.由于该饮食禁忌的核心是圣牛信仰,因此禁食牛肉处于禁忌等级的顶端。与这种饮食阶序相对应的种姓阶序是处于顶端的婆罗门、中间的非婆罗门和底端的不可接触者。由此,达利特被强制纳入这种身份阶序体系。洁净与不洁在社会情境中对应着婆罗门与达利特之间的截然对立。禁食牛肉作为一项饮食禁忌得到普遍认可,它使达利特成为不洁的和非道德的,处于种姓阶序的最底端。而婆罗门则成为洁净之典范、母牛之化身。种姓歧视源于达利特被视为肮脏的,因为他们食肉,尤其是牛肉。宰牛者和食牛肉者成为不可接触者,甚至跟他们说话都会遭致污染。不同阶层的饮食实践逐渐被固化,并与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相联系。由此,饮食习惯差异不再仅是表面上的文化差异。一个人食用牛肉的行为不再是私人的口味问题,也不是纯粹的世俗之事,而是严肃宏大的政治和宗教议题,饮食实践与身份政治直接相关。正因如此,安贝德卡认为,食牛肉是导致印度贱民身份的根源。印度教赋予饮食以阶序性,并成为划分身份地位的基础,食牛肉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社会污名,被与“贱民”划上等号。“阶序人”由此诞生。
自建国伊始,印度便明确定位为一个世俗国家。然而,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护牛行动不断得到民众的支持,政治家也利用母牛保护表明“印度教特性”(Hindutva)。[注]Hindutva也译作“印度教民族主义”,它指一种主张印度教民族主义并建立印度教国家的政治运动。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英国殖民统治导致印度教的衰落,因而他们主张回归印度教传统。印度教徒集体建构的历史记忆将屠牛与民族压迫紧密联系起来:先是穆斯林征服者,后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圣牛信仰成为印度教高种姓的共同意识,它不断地唤醒宗教斗争的集体记忆。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断地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施压,要求扩大禁牛法令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孟加拉邦的印度教徒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地方政府给予穆斯林以特权,须禁止他们在古尔邦节屠宰母牛。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受理该诉讼,认为根据准据法,政府无权赋予穆斯林这种豁免权,因为伊斯兰教并没有规定“必须以母牛献祭”这种宗教义务。随后,该判决得到印度最高法院的肯定。在这一时期,“全国牛委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Cattle)还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立法、禁止屠牛。[注]Daphne Barak-Erez, “Symbolic Constitutionalism: On Sacred Cows and Abominable Pigs,” p. 429.而穆斯林则拒不接受将屠牛禁令强加于他们的宗教实践,认为这违背了印度政府对宗教表达自由和世俗主义所作的承诺。穆斯林也经常就屠牛争执向法院提请诉讼。例如,1959年,在哈尼夫·奎雷施诉比哈尔邦(Mohd. Hanif Quareshi v. Bihar)一案中,穆斯林屠户认为禁止屠牛侵犯了他们的职业自由和宗教习俗。在通常情况下,印度的法院认可禁止宰杀母牛,但认为应限制扩展至其他牛种,而且禁牛法令应基于理性,充分考虑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功用。从20世纪90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圣牛仍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族群之间紧张和冲突的持续来源,很多非印度教徒批判对圣牛的“封建情感”,由此导致的教派暴力也时有发生。在母牛成为印度教象征物的今天,它将继续成为政治动员、唤醒宗教情感和民族主义的工具。
印度宪法规定,保护母牛的权限属于地方政府,每个邦有权禁止或允许屠牛、食牛肉。印度最高法院也支持这样的立场,即禁牛乃地方政府之事,不宜在国家层面统一立法。因此,各邦根据当地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禁牛法令也有所不同。目前,全印度大约有24个邦已经通过法律禁止屠宰、销售母牛。[注]Ravi P. Bhatia, “Some Thoughts on Banning of Cow Slaughter in India,”TranscendMediaService,13 July 2015. https://www.transcend.org/tms/2015/07/some-thoughts-on-banning-of-cow-slaughter-in-india/各邦在关于牛的立法问题上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东北部各邦没有限制杀牛;喀拉拉邦虽有告诫性的建议,但并未明令禁止宰牛;泰米尔纳杜邦、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允许拥有执照者宰牛;安德拉邦、特伦甘纳邦、比哈尔邦、果阿邦和奥里萨邦禁止杀母牛,但是允许在拥有执照的情况下宰杀其他牛类;印度其他邦均严厉禁止杀牛。[注]Vaidehi Sachin, “Ban on Cow Slaughter: Every Community will be affected by it,”Linkedin,Mar 16, 2015. http://www.linkedin.com/pulse/ban-cow-slaughter-every-community-affected-vaidehi-sachin
四、神圣宗教权利与世俗护牛逻辑
关于圣牛、屠牛禁令的探讨无法规避更广泛意义上的食物禁忌与饮食模式。对印度教徒而言,饮食实践是种姓的外显标志。在印度,支配性的高种姓不到总人口的15%,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主动接触牛肉。而对作为“表列种姓”的“不可接触者”而言,牛肉是重要的食物来源,他们不仅吃牛肉,还以剥牛皮、处理尸骨以及生产各类牛制品为生。阿迪瓦斯和“其他落后阶级”(OBCs)——尤其是首陀罗中的低种姓,他们大多吃肉,而且也不会对吃牛肉感到惶恐不安。在印度教的历史中,并不只是达利特吃牛肉。在吠陀时代,牛肉是印度教徒的传统饮食构成。早期的雅利安人迁移到印度后,他们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保留着原来的文化传统,诸如游牧、动物献祭等,直到定居的农耕生活成为主要的生计模式。对婆罗门教而言,素食主义和不杀生虽有助于遁世修行,却与《摩奴法典》相矛盾。到了诠释经典的时代,随着素食主义的确立,宗教经典中关于献祭和肉食的记载成为令人尴尬的部分。[注]路易·杜蒙著:《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第235页。今天的一些极端的印度教徒甚至认为,宰牛、食牛肉的行为是侵入印度的印欧人带来的,素食主义才是本土性的习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母牛保护运动流行着经济论的观点,它强调母牛对印度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并能为人们带来富裕安康。由于殖民政府对确保殖民地的繁荣昌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雅利安社员并不是将母牛保护视为一项宗教特权,而是以经济必要性作出合法性论证,敦促殖民政府出面干预,并立法保护母牛。殖民地的宗教宽容政策既影响着印度的刑法,也形塑着公共话语。根据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的原则,如果将护牛定义为宗教问题,政府很可能不会进行干预。由于母牛在印度农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副产品,诸如牛奶等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还能增强心智,它甚至乃是“此世之福(dharm)的源泉”[注]C. S. Adcock, “Sacred Cows and Secular History:Cow Protection Debates in Colonial North India,”ComparativeStudiesofSouthAsia,AfricaandtheMiddleEast,vol.30,no.2,2010,pp. 309. 。屠牛行为也就成为自私自利、道德错误和罪大恶极,它置整个国家的公共福祉而不顾。这种世俗性的护牛逻辑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对道德进行计算,主张将屠牛行为进行罪化,使之成为国家司法行动的捕捉对象。在以普遍性的经济诉求作为护牛话语的前提下,保护母牛不再是印度教的私事,而是关涉国家利益和公民福祉的宏业。母牛还在“此世之福”的道德秩序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保护母牛不仅是物质性的需要,也是出于道德的考量。母牛保护主义者从而将“此世之福”转化为科学效用和世俗/公共的善,这正是现代公共政治和政府治理的重要范畴。由此,禁止屠牛已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而且是紧迫的政治议题。雅利安社的策略性动机可见一斑。这种以经济实用为基础的护牛主张也与19世纪末在英国和印度流行的自由理论相一致,雅利安社关于母牛话语中“此世之福”的阐述超越了经济和功利主义的原则,它将普遍性的道德和公共的善成为国家行动之基础。虽然此世之福不能等同于经济效用,但是其道德逻辑与功利主义追求的结果并不矛盾。
印度的宗教问题通常与其他非宗教性议题相互交织。在公民社会领域,为了成功地保护母牛,护牛主义者巧妙地遵循着一套世俗政治的逻辑,它表明母牛保护不是出于宗教伦理,而是经济理性。按照殖民政府的立场,宗教被看作神圣领域,外在于政府能够干预的世俗领域。然而,护牛主义者并不将护牛视为宗教权利范畴,它挪用自由主义话语中无差别的“公共的善”,从而超越狭隘的印度教情感、共同体利益和教派之争。在微观话语层面,这种关于圣牛的争论是围绕着宗教宽容的“政治语义学”而展开的。[注]C. S. Adcock, “Sacred Cows and Secular History: Cow Protection Debates in Colonial North India,”ComparativeStudiesofSouthAsia,AfricaandtheMiddleEast,vol.30,no.2,2010,pp. 297. 也就是说,宗教宽容的政治语义学形塑着母牛保护的地方性话语,使之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宗教和经济的语言里。国家禁止的不是宗教性献祭或神圣义务,而是损害农业生产和国计民生的屠牛行径。它将穆斯林以母牛献祭的宗教权利附属于更宏大的经济必要性,从而使国家的干预正当化。去宗教化的护牛逻辑还采取一系列话语策略,诸如以事实性的、充满政治色彩的世俗语言——“屠杀”,代替神圣的“献祭”,以抹除穆斯林宰牛的宗教色彩,政治话语的转译赋予母牛保护以公共伦理。
殖民政府以宗教自由之保障者自居,试图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不同宗教共同体。因此,作为基督徒的英国殖民者在处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事务时往往采取折衷的态度。然而,世俗事务很难与宗教问题彻底分离,圣牛意识深嵌于宗教信仰和现实政治,母牛的经济实用性也难以与它在印度教中的神圣性割裂开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策略性地利用经济效用和宗教权利进行自我辩护。穆斯林坚持以宗教自由捍卫母牛献祭的权利,拒绝政府和印度教徒强加的律令,认为母牛保护以经济主义为掩护,其背后的动机本质上是宗教性和教派主义的。他们呼吁政府公平对待不同共同体的宗教权利,屠牛禁令违背了印度政府对建设世俗国家的承诺,破坏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母牛保护也确实削弱了国大党在穆斯林群体中的公信力。母牛保护导致的冲突发生在不同层面上: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之间,它是宗教理念上的冲突;在印度教内部的高种姓与低种姓/达利特之间,它是宗教理性与经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
五、总结与讨论
圣牛在印度社会中具有难以取代的经济效用和宗教象征功能,它不仅提供牛奶和劳力,也提供宗教灵感。圣牛与种姓政治、教派冲突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它不再仅是饮食习惯或宗教文化问题,而且也是经济、法律与政治秩序问题。母牛崇拜是教派斗争(印度教与佛教、耆那教等)和理性选择的结果,婆罗门教通过母牛崇拜确立其统治地位。母牛在印度的文化结构、生产关系和政治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反过来又强化了它的神圣性,使之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象征和关键性的宗教特质。概而言之,圣牛联结了传统与现代、洁净与污染、神圣与世俗。在印度,关于圣牛的争论仍将持续,也正是在这种动态的权力竞争和话语张力之中,神、牛与人维持着一种共生性关系。
其实语言文字能否被熟练应用,主要就看是否有牢固的知识基础。教师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在语文阅读中要注重文字的积累。其实,在语文的教程中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要想有效提高语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阅读量。第二,除了积累课堂所学的知识以外,更要注重课外语言积累。因为课堂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光靠课堂讲解的话,是根本不能满足语言要求的,所以还要加大课外文献的阅读量。第三,有效记录生活中的文字。总而言之,教师不但要注重学生好习惯的养成,更要鼓励学生加强社会实践。
历史上的“粉红革命”[注]“粉红革命”(pink revolution)是纳伦德拉·莫迪在2014年竞选印度总理时提出的表述,他借以批评之前的政府大幅增加印度的肉类出口以及大规模屠宰母牛的现象。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如今,印度拥有全世界57%的水牛(Buffalos)和16%的家牛(Cattles),并且是全世界最大的牛奶生产国。[注]Anand Teltumbde, “The Holy Cow,” p.11. 印度还仍然维持着规模庞大的皮革制造业。因此,我们对屠牛禁令不必危言耸听,具体而言,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印度历史上,它不是第一次出现屠牛禁令,印度社会自有它的调适和应对机制;其次,它不是全国性的立法禁止,而是在邦的层次上;再次,禁止屠宰和食用的对象主要是瘤牛,通常情况下不包括水牛等其他牛种;最后,印度各邦针对牛的禁令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有些邦并没有全面禁止屠牛和食牛肉,如北印的西孟加拉邦、南印的喀拉拉邦以及东北部以部落为主的邦。此外,尽管存在不杀生的法则,但是将羸弱年迈的牛只卖给宰牛的屠户是数世纪以来的惯常做法。有些地区还将牛偷运到邻近可以屠宰的邦。而且,虽然很多邦颁布了禁止屠宰母牛的法律,但是它们未必都得到严格地执行。
IndianHolyCow,CastePoliticsandCommunalConflicts
WANG Qingfeng
Abstract: The Indian holy cow played key rol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irit and substance, symbol and sustenance, religious and economics. As a result of contending religious power and leadership, Brahman abandoned beef-eating, and they began to worship cow and be rigid vegetarian. Under the ethics of ahimsa, hierarchy of all creatures and sacred cow beliefs, the indiscriminate diet practices generated hierarchy, and became structuralization through religion. The caste hierarchy mirrored to the food order is Brahman on the top, non-Brahman in the middle, and the untouchables at the bottom. Diet practice was the visible feature of caste politics. In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holy cow was the main source of communal conflicts between Hindu and Muslim, and these two groups strategically use economic utility and religious rights for self-justification. Nowadays, the cow is the core symbol of Hinduism, and it will still be regarded as the tool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evoke religious emo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e future.
KeyWords:the holy cow banning of cow slaughter Hindutva caste politics communal conflict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冷战世界的民族冲突与治理特点研究”(11ZD135)。
作者简介: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陈沛照
标签:印度论文; 母牛论文; 印度教论文; 穆斯林论文; 牛肉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其他宗教论文; 婆罗门教论文; 耆那教论文; 锡克教论文;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冷战世界的民族冲突与治理特点研究”(11ZD135)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