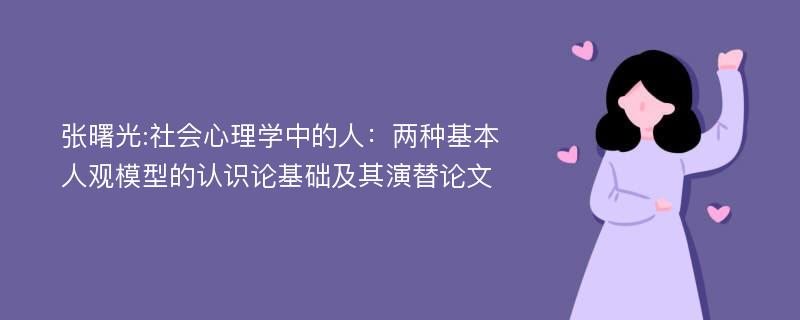
[提要]造成社会心理学分裂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者对于人性莫衷一是,以致一直未能建构出统一且广为认可的人观模型。英国学者布尔曾在其对社会心理学的人观的研究中,总结提炼出了两种基本人观模型,即“内在心理模型”与“人际与社会模型”,但未能阐明它们的认识论基础及演替动力逻辑。本文通过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析,不仅弥补了缺憾,还在此基础上以史为鉴,讨论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应具备怎样的心智素质。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基本人观模型;内在心理模型;人际与社会模型;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
一、引言
社会心理学自诞生以来,便是一门分裂的学科——不同“社会心理学”相互并存、彼此竞争。对此,国内学者郭远兵与孙时进曾作过极为形象的描述,“社会心理学像一个正在发育的青少年,受困于早期未解决的复杂情结,在一连串困惑中挣扎”[1]。其中,最大的困惑可能是对于人自身的困惑:何为“人”。正如美国学者杰克逊(Jackson,J. M)所指出的那样,造成社会心理学分裂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者对于人性莫衷一是,以致一直未能建构出统一且广为认可的人观模型。事实上,社会心理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研究者孜孜于建构“整合性人观”(unified conception of human nature)的历史[2](P.108)。
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为社会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探明方向,英国学者布尔(Burr,V)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中的人》(the person in social psychology)中,通过对实验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论、拟剧论、民俗学方法论、社会认同理论、标签理论、社会表征理论、话语心理学、社会建构论、批判心理学等一系列相继涌现出的可被统称为“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或理论所隐含的人观的由来及内容进行梳理与审视,总结提炼出了两种基本人观模型,即将“人”视为一种具有自足性、先在性(意即其总是先于社会而存在)、整合性(意即其是作为动机与认知的综合体而存在的)、一贯性(意即其心理与行为倾向通常具有前后一致性)的个体性存在的“内在心理模型”(the intra-psychic model),以及将“人”视为一种具有人际互依性、社会嵌入性、情景依存性的关系性存在的“人际与社会模型”(interpersonal and societal models)[3](P.133-143),同时还明晰了以由“内在心理模型”转向“人际与社会模型”的基本人观模型演替为核心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动向。最后,他从社会心理学的核心议题——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切入,在对两种基本人观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为社会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指出了方向:打破个体与社会二分的思维模式,辩证地理解和把握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既要看到个体积极参与建构社会的能动性,又要看到个体为社会所制约的被动性。
然而,布尔在其著作中未能阐明上述两种基本人观模型的认识论基础,及其演替的动力逻辑。本文有意于对这两方面作以探析,以期在弥补缺憾的同时,以史为鉴,讨论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心智素质。
二、分析框架的提出
基本人观模型对于社会心理学学术共同体而言,既是作为“学科文化知识”而存在的“整体性知识”,同时又是作为“基本潜在假设”(basic underlying assumptions)而存在的“元理论”(meta-theory)[4](P.36)。所谓“元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潜隐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及应用研究背后,且通常不为人所知的假设[5]。它作为“范式”(Paradigm)的核心构成要素,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定向策略”(orienting strategies),其作用在于为研究的展开“提供框架与方向”[6][7](P.27)。对此,艾布拉姆斯与霍格曾有过如下形象的阐述:
“一种元理论就像一本实用的旅行指南,它会告诉你去哪儿,不去哪儿;什么值得一看,什么不值得一看;从目前所在地抵达目的地的最佳路线是什么;最好在什么地方休息一会儿。元理论信念(meta-theoretical conviction)提供结构和方向,它明确了一个人(研究者)会问的问题,以及不会问的问题”。[8]
这意味着基本人观模型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具有二重性,即同时具有指导性和约制性,从而使与其所隐含的预设相一致的“知识图景”不断被构建出来。“知识图景”与“现实图景”或契合、或疏离。但可以肯定的是,“知识图景”与“现实图景”的疏离,必定会促动一部分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其所旁观甚或参与的知识生产实践,以及隐于其后并为之提供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又及与本体论、认识论相关联的基本人观模型进行反思与重构,从而使基本人观模型的演替成为可能,此即社会心理学得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由于问题意识使然,笔者在本研究中将更多地关注于认识论,当然,其间也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本体论,毕竟本体论与认识论是相统一的:本体论决定认识论,认识论反映本体论。
从逻辑上讲,“建构”先于“重构”;“重构”作为对“建构”的一种革新,是以对“建构”的反思为基础的,当然,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建构”。根据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来看,基本人观模型的“建构”与“重构”本质上都是群体性知识建构活动,它们除了受到既有理论与传统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学术共同体成员所置身的“历史与社会环境”(historical and social setting),以及其(特别是一些领袖人物)在“学术场域的微观世界”(the microcosm of the academic field)及外在“权力场域”(the field of power)中的位置等因素的影响[9](P.39)[10](P.239)。
图1以基本人观模型及其演替为线索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分析框架
参照上述分析,可以提出以基本人观模型及其演替为线索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基于这一框架,下面首先从“基本人观模型作为整体性知识”的角度,对两种基本人观模型的认识论基础加以探析,而后从“基本人观模型作为元理论”的角度,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反思推动下的两种基本人观模型演替进行梳理与分析。
精进电动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和动力系统提供商,技术路线覆盖纯电动、插电混合动力、混合动力等,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汽车电动系统解决方案。精进电动是行业内少数能全面涵盖新能源汽车最重要应用的动力系统及其核心零部件制造商,拥有丰富的产品组合,包括电机、电控、控制软件、新能源汽车专用变速器、减速器总成等。精进电动产品凭借出众的品质和技术优势赢得了全球客户的信赖。
例如笔者在上文所提及的,设计一个集合了各种地图的sdk的平台,通过GPS定位,一个用户若是觉得某个地方很不错,就可以给这个地方点赞,同时将这个地点的经纬度传送到后端服务器上。当查看热度图时,系统从后端服务器调取数据,通过相应的密度计算的算法将点赞集中的区域的设置为高亮的形式,这样就可以通过热度图来反映学生对什么地方感兴趣,从而给其他学生用作参考数据。
三、两种基本人观模型的认识论基础
相较于其它整体性知识,基本人观模型自有其独特之处——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两相合一。既然如此,那么人观的建构却为何如此之难(如果不难,社会心理学就不会存在学科分裂问题),换言之,作为认识客体的“人的存在”对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自身而言,为何不具有直接通达性?如欲回答这一问题,则要从人类的知觉谈起。正如柏拉图的“洞穴隐喻”(The Allegory of the Cave)所阐释的那样,人类的知觉天然地具有窄仄性,通俗地说,“我们在任一时间实际能够感知到的,仅仅是我们世界的极其微不足道的片段。不仅过往与未来之事件不可能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就连视觉或其它感官所能直接触及到的,也只是在空间中铺展开的当前世界的极微小的部分”[11](P.57)。基于此,不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人的任一存在面相(例如生物、心理、文化、社会、历史等)相对于人的知觉场而言,都有其显明通达亦即“在场”的一面,也有其隐然不露亦即“不在场”的一面,至于这些存在面相之间的关联,则更是难以直观把握的。
基本人观模型建构难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传统“认识论难题”,即“基于现实经验的知识如何能够跨越其界限而同样地应用于一切可能的经验使其转变为概念知识”,其关键点是“知识的整体是如何被‘构成’的”[12](P.3)。自苏格拉底以降,西方哲学家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孜孜以求,力图破解“认识论难题”。其间,他们先是关注“在场”、忽视“不在场”,推崇“理性”、贬低“想象”(亦即一种超越自身经验之局限性的认知能力),后又逐渐认识到“不在场”较“在场”更为接近事物的本质,“想象”通达“不在场”,并将其与“在场”联结、整合,建构出整体性知识的唯一途径。进而,开始关注“不在场”,推崇“想象”,并接力对“想象”在人类认识中的地位进行了审视与再审视。英国哲学家休谟和德国哲学家康德、胡塞尔堪称这一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前者的主要贡献在于为“想象”正名,并指出了“想象”在知识生产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后两者的主要贡献在于,以其各自建构的认识论体系分别揭示了人类藉由“想象”建构整体性知识(包括基本人观模型)的不同进路。
粗略地讲,康德的认识论体系建基于以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为渊源,以渐趋步入成熟阶段的人文精神为指引,以近代数学与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成果为依据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然而,这一思想框架从根本上酿致了“心”与“物”的分裂[13]。为了打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从而消弭“心”与“物”的分裂,胡塞尔在继承康德的理性批判精神的基础上,以“自我意识的自明性”为逻辑起点,以“自我——我思——所思之物”(Ego-cogito-cogitatum)为意识结构[14](P.64),发展出了主客合一的现象学认识论。
“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共生,从根本上决定了康德与胡塞尔两人所建构的认识论体系都必定会触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从而藉由“想象”隐含地建构出某一基本人观模型。但是,由于各自所力推的认识论取向使然,康德仅仅关注于“先验自我”,毕竟自我被其确立为唯一的认知主体,与此相应,他人只是自我的认知对象;而胡塞尔不仅关注于“先验自我”,认为“先验现象学是从‘先验自我’开始的,‘先验自我’建构了对象世界,也构造了主体自身”[15],而且还关注于“先验‘我们’”,毕竟自我与他人皆被其视作认知主体,从这一意义上讲,主体是复数性的。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从认识论上阐释“先验‘我们’”,或者说,针对“先验自我”与他人的共在何以可能,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所谓“主体间性”主要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性、统一性。在胡塞尔看来,“先验自我”与他人互为“他者”,“交互构造”,由此形成“具有相互融合的先验‘世界视域’”的共同体[16]。
就来自“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而言,其主要原因则是他们因身处域外,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经验,而更易于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审视。更进一步地说,“局外人”心态的具备使得这些社会心理学家也同样不再自缚于将社会心理学视为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偏狭定位,转而认同于将社会心理学视为涉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学科的开放定位,并据此力推跨学科的沟通与整合。例如,莫斯科维奇自其学术生涯开启,便一直是多学科交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支持者与实践者,他本人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在认识论上具有独立性的交叉学科,它能够将分散在诸如常人方法论、符号互动论,以及经济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群众心理学、语言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学科中的有关成分“联结”并“缝合”在一起[31],等等。
历史地看,康德与胡塞尔两人所力推的认识论取向均对后世心理学深有影响,其影响或隐或显地折射出基本人观模型建构的分野。具体而言,康德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其先验图式说之于以生物有机体隐喻人类认识活动的认识发生论、以计算机隐喻人脑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观具有奠基作用[17],其所引领的是一种偏于聚焦人的“主体性”——与“个体性”、“唯我性”、“自为性”、“自足性”等系同义语——的学术传统;胡塞尔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其基于想象学进路对以“还原的自然主义”(reductive naturalism)与“客观主义”(objectivism)为哲学基础的实验心理学的批判,以及对旨在探索“人类具有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意向性生活”(human subjective and intersubjective intentional life)的“‘纯粹’心理学”(‘pure’ psychology)之构建的推动上[18](P.100),其所引领的是一种偏于聚焦人的“主体间性”的学术传统。
由此联系前文可以推定,“内在心理模型”的建构是以康德所力推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为基础的;“人际与社会模型”的建构是以胡塞尔所力推的主客一元统一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具体言之,前一种基本人观模型以“封闭的人”为预设,将个体看作“超然于社会之外的真正的存在”,或者说,是“完全与其他人相脱离、相隔绝、完全独立自主的人”;后一种基本人观模型以“开放的人”为预设,将个体看作“或多或少地拥有一种相对的——但绝非完全的和绝对的——自主权”,而且“整个一生都必须向他人看齐,都必须依靠和依赖于他人”的人[19](P.25,38)。两者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去脉络化的,后者则是脉络化的——人与人在互为主体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始终嵌入在特定背景之中。
综上分析可见,基本人观模型作为“整体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想象性建构;它一旦被建构出来,即作为“元理论”,对其持有者在研究实践中的“想象”起到指导和制约作用。换言之,“想象”不仅对基本人观模型具有建构作用,而且在基本人观模型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之间起中介作用(参见图2)。当然,透过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想象”与认识论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后者一旦成型,便会对“想象”起到制约作用;最终推动实现基本人观模型演替的研究反思,也必定会对本体论与认识论,以及两者所制约的想象模式有破有立,通过对此进行梳理,即可厘清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心智素质(参见图2)。
制作:1.将苕粉用温水泡发,洗一下,沥干水;火腿切片;海带用水发好,洗去杂质,沥水,切块;黄豆芽去脚,沥干水,以上原料分别装盘待用。
图2以想象为核心的研究反思过程示意图
四、社会心理学研究反思推动下的基本人观模型演替
实验社会心理学是植根于“封闭的人”这一基本人观模型,且最早实现建制化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历史地看,在实验社会心理学长期占据着宰制性地位的社会心理学发展进程中,从来都不乏对潜隐在实验社会心理学知识生产实践之下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基本人观模型进行反思,并因此超越以“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为核心的“唯理智主义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的学者。所谓“唯理智主义偏见”是指一种以旁观者而非实践者的心态来看待世界,从而不假思索地将自己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同时对隐含在“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践操作”之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致于以“理论逻辑”(theoretical logic)代替“实践逻辑”(practical logic)的“学术无意识”(unconsciousness of intellectuals)[12](P.39-40,192)。
当然,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研究反思理应成为研究者共同参与的“集体事业”(collective enterprise),而不是压在单个学人身上的重担[12](P.36,40)。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心理学研究反思作为一项集体事业的兴起,就不可能有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或并行发生的由“封闭的人”到“开放的人”的基本人观模型演替,毕竟这并不是单个或少数学人能够推动实现的。鉴于此,有必要先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反思作为一项集体事业的兴起作以概述,而后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反思推动下的基本人观模型演替动力逻辑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社会心理学研究反思作为一项集体事业的兴起
实验社会心理学之于美国,是一种“本土社会心理学”,而其之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则更多地是一种“舶来社会心理学”。历史地看,实验社会心理学作为“本土社会心理学”,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并在遭遇经济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迎来了短暂的“黄金发展时期”(golden age)[20][21];其间又作为“舶来社会心理学”,经由著作译介、留学生教育、学术访问、短期培训等途径被输入到欧洲大陆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菲律宾、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由此形成了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以美国为“核心”(core),以其它发达国家为“半边陲”(semi-periphery),以发展中国家为“边陲”(periphery)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世界体系[22](P.162)。从(实验)社会心理学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力来看,“核心”最强,“半边陲”次之,“边陲”最差。伊朗裔美国心理学家莫伽达姆曾据此将这三者分别称为“第一世界”(the first world)、“第二世界”(the second world)及“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23]。客观地讲,“第一世界”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知识传播之于“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而言,实质上是一种以检验其实验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普适性为动因,以构建世界社会心理学为愿景的隐性殖民扩张。正是由此使然,“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最初发展出的社会心理学均被深深地打上“第一世界”的烙印,或者说,完全带有“美国味”[5]。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实验社会心理学危机日渐凸显,其中,它在“第一世界”的发生是以多重危机(包括经济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事件、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反越战运动等)交织并存,学生与学术研究资助者期求提升相关研究的可应用性及社会关联性等为背景;在“第二世界”的发生是以冷战对峙持续存在,欧洲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政治冲突、反战示威及民权运动纷涌而出等为背景;在“第三世界”的发生是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自信心大幅增强等为背景。面对危机,来自“第一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力图在对作为“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社会心理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重建公众对社会心理学的信心;来自“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虽然都希图在对作为“舶来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社会心理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但不同的是,前者力图使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回归本土社会历史与现实及既有学术传统,以冀打破美国的话语霸权;后者力图提升社会心理学与本土社会文化现实的契合性,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不难看出,20世纪60年代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知识生产体制因遭受重创而由紧转松,从而使反思得以蔚成“集体事业”的分水岭;反思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其一是以来自“第一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为主体,以本土社会心理学为客体的内生性反思(以下简称“内生性反思”),其二是以来自“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为主体,以舶来社会心理学为客体的外发性反思(以下简称“外发性反思”)。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来看,内生性反思者在数量上呈现出由少到多的变化趋势:前有奥尔波特(Allport, F. H)、布朗(Brown,J. F)、勒温(Lewin, K)等寥寥几人;后有卡特赖特(Cartwright, D)、多伊奇(Deutsch, M)、费斯汀格(Festinger, L)、格根(Gergen, K. J)、桑普森(Sampson,E.E)、谢里夫(Sherif,M)等众多学者;而外发性反思者在数量上则几近呈现出由无到有的变化趋势,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金(Kim, U)、莫斯科维奇(Moscovici, S)、泰弗尔(Tajfel, H)、特纳(Turner, J.C)、杨国枢、杨中芳等。耐人寻味的是,在以上这些学者中,不少人都曾在其学术生涯早期接受过实验社会心理学训练,继而在某一或某些领域从事具体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步入学术生涯中期或晚期之后,却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转向了对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批判与重建,其反思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本体论与认识论,以及与两者相关联的基本人观模型。
(二)社会心理学研究反思推动下的基本人观模型演替动力逻辑分析
1.“局外人”心态消解学术无意识对学术视野的宰制
社会心理学反思者大多因具备“局外人”(outsider)心态——通俗地讲,即其从未或不再一如既往地自视为实验社会心理学阵营中的一员——而得以摆脱“学术无意识”的束缚,从而使自己能够在反思中有效地扩展了“认知输入”(cognitive input)的范围[24](P.69-71),进而以更为丰富的想象力拓展了学术视野,由此推动了对本体论与认识论,以及其中所隐含的想象模式的重构,从而为由“封闭的人”到“开放的人”的基本人观模型演替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直接反映在研究视角或学科定位由偏狭到阔达的转变上。基于解释水平理论来看,这一转变意味着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与研究客体——“人”的“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趋于增加,其所持的解释水平也随之由低转高,从而能够更好地“看到”有关人的存在的“大图景”(big picture)[25](P.123)。
就来自“第一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而言,他们之所以具备“局外人”心态,或是因为其一直游离于学术场域的中心之外,勒温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或是因为其学术志趣转向或年事已高而淡出学术场域的重要位置,奥尔波特、布朗及多伊奇等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或是因为其能动性因自身所嵌入的知识生产体制受创——亦即社会心理学危机的发生——而得到极大释放,从而使有关自身及其学术实践的反思意识大为增强,费斯汀格、格根、谢里夫、卡特赖特等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例如,勒温在其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移居美国之后,因不满于彼时社会心理学与现实生活的疏离,而格外强调和重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发展,并为此而在二战接近尾声时满怀社会关怀精神地创建了致力于推进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继而试图从“群体生活”(group life)切入,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构建以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联为焦点的宏大心理学理论,这一抱负在勒温所撰的一篇明确提出“为研究群体生活而整合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论文中有充分的体现[26][27](P.33);又如,奥尔波特在二战结束后,带着对曾倾力推广的实验法的失望、曾斥为“群体谬误”(group fallacy)的集体行动的兴趣,以及曾予以否认的社会复杂性的执迷,转向了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的集体行动结构、动力及系统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对其早期观点及研究取向进行了批判性重估[28];再如,费斯廷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乏新可推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心生厌倦,于是便不恋已获盛誉,改而从事知觉研究,但到了70年代末,却又因不满研究在对“愈来愈狭隘的技术问题”的沉迷中失却了原初关怀,而毅然决定关闭实验室,并由此抱持着“为能够看清人类社会而寻觅一个相距足够远的立身之处”的信念,转入比较史学、古生物学等其它研究领域,其学术兴趣最后定格在文化与认知关系方面[29][30]。相较于实验社会心理学惯有的偏于关注他人的各种在场(包括现实性在场、想象性在场及隐含性在场)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或个体头脑中的信息加工过程的研究视角,以上这些社会心理学家所力推的研究视角有了很大的扩展。
以上三位学者堪称社会心理学界的巨擘,他们无不或隐或显地指出了个体与个体的相互依存性,以及社会相对于个体的突生性。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维奇与多伊奇直接阐明了个体与社会互为建构的关系。
刚从厂里出来,贾鹏飞身上和头发上还沾着零星的木材灰屑,范峥峥为他拂去一些,看着以前英俊、而现在眼角也出现皱纹的贾鹏飞,眼圈红了一下。
河湖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资源、水生态的重要载体,河道湖泊空间及其水域岸线是强化河湖管护、维护河湖健康的生命线。但我省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滞后,目前普遍存在河湖管理和保护范围边界不清、水土资源产权不明等问题,导致一些开发建设项目、生产经营活动及人为活动随意侵占河湖范围,与水争地、侵害水域空间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威胁河湖生态健康,损害河湖生态环境。
2.学术视野的拓展推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再认识
(1)突发疾病、意外伤害的处置预案。志愿者在户外工作中遇到游客突发疾病,应立即就近处置送往最近的医院就诊或拨打120急救。
此外,参会代表们还参加了“我们的海洋2018” 会议的一系列边会和展览,与各国与会者交流海洋保护各相关议题所面临的挑战和国际行动的进展,例如海洋塑料污染、珊瑚礁的未来、蓝色经济、蓝碳、全球渔业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可持续海鲜采购链。会议最后一天,参会代表们前往珀尼达岛海洋保护区实地考察。
例如,奥尔波特曾在对其早期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与还原主义研究取向——将“社会”还原为“个体”,通过研究“个体”来研究“社会”——进行批判性重估时指出,“孤单的个体”(The lone individual)固然可以量度,但却难找到,即便能够找到,仅对其进行研究,也很难藉以理解和把握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毕竟由于彼此之间的互动使然,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迥异于其独处时的行为[32]。
3.“社会”的重新回归带动脉络化研究取向的兴起
学术视野的拓展使社会心理学反思者得以全面深彻地审视人的存在,从而开启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再认识。从总体上看,社会心理学反思者大都倾向于摒弃以“封闭的人”为预设的“内在心理模型”,转而选择抱持以“开放的人”为预设的“人际与社会模型”。为了说明这一点,在此援引以下数例予以佐证:
再如,多伊奇曾在回顾其学术生涯时含蓄而不失犀利地指出,美国社会心理学知识生产有其文化局限性:美国社会是高度个人主义社会,身处其间的社会心理学家在崇尚个人奋斗、个性自由、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美国精神影响下,过于关注发生在个体“孤立头脑”(isolated head)之中的心理事件或过程,却忽略了个体的参与建构,因而反受到某种制约,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个体的社会关联特性”(socially relevant properties)与“社会结构的心理关联属性”(psychologically relevant attributes)[34](P.1-34)。
其一,地域文化广泛存在。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诸多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如以今之陕西为中心的秦文化、以今之山西为中心的晋文化、以今之山东为中心的齐鲁文化、以今之四川为中心的巴蜀文化、以今之湖南、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和以今之浙江、福建为中心的吴越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一直承传、发展到今天并还发生着重大影响。
又如,莫斯科维奇曾在对尤为关注个体的内在心理过程特别是所谓“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但同时大都忽略了“情景的互动面相”(interactional aspects of the situation)的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的社会文化根源及其逻辑、后果、走向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区分出了三种社会心理学,即“分类性”(taxonomic)社会心理学、“区隔性”(differential)社会心理学、“系统性”(systematic)社会心理学。其中,第一种社会心理学无视“主体”在人格类型上的差异,但视“社会”为“客体”的一种属性,由此将“客体”划分为“社会性客体”与“非社会性客体”,并重点关注“客体”的属性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第二种社会心理学无视“客体”在属性上的差异,但却基于人格特征(例如认知风格、情感特征、动机、态度等),将“主体”划分为不同类型,并重点关注“主体”的人格特征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第三种社会心理学聚焦于因多个“主体”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地同其所共有的物理或社会环境发生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整体现象。在同一研究中,莫斯科维奇还以唯一可观照和阐释社会互动过程的“系统性”社会心理学——可以具象化为动态三角形“自我-他人-客体”(Ego-Alter-Object)——为参考,深刻厘清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及“社会客体”(social object)的内涵:“社会”是由“群居的个体”(collective individuals)之间的关系构成,且自有其历史、规律及动力的系统,它作为一种先于个体而存在、“被给定”(given)的环境,以其法则不断生产着个体;群体与个体作为社会客体,相互控制着对方,并建构着他们的“团结纽带”(bonds of solidarity),以及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不同之处[33](P.17-68)。
社会心理学反思者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再认识,使“社会”重新回归社会心理学。当然,一起回归的还有“文化”与“历史”,毕竟“社会”、“文化”与“历史”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社会心理学反思者大多主张将“社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与“历史”纳入研究视域,从而直接推动了脉络化研究取向的兴起。脉络化研究取向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基本人观模型演替的真正实现,还意味着想象模式的破立。仅从以下几位颇具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学反思者的研究中,便可窥一斑。
以提出社会认同理论而闻名的泰弗尔在其去世前不无忧虑地以“真空中的实验”(Experiments in a vacuum)为题撰文指出,由于许多研究者时常基于“实验能够为理论检验提供(将“历史”与“文化”排除在外的)‘纯粹’(pure)的环境”这一预设,而开展一些与现实相疏离的实验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正逐渐沦为一门无足轻重的“被实践于社会真空之中”(practised in social vacuum)的社会科学,然而,从根本上来讲,所谓“‘纯粹’的环境”不可能存在,毕竟身为个体的被试始终会带着其所属群体所共享的“历史”与“文化”参与到实验中,因此,与其徒劳地通过创设“纯粹”的环境来控制“文化”与“历史”,还不如将所欲研究的心理因素置于相应的文化与历史脉络下加以审视和观照,事实上,也惟有如此,才能构建出既见“个体”,又见“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的有意义的理论[35](P.69-121)。
瓦格纳(Wagner, W)、杜维恩(Duveen, G)及法哈尔(Farr, R)等人对在莫斯科维奇所谓“系统性”社会心理学的框架下,发展出的社会表征理论及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评述时,指出社会表征理论作为一组可资以研究现代社会中的心理社会现象的概念与观点,其本身就隐含有一种脉络化研究取向——“惟有将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置于其所嵌入的历史的、文化的,以及宏观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对其予以正确理解”;引入这一研究取向,正是为了克服建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以及“从功能上将主体与客体区隔开来的认识论”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中现有各种理论及取向的种种缺点[36]。
杨中芳在探讨“如何深化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这一问题时,直接将“本土心理学”界述为“在考虑研究个人的心理活动或行为现象时,将‘文化/社会/历史’脉络放在思考架构之中的一类研究”[37]。在同一篇论文中,她还专门讨论了如何将“文化”、“社会”及“历史”置于本土研究思考框架之中。
由此联系进化心理学家所提出的有关观点——进化心理学能够为心理学(包括社会心理学)及其它社会科学提供元理论基础[38];“文化与社会的发生以心理为基础,心理的发生以生物进化(biological evolution)为基础”[39](P.635),可以将此处所谓“脉络化研究取向”拓展为一种同时将“生物(进化)”与“社会”、“文化”及“历史”纳入视域的研究取向。引入“生物(进化)”面相,将有助于社会心理学研究更好地认识人类的心理何以是“一种心智,多种心态”(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40]。当然,从广义上讲,“生物(进化)’”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只不过它更多地是指人类种系发展史,因此可将之归入“历史”面相。
五、讨论与结语
透过前文分析,至少可以看出三点:其一,基本人观模型实为一种想象性建构,它作为“元理论”,通过影响“想象”的建构作用而对社会心理学研究产生影响,而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则可以通过反思自身及其学术实践来重构基本人观模型;其二,反思作为一种以破陈立新为其目标指向的认识过程,同样无法绕开所谓“认识论难题”,因此它也必然要以想象为支撑,否则无以展开;其三,社会心理学研究反思在没有偏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核心议题的前提下,力主将人的多重存在面相——“社会”、“文化”及“历史”(包括“生物(进化)”)——纳入研究视域,由此以个体与社会的辩证互动为基底,建构出一种兼顾宏观、中观与微观的新型想象模式。
上述前两点无疑表明,“想象”在整个社会心理学研究实践中处于核心地位。当然,至于“想象”是否足以支撑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做出能够使人更好地洞彻人性、理解社会的研究,则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具备的心智素质。那么,以史为鉴,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应具备一种什么样的心智素质呢?基于上述第三点,并联系前文对“内在心理模型”与“人际与社会模型”两种基本人观模型,在社会心理学反思推动下发生演替的动力逻辑所作的分析来看,它应是一种以“开放的人”为预设,以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为焦点,将有关社会心理与行为置于“文化”、“社会”与“历史”(包括“生物(进化)”)等远端宏大面相之间的交织互动中加以审视和观照,从而使人在理性认识层面跳脱出个人经验及近身情景或环境之局限的心智素质。为方便表述,可将之称为“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
多模射频前端的实现包括硬件电路的搭建以及FPGA对射频链路的配置,其处理框图如图5所示。多模射频接收链路配置模块主要包括:各芯片写控制模块,射频混频参数查找表模块及指令接收模块。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的认识,还需结合社会学、进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已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其基本内涵与理论框架进行探析,以冀正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文化”、“社会”与“历史”(包括“生物(进化)”)三者的交织互动,以及其与“心理”的关联。
八是深入推进抗旱基础工作。继续开展重要江河、湖泊、重点水库旱警水位(流量)的确定工作,为抗旱指挥调度和应急减灾行动提供技术支撑。加强墒情监测站点建设,完善旱情监测网络和预警系统。深入开展旱灾评估标准研究,完善旱灾影响的评估方法指标体系,为抗旱指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郭远兵,孙时进.叙述社会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特异性——以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为契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
[2]Jackson, J. M. Social psychology, past and present: An integrative orientation[M].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8.
[3]Burr, V. The person in social psychology.[M].London: Psychology Press, 2002.
[4]Schein, E. 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M].San Francisco : Jossey-Bass, 2004
[5]Hjrland, B. Theory and metatheo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a new interpretation[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98, 54(5).
[6]Finkel, E. J. The I3 Model : Metatheory, Theory, and Evidence[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4, 49.
[7]Wagner , D. G. The Growth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M].Beverly Hills , CA : Sage Publications, 1984.
[8]Abrams, D.,& Hogg, M. A. Metatheory: lessons from social identity research[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4, 8(2).
[9]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0]Mannheim, K. Ideology and utopia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4
[11]Cohen, M. R. Reason and nature[M].Oxford, England: Kegan Paul, 1931.
[12]雷德鹏.走出知识论困境之途——休谟、康德和胡塞尔的想象论探析[D].复旦大学,2005.
[13]贺炳团.胡塞尔是如何克服康德二元论哲学的[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14][美]维拉德-梅欧,V.胡塞尔[M].杨富斌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
[15]王鹏.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及其困境[D].吉林大学,2009.
[16]李金辉.自我与他者关系:一种主体间性现象学的反思[J].江海学刊,2015(3).
[17]惠莹.试论康德、皮亚杰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观[J].社会心理科学,2010(Z1).
[18]Moran, D. Husserl’s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德]埃利亚斯,N.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M].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0]House, J. S. The three faces of social psychology[J].Sociometry, 1977, 40(2).
[21]Sewell, W. H.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Golden 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Psycholog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9, 15(2).
[22]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volume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3]Moghaddam, F. M. Psychology in the three worlds: As reflected by the crisis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move toward indigenous third-world psychology.[J].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7, 42(10).
[24]Lehrer, J. 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M].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25]Trope, Y., & Liberman, N. Construal level theory[A]// Van Lange, P. A. M., Kruglanski, A. W. & Higgins, E. T.,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One)[C]. London: Sage, 2011.
[26]Lewin, K.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Sociometry, 1945, 8(2).
[27]Patnoe, S. A narrative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The Lewin tradition[M].New York/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8.
[28]Faye, C. L. A problem of cosmic proportions: Floyd Henry Allport and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ity in 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y[D].York University, 2013.
[29]Festinger, L. (ed.). Retrospections on social psychology[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0]Schachter, S. Leon Festingery[A]// Biographical Memoirs (V64)[C].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94.
[31]Moscovici, S. Preconditions for explan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 19(5).
[32]Allport, F. H. Part I: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Z].Allport ,F.H.papers (Box 1, Folder: Methods in social psychology: Schools and approache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 1948.
[33]Moscovici, S. Society and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A]// Israel, J., & Tajfel, H., (eds.). The context of social psychology: a critical assessment[C]. London: Academic Press,1972.
[34]Deutsch, M. 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psych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Rodriguez, A., & Levine, R. V.,(eds.). Reflections on 100 Years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C].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999.
[35]Tajfel, H. Experiments in a vacuum[A]//Israel, J., & Tajfel, H.The context of social psychology: A critical assessment[C]. Oxford, England: Academic Press, 1972.
[36]Wagner, W., Duveen, G., & Farr, R., et al. Theory and Metho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1).
[37]杨中芳.试论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学研究:兼评现阶段之研究成果[J].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1).
[38]Buss, D. M.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J].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5, 6(1).
[39]Barkow, J. H. Beneath new culture is old psychology: gossip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A]//Barkow, G., Cosmides, L., & Tooby, J., eds.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C].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0]Shweder,R. A.,Goodnow,J. ,et al.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development: One mind,many mentalities [A]// Damon, W.,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5th Ed., Vol. 1)[C]. New York:Wiley,1998.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1—021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群己关系视角下城市商品房社区居民的社区感研究”(18YJC8400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曙光,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山西 太原 030006
收稿日期2018-10-20
责任编辑程融
标签:社会心理学论文; 社会论文; 模型论文; 认识论论文; 的人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群己关系视角下城市商品房社区居民的社区感研究"; (18YJC840054)论文;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