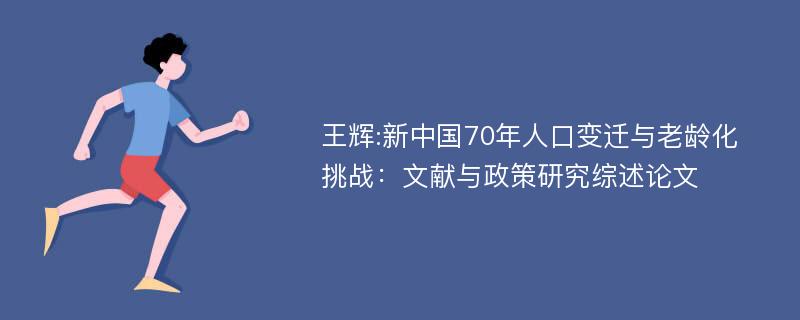
摘 要:本文回顾新中国70年以来人口的变迁历程,详细梳理相关的理论以及政策研究文献,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人口增长率变化的原因,总结分析当前中国面临的老龄化挑战,以期得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应对方案。文献分析表明: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生育率过低导致,而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一胎化政策,不能够完全解释6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养子成本的迅速上升,都是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主要结论是:在“人口转型”的大背景下,低生育率的形势往往难以逆转,通过放开生育限制或财政补贴鼓励生育来提高生育率的作用会相当有限,大批量放开移民的政策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延迟退休年龄是短期内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可行方案,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逆转老龄化趋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并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通过不断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改革,这样才能够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有效地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文的分析与结论,为正确认识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积极稳妥地制定应对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人口变迁; 计划生育; 人口转型; 人口红利; 老龄化
中国是人口大国,截至2018年末,人口总数近14亿,占世界18.4%。人,既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众多的人口,既可以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负担。回顾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复杂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最初的三十年间,中国的人口从6.02亿增长到9.62亿,年均增速为18.9‰,而同期人均GDP由90.5美元增长到307.77美元,年均增速仅为4.3%。1978年起,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推行了强制性的“一胎化”独生子女政策。从那时起至今四十年间,中国人均GDP以每年接近9%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人口的增速却降到了9.7‰[注]本段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其中人均GDP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只不过此时已不再是人口数量的问题,而是年龄结构的问题。中国正以极快的速度步入老龄化社会:1982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为4991万,仅占总人口4.9%;而到2018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达到1.66亿,占比超过11.9%。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当前的生育率过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是否是长期执行计划生育的结果?仅靠放开计划生育是否能彻底解决老龄化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能否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积极妥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社会风貌,同时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
目前文献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积累,但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系统、全面、深刻的梳理和总结的综述性文章尚不多见。同时,针对中国具体情况对老龄化问题进行评估与分析,并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符合国情的政策建议文章亦不多见。本文希望在这些方面作出有益的尝试。本文的主要特色有三点:第一,文章利用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和各类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梳理了人口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键事实,并提供了大量验证支持人口学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实证证据。第二,文章总结了前沿文献的重要观点,结合已有研究建立了严谨扎实的逻辑分析框架。第三,文章基于国际视角,同时参考有代表性案例与大样本数据证据,总结出人口转型与老龄化背后的一般规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回顾七十年来中国人口的变化历程,并总结各时期重要的人口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第二部分介绍“人口转型”现象,阐述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重要影响;第三部分讨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后果,并基于增长模型分析并量化不同的影响渠道;第四部分总结中国应对口老龄化挑战的可行方案;最后一部分为文章结论。
一、 新中国70年的人口变迁与计划生育政策
从图1中可以看出,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数量的基本上是呈线性增长:前三十年间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增长至1978年的9.6亿,增长了0.8倍;之后四十年人口进一步增长至2018年的14亿,为1978年的1.5倍。但这种线性的增长趋势,容易使人忽略一个背后的事实,即以复利率(compound rate)计算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实际上在不断下降。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注]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出生人口-年死亡人口)/年平均人口*1000‰=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决定的。图2反映了建国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以及死亡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由于建国后医疗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死亡率在短期内快速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Banister and Hill,2004),因此,人口生育率的变化,是中国人口增长率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图1 中国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图中纵向虚线表示1978年。
图2 中国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随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图中纵向虚线表示1978年。
图3 中国总和生育率随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度量一国人口生育率的一个直观且常用的指标是“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量,反映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倾向。图3展示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随时间变化趋势,总和生育率在建国早期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历史顶峰(接近8),然后在经历了一个快速下降的时期后持续走低。建国以来有哪些重要的政策或事件影响了这一重要指标的跨时变化,是本节要讨论的重点内容。
(一) 1978年之前的人口政策以及生育率变化
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政治、军事上的对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新中国的前途非常“悲观”。特别是在人口问题上,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紧缺的耕地与众多的人口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国政府靠自己将无法解决全国5亿多人的吃饭问题。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他的《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强有力地批判,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10页。”。毛泽东强调了“人”在社会中作为劳动者和生产者的作用,也间接为建国初期的人口观定下了“人多力量大”的基调。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刚刚结束,战后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稳定与改善,生育率大幅增加,人口数量呈现出快速、持续增长的态势。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数量已经达到6.02亿。
在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工业基础薄弱,快速膨胀的人口数量与社会生产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1957年3月,以马寅初、邵力子等为代表的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们先后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上发言,提出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的主张和建议。例如马寅初在他的《新人口论》中指出,“建国4年来中国人口增殖率为2%,照此推算,如果不控制人口,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口增长太快势必将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同时,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女性地位的改善,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节育的意愿也越来越强。1954年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就为已婚妇女干部生育负担重的问题致信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信中写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是带普遍性的”,“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地拟定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计生的重要性开始受到中央的重视,之后以政策宣传和推广节育为主要方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初步实施,使得第一次生育高峰有所回调,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4年的24.78‰下降到1955年的20.32‰。然而1957年4月开始的反右运动让实践不久的计划生育政策最终停摆。
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由于死亡率快速升高,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长陷入停滞,1960年甚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但是随着1962年后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得到控制,人口数量再次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到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7.2亿。
《全芳备祖》所辑陈景沂词共三首,《全宋词》俱收,见第4册第3022页。其中卷一梅花门《壶中天》全然无差,而另两首,《全宋词》与宋刻本文字稍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家正常的生产活动受到了严重干扰,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965年的2.14亩减少至1970年的1.84亩,人口数量与粮食产出不匹配的状况难以为继,人口数量过快膨胀的问题难以调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与井喷式的人口数量是不匹配的,经济构成以低生产效率的农业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农业耕地面积非常稀缺,重工业也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使得人口数量对于粮食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劳动力严重过剩更使得年轻人就业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央开始把人口控制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1971年7月8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地区以外,都要加强这一工作(计划生育)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工作,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做出显著成绩”。同时参照部分地区的经验和做法,中央逐步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杨发祥,2004)。“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稀”指生育间隔在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同时为了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1973年7月国务院批准恢复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即后来计生委的前身),地方也开始建立和健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虽然这一阶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原则上以群众自愿为基础,与之后全面实施的严格“一胎化”政策存在本质区别,但政策在实际推行时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Zhang,2017),实施期间全国的结扎数量和引产数量大幅上升(Whyte et al.,2015)。虽然“晚、稀、少”政策很好地控制了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势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这一时期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5~6下降到2~3的水平)。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到1978年全国人口数量还是达到近9.6亿。
(二)1978年“一胎化”政策的制定背景
人口形势的严峻与宏大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是70年代末施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的主要原因(Peng,1996;Hesketh,Lu,and Zhang,2005)。
首先,由于建国前三十年积累了大量人口,有限的自然资源与膨胀的人口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人地矛盾非常突出。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在90年代仅为1.3亩左右,是美国的1/9、欧洲的1/3、印度的1/2(Madison,1998),中国需要用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世界25%的人口。其次,中国当时农业的生产率较低,而城市的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给严重过剩,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就业问题。再次,建国初期“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会在1970年代中后期步入婚育年龄,这意味着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将迎来新的一波生育高潮。假如不加以限制,人口数量很可能在这一时期快速增加。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决策。中国的人均GDP在1978年为$250左右,要想在20世纪末之前翻两番[注]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达到$1000的水平,意味着人均GDP要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GDP的增长速度需要比人口增长速度快7个百分点。在这个意义上,快速的人口增长无疑会成为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压力。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或会见外宾的多个场合中反复指出,“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和底子薄”[注]《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49~150页。、“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地控制”[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26页。、“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只有250到260美元……但是我国人口多,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1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增加1000亿美元。人多有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60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8年,“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成为基本国策。次年1979年,被文献普遍认为是“一胎化”政策的起始年(例如,Schultz and Zeng,1995;Attane,2002;Peng,2011;Wang,2012)。随后,官方媒体上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为实行一胎化政策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与研究支持,使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逐渐形成了共识。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的问题》的文章,对于中国未来生育率和总人口数量的关系进行了预测,并指出了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于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性。同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不可或缺的选择。1980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党中央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号召党团员作为表率少生、优生;1983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大家都来算人口、耕地、粮食账》的评论员文章,提出力争在20世纪末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
(三)“一胎化”政策的理论基础
上述看待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观点,非常符合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1798年,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出版了著名的《人口原理》。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认为,只要条件适宜,人类总以极快的速度繁衍,因此,任何原因导致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在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下,人口的增加又会降低每个人能够拥有的生产资料,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该理论的重要结论是:任何短期的经济增长都会被随之而来的快速人口增长所抵消,这一现象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人均产出长期陷于停滞、且各国人均产出差异较小的现象。在以农业为主、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阶段,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会相互制约,假如不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那么总产出的增加并不能带来人均产出的同等增加,实质性的经济发展会被人口数量所拖累。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宏伟目标,控制人口是一个必要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人口政策的出发点实质上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延续,强调的是人口的过度增长对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制约作用。这是基于当时特定历史阶段与经济发展环境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历史客观性。但从现在的角度看,容易发现当时的人口政策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实与变化,使其不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建国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的不断恢复与繁荣,加上医疗与公共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了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生育率的提高,全球人口都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增长了1.82倍,而同期世界人口也增长了1.76倍,欠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增长速度更快,分别增长了1.96倍和2.01倍[注]根据世界银行人口数据计算。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这说明人口快速增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例如,在教学《背影》一课时,教师在引导学生着重赏析“父亲过月台”的一系列动作描写之后,可以引导学生感受这些字眼中融合的父爱、作者写下这篇散文所赞颂的父爱及对父亲的爱,然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请学生分享生活中父亲对自己的爱,并请学生说说“作为学生,该如何去回报父亲的爱”。如此,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在课堂上有意识地渗透了人文素质教学,发挥出了现代化教学的教育职能。同时,通过通俗情感性教学,教师将教材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引导出学生的共情,促使学生“有话可说、有情欲诉”,增加学生积极交流的欲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第二,马尔萨斯理论的失效。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与经济的发展趋势开始背离了马尔萨斯理论的预期,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战后人口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带来人均收入的降低,反而出现了经济和人口同时增长的全新局面。马尔萨斯理论失效的重要原因是其没有估计到工业革命之后,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不再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取而代之的是物质资本,即机器、设备、厂房等。这正是当代经典经济增长模型—索罗模型的基本设定。不同于悲观的“马尔萨斯陷阱”,索罗模型认为,一国只要能够实现物资资本的不断积累、技术的不断进步,就能够超越自身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第三,忽略了“人口转型”的重要作用。“计划生育”制定过程中,参考了诸多人口预期模型的结果。但这些模型均是依据历史数据,假设人口的生育率维持在一定水平,进而推导出未来人口的数量与增长速度。事实上,这种假设忽视了20世纪人口学发现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人们的生育意愿在工业社会环境下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降低。这一现象称为“人口转型”。该现象直接与马尔萨斯基于农业社会的观察相左,也是马尔萨斯理论失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关于“人口转型”的原因与相关分析,本文将在下一章节进行详细介绍。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70年代末的人口预测模型没有考虑“人口转型”这一现象,会导致对未来生育率的高估,从而高估了潜在的人口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人口数量形势的严峻性。
(四) “一胎化”政策的执行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施行了强制性“一胎化”政策并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的大国。这样一个深刻影响每一个家庭的政策能够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迅速铺开并有效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因此,了解政策的执行细节,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并评估该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重点介绍其执行过程中的行政立法、执行机构、奖惩机制、以及人群差异化等四个方面。
1.行政立法
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经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53条指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被纳入国家根本大法,成为基本国策。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经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条文“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第49条: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第89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领导和管理计划生育工作”。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经修订的《婚姻法》,修订后第2条第2款:“实行计划生育”、第5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以鼓励”、第12条:“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此外,在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收养法》、《母婴保健法》、《劳动法》、《刑法》等法律中均有涉及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
2.主管机构
为了指导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开展,作为临时性的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于1981年3月6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会议同意,升格为部委一级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和推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计生委)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令,管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实现各个时期的人口发展规划,使之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计生委的主要职能包括拟定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发展规划、组织和实施计划生育、督促和检查地方落实情况等。1979至1984年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建立起了地方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基层执行机构,形成了自上到下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统一管理的工作网,全国计生(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从1979年的4.5万人迅速增加到2001年的52.7万人(杨发祥,2004)。这一庞大的政府机构为“一胎化”政策在全国范围的铺开提供了必要的人员保障。
3.奖惩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在以上的计算过程中我们没有考虑到不同年龄群体的异质性,在加总过程中采取了相同的权重。而事实上,由于儿童和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存在差异,两者所带来抚养压力并不相同(Weil,1997)。Cutler et al.(1990)把个体总消费分解为非医疗支出、公共教育支出和医疗保障三个方面,并利用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消费数据进行加总,发现0~19岁人口的消费需求仅为20~64岁人口的72%,但是65岁及以上人口的消费需求是20~64岁人口的1.27倍。经过消费加权后重新计算,他们发现美国在“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红利期的抚养比明显降低,然而人口红利消退期的抚养比明显升高。这说明对于受到人口转型影响、步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来说,实际的抚养压力会更高。借鉴Cutler et al.(1990)的方法,我们也对中国的抚养比进行了调整。图11B展示了调整后的总抚养比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到考虑到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相对更高这一因素,在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阶段中国将面临更大的社会抚养压力。
光线从背后照过来,叶晓晓半躺在一张贵妃榻上,右手支着头,左手顺着身体轻轻抚在髋骨上,头微扬。光线打在脸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小麦色光芒,身体的调子半明半暗,立体感很强,光洁如玉的身体因为青春和饱满微微发出润泽的光芒。
除了上述罚款外,违反独生子政策的家庭还无法享受一系列社会福利,如子女上学、医疗等都不能享受补贴价格。违反独生子女规定的个人在企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机关中的工作晋升会受到很大影响。
图6显示了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以及人均GDP的关系。首先,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越低,这印证了人口转型的现象;其次,样本中的大部分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总和生育率都已经降到了2.1以下(TFR=2.1在图中以虚线表示),这说明老龄化是一个全球现象,而不是某些国家特有的个案(Lutz et al,2008)。198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为3.82亿,2017年增加到9.62亿,预计2050年将达到21亿,同时所有国家在2017年到2050年间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均会增加[注]“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7 Revision”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7-revision.html。
4.人群差异化
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在“一胎化”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政府采用了因地制宜地区别对待方针。
第一,城乡差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广大农村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再加上农村长期受到“养子防老”、“传宗接代”等生育文化影响,国家的生育政策与家庭或个人的生育需求之间存在重大反差。农村地区多次出现抵制“一胎化”政策的情况,部分对立严重的地区还出现了恶性事件。此外,由于农村相比城市人口密度低、分布分散、交通不便,并且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在农村推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难度远高于城市。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针对农村计划生育推广难度大的特点,提出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地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限制的具体要求,明确指出“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在基层农村的实际执行过程中,被证实是行之有效、覆盖面广且争议较少的方式是根据家庭第一胎子女的性别差异化执行,如果是女孩,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如果是男孩则不允许生二胎。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农村地区执行的实际上是“1.5胎”政策。
第二,汉族与少数民族差异。考虑到少数民族人口基数比较小、主要分布在相对偏僻的农村地区、生产水平较为落后,并且长期受到自身文化习俗熏陶的特殊情况,国家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内部基本没有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但是随着“一胎化”政策在全国大范围推广,1987年中国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批示》,批示指出“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以适当放宽一些”。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夫妇一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个别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先后顺序不同,并且通常都是经过试行后才开始全面推广,不同地区控制人口增长的效果差异很大。
综上,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过程中采取各项切实有效的护理可有效减少患者致残致死率,提高生存质量。
(五) “一胎化”政策效果评估
“一胎化”政策在降低人口生育率上有多大贡献?从图3可以看出,自1978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政策实施前的2~3下降到了现在的1.5左右。人口数量基本达到了“在2000年前将人口控制在12亿”(2000年实际人口为12.67亿)的目标。同时,人口增速大幅放缓,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进入21世纪后已经下降到7‰以内。在一胎化政策的最初20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了70%,是人类历史上下降速度最快的记录(Chen and Liu,2009)。严格“一胎化”政策也催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家庭,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家庭为1.5亿户,占全国家庭的近37.5%(总共约4亿户)。从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角度来看,“一胎化”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图4 总和生育率跨国比较(1960-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进行整理。
但是,基于这些观察就将近三十年的生育率降低全部归因于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是十分武断的(Zhang,2017)。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如图3所示,在严格“一胎化”政策全面推行之前,中国已经实施了多年的“晚、稀、少”政策,生育率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因此“一胎化”政策时期也很可能包含了前期政策的滞后性影响。第二,“一胎化”政策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开始,在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家庭生育观念和生育决策也悄然发生改变。第三,近几十年来生育率降低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图4中列举出了一些没有长期实施过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国家,其生育率与同时期的中国相类似,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
因此,想要准确识别“一胎化”政策的影响并不容易,已有文献采用的方法可以主要划分为两类。第一,在家庭微观层面,控制家庭特征和时间趋势后比较政策实施前后家庭生育二胎或多胎的情况(Ahn,1994;Ding and Hesketh,2006;Whyte et al.,2015)。要想估计独生子女政策下,家庭的生育意愿降低了多少,关键是要知道“如果没有独生子女政策,这些家庭原本的生育意愿”。这样一个反事实的数据在实际中是无法观测的。而此类文献的主要想法就是,利用在政策执行前、不受“一胎化”政策影响家庭的生育倾向来近似的度量上述的反事实生育意愿,这样就能识别政策的实际效果。
第二,利用“一胎化”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差异性执行(例如不同省份的超生罚款、汉族与少数民族),将微观家庭数据和地区数据结合识别政策“强弱”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McElroy and Yang,2000;Li et al.,2005;Liu,2014;Huang et.al,2016)。这一做法则要求政策的差异性是严格外生的,该假设在户籍制度抑制跨人口流动的情况下,能够近似地得到满足。
这里对文献利用上述方法所发现的结果进行总结。Cai(2010)利用2000年江苏和浙江的县级数据,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和人均FDI)可以解释67%的生育率变动,但是在加入政策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度只提高到71%,说明在给定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一胎化”政策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Li et al.(2005)发现“一胎化”政策显著降低了家庭生二胎与三胎的概率;McElroy and Yang(2000)发现计生罚款每增加1500元,生育率就会降低0.33~0.47;Wang et al.(2017)构造了模型,基于观测到的人口变化数据模拟了一些反事实的人口变化趋势,发现假如在1980年没有执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总和生育率最晚也会在2010年左右下降到1.5~1.6左右(实际是2000年达到1.6左右)。这意味着,没有“一胎化”的政策,人口生育率也会降低,而“一胎化”政策的一个显著效果是加速了这种生育率降低的过程,使后文所讨论的一系列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
综上所述,从政策效果来看,“一胎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政策制定初期控制人口数量、推动优生优育的目标,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通过文献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胎化”的政策并不能全部解释近40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比如,周边的没有施行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其生育率同样发生了显著降低。因此,似乎是存在其他的力量,深刻影响着生育率的动态变化。这一现象即为前文所提到的“人口转型”,在接下来的一节里会进行重点讨论。
二、 人口转型与老龄化
“人口红利”的枯竭,首先体现在劳动力数量的迅速减少。如上文所说,中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50、60年代维持在了较高的水平。这些“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会在20世纪70、8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会导致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人口红利开始体现。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每个代际出生的人口逐渐减少,因此当“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劳动力在2010年2020年开始退休的时候,新补充进来的劳动力便不足以补充退休所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因此总体劳动力数量不断降低。
图5 世界主要大洲总和生育率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进行整理。
上述图像中所展现出来的,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前工业时代”过渡到“工业化”经济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人群生育率下降的现象,被称为“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人口学家沃伦·汤普森(Warren Thompson)于1929年提出[注]1934年,法国人口学家阿道夫·兰德里(Adolphe Landry)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发现出生率下降与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出现的现象较为普遍。美国人口学家佛兰克·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在20世纪40和5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并用人口转型的角度对其他国家的人口趋势进行预测。。在那之后,该现象不断地被数据所印证,成为20世纪世界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文献中所提到的人口转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中国来说,1990年以来中国的TFR就开始低于世代交替的2.1水平,并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持续走低(见图3)。到2017年底,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1.9%,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图7报告的是反映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金字塔”,并通过跨年比较体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从建国初期到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从“金字塔形”逐渐转变为“纺锤形”,在未来甚至会变成“风筝形”,这意味着年轻人的绝对数量在减少、年龄分布的中位数不断上升,同时年轻人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占比不断增加。
第二,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削弱了“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经济不发达、收入水平较低,同时金融体系还未建立,个体常常难以在劳动年龄期间准备足够储蓄来维系老年时期的生活开支。同时现代福利制度尚未出现,缺乏对于广大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和强制储蓄措施,家庭仅能依靠后代来解决老人赡养问题。随着工业化的到来,人均收入开始快速增加,人们有条件通过储蓄来维持年老时的生活支出。同时以缓解贫困问题、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条件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始出现,现代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们可以利用借贷来平滑消费实现效用最大化,多种形式的理财和融资渠道也促进了储蓄的积累(Gurley and Shaw,1955)。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得即使是低收入群体也可能通过转移支付来维持生计,过去“养子防老”的动机逐渐弱化,从家庭层面生儿育女不再是养老的必要保障,这也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第三,婴儿死亡率下降。在过去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中,由于医学知识的匮乏,接生过程中常常出现因为未消毒彻底而导致肺炎、麻疹、猩红热、伤寒等传染病,导致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在1861年的英国,只有70%的新生儿能过活到10岁(Doepke,2005)。高婴儿死亡率意味着相当比例的新生儿无法成长到成年,父母只有通过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保证一定的存活子女数量。然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婴儿死亡率在近两百年来迅速下降。以瑞典为例,176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全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2%,而到了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死亡率下降到15%,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7%[注]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TO),这里以瑞典为例是因为瑞典是唯一一个记录了长期婴儿死亡率的国家。。更高的婴儿存活几率使得家庭不再需要生育较高数量的子女,生育率和出生率也随之降低(Doepke,2005)。
第一天纯是赶路,620余公里之后,在林西住宿。所可提者是林西的“振兴楼饭庄”,菜做得甚可口,尤其是“招牌茄子”和本人点的“茄丸子”。此后数天,这样的口福难再复制。
第四,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迅速上升。在农业社会,抚育孩子的直接成本主要是食物供给,只要身体好,有力气就能够参与农业生产,创造收入。而进入工业社会后,新的生产方式对于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现代社会的教育理念越来越重视人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不仅要身体好,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这些都需要通过教育与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来积累,而这些投资在当代社会都远比食物供给更昂贵[注]根据2015年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与促进中心测算,对于一个美国中产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到17岁平均需要23.36万美元,而在英国抚养一个孩子到21岁平均需要22.92万英镑,分别达到了当年家庭收入中位数的4.5倍和6倍。。在给定家庭预算约束下,当养子成本上升时,家庭会通过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以提高单个孩子人力资本的积累。这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Gary Becker所提出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Becker,1991)。
第五,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抚养孩子不仅需要直接的物质投入,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人的体力劳动,女性在家庭外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因此出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在现代社会中,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机器替代人进行简单的体力劳动成为常态,身体素质不再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女性在相当多的工作岗位中表现出不亚于或优于男性的生产效率。在女性广泛参与市场劳动的过程中,因生育以及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机会与家庭收入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在美国,女性生孩子每晚一年,年收入平均增加9%,工资平均增加3%,工作时间平均增加6%(Miller,2011)。在中国,每多生育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下降7%(於嘉和谢宇,2014)。从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生育决策,随着生育成本的增加,家庭为实现效用最大化会降低生育意愿,总和生育率随之降低。
图6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或组织人均GDP与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进行整理。
由人口转型所导致的生育率降低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维持一国跨代际人口数量保持不变的总和生育率称为“世代交替水平”。世界的平均“世代交替水平”为2.1[注]“世代交替水平”之所以高于2,是因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夭折的情况。综合各国儿童死亡率的情况,国际上一般把TFR=2.1作为维持代际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当一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时,新增人口数量便会低于上一代人口数量,这不仅会导致长期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会导致年轻人所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小,相应的,老年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导致老龄化现象。
除了对个人的惩罚措施外,很多省份还采取了“连坐联保”的方式对超生家庭夫妻双方和所在单位进行额外处罚。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情况也成为所属单位或辖区负责人的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指标,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力,使得地方政府与基层单位有充分的动机深抓落实相关工作。
能推进企业文化的发展。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员工共同认知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与企业理念在文化层次上的体现,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通过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活动调动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指过腔音调,即连接前后两个字腔之间的过渡性腔调或音调。二指过腔的音乐材料,即剧种主调①昆曲剧种的主调,昆曲南曲是 re、do、la,昆曲北曲是 do、si、la、so、fa、mi。详见拙著《昆曲音乐研究——周来达戏曲音乐学术论文选》中的《昆曲有主调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年。和本唱调音阶中的自然级音。三指创作过腔的方法。有旋律必有旋法,创作过腔旋律的方法,即为过腔创作法(下称“过腔法”)。四指过腔法是由曲圣魏良辅首创的昆曲音乐思想创作表演技术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魏良辅“过腔接字,乃关锁之地”说的产物。
第一,新的生产方式降低了社会对于人口数量的需要。在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由于气候、生产技术和土地供给的限制,增加劳动力供给成为提高产出的主要方式。从家庭的角度考虑,必须要尽可能地生育更多的后代,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可以活到成年,人们具有很强的生育意愿。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时代,新技术的产生使得生产关系出现了根本性改变,资本和技术开始在生产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机器的使用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他要素对于人力的替代作用使得生产过程对于人的数量需求大大降低,社会对于新增人口的需求逐渐弱化。此时生育更多的人口不再是提高总产出的关键因素,提高人口质量成为核心要求,生育率和出生率从而逐渐降低。
图71950、2015、2050年中国人口结构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根据《社会保障绿皮书(2019)》[注]《社会保障绿皮书(2019)》由“社会保障绿皮书”编写组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为:
第一,老龄人口总量大。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较大,老年人口比例增加1%就意味着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增加近1400万。到2017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已经达1.6亿,与世界人口排名第8位孟加拉国的总人口相当。
第二,老龄化速度快。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UN,WHO),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时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1%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图8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给出了主要国家达到不同老龄化阶段的时间点。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人口转型、并且老龄化的时间早于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预计2025年就会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距离“进入老龄化”仅用了25年,而美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70年,英国用了45年,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用了30年。按目前的低生育率状况来看,中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所用时间最短的国家。
图8 世界部分国家老龄化时间趋势表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进行整理。
第三,“未富先老”。目前中国的人均GDP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距离。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约7300美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0.6%。若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当人均GDP相同时,韩国、巴西、南非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仅为5.1%(1990年)、3.8%(1985年)、4.7%(2010年);而当老龄化程度相同时,日本、韩国、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2800美元(1987年)、22100美元(2010年)、25500美元(1974年)[注]本段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人均GDP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远远高于同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应的社会福利体制与养老机制尚未健全,这对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提出了重大挑战。
刑罚的价值观不仅在于惩罚犯罪人,也在于保护被害人,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杀人偿命能够有效地兼顾这两方面的效益,从而使得该观念能根深蒂固。
三、 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会在生育率较高(TFR高于世代交替水平2.1)时出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体中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进而使得产出的数量增加,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二,是经济体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的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从事劳动生产与价值创造,而需要劳动力赡养或照顾的人口比例减少,社会负担小,生产剩余多,储蓄率、投资率高,这也有利于经济发展。
一是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改革办公室,研究制定并下发了《中国石油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意见》《中国石油“十三五”改革专项规划》《中国石油混合所有制专项改革方案》等纲领性文件,指导和规范中国石油深化改革,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规划。
由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趋势,会使中国目前的人口红利几近枯竭,进而对中长期的社会经济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以下分为五大方面予以阐述。
(一) 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且维持在较低水平,固然受到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但“一胎化”政策并不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从图4中已经可以看到,诸如印度、韩国、以及泰国等国家,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其生育率与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呈现出了显著下降的趋势。图5给出了全球范围内的趋势。图中有两个趋势十分明显:第一,给定时间,经济更发达的大洲拥有更低的总和生育率;第二,给定一个大洲,伴随着跨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其长期生育率均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目前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农业生产运营过程中,应当将网络作为依托,全面推动农业电商的发展。政府应当经过发布诸多优惠政策增大对农业发展的帮扶力度,应当推动农业电商公司的发展,可参考中外成功公司的电商发展实践经验,积极推动农业电商地发展,增强农业电商平台和有关领域间地沟通协作,积极丰富农产品的销售途径。
图9展示了中国不同年龄段的出生人口数量。1980-1989年出生“80后”数量为2.4亿,而“90后”锐减到1.85亿,“00后”进一步减少到1.47亿。在生育率为1.4~1.6的水平下,中国每个代际人口数量减少将近30%。在“80后”退休的2040年,补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后”其人数仅是“80后”的1/2[注]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一个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为20岁,平均退休年龄为60岁。。
分别采用BP神经网络预测法和基于小波变换的BP神经网络预测法对2012-2016年间的1∶00-6∶00,7∶00-12∶00,13∶00-18∶00,18∶00-24∶00这4个时间段进行预测和误差分析,预测结果和相对误差如图1~图8所示,图中实线代表交通事故的实际情况,虚线代表交通事故的预测情况。预测方法误差对比情况如表2所示。
图9 中国不同年龄段出生人数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图10 劳动力数量和相对占比随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2015年后的数据为预测值。
图10描述了中国劳动力数量与人口占比的动态变化趋势。图中所显示的趋势与上述分析相吻合。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2015年前后达到约10.15亿人的峰值。之后随着新增人口数量减少、人口结构不断老化,劳动力数量预计将出现持续减少。预计从2015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数量将下降约1亿人;到2050年时,中国将仅有约7.66亿劳动人口,仅为2015年劳动力数量的75%(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17)。这意味着从2015年到2050年的35年间,劳动力年均减少速度为0.8%。
按照索罗模型,劳动力的减少会对经济产出产生直接影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力之间替代率的大小。按文献中所估计的参数推算[注]假设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为Y=AKαL1-α,其中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α反映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回报份额。在文献中,α=1/3是一个较为常见的取值,而对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实证估计结果也大致在这一数值附近,如白重恩和张琼(2014)等。,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注]这意味着,假设索罗模型中的资本存量(K)以及全要素生产率(A)保持不变。,中国未来30年劳动力年化0.8%的减少会导致经济总量面临年均0.53%的下行压力。以此速度累计30年,这对于中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是潜在的重大挑战。
需要强调的是,劳动力数量的变动相对于生育率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给定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常年稳定在1.5左右,即便近几年有任何生育率的变化,其对劳动力的影响都会在20年后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图10中对于劳动力数量的预测直到2040-2050年都应该是相对准确的。由此可知,未来二三十年中国适龄劳动力的大幅减少是必然趋势,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与挑战。
(二) 抚养比增加导致的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人口红利”枯竭的另一个表现是,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减少,社会抚养比不断增加。这里,“社会抚养比”定义为非劳动力人口(15岁以下,65岁以上)与劳动力人口(16~64岁)的比率,衡量的是一个社会中非劳动力人口给劳动力人口带来的抚养负担。
图11A显示了中国“社会抚养比”跨时间的变化趋势。其中社会总抚养比被分解成了青年抚养比(16岁以下人口数量除以16~64岁人口数量),以及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数量除以16~64岁人口数量)两部分。可以看到,抚养比的趋势明显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字形,这是人口转型过程中抚养比会呈现的典型变化。2015年之前,由于计划生育实施与人口转型导致的生育率的降低,单个劳动力所需要抚养的儿童数量减少,社会抚养比自1970年的峰值以来降低了50%,人口红利趋势明显。2015年是一个重要拐点,由于20世纪50~60年代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开始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多为独生子女,因此老年抚养比开始大幅增加,老龄化趋势明显,养老负担加重。到2055年,总抚养比负担会回到1970年的峰值(约8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OECD国家的平均抚养比为54%,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抚养比分别为51%和44%,可以看到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未来面临的抚养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诗人空间视点徘徊移动,游目遍览,将高山、白云、众壑、河流及人都纳入了同一空间中,高者近天,远者至海,大至分野,群山重叠,且云烟渺渺,几乎囊括了中国山水画之“六远”法,难怪沈德潜谓“四十字中,无所不包,手笔不在杜陵下。”〔3〕
为了确保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计划生育的奖惩措施。首先,对于严格履行“一胎化”政策的家庭,由政府颁发“独生子女光荣证”,并给予补贴。例如北京市的独生子女家庭可以领取每月10元的独生子女补贴直到子女满18岁。其次,对于违反“一胎化”政策的家庭,需缴纳罚款。《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由于各省级政府获得了自行确定罚款标准的自主权,不同省份的罚款力度也有所差异。Scharping(2013)详细总结了不同时期不同省份超生罚款的数额。例如:在北京市,如果超生行为发生于1982年之后,则该家庭需要连续七年交纳家庭年收入的10%;而在1991年之后,超生罚款政策改为一次性缴纳家庭年收入的5倍。
综上所述,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中国总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中国正面临着养老负担不断加重的巨大压力。目前中国的养老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前者相当于是随用随付(pay as you go)的支付方式,即当期劳动力群体缴纳的养老保险会用于支付退休群体的养老金;后者由国家强制提取,退休前个人无法提前支取,相当于一种强制储蓄。根据Sing(2005)的研究结果,长期以来中国的个人账户余额几乎为零。2018年中国开始全面实施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说明一些地方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根据人社部社保事业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2017》,黑龙江、辽宁、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青海养老金当期收不抵支,其中黑龙江累计结余已穿底,欠账232亿元。而在2014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只有2个。另外河南、广西、江西、海南、内蒙古、湖北、陕西、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等14个地区可支付月数已不足1年。假如扣除政府的财政补贴,全国将会有20多个省(区、市)出现了当前收不抵支。伴随着社会抚养比的进一步上升,这一问题会更加严重。
图11A 抚养比随时间变化情况(无调整) 图11B抚养比随时间变化情况(调整后)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三) 抚养比增加导致的储蓄率暨投资率下降
除了增加养老负担之外,抚养比的恶化还会导致社会储蓄率的下降,降低投资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这是人口红利枯竭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当社会抚养比较低、人口负担压力较小时,家庭在扣除消费后进行储蓄的空间比较充裕,政府也没有较高的养老金转移支付负担,可以进行更多地投资。然而随着社会抚养比增加、人口负担压力增大时,储蓄投资的空间也随之变得有限。
刚踏入中科大堂,墙上高挂着的“中科梦”三个醒目大字即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本以为是仿照“中国梦”定下的“中科梦”,但和余培宽董事长一番交流后我们方知,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中科梦”是个百年梦想,创办百年企业是中科人不竭动力,早在2007年“中科梦”便被写入了公司手册,彼时距离中科成立仅5年。
图12 日本储蓄率与抚养比的随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以中国的邻国日本为例,作为同属东亚地区、文化背景相近、经济曾快速发展腾飞的国家,日本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到目前为止也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图12反映了日本的储蓄率与社会总抚养比随时间变化趋势。可以看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总抚养比上升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储蓄率一路下行。
日本的情况并不是个案,图13进一步展示了1960年至2015年世界范围内储蓄率与抚养比的跨国统计结果,图中气泡大小反映了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可以看到,储蓄率与抚养在不同年份始终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储蓄率与抚养比的负向关系越来越明显,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的负向作用不断增加,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将面临储蓄与投资不足的挑战。Li et al.(2007)就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计量分析,其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总储蓄率将下降0.6个百分点,投资率降低0.7个百分点。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抑制了资本的形成与积累,从而最终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实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资本的迅速积累与不断深化。根据Brandt和Rawski(2008)的估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深化(即劳均资本存量)对于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率达到约40%。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的储蓄率降低和资本积累减缓将是一个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挑战。
1960年 1980年
2000年 2015年
图13 不同时期世界范围内抚养比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四) 对于创新创业的抑制
除了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占比降低、以及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之外,老龄化还会通过减缓一国的创业创新活力来影响经济发展。Liang et al.(2018)通过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创业比例,发现了图14所示的规律。
图14A 美、英、日创业人口的年龄分布图 图14B不同年龄的国家组创业人口分布
资料来源:转引自Liang et al.(2018)。
首先,如图14A所示,创业人口比例随年龄增长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趋势。其次,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中,任何年龄段上的个体创业几率都会降低。图14A中列举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图14B按照年龄中位数的高低,将所有国家被分为三组,可以看到,中位数年龄较低的国家组在任意年龄上都具有更高的创业比例。再次,由于倒U型的存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创业高峰的年龄,但这个高峰年龄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被推迟。在图14A中,美国的创业高峰出现在30岁左右,而这一高峰年龄在英国被推迟到了30~40岁,在日本被推迟到了40~50岁。
为解释上述现象,Liang et al.(2018)认为,年轻人在创业创新上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积累一定的行业经验以及必要的人力资本后,其创业的倾向性才达到最高。这就是为什么创业倾向与年龄之间的关系为“倒U”形状而不是单调递减。而老龄化国家中的企业更容易具有老龄化的员工结构,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高级、重要的岗位往往被资历高的老龄员工占据,年轻人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在公司被晋升到对积累创业所需业界经验有利的职位,人力资本积累缓慢。进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降低了所有年龄段的创业倾向与比例。在将所有效果加总到国家层面后,Liang et al.(2018)的实证结果表明,一国中位数年龄每增加一个样本标准差(约为3.5岁),能够导致该国的创业率减少2.5%,这相当于样本平均创业率的40%。Liang (2018)对此模型进行了拓展,并对主要经济体21世纪中在创新创业活力上进行了预测与比较,得到的结论与上述规律是一致的。
(五) 老龄化对于人均产出的影响
相比于总产出,人均产出(人均GDP)更能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以及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一部分本文将详细讨论人口老龄化对于人均产出的影响。
为了帮助分析,我们首先要厘清人均GDP与劳均GDP这两个概念,人均GDP表示(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货币衡量的)平均每单位人口生产出的商品或服务,而劳均GDP表示平均每单位劳动力生产出的商品或服务。其中,
人均GDP=劳均GDP×劳动力人口比例
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求微分,可以得到:
人均GDP增长率=劳均GDP变化率+劳动力人口比例变化率
这说明人均GDP增长率会受到劳均GDP变化率(即生产效率)和劳动力人口比例变化率的共同影响。图13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比会从2015年的峰值75%,下降至2050年的60%。这意味着,在劳均GDP变化率恒定的情况下,人均GDP的增长率将在35内下降20%(1-60%/75%=0.2),即每年下行约0.6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会导致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劳均GDP增长率。劳均GDP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均资本存量(可理解为每个工人所操作的机器的数量)。当劳均资本存量增加时,这一过程被称为“资本深化”,生产效率提高,劳均GDP增长率为正;当劳均资本存量减少时,这一过程被称为“资本稀释”,生产效率降低,劳均GDP增长率为负。
从短期来看,刚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虽然劳动人口比例下降,但是由于人口减少,劳均资本存量增加,“资本深化”的影响超过了“资本稀释”,人均GDP增长率为正;但在长期,随着社会抚养比增高,储蓄率降低导致社会总投资不足,资本长期折旧率较高的时候(资本从长期来看总会被全部折旧殆尽),劳均资本存量减少,“资本深化”的作用不足以抵消“资本稀释”,导致人均GDP下降,人均GDP增长率为负。因此,伴随着人口转型,人均GDP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图15 人口转型过程中消费水平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转引自Weil(1997)的图6。
以美国为例,Weil(1997)将二战后美国出现的“婴儿潮”(Baby Boom)带来的人口变动作为外生冲击,基于Solow增长模型中探究了人口转型期间人均消费的变化趋势,见图15。他发现在假定人口死亡率等条件不变时,短期内由于生率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将使得人均消费先逐渐上升,于转型开始后第47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开始前水平的1.14倍(如图15中过程①所示);随后开始逐渐下降并最终停留在稳态水平上(如图15中过程②所示),此时人均消费水平仅比转型开始前高4%左右(如图15中过程③所示)。由于Solow模型中人均消费是人均产出的线性函数,这一结果也说明了人均产出(人均GDP)在人口转型期间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最后达到稳态的趋势。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它意味着虽然人口转型过程最终会提升人均产出水平,但整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从中国进入人口转型期的时间点来看,中国当下很可能正处于上升期(人口红利期)结束的顶点,这意味着在未来的近50内,中国都将面临巨大的人均GDP下行压力。因此,在充分意识并合理预期到这一变化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以部分延缓甚至扭转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四、 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方法
在人口转型的全球背景下,由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还面临着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且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本章将梳理国际常见的应对措施,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每种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 放开生育限制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并且趋于稳定,即便放开生育限制到二胎,甚至多胎,在人口转型的大背景下,其效果也将会十分有限。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全大多数省份已经允许夫妇中一方是独生子女时生育第二胎,但是直到2015年底,也只有16.8%符合条件的夫妇申请了二胎[注]根据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5》推算。。2015年12月2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并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自2016年起开始实施放开二胎,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相应政策。然而二胎政策的促进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卫计委曾预测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为2023.2万,但是事实上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仅有1723万,比2016年还减少了63万。
图16 不同生育率下的老龄人口比例随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转引自Wang et al.(2017)。
Wang(2017)总结了文献中放开二胎对于生育率提高程度的几种可能性,并针对不同的可能性模拟预测了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变化趋势(图16)。可以看到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放开二胎也只能使得中国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即65周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21%)的时间点延后2-3年。这一结果符合直觉:由于当前的出生率不会影响20年后的老年人数量,现在出生的孩子在20年后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放开政策只能使得人口总数微弱上升,对缓解老龄化进程的效果十分有限。
(二) 鼓励生育政策
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原因在于生育率过低,而生育率过低的核心原因在于人口转型,仅仅放松生育数量管制必然远远不够,政策制定必须切实解决当今社会养儿育儿的成本高昂问题,才能有效地鼓励并提高生育率。全世界范围内,从1976年到2013年,为了应对老龄化而推行生育鼓励政策的国家占比从9%上升到27%(Wang et al.,2017)。目前各国通行的鼓励生育政策可以划分为3类:财政支持(即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现金、食品券,或减免税收)、日托和教育支持(即教育补贴)、怀孕和生产期福利(比如带薪产假)。例如在英国,拥有孩子的家庭根据孩子数量和家庭收入的不同,每周可以从政府领取13.55至210英镑不等的补贴,直到孩子成年(18岁);在德国,不管是否拥有公民身份,只要有孩子的家庭就能申请补贴直到孩子25岁;在俄罗斯,自2007年以来若家庭生育不少于3个孩子,那么政府会一次性给予每个孩子约25万卢布的奖励(约平均年收入的3倍)。
这些鼓励政策的效果如何?可以参考与中国生育文化相近的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日本与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已经持续了20年,但是收效甚微(日本TFR为1.4、新加坡TFR为1.3);韩国、台湾在10多年前也在推行相关政策,其结果有待观察,但目前仍无起色(韩国TFR为1.3、台湾TFR为1.2)。比较成功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北欧比如丹麦、冰岛和瑞典,生育率自2008年以来长期保持在1.7~2.0之间,但是仍然无法达到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水平[注]生育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
图17 生育补贴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转引自Liang et al.(2018),图中英文字母为国家名称简写。
图17显示了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生育补贴占GDP比例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相关性显著为正,说明补贴的效果在统计意义上是有助于提高生育率的;但问题是其斜率过低,补贴的效果在经济意义上不显著:大约每增加相当于GDP1%规模的生育补贴才可以使总和生育率上升0.1,这意味着平均消耗10%的GDP作为补贴才能使每个家庭多生育一个孩子。使用财政补贴来提高生育率,其成本无疑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对于还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而言,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来大范围鼓励生育无疑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发展阶段,如果力度不大则不会起到明显的效果。
(三) 延长退休年龄
延长退休年龄是目前国际上广泛应用的老龄化应对措施(Herrmann,2012)。延长退休年龄一方面能增加适龄劳动力,同时能降低退休人口,直接降低老年抚养比。许多发达国家在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试图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困境。从1992年到1998年这6年间,有17个国家延迟了法定退休年龄,其中大部分是OECD国家,例如捷克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爱尔兰从65岁提高到66岁,意大利从60岁提高到62岁,新西兰从60岁提高到65岁(Schwarz and Demirgue-Kunt,1999)。2010年法国也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则在2010年从65岁延迟到67岁。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目前普遍在65岁以上,而中国是60岁。但是需要注意到,中国的城镇职工、特别是城镇妇女,很早就退出了劳动力大军,使得实际平均退休年限在57岁左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预期寿命有了长足的增长,给定目前中国的预期寿命为76岁,还有很大的延长退休年龄空间。
但是,延迟退休的政策不是万能的,其效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图18 劳动力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延迟退休5年前后)
资料来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2015年后的数据为中等情况的预测值。
第一,延迟退休的年限受到预期寿命的限制,政策空间存在天花板。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81岁左右,假设平均退休年龄为67岁,那么平均每位劳动者退休后可以领取14年的养老金。考虑到中国目前的预期寿命为76岁,若对标发达国家十多年的退休养老时间,那么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最多只能推迟到65岁左右。
第二,延迟退休治标不治本,既无法影响总和生育率,也无法逆转老龄化人口结构所固有的长期趋势。以中国目前的情况举例,假设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劳动力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图18所示。诚然,延迟退休情形下的劳动力数量显著高于没有延迟退休情形下的水平,这说明延迟退休可以一定程度上延缓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是,图中两条曲线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延长退休只是改变了劳动力群体的定义,没有真正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因此只是推迟并减缓了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到来,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老龄化问题。
第三,由于退休政策设计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其推行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社会与政治成本,不能搞一刀切。需要分时分人渐进式地推进,而这样做必然会延长其发挥效果所需的时间。
(四) 接纳更多国际移民
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放松移民政策来吸纳国际移民,特别是年轻移民来应对老龄化问题(Bloom,Canning,and Fink,2010;Herrmann,2012)。年轻移民不仅能够补充劳动力,而且还有助于促进创新创业并提高接收国生育率。事实上,移民接收国无偿获得了移民迁出国对于移民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当于搭了迁出国的便车。从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跨国流动数量来看,发达国家吸纳了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移民,并且美国吸纳移民的数量远超过其他国家,这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少有的,能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接近世代交替水平2.1的国家。香港也是通过移民来缓解低生育率困局的成功案例,根据香港劳动及福利局数据,2017年香港本土居民总和生育率只有1.126,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但是香港通过“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优才计划)、“专才计划”等移民政策,吸纳了大量来自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年轻人口,使得香港仍然能维持劳动人口比例和总抚养比相对稳定。
从移民数量占国家人口比例的地区分布上看,中国吸纳的移民占总人口比例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较低水平,政策空间较大。然而由于文化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目前对于汉文化以外的移民吸引力还比较有限。此外,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移民开放的幅度需要非常大才能够弥补人口的不足,开放环境下能否妥善处理本国居民与外国移民的关系,容纳外国移民融入社会也需要谨慎论证。就目前的国情而言,全面放开移民政策并不是合适的政策选择。
但是考虑到文化、血脉的同源性,若能针对海外华侨、华人同胞,特别是具备高知识、高技能的人才,鼓励其回国学习、工作则不失为一种值得努力的方向。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于2007年发布的《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报告指出2007-2008年间海外华人华侨人口已达4543万人,若用历史数据保守估计,目前海外华人华侨数量至少为5000万人。2018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报告指出目前海外华人华侨在申请国内的签证和“绿卡”(永久居留证)时还存着诸多限制,应当有针对性地放宽外海同胞的永久居住权的发放,为海外人才回国工作、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海内外同胞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民族民心相通,还将有助于缓解当下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困境。
(五) 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用以抵消劳动力减少的负效应,是文献中经常提及的应对老龄化的另一个渠道(Prettner,2013)。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两种途径:第一,劳动力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改善;第二,现有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置与利用。
图19 中国和欧洲相对美国劳均产出随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进行整理。
图19刻画出了欧洲与中国相对于美国劳均产出的跨时变化,即将美国每年的劳均产出记为100%,并用欧洲与中国的劳均产出与之相对比。可以发现,欧洲相对于美国的劳动力生产率常年稳定在60%左右。而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由最初仅为美国的5%迅速上升至20%。虽然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同时也说明中国在此方面的改进空间大,即便能追上欧洲的水平,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这里所提的“提升空间”十分重要,因为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并不是特别针对人口老龄化才提出的方案。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提升劳动生产率,都会尽力做好。因此,对于已经比较发达的国家,如上图所述的欧洲国家,劳动生产率已经到达瓶颈,提高空间较小;而中国的提升空间则较大,关键是如何发挥政策红利,有效地加以利用与实现。
提升劳动生产率,首先是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能够创造提高个体、社会、以及经济福利的知识、技术、本领、以及健康状况等属性(OECD,2001)。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来自健康的改善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迅速上升(Heckman,2005)。在健康方面,人均预期寿命由1982年的67.8岁提高到2015年的76.3岁[注]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在教育方面,中国于2011年实现了“两基”目标,即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1998年开始施行大学扩招,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4.5%,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0年的4.0年上升到2015年的9.6年(Li et al.,2017)。
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在基础教育方面,需要进一步普及高中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则应该保持目前的高教扩招规模。到2015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人口已经达到1.7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4%。目前中国每年毕业的大专以上学历学生为700~800万左右,如能保持,30年内还能再产生2~3亿的具有高等学历的劳动者,这几乎已经赶上了美国的全国人口。未来中国将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是中国在21世纪发展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最重要财富。
在文献中,Vogel,Ludwig,and Borsch-Supan(2013)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评估了不同的应对老龄化的方案,发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并辅以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人口转型带来的福利损失。Li et al (2017)研究了世界各国人均教育年限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利用这一关系结合中国未来的教育年限提高,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期。文章假设了比较乐观的教育发展情形,即高教扩招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农村高中入学率在2020年达到100%,城市高中入学率维持当前的100%。在此情形下,中国的平均教育年限将在2035年达到10.7年。这意味着每年教育年限会提高0.1年,进而带来人均GDP每年2.2%的增长。
虽然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如果能够使有限的劳动力能够有效地在不同的行业、地域、以及城乡之间进行配置,则能够充分发挥其价值,从而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根据经济学理论,劳动力最优配置的结果,一定会使得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或者行业间、城乡间)的边际回报趋同。在此过程中,建立一个充分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至关重要。
以中国实践来看,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改善,对于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Li et al (2017)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的主要来源:其一是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能够生产更高价值的工业与服务业转移;其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转制(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使得劳动力由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转向边际回报较高的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其三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使得教育的回报越来越体现其真实的价值,“造火箭的不如卖鸡蛋的”这样脑体倒置的情况一去不返。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升,贡献了改革40年人均GDP增长的60%。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上述改善空间在未来会不断缩小。许多文献(Cai,2010;Meiyan,2010;Zhang et al,2011)都认为城市农民工增长已出现减缓,这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同时,私有企业目前已经吸纳了80%的劳动力,在所有制之间的劳动力转移余地已经很小。在此形势下,要想盘活现有劳动力资源,就需要识别当前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因素,并有针对性地实施改革。下面,本文将从城乡间、城市间和不同人才层次间的三个角度,具体讨论劳动力要素配置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可行建议。
1.城乡间的配置效率
目前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转移尚不充分,近年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以“就地、就近”为主要特征,未能充分利用城市的集聚效应。截至2017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8.5%。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自2015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和增速均逐年提高。但从增长模式上看,本地农民工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速,2011-2017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也由2011年的62.8%逐渐下降到2017年的60.0%,省内流动农民工增量占外出农民工增量的96.4%。2018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展示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镇人口的年度增量构成中,约16%为城镇人口生育带来的自然增长;5%为农转非人口;26%来自农民工的增长;而占比最大的53%来自于就地变更——即通过行政区划变动导致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极大地减少了人口迁移的成本,有效规避了当前存在的制度壁垒的限制。但其问题在于劳动力在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没有发生就业类型和居住地的变化,无法充分利用城镇地区集聚效应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因而未能真正实现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
众多制度壁垒的存在共同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出现,其中户籍、社会福利、生活成本等因素的作用尤为突出。李富有等(2013)指出户籍制度通过其绑定的权益福利制度,导致了城乡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并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较低的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段亚伟(2015)发现社会保险过低的统筹层次影响了各地区的就业概率,进而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向。而贾男和马俊龙(2015)发现非携带式的医疗保险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锁定效应,参加新农合使得农村留守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概率降低了34.7%。以住房成本为代表的生活成本差距也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中的重要因素。李勇刚和周经(2016)发现房价抑制了农村生育劳动力的转移,于静静和王英杰(2017)同样指出较低的住房支付能力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就业的概率。
2.城市间的配置效率
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有效配置尚未实现,城市规模分布偏离最优水平。根据城市人口规模的齐夫法则(Zipf’s Law),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而服从此规律时城市人口排名的对数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对数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齐夫法则已经在众多国家中得到了验证,图20A展示了美国1991年的城市人口分布的情况,不难看出也基本上符合这一规律。齐夫法则反映了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带来的规模效应可以相当程度上抵消掉边际成本的增加,因此大城市的规模增长速度并不会自然地落后于小城市。图20B给出了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排名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国城市的人口分布状况并不严格地服从齐夫法则,尤其是在人口规模最大的超大城市和规模相对靠后的小城市部分,均体现出城市人口规模相对不足的特征。
图20A 美国城市人口排名与人口规模的关系 图20B中国城市人口排名与人口规模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Gabaix(1999)的图1。资料来源: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目前已有大量相关文献指出中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量整体上还相对不足(Au & Henderson,2006;张自然,2015;王小鲁,2010)。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认为,作为一个总人口接近14亿的大国,中国未来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数量将达到10个或以上,而根据2016年末的数据,中国目前只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4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土地供给不足导致的房价过高,以及严格的落户政策可能是这一现象的主要成因。
现有文献已经证实了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限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Henderson et al. (2018)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相关估计,表明城市间存在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导致的迁移成本,造成了劳动力无法实现完全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得总产出水平低于理想情况达1.6%。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差异也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Hsieh & Moretti(2019)基于美国的数据发现,具有高生产力的城市因面临更严格的土地供给政策而被人为地推高了房价,这导致劳动力没有充分地流入这些高生产效率的地区,从而使得美国在1964-2009年间的经济增长距离没有扭曲的理想情况低了36%。这一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的相关问题评估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3.不同人才层次间配置
劳动力的人才层次构成上存在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出现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的情况。以高技能人才为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过程中,中国正从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过渡。2003-2013年间,就业增长最快的制造业行业也主要由高技能行业构成,例如核辐射加工业,烘炉、熔炉及电炉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环保、社会公共安全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等行业。但相比日益扩大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中国目前全部就业人员中仅有6%为高技能人才,规模还十分有限。而按照国际经验需要在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占比至少应达到15~20%,这中间还存在着1 000余万人的缺口(刘世锦,2018)。
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以户籍为代表,涉及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多方面制度的综合改革亟待推进。下面将文献中的一些重要建议(Li et al,2017;周黎安,王辉,唐遥,2019)总结如下: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户口对于居民流动自主权的桎梏。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使其仅成为居民登记管理的系统,而与居民是否能够享受公共服务脱钩(World Bank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P.R.China.,2014)。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城镇和农村居民定居的主观意愿,强化市场对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可以考虑进一步推广“居住证”制度、“积分落户”制度等多种灵活的政策手段作为户籍制度的补充和替代,逐步有序放开城市的落户限制。
第二,解决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时社会保障可携带的问题,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其核心在于完善外来人口进城落户时原有权益的处置机制,同时保障落户后获得迁入地公共服务的平等权。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采取“钱随人走”的转移支付原则,强化常住人口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身份,设计和实行与之相匹配的公共财政机制。另一方面,依法保障外来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保障各类劳动者共享城市发展红利。
第三,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选择权。地方政府应当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目标,采取因地制宜的落户政策,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设计落户制度,实现不同层次人才的准确匹配;同时应当积极推动农业振兴,培育农村优势产业,采用市场手段吸引和奖励农村所需的各类实用人才,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避免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出现人才“空心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并非越大越好,过于频繁的劳动力流动会增加搜寻与匹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反而可能降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不利于劳动者、企业乃至全社会的收益最大化。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增加市场的信息流动,从而尽量避免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恶性竞争和无效率的流动。
第四,放宽高校的自主招生与专业设置权限,使得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能够针对未来市场需求进行灵活调整,加大专业人才供需的匹配程度。
五、 结论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人口变迁,详细梳理了相关的理论与事实。基于最新的数据与研究结果,以全球的视角,聚焦中国的实际情况,刻画出了人口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了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总结出老龄化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以及可行的应对方式。
首先,“人口转型”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的深化,养子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的迅速上升,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不断地降低,这是20世纪人口学意义上的重大现象。理解“人口转型”现象背后的逻辑为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低生育率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国的老龄化进程由生育政策和“人口转型”共同驱动。各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能完全解释近70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是在“人口转型”的基础上加快了生育率的降低速度,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
其次,随着人口生育率的不断走低,人口年龄结构会趋向老龄化,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着老龄人口总量大、老龄化速度快和“未富先老”的重要特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是对中国21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老龄化不仅会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还会使得社会养老负担加重,进一步引起社会总储蓄和总投资减少。在老龄化严重的社会,由于资历深的年长员工占据企业高层职位,导致年轻人在企业内部的上升通道受阻,减缓了与行业相关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降低了其创新创业发生的概率。从人均产出的角度来看,受“资本深化”的影响,人口的减少在短期有助于提高人均产出;但是在长期随着投资的减少,“资本稀释”的作用会使得人均产出在达到峰值后显著下降,给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巨大压力。
最后,本文结合国际经验提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可行方案。在“人口转型”的大背景下,一个社会低生育率的形势往往难以逆转,通过放开生育限制来提高生育率的作用会相当有限,而通过财政补贴鼓励生育的做法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成本又过于高昂,大批量放开移民的政策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延迟退休年龄是短期内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可行方案,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延迟退休“治标不治本”,只是推迟了劳动力短缺的到来,并不能从根本上逆转老龄化趋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应当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并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通过不断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改革,释放人才红利,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张琼,2014:《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第10期。[Bai Chongen and Zhang Qiong, 2014, Analysis of China's Return on Capital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JournalofWorldEconomy, 10.]
[2] 段亚伟,2015:《社保统筹层次过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扩展的托达罗模型的解释》,《财贸研究》第3期。[Duan Yawei, 2015, The Impact of Low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Co-ordination on Rural Labor Mobility -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Extended Todaro Model, FinanceandTradeResearch, 3.]
[3] 贾男、马俊龙,2015:《非携带式医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锁定效应研究》,《管理世界》第9期。[Jia Man and Ma Junlong, 2015, The Locking Effect of Non-Portable Medicare on Rural Labor Flo, ManagementWorld, 9.]
[4] 李富有、郭小叶、王博峰,2013:《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影响分析——基于改进的托达罗模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Li Fuyou, Guo Xiaoye and Wang Bofeng, 2013,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n the Trend of Rural Labor Mobility Based on the Improved Todaro Model, JournalofShaan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6.]
[5] 李勇刚、周经,2016:《土地财政、住房价格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与管理研究》第8章。[Li Yonggang and Zhou Jing, 2016, Land Finance, Housing Price and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ResearchonEconomicsandManagement, 8.]
[6] 刘世锦,2018:《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8-2027:中速平台与高质量发展》, 中信出版社。[Liu Shijin, 2018, Ten-year Prospects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2018-2027: Medium-speed Platform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ITIC Press.]
[7] 王小鲁,2010:《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第 10期。[Wang Xiaolu, 2010, Economic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Path and Urban Scale in China, EconomicResearchJournal, 10.]
[8] 於嘉、谢宇,2014:《 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人口研究》第1期。[Yu Jia and Xie Yu, 2014, The Impact of Fertility on Female Wage Rate in China, PopulationResearch, 1.]
[9] 杨发祥,2004:《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Yang Faxiang, 2004,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Family Plan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DissertationofZhejiangUniversity.]
[10] 于静静、王英杰,2017:《住房支付能力影响农业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第3期。[Yu Jingjing and Wang Yingjie, 2017,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Housing Affordability on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Flow, TheTheoryandPracticeofFinanceandEconomics, 3.]
[11] 张自然,2015:《中国最优与最大城市规模探讨——基于264个城市的规模成本-收益法分析》,《金融评论》第5期。[Zhang Ziran, 2015, Discussion on China's Best and Largest Urban Size: Based on the Cost-Benefit Method of Scale Analysis of 264 Cities, ChineseReviewofFinancialStudies, 5.]
[12] 周黎安、王辉、唐遥,2019:《要素配置改革的“破”与“立”》,《财经》第6期。[Zhou Li'an, Wang Hui and Tang Yao, 2019, The "Breakdow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duction Factor Allocation Reform, Caijing, 3.]
[13] Ahn, N., 1994, Effects of the One-child Family Policy on Second and Third Births in Hebei, Shanxi and Shanghai, 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 7(1): 63-78.
[14] Attane I., 2002,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 Overview of Its Past and Future, Studiesinfamilyplanning, 33(1): 103-113.
[15] Au, C.C., and J. V. Henderson, 2006,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 73(3), 549-576.
[16] Maddison A., 1998,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Run,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17] Banister J. and K. Hill, 2004, Mortality in China 1964-2000, Populationstudies, 58(1): 55-75.
[18] Becker G., 199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 Bloom D. E., D. Canning and G. Fink, 2010,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for Economic Growth, OxfordReviewofEconomicPolicy, 26(4): 583-612.
[20] Brandt L. and T. Rawski, 2008,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Cai F., 2010,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ChinaEconomicJournal, 3(2): 107-119.
[22] Chen F. and G. Liu, 2009,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opulation Aging, Springer, Dordrecht, 157-172.
[23] Cutler D. M., J. M. Poterba, L. M. Sheiner, L. H. Summers and G. A. Akerlof, 1990, An Aging Society: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 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 1-73.
[24] Doepke M., 2005, Child mortality and fertility decline: Does the Barro-Becker Model Fit the Facts?, 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 18(2): 337-366.
[25] Ding Q. J. and T. Hesketh, 2006, Family Size, Fertility Preferences, and Sex Ratio in China in the Era of the One Child Family Policy: Results from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urvey.
[26] Gabaix X., 1999, Zipf's Law for Cities: an Explanation, 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114(3): 739-767.
[27] Gurley J. G. and E. S. Shaw, 1995, Finan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 45(4): 515-538.
[28] Heckman J. J., 2005, Chin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hinaEconomicReview, 16(1): 50-70.
[29] Hesketh T., L. Lu, and Z. W. Wang, 2005, The Effect of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after 25 Years, 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 353(11): 1171-76.
[30] Henderson J. V., D. Su, Q. Zhang and S. Zheng, 2018, Local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in China, WorkingPaper, 42.
[31] Hsieh C.-T., and E. Moretti, 2018, Housing Constraints and Spatial Misallocation, AmericanEconomicJournal:Macroeconomics. 11(2), 1-39.
[32] Herrmann M., 2012, 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xieties and policy responses, JournalofPopulationAgeing, 5(1): 23-46.
[33] Huang W., X. Lei, and A. Sun, 2016, When Fewer Means More: Impact of One-child Policy on Education of Girls, WorkingPaper.
[34] Li H., P. Loyalka, S. Rozelle, and B. Wu, 2017, Human Capital and China’s Future Growth, 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 31(1), 25-48.
[35] Li H., J. Zhang, and J. Zhang, 2007, Effects of Longevity and Dependency Rates on Saving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ross Countries, 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 84(1), 138-154.
[36] Li H, J. Zhang, and Y. Zhu, 2005, The Effe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Fertility in China: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cussionPapers, 19.
[37] Liang J., 2018, The Demographics of Innovation: Why Demographics is a Key to the Innovation Race, John Wiley & Sons.
[38] Liang J., H. Wang, and E. P. Lazear, 2018, Demographics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126(S1), S140-S196.
[39] Liu H., 2014, The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Evidence from the Relaxa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 27(2): 565-602.
[40] Lutz W., W. Sanderson, and S. Scherbov, 2008, The Coming Acceleration of Global Population Ageing, Nature, 451(7179): 716.
[41] McElroy M. and D. T. Yang, 2000, Carrots and Sticks: Fertility Effects of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 90(2): 389-392.
[42] Meiyan W., 2010,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Fall of Labor Input: Has China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 ChinaEconomicJournal, 3(2): 137-153.
[43] Miller A. R., 2011, The Effects of Motherhood Timing on Career Path, 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 24(3): 1071-1100.
[44] Peng X., 2011, 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Science, 333(6042): 581-587.
[45] Prettner K., 2013, Population Aging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 26(2): 811-834.
[46] Scharping T., 2013, 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2000: Population Policy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Routledge.
[47] Schwarz A. and A. Demirgue-Kunt, 1999, Taking Stock of Pension Reforms Around the World, World Bank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8] Schultz T. P. and Y. Zeng, 1995, Fertility of Rural China. Effects of Local Family Planning and Health Programs, 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 8(4): 329-350.
[49] Sin Y., 2005, China: Pension Liabilities and Reform Options for Old Age Insuranc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50] Vogel E., A. Ludwig, and A. Borsch-Supan, 2013, Aging and Pension Reform: Extend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51] Wang C., 2012,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1970-2010, Contraception, 85(6): 563-569.
[52] Wang F., Li. Zhao, and Z. Zhao, 2017,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Their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 30(1): 31-68.
[53] Weil D. N., 1997, 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Aging, HandbookofPopulationandFamilyEconomics, 967-1014.
[54] Whyte M. K., W. Feng, and Y. Cai, 2015, Challenging Myths abou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TheChinaJournal, 74: 144-159.
[5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56] Zhang J., 2017,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Family Outcomes, 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 31(1), 141-160.
[57] Zhang X., J. Yang, and S. Wang, 2011, China has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ChinaEconomicReview, 22(4): 542-554.
SeventyYearsofPopulationDynamicsandtheCurrentAgingChallenge:ALiteratureReviewandPolicyAnalysis
WangHuiandYangQingxu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acts about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in China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policy analysis, discusses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sedemographic changes, and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dealing with the aging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urrent trend towards an aging society is a consequence of low fertility rate. The long lasting demographic control policies in China cannot fully explain its fertility decline since the 1960s. Industrialization, improving social welfare, and the escalating child raising costs are all important contributing factors. In light of these view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due to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ow fertility rate is really hard to be recovered. Policies such as releasing the birth limit, or subsidizing child|raising will not be effective.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s not an option, either.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ne feasible option is to extend the retirement age. But even this on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completely. In the long|run, the best strategy China should consider is to improv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rease the allocative efficiency of its labor. Only after more profound reforms in the labor market, can China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aging challenges, and transform its “demographic dividends” into “talent dividends”. The paper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appreciate China’s current demographic situation, and to design effective policies that should sui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KeyWords: Population Dynamics; Demographic Contro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Aging
DOI:10.13948/j.cnki.hgzlyj.2019.02.002
*王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jackie.wang@gsm.pku.edu.cn;杨卿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qxyang1996@pku.edu.cn。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671007)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 责任编辑 邓 悦
标签: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中国论文; 劳动力论文; 政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宏观质量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671007)的资助论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