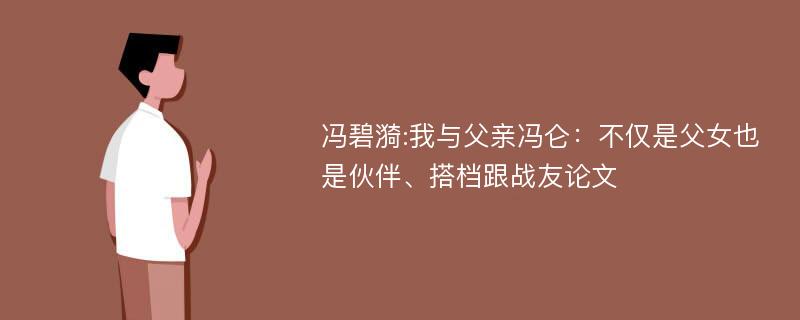
我的父亲冯仑,今天60岁了。我想写一篇文章,送给他。
6月底的一个下午,我陪父亲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一家媒体专访。采访前,对方团队与我对接时,表达了他们希望冯仑先生能多聊聊跟太空、航天相关的话题。“他简直是脑洞最大的一个企业家”,记者对我说,“怎么会对太空有这么多想象?太酷了。”
于是采访从“风马牛1号”卫星开始,聊到他对航天商业化的兴趣,聊到他投资的太空基因库,聊到他想要去火星、去月亮的冲动,以及那个终极的、近几年让他痴迷的话题:探索在火星上创建一种人类新文明的可能性。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记者几乎没问什么问题,只听他滔滔不绝,将自己的太空梦做着完整而生动的叙述。
我一直坐在他5米之外的桌边安静地听。这一天艳阳高照,逆光的房间里,挨着窗户坐在沙发上的他,轮廓被内外光线的反差勾勒得格外清晰。我听着他那兴致勃勃的语调,讲述着那些让他深深着迷的太空科技以及他的太空人类文明重造计划。我听着,听着,默不作声着,内心却陷入了浓浓的难过。
表面上当然是波澜不惊,让自己不会在他、在工作人员面前露出情绪化的马脚。与此同时,忧伤的情绪却抵挡不住地上涌。我迎接着它,感受着它,攥着拳头,突然也理解了它:这股难过,出现在每一次我听他,我的父亲,讲述他的太空理想的时刻。它的根由无比简单而幼稚,以至于我羞耻于表达它:
我害怕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的父亲会去到一个很大、很远的地方,去实现他那在外人看来极端,在自己看来浪漫的太空梦。我害怕他离开地球,离开他的家人,离开我。我害怕失去他。
由表7可知,从人均GDP来看,2012—2016年青岛市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从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来看,青岛市的工业化水平属于工业化中期,这可能与青岛市的产业结构还不够完善有关。从人口城市化率来看,青岛市的工业化水平属于工业化后期,但由于我国严格的城市人口户籍政策,导致大量迁移到城市的人口不被登记为城市人口,致使此结果与实际状况相比有一定的滞后;受制于且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均衡性,青岛市的人口城市化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整体进程。通过对以上四个指标的综合分析,本文认为青岛市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处于向后工业化迈入阶段。
美国BIM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与推广政策非常类似,形成了以美国国家BIM标准(NBIMS)为主,建筑行业职业组织应用标准和大型业主BIM工程实施指导为辅的多样化发展的技术标准生态圈。
由残差曲线图可以得到残差的最大绝对值为0.520 mm,说明预测模型求得的沉降值与实测值很接近,预测模型具有很好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
我对“父亲”这个角色开始产生撕裂感
电话想起的时候,丁小强正忙着出牌。手机就搁在边上的茶几上,一扭头就可以看见屏幕。是布雅兰打来的,时间刚过九点。丁小强放下牌站了起来(他只穿一条花格短裤),对笑吟吟坐在对面的杜一朵说,不许赖皮偷看。杜一朵眨了一下眼睛,她的眼睛泛着酒后的红光。她看着丁小强中年发福的肚腩和肚腩下面的贴身小包裹就嘻哈哈地掩口笑起来。
图片来源:http://www.kaixino2o.com/web/bx/user/13886122240/user_article.html?index=147299
“爸爸是个传奇”这个概念究竟是何时被装进我幼小的大脑的,现在已无从追溯。但它一旦被确立,就在儿童时期的我的心里扎下了根。
我不太知道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有个现在还被家里老人经常提及的段子,是我在6岁去小学面试时,被老师问到爸爸的职业是什么。“教授”,我答。“在哪里教书?”“在万通公司”。据说老师当时一脸错愕。)也不知道为何总是见不到他,只是在困惑中被大人灌输着一些抽象的概念,“爸爸在外面干事业”“爸爸在折腾”,诸如此类。
3岁时,我被送去了每周只返家两次的半全托幼儿园。6岁时,我开始上寄宿小学,每周只有周末被接回家。寄宿的校园生活是快乐的,但也让我,一个敏感的小孩,对仅能在有限时间见到的家人充满更多的依恋跟不舍。
但我能依赖的对象是有限的,确切来说,只有妈妈一个角色。上小学的时光里,爸爸这个角色的传奇色彩在我心里被进一步加深了,原因,想来有几个:
家里的生活条件愈变愈好,而这“多亏了你爸爸的打拼”;开始频繁听到大人们用夸赞的语气讲述“万通”这个公司做得不错,而这“是你爸爸的公司”;此外,最根本的一点,是我到了开始有偶像崇拜意识的年龄。
妈妈固然是优秀的,但她离我的生活太近,与此同时,我的爸爸,那个总是见不到的、在外折腾的人,成为了被我仰视、崇拜的角色。我越是见不到爸爸,越是迫切地在脑海中深化着他的光辉形象。对于一个需要陪伴却总得不到的孩子来说,这大概也是自我合理化最直接的一条路径了。
就这样,在成长过程中,“爸爸很了不起”被作为既定事实扎根在了我的意识里。与此同时,我还拼命抓住了另一条讯息,那就是“爸爸很爱我”。
2016年年中,我与父亲爆发了记忆里两个人最激烈的一次争吵。这次争吵让当时的我们疏离,却也为之后我向他的走近埋下了种子。
据母亲讲述,当时,哪怕父亲是在我已熟睡的深夜回家,他也会走进我的房间,默默留给我一个额头上的亲吻。
我有一个很伟大的爸爸,他很爱我。这样的两条信息,已经足够支撑着我,让童年的我坚信,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1.4 文献质量评价 随机对照研究采用Cochrane协作网推荐的Jadad量表评价纳入研究的随机方法、盲法、 基线相似性及失访退出等指标。将得分≥3分定为高质量研究。纳入的非随机对照研究采用MINORS评分量表,评分≥13分则纳入Meta分析。
十四五岁开始,我对“父亲”这个角色开始产生撕裂感。那段时间,我从公立中学转入国际学校并开始准备出国,而父亲则出版了《野蛮生长》,这部为他的公共影响力奠定基石的重要作品。
与此同时,他忙于开拓纽约中国中心、立体城市等诸多充满想象力与挑战性的项目,同时还牵头各类社会公益组织。他比原来更忙,出差更加频繁,与家人也更少团聚了。
谈话间,他告诉我最近投资了一颗卫星,计划在下一年发射,并打算与直播平台合作,用卫星向大众搞太空直播。像往常一样,他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信,激情洋溢地高谈阔论着。
视自己为被牺牲者的我,陷入到了对父亲的怨气里。为什么他每天都是凌晨才到家,大部分时候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为什么全家人一起吃个饭,时间要一改再改,都只为迁就他的行程?为什么他从不出席我学校的运动会或家长会,唯一一次答应参加,却连我上几年级、在哪个班都一无所知?
二是建立纵向会商机制。加强与各级资金专责小组的沟通联系,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同时,加强对各市的业务指导和专题培训,提高基层扶贫干部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一次痛苦的争吵,迫使我正视我与父亲之间的距离,也让我第一次以女儿的身份触碰到了他的敏感跟脆弱。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ESP研究起步,我国英语教育界也开始关注ESP教学,并在80年代兴起一股科技英语学习热。由于ESP教学在当时大学英语教学中定位不明确,并且当时大学生普遍英语水平不高,ESP教学没有在我国高校发展壮大,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边缘化。在2004年和2007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没有提及专业英语教学根本,大有被遗弃的趋势。
图片来源:http://marcelsnow.lofter.com/post/27b08d_6f67dfe
我发现,与陪伴我的成长相比,他的热情更多投入在社会里,在他的事业中。在他的世界里,对家庭生活的缺失似乎是合理的,社会理想与公共使命一定总会高过家庭。这样的发现,让十几岁的我感到痛苦。
然而,每当面对他时,我的这些复杂情绪却又总能被掩盖下来。原因想来大概有二。
其一是我们见面时间实在太少(每年只有在我的假期、他也刚好有空的时候见上几面,一年不过寥寥几十天),少到都还来不及让正面矛盾发生;
其二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我对他依然充满着尊敬跟崇拜。他不是能陪伴在我身边的好爸爸,但他作为一个“人”的优秀品格——他的坚韧、他的幽默、他的勇敢、他的创造力与他的担当等等,时时刻刻都在发着光。
1992年7月,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一年,我父亲33岁,刚刚开启他的创业岁月。我在北京出生,在妈妈、爷爷、奶奶跟阿姨的陪伴下度过童年。爸爸这个角色,物理上是有的,但大部分时候,都以符号或传奇的方式存在。
我怨他,但我也敬他、爱他。
对我父亲而言,这几年,人生也在发生着大变化。2015年,他从一手创办的万通公司退出,剥离了二十多年都习以为常的“万通董事长”标签。与此同时,他转型并重组御风资本,专注于大健康不动产、安保及文旅等方向的投资迄今。
数据计算对比显示,实验组中风后吞咽障碍患者护理后护理满意度评分(90.54±5.51)分,参照组中风后吞咽障碍患者护理后护理满意度评分(83.24±4.2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705,P<0.05)。
在形式化地问了我几句学校怎么样、最近上了什么课之后,他便开始侃侃而谈他最热衷的、发自内心相信的宏大命题——从人生讲到社会,从社会谈到责任,从责任再聊到理想、使命。
他说的都是真理,但当时的我,一个与父亲好久没见的、等他到凌晨的困顿的女儿,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机械地点着头,心中的委屈感越来越重,终于忍不住趁他去洗漱时冲进了卧室,抱着母亲痛哭流涕。“为什么我的爸爸总跟我说他在外面跟别人说的一样的话?”我抹着鼻涕咆哮,“他说的都有道理,但为什么他不能问问我的个人生活,跟我说说只有父亲会跟女儿说的话?”
在这个成长阶段,让我强烈不适的另一点,是父亲的知名度。《野蛮生长》及之后几部书的影响力在发酵,他的言论被更多人熟知、认同甚至推崇。每次回到国内,处在身边人及媒体对他的关注中,作为女儿,我只觉得不知所措。
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再只是我的父亲,而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为什么很多人开始以“冯仑的女儿”这个角色来看待我?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这个角色?这些连续的、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让我充满了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要待在国外,远离认识他的人,想要借着这样的逃避,为自我的迷茫感找到合理解释。
种种对父亲的别扭与委屈,伴随着我从十几岁一直到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我在求学、在成长,在建立自我;他在工作、在创造,在变得更有名气的同时开拓更大的商业版图。我们在相见时总能拥抱跟手拉着手,我们对彼此关切,为彼此的成就与成长骄傲,但两个人之间,也始终有着隔膜。
当然,在国家权力和政策调试下,适应政府治理需求只是网络政治参与娱乐化产生的一个方面。相反,个体网络行为的选择首先是要满足自我政治参与的需求,使得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个体表达诉求的有效渠道。而网络政治参与娱乐化的灵活性与抗争性优点,无疑为个体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有效手段。
我深爱着他,也并未对他,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产生过动摇。但在世界观与人生观飞速震荡的那些青春时光里,在将“父亲”从符号转换成“人”的过程中,我感到不安,并开始长大。
我第一次以女儿的身份触碰到了他的敏感跟脆弱
与大多数传统中国家庭不同,我的父母对于家庭内部爱的表达格外重视。从记事开始,爸妈两个人就会用语言跟肢体动作不断向我传达爱意,并告诉我,这样的表达是亲情中很重要的事。我虽不常见到爸爸,但每次见面,他都会亲昵地抱抱、亲亲我,用宠溺的语气与我对话。
对于一场悲剧来说,最好的纪念不是痛哭,而是向灾难证明我们的文明足够坚强——1517条生命提醒着后人,没有“不沉的方舟”:“世界上任何无法预料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要时刻警惕,思索人性,保持谦卑与怜悯。”
那天,来旧金山出差的父亲约当时在硅谷工作的我见面。他急着赶飞机离开,我只能去机场与他碰头,一起吃顿简餐。
外部的变化是飞速的。《野蛮生长》的影响力让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人物,而我,则在经历从一个儿童到成年人身份感上的重大转折。当我开始用更为成熟的、青春期少女的眼光审视他时,我发现,父亲外部的成功,那些辉煌的、美丽的、闪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就是他对家庭生活的牺牲。
我觉得他疯了。为什么?为什么毫无科学背景的他会嚣张到觉得自己可以做这样的事业?为什么他不能像别的商人一样,踏踏实实地做好眼前的生意?为什么他一定要挑战、要妄想,为什么他总是如此理直气壮,为什么他觉得他可以?
在试着插话几次无果后,我爆发了。我撂下筷子,无法遏制地提高了语调,用愤怒的声音对他提出质疑。面对情绪在失控边缘的我,父亲也愣了,从未对我责骂过的他用力地拍着桌子,大声嚷嚷起来。
几分钟的时间里,两个人的情绪都越来越上头,话也越说越重、越说越伤人。我觉得他自大,他觉得我自私;我指责他疯狂,他指责我幼稚;我认定他对科学与技术毫无尊重,他认定我被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蒙了眼,变成了一个对长辈毫无敬意的、无礼的年轻人。
那场争执的结局,是我起身奔进了机场的女厕所,在隔间里抱着膝盖嚎啕大哭。而他也并未追上我,而是独自进了安检登机。之后,我们很多天没有联系,母亲在得知情况后试图与我们双方沟通,也没能促成我们任何一方的主动道歉。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与父亲的连接彻底丧失了。那些在成长过程中没被消解的、女儿对父亲的复杂情绪,借由这次争吵通通被翻了出来,以尴尬的姿态被暴露在外。我觉得我不再认识他,甚至无法再认同他;我为什么是他的女儿,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父亲?那些一直被我小心深藏的、私密的委屈,终于都兜不住了。
16岁那年,我独自去到英国读高中,自此开始了8年多的海外留学生活。这段时间里,对父亲的复杂情绪始终拉扯着我。在我心中,“父亲”分裂成了两个角色:一个是那个被大众熟知的“冯仑”,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受到社会肯定、公众拥戴的思想者;另一个,则是一个总不在家,并好像对此没有太多愧疚感的“爸爸”。
在情绪失控、理智分崩离析的那些时刻,我终于得以走近真正的他。他不再只是个象征意义的父亲符号,也不再是充满光环的、社会化的“冯仑”。在我心里,他终于真实了。他变成了一个“人”,有血有肉,有自尊、有坚持、有骄傲的人。
我们更平等了。其实,我们一直是平等的。
2017年初,我从硅谷回国,开始与同伴一起做一家英语自媒体。年末,“风马牛1号”卫星发射因外力延期,我参与到其运营里,与团队一起研究航天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探索商业化的可能性。
2018年,我正式出任风马牛传媒CEO,与团队一起经营“冯仑风马牛”“不相及研究所”两个新媒体IP,及“风马牛地产学院”这个房地产垂直领域的培训平台。
近三年的这些变化还都太近、太新,以至于我无法抽离出来进行客观的自我审视或总结。但大体来说,发生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我终于长大了,终于意识到“长大”这件事无法逃避。于是,我开始努力变成一个在公共领域里发挥自我,而非只在私人空间里探索自我的社会人。
有个记忆中的片段最能说明这种矛盾的情感。大学时期的某个暑假深夜,父亲像往常一样忙到夜里12点之后才回到家,精神头十足地拉着我聊天。
我们和解了吗?我不再执着于答案
父亲从没对我说起过这几年变化的动荡或艰辛,但作为女儿,我多少看在眼里。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是在五十多岁的年龄重新创业,从头开始设定战略、组建团队、建立制度,并在不断试错中再次完成从0到1的积累。他的经验、资源与影响力都还在,但落到具体的公司经营层面,一切都不容易。
目前的相关研究表明,中药黄芩素的研究仅停留在基础研究阶段,尚未开展与临床相关的研究。本研究为黄芩素抗肿瘤转移的研究和开展临床试验增添了新的基础理论依据,为寻找安全有效的抗癌药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他不再是曾经的上市公司的控制者,他又一次变成了一个创业者,一个需要面对新环境与新挑战的“老司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变成了一个更自由的人。于是,在过去这几年里,他有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参与公益、传道授业、写作表达、甚至偶尔也会“出格”,花时间折腾让他痴迷的太空事业。
他对人性、对社会制度有着世人少有的敏锐洞察,对人类的未来有巨大的、抵挡不住的好奇心。这样的性情支撑着他,让他充满激情,让他拥有无尽的想要建立新事业的力量跟勇气。
在这样的人生阶段,我们走向了彼此。如今的我们,不仅是父女,也是工作中的伙伴、搭档跟战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进入社会后的我最亲密的导师。
从公司管理、项目规划到人生方向,只要是我提出的问题或需求,无论有多繁琐唐突,他都会耐心解答,全力配合。他开始为我导航,而我,则努力学习着掌握平衡,在社会的大海里扑腾成长。
我们和解了吗?
我不再执着于答案,甚至不再认为这个问题本身重要。我们本就是不同的人,在一些问题上有各自的坚持,甚至在理念上有巨大的差异。但他与我都是开放的,我们愿意沟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也会在适当的时候为彼此做出迂回或妥协。
他依旧不是个会关心家人生活细节的父亲,但是,我也不再是个只执着于情感需求的孩子。
他永远不会像电视剧里的中国父亲一样,守着一桌饭菜等着女儿回家,但是,当我终于放下青春期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怨念,以社会人的身份与他建立关系时,我们仿佛也变得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亲密、更平等、更能信任对方。
色谱柱:XSelect® HSS T3-C18(1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乙腈(A)-0.5%醋酸溶液(B),梯度洗脱(洗脱程序见表2);流速:1.0 mL/min;检测波长:360 nm;柱温:25 ℃;进样量:10 μL。
2019年,他60岁,我27岁。我们能够释然地相处了,像这世间任何平凡的父女一样。我们能够更有默契地扶持对方了,像两个彼此独立,却又互相尊重的个体一样。
治疗前,2组卵泡刺激素及雌二醇水平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卵泡刺激素及雌二醇水平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60岁生日快乐,亲爱的老爸。愿你接下来的人生健康、平安,愿你更自由,愿你更辽阔,愿你始终有去到远方的勇气,愿你永远在路上。
标签:父亲论文; 爸爸论文; 太空论文; 的人论文; 让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商人》2019年第8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