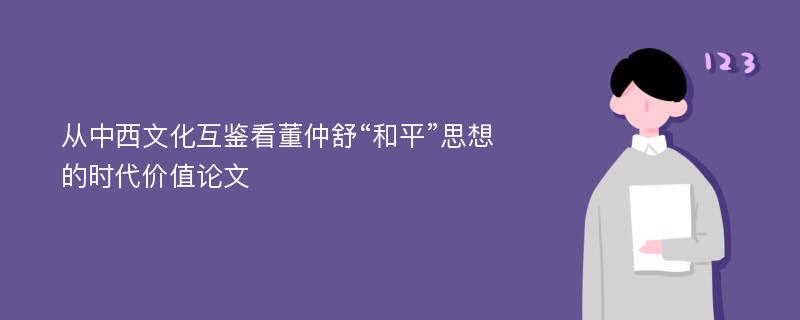
从中西文化互鉴看董仲舒“和平”思想的时代价值
季桂起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董仲舒的“和平”思想是对儒家文化传统的继承,其基础精神来自于儒家的“仁爱”理念,即“仁者爱人”。在他的“和平”思想中包含着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同时表现为多元包容、和而不同的意识,具有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思想元素,与同时期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比,显示出更为宽厚、仁和的性质。基督教文化的排他性,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仍然有着某种程度的遗存。相比之下,以“和平”为主导、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更大的思想优势。这也是董仲舒思想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董仲舒;和平思想;儒家文化;时代价值;仁爱
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董仲舒的思想不仅在古代社会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时代价值。当然,这种时代价值并非指他的思想可以在现代社会作简单的移植,而是说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可以向现代文明转换的元素,这些元素经过与现代社会的相互融合,经过现代文化的借鉴与改造,可以转换成为能够为现代文明所接纳的价值理念,其中“和平”思想即为其一。本文仅就董仲舒的“和平”思想这一要点,结合中西文化的互鉴,略作阐述,以此考辨董仲舒思想的时代价值。
和平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作为中国精神一直贯穿于中国人的生活中。《论语·学而》篇有言“礼之用,和为贵”[1]74。所谓“和为贵”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最为重要的;而“礼”的作用即在于用规范化的方式保障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睦关系。就个体而言,人与人之间是如此;扩而大之,就国家、民族、文化而言,也是如此。只有和睦相处,人类社会才能够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而“和”的基础,则是孔子所一再强调的“仁爱”理念。这一理念被表述为“仁者爱人”。由“仁者爱人”,孔子提出了和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64“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118以及子贡所言“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1]104。在儒家的这一和平思想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其中就包含了对对等人格的理解与尊重,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已经具有了相对于严格的封建等级而言一定的平等意识。从这一传统出发,儒家提出了“王道”的政治观与外交观,以反对强权主义的“霸道”。“王道”作为处理国家与人民、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其不可否认的思想价值。“王道”的宗旨即为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这正如孟子所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1]289而“德”的核心价值就是“仁”,“以德行仁者王”[1]289“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465。
关于这一点,董仲舒曾有过十分明确的论述。他在《春秋繁露·竹林》篇中曾表示对以武力解决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否定,认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应该以德服人:“《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2]48在董仲舒看来,国家的武力只是作为防御的力量而设置,不是用来随意发动战争以征服别人的工具。在本篇中,他还通过对司马子反擅自违背楚王之令而与宋国定约撤军一事的评价,深刻表明了他的和平思想及其人道主义精神。司马子反是楚庄王时期楚国的重要将领,《春秋》宣公十五年,他跟随楚庄王率军伐宋,包围了宋国都城多日,致使宋国军民断粮,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庄王遣司马子反探察宋国军情,宋国大将华元夜见司马子反,相告宋国困境,司马子反出于同情之心,在未请示庄王的情况下与华元订立停战盟约,促使庄王退军。对于这件史实,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2]54;另一种则是“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为美”[2]54。对司马子反的前一种评价所持有的准则是传统的礼法规制,即“《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2]54。用这一法则来看待《春秋》对司马子反之举的记载,《春秋》自身就出现了矛盾之处,“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诸侯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间也”[2]54。那么怎样看待《春秋》记史的这种矛盾之处呢?董仲舒给出的意见是“《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2]54。董仲舒认为,对司马子反做法的评价不能用一般的常规道理,而应该看到其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之处便在于人在紧急情况之下应采取什么方式处理应急问题。司马子反在了解到宋国“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情况后,被战争给宋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所震惊,情急之下与宋国大夫华元私下订立了和解盟约,这是情有可原的。“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2]54。司马子反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不合乎礼法规范,但体现了礼法的内在精神也就是“仁义”之道。在董仲舒看来,真正的“礼”应以“仁”为内涵,失去了“仁”,“礼”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道德价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2]55。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所以褒赞司马子反的行为,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礼法规则,像记载湨梁之盟那样来责怪其“轻君”“不臣”,正是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根本精神和注重和平的思想理念,所追求的即为“以德服人”!
梁爽(1987-),女,汉族,新疆乌鲁木齐人,经济系硕士,研究方向:国际收支,国际投资,国际货币流动,国际储备。
董仲舒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和平思想,其核心价值观就是人道主义,即把对人的生命存在与生存权利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用超越战争胜负的“大义”之求取代功利主义的“利害”之欲。这也表现了一种与和平思想相联系的战争观。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本篇中依据“和平”思想,还提出了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在胜负之上还有是否符合“仁义”要求的道德底线。战争不能仅仅以胜负来判断优劣,更应该以“仁义”作为衡量的准绳。符合“仁义”要求的战争,可以称之为“义战”;不符合“仁义”要求的战争,可以称之为“不义战”。孟子所谓的“春秋无义战”,也是从这样的标准出发的,这同当时所流行的法家、兵家等所秉持的以胜负为标准的战争观是根本不同的。这表现出道德主义的战争观与功利主义的战争观之间的巨大差别。显然,董仲舒这一和平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孔子所倡导的儒家“仁爱”思想,这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一直贯穿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当然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比较,在董仲舒的和平思想包括儒家的文化传统中缺乏个性主义这个元素。他的人道关怀主要是针对作为群体的“民”而非个体的“人”,在关照个体人格的独立权利与生存合理性方面,儒家思想是有些缺席的。这也难怪,因为儒家思想发端于农耕文化的宗法家族制度,其社会基础不具备形成个性主义的条件。在宗法家族制度的思想范围内,个性的独立与扩张无疑是被排斥的。所以,儒家的人道主义传统如果需要在现代社会继承下去,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现代性改造,也就是为其注入必要的个性主义元素,在合理的群己权界中确定其人道关怀的新的定位。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建构策略—2020年后中国减贫与发展前瞻探索系列研究之一………………莫光辉 张 菁(113)
由于医学具有高度专业性,医疗纠纷一旦呈上法庭,往往需要对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程度的轻重等问题进行鉴定,以便于法官结合案件事实进行裁判。95份判决书中,是否进行鉴定的情况见表3;案件进行鉴定情况,具体的鉴定事项见表4。
如果说《旧约》还属于犹太教的圣典,不足以代表基督教的精神,那么在《新约》里也有相应的排他性的内容。尽管《新约》中有“有人打你们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的似乎是和平主义的内容,好像基督教与犹太教相比抛弃了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主义的教义,但仔细审视《新约》的全部内容,基督教的排他性还是不容否认的。如《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里都记述了一则耶稣诅咒无花果树的故事。耶稣带领门徒传教,“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第二天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故事所包含的信息非常明确,那就是基督教的神是唯一的神,只有信仰这个唯一的神,才可能有神灵显现。这个故事也表明,基督教的所谓“宽恕”是有条件的,一棵无花果树竟然因为没有给耶稣提供果实就遭受了他的诅咒并因此而枯干死亡,这样的理念与和平主义相去甚远。由此也可看出,《新约》里所记述的耶稣的那些善举,都是为了传教的需要,而非“仁爱”之心的体现;对他的仇敌如法利赛人,他是不会吝惜自己的诅咒的,“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在《约翰福音》里,耶稣的宣教更明显地体现了基督教义的排他性:“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教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教他复活。”他还说:“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进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以上这两段话里的内容很清楚,耶稣把生命的权利垄断到了自己手里,也就是说他认为只有信奉了基督教的上帝和他这个上帝之子,才具有生命以及末日来临复活的权利,否则获得的即是死亡与毁灭。尤其是《新约》中所设置的“末日审判”,更是把所有的异教徒和信仰不诚者都排斥在了天堂之外。这其中哪有“博爱”的意思?至于后来西方文化由基督教发展出了“博爱”的思想,我认为,那是后来人对基督教义的发展,并非《圣经》原典的宗旨。
尽管儒家的和平思想与现代文明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如果将其与同时期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比较,我感到儒家的和平思想更为突出。从孔子开始直到董仲舒,都提倡华夏与四夷以文化上的共同体为基础和平相处。中国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国际关系素有和平的传统,排外意识并不突出。如董仲舒曾经论述过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华夏与四夷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一种和平主义的民族意识。他在《春秋繁露·竹林》篇中对晋楚邲之战的论述,涉及到了中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华夏夷狄之辨的问题。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尤其是西周之后,处于中原地区奉周王室为宗主的各诸侯国都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是三代以来华夏文明的继承者,处于优越的文明中心的地位,而把周围非华夏族包括楚国在内的其他地域的人们看作是未开化族群,以“夷狄”称之,采用贬低和蔑视的态度。管仲曾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3]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华夏与夷狄虽有地域差别,如《尔雅》所释:“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4]但更主要的区别在于礼法的有无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5]三代以来,礼仪、衣冠往往用来代指文明。但是,孔子等儒家文化的先贤又看到,仅仅从礼法、生活方式这些文化的表层现象区分华夏与夷狄之别还不够,还应该从文化的深层内涵来评价华夏与夷狄的文明差异,这种深层内涵就是支撑着礼法与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也就是“仁义”之道。孔子修《春秋》便是通过记史的“微言大义”,特别强调了华夏夷狄之别的后一层含义。在这一点上,董仲舒与孔子的立场显然是一致的,即他不认为文明的标准只是礼仪、衣冠这些外在的东西,更主要的还是有无“仁义”的道德内涵。有了“仁义”的道德追求,夷狄可以变为诸夏,而失去了“仁义”的道德追求,诸夏也可以变为夷狄。二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切以文明所达到的程度为标尺。孔子通过修《春秋》所强调又由董仲舒在本篇中所阐明的华夏夷狄之别的后一层含义,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检验,已被证明具有更为深刻的文化价值。这就是不同文化的民族只要秉承了“仁义”的价值观,就可以和平相处。
基督教文化则有所不同。从基督教义来看,基督教文化具有明显的排他意识。基督教以是否皈依其宗教教义为判断文明的主要标准。凡是皈依基督教而成为所谓“上帝选民”的即为进入文明之人,否则便是非文明之人即异教徒。这导致了基督教的战争观与儒家战争观的很大差别。如《圣经·旧约》中记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半岛,生活在西奈半岛的亚玛力(西奈半岛一个部落)人与以色列人争战,摩西遵照耶和华的训示:“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同时表示“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于是发起了对亚玛力人的灭族之战。在耶和华给以色列人的训词中有这样明显的排他内容:“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他们的)神像尽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与你们……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民众,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希未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到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罗网。”《旧约》中还记述,因为摩西率领的以色列人中有一部分没有遵照耶和华的指令行事,耶和华便命令摩西将他们除掉,“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最后只剩下了服从耶和华信仰的利未人。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东归的过程中,途经亚摩利人、亚扪人、巴珊人的领地,遇到了这几个部族的阻拦,摩西便遵从耶和华旨意将他们统统杀死,“他们杀了他(巴珊王)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这样血腥的记述在儒家思想中可曾有过?由此可见,在《圣经·旧约》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就是“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
基督教这一排他性的原典教义,曾经对西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远的如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残酷的宗教战争、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血腥殖民地开拓,近的如近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欧洲大陆国家的排斥犹太人运动等,包括纳粹德国所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苏联所代表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如从文化源头追根溯源的话,应该说都同基督教的原典教义有关。而且,在基督教原典教义中并没有天然的民主思想。基督教提倡“顺服掌权者”,支持权力对人们的绝对统治。《新约·罗马书》中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显然,这种“权柄神授”的观念是对专制主义的维护。时至今日,读过《圣经》之后,再来读当年霍尔巴赫对基督教的批判,仍然能够让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基督教向我们描述的那个从犹太人那里继承来的神的面貌就是这样。这个神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暴君;然而人们却以这个神为完善的典范;人们在他的名义之下犯下各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人们所犯的那些最大不过的罪,只要是支持他的,或是对他有好处的,总是一律被认为正当。由此可见,基督教自诩为道德提供一个坚不可摧的支柱,为人民提供最为有力的动机,以促使他们行善。其实对于人们来说乃是一个分裂、狂暴、罪行的来源;它借口给人们带来和平,其实只是给他们带来狂暴、仇恨、不和与战争;它为人们提供出无数种巧妙的办法来自寻烦恼;它在人们身上散布下种种为他们的祖先所不知道的灾难;基督徒如果有理智的话,是会无限地惋惜他的崇拜偶像的祖先的那种平安的无知的。”[6]当然,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经过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新教面目出现的基督教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中产生了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新的思想资源,并由此发展出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潮,这只能说是基督教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进步。马克斯·韦伯就曾经指出,新教与天主教相比,更强调了个人在世俗生活中的责任、价值与权利,而相对淡化了那种对宗教教义的神圣化追求及绝对的服从意识,从这里逐渐滋长了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精神[7]。另外,西方近代以来以民主为主导的新文明思潮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力于儒家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从16世纪中期起,尤其在17、18世纪,传统中国文化以较系统的方式被传入欧洲,从而在欧洲的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中掀起了一场持久的中国文化热或‘中国热’(被称为‘Sinophilism’)……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学说在一些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们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根据戴维斯的描述,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宋明理学、儒家学说的较复杂、较精致的理论形式,‘似乎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自然神论的伦理体系之理想原型’。儒家学说对于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可见诸法国的百科全书哲学家们(尤其是伏尔泰和魁奈)、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以及英国的廷都尔等人的著述中。这些一度在启蒙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热情地‘赞美中国古代文化,颂扬孔子学说之讲求理性、排斥迷信,并羡慕中国社会之圣人治国、贤者当政。持不同看法的人有之,但毕竟为数不多’。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看来,儒学‘是理性和常识的哲学,是宽容和德行的学问——它证明了道德从根本上说是独立于神学的’”[8]41-42。从这一东西文化传播的现象看,儒家文化还应该是助推西方文化走出基督教神学禁锢走向现代文明的思想资源之一。
所以,与同时期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比,儒家的仁爱精神以及董仲舒的和平思想显示出了更为宽厚、仁和的性质和与现代文明更为接近的文化素质。如果说现代文明缘起于西方的工业经济及市民社会的话,那么中国的儒家文化只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没有通过自身的改革走进现代文明的阶段。其实如果不怀偏见的话,在儒家思想中也具有向现代文明转换与发展的元素,如“仁爱”思想本身就天然地具有人道主义的性质、“和平”思想中包含着平等观念。在儒家文化的语汇中,与和平相联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同”。中国儒家文化主张“和而不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则是“同而才和”。支撑“同”的后面的理念即为同情与理解。孔子曾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180所谓“和而不同”,指的是人们的思想及对事物的认识可以不一致,但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和睦相处。我想,在这里“和”也可以理解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和睦相处,这就需要彼此之间的同情与理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指的由己而推诸人,从自己的心理感受出发,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其实就是同情与理解的基础。在《春秋繁露·竹林》篇中,董仲舒在叙述司马子反擅自定约退军的时间之后,有这样一段议论:“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2]54-55这就是儒家从“仁爱”理念出发,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同情与理解。从这里出发,儒家文化如果克服农耕文明狭隘的宗法制度和家族意识,与近代工业经济及市民社会相结合,是有可能发展出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文明,儒家和平思想也能够成为当今人类和平相处的普世价值。断定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关键还是在于这一文化中所遗传的具有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内在基因,其中作为和平思想之根基的人道主义即为重要的元素之一。关于这一点,有的西方学者曾指出:“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欧洲启蒙运动和西方现代性中的两个彼此相关——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精神支柱。西方现代性本身经历了许多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从精神层面上来说,西方现代性总会与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而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内容也会在西方现代性的演化中不断地获得新的规定。另一方面,一般认为,作为中国和东亚的传统文化之核心的儒家文化也是以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在此意义上,儒家文化按西方的标准来说也是现代的,或者说儒家文化本身就已经具有成为东亚社会的现代精神之潜力。”[8]51
当今世界各种地区冲突、国家冲突、民族矛盾、社会危机不断出现,人类社会的走向面临重要选择。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说:“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9]6他认为:“西方是而且在未来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当西方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正在面临着一个选择。其中一些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车’。其他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9]8亨廷顿反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之后“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将这种冲突划分为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的“普世文明”与其他未融入西方的“本土化文化”(如儒家文化、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等)之间的冲突。“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9]199。亨廷顿甚至断言,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是无法融入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么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9]68。为了保障西方文明在这场冲突中的优势地位,亨廷顿主张以西方大国作为核心国家构建由西方基督教国家而组成的经济、政治、军事联盟,阻止俄罗斯东正教、伊斯兰教、儒家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并且以西方的“普世主义”文化作为范式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世界秩序,向西方之外的其他地区积极推广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当然,亨廷顿最后希望各文明之间能够达成彼此的谅解,避免冲突上升为战争而危及整个人类社会,有可能的话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促使人类社会和平发展。
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看出,现代西方文化自身也有着深深的矛盾,即西方世界不愿放弃最近几个世纪所形成的文明优势,希望西方的轴心文明仍然能够主导未来世界,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他文明的崛起正在打破西方文化中心的格局,“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9]372正在到来。在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思想中,既有着从基督教所遗传下来的文化的排他性,也有着现代文明不得不承认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等理念,他们相对于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局限性。当然,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这其中儒家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一些价值观逐渐得到了其他地区文化的认同。孔子2569周年诞辰之际,孔子诞生地曲阜尼山举办了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各国学者齐聚中国探讨儒家文化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意义。“中外专家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仁者爱人’的仁爱观,要求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履中致和’的中和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衷共济,协和万邦;‘民胞物与’的自然观,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约己以礼’的道德情怀,‘讲信修睦’的伦理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对于不同文明相融相通、同命同运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0]我想,尼山论坛中外专家的这一共识,也同样可以用来评价董仲舒的思想及认识董仲舒思想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 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左丘明.左传: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134.
[4] 徐朝华.尔雅今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227.
[5] 李学勤.春秋左传正义[M].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587.
[6]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56-557.
[7]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8]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9]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6.
[10] 佚名.尼山论道:中外学者共话文明相融[N].参考消息,2018-10-08(16).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Dong Zhongshu’s “Peace”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Refer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JI Guiq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Dong Zhongshu’s “peace” thought, which is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is based on Confucian idea of benevolence, i.e. “Those who are kind love others”. His “peace” thought involves values of humanity and consciousness of tolerating other ideas and seeking harmonious but different ideas, and it has ideological elements that can transform into modern society. Compared with western Christian culture of the same period, it is more lenient and benevolent. The exclusiveness of Christian culture still remains to some extent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le Confucian culture, with “peace” as the dominant factor and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has greater ideological advantages in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is is also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peace thought; Confucian culture; contemporary value; benevolence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2.007
作者简介:季桂起(1957-),男,河北南皮人,教授,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2-0047-07
收稿日期:2018-10-22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