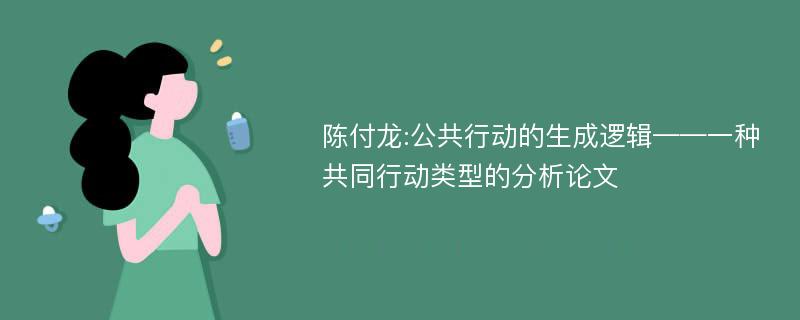
[摘要]作为对共同行动的一种理念升华与实践提炼,公共行动以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旨归,是国家与社会共同建构的结果。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公共行动的基轴与象限,预设了公共行动的实现机制。作为一种共同行动类型的逻辑回应,在不同的共同体形态中行动者之间达成“意向一致”的形式不同。基于政治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基于阶级利益共识的共同行动、基于公共责任默契的共同行动,行动者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中分别占有不同的主导地位,进而导致公共行动的变形镜像、消解困境、和谐发展的逻辑生成。
[关键词]公共行动;共同行动;生成逻辑
公共行动是现代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影响公共决策的一种重要的途径与方式,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不同学科中,公共行动的概念呈现出笼统、语意不清、语义多元的事实,导致其在不同的案例中概念内涵不同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一文中指出:“对日常的运用来说,在所谓的定义中对最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质所作的简短解释,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1](P.351)按照恩格斯对如何下“定义”所作的论述,运用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公共行动是现代公民在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内所展开的一种以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社会活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P.394)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人的发展与共同体密不可分,人的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但是,由于行动者之间“意向一致”的形式不同,基于政治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基于阶级利益共识的共同行动、基于公共责任默契的共同行动,行动者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三种不同的共同体形态中占有不同的主导地位,进而影响着公共行动逻辑的有序生成。
一、基于政治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公共行动的变形镜像
“个体行动”与“共同行动”是对人类行为的两种区分。共同行动是人的共同体生活的确证,理性主义与行为主义对产生共同行动的基础有着不同的认识范式。理性主义认为,共同利益是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寻找共同利益是促进行动者共同行动的有效方式;行为主义认为,“意向一致”是共同行动的主观基础,行动者之间“意向一致”则是共同行动的基础性前提,获取“意向一致”是促进行动者共同行动的有效方式。行为主义认为,“认同、共识与默契”是“意向一致”的三种形式,因此,除了理性安排的组织协作行动之外,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与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三种共同行动的基本类型,这三种基本类型存在于不同的共同体形态之中。[3](PP.355~362)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对不同共同体中的共同行动类型的分析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的分析,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分析。这三种共同行动类型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中事实上并非独立而是相互交织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共同体中哪一种共同行动类型占主导地位而已。从领域划分的视角考察,“在私人领域中,存在着共同行动,也存在着个体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个体行动是私人领域中一切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或者说,私人领域中的共同行动是从属于个体行动的,是服务于个体行动的目标的。然而,公共领域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公共领域中的一切活动其实都应当被理解成共同行动”[3](P.357)。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之所以能展现出共同行动的精神面貌,除了在理性安排下以协作行动的形式出现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行动者之间在某项行动上产生了“行动的意向一致”。只有行动者在“是否共同行动的意向”和“如何共同行动的意向”两种不同的行动意向上达成一致,行动者才能真正地开展共同行动。按照张康之的阐释,在“是否共同行动”和“如何共同行动”两种行动意向上,直接形成了共同行动发生的两种不同路径。[3](PP.360~361)因此,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型公共领域还是中世纪时期的代表型公共领域中的一切活动都应当被看作为共同行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共同行动缺乏言说的公共性,不能将其误读为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旨归的共同行动,而且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共同行动并不鲜见。共同行动并不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理性行为,因为在农业社会中无所谓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用利益分析方法来分析农业社会中行动者之间的共同行动的原因与动力具有理论上的缺陷。人们共同行动的发生机制是认同,共同行动是根植于认同基础之上的,共同行动是一种基于政治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共同行动者之间并没有鲜明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行动带有一种强力支配性的色彩,行动者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共同行动的结果在不同行动者之间是不相等的,认同即意味着“自我”牺牲。权力强制是一种获取无条件认同的常态现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古律便是一种臣民对君主无条件认同的历史注脚。虽然从表面上看强制或奴役的办法是最简单可行的,但是,强制的认同基础最差。人们之所以认同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获取认同更多是权力操纵或影响的结果,是一种权力意志的产物。在集权社会中,民众是没有“自我”的,其往往是被统治者所愚昧的对象。民众认同不是出于实现“自我”的一种自愿性认同,与其说是一种主观上的情感认同,不如说是一种实质上对权力的服从。“强制、欺骗、诱导与煽动是获取认同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如果说还有其它方式的话,也主要是这些方式的变体。”[3](P.371)阿伦特认为,“行动”与“语言”构成了城邦型公共领域的人际交往,城邦公民是一种“能说会道”的政治动物,但在“基于政治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中,行动者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交往是一种单向信息流,在强力的操纵与影响下,人们在公共领域中附和他者的思想价值观念、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成为一种明哲保身的行为。基于政治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也往往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行动者向处于弱势地位的行动者的单向信息流,共同行动以“命令—服从”“诱导—听从”或“煽动—响应”的方式得以建构。基于政治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的“意向一致”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而是所谓的领袖及其追随者所制造出来的产物,并不是出自于行动者的内心。共同行动的结果不具有合理性,且是不道德的、公共性阙如的,这种共同行动是农业社会中的常见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意向一致”的形成过程即是一种“洗脑”的过程,共同行动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领袖制造出来的。“这种人工制造的东西常常在现实中与古典理论中的普遍意志相一致。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便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而只能是它的产物。”[4](P.388)历史表明,在集权社会中,“认同是一种放弃自身意向而以他人意向作为自己意向的结果”[3](P.371)。个人成为了黑格尔言说意义上的“为他的存在”,政治强力成为了集权社会中获取认同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作为一种反应行为,认同通常是在政治强力或其变体形式刺激下的一种行为反应。
随着行业的发展和南方航空管理制度不断地规范,程凤萍回忆:“33年来,我不记得接待了多少旅客,受过多少委屈,救过多少人。空姐的任务就是让旅客开心地到来,开心地离开。对待小孩就是阿姨,对待老人就是闺女,对待盲人就是拐杖、对待病人就是医护。”多年的职业习惯让程凤萍在迎接旅客登机的时候都善于观察每一位旅客的表情和神色,稍有反常的情况她都会叮嘱机舱乘务员特别留意,随时都关注晕机或者身体不适的旅客。
众所周知,“强力”可以以个体形式或共同体形式存在。在农业社会中,强力多是以共同体形式存在,认同也多是一种群体性认同,是强力命令下的集体性或群体性的服从。人们之所以服从强力是基于一种无可奈何或明哲保身的所谓的感性行为,而不是基于一种共同义务的理性行为。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通过命令而强制获取认同成为集权社会中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但是,通过强制方式所获取的认同是不道德的,是注定要难产的,因为强制导致服从,服从背后的认同也只是在“强力”命令下的一种形式认同,而不是行动者基于“合意”的实质认同。任何“强力”本身都不具有正当性,都不可能转化为人们的正当权利。“强力正当性说”也完全是统治者维护其自身统治的一种合法性欺骗,经不起理论与实践的检验,其在政治实践领域直接造成了对普通民众的意志褥夺。因此,可以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直接推翻了强力正当观,认为任何强力本身都不具有正当性是卢梭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需要明确的是,否定集权社会中的“强力正当性说”是反对强力自己给予自己正当性、以自己的强大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并不是说强力不能具有正当性。强力要获得正当性必须接受卢梭所言说的“公意”基础上“契约”的洗礼。只有经过“契约”的洗礼,强力才能获得正当性,才能得到人们的承认。事实证明,在集权社会中,行动者多是出于对强力的恐惧而附和行动,共同行动也更多地异化为一种权力指令下的政治运动或群众运动。行动者严格按照强力编码所设定的图式行动,行动者如同温顺的羊群没有领头羊来当家作主则变得无所适从。在所谓的英雄、领袖的人心蛊惑或动情的煽动下,行动者极有可能呈现出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成为个体意识泯灭的“群氓”,行动者在共同行动中并没有“个人自大”而是“合群自大”,群众也等同于无意识的群体,所谓的“谋杀无动机”也往往成为一种极其可怕的力量。正如罗素所言,“在目标一致的热烈集会上,群众有一种热情和安全交织的得意感。这种共有的情绪越发强烈,直到排除一切其他情感,只剩下一种因‘自我’倍增而产生的权力兴奋感。集体兴奋是绝好的麻醉。其间,理智、人道、甚至自我保护很容易被遗忘。这时候,残忍的屠杀和英勇殉难同样是可能的。这种麻醉和其他种类的麻醉一样,它的快感一旦被体验到,是很难抗拒的。”[5](P.17)为此,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共同体中的等级结构决定了人们的共同行动是基于政治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家元共同体是造就认同的社会环境,它的等级结构决定了它并不需要达成共识,或者说,它不需要让共同行动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3](P.371)从而消解了家元共同体中共同行动的言说公共性,公共行动在事实上也沦为一种公共性抽离了的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公共行动往往被政治强力所诱导、操纵,甚或沦为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士谋求自己私利的工具。人们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的共同生活等同于公共生活,将共同行动等同于公共行动,实则是对历史镜像的一种极大误读,因为公共行动只有在市场出现之后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与良性互动之中才能真正生成。
“听、说、读、写”是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在新时期提高核心素养是新时期教学发展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重点任务之一,尤其是在阅读教学中,要充分利用阅读教学的多样性,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行全面的培养。同时要对教学现状进行全面分析,找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措施,从而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基于利益共识的共同行动:公共行动的消解困境
分化、异质、多元是“虚幻的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形成共识成为多元民主社会的内在诉求。“共识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在政治意义上,它指的是与政治体系有关的信念,是指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对既定问题达成普遍一致协议的状态。”[6](P.155)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中,多元差异是共识形成的前提与基础,共识是多元差异整合的目的与结果,人们在多元差异中寻求共识是工业社会的必然诉求。共识是感召人们的一种软力量,在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公众舆论是共识产生的必要条件。共识是建立在自由独立的公众舆论之上的,共识源于一定的公众舆论,没有经过反复的理性沟通与妥协就难以形成一定的公众舆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也就无法形成共识。按照萨托利的分析,共同体层次的共识(基本共识)、政体层次的共识(程序共识)、政策层次的共识(政策共识)是共识的三个层次。[7](P.101)其中,共同体层次的共识是现代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首要共识,表征为对民族国家的认可、认同与捍卫。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能展开共同的政治行动,首先需要在政治共同体层次达成共识。“因为一个共同体是需要建设的。共同体不能日日创新,但也不能仅靠一段共同的历史和过去创建时的神话或事件来维系。建立或重建共同体的构建行为的必要性,对于新的共同体,如世界各地区或全世界的共同体的构建尤其重要。”[8](P.81)政体层次的共识表征为人们认同、认可某种行为规范的准则与程序,捍卫与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离不开政体层次的共识,需要以政体层次的共识作为社会调节活动的规范与准则。政策层次的共识表征为人们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是民主制度的特征要素,也是各种不同意见、不同思想、不同看法甚或社会反对派出现的背景。没有政策层次的共识,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之所以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就在于这个社会对各种不同的意见、思想或看法等持有较强的宽容性,而且能够将其统一于共识。西方政治思想对共识理论也有着深刻的阐释,个体同意基础上的契约共识理论和交往对话基础上的多元共识理论分别是西方多数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思想基础。在多元社会中,对于如何整合社会多元价值观和形成政治共识,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分别站在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在学理层面开出了不同的处方。其中,自由主义主张以公共理性整合思想价值观的多元性。针对自由主义的主张,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以任何理由为任何一种道德主张辩护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主张放弃自由个人主义,以公益政治学代替权利政治学,重叙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以谋划共同行动。俞可平指出:“当代社群主义者的社群概念基本上导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社群界定成为达到某种共同的善的目的而组成的关系或团体。”[9](P.75)自由主义则以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和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为典型代表。罗尔斯认为,各种不同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之间可以形成共识,并各自独立。“此种理性的自由观念可以获得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之重叠共识的支持。因为,通过使该政治观念与各种完备性学说及其对政治美德之重大价值的公共认识之间达成一种一致和谐,这种共识便得人们的顺应。”[10](P.182)哈贝马斯针对现代哲学范式实现由主体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转换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在交往行动中经过理性的反复协商、对话形成商谈共识。“参与者应该无保留地追求他们的语内行动目的,他们的同意是同对于可批判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相联系,并表现出准备承担来自共识的那些同以后交往有关的义务。”[11](PP.4~5)通过比较二人的共识理论不难发现,“公共理性”是罗尔斯为形成“重叠共识”所设置的原则。“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10](PP.225~226)对于理性的公共性特质,罗尔斯从理性的自身、目标、本性和内容等原初问题进行论证,认为“作为自身的理性,它是公共的理性;它的目标是公共善和根本性的正义;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10](PP.225~226)。“有效性”是哈贝马斯为形成“商谈共识”所设置的原则,他提出“有效性”是实现“实践理性”向“交往行为合理性”转变的必要条件,命题之真实、主观上的真诚和规范上的正当是“有效性”的三个向度。[11](P.6)可以说,在尚未找到更好的整合社会多元价值观的方法论之前,将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作为当今整合社会多元差异形成政治共识所要遵循的原则,无疑有利于政治共识在现代民主自由社会中的形成。
“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对话特征。”[13](P.296)在某种程度上,实质民主的背后是共识,民主是差异中寻求共识的一种实践。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认为掌握话语主导权即掌握了主导权力。当今人们交往行动的多元性也使得公共话语而非强制暴力成为建构人们共同行动的有效工具。但是,在多元社会中,公共理性和有效性的要求也往往会受到各种话语形式的冲击,民主追求产生变异,特别是受到两种话语形式的影响与操纵,即霸权独白和无责漫谈。[14](PP.348~355)这两种话语形式共同阻碍着政治共识的有效生成。一方面,霸权独白是一种交往行动中强势者表达自己意志的方式。强势者可以凭着自己所掌握的话语主导权提出对公共问题的见解与主张,甚或利用自己的话语主导权来煽动人们的情绪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偏好。意识形态操纵、个人霸权、公共舆论等都会成为霸权独白的来源,在交往行动中,共识被消融于“公共舆论”之中是霸权独白的现实写照与清晰表现。因为在权力与资本的共同宰制或操纵下,作为人们在社会秩序基础上的一种公开反思的共同结果,公共舆论往往受到权力与资本的影响与控制。作为一种权力与资本意志侵蚀下的强制性共识,人们在交往行动中往往会陷入“公共舆论”的陷阱。另一方面,无责漫谈则走向了话语交往的另一个极端,是一种无须承担任何身份责任、去中心化的不以谋求任何共识为目的的话语表达形式。非正式聚会中的闲聊胡侃、具有低级趣味的争吵谩骂、交往行动中的谣言谎言等各种各样的话语泛滥正是“无责漫谈”的具体表征。“微博是用来骂人、微信是用来吵架的、公众号是用来裸奔的,然后博客就是写给自己看的”[15]的隐喻调侃正是“无责漫谈”的现实写照与生动表达。“霸权独白”与“无责漫谈”不过是以一种更为隐性的控制机制影响、操纵着人们的交往行动。“话语不真实的命题”明显有悖于罗尔斯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理性”与“有效性要求”的核心原则,营造的是一种自由但不放任的多元话语秩序,导致交往行动中“独白者”与“听众”之间的力量失衡。交往行动朝着话语强势的独白者的偏好倾斜,直接消解了人们交往行动的开放性与公共性,不利于政治共识的达成,消解了建构公共行动与拓展公共利益的公共性。
张康之指出,共识在农业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农业社会中的人们也不会有谋求共识的愿望,农业社会中只存在感性意义上的认同。作为一种整合、统一多元差异的共识只存在于工业社会之中,现代工业社会不仅呈现出共性,而且呈现出差异,共识正是在差异与共性的基础上获取的。差异与共识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前提,倘若政治共识阙如,多元社会极有可能出现分裂甚或崩溃。[3](PP.25~29)因为“在多元社会中,社会按照宗教、意识形态、语言、文化、民族或种族的分界线高度分化,形成了拥有各自的政党、利益集团和传播媒介的实际上彼此分离的次级社会,导致了多数民主模式所必需的弹性缺失”[12](P.23)。要看到在农业社会中存在的共识并不是在多元差异的基础上经过理性的反复沟通与妥协而形成的,而是靠对权力的恐惧威胁或欺骗而获得的,所以在独裁统治或集权社会中所形成的共识更多是一种“伪共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虚幻的共同体代替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创制秩序代替了自然秩序,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的等级制度土崩瓦解。“政治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共同行动如若再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所以,族阈共同体中的共同行动主要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的。”[3](P.19)基于利益共识的共同行动进而取代了基于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人们的公共行动只有以利益共识为指向才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交往行动者之间也只有形成了利益共识,交往行动才算完成了使命,公共行动才可能真正实现。
三、基于公共责任默契的共同行动:公共行动的和谐发展
默契是人们展开共同行动的主观基础。“默契则表现为处在共同语境中的人们对于行动的最优理解,当准备参与共同行动的人们对需要采取的行动达成了理解上的一致性时,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共有的最优理解了。”[16]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消灭了“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和解(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得到了真正的实现。劳动成为真正的自由自觉的社会劳动。人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彰显。这里看不到阶级、看不到国家、看不到暴力机关,也看不到利益差别,是一个最民主、最公正、最平等、最自由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里的社会秩序既不是“自然秩序”的现代复活,也不是“创制秩序”的简单翻板,而是基于人们各尽所能的责任编码所建构起来的合作秩序。共识以差异与多元为前提和基础。在“真正的共同体”下,由于“三大”差别消失,利益的差异已不再存在。由于“自由个性”的实现,归属于不同身份、阶级的多元主体也不存在,通过多元主体差异的整合来谋求共识也没有了自己的空间,人们只能在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认同中确证人类的解放,基于利益共识的共同行动也走向了“历史终结”。尽管人们也许会因为对共识的留恋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去修缮公共行动,但这无疑会陷入毁灭性的失败。同样,“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基于强力认同的共同行动也不可能会出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共同行动建立在“心灵契合”的公共责任默契的基础之上,这种基于公共责任默契的共同行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基于权力强制性默契的共同行动。这种基于公共责任默契的共同行动是一种以主体间的平等承认为前提的具有合作性质的共同行动,交往主体在共同行动中有着天衣无缝的配合与协作。默契成为一种人们展开共同行动的主导性的发生机制,默契的动作不需要指令,默契输入了交往主体心灵共同编制的程序密码,是一种简洁的心灵认同。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每个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都很高,人与人之间的认知能力、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觉悟都处在同一水平线,这直接为公共责任默契的达成提供了主体基础。但是,如果基于公共责任默契的共同行动没有“社会共识”作为支持,这种基于公共责任默契的共同行动也难以得到长期性的发展,人们的共同行动极有可能沦为一种协作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共识”的获得不再是政治权力指令下的统一性获得,也不再是多元主体凭借公共理性对多元差异进行整合而形成的一种“重叠共识”获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共识”的原则,“共识”获得是通过人们的自由劳动、工作分工和最广泛的民主参与实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P.294),这一至理名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对未来新时代精神加以高度概括的命题,隐喻公共责任默契来源于交往主体的共同目标与任务,即“人类大我”公共世界的塑造。因为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共同体生活是个人之乐事,个人信念是共同体生活之乐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图景。同时,其也隐喻公共责任默契是“自由个性的个人”自由自觉的结果,是人们主动将自我融合于公共世界之中的一种意向。公共责任默契促使人们在自由活动中进行合作选择。而且人们在合作中有着相互的配合与支持,人们之间形成的公共责任默契不仅是目标上的一致,而且是手段与方式上的一致。公共责任默契以合作面目体现在人们的具体行动之中,人们之间的默契性合约关系是无以言明却又心照不宣的内在约定。它构成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的一种社会资本,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社会资本不再是以社会网络、资源、期望与能力等具体形式体现,而是以默契性合约的具体形式体现。默契性合约深深地嵌入于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组织之中,表征着主体之间的和谐互动。随着这种社会资本的累积,基于公共责任默契的共同行动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这种共同行动也并不是一种彼岸理想的预设或价值的悬设,而是一种自觉生成的合作性运动。合作性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财富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这是高度合作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固有特质。“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P.832)这里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区别于以往植根于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也有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所有制。它是一种植根于每个人都各尽所能且基本生活都得到充分保障下的社会财富共有基础上的劳动所有制。
②宝钗听了,愁眉叹道:“……等我和妈再商议,有人欺负你,你只管耐些烦儿,千万别自己熬出病来。”(第五十七回)
马克思在考察批判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联合劳动制度产生的必然性,描绘了联合劳动制度取代雇佣劳动制度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与终级旨归,明确地指出“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19](PP.605~606)。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社会中联合劳动制度致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形式走进了“历史的坟墓”,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两大阶级对立也步入了“历史的终结”,“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20](P.219)因此,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资本雇佣下的劳动也不再存在,联合劳动合作制度彻底颠覆了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合作不再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基础上的一种人对人依赖性的简单合作,而是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大规模的合作。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合作思维方式成为一种人们认识生活世界、建构生活世界的方法论。共产主义的劳动合作充分实现了民主,每个劳动者都以平等的资格参与劳动生产计划,劳动成为一种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每个劳动者都具有高度的劳动义务感,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自愿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21](P.305)。需要加以澄明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则并不意味着要消灭人的社会角色差异。建立在劳动者兴趣爱好基础上的劳动分工与工作分工依然是存在的,但是联合劳动的合作生产方式与人们的劳动义务感等则完全可以使劳动者的私人利益与社会的共同利益协调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在更高物质基础上的统一,获得了自由选择劳动部门的平等与“人类大我”共识的支持,人们对联合劳动这种责任的担当和现实行动正是交往主体之间公共责任的默契品质与合作精神的时代注解。总而言之,“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会受到资本与市场的操纵或影响。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其是以产品经济为其基础的,这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体现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之中,而是直接体现在产品交换之中。同时,人们的共同行动也不会受到强力编码的设定,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会沦为权力意志下的集体行动,也不会出现集体无意识的现象。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取代了国家的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功能,劳动者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利,自觉、平等地参与社会管理与自治,这里没有国家,也没有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公共权力失去了政治性质。因此,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们公共行动已不再受权力意志和资本意志的宰制,公共舆论是在以“合作”为轴心的基础上加以建构起来的,建构人们公共话语的是合作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在更高物质基础上和共产主义觉悟下的合作成为一种整合人的力量的新型方式,公共行动会在基于公共责任默契的共同行动基础上由合作编码建构起来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伯特兰·罗素.权力论[M].勒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6]戴维·米勒,韦农·波各丹.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7]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8]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M].高凌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9]俞可平.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A].刘军宁,王焱.自由与社群[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1]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2]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M].陈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A].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4]张凤阳.政治哲学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5]汪洋.众神狂欢时代“批评”何为?[N].21世纪经济报道,2016-09-05.
[16]张康之,张乾友.论共同行动中的共识与默契[J].天津社会科学,2011,(5).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Public Action-an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Common Action
CHEN Fu-long
(SchoolofMarxism,NanchangInstituteofTechnology,NanchangJiangxi330099,China)
[Abstract]As a concept sublimation and practice refinement of common action,public ac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which is aimed at pursuing and realizing public interests.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constitutes the basis of public action,and presupposes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action.As a logical response of the types of common actions,different actors have different forms of consensus in different community forms.Based on common action of political strong identity,common action of the consensus of class interests and common action of tacit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actors occupy different dominant positions in the"naturally formed community","unreal community"and"real community",which lead to the logical generation of deformation,dissolution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public action.
[Key words]Public Action;Common Action;Generative Logic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9)02-002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研究”(编号:15BKS039)。
[收稿日期]2018-06-15
[作者简介]陈付龙,男,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2.005
(责任编辑 屈虹)
标签:共识论文; 共同体论文; 社会论文; 强力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行政管理论文;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研究”(编号:15BKS039)论文; 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