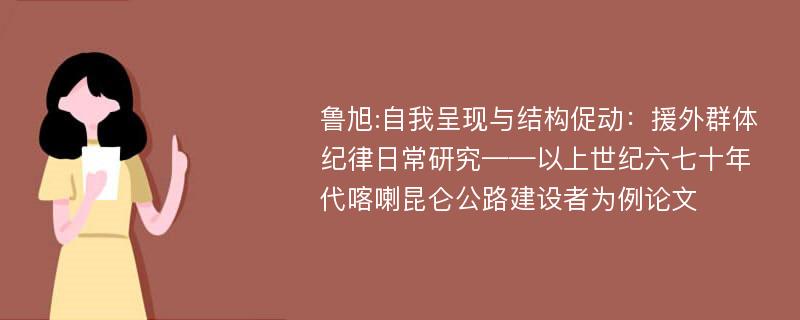
摘 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喀喇昆仑公路建设者执行严格的外事纪律,特定的时空情境打破了群体间既有的交往边界,群体间的日常接触逐渐形成了特定场合中新的常规生活,这种新的例行化在时空范围内的绵延促进了隐匿的结构转化过程,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国家间的观念结构。行为体的自我约束性不仅意味着国家意志层面的非武力,更体现在直接相关群体日常接触中的自我呈现。在“一带一路”建设逐渐深入推进的现实背景下,对喀喇昆仑公路建设者纪律日常的研究,为时下的境外合作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喀喇昆仑公路建设者;自我呈现;结构促动;纪律日常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理论阐述
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在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社会科学领域对这条公路建设的研究,目前除在国际关系学领域零星可见之外,几乎并无其他。本文立足情境社会学视角,对此案例予以探视。笔者在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援助巴基斯坦修建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者进行口述访谈时发现,受访者面对与巴基斯坦当地人交往的问题时,首先会意识到他者对中国筑路员工“非常友好”,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双方交往的事件记忆和图像记忆在现实与网络中比比皆是;然而当笔者希望他们进一步讲述与当地人的具体故事时,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由于外事纪律的严格,工人活动范围有限,对当地人禁止接触。何以出现这种似乎存在“矛盾”的讲述,除去遗忘或访谈情境等偶然性因素,是否还存在其他的解释?在讲述者的话语中,“友好”与“纪律”是显著的关键词,它们各意味着什么,并导致了怎样的后果?本文试图从“拟剧”理论出发,通过筑路员工对“纪律日常”的回忆口述,考察筑路人员在纪律性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探求建设者群体的“共同在场”以怎样的姿态得到维持,并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较微观层次的考察,本案例相对国际关系的宏观命题而言,自有其有限性;然而,作为中巴战略合作典范的喀喇昆仑公路,是两国间事实同盟以及友谊象征的代表符号[1]21。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之际,本案例的分析,将对时下的境外合作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在SUSAN算法中,每个像素对USAN的贡献值主要是由其与原子核亮度差的指数函数式(4)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同时也对二元方程进行了对比分析,但上述的指数方程的贡献是众多方法之一。因此,本文也将比较二进制方法。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在戈夫曼的理论体系中以“拟剧”表演的角度得以理论化,个人或群体日常行为具有“表演”性质,目的在于通过维持特定情境,建立特定印象。“表演”一词“指代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用‘前台’来指称个体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前台的组成部分可以包括:官职或官阶标记;衣着服饰;性别、年龄、种族特征;身材和外貌;仪表;言谈方式;面部表情;举止等等[2]19-20。戈夫曼的分析有意形成系统性的表演技术,为此,行为体个人抑或群体在特定情境中呈现为“剧班”。“剧班”搭建舞台,并被区分有前台和后台;前台紧张,刻意“装扮”;后台松弛,恢复“真实”。“前台”呈现的时空范围,限制在戈夫曼所谓“区域行为”的概念中。“表演促生的印象和理解就渗透在这样一个区域和时间的跨度之中,从而使身处这一时空之中的人能够观察这种表演,并受到由表演促成的情境定义的引领。”[2]93
李叔和最近越来越烦老梅,他对老梅无休止的要求产生了恐惧。自从和付玉续上旧情之后,他更不愿理老梅了。老梅有些不甘,打手机问李叔和,好好儿的,为啥不听使唤了?
戈夫曼聚焦的社会互动的“剧班”控制技术及舞台崩溃的后果,是对日常活动的微观注视。他的理论曾一度被认为缺乏宏观的结构关联而被冷落。而这一点,在吉登斯对“结构化”理论的构建中得到了极力辩护和更好发挥。以“共同在场”的技术,将特定情境在时空中绵延开去。时间维度上,行为体的“日常接触一般总是作为例行常规发生的”[3]67。“例行常规”表现有一种强烈的反复性,反复的例行化即具有了结构的属性;在空间分析方面,吉登斯引入“区域化”概念,“区域化”将互动情境中的前台和后台进行分离;他对戈夫曼的纠正在于,“前台”的呈现并非机械的表演,而应将行为体的意图纳入考察,即处于前台的是一个“主我”。吉登斯将具体情境中的实践和制度化的实践进行关联,宏观“系统整合”发生在同属“时空边缘”内不同区域的相互联系中,从而消解所谓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对立。新的“例行常规”发生在“主我”面临“紧要情境”时,亦即重新形成区域化的过程。“结构二重性”是结构化理论的内核,强调结构既是行动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使得吉登斯对待“变迁”需要关联不同结构类型的社会,以及跨社会系统的情境,从一种“世界时间”或“局势”的影响中发现[3]112-122+230。
1.5.1 提取DNA 将鱼体背、腹两侧及尾部肌肉200 g剪碎后使用DNeasy®Blood&Tissue Kit试剂盒对样本进行提取,按照说明书的步骤进行操作,所得DNA溶液作为PCR反应的模板。
在国际关系研究相关议题中,结构化理论以及符号互动论观点为建构主义理论家温特的本体论思考提供了基础[4]144。符号互动论者库利认为,“社会在它最现实的方面,是人的观念之间的联系。社会的存在需要人们在一起,但人们只是在人的观念中在一起。”[5]83米德进一步发展“主我”“客我”的概念关系,认为“主我”能够把“客我”用作实现大家全都关心的事业的手段[6],即依照他者而定位自我。建构主义综合以上两者将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界定为一种观念文化的建构,国家行为体具有施动性,因为“国家也是人”。国家行为体通过对他者的认知,建构观念或转变观念,从而形成互动双方的特有关系文化,即“共有知识”。总之,是观念建构了利益和权力,前者与后者同时产生,并非因果关系。温特就此总结出三种无政府文化,分别为“杀戮”的霍布斯文化、“竞争与对抗”的洛克文化以及“友谊”的康德文化[4]298-299。该理论局限在整体主义的视角,在“世界社会”逐步形成的当下,应当丰富其内涵。
二、在场群体及国家间既有观念结构:公路建设背景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援巴筑路员工,身处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那里没有想象中的“遍地是黄金”。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相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进入这种“紧要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超越常规的生命挑战是一种决定性的特征因素。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导致其群体在相当程度上失去对身体的某种自主性把控。筑路人员常把这次援建比作没有硝烟的战争,要面对随时来临的危险与牺牲。他们常年身处巴基斯坦境内北部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将其与外部世界隔绝。枯燥乏味的工地生活加之外部自然环境威胁,导致普遍化的焦虑、寂寞、甚至恐惧心理的出现;而这种心理反应,形成了吉登斯结构化体系中动机激发的情境条件。
近日,沃尔沃卡车为其FH、FM及FMX车系的D11、D13柴油发动机展开一系列改进,以满足最新欧6 D阶段排放标准,进一步为运输从业者降低燃油成本。
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受美国的合围封锁,“敌我”对峙。更具挑战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国与苏联的密切同盟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回支援专家以及两国在边境上的争议,严重地影响了两个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西南边境,印度野心膨胀,抛弃两国友好外交传统,其对待西藏问题以及两国边界问题的态度,冷却了两国热情。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后,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工程股队员刘伯涛常跟随专家、技术员到公路沿线搞勘察、测量,他们三三两两独立外出工作,对执行外事纪律有着更多的感受。一次,刘伯涛正在测量,远远看见几个巴基斯坦姑娘好奇地想看他们。当时埋头工作的刘伯涛以为姑娘们不会靠近自己,谁知道,姑娘们竟来到自己身边,问这问那,还要向刘伯涛学习说中国话。这一下差点没把刘伯涛吓晕过去。用刘伯涛的话说:“当时抓外事纪律特别严,我看见巴基斯坦姑娘靠近自己,就像发现泥石流向我压过来,吓得我丢下测量器材,拔腿就跑。”[14]
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队伍,主力来自部队以及作为“准军事实体”[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准军事实体”,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门户网站http://www.xjbt.gov.cn/bt/ 2018-12-17. 的兵团。1968年,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自治区交通厅等单位,抽调、组建的总数8000余人的筑路大军陆续进入巴基斯坦[7]。“修筑中巴公路巴境喀喇昆仑路段156公里”,“此后,巴基斯坦再次请求中国将喀喇昆仑公路延建到塔科特,中国方面于1974年又从新疆军区各部队和生产建设兵团选派8700余名官兵,国内其他省区也选调援巴筑路员工400余名,共9100人,开赴巴基斯坦投入第二期工程。”[8]1978年,即所谓“水毁工程”,中方从第二期施工队伍中留下 2000 余人,再由国内选调 1000 多人予以补充,组成了 3750 余人的施工队伍进行第三期工程。十余年间,共有两万余中国筑路员工出国援助巴方筑路。另外,作为配合施工、安全防卫以及相应的联络工作的需要,巴基斯坦政府同样派出数万人的施工队伍,单是第二期就有6000余人[9]。修建喀喇昆仑公路,人力派遣数量巨大,机缘性地提供了边界明确的群体间共同在场的机会,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互动与认知。
漫山遍野的杏子落到地上,我们给人家扫起来,堆在那里,没人去吃;吃饭的时候,偶尔杏子落到碗里,也要捡出来,放到一边。[注]李JZ,援巴筑路工程人员,访谈时间:2018.08.14,访谈地点:河南濮阳。曾有一位中队统计员,一位友好的巴方朋友常来看他,有次送他一个苹果,他不收,巴方朋友就放在地上走了。他后来拣起苹果放进了抽斗,几天后把苹果吃了,被撤职处分了。[注]袁SP,援巴筑路工程人员,访谈时间:2018.12.16,电话访谈。
“我们去的时候,在相对封闭的北部山区,收音机都很普遍了。他们当地老百姓常在外面,拿着烟袋,背上收音机。我们看到了,就不敢靠近,以为是“苏修特务”,带着情报发报机。我们不知道那是收音机。”[注]郭ST,援巴筑路工程人员,访谈时间:2018.10.12,访谈地点:乌鲁木齐。“当地老百姓也不和我们接触,他们担心自己被‘赤化’”[注]唐QX,援巴筑路医护人员,访谈时间:2018.10.09,访谈地点:乌鲁木齐。“修路之初,很多人对我们不友好,有的朝我们扔石头,有的放冷枪,干扰施工。当时巴基斯坦人可以分为三类,亲美的、亲苏的和亲中的,亲苏的也挺多,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比较紧张了。”[注]王HS,援巴筑路工程人员,访谈时间:2018.10.02,访谈地点:乌鲁木齐。
特定的时代背景,导致“敌我”观念普遍化以及认知神秘化,双方之间“敬而远之”。从亲历者的讲述看,这些带去“友好”的人,在当地看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更像伪装的敌人。此时中巴两国间的状态结构吻合温特对“洛克文化”的阐述,洛克文化尊重他国主权,少有侵略;国家主体间是自助的,也是合作的。对于“敌人”的描述,实际上已不具有侵略者的威胁和杀戮的意义[4]287,而只是双方竞争关系的认知表征。
三、援外群体的“纪律日常”及其结构化实践
在戈夫曼对“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进行“拟剧”化的分析中,“表演人生”的认知理念被反复强调,似乎表演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种立场有些绝对[10],也有些泛化。本文所讨论的,并非日常生活全部意义上的自我呈现,而聚焦在面对境外他者时,援外人员的“自我”或“群体自我”在工地的日常活动中,依照纪律对言行、观念进行约束和调适而作出的特定表现。这种日常活动发生“在生活的给定时期,具有‘每一天都发生’的无条件的持续性特征”[11]。
在韦伯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纪律”被解释为“彻底理性化地、亦即有计划地、准确地、无条件的放弃任何自己的批评去执行得到的命令,而且仅仅针对这一目的不断地在内心上调整自己的态度”[12]。库利则力图发展一种“自由纪律”,他说“我们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全世界所需要的是发展一种自由纪律,它应立足于贡献性竞争而不是强制和机械作用之上。”“自由纪律建立在这样一个目的之上,即个体必须具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对他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会按照它的意志去控制和指引他任性的冲动。”[13]120因此,我们所讨论的“纪律日常”可以解释为,在一个目标理想的指引下,在一个给定的持续性的时期内,行为体有计划地、准确地执行得到的命令,它立足贡献性竞争,并按照这个目标不断调整自我的态度和行为。
(一)筑路员工“剧班”与国家“前台”
纪律是一种力的约束形式,体现为对象化的规范与一致,同时,行为体还需要在个人意志层面进行内化的调整与强化,以建构意识层面的合法性。喀喇昆仑公路建设者群体来自部队、兵团,体现出具有明确纪律观的群体属性。通过调查访谈可以发现,援巴群体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与“革命”意识,在他们当下的讲述中,诸如“国际主义战士”,“写血书”“表决心”“传播无产阶级友谊”“医治巴方病人作为政治任务”等词汇高频率出现。这些“较高层次”的纪律意识,要求自我在面对他国情境时,相关行动实践能够剔除或规避与标准相冲突的行为,以达到理想状况。作为建设者主力,援巴筑路员工自我定位于国家“前台”区域,将彼时的人物时空隐喻为国家“脸面”,实施控制性、管理性的印象表达。
援巴筑路员工出境后的兵营依印度河安扎,人烟稀少,与当地村庄和百姓远隔;各营地帐篷相对集中,并围成矩形而建,中间场地另作其他功能用地,亦可作娱乐体育场地;但遇地势险要地段,搭建住所只能依势而为,无它可言。在施工场地、帐篷生活区以及筑路医院,常有巴方配备少量工兵护卫,筑路员工与护卫工兵之间明确界限,不得过多接触,双方之间以象征性的礼节进行互动,即以极为简单的手势或用语开始并结束。筑路人员无论在原单位职务高低,出国前均脱下军装,着蓝色便服;工人之间不再以职衔称呼,而代之以同志相称。制度、规章、纪律充溢在工地的日常生活中,“注意事项守则十六条”是援外纪律的官方书写,而筑路工人对纪律的认知是“不动巴方一草一木”。正如他们常回忆到的:
由于国家性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传统观念在援外筑路群体面对异文化环境时不自觉地流露于言行。国际形势的对立格局以及鲜明的“革命”人生观,对普通民众思想观念里的“敌我”分类影响很深。因此,对于即将走出国门、执行着严明组织纪律的中国军事组织群体来说,每个成员都努力维持着“提高警惕”的心理状态。
“今天,我给一个巴方病人打洗脸水,又倒掉尿壶里的小便,有个中国病人给我提意见,他认为,这样做在巴方病人面前显得奴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把平凡的护理工作看得下贱,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坏东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为人民服务应该感到光荣。由于巴方社会制度不同,基层人民受歧视,而在我们的医院却受到同中国人一样的招待,医生们认真看病,护士们周到护理,让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好。”[16]205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共同的命运摆在两国面前。严峻的形势使得两个国家考虑合作突围。因此喀喇昆仑公路应运而生。喀喇昆仑公路全程跨越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边界,横穿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印度河流域等气候、海拔、地形差异极大的不同区域,是“流血的山谷”,是“生命禁区”,工程艰难。公路建设共分为前后两段,第一阶段:红其拉甫至哈里·格希(1968-1971);第二阶段:哈里·格希至塔科特(1974-1978),另外还有1978-1979阶段的水毁修复工程。
“不协调角色”的出现,往往导致意外的后果,使得某种层次上的“自我呈现”暂时失效,而这种“舞台”的崩溃,正是一种规范压力所导致的结果。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的“前台”存在统一性,也正因此,少数人在处理由于工程以及生活环境压力所产生的个人的负面情绪时,常常使用的“弱者的武器”便是故意暴露“后台”,将磨得破烂的裤子、鞋子故意呈现给他国“观众”,以表达对剧班内部有些条件的不满。援外人员的境外施工,需要保持高品质的纪律意识,长期的实践内化了这种约束意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建设者回忆当时的境外生活时,“外事纪律”在个体回忆进路中所产生的阻碍作用,因为与他者的接触也就成为处于纪律边缘的“非日常”事件。这种意识之深,影响至今。群体日常的约束性,来自对他者认知的神秘性、隔离性、警惕性,来自不同阵营间的结构压力。援巴人员只能以谨慎的姿态、在日常琐碎的细节中全面践行制度规范,维持国家“前台”。
(二)纪律调适:建设者的交往跨越与认知转型
对限制交往与接触的纪律的“破坏”,是拟剧表演中的“角色外的沟通”。工程队的人们常说,他们不能和当地人接触,也不敢靠近,但双方都相互好奇,时间长了,熟悉了,相互之间感觉到没什么事,也就开始有一些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互动的触角伸向了其他范围的区域,更多的“后台”暴露而推向“前台”,但此时的前台“允许人们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中表现出‘退化行为’”,而“标志着这类情境的,不是关键情境所产生的焦虑的骤升,而是其反面,是消除了在日常生活其他场景中对身体和姿态进行严格控制的要求所导致的紧张。”[3]122他们谈如何挣钱,娶媳妇,相互开玩笑,新的区域化实践,帮助找寻到更多的共有特质。吉登斯对行为体的动机激发过程进行分析时,使用了“紧要情境”的概念,它专指与既有常规发生剧烈断裂的情境,会对其行为体带来巨大压力或焦虑。行为体在紧要情境中将努力寻求“本体性安全”,重建“基本安全系统”。基本安全系统是一种心理状态描述,日常社会生活在正常情况下包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紧要情境中,行动者可以借助交往技巧这种机制,再生产出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状况。当然,基本安全系统并不能完全遏制紧要情境中的焦虑,这也是紧要情境的典型特征。行为体在紧要情境中发生了某种‘再社会化’过程,重新建立起(有限且极其含混的)信任态度;这个过程首先是焦虑被强化,再是退化,然后是重新建构典型的行为模式[3]59-60。“产生对他人的信任感是基本安全体系最深层的要素。”[3]46这也就揭示了行为体重新建立例行化常规的动力学机制。
其中Emix为混合能,即两种物质由于相互混合而较纯净物状态所产生的自由能变化.在传统的Flory-Huggins模型中,各组分均占据一晶格点位.对于配位数为Z的晶格,其混合能为
《法制晚报》在刊发这条消息时,配了一幅漫画。画面中的两个人,正举着手机飞跑。其中一个一边跑一边说:“快点,还有5公里,走访还没有完成!”这真是可笑,在大街上跑步,就算是走访吗?而某些上边的考核者,看的只是行走的里程数字。至于你在哪里走,去干什么,全凭“指下生花”。
二战以后的世界,战略联盟差异导致了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结构性的两相对立,呈现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相互对垒;各阵营成员国在政治上针锋相对,经济上相互封锁,意识形态上相互破坏攻击。
施工的复杂性带来工程人员与当地人愈加丰富的日常接触,包括土地占用,引水改路,医疗救护等,事件的解决始终以外事纪律相关要求为关键原则;同时,援外人员在当地的棘手问题,也常常受到当地工兵与普通百姓的帮助。群体的“聚集”或“邂逅”愈发呈现社会互动性,积累着各自对他者的观望、认知和感受,并建立最初的信任,消除对方敌意的预设。尤其具有明确时空边界的“社会场合”,因其更加明确的互动仪式性,成为形塑高层次“信任”关系的典型场所。中国筑路医院并不承担对当地人的医疗救治任务,但几次突发案例,逐步改变了当地人的冷淡、怀疑,而建立起信任和依赖。例如在洪扎(Huzza)地区,洪扎王的弟弟的案例,几次棘手的妇女难产,巴丹地震现场救治等,这种互动性的“自然仪式”带动了在场双方的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
“起初巴基斯坦当地人自上到下,从洪扎王家族到老百姓,对我们并不信任,即便有的到医院来看病,拿到我们开的药,转身就扔了。”[注]关CZ,援巴筑路医护人员,访谈时间:2018.10.13,访谈地点:乌鲁木齐。“后来在帕苏(Passu)有个成功案例。当地妇女不能外出治病,有病都找巫医。巫医有药时给一些药,无药时就念咒文。有一位村长的老婆肚子胀大,又没有怀孕,巫医说是魔鬼缠身,让旁人感觉恐惧。村长偷偷地把老婆送到筑路医院求助。医生诊断是良性肿瘤。当地落后封闭,让一个妇女暴露身体接受临床手术,家人要承受很重的思想压力和舆论负担。而且愿意为手术输血的巴方老乡,在抽血时也都吓跑了。医护人员自己献血,进行了手术。她丈夫激动地跑出帐篷,大喊:胡达!胡达!”[注]袁SP,援巴筑路工程人员,访谈时间:2018.12.19,电话访谈。
情境性的互动仪式,所产生的感激、兴奋、欢愉,是过程性的短期情感;而作为结果,则是长期的团结感。长期情感以“情感能量”的形式得以保持,这种情感能量具有认知的因素,它以符号化的形式在记忆装置中保存下来[15]。援巴十余年间,中国筑路医院门诊接收当地就诊者近万人,手术56人次;中国医生被当地人称作“神医”,是“胡达”派来的[16]35。这种认知实际上超越了以面对面情境为主要特征的“周遭世界”,在更高层次的“共同世界”进行了理念建构。与此同时,群际认知与交往的逐渐转变在援外人员自我呈现的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方面实现了同步的转换。有位医护人员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
历史上,19世纪中叶的莫卧儿帝国,已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属地,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56年,巴基斯坦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员。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传统盟国,巴基斯坦延续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语言文化。然而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并不太平,其与邻国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持续争议,导致两国冲突不断,几次印巴战争给巴基斯坦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尤其在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印度的不宣而战,使巴基斯坦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帮助。1965年的印巴战争最终促成喀喇昆仑公路这条战略公路的上马,但作为美国传统盟国,巴基斯坦因顾忌美国反对,此前在修路问题上态度反复[1]21。
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为六十年代的中国与巴基斯坦提供了“共同在场”的机会,两国建设者在喀喇昆仑山脉间相遇,并搭建“自我呈现”的“前台”。工程初期,其边界就在于保持距离,不受资产阶级风气侵染,展现无产阶级友谊。因此,在纪律性日常行动中,对行为的僭越预设着严重的后果,不得触碰。建设者的自我呈现犹如库利对“镜中我”的某些阐述,他说,“只要一有别人出现,就像鲍德温教授所说的,一种‘对他人的意识’,即意识到别人对他的观察,就会引起模糊的不舒服、怀疑和紧张的感觉。一个人感到他的社会形象正在外露着,由于不知道那个形象究竟怎么样,他就暗中警戒着。”[5]145
表盘以白色珍珠母贝为背景装饰,缔造深邃感和立体感,与海洋风格相契合,珍珠母贝的天然虹彩重现波光粼粼的海洋之美。 偏心时分盘亦点缀一圈帕拉伊巴碧玺,配备白18K金材质时标,并于12点钟位置饰有一颗美轮美奂的祖母绿型切工钻石。逆跳秒针功能的魅力在于指针沿着秒盘的弧形轨道不断游走,当秒针到达30秒刻度时,会以逆时针方向跳回起点,周而复始。海洋Ocean系列20周年限量版双逆跳功能36毫米自动腕表搭载优质瑞士自动上链机械机心,具备65小时动力储存。前沿科技打造的硅材质扁平状摆轮游丝,有助于提升机心的等时性,确保机心经年累月完好运行。
援巴群体与当地人从神秘到认知,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综合因素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信任关系逐步在群体间建立起来。“纪律”作为援外人员口述回忆中的关键词,反映出相关群体面对他者时“自我约束”的状态。自我或群体自我“前台”的良好维护,以亲社会行为的姿态交往他者,他者便能够消除心理障碍,通过镜式反映,以同样的亲社会姿态反馈回来,形成群体间的“共有知识”保存下来。在结构化分析中,区域化情境互动作为某种角度的出发点,能够将互动最亲密、最细微的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方面远为广泛的性质联系起来[3]112。因此,渗透在日常接触中的情境互动,具有十分宏观的结构化意义,它为广泛的时空范围内的“系统整合”即国家间良好关系的建构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四、群体品质、身份塑造与国家间观念文化
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援助巴基斯坦修建喀喇昆仑公路的口述,建设者们常常首先意识到境外施工期间的组织纪律性,其无论集体或者个人,都以强烈的国家意识和“革命”意识约束自我。这种约束散布在言行、仪表、活动范围、思想意识等施工期间的方方面面。“前台”的搭建与维护,并不是虚假的表演,其包含着施动者的意图,包含“亲社会行为”的动机。特定的时空情境,导致群体间不断增加日常接触;纪律日常中的自我呈现,作为他者的“客我”在他者自身得到建构,而镜式反应的机制,使这种反应折返,建构着建设者群体“主我”;双方群体从边界、神秘甚至敌意的模糊性认知逐步建立起群体间的信任关系。情境互动仪式在其本身所属的过程中产生情感,或者感激,或者欢愉,而作为这种互动的长期结果,则产生一种团结感,它以符号化的形式,保存在“情感能量”中。特定情境中的互动,其经验范围限制在“周遭世界”,它是表面的、直接经验的,而这种情感的符号化转化,则会超越这个范围,形成“共同世界”层面上的理念建构,它可以是地区性的[17]。当下,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建构、衍生了不少的关系隐喻,如“巴铁”“brother”“中巴友谊万岁”,持续作用在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的关系建构中,这些符号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来自六七十年代筑路期间双方日常交流句尾“后缀”:“金巴多斯特”(中巴友谊)“金达巴(友谊万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将国家间无政府状态界定为一种观念或者文化,观念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国家间形成何种文化,取决于行为体采取何种行为,当然,这种行为也会再次建构它的文化,这种理论主要指向了国家行为体。然而,随着当下世界交往主体的多元性,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社会”悄然而起。社会学的经典命题认为,社会是人类建造的,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因此,这种建构主义的视角应当扩展至具体的微观层面。在温特的建构主义体系中,“自我约束”是必要不充分条件,其核心要义是“使之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层面的一个认知的维度。
监督是一项要求极高的系统工程,影响监督效力的因素本身也是综合且复杂的。尽管目前我国的纪检监察派驻制度成效显著,然而其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改革与探索,以期尽快解决影响我国纪检监察派驻功能发挥的问题。
祝国寺的“和谐”有不同的层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有寺庙内部人与人的和谐,还有寺庙与周围社区、与相距不到3公里的东川城市的和谐。当然,还有“以大带小”的管理实践成功营造出的东川全区佛教寺院的和谐。
五、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外合作项目在世界范围以及工程数量上不断增加,中国驻外工程人员在与当地共谋经济效益的同时,作为文化承载者,也带去了中国形象与文化。然而由于人员数量上的陡然增加,以及相关自我管理制度的尚不完善,一些违背制度、冲撞异文化的行为影响了他者对于中国的认知。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实际发挥着国际化的效应,甚至能够影响到国家间关系。群体认知与经济援助同等重要,或者更甚;好的合作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种相处的方式。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援建喀喇昆仑公路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在意识层面,须树立与国家理想相融合的高层次纪律观念。这种观念不单纯指向机械的强力的身体约束,其更应表现为“群体自我”内化了的自由纪律意识。自由纪律意识连接着国家与个人,不通过“事件”的激发产生情绪,而表现为更加日常化的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下支持每一个人“奋斗的年代”,纪律问题和理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能唤醒自己的一种社会性的或者说是社会宗教性的精神和理想,纪律也会随之产生以体现这种精神和理想;一个人觉得他和他的祖国心心相印,他就会为祖国付出宗教般的情感,这种情感是纪律最高尚的基础[13]122。在国家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世界性的交流和往来无疑需要这样的一种意识。
其次,在社会层面,注重群体的整体性呈现。当下常有的出境培训一般包括“尊重当地文化习俗”的规范要求,而这仅仅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尊重当地文化未必会被当地文化所尊重,因为其中还涉及到是否能够以他者的态度来建构自我的方面,这种被“观看”的境遇,在踏入境外异文化的第一步时,便已开始。
最后,在个人层面,注重“主体间性”在日常接触层面的表达。全球化时代国际行为体愈加多元,而无论国家、社会、个人层次的交流互动,最终都将落实到个体层面,尤其在数量庞大的境外建设群体中,与异文化的交流更表现为一种日常化的接触。因此,必需在这种日常接触的层面建立“主体间性”。这就要求在面对他者时,应将他者的每一个成员看作与我群相似的真正的人,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之进行交往,而不能将互动的他者中的个体看作一颗颗功能性的“螺丝钉”。
参考文献:
[1]成晓河.中巴战略合作的典范:喀喇昆仑公路[J].南亚研究,2010(2).
[2]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刚要[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王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6]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240.
[7]刘向晖.跨越天堑葱岭古道变坦途——中巴公路修建始末(续)[J].湘潮,2005(8):50.
[8]喀什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喀什地区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1306-1307.
[9]王复华,口述.中巴公路的修建[J].顿时春,陈伍国,整理.百年潮,2009(2):40.
[10]张士闪.欧文·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J].民俗研究,2011(2):2.
[11]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5.
[1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90.
[13]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过程[M].洪小良,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4]异域天路湘西[Z/OL][2018-08-04]https://user.qzone.qq.com/1197682637/blog/1280899224
[15]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74.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原23医院战友联谊会编.天路遗梦——中国人民解放军原23医院援巴战友忆海拾萃[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2018.
[17]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M].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45-252.
SelfPresentationandStructureChange:StudyofDisciplineinEverydayLifeaboutPeopleWorkingAbroad:BasedontheBuildersofKarakorumHighwayin1960s
LU Xu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In the 1960s, the builders of the Karakoram Highway implemented strict discipline of foreign affairs. However, harsh environment made the builders encounter "critical situations" and had corresponding disciplinary adjustments, breaking the existing boundaries of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groups; the contact in daily life between groups gradually formed a new routine life on the highway. And it promoted a hidden proces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pace-time scope, and shaped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between two countries. So, the self-discipline means not only the non-force of the will of the State, but also reflected in the daily contact of the directly related groups.
Keywords:the builders of Karacoram Highway; self presentation; structure 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9)03-0034-09
DOI:10.16614/j.gznuj.skb.2019.03.005
收稿日期:2019-2-20
作者简介:鲁 旭,(1989—),男,山东泰安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口述史、社会人类学。
责任编辑 彭国胜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巴基斯坦论文; 情境论文; 纪律论文; 群体论文; 互动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