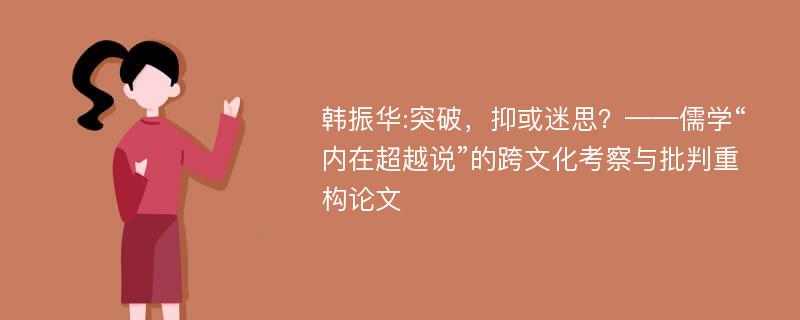
【摘 要】儒学“内在超越说”是现代新儒家在中西比较视域中的跨文化理论重构。然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它不断受到来自新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阵营的质疑。安乐哲、冯耀明、郑家栋等学者通过剖析“immanence(内在)”与“transcendence(超越)”在学理层面的相互悖反性,阐明“内在超越说”的不可证立性质。相较于“超越性”,他们更为强调儒学的“内在性”,认为“超越性”话语过时而“毫无生气”。尽管“内在超越说”所实际指涉的“万物一体”、“仁体”观念是传统儒学境界论意义上的真实存在,但当代质疑者所共处的“现代性”境遇(知识型)使得他们无法弥合“存有”与“价值”的裂隙,而更倾向于解构“内在超越说”的有效性。在“内在超越说”已经被问题化的前提下,借鉴“批判哲学”的思路,充分挖掘并发挥“内在超越说”的文化批判潜能,是这一学说打破单一的宗教性/精神性理解模式,实现哲学重构的可能路径。儒学“内在超越说”是一个文化“混血”的哲学命题,这标示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学的当代诠释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如何经由批判性的现代重构,超越那种相互绝缘的对比研究模式,走向一种真正有“孕育力”的跨文化立场,从而使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不再停留于一种死板僵化的、避免“受孕”的、各居其位的静态分析中,仍需细细思量。
【关键词】内在超越 内向超越 儒学 批判哲学 重构
一、 导语: 理论反击与跨文化问题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一批华裔学人以“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来概括儒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色。“内在超越”这一说法的产生,带有很强的应激性。换句话说,它首先是身处中西文化冲撞旋涡的中国学人,面对西人所持中国观念的冲击,进行的理论自卫、回应与反击。
考察这一问题的“前史”,我们须把目光投向200年前的欧洲。19世纪初,以耶稣会士(Jesuit)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向欧洲传递的大量中国知识终于促成了“学院派汉学”的诞生,1814年底,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国汉学”为代表的学院派汉学的诞生,其大背景是欧洲高等教育界出现“哲学系”,“哲学史”和“欧洲个性”在理念中融合为一的时代。注程艾蓝:《“汉学”:法国之发明?》,收录于杨贞德编:《视域交会中的儒学:近代的发展》(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15 ~42页。如果说,早期耶稣会士从一种准自然神论(或理神论,Deism)的立场出发,在儒学中发现了充足的“自然理性”,进而将孔圣人称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注]1687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等人编译出版的《西文四书直解》,拉丁文标题即为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国哲学家孔子)。耶稣会士翻译儒家经典时表现出很强的理性化倾向,这其实是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的“遗产”——“圣徒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其他经院哲学家思想的结合在基督教的理性和宗教性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完全的和谐”,而“耶稣会士的学术性倾向比宗教神秘性倾向更明显”。参考孟德卫(Mungello E.David)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与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09页。那么,到了19世纪初,欧洲高校哲学系对欧洲个性的构建,不再建基于宗教(基督教)的普适性之上,而是建基于哲学理性的普遍性之上,其结果则是孔子的学说在黑格尔等人那里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一位“实际的世间智者”说出的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注]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2013年重印),第130页。黑格尔认为孔子的学说欠缺超越性、宗教性,身处“大家长的专制政体”下的中国人并不需要一位“最高的存在”,因而中国宗教在黑格尔那里仅属于低级的“自然宗教”,并没有迈进“自由宗教”的门槛。[注]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0 ~133页。黑格尔的以上观点绝非孤鸣绝响,其实是典型欧洲思想的一种代表。故而,这些观点甫一提出,便在西方产生了普遍的应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内在超越说”常常与宗教性问题纠缠在一起。一直以来,儒学和中国文化往往被视为一种世俗文化。比如说,梁漱溟就认为中国人“最淡于宗教”,而浓于伦理。[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0页。在西方,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可以作为一个代表。在《儒教与道教》(1916)一书中,韦伯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超越尘世寄托的伦理,没有介于超俗世上帝所托使命与尘世肉体间的紧张性,没有追求死后天堂的取向,也没有原罪恶根的观念。换句话说,儒学和中国文化是世俗性的,在这一点上它迥异于西方柏拉图主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传统。
至20世纪中叶,黑格尔、韦伯等人的观点在中国学人那里得到了一种反弹性的回应。1958年,主要由唐君毅起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驳斥了黑格尔的观点。这份宣言指出,中国文化虽无西方制度化的宗教,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化只重视伦理道德而缺乏超越性的宗教精神;实际上,中国文化中超越的宗教精神与内在的伦理道德融为一体,所以,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宗教的“外在超越”,而是“既超越又内在”的。之后,牟宗三、唐君毅又在《中国哲学的特质》(1963)、《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6)、《中国哲学十九讲》(1983)、《圆善论》(1984)等著作中反复申说这一层意思,遂使“内在超越说”成为现代新儒家论说儒学和中国文化特性的经典论述。除牟、唐之外,大部分现代新儒家(特别是梁漱溟、熊十力、刘述先、杜维明、李明辉)都专门论述过“内在超越”,主张儒学不同于西方的“外在超越”,而注重内在超越。有些亲近儒学的历史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如,2014年,历史学家余英时出版了《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注]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化和思想在轴心突破之后就形成了重“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的倾向,追求“心与道的合一”这种最高境界。不难看出,“内向超越”的提法和“内在超越”具有一种家族相似性。
无独有偶,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期”(Achsenzeit; the Axial Age)理论,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地区的人类世界(希腊、中东、印度和中国),在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时期,均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而开始探询根本性、超越性、普遍性的问题。轴心时期体现了人类哲学和思想的创造性,具有“哲学突破”的性质。换言之,一种文化只有当它发现了“超越性”,才可能在轴心时期完成向高等文明的转化。1975年,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发表了《古代中国的超越性》[注]Benjamin I.Schwartz, “Transcendence in Ancient China,” Daedalus (spring 1975) 57-68.一文,讨论了儒、道、墨三家在“超越”问题上的看法。史华慈认为,孔子、孟子通过聚焦道德精神生活的主体或内在面,关注伦理的内在源头这一内向超越维度,实现了道德规范的内在化(internalized),由此实现了对于外在社会—政治秩序的超越(孟子尤其如此)。
税法秩序主要由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组成。其中内部秩序指税务机关在履行指责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各类行为规范,主要表现为征税行为。而外部秩序主要指纳税人、相关利益集团乃至地方政府在税收领域的各类行为规范的总称,主要表现为纳税行为。
总之,中、西学人关于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论,并非产生于绝缘、孤立的文化语境,它从一开始便是中西“冲击—回应”思维模式的产物。从另一角度而言,它是跨文化理解与比较研究的结果;不仅此间的问题意识如此,其理论资源与论证话语也是跨文化的。这一“跨文化”特征为传统的儒学研究增添了新的质素,传统儒学蕴含的某些思想潜能借此得以发挥。但是,正如学者们指出的,“今天,在儒家脉络内外,‘天命’与心性的存在与意义,已并非自明之理,而需要概念性、哲学性(而非局限于思想史、学术史)的厘清”。[注]钱永祥:《如何理解儒家的“道德内在说”——以泰勒为对比》,载《“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十九期(2008年1月)。“跨文化”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难,“内在超越说”亦遭遇了来自多个思想阵营的质疑。
二、 问题化的“内在超越说”
“内在超越说”提出后,完全赞同者有之,补苴罅隙者有之,批评质疑者亦不乏其人,而后者往往来自一批表面上非常讲求学理化的学者。今天我们讨论“内在超越说”,似乎首先应该将其问题化(problematize),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观点接受下来。我们首先从中、西学界三种有代表性的质疑观点说起。
第一种质疑的声音来自西方汉学家群体。谢和耐(Jacques Gernet)、安乐哲(Roger T.Ames)、郎宓榭(Michael Lackner)、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等学者认为,“transcendence”这个词有很强的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背景,用它来表述儒学和中国思想,其实是格格不入的,而且很可能会引起概念上的混乱。安乐哲这样说时,主要针对的是史华慈和牟宗三。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认为,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灌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因此,我们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说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Immanent与Transcendent是相反字),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尽管安乐哲明白牟宗三其实很清楚“Immanent”与“Transcendent”的背反性,但他仍然认为牟宗三的这种做法不妥。有意思的是,安乐哲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思想的宗教性!只不过,安乐哲始终强调“诠释孔子思想的三项基本预设假定”,即“内在性”(immanence)与“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对比、“两极性”(polarity)与“二元性”(duality)的对比、“传统性”(traditional)与“历史性”(historical)的对比。在这种比较框架中,标示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是“内在性”、“两极性”和“传统性”,而非“超越性”、“二元性”和“历史性”。倘若以后者来诠释儒学与中国文化,则必然产生圆枘方凿的后果。[注]安乐哲:《中国式的超越,抑或龟龟相驮以至无穷》,收录于第三届新儒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儒学的现代反思》,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后以《中国式的超越和西方文化超越的神学论》为题,收录于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与“超越性”论述相对,安乐哲更偏爱“新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式的解读方案。[注]关于英美汉学研究中的“新实用主义”倾向,可参考拙文:《“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汉语哲学建构——欧美汉学界对于先秦中国思想的不同解读》,《华文文学》2014年第2期,以及罗哲海:《评汉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其次,倘若由于“内在超越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困难,便对其采取一种折衷变化,比如说仅强调“内在性”而不谈“超越性”,那么产生的问题可能更多。在西方汉学家那里,突出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内在性”,并与西方文化的“超越性”进行对比研究,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进路。除了前文提到的安乐哲以外,朱利安是目前致力于此而影响最大的汉学家。在《过程或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ProcèsouCréation:Uneintroductionàlapenséedeslettréschinois, 1989)、《内在之象:〈易经〉的哲学解读》(Figuresdel’immanence:PourunelecturephilosophiqueduYiking,leclassiqueduchangemen, 1993)、《从“存在”到“生活”:中欧思想关键词》(Del’EtreauVivre.Lexiqueeuro-chinoisdelapensée, 2015)等著作中,朱利安反复申说中国哲学的“内在性”与“非超绝性”[注]朱利安区分了“超越”(going beyond)和“超绝”(above and cut off),他认为中国思想有超越性层面,但这种超越并不指向一种绝对的外在性,而指向“内在的绝对性”(absolution of immanence)。,并与欧洲思想的“超绝性”进行对比。“天”在中国思想中并非表征着形而上学的超越维度,而只是表示一种“绝对的内在性”。汉学家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批评朱利安理想化了中国思想的“内在性”,严重忽视了“内在性”与中国中世纪专制政治(despotism)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中国思想之“内在性”严格说来只是西方汉学史上长期形成的一个“神话”或“迷思”(myth)!朱利安和毕来德都未经反思地接受了这一“成见”,从而严重忽视、甚至否认了中国思想中的超越性或批评性维度。他们的争论可谓激烈,亦各有其洞见,然而由于未能将这一成见“问题化”,到头来争论的只是谁能对“内在性”这个未经反思的前提断言做出更恰如其分的评价,终究是盲视的。
又如,余英时主张以“内向超越”说取代宗教意味浓厚的“内在超越”说,这一做法用于描述轴心时期儒家思想的起源是比较恰切的,但是却无法完全涵盖儒学从汉代至宋、明的后续发展。相比“内在超越”说,“内向超越”说的理论概括力来得要弱一些。另外,“内向超越”标示了一种彻底的人本主义向度,而缺失了宗教超越维度。世俗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取向,但世俗化之后的现代人往往丧失对天、地、人的敬畏,更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现代世俗世界之中倡导宗教(再)皈依,就是要向宗教和超验现实敞开自己的心灵,以突破现代社会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内在框架,让自己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注]Charles Taylor, ASecular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68.显然,“内在超越说”所包含的宗教信仰维度更能与泰勒的主张展开跨文化对话。[注]任剑涛教授认为,“内在超越说”并不是传统儒家的本然追求,而且,在现代处境中,没有必要将儒学的宗教性引为儒家价值辩护的方式;儒家强调基于道德信念的秩序安排,具有跟基督教一样的收摄人心、整合社会的作用(见《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宗教信仰、道德信念与秩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此文收录于其《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笔者并不同意其对“内在超越说”与传统儒学关系的判定,但赞赏其基于“现代处境”对传统儒学资源的价值重构。而从比较哲学/神学的视域来看,美国波士顿学派的南乐山(Robert C.Neville)、白诗朗(John Berthrong)透过“过程神学”、“创造性”等概念进行的儒(特别是朱熹代表的理学)、耶对话,是这一跨文化对话的最新成果之一。
第二种质疑“内在超越说”的声音来自分析哲学阵营。冯耀明在《当代新儒家的“超越内在”说》[注]冯耀明:《当代新儒家的“超越内在”说》,载《当代》第84期(1993年4月)。一文中认为,在严谨的“超越性”意涵之下,“超越性”与“内在性”的概念是互相矛盾而对立的,绝不可能存在有所谓“内在的超越”。牟宗三所说“有绝对普遍性,越在每一人每一物之上,而又非感性经验所能及”者,其实只是康德意义上的“超验”,只是就抽象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亦即康德所谓“客观性”的意义上而言之,实非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以“超越”之名来指称“超验”之实,只会导致概念混乱。后来,在《“超越内在”的迷思——从分析哲学观点看当代新儒学》[注]冯耀明:《“超越内在”的迷思——从分析哲学观点看当代新儒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冯氏进一步指出,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的“超越内在”说不仅不够“超越”,甚至也不能说是“内在”。这是因为,熊十力等人的心性论,“背负有本体宇宙论的极沉重的包袱”,而“对于概念或原理言,我们虽可以心理学地说‘内化’或‘内具’(internalized),却不能存有论地说‘内在’”。冯氏进而分别列述南乐山(R.C.Neville)的“创生新说”。李维(M.P.Levine)依据克逊(W.D.Hudson)及史麦特(N.Smart)而构想的“泛神新说”,杜兰特(M.Durrant)和施士(J.Zeis)分别根据格奇(P.T.Geach)的“同一理论”而发展出的“化身新说”和“位格新说”,说明这些比当代新儒家之论说远为深刻而新颖的“超越内在”说,也是难以证立的。
如果说以上两点还只是对“内在超越说”之必要性的有限辩护,那么,借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哲学的思路,充分挖掘并发挥“内在超越说”包含的文化批判潜能,是这一学说打破单一的宗教性/精神性理解模式,实现哲学重构的可能路径。“内在超越说”与儒学的工夫论、境界论息息相关,这使得对于“内在超越说”的理解,常常停留于重视个体身心修养和精神转化的心性论(即所谓“内圣”)领域。这一理解模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内在超越说”其实从一开始就具有丰富的文化批判潜能,而此点却常常被人忽视。
首先,“内在超越说”固然有其因应西方批评的面向,但同时亦有其源于儒学自身思想传统的强大概括力。不管是儒学的哪个流派,都强调主体心性的重要性;不管是哪个时代的儒学,亦多强调主体心性与道德宇宙的沟通、联结。尽管心性与宇宙的连续性在今天已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但“内在超越说”所指涉的“万物一体”观念是儒学史上无法抹煞的一种重要存在。就此而言,“内在超越说”有其阐说立论的有效性。当我们论说传统儒学的“形上学”思想时,“内在超越”尤其是无法避开的一种论述。[注]友人齐义虎提示笔者,“万物一体”强调的是万物之间的连续性,而“超越”一词却标志着一物对另一物的疏离、相胜,这两个词的内在意义指向是迥异的,因此最好延用中国自己传统的术语来进行表述。这一提示很有针对性,然而却有自我封闭化和拒斥跨文化思想对话的嫌疑,故笔者不取。
式(14)可以等效为任意稀疏结构的MMV模型[9],通过求解最小0-范数问题进行并行重构,具体过程可以表示为
法兰克福学派向来以其“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闻名。到20世纪六十年代,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通过在认识论层面上讨论“知识”,将“批判性知识”确认为一种独立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外的,以自我反思和解放(emancipation)为导向的认知与兴趣类型。[注]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undInteres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8).与这种批判理论相关的哲学释义学,在方法论上要求通过一种“理性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来完成对批判性“潜能”的释放。所谓“理性重构”,是指把存在于特定类型现象背后的那些普遍而不可回避的、然而尚未结构化的前提条件,通过明晰化、系统化的理论表述出来。它与智力的深层结构息息相关,其任务不是描述现实中所是的事物(“实然”),而是按照应该是的样子确立现实事物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应然”)。借助这种“重构”,一种前理论的实际知识(know how),可以整合到确定的理论知识(know that)之中。儒学“内在超越说”所包含的文化批判潜能,可以通过“理性重构”而得以充分释放,并参与当下的文化对话。
在郑家栋之前,台湾学者李明辉已经指出牟宗三把transzendent译作“超绝”,而把“超越”留给transzendental;transzendental意指先验,并非“超乎经验”,所以与immanent(内在性)并非矛盾的概念。[注]李明辉:《儒家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年。只不过,李明辉出于护教心态,仅仅揭示出牟宗三未按康德原意来立论,而安乐哲对牟宗三的理解是错误的;所以未能如郑家栋那样继续指陈牟宗三思想中的断裂之处。
郑家栋没有像安乐哲、冯耀明那样明确地点出自己运用的理论方法,但是其与安、冯的前提预设和论证结论是近似的。概括地说,他们的预设和结论都共享了“现代性”境遇的一些典型特征:知识的独立性,存有与价值的分立,主体性的张扬以及宗教信仰的扬弃。然而,从宏观视角来看,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因应的正是现代性的大背景,亦即,现代新儒家是世界范围内“反思现代性”思潮的一部分。相应地,以“现代性”的眼光来分析、评判现代新儒家“内在超越说”的自相矛盾,是从一开始便已注定结局的理论演练。这也让笔者想起史华慈在《中国古代的超越性》一文中所揭示的,先秦儒、道两家的超越主义都表现出保守、反动的(reactionary)面相,然而认为超越性元素就是要对抗静态的、缺乏反思的传统主义观念,那也是错误的。“超越主义”也可能部分表现为对于高等文明的理性化(韦伯意义上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e)倾向的反动。现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儒学“内在超越说”,同样也具有较强的保守(或曰“守成”)主义色彩,此点本不必讳言。
三、 突围路径: “内在超越说”的理论潜能
对于身处现代性语境的普通读者而言,读懂现代新儒家所讲的“内在超越说”,有一个根本的困难,即如何才能理解心性论与宇宙论的合体问题。或者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的话,如何才能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个中关键之处在于,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可以在人的道德性体、心体与宇宙的性体、心体之间建立一体必然之联系。而此点何以可能?即便对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专家学者而言,理解此点也属不易。例如,前引钱永祥论文即称,“阅读牟宗三著作的过程中,笔者感到最困难的地方,即在于确定他心目中此处的联系(按,即人之道德性体、心体与宇宙的性体、心体之间的“联系”),应该如何理解”。[注]钱永祥:《如何理解儒家的“道德内在说”——以泰勒为对比》,载《“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十九期(2008年1月),第7页脚注11。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最终落脚点在“形上学”,而钱永祥“道德内在说”所讲“道德的实践之可能性与条件”,在整体思路上似乎属于牟氏所谓的“道德底形上学”(康德术语)范围,因此是歧出的。“万物一体之仁”是钱氏“感到最困难的地方”,认为“道德内在说涵蕴着什么样的形上学结论”,“陈义太高”,“是很棘手(但也有趣)的问题”,最终存而不论。这似乎是一个概念式“论证”永远无法自行抵达的领域,而只能诉诸“体证”或所谓“智的直觉”。“内在超越说”的精微之处,有点拒斥概念式论证,而更多指向儒学的工夫论、境界论,有自我神秘化之嫌,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对其的理解与诠释。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如果说“内在超越说”之提出,主要是要反驳黑格尔、韦伯等西方学者对儒学和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的批评,那么,现代新儒家学者理应依循批评者所使用的“内在”、“超越”之定义来作出反驳;若随意变换批评者所使用的定义,则难有反驳可言。但事实是,西文严格定义中的“既超越又内在”必不能证立,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并未严格依循康德等西方哲人的定义,难免有偷换概念之嫌。既如此,以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回应西方的“外在超越”,便成了鸡同鸭讲,无法构成真正的比较研究和对话,而只是一场虚拟的自说自话而已。用安乐哲的话来说,“超越性”话语是毫无生气的。就此而言,提出“内在超越说”其实甚无必要。
然而,“内在超越说”因此便是无效的累赘话语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平衡施肥、不同的钾肥施用量如何影响化肥的吸收利用,并对作物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在参会人员切身观察试验田水稻生长情况后,唐湘如教授在技术交流会上为大家讲解了平衡施肥技术及钾肥的相关知识。据唐教授介绍,目前我国氮肥、磷肥用量偏高,氮肥的使用量约占全世界的30%,而钾肥用量偏少。中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平均利用率仅为40%左右。不合理施用化肥导致的氮、磷过剩,不仅加大了化肥的流失,而且流入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其负荷已远超过工业点源所占的负荷。
第三种质疑来自现代新儒家内部,以及立场接近现代新儒家的学者。同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主张儒学是一种“道德性的人文主义”,“仁”(自觉的精神状态)引发“无限要求”,由此指向“忠”与“恕”。他在《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一书中主张儒家持一种“道德内在说”,而不主张宗教意义上的“超越”说。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前,徐复观曾向主笔唐君毅提出过两点修正意见,其中一条便涉及这份宣言中透露出的过浓的宗教意识:唐君毅在原稿中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宗教意义,而徐复观则认为,中国文化虽原来也有宗教性,也不反宗教,然而从春秋时代起中国文化就逐渐从宗教中脱出。徐复观修改了这一部分的原稿,但唐君毅并没有接受这个修正建议。余英时先生主张以“内向超越”而非“内在超越”来标示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特征,在理论初衷上与徐复观相同。[注]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载《二十一世纪评论》第58期(2000年4月号)。或参考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二章。针对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经由实体化的“心体”走向独断论,李泽厚先生亦曾撰文,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超越性,主张以“情本体”来取代超越性。[注]李泽厚:《当代新儒学论衡》“前言”,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值得注意的是,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在质疑“内在超越说”时,除了遵循“transcendence”一词在西文中的严格用法外,还往往沿袭早期耶稣会士的做法,对轴心期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与汉代及汉代之后的新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做出严格区分。在儒学发展史上,汉代儒学将“宇宙论”纳入自身之中,宋明理学、心学则强化了儒学的“本体论”话语。从个体修养论(工夫论、境界论)的角度看,后世儒家强调人与宇宙的一体化,比如张载的“民胞物与”说、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都是这样。尤其从生命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 for life)的立场来说,儒学强调个体生命在世的德性修养(“存神尽性”),可以在个体生命终散之后“利天下之生”。王夫之说:“是故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自我尽之,生而存者,德存于我;自我尽之,化而往者,德归于天地。德归于天地,而清者既于我而扩充,则有所裨益,而无所吝留。”(《周易外传·系辞下传》)他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终极关怀”意识。冯友兰说这是“事天”的“天地境界”,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精神转化/升华”(spiritual transformation)。而且,它首先是个体工夫修养领域的精神体验;至于是不是表现为对习俗的批判、超越,反而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是大部分现代新儒家(不包括余英时)界定“内在超越”时的核心意义。由于安乐哲等人在质疑“内在超越说”时主要依从轴心时期的原始儒学理念,宋明儒家和现代新儒家发展和强化了的儒学精神性维度并不被看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对儒学的理解是一种“以源代流”的简化主义见解。另一方面,由于对“transcendence”意涵的理解是提纯后的结果(所谓“严格的用法”),他们将西方思想与“transcendence”划等号的做法也是极为偏狭的。总之,安乐哲等人在对中、西思想传统双重简化的前提下进行中、西思想的比照研究,亦是问题重重的。
正在气头上,镇长来了电话。镇长说,滑头,你在骂我吧。我晓得你说我消息不灵通,是吃屎的。把茶场给了牛皮糖,是个祸兜子。
治疗后联合组收缩压及舒张压分别为109.5±11.3mm Hg和72.5±8.9mm Hg,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的130.1±11.82mm Hg和86.7±7.6mm Hg(P<0.05);联合组心率为84.7±11.7次/分钟,优于对照组的115.9±12.2次/分钟(P<0.05)。
在冯耀明看来,主体心性是传统儒学的根本。而熊十力等人所持论的这种“宇宙心灵”吞没了“个体心灵”,它的“实体性”之义淹没了“主体性”之义,它带来的“气质命定论”将会使道德觉悟或自由意志成为多余之事,使良知或明觉在生命转化中扮演无可奈何的角色。而分析哲学便如同“奥卡姆的剃刀”(Occam’s Razor),本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If not necessary, not by entity.)的理念,可以去除跟儒学心性论捆绑在一起的宇宙实体论残余,恢复儒学的本真原貌。然而正如前述,心性论与宇宙论的合体绝非现代新儒家的向壁虚构,汉代以来的儒学理论建构多有致力于此者。2014年陈来先生出版的《仁学本体论》[注]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延续了宋、明儒直至现代新儒家的思路(所谓“接着讲”),以“仁体”打通原始儒学、宋明理学与心学、现代新儒学,仍以“形上学”建构为旨归,是统心性论和宇宙论于一炉的最新尝试。分析哲学是一种很好的理论分析工具,但它具有很强的反本质主义、反形上学倾向。当下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盛行的是分析哲学的理论方法,倘若不加分析地搬用分析哲学来处置、裁断传统儒学的所有问题,难免产生妄裁历史的反历史主义后果。
大陆儒学学者郑家栋在《“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注]郑家栋:《“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一文中,尝试从语词概念的厘清切入来讨论“超越”与“内在超越”的问题:康德将之前混用的transcendental与transcendent做了明确分辨,完全在经验范围之外的才是“超越”(transcendent),而“先验”(transcendental)是指作为必要的条件以构成经验之基础的那些先验因素言。与通常用法不同,牟宗三把transcendent译作“超绝”,把transcendental译作“超越”,因为他认为transcendent与经验界完全隔离,一去不返,而transcendental则不能离开经验而反过来驾驭经验。牟宗三主张,在儒学传统中,宇宙万物都建基于一普遍的道德实体,而此一普遍的道德实体同时亦即是人的本体——即无限智心/仁体/智的直觉——所以是既超越又内在的。这样,牟宗三把神对于人而言之存有意义上的超越性扭转为人自身的超越祈向及其潜能。郑家栋认为,儒家内圣之学包括两条线索:以《中庸》、《易传》为代表的宇宙本体论的系统,以及由子思、孟子一系发展而来的心性论的系统。在今天有关儒家思想“内在”与“超越”之关系的讨论中,人们常常是从前一线索提出问题,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到后一线索去说明或回答问题;亦即从认定“天命”、“天道”的超越性内涵始,而以肯定吾人的道德心性具有自我超越的内在祈向和无限潜能终。这样一种思路犯了“存有”与“价值”相混淆的谬误。而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可说是典型地体现了上述理路。[注]无独有偶,学人陈振崑在评论唐君毅的“天德流行”论时,亦指出,虽然唐君毅有意要开展一个“乾坤并建”,“天命”与“性命”并存之“既超越又内在”的天道观(这在天人关系的阐发上无疑具备了高度的价值﹐启发了现代人融合宗教精神与人文价值的超越向度),但却只成就了一种内在于人的主体的超越性。虽然他在理想上挺立了人的孤峭的道德主体性,却同时遗忘了天道涵藏万有、生生不息之动力的开显。见陈振崑:《论天德流行的超越性与内在性——唐君毅先生的天德流行论初探》,载《哲学与文化》第26卷第8期(1999年8月)。
关于儒学包含的批判性潜能,汉语学界已有的论述,多强调传统儒学以心性之说确立“道统”以与“政统”抗衡的一面。然而,一方面,这种论述往往停留于“实际知识”的层面,未能立足于理性重构,其哲学建构性尚不充分。另一方面,这种论述亦有意无意流露出儒家以道统自任本身具有的浓厚保守气息,儒学由此便仿佛自异于现代社会之外,而缺乏一种思想/文化建构的参与意识。无疑,开掘儒学“内在超越说”的文化批判潜能,需要一种更为宏大而纵深的视野,以及一种更具普遍主义色彩的视角。
[本刊讯] 为满足广东省护理人员刊登科技论文的需求,《上海护理》编辑部将于2012年6月编辑出版《上海护理》增刊1。敬请广大作者与读者予以关注。咨询电话:62671836。
我们不妨同时将目光转向域外的中国哲学研究界。在诠释儒学和中国古典文化时,首先将“超越性”与文化批判意识明确关联起来的,是汉学家史华慈。他曾经指出,轴心时期的中国思想家认识到,在规范性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某种可悲的鸿沟。而在这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与实际状况之间的断裂中,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超越因素;“天”就是关心儒学救赎使命的超越的意志。换言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与张力本身就蕴含了理想对于现实的超越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深度批判意识与反思性;而这种超越性和批判意识的源头,则是“天命的内在化”。历史学者张灏以“超越的原人意识”为关键词来概括轴心时期思想创新的根本特征,而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超越的心灵秩序与现实政教合一的“宇宙王权”(cosmological kingship)的紧张性,以及其中蕴含的突破契机。[注]张灏:《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载《二十一世纪评论》第58期(2000年4月号)。
坝体稳定泄流与形成冲切条件泄流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泄流渠的稳定问题,后者要对渠道形成溯源冲刷,而前者则要形成稳定的渠道,具体区别参见表3。
而能够将轴心时期儒家伦理学与批判哲学结合起来的最佳范例,笔者以为应首推德国汉学家罗哲海(Heiner Roetz)。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注]Heiner Roetz, DiechinesischeEthikderAchsenzeit.EineRekonstruktiondesDurchbruchszupostkonventionellemDenken. Frankfurt/M.: Suhrkamp, 1992. 英译:ConfucianEthicsoftheAxialAge,AReconstructionundertheAspectoftheBreakthroughtowardPostconventionalThink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中译见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罗哲海将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先秦哲学、伦理学置于传统习俗伦理崩溃的时代背景中,强调它们是应对社会和文化危机的产物:传统的确定性(特别是伦理)已经土崩瓦解,这是中国道德哲学得以形成的根本问题语境。先秦诸子各家的思想建构,都处于“具有世界史向度的早期启蒙新纪元”之中;与之前相比,它们在思想上实现的“重大突破性进展”表现在:“通过反思和超越性而不再为实体性和生命的局限性所囿,神话意识形态为理性所战胜,个人主体的发现,向历来接受之一切事物加以质疑,在两难困境中慎重思索,以及历史意识的发展等。”[注]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第34、274页。在罗哲海看来,就孔子、孟子的大体而言,儒家并没有像“前儒家文献”那样强烈地从超越性的上帝、天那里为伦理学寻求终极凭据,亦即,儒家的“道”是由人自行主动培养的,而非通过任何天国(宗教论述)或本体论(形上学话语)的规范来预先定位。[注]这也是罗哲海批评杜维明的原因之一,参考Heiner Roetz, “Confucianism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ligion, and Secularization: Questions to Tu Weiming,” Dao 7(2008): 367-380.然而,儒家伦理学却同样获得了“后习俗”(post-conventional)层次的批判立场和对于现世习俗的超越。孟子以“人心中存在道德发端”的理论,以及他的道德现象学把握住了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关键:“人类具有不依赖传统,仅靠自身而发展出道德的可能性。”[注]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第34、274页。而且,孟子由此还获得了一个激烈批评暴政的立足点——执政者如果没有从人类具有道德潜能的角度来运作政治,那么就是“罔民”、“率兽而食人”。
流通渠道的末端多是C类以下传统小店。对百雀羚新品来说,这种小终端既不能有效传播展示百雀羚本草属性的品牌形象,又不能与目标消费群实现紧密良好的接触,因此,传统流通渠道已成为百雀羚必须突破的一道瓶颈。
罗哲海对儒学文化批判潜能的重构,是借助“轴心时期”理论、“后习俗”理论的双重视野展开的。而其所以能如此申论,则与其领受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有着密切关联。[注]参考拙文:《“批判理论”如何穿越孟子伦理学——罗哲海(Heiner Roetz)的儒家伦理重构》,《国学学刊》2014年第3期。他认为:“‘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理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而加以充分利用。”[注]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第7页。另可参考:Heiner Roetz, Gibt es ein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in InformationPhilosophie, 30. Jg., Heft 2, Mai 2002, p. 31.罗哲海将这种诠释学称为“批判性现代重构”,并与安乐哲等美国实用主义汉学家的“复辟/复原论”自觉划清了界限。值得注意的是,罗哲海的论述有意避开了儒学“内在超越说”的本体论维度,而着重发挥其批判性潜能,从而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传统构成了深层次对话。在让儒学(尤其是儒家伦理学)参与当代前沿思想对话的维度上,罗哲海做出了值得赞赏的努力。
罗哲海的弟子、汉学家何乏笔(Fabian Heubel)也认为,现代新儒家的“内在超越说”富有发展潜力:“对批判理论而言,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牵涉到批判如何可能的问题。”所以,由“即内在即超越”的角度有助于理解当代批判思想的发展方向。[注]何乏笔(Fabian Heubel):《跨文化批判与中国现代性之哲学反思》,《文化研究》第八期(2009年春季号)。虽然新儒家哲学与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的鸿沟难以彻底跨越,跨文化研究的难度不容低估,但是,像“内在超越说”这样的“混血”命题,超越了朱利安式的相互绝缘的对比研究模式,体现了一种真正有“孕育力”(fertility; fécondité)的跨文化立场,仍是值得肯定的思想进路。
四、 小 结
综上所述,儒学“内在超越说”合心性论与宇宙论为一炉,既蕴涵了宗教性诠释的可能,又包容了文化批判性的丰富潜能。前者指向内在的工夫论、境界论等个体修养论内容,后者则指向外在的政治—文化批判性发挥。前者标示了儒学的宗教性、精神性,而后者则标示了儒学的批判性。
牟宗三、唐君毅所讲的宇宙论意义上的超越性,是接着宋明儒学而讲;而其对“内在”之强调,则与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哲学合拍。遗憾的并不是牟、唐沿用了宋明儒的宇宙论,而是他们并没有在批判哲学意义上张扬儒学的外在批判性,最终极易滑向那种单纯突出心性儒学的进路。与之相关,蒋庆等偏爱今文经学的学人,通过开掘和复兴所谓“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儒学面向,批评港台新儒家只讲心性,不讲政治,只讲内圣,不讲外王。然而,蒋庆的这种论述其实窄化(甚至僵化)了儒学批判性的全部可能。
儒学“内在超越说”是一个文化“混血”的哲学命题,这标示着中国古典哲学的当代诠释早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如何经由批判性的现代重构,超越那种相互绝缘的对比研究模式,走向一种真正有“孕育力”的跨文化立场,从而使中、外文化不再停留于一种死板僵化的、避免“受孕”的、各居其位的静态分析中,仍需细细思量。
Breakthrough,orMyth? — ACross-culturalInvestigationandCriticalReconstructiononNewConfucian’sTheoryof“ImmanentTranscendence”
Han Zhenhua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Immanent transcendence” is a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new Confucianism in the cross-cultural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owever, it has been challenged from the new pragmatism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camp since the 1990s. Roger T.Ames, Fung Yiu-ming, Zheng Jiadong and other scholars clarified the unprovable nature of “immanent transcendence” by analyzing the incompatibility of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at the academic level. Compared with “transcendence”, they prefer the “immanence” (or inwardness, intern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elieve that the “transcendence” discourse is outdated and “inanimate.”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all things” (万物一体) and “Ren-ti” (仁体) actually referred to by “immanent transcendence” is the real existence in the sens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realm theory (境界论), the modernity situation or the knowledge type (l’épistémè) of modernity in which contemporary skeptics coexist makes them unable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existence” and “value,” and meanwhile more inclined to deconstruct the validity of “immanent transcendence.” Although in such a problematized context, the theory of “immanent transcendence” could make reference to the ideas of Cr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refore its rich potential of cultural criticism could be realized. This is a possible approach to break the only religious/spiritual mode of understanding, and achieve its rebirth with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ce” in Confucianism is a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of a cultural “hybri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has been a cross-cultural work. Today, how to overcome the contrasting research mode of mutual insulation through critical modern reconstruction, and move towards a cross-cultural position that truly has more fertility so that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could avoid from staying infertile and isolated statically with each other, deserve further reflection.
Keywords: immanent transcendence; inward transcendence; Confucianism; critical philosophy; re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韩振华,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90年以来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进展及理论回应”(项目批准号:16ZXB00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船山学的跨文化发展与当代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7BZX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16JT001、2016QZ004)。
[责任编辑晓诚]
标签:儒学论文; 儒家论文; 越说论文; 哲学论文; 中国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990年以来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进展及理论回应"; (16ZXB00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船山学的跨文化发展与当代建构研究"; (项目批准号:17BZX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6JT001; 2016QZ004)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