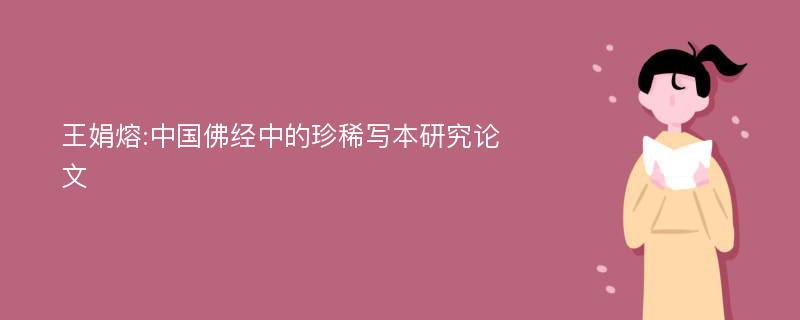
摘要:佛教的弘法活动对经书产生了极大需求,佛经写本是满足这种需求的一种方式。写本的抄写者或者组织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或者亲近佛教的优婆塞、优婆夷。他们抄写佛经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自身断三毒、求解脱、证法身;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末法时期的众生有法典可循。在留存的佛教写本中,一些珍稀写本与同时代的普通写本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如以鲜血抄写的血经、在石头上刻写的石经、富贵的金经等。
关键词:佛教;写本;血经;石经;金经
佛教发源于印度,大约于两汉之交传入我国。由于佛教的教理与中国本土文化儒家、道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所以很快被接受并广泛传播。经过两千多年的融合发展,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谈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避开佛教,而佛教的传播,首先需要对佛教三藏进行翻译和抄写。宋代之前,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佛教的文献经典主要以写本形式体现,依靠手书流通。宋代以后,中国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刷佛教文献经典,刻本形式居于主导地位。对佛教而言,即使在刻本阶段,刻本印刷的佛教经典取代了写本的地位,但写本的佛教典籍并没有消失,即使现代社会佛教的写本仍然存在。在刻本时代之所以存在大量写本,是因为此时人们抄写的目的是积功累德、祈福、供养等,而流通的作用是其次的。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几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佛教写本。
[10]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11,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72.
资源总量有限、环境容量有限,而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和生态产品都是有价的,通过市场主体去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状态,有利于调动很多社会团体参与保护和利用。参照资源价格,科学合理地确定计量其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做到“使用资源有偿、损害生态赔偿、作出贡献补偿”。建议开展京津冀生态产品市场机制试点工作。
一、虔诚的血经
血经是佛教写本书籍的特色之一。血经,顾名思义就是以鲜血为墨所抄写的经书。佛经中有“剥皮为纸,以血为墨,折骨为笔”[1]的说法。抄写血经所使用的血是人体之血,且在人体采血的部位并不是随意的,而是非常讲究的。一般来说,采血的部位是人体最敏感的指尖和舌端。刺舌和刺手所得的血不能直接用于书写,否则会导致发黑结块并迅速脱落。所以,从人体采的血还要加入矿物质搅拌后才能用于书写。
血经的出现是有佛教义理做支撑的。佛教认为,人生是诸行无常,一切皆苦。人们为了离苦得乐,就要修行。造成烦恼痛苦的原因是我执和法执,它们是万恶之源,所以修行首先是祛除我执和法执。其中,祛除我执的方法就是祛除“贪嗔痴”三毒,贪嗔痴是表面现象,它的背后是我执,贪嗔痴是“我贪”“我嗔”“我痴”,一切的人我是非、党同伐异都是因我而起。贪是万恶之首,由于贪人们没有得到的想得到,得到的怕失去,得到了还嫌少。贪心使人们整天贪得无厌、患得患失;嗔指的是,如果喜欢的东西失去了,或想得到的得不到,就会产生嗔恨之心,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所谓痴,就是在贪心和嗔心的作用下人们会利令智昏,从而产生愚痴之心。“贪嗔痴”三毒是人们轮转生死的根本,它创造了八苦、八难,它制造了人生无尽的烦恼。如果能去除贪嗔痴,人们也就放下了我执,离真如本性近了一步。而减轻乃至于祛除三毒之一的贪,唯一的方法就是布施,布施就是放下。贪与布施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贪是进,布施是出,两者是相克的,所以用布施对治贪欲。布施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精神布施就是放下自己所执着的思想,不固执己见;物质布施包括两方面,一是要减轻对依报世界色声香味触法的贪婪,二是要放下对色身的执着。佛教认为,这个色身只是假我,正如《坛经》中所说“五蕴幻身,幻何究竟?”庄子也说“生者寄也,死者归也。”而色身中血液对人的重要性无可比拟,如果能将血液都布施出去,还有什么不能布施呢?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呢?所以虔诚的修行者为了对治贪欲、除三毒、祛我执、证悟真如自性,纷纷抄写血经。
血经抄写过程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能成功抄写血经的人,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视死如归的精神,非虔诚的修行者所不能为。血经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物,由于其在抄写过程中有不健康不卫生等弊端,在当今社会并不提倡。但是,血经制作背后的精神是值得弘扬的,只就这种精神而言,如果普通人能拥有,何事不成?何功不就?我国自古以来有很多血经,但由于年代久远及未妥善保存而遗失或损毁的居多。所以血经极其珍贵,是佛经乃至中华传统文化中稀释珍宝,它所承载的精神力量是普通写本无法比拟的。
庐山博物馆现珍藏着一部佛教血经——《华严经》,共81卷,近200万字。该血经的抄写者是清代的普超和尚,他在庐山刺指取血,历时十五个春秋。当一只手指挤不出血珠时,又刺另一手指,以非凡的毅力抄完了《华严经》。于完工后的第二年,由于出血太多,身体亏损太大,年仅45岁的普超和尚就圆寂了。普超用血抄写的《华严经》,字迹呈暗褐色,小楷体,字径半寸有余,笔画端正圆润,一丝不苟,颇见功力。这部血经尾页有不少名人题词,如近代著名学者康有为、梁启超、罗家伦等。康有为题:“尊之,敬之,护之,保之。”梁启超题:“《华严经》洋洋乎81卷,寻常僧俗能读终卷者百不一二,况乃书写,又况乃攒一指之血写数百万言者哉!实未闻焉!”罗家伦题:“刺血写经,成此巨帙,非有极伟大之热忱,曷克臻化。”[2]另外,还有珍藏于江苏苏州西园戒幢律寺,由元代善继和尚抄写的血经;珍藏于安徽九华山历史博物馆,由明代无瑕禅师抄写的血经。
二、传世的石经
根据工程相互关系,采用ABAQUS计算软件对施工阶段进行模拟,主要分析隧道施工对群桩基础的变形影响,应力应变的本构理论采用Mohr-Coulomb 线弹塑性模型。模型中根据勘察地层设置隧道周边土层,各个部分的材料参数见表2。其中考虑衬砌连接的不连续性,将衬砌的弹性模量按0.15 进行折减,桥台以上结构作为荷载计算。几何模型如图2所示。
为什么在石头上刻经文?从佛教上看,佛家认为天地之间一切人事物都是无主宰、非自然的,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生住异灭的,对人而言都是生老病死的,即有生必有灭,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合会终别离,有命咸归死。这个道理对佛教及其经典也不例外,佛教及其经典也面临生住异灭,佛教及其经典也不是永恒不灭,也终有湮灭的时候。释迦牟尼将佛法的存在分为三个阶段,即正法时代、像法时代和末法时代,正法五百年(也有说一千年),释迦牟尼佛入灭后五百年为正法时期,此时有佛法存在,人们依教修行容易证果;像法时代一千年,有佛法存在,此时人们纷纷建庙、造塔、造佛像,供养诸佛的形像,只是向外求没有反躬自问,修行不易成功;末法时代一万年,人们诽谤佛法,佛法即将消失,佛教经典难觅,修行的人极少且不会证果。末法时代以后佛法完全消失。根据这个理论,人们担心末法时代及其以后,“法难”出现时,佛典毁逸,佛法无传,人们无法可循,为了度末法时代即以后的众生,使他们在法灭后修行时有佛典可依,就开始刊刻石经,所以石经不是为当时的人们修学佛法用的。古人认为,无论是印刷或者抄写在纸上的经典都是会损毁并消失的,而镌刻在坚硬的岩石上的佛教经典能长期保存。为了经典能流传更长时间,人们将经典刻在碑版上、摩崖上,宝幢上,形成一道中国佛教文化传播的亮丽风景——石经。当然,刻写石经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积功累德,为了自己的修行,为了积累修行的资粮,这一点与抄写血经的原因一致。
为了存放如此大量刊刻了佛经的石板,僧人们陆续在石经山上开凿了九个石洞用于存放石经版,其中雷音洞是最早开凿的,为开放式,又称华严堂、石经堂,洞内宽广如殿,四壁镶嵌146块经版都是静琬早期所刻。其余八个石洞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炉熔铁锢封,以待末法时代开启充为经本之用。另外还有部分石经藏于云居寺西南压经塔之地穴中。
为什么房山会产生如此宏伟的石经?从当地的自然环境看,当地盛产大理石,具备刊刻石经所需的大量石材,静琬和弟子们可以就地取材,能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因开采了大量石料,当地的山因之易名为石经山。从时代背景看,中国南北朝时期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灭佛事件,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诛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废除全国的佛家,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北周武帝宇文邕,下诏书禁佛,毁灭佛教经书以及佛像,并下令让佛教僧人还俗。这两次灭佛事件给佛教以沉痛的打击,佛教徒们对佛法的延续产生深深的忧患意识。加之,当时还流行着释迦牟尼出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77)的说法,如果据此推算,则末法时代已经来临,佛法将有灭亡的危险。所以人们积极谋划如何更好地保存佛教经典。正如静琬在题记中所示,他发愿刊刻这部石经,不是为了当时的佛经传播,而是为了供末法时代,佛法难觅时充经本之用。
“为了工作,我有愧于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为了事业,我忽略了亲朋的内心感受。孩子在读书和备考期间,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常常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丈夫患上肝病好几年了,我却一拖再拖。现在,孩子考上大学了,正好可以携带丈夫一起检查治疗。可是,此时学校正准备迎接省级标准化学校验收,我不能就这样丢下学校走了。谁叫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呢?我只能泪眼晶莹地目送丈夫和孩子上了火车……”这是范金英日记中的一段话。
图1 房山石经
图2 雷音洞
我国现存的佛教石经很多,但具代表性首推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它历时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亦称房山石经。房山石经的发起人是隋代的静琬,他是南岳慧思的弟子,慧思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第二代祖师,静琬秉承师傅的意愿并发愿刊刻石经。静琬在隋炀帝时开始刊刻,曾得到隋炀帝皇后的资助,他一辈子没有下山就在洞里刻石经。静琬圆寂后,由其徒弟们继续他的刻经之业,就这样经隋、唐、五代、辽等历朝陆续刊刻,直到明代,绵延一千多年。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人力物力,对房山石经拓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研究,并已正式出版。仅就现在发掘拓印的经碑,经整理、查对、拼接、分类编目,初步统计,总刻佛经1125部,3480余卷,14510余块。[3]其中4196块隋唐石经为国之重宝。
石经是刻于碑版、摩崖、宝幢上的经典。通俗地讲,就是以坚硬的岩石为纸,以刻刀为笔,在石头上“抄写”经书。我国刻写石经的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始于汉平帝元始元年(西元1),王莽命甄丰摹古文《周易》《尚书》《诗》《左传》于石,此为石经之始。以后各朝代都有石经留存,我国现存的石经有: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房山石经等,石经所刻写的经典涵盖儒释道三家。我国留存有大量的佛家石经,石经虽然不是佛家所独有,但从规模和质量看,佛家把石经使用到了极致。
房山石经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之石刻大藏经,是世界文化宝库的一大奇观,被誉为“北京的敦煌”,叶曼先生称其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房山石经中辽金时期的刻本是依据已经亡佚的《契丹藏》为底本刊刻,对研究《契丹藏》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房山石经中保存了一批历代诸藏都没有收录的绝世孤本经。另外,房山石经中还保存了不同时期的一些伪经。现在,这些石经,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房山石经对研究我国传统文化、金石书法、政治经济、人文艺术等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
三、富贵的金经
金经就是用金银粉抄写佛教经典。抄写人或用金粉,或用银粉,或两者都用。金粉或者银粉并不能直接用来书写,而是与粘合剂调和后形成金泥或者银泥才能用于书写。写经完毕,为使金银粉黏附力更好而不致成块脱落,还要用工具涂砑,让金银粉充分“涂”在纸上,并且光亮好似“鎏金”一般。银粉容易氧化变色,时间既久,不如金粉经书那样鲜艳如新。金银粉合用抄写的佛经,往往遇到“佛”字用金粉,遇到“菩萨”名用银粉,以示不同。这种金经装帧奢华,极其漂亮,但其成本却很昂贵,不是普通人能够承担的,只有达官显贵且是虔诚的佛教徒才能完成此事。我国历代用金银粉写经的不少,史料中的记载很多,但金银书存世的并不多见。[4]
甘肃张掖大佛寺的藏经殿藏有一部明代的佛经——《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大明三藏圣教北藏》集经、律、论三部,共收佛经1621部,6361卷,极其珍贵,是大佛寺的镇寺之宝,被喻为“佛学百科全书”。而其中,以《大明三藏圣教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用金、银粉书写在昂贵的绀青纸上的金经,简称张掖金经,则是珍宝中的珍宝,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认为国宝。《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它汇集了般若系16种经典,共600卷,唐玄奘译。作为大乘佛教基础理论,此经被尊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唐代曾奉被为“镇国之典”,后世诸类大藏经也多以此经为首部,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经籍之一。张掖金经的发起人是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钦差太监王贵,他对佛教很感兴趣,出资组织地方的书画名士抄写金经。金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长达二十多万字,以千字文排序,现存558卷(279本),并于每函卷首扉页置精美的金线描曼荼罗画一幅。王贵不惜巨资书写这部现今国内保存的惟一明代金银粉经,原因是“上以图报列圣宠赐之洪恩,下以效资宗祖栽培之厚德,更计显考昭勇将军王公、显妣吴氏太淑人,由乎善利泛慈航,登彼岸于菩提,次及己躬雪衍,尤增富寿于景运。”[5]意思是说:一是为皇帝歌功颂德,“上以图报列圣庞赐之洪恩,下以效资宗祖栽培之厚德”;二是超度已故父母的亡灵,使之“泛慈航登彼岸”;三是祈求佛祖护佑自己久病之身早日康复。
图3 张掖大佛寺镇寺之宝金银书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佛经的写本中,除了血经、石经、金经外,还有绣经等。绣经就是绣女以丝线为墨,以绣针为笔,以布为纸,所绣写的经书。所有这些特色鲜明的写本方式,都是以佛教的教义为理论依据的。在所有佛经中都有关于佛经抄写功德的论述,如《金刚经》中说道“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6]楞严经中关于书写楞严咒的功德描述“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7]这些经文都是对抄写佛经者功德的描述,所以,为了追求功德,即使在刻本阶段,写本佛经仍然存在。在此基础上,如果能舍弃自己的财富,身体的血液,不辞辛苦,坚忍不拔地造就血经、石经、金经、绣经等,则功德更是不可言说。有此理论依据,所以为了积功累德,为了弘扬佛法,为了自己的修行,为了离苦得乐,为了度众生,为了供养,为了祈福,为了超度等等,修行者们便前赴后继、不计成本、不惜生命地进行着各种方式的写经、刻经。他们这种为了信念舍弃一切,甚至生命的精神是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而留存的经书写本不仅是佛教的重要文物,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参考文献:
[1]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卷上[M] .大正藏·宝积涅槃部(第12卷)No.0382.
[2] 孙丽娟,傅加令.血经[J] .佛教文化,2001(10):68-69.
[3]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 任继愈.中国版本文化丛书 佛经版本[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 王康,李淑芳.张掖大佛寺藏金银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降魔曼荼罗[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4):24-31.
[6]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M] .大正藏·般若部(第8卷)No.0235.
[7] 唐般剌蜜帝.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M] .大正藏·密教部(第19卷)No.0945.
A Research on the Rare Manuscript 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WANG Juanrong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Beijing 102600,China)
Abstract:The Buddhist activities of Buddhism have created a great demand for scriptures,and manuscripts are a way to satisfy this demand.The scribes or organizers of the essays are devout Buddhists or Upāsaka and Upasika who are close to Buddhism.There are two main purposes of copying the Buddhist scriptures,one is cutting off three poisons for themselves,seeking extrication and proving the dharma body,and the other is hoping that therewill have a code can be followed by sentient beings in the last dharma period through their efforts.In the remaining Buddhist manuscripts,some rare ones have distinctive features compared with the ordinary writings of the same period,such as For example,the blood sutra copied in blood,the stone sutra carved in stone,the rich golden sutra and so on.
Key words:Buddhism;manuscript;blood sutra;stone sutra;golden sutra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626(2019)08-0047-04
收稿日期:2019-06-10
(责任编辑:周宇)
标签:石经论文; 佛教论文; 写本论文; 房山论文; 佛经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论文; 北京印刷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