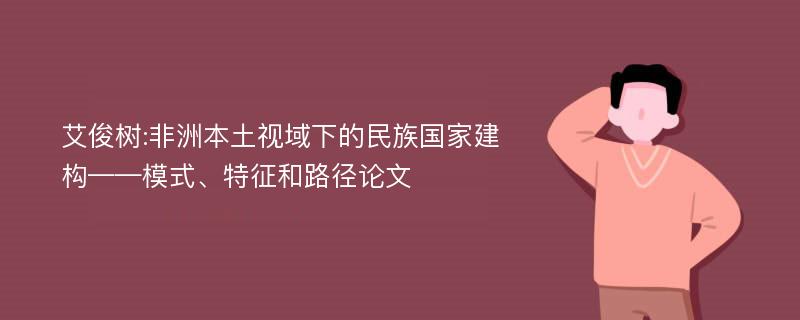
区域研究
[内容摘要]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与实践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演进关系。鉴于现有民族国家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还须从其自身历史中寻求理论依据。从文明史观来看,非洲民族国家建构整体上呈现为“先国家再民族”模式和“后发型”、“反复性”、“外部干预”三种基本特征。加纳作为当前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范例,其民族国家建构进程既符合一般性的非洲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和特征,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为本土文明与外来化文明两种体系在现代国家框架内的冲突斗争,并在民主化下走向一条扬弃二元对立的新路径。加纳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对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非洲民族国家 文明史观 加纳
随着20世纪中期去殖民化运动的全面开展,非洲大陆涌现了数十个新兴国家。自此,民族国家建构就成为非洲[注]本文中的非洲均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主题。然而,数十年间,非洲国家普遍出现了政治动荡、经济发展滞后和内外冲突不断等各种问题,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长期陷入僵局。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第三波民主化”在非洲的扩散,非洲政治发展和民族国家建构曾再度引发世界的广泛关注,但在“民主化”过程中又很快出现了武装冲突加剧、地方民族主义、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合流、威权主义合法化、国家外债攀升和市场调控失灵等新问题。至21世纪初,非洲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的前景又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这导致西方对非洲未来命运的看法充满悲观情绪,国际上也广泛出现了一种失败国家的论调。[注]失败国家一词最早由赫尔曼和拉特纳于1992年提出。它最初用于指代一些出现政治衰退、经济崩溃和内乱的发展中国家,并给这些国家贴上“威胁国际安全”的标签。参见Gerald B.Helman, S.R.Ratner, “Saving Failed States,” ForeignPolicy, Vol.71, No.89, 1992, pp.3~20。随着“9·11”事件后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推进,学界进一步从国家制度、社会等内在层面和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等外在层面对失败国家进行了界定。参见Stein S.Eriksen, “The Theory of Failure and the Failure of Theory: ‘State Failu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umforDevelopmentStudies, Vol.32, No.1, 2005, pp.295~298;Charles T.Call, “The fallacy of the ‘Failed State’,” ThirdWorldQuarterly, Vol.29, No.8, 2008, pp.1491~1507。在2009年美国和平基金会公布的失败国家排行中,被认为处于“紧急状态”(alert states)的非洲国家占22个,处于“警告状态”(warning states)的非洲国家占31个(部分国家同属两类)。参见李伯军:《非洲民族国家建构面临的挑战与国际法》,《法治研究》2011年第3期,第91页。
但是,从当前非洲大陆整体形势来看,非洲民族国家的前景也并非一片灰暗。一方面,部分国家自“民主化”以来积极进行改革和实践,已初步实现了政治平稳、族际关系秩序化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民主化”以来曾出现严重冲突和危机的国家,近年来整体上也逐渐呈现缓和态势。鉴于非洲在现代化之路上的挫折和教训,我们不应简单地将“民主化”视为解决非洲问题的普适良药,但也不应盲从于悲观论调,而是要重新回顾和反思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和实践。当前,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探讨重心已不应再像以往那样将某种既定的模型或框架作为蓝本,用来制定非洲国家发展的行动目标和实践纲领,而更应该转向非洲本土视域,立足于非洲历史,总结不同文明和族群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未来之路提供明灯。因此,本文试图对现有民族国家建构理论进行简要的批判性回顾,并结合非洲历史发展进程来总结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一般模式和特征,再通过考察当代非洲部分典型国家的案例,探讨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可能性路径。
一、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建构理论
民族国家一词首先见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但早期民族国家概念更侧重于主权国家的含义,以确立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形式来对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随着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和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学、社会学对民族国家理论的推动,民族国家概念也出现了相应的新内涵。一般来说,现代民族国家是指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具有统一阶级利益及同质性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而民族国家建构一般是指在各方面打破国内各地区和族群间的壁垒,建立和健全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的文化模式。[注]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204页。而在民族国家建构实践中,一国内部文明的发展及其衍生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是影响统一民族国家内聚力、自决度和开放性的重要因素。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由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组成的双向进程。[注]Samuel E.Finer, “State- and Nation-Buildingin Europe: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arls Tilly,ed., TheFormationofNationalStatesinWestern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85~89.就国家建构而言,它是由领土空间和国家权力与行为的政治整合。如果说,领土疆域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地理空间基础,那么国家政治权威的形成就赋予了它灵魂。国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塑造既来源于主权和话语体系,[注]Charles Tilly, TheFormationofNationalStatesinWestern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7.也受到“外部行为体”介入干预后的影响;[注]Francis Fukuyama, Stating-Building:GovernanceandWorldOrderinthe21st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民族建构则是在特定政治地域和国家权力下,各族群之间通过共同经济社会活动而形成共同语言、文化和心理,从而形成基于民族主义观念下的“想象的共同体”。[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这既强调了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的客观存在,也体现了这些民族和文化群体在共同意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是同步进行和相辅相成的,国家建构为民族建构提供政治庇护和支持,而民族建构又为国家建构提供合法性来源和理念支撑。
如上所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政治发展进程、历史根基和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呈现了不同的建构模式和发展特征。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学界大多倾向于用历时性视角,将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大致分为原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后发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和跨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3种。原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通常突出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历时性发展特征,如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建构经历了从“传统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再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注]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40页。后发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主要是指从宗主国那里继承和移植相对成熟的社会文化体系,后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从而开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情况。[注]于春江、于春洋:《论后发形态民族政治发展模式——以民族国家及其构建为视角》,《理论月刊》2013年第4期,第134页。跨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主要研究的是在国家、民族发展史上出现非连续性或断裂性的地区,诸如非洲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和工业社会等历史发展阶段,而直接从部族社会被拉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之中,这就形成了李安山所描述的“十分复杂甚至痛苦的过程”。[注]李安山:《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兼论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民族建构的作用》,《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第7页。除上述历时性视角外,部分学者还用共时性视角,通过对民族国家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中的各项因素进行横向比较来得出结论,如安东尼·史密斯根据民族国家的产生机制、社会基础和政治理念的差异将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划分为“族群的民族模式”(an ethnic model of the nation)和“公民的民族模式”(a civic model of the nation),[注]Anthony D.Smith, NationalIdentity,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p.11.而菲利克斯·格罗斯基于相似视角则将民族国家分为“部落国家”和“公民国家”两种类型。[注]Feliks Gross, TheCivicandtheTribalState:TheState,EthnicityandtheMultiethnicStat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8, pp.6~12.迈克尔·曼则通过区分基础权力和专制权力两种形式,[注][英]迈克尔·曼著,陈海宏等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270页。总结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威权国家”、“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3种理想形态。
她喜欢波提切利细腻稳健的笔法,她从画家笔下那些丰满白皙、充满肉感的女人体里,感受到了活生生的女人气息。那些女人神态端庄安详,体态优美,将那些几近完美的裸体坦然呈现在人们面前。但她们的目光游离在画面之外,你看,或者不看,她们根本不在意。
长期以来,民族国家理论主要由西方话语所主导,其在民族国家及其相关概念、民族国家类型和特征分析上都体现出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主要体现在:首先,现有理论架构通常是从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特征中总结出一个普遍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并将其作为全球民族国家建构的通用模式来看待。这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民族国家建构需遵循其本土历史文化根基这一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般掩盖个别”的特点。其次,学者往往先验地构想出一种“理想的”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并基于这种理念制定出一系列假设性判断,用来作为民族国家建构实践的方法参考。这忽略了对具体对象实际经验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思辨先于实证”的特点。不过,学界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视角,以及“双分”和“多层”的分析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较系统的方法论参考。
大数据驱动下,信息融合的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图书馆的各类数据库资源、信息系统资源,还包括各类感知设备所采集的信息,以及图书馆用户行为数据等。将这些信息进行全面整合,最终实现终端应用、大屏展示和移动APP上的信息联动,是智慧图书馆信息系统实施的基础。
二、文明史视角下的非洲民族国家建构模式
一般来说,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不同于欧洲和东亚古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它具有其自身特殊性的发展模式。[注]刘鸿武:《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国家统一构建进程》,《西亚非洲》2002年第2期,第18页。我们不能把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经验在非洲进行简单的移植和套用,而应该以非洲历史的自身特点为基础,从历时和共时的维度对非洲整体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分析,以此归纳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模式和特征。
在社会经济方面,这一时期加纳经济发展出现了较严重的停滞和衰退。独立之初的前3年间,加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年均人收入增长率为4.8%,外汇储备为4.8亿美元,远超同时期的其他非洲国家和地区。[注]Douglas Rimmer, StayingPoor:Ghana’sPoliticalEconomy 1950~1990,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2, pp.76~77.但自1960年后,由于国营经济经营不善、生产技术落后、工业化成本巨大以及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加纳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出现赤字。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一方面大量借款,导致每年政府负债量远高于收入总和。[注]Austin Gareth, “National Poverty and the ‘Vampire State’ in Ghana: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Vol.8, No.4, 1996, p.556.另一方面,政府一昧地采取片面的货币升贬值策略,又引发了国内严重通货膨胀。此外,腐败问题及不完善的税收和市场体系也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总体上,20世纪60年代后加纳经济发展陷入长期的停滞,其中1972~1981年这10年间还呈现出明显的负增长态势(见表2)。经济问题加剧了族群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成为该时期制约民族国家建构的另一大因素。
19世纪末欧洲国家确立对非洲大陆的统治地位后,便开始将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移植到非洲,企图终止和改造非洲原有的文明发展模式,建立起一种以西方文化、技术和理念为主导的现代文明。但实际上,宗主国对非洲的“全面西化”并不成功:在地域分布上,殖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仅仅在部分沿海地区以及内陆地区的中心城市有所进展,而非洲内陆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原有的状态;在政治制度上,宗主国的政治体制开始仅在沿海直属殖民地内方可施行,后来虽然逐步扩展到内陆一些地区,但覆盖程度始终有限,并未系统地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行政机制。并且,对于一些在前殖民时期文明和国家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宗主国往往采用间接统治的手段,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了其原有的政治制度;在经济模式上,尽管工业化和经济型农业开始在一些地区出现,但既不集中也不成规模,且不同地区的主要经济行为体和商品市场也表现出较大的差距;在文化形态上,尽管西式民主自由观念及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影响到一部分本土上层精英,但并未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广泛影响,内陆的文化体系未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但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边界划分和政治体制的移植确实为非洲“现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去殖民化浪潮下,各殖民地迅速而直接地继承宗主国的遗产而转换为新兴主权国家,但此时这些国家还不是完全的“现代国家”,更不是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这是因为:首先,此时的中央政府大都只是一种“地方政府”而非“全国性政府”。尽管这些国家拥有现代性的主权范围,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结构,在名义上实现了对主权领土的管理,但实际上此时大多数国家中央政府的管控范围仅限于首都及主要城镇,而未真正扩展到整个领土范围。其次,由于此时的国家只是形式上的(或概念上的)国家,尚未给异质性突出的各族群构建共同的国家观念、经济基础和文化纽带。[注]L.Laakso and A.O.Olukoshi, “The Crisis of the Post-Colonial Nation-State Project in Africa,” in Abedayo Olukoshi and Liisa Laakso,eds.,ChallengestotheNation-StateinAfric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1996, p.13.然后,此时非洲大多数地区还普遍停留在以单一商品作物为主的粗放型国营种植业和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农业,矿业和轻工业发展程度低且发展严重失衡。[注]A.G.Hopkins,AnEconomicHistoryofWestAfrica, London: Longman, 1973, pp.172~181.中央政府的财政覆盖和政策导向仅能在少数大型国有企业中起作用,广大地方还未能真正被纳入到国民经济的轨道,市场一体化和产业规模化远未完成。再者,尽管民族主义精英继承了宗主国政体,掌握了领导权,但其能力薄弱、经验不足,不能将国内各方势力有效统合在一个平衡有序的政治生态之中。
自1957年加纳共和国成立至1982年年初罗林斯军政府上台这段时期,本土文明下的自发性民族国家建构与外来化文明下的民族国家重构两种路径之间的交叉互动成为加纳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核心主题。在政治方面,外来化的政治势力与本土势力之间为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展开了激烈对抗,以期通过合法暴力垄断的方式攫取国家资源,推动自身体系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发展。代表不同族群的利益集团在夺取政权后,往往采取集权式的政体形式,将个人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志,并推行族际政治以挤压其他族群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建立起统一性的国家秩序。在人民大会党(Convention People’s Party)一党专政时期,以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为核心的外来化精英通过宣扬统一民族主义、打击本土酋长集团的反对党势力、强化对地方控制、垄断民间社团、建立高度集中的党政体系和层级结构,[注]关于人民大会党执政时期的措施,详见Dennis L.Cohen, “The Convention People’s Party of Ghana: Representational or Solidarity Party,” CanadianJournalofAfricanStudies, Vol.4, No.2, 1970, pp.192~194;Jon Kraus, “O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hange in Ghana,” 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 Vol.7, Issue 1, 1969, pp.122~124;Trevor Jones,Ghana’sFirstRepublic1960~1966:ThePursuitofthePoliticalKingdom,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77, pp.105~110。力图消灭本土文明的存在,将外来性民族国家模式覆盖到全国。但本土势力举起地方民族主义大旗对其进行顽强抵抗,人民大会党无法单纯依靠武力和集权将本土势力彻底消灭,反而因其加剧内外矛盾而被推翻。1966~1969年全国解放委员会(National Liberation Council)临时政府(第一军政府)执政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瓦解和统一意识形态的缺失,致使本土文明和地方民族主义出现强势反弹,最终导致以阿坎沙文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布西亚(Kofi A.Busia)文官政府的上台执政。但布西亚政府过于急躁地推行族际政治又引发了“边缘化”族群的普遍不满,[注]布西亚的进步党(Progress Party)在1969年大选中获胜后,其组建的新内阁的19名成员中阿坎族占了14名之多。其余5人中,3名为北方人,加(Ga)族和关族各1人,但无一名埃维族。同时布西亚还开除了500多名埃维族公务员,剥夺了大量埃维族军官的军权。这种极端的地方民族主义做法引发了全国普遍不满,布西亚本人也被称为“部落总理”(tribal prime minister)。参见Anja Osei, Party-VoterLinkageinAfrica:GhanaandSenegalinComparativePerspective, Berlin: Spriger Verlag, 2012, p.108。使其难以控制混乱局势而倒台。1972~1979年第二军政府时期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建立“文官—军人”联合政府,弘扬历史文化,促进宗教和解等),力图重建统一性的民族主义,重新推动外来性民族国家建构,但又因自身局限性和改革不彻底性导致政变频繁,政局混乱。总体而言,自独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本土与外来化两种体系之间在政治上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相互斗争的零和博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钟摆式政治”[注]学界一般倾向于用该词来形容加纳独立后反复在民选政府和威权政府、文官政治和军人政治之间摇摆的现象,参见Deborah Pellow,ed., Ghana:CopingwithUncertainty,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6, p.89。(见表1)。双方矛盾难以在加纳国家框架内得以有效调和,民族国家建构缺乏良性有序的政治基础。
图1 非洲民族国家建构模式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自发地或被动地进行了“民主化”实践,[注]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1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至少有35个国家进行了民主选举,其中有22个国家进行了两次全国性选举。参见Richard A.Joseph, R.Pinkney,eds., State,ConflictandDemocracyinAfrica,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p.13。至今,除斯威士兰实行君主制和厄立特里亚实行一党制外,其他52个非洲国家均已实行多党制和定期选举制。但整体上问题重重。一部分国家在威权政府解体后经历长期内战,国家陷入实质上的分裂或无政府状态,如刚果(金)、索马里、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苏丹等;一些国家的威权势力操纵选举,政体实际上仍是专制主义的继续,如坦桑尼亚、喀麦隆、乍得、加蓬和毛里塔尼亚等;一些国家虽表面上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当权者不断试图以修改宪法或其他方式延长任期,[注]即近来国际上讨论较多的“第三任期”问题。对此学界大致有两种不同态度,一种认为这是明显的“民主衰退”的体现,并着重于分析其成因和应对方式,参见Larry Diamond, “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JournalofDemocracy, Vol.26, No.1, 2015, pp.141~155;Tukumbi Lumumba-Kasongo, “Africa’s Third-Term Syndrome,” Georgetow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8, No.1,Winter/Spring 2007, pp.127~129。另一种认为这是非洲国家按照自身实际对现有政体模式的调整,其并非是要倒退回绝对的威权主义,参见Rita Abrahamsen, “African Democracy: Still Disciplined after All These Years?” InternationalRelations, Vol.27, No.2,June 2013, pp.241~245;R.Mattes and M.Bratton, “Do Africans still Want Democracy?”http://afrobaromet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olicy%20papers/ab_r6_policypaperno36_do_africans_want_democracy.pdf,pp.5~13。破坏民主准则,如乌干达、津巴布韦、多哥和刚果(布)等。可喜的是,现仍有少数在民主政体下保持着政治平稳,并实现经济增长、文化同质性和一体性程度加快、统一国家民族意识不断增强的国家,如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至今,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已初见成效。
综观非洲历史的总体脉络,不难发现,现代非洲民族国家建构可视为是一种在“先国家再民族”的特定模式下的发展理路:一方面,非洲各地区各部落和族群首先需要在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特定时空范围并对内合法行使主权的国家概念,并建立一种在形式上覆盖到全国范围的政府框架,然后在此框架下进行政治整合、经济规划和社会建设,从而为民族观念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另一方面,在“现代国家”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建立一种具有共同性的语言、习惯和身份认同的公民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消除部落文化、部落认同对统一民族建构的桎梏,形成一种建立在国家框架和公民社会下的民族共同体。而在民族共同体中,统一民族观念、族群实体和高度凝聚的文化价值观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在上述过程中,国家建构尤其是政治体制建构与民族(国族)建构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建构是国家认同的先决条件,国家认同又是公民社会和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前提;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和民族共同体又能反过来作用于国家建构,从而使三者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达成融贯统一。
三、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特征
总体上,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体现出“后发型”、“反复性”和“外部干预”3个基本特征。
此外,外部干预也是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中一个较显性的特征。由于独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非洲国家内部本土文明与外来化文明之间的对立冲突难以从根本上调和,各国内部的中央集权和文明同质化大都以失败告终,非洲国家难以在自身范围内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和挫折并继续推动民族国家建构,这就需要外部因素的介入为打破僵局注入新鲜活力。同时,非洲国内动乱尤其是族际冲突往往在得不到有效控制下扩大为跨国冲突乃至区域战争,国内问题演化为国际问题,这就为地区与国际组织的介入提供了合法性和必要性。此外,独立后非洲各国政府维持财政平衡的方式曾在较长时期内不是依靠公共税收和出口贸易,而是依赖于国际援助和借款,[注]Jeffrey Herbst,StatesandPowerinAfrica:ComparativeLessonsinAuthorityandContro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0, pp.124~125.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主导下的经济机构将其制定的理想发展模式施加于非洲提供了契机。
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后发型”主要体现在:按照民族国家的“先天层面”和“原生型”理论,可以认为,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大陆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自发性民族构建,只不过相较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其发展程度比较滞后。在此,有必要对民族这一概念作简要说明。民族一词主要起源于西方语境中的“民族与国家同一性”观念。西方学者通常以“时间推移下的演进性、空间转换下的特殊性、多元视角下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下的建构性”[注]郝亚明:《试论民族概念界定的困境与转向》,《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3~9页。4种基本模式为理论基础,以民族国家建构的多元性、特殊性和实在性为研究对象,以期得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认识。通常情况下,民族一词代表的是观念上的意义而非实在上的意义。从人类发展的自然和社会两重性来看,人类不存在民族这一概念下的形态,而只存在诸如家庭、部落和族群等客观实体。民族实质上是近代欧洲人在既有领土国家范围内的族群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之上想象的一种共同体。西方世界力图以此确立起规范性的国际行为体,并使之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单位而存在。[注]John W.Meyer,ed.,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103, No.1, 1997, pp.148~149.因此,民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欧洲具体实际和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并以某种政治目的或实践为导向,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能普遍适用。
企业成本核算准确度的高低,是和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企业高管的重视度分不开的,只要企业的财务人员深入了解生产工艺流程,合理确定成本中心,准确归集成本物料对象,采用合适的成本核算方案,在保证成本核算准确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成本效益原则;另外企业高管的重视程度也是成本核算准确性的重要保障,高管要对涉及成本核算的各个物料流转控制环节起到监督核查作用,保证各环节基础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财务归集核算成本提供基础保障。
近代以来,随着外来文明的进入,除少数地区尤其是西非地区出现了新兴族群和国家的崛起外,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领土国家被瓦解,自发性民族建构进程被破坏和中断。至19世纪末,非洲本土文明的内在自决能力全面丧失,已基本无力掌控族群和国家发展的命运。因此,外来文明(宗主国)便在某种程度上肩负起重构非洲民族和国家并引领其发展的重任。于是,宗主国首先是试图按照某种政治目的下的区分标准强制划分非洲民族,并推行族际政治,其中典型的有比利时对图西人和胡图人的划分、英国对所谓乌干达民族的构建等。但是,整个殖民时期外来文明在非洲的根基始终比较薄弱,在非洲直接存在和统治的时间过于短暂,对非洲本土文明的同化或再生的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殖民时期外来文明对非洲民族的重构程度是较低的,在短时间内强制生产民族的努力大都以失败告终。同时,宗主国将欧洲模式在非洲的移植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按照现代国家的形式划分殖民地边界。但是,这严重割裂了非洲本土文明的族群和文化分布空间,以一种简单且畸形的方式为非洲“现代国家”的诞生提供了框架。[注]据苏联学者葛罗米柯(Anat A.Gromyko)的统计,非洲现代国家的边界有44%是按经纬度划分的,有30%是按直线或曲线划分的,只有26%是按山川地形等自然地理边界划分的,参见Anat A.Gromyko, “Colonialism and Territorial Coflicts in Africa: Some Comments,” in C.G.Widstrand,ed., AfricanBoundaryProblems,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1969, pp.165~166。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殖民地边界的划分并非完全是主观武断性的,但其造成的客观事实是不能回避的。因此,非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外来模式下的现代国家框架和尚未完成的内部民族构建,从而导致非洲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必然在一种后发且被动的状态下进行。
独立2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一方面,自发性民族国家建构因其缓慢和落后性已不适宜作为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主流模式,同时其封闭和排他性所催生的地方民族主义,更是成为民族观念建构的一大桎梏。它从根本上已不能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另一方面,外来性民族国家重构因其根基未深、实力不足,既不能完全同化本土文明,又不能建立一种平稳有序的政治体制来推动国家发展,因此加纳民族国家建构亟需打破现有体系的桎梏而寻求一种新路径。1982年罗林斯(Jerry J.Rawlings)上台后深刻意识到将民族国家建构建立在一种统一的、良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必要性。以往实践证明,集权政治和无序的政党政治已无法引领这一使命,而只有民主政治和公民政治才可能平衡权力和利益分配,缓解两大体系之间的矛盾对立,进而逐步形成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意识形态。鉴于此,罗林斯继承了阿昌庞民众主义理念,摒弃以往为地方民族主义、威权主义、政治腐败和意识形态冲突提供温床且毫无民主实质的政治形式,开启将民主制度和理念深入基层民众的“无党选举”政治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效。[注]阿昌庞曾在1975年提出民众主义,认为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对政党的有效制约机制,那些有足够金钱资助的政党就会轻易采用不当手段在选举中获胜,而且在国计民生极为贫困的情况下谈论民主毫无意义。因此他提出可以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直接从民众中选出政府官员。参见Mike Oquaye, PoliticsinGhana,1982~1992:Rawlings,RevolutionandPopulistDemocracy, Accra and New Delhi: Tornado Publications and Thomson Press India, 2004;Maxwell Owusu, “Politics without Parties: Reflections on the Union Government Proposals in Ghana,” AfricanStudiesReview, Vol.22, Issue 1, 1979, pp.89~108。但是,阿昌庞这一理念未得到贯彻施行,反而成为军队进行独裁统治的借口。罗林斯发展了这一理念并付诸实践:建立国家民主委员会(National Democracy Commission)作为无党选举的监督机构,并颁布《地方政权和地区选举法》,为选举提供法律保障。然后于1988年年底至1989年年初成功实行了第一次无党选举,从12842名参选人中选出7260个议席,组建了110个县市议会。参见Richard C.Crook, “No Party Politics and Local Democracy in Africa: Rawlings’ Ghana in the 1990s and the ‘Ugandan Model’,” Democratization, Vol.6, Issue 4, 1999, p.122。同时,全方位推行经济复兴和调整计划,其主要表现为:降低行政开支,严厉打击腐败,适度增加税收,稳定金融秩序,改革公私企业,扶植农矿业,发展进出口贸易,加强民生保障。在一系列措施之下,政府外汇收入和国内投资量得以显著增加,财政赤字降低,进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国民经济负增长得到有效扭转(见表3)。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反复性”主要体现在:如前所述,独立后非洲国家是在一种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状况下被迫卷入到西方话语下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中,这使得非洲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本土文明与外来性民族国家模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在政治上主要呈现为多方形成博弈局面,前政府文官、部落酋长、教会、社团和政党等纷纷在新政府框架内竞争和倾轧,其主要可分为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的外来化势力和以部落酋长为主的传统势力两大阵营;在经济上主要呈现为以制造业、采矿业、港口贸易和单一经济作物种植业为主的现代化产业,与以自给自足为主的传统自然经济[注]Dambisa Moyo, DeadAid:WhyAidIsNotWorkingandHowThereIsaBetterWayforAfrica, Macmillan, 2009, p.58.之间的对立;在社会上主要体现为区域封闭性和阶级结构固化,地方自主性和部落意识突出;在文化上则主要体现为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共生和激烈冲突。
在独立之初,非洲各国从内外两个层面对民族国家建构作出了努力。在外部层面主要希冀于改变现有国家边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群跨界和文化空间割裂问题。但出于防止因边界冲突而导致国际战争的考虑,非统组织(OAU)最终于1964年确立了“非洲国家边界不可更改”的原则,并积极干预非洲各国的边界争端,[注]Jeffrey Herbst,“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Boundaries inAfrica,”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43, No.4, 1989, pp.673~674.使得一国通过改变边界来调整国家框架的试图几乎成为不可能。在内部层面,非洲各国纷纷抛弃独立之初的西式多党政治和议会制,转向一党制或军人政治,试图通过扩大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和经济规划来实现国家公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在文化上推行统一性的意识形态,如尼雷尔的“乌贾马”(ujamaa)主义、塞古·杜尔和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卡翁达的人道主义、肯雅塔的“哈兰贝”(harambee)主义等。[注]L.Laakso and A.O.Olukoshi, “The Crisis of the Post-Colonial Nation-State Project in Africa,” in Abedayo Olukoshi and Liisa Laakso,eds.,ChallengestotheNation-StateinAfric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1996,pp.13~14.
在非洲历史上,绝大部分地区的族群还远未发展到西方意义上的民族阶段,即便是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些族群仍停留在“前民族”(pre-nation)阶段。这是因为:首先,非洲的传统社会结构主要体现为“家庭—部落—族群”的层次,而尚未成功地从族群阶段上升到民族阶段:在共同生活地域、生产方式、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下,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部落先得以形成。不同部落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共处和接触,并在物质资源、政治权力和发展机会等诸多方面展开竞争。在激烈竞争中,某一部落在一定程度上和局部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的现象必然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主体部落对周边部落进行征服和统治,从而形成统一族群。而族群中的主体部落必须主导平衡各部落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保证自身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实现族群内部稳定和自决发展。这种部落—族群的结构典型的有阿散蒂—阿坎族系、祖鲁—恩古尼族系、马林凯—曼德族系、豪萨—富拉尼族系等。然而,由于上述部落—族群结构形成时间较晚,规模较小,程度较低,尚未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环境下进行全面深入的文化聚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注]按照部分非洲学者的看法,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族体在民族建构过程中须经过6个阶段,即共生(co-existence)、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征服(conquest)、妥协(compromise)和聚合(coalescence)阶段。其中,聚合是文化融合和统一价值观塑造,即民族观念形成的关键步骤。参见李安山:《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兼论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民族建构的作用》,《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第8页。其次,对应于上述社会结构,非洲传统政治体制主要体现为“家长制—酋长制—酋邦(王国)制”的层次,而代表部落政治的行为体——酋邦(王国),其大都出现了中央集权程度较为松散、行政层级系统不完善、经济开放度与人口流动性不高等各种问题,[注]Frederick Cooper, AfricaintheWorld:Capitalism,Empire,Nation-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50~52.从而限制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对领土范围的暴力垄断能力以及统一政权的合法性塑造,进而间接制约了文化的融合和统一,最终导致在整个前殖民时期,非洲大陆普遍存在民族构建尚未完成的问题。
以上举措的目的在于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和政府职能,打破非洲传统静态的部落政治和封闭式社会经济,构建新的统一文化观念,以外来化文明的模式同化本土文明,最终消除本土文明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种种桎梏。然而,从结果来看,这种方式不仅未能达成初衷,反而加剧了国家内部混乱,导致民族国家建构的停滞。这是因为:首先,集权政治导致的专制、腐败问题不仅在法理和情感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地位,也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平衡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同时,家长制政治传统不仅未被消除,反而在集权政治下成为常态。[注]学界一般也将传统部落政治中的家长制在非洲现代国家政治体系内的扩展称为新家长制(neo-patrimonialism),参见Daniel C.Bach and Mamoudou Gazibo, NeopatrimonialisminAfricaandBeyo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Diana Cammack, “The Logic of African Neopatrimonialism: What Role for Donors,”DevelopmentPolicyReview, Vol.25, No.5, 2007, pp.599~614。其次,中央的经济规划因缺乏财政基础和社会支持而陷入停顿,以初级产品贸易为支柱的依附性经济长期得不到扭转,税收贯彻度和执行力低下,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增长和公共事业建设。同时,错误的产业调整和严重的外援依赖还导致通货膨胀、外债加剧和粮食危机等严峻问题。[注]L.Laakso and A.O.Olukoshi, “The Crisis of the Post-Colonial Nation-State Project in Africa,”in Abedayo Olukoshi and Liisa Laakso,eds.,ChallengestotheNation-StateinAfric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1996,pp.16~17.政治、经济问题激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缺失和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族群身份的认同,致使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崛起,并形成一种以夺取专制权力、攫取物质资源和维护部落利益为直接目的的零和博弈。这成为非洲国家在独立后频繁出现军事政变和族际冲突的直接原因,也是非洲现代国家建构陷入反复性的重要原因。由于国家政治失序、制度失灵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非洲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问题长期存在,致使中产阶级群体十分薄弱且长期得不到发展。这不仅制约了公民社会的自然形成,同时也无法在国家权力下的强制性文化统一失败后继续促进文化的自然聚合,从而致使统一民族观念往往变成海市蜃楼。
当然,不同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具体体现也各不相同,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本土与外来性、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态势下,往往文明同质性较强的国家其民族国家建构之路就会相对平坦,其反复性的程度较小,周期也较短。这种一般体现为在前殖民时期未形成中央集权国家和主体族群,在殖民时期被外来文明同化程度较深,且去殖民化以后几乎完全在外来模式下进行民族国家建构,比如坦桑尼亚、赞比亚、南非、布基纳法索、加蓬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而文明异质性较强的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其反复性就不可避免地程度较深,周期也较长,当代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这个过程。
上林路站是16号线和1号线二期车站的换乘站,位于世纪大道与沣泾大道交汇处。1号线二期上林路站为地下二层、宽11 m的岛式站台标准站,沿世纪大道东西向敷设。该站在设计时,未考虑与其它线换乘,未预留换乘节点,因此需后期接入改造。目前,该站的围护桩、冠梁、挡墙已施工完成,一、二段底板已浇筑。世纪大道与沣泾大道的十字路口四个象限均有在建楼盘,十字路口北侧约300 m处有上林大桥。
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外部干预可大致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前者一般是针对一国或地区范围内国家职能严重衰退或失灵,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并可能或已经导致战争扩大化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这种干预行动一般由联合国或非盟(AU)发起,周边邻国采取行动,非洲历史上的欧加登战争、比夫拉战争、乍得内战、刚果(金)内战、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内战和卢旺达大屠杀,以及一些区域冲突、粮食和疾病危机等几乎都有外部干预的存在。后者一般是西方世界基于国际法建立起一种关于区域和国际事务的准则或秩序,以及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将非洲国家卷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由于非洲国家经济的对外依附性,国家财政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际金融机构政策的影响,从而陷入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严重制约了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随着国际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和原油等工业原料价格的不断攀升,非洲国家大都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退,[注]Isiaka A.Badmus, “What Went Wrong with Africa? On the Etiology of Sustaining Disarticulation of the African Nation-States,” LawandPoliticsinAfrica,AsiaandLatinAmerica, Vol.39, No.3, 2006, pp.276~277.伴之而来的是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为了应对危机,非洲各国普遍将希望寄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援助上,同时也大都被迫受它们所要求的民主化改革等政治裹挟。[注]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西非国家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中,明确提出要求实行多党政治和民主选举制。在此之下,西非国家如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纳、贝宁和多哥等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启动了民主化改革。参见Anja Osei, Party-VoterLinkageinAfrica:GhanaandSenegalinComparativePerspective, Berlin: Spriger Verlag, 2012, pp.110~111。总体上看,非洲不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是在外部干预下被强制提上议事日程的,它与这些国家当时的现实发展需求有所脱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瓦解和破坏了当时一些国家既有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秩序,从而造成在民主化前10多年间非洲一些国家出现较之以往更为严重和剧烈的动荡,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更为频繁。[注]贺文萍:《论非洲民主化》,《西亚非洲》2002年第6期,第27页。西方世界所赞誉的“非洲第二次解放运动”[注]Richard A.Joseph,R.Pinkney,eds.,State,ConflictandDemocracyinAfrica,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p.13.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不过,需指出的是,民主化对非洲民族国家建构可能的促进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这是因为:民主化本质上属于一种新的外来模式,它在非洲的全面覆盖在某种意义上可为非洲的外来化民族国家建构注入新鲜血液。由于“先国家后民族”的模式已成为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必然,非洲各国与其陷入到在本土与外来化之间的矛盾泥潭中不能自拔,不如在既成的民主化潮流下,努力将新的外来模式与本国实际问题相结合,据此应对民族国家发展中的未解问题和新挑战,逐渐形成一种既有本国特色又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方法路径。在此过程中,非洲各国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时刻关注具体问题,将民主化下的政治建设与国家发展、民族构建的整体进程相融贯和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民族国家建构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非洲具体国家的实践路径,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为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整体理路提供参考。
四、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以加纳为例
在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整体模式和特征下,各国因各自族群分布、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使得其各自在民族国家建构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所不同,并随着其自身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其中,加纳作为当前非洲大陆为数不多的民族国家建构进展较快的国家,其民族国家建构的特殊历史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具体路径并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一般特征相对照,来得出相应的理论共识。
13世纪至16世纪末,西苏丹草原南部一带的一些族群迁徙至今天加纳中南部地带,与当地部落融合后陆续建立了一些土邦(native state)。[注]关于沃尔特和黄金海岸地区原住民的历史尚不可考。一般认为今天居住在加纳境内的3个主要族群阿坎人、莫西—达戈姆巴(Mosi-Dagomba)人和埃维(Ewe)人的祖先大约在公元1200年左右开始陆续从今天马里南部沿上沃尔特地区(今布基纳法索)迁徙至黄金海岸地区,并先后建立起一些土邦。其中阿坎人建立的土邦主要有阿丹西(Adansi)、邓克拉(Denkyera)、阿克瓦穆(Akwamu)、冈扎(Gonja)、芳蒂(Fandi)和阿散蒂(Ashanti)等;莫西人建立的土邦主要有达戈姆巴(Dagomba)、南肯塞(Nankanses)和曼普鲁西(Mamprusi)等;埃维人建立的土邦主要有阿克拉(Accra)和安罗(Anlo)等。参见[英]威·恩·弗·瓦德著,彭家礼译:《加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8~82页;Richard Gray,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 Vol.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98~324。17世纪后期阿坎族的一个支系部落阿散蒂(Ashanti)开始兴起,至19世纪初形成了领土范围较广、族群成分较复杂且具有一定中央集权程度的王国。这一时期,以阿散蒂国家为框架、阿坎族为主体的自发性民族国家建构已经启动。[注]其主要表现在:首先,尽管国内各部的地区议事会对王权存在一定的制约力,但至少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和王权的象征形态(金凳子)。其次,在原先的部落基础上,通过战争兼并和社会开放,吸收了大量周边部落民进入国内,使阿坎族的人数和空间范围得到了极大扩展。此时的阿坎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突破了部落性的语言习俗、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范围等天然界限,开始向一种基于具体族群之上的抽象“民族”转变。然后,对内增强了不同部落和族群之间的凝聚力,对外形成了以阿散蒂为中心的对周边族群(如北方部落群、东部埃维族联盟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外来化”族群)的向心力,其文化范围已超出了其领土范围。在全面殖民时期,英国在黄金海岸内陆地区的间接统治一方面维持了内地大部分土邦和部落的半自治地位,使本土文明原有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语言文化得以大部分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在沿海地区的直接统治使沿海族群原有的发展模式完全被外来模式所替代,逐渐形成了与内陆本土文明相对立的外来化文明。自此两种文明体系在现代加纳国家框架内的对立形势得以奠定。
在屈原和宋玉的辞赋中,呈现出人与神、神与神之间相恋相离的欢乐哀愁,神的美、韵和感情,都在这些优美而哀伤的文笔中缓缓展开。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屈原的《九歌》,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神性当中人性的方面,而且还歌颂出一首最动人的赞歌:东皇太一伟大而高贵,但同时具有人情味;湘夫人多情多怨,为爱人苦苦守候;湘君多愁善感,情系伊人……在屈原笔下,神不在高高在上,无所不能,他们也和凡人一样苦恼、忧愁,恍惚间,仿佛神界亦乎人界,人界亦乎神界……
因此,独立后的非洲各国普遍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首先,如何建立一种适合本国实际的、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自决力的政体。这种政体一方面要致力于将国内原本分散的各方势力统合在一种政治模式之下,有效平衡各方之间的矛盾,并在一个统一政治目标下促进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建立起适合本国的经济体制,制定中长期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计划并贯彻实施,在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逐步降低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其次,在统一政治体制下,如何将国内众多分散的、异质性突出的部落或族群统筹在同一政治生态之中,并发展出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和认同度的国民文化体系,使原本因文化异质性而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突出的族际关系得以改善。这样,非洲国家才能从实质上的部落国家走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现代民族国家。[注]刘鸿武:《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但是,由于非洲现代化的后发性和被动性,致使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本土文明与外来化文明[注]在本文中,本土文明是指非洲各族群在前殖民时期所自发形成的各文明;外来文明是指16世纪初至20世纪中后期曾在非洲大陆上存在的非本土文明,如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外来化文明是指一部分本土文明在外来文明的影响下逐步丧失自身的本土性,并按照外来文明模式来发展自身的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长时期内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从而导致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一段时期内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族际矛盾加剧和地方民族主义等问题,部分国家陷入长期内乱甚至区域战争,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中断、停滞甚至倒退。
表1 1957~1981年加纳政治发展简况
时间政权性质最高权力机关最高领导人代表势力所属部族意识形态1957~1966第一共和国人民大会党夸梅·恩克鲁玛外来化上层精英沿海外来化族群全国民族主义、社会主义1966~1969第一军政府全国解放委员会约瑟夫·安克拉赫军警无无1969~1972第二共和国进步党科菲·布西亚内陆知识分子及部落酋长阿布阿夸(阿坎族)阿坎沙文主义1972~1979第二军政府救国委员会阿昌庞,后为阿库福军警及部落酋长阿散蒂(阿坎族)全国民族主义、无党民主1979~1981第三共和国人民民族党希拉·利曼少数知识分子北方部族温和自由主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非洲历史发展的总体特色来看,非洲大陆由于其先天的较为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后天的较为独特的种族迁徙运动,导致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在前殖民时期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与欧亚和北非等地区相比较低,且不同族群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体制、族群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因此,尽管非洲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文明,[注]按照社会文化史和文明史观,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文明的内在本质体现。也就是说,文明的存在是由其内在的文化形态而决定的。参见[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2~104页;Arnold J.Toynbee, AStudyof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ames Hudson, 1972, pp.43~45。虽然历史上非洲各族群的发展情况各异,但各自都形成了其内在的独特文化,因此本文拟用文明一词来统称非洲前殖民时期的不同形式的部落、酋邦和王国(帝国)。如西苏丹草原文明(加纳、马里和桑海)、森林文明(阿散蒂、达荷美、奥约等)、湖间文明(布列奥罗、布干达等)、斯瓦希里文明(东非沿海各商业城邦)、南部大河文明(刚果、隆达等),但总体上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族群仍然处于一种较低的发展状态。这主要体现为:政治上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的政治共同体(部落联盟)为主要形式;经济上以采集型农业、简易手工业和物物交换的商业为主要特征;社会上以酋长(或国王)、长老(家长)、自由民(部落成员)和奴隶的阶层划分为主要结构;文化上以祖先崇拜、泛神论和部落习俗等为主要载体。而上述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文明,在政治形式上也只是从部落联盟上升到中央集权王国,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并未出现实质性的突破。可以说,在整个前殖民时期,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的、文化多元性十分突出的“前现代国家”(pre-modern state)或“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注]Basil Davidson, TheBlackMan’sBurden:AfricaandtheCurseoftheNation-State, London: James Currey, 1992, pp.29~31.
表2 1972~1981年加纳经济发展简况(单位:%)
年均增长率总增长率GDP农业总值工业总值人均收入出口总额国内投资率实际利率实际通胀率实际工资率实际农业保护-0.5-1.2-1.2-3.1-8.4-5.1-30.034.8-13.4-90.0
资料来源:Edward V.K.Jaycox,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World Bank’s Perspective,” AJournalofOpinion, Vol.18, No.1, 1989。
HPLC-QAMS同时测定复方黄芩片中6种活性成分的含量……………………………………………………… 胡 丹(11):1510
综上所述,Netrin-1联合Kim-1对新生儿窒息后AKI风险预测效果比较理想,敏感度、特异度高,有利于及时发现AKI,有针对性地调整治疗方案,改善预后,降低死亡率。
由传统BGM方法步骤(4)可知,传统BGM方法中对小扰动进行动态调整的尺度化因子ct是一个只随高度层变化的量,在某一特定高度层为一定值,即只对繁殖模大小进行调整,而并未涉及小扰动某一层水平方向上的空间分布的调整。
表3 1982~1991年加纳经济发展简况(单位:%)
年均增长率总增长率GDP农业总值工业总值服务业总值国内投资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国内投资占GDP比财政赤字/盈余占GDP比实际通胀率5.12.39.17.811.411.39.9-5.0-8.010.8-0.7-108
资料来源:Ajay Chhibber, Stanley Fischer, eds., “Economic Reform in Sub-Saharan Africa,”https://hvtc.edu.vn/Portals/0/files/635822493178749673Economicsreforminsub-SaharanAfrica.pdf。
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突破以往30多年的反复和调整期,开始进入一个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在这一时期,以往本土文明和外来化文明两种体系下的民族国家建构路径逐渐被一种新路径所取代。这种路径一方面立足于加纳本土历史的经验实在,面向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又充分吸收外来模式的精髓,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致力于解决民族国家发展中的未解难题,并时刻应对未来的新挑战。因此,在这一时期,以往两种体系、两种路径之间的对立性逐渐淡化,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融贯统一的特征。
(一)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和创新思想能力。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律的价值。儒家思想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财富,蕴含着许多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优秀品质。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历史的价值是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的。《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新课程的概念∶“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根据历史教学的特点,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尊重历史,追求真理。”
在政治方面,这一阶段加纳政体经历了一个从无党制到多党制再到两党制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际社会将民主制在非洲的再移植,加纳作为国际金融机构重点援助国之一,也与其他西非国家一样面临着民主改革的外部裹挟。同时,在“无党民主”的基层民主建设和县市议会选举下,政党选举的秩序和社会理念开始形成,为有序竞争塑造了良好的氛围。此外,国内在野政治势力的诉求和社会舆论的导向也间接地促使政府重开党禁。[注]Wilson K.Yayoh, “Resurgence of Multi-Party Rule in Ghana, 1990~2004: A Historical Review,”TransactionsoftheHistoricalSocietyofGhana,New Series,No.10, 2006/2007,p.133.1992~2000年,加纳政局呈现出一种“多党制下的民主初步实践”态势。首先,中央政府传统威权与地方本土势力之间的博弈仍然是主旋律,其主要体现为以前罗林斯军政府为核心的全国民主大会党(National Democracy Congress)与以布西亚及本土酋长势力为核心的新爱国党(New Patriotic Party)之间的竞争。其次,除上述两大党派外,还存在众多恩克鲁玛传统下的小党派[注]原恩克鲁玛传统的政治势力因内部分化而形成人民全国大会党(People’s National Convention)、人民遗产党(People’s Heritage Party)、全国大会党(National Convention Party)、国家独立党(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人民民主与发展党(People’s Party for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等诸多小党派,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合,后逐渐在政坛上变得无足轻重。参见Kwame A.Nins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Ghana,” KonradAdenauerStiftung, 2004, p.4。和无党派人士,从而使政党格局呈现“单级—多元”并存的态势。再次,民主机制尚不完善,占优势的一方往往因缺乏有效制约而居于垄断地位,且因监督力量的缺失导致选举中可能存在操纵和舞弊行为。最后,地方性、族际性在选举中表现十分明显,各党派候选人在各自所属部落和族群地区的支持率非常高(见表4),而在竞争对手所属族群地区则较低。
表4 1992~1996年加纳政党选举简况
时间主要政党候选人所属部族总得票率(%)得票最高地区该地区得票率(%)该地区得票占总得票比(%)1992全国民主大会党杰瑞·罗林斯埃维族58.3沃尔特省93.319.1新爱国党阿杜·博亨阿坎族30.4阿散蒂省60.535.5人民全国大会党希拉·利曼北方部族6.7上西部和上东部省37.1和32.542.51996全国民主大会党杰瑞·罗林斯埃维族57.4沃尔特省94.516.8新爱国党约翰·库福尔阿坎族39.6阿散蒂省65.829.3人民全国大会党爱德华·马哈马北方部族3.0上西部和上东部省14.2和13.734.8
资料来源:John A.Wiseman,ed., DemocracyandPoliticalChangeinSub-SaharanAfrica, London: Routledge, 1995, p.106;Joseph R.Ayee, “The December 1996 General Elections in Ghana,” ElectoralStudies, Vol.16, No.3, 1997, p.418。
2000年至今,加纳政局呈现出“两党制下的平衡性民主”的发展路径(见表5)。首先,威权主义逐渐消退。罗林斯退隐后,全国民主大会党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注]Sarah Brierley, “Party Unity and Presidential Dominance: Parliamentary Development in the Fourth Republic of Ghana,” JournalofContemporaryAfricanStudies, Vol.30, No.3, 2012, p.431.同时军队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军队已不再作为国家安全功能的唯一主导和执行方,而是作为安全机制的一部分而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为防止军人干政提供了制度保障。[注]Emmanuel K.Aning, “Ghana Election 2000: Implications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AfricanSecurityReview, Vol.10, No.2, 2001, pp.39~40.其次,政治格局开始由“单极—多元”转为两极化。新爱国党的发展和全国民主大会党的相对衰退使双方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的均衡局面,而恩克鲁玛派各党因进一步分裂而导致瓦解或改组,其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自2000年后,加纳政坛已形成两党势均力敌、轮流执政的局面,尤其是在政府换届的2000年和2008年大选中均出现了因当选人支持率不过半,且竞选双方差距微弱而重选的情况。再次,民主监督得以有效保障,全国民主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等机构的法律权威和独立作用愈发明显,[注]Emmanuel Debrah, “Measuring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Success in Ghana: The Case of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993~2008,” AfricanStudies, Vol.70, No.1, 2011, p.37.媒体舆论和国外第三方机构(如外国观摩团、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特使等)的作用也得以充分发挥。[注]Jonathan Temin, D.A.Smith, “Media Matters: Evaluating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Ghana’s 2000 Elections,” AfricanAffairs, Vol.101, No.405, 2002, pp.590~594.最后,在政治平衡下,政府致力于发展党内民主,打击腐败和政治庇护,淡化政党地方性和族际性,[注]Joseph R.A.Ayee,“The Evolution of the New Patriotic Party in Ghana,” SouthAf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15, No.2, 2008, pp.196~201.使得地方民族主义在政治生态中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从结果来看,历次大选中竞争双方及其代表族群均能够尊重选举结果,实现政权平稳移交,而未出现大规模骚乱和冲突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政治平衡下,以往零和博弈式的政治斗争得以扭转,政治生态已趋于理性和秩序化。
表5 2000~2016年加纳政党选举简况
时间主要政党候选人所属部族总得票率(%)得票最高地区该地区得票率(%)该地区得票占总得票比(%)2000全国民主大会党约翰·米尔斯沿海部族44.8沃尔特省88.817.6新爱国党约翰·库福尔阿坎族48.4阿散蒂省75.530.62004全国民主大会党约翰·米尔斯沿海部族44.6阿克拉特区46.321.1新爱国党约翰·库福尔阿坎族52.4阿散蒂省74.627.32008全国民主大会党约翰·米尔斯沿海部族50.2阿克拉特区52.121.4新爱国党阿库福—阿多阿坎族49.8阿散蒂省72.429.22012全国民主大会党约翰·马哈马北方部族50.7阿克拉特区48.323.3新爱国党阿库福—阿多沿海部族47.7阿散蒂省73.928.82016全国民主大会党约翰·马哈马北方部族44.5阿克拉特区46.719.8新爱国党阿库福—阿多沿海部族53.7阿散蒂省76.028.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加纳选举委员会(Electoral Commission of Ghana)历年统计数据自制。
在社会经济方面,这一阶段加纳经济发展在经历了短暂调整期后,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尽管罗林斯时代的经济调整和恢复计划在宏观上扭转了加纳经济衰退的局面,但其中一些短期措施(如大量借债、货币贬值和提高税收)也出现了一定的后遗症,其中政府投资项目收益缓慢、财政长期赤字和国内通货膨胀不断加剧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制约加纳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注]Emmanuel Kwesi Anning, “Ghana Election 2000: Implications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AfricanSecurityReview, Vol.10, No.2, 2001, p.44.2000年后,新爱国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纠治积弊,调整发展战略。首先,放缓货币贬值速度,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其次,加入“重债穷国协议”(HIPC),力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债务减免,而不是将无限制货币贬值作为降低债务的唯一方式。再次,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继续加大对工业和服务业的投入,推动制造业、通信、能源、冶金和运输业等的全面发展。[注]Joseph R.A.Ayee,“The Evolution of the New Patriotic Party in Ghana,”SouthAf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15, No.2, 2008, pp.198~199.上述措施促进了政府财政平衡,缓解了社会压力,增加了政府投资和公共服务力度,优化了产业结构。2005年以后,加纳GDP以年均8.8%的速度增长,人均GDP和人均GNI也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见表6)。与此同时,社会贫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05年的31.9%降至2012年的24.2%。随着政府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加大,出生婴儿存活率和基础教育入学率都有显著提高。此外,政府还长期致力于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建设,提高工资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表6 2006~2017年加纳经济发展简况(单位:美元;%)
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GDP总值204亿247亿285亿260亿321亿395亿419亿478亿390亿373亿428亿473亿GDP增率———21.315.2-8.923.823.06.014.0-18.2-4.514.610.6人均GDP92210901224108613121574162918141449135315171641人均GNI6008001160120012501400156018901940196018401880
资料来源: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ghana?view=chart。
总体上看,近20多年来,加纳国家建构步入了一个以民主机制为根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良性发展的新路径。在此之下,加纳民族建构的进程也随之不断提速,加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呈现出较好的稳定发展态势。首先,尽管政治生态中精英政治和族际政治成分还未完全消除,但威权主义因素几乎已不存在,民主体制日趋成熟。政治博弈已不再以文明、族群之间的冲突为显性特征,不同阶层、不同部族的政治诉求和参与能够在民主政体中得到合理释放。其次,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区域统筹规划的不断加强、社会公共建设的不断发展,沿海与内陆地区、主体族群与边缘部族、城镇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不断缩小,各部落和族群均能够在加纳一国范围内实现生存和发展,并在资源竞争和文化交流上实现常态秩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有效缓和了因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的族际矛盾,促进建立在族群和解之上的全国性政府的发展。全国性政府的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规划和社会建设,为民族观念的构建提供现实环境。再次,在意识形态上,加纳公众意识在民主化的影响下已不再以某种单一意识形态为主导,而是在多元意识的基础上整合和发展。[注]Eric O.Wiafe, TowardsaNewConsciousnessforaBetterAfrica:SomeTopicalIssuesinGhana,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0, p.21.而精英意识也不像以往那样具化为多种意识集团的分立,而是形成两级并立。精英意识的主导性已由个体性向共同性转变,精英意识的趋向性也从追逐私利向追逐价值转变。因此,民主化一方面为公众权利和个体自由的实现提供了现实载体;另一方面又为精英与公众之间共同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导向。公民社会理念已从一种观念上的海市蜃楼变成一种在现代国家框架内和民主机制下的全民性共同意识,这种共同意识对加纳民族意识的构建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当前来看,尽管加纳统一民族观念尚在孕育和发展之中,但未来加纳民族国家建构之路必将减少不少坎坷。
五、结 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纳民族国家建构既符合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一般模式,也体现了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前殖民时期以阿散蒂王国为框架、以阿坎族为载体的自发性民族国家建构,还是去殖民化以来以加纳现代国家为框架、以加纳统一民族构建为载体的外来化民族国家重构,都是在“先国家再民族”的整体模式下进行的。与非洲大部分国家一样,现代加纳国家的成立和民族构建进程的开启都始于现代国家理论下的去殖民化运动,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传统与现代化、本土与外来化之间的斗争而在反复和曲折中徘徊。同时,外部干预下的民主化改革为加纳民族国家建构走向良性发展轨道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后发型”、“反复性”和“外部干预”特征在加纳一国中也得以很好地体现。
但是,加纳民族国家建构也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那就是本土文明主导的自发性民族国家建构与外来化文明主导的民族国家重构在现代加纳国家领土空间内并非完全呈现出时间上的先后存在,而是一种交叉式的递进,这两种体系的对立成为制约加纳统一国家和统一民族构建的桎梏。而加纳之所以能够成功打破这一桎梏以促进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因为充分将外来化民主模式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走出一种适合本国实际需求的民主化发展路径,从而实现政治平衡、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文化交融和族群和解,并促进统一民族观念的构建。这充分证明了一国须与时俱进,不断扬弃自身既有文明体系,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辩证发展,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洲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须在一个以本土实际为根基并持续从外来理论中汲取养分的理路下进行。今天,加纳民族国家建构已呈现出较好的局面,而随着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不断加快,未来我们还将能够从更多的国家中寻找例证。
“作文难,难文”这是小学语文教师的深切体会。老师教的筋疲力尽,学生写的痛不欲生,这是小学作文教学的常态。要想孩子们对作文产生浓厚的兴趣,消除畏难心理。新课标中所指出的“中年级学生要留心周围事物,乐于书面表达,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小学三年级学生作文的起步阶段,教师对学生兴趣的培养比对作文方法的教学更重要。如何培养学生对作文的热情,带领孩子们开启作文的兴趣之门呢?
[作者简介]艾俊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德凯,四川警察学院助理研究员
*感谢《国际关系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
标签:国家论文; 非洲论文; 民族论文; 加纳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各国政治论文; 非洲政治论文; 《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四川警察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