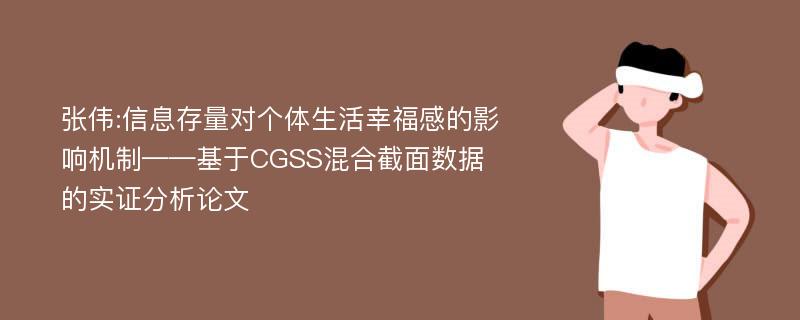
摘 要:基于CGSS混合横截面数据,探讨了信息存量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信息存量作为一个复合性概念,在实践中可操作化为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和媒介信息获取频率。以此为基础,通过建立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结果:首先,教育和媒介信息获取频率对个体的生活幸福感均具有正向影响;其次,2010—2013年这三年间,受教育年限和新媒介信息获取频率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保持稳定,而传统媒介信息获取频率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则呈逐渐削弱的态势;最后,信息存量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在以对内的“经济状况评价”和对外的“社会公平认知”为中介时,受教育年限和媒介信息获取频率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路径表现出较大差异。
关键词:信息存量;教育;媒介;个体生活幸福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一、问题的提出
英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其1817年发表的《略论古今社会状况所造成的一些谬见和弊害》一文中指出:“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1]那么究竟怎样的生活才称得上幸福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给出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描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民的生活幸福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7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国大陆地区的幸福指数分值为5.273,位列第79位。该报告还指出:“中国人并不比25年前生活得幸福。这里的福利继续落后于经济增长,在过去25年中,中国的经济产出增加了五倍,但在1990年到2005年间,幸福感下降了。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人们的幸福度仍然低于25年前。”[2]由此印证了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提出的“幸福悖论”[3],即国家经济增长不会必然提升国民的生活幸福感。
在解这道题时,学生就要先分析电阻与滑动变阻器的串并联关系,找到电表测量的用电器,仔细的分析电路图,当滑片b端滑到a端时,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变化情况。在结合题目所给已知条件求解问题。
事实上,影响幸福的因素多种多样,经济状况只是其中一种。在信息社会,信息存量的多少逐渐成为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指标。这里所说的信息存量是一个增长性概念,它不仅指代个体已知的信息量,还包括个体从外界获取的信息量。对个体而言,信息存量也会影响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评价。幸福作为一种主观生活状态,其高低等级并不取决于他者的眼光,而是个体在综合众多权重不一的参照物后做出的自我评价,因此,个体的信息存量与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就像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一样,需要进行细致的考虑。一方面,信息存量可以被视作一种“文化资本”,①“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厄将资本具体划分成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且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它不仅影响到个体能够获取的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也会通过多种机制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4],从而可以认为信息存量越大,个体幸福的可能性越高[5];另一方面,信息存量越大,个体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也越全面和深入,当现实情境与理想状况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差距时,个体内心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力感也会越强,进而降低个体的幸福感。此外,信息的指向也会影响人们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评价。如同李普曼所言,“外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可能有所差异”[6],也就是说,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呈现出来的。因此,获得越多负面的、消极的信息,人们可能越痛苦;反之,获得越多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人们可能越幸福。
一位成功的画家必具两个基本品质:认真地面对客观世界,在观察、分析中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汲取创作的灵感;善于审视和寻找自我,不断从自我的体悟中发掘自己的才智与潜能,找到自身在艺术中的位置。对艺术家来说,表现客观世界和表现自我,应该是合二为一、互为表里的。从表面上看,画家画的是客观对象,实际上是在画自己,是在呈现自己的主观世界。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断摄取信息几乎成为每一个人本能性的生命活动。这种活动真的有助于推动人们达成“获取幸福”这一人生目标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用受教育年限和媒介信息获取频率来衡量个体的信息存量,同时将媒介划分为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两种类型,然后分别考察它们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
这种模式较适于土地紧张的中小肉牛场。购置粪肥一体化发酵设备,固体粪污置于反应器内进行好氧发酵,发酵周期一般为7~12天,发酵后的粪肥可作为有机肥出售,液体粪污通过污水池处理后还田。该模式优点是发酵周期短,占地面积小,自动化程度高,密闭系统臭气易控制;缺点是处理量小,投资较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生活幸福感与需要的满足程度具有重要关联。格雷认为,“人的需要有两种:一是作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二是作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第一种需要表现为人对食物、衣服和住房的需求,即生存所需的物质保障;第二种需要则表现为人所具有的求知欲望,即精神需要的满足,“人的天性使所有的人都具有求知欲;然而我们要在精神上得到幸福,那么就必须使智慧的种子——求知欲——开花结果,否则它会白白埋在那里,得不到什么益处”[7]。如何满足求知欲呢?格雷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习惯、周围的人们的榜样或影响来达成。由此可见,教育是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最重要条件之一。绝大多数学者都支持教育对生活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例如,奥斯瓦尔德(Oswald)认为教育与生活幸福感之间的正向相关是一个基本性的结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具有较高生活幸福感的居民的基本特征[8];布兰奇福劳(Blanchflower)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对人们的生活幸福感有较强的正效应,即使控制了收入,教育对生活幸福感仍然有显著影响[9]。
在生活幸福感的经验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调查都将因变量生活幸福感设置为定序层次的变量,因此建立有序选择模型是最为恰当的。虽然很多研究表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或是序次Logistic/Probit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具有稳健性[23],但是,基于如下两方面的考虑,本文选用序次Logistic模型来呈现变量间的关系结构:第一,由于有序选择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使用OLS方法并不能消除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尽管OLS方法可以得到这种情形下参数估计量的稳健标准误,但参数估计量本身不再是有效的。第二,在有序选择模型中,参数估计量衡量的是解释变量的变化导致被解释变量取某一个值时概率的变动,如果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可能使被解释变量的取值超出有效范围,此时考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没有意义。
在信息时代,个体的教育程度虽然与其信息存量呈现正向关联,但这种关联的强度也要相对削弱很多。其原因可归结为两点: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教育程度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呈现不断缩减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用一个人的教育程度来衡量其信息存量可能会有所偏颇;第二,普遍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并没有消除不同个体之间的“信息鸿沟”,这来自人们信息素养上的差异,而在信息素养的核心构成中,最重要的是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那么,信息来自哪里呢?对一般人来说,当今社会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就是媒介。因此,一个人的信息存量还可以通过其使用媒介的频繁程度体现出来。事实上,利用媒介来获取信息是维持人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途径,同时信息还是一种文化资本,对社会中的个体而言,获取信息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活动,它还是向其他场域如经济、社会等流通或竞争的惯习资源[18]。
实质上,更多的研究表明,教育这一变量所对应的系数值往往会随着模型中其他变量的纳入而发生变化。罗楚亮对中国城镇居民生活幸福感与教育和收入关系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主观上感觉幸福的比例越高,但在控制了收入等变量后,受教育水平高的居民感觉幸福的比例反而会更低[14]。 奇斯(Knight)等人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教育的解释系数因模型中引入变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具有不稳定性[15]。
CGSS 2010年、2012年和2013年度的问卷都在“社会态度”这一测量模块设置了反映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可供选择的回答包括: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其编码为1~5。因变量“生活幸福感”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分布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三年间的差异不大,较多的人处于“比较幸福”的水平,且在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上升状态。
根据上述分析,当把教育状况作为一个衡量个体信息存量的测度标准时,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教育程度对个体的生活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且其中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
(二)媒介使用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与此同时,另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些研究表明,教育与人们的生活幸福感之间没有关系[10],或仅存在非常微弱的联系[11]。 还有些研究从期望理论出发,认为教育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负向的。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期望理论,人们是否感到幸福取决于其期望是否得到满足,过高的期望会对人们的生活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而更高的教育水平使人们的期望水平提高,因而不利于生活幸福感的提升[12]。例如,斯塔特勒(Stutzer)的研究发现,受过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其幸福感高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认为其原因是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收入期望低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期望容易得到满足,因而幸福感也会处于较高的水平[13]。
在媒介化的信息社会中,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感知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形式的媒介。当媒介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时,媒介内容对社会真实的再现将有力地塑造甚至扭曲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例如,人们看电视越多,就越会认为真实世界像电视中所描绘的那样。有研究发现,大量收看电视节目和广告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大多数人都像电视里表现的那样富裕和舒适,从而高估社会中的平均生活水平[19]。由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与他人比较的基础之上,因此当人们相信社会上的其他人都比自己过得好时,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评价则会随之降低,并且,这种比较不仅发生在同一群体中的不同成员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基于这一理论,媒介信息事实上构成了个体在评价自身生活状态时的参照系统,个体通过对比媒介中“一般化他人”的生活状态,形成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认知和评价,如果这种媒介生活状态是偏于理想的,那么个体自评的生活幸福感就会偏低;反之,个体自评的生活幸福感则会偏高。
式中:α为归一化的反应进程;A为指前因子;n为反应级数;E为活化能;R为理想气体常数;t为反应时间,T为样品温度。在绝热追踪阶段,当环境温度和样品温度时刻相等时,满足样品反应自放热完全用于系统温度升高的条件,则可得到热平衡方程:
综上所述,本文继续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媒介信息获取的频繁程度对个体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由于不同媒介在拟态环境塑造上的差异,它们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传统媒介信息获取越频繁,个体的生活幸福感越高;新媒介信息获取越频繁,个体的生活幸福感越低。
“拟态环境论”提供了理解媒介与个体幸福感关系的另一个视角。该理论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主观现实”是在人们对客观现实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为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一种“拟态”现实[20]。这种拟态现实与人们的生活感受息息相关。由于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评价不仅局限于自身,还来自个体对所处环境的感知,这里所说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谓的“拟态环境”,相对于生活在混乱无序环境中的个体,处于健康有序环境中的个体在评价自身生活状态时有可能给予更高的估计。因此,个体对自身生活幸福感的评价不仅与其媒介信息获取情况有关,还与其使用的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有密切关联。就中国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报纸、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介相对而言受到较强的行政约束,因而它们塑造的拟态环境在价值导向上较为积极;与此不同的是,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媒介更为开放自由,由于信息源的散布性以及信息传播的实时性,人们透过新媒介所感知到的是另一种拟态环境,它们在价值导向上可能更为消极。
1.1 调查对象 2016年在某地区部队医院接受健康体检的海勤人员,包括在该医院参加统一健康体检的某部队干部、士官和战士。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和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2012年和2013年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上述三个年度的社会调查均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分别在全国范围内抽取480个村/居委会,再从每个村/居委会抽取25个家庭,并利用KISH表确定被访者,最后以结构化访谈的形式获得调查资料,三个年度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量分别为11783、11765和11438。自2010年开始,CGSS使用的调查问卷在问题的设置上基本保持一致,这就为研究者构造混合横截面数据(Pooled Cross-Sectional Data)提供了便利。相较于单一年度的横截面数据,混合横截面数据拥有更大的样本规模,可以使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加准确;它还能同时呈现变量关系在时空上的变化,进而增强数据分析的深入性[21]。剔除在主要变量上存在的缺失个案后,本文使用的数据共计包含28557个有效样本。
(二)因变量
相关研究中更准确的一种处理方式是将教育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部分,其中,直接影响可以理解为教育活动本身给人们带来的积极的心理或精神体验,而间接影响则是教育通过影响收入等其他变量进而对人们生活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沿袭这种思路,一些研究者对教育影响生活幸福感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Cuñado和 Gracia认为,教育可以通过收入和劳动地位对生活幸福感产生影响,并且教育对生活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正向效应[16];金江与何立华在对武汉城镇居民教育与生活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将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作为教育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17]。
表1 因变量的频数分布表(N=28557)
2010年2012年2013年 合计生活幸福感 频数 % 频数 % 频数 % 频数 %非常不幸福 188 2.00 150 1.51 134 1.45 472 1.65比较不幸福 707 7.50 692 6.98 660 7.15 2059 7.21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1636 17.36 1492 15.06 1646 17.84 4774 16.72比较幸福 5373 57.03 5935 59.90 5525 59.88 16833 58.95非常幸福 1518 16.11 1639 16.54 1262 13.68 4419 15.47合计 9422 100 9908 100 9227 100 28557 100
(三)自变量
教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传授过程,因此,能够反映个体信息存量的最直观的操作化指标就是教育程度。为了方便后期的数据分析,本文使用定量社会研究中常用的处理方式[22]将CGSS数据中对教育程度的编码转化为尺度变量“受教育年限”,具体规则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0;私塾、扫盲班=2;小学=6;初中=9;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①由于样本中选择最高教育程度为“其他”的个体只有15人,且未注明具体内容,因此,本文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将其视作缺失值。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受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87年,标准差为4.590年,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年和19年。
根据前文的分析,信息存量还可以测量为个体使用各种媒介获取信息的频率。CGSS问卷利用5级李克特量表将个体使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等媒介获取信息的频率编码为: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非常频繁。上述6个问题之间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为 0.6740,在统计学上处于可接受的水平,因而在测量上具有内部一致性。将反映这6个问题的变量纳入因子分析模型,可形成“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两个因子,其中前者在使用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获取信息上的载荷显著,后者在使用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两个变量上的载荷显著,具体如表2(见下页)所示。这一结果与本文的理论设想相一致。
(四)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将一系列可能影响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分析模型。这些控制变量共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民族、宗教、户口和婚姻;第二类为家庭状况的测度变量,包括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名下是否拥有住房和子女数量;第三类为身体状况的测度变量,包括自评的身体健康状况和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简称BMI);第四类为工作和社交状况,包括是否有全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长、社交/串门的频率以及工作之余的休息放松状况。除此以外,本文在后续的分析模型中还加入了调查年份和受访者所在的省份为虚拟变量,以控制变量影响上的时空效应。四类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媒介使用状况描述及因子载荷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子载荷①(传统媒介)报纸 2.184 1.279 1 5 0.757杂志 1.858 1.041 1 5 0.647广播 1.864 1.170 1 5 0.629电视 4.143 0.959 1 5 0.600(新媒介)互联网 2.063 1.505 1 5 0.818手机定制消息 1.578 1.089 1 5 0.760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8557)
分类 变量 均值 标注差 最小值 最大值性别(男性=1) 0.505 0.500 0 1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 48.233 15.700 17 97年龄平方 2572.902 1584.027 289 9409民族(汉族=1) 0.914 0.281 0 1宗教(信仰宗教=1) 0.877 0.329 0 1户口(非农业户口=1) 0.469 0.499 0 1婚姻(已婚=1) 0.821 0.383 0 1家庭状况家庭收入的对数 10.290 1.072 4.605 15.607拥有的房产数量 1.102 0.546 0 10子女数量 1.743 1.287 0 11身体状况自评的健康状况 3.633 1.095 1 5身体质量指数 45.195 6.929 19.253 284.799工作和社交状况工作状况(有工作=1) 0.649 0.477 0 1每周工作小时数 30.813 26.804 0 84社交/串门的频率 2.749 1.028 1 5休息放松状况 3.399 0.949 1 5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混合横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
(2)由l1⊥l2发现k1k2=-1是个难点,教学中您并没引导学生发现这个结论,比如,用几何画板动态演示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斜率之间的关系,或者让学生计算两条直线倾斜角分别为30° 和120° ,60° 和150° ,45° 和135° 时,k1与k2的关系,由特殊猜想出一般的结论,然后再进行证明.您是开门见山,直接让学生寻找k1与k2的关系,这样做是不是为后面的教学多留一些时间?
表4汇报了混合横截面数据的序次Logistic估计结果。考虑到年份和区域可能带来的影响,表4中包含的5个模型均加入了年份虚拟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在这5个模型中,模型1汇报了基准模型(不包括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及其媒介信息获取频率等反映个体信息存量的变量)的估计结果,根据这一结果,纳入模型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家庭、身体以及工作和社交等四个层面的控制变量至少在5%的水平上对个体的生活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表4 混合截面数据分析结果
注:∗∗∗p<0.01,∗∗p<0.05,∗p<0.1;括号里是稳健的系数标准误;为节省篇幅,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包括省份虚拟变量)与常数截点的输出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教育年限 0.019∗∗∗ 0.008∗∗ 0.013∗(0.004) (0.004) (0.007)新媒介使用频率 0.038∗∗ 0.029∗ 0.012(0.016) (0.017) (0.028)传统媒介使用频率 0.151∗∗∗ 0.143∗∗∗ 0.197∗∗∗(0.014) (0.015) (0.025)教育年限×2012 年 -0.009(0.009)教育年限×2013 年 -0.005(0.009)新媒介使用频率×2012年 0.013(0.036)新媒介使用频率×2013年 0.035(0.037)传统媒介使用频率×2012年 -0.061∗(0.033)传统媒介使用频率×2013 年 -0.104∗∗∗(0.035)年份(2012 年) 0.070∗∗ 0.070∗∗ 0.077∗∗∗ 0.077∗∗∗ 0.079∗∗∗(0.030) (0.030) (0.030) (0.030) (0.030)年份(2013 年) -0.239∗∗∗ -0.237∗∗∗ -0.217∗∗∗ -0.216∗∗∗ -0.219∗∗∗(0.030) (0.030) (0.030) (0.030) (0.030)控制变量 √ √ √ √ √N 28,557 28,557 28,434 28,434 28,434-2LL 4372.94 4399.34 4468.16 4472.58 4490.48 Wald χ2 3763.97 3809.60 3902.84 3909.51 3920.77 Pseudo R2 0.0662 0.0666 0.0679 0.0680 0.0683
以往学者在分析教育和幸福感的关系时往往以经济收入为中介变量,其潜在逻辑是文化资本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进而影响个体的生活状态。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个体层面的文化资本积累与其信息获取能力具有重要关联,也就是说,知识和信息可能都会对个体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生活幸福感。为此,有必要将个体的经济状况作为中介变量加入结构方程模型之中。就此而言,由于个体对自身生活幸福感的评价具有主观性,选择同样具有主观性的个体对自身经济状况的评价来测量个体的经济状况比绝对的经济收入可能更适合。除此以外,信息存量又会直接影响个体对社会环境的感知,处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个体为改善自身生活状况而进行的劳动付出更有获得回馈的可能,因此,社会公平感可能是另一个信息存量影响个体生活幸福感的中介变量。这就从内外两个方面构建起信息存量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作用路径,最终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及使用极大似然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
模型3则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中的信息获取频率作为解释变量,相较于基准模型,模型3的似然比卡方检验统计值增长了95.22,对应的p值小于0.01,因此,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这两个解释变量。根据模型3的估计结果,使用传统媒介和新媒介获取信息的频率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其中前者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后者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接触传统媒介中的信息越频繁,越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此外,虽然很多人认为互联网等新媒介中的信息会更加真实地呈现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放大效应”,因而接触新媒介中的信息越多,个体也就越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幸福,但是,模型3中数据分析的结果却与此相悖:不管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个体获取的信息越多,越倾向于认为自身具有较高的生活幸福感。
模型4同时加入个体的受教育年限以及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中的信息获取频率到模型之中,与模型1相比,该模型的似然比卡方检验统计值增长了 99.64,对应的 p 值小于 0.01。 根据模型 4,本文用以测量个体信息存量的两个层面的解释变量“受教育年限”及“媒介信息获取频率”均对个体的生活幸福感发挥显著的正效应,其中,受教育年限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新媒介中的信息获取频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传统媒介中的信息获取频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与在基准模型上分别各加入受教育年限以及媒介信息获取频率进行估计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模型5则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受教育年限、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中的信息获取频率与年份虚拟变量(以2010年为基准)的交互项。之所以进行如此处理,是因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可以反映信息存量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在2012年和2013年相对于2010年的变化,这也是使用混合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时具有的一项优势。根据模型5的估计结果,受教育年限及新媒介信息获取频率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说明教育以及新媒介使用状况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在2010年到2013年间保持基本稳定的状态;传统媒介信息获取频率与2012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61(10%水平显著),说明相对于2010年,传统媒介使用状况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在2012年缩减到原来的94.08%;传统媒介信息获取频率与2013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04(1%水平显著),说明相对于2010年,传统媒介使用状况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在2013年进一步缩减到原来的90.14%。
(二)信息存量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根据混合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受教育年限、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中的信息获取频率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在近年来的动态变化。由于受教育年限、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中的信息获取频率反映的都是个体的信息存量,前文的分析结果表明,信息存量越大,个体的生活幸福感也越高。但是,这种正效应是通过何种方式发挥影响的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使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信息存量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模型2汇报的是在基准模型上加入受教育年限后的估计结果。相对于模型1,模型2的似然比卡方检验统计值(-2LL)增长了26.40,对应的p值小于0.01,说明加入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来估计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能改善模型的估计效果。就其具体影响而言,回归系数0.019表明在控制变量取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个体,有更高的概率在评价自身生活幸福感时给出更高的评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中的部分内容,即教育程度对个体的生活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归根结底,若要真正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打而不死的“千年僵尸”,还得从两个方面去着力:一是建立科学的工作考评机制和选拔任用机制,使踏踏实实干事的人得到承认,不让老实人吃亏,进而更好地鼓励人们干实事务实效,而不是靠官僚主义来推进,靠形式主义来“完成”;二是疏通民主渠道,推进制度创新,为群众监督创造有利条件,使不科学不合理甚至错误的决策能得到纠正,避免其催生形式主义,滋养官僚主义。而这,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图1 信息存量影响个体生活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图1中的估计结果,经济状况评价和社会公平感在信息存量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上都起到部分中介效应。由于个体的经济状况评价和社会公平感这两个变量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30和 0.54,均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都呈现为一种正向的效应,这也支持了本文提出的观点:个体对自身生活幸福感的评价一方面来自自身的相对生活水平,另一方则依赖于所处社会环境的公平性。此外,从个体信息存量对其生活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来看,受教育年限以及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中的信息获取频率在分别以经济状况评价和社会公平感为中介时所发挥的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而言,个体的信息存量越大,那么他自评的经济状况也倾向于越好(各路径系数均在0.01的水平上呈现出正向效应),这也间接增强了个体的生活幸福感;但是,个体的信息存量对其社会公平感所发挥的作用则存在差异性,其中,教育年限对社会公平感的路径系数为-0.046,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在以社会公平感为中介时发挥的是消极影响,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更高教育所产生的个体对社会公平的更高期望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偏差。在信息媒介上,使用传统媒介和新媒介获取信息的频率对人们社会公平感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024 和-0.061,分别在 0.05 和 0.0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是相吻合的:“议程设置”更容易在传统媒介中发挥作用,传统媒介中所传递的信息更具有积极的导向性,因而接触这方面的信息越多,社会公平感也越强,从而能间接增强个体的生活幸福感;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相比,进一步消弭了传统社会话语权和信息传播权的中心化状态,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信息透明度和意见表达的均衡性与多元化,建构了对于真相追逐的公共空间”[24],因而在特定的时间阶段,个体通过新媒介获取的信息越多,其社会公平感越倾向于更低,这会间接削弱个体的生活幸福感。
总而言之,信息存量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过程,从直接的路径上来看,它能发挥正向效应;但从间接的路径上来看,它所发挥的效应又因不同的中介变量而有所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在宏观社会层面上,信息是界定当今时代特征的重要属性,它本身即是社会的重要财富,不仅如此,信息流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信息源成为社会中的重要权力源;在微观个体层面上,信息也会影响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及所处社会境况的认知。本文首先利用CGSS 2010年、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构成一个规模更大的混合横截面数据,然后从受教育年限和媒介信息获取频率两个维度来界定个体的信息存量,最后通过序次Logistic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它们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作为衡量个体信息存量的两个维度,受教育年限和媒介(包括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信息获取频率都对个体的生活幸福感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个体的信息存量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对自身的更多理解,同时也会拓展与外在世界的紧密连接[25],这在事实上强化了个体能够感受幸福的能力。除此以外,在个体的生活领域,信息还会以两种方式来增进人们的生活幸福感:一是它给我们开辟了享乐的新的源泉;二是它给我们提供了选择一切其他乐趣的线索[26]。也就是说,人们所获取的信息契合并拓展了人类作为高级生命有机体所需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因而能够直接促进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英法限定词在类别用法上有着相似之处,例如英语里a fish,the fish,some fish在法语里都能找到对应的冠词,即un poisson,le poisson,du poisson。但不同的是,在法语中,除了特定情况,一般名词前面都需要用限定词来修饰,而英语里面,则出现了一个叫作“零冠词”的概念——即名词前面没有不定冠词、定冠词也无其他限定词的现象,例如表示抽象概括意义时,不可数名词或复数名词前就用零冠词,好比语料中的题目,法语原题为 De l’oysiveté,“l’”原形为定冠词“la”,但是参考多个英译本,题目翻译均为省略了冠词的Of idleness。
其次,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受教育年限以及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中的信息获取频率与年份的交互项,阐明了信息存量对个体生活幸福感影响的变化趋势。具体而言,受教育年限以及新媒介信息获取频率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在2010年到2013年间保持基本稳定的状态,而使用传统媒介获取信息的频率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则在这几年间呈现出逐渐缩减的趋势。教育的影响保持稳定缘于教育结构和教育效应的稳定性,新媒介使用状况的影响保持稳定则可能来自问卷测量上的不足。根据数据分析过程,新媒介的使用状况通过CGSS问卷中的两个测量项目反映出来,即“过去一年中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和“过去一年中使用手机定制消息的频率”,而事实上,随着手机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以及网络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包括移动社交网络和移动资讯应用在内的新媒介逐渐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由于未将这种新变化考虑进来,新媒介使用状况也就保持了一种相对的稳定性。传统媒介信息获取频率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逐渐缩减则与传统媒介的两个发展趋向密切相关:一是整个媒介生态中传统媒介影响的式微;二是传统媒介的转型使其内容生产逐渐细分和专业,同时削弱了议程设置的功能。
最后,信息存量对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它除了发挥直接的增益效应之外,还会以个体的相对经济状况和对社会公平性的评价这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为中介而发挥不同的间接效应。从对内的经济状况评价来看,在现代社会,能否获取信息以及获取信息的程度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个体获取社会资源和改善生活质量状况的能力,从而影响到个体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评价,并进而影响到个体的生活幸福感。从对外的社会公平性评价来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个体会产生一种关于社会公平性的上行期待,这就造成了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反而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更低,由于社会公平感对个体的生活幸福感有着正向影响,从而在以社会公平感为中介的路径上,受教育程度会削弱个体的生活幸福感;媒介信息获取频率对个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则与我们日常感知的情境相符合,具体而言,使用传统媒介获取信息越频繁,个体的社会公平感越高,进而也会增强个体的生活幸福感,反之,使用新媒介获取信息越频繁,个体的社会公平感越低,进而则会削弱个体的生活幸福感。根据新闻传播学中的媒介依赖和议程设置等相关理论,社会公众通常无法直接达成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而需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来实现,但是,大众传播媒介不会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而是塑造一种象征性现实,它对社会公众的认知具有明显的建构作用。相较于传统媒介,新媒介更少受到议程设置的影响,因而新媒介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舆论场,人们通过其中的信息认识到切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可待改进的社会境况。因此,在以社会公平感为中介时,媒介信息获取频率的影响会因媒介性质而有明显差异。
本文的研究仍有不足,例如,信息存量在测量中最好是一个整合性概念,用受教育年限和媒介信息获取频率来衡量在概念操作化的严谨性上有可商榷之处;此外,在模型的设计上还可以补充一些新的变量以提升模型的整体解释效力。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未来的研究加以改进。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各级工会要以中国工会十七大为重大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勇于担当、锐意进取,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奋力谱写新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英]罗伯特·欧文.欧文选集:第1卷[M].柯象峰,何光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20-221.
[2]HELLIWELL J, LAYARD R, SACHS J.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7[R].New York: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2017.
[3]EASTERLIN R.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G] //DAVID P A,REDER M W.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89-125.
[4]郭慧玲.由心至身:阶层影响身体的社会心理机制[J].社会,2016,(2):146-166.
[5]BUKENYA J O, GEBREMEDHIN T G, SCHAEFFER P V.Analysis of Quality of Life and Rural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West Virginia Data[J].Growth and Change,2003,34(2):202-218.
[6][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23.
[7][英]约翰·格雷.人类幸福论[M].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11.
[8]OSWALD A J.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The Economic Journal,1997,107:1815-1831.
[9]BLANCHFLOWER D G,OSWALD A J.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7-8):1359-1386.
[10]FLOURI E.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idlife: The Role of Involvement of and Closeness to Parents in Childhood[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4, 5 (4):335-358.
[11]INGLEHART R, KLINGEMANN H.Genes, Culture,Democracy, and Happiness[G]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MA:MIT Press Cambrige, 2000:165-183.
[12]WILSON W R.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67, 67(4): 294-306.
[13]STUTZER A.The Role of Income Aspirations in Individual Happines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2004, 54(1):89-109.
[14]罗楚亮.教育、收入与主观幸福感[J].理工高教研究, 2006, (1): 1-5.
[15]KNIGHT J, SONG L, GUNATILAKA R.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4):635-649.
[16]CUNADO J, GRACIA F P.Does Education Affect Happiness? Evidence for Spain[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2, (1):185-196.
[17]金江,何立华.教育使人幸福吗?——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12, (6):36-43.
[18]郑恩,龚瑶.新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56-64.
[19]SIRGY M J, LEE D, KOSENKO R, et al.Does Television Viewership Play a Role in the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 [J].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98, 27(1):125-142.
[20]曹劲松.论拟态环境的主体建构[J].南京社会科学,2009,(2):98-103.
[21]PENNINGS P,KEMAN H,KLEINNIJENHUIS J.Doing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Methods and Statistics[M].Sage,2006:172.
[22]贺光烨,吴晓刚.市场化、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中的性别收入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15, (1):140-165.
[23]FERRER-I-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5-6):997-1019.
[24]喻国明.微博影响力的形成机制与社会价值[J].人民论坛,2011,(34):9-11.
[25]CHEN W.How Education Enhances Happiness: Comparison of Mediating Factors in Four East Asian Countrie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2, 106(1):117-131.
[26][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1卷[M].柯象峰,何光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06-207.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Stock on Individual’s Happiness——Findings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s
ZHANG We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The impa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information stock on individual's happiness is discussed by analyzing the pooled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CGSS.As a complex concept, information stock can be operationalized to one's education and medium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 practice.On this basis, the paper gets some results by using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generaliz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thods.First, education and medium information retrieval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individual's happiness.Second, from 2010 to 2013,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and new medium information retrieval on individual's happiness remains stable,whereas it continues to decline for traditional medium information retrieval.Finally,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stock on happiness is complex.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paths of education and medium information retrieval on happiness when taking the internal“subjectiv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external“social justice cognition” as mediator variables.
Key words: information stock;education; medium;individual life happiness; CGSS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4-0062-10
收稿日期:2019-03-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质量理论视野下的网络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的建构研究”(18BSH032)
作者简介:张伟(1986—),男,江苏邳州人,讲师,博士,从事网络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唐魁玉]
标签:媒介论文; 个体论文; 幸福感论文; 信息论文; 变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质量理论视野下的网络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的建构研究”(18BSH032)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