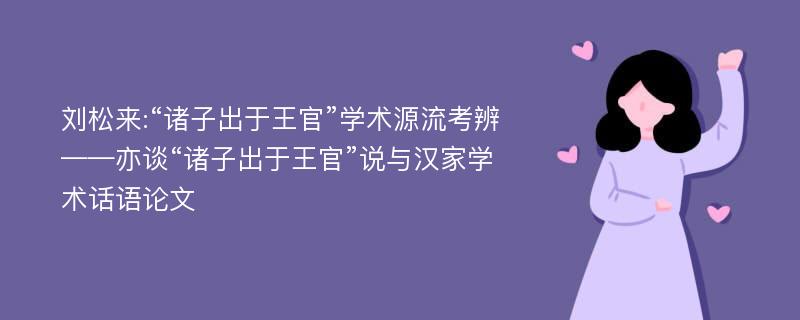
[摘要]《诸子略》中揭橥的众家学术高下之别,实为晚周诸子争鸣的结果。其中“诸子出于王官”说对《周官》的附会,乃是刘歆借古文经学套路树立“学术出于王官”文化理念的有益尝试。刘歆以《七略》传达“学术出于王官”理念之意图,为的是承接宗周以王官之学分掌典册之传统,进而通过有意识的典册梳理与阐释,实现汉代经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从经学内部发展演变的历史角度而言,“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出现,则是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在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古文经学试图通过对《春秋左氏传》所包含的“历史化”路径的倚重,完成经学话语体系的重构。
[关键词]诸子出于王官;《七略》;刘歆;今古文经学;学术源流
一、“诸子出于王官”说辩正
邓骏捷先生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与汉家学术话语》(以下简称“邓文”)一文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种所谓‘汉儒附会揣测之辞’的‘诸子出于王官’说,究竟基于怎样的学术思想基础和思维模式?又反映了创说者刘歆什么样的主观意图?更为重要的是,其与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何种联系?是否体现了汉人构建诸子之学的意识形态?”[注]在此基础上,作者指明了研究思路:“尝试通过考察‘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构建过程和核心内容,探寻其形成的内在理路;同时结合刘向、刘歆的学术经历和旨趣,以及西汉政治、学术的发展,将‘诸子出于王官’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阐述其与汉家学术话语的关系。”[注]邓骏捷:《“诸子出于王官”说与汉家学术话语》,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9)。上述问题皆以“诸子出于王官”说为立足点,深刻触及了《七略》所反映的汉文化意识形态的成因,同时对随后汉文化发展过程中政治和学术的呈现状态有所剖析。据此,我们认为“邓文”极富见地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过认真拜读之余,还是发现文中尚有不少未尽人意和不妥之处,在此提出,以就教于作者和方家。
第一,前述一系列问题的末一问逻辑上不够严谨,未能与前问环环相扣、突出应有的重心。“诸子出于王官”说有“汉儒附会揣测”的成分,不仅基于刘歆本人的学术思想基础,也同学术文化、时代政治的发展密不可分。作者前三问既已表明对上述观点的认可,末问便稍显赘余;倘若一定要保留此问,则“体现了汉人构建诸子之学的意识形态”一事,以“是否”发问不如用“何以”冠之更合乎由表及里的逻辑理路。
一方面,工程建设对钢筋的需求量大,同一项工程对钢筋产品的型号、规格要求较多,同一批次所需的供货量多少不一,施工企业又希望能及时供货,这对于希望批量供货的钢铁企业来讲难以满足;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一些大型钢厂退出了建筑用钢的生产,而小钢厂又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不愿意投入高强钢筋的研发。
地层划分的基础和研究内容是地层的整体特征,整体特征是指地层的组成,地质结构,层序,厚度和接触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沉积类型;(2)生物区系;(3)分层结构;(4)构造特点,如接触关系、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构造环境条件和构造的发展过程都是这些特征形成的基础。因此,构造格局及其阶段发展是地质综合区划的主要依据。
第二,文中对“诸子出于王官说”“构建过程和核心内容”的考查,实际只是对今见材料的比照搜集和外在成果的剖析梳理,不足以单独证出“其形成的内在理路”。文章材料所涉,主要限于对“诸子出于王官”说如何“反映了儒家经学在吸纳融会其他思想文化资源、转化丰富自身体系时的垄断姿态”进行细致剖析。但“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内在成因,必不止于当时的政治需求,更在于文化自身发展对学术的要求。作为西汉学术至尊的今文经学由于自身的“虚妄”而导致学理和实践方面的困境,文章始终未能正面论及。这就使得“内在理路”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第三,在完成“诸子出于王官”说构建模式的梳理之后,作者本欲“将‘诸子出于王官’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这应是全文探究的重心,但在实际行文中,作者却回到了梳理过程的起点,以“汉家话语”视角切入,整理出“汉代统治思想上的一些变化”,以此作为“诸子出于王官”说构建材料的辅助论证,因而明显偏离了全文的探究重心。
刘歆青年时期随父校中秘典册,有机会接触浩如烟海的先贤文化,进而见宗周王官学术之优、诸家学术之长,明了众学“官人安民”之旨归。中华文明“独特的生存方式”之初生远在文字产生之前,但文字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人类思维的深度与广度。而典籍的出现更使得“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得以记录和保存,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商以前,《夏小正》已经开始记录天文历法[注]韩高年:《上古时仪式与仪式韵文——论〈夏小正〉的性质、时代及演变》,载《文献》,2004(4)。;《尚书·多方》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注]阮元:《阮刻尚书注疏》,94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至宗周,不仅对前代文明加以继承和保存,如大卜之官“掌三《易》之法”[注]孙诒让著,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23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更开始对当世文明进行类总,建立起富有文化特征的宗周官学体系,因而“到西周和春秋时期,典册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注]陈来:《国学发展简史(上)》,载《文史知识》,2014(10)。;秦“以吏为师”,典册藏于官府;“汉兴以来,承用秦法”[注]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717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所赖皆先秦典籍对王官之学的系统保存。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邓文”的基础上,对“诸子出于王官”说展开进一步探讨,以期对这一重要学术命题进行更为全面的阐释。
总体而言,政治、学术都是文化的构成元素和人类活动的重要领域。[注]梁启超:《什么是文化》,载《晨报附刊》,1922-12-01,2版。传统的政治与学术共构文化主体,并无彼此隶属关系。《尚书·皋陶谟》载大禹言“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注]阮元:《阮刻尚书注疏》,236-23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其理想目标在“能哲而惠”。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有关传统学术和政治的论述,其中“知人”和“官人”都是“安民”必不可少的因素,二者既是传统学术的天然品格,也是传统政治的终极追求。
政治植根于现世的特征使得其对文化的时代需求更为敏感,于是在社会生活中常常显示出先于学术的貌似“支配性”表征。事实上,政治与学术对时代文化同等重要。学术与时代政治不恰合,必然导致当世“共业”不能被合理运用,同时也就意味着各文化领域无法顺畅发展,社会必然因此陷入混乱。强秦的覆亡已经让汉家帝王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从高祖到武帝,都在呼吁学术同政治合作,共铸造福民众之宏业。从汉初“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注]班固:《汉书》,116、161、2523、155-156、161、1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的修养生息,过渡到初中期“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注]班固:《汉书》,116、161、2523、155-156、161、1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的积极进取,政治家的诉求已然从文化承接磨合转为奋起出新。与此相呼应,学界也发出了相同的声音,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注]司马迁:《史记》,3993、37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对汉初学术发展的总结,到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注]班固:《汉书》,116、161、2523、155-156、161、1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的开拓,无不在在显示出学术希望通过调整与政治的合作方式,以求与之共构安定和谐文化的强烈用心。
梁启超认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构成的关注点,在“求秩序,求娱乐,求安慰,求拓大”,将“求秩序”摆在文化首位;柳诒徵亦以“参天地”“立人极”“尽物性”为中华文化最为“博厚高明”处[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何晓明同样认为整个人类活动这一“庞杂的认识对象”之所以产生,在其“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而对“独特生存方式”即“文化”[注]即何晓明先生所谓“狭义‘文化’”。参见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绪论,1-1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的探索,正是中国传统学术和政治的共同目标。陈寅恪曾言:“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注]陈寅恪:《陈寅恪诗集》,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可谓从传统学术与政治协作角度,对中华文化特点最贴切精到的概括。“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提出也是如此,不仅如“邓文”所言,是依顺政治的力量,“因应了西汉以来学术文化整合发展的趋势”,而且更是儒学顺应西汉学术发展内部需求,跳出今文经学困境而转向古文经学求新生的必然选择。
二、《七略》学术体系与宗周王官之学
“诸子出于王官”说源自《七略》中的《诸子略》,而《诸子略》归“九流十家”于王官,不仅由于刘歆看到诸子同《周礼》所记载的王官确有学理联系;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宗周王官之学统而为一又互不相倚的形态是这一时代各类学术和谐发展的最恰切方式,是当时达成中华民族“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的最妥帖途径。刘歆述《七略》明显具有构架体系、总揽众学的意图,原因在于他已然发现诸子之学与王官之学间的内在联系:新兴诸子之言,“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注]。也即是说,“九流”诸子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意义,“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注],因而假之以构成一大学术体系不失为明智之举。
从整体学术思路来看,“诸子出于王官”,其实只是刘歆欲以“学术出于王官”构架汉代全新一统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汉志》保存的《七略》中就多处体现了这点。《六艺略》“易”类小序言:“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注]言《易》之所作,是章法天地、了解自然之学,其接通人神的作用正是试图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渠道。“诗”类小序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注]以《诗》为体察民风、沟通人情之有效途径。《诗赋略》序言:“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注]以诗赋为邦国之间文化交通之媒介。此外,《兵书》上乘之用“以威天下”[注];《天文》所纪,“圣王所以参政”[注];《医经》“以起百病之本,生死之分”[注]班固:《汉书》,1746、1746、1704、1708、1755-1756、1762、1765、17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这些都清楚地阐明,各种学术皆有“官人”“安民”之用,与诸子之学殊途而同归。
“邓文”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偏差,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将“诸子出于王官”说单纯作为汉家的“学术批评体系”看待,未能进一步指出这一学术体系的文化构建意义;二是以当时材料为中心梳理学术脉络,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汉家学者”在“汉家学术”中的作用,绕开了刘歆“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因而简化了“汉时学术材料”与“汉家学术话语”的关系;三是对汉代经学的理解过于笼统,未能从今古文经学之别的角度考察经学话语体系的嬗变。
宗周官学之形成,诚如“邓文”引沈文倬先生言:“这种百官在任职实践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经过不断修订,不断条理化,汇集起来。”官守之学早在远古分散的部族时期就以较系统的形式出现,《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答昭子问:“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386-1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其中就载录了多个部族的官守系统,足见以图腾崇拜为核心的社会系统遍布各个部族文化区。
农业园区是资源整合的系统,在园区中实施整合组件发展措施,锁定农业发展问题,总结经验,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传统农业升级、转型,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到农业发展中去。实现互联网技术和农业生产技术相结合,不断发展和完善“农业+互联网”农业技术,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合作平台,不断进行互联网技术的投入和革新,引入先进技术人才,在生产、经营、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提升,不断优化服务系统,提高服务质量,减少企业运营成本压力,提高农产品销售能力,促进农业产业链升级。
以宗周王官之学为代表,部族文化中的官守之学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却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典籍进入文化建构过程,在加速了部族文化繁荣的同时,也使得以地域生活方式为基础的部族官守之学显示出自己的局限。晚周诸子的争鸣,不仅标志着以宗周官学为代表的部族文化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学术的发展需求,而且在激烈的争鸣中还为文化的重组探索出了新的雏形:中华学术开始由早期以官守为分支的地域性部族学术向更为合理的以学理为分支的学派性民族学术转变。[注]李会康、刘松来:《晚周百家争鸣》,载《光明日报》,2018-04-09,13版。
儒家学术意愿同汉家政治意图的高度吻合,使得双方的合作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事实上,汉武帝即位之初便决意择儒学为汉家王朝所用,建元六年,“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注]班固:《汉书》,116、161、2523、155-156、161、1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儒学自此正式走上同汉家王朝合作的道路。学术建立与政治的联系,一方面是探寻引导学术入政治系统的合理途径,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双方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作为汉武帝择出的儒生代表,公孙弘适时提出了从学业优异的儒生中选拔各级官员的立法建议,从而将汉武帝延揽儒生参与朝政的政治构想上升为一种国家的法律制度,终于找到了一条学术入政治系统的合理途径。“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注]班固:《汉书》,3596、3617、3617、2518-2519、24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不同于秦对学术生硬的“始复古制”,汉初承秦制更多表现出对汉之前,即周秦优秀文化元素的总体包容,正所谓“汉人于吾国之文明,既善继往,兼能开来”[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5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汉初对民间学术的容纳态度,直接体现在“废挟书令”上。《汉书·惠帝纪》载:“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注]班固:《汉书》,2145、90、170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不仅提供自由的学术土壤,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注]班固:《汉书》,2145、90、170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大力提倡学术的复苏拔节。在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中,秦代被坑覆的诸学种苗纷纷复苏,迅速成长起来。可见,刘歆《七略》“诸学出于王官”学术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因应时代政治的需要,以实现对诸子学术的统领,更是通过承接“百家争鸣”之后的周秦之学,对载诸典籍的中华文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体系重构。
三、“天人感应”与今文经学的困境
霍金告诉我们,如果说牛顿力学摆脱了绝对空间,使空间相对化,那么量子力学则接着摆脱了绝对时间,使空间、时间都相对化,均变成动力量。[11]33-34这样以量子力学为背景的数码摄影,就会以更多维的时空存在替代以牛顿力学为支撑的传统摄影中的绝对时间观念。那么摄影的能量共享、存在迭加、意义多重就不证自明。正因为如此,里奇指出:
相较于其他学术,儒家以人伦为重而切当世之事,故其走向文化中心成为学术总领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汉武帝早在即位之初就敏锐地感觉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注]司马迁:《史记》,3993、37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的“黄老之术”已不能适应当世政治文化需求,“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注]班固:《汉书》,116、161、2523、155-156、161、1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随后,建元六年,汉武帝重申“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注]班固:《汉书》,116、161、2523、155-156、161、1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公孙弘、董仲舒二人,一长于政治制度,一长于学术文化,在儒学走上总领众学的道路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生的各种活动中也可以发掘许多写作素材,教师要善于抓住它们与作文的联系,指导学生进行相关积累。比如开运动会,可让学生注意观察,描写运动会中的一个场面或一个运动员的表现;进行跳绳比赛,可让学生观察比赛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开一次班会,可让学生写《我当主持人》《第一次表演节目》《最精彩的一个节目》等;参加了校园英语节的活动,可写活动中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事、场景等。由于这些素材贴近学生生活,学生又进行了观察,有体验,因而可以有感而发。
汉武帝集贤良而择儒生具有深刻的文化因缘。一方面,儒学重心更贴近“能哲而惠”的传统学术品格,可使明主贤臣为文化创建所做出的努力更能被历史察见;另一方面,就现世效果而言,“儒家的德治仁说能为君主政治进行某种修饰和补充,特别是儒家的各种仪制典章,可以将专制主义暴力统治装点得温情脉脉”[注]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10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事实上,儒学的这种“修饰性”品格的确为政治家治世所必需。汉武帝在二次“诏贤良”时,表达了对“唐虞”之世的向往。可见,汉王朝的确需要明“礼”尚“仁”的儒家学说参与文化构建。从儒学自身的角度来看,对文化的关注使得其在“修饰性”之外还对政治有一定的“导引性”,即通过“惩恶劝善”的方式同政治合作,以发挥传统学术的积极作用,因此同政治结缘乃是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诸子学术在经历秦代的短暂僵化之后,至西汉初中期再次焕发生机。秦制“以吏为师”,看似承旧,实则逆历史而动。学术在晚周散入诸子,对各文化领域的探索、构建早已不是王官特权。诚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言:“东周以外,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2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学术的粗暴复古已是逆水行舟,“挟书律”的颁行更是壅川之举。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得有秦一代根植于诸家学养之上的文化种苗《吕氏春秋》虽“集诸儒,使著其所闻”[注]高诱:《吕氏春秋·序》,载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却遭到雪藏的厄运。至汉初,诸子之学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淮南子》的出现正是这一趋势的显著标志。《淮南子》著述目的与《吕氏春秋》“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乎人”[注]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6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相似,也是为了“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注]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217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二者之间似有明显的承续之意。但在篇目设置上,《淮南子》却显露出新时代的文化特征,如将论述兵战之事的篇章命名为《兵略训》,而非《吕氏春秋》那样照搬宗周学术,将相应内容命名为《秋纪》。正因为《淮南子》承晚周诸学余绪且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所以深受当政者喜爱:“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祕之。”[注]班固:《汉书》,2145、90、170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以《淮南子》之鸿制,可知景帝时学术新风已然大开。
公孙弘提出的举措虽然在官员组成结构方面实现了汉武帝延揽儒生的政治构想,但“对专制统治者来说,严密控制人的思想意志与约束人的行为同等重要”[注]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211、184、211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汉武帝需要的不仅仅是儒生的自觉参政,更想要的是借助儒学建构起一套与专制政体协合的意识形态。为此,汉武帝再选瑕丘江公同董仲舒辩难。“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注]班固:《汉书》,3596、3617、3617、2518-2519、24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关键时刻公孙弘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注]班固:《汉书》,3596、3617、3617、2518-2519、24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其实早在建元六年的应诏策对中,董仲舒就以学识深厚居同僚之首而与公孙弘同出,之所以未被首先择出参与政治与学术构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儒学(董仲舒之学)尚未完成向封建专制王朝官方学说的过渡,因而武帝只能对它采取选择性的接受”[注]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211、184、211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儒,董仲舒“为人廉直……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注]司马迁:《史记》,37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择“为人廉直”的董仲舒为代表来建构政治与学术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当是汉武帝的无奈之举;而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注]班固:《汉书》,3596、3617、3617、2518-2519、24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将绝对威严留给“天”,则体现出董仲舒作为时学领袖面对政治“邀约之手”时的良苦用心。
宗周王官之学则具有更为深刻的文化意义,开始将文化重心由神鬼转向人间,从而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全新时代。随着各种知识载诸文字,对人类文化的探索逐渐成熟。钱穆先生曾言:“(礼)是‘当时贵族阶级的一种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这一种习惯与方式里,包括有‘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三部门的意义,其愈后起的部门,则愈占重要。”[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可谓至论。自商至周,正是“后起部门”替位的重要阶段。“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德,事鬼敬神而远之”[注]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7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可见宗周王官之学的重心由神而至人,在晚周已是学界共识。上述转化可谓奠定了中华学术的基调,而典籍也在转化过程中逐渐成熟并担负起中华文化载体的重任。不仅宗周王官之学通过不同职官分掌的典籍得以完备,宗周的王官制度也因此得以保存。宗周官学重心的转变与典籍的成熟显然为身为古文经学大家的刘歆重构学术体系提供了足够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是《七略》问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缘。
由于缺少冰雪运动的发展条件,我国冰雪运动相关项目普遍缺乏群众基础,与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受众广泛且成本较低的体育项目相比,国人对冬季体育运动,如冰球、冰壶的参与度明显较低。此外,我国在冬奥会上的表现与挪威、加拿大以及德国等传统冰雪强国始终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因此,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冰雪项目成绩上存在差距导致冬奥会在我国的关注程度不高,这对冬奥背景下北京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对“天”的独特解读,是董仲舒的极大创举。一方面,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导出“君权神授”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注]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311、18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的见解,巧妙破解了汉天子生杀予夺权力的合法性难题,“从宇宙论的哲学高度为汉代封建专制政体的运行和政治伦理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注]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211、184、211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另一方面,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之首,卓然提出“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注]班固:《汉书》,3596、3617、3617、2518-2519、24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这不仅重新树立起“天”的绝对权威,更将“天人相与之际”摆在了仅次于天的位置。这就使得人君也需要“强勉学问”“强勉行道”,才能够“闻见博而知益明”“德日起而大有功”,学术因此取得了在理论上与政治平起平坐而共构文化的机会。
必须指出,董仲舒借助“天人感应”学说以换取话语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得今文经学付出了牺牲学理的沉重代价,以至于在随后的发展和运用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由表2可知,日粮不同普鲁兰酶添加水平对3~28日龄临武鸭生长性能各指标均无显著影响(P>0.05)。不过添加100 g/t和150 g/t普鲁兰酶的2个试验处理试鸭平均日增重较对照处理Ⅰ分别高出2.15%和0.87%。另外,试验除日粮250 g/t普鲁兰酶添加水平处理的试鸭料重比高于对照处理Ⅰ外,其它4个普鲁兰酶添加水平处理的料重比低于或与对照处理Ⅰ持平。故从生长性能结果角度考虑,3~28日龄雌性临武鸭玉米-豆粕型日粮中普鲁兰酶添加水平以100~200 g/t为宜。
一方面,“天”的概念虽然在接通“孔子之术”即先秦儒学同当世儒学时形成了捷径,却无形中舍弃了儒学天然的学术中心位置,客观上割裂了儒学同诸家的学理联系。在为儒学立位时,董仲舒过分推重了“天”的力量,以《春秋》为“应天作新王之事”。诚如周予同先生言,今文经学“尊孔子是‘受命’的‘素王’”,将《春秋》描述为孔子受“无常”之“天命”为“后圣”而制。这样虽然将孔子立于整个学术系统的顶端,却在客观上割裂了孔子所主张的“仁”“礼”核心同宗周学术系统的联系。原始儒学立足于宗周文化,“礼”作为“当时贵族阶级的一种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是关乎人类文化的核心范畴。经过晚周的内部分流与诸子间的交流,儒学本身也得到了发展,已然接纳和联通了更多知识,成为儒学同诸学联接的天然桥梁。董仲舒本人对阴阳灾异学说的熟习,即是最有力的佐证。而对“天”的过分倚重,则使本应居于文化中心而统领众学的儒学,变成了在“天”的授命之下强行上位居首的学术,从而大大削弱了其作为众学统领的学理依据。
另一方面,为汉王朝立符授命的“三王之道若循环”论,是借阴阳五行之说使汉王朝迅速正名,儒学也因此放弃了本身的学理优长。原始儒学之长,在孔子推重的学术核心,经过周秦之际的发展,这一优长主要体现在对《春秋》蕴含的“仁”“礼”(尤其是“礼”)思想的阐发进而丰富之上,董仲舒本人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注]司马迁:《史记》,40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董仲舒所言的“是非”之辞体现了儒家学者对历史更迭的看法,是儒学历史观的精华所在。董仲舒依“天”阐释三代正统之接替,无异于放弃了春秋“是非”之辞中的合理看法:“董仲舒这种历史变化的观念……在表述时,却不说明是由具体史实变化而实行归纳而得,却采用了相反的逻辑方法,从演绎而得。”[注]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5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陈其泰所言与逻辑相反的演绎,指的正是董仲舒十分倚重的“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五行理论本身及其“演绎”方法均具有很强的主观臆测性,所以董仲舒费心费力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犹如云上重楼,无形中失去了扎实的学术根基。
董仲舒借助“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五行理论构建的今文经学体系虽然缺乏扎实的学术根基,但客观上却促成了学术同政治携手,不仅树立起汉家王朝的绝对权威,而且使儒学成功获取了话语垄断权,居于独尊之位。但作为官方学术,今文经学在面临实际问题时,不能立足于中华文化已基本成型并被汉王朝赞赏的“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而只能依靠并不完备以致漏洞百出的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势必步入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
以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观之,刘歆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编纂《七略》,不止如“邓文”所言,“是在建立沟通诸子百家与上古学术的理论体系”,更是希望通过沟通诸子百家同上古学术的方式,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即在新的文化环境下,通过调整学术形态实现与政治联姻,共构和谐文化,从而达致“官人安民”之目的。
四、古文经学替位与“诸子出于王官”
为了换取学术话语权,避免政治一言堂,董仲舒依托“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五行理论构建起完整的“春秋公羊”学体系,使今文经学迅速立于尊位,但这一体系由于缺乏扎实的根基,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步入困境。
今文经学面临困境的现实清楚地表明,要想真正稳固同政治合作的地位,儒学必须跳脱既有的“天人感应”牢笼,将学术“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换言之,只有真正接通汉时学术同先秦学术的筋脉,才能恢复原始儒学的活力;只有这种具有活力的儒学才有资格同当世政治携手,共同实现学术“知人”背后更深刻的“官人安民”价值。在儒学内部,后出的古文经学因不必刻意迎合政治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品格。在长期梳理点校先秦典籍的过程中,以刘歆为领军人物的古文经学家最终发现,具备“资治通鉴”性质的《春秋左氏传》不失为接通古今学术的恰当媒介。
刘歆习古文经,同其父刘向的治学经历密不可分。刘向治《穀梁春秋》,曾“讲论《五经》于石渠”[注],熟习今文经学并笃信阴阳之术,曾上书言:“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注]元帝朝,刘向即“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注],多次上书元帝言宦臣外戚之事。这些谏书可谓极今文经学之能事,表奏起因则言“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注];说理亦言“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注]班固:《汉书》,1929、1941、1932、1932、19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刘向的谏奏非但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招致牢狱之祸。逮至汉成帝之世,由于成帝雅好《诗》《书》且常常“观古文”,所以诏刘向校天禄、石渠所藏典册,刘向因典册之便,再次启奏,“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此举虽然洗清了自己前朝诬苦,“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但阴阳灾异天谴之说毕竟缺乏严密的逻辑理路,只能通过附会往事指出当今不足,不能真正推求未来而提出有效措施。所以在成帝“终不能夺王氏权”[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的情况下,刘向的反复谏奏,终使成帝失去耐心,于是面诏刘向:“君且休矣,吾将思之。”[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研究的结果表明学生总体来说缺乏与策略相关的意识。他们相对来说缺乏丰富的策略储备,例如他们对学习策略不大了解。因此,他们不能实施恰当的学习策略和有意识的控制学习策略的使用[6]。所有这些都说明学生在不同的语言学习任务中实施恰当的学习策略以及控制策略使用方面的能力比较低。因此学习策略的培训也是迫在眉睫。学习策略的训练旨在帮助学习者考量影响自己学习的因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这样学习者才可能更有效的学习,并且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它更加关注的是学习过程,因此强调是如何学而不是学什么。因此高校应尽可能地为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指导,让学生掌握如何自主学习英语的能力。
古文经学家不同于今文经学家的“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显示出对学术本位以及儒学核心的坚守。首先,在对待政治的态度上,古文经学作为官学陪衬,虽然未能像今文经学那样直接参与文化建构,但也从未走向与今文经学乃至汉家王朝相对抗的一面。是以汉成帝召尹咸、翟方进从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之书时,两位能积极参与并与刘歆通力合作,“共校经传”。其次,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作为在野学术,古文经学也从未因今文经学一时之盛而放弃对儒学核心价值的遵循。古文经学家们从未停止整理文化典籍,他们相与“传训故”,以存真学为义,为真正参与文化建设一直在做学理上的准备。
作为汉室宗亲,刘歆与其父同样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同时更具深邃的学术见地。他看到今文经学已然失去学术应有的价值,不仅不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应有的指引,反而成了单纯鞭策、乃至指责政治的文化元素,正逐渐走向政治文化的对立面。今文经学大儒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以“天人感应”为根基的今文经学虽然赋予了他们入朝为官的身份,但儒学立礼安民的核心特质才是他们赖以立身的资本。刘歆对学术的根本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他敏锐地发现,今文经学“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不能对文化运行有真正助力;而在学者自身价值和品格上,今文经学者更是“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疾,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不仅失去了学者“官人”“安民”的根本追求,甚至在基本的“知人”态度上也是为了眼前利益毫无应有的君子立场。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虽然没能完成“冀得废遗”的学术愿望,却卓然道出:“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由此可见,今文经学家群体已然丧失了学者应有的品格,今文经学的衰亡已成历史之必然。
荷里路德宫,又名圣十字架宫,位于爱丁堡皇家英里大道的尽头。离荷里路德宫不远,有一座死火山,名为“亚瑟王宝座”,同样是爱丁堡的知名景观之一。登上“亚瑟王宝座”,可以俯瞰荷里路德宫的全貌,景色十分优美。
“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诟病,而学衰。”[注]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诚如皮锡瑞所言,中华学术的终极追求,在“官人安民”,在“有用”。刘歆以汉室宗亲居当时儒学之尊位,“沉靖有谋……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自然不会眼看汉家官学走向绝境。在校书过程中,刘歆接触到《春秋左氏传》并向《左氏》大家尹咸和翟方进“质问大义”,“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发现其中释《春秋》之条法所蕴含的儒学大义正是原始儒学的精华所在。于是,他援今文经学发明义理的优长入古文经学,“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使得《左氏》之学摆脱了“学者传训故而已”的窘境,“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注]班固:《汉书》,1950、1950、1950、1963、1970、1970、1971、1971、1967、1967、1967、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既是为了加强《左氏》之学的政治实用性,也是为了使经学跳出今文困境的学术创新。“《春秋左氏传》不但释经,而且用丰富的史料来解释《春秋》所记载的二百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政治主张往往寓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注]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227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经过刘歆的“引传解经”,《春秋左氏传》不仅显示出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所无法比拟的学理优长,而且其传文中所蕴含的儒学理念,正是汉家王朝苦苦寻求的“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注],亦即“古今王事之体”[注]。其中对春秋两百余年历史事件的演绎评骘,正是先秦儒家将“仁”“礼”具象至“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中的“一家之言”。可以说,至刘歆治成《左氏》之学,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所悬置的“甚可畏也”的“天人相与之际”的迷案才开始被揭橥。换言之,汉家王朝是借助古文经学之手,才真正触碰到儒学本要,而《左氏》之学,正是接通汉时学术与原始儒学的联系纽带。
当儒学的本原与优长被真正触及,以之为中心的发掘工作便一发而不可止。刘歆在整理中秘典册的过程中,一方面发现儒家学说同诸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另一方面,刘歆受到宗周以王官之学分统典册的启发,开始以学理为纲总归旧学,尝试通过典册的整理归纳,重新建立起一套较为切实的汉家学术体系。
应当指出,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学术建树与刘歆借《左氏》以为“资治通鉴”的学术回溯,实际上是儒学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历史状况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二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注]班固:《汉书》,2495、161、2525-25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可谓体大精深。然而董仲舒借“天人感应”学说构建今文经学体系的做法,难免使这套学术体系陷入“虚妄”的困境。至刘歆时,今文经学明显偏离学术轨道,已然成为一种谋取利禄的工具,儒学原有的核心价值逐渐淹没于“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的“烦言碎辞”之中。作为经学大家和汉室“骨肉之亲”,刘歆对此可谓心知肚明,其对古文经学的推重,既是为了促成汉家王朝与儒学再次结缘,也是希望以《春秋左氏传》《周礼》等儒家典籍为核心经传,实现中国学术文化在宗周之后的重新建构。从文化视角看,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问鼎学术至尊的宝座,乃是一种水到渠成之举。毫无疑问,唯有将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说置于汉代经学这种演变态势中来加以观察,才能对其内在理路有更清晰的了解。
居住区植物虽然众多,但整体归纳为夏日繁花似锦,冬季以暗淡的灰色调为主且多雪,可以利用冬季的雪景营造特色景观。东北的冬季较为寒冷,城市特色较易突出,稍加装饰就易形成特色显著的冬季景观。而华北及华中部分区域冬季没有东北冬季时间长,降雪量也比较小,当植物进入落叶期,除了建筑色彩以外,其他背景色都处于灰暗的状态下,居住区植物景观特色不明显。也就是说,季相变化不仅影响植物景观,而且影响整个居住区的基调色。
五、《诸子略》附会《周礼》王官制度的古文经学理路
诚如“邓文”所言:“无论《周礼》是否刘歆伪造,从典籍记载的角度而言,宗周王官制度一开始便带有若干构建性和想象性。”[注]邓骏捷:《“诸子出于王官”说与汉家学术话语》,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9)。而刘歆在《诸子略》中对古文经尤其是《周礼》的承接,则是在汉时学术基础上的构建和想象。作为古文经学家,刘歆对学术构建有自己的看法,也更具有“承旧”的古文经学的思维特征。欲发明刘歆对古文经的运用,不应止于深究《诸子略》中王官同真实王官的不同,更应探求二者相合相接的深层原因。
《诸子略》作为刘歆承古文经陈述王官制度的直接产物,体现了汉代古文经学家总条例以发义理的内在理路。王葆玹先生曾经指出:“《春秋》左氏学的条例日益增多,扩充到古文的《易》学、《礼》学当中,从而使古文经学全面的条例化或义理化”[注]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2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刘歆身为古文经学尤其是古文《礼》学大家,在《诸子略》这一条列前学的重要篇章中,自然倾注了古文经学的一贯学理。细查《诸子略》所陈诸家与《周礼》所载王官之联系,可对刘歆构篇的“思维模式”进行发明,进而探索其“主观意图”。
对《周礼》条例的熟用是《诸子略》论诸家学理的主要依据。儒家是《诸子略》首先论述的对象,也是论述中对《周礼》条例最为倚重的一家:“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注]班固:《汉书》,1728、1736、1746、1732、17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盖出于司徒之官”,将儒家的学术定位与《周礼·地官司徒》联系起来。随后言其学术意义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这与《周礼·地官司徒》中论述“大司徒之职”几乎完全吻合,即“佐王安扰邦国”[注]。而儒家的学理依据,“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也和《周礼》所论大司徒应有的品学储备“六德:知、仁、圣、义、忠、和”[注]孙诒让:《周礼正义》,1557、9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十分吻合。通过对《周礼》所录王官的呼应,论中儒家的众学统帅之位可谓呼之欲出。
《易》也是《诸子略》借经述名,联结诸子与王官之一端。“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注]班固:《汉书》,1728、1736、1746、1732、17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在述法家的学理所长之前,楔入“先王以明罚饬法”,假《易》经《象辞》将法家之论同“先王”相接。末论诸家同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更称“《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注]班固:《汉书》,1728、1736、1746、1732、17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此句只是《系辞》中句,而同样称之为《易》,明显是古文经学家发挥条例,假经文以成义理的惯用阐释手段。
对“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的称述,也是联系诸子同王官之一端。在儒家之末,刘歆言“五经乖析”的原因是“违道离本”,未能追随“已试之效者”。在叙述学理依据之后,儒家显然已经是无可置疑的统帅之学。但刘歆并未止于此,随后又补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再次为儒家学术同周室正宗的联系正名;继而将“宗师仲尼”搬出,以示其学派之尊位;对名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的论述中,“孔子曰”同样作为重证反复出现;对道家的论述则曰“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注]班固:《汉书》,1728、1736、1746、1732、17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2)菜单页面设置“开始游戏”、“象棋历史”、“象棋 规则”、“退出游戏”几个板块。点击“象棋历史”与“象棋 规则”可分别进入象棋历史介绍与游戏玩法介绍页面;
即使未直接称引上述诸条者如阴阳家,其所出的“羲和之官”,也出自《尚书·尧典》;而杂家先流“议官”所重,在“兼儒墨,合名法”,自然合于诸条。由此可见,刘歆所述诸家,其方法无出“归纳条例,演绎义理”之古文经学套路;其论据亦无出古文经学“承旧”范畴。
刘歆对“诸子出于王官”的列述并非简单附会《周礼》,而是总结诸子争鸣,参照秦汉之际的学术整合对诸子之学长短的全新阐释;在归纳诸子入《周礼》所载王官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意见鲜明的高下排序。其论儒家“于道为最高”;道家“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而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均不置地位高下之评,只是举其所长,明其所短,以示可用;末至小说家,则“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君子弗为”“然亦弗灭也”[注]班固:《汉书》,1728、1736、1746、1732、17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显而易见,刘歆对诸子和以《周礼》所载为主体的王官制度的条分缕析,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学术梳理和意义重构,完全可以视为古文经学“条例”“义理”手法的一次具体实践。
六、结语
总之,刘歆“强化汉朝五经官学的权威性”,不仅是为了“反映学术大一统下的汉家学术话语”,而且更是希望倚重汉家的政治权威,对偏离中华传统学术立场的今文经学进行纠偏。为了“更深入探讨具有东方特色的‘政学合一’而非‘政教合一’的权力架构以及汉代之后历代不约而同的学术取向”,或许应在“邓文”所言学术批评之外,将学术置于更深广的文化视野中作更“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注]邓骏捷:《“诸子出于王官”说与汉家学术话语》,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9)。之思考。这样的视角不仅可以使“政学”问题得到更有力的解决,也更有助于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2)当m=1时,G ~=S3或G为2n(2n-1)阶Frobenius群,其中Sylow 2-子群正规,2n-1为素数.
就文化意义而言,“诸子出于王官”说既是刘歆梳理先秦典册体系重构汉代文化学术的产物,亦是汉代儒学在今文经学形态下面临“虚妄”困境的一种自救之举。一方面,作为汉代儒学大家,刘歆由今文转向古文,表现出极深厚的学术积累、极高远的学术见地和极宽阔的学术胸襟,是以能抛开学术偏见,发现并积极发掘古文经的优长,使汉代经学得以重新回归先秦儒学以“礼”“仁”为核心的轨道,即“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之中;另一方面,作为汉室宗亲,刘歆不仅真正认识到学术对于文化构建的意义,更以政治家的身份对学术表现出一般儒生所不具备的信仰。这不仅使得汉家王朝开始真正将学术从对面转置并肩,开启了与学术合作的局面,更使得典籍开始被有意识地作为文化传承重器被正面运用于文化建构之中,以《七略》为载体的“诸子出于王官”说,正是这一观念意识产生的硕果。
“改革开放”,小朋友们对这个词并不陌生吧?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1978年12月至今,整整40年过去了。在过去的40年间,因为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富强,人们的生活也一年更比一年好。
就学术意义而言,“诸子出于王官”说体系的建立是刘歆对当时知识体系的重组和保存,是推重古文经学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刘歆在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过程中,深刻体认到宗周百官之学“尊礼尚德,事鬼敬神而远之”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是对中华民族最恰切“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即中华文化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刘歆由此清楚地意识到,通过对先秦传世典籍的梳理阐释以保持学术同当世社会现实的血脉联系,是文化传承的最佳方式。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以为“诸子出于王官”说绝非单纯的学术史观问题,而是包含了更为复杂的文化密码,唯有辨析清楚其学术源流,才能破解密码,从中获取丰富的文化信息,并得到启迪。
TheAcademicOriginoftheTheorythat“TheHundredSchoolsofThoughtOriginatedwithCourtOfficials”:FurtherDiscussionaboutScholarlyintheHanDynasty
LIU Songlai,LI Huik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
Abstract: The relative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to Zhou Li showed up in the strategies of the hundred schools are actually the results of the Great Debate raised along with the decay of Zhou dynasty.The intentional analogy showed up with the theory that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Originated with Court Officials” is an advantageous effort Liu Xin brought up to set up the more macroscopical cultural theory that “all Scholarship Originated with Court Officials”.The purpose that Liu Xin delivered this theory with Seven strategies is to carry on the tradition formed during Zhou dynasty that all books managed by related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refore build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for Han Dynasty with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by teas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mained ancient codes and records.From the internal aspect of Confucianism’s development, the dilemma that Present Characters School faced was the root cause and direct trigger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theory that “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Originated with Court Officials”, it’s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Confucianism that the Ancient Characters School tried to by practicing the historicization feature of Chun Qiu Zuo Shi Zhuan.
Keywords: The Hundred Schools Originated with Court Officials; Seven strategies; Liu Xin; Present and Ancient Characters School of the Confucianism; academic origin and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 刘松来: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会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 南昌 330022)
本文试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学术源流进行考辨,兼论及“诸子出于王官”说与汉家学术话语的不同理解。
(责任编辑林间)
标签:学术论文; 经学论文; 王官论文; 诸子论文; 董仲舒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