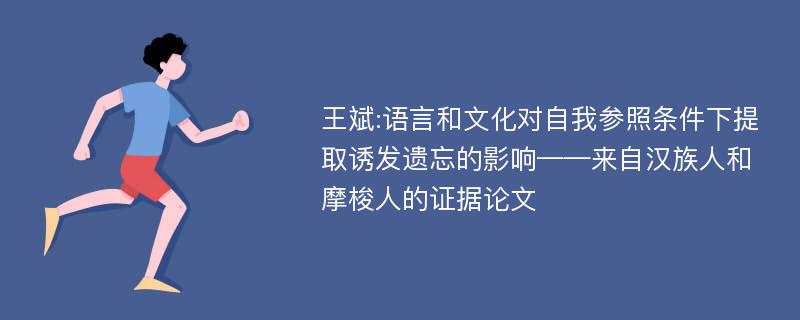
摘 要 采用提取诱发遗忘范式考察摩梭人和汉族人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的加工规律, 发现摩梭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条件下都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而在一般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 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条件下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而在姨母参照、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这表明, 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影响人的自我构建, 在汉族人的自我结构中包含有母亲, 而摩梭人将母亲、姨母皆作为重要的他人纳入自我建构中, 使得母亲参照和姨母参照产生与自我参照同样的记忆优势。
关键词 提取诱发遗忘; 自我参照加工; 母亲参照加工; 姨母参照加工; 跨文化研究
1 引言
在回忆记忆内容时, 会对其他相关材料产生抑制, 使其回忆量降低(Anderson, Bjork, & Bjork,1994), 这种现象被称为提取诱发遗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提取诱发遗忘在生活中很常见, 比如, 在观看一部影片之后, 人们常回忆起一些情节, 而淡忘其他情节。
研究提取诱发遗忘的经典范式是提取练习范式(Anderson, Bjork, & Bjork, 1994)。在学习阶段让被试学习以“类别名称–样例”形式呈现的词对, 如“Fruit–Orange”、“Fruit–Tomato”; 在提取练习阶段从一半类别中选出一半进行线索提取, 如“Fruit–Or____”, 要求被试根据线索写出完整的样例词。干扰阶段之后是测验阶段, 要求被试回忆所有类别的样例词。材料分为三类:Rp+, 即经过提取练习的词对; Rp–, 即类别经过提取、样例未经过提取的词对; Nrp, 即类别和样例都未提取过的词对, 该类别也被称为基线水平。结果发现, Rp+材料的回忆率显著高于Nrp材料, Rp–材料的回忆率低于Nrp材料,表现出提取诱发遗忘。提取诱发遗忘既可以在单词记忆的简单的情境中发生, 也可以在情绪(Barber& Mather, 2012; Kobayashi & Tanno, 2013; 毛伟宾,赵浩远, 东利云, 白鹭, 2016)、算数问题(Campbell& Thompson, 2012)等复杂的情境中发生。但是, 也存在着一些边界条件。自我参照是提取诱发遗忘的边界条件之一(Macrae & Roseveare, 2002)。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 SRE)是指凡与自我有关的加工均会导致最优的记忆效果(Rogers, Kuiper,& Kirker, 1997)。Macrae和Roseveare (2002)考察在自我参照、朋友参照和一般他人参照条件下的回忆,发现与朋友参照条件和一般他人参照条件不同, 被试在自我参照条件下并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研究者认为, 自我促进了对记忆信息的精细整合,自我参照的材料会受到独特的精细编码(Macrae &Roseveare, 2002), 因而在提取时不会受到抑制。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东西方人的自我存在着差异。西方人的自我具有严格的边界, 自我中仅仅包括自己, 强调自我是一个有边界的、独立于他人的实体; 东方人的自我边界模糊, 在自我中不仅包括自己, 还包括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的重要他人,强调自我与他人的依赖关系(Markus & Kitayama,1991; Plaut, Markus, Treadway, & Fu, 2012)。朱滢和张力(2001)发现, 中国人在参照自我特质判断和参照母亲特质判断时, 二者的回忆成绩相当, 说明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包含有母亲。杨红升和朱滢(2004)进一步将自我与提取诱发遗忘相结合, 发现自我参照加工和母亲参照加工都不抑制相关的材料, 说明母亲参照是提取诱发遗忘产生的边界条件。对集体意识更强的日本文化研究发现, 比起一般他人参照条件, 日本大学生在自我参照、朋友参照和家人参照条件下都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Uchida,Ueno, & Miyamoto, 2014)。文化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 内侧前额叶参与了与自我相关的刺激加工(Northoff et al., 2006; Han & Northoff, 2009)。研究者比较丹麦人和中国人参照自己加工的脑电波, 发现丹麦人比中国人内侧前额叶的神经活动水平更高(Ma et al., 2014)。在东方文化中, 参照自我和参照亲密他人的加工具有共同的神经表征。西方人仅在自我参照条件下激活了内侧前额叶, 而中国人在自我参照条件下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出现了内侧前额叶的激活, 而且在母亲参照条件下和自我参照条件下所产生的神经激活水平相当(Zhu, Zhang,Fan, & Han, 2007; Vanderwal, Hunyadi, Grupe,Connors, & Schultz, 2008; Wang et al., 2012; Wuyun et al., 2014)。除母亲以外, 研究者也把参照对象扩展到其他的家庭成员。例如, Han, Ma和Wang (2016)要求被试分别参照自己、配偶、子女和一般他人做人格特质判断, 发现相比起一般他人参照条件, 男性和女性在自我、配偶和子女特质判断时内侧前额叶有类似的神经活动。研究还显示, 与亲密他人相联系的自我具有动态的认知神经表征, 这种表征会因为文化启动的不同而变化。Ng, Han, Mao和Lai(2010)考察具有双文化背景的香港人在不同文化启动下的自我表征变化, 发现在受到中国文化符号图片启动后, 被试在自我与母亲的特质判断任务中均表现出内侧前额叶的活动增强; 在受到西方文化符号启动后, 内侧前额叶的活动在母亲判断任务中出现了减弱, 却在自我判断任务中有所增强。这种自我表征的暂时性的动态变化与自我建构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一致, 反映了文化价值长期累积的影响。
作为独特的文化形式, 宗教对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具有较大的影响。宗教信徒和非信徒的自我神经表征存在着差异。在自我特质判断中, 中国佛教徒和基督教徒激活了背内侧前额叶,非宗教徒却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Han et al., 2008;Han et al., 2010)。Han等(2008)发现, 中国佛教徒在释迦牟尼参照下背内侧前额叶有持续的激活, 而且与非信徒比, 扣带回也参与自我人格特质判断。中国基督徒在耶稣参照下背内侧前额叶的激活明显高于非信徒(Han et al., 2008)。Wu等(2010)发现, 藏族人在自我特质判断时背内侧前额叶和腹内侧前额叶未激活, 却激活了颞中回, 说明藏传佛教的“无我”教义使得信徒的自我感降低, 未出现自我参照效应。回族大学生在阿訇参照条件下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周爱保, 张奋, 马晓凤, 李建升, 夏瑞雪, 2015)。可见, 宗教领袖作为宗教文化中的重要他人, 成为信徒的自我的一部分。
在自我的形成和发展中, 语言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语言既是文化的属性, 又是文化的部分, 还是文化的条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2006)。由于在不同语言中沉淀了不同文化有关人格的理论和原型, 个体在掌握某种语言时, 也就掌握了该语言代表的文化有关人格的看法。因此, 语言影响人格(张积家, 于宙, 乔艳阳, 2017)。人格具有复杂的结构, 自我是广义人格的一部分。语言是否影响自我构建?Bakhtin (1998)认为, 自我是在语言中与他人密切互动构建的实体。自我与他人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维果茨基(1986)认为, 自我是在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不断成熟转化的结果, 与他人对话是自我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 语言影响自我也得到了诸多实证研究的证实。例如, 在相同参照比较下, 不同类型的记忆材料产生的自我参照效应大小不同。对亚裔加拿大人而言, 在集体特质材料记忆中, 出现了明显的自我参照效应; 而在个人特质材料记忆中, 他人参照效应却比自我参照效应更大,出现了自我参照效应的逆转(Wagar & Cohen,2003)。对维吾尔族被试而言, 以维语作为启动材料时, 自我参照加工的成绩显著优于其他条件; 以普通话作为启动材料时, 自我参照加工及母亲参照加工的成绩显著高于其他条件(祖力皮努尔·艾力,2016)。此外, 多项研究发现, 相比起消极效价的形容词, 人们对积极效价形容词的自我参照效应更加显著(D’Argembeau, Comblain, & van der Linden,2005; D’Argembeau & van der Linden, 2008;Sedikides & Green, 2000; Leshikar, Park, & Gutchess,2015; Durbin, Mitchell &Johnson, 2017)。对中、英两种语言比较发现, 中国留学生在中文条件下对自我具有更多的集体主义描述,更认同中国文化的观点, 在自尊测验中得分较低(Ross, Xun & Wilson,2002)。乔艳阳、张积家、李子健和江姗(2017)发现,语言影响汉、苗、回族大学生的自尊, 没有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文字的回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显著高于有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文字的汉族大学生和有本民族语言却不经常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苗族大学生, 但内隐自尊水平却显著低于汉族、苗族大学生。
语言包含有诸多的成分, 如词汇、语义、语法、语音、语用等。亲属词是语言的重要词类。亲属词表征亲属关系, 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婚姻和文化信息。研究表明, 亲属词影响亲属关系认知, 其途径有:(1)语言标记。不同的语言对亲属关系作不同的区分, 有不同的标记。(2)知觉类别效应。人们对本民族语言的亲属分类维度更加敏感, 对本民族语言没有的亲属分类维度不敏感。例如, 摩梭人的亲属称谓属于类别式, 同辈分、同性别的亲属称谓相同,因此在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出现了辈分维度(肖二平,张积家, 王娟, 林娜, 2010)。(3)理论和语境(肖二平,张积家, 2012)。张积家、王娟、肖二平与和秀梅(2013)发现, 在满月酒、结婚和吊唁情境下, 摩梭人与汉族人分别对亲属词有不同的分类。亲属称谓是否影响自我建构, 如果影响, 就为语言影响自我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沈雪芬在大会致辞中肯定了南浔木地板产业的发展,并表扬了包括世友地板、久盛地板、森林之星地板等优秀地板品牌。她相信,中国地板产业必将形成新的格局,并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摩梭人是居住在川滇交界的母系群体, 他们以泸沽湖为中心, 被称为“地球上最后的女儿国”。摩梭人的婚姻形式为“阿注婚姻”。建立阿注关系的男女彼此互称“阿注”[汉译为“朋友”, 心理含义也是“朋友” (肖二平, 张积家, 王娟, 2015)], 男子夜晚到女子家中访宿, 第二天清晨返回到自己家中。偶居的男女不组织家庭, 属于不同的经济单位(詹承绪, 王承权, 李近春, 刘龙初, 2006)。这种“暮合晨离”的两性关系使得摩梭人形成了母系家庭。这种母系家庭由一个始祖母及其姐妹的后裔组成, 其后代是上一代女性成员的子女, 男性成员的子女属于其“阿注”的家庭。摩梭人从小就与始祖母、母亲和母亲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 与母系血缘的同辈人相伴成长, 由母亲和母亲的姐妹共同抚养长大, 将母亲及其姐妹一律视为“自己的母亲”, 将自己和姐妹的子女一律视为“自己的子女”, 形成了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在摩梭语中, 有一个独特的发音――“咪”, 其基本义是“母亲”, 冠于女性称谓之后是女性的通称义, 冠于名词之后表示“大的、主要的、首要的”。摩梭人将母亲视为伟大的象征, 这种文化反映在语言中, 表现为凡有“大的、重要的、主要的”等意义的词后面都带“咪”。在“母亲”与“大的、重要的、主要的”之间建立了联系, 映射出摩梭人具有“尊母崇母”的文化心理。摩梭人将母亲和母亲的姐妹都称为“阿咪”。“阿咪”在摩梭语中是一个复数概念, 在所有阿咪中, 长于母亲者被称为“阿咪直”(大妈妈), 幼于母亲者被称为“阿咪吉” (小妈妈),有时甚至连大、小都不区分,更无所谓“姨”了(詹承绪 等, 2006; 严汝娴, 刘小幸, 2012; 许瑞娟,2014)。在摩梭文化中, “母婴”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的起点, “这种骨肉相连你我一体的血浓于水, 却延伸及推己及人恩泽终生的层次, 甚至拓展为整个文化无处不在的深层结构”。因此, 摩梭文化可以概括为“阿咪”文化(周华山, 2010)。
为了更好地推进会计信息化管理工作,对于企业而言,必须从员工的思维能力、企业的管理制度以及会计工作自身的特点出发,来进行完善。
与摩梭人不同, 汉族人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符合费孝通(1985)提出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 是一种同心圆式的社会关系, 从自己开始,仿佛一枚石子投入了水中, 波纹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越推越远, 越远越薄。在波纹波及的范围内, 对象属于自己人; 反之, 对象属于外人。因此, 汉族人是以“自己”为中心, 与自己关联的人按照与自己关系的远近、亲疏排列在不同位置上, 离中心越近,与“我”的关系就越亲近, 就属于“圈内人”; 离中心越远, 与“我”的关系就越疏远, 就属于圈外人。汉族人用容器隐喻(内/外)来映射人际关系的亲疏,“内”表示个体与对象关系亲近, “外”表示个体与对象关系疏远(Lakoff & Johnson, 1980; 汪新筱, 江姗,张积家, 2018)。费孝通(1985)认为, 血缘和地缘等客观属性是汉族人区分“内/外”的重要因素。家族、家门、氏族是划分圈内人的重要标准。张积家(2018)认为, 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共同决定的:在宏观上, 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重视容器隐喻; 在微观上, 在同一“容器”的内部, 又存在着差序格局。
因此, 对父系制的汉族人而言, 父系亲属是“内”, 母系亲属是“外”。摩梭社会是母系社会, 血缘以母系来计算, 继嗣以女性血缘为线索。因此,母系亲属是“内”, 父系亲属是“外”。以往对自我的研究多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 较少涉及语言对自我的影响, 而且已有研究表明, 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包含有母亲。在母系文化中的摩梭人, 其自我是否与汉族人有异?在摩梭人的心中, 到底有几个母亲?摩梭人将姨母称为“阿咪”, 究竟是一种客气的人际关系策略, 还是他们在认知上真的将姨母与母亲等同?母亲及姨母作为与摩梭人的自我紧密联系的他人, 是否都成为摩梭人自我的一部分?笔者猜测,由于在摩梭人的语言中母亲与姨母共享“阿咪”称谓, 可能导致他们对母亲与姨母的认知趋于等同。而且, 摩梭人的母系制家庭和语言中独特的“阿咪”称谓也可能使摩梭人的自我具有不同特点, 他们的自我边界会比汉族人更加模糊, 在自我中除了有母亲以外, 还可能包括姨母。拟采用经典的提取诱发遗忘范式, 探讨摩梭人是否将姨母纳入自我的结构中, 以揭示汉族人和摩梭人的自我结构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131名摩梭人, 均来自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年龄范围12~35岁, 男性72人, 女性59人, 平均年龄为15.6 ± 3.7岁, 由于被试选择的限制, 被试多数为中学生, 只有小部分为成年人(20~30岁的被试有3人, 30岁以上的被试有4人),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126名汉族人, 来自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和拉伯乡, 年龄范围13~38岁, 男性67人, 女性59人, 平均年龄为14.6 ± 2.6岁, 被试也多为中学生,小部分为成人(20~30岁的有2人, 30岁以上的有1人),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将131名摩梭被试和126名汉族被试分配到不同加工条件。摩梭被试:自我组31人, 母亲组36人, 姨母组31人, 他人组33人; 汉族被试:自我组31人, 母亲组30人, 姨母组34人, 他人组31人。实验前对被试访谈, 能够区分汉语中“母亲”和“姨母”含义的被试方可以参与实验。另外, 只有家中有姨母的被试才参与姨母组的实验。
2.2 材料
32个代表室内物品和室外物品的名词, 代表室内物品和室外物品的双字词各16个, 每一个名词的第一个字在全部双字词中都是唯一的。呈现形式为“类别–样例”, 如“室内用品–衣柜”、“室外用品–雨伞”。实验材料来自周爱保等(2015)的研究, 表示室内物品和室外物品的名词熟悉性均经过评定。将32个双字词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提取练习项目,即类别名称及样例首字在提取练习阶段都出现的8个词对, 标记为“Rp+”; 第二类为类别名称在提取练习阶段出现过但样例未出现的8个词对, 即与“Rp+”属于同一类别但未经过提取练习的词对, 标记为“Rp–”; 最后一类是类别名称和样例均未做过提取练习的16个词对, 标记为“Nrp”。在正式实验之前, 另有4个练习词对。
2.3 设计
2(民族:摩梭/汉族) × 4(加工任务:自我参照加工/母亲参照加工/姨母参照加工/他人参照加工)× 3(项目类型:Rp+/Rp–/Nrp)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民族和加工任务为组间变量, 项目类型为组内变量。
此外,对于西文文献的编纂,国立北平图书馆也延揽了专门的人才。例如顾子刚于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史学系,长于英语及西方文化研究。入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前他曾在清华学校图书馆任参考馆员,1924至1925年间多次在《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介绍英文书籍。梁思庄于1930年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3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她精通英语,尤其擅长西文图书编目。
2.4 程序
采用经典的提取诱发遗忘范式, 包括4个阶段:
百日咳一年四季均可发病。百白破疫苗应用前(1954—1969年),病例构成比最高月份 (7月,9.91%)和最低月份(10月,5.43%)相差4.48个百分点。疫苗推广使用时期(1970—1989年),最高月份(5月,12.90%)和最低月份(10月,4.07%)构成比相差8.83个百分点。百白破疫苗接种率90%以上时期(1990—2017年),最高月份(6 月,15.41%)和最低月份(11月,1.73%)构成比相差13.68个百分点。随着1970年疫苗的推广使用,季节性流行特征凸显,呈现春夏季明显高发的趋势。见图2。
(2)提取练习阶段:学习的名词呈现完后, 马上进行提取练习。提取练习随机从呈现的室内用品和室外用品中选取一类, 从中随机选取8个名词以“类别名称–样例”的形式呈现给被试, 但样例名词只给出第一个字, 如“室内用品–衣__”、“室外用品–雨__”等, 被试需要回忆并在答题纸上写出残缺的单字。在每种加工条件下, 随机选取一半被试将室内用品作为提取练习词对, 另一半被试将室外用品作为提取练习词对。每组词对呈现5 s, 先后呈现3次。
共发放调查问卷1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077份,有效回收率89.75%。977名医学生中,男403例,女574例,其中18岁以下者占2.97%,18~25岁者占比96.93%,2017级227例(23.23%),2016级275例(28.15%),2015级263例(26.92%),2014级212例(21.7%);参与过医患沟通课程者93例(2014级麻醉专业46例、2014级临床专业47例),未参加过者884例,及100名非医学生。
1003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by 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 and cardioembolism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1 segment occlusion: a single 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4(加工任务: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他人参照) × 2(项目类型:Rp+/Nrp)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 在摩梭被试中,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127)=1394.25,p 〈 0.001,=0.92, 95%CI=[0.46,0.51], Rp+项目的回忆率显著高于Nrp项目; 加工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127)=0.21, p 〉 0.05; 项目与加工任务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3, 127)=1.03,p 〉 0.05。在汉族被试中,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122)=538.94, p 〈 0.001, = 0.82, 95%CI =[0.41, 0.49], Rp+项目的回忆率显著高于Nrp项目;加工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122)=0.95, p 〉0.05; 项目类型和加工任务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3,122)=1.76,p 〉 0.05。这表明, 在不同民族中, 提取练习对提取促进记忆具有显著影响。因为Rp+材料是被试在提取练习阶段提取过的, 所以Rp+材料的回忆率显著高于基线水平的Nrp材料。
(4)回忆阶段:要求被试自由回忆并且在答题纸上写出学习阶段出现的室内用品和室外用品的名称, 顺序不限, 时间不限, 直到被试停止作答。
3 结果与分析
3.1 总回忆率
不同民族的被试在不同加工任务下的总回忆率见表1。
4.2.2 语言对自我的影响
2(民族:汉族/摩梭人) × 4(加工任务: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他人参照)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49)=2.01, p 〉 0.05;加工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249)=0.54, p 〉 0.05;民族与加工任务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3, 249) =1.52, p 〉 0.05。这表明, 民族与加工任务对总回忆率没有显著影响。
3.2 提取促进记忆
摩梭被试和汉族被试在不同条件下对Rp+材料与Nrp材料的回忆率见表1和图1。
(3)干扰阶段:在提取练习阶段之后是3分钟的干扰阶段, 计算机随机呈现两位数或3位数的加法,要求被试算出结果。
3.3 提取诱发遗忘
比较摩梭、汉族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Rp–材料与Nrp材料的回忆率, 结果见表1和图2。
4(加工任务: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他人参照) × 2(项目类型:Rp–/Nrp)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表明, 在摩梭被试中,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27)=1.22, p 〉 0.05; 加工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127)=2.16, p 〉 0.05; 项目与加工任务的交互作用显著, F(3, 127)=4.00, p=0.009,= 0.09。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条件下两类项目的差异均不显著, F值均小于0.30,ps 〉 0.05; 在他人参照下, 两类项目差异显著,F(1, 127)=12.65, p=0.001, 95%CI=[–0.15,–0.04]。在汉族被试中, 项目类型的主效不显著,F(1, 122)=3.51, p 〉 0.05; 加工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122)=0.94, p 〉 0.05; 项目类型与加工任务的交互作用显著, F(3, 122)=2.98, p=0.034, =0.0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 两类项目的差异均不显著, F值均小于0.60,ps 〉 0.05; 在姨母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 两类项目的差异显著, F姨母参照(1, 122)=4.78, p=0.031,95%CI=[–0.14, –0.01]; F他人参照(1, 122)=7.29, p =0.008, 95%CI=[–0.16, –0.03]。
表1 摩梭、汉族被试在四种不同加工任务中的回忆率
注:*p 〈 0.05, *** p 〈 0.001; (Rp+) – Nrp:提取促进记忆, (Rp–) – Nrp:提取诱发遗忘
任务 民族 N总回忆率 Rp+ Rp– Nrp (Rp+) – Nrp (Rp–) – Nrp自我摩梭 31 0.42 (0.07) 0.80 (0.08) 0.31 (0.10) 0.29 (0.11) 0.51 (0.11) *** 0.01 (0.11)汉族 31 0.41 (0.07) 0.79 (0.14) 0.29 (0.12) 0.27 (0.15) 0.53 (0.23) *** 0.03 (0.20)摩梭 36 0.43 (0.05) 0.78 (0.10) 0.31 (0.08) 0.30 (0.07) 0.48 (0.12) *** 0.01 (0.07)母亲汉族 30 0.43 (0.08) 0.76 (0.16) 0.33 (0.17) 0.32 (0.11) 0.44 (0.18) *** 0.01 (0.18)摩梭 31 0.41 (0.09) 0.78 (0.11) 0.29 (0.11) 0.28 (0.14) 0.50 (0.16) *** 0.01 (0.16)姨母汉族 34 0.44 (0.12) 0.78 (0.16) 0.29 (0.14) 0.36 (0.21) 0.42 (0.28) *** –0.07 (0.18) *摩梭 33 0.40 (0.08) 0.76 (0.16) 0.21 (0.13) 0.31 (0.14) 0.45 (0.19) *** –0.10 (0.23) *他人汉族 31 0.44 (0.10) 0.78 (0.13) 0.26 (0.13) 0.35 (0.15) 0.42 (0.16) *** –0.09 (0.20) *
图1 摩梭被试和汉族被试在不同条件下对Rp+材料与Nrp材料的回忆率
图2 摩梭人和汉族人在不同条件下Rp–材料与Nrp材料的回忆率
图3 摩梭被试四种加工条件下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图4 汉族被试四种加工条件下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对四种加工任务的Rp–与Nrp的回忆率做配对样本t检验, 分析在不同的加工任务中两者的差异是否显著。如果Rp–类词对的回忆率显著低于Nrp类词对, 则表明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结果发现, 摩梭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和姨母参照条件下两者的差值都不显著(见表1), t自我参照(30)=0.69,p 〉 0.05, t母亲参照(35)=1.00,p 〉 0.05, t姨母参照(30) =0.35, p 〉 0.05, 在他人参照条件下两者的差值显著,t他人参照(32)=–2.38,p=0.024,d=0.74, 95%CI =[–0.18, –0.01]。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两者的差值不显著, t自我参照(30)=0.73,p 〉 0.05,t母亲参照(29)=0.31,p 〉 0.05, 在姨母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两者的差值显著, t姨母参照(33)=–2.21,p=0.034,d=0.39, 95%CI=[–0.13, –0.01], t他人参照(30) =–2.61, p=0.014,d=0.64, 95%CI=[–0.17, –0.02]。这表明, 摩梭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和姨母参照条件下都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在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图3); 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而在姨母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见图4)。即, 仅有摩梭被试出现了姨母参照效应。
3.4 排除输出干扰的影响
汉族人和摩梭人在母亲参照条件下均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再次证明了朱滢和张力(2001)的发现, 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包含有“母亲”。两个民族在姨母参照条件下的回忆出现了差异:摩梭人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汉族人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这表明, 对摩梭人而言, 在姨母参照加工时自我同样发挥作用, 使得记忆材料得到了精细加工, 在提取练习时未抑制Rp–材料, 因而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因此, 文化影响自我及其基本认知过程, 摩梭人已经将姨母整合进自我之中, 成为自我的一部分。然而, 在汉族人的自我中, 却不包含姨母。所以如此, 与两个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有密切关系。
4 讨论
4.1 关于总回忆率和提取促进记忆
在四种参照条件下的总回忆率无显著差异, 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Markus & Kitayama, 1991;杨红升, 朱滢, 2004; 周爱保 等, 2015)。但是, 将材料分为Rp+、Rp和Nrp比较时, 摩梭人和汉族人的自我参照条件相对于他人参照条件出现了记忆优势。另外, 两个民族在四种参照条件下的提取促进记忆差异显著, 也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在提取练习阶段加强了线索和目标词的联结, 在回忆阶段就容易首先回忆出来。
(3)加快发展新型接续产业是实现金昌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2018年8月6日,金昌市八届六次全体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是坚持以落实新发展理念为主线,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崛起。要加快发展新型接续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生物医药业等对第三产业发展带动性强的接续产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
4.2 关于姨母参照条件对提取诱发遗忘的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 摩梭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条件下均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在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 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条件下均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在姨母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已有研究显示,实验结果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并不一定是由于在提取练习阶段对Rp+项目的提取练习而对Rp–产生抑制导致的, 也可能是由于输出干扰引起的(Tulving & Arbuckle, 1963; Criss, Malmberg, &Shiffrin, 2011)。即做过提取练习的词对(Rp+)在回忆阶段更容易被首先回忆出来, 从而干扰了与这些词对属于同一类别但未做过提取练习的Rp–的回忆率, 使其低于基线水平。即, Rp–项目的回忆顺序晚于Rp+项目而对Rp–项目的回忆产生了干扰。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 采用Macrae和Roseveare (2002)的检验方法, 在Rp–的回忆率显著低于Nrp的条件下, 分别计算每个被试的Rp+和Rp–项目在整个回忆序列中的平均位置, 然后两者相减, 根据差值将被试分为高、低两组, 检验这两组被试的Rp–与Nrp的回忆率差值差异是否显著, 若不显著, 则二者回忆顺序对提取诱发遗忘没有影响。摩梭被试在他人参照条件及汉族被试在姨母参照、他人参照条件下都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所以对这三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F摩梭–他人(1, 31)=0.06, F汉族–姨母(1,32)=1.84,F汉族–他人(1, 29)=0.09, ps 〉 0.05, 差异均不显著, 因此可以排除输出干扰的影响。
4.2.1 文化对自我的影响
城市防洪应急预案是防御和处置城市各类洪涝灾害的实施方案,必须具有高度的完整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应根据城市发展实际,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修订完善已有应急预案,不断提高预案的实效性。构建覆盖各项工程、各个单位、各个小区的城市防洪排涝预案体系,使基层防御工作有章可循。完善不同类型洪涝灾害的专题应急预案,分析各类灾害风险,针对不同等级风险制定相应防御方案,不断提高预案的针对性。
因此, 无论是“内外”二分的亲属制度, 还是“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 都直接反映了汉族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然而, 在摩梭文化中,女性却具有崇高的地位。母系血缘是维系摩梭人家族的纽带, 由母系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单位称为“家屋”。“家屋”被摩梭人视为独立而神圣的生命实体, 其价值超乎任何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屋”都有自己的名字, 这也成为屋内人们的姓氏。“家屋”对摩梭人而言不是一堆木头搭成的“物”, 而是凝结了摩梭人祖先长久漂泊之后定居的夙愿。因为先祖的游牧生活伴随着贫困、危险和匮乏, “家屋”则注重稳定、团结、永恒和拒绝分离(许瑞娟, 2014)。因此,摩梭人尤其强调亲兄弟姐妹厮守终生, 拒绝婚姻,因为婚姻会导致“家屋”分裂。只有人在屋中, 屋在心中, 才能够心连心, 屋永存。所以, 摩梭人视“家屋”为感情的终极归宿。“家屋”的团结和谐是摩梭人内心中最幸福的向往。摩梭人男不娶, 女不嫁,偶居的双方各居母家, 男子除了夜晚访宿女子家外,其余时间回到自己家中生产与生活, 兄弟姐妹关系最为亲近。在摩梭母系家庭中, 女人的身份是母亲或者姐妹, 而非妻子; 男人的身份是舅舅或者兄弟,而非父亲或者丈夫。摩梭人从小就与母亲、姨母、舅舅生活在一起, 与母系亲属的亲密程度最高。对生父或其他父系亲属, 虽然也具有共同血缘, 但是,除了少数感情深厚者外, 大多亲密度不高。汉族人虽然小时候与兄弟姐妹一起生活, 长大以后却各自组建了独立的家庭, 兄弟姐妹的关系会随着距离远、联系频率低而逐渐疏远。因此, 虽然姨母对汉族人和摩梭人而言具有相同的客观血缘关系, 但是,他们与个体之间的亲密程度却受到联系频率影响,感情联系有着天壤云泥之别, 最终导致摩梭人将“姨母”纳入自我结构中, 而汉族人的姨母却不在自我之内。
汉族是典型的父系社会。汉文化一直主张“亲疏有别”:血缘关系越近, 亲属的亲密程度越高, 在亲属网络中距离越近。在汉族人的传统观念里, 亲属被内、外二分。“内”是指宗亲, 包括父系同姓亲属、父系未出嫁女性和父系男性的配偶; “外”是指非宗亲, 即外亲, 包括母系亲属、妻系亲属、父系女性(姑、姐妹、女儿)的子女, 如外祖父母、姨母、外甥、外孙等(骆明弟, 2008)。《尔雅·义疏》:“言外者所以别于父族也。”可见, “外”是为了区别内亲和外亲而设立的。汉族人重内亲、轻外亲。古代汉族人为了突出“宗亲”以示其“正”, 宗亲以“堂”称之,如“堂叔、堂侄、堂哥、堂妹”等。与“堂”相对, 表示外亲的是词素是“表”, 表亲又分为舅表、姑表和姨表。在表亲中, 舅表最亲, 舅舅虽然是外亲, 但各个民族都有“尊舅”的传统。在汉语谚语中, 有“三代不出舅家门”、“娘舅为大”的说法。因为舅舅的家族为“我”的家族提供了母亲, 使“我”的家族得以延续, 因此应当感恩。其次是姑表亲, 姑姑是出自宗族的女性, 是父亲的姐妹, 姑表亲也具有父系血缘。对汉族人而言, 姨表亲之间由于缺乏父系血缘联系, 又不具有感恩的理由, 所以最为疏远。例如,在《红楼梦》第二十回中, 宝玉对黛玉说:“咱们是姑舅姊妹, 宝姐姐是两姨姊妹, 论亲戚他比你疏。”在汉语俗语中也有:“叔伯亲, 骨肉亲, 堂亲三代,世代同姓三分亲。姑舅亲, 辈辈亲, 姑表二代, 打断骨头连着筋。姨娘亲, 当辈亲, 姨表一代, 死了姨娘断了亲。”堂亲三代是指:亲堂兄弟姐妹(又称叔伯兄弟姐妹, 同一祖父)、从堂兄弟姐妹(同一曾祖父)、远堂兄弟姐妹(同一高祖父); 姑表二代是指:姑舅表兄弟姐妹、姑舅表兄弟姐妹的子女; 姨表一代是指:姨表兄弟姐妹。对汉族人而言, 只有这些人才算是亲属。从叔伯亲到姨娘亲, 汉族人的亲属范围迅速缩小, 可见汉族人对姨表亲的轻视。
(1)学习阶段:在计算机屏幕上每5 s呈现一个单词对, 采用“类别名称–样例”形式, 如“室内用品–衣柜”、“室外用品–雨伞”。在呈现词对的同时, 四组被试分别想象自己、母亲、姨母和他人(姚明)在某时间或某地点看到该单词代表的物品, 同时要用一句话口头报告所想象的情景。口头报告的形式必须完整, 即包括主语(“我”、“母亲”、“姨母”、“他人”)、谓语(看到、看见、买了)、宾语(该单词所代表的物品)以及一个地点状语或时间状语, 如“我昨天看到一件衣柜”、“母亲在家里看到一个脸盆”、“姨母在商场买了一把雨伞”、“姚明在操场看见一个足球”等。每一被试随机安排在某种条件下单独完成任务。
另外, 汉族在封建社会中也存在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 嫁给同一男子的妇女有“妻、妾”之分。妻又称“正室、结发、原配”, 妾又称“偏房、侧室”。《说文解字》:“妾, 有罪女子。”“妾”的本义是女奴,也用来表示男子在妻子以外另娶的女子。在古代,父亲的正妻为“嫡母”, 父亲的妾被称为“庶母”。妻所生的长子是嫡子, 其余的儿子为庶子, 妾所生的儿子比妻的庶子地位更低(谢玉娥, 1999)。在古代,汉族人也称父之妾为“姨”或“姨娘”。如在《红楼梦》中, 探春与贾环虽然是赵姨娘亲生, 却只能称为赵姨娘为“姨娘”而不能称为“娘”。在近代, 称富人取之妾为“姨太太”, 以别于作为正妻的“太太”。可见,在封建社会中, 汉族人存在着多个女性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模式, 但妻妾有尊卑之别, 子女有嫡庶之分。子女与生母及其他母亲的亲疏关系受生母的地位影响, 使得子女不可能得到所有母亲的宠爱,母亲也不可能将其他女性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同等对待。
自我以开放的形式与文化发生作用。自我在文化中形成和塑造, 反过来又再现或再造文化(葛鲁嘉, 周宁, 1996)。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信念、交流方式, 自我表征也存在着差异(朱滢,2007)。在西方文化中生活的人形成了独立型自我,在东方文化中生活的人形成了依赖型自我(Markus& Kitayama, 1991)。独立型自我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分离性, 依赖型自我拥有更多的公共成分, 人们注重与他人保持和谐关系, 与重要他人互有重合。杨红升和朱滢(2004)的研究表明, 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包含有母亲, 在母亲参照条件下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这一看法在汉族人和摩梭人中均得到了验证。而在姨母参照条件下, 汉族人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摩梭人则未出现。
“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徐艺,听我一句临别赠言,永远不要沾上赌博,否则,你早晚和我一样,从人生的最高处瞬间跌到地上,永远起不来。是的,永远。不过,我要谢谢你,小兄弟,是你让我明白我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刚才……我似乎有些留恋这个世界,但你给了我最后的勇气,你可以走了。”
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理解是文化移植的过程。每一语言都有表征亲属关系的亲属词, 它们既是人对亲属关系认知的产物, 又影响人对亲属关系的认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2006)认为, 亲属关系既具有生物学基础,也需要通过语言的反复使用来加以巩固。人类社会有两大系列亲属现象:一是由不同称呼语词表达的亲属关系语词系统, 二是由亲属的相互态度构成的亲属关系态度系统。亲属之间的相互语词称呼, 构成了实际亲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使用亲属关系语词系统的个体或群体, 由于语词所表达和指谓的特定关系, 在行为上受到了语词规定的约束。使用这些语词就等于“做”这些语词所规定的关系规则。亲属关系的传承需要亲属称呼系统的确认。亲属称谓规定了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和态度规范, 也包含着个人拥有的权利和责任。个体在使用亲属词时, 同时也隐含着实行由亲属关系要求的不同态度,如尊敬或亲近、亲情或敌意等。因此, 对于同一亲属, 讲不同语言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这些蕴含在语词意义中的亲属之间不同态度的因素, 包含着比语词称呼关系更重要的心理、情感和社会关系因素,在保障亲属关系维持和运作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些看法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一致。恩格斯(1972)指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 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 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研究表明, 语言标记影响亲属词认知(汪新筱等, 2018; 肖二平, 张积家, 2012)。在语言中, 某些基本的、经常出现的成分被认为是有标记的(理查兹, 2000)。语言标记使得人们更容易选择某些认知途径、认知过程和认知策略。不同民族的语言将亲属词划分为不同的维度, 具有不同的标记。汉语用“内、堂、外、表”来标记亲属词, 如称呼姐妹的孩子为“外甥”或“外甥女”, 称呼女儿的孩子为“外孙”或“外孙女”。这种亲属标记在记忆表征中更加凸显,个体在加工中会格外留意, 从而更容易将“内亲”或“堂亲”看作是“自家人”, 将“外亲”或“表亲”当成“外面人”。这种“内外”有别、“堂表”有别的分类一旦形成, 就会使人们对这两类亲属采取不同的态度。姨母在汉族亲属制中属于表亲。表, 外也。《说文解字》:“表, 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 以毛为表。” (许慎, 1963)。表亲在汉族人具有差序格局特点的亲属关系网络中处于离自我中心较远的位置,因而汉族人与姨母的关系一般比较疏远。
摩梭人十分重视母系血缘亲属的心理情感和“家屋”本位的传统文化。摩梭亲属词以女性亲属词为主, 父系亲属称谓和姻亲称谓少, 而且大多以母系亲属称谓的叙述方式来表达(肖二平 等, 2010)。摩梭亲属称谓也不区分直系和旁系, 姨表兄弟姐妹与兄弟姐妹同称, 没有“堂、表”的概念。摩梭人将生母和生母的姐妹都称为“阿咪”。“阿咪”文化让摩梭孩子自幼共享所有母亲的爱, 也让摩梭儿童自幼形成了博爱式的“多元思维”, 长大以后也少有独占情人的欲望。肖二平等(2010)发现, “阿咪”被分在核心家庭成员的长辈中。在摩梭人的观念里, 所有的母系血缘亲属都是自家人, 很少刻意区分谁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认为母亲及其姐妹都是自己的母亲,亲生或非亲生的区分并不重要。过去, 很多摩梭孩子直到成年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 有时非生母比生母对自己还要好。只要来自同一个“家屋”,就是亲人, 就是“同一根骨头”, 不分彼此。因此,“阿咪”称谓不仅表达了个体对姨母的尊重, 也拉近了个体与姨母之间的心理距离。母亲与姨母共享“阿咪”称谓, 个体对她们也就产生了同样的态度。周华山(2010)说:“ ‘阿咪’已经从生物学词汇提升为一种整体文化的核心符号, 一种集体潜意识, 不单代表着对妇女主体与地位的肯定,更是一种以情感和谐、家族团结、敬老爱幼为本的思想模式与价值观。” “阿咪”的慈爱不仅弥漫在每一个摩梭家庭里,更是摩梭文化的主旋律。摩梭人在反复使用“阿咪”来称呼母亲和姨母时, 与所称呼者的“母子”关系便得到了确认和巩固, 同时也隐含着实行由“母亲”称谓所包含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亲近态度, 使他们在心理、情感上将母亲和姨母看得同等重要, 并且使这种“母子”关系得到了较好的维持和运作。喊一声“阿咪”, 称呼者与被称呼者的内心顿时会暖意丛生, 情感会迅速地亲密起来。因此, “阿咪”称谓不仅体现了摩梭社会讲究伦理秩序的社会风尚与优良传统,更体现了摩梭家屋的“一辈子关爱、不分彼此”的情感理念。因此, 摩梭人视“姨母”如生母, “姨母”和生母均被纳入自我中, 使得自我结构的边界比汉族人更加模糊。近年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很多摩梭人从“家屋”中分离出来建立了独立的家庭。但是, 千百年来的摩梭母系文化、“家屋”本位文化仍然根植于年轻一代的摩梭人心中。
佐科维强调,印度尼西亚有信心成为世界海上轴心,通过《印度尼西亚海事政策和行动计划》(Indonesia Maritime Policy and Action Plan),在全球海事力量中发挥关键作用。该计划包括改善海上连通性、发展和升级477个海港,以及大幅度减少海洋塑料废物等等。他还指出,由于气候变化、水污染和塑料垃圾,海洋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海洋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也存在着不一致之处。Dai等人(2014)发现, 相对于陌生女性, 摩梭儿童识别生母和姨母的面孔诱发出更大的右侧N170成分, 但识别生母面孔比识别姨母面孔诱发出更大的N1成分、左侧N170成分和P300成分。这可能是因为被试的年龄较小(平均年龄5.8岁),对哺乳自己的生母的依恋程度更高所致。但是, 随着个体在家屋中逐渐长大, 个体为传统摩梭文化所濡化, 生母与姨母的界限就趋于消失了。另外, 由于被试选择的限制, 本研究的被试年龄差异较大,有少量是成年人。年龄不同,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年龄和文化对自我建构的交互作用。
2.2比较两组患儿外漏、低血糖、皮下沉积等并发症发生情况,具体情况(见表2),实验组共有3例患儿发生并发症,对照组共有7例患儿发生并发症,实验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总之, 文化和语言均与自我休戚相关。独特的母系文化和由此衍生的亲属称谓深深地影响着摩梭人的心理和行为, 进而影响着摩梭人的自我的形成和发展。
5 结论
(1)在汉文化和摩梭文化中, 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都是引起提取诱发的关键因素。
(2)在摩梭文化中, 姨母参照是除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之外的影响提取诱发的又一关键因素, 姨母作为重要他人被整合于摩梭人的自我结构中。
(3)语言和文化均是自我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评价结果来看,2000—2005年研究区人为干扰主要为中度正向干扰与轻度负向干扰,在整个研究区分布都较为均匀;2005—2010年人为干扰主要以正向干扰为主,轻度正向干扰与强度正向干扰主要集中在甘孜县、色达县、壤塘县以及阿坝县,石渠县则以中度正向干扰为主,若尔盖县与红原县中度正向干扰零星分布,负向干扰以中度为主,零星分布于研究区;2010—2014年研究区人为干扰主要以轻度负向干扰为主,轻度负向干扰集中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各县,强度负向干扰零星分布于研究区,中度负向干扰主要分布在若尔盖县与红原县,人为正向干扰区域较小,除若尔盖县轻度正向干扰较为集中外,正向干扰零星分布于其他县。
参 考 文 献
Anderson, M.C., Bjork, R.A., & Bjork, E.L.(1994).Remembering can cause forgetting:Retrieval dynamics in long-term memor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0(5), 1063–1087.
Bakhtin, M.(1998).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on Press.
[巴赫金.(1998).巴赫金全集: 卷4.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Barber, S.J., & Mather, M.(2012).Forgetting in context:The effects of age, emotion, and social factors on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Memory and Cognition, 40(6), 874–888.
Campbell, J.I.D., & Thompson, V.A.(2012).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of arithmetic facts.Journal of Experimental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38(1), 118–129.
Criss, A.H., Malmberg, K.J., & Shiffrin, R.M.(2011).Output interference in recognition memory.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64(4), 316–326.
D’Argembeau, A., Comblain, C., & Van der Linden, M.(2005).Affective valence and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Influence of retrieval conditions.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6(4),457–466.
D’Argembeau, A., & Van der Linden, M.(2008).Remembering pride and shame:Self-enhancement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Memory,16(5),538–547.
Dai, J.Q., Zhai, H.C., Wu, H.Y., Yang, S.Y., Cacioppo, J.T.,& Cacioppo, S., Luo.Y.J.(2014).Maternal face processing in Mosuo preschool children.Biological Psychology, 99,69–76.
Durbin, K.A., Mitchell, K.J.& Johnson, M.K.(2017).Source memory that encoding was self-referential:The influence of stimulus characteristics.Memory, 25(9),1191–1200.
Engels, F.(1972).The origins of families, privates, propertysystems and states.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les (4).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4).
[恩格斯.(197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北京:人民出版社.]
Fei, X.T.(1985).Local China. Beijing:Joint Publishing.
[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Ge, L.J., & Zhou, N.(1996).From th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to culture and self:The transfer of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gravity.Seeking Truth, (1), 27–31.
[葛鲁嘉, 周宁.(1996).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心理人类学研究重心的转移.求是学刊,(1), 27–31.]
Han, S.H., Gu, X.S., Mao, L.H., Ge, J.Q., Wang, G., & Ma,Y.N.(2010).Neural substrates of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in Chinese Buddhists.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5(2-3), 332–339.
Han, S.H., Ma, Y.N., & Wang, G.(2016).Shared 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self and conjugal family members in Chinese brain.Culture & Brain, 4(1), 72–86.
Han, S.H., Mao, L.H., Gu, X.S., Zhu, Y., Ge, J.Q., & Ma, Y.N.(2008).Neural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belief on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Social Neuroscience, 3(1),1–15.
Han, S.H., & Northoff, G.(2009).Understanding the self:A cultural neuroscience approach.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178, 203–212.
Kobayashi, M., & Tanno, Y.(2013).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of words with negative emotionality.Memory,21(3),315–323.
Lakoff, G., & Johnson M.(1980).Metaphors we live by(pp.30–32).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shikar, E.D., Park, J.M., & Gutchess, A.H.(2015).Similarity to the self affects memory for impressions of others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70(5),737–742.
Lévi-Straus, C.(2006).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Beiji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8)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2006).结构人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uo, M.D.(2008).On the cultural nature of Chinese kinship appellation.Guizhou Culture and History, (4), 102–106.
[骆明弟.(2008).汉语亲属称谓之文化性初探.贵州文史丛刊,(4), 102–106.]
Ma, Y.N., Dan, B., Wang, C.B., Allen, M., Frith, C., &Roepstorff, A., Han, S.H.(2014).Sociocultural patterning of neural activity during self-reflection.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1), 73–80.
Macrae, C.N., & Roseveare, T.A.(2002).I was always on my mind:The self and temporary forgetting.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9(3), 611–614.
Mao.W.B, Zhao H.Y, Liu.L.Y., & Bai.L.(2016).The emotional memory trade-off effect in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8(10), 1219–1228.
[毛伟宾, 赵浩远, 东利云, 白鹭.(2016).提取诱发遗忘中的情绪记忆权衡效应.心理学报, 48(10), 1219–1228.]
Markus, H.R., & Kitayama, S.(1991).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Ng, S.H., Han, S.H., Mao, L.H., & Lai, J.C.L.(2010).Dynamic bicultural brains:fMRI study of their flexible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significant others in response to culture priming.Asian Journal Social Psychology, 13(2), 83–91.
Northoff, G., Alexander, H., Greck, M.D., Bermpohl, F.,Dobrowolny, H., & Panksepp.J.(2006).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in our brain—A meta-analysis of imaging studies on the self.NeuroImage, 31(1), 440–457.
Plaut, V.C., Markus, H.R., Treadway, J.R., & Fu, A.S.(2012).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well-being:A tale of two citie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12), 1644–1658.
Qiao, Y.Y., Zhang, J.J., & Li, Z.J., Jiang, S.(2017).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lf-esteem of college students of Han, Miao, Hui ethnic groups.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on Ethnic Minorities,28(3), 73–78.
[乔艳阳, 张积家, 李子健, 江珊.(2017).语言影响汉、苗、回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民族教育研究,28(3), 73–78.]
Richards, J.C., Platt, J., & Platt, H.(2000).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 applied linguistics (in Chines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理查兹, 普拉特, 普拉特.(2000).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Rogers, T.B., Kuiper, N.A., & Kirker, W.S.(1977).Self-reference and the encod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9),677–688.
Ross, M., Xun, W.Q.E., & Wilson, A.E.(2002).Language and the bicultural sel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Bulletin, 28(8),1040–1050.
Sedikides, C., & Green, J.D.(2000).On the self-protective nature of inconsistency-negativity management:Using the person memory paradigm to examine self-referent memor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6),906–922.
Tulving, E., & Arbuckle, T.Y.(1963).Sources of intratrial interference in immediate recall of paired associates.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5),321–334.
Uchida, Y., Ueno, T., & Miyamoto, Y.(2014).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The importance of “significant others”in the attenuation of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in Japan.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56(3), 263–274.
Vanderwal, T., Hunyadi, E., Grupe, D.W., Connors, C.M., &Schultz, R.T.(2008).Self, mother and abstract other:An fMRI study of reflective social processing.NeuroImage,41(4),1437–1446.
Vygotsky, L.S.(1986).Thought and Language.Cambridge,MA:MIT Press.
Wagar, B.M.& Cohen, D.(2003).Culture, memory, and the self:An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self in long-term memor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9(5),468-475.
Wang, G., Mao, L., Ma, Y., Yang, X., Cao, J., Liu, X., Wang,J., Wang, X., Han, S.(2012).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close others in collectivistic brains.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7(2), 222–229.
Wang, X.X., Jiang, S., & Zhang, J.J.(2018).Effect of the spatial linguistic symbol on the container metaphor of seniority rules.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0(9), 953–964.
[汪新筱, 江姗, 张积家.(2018).空间语言标记影响亲属词的空间隐喻. 心理学报, 50(9), 953–964.]
Wu, Y.H., Wang, C., He, X., Mao, L.H., & Zang, L.(2010).Religious beliefs influence neural substrates of selfreflection in Tibetans.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5(2-3), 324–331.
Wuyun, G., Shu, M., Cao, Z.J., Huang, W., Zou, X., Li, S.,Zhang, X., Luo, H., & Wu, Y.H.(2014).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and the mother for Chinese individuals. Plos One, 9(3), e91556.
Wu, Y.H., Wang, C., He, X., Mao, L.H., & Zang, L.(2010).Religious beliefs influence neural substrates of self-reflection in Tibetans.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5, 324–331.
Xiao, E.P., Zhang, J.J., Wang, J.(2015).The ‘A zhu’relationship under the sexual union in Mosuo matrilineal society:Akin to kinship or friendship?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7(12), 1486–1498.
[肖二平, 张积家, 王娟.(2015).摩梭走访制下的阿注关系:亲属还是朋友?心理学报, 47(12), 1486–1498.]
Xiao, E.P., & Zhang, J.J.(2012).National language influences national psychology:Evidence from classifying kinship words.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8),1189–1200.
[肖二平, 张积家.(2012).从亲属词分类看民族语言对民族心理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 20(8), 1189–1200.]
Xiao, E.P., Zhang, J.J., Wang, J., & Lin, N.(2010).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kinship words of the Mosuo.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2(10), 955–969.
[肖二平, 张积家, 王娟, 林娜.(2010).摩梭人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心理学报, 42(10), 955–969.]
Xie, Y.E., (1999).A look at the traditional gender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women from the ancient appellation custom.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9(5), 111–115.
[谢玉娥.(1999).从古代称谓习俗看我国妇女传统的性别文化身份.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9(5), 111–115.]
Xu, R.J.(2014).A study on Mosuo matriarchal culture terms.Beijing: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许瑞娟.(2014).永宁摩梭“母系”文化词群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Xu, S.(1963).Shuo wen jie zi.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许慎.(1963).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
Yan, R.X., Liu.X.X., (2012).Research on Mosuo mtrilineal system. Kunming: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严汝娴, 刘小幸.(2012).摩梭母系制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Yang, H.S., & Zhu, Y.(2004).The self an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6(2), 154–159.
[杨红升, 朱滢.(2004).自我与提取诱发遗忘现象.心理学报, 36(2),154–159.]
Zhan, C.X., Wang, C.Q., Li, J.C., & Liu, L.C.(2006).The‘A zhu’ marriage and matriarchy family of Yongning Naxi nationality. Shanghai:Shangha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詹承绪, 王承权, 李近春, 刘龙初.(2006).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Zhang, J.J.(2018).Container metaphor, preface-structure and national psychology.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39(5),214–221.
[张积家.(2018).容器隐喻、差序格局与民族心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9(5), 214–221.]
Zhang, J.J., Wang, J., Xiao, E.P., & He, X.M.(2013).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circumstance on kinship words’conceptual structur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5(8),825–839.
[张积家, 王娟, 肖二平, 和秀梅.(2013) 文化和情境影响亲
Zhang, J.J., Yu, Z, Qiao, Y.Y., (2017).Language influence on personality:Research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28(4), 74–82.
[张积家, 于宙, 乔艳阳.(2017).语言影响人格:研究证据与理论解释.民族教育研究, 28(4), 74–82.]
Zhou, A.B., Zhang, F., Ma, X.F., & Xia, R.X.(2015).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imam-reference processing:Based on the retrieval-induce forgetting paradigm discussed.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7(6), 757–764.
[周爱保, 张奋, 马小凤, 李建升, 夏瑞雪.(2015).阿訇参照效应的文化差异:基于提取诱发遗忘范式的探讨.心理学报, 47(6), 757–764.]
Zhou, H.S.(2001). Is it 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Beijing:Guangming Daily Publishing House.
[周华山.(2001).无父无夫的国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Zhu, Y.(2007).Culture and self.Beij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cation Hose.
[朱滢.(2007).文化与自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Zhu, Y., & Zhang, L.(2001).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about self-memory.Science in China (Series C), 31(6), 537–543.
[朱滢, 张力.(2001).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 中国科学C辑, 31(6), 537–543.]
Zhu, Y., Zhang, L., Fan, J., & Han, S.H.(2007).Neural basis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self-representation.NeuroImage,34(3), 1310–1316.
Zulipino, A.(2016).Uyghur individual’s self-reference effect based identity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Xinan University.
[祖力皮努尔·艾力.(2016).维吾尔族身份启动对自我参照效应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属词的概念结构.心理学报, 45(8), 825–839.
Influenc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on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under the self-referential condition: Evidence from the Han and the Mosuo
WANG Bin; FU Ya; ZHANG Jiji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Cultural, and Psychology;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the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individuals may forget related information during the retrieval process whenever they try to remember something.Studies have shown that“self-reference” is one of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RIF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 indicating that RIF is only eliminated when the recalled materials are related to self-concept (known as the “self-referential effect”).In the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RIF was observ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elf-reference and maternal reference.The Mosuo people are raised in a matrilineal society, in which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ir mothers and aunts to the same extent.Such people consider their aunts and natural mothers as equally important.Conversely, the Han is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the Mosuo’s.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of the Mosuo and Han on their self-cognition and processing,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ir aunts on their self-conception.
Tested participants included 131 Mosuo and 126 Han from Yunnan’s Ninglang District.The experiment had a 2 (Nationality:the Mosuo, the Han) × 4 (Conditions:Self-reference, Mother-reference, Aunt-reference,Other-reference) × 3 (Retrieval Factor:Rp+, Rp-, or Nrp items) design.Nationality and condition were manipulated as between-subject factors, and the retrieval factor was manipulated as a within-subject factor.The study had four phases.(1) Study phase:Participants were shown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monitor, with a series of 32 category exemplars in random order.They were instructed to memorize the exemplars while associating them with the paired category.(2) Retrieval-practice phase:Here, participants were sequentially presented with word-pair forms of eight cues that could probe their memory.Each cue comprised a category name and a first initial character of an exemplar.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call the target exemplar in the written form in response to each cue.(3) Distractor phase:Participants were requested to perform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within three minutes.(4) Final test phase: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produce a written recall of as many exemplars as possible in response to each presented category nam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in the Mosuo culture context, RIF was not observed under self-referential,mother-referential, and aunt-referential encoding, and was found only for other-referential encoding, and (2) for Han participants, RIF was observed in the aunt-referential and the other-referential encoding, but not in the self-referential and mother-referential encoding.
The present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first, in the Han and Mosuo cultures, self-reference and maternal reference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cause RIF.Second, in the Mosuo culture, aunt-reference is another key factor that influences RIF aside from self-reference and maternal reference.Aunts who are integrated in the self-concept of the Mosuo people are also important to such individuals.Finally, (3)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rucial factors of self-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mother-referential processing; aunt-referential processing; cross-cultural research
分类号 B842; B849:C91
收稿日期:2018-04-24
*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语言影响人格:来自双语者与双言者的行为与生理证据” (项目编号:17XNL002)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科研项目资助。
注:张积家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张积家, E-mail:Zhangjj1955@163.com
标签:姨母论文; 自我论文; 母亲论文; 汉族论文; 亲属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心理过程与心理状态论文; 《心理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语言影响人格:来自双语者与双言者的行为与生理证据”(项目编号:17XNL002)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科研项目资助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