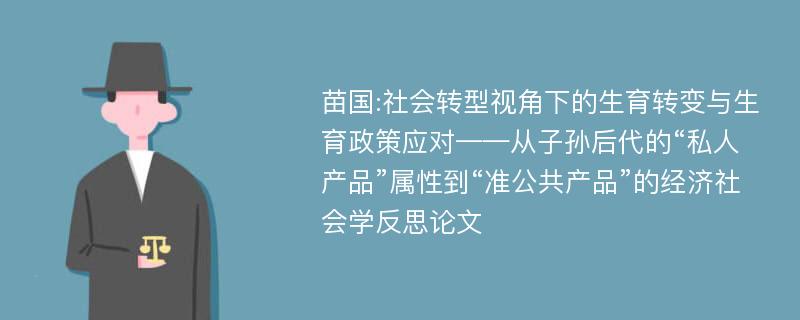
人口健康研究
摘要:人类社会普遍出现的低生育水平现象是“现代性”入侵,也是子孙后代从“准私人产品”走向“准公共产品”的必然结果。人类自然繁育激励机制遭到“现代性”破坏是出现低生育现象的根源。借助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个体化”与“脆弱性”概念,分析东亚“低欲望社会”与西方“单身主义”表征背后,现代化社会转型对人类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人为建构的“现代性”让“生育成本走高、收益走低”,“抑制-替代”作用上升、激励不足严重抑制自然状态下的生育行为。西方凯恩斯主义式的“生育政策刺激”,或者“福利型”溺爱不仅很难保证生育率恢复正常,反而人为降低了“自然生育意愿”,并干扰了社会成员的理性判断与未来预期。长期来看,维持人类社会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附近,主要依赖于人口再生产的“自发、自然市场机制”:生育文化重建、婚姻宽容、生育选择自由与育儿成本下降。中国生育政策如照搬西方模式,其基本思路存在路径偏差,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与政策预期也有较大距离,需要进一步调整与完善。
关键词:社会转型;生育转变;商品到公共产品;生育政策
1 前言
人类的“生育行为”不同于其他生命体的“生殖行为”,费孝通先生(1998)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提出三个论断“人类生育制度中包含生和育两个部分,供给新的社会分子是人类生育制度的任务,家庭是现代的产物”。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一直关注婚姻、家庭、社会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制度与文化变迁视角研究人类生育行为的嬗变,婚姻、家庭与性的“现代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线索(费孝通,1982,1983;沈奕斐,2013;陈映芳,2010;王跃生,2006;彭希哲,胡湛,2015;唐灿,2010;郭志刚,2010)。虽然传统的“乡土中国”在逐渐被“现代中国”所代替,但费孝通先生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生育制度”理论依然享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潘允康(2010)将其精华总结为:“以‘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为中心的婚姻家庭本质论、以‘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为模式的婚姻家庭结构论和以‘双系抚育’为中心的婚姻家庭功能论。”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扩散与城市化的加速,以及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科技的普及,社会学家发现,现代意义的社会变迁使得人类的婚姻制度与家庭关系再一次发生了巨变,性行为与生育行为的“分离”,家庭从“生产单元”逐渐转向“消费单元”,人口再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正在经历一场“现代性革命”。虽然附着于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并未消失,现代化转型带来的“外部性”冲击,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复杂组织架构,在制度层面让人类繁衍的危机从“马尔萨斯陷阱”逐步让位于“低生育率陷阱”。
迈向“现代化”,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一种时代趋势。在世界范围内,特别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先是发达国家,后是发展中国家渐次进入低生育水平行列。“当前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85个处于低生育水平,其中,24个处于很低生育水平,而这24个国家都分布在欧洲和东亚”(茅倬彦、申小菊、 张闻雷,2018)。在笔者看来,现代化进程中“极致理性”、“高度组织化”带来的工业科技、城市化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等系列“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保障了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运转,但在“繁衍”议题上极大地削弱了人类的“繁育力”。一般说来,越发达的国家地区,生育率越低迷,以现代化为最终追求的社会发展模式,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人口再生产“产出效率”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西方与东亚发达国家,严重的少子老龄化担忧成为各国政府的“心头大事”,如何应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低生育率陷阱”,从社会转型视角,提出新的认知框架与制度反思迫在眉睫。本文希望从经济社会学角度,沿着人类子女后代的“再生产”从生物本能,向理性“(家庭)私人产品生产”再到公共产品转变这一线索,从制度经济学的作用机理、实质表征再到当下应对之策的不足之处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反思。
2.3.1 一般护理 患者一般采用全麻或硬膜外麻醉,回病房后取去枕平卧位6 h;如腰麻则需去枕平卧12~24 h,头偏向一侧,保持呼吸道通畅,以免呕吐物、分泌物呛入气管,引起吸入性肺炎。6 h后取半卧位,利于腹腔引流,同时减轻腹部张力,促进切口愈合。协助患者每2 h床上翻身1次,大多数患者常因担心活动会牵拉伤口引起疼痛、渗血、切口裂开而不敢翻身活动,护士应耐心讲解早期活动的重要性,促使患者主动配合。
2 文献回顾:社会转型视角下的生育转变
2.1 现代化与人口转变
作为一个被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普遍关注的“跨学科领域”,关于人类族群繁衍的基础变量“生育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受到高度关注(Becker G.S.& Lewis H.G.1973;Becker,G.S.1976;Bongaarts,J.2001;Easterlin,Richard A,1975,1978;Freedman,Ronald,1979;Leibenstein,Harvey.1974;Baudin T.2010)。回顾涉及低生育率现象的各种理论范式,西方的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理论提出多种解释:弗里德曼(Freedman)在其所著的《生育下降的理论》一书中认为: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宏观发展的变化如工业化、文化等导致社会、经济、政治组织转变的结果。生育率下降并不限于社会结构某一或某些子系统的变化,很可能还与文化因素有很大的关系。”邦戈茨与沃特金斯(Bongaarts and Watkins,1996)认为人口研究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社会婚姻关系中的性需求增加,使婚姻解体更容易,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变小,而其他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则有所加强”。(42)从社会变迁视角,冯德卡认为,两次人口转变基于不同的家庭模式,第一次人口转变中的主导家庭模式是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bourgeois family model),而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被“个人主义家庭模式”(individualistic family model)所取代(吴帆、林川,2013)。但社会转型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并不容易采用定量模型给以“操作化”,因此,如何在理论上进行机理分析,并评估这一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边际贡献”变得具有挑战性。 以莱宾斯坦(H.Leibenstein)和贝克尔(Gary S.Becker)为代表的子女“成本效用”理论,指出现代社会经济因素依然是生育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子女“由质量向数量替代”是一种合乎经济理性的“必然选择”,因此,伊斯特林(Richard A.Easterlin)提出的整合模型(Synthesis model of fertility)为代表的生育供给需求理论,将子女视为一种“商品”进行经济计算分析,受到了许多非经济学研究的质疑。当然,在本文中,笔者的立论基础并不是前人所批评的研究者“滥用经济效用”(Hirschman,Charles,1994),而是谨慎地发现,子女后代在现代社会正在向“准公共产品”演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产品的“福利诅咒”已经在摧毁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的正向激励机制,人口政策方面的福利举措又在成为人口再生产的“巨大威胁”。虽然人们对低生育现象背后的社会学、经济学解释范式的“技术细节”有各种争论,但多数研究者都能达成基本共识:进入21世纪,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ism)所担忧的人口爆炸已成昨日黄花,能维持高生育率的国家几乎消失,越来越多的国家迈进“低生育率”行列,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旦引入“现代化”的各项理念与生产生活方式,人口再生产无论是在生物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会受到严重抑制。
2.2 制度主义框架视域下的社会转型与生育行为
人类繁衍与动物繁殖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两性生殖”在生物学意义上源自于生命的本能冲动(费孝通,1998)。自然模式下,生物种群规模主要受限于自然资源约束与同等生态位的物种竞争。但由于人类设置复杂的经济社会制度,人类繁衍的生物本能的达成不再隶属于自然模式。动物性以外,理解人类繁衍愈加“复杂”的社会性与个体化的冲突与人类组织“脆弱性”,需要一种制度主义视角。这其中,最重要的嬗变是:生命繁衍的“自发、自生秩序”被“组织”或者“人造秩序”所规制(齐格蒙特·鲍曼,2002;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Turner,Billie Lee,et al.,2003;Easterlin,Richard,Robert Pollak,and Michael L.Wachter,1980)。无论是“宗教、道德和法律、婚姻与家庭”,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人类繁育的“自然的、自由的”性交配选择都被大幅度缩减。例如,在婚姻与家庭变革“平等、自由、品质生活”等口号的背后,城市化背景下,现代都市男女的婚配变得愈加困难,男女双方的“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财富资源、社会地位感知”等都在“干扰”生物学意义的自由、自愿匹配。婚育之外,人类也更乐意把生育剩余(节约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比如消费主义、性解放),理性利益计算作为“激情的驯服者”,城市家庭普遍选择子女质量追求替代子女数量需求。同时,在家庭生育为主流价值观的模式下,制度文化无法容忍“非婚生育”,中国都市青年的成婚困难、婚姻脆弱性上升都会对国家与民族合理人口规模与合理结构造成严重冲击。
1.3.1 冠脉造影所示IRA前向血流情况。IRA前向血流定义:TIMI 3级或TIMI2级为有前向血流;TIMI 0级或TIMI 1级为无前向血流。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在过去30年经济社会或多或少都取得了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追求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发展、妇女就业率上升与地位提升等成为“普世”的社会主流发展趋势(陈友华,苗国,2016)。随着人类社会组织复杂度的提升,特别是教育体系的扩张,就业市场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子女“投资-回报”观念的“理性化”熏陶加强,子女后代“再生产”被社会化组织裹挟,其私人产品属性进一步走向“公共产品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本身“不可逆”,使得我们认识中国生育转变与生育政策应对,需要一种“未雨绸缪”的高瞻远瞩。
还有四人曾被册立为太子但在死后没有获得谥号,分别是唐高宗的长子李忠、唐玄宗的次子李瑛、唐敬宗第六子李成美、唐昭宗长子李裕,他们被废黜太子之位以及没有获得谥号的原因相当复杂。“没有获得谥号的四人尽管可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也说明他们生前的事迹没有值得赞赏或者怀念和悯惜之处,也可以说是对他们一生的否定。曾为太子而不能获得太子谥号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其后人则会因为谥号一事而深感遗憾,也就出现了李承乾死后将近百年之时他的孙子李适之向唐玄宗讨要封谥的之事,足见谥法制度在古代社会中的影响之大。”唐代太子死后能否获得谥号既与他们生前的品行有关,也存在在任皇帝对于他们的感情因素。
3 实质:社会转型与生育行为
3.1 现代化与少子化:“私人产品”的嬗变
3.3.1 东亚的“低欲望社会”
在生物学上,群居生活为最早期的人类社会成员创造了竞争优势,因为群居意味着分工、合作、安全与保护,更容易获得食物,以及“对群体有利”的繁衍后代的机会。但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以及现代国家福利提供的社会保障使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生活——单身生活成为了一种可能。单身在现代社会有许多表现形式:单身、单亲家庭、分居、稳定的性伴侣但不结婚、甚至不稳定的性伴侣,等等,家庭这一传统的社会细胞或者说基本组织单位,在西方日渐衰微。有数据显示:1950年,仅有22%的美国成年人是单身,同时,400万独居者(约50万独居年轻人)占到了美国住户的9%。2015年,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正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一人生活,独居人口占美国户籍总数的28%。1996年全球有1.53亿独居人口,2006年有2.02亿独居人口,短短十年间增长了33%。(49)[美]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6页。 目前,人类社会独居人口急剧增加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性趋势。这一现象给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尽管东方的传统“家思想”根深蒂固,在多数社会形态下,长辈、宗教组织、保守主义团体都在告诫年轻人:“不婚、不生”独自生活未来将导致孤独和与世隔绝的孤立。也许,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向我们揭示了“绝大多数单身者正热忱地投身社会与社交生活中,他们比同龄已婚人士更热衷于外出就餐、锻炼身体、参与艺术及音乐课程、公众活动、演讲以及公益活动。也许,这个时代,独自生活在逐渐成为主流,一种人们既被时代胁迫着接受又乐意为之的矛盾主流。”(50)[美]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7页。 过往人类社会从未拥有如此庞大的独居者人口,这也意味着人们无法从过往的历史中获得经验教训,中国未来的社会走向将取决于今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选择。
图8、图9分别为实验系统跑车过程中GPS信号失锁后BP神经网络辅助的东速和北速以及东速、北速漂移情况,在GPS信号失锁后的200 s中,东向、北向速度漂移分别最大达到0.88 m/s、0.57 m/s。
图1 从“自然平衡模式”到“理性有序模式”生育行为的经济平衡点
在自然平衡模式下,调控人口的是“马尔萨斯原理”——“除非受到抑制,人口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抑制人口的决定性因素是生活资料,人口总是被抑制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水平之下。”进入到现代“理性有序模式”后,首先是子女的“商品化”(准确来说是私人产品化),让人类再生产的意愿与选择经历了“质量替代数量”的理性抉择。进入后工业社会,养育子女成本因为其公共产品化而进一步飙升,现代制度的高成本“嵌入”育儿过程,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44)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一书中提到的那样:“处理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理性的力量,而它们没有。”养育子女追求回报是人类经济理性使然,社会制度与公共舆论把爱与付出视为美德,其背后的“潜台词”恰恰印证了人类“自私”之本性从未褪去,生育激情本能到生育理性,再到压倒不求回报的“爱行为”(只付出不计回报),前者才是家庭与人口再生产延续的主要动力,后两者则演化为“质量替代数量”的抑制作用,甚至成为丁克一族自愿放弃生育的理由。保持生育水平不低于更替水平是人类族群存续的必要条件,但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宏观危机视角很难被个体视角所感受。
3.2 后工业时代的“公共产品”:家庭变迁与生育行为
换言之,生育成本构成中的“物质问题”(传统社会养育子女最担心的是吃饭问题)在现代社会容易解决,但“心力问题”(人力服务也是一种重要的成本)却并未因为人类经济组织效能以及社会分工专业度提升而下降,子女养育资源投入演变为一项家庭社会资源的全面比拼。在这场“质量竞争”中,一方面是需求端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利维坦”的作用不可小觑。无论是高房价、高教育费用、高医疗费用,公共产品服务价格昂贵本质上是市场竞争不足的结果。这其中,竞争不足、权力垄断的形式非常多样,既有明面上有牌照控制、准入控制、教育年限严控、“教育减负”、“整顿课外辅导班”一刀切等等“武断”规制类型,也有很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合法”、“合规”需要(46)公立教育系统强制规定教育年限,这种“学制”的“刚性年限”大大推后了青年人口的就业、婚配,甚至部分错过了“财富创造与人口繁衍”的最佳生理期,学制刚性而非自由选择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净损失”是难以估算的,这种强制性教育制度,在许多方面都违背了“自然规律”,更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同样类似的,“就业社会保障制度”设置整齐划一的强制退休年龄,而不是“企业”与“雇员”自愿、自由协商一致达成契约,也会带来大量劳动力“提前退出”损失,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少子老龄化”境况下最终都会沦为“旁氏骗局”。。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以公共服务为“民生”的旗号,扩大政府对公共服务与福利输出的供给,干涉范围越广、越深,竞争度越低,百姓实际为之付出的成本越高。可以看到,生活、教育、住房、医疗等成本的急剧增加,使得孩子的家庭抚养成本急剧增加,而政府干预极难弥补,“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成本一旦产生就不会消失,只能转移”,任何“物质型”的、“保护不平等一方的”、“同情弱势群体”的鼓励性生育政策,其福利支出增加都需要他人付出更多的代价来“买单”,更何况,任何政府福利的发放都有着大量的腐败、机会成本与输送“损耗”。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义务教育免费、生育补贴的钱或许只是购买昂贵商品房的“微弱反哺”。再比如,政府对企业实施严格的孕产妇保障,会让女性在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求职过程中遭受严重的就业歧视。(47)从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消除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女性生育不只是实现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同时也是增加人口规模,帮助社会进行族群繁衍,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需要对女性生育进行政府补偿以实现社会最优生育水平,让企业和家庭来补偿时,最终补偿成本仍然会转嫁到女性个人身上,造成就业歧视(甘犁,2018)。除非彻底洗心革面,彻底回归“自由市场模式”让更多市场竞争主体介入,否则,“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的政府干预,只会加重“新三座大山”的负担。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1990)所言:“激励是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因素”,无论是财富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消费总比生产容易,“放纵自在”的消耗生命与“负责任”的养育生命,难度系数的差别“一目了然”。假如在人口再生产方面缺乏激励机制,由于社会转型和变迁,子女从出生、到教育、到就业、再到社会保障,“育儿”所需注入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与越来越复杂。(45)子女假如是简单商品,具有长期、中期、短期的内在价值(无论是数量和质量维度,投入资源未来有回报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商品,个体理性总是乐意为“有回报”的事情买单,这种激励是良性循环激励),当子女演进为了公共品(个体投入的资源更多的是为他人做嫁衣,那么激励就变为恶性循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社会,对子女质量追求在集体意识削弱,个体化不断凸显的时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只是“不计回报”的“爱”需求很难维持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性。人们觉得子女预期收益下降、成本不断攀升,生育激励机制之所以出现根本性逆转,反映的是家庭分工逐渐被社会分工所代替的社会转型后果——传统社会中育儿成本多由夫妻双方承担,在现代社会则部分由国家与社会承担,还有部分需要通过社会、市场进行购买”(陈友华,苗国,2016)。假如这些分工都由市场承担,并由自由竞争带来的高效率,成本应该比个体独自承担要低。比如,年轻人普遍认为“外卖就比自己做饭要省时省力”。但诸多分离出来的社会分工并非由市场机制提供,特别是跟育儿相关的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膨胀”,最终买单的都是纳税人。也就是说,“免费的义务教育其实并不免费,只是其教育费用承担发生了转嫁而已”,西方社会的谚语“freedom is never free”(“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更是发人深省。“育儿行为”的成本嵌入到社会化机制之中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化”,或者说育儿资源需求的外部性转移,让生育子女行为从“商品”走向“准公共产品”,如果匮乏自由竞争,“不负责任”地抬高成本才是“资本或者资源(权力)掌握者”一种经济理性行为。
观察PICC置管期间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情况,记录导管留置时间,患者出院前,利用本院自制问卷调查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程度,内容包含服务态度、护理操作、并发症预防、护理方式4项,每项内容包含25个条目,每条目1~4分评价,每项总分100分,总分≥80分判定为满意,分数越高表示满意程度越高[2]。
3.3 东亚与西方的“低生育行为”背后的社会转型经验
把人类历史拉长,人口族群繁衍的演化历史主要分成两个时期: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之后。早期的子女数量追求或许是一种低生产力水平下的“经济理性”,进入现代社会,子女“质量论”抬头也是一种高生产力水平下的“经济理性”进化。(43)纵观人类历史,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三百年间人类文明的胜利源自一件“开天辟地”式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除非受到抑制,人口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抑制人口的决定性因素是生活资料,人口总是被抑制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水平之下。”在工业文明产生之后,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传统社会的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马尔萨斯陷阱”就此产生。但是从人类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的成因来看,性行为与生育之间的联系多数情况下处在各种制度“规训”不断加强的状态。
日本由传统走向现代化是东亚社会的奇迹,“彬彬有礼”、讲究秩序是日本文化长期塑造的结果,也使得日本成为文明社会的代表之一。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东亚的“低欲望社会”以日本最为典型。具体表现为:日本年轻人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不婚比例不断上升。这背后反映的是日本青年一代对于生育、消费和投资的欲望与父辈一代无法“同日而语”。为何这一代年轻人对性生活和婚育越来越不热衷?同时,为何这股思潮还颇具“传染性”?在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大城市与港澳台地区,类似“单身族”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这不仅是因为线下两性“实体接触”昂贵又“麻烦”,年轻人面对丰富的、触手可及的互联网欲望影像,会有显著的“替代挤出效应”,“低成本”与“麻烦少”都促使年轻一代通过网络从线上轻松获取大量的“性释放”资源,这是一种传统“面对面”社会交往能力的退化,不仅印证了吉登斯的“非在场理论”(absent theory),更是严肃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48)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从“单个的个体”到“整体性的制度”,“价格”(成本)机制扮演了重要角色。两性通过婚姻获取性释放的渠道成本较高,与现代社会充斥大量低成本性释放渠道相比,由于价格(成本)机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制”,其结果是,只要给个体自由,那么个体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新制度,两性交媾的价格“双轨制”让传统婚姻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不婚不育现象的蔓延也是制度冲击的必然后果。
事实证明,四川省医门诊患者服务中心通过整合医院现有资源,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真正实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一站式、一体化服务,提升了医院的形象品牌,增强了医院软实力和竞争力,赢得了患者和医疗同行的广泛认同。
性是人类的本能,在传统社会,“性”的替代物几乎没有,并缺少避孕节育手段,因而性与生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传统社会生育孩子多,并不完全是人们的意愿,其中有部分属于“非自愿”生育,生育崇拜不仅是低生产力状态下的需要,也是一种“激情本能”“自然释放”的结果。进入工业化时代,子女作为家庭依靠的时代不断远去,由于人类创造财富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而削弱了对子女的数量要求,按照贝克尔(Gary S.Becker)的理论,子女可以视为一种需要理性分析的“商品”,生育子女追求的是一定的合理回报。虽然这种纯粹的经济理性分析遭致了许多批评,但人类的子孙后代其实一直都是一种“特殊”商品(交易受限、功能复杂的特殊产品),其效用一是基因延续的本能作用,另一则是个体未来生活保障的来源。生育激励机制的衰退,大体经历了两大“下降”过程,如下图1所示。
3.3.3 “低欲望社会”与“单身社会”的社会后果
家庭与人口的再生产模式取决于自发市场秩序的后果,生产力发达,个体才能从家庭义务中摆脱出来,家庭不再是生产中心,而变为一个消费中心,人口再生产在财富暴增“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个体化家庭”模式演进,社会团结不再由神圣的集体意识(宗教与宗族观念)来承担,而是异质性个体之间的市场机制链接和个体文化的认同凝聚。只是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理在持续作用,任何非“自发市场秩序”之下的“制度规训”与“美好追求”都隐含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与制度摩擦。在传统社会,婚姻制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因为它符合两性抚育下一代的需要,换言之,具有经济比较优势。随着现代性社会的来临,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讲,原本两性结合的交易成本从简单生物学意义的“基因匹配”到“物质财力、文化、阶层甚至信仰、情感层面”的“登对”,诸多组织制度、道德规范与文化禁忌因素给婚姻本身带来了许多“交易摩擦”。这种摩擦大幅度抬高了婚育的机会成本与门槛。在一些国家,为了保卫两性“合法婚姻”甚至设置了“极高的准入与撤离”门槛。例如,爱尔兰等天主教国家必须从一而终,禁止夫妻离婚,但人们的理性选择不是维持传统的“终生不渝”的婚姻美德,而是让结婚率不断创下新低,高昂的制度成本甚至革新了婚姻与家庭样貌——这在西方、东方发达国家,出现单身社会或低欲望社会就变得容易理解起来。
3.3.2 西方的“单身社会”
在近代卫生和医学技术革命之前,人均寿命始终低于40岁,妇女在性成熟之后,绝经或死亡之前,平均有20年多的生育期,每个孩子9个月的孕期加2、3年的哺乳期,扣除两次生育之间的随机间隔和流产,生育率大约在4到7之间,而孩子在性成熟之前的死亡率高于50%,照此推算,即使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总和有效生育率(即存活至生育年龄的孩子数)也并不比替代水平高出多少。因此,在与微生物、病菌和病毒的对抗中,人类的境况十分脆弱,特别是对于脆弱的儿童,稍有闪失或不测,人口与基因延续便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抑制。人类在医疗科技欠发达的时代,拥有更多的子女来规避这种风险是一种经济理性,并建构所谓的生殖崇拜与“多子多福”等文化,显然,在现代社会,保持家庭子代存活概率更高成为可能,生育率下降情形下,人类再生产模式才能转向“低生育率、高质量追求”模式。
4 表征:社会转型与生育文化
4.1 个体化与脆弱性
20世纪60年代,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的婚姻、生育和家庭行为模式出现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同居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形式甚至有代替婚姻的趋势,生育与婚姻逐渐分离,非婚生育比例越来越高,被人口学家认为是“第二次人口转变”(吴帆、林川,2013)。在中国,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带来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观念和个人价值观的深刻变革。现代社会变迁与传统结构相遇,使传统的社会性约束力下降,个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个体化”是指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等范畴的逐渐弱化,个体日益从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中脱离,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这些都滋养了“独立文化”的产生,特别是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就业几率的大幅提高,社会流动能力的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国家中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个体能够有更多自我实现与自我追求,从“为他人而活”慢慢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开始追求“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个体追求自我以及这种纯粹的亲密关系之时,性、婚姻与生育之间的传统生命历程轨迹便发生了重新排序或断裂。性的发生不再必然以婚姻与生育为前条件,人们的婚姻家庭和生育行为模式也相应产生了“个体化”的变化趋势。
与此同时,人类依赖社会资源抚养下一代在面临“脆弱性”的挑战。大量的生物学研究显示:“相比独立繁殖的生物,合作繁殖的物种更能适应极端环境,团结才能活下去。”(52)Cornwallis,C.K.,et al.,Cooperation facilitates thecolonization of harsh environments.Natureecology&evolution,2017,1(3):p.057.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对于客观物理环境困难的克服,一方面利用独特的智能打造了精密、复杂的知识与资源组织体系,诸如现代农业科技、工业、能源及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让人类不再惧怕极端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人类的繁育还高度依赖“组织化程度”极高的经济社会组织,比如家庭、职业分工、医疗与学校等社会制度。但这些“便利”科技、复杂社会组织与高生产力水平,宠溺出人类严重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特质与“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幻觉:我们的社会制度搭建了五花八门的“安全壳”,一旦这些“套中人”从“安全壳”中脱离,迁徙、觅食、捕猎、保暖、繁殖、对抗外敌能力的全面退化,个体生存都面临严重的危机。或许,人类生育本能的退化,也成为人类脆弱性的又一明证(53)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度依赖辅助生殖医学。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每年辅助生殖治疗超280万例,以每人治疗费4万元人民币计算,这个市场规模大约为1120亿人民币。辅助生殖如此庞大的规模与中国人生育能力下降有关。据相关医学专家称,中国男性的精子计数(即每毫升精液中的精子数目)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1亿个,大幅下降到了2012年的2000万个。相关报道指出,精子计数较低、妊娠年龄推迟和其他健康障碍之类因素正在让许多妇女更加难以受孕。。
4.2 科技与宗教
“单身社会”、“低欲望时代”是一个异常严肃的社会危机。表面上看,生产力发展带来了个体的经济独立,并塑造了一个全面“个体化”的时代,社会成员似乎可以不太直接依赖组织(家庭、企业、社会)而生存下去。但事实上,保证人类生存的物质与能源、信息资源的交换系统非常复杂,人类社群的组织形态应变得更紧密、更依赖与他人协作,个体化生存本是难以行得通的,却在表面上变得“合情合理”,人际关系与家庭组织方式的“原子化”也似乎成为一种趋势。以至于在大都市,恋爱与婚姻成本极高,即便成家想多要个孩子的愿望也越来越难实现。客观来看:一方面,是生物繁殖力的下降,这也许与人类在城市条件下的高密度居住带来的环境改变(污染与情绪压抑)有关,以及女性生育年龄的大幅度推迟导致生物角度“繁殖力”的大量损失(51)“Sperm Counts Continue to Fall”,https://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8/10/sperm-counts-continue-to-fall/572794/ ;另一方面,大量社会构建的“安全壳”机制毁坏了人口再生产的激励机制,“一个人可以活得不错,能自由自在干嘛追求责任束缚,至于养育下一代,自己还没活明白,就不要拖累别人了,若被问到年纪大了怎么办,‘还没想好’、‘想太多太远那么累干嘛’自然是一种超脱,不是还有退休工资(社会保障体系)吗?”。
但是,人类的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达,也有相应的“外部性”,特别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生态环境负面因素,使得生育年龄推迟与生育力下降。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不仅人们的结婚年龄逐渐推迟,其生育年龄也大大延后,不仅降低了生育的可能性,甚至错过了生育的最佳时机,而且还大大缩短了生育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生活与工作压力增大等,使得人们的生殖力下降,不孕率持续攀升(陈友华,苗国,2016)。此外,受生育年龄推后与生育时生理机能下降、营养改善导致胎儿普遍增大、孕妇承受痛苦能力下降、信任缺失与医患关系紧张而导致医患双方风险过度规避等众多因素影响,选择人工辅助生殖、剖腹生子的妇女在中国越来越多。而借助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剖腹产增多与其再生育力下降也是整体社会环境背景下“人类自然繁育力”下降的无奈产物。
此外,互联网技术带来了人类交流模式的嬗变以及两性关系的“微妙”转型,过去宗教是控制人口再生产的重要变量,西方教会都有“鼓励生育”的倾向,但在现代社会,传统宗教的影响力式微,科技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新宗教”,这让看似紧密联系的人类其实是异常孤独的群体。尤其是在大都市,现代城市生活大幅度扩大了个人的择偶空间,但它的流动性与关系松散性却压缩深入了解机遇,甚至“对未知的恐惧”与“过分的物质心理准备期”大大延长了择偶过程,在漫长的单身期,为了满足情感与生理需求,人们的经济理性更想建立短期和尝试性的联系,而非长期稳固的契约,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性和婚姻家庭的观念与文化变迁。青年一代的成长伴随着手机和智能电子玩具。如今的我们既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才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作为经济成本最低的交往方式,更容易获得比较优势。生儿育女需要的是两性的亲密关系,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两性却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对立。
2)培训机构缺乏全程指导支持服务。混合式远程学习强调的是线上线下的交流合作,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研修活动中的指导以及相关评价工作,都需要通过培训机构的网络平台来解决。
4.3 社会转型与低生育率形成的综合解释框架
常识告诉我们,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只有在得到现代最核心的社会制度——家庭、经济以及国家的支持下,才能成就所谓个体“独立”与“解放”。目前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个体化社会”、“消费主义”以及“低欲望单身社会”和“群体性”孤独,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体现,更是一种经济理性塑造的社会行为,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机制同样如此。它是人类创造的“极致理性”现代性——市场力量、社会转型与国家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社会转型与低生育率形成的综合解释框架
依图2所示,社会转型带来的现代性“入侵”,主要在生产与生活方式两个主要方面作用于人口再生产,首先是家庭生活方式的承载体婚育制度,现代社会普遍出现了“性-婚育-生育”三者分离的现代性表征,这种嬗变的出现源自于现代生产方式——工业革命以及信息科技带来的“个体化”幻觉与宠溺的“脆弱性”,除了现代性的入侵,还有一股力量,就是国家干预,人类搭建的“制度”——教育、医疗、法律与社会保障等制度,在不断完善中挤压着“自然秩序”的发挥,以上三股力量似乎都再助长“性-婚姻-生育”三者的分离,由此呈现了三大趋势:
一是子女由商品向公共产品转变。与其他公共产品的价格走势一样,这种转变意味着子女养育成本的飙升,如本文的图1所示,当人类感觉生育子女如此不划算时,后代的日渐“稀少”是大势所趋。
二是生育激励机制的消散。人类由激情驱动的性行为是生育的原动力,而人类发现这种无序激情需要被“有序理性”所驯服,人类制度文化越发达,对本性的约束越强烈,现代性逐步“规训”人的本能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三是激情快乐本能“转移”。人类智能与科技搭建的“安全屋”,不仅宠溺人类社会的脆弱性,更提供了大量本能释放的“替代渠道”,世界各国的低欲望与单身社会的来临就是明证,现如今婚姻与性已经在西方国家彻底分离,婚姻与生育的解体也已经基本完成,而生育与性的联系,也许伴随着人类科技的“想象力”,这点“微弱联系”也可能会最终消亡(克隆技术即为一种可能)。
5对策与反思
5.1 结论
人为建构的“现代性”让“生育成本走高、收益走低”,“抑制-替代”作用上升、多育子女激励不足严重抑制自然状态下的生育行为。正如福柯所说,性是规训和生命政治的结合处。当我们担忧年轻人性生活越来越少时,其实就将其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毕竟生育担负着调节国家人口数量与结构的重任。生育率长期低位徘徊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本文同时依托子女后代属性转变与家庭功能转型这两个重要维度,通过透视少子老龄化的内生机制,对“鼓励生育政策”的经济、社会后果展开社会学反思,尽管某些国家采取了系列鼓励生育政策,使其从极低生育水平有所回升,但这种刺激效应本质上属于福利主义式的“无奈挣扎”:“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成本不会消失,只能转移”,“物质鼓励性”的生育政策支出增加都需要他人“买单”,单纯利用“物质诱惑”或“女性保护型”的公共政策刺激生育行为很难逃脱“低生育率陷阱”。
人类美好社会的建立不是仅仅依赖于口号和美好愿望的“无源之水”,而是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艰难道路,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堕落是人性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西方的基督教伦理中,视贪求金钱、权力和性为人类堕落的三大罪恶,一并予以谴责,但这三大罪恶却从经济规律角度,刺激了物质生产、组织搭建与人口再生产。人类用文明制度在规制“罪恶”,但任何的自由、平等、体面的“解放诉求”以及人类对“精致品质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暗含”系列成本,作为地球上生物链顶端的智能生物,人为制度(manufactured institution)的搭建从帮助人类繁衍跨越“马尔萨斯陷阱”,转而因制度成本高昂束缚了自然繁育力。只是某些时候,这些诉求成本“隐藏的很深”,使得公众很难察觉“隐形成本”对人类繁衍的“负面作用”。(54)其实,从家庭经济角度,传统意义的婚姻与家庭保障了人类繁衍,但到了现代社会,组成家庭的制度成本太高,人们就不再选择婚姻,如西方的单身社会与东亚的低欲望社会。
随着信息与交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资本、劳工、信息、资源、商品等要素的跨国、跨境、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全球化与网络化让传统社会的边界被打破,按照吉登斯的“在场与非在场”理论,过去需要“面对面”才能实现的社会互动行为,在全球网络化时代,人类的各项行为见面与否变得并不再那么重要(包括人类性需求的“释放”行为),这种现代性冲击最重要的影响是“人类行为与观念”的模仿可转瞬达成,这意味着人类生育行为的变化会是异常动态性并附有传染性的(Baudin T.2010)。即便是在中国偏远的农村地区,东方传统的家庭与婚姻模式都在“向现代化模式”不断“进化”,甚至走向“更彻底”的式微甚至解体,这与西方“单身社会”以及东亚“低欲望社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整体来看,个体化社会中,社会成员追求的“独立、自我”开始代替集体主义时代整齐划一的“强制、义务”的家庭伦理(阎云翔,2006)。这让人们感受到“传统价值伦理”束缚解绑后,经济因素“无形枷锁”及信息爆炸带来的“欲望羁绊”张力所带来的无力与失控感,是“公民-国家-社会”、“想象共同体”中普遍存在的“现代病”,因此,生育转变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对话以及勾连展开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有了独特的学术反思价值。
5.2 对策
家庭人口再生产本应是一个市场(自然秩序)调节的过程。养育子女需要动用许多个人与家庭资源,无论东方与西方、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任何期盼公权力介入“资源分配”,来改善人类境遇的愿望都可能是“南辕北辙”。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子女的属性发生了嬗变,孩子由传统社会的私人产品在现代社会逐步具有了公共产品的某些属性,这会产生一种公共领域典型的搭便车效应。而这种搭便车效应会形成某种路径依赖,即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发展起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低生育”背后的利益集团不仅仅是走向终结的“计生委”,40多年来,与计生政策紧密捆绑的利益主体在不断扩张。(55)发达国家都在为如何提高生育水平而绞尽脑汁,而中国却“长期忽视”少子老龄化可能蕴藏的巨大风险。这种忽视背后看似是一种“利益团体”与“利益机制”在作祟。中国这个“全能型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而生育政策是一项代价昂贵的公共政策。从政府支出角度,与之相关的教育与社会保障支出,是多数国家的财政噩梦。“福利刚性”与“财富支出的期限错配”导致青年群体看到今天的老年人依靠社会保障过得还不错,甚至很滋润,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晚年也能活得不错,甚至比现在的老年人活得更好。而这一点在政府的不断承诺与许愿下甚至被不断强化与放大,西方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中国不应向这些“只顾短期、不顾长远”的社会政策学习。尽管这一部门在强烈的反对声中“被改革”,但影响生育行为更大的利益集团——社会保障与公共卫生却变得“更强大、更有话语权”,政府职能转变不是简单的“小政府、大社会”口号,而是改变底层的利益规则,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56)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3页。源自西方的福利国家思想,不仅在摧毁西方的经济繁荣,还正在通过少子化在消亡人类社会本身,这其实是一种“国家特殊利益集团”干预人类社会自然运行的“利维坦”,而我们多数人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具有较大偏差。生育政策调整,在现代社会,“理性有序”模式已经不可能回到原始的“自然平衡模式”状态,其转变必须寻求彻底的改革:“逐渐放开生育政策管控”,归还生育选择自由(愿意多生养小孩的家庭,满足任意数量诉求,填补低生育欲望群体带来的“生育损失”),文化与制度层面转向婚姻宽容(即便是非意愿结婚生育,也应对“非婚生育”宽容),通过鼓励市场主体自由竞争,让市场化组织降低育儿成本,并进行生育文化重建。
5.3 反思
马克思所断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仍具有强大的普世性,关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话语体系竞争背后主要取决于国家或区域经济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回过头来看,人类社会迈入现代化的最大代价可能就是少子化危机,现代化入侵构成的社会转型对人类繁育后代设置了太多制度成本与交易摩擦,这种现代性的入侵是不可逆的,暂时还未找到治愈良方,人类组织的干预和对策越多,意味着额外需要支付的成本越大,多数人渴望的政策福利应对之策不过是自己的毒药与他人的负担,只不过这种成本支出可以通过“障眼法”和“话语术”被巧妙地转移给他人,或者被暂时隐蔽,人类文明走向的悖论在于我们介入或者不介入似乎都是一个死局,现代化的过程本身是一种文明的“自杀”,既然我们无法退化为原始社会,那么这种社会转型的代价人类必须要自己承担。这里我们只能呼喊:在生育政策方面进行彻底的“供给侧”改革,逐步放开生育数量管控,在教育与社会保障方面减少承诺,让国民为自己负责,为未来负责,这才是治本之道。虽然,这一学术断言非常“政治不正确”,也会遭致剧烈的社会批评,但经济学规律不会因为舆论批评而走形。
(1)全风化层在红粘土剖面中占的比例比较大,远大于其他结构层,并且其中夹杂铁壳和铁质结合带,而半风化层在剖面中所占的比例较小。
我们在持有悲观预期的时候,还要借助于理性来思考,为未来找到一丝光明。用“他者”心态审视自己国家的社会转型之路,所谓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多暗含一种西方优越论,以及弱者必须汲取这些强国发达的“优势”,比如工业科技文明与城市化发展路径,这当然是一种善于自我反省与学习的表现,但另一种善于学习是“去其糟粕,取之精华”。我们不能否认,特殊利益集团的过度繁殖会腐败我们的社会根基,腐败的文化会摧毁我们的共同体连接,个体化、消费主义入侵以及家庭的解体就是西方文化中极具腐败因子的堕落之源,而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与家庭共同体组织原则有着“许多优良基因”需要得到传承,“多子多福”、“家庭责任”在现代意义上,有着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优越之处”,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根除各种利益集团,毕竟国家的繁荣一定会带来“既得利益群体”。但我们要反思的是“凡是西方的都是先进的”是一种糟糕的“弱者心态”,我们要尽力摒除糟粕,保留我们自身文明的“优秀传承”,真正走向“四个自信”。
(3) 若{Oi:i∈I}⊆O(X),{csOi:i∈I}⊆τ,下证∪i∈IcsOi∈τ。由∪i∈IOi∈O(X),又只需证cs(∪i∈IOi)=∪i∈IcsOi即可。
参考文献: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沈奕斐.个体家庭iFamily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美]美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美]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奥地利]弗里德利·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日]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Baudin T.(2010)“A Role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Fertility Transitions.”[J].MacroeconomicDynamics,14(4):454-481.
Becker G.S.& Lewis H.G.(1973)“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81(2)Part 2 New Economic Approach to Fertility,p 279-288.
Becker G.S.& Tomes N.(1976)“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84(4)Part 2,Essays in Labor Economics in Honor of H.G.Lewis,p 143-162
Becker,G.S.(1976)“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ngaarts,J.(1978)“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J]. 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no.1:105-132.
Bongaarts,J.(2001)“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A].in R.A.Bulatao and J.B.Casterline(eds.),Gobal Fertilily Transition[M].New York:Population Council,pp.260-281
Bongaarts,John,and Susan Cotts Watkins.(1996)“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ontemporary fertility transitions.”[J].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639-682.
Duncan MacRae,J.(1978)“The Sociological Economics of Gary S.Becker”[J].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83(5).
Easterlin,Richard A.(1975)“An economic framework for fertility analysis.”[J].Studiesinfamilyplanning.54-63.
Easterlin,Richard A.(1978)“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fertility:A synthesis”[A].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C].
Freedman,Ronald.(1979)“Theories of fertility decline:A reappraisal.”[J].SocialForces58.(1):1-17.
Hirschman,Charles.(1994)“Why fertility changes”[J].Annualreviewofsociology:203-233.
Leibenstein,Harvey.(1974)“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Promising path or blind alley?”[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12.2:457-479.
Easterlin,Richard,Robert Pollak,and Michael L.Wachter.“Toward a more general economic model of fertility determination:Endogenous preferences and natural fertility”[A].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81-150.
Turner,Billie Lee,et al.“Illustrating the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for vulnerability analysis:three case studies”[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C].14(2003):8080-8085.
陈友华,苗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低生育率:新机制与新特点[J].人口与发展,2016,22(5):15-23.
陈映芳.国家与家庭、个人——城市中国的家庭制度(1940—1979)[J].交大法学,2010,(1):145-168.
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天津社会科学,1982,(3):2-6.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7-16.
甘犁,2018,中国如何逃离“低生育率陷阱”[J/OL].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8/0503/4446791.shtml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08,32(4):1-12.
茅倬彦,申小菊,张闻雷.人口惯性和生育政策选择:国际比较及启示[J].南方人口,2018,33(2):15-28.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0,(3):152-156.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5,(12):113-132.
潘允康.试论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J].天津社会科学,2010,(2):52-57.
吴帆,林川.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52-61. ▲
FertilityTransformationandFertilityPolicyResponse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Transformation:EconomicandSociologicalReflectionsfromthe“PrivateProduct”to“Quasi-publicProducts”Attribution
MIAO Guo,CHENG You-hua
(Schoolof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46,China)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low fertility which is common in modern society is the invasion result of“modernity”and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the descendants of children moving from“private commodities”to“quasi-public products”.With the concept of“individualization”and“vulnerability”in the context of“social transform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East Asia’s“low desire society”and Western“singleism”,and explores the law of population system:suppressing the increase of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insufficient incentive mechanism to seriously inhibit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the natural state.The“modernity”of human nature breeding incentives is the root mechanismof the low fertility phenomenon.Keynesian“policy stimulation”or“welfareintervene”is not only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at the“fertility rate”returns to normal,but“man-made”policyreduces the“natural fertility willingness”and interferes with the“rational judgment”and“future expectations”of members of society.In the long run,maintaining the fertility level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vicinity of“replacement level”mainly depends on the“spontaneous and natural market mechanism”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more freedom of birth selection,marriage tolerance,market-oriented organization,lowering childcare costs and birth culture reconstruction.If China’s current fertility policy is copied from the Western model,its basic thinking has a path bias,stray from policy expectations and needs further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Keywords:Social Transformation;Fertility Transformation;Commodity to Public Goods;Birth Policy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1-27;修订日期:2019-04-2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口转变视角下教育结构失衡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研究”(课题编号:14CRK017)、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重点学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7ZDA12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超大间隔生育的形成与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GD18CSH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苗国(1984—),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友华(1962—),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编号:1674-1668(2019)04-0117-12
标签:社会论文; 人类论文; 家庭论文; 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口转变视角下教育结构失衡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研究”(课题编号:14CRK017)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重点学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7ZDA12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超大间隔生育的形成与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GD18CSH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