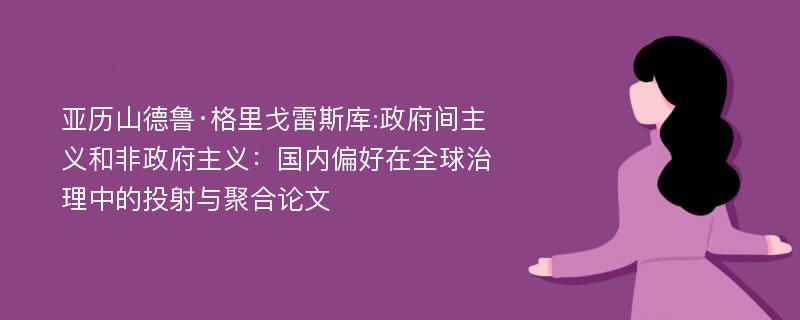
内容提要 | 近几年,随着特朗普决定美国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关于政府间主义和非政府主义的选择成为国际治理中的热点话题。为分析这一现象,作者提出假说:一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即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采取的政策是该国将国内偏好投射至对外政策的结果;同时,全球治理的整体架构取决于强国偏好的互相妥协与聚合。通过研究教育领域的全球治理案例,作者验证了上述假说。由此可见,美国对外不断退出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复兴的现状。最后,作者为全球治理领域中政府间主义和非政府主义的趋势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 键 词 | 国内偏好 全球治理 政府间主义 非政府主义 非政府组织
全球治理中的政府间主义
1919 年4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国代表在法国戛纳会面,商讨成立红十字联合会[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 以 下 简 称LRCS)]——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而不是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以便在和平时期应对国际卫生问题。几个月后,一场斑疹伤寒横扫欧洲,新成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下简称国联)]并没有选择在机构内部建立政府间的卫生组织,也没有寻求1907 年就已经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公共卫生局(International Off ice of Public Health)的帮助。国际联盟反而要求LRCS 牵头,对抗这场流行病。但是在1923 年,各国政府组建了联盟卫生组织[League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LHO)],这一组织取代了LRCS 在对抗传染病领域的牵头地位,或在更广义的层面上说,取代了LRCS 在卫生领域“全球管理者”(global governor)的地位。在20 世纪30 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国际联盟成员国显著降低对LHO 的资金和人员投入,LHO 活动开始减少。事实上,如果不是非政府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了其一半左右的工作,LHO 可能已经关门大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角色逐渐清晰,负责“协调整合”(orchestrate)国际资源。但观察家指出:在过去十年,WHO 越来越“无关紧要”;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基金会支持WHO 等政府间组织,也支持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公私合作倡议(private-public initiatives),如全球卫生研究论坛[Global Forum for Health Research(以下简称GFHR)]。目前,全球近一半的卫生资金的来源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
其他问题领域存在相似的历时性变化,即全球治理在政府间主义与非政府主义之间左右摇摆。为何政府选择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解决全球问题,而不是允许或鼓励非政府行为体(如国际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和私有企业)牵头?此等决定实则是政府间主义最有意义的表现形式。我们也通过考量政府参加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定,研究了我们的论点能否被应用至政府间主义的其他表现形式。
我们将政府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定看作是有明确目的的选择。长期以来,现有文献把重点放在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的选择,而如何选择主要取决于各国开展政府间合作的能力。我们为现有文献引入了第二种选择:政府在全球治理中选择推行政府间主义还是非政府主义。不论某国政府是否有意参与某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我们在研究各国创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作能力之前,应该先搞清楚上述“第二种选择”。
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指各国政府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共同问题。非政府主义(Nongovernmentalism)的含义更加广泛,是指在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不是主要全球管理者的情况下,所有其他可能用于解决此类问题的选项。所以相较于政府间主义,非政府主义有更多可能的表现形式。
首先,由于全球治理行为体类型不同,非政府主义的形式也不同。诚然,在全球卫生领域,类似LRCS 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或类似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的私有基金会,又或是类似GFHR 的公私合作都曾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认为,尽管上述三类行为体之间存在差别,但对于所有政府行为体来说,此类非政府实体看起来都十分相似。当激进型政府决定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作为时,它们可能会排挤一种或多种非政府行为体,政府间主义兴起;当政府不作为或鼓励他人作为,不论何种非政府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政府间主义都将衰微。
其次,政府行为体在解决共同问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决定了非政府主义的形式。在某些案例中,政府直接不作为,让非政府行为体填补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空白,并且此类政府也不关心非政府解决方案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在另一些案例中,政府完全掌控问题领域,不允许非政府行为体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但是大多数案例都处于纯粹政府消极主义(passivism)和纯粹政府激进主义(activism)两极之间的某一点。比如,政府行为体可以积极寻找政府间与非政府混合的解决方案,比如由政府间国际组织协调整合非政府行为体,或发起公私合作。政府也可直接鼓励采用某种特定非政府解决方案。
我们必须指出,全球治理的非政府性质不仅要看政府是否允许或鼓励非政府行为体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还要看此类行为体是否接受上述角色。非政府行为体的选择非常重要,但我们认为如果想完整解释其复杂性,必须进行另一项独立、全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只研究政府的选择:是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解决全球问题还是将全球治理工作交给非政府行为体。我们认为,当政府更倾向于亲自动手解决全球问题时,政府间主义则兴;当政府更加倾向于不干涉,全球治理可能会变得更加“非政府”。
我们的成果不仅丰富了有关政府间合作问题和多边主义问题的研究,也补充了有关非政府行为体(不管是独立运作的还是接受“协调整合”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的研究。有些研究的关注点与我们相似,着重强调政府间倡议和非政府倡议之间的不同(比如,相较于更加灵活的非政府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门槛更高),或从政治自由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角度分析国家之间的不同。
在承认上述论点的同时,我们认为,政府做出成立或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国向全球治理投射国内偏好(domestic preference)的结果。我们特别强调,在处理国内问题时采取较为激进方式的政府很可能在全球治理中推崇“亲自动手”(即政府间)的方法;而在国内采取较为消极方式的政府很可能接受或推崇非政府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已有学者使用相似观点解释了美国新政时期的激进主义和二战后全球纷纷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研究将此种推理方法推广至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的政府偏好。我们的历史研究法在广义上完善了近期的研究:从更加广阔的视角观察过去十年明显的线性趋势,提出存在周期性动态(cyclical dynamics)的观点。
在我们研究的大多数时间段,美国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研究美国案例时,我们首先列举了可以证明美国国内政府激进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存在关系的一些表面证据,之后我们阐述了上述关系背后的机制。基于现有文献,我们发现可能存在两种机制:一种基于意识形态(ideology),一种基于机构(institution)。之后,我们讨论了倾向政府间全球治理或远离政府间全球治理给政府带来的不同利益聚合。以下章节用于验证我们的论点。首先,我们研究了教育领域中的全球治理案例。在该案例研究中,我们使用统计方法分析了过去一个半世纪间各国创建和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据。分析结果支持我们的主要论点。最后,我们讨论了本文论点的重要性。
向全球治理中投射国内激进主义:美国政策中的初步证据
所有国内政治系统都要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确定在解决共同问题时政府的参与度。当然,政府并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唯一选项。本文认为政府部门(government sector)是三种国内部门中的一种,其他两种是商业部门(business sector)和志愿非营利部门(voluntary nonprof it sector)。基于上述理解,当政府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时,来自其他两种部门的非政府实体(不管是市场、非政府组织、私有基金会,还是混合型公私实体)就被挤出了治理流程。反之,当政府在治理中选择消极方式,其他两种部门中的一种或两部都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政府激进主义可能是受某些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比如国家主义(statism)和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消极主义通常源自主观故意,其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和民主多元主义(democratic pluralism)意识形态有关。自由放任主义认为私有部门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民主多元主义认为志愿非营利部门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后两种意识形态都呼吁政府应该扮演更小的角色,而非政府行为体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必须指出上述意识形态并非一定与激进主义或消极主义对应。一些集权主义国家鼓励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民主国家的政府也曾拥抱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意识形态。但单独来看,这些意识形态确实帮助政府决定是否干预国内问题的解决,因此意识形态确与本研究有关。
历史上,有关政府激进主义的问题被多次提及。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进步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展开激烈争辩,焦点是政府是否应当扮演医保和劳工等社会问题解决者的角色。20 世纪30 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美国出台“新政”,新政使政府功能急剧增加。冷战期间,政府扮演的角色更多,这导致发达国家中开始出现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但这种向激进政府迈进的趋势并未持续。20世纪80 年代末,共产主义式微导致前苏联集团(former Soviet-bloc)国家的政府功能减少。在早期进步主义时代和新政时代之后,进步主义退潮的时代接踵而至。最具标志性的可能是在20世纪80 年代,以英美为首的许多国家鼓励对公共事业的放宽管制,鼓励私有化。尽管在冷战后政府功能减退进程有所放缓,但有学者指出,“非治理”(ungovernance)领域被故意放开,使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可以参与。
美国的政策说明了国内政府激进主义与对政府间主义的支持经常密切相关。尽管按照当今的评判标准,一战前美国政府激进程度并不高,但当时美国进步主义者制定的法律可谓石破天惊。当时的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着手建立强有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进入此前非政府实体控制的问题领域。比如,威尔逊支持用政府间机构(或混合型机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ILO)]替代非政府的国际劳工立法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一战后不久,沃伦•哈定总统提出“回归常态”(return to normalcy),美国国内政府激进主义退潮,美国的政府间主义也受到影响,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参议院决定不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在整个20 世纪20 年代,美国非政府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比美国政府更加主动,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红十字协会(American Red Cross)。
类似的情况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20世纪30 年代,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甚至在二战之前就开始拥抱政府间主义。美国(1934 年加入ILO)在ILO 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中表现活跃;在国联中美国也有所作为,如支持布鲁斯委员会(Bruce Committee)评估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中的潜在作用。在二战末期和二战后,美国政府间主义有变强趋势,比如在1945 年美国支持成立WHO。从国内看,罗斯福支持1943 年《瓦格纳-穆雷-丁格尔法案》(Wagner-Murray-Dingell Bill),该法案寻求建立全国性的医疗和医院体系。而在罗斯福去世后一年的1946 年,共和党人掌控了美国国会,国内政府激进主义又一次遭受打压。在国际上,美国对成立新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支持力度降低,也不太想利用现存政府间国际组织处理外交事务,它甚至在犹豫要不要加入自己曾经帮助创建的WHO。
承担国际任务是国内机构成长的一种方法。当国内机构开始与外国类似机构合作,机构的代表可以学习宝贵的经验,获得更多预算,机构设置的国际办公室可以创造新职位,机构也可以通过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获得声誉。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国内政府机构的政府官员带头支持国际倡议,最终成功创建政府间国际组织。例如前文中提及的联盟卫生组织,它在1923 年时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就是来自英国卫生部(成立于1919 年)和法国卫生部(成立于1921 年)的代表。同理,国内非政府机构的高级领导也会尽力争取成立国际非政府组织。
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形势逆转,美国国内激进主义显著增强,这一点从联邦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人们更加支持政府间主义。美国支持成立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成立于1973 年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同时美国支持赋予现有机构更大的权力,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担任行长时期的世界银行。
但在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又一次削弱政府在国内的功能,并在全球治理中远离政府间主义。美国反对成立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甚至从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中撤出。比如,在1981 年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上,里根政府拒绝支持成立由政府独立出资的国际机构,而是偏向公私共同出资、更加非政府化的选项。直到2009 年,即在美国再一次支持政府激进主义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可再生能源机 构(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才得以成立。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政府激进主义一直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同时,美国的全球政策经常故意不采用政府间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尽管其频率没有20 世纪80 年代高。非政府行为体[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和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接手了本可以由政府间国际组织处理的国际问题。
至20 世 纪50 年 代,UNESCO 的 非 政 府要素开始消退,部分原因是美国麦卡锡主义者施压,联合国成员独立性降低。另一个原因是1954 年前苏联加入后,开始在UNESCO 工作方法和政策中推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20 世纪60 年代和20 世纪70 年代,许多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采用了前苏联的政府间主义方法。
Michael Mauer:现代科学认为,直觉是一种来源可信的理解力或洞察力,特别是在需要做出决策的复杂情境下,它能根据我们的直观本能做出判断。人类的大脑经过漫长进化之后,针对有意义的事情可以闪电般地做出评估,并以安全方式执行。因此而产生的本能感觉聚合体,便是直觉,但我们也必须要将基本直觉与智慧直觉区分开来。
作品《繁忙的渔港》采用线描装饰性手法,描绘广西北海涠洲岛的渔民正在整理渔具的繁忙景象,特意加入一些装饰飘带、云彩等元素,丰富其装饰效果和忙碌氛围,画面富有音乐感,仿佛在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质朴。
解释“国内-国际联系”
我们假设存在两种重要机制将国内政府激进主义和政府间主义连在一起。第一种机制为国内-国际的意识形态联系,第二种机制为某国国内机构可以影响该国采用政府间解决方案的兴趣和能力。
结合图6(b)和图8可见,在限制膨胀过程中,吸水膨胀受体变约束,纯膨润土孔径>1μm的孔隙被挤压。当限制膨胀约束卸除,回弹稳定后,由于颗粒膨胀挤压约束作用,纯膨润土孔隙分布范围依然较窄。
此种国内-国际机构性联系的主要促成者是在各国国内特定职能机构任职的、在国际上代表各自国家的官员。本文认为,这些人不仅会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也会保护自己机构的利益。相应地,人们普遍认为机构是理性的、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体,它们在主动追求生存和成长。在达到生存阈值(即机构成长到足够大,与主要客户建立了常规化关系)之前,成长一直是一个机构在早期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一家机构成立后的几年里,许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机构创建者会选择离开,前往更有活力的环境,因此该机构的成长速度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但就算在后期,一家机构仍然有获取物质资源和声誉的动机。
tere kümün öɡdör(ööɡedör)tere tuqai ü (那个人昨天就把那件事说了)
上述对于意识形态的认识对我们的研究有以下意义。第一,当统治精英发生变化时,国家推崇的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第二点与第一点相关,我们认为意识形态与精英的相关度要大于低级别官员,因为即使政府发生改变,低级别官员的职位仍倾向于保持不变。此外,由于精英参与多个问题领域的政策决策,前后一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更加可能展现出意识形态倾向。
而最爱用来搭配蟹的干白,非Penfolds Bin 311莫属。自2005发布了首批年份以来,它一直是我心中冷凉产区风格的优质霞多丽代表。今年新发布的年份为2017,相较于上一年份,它延续着凉爽气候产区的风格特点,不同之处是它由单一产区变为了多产区混酿。新年份的霞多丽葡萄溯源地不再仅仅限于新南威尔士州雪山南坡高纬度凉爽气候风格的唐巴兰姆巴,更是择取了大部分来自于阿德莱德山区与塔斯马尼亚的葡萄果实。采用橡木桶发酵,并在旧法国橡木桶中熟化八个月,而这些橡木桶曾用于熟化“酒后”雅塔娜葡萄酒。加上定期的搅桶,完美地构建出这款酒整体馥郁的口感,完美的酸度以及风味的复杂度。
目前,改变术前炎症状态和免疫状态的治疗能改善恶性肿瘤患者的长期预后。所以血常规中炎性指标的计数及其比值的分析作为胃癌患者的治疗及预后预测的指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应用于肿瘤患者的早期发现,通过改善炎症及免疫状态以达到良好的预后效果。尤其是NLR和LWR,前者可以帮助观察胃癌浸润深度、淋巴结的转移、肿瘤分期,而后者作为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会成为一种肿瘤评价的新指标。相较于其他肿瘤信息获取的方式,血常规更简单、方便、经济、可重复性强,而且更为安全。结合其他相关检查可以更好地对胃癌患者进行准确的风险分层,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有效的参考。
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意识形态(不仅在不同的问题领域,还在国内和国际两个舞台)能够约束信念和行动。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我们认为当意识形态支持国内政府激进主义时,顶层官员也倾向于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推崇政府间主义。人们认为1941 年罗斯福发表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演讲标志着美国开始参与二战,这是美国国内政策中激进主义向对外政策投射的一个案例。换言之,激发政府采取国内行动的意识形态也会使政府采取国际行动解决全球问题。
反之,当政府在国内拥抱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意识形态,那么他们不太可能在国际舞台支持成立新的政府间机构。比如,在1988 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认为成立强有力的欧洲机构不可取,她表示:“我们在英国国内成功地限制了政府的触角,这绝不是为了让它们在欧洲层面恢复原形。”
意识形态可能会迫使精英将对外信念和国内关于政府激进主义的信念联系起来,原因有几点。比如,上述个体可能仅仅为了避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想使个人信念保持内外一致。一些政治领导人认为:自己的政府出手解决了国内问题,却对国际上面临相似问题的其他国家的个体视而不见,这很难让人接受。另一个可能是,就算一些精英认为没有必要保持内外一致,他们仍然可能采用相似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此举是为了避免国内(甚至国际)民众指责其真诚度。举例来说,一位政府首脑在国内宣传NGO,却在国际上抵制NGO,这种行为难度很高。此种内外不一致可能会动摇意识形态,进而使民众对一些重要的政府政策产生怀疑。我们认为,精英应该使用规范术语(normative terms)而非实用主义方式(pragmatic ways)来呈现此种因意识形态促生的、国内信念和国际信念之间的联系。
另一种有关此种国内-国际联系的解释本质上是“机构性的”(institutional)。我们认为在政府为了解决国内问题成立对应机构或赋予现有机构更大权力后,它们更加有可能寻求类似国际问题的政府间解决方案。此种机构内部包含具有必备技能和既得利益的官僚团体,他们有理由成立和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比如,ILO 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强国在彼时成立了劳工部(法国1906 年,美国1913 年,英国1916 年)。1918 年,上述部门的官员开始商谈组建ILO 的事宜。
所谓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连贯一致的成套理念。不同信念体系之间存在互相矛盾,而意识形态则将其中一些信念聚成一类,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具有严格、死板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规范个体的信念和行动。相较之下,本文认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意味着挑选出一些在特定情境中最有用的信念体系(不论这些信念体系是否能组成一个整体)。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描述了社会中通常为政治精英的一小群人的信念体系。
电源结构明显优化。火电装机占比由2015年约75%下降至2030年的55%,新能源装机占比由2015年的3%大幅提高至15.5%。
下图展示了这两个假定机制如何将国内激进主义和政府间主义联系起来。如箭头1 所示,激进的意识形态可以同时增强国内和国际机构。之后,即使当此种意识形态不再流行,新成立的国内机构仍然会增加成立或赋权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可能性,因为国内机构的官员通过拓展国际项目可以获利(箭头2)。其中一个或两个机制可以在某一特定时间运作。
图:将国内政府激进主义和政府间主义连接起来的机制
尽管分辨两种机制产生的效果十分困难,上述的讨论还是指出了一些潜在的不同。第一,以机构为基础的机制往往功能范围更窄,局限于某一个问题领域。例如,国内劳工机构的官员更可能在劳工问题领域推崇政府间主义。这些人的既得利益和专业才能决定了他们不太可能影响其他问题领域。相较之下,意识形态机制适用于各个层级的治理,也适用于各个问题领域。这是因为,不同问题领域内所有支持扩张或削弱政府激进主义的决定都是受到某一种相似信念体系影响的结果。
第二,使用意识形态武器支持或反对政府间主义的人通常是精英。相较之下,以机构为基础的机制会借国内专门机构代表的手实现。我们认为,这种机构(如卫生部)的官员直接参与成立国际机构的决策可以作为是机构机制存在的证据之一。
第三,由于国内机构在前期(到达生存阈值之前)更加注重成长,我们认为在国内机构成立伊始的几年内,机构机制会占上风。之后,意识形态机制更有可能决定某一机构是否推崇政府间主义或非政府主义。
基础设施承载的压力具有周期性特征,在黄金周期间明显供需失衡,交通难、住宿难等问题困扰游客,拥堵现象常见;而黄金周结束,大部分设施闲置。为分享黄金周经济效益这块大蛋糕,各地争相扩建旅游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在黄金周之外的时间导致恶性竞争。基础设施供给的稳定性与长假消费需求的密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给旅游业的运营管理和平稳发展带来很大困难。
第四,意识形态的特点是信念必须前后一致,因此我们认为:支撑意识形态机制的论据必须在本质上是规范性的;对比之下,支撑机构机制需要技术性、实用性的论据,从而研究政府间方法和非政府方法哪种更有效。
偏好聚合:几种假说
前文指出:个体国家倾向于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输出激进的国内偏好。但不同个体国家的偏好如何聚合,从而塑造更加全球化的政府间架构?众所周知,每个国家的偏好有所不同。比如,在1919 年的戛纳医学会议(Cannes Medical Conference)上,美国推崇非政府模式。英国则偏好政府间机构,并提出:“预防疾病、维护人民健康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和责任。”一位英国官员解释了上述差异,指出尽管两国政府都在“官方工作”(off icial work)和“志愿工作”(voluntary work)之间找到了平衡,“但是在英国,官方工作占主导;在美国,情况是相反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当时英国卫生部刚刚成立,而美国在后来几十年都没有一家全国性的卫生部门。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强国间对政府激进主义偏好分歧更加严重的例证,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前苏联。
为了解释国内偏好如何在全球层面聚合,我们提出了两个相关的假设。第一,我们假定最强国在塑造全球治理中起到的作用最大。我们从最强大的国家开始开始研究,因为长期以来,现存的相关研究皆指出霸权国一直用其偏好和样板塑造全球架构。但我们也测试了2~3 个最强国是否会联合起来,共同影响全球治理中政府间主义的程度。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成立某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会谈不需要所有未来成员国的参与(因为许多国家认可强国的决定),但还是需要1~2 个强国参与才能作出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定。三个以上国家的情况比较罕见。例如,尽管创建国联的倡议由美国官员提出,但美国还是在提出倡议后和英国进行了商议,之后与法国商谈(之后又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更低级别的商议)。类似的情况还有联合国:美国国务院提出意向,其后在1941 年12 月与英国官员商谈,在1943 年与前苏联商谈。
第二,我们假定当强国决定全球治理架构时,最终结果取决于它们偏好的互相妥协,偏好可能相似(如成立WHO),也可能不同(如成立LRCS)。总体上看,我们认为强国对政府激进主义的平均支持程度将会决定最终结果。
上述论点引出下列主要假说:
假说一:一个或几个最强国国内激进主义的程度愈高,政府间国际组织愈加有可能成立。
我们利用假说一的逻辑,预测了一国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可能性,得到假说二。
此外,非政府行为体在一些问题领域处于劣势。在一些政府特别关心的领域,如领土争议领域,非政府组织执行国际合约的能力还不够强。从广义上说,当某一问题领域中主权成本很高(比如安保领域),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性将会降低。上述非政府行为体的缺失并非仅仅因为政府试图霸占这些问题领域,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非政府行为体不适合处理类似问题。因此,在验证本文中有关政府成立和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主要论点时,我们综合考虑了组织密度和主权成本及二者可能引起的变化。
同时,我们根据现有研究文献确定了非政府行为体在塑造全球治理中的潜在作用。早期研究倾向于认为政府行为体一旦决定在全球治理中扮演强势角色,它们将会直接介入,取代非政府行为体。近期的研究则往往宣称当政府行为体存在控制全球治理的强动机时[特别是当某一领域存在很高的主权成本(sovereignty costs),如安保领域],它们几乎将凭一己之力影响该问题领域。但是该研究文献也指出非政府行为体通常有自己特定的偏好,它们可能会采取与国家利益相悖的行动。
本文也指出非政府行为体与其他组织机构一样,它们理性地运作,追求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最大化。当政府袖手旁观时,新的非政府实体会趁机成立,现存实体则会抓住机会成长,两者共同占领它们擅长的专门领域。即使政府并未完全对某一问题领域袖手旁观,非政府行为体仍然能够通过参与全球治理获益,它们通常会试图与有相同目标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合作,通过协作获得物质资源、专业人士和声誉。
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定并非仅仅基于狭隘的机构利益,政府行为体允许或鼓励它们的决定也并非仅仅基于意识形态或国内机构因素。上述决定也有可能源自两种行为体之间的功能差异性:在不同时间、不同问题领域存在优势或劣势。换言之,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一种行为体可能更具优势。非政府行为体很灵活,成员具有创业精神,入门成本较低,上述优点使它们可以比政府间国际组织更快地进入某一全球问题领域。一旦非政府行为体变成主角,它们可能会开始制造问题,充当某一问题领域的“守门人”,保证自己的地位。
尽管在一开始,非政府行为体的上述特征可以吸引人们成立更多的新兴行为体,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增长会逐渐放缓,因为剩余的专门领域将会变少,非政府行为体之间出现竞争关系。因此,非政府行为体密度增加可能会导致其他类型行为体(比如政府间组织)介入。
假说二:某国国内政府激进主义的程度愈高,某国愈加有可能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
下一节将会通过深度研究教育问题的全球治理验证我们的观点。教育对于政府间主义来说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教育在塑造思想和国家认同方面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各国都认为不能让外部势力对教育产生影响。在二战前也确实如此,由于教育和主权联系紧密,各国都认为政府间国际组织不能参与此问题领域。
我们选择全球教育作为关注点的原因在于:一个半世纪以来,全球教育的政府间属性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存在一些非政府行为体优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案例,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取代非政府行为体的案例,以及一些强国参加或退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案例。此种显著变化使我们拥有大量连贯的案例,用于测试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在每一个全球治理发生变化的案例中,我们研究了几个最强国家中政府/非政府国内机构在处理教育问题中的参与度。我们同时研究了上述国家官员是支持采用政府间方法还是非政府方法,来处理全球治理中的教育问题。我们试图得出如下结论:政府积极处理国内教育问题的国家更有可能支持成立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即假说一);政府积极处理国内教育问题的国家更有可能加入这些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即假说二)。
此外,本案例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基于意识形态的机制”和“基于机构的机制”。我们认为国内教育机构的官员专注于成立和加入教育领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基于机构的机制),高层官员则将他们有关教育领域的观点同更宏观的发展联系起来(基于意识形态的机制)。同时我们认为,在国内专业机构成立后的刚开始的数年内,其官员推动成立国际组织的积极性最高。最后,我们认为相较于国内专门机构的官员,顶层精英最有可能就采用某一形态的全球治理提出规范的观点。
教育领域全球治理中的政府间主义
教育领域中第一个成功的国际共建案例是非政府性质的:1899 年在瑞士日内瓦成立的国际新校办事处(International Bureau of New Schools)。尽管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全球涌现了许多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但是人们成立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如1885 年的常设国际教育委员会(Permanent and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最终解散。一战之前,由于大多数国家国内没有全国性的公共教育机构,人们尝试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但也有例外。18 世纪晚期,普鲁士成为第一个对教育机构实施部分中央集权的重要国家。法国紧随其后,在1828 年成立了公共教育部(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相较之下,英国的教育系统主要是私有的,二战前,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微乎其微;直到1944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通过,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才应运而生。美国在1867 年成立了许多小型联邦教育办公室,在1939 年和1953 年进行了微升级,但其整个教育系统仍是高度分散的;直到1979年,美国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才成为内阁级部门。
早期,美国没有集权的联邦教育机构,这限制了其参与成立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商谈的能力。1912 年,美国教育办公室(US Off ice for Education)没有参加成立一家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谈,而是委任了非政府组织美国学校公民联盟(American School Citizenship League)主 席 范 妮• 弗 恩• 安 德 鲁 斯(Fannie Fern Andrews)作为美国教育办公室“特别合作者”代表美国参与会谈。
二战后成立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计划起源于英国。战争期间,该国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现代福利国家。1942 年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号召人们解决社会“五巨恶”(f ive giant evils):肮脏、贫穷、失业、疾病和蒙昧(squalor, want, idleness, disease and ignorance),1944 年的《教育法案》促使成立了教育部,强化了政府的功能。
由于国联没有处理教育问题的机构,成员国将任务交给了非政府行为体。例如,在1920 年,国联理事会向非政府组织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提供了资金支持,让其建立一所国际大学,而不是国联自己成立大学。
1921 年,一些小国建议国联成立处理“智力合作”(intellectual cooperation)问题(包括教育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英国代表是这一提议的主要反对者,他指出英国有“强烈的自由和个人主义传统”,并解释了为何智力合作“应该交由私有组织和个体解决”。支持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家很少(意大利是唯一支持这一倡议的强国),提案最终失败。国联理事会最后的报告反映了英国的主张:“在当今国际环境中,智力合作最好由自发努力推进。”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从长江到黄河南岸共设有13座梯级抽水泵站,总扬程65 m。淮河及沂沭泗河流域每年有大量洪水和余水通过淮河入江水道和入海水道排入长江、黄海。东线工程的部分泵站工程可利用这些洪水和余水反向发电,这些泵站有江都三站、沙集站、刘老涧站、泗阳站、淮安站等,有的泵站年最长发电时间达9个月。泵站反向发电既取得了良好效益,也充分利用了水资源。
几个月后,强国对建立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看法似乎出现了变化。法国公共教育部部长莱昂•贝拉德(Léon Bérard)说服了他内阁中的同僚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共同推动成立了一个专门用于处理大学间和学校间国际人才关系的国联办公室。即使这样,英国的反对还是让国联下了结论:“全国教育应该且永远应该处于国联办公室的能力之外。”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国联不会处理教育问题的态度已经明朗,因此那些支持者开始推进两个机构的成立。第一个是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以下简称IIIC)],1924 年法国大选后的激进政府提出了成立该机构的倡议。针对教育领域,法国公共教育部的官员偏向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但之后他们意识到国联的其他大部分国家不会支持。因此,他们向公开支持国家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的新任部长弗朗索瓦•艾伯特(François Albert)提出建议,成立一个由国联管理的IIIC。该研究所将教育当作智力合作的一部分,并且所有资金由法国政府筹措。由于不用出钱,国联成员国同意成立该机构(驳回了英国象征性的反对)。但尽管法国试图让IIIC 处理某些教育问题,国联仍拒绝将研究所的职责扩大至这一领域。
查阅资料可知,明朝永乐之前,西藏未发现有印刷工艺存在。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朱棣诏宗喀巴入京(南京),宗喀巴谴弟子释迦也失前往。是年,明成祖下令在南京制成藏文经书的铜印模版,印刷经文,赐给西藏各政教领袖。 由此可知,西藏印刷行业可追溯至明朝永乐年间,在南京制成铜版,为西藏印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其影响下,西藏古代印刷业正式起步。
第二个是非政府性质的国际教育局[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以下简称IBE)],该机构于1926 年由几个小国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于瑞士日内瓦,洛克菲勒基金会承担了大部分资金。IBE 的职责是参与国联拒绝承担的教育类任务,但是没有大国支持它,法国政府原本认为一个IIIC 就足够了。到了1929年,因为没有政府出资,且国际社会涌现出更多争夺资源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BE 已经无法完成创始人设计的任务。但在那时已经有足够多的国家(包括法国)愿意将IBE 转型为政府间国际组织。拥有强势国内教育机构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加入了政府间性质的IBE,英美两国没有加入。由于成员国数量不多,IBE 只能参与一些小型的教育任务。二战后,IBE 并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在1919 年巴黎和会上,非政府组织要求国联解决教育问题,建立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教育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然而成立国联的四个强国无视了这一要求。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的集中体现[1]。当今世界科技高速发展,创新战略位置日益突出,作用日益深远,人才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为此世界各国将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研究生教育摆在了更加突出位置,研究生教育成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和渠道。因此,有效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培养在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最主要目标。
理查德• 巴特勒(Richard Butler)负责监督新教育部的建立,他希望扩展教育部的功能。他很快认识到机会所在:他和流亡伦敦的8 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开启会谈,并将会议常态化,讨论战后教育重建问题。在1943 年1 月,新成立的同盟国教育部长会议[ Conference of Allied Ministers of Education(以下简称CAME)] 号召成立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教育重建局”(United Nations Bureau for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在1943 年7 月,因美国施压,CAME 将其会员资格拓展至非欧洲国家。美国国内教育领域激进主义兴起后,美国开始对上述新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产生兴趣。事实确实如此,罗斯福政府在提升政府功能的过程中,1939 年新成立的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Agency)接管了小型的教育局并使其转型为综合性的办公室。同英国教育部一样,新的美国教育办公室(US Off ice of Education)希望通过国际倡议拓展自己的工作范围。例如,1941 年它提议在西半球成立一家人才和教育类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944 年4 月,美国派出一支熟悉教育政策的代表团(包括来自新成立的教育办公室的高层官员)首次参加了CAME。美国很快控制了CAME 的进程,提交了成立一家“全新机构”的议案。这一机构是严格意义上政府间性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基本没有作用。美国代表使用规范术语表达了成立国际组织的需要(美国创作的UNESCO 章程序言中提及了上述需求),他们支持成立政府间机构的表述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指出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补充完善已经在教育、文化和科学领域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
法国使用已经存在20 余年的ILO 作为混合型组织的样板,供UNESCO 借鉴经验。它提议:每个成员国代表包含2 名政府代表和3 名全国性教育和文化NGO 代表。和ILO 相同,代表独自投票,并不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投票。小国偏好此种方式,坚信该方式可以抑制强国的影响力。法国也支持这种架构,认为该架构可以拉拢与IIIC 交好的位于巴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从而使它们支持法国的主要目标:将新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总部设在巴黎。英美则辩称不发达国家没有能力派出5 名代表,号召每个国家持有一票。
综上所述:在减速制动过程中,在流体阻力及阵列本身的惯性等作用影响下,阵列A与阵列B、信号发射气枪与信号接收分支阵列A均逐渐靠近;母舰减速缓和了阵列变形状态的间距变化;若减速制动过程中加速度过大,会导致阵列自身的摆动加剧从而使得分支阵列难以保持平衡。因此,在减速制动过程中阵列A、阵列B无法继续保持平行前进。
在1945 年11 月伦敦召开的准备大会上,代表们面临两种选择:英美提议的完全的政府间组织;法国提议的混合型组织,政府和非政府实体都有会员资格和投票权。谈判期间,英国和美国大体上确保了机构的政府间属性,但同时也默许了一些非政府要素。他们同意UNESCO执行委员会的个体可以来自非政府组织,且他们代表个人而不是政府。此外,尽管国际非政府组织没有投票权,但UNESCO 章程号召成员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一定的磋商与合作”,此后整个联合国系统有了样板。它还规定新成立的机构可以向国际非政府组织注资,以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未有类似的规定。战后初期,大部分UNESCO 项目都下发给了当时已经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或新的通常由UNESCO 出资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相似的国内激进主义-政府间主义平行趋势也出现在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前苏联/俄罗斯。国内趋势和国际趋势之间存在一种明显联系,我们该如何解释?
在20 世纪70 年代晚期,美国开始抱怨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政策。观察者认为由于存在强有力的保守意识形态因素,里根执政时期紧张关系升级。在1983 年12 月,美国威胁退出UNESCO,宣称UNESCO 充斥着“国家主义”,“倾向发展政府机构而非私有私有部门”。 1984年美国退出该政府间国际组织。一年后,英国以相同理由退出。
美国在缺席UNESCO 的20 年里,寻求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教育援助,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如果是美国影响力较强的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会推动此类政府间国际组织更多地参与相关问题领域。同时,上述两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开始将更重要的任务交给国际非政府组织。2000 年起,由于欧盟的努力,主要由世界银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方式(认为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推动教育系统由公立转向私有)和UNESCO 推行的“基于重新分配的方式”(redistribution-based approach)开始趋同。
今年的航海日活动以会议论坛形式为主,包含中国国际海员论坛、全球绿色航运论坛等多个国际性论坛,吸引了大批来自国际海事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外知名航运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海事英语是航海领域广泛应用的专门用途英语,其专业特色体现在用词规范、语法简洁,同时有着大量的专业术语、缩略词和“单指涉”词,例如,chief officer表示“大副”,而非“主管官员”,chief engineer为“轮机长”,并非“总工程师”,draft意为“吃水深度”,不是“初稿”,loss的翻译是“灭失”,而非“丢失”。可见学习专有词汇是掌握海事英语的重中之重。
美国于2003 年重返UNESCO,它继续在该政府间国际组织内部助长非政府要素。2012 年,在UNESCO 通过战略伙伴关系政策框架过程中,美国起到了主要作用,该政策框架将UNESCO与私有部门的关系正式化。自此以后,类似盖茨基金会和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s)的强大私有组织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独立地参与国际教育项目。在UNESCO 内部,相较于政府,私有基金会通过自愿捐助的方式贡献更多。上述变化可以视为该问题领域近期向非政府主义靠拢的又一证明。
案例研究
上述描述性文字为我们的论点提供支撑,即:政府积极处理国内教育问题的国家更有可能支持成立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即假说一);政府积极处理国内教育问题的国家更有可能加入这些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即假说二)。20世纪早期,法国采用激进方式处理教育问题,它同时是成立教育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主要支持者。法国成功创建了IIIC,尽管该机构无法全面处理教育类问题。1929 年,性质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IBE 成立,政府在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成为会员国;彼时持有非政府倾向的美国和英国则没有加入。
二战后,美国和英国在教育领域向政府参与转变,他们也支持成立了一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前苏联开始向UNESCO 等政府间国际组织投射其国内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到了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和英国在国内治理中脱离激进主义。他们批评UNESCO 的国家主义方式,最终从该机构退出。而在国内教育问题领域政府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的强国并未退出。近20 年来,美国向全球推广其国内公私合作模式,这导致教育领域向非政府主义靠拢。
总而言之,案例研究表明:向政府间主义转变的主要支持者是有强烈国内激进主义偏好的强国,而在本国反对激进主义的国家则支持向非政府主义转变。
我们也认为,国内教育机构的官员会促成建立和加入国际教育组织。事实正是如此:一战前成立教育类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尝试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强国国内没有相应机构,无法派出代表商谈政府间协议。比如,在1912 年美国委任一家NGO 领导人作为代表参与国际会议,商讨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其结果是全球治理仍然是非政府性的。
一战后,商讨教育领域内合作可能的英美代表并非来自弱势的国内政府教育办公室,而是来自政府高层机构。彼时,法国公共教育部(强有力的专门机构)是成立一家新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主要支持者。教育部长为内阁成员且与外交部长(他的同僚)有直接联系,上述事实证明了法国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支持。
英国在二战后计划成立UNESCO,这一想法来自其新成立的教育部。美国也是在1939 年教育办公室扩张后才开始准备在这一领域进行政府间谈判。二战后,所有主要国家都成立了相应机构,这是在政府间国际组织内商讨教育领域详细问题的必要前提。
纵观教育领域内的演进,我们发现在一些案例中政府官员援引意识形态支撑自己的论点。20 世纪20 年代和20 世纪80 年代似乎就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反对政府间主义;又如冷战期间,前苏联支持政府间主义。正如我们预测,处理多重问题领域的高级官员(而不是教育机构的官员)提出了这些观点,而且采用了规范化表达。
因此,全球教育治理的政府间性质的变化表明存在两种机制:以规范为基础的机制和以机构为基础的机制。不出所料,我们可以在二战后美国和英国成立教育机构之后的数年间找到“机构机制”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导致新的国内机构成立。除此之外,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好的政府高层精英决定了是否委任国内教育机构官员参加国际会谈,最终决定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命运。上述事实表明,“机构机制”是导致全球治理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而“意识形态机制”是必要原因。若要更好地理解两种机制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深入研究其他问题领域的发展史以及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潜在差异。
教育领域的历史提醒我们:除了国内意识形态和机构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全球治理中的政府间主义。诚然,全球治理的周期性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国兴衰、强国国内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机构变化的结果,但是对政府间主义或非政府主义的倾向可以用影响强国利益的其他因素来解释。比如,法国支持混合型UNESCO的主要原因是其想让新政府间国际组织将总部设在巴黎。同理,使UNESCO 中非政府要素消退的美国麦卡锡主义倾向源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而非国内政府激进主义的投射。
结论:研究发现的意义
总结起来,当强国在国内推行政府激进主义时,它们更有可能推崇政府间主义。该结论对讨论国家在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研究进行了补充。总的来说,当国家坚信自己必须参与处理全球问题,且它们能够与他国合作时,它们更加有可能寻求全球问题的政府间解决方案。
但我们的发现并不仅仅反映了国家的选择:是否成立或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研究领域,它们还有其他重要的意义。将近期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放在广阔的时间语境中,我们可以理解变化很可能是暂时的,而且并不像某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即国家正在失去对全球治理的控制权。政府间主义和非政府主义之间的左右摇摆并非无迹可寻,出现周期性反复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系统性因素(如国际冲突、经济互动或对民主的支持程度)出现了变化,但通常强国兴衰以及国家经历的意识形态变化也会引起反复。正如我们所见,美国政府在冷战前半段支持政府出面解决问题;而在20 世纪20年代与20 世纪80 年代后,它却支持非政府性质的解决方案。2016 年参加美国总统初选和大选的候选人的观点截然不同,不同的候选人上台,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对政府-非政府的偏好就会迅速改变。
从理论角度说,我们的发现支持了以下论点:国内意识形态和机构对全球架构产生影响。为了理解全球发展,我们必须将结构性因素(与冲突、互相依赖和权力分布有关)和国家偏好结合起来,正是这类“社会目的”(social purpose)影响着全球治理机构的性质。本研究认为,国家偏好能够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立和某国的成员国身份产生影响,这厘清了国内领域和国际领域之间存在的又一联系,而长期以来的观点是,我们必须使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上述两个不同的领域。
我们的研究响应了世界政治理论(world polity theory)界的号召,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研究非政府行为体或政府间行为体在何种条件下会占据优势的一般理论。我们从政治学角度而不是社会学角度(社会学衍生出世界政治理论)出发审视了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在考虑了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后,又着重强调了强国及其改变全球治理的能力。事实上,我们认为我们的研究,即专注于政府决策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立/用处(通常是政治学研究领域),必须与解释跨国非政府行为体和社会力量如何应对政府改变全球系统的行动的研究(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结合起来。
这种双管齐下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未来政府间主义和非政府主义趋势研究领域最光明的方向。它使我们能够回答本研究中一笔带过的一些问题:当强国留下的空间不多时,非政府行为体能否改变全球治理的性质?当政府持允许或鼓励的态度时,非政府行为体需要何种条件才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探究上述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政府间-非政府连续统一体的过去和未来。
作者简介 | 亚历山德鲁·格里戈雷斯库(Alexandru Grigorescu),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政治学教授;恰拉扬·贝瑟(),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政治学博士
译者简介 | 史万春(1990—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200444)
*原文来自Alexandru Grigorescu and Çağlayan Başer, The Choice between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Nongovernmentalism: Projecting Domestic Preferences To Global Governance, World Politics, vol. 1, 2019, pp. 88-125.
(责编:李天驹)
标签:政府论文; 国际组织论文; 美国论文; 主义论文; 机构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论文; 行政管理论文;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6期论文; 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