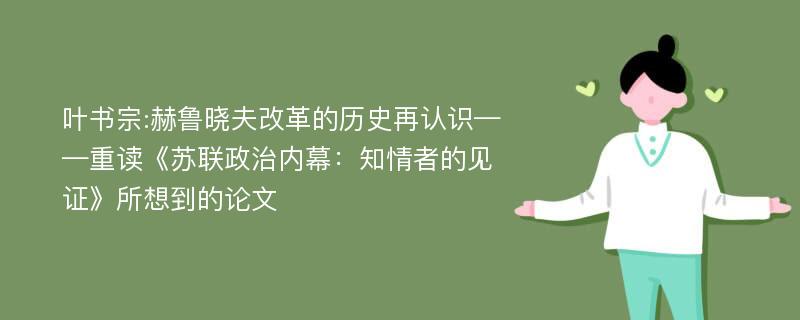
摘 要: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特点是,社会主义从理论成为从一国开始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关键。首先在苏联建成的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确实使原先相对落后的、农业的俄国,一跃成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可是,斯大林体制从理论到实践都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规划的“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这一理想目标。赫鲁晓夫改革的积极意义在于,既为自1861年开始的俄国农奴解放运动画上了句号,又力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走上现代文明的轨道。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赫鲁晓夫改革前后不一贯,半途而废。
关键词:斯大林体制;赫鲁晓夫改革;农奴制残迹;社会主义国家
有关苏联的众多人物评传和回忆录中,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以下简称《见证》)。这本书之所以影响大,不仅因为作者是前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参与了各项重要的政治事件,直接为苏联时期的许多政要做过工作,知道的事情多、细,更因为作者在书中体现出某种俄罗斯人的诚实本性和作为学者应有的学术良知。因此,他的记叙、看法,相对比较客观、可信。也因此,《见证》对于研究苏联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赫鲁晓夫改革的看法,总的来说,《见证》是比较客观的。不过,《见证》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某些评论,在时光流逝了半个多世纪,在苏联历史档案陆续解密,历史真相更为清晰地显露之后,就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了。
从表2中也不难看出,在各段肋骨的骨折中,影像与临床诊断符合率很高,已达到了96.6%。对于发生于分段交界区与临床诊断不符合的骨折,可以利用CT的VR、SSD等重建或体表放置标志物扫描等方法来确定。对于细微骨折、骨挫伤和肋软骨的不典型骨折,可以通过CT薄层、MPR、CPR、VR和软骨成像等多方法、多角度观看,以及多位医生综合分析。对于影像仍不能确定而临床又高度怀疑的骨折,建议在4~5周[11]再行CT复查,此时肋骨内外骨痂最多,检出率最高。
为了进一步验证方法的可靠性,按照实验方法测定Co光谱分析标准样品系列YSS005-1和YSS005-2中Cu、Fe、Ni、Cd、Zn、Mn、Mg、Si、As含量,标准样品系列采用盐酸进行消解,结果见表12。
赫鲁晓夫改革前后不一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见证》认为:“不能把赫鲁晓夫这种前后不一贯的原因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打算(争权),尽管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1]140-141这一评论就值得辨析了。
先说说“斯大林主义”。
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军事纪律要求来看,简洁的军事训令和一贯的思想训练是不是军队万众一心、赴汤蹈火、令行禁止、无往不胜的重要原因呢?
《见证》所称的“斯大林主义”一词,最早是1956年11月16日,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在一次演说中提出的。铁托在那次演说中,还使用了“斯大林制度”“斯大林主义分子”“斯大林主义立场”“斯大林主义方法”等词。[2]17,19同年11月19日,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发表评论,针对铁托创造“斯大林主义”一词,批评说:“企图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党’和‘非斯大林主义者党’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3]40因此,“斯大林主义”一词,苏联有一个从拒绝接受到逐渐使用的过程。1966年3月23日,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曾说自己多年来一直被称为“斯大林分子”。同年10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全苏思想工作者讨论会,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鲁斯塔维利话剧院导演斯图鲁阿发言时曾这样说:“我们有时被称作斯大林分子,但我们并不感到有什么可耻,而是为自己是斯大林分子而自豪。我是斯大林分子,因为在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年代里,我国人民的胜利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是斯大林分子,因为在卫国战争的岁月里,我国人民的胜利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是斯大林分子,因为在战后恢复国民经济阶段,我国人民的胜利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①见《全苏思想工作者讨论会——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新尝试》,载[苏]罗·麦德维杰夫编:《政治日记1965—1972》,第122页,阿姆斯特丹赫尔岑基金会(俄文版);另见叶书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第17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使用“斯大林主义”一词。②见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14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本文不考订铁托关于“斯大林主义”及其演绎的诸词的含义,也不细察苏联从拒绝到接受、使用的过程,以及含义的演变。本文认为,当今通常所说的“斯大林主义”,一般是指斯大林的理论体系,以及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所以,除非引文,本文以下不使用“斯大林主义”,而使用“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体制”。
不错,诚如《见证》所说,赫鲁晓夫改革确实是前后不一贯、虎头蛇尾的。而赫鲁晓夫改革出现这种情况,也确实和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有关。不仅如此,再进一步说,赫鲁晓夫就是在斯大林体制的襁褓中,由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干部之一。可以说,没有斯大林时代,没有斯大林体制,就没有赫鲁晓夫。可是,尽管历史事实确是如此,还是不能把赫鲁晓夫改革的前后不一贯、虎头蛇尾,归因于他出自斯大林时代,归结为他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恰恰相反,赫鲁晓夫改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不是“纯属”,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倒是他的个人因素决定的。
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当过煤矿工人、机械修理工。1918年,24岁的赫鲁晓夫加入俄共(布),参加过红军,进过顿巴斯的一所技术学院学习,并成为这所技术学院的党委书记。之后,在基辅的某区担任过区委组织部长。1929年,赫鲁晓夫进莫斯科工业学院,并很快从学员成为学院的党委书记。1931年,赫鲁晓夫当上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书记。1934年,赫鲁晓夫又成为党中央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又成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1935年3月9日,《工人莫斯科》编者曾这样评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是一位经受过斗争和党的工作考验的工人,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他是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教育下的那一代党的工作人员中的杰出代表。N.S.赫鲁晓夫是在运用斯大林的工作方法的著名能手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导下,在近年里和党一起逐步成长起来的,他是我们光荣的莫斯科党组织的好领导。”①转引自[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德树等译:《赫鲁晓夫》,第1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938年1月,赫鲁晓夫被提名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成为当时苏联党和国家的10名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赫鲁晓夫这些顺应人心、民意的司法制度改革,使苏联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向前跨进了踏实的一步。
因为直到斯大林逝世,苏共,包括俄共时期,在领导夺取国家政权和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精英辈出。可是,这些精英们只要稍露违背斯大林意志的锋芒,无不被一一翦灭。由于斯大林时代是个扼杀精英的时代,才使得像赫鲁晓夫这样虽然也有政治头脑,但是更多的是巧于心计的政坛人物,不仅能平安地度过大清洗和历次运动的劫难,而且还能被斯大林所赏识,跻身于苏共中央核心领导圈。赫鲁晓夫的这种个性特点就是他的个人因素。可以说,赫鲁晓夫的这一个人因素,既是他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成功之本,也制约了他对斯大林体制的认识,制约了他在当政之后,主持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进程。
周大毛说,看吧,这孩子迟早要犯事。唉,也难为驮子了,他娶了个常爱兰,常爱兰随身带着个炸药包。现在这炸药包还小,以后这炸药包大了,不要把天炸出个窟窿来。
当赫鲁晓夫能与斯大林并排站着的时候,从年龄段上说,赫鲁晓夫属于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这一辈;可是从经历上看,他又不属于“老近卫军”的行列。从文化知识基础来说,赫鲁晓夫恐怕连小学也没有毕业,就进了技术学校、技术学院,而且也没有真正读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来说,赫鲁晓夫更显浅薄,只学得一点当时被称为“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那么,在斯大林时代,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干部,为什么能在苏联政坛如此急剧地上升,成为“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教育下第一代党的工作人员的杰出代表”呢?这除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发起的“深挖沙赫特分子”“反右倾斗争”中的出色表现,也即“政治敏锐性”之外,那就得益于结交了两个人:斯大林的妻子娜·谢·阿里露耶娃、卡冈诺维奇。当然,结识这两个人,也与赫鲁晓夫的政治敏锐性有关。因为赫鲁晓夫担任莫斯科工业学院党委书记时,阿里露耶娃也在工业学院上学,并且还是学院的党务工作者。工业学院中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阿里露耶娃的身份,赫鲁晓夫就是其中之一。赫鲁晓夫与她关系很好,并亲近地称她“娜佳”。斯大林正是通过阿里露耶娃,详细地了解赫鲁晓夫在“反右倾斗争”以及在其他工作中的出色表现的。关于和阿里露耶娃的交往,赫鲁晓夫到晚年有这么一段回忆:“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物,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作为人民的敌人而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样幸免的?我确实忠诚于党这个事实,一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而且他们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为什么逃脱了他们的那种不幸命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谢尔盖也夫娜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4]75阿里露耶娃向斯大林的汇报,当然也影响到卡冈诺维奇对赫鲁晓夫的认识。很快,赫鲁晓夫成了卡冈诺维奇的“助手”,于是一路飙升。
没有斯大林,离开斯大林时代,就没有赫鲁晓夫。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确实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赫鲁晓夫的急速上升,又是他个人因素的实际运用的结果,是他的“实用主义”和“虚荣心”在斯大林时代小试牛刀的成就。
更为离奇的是,1934年11月5日,按照斯大林的意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置“特别小组”(简称“奥索”),以及下属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三人小组”,作为审讯和执行的直接机构。“特别小组”可以绕过法院自行审判,并作出判决。1935年5月25日,这种权力被扩大到“三人小组”。不久,又出现了与“三人小组”并行工作的“两人小组”。“三人小组”与“两人小组”审理“案件”极其荒唐:常常是只审理“案件”所涉及的人员名单,不召见“罪犯”本人、证人,不审核审讯人员收集的“材料”,就贸然作出判决。“判决”经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批准后,“小组”立即执行。这种无视现代司法程序的做法,造成多次出现被处决“罪犯”的名单,密密麻麻地写在一张旧纸头上,有的连父名、名字、姓,都或张冠李戴,或颠三倒四。1935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加以消灭”。于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创造出了“人民的敌人”这一含义不清的罪名,为滥关甚至错杀无辜制造出一条法律依据。
二战后,赫鲁晓夫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曾建议赋予集体农庄庄员大会以驱逐农庄“不良分子”的权利。不久,又在基辅州什波良斯克区搞出一个创举:一年内完成1949—1951年畜牧业的三年发展计划;口号是:“什波良斯克人让时间服从于自己。”赫鲁晓夫冒尖地表现出迎合斯大林正需要的“革命”极端性。
参考王坤等对长三角的研究思路与方法[8],建立指标体系(表1):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作为一级指标,城镇化发展水平下设立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4项二级指标,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下设旅游经济效益、旅游市场规模、旅游发展效率3项二级指标.
赫鲁晓夫既有迎合斯大林需要的极“左”表现,又有面对现实、体察民众饥寒的真情流露。1947年,苏联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乌克兰尤其严重。作为草根出身、喜欢深入基层第一线的赫鲁晓夫,面对乌克兰农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惨状,曾向斯大林建议,在灾区建立“施粥所”,赈济灾民。对各地农村自发搞“劳动小组承包制”,赫鲁晓夫则睁一眼、闭一眼。为此,赫鲁晓夫因“倡议匆忙”,“决定重大问题仓促”,被撤销了在乌克兰的职务,调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搞合并集体农庄,建农业城。为此,1951年4月2日,联共(布)中央在一封内部信件中,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冒险主义”。赫鲁晓夫自己也十分机敏,连忙向斯大林递交承认错误的检讨信。
这就是赫鲁晓夫!他虽然面对苏联社会现实,关注并希望改善群众的生活;但是,他更注意的是必须面对斯大林。赫鲁晓夫与酝酿改革的“列宁格勒事件”,绝不沾边。对“列宁格勒事件”的要人沃兹涅辛斯基,斯大林一会儿要杀他;一会儿说他毕竟是经济学家,应当让他当国家银行行长。赫鲁晓夫只听着,绝不表示意见。如果不是这样,赫鲁晓夫恐怕即使不掉脑袋,也要蹲大狱。这就是赫鲁晓夫!这就是赫鲁晓夫为什么在斯大林死后才开启改革,以及改革过程之所以发生那种特有现象的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
反过来说,能否有这么一位,既不是斯大林时代,也不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的人,能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站出来领导、主持,改革斯大林体制呢?回答是:绝对不可能,绝对难以想象。20世纪社会主义在苏联民族国家的实践决定了,改革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者,只能出自这个体制;只能是出自这个体制内部,既有几分狡黠、又有政治头脑的核心干部,别无可能。
因此,《见证》认为:“不能把赫鲁晓夫这种前后不一贯的原因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主要问题在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实际上,恰恰相反。
怎样看待揭露斯大林与改革斯大林模式之间的关系?
《见证》说:“当时许多人已经很清楚,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了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1]139《见证》所说的意思很清楚: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体制。《见证》认为:赫鲁晓夫改革之所以半途而废,就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反掉斯大林体制。《见证》的这种看法,粗看起来,不无道理,但是细究起来,也是值得辨析的。
其一,斯大林与斯大林体制,虽然不能画等号,但是也有内在联系。由此,反对斯大林个人问题,不可能不牵涉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即现行通称的“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体制是指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是苏联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无所不包的制度体系。这个无所不包的制度体系当然有核心内容,也有渐次外溢的延扩内容。但是不管怎样,斯大林体制是斯大林在苏联这个国家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制度,是一个整体。如同斯大林与斯大林体制既有区别,又不能分割一样,揭露和反对斯大林个人问题,消除斯大林个人给苏联社会主义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维持斯大林体制。
历史的实际也表明,赫鲁晓夫在反对斯大林个人的同时,也在对斯大林体制的很多方面,有所否定,有所扬弃。
1953年9月3日,就在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那次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揭露了苏联农业生产的严重落后,并说:“根源是在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在于农业领导中的缺点的原因,即我们自己所造成的原因。在这些原因之中,首先是在许多农业部门中违反了物质利益的原则。企业和每个工作人员因付出劳动而得到物质利益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5]320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这在当时确实是振聋发聩的,随后就对斯大林的农业体制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改革斯大林农业体制的重要措施是:取消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改行合同收购制。
1953年9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决议:自1953年下半年起,免除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羊皮;免除城市居民和工人村居民应义务交售的牛奶、乳酪;取消1953年1月1日以前历年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积欠;免除公职人员应向国家交售肉、蜂蜜、毛、猪皮的义务。1954年6月24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免除集体农庄庄员、工人、职员、渔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社员的私人副业向国家交售谷物的义务;勾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个体交售者的私人副业在谷物义务交售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实物报酬方面的全部积欠。1958年6月1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取消义务交售制的专门报告,建议实行集体农庄按国家为各个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价格,将产品卖给国家的制度。6月30日,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从1958年7月1日起,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粮食、油料、马铃薯、蔬菜、肉、奶、蛋、羊毛、饲草的制度,同时取消向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专业站交纳实物报酬的制度。从这天起,国家实行统一的农产品收购办法。
至此,斯大林以国家的名义作为法律的义务交售制,也即斯大林规定的、全国农民必须向国家缴纳的“贡税”,实际上是某种封建性赋役,终于被废除了。义务交售制的废除,使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农民最终摆脱了农奴性赋役。这一改革,事实上是为自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农民改革法令》开始的、俄国农奴解放运动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也卸掉了阻碍东斯拉夫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历史包袱。
诚然,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仍然维护集体农庄制度,吸入的市场经济法则也极其有限,更不可能真正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但是不管怎样,撇下它的深远历史意义不说,不能否认,这至少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某种体制性改革。
近年来,国产电梯品牌迅猛发展,以康力电梯、江南嘉捷、远大智能、广日电梯、东南电梯等民族品牌为代表的电梯企业不断占据国内市场份额,但是其综合实力较国际知名电梯企业来说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在制造和管理上的差距尤为明显,导致生产成本过高,竞争力不足。由于电梯产品种类繁多、参数复杂,且用途独特、安全性要求严格,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电梯市场不断走向多样化及定制化的柔性制造模式,因此实行切合我国电梯制造企业的实际情况的精益生产方式,在企业研发、生产及管理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赫鲁晓夫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健全苏联社会主义法制的改革,更不能说是只局限于反斯大林个人问题。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突出地与现代法制社会背道而驰的国家政治生活是:承担和直接实施国家暴力镇压职能的内务机关自成系统。斯大林时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置苏联宪法以及国家司法机构、司法程序于不顾,只听命于斯大林个人。
也是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不仅躲过一次次劫难,并且上升为斯大林倚重的左右手。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是:改革斯大林体制的司法制度,既不能等,也不能乱。
斯大林离开人世后的第21天,即1953年3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联内务部部长贝利亚,就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关于实行大赦的报告。报告中特别提到:目前在各劳动改造营、监狱、劳改队,关押着2526402名不同刑期的“囚犯”;在内务部专门监狱里,关押着221135名“间谍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民族主义分子”等“特别危险国事犯”。这份关于实行大赦的报告说:“国家没有必要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大量的犯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因为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罪行被判刑的,其中包括妇女、少年、老人和病人。”[6]395被关押的这近275万“罪犯”及其亲属喊冤的申诉信,几乎像雪片似地飞向各级机关。仅苏联高等法院,就收到3万多封这类申诉信。根据“特赦”令,截至1953年8月10日,共释放了1032000人。①见[俄]亚力山大·佩日科夫著、刘明等译:《解冻的赫鲁晓夫》,第230页,新华出版社,2006年。1953年3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将劳改营、劳改队及其机构、军事化的警卫队,移交苏联司法部;苏联内务部编制内,只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的特别集中营,以及原战俘中被判刑的战俘的集中营。
先释放被冤枉的人,再改革斯大林的司法制度。实际上,释放被冤枉的人,本身已是对斯大林司法制度的否定。这就是当时苏联的国情。
接着,赫鲁晓夫在恢复和建设法制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是,“二十大”召开之前,恢复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取消了斯大林随心所欲设置的“特别小组”“三人小组”“两人小组”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审讯、执行机关。1953年9月27日,根据苏联总检察长发布的命令,又在各地区检察院成立了监督国家安全机关侦讯活动的部门,明令国家安全机关必须遵守和履行诉讼规范的全部规定,并向监督机构报告自己的全部活动。这样,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成为当时苏联社会正式、公开、受欢迎的主题。
为了从理论上提高对苏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认识,健全司法制度,赫鲁晓夫取消了斯大林时代在这方面的实际封锁,积极鼓励开展司法科学研究,活跃司法理论讨论。在这些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1958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的《苏联刑法原则》。新的《苏联刑法原则》规定,只能根据法院对案件的全部情况仔细考虑之后作出的判决,才能采取惩罚措施;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从14岁提高到16岁;剥夺自由的最大年限从25年减为15年;废除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为什么这样说?
文化艺术领域的“解冻”,也不能不说是对斯大林体制的某种改革。
斯大林时代,文化艺术领域完全被禁锢在斯大林规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死胡同里,僵化、死寂一片。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10月号《旗帜》杂志,发表了作家伊·格·爱伦堡的论文《谈作家的工作》。爱伦堡的论文从文艺理论上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发起挑战。1954年5月,《旗帜》杂志发表了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第一部,则以文艺创作的实际,超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无论是爱伦堡的论文《谈作家的工作》,或者小说《解冻》第一部,都存在很多问题。不过,爱伦堡发表的论文和小说,其积极意义在于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开了第一枪,打破了斯大林时期僵化的局面。
选取适合的截止高度角,保障算法的可用性,设置好检测门限阈值,可以有效地进行周跳的探测。成功探测到周跳后,利用Chebyshev多项式拟合进行计算修复。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方案可以有效地对独立的单频接收机发生的周跳进行探测和修复,减小了对接收机性能的要求,增强系统的可靠性。
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亚·伊·索尔仁尼琴反映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在苏联文艺领域几乎产生了阶段性的影响。1962年初,索尔仁尼琴把这部小说的书稿,送给《新世界》杂志主编、苏联著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虽然看过书稿的人,都认为写得很好,包括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可是谁也不敢拍板。书稿最后被送到苏共中央主席团。赫鲁晓夫认为,小说的价值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的真实情况。就这部作品可不可以发表,苏共中央主席团进行讨论、表决。赫鲁晓夫问:有没有反对?看到没有反对,赫鲁晓夫说:没有反对,就通过。这样,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的发表,在苏联文艺创作领域,基本上冲垮了斯大林设置的框框。对待文艺创作,赫鲁晓夫曾这样说:“应该让读者有机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不应当对我们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出判决,好像他们在接受审判似的。”[7]135-136
支持“利别尔曼计划”讨论,可以说是赫鲁晓夫作出的、改变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观念的历史性贡献。
历史赋予首先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有二:
利别尔曼的文章,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苏联经济学界反映强烈。
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就利别尔曼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于是,由《真理报》编辑部发起,开展关于完善经济管理问题的讨论。讨论从“如何使企业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问题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的方法,完成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工作人员的方法,等等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成本、劳动生产率等多方面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苏联全国性报刊,以及其他地方性报刊、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报,都刊登文章,参加讨论。这场大讨论,从1962年9月开始,到1963年底告一段落。其间,仅《真理报》编辑部就收到1000多篇讨论文章。此外,除了刊登文章之外,还举行多次全国性的讨论会。
本课题的纸病检测系统平台采用“CCD相机+FPGA+计算机”的结构模式,该系统主要由CCD相机、FPGA数据处理系统、上位机3部分构成。该纸病检测系统硬件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其中,CCD相机选用DALSA公司S2系列线阵相机S2- 12- 02K40- 00-L,其灵敏度高、对光照的要求更低。FPGA芯片采用Altera公司Cyclone IV系列芯片ep4ce115f29c7n,内部含有丰富的硬件资源。SDRAM采用IS42S16160D,主要用于跨时钟域传输中对图像数据的缓存。以太网芯片采用DM9000A,该芯片内部集成10/100M自适应收发器,用于FPGA与上位机的通信。
这场历时一年多的大讨论,气氛之宽松、认真、热烈,是自列宁逝世以后从未有过的。讨论还越出了苏联国界,把东欧各国的经济学界也卷了进来,成了一场“国际利别尔曼冲击波”,击碎了斯大林体制关于价值规律、利润、物质刺激等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理论。这场大讨论,对于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种20世纪世界经济大市场形成后的某种向隅式“孤岛经济”,如同釜底抽薪。这场大讨论,不仅是根据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实际上也扣响了世界市场经济的门环。
本文不细述赫鲁晓夫改革。本文只是择要列举赫鲁晓夫采取的某些重要举措,说明历史的实际是:反对斯大林个人问题,必然要改革斯大林体制。至于改革的深度、广度,另当别论。
其二,不可能想象,赫鲁晓夫能对斯大林体制有根本性的认识;更不能期望,也不可能,像赫鲁晓夫这样“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斯大林体制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在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为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现实。理论上构建的理想社会蓝图和真正建立起来的社会现实,总有差距,几乎是人类历史前进的不可违抗的法则。如同人文主义思想家们设计的“理性王国”,在现实世界上建立起来的,不过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一样,斯大林在苏联创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构建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吻合。斯大林参与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使俄国社会有了巨大发展,使苏联国家空前强大起来,但是也给人民带来一些几乎是难以言状的灾难。总之,斯大林参与体制既在推进苏联国家、社会的发展方面有跳跃式的贡献,但是距离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第一阶段,问题多多,相距遥远。
如同社会发展是永远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样,斯大林去世后,不管是谁想完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也即消除斯大林个人给苏联社会主义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改革斯大林体制,都只能在斯大林体制的基础上,从当时苏联社会实际出发,逐步进行。假设当时真有比赫鲁晓夫更高明的超智者,在斯大林离开后,立马就要完善苏联社会主义,并从“根本上”变革斯大林体制。可是,实际问题是,这个“根本”的线,又划在哪里?这里,不免杞人忧天:假设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像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推翻临时政府那样,把斯大林体制从根本上推倒,那么,苏联社会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因此,即使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恢复、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无论是法规、政策、措施,都只能从苏联当时的实际国情出发,逐步地、具体地一件一件做。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欧洲共产主义”所崇尚和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毕竟是两码事。而且“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为止,仅是近乎“理想国”之类的、纸面上的东西,是海市蜃楼。更何况斯大林体制是在20世纪上半期那个特定的苏联国内外环境下建立、存在的。因此,改革斯大林体制,同样要受苏联的国内外环境制约。
所以,本文认为,赫鲁晓夫当政前期,也即大致上到1958年,对斯大林体制的改革,是从苏联实际国情出发,针对苏联社会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采取可行的措施而进行的,是深得苏联人民拥护,有利于推进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改革运动。
赫鲁晓夫当政后期,可以说是完全乱了阵脚。赫鲁晓夫改革前后不一贯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本文不具体、详细展开论述,只是举出其中最为糟糕的举措,莫过于1962—1964年实行的“改组党、苏维埃、工会、共青团机关”的改革。
1962年秋,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按照生产原则划分党组织,建议将党组织划分成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与改组党组织相应,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组织,都进行同样的划分。赫鲁晓夫之所以提出这种改组,是认为对于规模日益庞大的党组织来说,只有将之划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两部分,才便于集中精力,管理好生产。可是,这一改组,可以说是全国乱成一锅粥,招致上上下下干部的反对。这一改组,是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轻率、匆忙,采取重大措施仓促,是赫鲁晓夫“个人因素”的、另一面的典型表现。
引进混合式教学方式,每个项目的学习都以学生为中心,以“做会、做懂”为目标。通过前期的学生线上分层次有针对的学习,中期的线下课堂难点重点讲解答疑,再到最后学生线上自主完善提高。充分应用混合式教学的便利,让学生做到“学、做”一体化,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教学过程中,我们将教学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具体的实施流程如图所示:
怎样认识赫鲁晓夫改革的积极意义?
关于赫鲁晓夫改革的意义,《见证》认为:“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赫鲁晓夫——引者注)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1]141《见证》这一评论,总体看来,也可以说是对的。可是,细究起来,这是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时代意义的认识问题,因此也值得重新辨析。因为如实地认识赫鲁晓夫改革的时代意义,特别是认识赫鲁晓夫改革留给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影响,将有助于推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认识赫鲁晓夫改革的时代意义,基本点是认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同胜利”,而是在俄国一国首先胜利。因此,首先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历史地承担着此前未能预见到的使命。只有从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新使命出发,才能恰当地认识赫鲁晓夫改革的时代意义。
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刊登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文章总的精神是:建议减少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按盈利率的高低来评价和奖励企业。9月20日,《真理报》又刊出利别尔曼的文章。文章阐明:把利润作为衡量生产的经济效率的总的(不是唯一的)指标,可以取得成效。10月中旬,利别尔曼在《经济报》编辑部举行的讨论会上,补充自己的观点:在我的建议中,利润并不是评价企业的“模子”,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盈利定额,以便让企业自己努力去提高利润。
如果说爱伦堡只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提出挑战的话,那么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问世,就掀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肖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中,凭借细腻而又富有神韵的艺术笔调,以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为历史背景,通过表现主人公索柯洛夫的个人遭遇,纵情地讴歌人性的真、善、美。这样,苏联文坛真的活跃起来了。1958年5月28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修改联共(布)中央1948年2月10日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全心全意》的评价。决议认为,把肖斯塔科维奇等天才的作曲家说成是音乐中的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代表,是个人斯大林时期突出的缺点,反映了斯大林对某些艺术作品的偏见和主观态度。1959年5月18—23日,全苏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文艺创作上没有什么渺小的主题,只有对主题的渺小处理;生活方式、家庭关系、爱情生活,对谁也不是禁止写的主题。
其一,首先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地承担着到达理想社会彼岸之舟的使命。可是,斯大林体制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却偏离了这个根本方向。赫鲁晓夫改革的时代意义就在于重新拨转方向,使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回到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逐步建设来实现的现实中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作这样的科学而又明确的概括:“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马克思、恩格斯还原则性地规划了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组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被压迫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将会是“共同胜利”,或者世界主要大国“同时胜利”,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都没有涉及一国或者几国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
古往今来,客观世界的发展,总是超越任何智者的主观规划,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20世纪的世界并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整体或者主要大国同时进入社会主义,而是俄国一国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无论从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都提出了到达“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也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要有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核心问题,就历史地落在了首先胜利的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国家身上。
苏维埃俄国建立前夜,列宁虽然对于首先在俄国一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已经非常明确了,可是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怎么样的呢?列宁还是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来进行理论构建。列宁有这样一段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表述。列宁说:“‘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9]192列宁甚至认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几乎可以不要了,而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列宁的思想很清楚:一国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是需要的,但是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是“消亡中的国家”,“半国家”。苏维埃国家建立后,列宁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面对现实情况,列宁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有很明显的转变,即:将原来认为可以不需要了的那部分,提到了一国社会主义国家的首位。列宁把一国社会主义国家,集中为无产阶级暴力专政,并且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0]594-595当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的这一转变,也和苏维埃俄国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以及与考茨基的论战有关。但是不管怎么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一情绪化论述,总是带有某种极端性。
苏维埃俄国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建设一国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转折。按列宁思想发展来看,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肯定也会有新的转变和发展。但是,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如同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只能解决急需解决的军事领导问题一样,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只能解决迫在眉睫的苏维埃俄国怎样生存问题。现实对苏维埃俄国和列宁无比残酷的是,全国刚刚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底起,列宁就经常患病和休养。1922年5月,列宁又中风了,实际上丧失了工作能力。在生命最后的一年八个月里,令人惊叹的是,列宁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还是对后事作了安排,并且也想到了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和管控问题。如果假以天年,有理由相信列宁定会进而从国家立法层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特别是对国家权力的使用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制定新的措施、法规。何况列宁是学法律的,而且长期生活在西方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氛围中。
墨颜躲到我身后,讪讪道:“那个,天君旨意是令我辅助你捉妖!这下海之事,本仙子就不亲力亲为了,给你一个立头功的机会……”
总之,母语的迁移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它们互相作用,共同制约着母语迁移,不存在某个因素决定了母语的迁移,这也就是不同的做不同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果。
列宁逝世后的五年里,也即新经济政策的五年,联共(布)党围绕各种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其核心还在于认定谁应是决定一切的国家最高领导。争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学习和使用行政权力的过程。尘埃落定,斯大林打倒了各反对派,成为一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建设者。
斯大林对一国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新的创造。
1.对代理机构的约束降低后代理机构缺乏自律。放开资格限制后,代理机构不用考虑资格的审批和升级,即使违法违规被列入不良信用记录也可以重新注册一家公司继续从业。更有甚者,有些代理公司成立的目的有可能就是代理一个较大的采购项目,项目完成后就注销,从而逃避监管。
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演说中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斯大林继续补充说:“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恰恰相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11]149-150这是斯大林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斯大林既将这一理论当作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又作为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理论和立国之本。
显然,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国家理论,违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发挥了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那种特定形势下,并且是在与考茨基论战中的某种激烈表述。更加应当注意的是,列宁虽然有过这样的激烈表述,但是并没有将之付诸苏维埃俄国的专政实践。
斯大林就不同了。他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废除了新经济政策,迫使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异乎寻常地强化国家暴力机器,实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镇压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职能,被斯大林片面化了。社会主义国家——到达理想社会彼岸之舟,被斯大林扭偏了航向。赫鲁晓夫改革,废除了封建性赋役;至于在苏联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更使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司法系统,从斯大林的“中世纪”过渡到现代文明状态,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扭转了斯大林的错误航向。正是由于此,才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一崇高理想,重新回到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一步步向之迈进的实践中来。
其二,历史也赋予首先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着到达“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这一理想目标的示范功能。赫鲁晓夫改革虽然离理想目标还非常遥远,但毕竟是敲裂了斯大林体制封闭的外壳,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发挥示范功能的方向。
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是既不让外部世界看苏联,也禁止苏联人民看外部世界。19世纪20年代,新理想社会实验家、英国人欧文,带了800多人到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创办共产主义移民区,一种名叫“新和谐村”的示范性公社。欧文的实验室试验当然是以破产和失败而告终。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离不开世界性市场、世界性体系业已形成的地球,但斯大林却尽可能地动用国家的一切行政权力,自我封闭,与外部世界隔绝,建设“孤岛社会主义”。
因此,中国版南海争端国际意象的塑造和推广还需通过具体的外交政策和精准的国际舆论引导才能真正获得相关国家的认同。一方面,使建立在客观、尊重历史源流、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公正基础上的“中国版”南海问题国际意象为各方所周知乃至认同;另一方面,对于在南海问题上的误导性意象必须予以坚决回应乃至驳斥以正视听。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严禁公民出国。在关死正常交往渠道的同时,则以无比严酷的法律,惩治胆敢离开苏联国家者。1934年,苏联法律规定:对逃往国外的人的家属、受其抚养的人,可判处流放西伯利亚5年。1935年,又出台更为严厉的法律: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和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10年以下徒刑,其他成员判处5年徒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又将闭门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为闭门建设共产主义。1946年,斯大林明确地说:“‘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苏联这样的国家的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12]478斯大林实际上是将“孤岛社会主义”发展为“孤岛共产主义”。在这同时,由于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范围,斯大林又认为:由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进而发展为“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斯大林说:“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3]594“一国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等思想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将“孤岛社会主义”,发展为“孤岛共产主义”的逻辑结果。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不仅逐渐开放了公民出国的正常渠道,更允许国外人士来苏联旅游。自1956年至1962年12月,大约有50万外国人,涌进苏联旅游。本文不评论苏共二十大,以及以后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国家问题的一些理论思想。本文只是认为,无论怎样,赫鲁晓夫总是突破了斯大林的“孤岛社会主义”,使首先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承担起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示范功能。
赫鲁晓夫算不上伟大人物,但是也并非如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的平庸之辈。当然,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观念基本上没有跳出斯大林社会主义的范围。赫鲁晓夫甚至还接过了斯大林的大国霸权主义,继续控制东欧,镇压匈牙利改革。赫鲁晓夫改革确实也是虎头蛇尾、前后不一贯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总体设计、整体目标。可是,赫鲁晓夫改革看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上却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的。历史表明,这既是赫鲁晓夫改革对推动苏联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是赫鲁晓夫改革留给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怎样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可贵历史遗产。
1917年俄国革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赫鲁晓夫改革由于复杂的原因也是半途而废。但是,赫鲁晓夫改革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之先河的某些做法和时代意义,并不随着苏联的不复存在而烟消云散。
参考文献:
[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2][南斯拉夫]铁托.在普拉南斯拉夫人民军俱乐部向伊斯特里亚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发表的演说(1956年11月11日)[M]//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3]塔斯社评述铁托演说[M]//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4]赫鲁晓夫回忆录[M].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5]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6]贝利亚关于实行大赦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3月26日)[M]//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列宁.国家与革命[M]//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M]//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斯大林.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M]//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12]答《星期日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韦尔特先生问(1946年9月17日)[M]//斯大林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斯大林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Historical Reconsideration of Khrushchev’s Reforms: Ref l ections from Re-reading Inside Story of Soviet Politics: the Witness of an Insider
YE Shuz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The basic feature of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is that socialism became practice of socialist state building beginning in one country.To build what kind of socialist state became the ke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Stalin’s socialist system first built in the Soviet Union actually enabled a backward and agrarian Russia to leap into an industrialized socialist power.However,a socialist state of Stalin system deviated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from Marx and Engels’s ideal of “an association of free development of all”.The epochal significance for Khrushchev’s reforms was that they both completed the Russian serf liberation movement since 1861 and shifte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legal system onto the modern civilized track.Because of variou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Khrushchev’s reforms were incoherent and unfinished.But their epochal significance never vanished even though the socialist state of Soviet Union disappeared.
Key Words:Stalin system; Khrushchev’s reforms; debris of serfdom; socialist state
中图分类号:D751.2;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3-0075-11
收稿日期:2019-04-10
作者简介:叶书宗,男,浙江天台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孙小帆]
标签:斯大林论文; 赫鲁晓夫论文; 苏联论文; 体制论文; 社会主义国家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世界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