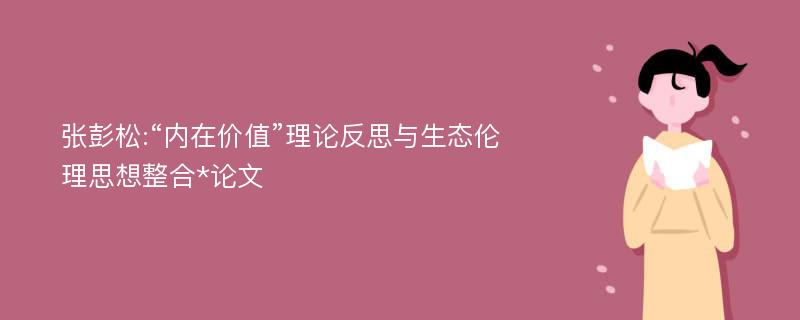
【伦理研究】
关键词:内在价值;生态伦理;整合;生活基础
摘要:以自然“内在价值”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论证生态伦理的道德合理性根据,却难以得到以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文化接受和认同。但如果转换研究视角,从反思“现代性”的批评语境中,对人的“内在价值”进行实质性探析,能够发现疏离自然伦理维度的“现代性”伦理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在包含着无法解决的主观主义的道德心理困境。正是在超越“现代性”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性主题反思中,彰显出关于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对于现代社会伦理所具有的客观基础、人文意蕴和伦理意义。作为具有实践伦理学特质的生态伦理,以“内在价值”探讨为切入点,通过打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对称性破缺”,为“绿色乌托邦”辩护,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思想整合的生活基础。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继承了工业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扭转了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建设循环经济、生态政治和科学发展等宏观战略,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生态文明的启蒙先导,生态伦理思想拓展伦理内涵,将道德关怀的主题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拓展到生命和自然界,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尽管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和发展增强了人们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调节了人对待自然的行为规范,然而在以“人是目的”为价值圭臬的“现代性”全球伦理话语中,仍面临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两难选择”的道德困境。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但这种争论更多的是关注形式上的探讨,缺少现代伦理生活与自然之间的整体考量,没有厘清自然的“内在价值”问题,也就阻碍了从理论反思走向道德实践的现实通道。“内在价值”问题,是当代生态伦理思想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争论的理论焦点,也是能否走向生态伦理整合及其道德实践的关键环节。以往,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常常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却很少从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关联入手,似乎把人的“内在价值”当作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公理来看待,致使生态伦理思想游离于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难以走出两难处境。本文试图转换研究视角,从反思人的“内在价值”入手,从形式化分析引向实质性探究,为生态伦理整合打开一个理论突破口,以便有利于生态伦理思想的道德实践,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人的“内在价值”之实质性探析
通常,生态伦理首先要论证自然“内在价值”的道德合理性,并以此作为生态伦理学的核心理论问题。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当代生态伦理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整合的焦点,也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社会中,跳过对人的“内在价值”的探究直接讨论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伦理的合法性论证不管多么合理和深刻,都是很难被现代人所接受和认可。如果转换论证思路,通过对人的“内在价值”的实质探究,能够显现出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之间关联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继而对自然“内在价值”的道德合理性论证才会有效。进一步说,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无非为了某种伦理的目的而进行的,因此作为对生态伦理学出发点的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脱离现实的论证也许仍然是某种论证,但脱离现实的伦理就什么都不是了”[1]449。的确,即使没有人在场,大自然中的价值也仍然能够存在;但没有人就不会有伦理学。
在“现代性”伦理语境下,人们从人的“内在价值”出发,很容易理解和坚持自然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从历史角度探寻,由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有待批判的、开放的系统,人类传统伦理的自然观或宇宙论与后现代生态世界观都能够提供论证自然“内在价值”的思想资源。因此,在“现代性”批评视域下,辩证理解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的“内在价值”之间的关系,才是生态伦理整合的理论进路和内在逻辑。
从以上的宏观理论分析来看,以往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都是从外在于人类的“内在价值”方面入手,证明生态系统的自满自足,即自然物之间通过彼此联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动态平衡效应;自然是有经验目的性的存在,它们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用来实现人类主体目的的手段。这种思路试图从直接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来确立生态伦理学成立的合法性基础。但是,由于缺乏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的“内在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生态伦理促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性理论硬核”和“核心范畴”往往被看作是自然与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的存在,似乎有过分追求意境高远而脱离现实之虞。
其实,在“现代性”批评语境下,间接考察人的“内在价值”,从相对意义上更有效地说明自然的“内在价值”在生态伦理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毕竟任何理论的探讨都应该与人的问题相关,都必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利益的生态伦理学是没有生命力的。的确,人具有“内在价值”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康德所说:“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2]47无疑,人的“内在价值”是现代人类最为熟知最为关切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现代价值意识和道德观念的代名词。但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现状,不仅在于承认人具有“内在价值”——这是“现代性”道德的价值合理性的理论基石,而且在于对人的“内在价值”的理解是否充分、全面和透彻,这直接决定了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然的“内在价值”相关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关乎生态伦理对现代社会伦理的深远持久的影响。
幼苗根系的形态学指标中的根长、根系表面积等均可作为衡量幼苗水分吸收的重要参数,幼苗根系长、根系表面积大,更有利于幼苗对水分的吸收和利用[12]。试验结果显示(表4),其他处理甜瓜幼苗的根系总长度、根系表面积、主根长均低于25/15℃处理,甜瓜幼苗处于过高或过低温度生长条件下时,根系的生长受到抑制,导致根系根长、根系表面积等指标降低,从而影响甜瓜幼苗根系对水分的吸收。
鉴于此,如果抽象地谈论人的“内在价值”,现代文明中的社会伦理无疑是最完善合理的;而就现实的具体层面而言,人的“内在价值”并没有真正体现在人类自身的利益(包括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是“个人自我成为了现代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其道德认知的必然结果则是,以个人或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价值观开始成为宰制现代人类道德意识的基本‘观点’”[3]7。以个人或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伦理价值观,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个人的独立、自由、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负责的现代人格,加快“个体化”的历史进程,因此,人们也常常把它作为现代文化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会衍生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并不能直接形成人类利益的正当自我关注。实际上,以“现代性”为价值观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真正把人类的利益当作其行为的指针,而是深陷在个人利己主义的泥潭中,为满足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和后代的利益,最终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
纵使谈个人的价值和意义,“现代性”社会中个人的“内在价值”也不充分。“现代性”助长了个人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个人的“内在价值”远没有个人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合理。从形式的合理性来看,在现代社会中,人本身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和目的,人所从事的一切都是为了自身,个人利益或自我实现是人的活动最强有力的原动力。若从实际情况来分析,个人的命运并不由自己主宰,而总是服务于他自身之外的齿轮,或者说个人的生命屈从于个人生命之外的目标。弗洛姆指出:“现代人相信自己是受自私动机的驱使,而实际上他生命的目的却并非他自己的。”[4]81尽管现代社会结构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却切断了个人与他人内在情感的天然纽带,使个人陷入越来越孤立、孤独和恐惧的无名状态中。根本原因在于,摆脱传统文化束缚之后,现代人又被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所压制和强迫,永不餍足地追求物质财富,无法自制!如施韦泽所说:“现代人就像一只漏了气的皮球,总是保持着外力让它成为的样子。整体支配着现代人。”[5]58现代人普遍认为只有不断地向外扩张、追求和支配,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才能彰显、证明和实现自身的“内在价值”,然而,富有悖谬意味的是,每个人越以此凸显自己,越感受不到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和意义,乃至内心生活空虚与无聊。
选取一场典型降雨的完整过程,监测24小时内水源地的水质变化。在降雨开始0h、0.5h、1h、1.5h、2h、2.5h、3h、4h、5h、6h、9h、12h、15h、18h、21h、24h时在五个监测点分别取样。采集的样品均移入洁净干燥的取样瓶中,密封保存,在样品上贴标签编号,同时记录采样的时间、地点、降雨持续时长等信息。在水厂处设置自动雨量计用于监测实时降雨数据。水质监测指标中浊度、pH、DO、电导率在取样后现场监测;COD、氨氮、TN、TP及重金属指标带回实验室进行监测分析[4]。
二、自然“内在价值”的人文意蕴
从形式上以人的“内在价值”为根据,抽象讨论自然的“内在价值”,无法证明“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以这种方式论证的生态伦理思想仅是现代社会伦理范围的拓展而已,并不意味着什么伦理学变革,也凸显不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具有的道德意义。通过对人“内在价值”的实质性探究,揭示出现代人内在精神的物化倾向,变成所谓“外在善”的附属品,“以及与此相伴的人与物的关系超过人与人的关系”[7]228。以形式合理性回避或掩盖实质合理性,这种对人“内在价值”的过分突出和强调,只会加剧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心灵对抗,造成了现代人特有的“强烈的神经症冲突”[8]3,陷入焦虑与敌意相互助长的恶性循环中。因此,现代社会伦理不应该仅仅建立在一些对法律进行拙劣模仿的概念上,更需要在人“内在价值”的形式合理性基础上,充实道德的内涵,提升现代人的生活品质和精神内涵。
由此看来,现代社会伦理对人“内在价值”的强调,理论上严格地限定在社会普遍规范的道义论向度之内,而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充分地发展为人的自主性,也未能形成人与人之间“道德上的休戚与共”,而是被一种无可名状的异己力量所左右和主宰。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与他人在一起,他人同样也与他人在一起。在日常状态中,没有人是他自己。他是什么以及他如何是——这都是无人:没有人,但又是所有的人相互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不是他自己。”[6]14人的这种状态相当于艾略特所描述的“空心人”、罗洛·梅所理解的“空虚的人”和理斯曼研究的“孤独的人群”。不论对现代人的这种表述方式有何种差异,都说明一个问题,在以“现代性”为建构的全球化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具有某种形式上的道德合理性,但更深层面,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却缺少了一些实质性内涵,如自然伦理维度对社会伦理道德力量的担保。原本人类就生活在自然共同体中,只是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理性程度的普遍提高,人才逐步疏离自然,局限于社会共同体中。在疏离自然所建构的现代社会共同体中,人不仅外在于自然,把“自然”等同于“物质”,视自然为人类攫取的资源库,却不必为之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而且,也将社会伦理关系物化,对人类社会生活作简单外部性的理解,成为人们竞相逐利的竞技场。
通过对人的“内在价值”的实质性探析,揭示现代伦理文化的主观主义的道德心理困境,反观出自然“内在价值”之于现代社会伦理的客观基础、人文意蕴和伦理意义。这样一种基于自然“内在价值”的生态伦理思考,并不是否定人的“内在价值”,而是把人的“内在价值”限定在社会伦理生活中,不能完全僭越到自然的价值论层面,为自然的“内在价值”保留存在论的理论空间。人的“内在价值”既表现在颠覆前现代社会中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等级制度所确立的现代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也相应于自然的工具价值而实现人的利益和幸福的终极目的,但如果没有以自然的“内在价值”为内涵的生态伦理作为前提或基础,现代社会伦理就会完全滑入人类中心主义,表面上也在强调保护自然,而“实际上却是延续着一种人本主义的幻觉”[13]208。因此可以看出,生态伦理并不是现代伦理文化的外在限制,而是一种内在需要。
再次,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确认,为生态伦理保护自然的主体性依据提供客观性基础。生态伦理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和解决,往往基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考虑,却很少触及现代生态危机背后深层的心理、情感和精神层面的伦理文化危机。正是内在的空虚、焦虑,使不知足的现代人更加追逐于外在的物质条件,满足无法实现的幸福幻觉,不仅使自身难以自制,也在客观上破坏了大自然生态系统的自主恢复平衡能力。借助于生态文学,能够揭示出现代伦理文化过分注重物质生活,忽视精神生活的自主创造性,导致精神生态的失衡,造成现代人永不知足的“幸福悖论”及无法自制的“囚徒困境”。生态心理学进一步论证了人类社会理性发展和建构中,特别是以工具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伦理文化压抑了人与自然之间情感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激发和凸显出不断向外越界和索求的人类中心主义,演变为破坏人与整个世界和谐关系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吸收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生态伦理也应从主体的内在根据,关注现代人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探寻精神生态的平衡与人的幸福,为保护自然提供深层的理由。
即 ‖F(X)-F(Y)‖≤‖X-Y‖。故得证F的Lipschitz常数为1。注意到2F(X)=I,从而F(X)是强凸的。
首先,在以“人是目的”为圭臬的现代伦理话语中,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反其道而行,反思现代主流价值观中控制和支配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走出主客二分的固定思维模式,才能重新开启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组成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共同体。没有客观的自然存在,不承认自我维持的自组织系统的生态整体,就无法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遑论对自然价值的尊重。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但也没有否认人的先决条件,即自然的先在性,承认人是自然界的历史产物。我们人类“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0]383-384因此,确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建提供了必要。
(3)虚拟水战略对社会环境的影响。通过实行虚拟水战略,增加棉花进口相当于减少人工数33. 25万人、41. 56万人,但是不一定会带来失业问题。同时对于农户增收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机遇。
其次,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目的是扭转现代伦理文化观念的人类中心性,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为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提供了可能。自然是人存在的前提条件,但要想成为人,还得经过人的社会化过程,否则就成为“野人”。马克思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但只有与人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才是存在着的,具有现实的意义,否则,自然“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指出,“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1]296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只是生态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体现出自然“内在价值”的人文意蕴。如前文所述,以“人是目的”的现代伦理话语突出人的“内在价值”的形式合理性,却忽略实质性探究,使现代人类的社会生活愈益疏离自然,也疏离自身,只能局限于自己的利益及其最大化,却缺少对他者的关注,难以突破从自我到他者的内在超越。生态伦理论证自然“内在价值”,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将人类社会置于自然共同体中,“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含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2]194。在包含人类社会的自然共同体中,人对自然的尊重促进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内在和谐,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归属与和谐的爱。
其二,由于与自然的疏离,社会缺少了自然情感的纽带,不仅成为一架生产利润的机器,而且外在于个人,只能被看作是工具性的社群。这个社群只是依靠一种外在的形式化准则建构起来的,在这个规则当中,尽管每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价值,却没有唤起成员的归属感和公共善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性”境遇下的“社会”,与其说是人的本质属性,不如说是人生的竞技场、游戏场。在这种单向度的社会中生活,个人以自我为中心,而自然、社会和人伦关系则成了不言而喻的条件和“用具”(海德格尔语)。以这种方式抽象地看待人,不仅人与自然疏离(“Alienation”,意指疏远、转让、异化、精神错乱),而且也与自己的本性找不到统一,缺乏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指出:“我们的世界已经解魅了;它不仅使我们与自然不和谐,而且与我们自己也不和谐。”[9]53在外部征服自然界、脱离自然界的内核所形成的人类社会伦理文化观念中,不仅造成自然边缘化或客体化,沦为人与自然对立的“环境”[注]一般而言,“自然”与“环境”这两个概念的含义相同,可以替换,但认真推敲,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自然”概念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观,其思想重心在于“本性”“内在根据”等,而“环境”概念产生于近代,相对较晚,倾向于“物质的集合”“事物的总和”。参见吴先伍《从“自然”到“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同时也改变人本身,转变成过度依靠外部力量来支配自身或彰显自我存在价值的机械化生活方式。
以往的生态伦理研究默认现代价值观对人“内在价值”的道德合理性根据,以之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来论证和思考,致使关于自然“内在价值”的伦理判断缺乏足够论据支撑来应对和反驳。通过对人的“内在价值”从抽象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具体的实质性探究,能够看到人“内在价值”的不充分性,其中的缘由正在于缺失现代人类社会生活对待自然的伦理态度及内在维度。生态伦理出于对自然的热爱而保护自然,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是为了牺牲人类的利益和幸福而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而是在“人道主义的僭妄”(戴维·埃伦费尔德语)的“现代性”境遇中重新发现自然的“内在价值”,打破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的永恒支点。
三、生态伦理整合的生活基础
实质探究人的“内在价值”,就是要避免抽象地谈论人。毫无疑问,只有关注人,才能谈得上理论的构建,也只有人才能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人的实质概念的缺失,恰恰在于一个非常普遍的现代道德观念,即抽象地看待人。其一,现代人看重人的社会属性,逐渐脱离并掩盖人的自然属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人的世俗生活的比重增加,似乎越来越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其实不然,这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随着“现代性”的形成和扩展,人的自然属性不断异化为被社会制造出来、刺激起来的欲望,凸显出人的社会属性的“现代性”价值。相对于以往任何时代,人的社会属性在“现代性”的境遇中具有独特内涵与意义,以致于只有通过人的普遍的社会属性才能证明人的“内在价值”。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中,在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由于看不到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漠视了人的心理、精神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结”,既无法证明自然“内在价值”的合理性,也理所当然地将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物之间关系的调整,完全归结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
那时,我还写过一篇《昭君何以“请出塞”》,因为我从来不认为王昭君是为了民族大义而自请远嫁的,也从来不认为她是为爱情而去的。当时读宋人的《鹤林玉露》,其中看到批驳王安石的“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指其“悖理伤道甚矣”,又给我“壮了胆”,就写了这篇杂谈,先后发表在《郑州晚报》和《苏州日报》上。后来,我有机会先后去了湖北兴山的昭君故里和呼和浩特的青冢,这种历史观念与现场观感相融会,又写了8000余字的散文《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发表十几年后还有刊物转载这篇散文。
尽管如此,生态伦理思想不能止于关于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之间的讨论,更应该由理论思考进入到社会实践的现实层面,关注社会伦理文化中的生活方式与幸福,才能使生态伦理整合得以充分体现。因为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不是缘于理论上的困境,而恰恰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才进入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思考与现实需要。关于人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的“内在价值”之间的讨论,不在于探究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何种伦理更有价值,而在于将两种伦理融合成现实生活中的内在要素,促成人的幸福生活的实现和完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只要一谈人的生活和幸福,似乎就必须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考量,不需要参考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语境,这一方面是人们的思维惯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没有真正理解生态伦理思想的实践伦理学(也称作“应用伦理学”)特质。实践伦理学始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最终目的是实现幸福的“生活之道”[14],关于伦理知识的探讨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只有昭示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和幸福,这种讨论才具有实践的意义。
术中探查发现28例宫颈腺癌患者中盆腹腔组织粘连 20例(71.4%),其中致密粘连 4例(14.3%),主要表现为盆腔组织与膀胱粘连10例(35.7%),盆腔组织与肠管粘连8例(28.6%),腹膜、大网膜与肠管粘连3例(10.7%);放疗后4周以内手术的5例患者比放疗4周后手术患者盆腔组织苍白,粘连,水肿明显严重。
具有实践伦理学特质的生态伦理思想,面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生态危机所作出的伦理回应,最终必然走向生态伦理的道德实践,改变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由过去物化的生活方式转向精神生态协调与平衡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的幸福生活。关于人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的“内在价值”之间关系的讨论,目的就是使人更好地过一种精神生态平衡的生活方式,实现顺应自然的幸福。这种“好生活”的幸福追求在以“资本的逻辑”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文化中,需要以自然的“内在价值”为核心的自然中心主义伦理来校正、调整和完善,既承认自然的客观价值,又要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中剥离出人的价值的道德合理性,而不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价值的颠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生态伦理思想的整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以往对生态伦理思想的整合,不考虑具体的现实问题,抽象地讨论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的融合,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性”境遇中的意识形态话语,表面上是以人的“内在价值”为根据,捍卫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的实践本性,却没有真正考察人的“内在价值”的实质性,不加质疑地“把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作为生态道德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尺度,把人道原理作为生态伦理学深层的价值论基础”[15],掩盖或遮蔽了现代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的僭妄”这一深层的“现代性焦虑”。
与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不同,通过对现代伦理文化中人的“内在价值”的实质性探究,映衬出自然“内在价值”的人文意蕴,这种自然中心主义伦理,表面上似乎是追求言说的自由和境界的高远,缺乏对现实的关注,而实际上却是对现有秩序不合理、非正义成分的否定和扬弃,避免现有秩序的永久合理化、挑战现有秩序的绝对合理性社会批判力量。按照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人类历史的演进可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在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中,必然萌生出与之抗衡的人类自我更新和完善的乌托邦力量。“有一点很清楚,即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根据乌托邦成分的变化去理解。”[16]268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中心主义伦理带有超越现实的乌托邦色彩,在近乎绝对优势的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伦理话语体系中,打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对称性破缺”[注]曼海姆从时间的维度来呈现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个概念,即意识形态是过去或历史的沉淀,而乌托邦是未来的憧憬。而且它们的关系常常处于一种“对称性破缺”的态势之中:总是过去侵吞了将来,保守战胜了创新。而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过去和将来的“对称性关系”。在曼海姆看来,仅仅依靠“意识形态”对现存秩序无条件的维护,无法实现人类的进步,人们还需要“乌托邦”打破既有与陈腐,去展示新生与将来。态势,寻求对称性关系和思想的平衡,为“‘绿色乌托邦’辩护”。“绿色乌托邦是竖在我们现代人面前的一座灯塔,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有足够的亮光,而在于我们的心灵还能不能够被它照亮。”[17]196之所以需要绿色乌托邦,并不是停留在纯粹的主观想象或静观、省思的意识中,而是要采取反对态度,认清现实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物化生活”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因而可以着眼于更好生活质量的选择,获得不同的结果。关键不在于预设一个完善的方案,而是我们走出对现实的容忍、依赖和迷恋,形成一种追求新生活的向往。绿色乌托邦“是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对现实生活非理想性的不满,是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化构想,但它的核心却是一种要敢想敢做、身体力行的精神”[17]197-198。因此,绿色乌托邦与其说是生态意识的启蒙,不如说是一种自愿、自觉地扭转当下人们的“物化生活”,转向“生态生活”[注]卡琳·克里斯坦森针对当代的环境问题,倡导绿色消费,“生态生活”,使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天然节奏、自然循环相一致,“在我们的生活中提供一种幸福和沉稳的感觉,而不是使我们完全失常”。参见卡琳·克里斯坦森《绿色生活:21世纪生活生态手册》,朱曾文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序和引言。的伦理态度和实际行动。进一步说,生态伦理的价值观拓展、伦理样态的转变,通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制约与权衡,达至生活方式的完善与幸福内涵的提升,“即生活之善,生活之幸福”[18]284。
当然,究竟是愿意过“物化生活”还是“生态生活”,在自由民主化的现代社会,首先取决于每个人的自主决定和自愿选择。两种生活实质性不同,自觉性差异较大。“物化生活”更符合大众的审美,更容易被社会认同,但很难获得个人真实的幸福感,往往被消费时尚所牵引。“生态生活”一般很难达到社会功利的价值标准,但能够不随波逐流,更遵从内心的指引和生态良心,崇尚自我节制的简朴生活,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幸福生活。[注]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一书没有使用“物化生活”和“生态生活”这两个概念,而是比较“消费主义”和“环保主义”,表明了两种生活方式和幸福追求的不同样态。参见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7页。在现代文化多元的自由民主社会生活中,这两种生活都是基于每个人自愿选择的生活样态,却追求着不一样的幸福,个中滋味,需耐心品味,才能自知。其次,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既继承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又要避免威胁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以及更为深层的心理、情感或精神的文化危机,就不能仅仅止于现代伦理的形式化分析,而要进入到实质性探究,实现“生态生活”的幸福追求。“生态生活”不仅是基于现代自由民主时代的自愿原则,更是遵从内心而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自觉。虽然在文明转型过程中,生态伦理思想依然靠自然中心主义伦理的“绿色乌托邦”抗衡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来实现思想整合,尚未达到完全的自觉,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走出“物化生活”的外在牵引,逐步走向“生态生活”的内向超越,趋于社会生活的主流,生态伦理的思想整合才成为可能,形成生活的自由自觉。
参考文献:
[1]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 弗罗姆.逃避自由[M].刘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5] 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孙周兴,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7] 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M].谷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 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M].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9] 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M].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候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3]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4] 卢风.应用伦理学、伦理知识与生活之道[J].道德与文明,2007(4):10-14.
[15] 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1997(3):45-53.
[16]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7] 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M].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
[18]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Reflectionon“IntrinsicValue”TheoryandIntegrationofEcologicalEthics
ZHANG Peng-song
(CollegeofPhilosophy,HeilongjiangUniversity,Harbin150080,China)
Keywords: intrinsic value; ecological ethics; integration; life as basis
Abstract: To establish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natural “intrinsic value”, and to demonstrate the moral rationality of ecological ethics, it is hard to be accepted and identified by modern ethical culture that is based on human “intrinsic value” as the core. But if the thesis transforms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carries out substantive analysis of human's “intrinsic value” from the critical context of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we can find inextricable moral psychological dilemma of subjectivism in the ideology of modernity ethics that alienates the natural ethics. It is the critical theme reflection of transcending the “modernity” ideology that highlights the objective basis, humanistic implication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argument of natural “intrinsic value” for modern social ethic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intrinsic valu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rough breaking the “broken-symmetry” between ideology and Utopia, as an ecological ethic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ethics, it defends the “ecotopia” and seeks the life as ba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natural centralism.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9)01-0056-07
DOI:10.14182/j.cnki.j.anu.2019.01.008
*收稿日期:2018-05-25;
修回日期:2018-09-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KS120)
作者简介:张彭松(1974-),男,黑龙江同江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伦理、应用伦理与中西伦理比较。
责任编辑:钱果长
标签:伦理论文; 价值论文; 自然论文; 生态论文; 人类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KS120)论文;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