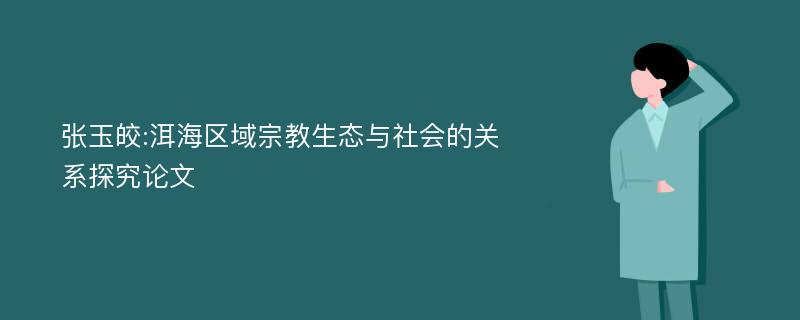
摘 要:理论界对宗教生态学的讨论逐渐由宗教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平衡转向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态和谐、社会结构稳定之间的关系。在宗教生态论视域下,研究洱海区域宗教生态系统内部的递变和融合及其与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矛盾和调适过程,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现出宗教历史变迁轨迹,为更好地促进今天的宗教生态平衡与宗教关系和谐提供借鉴。
关键词:洱海区域;宗教生态;社会;互动关系
宗教生态学理论所研究的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信仰文化圈内,宗教诸种关系及其态势,包括宗教内部的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宗教多样性结构及其适应社会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失衡、重建的规律,并涉及文化圈之间的关系。[1]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宗教生态的兴衰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宗教生态的变迁源于现实的社会根源,而非单纯宗教生态内部结构的变化,即某些宗教的极速膨胀和某些宗教的衰颓让位。也就是说,以鼓励某些宗教发展来抑制另一些宗教发展,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宗教生态的平衡和宗教关系的和谐。社会结构的变迁是造成宗教生态失衡的重要原因,表面上的宗教生态现象,实质上却是社会生态、社会结构的稳定问题。[2]以“社会生命系统”的整体性视角把握宗教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关系,着眼于宗教与非宗教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宗教信仰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寻找解决宗教信仰平衡的途径,有助于宗教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洱海区域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区,同时也是多元宗教共存地。数千年来,洱海区域民众的宗教信仰几经递变,从原始宗教、巫教信仰的纷繁复杂,到佛教传入后的一家独大,再到本主信仰的绵延不绝、多元宗教文化的因革发展,其宗教生态的动态变化与洱海区域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洱海区域独特的社会结构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宗教生态,而宗教生态也影响当地的社会状况。
一 宗教生态与自然的关系
洱海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北起洱源县南端,南至下关镇,因其形似人耳,故名洱海。洱海是云南高原仅次于滇池的第二大淡水湖泊,形成于冰河时代末期,属高原构造断陷湖泊,海拔1972米。洱海湖区冬夏短,春秋长,四季如春,湖区的水生动物种类繁多,物产资源十分丰富。洱海沿岸最大的山脉是云岭山脉南端的主峰苍山,苍山十九峰巍峨雄壮,与秀丽的洱海风光形成强烈对照,每两峰之间都有一条溪水奔泻而下,流入洱海,形成著名的十八溪,千百年来十八溪灌溉着苍山东麓、洱海西岸、两关(龙首关和龙尾关)之间的一百多个村落。在苍洱之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大理坝子,背山面水,气候舒适,自古以来有着“夏不甚暑,冬不甚寒,四时略等”的美誉,广阔的平坝地区自然条件适合人类生存,土壤条件适于农作物种植,故而成为一个较早发展起来的人类聚居区,也孕育了纷繁多样的原始宗教信仰。
(一)自然大环境孕育了多样性的原始宗教信仰
从宏观角度来看,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一个民族所占有的特定自然空间和生存环境,孕育了该民族特有的文化。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同人类的祖先逐步摆脱动物性,开始探讨自然与人生的奥秘、向往神圣美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3]洱海区域先民面对大自然给予的恩赐或灾祸,运用较为朴素简约的思维观念,认为自然物和自然力具有生命、意志以及强大能力,即产生了“万物有灵”观,由此逐渐形成了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等多样性的原始宗教信仰。如:“天母地公”崇拜和祭祀,水神、河神崇拜,“阿央白”生殖崇拜,“己弄吾”生死观,“完乃”不死的灵魂观等。洱海区域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化历史,洱海先民曾经依仗着洱海生产生活,环绕着洱海进行原始农耕。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旱涝丰欠是大事,对雨水的关注可能是最为迫切的,因此,在自然气候利用上,先民常祈求神灵护佑。在盛行万物有灵的洱海先民认为有专门对雨水进行管理的水神,如“龙王”;在白族原始宗教信仰中,有大量的龙崇拜。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凡与水有关,就必然有“龙”的观念出现。每当久旱不雨时,求雨仪式就成为人神沟通的途径之一。由巫师祝祷求雨,举行“祭龙”“搅龙潭”等宗教活动。作为临近湖泊和依山而居的族群,洱海先民崇奉水神、山神。又因农耕生产的重要性,洱海先民崇奉土地神和五谷神。这些原始宗教信仰与洱海区域先民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自然大环境的特点体现在其丰富的原始宗教信仰中。
(二)地理小单元产生了差异性的本主信仰
从微观角度来看,洱海可以分成若干地理小单元,洱海的东、西两岸,以及一北一南的上关和下关,是构成洱海大区域的不同组成部分。相应地,对于当地人来说,洱海区域内部的宗教文化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南诏图传》中的金鱼海螺图用两条首尾相接的蛇将洱海的地理空间勾勒出来,表明历史上洱海区域的文化主体已具有某种关于空间的认识,其居北的海螺与居南的金鱼被认为具有象征意义,代表南诏的疆界,或者不同的图腾氏族。[4]东边的蛇首与西边的蛇尾具有着相互区分的宗教象征意义。在古代,居北的上关和居南的下关是边塞要地,具有军事意义。洱海区域民众很早就与中原汉族、吐蕃人等发生过接触,除了军事战争外,也包括宗教文化的相遇和冲突,而上关和下关就是这些冲突的地理边界。下关的将军洞是一个典型例证。将军洞也称将军庙,供奉唐朝将军李宓。李宓是一位异域异族的本主神,虽然是唐朝攻打南诏而失败身亡的将军,但却受到下关民众的虔诚供奉,香火不断。据学者考证,建将军庙的初衷源自李宓家族的后人对其先祖的追思,因此在建庙初期,只有关内汉族礼奉。而关外人则在天王庙中的前殿塑阁逻凤像,称其为本主。为此关内外的民众互相攻击,关内人称阁逻凤凶残狠毒,背叛唐室;李宓一家忠烈,理应作为忠臣被后人祭奠。而关外人认为阁逻凤英勇抗敌,统一全诏,是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李宓是昏君,唐王帮凶,屠杀大理民众的刽子手。多年来相互争辩,逐渐地双方采取拦禁的办法:每年八月十五日关外派人把守,不准南岸的关外居民祀奉李宓;二月八日关内派人把守北岸,不许关内民众祀奉阁逻凤。[5]由此可见,洱海区域早期历史中由于族际战争而使下关这样的边界地带产生了对待将军洞本主信仰的不同态度,下关在历史上的军事边塞作用标志着族群之间的分立,也导致了民族间宗教信仰的差异。
上关和下关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历史原因,导致当地民众信仰不同的神祇,而洱海东、西两岸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也导致了宗教信仰的相互分化。洱海西岸平坝地区土质肥沃,溪流遍布,宜于农业耕作。而洱海东岸则地势低沉,多山地丘陵,荒芜贫癖,与西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道路交通不便,海东在历史上一度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透过自然地理空间的差异,在海东海西的宗教文化中,也产生了差别。在海东的白语中将洱海边以捕鱼、驾舟楫为生的海边民称为“海民子”,从事农耕的人就称为“干白子”。据王富《鲁川志稿》研究:“干白子从事农耕为主,全民信仰本主和佛教;海民子从事洱海水上运输和捕捞,民国前无农耕,只信仰本主,不信仰佛教。”[6]当地村落中的许多重要节日和民俗活动,如火把节、绕三灵等,都是按照农业耕作的时间和节令安排的,而非按照其他生产活动的时间来安排,体现出由地域不同导致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从而造成宗教信仰的差异。
(三)宗教生态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一地的宗教生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洱海区域的独特自然大环境,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原生宗教信仰。在洱海区域内部的地理小单元,也产生了相互区分的宗教信仰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生产生活有了技术保障和科学支持,过去那种恐惧自然灾祸、祈求自然恩赐的心理和需求已不复存在,加之宗教的广泛传播早已打破了地域限制,因此宗教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日渐减弱。
评价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一环,新课程标准更是强调了要改革传统观念中以考试的形式只评价学生学习结果的弊端,提倡要注重数学学习过程中的合理评价。也只有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健康,教学才能有效,学生的数学能力才能发展。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评价?笔者觉得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宗教生态也反作用于自然环境,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宗教思想和宗教仪式中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由于自然环境对农耕活动的重要性,对自然的尊崇和保护被融入到宗教仪式、宗教观念乃至生活习俗中。洱海区域的白族尊崇动植物为本主,有相关的宗教禁忌,要求人们礼敬自然、天地,追求人神的和谐共生,在客观上产生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效果。后来传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提出了对自然、动植物、生态环境的保护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7]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宗教生态以神圣的名义,以整合各宗教生态伦理思想的力量,礼敬自然,爱护自然,强化着人们的自然保护意识,对促进自然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 宗教生态与经济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都要依法打击。”[注]习近平:《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人民日报》2015年8月26日,第1版。打击试图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利益、践踏民族尊严的行为,要有法可依,依法打击。通过制定、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相关法律,震慑和打击分裂分子、破坏分子。
大部分历史文化名村代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曾辉煌一时的文化,村内无论是有形的古建筑遗址、宗祠、文馆还是无形的民间习俗,都是其代表古文化的遗产与积淀,是古村落的核心价值,是古村落保护的主要内容。不少建筑古旧破损,遗址断壁残垣,是沧桑岁月留下的痕迹,印记着流坑的荣辱兴衰。遍布全村的匾联、丰富的家谱记载,为古建筑留下时间佐证,为研究明清演变时期的民居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除此之外,流坑古村文化资源较丰富,除了逐步形成的书院文化、血缘宗祠文化,还保存了傩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及寺庙灯会、龙舟竞渡、轻乐吹奏等诸多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化。
(一)农业生产孕育了相关的宗教信仰
洱海区域原始社会的宗教生态以各种原生型宗教信仰为主,内部结构较为稳定平衡。原始社会的宗教祭祀活动虽然不能直接促进生产,但是由信仰带来的希望可以鼓励先民更加努力劳作,企盼丰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质财富的积累。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带来了宗教文化的繁荣发展,佛教的传入打破了洱海区域宗教生态的内部平衡,由于统治者极力推崇,佛教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佛教僧侣一度是唐南诏、宋大理国乃至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的上层阶级,统治者加封的师僧或国师,直接参与政权,拥有很大的特权。由于寺院经常被“拨给”或“施舍”大量土地和田产,大寺院就成为大领主,僧侣阶层不但是宗教文化垄断者,也是主要统治阶级之一。统治者大兴寺庙,寺庙建设极尽奢华,耗费了大量财力和物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外,帝国主义借助传教活动对洱海区域人民的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使洱海区域的经济社会遭到严重冲击。由此可见,因某些宗教的过度发展致使宗教生态的失衡,对经济生产也有着消极影响。
(二)商贸发展促进了外来宗教的传入
唐南诏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以血缘关系建立的部落、家族组织形态被打破,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建立。唐南诏王室调整了宗教政策,在吸收唐王朝推行的宗教政策的经验基础上,由对宗教神圣力量的盲目服从,转向有目的性的利用。佛教密宗“阿吒力教”与唐南诏政权紧密联系,积极参与了唐南诏的封建统治。阿吒力教通过编纂大量神话,广为宣传“王权神授”。《南诏图传》生动地记载了唐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被神化了的历史,佛教成为巩固唐南诏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唐南诏统治阶层极为重视阿吒力教的安邦定国作用,允许阿吒力僧参与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和决策。剑川石窟中有一组唐南诏宫廷群像,居中者为唐南诏王阁罗凤,其左侧有位与他平行而坐的僧人,头上戴着曲柄伞,手持念珠,此人为阁罗凤之弟、密教国师阁陂和尚,他曾为唐南诏联络吐蕃,为对唐作战起过很大作用。不仅唐南诏的国师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唐南诏官员也多从僧人中选拔上来,由王室授予各种尊号,如“无量神功国师”“神通妙化卫国真人”等。唐南诏自中期以后,王室成员皈依佛法者众多。唐南诏以后的大长和国也尊崇佛教,国王郑买嗣曾铸佛万尊,为他杀绝唐南诏王室八百人忏悔。宋大理国建立之后,佛教被定为国教,统治阶层采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策略,推行全民信教。宋大理国的崇佛风尚年盛一年,国王不仅极力推崇佛教,且屡屡让位为僧,真正开创了历史上少有的“帝僧”王国,佛教与上层统治者的关系极为密切。《南诏野史》载:“段氏据云南二十二主,三百六十年。段世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以僧道为官,属亦以佛法为治。称之为佛教国,亦未始不可。故其民咸知佛法,易于治理。而不尚军旅。”《云南通志》亦载宋大理国“凡官属大都用佛徒以佐治理。而佛徒亦多读儒书,故称儒释焉”。“僧为官,官为僧”的政治局面是宋大理国时期政教关系密切的例证。
随着唐南诏与吐蕃、中原的来往增多,佛教开始进入洱海区域,宗教生态内部结构产生了剧变,由原来的巫教统领各原始宗教的均衡发展状态,演变为佛教一教独大的不平衡状态。从寻阁劝和劝利盛时期开始,唐南诏王室逐渐开始崇奉佛教,修建寺院,佛教在唐南诏后期占据优势地位,到了宋大理国时期成为了国教。在历代宋大理国王中,有“禅位为僧”“避位为僧”或“废为僧”者数人。直至明清时期,寺院仍占有大量的土地田产,如明弘治、万历年间,鸡足山悉檀寺一寺通过买卖集中的土地有几千亩,这类大寺院有很多。“叶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鸣钟”。佛教在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传播极为广泛,佛教圣地众多,大理成为名副其实的“妙香佛国”。另一方面,忽必烈率军攻入大理城后,多次派军戍守和屯垦大理,大批回族军士、工匠落籍大理,伊斯兰教借此传播和发展,但影响并未超过佛教。面对经济往来活动中涌进的外来宗教信仰,本土民族也在自己的传统宗教中去寻找可以与之抗衡的精神资源。因此,外来宗教在与本土宗教的斗争与融合过程中,构建着新的宗教生态结构。
建立和完善河长制工作的监督、评价和问责制度,拓宽公众参与渠道,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实现对区域范围内河湖的有效保护。
(2)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同步提升人民道德素质。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素质提升与之不匹配、不同步,在某些群体中甚至严重不匹配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西藏地区人们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落后,但是网络化进程丝毫不落后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西藏互联网用户总数甚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当互联网经济为藏区人民带来巨大实惠的时候,遵守法律法规的约束感、遵守经济秩序的道德感同金钱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网络版权保护问题凸显。对假冒、以次充好和恶意篡改等侵权行为在法律制裁、加强监管的同时,应该从根本上提升民众道德素质。
(三)商业经济发展促使了宗教生态格局的改变
“以教辅政”是中国政教关系的主要特点,作为较早地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洱海区域,随着唐南诏奴隶制统一政权的建立,在“神道设教”思想的指导下,宗教不再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是以其特有的超验形式,作用于政治,发挥着辅助政治的作用。唐南诏武力统一六诏后,着手开始其政治建设,重新调整了外交关系,在“苍山会盟”中,异牟寻“请”来道教诸神作为见证,恢复了与李唐的臣属关系,道教成为了政治王权最初的辅化者。随着唐南诏社会的全面发展,唐南诏政权进一步打通了与周边地区的路径,佛教便借由通商、往来等便利从中原、吐蕃传入,宗教生态内部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首先,佛教密宗逐步占据了首要位置,成为上至王室、下至民间的近乎垄断型宗教。其次,道教在上层社会的影响较弱,仅在民间仍有传播。再次,本土巫教不论在上层还是民间都有一定影响。在这种宗教生态之下,原来的“神权政治”被打破,神权逐渐被置于王权控制之下。
(四)宗教生态对经济的影响
洱海区域是云南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有考古资料和数十处遗址证明,以洱海为中心的平坝地区是典型的农业聚落,农业是洱海区域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8]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的强大力量,先民们不得不将生产生活依靠于超自然的力量,进而产生了原始宗教信仰,其中以自然崇拜最为多见,与采集、畜牧、渔业相关的动植物崇拜也十分常见。伴随着粮食生产过程,相关的宗教祭祀也渐渐兴盛起来。如洱海区域典型的稻作祭仪“绕三灵”,在每年播种之前,白族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栽秧会”也是洱海区域白族历来注重水稻栽插农时节令的体现,每年夏至时节由村民举行“开秧门”、本主庙敬香和献祭、“关秧门”等祈求水稻丰收的农事祭祀活动。[9]借助于宗教的力量,洱海区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维系下来;又因农业生产的需要,宗教生态呈现出原始宗教和农业祭祀兴盛的特点。
随着政府对宗教的管理日益规范化,宗教生态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向着良性友好的方向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捐款建设宗教场所、资助宗教团体的行为越来越多,促进了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宗教生态的良性运作也对经济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以宗教为依托的旅游经济逐步兴盛,承载着洱海区域历史文化的各大宗教显现出其经济价值,如近年来兴起的“宗教生态旅游”,正是以有形的宗教文化设施作为发展生态旅游的依托,通过挖掘宗教的生态伦理观念,达到自觉地保护、美化环境,完善自身建设的目的。[10]不同宗教的经济伦理思想也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基督教教义主张通过紧张的劳动,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进而获得拯救,在戒律中禁止抽烟、喝酒,对信众的经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各个宗教的慈善和公益活动为缓解社会贫富不均、解危救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 宗教生态与政治的关系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自然环境、经济生产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存要素,而资源的掠夺和利益的冲突,时常与宗教团体之间价值观、信仰方向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通过政治斗争表现出来。宗教生态和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统治者往往运用政治手段对宗教间及宗教内部的各种矛盾加以调节,政治是影响宗教生态的又一个重要维度。
(一)“神权政治”促进宗教生态的良性发展
“神权政治”是指宗教组织与政治权力机构的完全合一,巫师成为社会的最高领袖。“神权政治”一般与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相重合。氏族部落时期,洱海区域的宗教信仰与部落、村寨、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新唐书·南蛮传下》中提到:“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所谓的鬼主,是巫师的前身,身兼数职,既是祭祀活动的主持者、人神关系的沟通者,又是部落、村寨的首领。无论大小事务,都要通过鬼主对鬼神进行隆重繁琐的祭祀后方可处理。在洱海区域的白族先民中,曾出现过一批专业神职人员,形成了白族特有的民族宗教系统——“朵兮薄”教,也称为巫教。“朵兮薄”是白语音译,意思是“神秘的主宰者”,“朵兮薄”是洱海区域白族先民的祭司,即巫师。“朵兮薄”的地位很高,是重大宗教祭祀活动的主角,耕种前要祭地神,希望它保佑庄稼丰收;打猎时要祀山神,目的是请它保佑猎获野兽,等等。同时,“朵兮薄”还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对部落、村寨、家族中的事务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备受尊崇。原始部落时期,宗教与政治事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巫教几乎统领了所有的原始信仰。由于当时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和家族,此基础上形成了家族奴隶制,为了稳定政治秩序,部落、家族首领借助巫教的力量,可以强化血缘关系,增强部落、家族的认同感和排外性,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争端,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也可借此不断地巩固自身地位。宗教对各部落、家族的重要作用不断凸现出来,维护着部落、家族的规则和秩序,宗教生态趋于稳定和平衡状态。
(二)“神辅政治”与宗教生态的兴衰嬗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不如以前紧密,在经济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进行解决,进而宗教中关于禳灾避祸的功能逐渐衰退,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逐渐疏离。但宗教的身影也并未完全从经济舞台上消失。商业经济时代,各国家、民族为了争夺市场和资源,开始进行了比农牧经济时代更为全面、激烈的争夺,传统的以自然地理和军事要塞划定的边界被突破,商品在世界各国家和民族间流通,使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空前增强。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增加,新一轮的市场开发和资源掠夺拉开帷幕,而一部分基督教传教士则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民族侵略的先锋队。从19世纪中后期起,法国和英国就借着政治条约的便利和经济支持,不断派人向洱海地区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一些传教士打着传播上帝福音的旗号进行宗教资源的掠夺。虽然欧洲国家的传教活动遭到了白族民众的强烈抵制,但西方宗教的传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洱海区域的宗教生态,使其注入了新鲜血液,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原有的宗教生态格局。
宗教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发展状况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只有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的前提下,人类才有条件进行宗教、哲学、艺术等社会思想文化活动,而且这些社会思想文化都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因此,研究一地的宗教生态,要将其放在特定的经济生产发展过程中。
随着唐南诏的崛起,洱海区域成为了唐南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政治一统的局面下,唐南诏的经济生产得到了发展,商贸往来大大加强,与周边地区甚至与东南亚、波斯都有贸易活动。洱海区域是云南通向印缅、西藏的咽喉要地,又是古道“西南丝绸之路”的关口,经济贸易的发展使洱海区域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状态被打破,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有所加强。经济文明的兴盛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外来宗教的传入给洱海区域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宗教场所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选取支架材料为Q890钢,屈服强度为890 MPa;弹性模量E=210 GPa;摩擦因数μ=0.3;密度ρ=7 850 kg/m3;使用自动划分网格功能,细化网格,调整网格的相关性和关联程度为40,网格的平滑选用Low,网格的过渡选用Fast。共划分125 907个网格。网格划分后的有限元模型如图5所示。
其次,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例如,部分企业在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并不注重计算机网络信息数据的安全管理,以致于计算机网络系统运行时网络信息数据安全性得不到保证,不完善的制度会被网络黑客钻空子,入侵到企业系统后就会影响企业整体网络系统的运行,严重的话会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元代以后,统治阶级明确了儒、释、道三教的正统地位,阿吒力教的影响式微,最终被视为邪教,遭到了打击和排挤,逐渐走向消亡。由于佛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自元代开始在中原逐渐衰落的汉传佛教信仰,在洱海区域直至明代仍保持着相当兴盛的势头。又因佛教的教权并未越过王权,使得在洱海区域没有像唐王朝一样,发生类似“三武一宗”灭佛的较大规模、极为残酷的宗教战争。宗教更迭最为剧烈的应属佛教内部汉传佛教诸教派和阿吒力教派之间的兴衰,这主要由于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加强了对洱海区域的集权和控制,中原文化越来越深地影响着洱海区域白族族群。此后,洱海区域的政教关系在中原文化的儒教和宗法性宗教的影响下,日渐建立了较为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在保证政治一统的前提下,使宗教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
(三)“政教分离”与新时期的宗教生态
一般来说,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统治对人们的控制力量相对削弱,从而有利于外来宗教的渗透和侵入。在封建制度走向衰亡之际,帝国主义趁虚而入,以传播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的方式,企图对洱海区域白族进行文化侵略。凭借着帝国主义的在政治条约上的支持,基督教、天主教得以传入洱海区域并扎根,洱海区域的宗教生态也因此发生着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完全废除了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神辅政治”等形式,坚持“政教分离”,既不利用政权来推行某种宗教或禁止某种宗教,也不允许利用宗教来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事务;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严格了宗教管理制度,要求宗教界坚持爱国主义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和支配。因此,在新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引领下,宗教不再与政治紧密相连,政治对宗教生态的影响相对减弱。
(四)宗教生态对政治的影响
前文阐述了洱海区域历史上宗教生态作用于政治的途径和方式:宗教生态内部以巫教整合各原始宗教,通过“神权政治”的形式与政治权力实现了一体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参与社会利益的调整;宗教生态内部一教独大的佛教各教派通过“神辅政治”的形式作为政治的组成部分,对政治权力发挥辅助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宗教生态的发展演变脱离了政治控制,政治与宗教各自独立,平行发展,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政教关系模式。由此可见,宗教生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全部过程,宗教生态的演变对政治关系、政治活动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往往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宗教生态通过发挥社会功能来对政治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除了武装力量和经济力量外,文化和心理力量也十分重要,统治者需要树立政治正当性,也需要得到统治者的认同,所以一个统治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之后,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用各种手段来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在千百年的历史实践中,宗教就是论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之一。凡是受到统治阶级支持和提倡的各种宗教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巩固整治统治的作用。如巫教对原始社会洱海部族秩序的维护,以及唐南诏、宋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对政治统治的维护。其次,统治者除了实行政治统治外,还要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因为宗教自身具有的超越性,它可以使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信仰,通过宗教戒律制约信徒的言行,宗教由此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范畴内。宗教的社会整合作用表现在:群体凝聚作用,行为规范作用,心理消解作用,制约君权作用。[11]宗教生态的和谐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宗教的社会管理职能,对政治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四 宗教生态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民族文化的演进过程,总是同宗教的发展变迁密切相关。氏族部落的原始文化与原始宗教是浑然一体的,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同民族宗教是紧密相连的,尽管宗教不是民族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它是整合族群、形成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的根本力量。[12]洱海区域以白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传统,并非一元单向的发展,而是在民族形成之初就是多元共生的。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宗教生态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朝着多元多层多向发展。
(一)民族文化的多源性促成了宗教生态的多样性
白族并非单一民族体,而是由多个民族融合共生的民族共同体。原始社会时期,活跃于洱海区域的白族先民就开始不断同化或融合附近各族。在洱海区域出土的原始社会遗址显示出洱海区域的原始文化集合了南北多地的特色,如居民种植水稻,从事渔猎、采集和捕捞,具有南方文化色彩,同时出土的尖底瓶、瓮棺等,却又受到北方仰韶文化的影响;出土的有肩有段石器具有南方文化特征,但也发现黄河流域的带耳陶器和器上的锥刺纹,大概是后来的古代氐羌人征服当地土著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洱海青铜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则可从其文化遗存中的铜戈、铜钟、铜豆源出于商、周青铜文化而证实。通过多种文化的融合、互补,在这一区域内形成了既有本土文化特征,又具甘、青氐羌、沿海百越及中原文化因素影响的独特青铜文化类型。[13]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化交流、融合,多元文化孕育出多样性的宗教生态结构。西北的氐羌文化和草原文化沿着岷江、金沙江南下,将其源于万物有灵信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一切信使鬼巫”的宗教传统带入了洱海区域,形成了洱海区域的原始宗教信仰,即巫教。在洱海区域早已有所影响的百越、楚等东南海洋文化,将其所传播的稻作祭仪留存了下来。西北内陆的宗教文化、东南沿海的宗教文化与洱海区域的土著宗教文化结缘更生,共同构成了洱海区域宗教文化的根底,使洱海区域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宗教生态。
(二)汉文化的理性包容塑造了宗教生态的和谐传统
古典文献中的洱海曾被称为叶榆泽、昆弥川、洱河等。洱由汉字“耳”而来,海是云南习俗中对湖泊的特有称谓,从洱海名称的由来,可以看出中原地区与洱海地区的往来之深。汉文化具有的人文理性和包容性特点,促成了洱海区域宗教生态少有冲突、较为和谐的局面。早在公元前3世纪,汉族先民秦人已经到达洱海区域。[13]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汉族就开始迁入洱海区域。唐南诏与唐王朝一直保持着臣属关系,唐南诏的制度在某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仿制中原,受到中原汉文化影响很深。宋大理国与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元代郭松年来到大理,在其所著《大理行记》一书中提到大理之民的冠婚丧祭之礼,略本于汉族。可见当时的祭祀之仪已深受汉文化影响。明王朝以儒家教礼融化本地风俗,选拔儒士,为师为官,儒家礼制也在洱海区域逐步建立,如《滇志·风俗》载,洱海区域的礼制有冠礼、婚六礼、丧礼、祭礼。随着礼制的确立,儒家思想在白族文人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明清时期的白族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民本思想和忠孝仁义思想,并把孝、悌作为训诫子孙的道德律令。[14]
从洱海区域与中原的关系来看,历来有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来往,其关系超过西藏与印缅。所以,其宗教受中原的影响最深,并在本主信仰中就有所体现,如平民本主大多是在汉文化中被推崇的孝子、节妇,历来与白族发生过战争的一些将领也被奉为本主。佛教教派在洱海区域的兴盛发展也是汉文化影响的典型例证。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汉文化,体现着以人文为主导,宗教理性大行其道的精神方向,多神多教并存。无论是人文思想还是宗教文化,其核心价值都是以仁为本,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德为贵,以义为上。汉文化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温和的,所以宗教极端主义不会成为主流意识。洱海区域的宗教生态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易于接纳外来宗教文化,较为平稳发展,虽有过因政治需要导致佛教独大的失衡状态,但因其文化底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并未发生残忍的宗教战争,而是将理性和谐的宗教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2曾分娩过染色体异常胎儿的孕妇,再次怀孕时生产此种患儿的几率是1/60,比正常孕妇高出10倍。可能是父或母一方有未被查出的染色体异常,或是上次发生染色体畸形的原因还在。
(三)宗教生态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从白族族源的多元性及其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可以看出,开放和包容是白族文化最主要的特征。白族文化吸收了大量的秦蜀文化、古越文化、荆楚文化、吐蕃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且源远流长、兼容并包的特色。[15]正因为这种文化品质,使得洱海区域的宗教生态呈现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洱海区域的宗教生态在白族社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吸收其他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儒家宗教观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众多文化样态,使白族的民族文化融合了多种宗教因素,不断地塑造着白族人文精神和民族品格。
五 结语
宗教生态内部的平衡或失衡,呈现出复杂的社会效应乃至政治效应,涉及到社会宏观管理的相关问题。某个宗教信仰群体的扩大,当然有其历史根源、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但主要原因在于现实的社会根源,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矛盾。以洱海区域为例,通过考察其历史上的宗教变迁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可知宗教生态的变迁从根本上说是受到社会诸多方面的影响,是社会存在在人们思想和心理上的反映。而哪些因素会导致宗教生态的失衡?我们认为,政治制度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只有适合宗教生态良性发展的政治土壤,才能孕育出和谐的宗教生态;只有摆脱国际强势政治的影响,才能实现宗教生态的独立发展。其次,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可能导致人们心理失衡,进而寻求某些宗教中的情绪纾解,导致宗教生态内部结构的变化。最后,文化模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宗教生态的健康运行。从现实角度来看,宗教生态的结构变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宗教政策导向、经济基础变动、生产关系调整、民族文化兴衰的反映,立足于这些客观现实,对宗教生态发展进行制度引导,是社会管理部门可借以参考的思路。
总而言之,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共处于社会生命系统中,只有社会稳定和睦,宗教生态才能趋于平稳,只有二者协调发展,相依互动,才能在不断更新与交互作用中维持活力。宗教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使宗教生态良性发展,趋利避害,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考察其与社会的关系态势将是题中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牟钟鉴.宗教生态论[J].世界宗教文化,2012(1):1-11.
[2]李向平.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J].上海大学学报,2011(1):124-140.
[3]宝贵贞.中国少数民族宗教[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4.
[4]段鼎周.白子国探源[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112.
[5]李一夫.白族本主调查[M]//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本主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83-84.
[6]王富.鲁川志稿[Z].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2003:14.
[7]熊坤新,张兴堂,扎西,阴赵丹.神州聆听十九大 同心浇铸中国梦[J].大理大学学报,2018,2(3):1-8.
[8]《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白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34-37.
[9]金少萍.大理白族稻作祭仪及其变迁[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3):48-51.
[1 0]侯冲.宗教生态旅游与21世纪人类文明[J].思想战线,2000(5):90-92.
[1 1]张践.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0-68.
[1 2]王志捷.宗教与民族文化[M]//牟钟鉴.民族宗教学导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171.
[1 3]李云峰.南诏时期宗教的递变及文化的互动(上)[J].楚雄师专学报,1994:36-46.
[1 4]李晓斌.历史上云南文化交流现象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02.
[1 5]赵金元,饶清翠,凡丽.白族文化的包容性及其现实意义[J].中国发展,2009(3):80-85.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Ecology and Society System in Erhai Lake Area
ZHANG Yu-jiao1,2
(1.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Sociology ,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China; 2. Journal Editor's Office of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3, China)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religious ecology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in the recent years gradually changes from the balance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religious ecological system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balance and social ecological harmony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view of religious ecology, study on the alternation and fusion of internal religious ecological system in Erhai lake area and the process of contradiction and adjustment between religious ecology and social system can more clearly show the religious history change track, and provide reference to promote today's religious ecological balance and religious harmony relationship.
Key words: Erhai lake area, Religious ecology; Societ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9)01-0080-07
DOI:10.13963/j.cnki.hhuxb.2019.01.020
收稿日期:2018-05-07
基金项目:大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KYBS201633)
作者简介:张玉皎(1988-),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博士,博士后,编辑,研究方向:宗教学及佛学。
[责任编辑龙倮贵]
标签:洱海论文; 宗教论文; 生态论文; 白族论文; 区域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红河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大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KYBS201633)论文;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论文; 大理大学学报编辑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