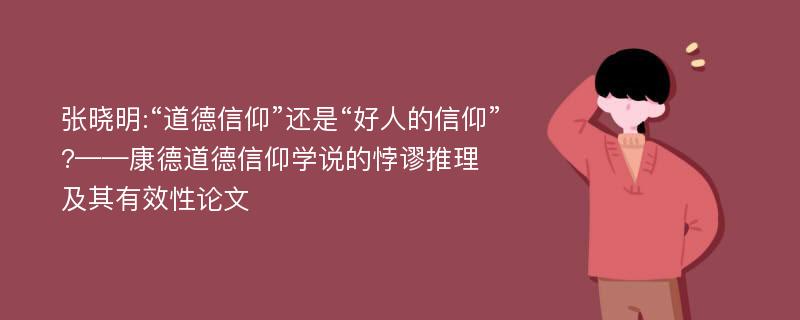
摘 要:康德伦理学始于道德法则,终于“道德信仰”;他用宗教辅助道德,又用道德为宗教辩护。在对信仰所做的“道德论证”中,康德运用了悖谬推理的方法,即从至善如若不可能将导致实践悖论出发,推论出保障至善实现的一些信仰对象。这个“道德论证”向来为人所诟病,不仅由于其中包含某些逻辑矛盾,也由于其结论令人失望。“道德论证”所推论出的“道德信仰”不过是道德的副产品,被私人化为纯粹的个人选择,甚至是“好人的信仰”。这恐怕与康德“为信仰留地盘”的初衷相悖,没有证成信仰,反倒促成了不信。
关键词:道德信仰;道德论证;悖谬推理;德福一致
我们知道,康德伦理学始于道德法则,终于“道德信仰”;他用宗教辅助道德,又用道德为宗教辩护。这种对信仰的道德辩护被康德称为“道德的论证”[1]308。该论证的关键之点在于德福严格一致的“至善”理念:纯粹形式的道德律经由“至善”的综合而推论出一系列宗教理念。康德为“道德信仰”所做的“道德论证”向来为人所诟病,这不仅由于其论证中的某些逻辑不一致,也由于,如本文将指出的那样,其结论令人失望。经“道德论证”推论出的“道德信仰”不过是道德的副产品,被私人化为纯粹的个人选择,甚至是好人才会有的信仰。这个结论恐怕与康德“为信仰留地盘”的初衷相悖,没有证成信仰,反倒促成了不信。
本文从考察“道德论证”的推理逻辑——悖谬推理入手,分别分析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两个论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讨论该论证得出的“道德信仰”具有何种性质和有效性。
一、“道德论证”的悖谬推理
众所周知,康德伦理学起始于从德性中彻底排除幸福,从而抽绎出纯粹形式的道德法则,亦即纯粹的德性,这是他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主要工作,但是紧接着,他又主张德性与幸福必须在至善理念中重新综合起来,并且要成“精确的比例”[2]615。至善在第一批判的结尾曾作为思辨理念而出现,但在第二批判中主要是一个实践概念,“一种实践的善,亦即通过行动而可能的东西”[3]155。也就是说,至善应当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是人行动的作品。至善所要求的“综合”指德性与幸福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即德行把幸福当作某种与德行意识不同的东西产生出来”[3]152。德性必须能够产生幸福,这种内在联系才是德福一致的真义,也是它难以实现的原因所在。幸福已属不易,何况偶然地,或通过邪恶手段得到的幸福并不构成至善,而且谬以千里;只有德性行为本身产生的幸福,才跟德性一起构成至善。所以,至善概念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德性完善,二是德福一致;其中第一义是至善的至上限制条件,必须首先得到满足,第二义也须同时满足,缺一就不成其为至善。然而不幸的是,在人这里,两个条件都满足不了,结果导致了实践的悖论。
以上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的学生在物理学习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难,这些都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妥善应对,并给出合理的应对方案.
问题出在人类的有限性上。康德并不否定人的自然本性,也承认感性幸福的价值。有德之人的感性欲求应该得到满足,这是至善的应有之义。问题在于人类实现德福一致的能力不足,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人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人类意志并不神圣,理性总要与感性欲求斗争,所以人无法在道德上达到完善,至少在今生如此。这就导致至善的首要条件——德性完善即得不到满足。其次,人类在认识能力上有限。第一批判论证了人类的认知局限于感性领域,无法触及物自体,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是一个物自体,因此我们无法确知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否像古典哲学告诉我们的那样,是一个善的世界。自然科学告诉我们,自然无所谓善恶,也不关心善恶。好人不一定得好报,坏人也不一定受惩罚,一切都是随机偶然的。对于物自体的认知企图导致了思辨理性的二律背反,因此世界是否是善的,或者说至善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被悬置起来了,然后移交给了实践理性。实践哲学宣布至善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课题——世界本身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假设)我们可以通过行动改善之。必须看到,这里的确包含了一个假设,即我们的道德行动能够使世界朝着有利于好人的幸福的方面发展。然而由于第三,人类在实践能力上也是非常有限的:人不是上帝,自然并非按照人的意志运行,所以幸福并不取决于人的德性,而是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知识和对这种知识用于自己的意图的身体上的能力”[3]156。
这样,由于人类在道德、认知、身体三个层面上的有限性,德福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实现至善作为一个实践课题仍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这就导致了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因为至善如果不可能,那么道德法则就是在命令实现一个不可实现之物,这显然是违背理性的,并且使人类的道德生活变得不可理喻。正是这个悖论迫使有限理性求助于道德信仰。于是康德对信仰做了以下“道德的论证”:“我们的义务是促进至善,因而不仅有权、而且也有与这个作为需要的义务结合着的必要,来把这个至善的可能性预设为前提,至善由于只有在上帝存有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它就把它的这个预设与义务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即在道德上有必要假设上帝的存有。”[3]172灵魂不朽也与此类似。这样,上帝以及灵魂不朽成了有限的人类理性能够“在道德上一贯地思考”[1]308注和行动的主观条件,而不是被当作客观存在的实体。这种对灵魂与上帝的特殊态度,康德称之为“纯粹的理性信仰”[3]173,199或者“道德的信仰”[1]329,即“理性在把对于理论知识来说难以达到的东西认其为真时的道德思维方式”[1]331。该信仰的对象是“必须预设为最高的道德终极目的之可能性的条件的东西”[1]331,即上面提到的上帝和不朽理念。
(4)假设二:有限理性存在者在今生或来世都达不到神圣性;
二、从德性完善到灵魂不朽
康德对灵魂不朽的论证是这样的:
至善在现世中的实现是一个可以通过道德律来规定的意志的必然客体。但在这个意志中意向与道德律的完全适合却是至善的至上条件。所以这种适合必须正如它的客体一样也是可能的,因为它被包括在必须促进这个客体的同一个命令之中。但意志与道德律的完全的适合就是神圣性,是任何在感官世界中的有理性的存在者在其存有的任何时刻都不能做到的某种完善性。然而由于它仍然是作为实践上的而被必然要求着,所以它只是在一个朝着那种完全的适合而进向无限的进程中才能找到……但这个无限的进程只有在同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某种无限持续下去的生存和人格(我们将它称之为灵魂不朽)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所以至善在实践上只有以灵魂不朽为前提才有可能……[3]167-168
这个证明的关键是命题(1),它既是第一组论证的前提,也是整个论证的前提。“至善在现世中只有在假定了一个拥有某种符合道德意向的原因性的至上的自然原因时才有可能。”在这句非常拗口的话中康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世界是统一的吗,如何统一?这是自笛卡尔以降的现代哲学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物质既然被认为是完全惰性的,与精神绝缘,世界就分裂为“物质—精神”的二元对立结构,那么二者之间如何沟通和统一就成了重要的问题。笛卡尔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困难。随着牛顿物理学的极大胜利,“物质”或“自然”一方逐渐压倒“精神”一方,自然因果律被认为支配一切领域,包括人类的社会、精神生活在内。笛卡尔均衡的二元论结构被打破,终于被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取代。这种唯物论认为,人是机器,或至少跟其他动物没什么两样,受自然法则支配;在伦理学上他们主张,人只受感性欲望支配,快乐或幸福是唯一的行动目的。以这种方式,唯物论哲学解释了世界的统一性——统一于物质。康德认为,这类哲学将人降低为物,损害了人类的尊严,使自由,以及属于自由领域的道德和信仰都不可能了。于是先验哲学从认识论入手,批判人类理性的狂妄自大,将自然律的适用范围限制在现象界,把本体界留给了自由或道德律。这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二元论:道德与自然分属于不同的世界,受各自的法则支配,所以康德也必须解决二者的统一问题。至善学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它是道德与自然统一的综合体,但这种综合并非机械地组合在一起,也并非靠某种神秘的先定和谐,因为道德与自然不像笛卡尔的精神与物质那样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现象不具有实体性,只是本体的表象,所以归根到底二者还是一个世界。而它们的结合方式,如前所述,是一种实践的产生关系:道德意志以行动的方式影响自然,将其改造成一个道德的世界。然而,道德行动能否成功?或者说,人类行动能否使自然变得更加道德,对好人有利?这正是道德信仰学说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指出了,对于有限的人类来说,不能指望自然符合我们的意志,因为显然它是按照自己的法则运行的,这就产生了上述引文中“道德意向的原因性”和“自然原因”之间的矛盾。
(1)至善是道德律的必然客体;
(2)假设一:意志的神圣性是至善的至上条件;
通过两个三段论,康德由至善的道德必要性推出了其实现的“主观条件”——灵魂不朽。我们看到,在解决人类德性不完善这个问题时,上帝已经呼之欲出了,但他的正式出场是为了化解另外一个矛盾,那就是德福不一致的悖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道德论证”的逻辑属于悖谬推理:康德从至善缺位的不合理性推导出实现至善的诸条件。在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的两个论证中,康德同样运用了这种推理方式。
“科学是人类认知世界不竭的长河,技术是人类对生存发展方式不倦的创造.研究科学史,本质上也就是研究人类创造的历史,继往而开来,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5)神圣性只有在无限的进程中才能达到;
我们看到,这段文字包含两套论证,(1)—(3)是第一组论证,第二组论证[(3)—(6)]以第一组论证的结论(3)为前提,得出结论(6),它同时也是整个论证的结论。这两组论证体现了这样一个矛盾:人类“德性”达不到“神圣性”,而后者被认为是至善的必要条件。现在让我们来详细考察该论证的各个环节。
(6)结论二:灵魂不朽是道德上必须假设的。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不同人群可能对药物的敏感性不同,本例的重点是应用本研究提出的亚组识别的方法,判断患者所适用的药物。
所用NiAlW粉末是较规则的球形颗粒(见图1),由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金属材料研究所生产。喷涂前,将粉末置于80 °C的干燥箱中烘烤1 ~ 2 h以去除其中吸附的水汽,防止喷涂过程中送粉管发生堵塞,从而保证送粉顺畅。
设置电机转速分别从1 r/s到10 r/s进行测试,对比电机设定值与实测值,确定其一致性。当电机转速为1 r/s、2 r/s、5 r/s、6 r/s、8 r/s、10 r/s时,实测值与设定值如图11所示,分析后发现本文所研究的无线无源转速参数测试方法所测得转速值与设定值一致,所以此方法可实现常温环境下转速参数的测量。
首先,大前提(1)是康德伦理学的基本观点,认为道德律的对象不光是德性,而是德性与幸福的综合统一体至善,这意味着道德不以斯多亚贤人似的内心宁静为满足,还追求改善世界的现实功效。这是康德伦理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我们认为是应当接受的。观点(2)要求意志与道德法则完全符合,亦即达到“神圣性”,因为只有德性方面最大化,幸福方有资格成比例地最大,这样二者才能构成最完满的整体——至善。基于这两个前提,康德就推出了结论(3):道德完善是实现至善的首要条件。接着在第二组论证的大前提(4)中,康德坚持认为,神圣性是有限的人这辈子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于是理性被迫假设一个道德进步的无限进程,亦即命题(5),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有必要为了至善能够实现而相信灵魂不朽,即(6)。这是灵魂不朽论证的思路,也运用了悖谬推理法:如果死后灵魂不存在,德性就不可能完善,那么至善就不可能了;然而这是荒谬的,所以灵魂必须在死后继续存在。
这个推理看似非常合理,但却带有浓重的文化偏好,这体现在过于苛刻的道德标准和过于悲观的人性论两方面。康德将犬儒派、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与基督教德性进行了比较,指出它们的道德理念分别是素朴、明智、智慧和神圣;并且认为,基督教德性具有前所未有的“严格性”和“纯粹性”,所以最为优越。同时他又主张,这对人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3]175注,此处显然预设了某种“性恶论”的观点。启蒙哲学家大都对卢梭的“性善论”大加颂扬,康德却在宗教著作中提出“根本恶”(radical Böse)的思想,认为人性中具有一种“根本的、生而具有的恶”[4]32,因此神与人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神。以这种“性恶论”为前提,他才说神圣性不但是人在此生中,“甚至超出此生”[3]169-170,也永远达不到的。现在让我们来考虑,命题(2)所要求的神圣性命题和(4)中的性恶说合理吗?
首先我们来看神圣性这个条件。康德承认,人类不过处于“被造物的低微等级”[3]113,既然如此,西斯金质问:“以神圣的标准来衡量人类行为的价值,这公平吗?”[5]122在《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康德把这个要求比作圣经中上帝的命令:“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圣洁的。”[4]66在西斯金看来,这有点过分了,因为它相当于对人说:“要使你自己变成某种超出人类的东西(something more than human)”[5]135。对此,康德或许会回应说,对意志神圣性的要求并非没有根据,它是道德律本身的命令,因为道德律“自在地就是神圣的”,而人是“道德律的主体”,所以“在我们人格中的人性对我们来说本身必定是神圣的”。[3]180如果人性中本有神圣的部分,更准确地说,具有成圣的潜能,那么要求将它实现出来并不过分。康德主张,这个有待实现的理性人格才是“真正的自我”[6],所以他可以这样来回答西斯金的指控:道德法则并不要求你“变成某种超出人类的东西”,而是要你“变成真正的自己”。
然而道德律自身的神圣性何来呢?或许来源于启蒙时代对理性的信仰,在康德这里,神圣性单单被归给实践理性。如今实践理性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它就是非人格的上帝。叔本华形象地说:“在康德的学派中,实践理性及其定言命令,似乎越来越像一个超自然的事实,像一座人的灵魂中的德尔菲神庙,虽然由它的幽暗神殿所发出的神谕,可惜!未宣告将要发生的事,但却确实宣告应当发生的事。”[7]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既然实践理性是神圣的,要求理性人实现其人格的神圣性,按说没有什么问题。“道德律……导致至善的最先和最重要的部分即德性的必然完整性,并且由于这个任务只有在某种永恒中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就导致了对不朽的悬设。”[3]170但为何人就不能德性完善? 如上所述,(4)实际上预设了犹太-基督教的性恶论和人神二分信念。一神论宗教的神之高、之圣洁远非人所能企及,不像佛教中那样人人都可以成佛,这是康德跟东方信仰的不同之处,所以命题(5)中无限的道德进步才成为必要。
但命题(5)最令人费解:一方面是死后的“道德进步”如何可能?贝克指出,死后“灵魂不再处在时间条件之下,那么就无法理解‘持续、无限的进步’是什么意思。”[8]“持续”“进步”这样的概念在经验世界中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经验世界存在时间绵延,但很难想象,超验世界中如何能有道德进步?赛德(Patrick Shade)认为,这意味着康德将道德自我“再现象化”(rephenomenalization)了[9]。对此我们仅仅指出,意志及其德性都属于本体界,所以道德进步也是本体界的事,与时间条件并无必然联系。今生的道德进步当然体现在一个时间序列中,但只不过被表象为如此而已,实际上它也发生在超验世界;如同德性的进步虽然可以被表象为“程度”上逐渐提高,但这实际上是“质”的差别。因此不能认为,讲“道德进程”就把本体“再现象化”了。
另一方面,神圣性何以在“无限的进程”中实现,仍然不明朗。康德似乎认为,意志“神圣性”存在于一个人的生命“整体”中,而非今生或来世某一“时刻”的德性状态中。康德要求人的“整个生活方式”[2]616受道德法则支配,不允许“顿悟”式的“道德飞跃”,也不承认今生或来世的任何时刻有可能实现“人神合一”,因为某一时刻的道德飞跃不能代表一贯的意志准则,也不足以形成稳定的道德意向。这样,通过“视角转换”的方式,康德解决了人类德性与神圣性之间的矛盾——由“行动者视角”转变为“上帝视角”。只有在上帝的“智性直观”中,一个人持续的道德努力才被剥离掉时间的主观条件,被看成一个整体;也只有上帝才能洞悉一个人是否具有坚定不移的道德意向,而后者才是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人类理性对此事的无知可以保护他免于陷入道德懈怠,始终保持“与谦卑结合着的自重”[3]169,175,并在道德上精进不息。
(3)结论一:道德神圣性必须是可能的;
三、从德福一致到上帝存在
即使第一个条件能够满足,人类意志能达到神圣性,至善还是无法实现,因为“德福一致”仍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对人而言,道德与自然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分裂,其统一需要由上帝来保障。以下是康德对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
至善在现世中只有在假定了一个拥有某种符合道德意向的原因性的至上的自然原因时才有可能。现在,一个具有按照法则的表象行动的能力的存在者是一个理智者(有理性的存在者),而按照法则的这种表象的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原因性就是他的意志。所以,自然的至上原因,只要它必须被预设为至善,就是一个通过知性和意志而成为自然的原因(因而是自然的创造者)的存在者,也就是上帝。……至善由于只有在上帝存有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它就把它的这个预设与义务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即在道德上有必要假设上帝的存有。[3]171-172
该论证包含以下几个环节:
(1)大前提:实现至善要求道德意向即是“自然的至上原因”;
(2)定义一:根据对法则的表象行动的存在者属于理性存在者;
(3)定义二:根据对法则的表象行动的原因性就是纯粹理性的意志;
(4)结论一:“自然的至上原因”是一个有理性有意志的造物主,即上帝;
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发生率约14%[1]。近年来,我国GDM发病率明显增高,部分地区报道的发生率已达19.7%[2]。GDM产妇是糖尿病(DM)的高危人群,远期发生DM的风险明显增加[3-4]。GDM产妇产后进行血糖随访能够及时发现血糖异常,通过干预有效减少或减缓DM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但是,目前GDM产妇产后随访率普遍偏低,平均复查率<50%[5]。
(5)结论二:为了实现至善必须假设上帝存在。
这个证明也由两套论证构成:其中,(2)—(4)构成第一组论证,大前提(1)与第一组论证推出的结论(4)又构成一组论证,得出整个证明的结论(5)。
以碳酸盐为主的矿床主要包含钙质碳酸盐型矿床和镁质碳酸盐型矿床,一般矿物成分为方解石、石灰石和白云石等,同时还含有黏土矿物。这类矿床的地质成因一般为热液碳酸盐型、胶体沉积型和生物化学沉积碳酸盐型的矿床。在我国广西、湖南和广东三省碳酸盐岩地区,金属硫化物矿山经选别排出的尾矿分为四类:(1)方解石型尾矿, 如车河和黄沙坪选矿厂排出的尾矿 ;(2)白云石型尾矿, 如泗顶和古丹选矿厂排出的尾矿;(3)白云石-方解石混合型尾矿,如凡口选矿厂排出的尾矿;(4)铁白云石型尾矿, 如老厂选矿厂排出的尾矿[12]。
阿峰开着他的车来暹粒机场接我们,带着他的老婆和大女儿。这两天我的喉咙有些不舒服,他听出来了,经过一家药店的时候,把车停在路边,给我买了一盒润喉片。“这药很好,明天你的喉咙就会没事的。”他说。
该论证包含以下几个环节:
于是康德在命题(1)中提出,要解决该矛盾,就必须假设存在这样一种意志,它既是道德完善的,同时又是“至上的自然原因”,换言之,该意志不但完美地符合道德律,而且能够支配自然律,产生它想要的自然结果。接着根据(2)和(3)对理性和意志的定义,康德得出命题(4)中的结论:“自然的至上原因”是一个有理性、有意志的存在者;他按照对原则的表象(而非受感性冲动支配)行动,因此是位有人格的存在者——一位创世者,即上帝。所以康德得出结论说,只有上帝存在,一个合乎道德的自然世界,即至善,才可能想象,因为只有上帝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使自然律服从道德律,实现合乎道德的世界统一(圣经《诗篇》33:9)。
临床试验中,随着研究者对生物学、基因组学的了解愈发深入,更多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同样的疾病,因为患者之间存在的特征差异,药物疗效也不尽相同,特定的人群对某一个治疗有效,而另一特定人群对该治疗无效或比传统治疗效果差[1-2]。于是在获得了总体人群中的疗效后,研究者期待了解在不同特征人群中疗效是否和总体一致。这些不同的人群就是我们所说的亚组[3-4]。
这样,同样通过一个悖谬推理,康德从至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推论出一位人格神来。这是道德信仰学说的第二个论证,跟灵魂不朽论证一样,其中也存在许多困难。首先是人格神的观念。康德的上帝观与当时流行的自然神论不同,他指出这种区别在于,自然神论的上帝几乎等同于自然法则,不具有人格性,康德的上帝则是一位人格神:“自然神论者相信一个上帝,一神论者相信一个活着的上帝[summam Intelligentian(最高理智)]”[2]499。上帝是一个理性存在者,跟人一样,而不仅仅是某种世界秩序或规律,康德似乎认为这样的推论十分自然,然而在东方人看来,自然神论似乎更接近真理。牟宗三就批评康德的人格性上帝不过出于他的宗教成见[10],的确,如果只是要解决个人的德福一致问题,假设佛教那种“三世轮回”和“灵魂转世”观念足矣——同一人格在不同的肉身中存续,倒是能够真正实现德性与感性幸福之间的一致,也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
另外,“永恒中的幸福”也令人困惑。在大前提(1)中,康德强调至善是要“在现世中”实现的,但他随后又说,在“上帝之国”中所达到的德福一致,“与之(德性)成比例的福祉,即永福,却只是被表现为在永恒中才能达到的:因为……后者在现世中确实根本不可能以幸福的名义达到的(这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因此只能被当做希望的对象”[3]176。如今感性“幸福”被偷换成精神性的“永福”,至善概念也就悄悄变了味,从一个我们有义务在这个世界实现的实践概念,变成了一个永恒的超验国度。人死后如何能享受物质性的幸福?颇令人费解。如张传有指出的,德福一致只能是关乎现世的问题,即使灵魂不死,它也不再需要质料性的幸福,德福一致的问题也便取消了,除非康德相信基督教义中灵肉同时复活的观念。[11]然而在《形而上学讲义》中,康德明确否定了死后灵魂还有身体的假设。[12] 对于这个矛盾,伍德(Allen Wood)认为,鉴于我们对超验世界的无知,谁也无法从理论上断言,无肉体的灵魂就不能具有某种感性欲求,出于实践的兴趣我们可以假定之。[13]然而实践理性关心的是“造成和促进在现世中的至善”[3]172,死后的德福一致在道德层面上,可以说,并不那么重要。
康德的论证确实存在矛盾之处,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分别为了解决不同的问题:不朽是为了满足至善的第一个条件,即道德神圣性,而不是像投胎转世的肉体那样,提供一个承受幸福或灾祸的主体;上帝存在则为了保证德福之间的公正分配,但这种分配不以意志达到神圣性为前提,也就是说,上帝不但保证永福与神圣性相配,而且保证不同程度的德性享受相对应的幸福。归根到底,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这两个理念是要在一个“去魅的”自然世界中构建出道德的超验秩序,以便人们能够相信,好人遭殃、坏人享福这样的事只不过是表象。如果人能具有超出经验局限性的洞察力,就会发现在这些现象背后有上帝维系的公义秩序,所以道德失望是没必要的,只要人们一心行善,世界终将越来越接近至善——这才是康德煞费苦心想要证明的。因为,唯其相信,才能行动;唯相信至善可能,道德行动才合乎理性。
四、“道德信仰”还是“好人的信仰”?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至善”和“道德信仰”学说依赖于一种关于人类行动,或至少是道德行动的发生学说明。康德认为,理性存在者必然以其目的之可能性的信念为行动的发生学前提,追求不可能之事是违背理性的,荒谬的;目的之不可能性将挫败行为的动机,终致取消行为。同时,康德假设人类既无法认识,也无法促成其目的之实现,这样才有信仰的必要。有人也许会说,自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多矣,足见道德行动不必以其目的之可能性为前提。我们需要注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中的“不可为”并非逻辑上的不可能,如同“缘木求鱼”之类,只是成功的概率低之意;而康德认为,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至善的,没有一位上帝来维持世界秩序的公正良善,那么德性产生幸福这样的事就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如此道德行动就变成荒谬违背理性的了。
我们认为,人类行动的确以某些信念为出发点,无信念的行动是不存在的,但前两节已经指出,道德信仰论证中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很难说是成功的。即便我们承认道德论证能推出不朽和上帝,康德最后承认,这种信仰的确信性其实非常有限,成了只对个人有效的“私人信仰”,并且是有德之人才会选择的“好人的信仰”。这一节我们就检验一下,“道德信仰”的性质及其有效性如何。
2.1 古树名木的树种构成 王屋镇共有11科13属94株古树名木(表1),分别是豆科(槐属、皂荚属2种)、漆树科(黄连木属1种)、柏科(柏属、圆柏属2种)、壳斗科(栎属3种)、松科(松属1种)、榆科(朴树属1种)、胡桃科(胡桃属1种)、红豆杉科(红豆杉属1种)、七叶树科(七叶树属1种)、桑科(桑属1种)、银杏科(银杏属1种)。
1.2 主要仪器及试剂 PHOENIX-100型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美国BD公司),革兰氏阳性鉴定药敏复合板(美国BD公司);Cobas z 480 PCR扩增仪(瑞士罗氏公司);B100生物安全柜(济南鑫贝西公司);电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恒温金属浴仪(上海培清公司);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购买蛋白酶K、EX Taq聚合酶、琼脂糖凝胶、DL2000 DNA Marker,合成PCR引物序列。
所谓“信仰”,在康德看来,也是理性的一种认识状态,它介于有经验来源的客观“知识”与完全无根据的个人“意见”之间,是一种有理性根据但无经验验证的认识。之所以说它有根据,其根据就在于道德法则及其对象至善。康德说,“信仰是对道德法则的允诺的一种信赖”,此处的“允诺”即指至善——道德法则允诺了人类道德行动能实现至善,所以一切与此目的相关的东西也须信其为真。可见,真正被信仰的是道德法则和至善,或者说是实践理性,而非“来世”和“上帝”,后两者只是前者的理性推论。因此如康德多次强调的,道德信仰与正统启示信仰不同,不是信仰为道德奠基,相反,道德为信仰奠基。虽然他仍主张上帝为道德法则的立法者,但法则的权威,或者说人对法则的敬畏并非源于上帝的神圣性,反倒是纯粹理性的神圣性,人的尊严与价值也来源于此。“灵魂不朽”和“上帝”这类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形而上学对象,先是被“解构”,悬置了其本体的实在性,然后又被“建构”为“道德信仰”的对象。至善决定着灵魂和上帝的生死去留——如果没有它们至善同样可能的话,道德信仰就完全没必要了。所以“道德信仰”理论大大削弱了信仰的独立性和确定性。康德宣称,上帝与来世是“由我们所选择的”[3]199,虽然并非任意的选择,而是理性的必然选择。因为在康德思想中,信仰与道德同构:信仰根植于道德意向,“建立在道德意向的前提之上”[2]627,以至于有道德意向的人必然会有信仰。
但这又产生一个问题:信仰如若以道德为前提,那么只能是好人的专利。道德信仰实际上是种“好人的信仰”,只有好人会理性地选择信仰,坏人不尊重道德法则,也不关心实现至善,上帝若存在还要受到惩罚,那么为何要相信呢?不信对坏人来说更合乎理性。对此,康德也表示过忧虑,他承认:“如果你不关心首先使自己成为好人,至少是在成为好人的途中,那么你将永远不可能使你自己成为有诚实信仰的人。”[2]627不过康德相信,道德意向是某种先天的东西,根植于人格性的禀赋,除非一个人没有理性,否则不存在“道德上无所谓的人”[2]627,而正常人是不可能没有理性的。这样说来,“好人”并非指经验层面做了什么好事的人,一切理性人都是“好人”,都会选择道德信仰了。即便有人“由于缺乏善良的意向而与道德兴趣隔绝了”[2]627,康德辩称,理性也足以使他对上帝和来世心存畏惧,因为只要具备一点批判性思维,他就会明白自己至少无法证明这两者不存在。然而这种“消极的信念”[2]628显然并非道德信仰,只不过是奴性的他律。
第三、企业帮扶。县委、县政府积极动员全县效益好、实力较强的企业,帮扶2017年计划退出的贫困村及深度贫困村,鼓励企业依托自身优势,在劳动力转移就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扶持,以防止脱贫户返贫。
康德对理性先天就有道德能力这件事确信不疑,但是并未给予必要的说明。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承认人有这种道德禀赋,因而必然选择道德信仰,那么理性人对它到底有多确信呢?康德的回答不禁令人失望:“由于它是基于(道德意向的)主观根据,所以我甚至不能说:上帝存在等等,这是在道德上确定的;而只能说:我是在道德上确信的等等。”[2]627这样,道德信仰实际上是一种“私人信仰”,类似于私人语言,只对信仰者本人有效。这种信仰不能确定任何道德义务——道德义务唯独出于道德法则,甚至也不能确定宗教义务,除了道德的生活和意向以外道德信仰不要求任何东西,传统基督教认为重要的信仰实践(例如祷告)都变成多余的了。
不难发现,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信仰,对人的信仰,对理性的信仰。康德对待理性的立场在启蒙时代是比较独特的,一方面他批判那些独断地信任理性的启蒙哲学家,对思辨理性认识事物本身的能力表示怀疑和否定;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实践理性,认为只有它才能使人自由、有德性,并拥有真正的信仰。然而道德信仰理论表明,实践理性也并不那么自足,它需要信仰所提供的宇宙图景来支撑,而这种信仰所能达到的确定性却十分有限。“道德信仰”实则“好人的信仰”,甚至是只对我个人有效,不能用来要求其他任何人的“私人信仰”,这就是康德通过“道德论证”的悖谬推理得出的结论。
《纯粹理性批判》的B版序言宣称,批判哲学的重要任务是“从根子上铲除唯物论、宿命论、无神论、自由思想的不信、狂信和迷信”[2]25。不信被认为与狂信和迷信一样违背理性,唯一正确的信仰即“道德信仰”。然而这种道德化、理性化,同时也人化了的信仰,客观上推进了西方社会的世俗化浪潮,这本是“道德信仰”学说的逻辑所包含着的,却可能是康德始料未及的。
[参 考 文 献]
[1]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康德著作全集:第六卷[M].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SEESKIN K. Jewish Messianic Thoughts in an Age of Despair[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6]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杨云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6.
[7] 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M].任立,孟庆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68.
[8] BECK L W.A Commentary on Kant’ 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270.
[9] BEACH E A.The Postulate of Immortality in Kant: To What Extent Is It Culturally Conditioned? [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2008(4):501-502.
[10] 牟宗三.圆善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84.
[11] 张传有.对康德德福一致至善论的反思[M].道德与文明,2012 (3):80.
[12] KANT.Kant Lectures on Metaphysics[M]//AMERIKS K,NARAGON S , trans &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103, 282, 353.
[13] WOOD A W. Kant’s Moral Religion[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131-132.
“MoralBelief”or“GoodPeople’sBelief”?:TheParadoxicalReasoningandItsValidityofKant’sMoralBeliefTheory
Zhang Xiaoming
(DepartmentofPhilosophy,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Law,Chongqing401120,China)
Abstract:Kantian ethics began with moral law and ended with “Moral Belief”. He used religion to aid morality and morality to justify religion. In his “moral argument” on belief, Kant used the method of paradoxical reasoning, name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highest good would lead to the paradox of practice and deduced some objects of belief that guarante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ighest good. This “moral argument” has been criticized not only for its logical contradictions, but also for its disappointing conclusions. “Moral Belief” derived from “moral reasoning” is merely a byproduct of morality, which is privatized into pure personal choice or even “the belief of good people”. This did not prove belief, but contributed to unbelief instead, which might be probably contrary to Kan’ s original intention of “leaving a place for belief”.
KeyWords:moral belief;moral argument;paradoxical reasoning;harmony between morality and happiness
收稿日期:2019-07-18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S52)
作者简介:张晓明(1982- ),女,黑龙江富锦人,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教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9)05-0035-07
(责任编辑:张晓军)
标签:康德论文; 道德论文; 至善论文; 理性论文; 上帝论文;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S52)论文; 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