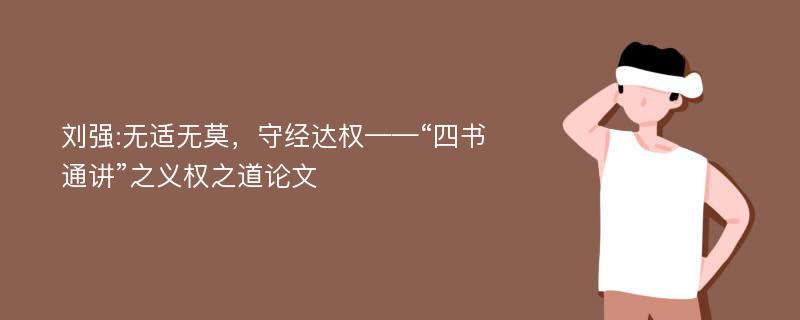
“四书通讲”(七)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许多人常将其概括为“仁义之道”。这无可厚非,但若细究起来,“仁”和“义”究竟并非一事。《易传》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显然以“仁义”与“阴阳”“刚柔”一样,皆为对立统一的 不同概念和范畴。所以,如果笼统地将“仁”“义”双称并举、等量齐观,自然有其约定俗成的道理,但也很容易造成对二者不同伦理特性和价值旨趣的遮蔽。“仁义”这一黏合度极高的词,其实有着某种不可“通约”的内在张力。而所谓“仁义之道”,也完全可以拆分为“仁道”和“义道”。“仁道”也即上一讲所揭示的“仁爱之道”,而“义道”的内涵,则可概括为“义权之道”。
“义者宜也”
就“义”字而言,要想明白其真义,必须先从字源学对其稍加追溯。“义”,正体字写作“義”,甲骨文已有此字。其义至少有四:
一曰“仪”。《说文解字》训“義”曰:“己之威仪也,从我羊。”“義”字从“我”,盖谓义出于己,由己决定;“義”字从“羊”,“羊”在“我”上,或与远古宗教祷祝仪式有关。段玉裁注:“義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从羊者,与美善同义。”这是对“义”的民俗学和伦理学解释。就此而言,“义”的行为也就是“美善”的行为。人有“义”心,正如人有“仁”心,皆可为“性善”论张本。
二曰“宜”。《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释名》也说:“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这个解释属于转注式的同音互训,与“仁者,人也”,道理相同。《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里的“义”就可解释为“宜”。
老道一边带着王祥去了古玩市场里各家大老板的店铺拜码头,一边给他讲解古玩市场里的一些小知识。比如古玩市场里的叶总从来不卖古董,但是无论权势还是资产都在这个圈子里首屈一指。比如专营古钱币的钱总身家百万,也是古董市场里的狠角色。不过据说钱总之前是千万富翁,就是踏入了古玩界,才把自己变成了百万富翁。再比如古玩界有“鬼打眼”一说,指的是“古玩界不打假”的行规。买卖了“打眼”货不但赔钱,还要丢人现眼。所以一旦“打眼”,发觉后事主会赶紧把事压下来,不再跟人提,否则被同行当笑料说出去,自己在这行就不好混了。这次,老道正是准备利用这一点去牟利,骗完人再让他吃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
三曰“我”。董仲舒《春秋繁路·仁义法》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这是把“义”放在人我关系中考量,以此彰显“义”的原则性和自洽性。
四曰“理”。孟子在谈到“心之所同然”时,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谓理也、义也。圣人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又,贾谊《新书·道德说》称:“义者,理也。”“义者,德之理也。”这里,“义”又与“理”同义。后世义理之学盖由此开出。
此外,“义”字还与“礼”“节”相近,如《论语·学而》有子的“以礼节之”;《礼记·礼运》:“义者,仁之节也。”同书《礼器》:“义理,礼之文也。”《乐记》:“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皆是。同时,“义”还可与《周易》“变易”之“易”相联系,含有“变通”之义。如焦循《孟子正义》在论及人性所以能善之原因时,就说:“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有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岂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①这说明,“仁”与“义”是相伴而行、相辅而成的。种种解读,颇多殊趣。
相比之下,“义者宜也”不仅更易理解,也更能揭示“义”的本质内涵。这一训诂,道出了“义”作为一种“应然性”价值,与“时中”和“权宜”等“或然性”价值的内在联系。因为“义”与“宜”通,故“不宜”之事便是“不义”之事。就此而言,“义”是一种较有弹性的价值判断和处事原则,与“仁”共同构成了儒家所认可的人性基础和道德理想。
“义”是“无可无不可”的智慧
不过,在更深广的意义上,“义”还代表着一种理性智慧。前面所引董仲舒的“反义为懵”,正说明一旦违反了“义”,人就会陷入昏昧懵懂,毫无智慧可言。在《论语》中,孔子对“义”的解读非常丰富,而其最终指向,则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智慧境界。因为“义者宜也”,故一切价值必须以“合义”为前提和基础。以下试就“义勇”“义信”“义礼”“义利”之关系稍做论析。
孔子目光如炬,对此类不合“义”的“小信”,一概斥之为“谅”。《论语》中两次提到“谅”。一次是在孔子回答子贡“桓公杀公子纠”,而管仲“不能死,又相之”的困惑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匹夫匹妇之为谅”,其实就是“小人之小信”。还有一次,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君子坚贞中正,但不固守于小信。
自然灾害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是指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现象。例如:火灾、地震、海啸、泥石流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突发状况有部分是可提前预知的,有部分为提前不可预知。旅游类志愿者在培训中也应该有所学习,在面临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时如何引导、解决与处理。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义以为上”,其实便是“尚义不尚勇”。也就是说,义勇之间,义在勇先,合乎义的勇才是值得提倡的,不合乎义的勇,非乱即盗。
(二)义信之辨。如我们所知,孔子十分推崇“信”的价值,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言忠信,行笃敬”的话,但他对于片面追求“信”的行为也有保留。我们一般都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是君子风度,但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却说: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这样的判断实在让今人大跌眼镜,“三观尽毁”。其实,《论语》中很多一时不能理解的道理,只要放在实践中来个“情景还原”,便可豁然开朗。据《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这个“孔子负盟”的故事说明,“信”如不合乎“义”,便是小人之信;而要挟之下订立的盟约,是为“要盟”——神且“不听”,何况人乎?此故事亦见于《孔子家语·困誓》,略有异文,孔子所说作:“要我以盟,非义也。”也就是说,“要盟”本不合“义”,若求“必信必果”,不是“硁硁然”之小人又是什么?孔子不听“要盟”,恰恰是合乎“义”的。
(一)义勇之辨。孔子虽然说过“勇者不惧”,但他对“勇”的价值认同,却是以“义”为前提的。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就是“义勇之辨”,成语“见义勇为”即由此出。见到合“义”的事而不去做,这是没有勇气的表现。换言之,不合“义”的事做得再多,也与“勇”无关,甚至有可能是“乱”。故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孔门中最好勇者莫过于子路,但孔子对他的批评也最多,诸如“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论语·述而》),“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等等。盖孔子以为,子路之“好勇”固然是一德性,然若不善加剪裁,则容易铤而走险,最终只能是“不得其死然”。子路后来的结局也印证了孔子的判断。有一次,子路向孔子请教:
5.独有的特异类宝石。昌乐不仅产出了世界公认的极品类型的蓝宝石,而且产出了大量珍贵的多彩蓝宝石,其中不乏国宝级珍品。如半为黄色半为蓝色的鸳鸯蓝宝石为世界独有,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另外,部分昌乐蓝宝石中含有奇特的包裹体,不少有奇异的活光效应,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精美图案。如“西天取经”“鱼探龙宫”“一帆风顺”均属世界罕见珍品,价值连城。
究竟什么是“谅”?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谅,则不择是非而必于信。”焦循说:“谅者,信而不通之谓。君子所以不谅者,非恶乎信,恶乎执也。”可见,信作为一种价值,必须合乎义。“言必信,行必果”之所以是“硁硁然小人哉”,就因为其最容易陷入“不择是非”“信而不通”的“执”与“谅”中不能自拔!这说明,在儒家看来,人世间一切正向的价值,都不是绝对的,都有一个合理的适用范围,都不应该成为束缚人的枷锁和牢笼!
(三)义礼之辨。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中,“礼”的地位和重要性自不待言,故孔子谈为政,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修身,则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主张“克己复礼”,要求“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又尝言“六言六蔽”,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又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可见,仁、智、信、直、勇、恭、慎等价值虽属美德,然一旦为人所“好”,皆难免存在偏失,唯“好学”方可救其蔽。值得注意的是,“好礼”“好义”则不在其列。不仅如此,孔子还赞美“富而好礼”者,又以“质直而好义”为“达者”(《论语·颜渊》)。何以如此呢?盖“好学”本身即含“好礼”“好义”之意,故“忠信如丘”易,“好古敏求”难,唯有通过“好学”,方能知礼达义。要言之,礼和义实乃节度与调适所有美德的砝码与权衡。而相比之下,“义”比“礼”更具灵活性,甚至“礼”亦必须合乎“义”。②如《论语·子罕》篇载:
比《世说新语》成书时间稍早,还有一些刘宋文献涉及“华亭鹤唳”或其相关故事,其中包括谢灵运名作《山居赋》。《山居赋》作于刘宋少帝至文帝两朝皇权更迭阶段,作者本人也恰因其背景、遭际与之前的人生抉择,置身湍急的政治涡流中。[注] 参见《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第1753—1772页。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说明,对于“礼”的追求如果过头,或“奢”或“泰”,都不为孔子所认可。孔子的“违礼”而“从众”也好,“违众”而“从礼”也好,都不是没有原则的首鼠两端,而是是非分明,都遵循了“义”的原则。
本系统主要由温度传感器模块模块、压力传感器模块、红外线传感器、超声波模块、液晶显示模块、人体感应模块、蜂鸣器模块以及STM32作为主控制板的系统装置,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野生动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维持生态环境稳定的重要一环,为了让野生动物更好的生存繁衍下去,不仅需要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同时,相关部门还要深入研究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不断完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建设,针对不同物种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以确保野生动物更好的生存发展。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10号矿体:该矿体是该区最大的矿体,呈扁豆体产出,在2线南—12线分布,总长为2 600 m,在4~8线出现,寒武系下面的岩层覆盖了4线的南部大多数矿体,黄土覆盖了8线的北部。该矿体厚度为5~302 m,平均为154.7 m,走向呈北北东方向,倾向南东,倾角为70°~80°。
这话乍一听似乎既无原则,更无立场,实则不然。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绝不仅是道德君子,还必须是智慧君子。这里的“义之与比”的“比”,即靠近义,与《学而篇》有子所言“信近于义”“恭近于礼”的“近”,实即一义。正如“忠恕”之间,孔子以“恕”为主,“礼义”之间,孔子则主张“义之与比”。“义之与比”是强调做任何事,都不能死守教条,不知变通,而是要“义以为上”,因时、因地、因人以制宜。只有这样,人的行为才是合乎“义”的,也是最具智慧的。
《论语·子罕》的下面一章尤为值得注意: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全新的航向。改革开放的征程没有穷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中国人民,高举旗帜,走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
数据均严格录入SPSS2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治疗有效率等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血压水平等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时,统计学有意义。
其实,孔子所反对的绝不是“信”和“果”,而是那个“必”字。任何事,一旦陷入“必”的状态中不能自拔,就一定会远离“义”的智慧。也就是说,“义”作为一种“应然性”价值,在与“时中”和“权宜”等“或然性”价值保持内在联系的同时,也与“必然性”价值划清了界限。换言之,“义”正是对治“必”的一剂良药。而“义”的本质便是“不必”。“不必”,也即“不执”。孔子的高足有若也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认为“信”只有接近于“义”的状态,诺言才可能兑现。
孟子深得孔子“义智”之真传,进一步提出了“惟义所在”的观点:
(四)“义之与比”。既然勇、信、礼这样的正面价值都有可能在实践上出现偏差,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做才算是“君子”呢?孔子在《论语·里仁》篇里给出了答案:
孟子的“舍生取义”,与孔子的“杀身成仁”遥相呼应,有效地将“义”的地位提升到了和“仁”并行不悖的重要地位,使其具备了“人的内在合理性”也即天赋“良知良能”的本质内涵。
很显然,这是从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之说演化而来。这里的“大人”即“君子仁人”,正与孔子所说的“小人”相对。孟子以“不必”来解释“义”,等于补充说明了孔子的言外之意。既然“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行径,那么大人君子该怎么做呢?难道要“言无信,行无果”吗?当然不是。一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完美回答了上述困惑和质疑。“不必”不是“无”,而是“不一定”“不必须”,正是对“必”的节制和超越。因为天下之事,一旦“必”了,就有可能陷入“不义”。而要想“义之与比”,就必须摆脱“必”的限制和束缚,让良知和道义真正获得选择和判断的自由。
(五)义利之辨。“义”的内涵中还包括如何处理与“利”的关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义利之辨”。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义利之辨。如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里其实已隐含着“义利之辨”,也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孔子并不排斥财利和富贵,不过财富显然也并非其真正“所好”。孔子“所好”者何?不过“义”字而已。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两次强调“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就是担心人一旦陷入对财富和物欲的追求,就有可能“绝仁弃义”。不仅如此,孔子还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切都以利为先,唯利是图,不仅心态失衡,怨天尤人,而且,也会招致他人更多的指责和埋怨。所以,在孔子那里,义利之辨也成了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最初是指地位阶层的差别,如郑玄就说:“贾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也说:“如郑氏说,则《论语》此章,盖为卿大夫之专利者而发,君子、小人以位言。”据此可知,孔子的本义并非赞美君子好义,批评小人好利,而是在做一个“应然性”的判断,即在上位的君子因不缺财利,故应当晓于仁义以化民;在下位的小人因为财利易被剥夺,故应当通晓获利之道。后来荀子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显然是从孔子的义利之辨而来。这说明,原始儒家的“义利观”其实是颇具“现代性”的。
在论及“仁”的价值时,孔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里的“志士仁人”,也可理解为“义士仁人”,因为能够“杀身成仁”,一定是长期“集义”的结果。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志”说:
如上所述,因为“义”的内涵十分丰富和灵活,也就使包括孝悌、忠恕、仁爱等伦理价值的儒学更具弹性和智慧。原始儒学固然重视伦理价值和道德境界,但也十分警惕道德的绝对化、极端化和教条化。换言之,真正的儒家,绝不赞同所谓“道德中心主义”。在世俗的政治生活和道德领域中,诸如仁、礼、孝、忠、信、智、勇等正面价值极容易被过分强调和推崇,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这就难免会造成理论和实践的偏颇和执迷。比如,对于孝道的过分强调,便极易堕入“愚孝”;对于仁爱的过分宣扬,常会导致“愚仁”;对于礼的教条化推崇,又可能导致“礼教杀人”;反过来,对于“利”的极端排拒,又会导致道德的虚伪和悬空。对此,儒学都有及时而又有力的矫正措施。这其中,“义”充当了“价值调节”或曰“道德减压”的安全阀和减速带,故而才有“仁义”“礼义”“孝义”“忠义”“信义”“勇义”等说法。也就是说,不管是多么高尚的道德,都必须合乎“义”。
一言以蔽之——“仁”是儒家的大慈悲,“义”是儒家的大智慧。
“义”是人的内在合理性
如果说,孔子对于“义”的阐发,更多指向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智慧,那么,孟子则赋予“义”一种更为刚性的价值内涵,成为君子安身立命的一种道德原则和行动纲领。在孔子那里,“义”与“仁”常常分开说,而在孟子这里,“仁”与“义”则如影随形,不可分割,成为“人性”中最为本原和内在的良知良能,也即所谓“天爵”:
孟子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
很显然,孟子是把“仁义忠信”当作上天赋予人类的“本质之性”的。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的“人性论”思想,有效地补充了孔子很少涉及的“性与天道”等本体论和形上学问题,尤其是孟子将“仁”和“义”都作为人性内在德性的原点,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比如,告子就认为“义”是外在于人的道德生命的,提出了“仁内义外”说: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孟子·告子上》)
这一段辩论十分精彩!告子以长、白立论,是站在客体角度看问题,孟子则以“长之”“白之”为说,则是从主体角度看问题。也就是说,敬长的行为看似是因为老者之年长,但敬长之心却是我们本心自具的。孟子“心学”的力量在此显露无遗。在讲“仁爱之道”时,我们提出了“仁”是人的本质规定性,那么同样可以说,“义”是人的内在合理性。“仁”是“情”之源,“义”是“理”之根,只有情理兼备,仁义具足,自然意义的人,方可成为社会、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人。儒学之所以是人学,正在于其义理上能圆融,逻辑上能自洽,实践上行得通。
孟子在论及“浩然之气”时,将其与“义”绾合,提出了“集义”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朱熹《集注》说:“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孟子的“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是说人的浩然之气是长期“集义”“事事皆合于义”的结果,不是“临时抱佛脚”式的一时的正义行为就可以养成的。此即所谓“从量变到质变”,没有“量变”,何来“质变”?王阳明的学生陆澄曾问道:“有人夜怕鬼者,奈何?”阳明回答说:“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乎神明,何怕之有!”④(《传习录》卷上)可见,“集义”乃是儒家修养的一种“工夫论”,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此章可谓“夫子四毋”。说孔子杜绝了常人都会犯的四种毛病,能够做到——不主观臆想,不武断绝对,不固执己见,不自我中心。这里的“意必固我”,相当于佛家所谓“我执”或“着相”。一个心胸狭隘、缺乏智慧、不知变通的人,难免会陷入这样那样的“我执”,囿于各种“名相”或“成见”,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君子。可以说,君子一生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要能够随时随地破除“我执”,摆落成见,执两用中,从善如流。如何破除“我执”?关键在于“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或,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糜、布侯之类。[13](P923)
因为孔子并不将义与利截然对立,故到了墨子,也就将义利等量齐观了。他说:“仁,体爱也。义,利也。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墨子·经上》)又说:“仁,爱也;义,利也。爱利, 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所利亦不相为外内。”(《墨子·经下》)所以应“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不过,正如熊十力先生批评墨子时所说的:“兼爱兼利,未尝不本于孔子之道。然言仁不酌以义,则仁道不可通也。……墨子非儒,殊不知其所非者,乃当时政俗之弊,正由儒者之道未行耳。”③墨子的这种“以利为义”的义利观显然不无流弊,儒家不得不起而矫正之,孟子就发现“以利为义”,会导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的后果,遂提出“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先义后利”的思想,其实也即《礼记·大学》所谓的“以义为利”。
桩基础是目前世界上应用非常广泛的深基础形式之一,对复杂地层、复杂荷载的适应性使其在未来具备更广阔的发展空间[1-3].对于预制桩基来说,动力或静力沉桩过程会引起周围土体变形,对临近建筑物、基础或地下建筑产生不利影响[4].如果对沉桩过程进行记录,会发现土体变形往往由桩-土界面开始,并通过土体颗粒的平动、转动和错动向外部扩散,最终形成周围土体中位移场与应力场的变化.因此,深入研究桩周土体变形发展有助于掌握沉桩挤土的基本机理,达到对沉桩不利影响进行预测和防治的目的.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将此章和上引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曰“义以为上”合起来看,则可发现,孟子的“尚志”,其实是对孔子“义以为上”的再次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志士仁人”一定是能行“仁义之道”也即“居仁由义”的有志之士、大人君子!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孟子的“人禽之辨”,固然以“仁者人也”为原点,但“义者宜也”,同样起到了奠基作用。正是经由孟子,“仁义之道”的结构性基础和本源性价值才真正得以开显和完善。
经权之道,唯义所在
如上所述,“义”是人的内在合理性,但这种内在合理性,仅是就人类的共性而言,具体到每一个个体或者曰“我”的外在行为,“义”也有可能被教条化(所谓“天经地义”),以至走向它的反面。这就必须有一更具智慧性和自由度的“杠杆”予以调节和变通。于是“义道”之外,还须辅以“权智”。这就涉及儒家的“经权之道”了。
我国作为东亚最大的沿海国家且作为《1979年搜救公约》的缔约国,参与海上救助活动自然也是十分频繁。面对搜救国协调权间竞合及冲突的状况,我国必须要明确自身应对权利冲突下的调和方式,以保障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海上救助合作的顺利开展,及时救助海上遇险人员。[10]
“权”的重要性,早为孔子所发现。《论语·子罕篇》载: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孔子将为学的境界分成四个阶段,即“共学”“适道”“与立”“与权”。四者之中,“与权”最为难至。权,本义为秤锤,“权然后知轻重”;这里引申为“权变”。孔子虽然没有提到“经”,但事实上已将隐含着“经权之辨”。“与立”其实就相当于“经”。经者,常也;权者,变也。
真正揭橥经权之道的是孟子。他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孟子·梁惠王上》)在辟杨、墨时,孟子先肯定子莫的“执中”,紧接着却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这里的“执中无权”,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可与立,不可与权”。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了“反经”的说法:“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反经”的“反”,应该理解为“反者道之动”的“反”;“反经”,不是死守经典,而是通达权变。在《孟子·离娄上》中,关于“嫂溺”的一段辩论尤为精彩: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这个故事涉及“礼权关系”,其实就是“经权之辨”。如“男女授受不亲”是“经”,则“嫂溺援之以手”,便是“权”;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经”,则舜的“不告而娶”便是“权”。孟子所谓的“权”,即权变、权宜、变通,其实就是孔子所谓“义之与比”,“无适也,无莫也”,以及“无可无不可”。“权”与“经”相反而相成,故权者,必反乎经者也。反经合道方为“权”。程子甚至认为:“权即是经也。”可见,守经达权乃是为学的最高境界。
综上言之,儒家的“仁义之道”其实是本末一体、并行不悖的。如果说“仁爱之道”是“本体”,那么“义权之道”就是“工夫”,二者缺一不可。就经权关系而言,“仁”即是“经”,“义”则为“权”。“仁”的扩充光大,直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义”的反经达权,又可使“万物周流而无碍”。一切正向价值,皆须合乎“义”;一切常道法则,亦当达乎“权”。质言之,权者,义也;义者,权也。呜呼!义权之道,于是乎颠扑不破矣。
①焦循:《孟子正义》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34页。
②刘强:《论语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04—105页。
③熊十力:《原儒》,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29页。
抗性淀粉是一类性质并非完全相同的碳水化合物,其抗酶解性质与淀粉的品种、来源、储存方式及食品加工过程有关。目前研究最热门的是RS3,为凝沉的淀粉聚合物。其主要由糊化淀粉经冷却后形成,为凝沉的直链淀粉[4]。
④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作 者: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竹林七贤》《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论语新识》《古诗写意》《世说三昧》《穿越古典》等著作十余种。
编 辑:得一 312176326@qq.com
标签:孔子论文; 孟子论文; 论语论文; 君子论文; 之道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名作欣赏》2019年第19期论文;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