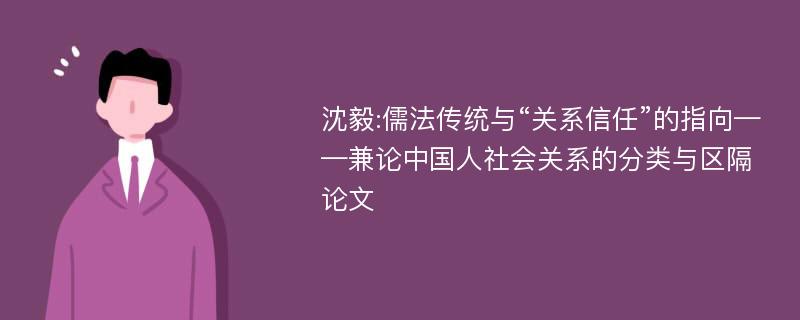
[内容提要]儒家伦理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特殊主义的差序式“关系信任”的根源。如果从更宽泛的文化传统来看,儒家伦理始终具有“推己及人”的社会信任建构作用,而法家功利主义传统则对某种缺乏信任的人际关系建构起到了核心作用。“大传统”的儒法张力反映在“小传统”的人际交往实践中,分别形成了附着于儒家伦理的以紧密性“情义”嵌入及“关系信任”为核心指向的“深度感情关系”,以及在法家思维作用下生成的某种缺乏信任而以纯粹利益为导向的“功利交换关系”。此外,现阶段互动较少而曾经单向受恩的“恩义负欠关系”与双向弱嵌入的“普通人缘关系”,则受到儒家伦理与道家思维的潜在作用。以深度人伦嵌入的“关系信任”为核心基础的“关系共同体”,对中国市场经济之中民营企业的充分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应该是儒家伦理在当今社会的生命力之所在。
[关键词] 关系信任 儒家伦理 法家思维 深度感情关系 功利交换关系
一、“关系信任”:从特殊主义文化到儒法传统区隔
信任问题是关乎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中心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在韦伯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普遍主义的商业信任及社会信任,新教伦理在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韦伯进行文化伦理分析的重要切入点。在此基础之上,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重新审视了15世纪—18世纪西方基督教民族的历史,特别论证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缘于“信任品性”的生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社会”是欧洲形成原生型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石(佩雷菲特,2016[1998])。与之相对照,自韦伯(2010)的《儒教与道教》开始,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特殊主义信任问题就已被正式提出,中国社会难以自发生成资本主义的根源可能在于中国式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问题。在此基础之上,福山认为中国社会在文化上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其理由是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恰恰造成了一般陌生人交往中的不信任(Fukuyama,1995:69-82)。这种普遍主义/特殊主义视角的分析,本质上是将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归结为某种德性信任的文化问题,从而构成了上述韦伯命题的核心。
在文化视角以外,卢曼的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的分析架构则在制度层面明晰了传统人际信任与现代制度信任的功能差别(卢曼,2005[1973])。应该说,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系统化制度共同促成了普遍主义信任的生成,在根本上成为保障西方原生型资本主义科技创新及经济腾飞的实质基础。与之相比,人际信任似乎成了对儒家文化圈的基本判定,同时其对中国式后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如雷丁对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即是旨在揭示个人关系及人际信任在海外华人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dding,1990)。对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本质上也正如金耀基(1983)等人所开始关注的儒家伦理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样的命题恰恰构成了韦伯命题的反命题。需要强调的是,雷丁虽然认为家族体系及个人关系网络提供了彼此合作的信任基础,但同样承认在关系网络之外始终是制度信任缺失的普遍不信任及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氛围(Redding,1990:83)。可见,福山-韦伯等人与雷丁-金耀基等人之间对华人特殊主义人际信任的基本判断是一致的,只是对这种特殊主义人际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持有不同的基本立场。
某种程度上,以雷丁等人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本质上正凸现了儒家伦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作用,但儒家伦理的实质立足点无疑还是在于家族亲属及朋友至交的紧密性人际关系。翟学伟曾经将此种核心性的人际信任命名为“关系信任”,他从个体交往的角度出发,认为“关系信任”是指“个体通过其可以延伸得到的社会网络来获得他人提供的信息、情感和帮助,以达到符合自己期望或满意的结果的那些态度或行为倾向”。“同关系信任相对应的机制则是信用制度的设立。应该说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强调的是前者,而西方社会更强调后者。”(翟学伟,2003)可见,“关系信任”的概念本质上恰恰是与“制度信任”相对应的“人际信任”,儒家价值理念的人伦“情义”构成了这种“关系信任”的实质性基础。由此,本文始终认为不适宜将“关系信任”理解为统摄中国人各种亲疏关系类型的泛化范畴(如陈云龙,2017),而是将其作为与“制度信任”相对立的“人际信任”来加以理解,其内核指向核心性紧密特殊主义关系中的“人际信任”,这无疑是中国式“关系本位”(梁漱溟,1987[1949])社会运行的核心特征之一。
事实上,翟学伟(2003)在对“关系信任”的研究中进一步提炼了“强信任”与“弱信任”的区隔,并说明中国式“强信任/弱信任”的信任程度差异并不同于“强连带/弱连带”(Granovetter[格兰诺维特],1973)的互动频率分隔,“关系信任”根本上应指向义务性关系嵌入程度较高的“强信任”。我们可以认为,“强信任”的“关系信任”除了某种空间的同质性而外,本质上还是嵌入人伦“情义”的差序网络之中,亦即是以某种“强情义”的私人“人伦”关系作为基础的。由此,这种以私人“人伦”关系为核心的“人际信任”或“关系信任”的积极抑或消极面相,构成了雷丁-金耀基与福山-韦伯等人两种不同观点所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儒家伦理的分析与评判之中,而对儒家伦理积极抑或消极作用的哲学及伦理学争鸣,往往聚焦于儒家伦理是特殊主义抑或普遍主义的“公”与“私”之争,其所讨论的儒家伦理中的“亲亲相隐”问题常常不是仅限于经济发展,而且指向整体社会秩序的公共规则。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批判儒家伦理的主要健将之一邓晓芒的整体立场,比较接近于社会学的特殊主义视角,即认为中国人的私人关系及儒家伦理对公共秩序及制度规则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私”对“公”的侵蚀是儒家伦理的一大弊端,特别是其对“亲亲相隐”问题的批判构成了其对儒家伦理批判的核心(邓晓芒,2010)。“亲亲相隐”的问题,费孝通在“差序格局”论述中也有所提及,他同样倾向于认为伸缩自如的儒家伦理暗含着中国人因“私”废“公”的面相(费孝通,1985[1947])。邓晓芒关于儒家伦理中“亲亲相隐”的基本观点与费孝通对中国人“私我”的论断是比较接近的,实质上也就回到了儒家伦理是特殊主义信任的基本命题:儒家“人伦”特殊主义之“私”对社会整体普遍主义之“公”构成了一定的侵害,亦即特殊主义的私人关系常常会对普遍主义的公共规则构成相当的侵蚀。
然而,在研习中国传统哲学的一批学者看来,这样的基本论断无疑是对儒家伦理的亵渎。如郭齐勇及其学生等人极力反对邓晓芒的观点,力图证明西方文明同样有“亲亲相隐”的社会伦理,在此基础上希望为中华儒家伦理的普遍主义性质正名(郭齐勇[主编],2011)。这样的哲学与伦理争辩始终是在文本层面上的争论,仅就伦理预设而言,儒家伦理的确指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断外推的社会目标,以至于某些儒家士大夫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理念,这样的文化理念蕴含着某种“由私及公”的“大同”式普遍主义价值取向。但是在中国社会中,一旦涉及核心性利益攸关的事件或情境,亲疏远近的“自己人/外人”的分隔始终还是根本性的,私人关系对组织制度及规则的破坏往往是常态。值得注意的是,“亲亲相隐”的法制问题,本身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法制与公共规则的问题,而在诸如民营企业的市场化组织中尽管同样存在着“自己人/外人”之类“亲亲相护”的组织绩效问题,但其中的主要面相一般并不涉及“亲亲相隐”的社会法制问题。
以上纠结于儒家伦理及其实践后果的争论,其实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文化传统中,难道只有儒家伦理在起作用吗?在儒家伦理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时,“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法家式价值观乃至行为实践自古至今始终存在,法家极端利己而不惜牺牲他人乃至所有人的“自我主义”通过传统官僚政治渗透于社会机理之中。①可以认为,某种不惜牺牲他人的“自我主义”的行为模式本身就暗含着法家功利主义的基本价值观,特别是其牺牲家人乃至“大义灭亲”的极端行为显然与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相悖。在政治权力主导的官僚场域之中,不择手段的“小人”往往能战胜“温良恭俭让”的“君子”,法家牺牲他人型的极端利己式“自我主义”往往会战胜儒家伦理的利他主义。在这样的儒法张力之下,多数个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常常趋于持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道家消极立场,某种“明哲保身”的杨朱式“自我主义”往往是应对法家功利主义及其权势威胁的必然选择,其最终也必将共同解构儒家式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大同理想。
由此,本文认为,儒法传统之间的张力不仅是长期以来传统中国政治体系与制度实践的内在矛盾,实质上也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与“人心”伦理的深层问题,在关于人性善恶的儒法价值的交错作用之下,普通人往往对外部社会形成可信任与不可信任两种类型他人的社会认知。在这个意义上,秋风曾提出儒法传统与信任重建的重要命题,力图凸显儒法文化传统的不同人性预设及其价值观,希望能在批判法家功利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对儒家仁义传统及其对社会信任建构的正面价值给予充分肯定(秋风,2013)。然而在现实中,儒家所倡导的诚信伦理在法家功利主义传统的冲击之下,多数个体可能还是趋于信任小范围边界内的“自己人”或“自家人”,对亲缘及拟亲缘关系的认同与信任成为某种以直系血缘及铁哥们朋友为核心的“小我主义”,亦即儒家伦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由带有普遍主义意涵之“仁”到特殊主义意涵之“义”的转向。要言之,儒家伦理本身虽然具有倡导“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积极面相,但在法家功利主义传统的冲击与道家自保传统的作用之下,某种小群体内部关系义务嵌入“抱团”的“小我主义”行为模式始终是常态。
应该说,中国人这种特殊主义或者说“小我主义”的“关系信任”虽然造成了外部公共规则与社会整体秩序的明显问题,但始终为私人性的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其内在地蕴藏着某种儒法文化传统的深层关联。如上所述,雷丁在对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研究中,曾指明特殊主义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是以儒家家族伦理作为核心基础的,与此同时,企业家往往对外部社会尤其是政府官员充满不信任。也正是海外华人企业家对外部社会及其法律系统的不信任态度,加剧了其家长制及私人关系网络内部“抱团”整合的必要性,这可能成为儒家伦理特殊主义信任得以强化的结构性动因(Redding,1990:115-142)。如果我们进一步细究则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不信任或者缺乏信任有时并不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完全消解,如雷丁上述的某些海外华人企业家虽然常常对外部社会乃至政府法制相当不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家不与各级政府特别是政府官员发生私人“关系”,甚至于某种在法家思维指引下的缺乏深度信任而以纯粹利益导向的政企私人“关系”的构建,是某些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就普通人而言,多数个体可能会在陌生人交往领域趋于封闭而走向某种小团体乡土型社会关系的“小我主义”,而一些活跃个体却可能不断突破自身交往的封闭性,致力于各种有明显工具性资源作用的“关系学”实践,以融入相关资源密集型的“关系网络”。血缘、地缘、姻缘、业缘、学缘等既有关系基础虽然在这种“关系学”建构与拓展中也可能发挥作用,但其导向往往不是根据“人伦”式的既有关系基础加以定位,而更多的是根据现实利益需求来进行调整互动。可以说,传统官僚场域中某种具有法家功利主义特征,更为直接明确的“关系学”实践与乡土社会中更具有“人情味”的儒家“人伦”关系的差别似乎是比较明显的。由此,“关系信任”也不仅仅是特殊主义文化的信任程度差异问题,其本质上还需要在中国人不同性质的“关系”类型差异中加以定位,亦即需要在对“差序格局”人伦边界问题及其“关系”分类的深入探讨之中分析中国人“关系信任”的具体指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中国人在不同情境下的社会关系建构与儒法文化传统的深层勾连。
二、既有的“关系”分类研究及其“关系信任”脉络
在已有的“关系”分类研究中,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始终是一个经典分类。黄光国综合已有的“人情”与“关系”研究,借鉴西方社会心理学中“情感性关系”及“工具性关系”的人际关系分类法,将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区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及“混合性关系”三种类型。在黄光国看来,以陌生人为主的“工具性关系”属于“合则来,不合则去”的一次性关系,彼此遵循“公平法则”的资源交换常常是即时实现的,并不存在长期的施报关系。“情感性关系”与“混合性关系”则属于长期的交往关系,均遵循中国人“报”的行为规范。以家人为主的“情感性关系”中的回报,遵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并不计较其所付出资源的代价。而在“混合性关系”的“熟人”关系之中,交往双方则往往遵循“礼尚往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交换性“人情法则”。在“混合性关系”的“人情法则”之中,资源支配者面对相应关系人的具体请托,常常将其所要付出的代价与对方的预期回报作比较,并根据对方的权力大小及关系背景来权衡轻重,最终决定是否给对方“做人情”,这种对当下代价与预期回报的权衡考量使资源支配者常常陷入“人情困境”当中(黄光国,1988a)。
杨中芳(1999)、杨宜音(1999)等人认为,在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中,情感性成分与工具性成分是一个维度的两端,“情感性关系——混和性关系——工具性关系”的划分可以类比杨国枢(1993)关于“家人——熟人——生人”的分类方式,可视作对“差序格局”的一种简化的解读方式。在人际信任及人际情感的理论架构中,杨中芳(Yang,2000)及杨宜音(2000)进一步突出了“义务”在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进而将“情感”区分为义务上的应有之情(“人情”)与内心的真有之情(“感情”),并就这两个维度相交叉的结果区分出了四种“关系”类型:高应有之情与高真有之情的“自己人关系”(亲人、铁哥们),低应有之情与高真有之情的“交往性自己人”的“友情关系”(挚友),高应有之情与低真有之情的“身份性自己人”的“恩情或交情关系”(恩人、合伙人),低应有之情与低真有之情的陌生人的“外人”式“市场交易关系”。总体来看,“自己人/外人”的信任发展理论强调了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情境性与变动性,其中以自发性“感情”要素为主导的“交往性自己人”通常还是要比以义务性“人情”要素为主导的“身份性自己人”更值得信任与依赖,亦即其理论建构中的“情感”要素似乎还是要优先于“义务”要素。②
与之对照,笔者在已有的对上述“差序格局”及“关系”分类的梳理分析中曾经指出,在“情”“义”“利”三个关系要素之间,中国人社会关系中的“情感”与“义务”常常是融为一体的“情义”嵌入,将“情”融于其中而趋于人伦利他的“义”才是构成“差序格局”的核心性要素,“义”“利”紧张与交融的相生相克构成了人伦关系的要核(沈毅,2007)。在某种程度上,义务性嵌入的程度常常也预示着利益层面的可信任程度,亦即双向的义务性嵌入程度或者说“情义”深浅本身就意味着相对于对方的可信任度。当然,交往双方的义务性嵌入程度并不一定完全对等,这也就意味着彼此就对方的可信任度往往有不尽相同的判断或排序,但总体上还是有比较类似的区间定位。“家人”一般意味着“放心关系”;有一定义务嵌入的“熟人”之间则构成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关系”;而在此之外的“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交往本质上是缺乏信任的,甚而可以称之为“无信任关系”(翟学伟,2014)。就陌生人的“无信任关系”而言,杨宜音(1995)较早时曾经批评了黄光国关于“工具性关系”的“公平法则”的判断,指出中国社会陌生人交往及市场交易中坑蒙拐骗的大量存在,使得普遍信任式的“公平法则”无法成立,这样的批评解释了私人关系与特殊主义信任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如果放到人际信任的“关系信任”的脉络中来看,翟学伟(2014)对中国人信任关系由内而外所作的分类,即“放心关系”“信任关系”及“无信任关系”,恰恰可以分别对应于黄光国及杨国枢所做的“情感性关系/家人”“混合性关系/熟人”及“工具性关系/生人”的关系分类。事实上,以“家人”为中心的“放心关系”无疑是高信任度的社会关系,这似乎可以类比日本学者山岸俊男提出的封闭性组织或网络所形成的“保证关系”(committed relationship)(Yamagishi&Yamagishi,1994)。③然而,与日本式集体主义文化不同,既有的对中国人社会关系的研究,往往更关注私人关系与人际信任的彼此对应性,亦即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家人”及“熟人”的范畴及其信任程度的差异上。这样,在“差序格局”的人伦性社会关系范畴之中,人际关系由内而外的亲疏远近,也就意味着彼此“情义”嵌入程度亦即信任程度由深至浅的逐步弱化,直至对“陌生人”缺乏信任,从而构成了“放心关系”“信任关系”“无信任关系”的差序性连续统。
由此,“家人”与“熟人”的区隔,似乎还可以用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的“强连带/弱连带”来对应分析,其内在的核心意涵可归之为由中国式的关系基础及后续交往所形成的信任程度的实质差别。与个人主义式社会关系的差别可能在于:中国式人伦关系的人际信任与人际情感常常是其交往的一体两面,即相互之间涉及工具性资源给予与交换的人际信任本身取决于彼此“感情”的“情义”嵌入程度,人伦性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是“情义”与“利益”交织发展的结果;而个人主义式关系的一般信任常常并不与彼此交往的程度有深度关联,个人主义式关系所蕴含的普遍主义道德标准显然不同于特殊主义“私德”的私人“情义”。正是这种社会信任与人际关系的相对分离,使得个人主义式“工具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的边界是相对清晰的。因此,个人主义式人际关系“强连带/弱连带”的要旨应该不在于格兰诺维特所关注的“镶嵌”式信任问题,其核心应当指向某种个人主义情感的强弱差别,亦即个人主义式社会关系的“强连带”应该可以对之于“亲密关系”的“情感性关系”,“弱连带”则可以主要对之于诸如商业及职业交往中“公平法则”导向的“工具性关系”④(沈毅,2013)。
如上所述,黄光国(1988a)用“混合性关系”来指称中国人熟人式的“人情关系”,这种“熟人”关系常常是长期性交往而非短暂性的,同时在本质上是特殊性(particularistic)和个人化的(personal),其关系交往常常需要遵循互惠式的“人情法则”。“混合性关系”应该是黄光国所作“关系”分类的最主要贡献,但随之则存在深化分析的困难。不同的二元分析维度均可构成其中间性“混合性关系”的提法,特别是“混合性关系”的模糊称谓恰恰忽略了其中的“关系”性质差别,亦即“熟人”关系内部可能存在不同性质的“关系”分类。如前述杨中芳、杨宜音等人从情感/义务的二维分析出发,本质上是将“混合性关系”再分为低应有之情与高真有之情的“友情关系”(“交往性自己人”),高应有之情与低真有之情的“恩情或交情关系”(“身份性自己人”)。这种“交往性自己人”与“身份性自己人”的区分,可以视为某种对“混合性关系”进行细化分析的努力。
三、“情义”与“利益”:“关系”类型的再定位
然而,吊诡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在社会互动层面所呈现出的“强连带/弱连带”是否必然同时意味着“强信任/弱信任”的差别呢?换言之,“家人”“熟人”“生人”这样简化的关系分类,是否足以说明人际互动频率的高低也就意味着人际信任程度的深浅?无疑,多数中国人在核心性的“家人”亲属及朋友至交范畴之中,行为取向更多还是“关系本位”或“伦理本位”(梁漱溟,1987[1949]),儒家人伦关系范畴中的“情义”与“信任”常常是其主要面相。然而在此之外,法家功利主义传统所指引的某种社会关系运作,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在儒家人伦范畴之外的,或者说在某种纯粹利益指引下的社会关系运作常常缺乏人伦义务的深度信任,并且这种功利导向的社会关系在某些时段内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交往互动频率相当之高的“强连带”。这样的交往互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彼此的利益需求程度,其内心却可能充斥着负向的情感以及不信任。由此,“情义”主导的内在义务信任程度与工具利益驱动的外在当下互动频率的彼此分隔,将为我们重新认识“混合性关系”乃至中国人社会关系的细化分类提供一种“情义”/“利益”二维的分析视角,这应该对深化理解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多重面相及内在关联大有裨益。
基于此,我认为小亮的主要问题有懒散、自控力差、缺乏明确的追求目标三方面。明确的追求目标是核心,因为人一旦有了明确的追求目标就会变得勤奋、自律。鉴于此,帮助小亮找到明确的追求目标,成了我教育转化小亮的首要工作。
经深加工后,每年的金花茶叶可加工成金花茶浓缩液0.3 t/hm2,按98.0万元/t计,折款29.4万元/hm2;金花茶年产鲜花可加工成干花茶450 kg,按干花1.2万元计,折款540.0万元/hm2。
进言之,在黄光国、杨国枢等人关于“情感性关系/家人”“混合性关系/熟人”“工具性关系/生人”的分类范畴之中,其所界定的“工具性关系”或“生人”关系一般是缺乏信任的一次性交往关系,通常并不作为中国人社会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在“情感性关系”的“家人”关系之外,“混合性关系”亦即“熟人”关系的指称就显得过于笼统,只有进一步推动对“混合性关系”内部差别的细化研究,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深化理解中国人“关系”实践的具体内容。在既有的一些研究中,已有学者将格兰诺维特的“强连带/弱连带”的分析框架引入黄光国的关系分类之中,进而将“混合性关系”区分为“次强关系”与“次弱关系”,但又将两者重新归为某种“中间性关系”(汪和建,2003)。这样的细化区分与重新命名本质上并没有突破“混合性关系”的基本意涵,只是关注到了其中存在的关系交往或信任程度方面的差别,始终还是相对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关系”分化。
事实上,对中国式社会关系的“强连带”与“弱连带”的区分比较困难,特别是外在的社会互动频率与真实的内在情感及人际信任并不一致。在交往频率较低的社会关系之中,大多是利益联结与情感互动较少的“普通人缘关系”,这样的“普通人缘关系”才是“弱连带”意义上的“熟人”关系,亦即一些互动较少的亲属、同事、同学、同乡、战友等普通熟人,往往由某些目前或曾经归属的组织群体或社会网络而联结,其互动更多地遵循工具性资源“人情”互惠的礼尚往来以及象征性资源“面子”互惠的形式主义规则,彼此之间的工具互助需求、“情义”交往嵌入及相互信任程度都是相对较弱的。在此基础之上,“普通人缘关系”以至于陌生人之间,如一方受到了非常重要的实质性帮助而又不能及时回报,则可能形成某种有所亏欠的“恩义负欠关系”。“恩义负欠关系”本质上是施恩者对受恩者超越先赋性的角色义务而给予了非常重要或及时的帮助,从而构成的对受恩者而言的单向负欠关系。理想型意义上的“恩义负欠关系”对于受恩者而言,更多地指向过去的“恩义”之情而通常已没有未来的“利益”需求了,同时双方甚或因为交往空间分隔及利益交集较少等原因而互动频率较低,这就有可能对受恩者而言构成某种长期负债式的“人情债”。即便如此,一旦施恩者提出某种具体请托,无论受恩者对其是具有积极回报的真实感情也好,还是不得不回报的“人情债”也罢,其“情义”嵌入的深度往往决定了受恩者一般将尽力给予施恩者适当的回报或补偿,因此施恩者对于受恩者未来的还报通常持有单向长期储存式的信任。
与之相对照,在交往频率较高的社会关系之中,则可以细分为更重视“情义”而彼此互助的“深度感情关系”与主要是工具利益导向的“功利交换关系”。“深度感情关系”常常是相互“信任”或“情义”相投的核心家人、直系亲属及朋友至交关系,这样的“朋友”往往是铁哥们、铁姐妹乃至于一生相交的“发小”,彼此的“情义”嵌入、信任程度及其关键时刻的工具性资源互助往往是拟家人的。这是传统乡土社会对中国人社会关系的主要影响,这种“义”“利”交融的“深度感情关系”始终是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核心领域(Yan,1996;Kipnis,1997;杨宜音,1999;沈毅,2007)。本文所要特别强调的是,交往频率较高的社会关系之中还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缺乏实质“情义”嵌入而主要是工具利益导向的“功利交换关系”,它往往指向资源支配者的“权力”地位所展开的“关系学”实践及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的较长期的依附性利益交换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互动频率较高的“功利交换关系”的建构与发展往往基于对未来有较为明确的预期利益诉求,却未必有真正与之相对应的以往“情义”伦理嵌入及人际信任,甚至在某些情境中有可能出现负向的情感与一定的不信任。但是,由于利益交换的需要特别是权力依附性的利益需求,这种负向情感与不信任有可能会被隐藏起来而进一步展开密切的阶段性乃至较长期交往。由此,以行为层面现阶段深度互动频率的高低为一个维度,以心理层面内在“情义”伦理的以往义务嵌入程度的深浅为另一个维度,我们可以考虑将中国人常规化的社会关系细化为四种“关系”形态(见表1)。
事实上,“功利交换关系”常常源生于对各类公共组织(也包括商业组织)职权的利益依附,交往双方之间往往会形成某种“公”“私”利益的输送与交换。同时,“功利交换关系”虽然在当下乃至未来某个阶段的互动频率较高,却有可能是一种双向缺乏信任而互相提防的社会关系,在极端意义上也会形成某种权力控制的“强制关系”(刘军等,2013)。然而,“功利交换关系”的一般范畴应该比“强制关系”的指涉更为宽泛,弱者在其中通常仍旧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或主动性。进言之,多数弱者是为了利益需求而主动向掌握资源支配权的强者运用“关系学”乃至“潜规则”的种种策略,进而建构及强化权力依附式的“功利交换关系”。由此,“强制关系”无疑属于“功利交换关系”的极端形式,但“功利交换关系”的一般范畴应该是面向权力或资源支配者且具有主动依附性而非被动支配性的关系形态。当然,所谓“上船容易下船难”,“功利交换关系”一旦启动乃至深度嵌入发展,相对的自主性就会逐步丧失,有可能随着单向或双向控制程度的加强,发展为某种深度权力控制的“强制关系”。
2.1 本组检查中1类(阴性)共1392例,占74.4%;2类(良性表现或行为)共332例,占17.7%,3类(可能良性)共103例,占5.5%,4类(可疑肺癌,其中又分4A、4B、4X类)共45例,占2.4%。
表1:“情义”与“利益”两个维度交叉的“关系”类型
当下至未来以往至当下既有“情义”伦理嵌入深(基于重要恩惠受施而心理认同程度高)既有“情义”伦理嵌入浅(缺乏重要恩惠受施而心理认同程度低)未来利益需求预期可明确(现阶段行为层面深度互动频率高)深度感情关系(核心家人、铁哥们)(双向长期互惠的深度“关系信任”)功利交换关系(关系学、潜规则)(纯粹利益交换,双向缺乏信任)未来利益需求预期不明确(现阶段行为层面深度互动频率低)恩义负欠关系(恩情、人情债)(施恩方对受恩方回报的长远信任)普通人缘关系(一般亲属、同乡、同事、同学、战友等熟人关系)(日常交往的双向一般信任)
进言之,“功利交换关系”的建立与维系需要“袭”“认”“拉”“钻”“套”“联”等“关系学”策略,包括“套近乎”、请客送礼、找中间人“拉关系”乃至于“认干亲”等诸多钻营策略(乔健,1982:348-350),其中某些缺乏底线的互动模式亦即官场盛行的“厚黑学”(李宗吾,1989)或“潜规则”(吴思,2002)。应该看到,这类“功利交换关系”较为直接而可预期的功利性动机常常是比较明显的,一旦没有了未来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当资源支配者无法掌控资源而失去了交换“价值”,这种“功利交换关系”大多也就随之终止了。进言之,在一定时段之内,“功利交换关系”的交往频率可能相当高,逢年过节请客、送礼的“拉关系”情感策略通常并不能改变双方对这种“关系”交往的基本判定乃至时间预期,即其所交往时间的长短基本上取决于工具性资源需求的时效。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场中的“人走茶凉”现象充分体现了这种“功利交换关系”的基本特征,这类由于权力兴衰而导致的“人情冷暖”,就呈现出中国社会特别是传统官场自古以来的功利主义特征。
②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到:“……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第二十七回)
由此,附着于结构性权力而衍生出的种种“关系学”的“功利交换关系”与“腐败/贿赂”之间,其边界常常也是模糊不清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力图强调“关系”或“关系学”不同于“腐败/贿赂”的纯粹金钱关系,其更多是希望强调“关系”运作中始终有情感与信任的要素,但往往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话语理解还是在实践操作中,“关系”与“腐败”之间都有着相互重叠的模糊地带(Yang,1994:58-64;Luo,2007:227-230)。虽然“人情/关系”与“腐败/贿赂”的边界是相当模糊的,甚至功利性目标非常明确的“人情请托”在表面上存在某种伦理“道德化”的合法性倾向(Smart,1993;阮极,2018),但如果将某种一次性的临时动员性“人情请托”与较长期的权力依附性“功利交换关系”作比较,就可以发现权力依附式的“功利交换关系”的非道德化面相,其表面温情之下的利益互惠常常会构成隐蔽性破坏公共规则乃至长期性“腐败/贿赂”的寻租性社会关系。
当年大红大紫的刘晓庆,就因一场税务风波,公司被查封,财产被没收,房产被拍卖,最后沦为阶下囚,在秦城监狱被关了422天。
事实上,有学者将黄光国的“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及“工具性关系”关系分类,修正为“义务性关系”(the obligatory type of guanxi)、“互惠性关系”(the reciprocal type of guanxi)及“功利性关系”(the utilitarian type of guanxi),并分别用“亲情关系”“人情关系”及“交易关系”来加以指称(Zhang&Zhang,2006)。“功利性关系”这一概念的确是对“工具性关系”的重要修正,即其已认识到中国社会大量存在着相当功利且可能旨在规避公共规则的私人关系,并且是相当缺乏真实信任及真情投入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功利交换关系”就是简单一次性的“交易/贿赂”关系,其中诸如请客送礼的策略性手段与较高的互动频率是相当常见的,但这种表面出于人情策略的“功利交换关系”本质上并不同于某种恩义导向的“主从关系”及“庇护关系”(Scott,1972;Walder,1986;Wank,1999)。⑤
舟曲特大泥石流因其规模之巨、伤亡之大,已成为人类地质灾害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如何预防泥石流灾害很值得反思。
进言之,在多数核心家人与朋友至交关系之中,儒家伦理一般还是占据优先地位,这在中国当下的市场或者说商场的“关系”实践中是很重要的。与之相对照,法家思维作用下的“功利交换关系”在官场中则更为凸显,这种关系更多地还是以“权力”依附作为基础的,或者说,“权力”与“信任”的差别构成了法家思维“功利交换关系”与儒家伦理“深度感情关系”之间的根本差别。“权力”与“信任”之别所导致的纵向服从关系与横向合作关系的差别,即使在市场条件下无疑也同样存在(Granovetter,2002,2017;罗家德、叶勇助,2007),但两者在中国社会中的根本性质差别却可能指向官场与商场的不同场域,并且“功利交换关系”所附着的“权力”更多地指向公共部门的行政权力而非市场交换中生成的经济权力。当然,商场中也是有“功利交换关系”的,官场中无疑也有“恩义负欠关系”乃至“深度感情关系”,但官场与商场之中权力集中度与选择退出权的根本差别,导致官场中更多地催生了“功利交换关系”,而在商场中更多地孕育了“恩义负欠关系”乃至“深度感情关系”。
在表1的分析架构中,我们可以较好地揭示出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未来预期利益需求与以往“情义”伦理嵌入两个维度的交叉分离。如前所述,过去的既有交往经验决定了彼此“情义”伦理的嵌入程度,“强情义”伦理嵌入的社会关系常常是核心家人、铁哥们等互动较多的“深度感情关系”,以及曾经受重要恩惠而有回报义务的“恩义负欠关系”,只有这样的深度人伦社会关系才意味着更多牺牲自我的帮助与付出,也是人们内心可以真正信赖的社会关系。与之相对照,现阶段深度互动频率的高低常常取决于当下及未来利益需求的明确预期,但互动频率较高并不意味着必然形成彼此的深度义务以及利益层面的真正信任。由此,这里所阐明的“功利交换关系”的重点通常是弱者由于当下及未来某时段内的高度利益需求而采取的种种“关系学”交往策略,其私人交往的时效通常也就取决于彼此利益需求的时间长短。某种意义上,黄光国所谓公平法则的“工具性关系”,本质上应是责任及义务比较明确的市场交易或公共事务中的社会角色关系。但是,在中国社会,由于常常出现权力寻租(包括职业权力的泛滥及其导致的普遍主义信任的匮乏),相当部分的社会角色关系被发展为带有某种寻租性质的“功利交换关系”,其本质上恰恰是要破坏市场交易与公务绩效的“公平法则”,因而在根本上偏离了本应具有社会角色化取向的“工具性关系”。
无论如何,“情义”与“利益”始终是中国人社会关系中的两大核心要素。笔者之所以将“情”与“义”并称,恰恰是因为中国人的“情感”与“义务”常常是一体化而难以明晰区隔的,“情义”根本上还是体现于在曾经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利益”的问题。由此,笔者曾经提出“关系”本质上是“义”“利”混合、相生相克而难于分类的(沈毅,2007)。然而,笔者的这一认识更为侧重于“义”“利”混合的“人情”往来的动态历史及其对当下关系的“情义”状态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关系”定位中面向未来的工具性“利益”需求预期这一重要维度。事实上,基于以往的工具性恩惠“情义”嵌入程度与展向未来的工具性“利益”需求预期通常并不是完全一体化的:“既有情义伦理嵌入”往往指向从过去至当下的交往历史,“强情义嵌入”的社会关系常常是核心家人、铁哥们、铁姐妹等“深度感情关系”,以及单方面有重要亏欠而需回报的“恩义负欠关系”;“未来利益需求预期”则通常指向从当下至未来的某个时段内的重要工具性资源摄取,其较为明确的“未来利益需求预期”除了求助于核心家人及铁哥们等“深度感情关系”之外,个体还有可能与原先缺乏关系基础的相关资源支配者建立与发展较为长期的“功利交换关系”。
休闲之事古已有之。休闲一般是指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目的一种业余生活。因此,休闲有消遣、娱乐和修养身心的涵义。它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与文化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它具有独特的文化精神底蕴,它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休闲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影响到个人能否全面、健康地发展自己[1]。
2.决策模式。网络达成了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个体与组织之间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深刻改变了这些社会主体的关系模式,也挑战着传统政府决策模式。传统地方政府决策是科层结构框架内的封闭型决策,决策权实质集中于领导干部及决策机构,决策执行遵循自上而下的单向路径,决策方法主要为基于典型调研的经验决策,决策驱动来自上级精神与地方治理需求、行政需要乃至地方发展情况的结合,基层政府、普通公务员和民众、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主体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实质过程之外。
四、“关系”类型的多重面相及其内在关联
在上述的各类“关系”形态中,核心家人或铁哥们等“深度感情关系”始终构成了“义”“利”皆高的核心性关系形态。某种意义上,如果将“义”“利”交融的“深度感情关系”对应于黄光国的“情感性关系”的话,⑥那么就可以将其对应于“熟人”的“混合性关系”区分为“功利交换关系”“恩义负欠关系”和“普通人缘关系”,其重点无疑指向“功利交换关系”与“恩义负欠关系”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形态。然而在黄光国所谓“混合性关系”的“人情法则”之中,资源支配者将按照自身付出的代价与请托者未来可能的回报做出比较,并兼顾对方的关系背景来权衡轻重,最终决定是否“做人情”给对方(黄光国,1988a)。从请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方法与资源支配者“拉关系”,使得在未来的请托过程中,资源支配者由于平时的“人情”亏欠,顾及请托者的“面子”而难以回绝。通过这种“面子”功夫的“关系”运作,能够使资源支配者做出有利于请托者的资源分配。这种“混合性关系”及“人情法则”的论述恰恰指向根据未来利益定位的“功利交换关系”,相对忽略了既有交往“情义”嵌入的“恩义负欠关系”的面相。
事实上,从黄光国(1988b)分析的《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一段材料来看,其所着力分析的“混合性关系”及其“人情法则”,也更为明显地凸现了法家功利主义色彩较强的“功利交换关系”,其实质就是个体发现自己的“熟人”群体中具有一定关系基础的某重要人物成了资源支配者,于是对其逐步展开“拉关系”的种种手段,力图将其发展成对自身更为有用的“关系”,亦即将原来交往频度较低的“普通人缘关系”乃至于没有交往的陌生人关系发展成为交往频度较高的“功利交换关系”。其实,资源支配者通常也对这种有求于己的“功利交换关系”有相当的体认,其“人情法则”更多的还是关注对方是否具有同等利益交换的价值与可能,通常并不会为小恩小惠所动而轻易给予对方重要的资源。因此,“功利交换关系”之中双方所顾及的“情面”其实更多的还是出于权力与利益交换的考量,而彼此之间的真实情感与实质信任常常是较弱的。
然而,与“功利交换关系”相对照,“恩义负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破原有的义务期待或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人重要帮助而形成的一种关系形态。在陌生人之间,施恩者有可能并不希冀受恩者的回报,但在熟人之间,恩惠施予者通常希望得到受恩者未来的长期性回报,这其中就蕴含着施恩者对受恩者未来回报能力及其“私德”的长期性信任。进言之,“恩义负欠关系”常常也发展自典型“弱连带”的“普通人缘关系”乃至无连带的陌生人关系,即资源支配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或喜好而将其重要资源给予某关系较远的普通他人,或是在他人落难时给予了重要援助(某些极端情境下甚至成为“救命恩人”),“恩义负欠关系”都有可能建构起来。单向“恩义负欠关系”通过不断加强互动及“人情”往来,同样会发展为“强情义”嵌入、强利益需求的双向“深度感情关系”。反之,某些“恩义负欠关系”也可能来自于双向深度嵌入朋友至交的“深度感情关系”的某种退化,这种退化可能是由于社会流动、阶层分化、代际传递等诸多原因导致的,但以往的交往及当时弱势方多受恩惠的“情义”始终是存在的,其内在的“情义”嵌入程度显然是“功利交换关系”所不能比拟的。
就现阶段的私人交往互动频率而言,在“深度感情关系”及“功利交换关系”这两种关系中,个体当面互动或联系交往较多,但实际上两者的情感认同、实质信任及其对未来交往时间的预期则可能有质的差别。进言之,个体常常会根据自身不同的重要时点而对不同的“关系”加以调整,个体的“深度感情关系”与“恩义负欠关系”是相对稳固的社会关系,在“功利交换关系”中,个人的交往时长往往取决于资源支配或利益需求的时间长短,“普通人缘关系”则涵盖了个体在各个群体与社会圈中更为普遍的弱连带式熟人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个体的差序信任是沿着“深度感情关系”——“恩义负欠关系”——“普通人缘关系”的路径而逐步弱化的,“功利交换关系”恰恰是一种缺乏实质信任而又有着特定利益需求的阶段性关系形态。应该说,基于以往恩情的“恩义负欠关系”构成了基于当下利益的“功利交换关系”的对立面,当然,不同组织场域及其催化形成的具有不同人格倾向的个体会将其“关系”发展的侧重点放在不同的关系形态上。总之,“普通人缘关系”向“功利交换关系”或“恩义负欠关系”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径实质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关系学”发展策略,其中也蕴含了不同文化传统特别是儒法传统的深层影响,这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人社会关系运作的多重面相打开了一个窗口。
总体来看,多数“恩义负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般熟人间“普通人缘关系”的长期性“人情”投资,如在职业或事业上施恩者与受恩者之间就有可能成为“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就此而言,“恩义负欠关系”之中的施恩方对受恩方往往有长远的利益预期与信任期待,其中蕴涵着某种阴阳转换的道家思维及其时间观(赵鼎新,2018)。当年的受恩者有可能在若干年后成长为或富或贵的资源支配者,施恩者此时却可能已经离开了财富或权力的中心,即使彼此之间的交往互动较少,但施恩者(乃至于其家属或后代)的请托对于受恩者而言常常还是难以回绝的,甚至于受恩者本身就在主动寻求报恩的合适时机。这样的“恩义负欠关系”恰恰构成了“功利交换关系”的对立面,个体对“恩义负欠关系”的情感认同常常是远在“功利交换关系”之上的。由此,相对于某些可以回绝的“功利交换关系”,一些更为重视恩情的资源支配者面对“恩义负欠关系”中的请托所可能陷入的“人情困境”往往才是最难处理的。因此,尽管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也指明了“人情”式“混合性关系”交往中“报”的规范作用,但其对“人情法则”与“人情困境”的阐释凸现了资源交换中可预期回报的某种“功利交换关系”,相对忽略了资源交换中常常不可明确预期的“施恩”与“回报”才是“恩义负欠关系”的本质内涵。对某些更为重视恩情的资源支配者而言,其所认定的请托者“面子”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请托方的权力大小及资源多少,曾经受到的恩惠特别是其早年所受的恩惠有时反而是更为根本性的。⑦
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理政思维。无论是在青少年时期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和世界观建立上,还是在仕途跌宕屡经坎坷之时,苏轼都矢志不渝地践行着以民为本的宗旨,一切从民本出发,造福于民。这在他的税赋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畏权贵,直言敢谏,仕途坎坷,九死不悔。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苏轼伟大的人格,宽厚的胸怀,同时,苏轼在税赋思想和税赋实践中,也为我们留下了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实践积累。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应该说,就“范进中举”的个案而言,黄光国(1988b)所分析的“请托事件”其实正指向科举制脉络下“官本位”亦即权力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某种程度上反而相对忽略了乡土社会的“人情”面相)。特别是对于掌握公共资源的资源支配者而言,“功利交换关系”往往是在资源支配者“上位”之后,有需求者逐步拉关系而刻意形成的;“深度感情关系”或“恩义负欠关系”则更多是在其“上位”之前由于人际交往或提前给予恩惠而自然生成的。当然,在某种关系网络或中间人的关系联结中,这几种不同性质的关系连带可能是同时存在的,如在“走后门”过程中通过各种核心性“深度感情关系”“恩义负欠关系”乃至较为疏远的“普通人缘关系”联结上某位重要的资源支配者,然后再通过直接互动如请客送礼等建立“功利交换关系”连接,进而达成相关的具体工具性目标。无论如何,在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框架中,“工具性关系”本应是市场交易或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关系,但中国社会常常会将这种社会角色关系发展成为长期性利益输送的“功利交换关系”。这样的“功利交换关系”无疑在西方个人主义社会的“名利场”及政治运行中也大量存在,但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更多的还是长期以来“官本位”社会结构及“升官发财”文化观念的伴生物,也充分体现了官场中法家思维作用下的功利主义特征。
进一步的问题或许在于:“深度感情关系”“恩义负欠关系”和“普通人缘关系”始终体现了儒家“人伦”义务的亲疏远近,极端性的“功利交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则已经突破了“差序格局”的“人伦”范畴。“功利交换关系”是针对资源支配者特意展开的,常常是弱者围绕着资源支配者,构成了大量依附性“功利交换关系”,当然,不同部门及系统的资源支配者之间同样可能构成各种较为对等的“功利交换关系”。然而,“功利交换关系”中真实性的情感与信任常常是匮乏的,官场中的“功利交换关系”甚至会趋于彼此提防乃至策略控制,并且这样的“控制”并不一定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宰制,很多情境下也可能弱者握有强者的种种“把柄”进而加以威胁。由此,这种法家“权势”主导的“功利交换关系”及其运作逻辑,根本不同于儒家“人伦”范畴中的关系形态,常常有发展为敌对关系乃至崩溃的危险,并随着资源支配者的离职或退位而终止,其较好的结果也最多是退化为“普通人缘关系”。比较而言,“普通人缘关系”可能通过“恩义负欠关系”发展为“深度感情关系”,反之,“深度感情关系”则可能由于交往的减少退化为“恩义负欠关系”,某些“恩义负欠关系”也会随着报恩行为的完成最终退化为“普通人缘关系”。这样的人伦“差序”关系的变化始终不适用于“功利交换关系”,“功利交换关系”往往是出于利益需要由“普通人缘关系”发展而来的,同样可能随着利益需求的终止而退化为“普通人缘关系”,但其常常处于关系紧张乃至破裂的边缘,始终无法发展为真正情感认同与深层信任的“深度感情关系”。
由此,个体往往将面临多重社会关系的分类认知与区隔实践,并且在不同时段根据以往交往的“情义”状况及其未来利益需求的变动而对不同的“关系”类型加以调整。“深度感情关系”与“功利交换关系”始终是人际交往频率最高却又具有本质区别,难以相互转化的两种“关系”形态。“深度感情关系”更多的是以他人为重,会做出自我牺牲的家人或朋友关系,而“功利交换关系”虽然往往以情感互动作为表象,本质上却是利益目标导向型关系,两者不同的儒法价值观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信任观。“深度感情关系”看重既有私人关系的人情义务,甚至可能是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功利交换关系”虽然也能由于利益需要或权力主导而形成表面有效的“合作”,但更看重彼此现阶段及未来的权势地位或利益联结,常常是缺乏信任甚而在关键时刻以牺牲他人自利或自保的。因此,“深度感情关系”中的高频度互动与真实情感常常是一致的,而“功利交换关系”中的高频度互动与内在情感往往是分离的。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式的“深度感情关系”往往体现为工具性资源层面的互助义务与深层信任,因而始终不同于个人主义式纯粹情感表达为主的“情感性关系”;而缺乏情感与信任的“功利交换关系”则可以由于权力依附或利益需要而发展成为某种表面上私人互动频率较高的强连带,这与制度化条件下个人主义式弱连带的“工具性关系”构成了鲜明对照。
从某些个体应对四种“关系”形态的基本态度来看,这样的划分也说明部分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有较大的分离。“功利交换关系”虽然在行为层面构成某些个体互动频率较高的“强连带”,但在心理上却往往相当疏远甚至充斥着负向情感。与之相对照,“恩义负欠关系”虽然可能处于互动频率的外围地带,甚至在某些时段内比“普通人缘关系”互动更少,但其内在深度的“情义”嵌入常常使其在心理认同上处于较为核心的地带。当然,不同的人格特质特别是外部组织场域对个体的影响,也会形成个体对不同性质“关系”的不同态度,如商场中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更倾向于将“恩义负欠关系”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官场中通常有更多的功利性个体,人们更倾向于将“功利交换关系”置于首位,特别是为了当下的“功利交换关系”而将曾经的“恩义负欠关系”置之不顾。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在为官之后,在对恩人甄士隐被拐女儿英莲(香菱)的判案中丝毫没有顾及当年所受的恩情,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无疑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场之中相当常见,这其实也说明官场场域中“恩义负欠关系”相对于“功利交换关系”的脆弱性。
总之,“差序格局”人伦关系的心理定位与信任程度由内而外可以区分为“深度感情关系”“恩义负欠关系”及“普通人缘关系”,但以往的研究恰恰忽视了在人伦义务之外缺乏人际信任却交往频度颇高的“功利交换关系”,特别是某些个体对阶段性“功利交换关系”的重视程度常常是在“恩义负欠关系”之上的。应该说,“情义”与“功利”本是中国儒法文化传统的一体两面,因此传统乡土社会与官僚政治场域中也相应主要存在儒家自我牺牲型“深度感情关系”与法家极端自利型“功利交换关系”的差别。在此之外,“普通人缘关系”的维系及“恩义负欠关系”的建构则体现了儒道结合、阴阳转换的长远关系理念。一个人即使难以或无意于培养出值得预先投入的“恩义负欠关系”,通常也会在各类关系群体中维系相对和谐的“普通人缘关系”,“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以备其中有日后富贵而值得结交依附的“功利交换关系”。在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弱连带式“普通人缘关系”始终是广泛存在的,“功利交换关系”更多还是存在于官场及职场之中,“深度感情关系”与“恩义负欠关系”则在有相当大的市场选择权及退出权的商场之中可能得到更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以双向长期性“关系信任”作为核心基础的“深度感情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式“人伦”关系“义”“利”交融的特征,其在深层意涵上则暗含着儒家伦理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机制。
五、“儒家伦理”及“关系信任”的历史渊源与作用机制
如上所述,“普通人缘关系”是广泛存在的弱连带式“熟人”关系形态,“恩义负欠关系”的实际储备数量及现阶段互动频率通常都是相当有限的,“深度感情关系”与“功利交换关系”则构成了个体现阶段互动频率较高的两种主要“关系”形态。传统“五伦”之中,“深度感情关系”更多地可以指向家人范畴内的“父子”“兄弟”“夫妻”及家人以外的“朋友”,共计四伦;“功利交换关系”则更多地指向传统“君臣”一伦在法家思维作用下的某种变种。事实上,至交铁哥们的“情义”相投恰恰体现了“朋友”一伦在家庭之外社会联结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商场中以核心企业家为中心,常常会形成由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人伦关系联结而成的“关系共同体”(胡必亮,2005;沈毅,2016)。当然,在企业家的“关系共同体”中,除了当下核心家人及铁哥们朋友的“深度感情关系”之外,现已“无用”但曾经受恩需要回报的“恩义负欠关系”通常也涵盖其中。不过,就市场的长远合作与发展而言,长期性交往的“义”“利”共生型儒家式“深度感情关系”,始终构成紧密性“关系信任”及其“关系共同体”得以生成及维系的主要关系形态。
“五伦”关系在实践中的这种异化走向,实质上也反映了传统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进程。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及至平天下的政治秩序目标,无疑是要达成其由“内圣”而“外王”的文化设想,尤其是要将此政治秩序目标寄希望于“圣君”。可以说,儒家的“道统”观念绵延不绝,诚如余英时所论证的,宋代“士大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儒学领袖们有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秩序诉求,“得君行道”成为宋代理学家的政治理想(余英时,2003[1999])。⑧事实上,在对政治秩序的“义”“利”之辨中,朱熹虽然始终强调“仁义”相对于“成败”的优先性,然而朱子不得不承认所谓“三代”至南宋,“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余英时,1998[1976]:99)这样的论述已然指明,即使是在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对“得君行道”的追求根本也是枉然,由“内圣”而“外王”的儒家政治理想在政治实践中始终是难以实现的。
正如余英时在其后续研究中所关注的,与儒家伦理政治理想的相对黯淡相比,明清的“士商合流”现象暗含着儒家伦理基调的内在转换及其积极价值。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科举名额并未随人口相应增加,“举业”的艰难使得“弃儒就贾”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宋明儒学“义利离”的矛盾观开始走向“义利合”的契合观,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传统可能正代表了这种儒家人伦日常化的趋向,儒家伦理也突破士大夫阶层的局限而走向平民化。可以认为,由于明清时期政治专制进一步加强,儒学本身也开始呈现出某种从“政治”转向“社会”的文化转型,与此同时,以王阳明等人为代表的“心学”传统也为儒家的这种“社会化”路向提供了思想基础。就社会价值取向而言,明清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已有相当大的提升,“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声望位序开始受到质疑,王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说法及沈垚的“四民不分”论都说明了明清士商界线渐趋模糊(余英时,2014)。明代中期以后,以徽商、晋商、甬商为代表的“儒商”大量生成,也为士商关系的交融一体奠定了商人群体的阶层基础,这事实上也成为儒家思想内在演变的社会阶层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传统“商帮”内部也存在诸多差异,有学者关注到,由于地域之间宗族制度发达程度的差异,徽商与晋商也有较大差异:地域宗族势力较强的徽商一般更多地依靠族法家规和传统习俗,通过“血缘”关系及家长权威约束同宗伙计;地域宗族势力较弱的晋商则更多地借助于家人及亲属之外的“地缘”关系开展商业活动,并通过允许人力入股的股俸制和号规习俗约束同乡伙计。由此,在意识形态及经商习俗方面,徽商更多崇尚朱熹理学和“举族迁徙”(血缘约束)的经商习俗,晋商则更多崇尚“关公信义”理念和“固土重迁”(地缘约束)的经商习俗(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2008)。表面上看来,晋商可能有着正式制度化的股权激励措施与家属控制措施,但其“地缘”关系实质上凸现了“家人关系”之外“信义”优先的“朋友”关系的重要性,或者说,传统社会中由于交往空间的局限,“朋友”常常是由“血缘”关系之外的“地缘”关系发展而来的,其中很多可能是在乡土社会中共同成长的“发小”。因此,笔者以为上述徽商与晋商的差别说明了“家人”与“朋友”在传统“儒商”经营中的不同作用机制,也说明正是核心家人及铁哥们朋友之间的“关系信任”亦即“深度感情关系”,构成了儒家人伦式“关系共同体”的主要基石。
在本研究中,由靶刺激(要求被试做出迅速按键反应的刺激)所诱发的P3即P3b,因而该成分反映了被试对靶刺激的主动觉察能力,属于随意注意,反映了认知加工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决策阶段[6]。研究结果表明,两个病例组P3b的波幅及潜伏期与正常对照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同时两个病例组之间也无显著性差异,似乎说明患者的随意注意功能并未受到患病和化疗的影响。
可以说,“朋友”一伦在中西方人际关系中的差异往往会被忽视(钱穆,2004:224-229)。衍生于家庭内兄弟人伦关系的中国式“朋友”关系,强调的正是“义”“利”混合而最终融为一体的“信义”关系,这在明清的传统商业扩展中已然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与之相似,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以核心家人及铁哥们朋友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成功的企业家背后往往都有着一个由一批重要的“深度感情关系”班底构成的“关系共同体”,这可能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财富不断增值的重要“关系资本”。在张德胜、金耀基看来,传统儒家“以义制利”的价值观依然影响着当下的一批企业家,因此对于“儒商”的研究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其经验研究似乎初步验证了当下“儒商”存在的可能性(张德胜、金耀基,1999)。由此可见,“以义制利”本质上是“先义后利”“由义及利”“义利交融”的互赢佳境,这样的状况通常也只有在市场条件下的商业合作中才有可能达成(张德胜,2002)。
可见,“义利交融”的“深度感情关系”与“先义后利”的“恩义负欠关系”,无疑应该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核心性议题与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关键。这样的“深度感情关系”及“恩义负欠关系”在民营企业家之间,或者企业家与其骨干下属的私人连带之间会特别凸显。在某种长期性的市场机制下,企业家的信誉及口碑非常重要,这是决定其未来能否维系重要客户与骨干员工的根本,这也要求企业家适当地舍弃自身当下的利益以营求未来更大的合作与共赢。这样的“关系理性”思维(林南,2004),使彼此的“关系信任”在经济活动中不断深化发展,而对以往“恩义负欠关系”的回报,也是提高企业家信誉与赢得口碑及人心的重要基础,或者是让其他“深度感情关系”有所预期而更为紧密的基石,从而有可能形成长期共赢的“关系共同体”。
因此,市场运行过程之中“关系信任”的建立与维系,通常来自于两者交往的“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及关系网络的“结构性嵌 入 ”(structural embeddedness)(Granovetter,1992)。比较而言,“深度感情关系”的交往式“关系性嵌入”始终是“关系信任”的主要运作机制,“恩义负欠关系”的口碑式“结构性嵌入”实质上却构成了对市场交易之中强势行动者更为长远的约束机制。与之相对照,官场之中或依附于行政权力的政商间的“功利交换关系”,其公与私之间的利益交换本身即是以权力存续作为前提的,其中的弱势行动者常常没有用脚投票的市场选择权乃至于最终丧失了退出权,“权力”的支配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取代了口碑或者舆论的重要性,这就注定了权力主导下的依附型“功利交换关系”(以至于极端意义上的完全“强制关系”)在出现利害矛盾的情况下,常常可能没有道德底线而选择牺牲他人,在某些极端情境下甚至会“丢车保帅”。
总之,市场或商场中的合作“关系”常常是某种长远性的积极关系,会为了“感情”与“恩义”而适度地牺牲自我,因为这样的牺牲所赢得的长远“关系信任”及其良好口碑往往是市场化企业立足于不败之地的基石。事实上,近年来著名的社会网络研究专家博特也开始关注到中国企业家在家人之外的私人“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并通过实证研究数据初步发现,中国企业家之间运用“关系”网络创业及巩固市场地位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而欧美企业的这一比例仅为十分之一。当然,在博特看来,中国和西方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机制并没有质的区别,主要还是量的差异(Burt&Burzynska,2017)。社会网络的形式主义研究虽然也关注到了中国社会与经济运行中“关系”合作的实质是血缘、地缘及朋友式的“深度感情关系”,但还是倾向于忽略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关系”与制度之间的相互替代性。
在笔者看来,这种经济发展中的“关系”网络作用量的差别其实是质的差别:西方社会的信用体系与制度发展是相对完善的,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社会资本所达成的信任机制更多只是补充性的;而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脉络中,基于企业家家人、朋友“深度感情关系”的深层关系性嵌入与网络结构性嵌入的“关系信任”机制,则常常超越公共规则及制度体系而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以血缘家族及朋友关系网络为核心的民营经济与家族企业的发展,始终不同于西方式以个体产权与合约为主要形式的家族企业,儒家人伦式差序网络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商业信任的基石(Wong,1996;Hamilton,1996)。与此同时,相当规模以上的企业家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官僚体系而构建自身的“关系”网络,这样的“关系”网络是以权力依附性质的“功利交换关系”为主要面相的。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功利交换关系”运作的重要性,才能厘清中国式“关系”现象的多重面相,并且理解雷丁(Redding,1990)所说的某种制度性信任的缺失与商业网络内部抱团式人际信任是同时存在的,从而进一步明晰儒家人伦式“关系信任”的核心指向。
六、结论与讨论
必须承认的是,这种以深层人伦嵌入的“关系信任”作为核心基础的“深度感情关系”,以至于以某些重要企业家为中心而构成的“关系共同体”,以他人为重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我利益的核心范围始终是比较有限的,很难如儒家“大同”理想那样推及“一般他人”。因此,我们对“儒商”的期待不能太高,特别是以企业家个人为中心的“关系共同体”始终有某种“小我主义”倾向,甚至于有可能在“关系共同体”之外牺牲他人与社会利益,从而对外部的市场秩序构成相当严重的挑战。即使在“关系共同体”内部,“义”“利”之间的交融共赢常常需要彼此谦让与相互付出,然而双方乃至多方利益的紧张难免会出现,家人及重要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信任”并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矛盾的发展同样会导致彼此信任的衰退乃至于“关系”的解体。无论如何,以儒家人伦式“关系信任”作为核心基础的“关系共同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过程中,积极作用应该还是其主要面相。
已有的关于“主从关系”及“庇护关系”的研究往往关注工厂单位制的“主从关系”中的“义气”和“感情”的成分(Walder,1986:170-175),研究者也认识到了某种侧重强调“情义”的“感情关系”与更为直接的“利用关系”的差别(Wank,1999:96),或是表面上更为长期,将感情与利益两者加以混合但本质上仍是功利性的目标算计式关系(target cultivation)(Walder,1986:180)。在恩义型的“主从关系”及“庇护关系”之外,官场式等级关系之中往往充斥着依附于权位及其资源所形成的“功利交换关系”,这种“功利交换关系”在某些阶段的交往频率虽然相当高,但它的维系更多是基于彼此的利益需要,很难达到真正的感情认同,甚至随时有可能根据利益需要及权力变更而改换门庭。因此,重新界定“功利交换关系”的内涵实质,应该有助于将某种更直接的功利导向的“关系学”与“感情”“义气”以及其他一般“人情”区分开来,否则极易将不同的“关系”形态混为一谈(如Yang,1994:58-64)。要言之,纯粹利益交换的“功利交换关系”始终是官场权力主导下等级关系的重要面相,这应该是关注恩义型等级关系形态的“主从关系”或“庇护关系”研究范式所忽略的。
因此,我们在认识到中国人社会关系“人伦”面相(梁漱溟,1987[1949];翟学伟,2016;周飞舟,2018;成伯清,2018)的同时,必须承认某种纯粹利益导向的权力依附性“功利交换关系”的大量存在,始终是中国社会及组织运行的重要特征,缺乏实质信任的法家功利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家“人伦”的范畴。当然,对不同本土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不同“关系”形态而言,“义”“利”交融而又存在内在紧张的“深度感情关系”及“恩义负欠关系”似乎还是更具有本土伦理文化特色的,“功利交换关系”在诸多社会文化乃至民主化的选票政治中可能同样也是常态,只不过在中国式“官本位”社会中的覆盖广度与涉入深度往往更为凸显。“关系社会学”未来对不同社会文化中“关系”的内容及其作用后果的分析,或许是其不同于“关系社会资本”研究(边燕杰,2017)的实质重点。
与法家功利主义传统比较,我们可以认识到儒家伦理直至今日对市场秩序的维护作用,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内部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可对儒家伦理期待过高。一些学者秉承新儒家的思想资源,力倡以儒家思想支撑起现代民主政治秩序,或者希望通过儒家伦理来构建整体性的儒家式现代秩序(秋风,2013)。笔者则以为,儒家人伦社会关系介入政治秩序,从根本上必将带来诸多消极性后果。“深度感情关系”及“恩义负欠关系”一旦涉入公共资源分配及公共规则实施的过程,其私人化的人伦“关系”就将对整体社会规则及公共秩序构成严峻挑战,对国有企业的运行绩效也可能产生相当负面的影响(沈毅,2016)。在市场化浪潮下,各类裙带式的政商一体化及其权力本位的恶瘤,始终是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杜绝的,这也是“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使命之所在(肖瑛,2014)。
总之,儒家伦理及其人伦“关系”的积极作用可能仍然主要局限于市场的“私域”范畴,私人关系一旦进入政治的“公域”范畴,随之而来的消极危险性就会剧增,这或许是当今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被评论为“异想天开”的依据(葛兆光,2017)。儒家建制化再度“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必然缺乏制度层面对绝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从而导致儒法合流式因私废公的各类“关系”泛滥。与之相对照,以家人及拟家人为核心的“深度感情关系”及其“关系信任”机制所促成的民营经济实体的不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伦理在市场经济中自然生成与自由选择的结果。或许,王阳明及其后学泰州学派的“心学”传统在民间经济而非政治体系中才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恰恰说明儒法传统及其指引的不同“关系”形态可能更多的还是不同组织场域中的选择性后果。无论如何,以深度人伦嵌入的“关系信任”为核心基础的“关系共同体”,对家族企业及民营企业在中国市场经济之中的充分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应该是儒家伦理在当今社会的生命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德]卢曼,2005(1973),《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韦伯,2010,《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阿兰·佩雷菲特,2016(1998),《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北京:商务印书馆。
边燕杰,2017,《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载《社会学研究》第5期。
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2008,《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载《管理世界》第8期。
陈云龙,2017,《关系信任:中国人信任的实践逻辑》,载《本土心理学研究》总第48期。
成伯清,2018,《心性、人伦与秩序——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载《南京社会科学》第1期。
邓晓芒,2010,《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1985(1947),《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傅春晖、渠敬东,2015,《单位制与师徒制——总体体制下企业组织的微观治理机制》,载《社会发展研究》第2期。
葛兆光,2017,《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载《思想》(台北)第33期。
郭齐勇(主编),2011,《〈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武汉大学出版社。
胡必亮,2005,《关系共同体》,北京:人民出版社。
黄光国,1988a,《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黄光国,1988b,《科举制度下的权力游戏:〈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社会行为分析》,载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金耀基,1983,《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载李亦园、杨国枢、文崇一(编著):《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李宗吾,1989,《厚黑学》,北京:求实出版社。
梁漱溟,1987(1949),《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
林南,2004,《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军等,2013,《强制结构理论及实验检验》,载《社会》第4期。
罗家德、叶勇助,2007,《中国人的信任游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钱穆,2004,《中国五伦中之朋友一伦》,载钱穆:《晚学盲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乔健,1982,《“关系”刍议》,载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秋风,2013,《儒法传统与信任重建》,载秋风:《儒家式现代秩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阮极,2018,《人情对贿赂及其“道德化”的影响——基于找关系入学的民族志研究》,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沈毅,2017,《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运动进程研究(1949—1976)》,载《开放时代》第2期。
沈毅,2016,《从“派系结构”到“关系共同体”——基于某国有中小改制企业组织领导“关系”变迁的案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沈毅,2013,《迈向“场域”脉络下的本土“关系”理论探析》,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
沈毅,2007,《“义”“利”混合的“人情”实践——对“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载《开放时代》第4期。
汪和建,2003,《人际关系与制度的建构:以〈金翼〉为例证》,载《社会理论学报》春季卷。
吴思,2002,《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肖瑛,2014,《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载《探索与争鸣》第6期。
杨国枢,1993,《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杨国枢、余安邦(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论与方法篇(一九九二)》,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杨宜音,2000,《“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本土心理学研究》(台北)总第13期。
杨宜音,1999,《“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杨宜音,1995,《试析人际关系及其分类——兼与黄光国先生商榷》,载《社会学研究》第5期。
杨中芳,1999,《人际关系与人际情感的构念化》,载《本土心理学研究》(台北)总第12期(人际关系与人际互动)。
余英时,2014,《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增订版)》,北京:九州出版社。
余英时,2003(1999),《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朱子文集〉序》,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余英时,1998(1976),《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载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翟学伟,2016,《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载《社会》第5期。
翟学伟,2014,《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载《社会》第1期。
翟学伟,2003,《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张德胜,2002,《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德胜、金耀基,1999,《儒商研究: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探微》,载《社会学研究》第3期。
赵鼎新,2018,《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周飞舟,2018,《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朱瑞玲,1990,《表达性人情和工具性人情》,载张老师月刊编辑部(编):《中国人的世间游戏:人情与世故》,台北:张老师出版社。
Burt,R.S.&K.Burzynska,2017,“Chinese Entrepreneurs,Social Networks,and Guanxi,”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ol.13,No.2,pp.221-260.Eisenstadt,S.N.and L.Roniger,1984,Patrons,Cli-ents,and Friends: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ust in Socie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ukuyama,Francis,1995,Trust: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Free Press.
Granovetter,Mark,2017,Society and Economy:Framework and Principles,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anovetter,Mark,2002,“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in Mauro Guillen,Randall Collins,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eds.),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Russell Sage Foundation:35-59.
Granovetter,Mark,1992,“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in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Eccles(eds.),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Structure,Form,Ac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pp.25-56.
Granovetter,Mark,1973,“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1360-1380.
Hamilton,Gray G.,1996,“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s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ommerce: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in Gary G.Hamilton(ed.),Asian Business Networks,Berlin,New York:de Gruyter.
Kipnis,A.B.,1997,Producing Guanxi:Sentiment,Self,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Lin,Nan,2001,“Guanxi:A Conceptual Analysis,”in Alvin Y.So,Nan Lin&Dudley L.Poston(eds.),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Westport,CT:Greenwood,pp.153-166.
Luo,Yadong,2007,Guanxi and Business,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Redding,S.G.,1990,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Berlin,New York:de Gruyter.
Scott,James C.,1972,“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6,No.1,pp.91-113.
Smart,Alan,1993,“Gifts,Bribes,and Guanxi:A Reconsideration of Bourdieu’s Social Capital,”in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8,No.3,pp.388-408.
Walder,Andrew G.,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nk,David L.,1999,Commodifying Communism:Business,Trust,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f,Eric,1966,“Kinship,Friendship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in Complex Societies,”in M.Banton(ed.),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omplex Societies,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pp.1-22.
Wong,Siu-lun,1996,“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Trust,”in Gary G.Hamilton(ed.),Asian Business Networks,Berlin,New York:de Gruyter.
Yamagishi,Toshio&Midori Yamagishi,1994,“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in Motivation and Emotion,Vol.18,No.2,pp.129-166.
Yan Yunxiang,1996,The Flow 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g,Mayfair Mei-hui,1994,Gifts,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Yang,Chung Fang,2000,“Psychocultural Foundations of Informal Groups:The Issues of Loyalty,Sincerity,and Trust,”in Lowell Dittmer,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N.S.Lee(eds.),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85-105.
Zhang,Yi&Zhang Zigang,2006,“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in China:A Link Betwee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s,”i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67:375-392.
注释:
①事实上,与儒家所推崇的“亲亲相隐”的家族主义传统相对照,法家所力倡的“大义灭亲”的国家主义传统也绵延不绝,甚至在当代政治运动中发展到极致(沈毅,2017)。在“大义灭亲”的传统之中,其内核本质正是牺牲人伦亲情的“自我主义”。
②这样的关系分类关注到了人际日常互动中“义务”与“情感”之间的紧张性,但相对弱化了人际交往过程中“利益”层面的矛盾,中国式朋友关系的义务嵌入程度往往是非常深的,深度嵌入的“友情”往往会发展为深度义务的“高应有之情”。反之,对于“恩情”也可能存在着较为真切的回报动机,其情感在人伦义务之外,同样可能是“高真有之情”。某种程度上,笔者以为“情感”与“义务”可以糅合为“情义”的一个维度,其核心应该是既有社会关系基础及其交往所形成的“情义”嵌入程度,其中通常蕴含着要为对方付出的私人义务,乃至于可能牺牲公共资源及制度规则。
对184名学生在学习动机各维度上的平均分(指各维度各题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各维度各题平均分标准差)进行统计,其中每个项目最高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中等临界值为3分,分值越高代表动机越强。具体结果见表1。
③按照山岸俊男等人的观点,这种封闭式的“保证关系”是一种无选择而没有风险的关系形态,因而并不存在是否需要给予信任的问题(Yamagishi&Yamagishi,1994)。无疑,这样的“保证关系”来自于乡土共同体的不可流动性,封闭性乡村共同体的惩罚性规则基本消除了恶意欺骗的可能性。应该说,“保证关系”不仅可以作用于家族内部,同时也能作用于乡村共同体乃至长期缺乏流动的组织单位之中,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体范畴内的非正式“脸面”作用机制与族规、乡约乃至组织制度的正式惩罚性规则,其本质上显示了集体主义文化的约束力量。按照这样的集体主义视角来分析,“家人”与“熟人”之间的差别可以相对弱化,而这种关系差别及其信任程度的差异却可能反映出中国社会运行的一些核心特征。
如果公益性的劳务派遣制度能够切实执行上述功能,那么其最显著的效果将是保护农民免受损失,使其不至于返贫,从长远看,也有利于移民的非农就业正常化。
④需要说明的是,格兰诺维特所界定的“强连带”与“弱连带”这一对概念是从认识时间的长短、情感的强度、亲密性及互惠交换的频率等四个维度来衡量的(Granovetter,1973)。但是,根本而言,互动频率是可以从社会行为层面加以衡量的客观指标。在个人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之中,互动频率往往取决于彼此的情感涉入程度,“强连带”通常意味着互动频率较高,情感表达为主的“情感性关系”,而在职业交往或经济交往中,则会出现某种互动频率相对较低的“弱连带”式“工具性关系”。在此之外,绝对意义上一次性交往的陌生人关系,通常并不构成社会关系研究的基本对象。
⑤等级性的“功利交换关系”需要区别于恩义导向的“主从关系”或“庇护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已有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理论研究往往强调了“庇护关系”与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或者将“庇护关系”视为某种权力不对等的“朋友关系”,进而也强调了“庇护关系”中的情感、义务及信任(Wolf,1966;Eisenstadt&Roniger,1984)。在此基础上,王大伟在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商业庇护主义”(commercial clientelism)的分析中,同样力图突出这种“庇护关系”中的情感与信任(Wank,1999)。但是,在笔者看来,必须区分家人感情型或师徒恩义型的“庇护关系”与非恩惠式利益交换的“功利交换关系”。如租佃关系中的“主从关系”本身就与家族关系有很大的重叠度,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这种“主从关系”可能带有较多家族血缘式的情义与信任。然而,对于中国传统官场中的政商关系而言,则常常是情感不足而缺乏信任的,彼此之间甚至有着权力强制乃至“把柄”控制。即使在王大伟(Wank,1999)所描述的当代中国式私人性政商关系中,“宴请”与“送礼”等人情化的策略虽然是常态,但这种表象化的“感情”常常遮蔽了由于诸多灰色地带的存在所可能导致的诸多不信任关系与各种权力控制策略。甚至在中小学入学、幼儿园入托、商品房购房、医院挂号等诸多涉及教育、住房、医疗等重要资源的生活事务中,也出现了大量“中间人”乃至“关系”型中介,使个人省却了“关系学”的烦扰而代之以灰色的直接利益交换链。在这样经营性的“关系”型中介自身的利益链条中,各类“功利交换关系”的深度嵌入更是通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权力控制体系来完成的,“关系”利益链条的分享者之间当然同样也存在着宴请、送礼等表象化的情感策略,但寻租性质的利益分成及其潜在的双向控制乃至于某种“强制关系”的形成可能还是其主要面相。
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所说的“感情”,可能比西方意义上的“情感”(feeling)更能体现中国人核心家人及朋友关系的日常状态,更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人人际关系中“情感”与工具性互助“义务”的密不可分,这一点也为海外人类学家所关注(Kipnis,199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中芳将某种深度交往而“义”“利”融合的关系发展阶段称为“高级感情阶段”(杨中芳,1999)。
施工采取“一炮一喷锚,短开挖快封闭支护”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围岩松动、岩石掉落等失稳现象的发生。特别是桩号8+530~8+640段短时间内频繁掉块,后加强一次支护,采用I18工字钢间距0.8 m,共138榀,Φ8网格0.2 m×0.2 m双层钢筋网,C25喷射混凝土24 cm厚,Φ22锚杆深入基岩2 m,间距1 m排距0.8 m成梅花状布设,连接筋采用Φ22,间距1 m,保证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
⑦朱瑞玲就曾经提出过“表达性人情”与“工具性人情”的概念(朱瑞玲,1990),实则认识到“人情”中“情义”与“工具”的双重面相,常常会分化为两类性质不同的“人情”关系。在她看来,“表达性人情”是自发性的情感,“工具性人情”则主要用于交换实质性资源,会产生人情负担乃至人情困境。“工具性人情”的提法其实已经指向“功利交换关系”,其本质上是某种目标动机明确的人情恩惠投资。笔者则以为,关键的衡量点是人情“恩惠”所施予的时间或时点,即施恩者是在受恩者平常时、落难时还是大富大贵时施予人情恩惠,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受恩者如何看待与界定这种“关系”的实质内涵。进言之,各类“关系”中无疑都夹杂着“情义”与“利益”的混合:“功利交换关系”本质上是将“关系”作为手段,而将自身的利益作为明显的首要目标;在“深度感情关系”与“恩义负欠关系”中,“利益”的互惠或单向的赠与体现了人伦义务或人情礼节的内在要求。个体通常会将“深度感情关系”及“恩义负欠关系”视作应该回报的重要“关系”,虽然利益也是这两类“关系”进退的重要“试金石”,但维持、发展或者回报核心性“关系”本身才是最终目标(Lin,2001)。然而,“深度感情关系”及“恩义负欠关系”这两类侧重于情义付出与回报的人伦“关系”,始终不能抹杀以利益摄取为首要目标与交往时段预期的“功利交换关系”的大量存在。
⑧从文化脉络来看,不对等的“恩义负欠关系”的原型或许是“师生”或“师徒”关系。在典型传统意义上的“天地君亲师”之中,“君臣”在实践中可能被扭曲为法家思维导引下的“功利交换关系”,“亲人”在实践中通常指向家人伦化的“深度感情关系”,“师徒”在实践中更可能形成某种儒道结合的等级化“恩义负欠关系”。当然,师生关系的法家功利化倾向在当今中国社会不断涌现,特别是自利型而非施恩型的“师傅”或“老师”引发了诸多问题,这也说明“师生关系”由于权力等级的存在有发展成为“功利交换关系”的危险。就更一般的社会意义而言,“师生”或“师徒”的等级关系虽然可能变质为纯粹利益导向的“功利交换关系”,但其内在的人伦意涵常常使其更多发展成为某种“施恩”与“回报”间隔时段较长,因而也较为明显的“恩义负欠关系”。即使在延续至今的“单位制”中,“师生”或“师徒”关系的“师徒制”所内含的人伦意涵很大程度上也不同于某种目标功利交换性“关系”(Walder,1986:178-179;傅春晖、渠敬东,2015)。当然,师生这种获致性“恩义负欠关系”的深入发展,同样可能成为义利一体化的家人式“深度感情关系”。
沈毅:河海大学社会学系(Shen Yi,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Hohai University)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6ZDA107)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019B19914)(项目编号:2019B30914)及江苏省第五期“333工程”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BRA2017422)资助。感谢翟学伟、甘会斌、卢崴诩、陈云龙等师友及审稿专家的批评意见,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周 慧
标签:关系论文; 儒家论文; 功利论文; 恩义论文; 性关系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6ZDA107)阶段性成果; 同时得到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019B19914)(2019B30914)江苏省第五期“333工程”科研资助项目(BRA2017422)论文;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