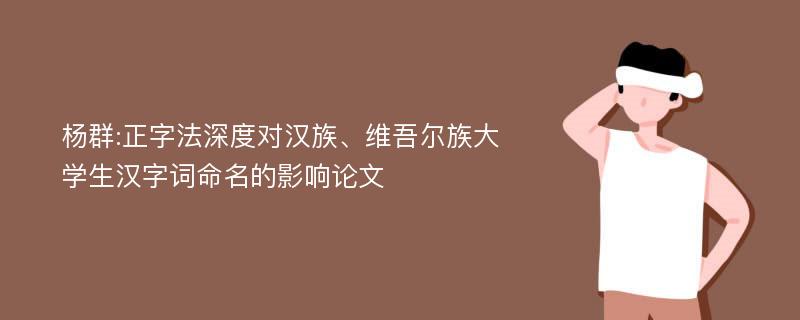
正字法深度对汉族、维吾尔族大学生汉字词命名的影响*
杨 群1 王 艳2张积家1
(1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 100872)(2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中心, 北京 100083)
摘 要 汉字的多音字数量众多, 种类复杂, 为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语带来了困难。通过两个实验, 考察正字法深度对汉族大学生和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汉字词命名的影响。结果表明, 无论是命名单字词还是命名双字词, 维吾尔族学生的反应时均比汉族学生显著长。对单字词, 两个民族被试的命名时间均受汉字的正字法深度和词频影响, 被试命名多音字的时间显著长于命名单音字, 命名低频字的时间显著长于命名高频字。对双字词, 两个民族被试的命名时间存在着词频与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对高频词, 汉族学生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与由单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维吾尔族学生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 对低频词, 汉族学生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 维吾尔族学生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与由单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整个研究表明, 正字法深度对两个民族大学生的汉字词命名的影响具有不同模式。所以如此, 与两个民族的母语特点、词汇获得年龄、语言熟练程度和语言加工方式不同有关。
关键词正字法深度; 词频; 语境; 维吾尔族
1 前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语言相通是民族间沟通的基本条件, 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 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特殊教学形式。麦凯和西格恩(1989)认为, “就世界范围而言, 双语教育对加强各民族相互理解是我们能够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就国家范围而言, 它是促进各个种族群体和平共处的最佳途径。”为了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我国宪法将“国家推广普通话, 推行规范汉字”作为基本国策。随着民族间的交往不断增多, 各民族同胞深刻认识到掌握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李旭练, 2015)。双语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也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加快发展双语教育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陈立鹏, 2016)。
新疆是我国特殊的双语教育区。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 仅维吾尔族就有983万人, 其聚居区庞大而且稳定, 区域文化的同质性高。据统计, 截至2012年, 全区学前和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班和民考汉的学生达到了167.86万人, 占在校生总数的66.6%。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 在上述成就背后, 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努力, 新疆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仍然未达到自治区政府提出的“民汉兼通”的目标。据新疆大学教务处2009年对入校少数民族学生调查:能够听懂汉语授课的学生占76.37%, 能够用汉语陈述学习内容的学生占56.83%, 能够阅读汉语教材的学生占61.24%, 能够用汉语撰写学术论文的学生占38.72%。即使是汉语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其汉语读、写能力也不容乐观。以新疆大学人文学院2013届的汉语专业毕业生为例:能够阅读汉语文献的学生仅有34.61%, 能够用汉语撰写毕业论文的学生仅有42.71% (赵江民, 符冬梅, 2013)。所以如此, 与汉字与维吾尔文的正字法深度的差异有很大关系。
改革创新,行业管理再上台阶。建立健全水法规体系,《四川省村镇供水条例》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四川省渔业船舶管理办法》已经完成定稿。全面落实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制度,初步制定了四川省主要江河湖泊的水量分配方案。严格工程建设管理和河道砂石开采管理。对在建工程实行全过程监督。积极推进水利项目招标投标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全面推行工程建设“四制”和财务审计制。落实河道采砂管理责任,实行河砂计划开采、总量控制、开采权公开招标等制度,强化河道采砂管理执法,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权责明确的长效管理机制。
正字法深度(Orthographic Depth)是指词的形态结构与音位结构的一致程度或透明程度, 亦即由形知音的程度。正字法深度对字词识别具有重要影响(张积家, 1998)。在不同语言之间, 正字法深度影响读者词汇通达时所采用的编码种类。正字法深度浅的语言容易使读者采用语言表面的音位策略, 正字法深的语言则鼓励读者用视觉码去加工词(Katz & Feldman, 1981)。在同一语言之内, 如果一个字形对应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读音, 会增加学习者学习和运用的难度(van Daal & Wass, 2016)。与单音字相比, 多音字的正字法深度深, 其命名潜伏期亦长(张积家, 王惠萍, 1996)。
马奴托海实际上指的就是伏尔加河与阿赫图巴河之间的河滩地。当然,阿赫图巴河左岸高坡上的大片区域也都在马奴托海的范围之内。可以想象,到了夏日,河滩里一定是草木茂盛,河水丰沛,柳树成荫,郁郁葱葱。而我们到来的这个时节,正好是俄罗斯的春末,树木刚刚吐露春呀,尚未长出绿叶。河滩里,榆树和柳树相互参杂,枯枝残叶,黑压压一片。而这一天,天公也不作美,天气阴冷,乌云密布,而且云层很低。远处的伏尔加格勒市,隐隐约约,隐藏在春日伏尔加河河面弥漫的烟雾之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景象,正好映证了新疆一首土尔扈特民歌里所唱的情景:
文字分为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索绪尔, 1995)。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 在语法上属于黏着语型。维吾尔文是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的从右往左的表音文字, 存在着严格的形–音对应关系, 容易见形知音。汉语用以表意为主、表音为辅的汉字来记录, 属于意音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来表示, 即使不依赖于语音, 也可据形知义。汉字在造字之初, 用一形一义一音代表一个事物或者动作、性状。《说文解字》说:“仓颉之初作书, 盖依类象形, 故谓之文, ……文者物象之本; 字者言孽乳而寝多也。”从甲骨文、金文的“文字画”来看, “物象之本”, 由单而复, 确实可信。从象形、指事、会意, 造字法即穷。假借和转注打破了一形一义一音的法则, 走向一字或一音多义, 或一义多音, 或一字多义多音的发展道路(徐世荣, 1988)。由于一音多义增加, 随后出现了形声造字法, 即组合表意的形符和表音的声符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发音跟随声符, 使汉字的形、音对应关系不再任意(张学新, 2011)。在一定的时期内, 通过形声原则来造字, 可以有效地表达新的事物, 却不需要增加新的音节。由于增字不增音, 导致汉字的字形越来越复杂, 同音字大量累积, 一字多音便不可避免。字形类似的字有不同的语音, 甚至同一字形也有不同的发音, 即多音字。由于汉字的形体定型且僵化, 不同的语音对应于不同的语义。据统计,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有544个多音字, 读音数量为2~5个, 读音的数量越多, 字数就越少。其中, 双音字有467个, 占85.85%, 三音字有65个, 占11.95% (朱力, 2012)。汉语多音字的读音变化具有区别词义、词性和语体的作用。如“喝”在读hē时表示喝水, 在读hè时表示大喊(喝彩) (汪泉兰, 2014)。因此, 与汉字相比, 维吾尔文字的正字法深度较浅。
汉字的多音主要有6种类型:(1)由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而形成多音, 如“弄”在读lòng时为方言读音, 意为小巷、胡同; (2)由文白异读而形成多音, 如“剥” (bāo)意指去掉外皮或壳, 在读bō时专用于合成词, 如“剥夺”; (3)由书面语和口头语兼录而导致多音, 这一类字的声母、韵母相同, 只有声调的差异, 如“绷” (bēng)有拉紧、张紧等义, 在口语中常读běng, 有板着脸、勉强支撑住之意; (4)由音译词、音译字而造成多音, 如“刹” (shā)在读chà时指佛教寺庙, 源自于梵语ksetra; (5)由记录语用场合而导致多音, 如“啊”有5个读音, 对应于不同的语气:ā-惊讶或赞叹, á-追问, ă-惊疑, à-应诺(音较短), à-明白过来(音较长); (6)由破读而导致多音, 某字产生了新的意义或语法功用, 为了在读音上有所区别, 读成另一种音。如“称”读chēng时表示测重量, 读chèng时同“秤”, 表示测量仪器(陈洋稳, 2015)。徐世荣(1988)将汉字多音字的产生归纳为辨义和分用两个总原因。辨义包括:(1)字性转化, 大抵是动/静字、虚/实字的转化, 如担dān (担负), dàn (重担); (2)引申扩展, 如奇qí (奇异), jī (奇偶); (3)细加区别, 如吐tǔ (吐露), tù (呕吐); (4)展转假借, 原有本字, 被另义借用, 此义只好再借用他字, 略改音读, 如hé (荷花), hè (荷枪、负荷)。(5)古义旧读, 文言诗文保留了古汉语的字义、字音, 如骑qí (骑马), jì (坐骑); (6)古今音变, 如曲qú (弯曲), qǔ (歌曲)。“曲”字古为入声。普通话无入声, 凡古入声字便变为其他声调, 字义借所变的声调分开来; (7)关系复杂, 一部分多义、多音关系的来历复杂或难稽考, 如臊sāo (腥臊), sào (羞臊)。分用包括:(1)文白异读, 文读即“读书音”, 主要用于文言作品; 白读即“口语音”, 用于白话文、生活用语。如嚼jué (咀嚼), jiáo (嚼不烂); (2)特定词语, 个别词由于专业上有特定的读音, 如轧yà (轧花机), zhǎ (轧钢); (3)专名特殊, 姓氏、人、地名有特殊的读音。如“朴”作姓氏读piáo不读pǔ, 皋陶的“陶”读yáo不读táo; “大宛国”的“宛”读yuān不读wǎn。(4)外语音译, 如“卡”kǎ (卡车), 不同于“关卡” (qiǎ); (5)习惯分读, 如尿niào (屎尿), suǐ (吓尿了)。总之, 汉语多音字及其读音数量繁多, 多音演变的类型和复杂性为学习者带来了困难。识记汉字多音字要遵循“据词定音”的原则, 要明意义、辨性质、析结构, 结合语境发准特定的一个音。
80个汉字双字词, 40个双字词由双音字与单音字组成, 即每一双字词中有一个字有两个读音, 双音字居于双字词的词首。40个双字词由单音字组成。80个双字词分为4组:20个多音高频词, 词频范围为285.7~2565.4次/百万; 20个多音低频词, 词频范围为2.3~47.6次/百万; 20个单音高频词, 词频范围为222.2~732.4次/百万; 20个单音低频词, 词频范围为2.3~25.7次/百万。多音高频词(M = 472.4次/百万)和单音高频词(M = 409.45次/百万)的平均频率差异不显著, t(38) = 0.55, p > 0.05; 多音低频词(M = 9.75次/百万)与单音低频词(M = 5.86次/百万)的平均频率差异不显著, t(38) = 1.50, p > 0.05。双字词的笔画数为7~27画, 多音高频词、多音低频词、单音高频词、单音低频词的平均笔画数分别为14.35、16.90、13.90、16.45, F(3, 76) = 2.42, p > 0.05, 差异不显著。实验前对构成实验材料的多音字也做了类似于实验1的调查, 维吾尔族学生在汉字单独呈现时均能够意识到它们是多音字。
用E-Prime编程。PET-SRBOX反应盒, 麦克风, 计算机。双字词呈现在PIII-667计算机屏幕的中央, 大小为280 × 167像素。被试的反应通过与反应盒连接的麦克风来进行记录。实验材料的呈现、计时及反应时和反应正误数据的收集都由计算机来控制。实验程序是:首先呈现“+”注视点500 ms, 空屏500 ms, 然后在注视点的位置呈现刺激, 时间最长为1000 ms, 被试对着话筒命名双字词。
综上所述, 维吾尔语具有严格的形−音对应关系和严谨的结构形式、较低的语境作用, 维吾尔族人的语言加工方式也具有分解性、抽象性、逻辑性和确定性, 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维吾尔族学生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时会存在着较大的困难。汉字的多音字数量繁多, 读音规则复杂, 字形与语音的对应关系模糊, 存在着一对二或者一对多的情况, 语境在决定字形对应何种语音上的作用关键, 这会导致维吾尔族学生对多音字的加工存在着困难。本研究的预期是:与汉族学生相比, 维吾尔族学生对汉字多音字的命名时间会显著长, 维吾尔族学生在对汉字多音字命名时利用语境的能力也会显著低。而且, 研究表明, 汉语母语者对高频词与低频词有不同的提取方式:对高频词倾向于以整词的方式表征和提取, 对低频词倾向于以词素的方式表征和提取(Andrews, 1989; Coney, 2005; 丁国盛, 彭聃龄, 2006; Grainger & Whitney, 2004)。因此, 可以预期, 与命名由两个单音字组成的双字词相比, 在命名首字是多音字的双字词时, 汉语母语者对高频词命名时会较少意识到双字词首字的多音性, 对低频词命名时能够较好地意识到双字词首字的多音性, 维吾尔族被试由于受母语加工方式影响, 无论是命名高频词还是命名低频词, 均能够意识到双字词首字的多音性, 但对双字词首字的多音性的认知要差于汉语母语者。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实验1考察汉族学生和维吾尔族学生对汉字单字词的命名, 旨在揭示正字法深度对汉族学生与维吾尔族学生对汉字词命名的影响; 实验2考察汉族学生和维吾尔族学生对汉字双字词的命名, 旨在揭示语境和词频在正字法深度影响两个民族学生的汉字词命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可以为改进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和汉字的教学提供心理学依据。
2 实验1:正字法深度对汉、维大学生汉字单字词命名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中央民族大学汉族大学生和维吾尔族大学生各30名, 男女各半。维吾尔族被试的大多数在读大学前一直接受汉语教育, 属于“民考汉”的学生①。部分维吾尔族学生属于“双语”学生, 他们学习汉语的时间从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开始, 在上小学以前都开始接触或学习汉语, 但家庭语言环境多为双语环境, 在分专业之前都上了两年预科, 汉语水平熟练, 均通过了MHK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四级和普通话等级考试。
2.1.3 材料
2(民族:汉族/维吾尔族) × 2(正字法深度:多音词/单音词) × 2(词频:高频/低频)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 民族为被试间变量, 正字法深度与词频为被试内变量。
终身学习是指每个社会成员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体发展的需要,贯穿于人的一生的持续的学习过程,学习不分年龄和人群,每个人都应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才能使自己适应新时代图书馆工作的新需求。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多读书才能让自己成为做人做事具有大格局的人,因此,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树立终身学习理念,追求终身学习目标,才是新世纪每个图书馆员的不二之选。[4]
2.1.2 设计
80个汉字单字词, 多音字和单音字各40个。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1986)中选取了20个多音高频词, 词频范围为338.5~3912.9次/百万; 20个多音低频词, 词频范围为7.7~281.5次/百万; 20个单音高频词, 词频范围为343.3~3869.8次/百万; 20个单音低频词, 词频范围为7.2~237.8次/百万。统计表明, 多音高频词(M = 1785.45次/百万)和单音高频词(M = 1773.62次/百万)的平均频率差异不显著, t(38) = 0.46, p < 0.05; 多音低频词(M = 92.89次/百万)与单音低频词(M = 94.42次/百万)的平均频率差异不显著, t(38) = −0.79, p > 0.05。全部词的笔画数为3~15划, 多音高频词、多音低频词、单音高频词、单音低频词的平均笔画数分别为7.55、8.80、8.10、7.20, F(3, 76) = 1.43, p > 0.05, 差异不显著。在正式实验之前, 请不参加实验的30名维族学生对所选的单字进行预测, 要求尽可能地写出汉字的读音, 如果字有多个读音则要求全部写出, 以保证实验中的多音字为被试所知晓。实验结束后, 要求被试判断实验材料中的单字哪些是单音字, 哪些是多音字, 被试回答的准确率达到99%, 说明实验材料有效。
实验1发现, 汉族学生与维吾尔族学生在命名汉字词时出现了相同的趋势:(1)均出现了多音字效应。被试命名正字法深度深的多音字的时间显著长于命名正字法深度浅的单音字。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Lukatela, Popadić, Ognenović, & Turvey, 1980; Bentin, Bargai, & Katz, 1984; 张积家等, 1996)。(2)均出现了词频效应。被试命名高频字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命名低频字。(3)两个民族的学生对多音字的反应均以优势反应为主, 而且产生非优势反应的比率差异不显著。这些研究结果体现了汉字认知的普遍性, 即两个民族的被试对汉字词的命名均受正字法深度、词频、多音字的优势音与非优势音的比率影响。两个民族的学生对汉字词命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无论是命名多音字还是命名单音字, 维吾尔族学生的反应时都显著地长于汉族学生; (2)词频效应在维吾尔族学生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维吾尔族学生命名高频字与低频字的反应时差异比汉族学生更大。
柴胡(批号:161201)、当归(批号:160501)、白芍(批号:160601)、白术(批号:160401)、茯苓(批号:161001)、炙甘草(批号:160601)、牡丹皮(批号:160801)、栀子(批号:160701)和薄荷(批号:160901)药材均购自山东百味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经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林慧彬研究员鉴定为真品。
PET-SRBOX反应盒, 麦克风, PIII-667计算机。刺激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中央, 字体为72号宋体。被试反应通过与反应盒连接的麦克风来记录。采用E-Prime编程。被试端坐在计算机前, 眼睛距离屏幕60 cm左右。首先呈现“+”字注视点500 ms, 空屏500 ms, 然后在注视点位置呈现单字词, 时间最长为1000 ms。要求被试对着话筒命名汉字, 被试命名以后, 汉字消失, 间隔1000 ms, 进入下一次试验。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反应的正误, 计时单位为ms, 误差为±1 ms。主试记录被试的读音。采用SPSS 19.0软件分析数据(下同)。
2.2 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前删除命名错误、短于300 ms长于2500 ms的数据及M± 2.5 SD之外的数据, 占7.46%。结果见表1。
以上培养基均经高压灭菌锅121℃高温高压20 min,冷却至50℃后加入氨苄青霉素(终浓度为100 ug∕mL)混匀,倒入平板凝固后方可使用。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1, 58) = 56.95, p < 0.001, ηp2 = 0.50; F2(1, 76) = 1693.07, p < 0.001, ηp2 = 0.96。汉族学生的反应时(M = 548.50 ms)显著短于维吾尔族学生(M = 841 ms), 二者相差292.5 ms; 正字法深度的主效应显著, F1(1, 58) = 35.23, p < 0.001, ηp2 = 0.38, F2(1, 76) = 33.52, p < 0.001, ηp2 = 0.31。被试对单音字的反应时(M = 678.25 ms)显著短于对多音字(M = 711.25 ms), 二者相差33 ms; 词频的主效应显著, F1(1, 58) = 81.11, p < 0.001, ηp2 = 0.58; F2(1, 76) = 6.79, p < 0.01, ηp2= 0.08。被试对高频词的反应时(M = 657.75 ms)显著短于对低频词(M = 732.25 ms), 二者相差74.5 ms; 民族与词频的交互作用被试分析显著, F1(1, 58) = 29.86, p < 0.001, ηp2 = 0.34, 项目分析不显著, F2(1, 76) = 1.15, p > 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汉族学生对高频词的反应时(M = 534 ms)显著短于对低频词(M = 563 ms), p < 0.001, 二者相差29 ms; 维吾尔族学生对高频词的反应时(M = 782 ms)亦显著短于对低频词(M = 901 ms), p < 0.001, 二者相差119 ms。词频效应在维吾尔族学生身上表现得更加显著。其他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只有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1, 58) = 52.77, p < 0.05, ηp2= 0.48; F2(1, 152) = 20.08, p < 0.001, ηp2 = 0.12。维吾尔族学生的错误率显著高于汉族学生, p<0.001。其余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 > 0.05。
在对多音字的反应中, 如果被试读出了频率高的词, 如将“便”读成了“biàn”, 可以称之为“优势反应”; 如果被试读出了频率低的词, 如将“便”读成了“pián”, 可以称之为非优势反应(张积家等, 1996)。汉族学生与维吾尔族学生对多音字的优势反应和非优势反应的比例和反应时见表2。
分析表明, 汉族学生的优势反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非优势反应, t(29) = −6.13, p < 0.001, d = 0.47, 二者相差61 ms; 维吾尔族学生的优势反应的反应时也显著短于非优势反应, t(29) = −3.37, p < 0.005, d = 0.25, 二者相差77 ms。比率差异显著性检验表明, 汉族学生与维吾尔族学生产生非优势反应的比率差异不显著, U = 0.77, p > 0.05。
表1 汉族学生和维吾尔族学生对汉字命名的平均反应时(ms)和平均错误率(%)
词类汉族维吾尔族 高频词低频词高频词低频词 反应时错误率反应时错误率反应时错误率反应时错误率 单音字522 (54)0.00 (0.00)547 (64)0.00 (0.00)759 (206)2.50 (4.04)885 (221)2.83 (4.64) 多音字546 (67)0.00 (0.00)579 (72)0.00 (0.00)804 (213)2.50 (4.09)916 (204)2.96 (4.78)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下同。
表2 汉族学生与维吾尔族学生对多音字的优势反应与非优势反应的比例与平均反应时(ms)
民族反应平均反应时次数比例(%) 汉族优势反应553 (116)97185.1 非优势反应614 (138)16414.9 维吾尔族优势反应830 (292)93487.8 非优势反应907 (312)13012.2
2.3 讨论
2.1.4 仪器和程序
系统平台整体架构包含展现层、应用层、应用支撑层、信息数据资源层和网络层等5层(见图5),其中三大子业务系统的架构设计如下。
实验1考察了被试对汉字单字词的命名。如果将多音字放在语境中, 多音字效应是否仍然存在?在多音字的表征中, 如果多音字的每一个语音都被激活了, 即使有语境存在, 也会因为存在着反应竞争而出现多音字效应。如果只有多音字的符合语境的语音被激活了, 在有语境时, 多音字效应就会消失, 被试识别由多音字组成的词和由单音字组成的词的时间就会相同。另外, 由于汉字词偏重于整体性、形象性、意合性和模糊性, 对其认知受语境影响大。汉字之所以出现多音字,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单字无法表达出多个意思, 于是就通过改变读音来区分。于是, 多音字就同时负载了不同的语义信息。如果将多音字放在双字词中, 既限定了语义, 也限制了读音。与汉字词不同, 维吾尔语词本身就负载了诸多的语音、语法信息, 对其认知受语境影响小。那么, 母语的差异是否使两个民族的学生对多音字有不同的加工模式?
无论是命名汉字单字词, 还是命名汉字双字词, 汉族学生的反应时均显著短于维吾尔族学生。这是由于汉语是汉族学生的母语却是维吾尔族学生的第二语言, 汉字是汉族学生的母语文字却是维吾尔族学生的第二语言文字。虽然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已经相当熟练, 但是, 汉语毕竟是他们的第二语言, 汉字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文字, 他们对于汉语和汉字的熟练程度还是不能够同汉语母语者同日而语。双语研究表明, 词汇习得年龄与第二语言熟练程度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Nichols & Joanisse, 2016 )。词汇习得年龄(age of acquisition, AoA )是指第一次以口语或者书面语的形式接触到某个词并且理解其意义的年龄。词汇习得年龄越早, 词汇加工就越迅速(陈俊, 林少惠, 张积家, 2011; Saito, 2015; 张积家, 陈穗清, 张广岩, 戴东红, 2012 )。陈宝国、王立新、王璐璐和彭聃龄(2004)发现, 词汇习得年龄和频率独立地影响着汉字双字词的识别。维吾尔族学生是在获得了母语口语词汇甚至是母语书面语词汇之后才学习汉语的, 他们对汉字词的习得远比汉族学生晚, 因而加工速度就慢。与词汇习得年龄相比, 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对双语表征和神经结构的影响就更大。研究表明, 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相当时, 两种语言的加工速度也相当; 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不同时, 优势语言的加工速度就快于非优势语言。在词汇判断中, 英−法双语者对熟练语言英语的反应快, 错误率低, 对非熟练语言法语的反应慢, 错误率高(Thomas & Allport, 2000)。还有研究发现, 对希腊语−英语双语者而言, 语言与语言熟练程度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如果被试的英语相对熟练, 对英语词的判断就比对希腊语词的判断快; 如果被试的英语不熟练, 对希腊语词的判断比对英语词的判断快(Orfanidou & Sumner, 2005)。对中−英双语者、中−日−英三语者、藏−汉−英三语者的词汇加工的研究也表明, 语言熟练程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崔占玲, 张积家, 2009; 李利, 莫雷, 王瑞明, 2008; 王悦, 孙尔鸿, 张积家, 2016; 王悦, 张积家, 2014)。在本研究中, 维吾尔族学生均是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根据双语认知的弱联结理论, 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语音表征、语义表征与词汇表征的联结均弱于单语者(Gollan, Montoya, Cera & Sandoval, 2007; 张积家, 张凤玲, 2010; 杨晨, 张积家, 2011)。维吾尔族学生在生活中使用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和文字, 决定了他们使用汉语与汉字的频率远不如汉语母语者高, 进而决定了他们对汉字词的熟练程度也远不如汉族学生。因此, 维吾尔族学生命名汉字词的时间就比汉族学生明显地长。
3 实验2:正字法深度对维、汉大学生汉字双字词命名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中央民族大学的维吾尔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各30名, 男女各半。维吾尔族学生的信息与实验1基本相同。被试未参加实验1。
3.1.2 设计
2(民族:维吾尔族/汉族) × 3(正字法深度:多音词/单音词) × 2(词频:高频/低频)混合设计。其中, 民族为被试间变量, 正字法深度与词频为被试内变量。
3.1.3 材料
阶段3过弯分析:通过几何法分析可知,当导向轮全部夹着弯曲轨道时,轨道两侧导向轮之间的距离为定值,即导向轮A与B或C与D之间的距离不变,弹簧形变量保持不变;导向轮均与轨道处于压紧状态,即导向轮B与轨道之间的偏移距离恒为0,如图7。相比于阶段1弹簧的变形增量计算如下:
3.1.4 仪器和程序
想要保证防渗墙有足够强的强度,务必要经过一番条件允许的结构运算。墙体的周围都是围土或者围岩,除了覆盖层以外在墙体的顶部以及大坝的上游和下游是围堰用的岩土,墙体的底部有基岩。这些围土、围岩的作用在于承载墙体以及墙体上方土堆的重量、上下游的水压以及地质灾害中地震的震力。防渗墙的结构不同其受力的状态可以主要分为两种形式:首先是高新强土石坝下覆盖层中的防渗墙,这样的防渗墙需要承载的压力来自于顶部心墙土体的巨大重量以及水压。其次就是,斜墙下的防渗墙以及石坝墙、施工围堰用的防渗墙,此时的水压力代替墙体顶部的土体的压中来承受压力。
Sapir-Whorf假设认为, 语言影响认知(Wolff & Holmes, 2011; 张积家, 2016)。威廉·冯·洪堡特(2001)认为,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维吾尔语与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 这会影响两个民族的语言加工方式。维吾尔语是典型的黏着语, 属于低语境语言, 强调语言形式的作用, 其特点是没有内部屈折, 每一变词语素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由于词根和变词语素的结合并不紧密, 词根和变词语素可以任意组合。这种靠变词语素结合语法意义的关联法使得维吾尔语结构严谨。维吾尔语的构词法采用“前缀+词根+ 后缀+ 后缀……”的形式(姑丽加玛丽•麦麦提艾力, 艾斯卡尔•肉孜, 古丽娜尔•艾力, 艾斯卡尔•艾木都拉, 2013), 在词缀中蕴含着丰富的语法信息, 词性固定、明确, 概念表达和所指定界分明。语言的影响会使维吾尔族的语言加工方式具有分解性、抽象性、逻辑性和确定性的特点(彭凤, 靳焱, 韩涛, 2013)。汉语是高语境语言, 无论是篇章、句子抑或是词汇, 其含义与发音对语境的依赖性强。受汉语影响, 汉族人的语言加工方式具有整体性、形象性、意合性和模糊性的特点(马燕, 2011)。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相比, 维吾尔族文化较为成熟与发达, 母语的社会功能强大, 母语与汉语的差距巨大, 导致维吾尔族人的语言加工方式与汉族人差异明显, 从而会使维吾尔族学生在学习与运用汉语时碰到诸多的困难。
3.2 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前删除命名错误、反应时短于300 ms、长于2500 ms及M± 2.5 SD之外的数据, 占4.92%。被试的错误率很低, 各实验处理的错误率不足1%, 故不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汉族被试和维吾尔族被试对双字词命名的平均反应时(ms)
词类汉族维吾尔族 高频词低频词高频词低频词 单音字516 (56)545 (52)702 (153)845 (185) 多音字513 (67)561 (54)736 (186)854 (168)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1, 58) = 60.00, p < 0.001, ηp2 = 0.51; F2(1, 76) = 1269.70, p < 0.001, ηp2 = 0.94。汉族学生的反应时(M = 536.25 ms)显著短于维吾尔族学生(M = 784.25 ms), 二者相差248 ms。正字法深度的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 F1(1, 58) = 9.74, p < 0.01, ηp2 = 0.14, 项目分析不显著, F2(1, 76) = 0.14, p > 0.05。被试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M = 652 ms)显著短于对由多音字和单音字组成的词(M = 666 ms), 二者相差14 ms。词频的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 F1(1, 58) = 283.14, p < 0.001, ηp2 = 0.59; 项目分析不显著, F2(1, 76) = 1.51, p > 0.05。被试对高频词(M = 616.75 ms)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对低频词(M = 701.25 ms), 二者相差84.5 ms;民族与词频的交互作用被试分析显著, F1(1, 58) = 83.91, p < 0.001, ηp2 = 0.59; 项目分析不显著, F2(1, 76) = 1.51, p > 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汉族学生对高频词的反应时(M = 514.5 ms)显著短于对低频词(M = 553 ms), p < 0.05, 二者相差38.5 ms; 维吾尔族学生对高频词的反应时(M = 719 ms)也显著短于对低频词(M = 849.5 ms), p < 0.001, 二者相差125.5 ms。词频效应在维吾尔族学生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民族、词频和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显著, F1(1, 58) = 8.52, p = 0.005, ηp2 = 0.13; F2(1, 76) = 37.66, p < 0.001, ηp2 = 0.33。
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高频词条件下, 民族与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显著, F1(1, 58) = 4.08p < 0.05, ηp2 = 0.07; F2(1, 38) = 25.79, p < 0.001, ηp2 = 0.97。均数比较表明, 汉族被试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M = 513 ms)和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M = 516 ms)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 > 0.05, 维吾尔族被试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M = 736 ms)显著长于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M = 702 ms), p = 0.001。在低频词条件下,民族与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亦显著, F1(1, 58) = 9.67, p < 0.01, ηp2 = 0.14; F2(1, 38) = 15.66, p < 0.001, ηp2 = 0.92。汉族被试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M = 561 ms)显著长于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M = 545 ms), p < 0.01, 维吾尔族被试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M = 845 ms)和由多音字组成的词(M = 854 ms)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 > 0.05。
3.3 讨论
实验2表明, 无论是命名由单音字组成的双字词还是命名由多音字组成的双字词, 两个民族的被试均存在着词频效应, 对高频词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对低频词, 而且词频效应在维吾尔族学生身上表现得更加显著, 这与实验1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 两个民族的被试在有语境条件下的多音字效应却出现差异, 这显示出词频对不同民族的多音字效应的调节作用:在高频词条件下, 汉族被试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和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说明他们对高频词认知不存在着多音字效应; 维吾尔族被试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 说明他们对高频词认知存在着多音字效应。在低频词条件下, 汉族被试对由多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 说明他们对低频词认知存在着多音字效应; 维吾尔族被试对由单音字组成的词和由多音字组成的词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说明他们对低频词的认知不存在着多音字效应。词频对两个民族被试的多音字效应起了调节作用, 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值得重视。
3.4 实验1和实验2的综合分析
由于实验1与实验2的被试是同质的, 为了进一步比较维吾尔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在有语境条件下(实验2)和无语境条件(实验1)的多音字效应的差异, 将反应时的数据合并, 进行了2(民族:维族/汉族) × 2(词频:高频/低频) × 2(正字法深度:多音字/单音字) × 2(语境:有语境/无语境)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其中, 民族和语境为被试间变量, 词频和正字法深度为被试内变量。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 116) = 116.50, p < 0.001, ηp2 = 0.50。维吾尔族被试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汉族被试。词频的主效应显著, F(1, 116) = 271.02, p < 0.001, ηp2 = 0.70。高频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频词。正字法深度的主效应显著, F(1, 116) = 44.96, p < 0.001, ηp2 = 0.28。被试对多音字或由多音字组成的双字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单音字或由单音字组成的双字词。民族与词频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16) = 89.13, p < 0.001, ηp2 = 0.44。词频效应在维吾尔族被试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字法深度与语境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16) = 13.68, p < 0.001, ηp2 = 0.11。被试在无语境条件下的多音字效应显著大于在有语境条件下。民族、词频与正字法深度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16) = 9.00, p < 0.01, ηp2 = 0.07。民族、词频、正字法深度与语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16) = 4.07, p < 0.05, ηp2 = 0.02。其余的主效应与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孟鲁司特可扩张支气管平滑肌,并有效降低患者的血管通透性。对于治疗哮喘、过敏性鼻炎具有良好的效果。除了哮喘之外,近年的研究中也表明,孟鲁司特在其他疾病的治疗中,也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如:慢性租塞性肺疾病、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囊泡性纤维症、病毒性细胞支气管炎、慢性荨麻疹、特应性皮炎、鼻窦炎、变态反应性真菌性鼻窦炎、中耳炎等疾病的临床治疗中。
由于本研究关心不同民族在有、无语境条件下的多音字效应的差异, 因此, 分别比较了不同民族在不同语境下的多音字效应。结果表明, 对汉族学生而言, 与无语境条件相比, 有语境条件下的多音字效应均有显著的降低:对高频词, 无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为24 ms, 有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为−3 ms, t(29) = 4.56, p < 0.001, d = 0.84, 差异显著; 对低频词, 无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为32 ms, 有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为16 ms, t(29) = 2.22, p < 0.05, d = 0.40, 差异显著。因此, 汉族学生对多音字的命名具有显著的语境效应, 有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小, 无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大, 说明他们利用语境的能力良好。维吾尔族学生的多音字效应不仅受有无语境影响(无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大, 有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小), 还受整词频率影响。对高频词, 无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为45 ms, 有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为34 ms, t高频(29) = 0.79, p > 0.05, 差异不显著; 对低频词, 无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为31 ms, 有语境时的多音字效应量为9 ms, t低频(29) = 2.22, p < 0.05, d = 0.41, 差异显著。无论有无语境, 维吾尔族被试对高频词认知时均能够意识到多音字的多音性, 但在认知低频词时, 在无语境条件下能够意识到多音字的多音性, 在有语境条件下意识不到多音字的多音性。
4 综合讨论
字词命名(word naming)是词汇提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字形信息首先激活了读者心理词典中的词形结构表征, 再激活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 进而启动发音动作(方燕红, 张积家, 2009)。本研究表明, 正字法深度、词频、语境等客观变量, 词汇习得年龄、语言熟练程度、汉字词使用频率、语言加工方式等主观变量, 均影响着维、汉被试的汉字词命名时间。
在应试教育下的写作教学中老师们往往会给出固定题目,固定格式,固定素材和基本大意,更有部分教师直接指定字数,给出范例,帮学生列出整体框架,指导学生照葫芦画瓢,此种传统固化的教学模式,不能让学生思维得到锻炼,能力得到培养。
4.1 关于汉字词命名的民族差异――语言熟练程度与习得年龄的影响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负责跨文化教学的实际操作。教师专业素养的高低,关系到跨文化教学的实际水平[3]。不少英语老师能够很好地讲解单词、阅读理解、写作等内容,但是一旦牵扯跨文化内容教学时,就会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很难为学生们进行高水平的讲解。正因如此,英语老师应当紧跟文化潮流,感受外国的文化氛围,在国外进行进修,接受专业的培训,在相应的讲座上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进而能够有效地指导学生学习跨文化知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4.2 关于两个民族的词频效应差异――汉字词使用频率与词汇习得年龄的综合作用
实验1和实验2发现, 两个民族的被试命名汉字高频词快于命名汉字低频词, 均出现了词频效应。但是, 比较而言, 词频对维吾尔族学生的汉字命名反应时的影响比对汉族学生更大。词频影响字词认知, 这一效应已经被诸多的实验研究所证实(陈宝国等, 2004; 谭力海, 彭聃龄, 1989; 张积家, 张厚粲, 彭聃龄, 1990; Brysbaert, Mandera, & Keuleers, 2018), 但是, 维吾尔族学生对汉字词命名的词频效应更大却需要解释。一种可能是与汉字词的使用频率有关。周有光提出了“汉字效用递减率”, 发现最高频的1000个汉字的覆盖率约为90%, 每增加1000个汉字, 覆盖率只提高了约十分之一(周晓文, 李勇, 2009)。据清华大学公布的6763常用汉字使用频率表, 汉语学习者认识500个汉字, 覆盖面为78.53%; 认识1000个汉字, 覆盖面为91.92%; 认识2000个汉字, 覆盖面为98.39%; 认识3000个汉字, 覆盖面为99.63%。在本研究中, 维吾尔族学生均通过了MHK四级考试, MHK四级考试标准是接受过1600~2000学时的现代汉语正规教育的学习者, 考生的汉语水平达到了基本上接近母语的水平。根据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标准, 我国中学毕业生要求认识常用汉字3500个左右。由于汉语不是维吾尔族学生的母语, 汉字不是维吾尔族学生的母语文字, 因此, 虽然维吾尔族被试都是大学生, 他们的识字量也不会多于3500个汉字。而且, 在这3500个汉字中, 维吾尔族学生对高频汉字词的使用可能更多, 对低频汉字词的使用可能更少, 这就进一步拉大了高频词与低频词的熟悉度的差异, 导致维吾尔族学生的词频效应比汉族学生更加明显。另一种可能是与词汇习得年龄有关。维吾尔族学生对汉字词的习得年龄明显晚于汉族学生, 他们对低频词的习得时间可能就更晚, 因而就拉大了命名高频汉字词与命名低频汉字词的反应时差异。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对员工的专业素质和IT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多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对信息化的掌握程度,还仅限于基本办公软件的操作和简单的网络搜索技能,要应对信息化的人力资源管理,还远远达不到要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施信息化后,从业者需要从事难度更大的工作,不但要求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和经验,同时要求具有良好的IT应用能力,这让很多员工产生畏难情绪,不愿意承受变化带来的压力,也害怕因为信息化的实施造成工作岗位的丢失。这些都成为阻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建设的因素,影响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实施。
4.3 关于两个民族被试的多音字效应差异――正字法深度与语境、词频、语言加工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的核心关切是正字法深度对汉、维学生对汉字词命名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 两个民族被试的多音字效应的差异体现了语境、词频、语言加工方式与正字法深度之间的交互作用。例如, 在实验1中, 无论是汉族学生, 还是维吾尔族学生, 命名多音字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命名汉字单音字, 说明正字法深度影响两个民族被试的汉字词命名。所以如此, 是因为汉字单音字的字形与其语音一一对应, 字形与音位之间的关系明确。在命名汉字单音字时, 字形表征的激活可以直接激活与之对应的语音表征, 因而反应就快; 汉字多音字的一个字形对应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语音, 字形和音位之间的关系模糊。在命名汉字多音字时, 多音字的两个语音都被激活了, 优势语音和非优势语音在命名中存在着竞争, 被试需要在两个语音之间进行选择, 反应时因而便延长了。因此, 被试对汉字单字词命名时的多音字效应主要是正字法深度的作用。张积家等(1996)发现了汉字单字词命名的多音字效应, 本研究采用不同民族的被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另外, 实验1发现的汉字词命名的多音字效应属于无语境下的多音字效应。在无语境条件下, 两个民族的被试均出现了多音字效应, 而且不存在着民族与正字法深度的交互作用, 说明对于孤立的汉字多音字而言, 两个民族的被试均可以意识到汉字多音字的多音性。这体现了汉字认知的普遍性。
实验2发现, 两个民族的被试在有语境条件下的多音字效应却出现了差异:汉族学生对多音字的命名具有显著的语境效应:在有语境时, 多音字的效应量小; 在无语境时, 多音字的效应量大。这说明, 汉族被试在对多音字命名时具有良好的利用语境的能力。维吾尔族被试的语境效应却相对低, 他们对高频词的命名甚至没有出现语境效应, 因为在无语境条件下和有语境条件下的多音字效应量差异并不显著。不仅如此, 两个民族被试的多音字效应的差异还体现在与词频的不同交互作用方式上。在有语境条件下(实验2), 汉族学生的多音字效应仅出现在低频词上, 并未出现在高频词上。这表明, 汉族学生的多音字效应受语境频率(整词词频)影响。对这种现象,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1)在高频词语境下, 汉族学生仅激活了多音字的符合语境的音位表征, 这一音位表征在固定词组中更接近于单音字的表征方式。学生对多音字的复杂语音结构并不敏感。但是, 在低频词语境下, 语境作用减弱了, 多音字的两个音位都被激活了, 学生对双字词中多音字的音位结构的双向性的敏感性增加了, 他们必须结合语境, 才能够决定该做出何种反应, 因而反应时便延长了。(2)汉语母语者对高频词与低频词的语音表征形式不同, 提取方式不同。高频词的语音表征具有整体性, 命名是根据双字词的固定一体化的语音表征进行的, 属于整词提取, 多音字的双向音位结构没有机会施加影响; 低频词的语音表征具有分解性, 被试在提取时分别提取词素的语音表征, 再整合成整词的语音表征, 多音字的不同语音就有激活并且有了参与语音竞争的机会, 使得整合过程变复杂了, 反应时也因此也就变长了。
在有语境条件下, 维吾尔族学生的多音字效应仅仅出现在高频词上, 在低频词上并不存在。这又该如何解释?双通道模型认为, 单词识别有两条途径, 一为词典通路, 即由字形表征激活传输到语音表征, 或者通过词性表征到达语义表征系统再激活语音表征; 二为非词典通路, 即通过词典外的形–音转换规则, 从亚词汇直接建构语音表征, 不需要再借助于心理词典的信息(Coltheart, Rastle, Perry, Langdon, & Ziegler, 2001)。维吾尔文是字母文字, 是一种规则化的透明文字, 其正字法深度浅(买合甫来提·坎吉, 刘翔平, 张微, 2011)。在维吾尔文阅读中, 个体利用所掌握的音位意识和字母发音知识, 运用字素–音位对应的语音解码策略进行新单词拼读。每一次成功解码都为获得特定单词的正字法信息提供了机会。买合甫来提·坎吉(2016)对维吾尔族儿童研究发现, 在维吾尔文单词识别中, 亚词汇水平的语音解码策略是阅读中的最基本策略。维吾尔族学生在高频词条件下对由多音字组成的双字词的反应时长于对由单音字组成的双字词, 说明他们对高频双字词命名采取了非词典通路, 即运用字素−音位对应策略来拼读, 此时多音字的两个语音都获得了激活, 竞争与选择延长了反应时间。而在低频词条件下, 由于被试对双字词不熟悉, 对组成双字词的多音字也不熟悉, 虽然也采用了字素−音素对应策略, 但字素不能够激活或者较难以激活多音字的所有音素表征, 只是激活了多音字的优势音素表征, 因此对由多音字组成的双字词与由单音字组成的双字词的命名时间就没有显著差异。但是, 维吾尔族学生的汉字多音字意识也在发展中, 因为对实验1和实验2的反应时的综合分析表明, 与无语境条件(实验1)比, 在有语境条件(实验2)下, 维吾尔族学生对低频词命名的多音字效应量显著降低, 说明语境开始对维吾尔族学生的多音词命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汉族学生与维吾尔族学生对双字词命名的多音字效应的差异也与双字词的语言表征有关。多词素词表征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主要有三种观点:(1)词素分解存储模型(Morpheme Access Modal, MA), 认为多词素词以词素分解的形式存储, 在整词通达之前, 词素表征先激活, 然后才激活整词(Taft & Forster, 1975)。研究者采用启动任务研究不同语言的被试, 发现词素启动效应与词素频率效应(Bien, Levelt, & Baayen, 2005; 王娟, 张积家, 许锦宇, 2014), 支持这一模型。(2)整词存储模型(Word Access Model, WA), 认为多词素词以整词的形式存储, 词汇识别由刺激输入直接激活整词表征来完成(Manelis & Tharp, 1977)。在汉语正常被试和脑损伤病人身上均发现了整词频率效应(Bi, Han, & Shu, 2007; Janssen, Bi, & Caramazza, 2008), 支持这一模型。(3)混合存储模型(Combined Access Modal, CA), 认为多词素词既存在着词素表征, 也存在着整词表征, 词汇识别是词素表征与整词表征激活的相互作用(Caramazza, Laudanna, & Romani, 1988)。在多词素词识别中, 词素和整词都发挥作用, 分解表征和整词表征并存(陈曦, 张积家, 2005)。整词和词素均自动进入了视知觉的早期模式辨认过程, 同时出现了整词和词素的双重表征模式(方杰, 2009)。对汉族学生而言, 高频词既存在着整词表征, 也存在着词素表征, 但整词表征的频率高, 词素表征的频率低, 命名时便以整词表征为主, 多音字词素发挥作用的机会就少; 低频词也存在着整词表征与词素表征, 但整词表征的频率低, 词素表征的频率相对高, 命名时词素表征容易激活, 多音字效应就容易展现。对维吾尔族学生而言, 受母语加工方式影响, 复合词的整词表征难以形成或者比较微弱, 无论是高频词还是低频词, 他们在命名时均是先激活词素表征, 再将词素表征整合成整词表征, 即采用了分解加工方式。高频词的词素表征容易激活, 可以激活词素表征对应的所有音位, 低频词的词素表征不容易激活, 只能够激活词素表征对应的优势音位, 因而就显示出与汉族学生不同的多音字效应。
综上所述, 两个民族被试的多音字效应差异体现了正字法深度与语境、词频之间的交互作用。在这背后, 是两个民族的语言加工方式的作用。汉字认知的整词表征与分解表征共存、整词提取与分解加工并用, 决定了汉族被试对高频词加工的整体性, 对低频词加工的分解性; 维吾尔文认知的分解表征和系列加工方式, 决定了维吾尔被试以类似方式加工汉字高频词和汉字低频词, 他们对这两种词均采用了分解加工方式。维吾尔被试对高频词中的双音首字比较熟悉, 因而能够意识到它们的双音性, 两种语音的同时激活延缓了反应时; 但是, 他们对低频词中的双音首字不熟悉, 不能够意识到它们的双音性, 因而只能够激活其优势语音, 因此对由双音字组成的低频词与由单音字组成的低频词的反应时就无显著差异。
本研究的结果对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与汉字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为了使维吾尔族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和汉字, 在教学中应该坚持以词为本位, 而不是以字为本位。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 以词为单位教学既有利于掌握汉语多音字的不同语音, 又有利于形成多词素词的整词表征, 使学生掌握符合汉语规律的认知方式。与此同时, 应该尽早地开展双语教学, 并且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家长的汉语水平, 使维吾尔族家庭能够达到维吾尔语与汉语双语并用, 提前维吾尔学生的汉语词习得年龄, 提高维吾尔族家庭的汉语和汉字的使用频率, 使维吾尔族学生能够尽快成为熟练的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
5 结论
(1)汉族学生与维吾尔族学生对汉字单字词的命名时间均存在着多音字效应和词频效应, 而且词频效应在维吾尔学生身上表现得更加显著。
(2)汉族学生和维吾尔族学生对汉字双字词命名中的多音字效应体现了正字法深度与词频、语境、母语加工方式的相互作用。
(四)地理实践。所有学科的知识学习,其主要目的都是要应用于实践活动当中,指导实践。地理学科也不例外,只不过地理实践素质较之我们所认识的地理实践勘测形式所不同,还包括了在课上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实践联系操作的部分,也算在地理实践素养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学生现今的主要任务是以学习为主,现实当中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课上进行模拟实践,既能够帮助学生加深知识理解程度,又能够培养学生的多方面意志品质。
参 考 文 献
Andrews, S. (1989). Frequency and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lexical access: Activation or searc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5(5), 802–814.
Bentin, S., Bargai, N., & Katz, L. (1984). Orthographic and phonemic coding for lexical access: Evidence from Hebrew.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0(3), 353–368.
Bi, Y. C., Han, Z. Z., & Shu, H. (2007). Compound frequency effect in word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anomia. Brain and Language, 103(1),8–249.
Bien, H., Levelt, W. J., & Baayen, R. H. (2005). Frequency effects in compound produ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2(49),17876–17881.
Brysbaert, M., Mandera, P., & Keuleers, E. (2018). The word frequency effect in word processing: A review updat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1–6.
Caramazza, A., Laudanna, A., & Romani, C. (1988). Lexical access and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Cognition, 28(3),297–332.
Chen, B. G., Wang, L. X., Wang, L. L., & Peng, D. L. (2004). The effect of age of word acquisition and frequency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double-character word.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 1060–1064.
[陈宝国, 王立新, 王璐璐, 彭聃龄. (2004). 词汇习得年龄和频率对词汇识别的影响. 心理科学, 27(5), 1060–1064.]
Chen, J., Lin, S. H., & Zhang, J. J. (2011). The word AoA effects in Chaoshan-Putonghua bilinguals’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43(2), 111–122.
[陈俊, 林少惠, 张积家. (2011). 潮汕话-普通话双言者的词汇习得年龄效应. 心理学报, 43(2), 111–122.]
Chen, L. P. (2016). Thoughts on strategically promoting “Ethnic-Han” bilingual education.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Ethnology, (2), 218–223.
[陈立鹏. (2016). 关于推进“民汉”双语教育的战略思考. 西北民族研究,(2), 218–223.]
Chen, X., & Zhang, J. J.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Chinese polymorphemic Words.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 120–126.
[陈曦, 张积家. (2005). 汉语多词素词识别及表征的理论和新设想.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120–126.]
Chen, Y. W. (2015).Several typical polyphonic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 Commercial Culture, (6), 103.
[陈洋稳. (2015). 现代汉语中几个典型的多音现象.商业文化,(6), 103.]
Coltheart, M., Rastle, K., Perry, C., Langdon, R., & Ziegler, J. (2001). Drc: A dual route cascaded model of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aloud.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1), 204.
Coney, J. R. (2005). Word frequency and the lateralization of lexical processes. Neuropsychologia, 43(1), 142–148.
Cui, Z. L., & Zhang J.J. (2009). Linguistic association model for Tibetan-Mandarin-English trilingual.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1(3), 208–219.
[崔占玲, 张积家. (2009). 藏-汉-英三语者语言联系模式探讨. 心理学报, 41(3), 208–219.]
Ding, G. S., & Peng, D. L. (2006). Mental recognition of Chinese words in reverse or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ole word processing and morphemic processing.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8(1), 36–45.
[丁国盛, 彭聃龄. (2006). 汉语逆序词识别中整词与词素的关系. 当代语言学, 8(1), 36–45.]
Fang, J. (2009). Representation of compound words in lexical access for speech production.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6), 1116–1123.
[方杰. (2009). 复合词在言语产生的词汇通达中的表征. 心理科学进展, 17(6), 1116–1123.]
Fang, Y. H., & Zhang, J. J. (2009). Asymmetry in naming and categorizing of Chinese words and pictures: Role of semantic radical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1(2), 114–126.
[方燕红, 张积家. (2009). 汉字词和图片命名与分类的比较. 心理学报, 41(2), 114–126.]
Gollan, T. H., Montoya, R. I., Cera, C., & Sandoval, T. C. (2007). More use almost always means a smaller frequency effect: Aging, bilingualism and the weaker links hypothesi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8(3), 787–814.
Grainger, J., & Whitney, C. (2004). Does the huamn mnid raed wrods as a wloh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8(2), 58–59.
Guljamal, M., Askar, R., Gulnar, A., & Askar, H. (2013). Uyghur homograph disambiguation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and optimal mapping pronunciation. Computer Engineering, 38(18), 22–25.
[姑丽加玛丽•麦麦提艾力, 艾斯卡尔•肉孜, 古丽娜尔•艾力, 艾斯卡尔•艾木都拉. (2013). 基于分类及最佳匹配读音的维吾尔多音词消歧. 计算机工程,38(1), 22–25.]
Institute of language teaching, Beijing Language University. (1986). Modern Chinese frequency dictionary.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Janssen, N., Bi, Y. C., & Caramazza, A. (2008). A tale of two frequencies: Determining the speed of lexical access for mandarin Chinese and English compounds.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23(7-8),1191–1223.
Katz, L., & Feldman, L.B. (1981). Linguistic coding in word recognition: Comparisons between a deep and a shallow orthograph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9, 157–166.
Li, L., Mo, L., & Wang, R-M. (2008). Semantic access of proficien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to a third languag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0(5), 523–530.
[李利, 莫雷, 王瑞明. (2008). 熟练中-英双语者三语词汇的语义通达. 心理学报, 40(5), 523–530.]
Li, X. L. (2015).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general language law in the minority areas. Minority Translation, (1), 34–38
[李旭练. (2015). 关于民族地区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一些思考. 民族翻译,(1), 34–38.]
Lukatela, G., Popadić, D., Ognenović, P., & Turvey, M. T. (1980). Lexical decision in a phonologically shallow orthography. Memory & Cognition, 8(2), 124–132.
Ma, Y. (2011). Inspiration of thinking way of Chinese and Uygur language to bilingual teaching. Journal of Nanch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26(4), 137–138.
[马燕. (2011). 汉维语言思维方式对双语教学的启示探讨.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6(4), 137–138.]
Mackey, W. F., & Siguan, M. (1989). Overview of bilingual education.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ress.
[M. F. 麦凯, M. 西格恩. (1989). 双语教育概论.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Mahpiret·Kanji. (2016).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Uyghur children's lexical decoding strategies. Bilingual Education Studies, (1), 20–15.
[买合甫来提·坎吉. (2016). 维吾尔族儿童词汇解码策略的发展特点. 双语教育研究,(1), 20–15.]
Mahpiret·Kanji, Liu X. P., & Zhang W. (2011). The lexical access of high frequency words in Uyghu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yslexia.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4(5), 1124–1129.
[买合甫来提·坎吉, 刘翔平, 张微. (2011). 维吾尔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高频词词典通达. 心理科学, 34(5), 1124–1129.]
Manelis, L., & Tharp, D. A. (1977). The processing of affixed words. Memory & Cognition, 5(6), 690–695.
Nichols, E. S., & Joanisse, M. F. (2016). Functional activity and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reveal the independent effects of age of acquisition and proficiency o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Neuroimage, 143, 15–25.
Orfanidou, E., & Sumner, P. (2005). Language switching and the effects of orthographic specificity and response repetition. Memory & Cognition, 33(2), 355–369.
Peng, F., Jin, Y., & Han, T. (2013). Gap in thinking manner between Han and Uygur analyzed from multiple angles in terms of vocabulary.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34(6), 88–94.
[彭凤, 靳焱, 韩涛. (2013). 从汉维词汇多角度分析汉维思维方式的差异.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4(6), 88–94.]
Saito, K. (2015). The role of age of acquisition in late second language oral proficiency attainmen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7(4), 713–743.
Saussure. (1995).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索绪尔. (1995). 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Taft, M., & Forster, K. I. (1975). Lexical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prefixed words.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4(6), 638–647.
Tan, L. H., & Peng, D. L. (1989). The effect of context and word frequency on tachistoscopically presented Chinese word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 3–8.
[谭力海, 彭聃龄. (1989). 快速呈现条件下语境与词频对中文语词识别的影响. 心理科学,(2), 3–8.]
Thomas, M. S. C., & Allport, A. (2000). Language switching costs in bilingual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3(1), 44–66.
van Daal, V. H. P., & Wass, M. (2016).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ability explained by orthographic depth and orthographic learning: A “natural” scandinavian experiment.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1(1), 46–59.
von Humboldt, W. (2001). The Humboldt corpus of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威廉·冯·洪堡特. (2001).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Wang, J., Zhang, J. J., & Xu, J. Y. (2014). The influence of semantic transparency and formation frequency on polymorphemic verbs.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2(6), 769–774.
[王娟, 张积家, 许锦宇. (2014). 语义透明度和构词频率对汉语动词多词素词识别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12(6), 769–774.]
Wang, Q. L. (2014). Non-Chinese people learn Chinese polysyllabic strategies. Journal of Hum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5(1), 174–176.
[汪泉兰. (2014). 非汉语人群学习汉语多音字的对策.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35(1), 174–176.]
Wang, Y., Sun, E.H., & Zhang, J. J. (2016). Sentence contexts affec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semantic processing of English phrasal verbs-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 researc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249–260.
[王悦, 孙尔鸿, 张积家. (2016). 句子语境影响汉-英双语者对英语短语动词的语义加工——来自眼动研究的证据.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249–260.]
Wang, Y., & Zhang, J. J. (2014). The masked translation effect with homograph and non-homograph in non-proficient Chinese-Japanese bilingual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6(6), 765–776.
[王悦, 张积家. (2014). 不熟练中–日双语者同形词和非同形词的隐蔽翻译启动效应. 心理学报, 46(6), 765–776.]
Wolff, P., & Holmes, K. J. (2011). Linguistic relativity. Wiley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 2(3), 253–265.
Xu, S. R. (1988). The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causes of more than a word sounds.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 14–18.
[徐世荣. (1988). 一字多音的产生、发展及其原因——《多音字汇览》序. 语言教学与研究,(3), 14–18.]
Yang, C., & Zhang, J.J. (2011). A comparison of the cyclical temporal reasoning between Cantonese-Mandarin diglossic speakers and mandarin speaker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4(4), 782–787.
[杨晨, 张积家. (2011). 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和普通话单言者周期性时间推理比较. 心理科学, 34(4), 782–787.]
Zhang, J.J. (1998). Orthographic depth and lexical cognition. Ludong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39–45.
[张积家. (1998). 正字法深度与字词认知.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39–45.]
Zhang, J. J. (2016). On the 10 relationships of nat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44–50.
[张积家. (2016). 论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十种关系.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44–50.]
Zhang, J. J., Chen, S.Q., Zhang, G. Y., & Dai D. H. (2012). Age of acquisition effects in deaf college student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44(11), 1421–1433.
[张积家, 陈穗清, 张广岩, 戴东红. (2012). 聋大学生的词汇习得年龄效应. 心理学报, 44(11), 1421–1433.]
Zhang, J. J., & Wang, H. P. (1996). A study on orthographic depth of Chinese words and reading tim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8(4), 337–344.
[张积家, 王惠萍. (1996). 汉字词的正字法深度与阅读时间的研究. 心理学报, 28(4), 337–344.]
Zhang, J-J., & Zhang, F-L. (2010). 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bilingualism and diglossia on picture naming and picture classific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2(4), 452–466.
[张积家, 张凤玲. (2010). 双语和双言对图片命名和分类的不对称影响. 心理学报, 42(4), 452–466.]
Zhang, J. J., Zhang, H. C. & Peng, D. L. (1990). The recovery of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classifying process (Ι).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2(4), 63–71.
[张积家, 张厚粲, 彭聃龄. (1990). 分类过程中汉字的语义提取(Ⅰ). 心理学报, 22(4), 63–71.]
Zhang, X. X. (2011). Meaning-spelling theor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writte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5–13.
[张学新. (2011). 汉字拼义理论: 心理学对汉字本质的新定性.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5–13.]
Zhao, J. M., & Fu, D. M. (2013). On the func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assessment in promoting Xinjiang bilingual educati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4), 70–73.
[赵江民, 符冬梅. (2013). 试论双语教学评价在新疆双语教育推进中的作用——以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现状为例. 语言与翻译,(4), 70–73.]
Zhou, X. W., & Li, Y. (2009).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efficiency. Chinese Researches, (1), 62–64.
[周晓文, 李勇. (2009). 汉字效用函数研究. 语文研究, (1), 62–64.]
Zhu, L. (2012). The origin of the polysyllabic characters in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number of pronunciation.The Literary World (Theoretical Edition), (12), 140–141.
[朱力. (2012). 现代汉语常用字中多音字的成因及读音数量考察. 文学界(理论版), (12), 140–141.]
Effects of orthographic depth on Chinese word naming for Han and Uyghur students
YANG Qun1; WANG Yan2; ZHANG Jijia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Cultural, and Psychology;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2, China)(2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ente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with a variety of languages.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among nationalities is basic and important. Hence, bilingual education is a special teaching form in which ethnic minorities inherit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familiarize Mandari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typical alphabetic language, Uyghur differs from Chinese. Specifically, mastering the Chinese polyphonic characters is difficult for Uyghur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more than one pronunciation. Orthographic depth denotes the consistency in grapheme-to-phoneme correspondence. In terms of inner language, polyphonic characters are less consistent than monophonic words. In relation to cross languages, orthographic depth affects the encoding of the lexical proces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rthographic depth on Chinese word naming tasks for Uyghur and Han nationalities.
The word naming task was conducted in experiments 1 and 2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orthographic depth. Thirty Han and thirty Uyghur students volunteered in each experiment, and each one participated in one experiment only. In experiment 1, eighty monosyllabic words with half poly and half monophonic characters were included. Among the poly and monophonic words, half reached high frequencies (343.3–3869.8/per million), and half had low frequencies (7.2–237.8/per million).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name words as quickly and accurately as possible. Repeated measure ANOVA was performed. The results corroborate that (a) naming latencies for polyphonic and monophonic words were longer for Uyghur than Han students, (b) monophonic words were named faster than polyphonic words for all the participants, and (c) the word frequency (WF) effect was larger for Uyghur than for Han students. Moreover, the authors recorded prepared responses using polyphonic words, which were pronounced with high frequency and named faster than the nondominant reaction but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experiment 2, eighty disyllabic words were selected, with the first syllables equally grouped into polyphonic and monophonic characters. Among the disyllable words, half reached high frequencies (222.2–2565.4/per million), and half had low frequencies (2.3–47.6/per million). The procedure was similar to that in experiment 1.The authors performed repeated measures ANOVAs by subject and item and found an interaction between WF and orthographic depth in the two groups. For the Uyghur participants, words with initial polyphonic characters were named slower than monophonic ones in high frequency disyllable words.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id not exist between polyphonic and monophonic characters. For the Han students, words with initial polyphonic characters were named slower than monophonic ones in low frequency disyllable words and displayed the same result with high frequency disyllable words.
The study validates that orthographic depth has different modes of influence on the nam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wo nationalities. This finding is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ther tongue, the age of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e level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he manner of language process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alities.
Key words orthographic depth; word frequency; context; Uyghur
① 民考汉, 是指少数民族学生在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时使用汉文答卷。民考汉的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报考运用汉语言文字授课的普通高等学校或者专业。民考汉的学生在维吾尔族学生中汉语水平最高, 他们从小接受汉语教育, 学校教育与汉族学生几乎没有差异, 可以流利地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写作及阅读。
收稿日期:2018-01-23
*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语言影响人格:来自双语者与双言者的行为与生理证据” (项目编号:17XNL002)阶段性成果。
通信作者: 张积家, E-mail: Zhangjj1955@163.com
分类号B842
DOI:10.3724/SP.J.1041.2019.00001
标签:多音字论文; 维吾尔族论文; 汉字论文; 汉族论文; 正字法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心理过程与心理状态论文; 《心理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语言影响人格:来自双语者与双言者的行为与生理证据”(项目编号:17XNL002)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论文; 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