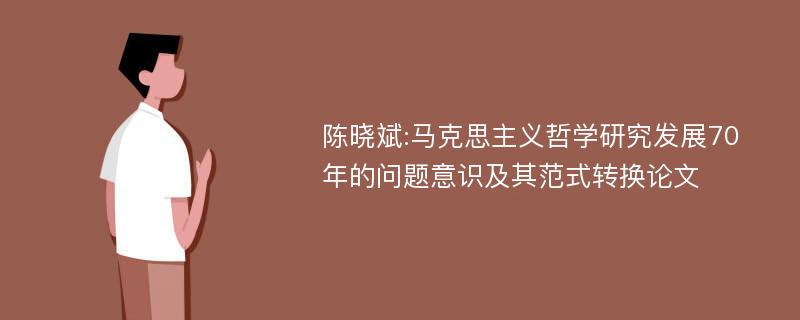
摘 要: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演变具有特殊的问题意识,既涉及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变迁的“时代问题”,也关联理论和文明创新自觉的“学术问题”。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由诉诸教科书体系的权威性走向诉诸经典文本的现实性,由注重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走向注重对中国问题的学理论证,从而主动创构了多元的、学术化的理论范式。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作为当代的“中国问题意识”,标明了走在范式转换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取向和历史责任,即在为中国道路的价值理想提供规范性哲学理念支撑的同时,进一步形成具有文明自觉的“中国化”研究范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意识;范式转换
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70年不平凡的历史征程。回望这一征程,虽然充满各种曲折,但通过不断探索、积累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获得了历史性发展,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范式,释放出巨大的理论能量。就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而言,其发展既缘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变迁在理论上激起的强烈回响,也缘于自身的理论自觉和深层结构。7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往往更加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变迁的历史性、现实性因素,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创构与转换主要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诉求。相比于各种“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必然更加密切。不可否认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更加特殊的发展线索。但应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演变不仅涉及中国社会现实变迁的“时代问题”,而且与理论和文明创新自觉的“学术问题”相关联。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观念和理论意识层面的主动创构越来越成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内在因素。因此,回顾和总结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需要将客观的历史现实因素和主观的理论意识创构有机结合并加以检视,既要洞悉理论发展的现实“所指”,也要在深层结构上理解其内在理路。本文试图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中国问题意识”过程中,进一步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创构与转换的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以此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取向和历史责任。
对图1所示系统,采用固定界面的模态综合法[15],分析塔的横向振动与线面外振动相互耦合时的动力特性.塔的固定截面主模态和约束模态分别假设为
一、体系的权威性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创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这表明,必须具有一种“中国问题意识”,抓住现代中国的历史处境和时代目标,才能深入地把握属于我们自身的、体现“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之理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语境下开始走上学术舞台。此时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9页。的梦想最真切地表达了现代中国的时代需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被社会历史实践证明了的理论体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最能满足这一时代需要的先进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政治指向,即满足两方面的国家需要:一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斗争和交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领导权”;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的制度与思想来引导大众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制度与思想,力求运用彻底的理论说服人、掌握群众并将其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页。
在HTK解码器的研究已经对声学模型的参数调优进行实验。针对Pocketspinx识别工具包的特点,基于对以下参数的调优构建的声学模型。
在实现“文化领导权”和以理论掌握群众的目标过程中,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也全面承续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是以意识形态的解释体系代表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融合学术研究、专业教学和意识形态于一身,成为“三位一体”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正如有学者指出:“它既是毋庸置疑的‘权威体系’,又被视为真理化身的‘科学体系’,还被当作普遍推广的‘教学体系’。”[注]杨学功:《在范式转换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论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三位一体”的教科书体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兼具学理性、现实性和通俗性,在理论斗争中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从思想上武装了广大的苏联民众,并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作用。该教科书体系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进入中国并备受研究者重视,而在建国后随着苏联哲学专家入华指导和大量苏联哲学著作被翻译,其研究范式更是被全面移植,成为一种代表马克思主义最高真理的研究范式。仅就理论研究来看,全面复制和移植苏联教科书体系确实使得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初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苏联“三位一体”的教科书体系在整体框架结构和基本原理叙述上呈现的完整性、严密性色彩,具有强大的说服人和掌握群众的理论力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再只是停留于革命的形式表达和理论书写,而是走向与现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各个层面的结合,并最终以哲学大众化的理论形式融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充分满足了当时“国家的需要”。
在推进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顺势而为,积极回应国内外社会实践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所提出的重大理论挑战,同时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并号召“回到马克思”,力求在整体、系统、深入地消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开创出新的研究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在面对“苏东剧变”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市场经济引发的拜物教普遍化、中国道路崛起引发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重大社会现实时,愈益贴近马克思的问题意识,走进马克思的问题场域,更加自觉地与马克思同行,推动研究范式的转换。从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到认识论、价值论和人学等不同研究方向的兴起,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视野扩展,从文本的深度耕犁到“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路径分化,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性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诠释与建构的研究论域延伸,从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到《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视域深化,从“回到马克思”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研究重心转换,研究者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彻底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研究范式的垄断格局,依据不同的理论资源和研究取向,充满理论自觉和学派意识地建构了各自的学术研究范式,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虽然这些研究范式都独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式,但它们也有共同之处:在思想特质上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现实性,在研究风格上采取学术化的研究态度。这些研究范式都呈现为学术化的治学方式,但并不表示学者的研究一定是远离现实的,有论者就指出:“有的人成天把‘现实’挂在嘴边,其实是‘非现实’地谈论;有的人不怎么喊‘现实性’的口号,但却通过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引导和深化了对现实问题的透视。”[注]杨学功:《在范式转换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论集》,第62页。诸多研究范式对于经典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异质性状况的学术化呈现,正是为了更精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更深入地理解时代精神,从而满足时代的需要。
如果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构出一定程度上属于自身的理论范式,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便摆脱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创构初期的模仿特征,显示出以经典文本和社会现实的交互阐释为中心的多元性、学术化的理论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不再是对某一理论体系的单向度选择与接收,而是理论观念、解释体系和学术认知的纵深发展,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综合变革过程。具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是从单一的建立“文化领导权”以掌握群众意义上的哲学教科书体系走向多元的学术化创新过程,同时也是作为思想指南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深刻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这种范式转换呈现出对经典文本的学术化认知与现实性作用之间的独特关联:一方面,研究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学术化探寻拓展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与广度,既使人们能够以理论自觉的方式去追问、理解经典文本的问题意识与论证理路,也使经典文本自身蕴含的思想力量与当代价值能够被研究者把握;另一方面,研究者的把握不可能穷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意蕴,因为研究者虽然在多元化、学术性的研究中力图从各个视角去理解和逼近经典文本,但是经典文本的思想力量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展开而逐步呈现的。在此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走向了一种诉诸于经典文本而面向社会现实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既力求“发挥马克思主义‘求真’的理性精神,凸显其在学术上的权威性、神圣性和科学属性,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诉求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又力求“发挥马克思主义‘求善’的价值意志,凸显其在实践上的动力性、影响性和政治属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提供现实的动力和源泉”。[注]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32页。
而在2008年,更准确地说,是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家更是加强了对于食品添加剂的监管。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保证人民食品安全列为重中之重,强调了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其中强调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则。与此同时,多项“标准”相继出台,将食品添加剂中22类的使用明确到了具体的食物,更对使用标准进行了严格界定。
二、经典的现实性与学术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权威性研究范式转换为对经典文本的多元性探寻的学术化研究范式,并非意味着其转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性。相反,这种范式转换之所以成为必要与必然,恰恰是因为它认为只有通过多元性的探寻、学术化的认知才能深刻理解经典文本的内在意蕴,才能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孤立化和程式化,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融入中国语境和中国经验,形成具体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论意识,最终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性。
污水换热器换热过程:换热器的一次侧,来自污水主干渠的15℃污水,通过重力作用进入水泵池进行收集。通过污水泵提供机械循环动力,污水进入污水换热器进行换热后,返回污水主干渠。换热器的二次侧,污水换热器启到水源隔离的作用,把二次侧的干净水提升到13℃,进入热泵进行换热。污水换热器的换热效率在90%以上。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广泛使用的是苏联哲学教科书。虽然新中国成立前李达和艾思奇已分别撰写了《社会学大纲》和《大众哲学》两部具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但它们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严密性上都不足以与苏联教科书相抗衡,也不足以成为中国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理论标尺。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甚至两国关系渐趋微妙,并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实质性的意见分歧,苏共不仅公开批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利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优势为自身的政治路线辩护,这使得编写中国人自己的教科书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动因,也由此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理论自觉。1961年,由艾思奇主编的第一本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正式出版,“结束了中国人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注]胡为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9页。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丹岩和高清海教授就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了质疑与辨析,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不是指形式上的彼此联结问题,不是作为组成部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是指内容上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这种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创新性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分化论”而受到了批判。虽然这种个案式的学术清醒和理论建构自觉并不能代表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但后来却成为超越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的改革先河。相关文献参见刘丹岩:《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第8-9页;高清海、邹化政:《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和分化》,《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第56-57页。虽然这部教材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观点依然没有彻底摆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范式,但它作为中国哲学界的一次再创作也具有自身特质,如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强调、对中国化经验的重视以及语言简单、文风清新的特点。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路碑,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创构出了一定程度上属于自身的理论范式,初步显现了理论的自觉。在范式的创构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现实相呼应,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领导权”缔造了深刻的理论斗争武器,而来自底层经验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注]“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一场从1958年延续到“文革”结束的群众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角是工农兵群众,所以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有学者指出:“学哲学、用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因为它并没有具体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没有明确的规划和宗旨;它是一个大时代的产物,带有相当的自发性。参见周展安:《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重探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及其内部逻辑》,《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第112页。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拥有大众化的表达方式。这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也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中重要的语境特征——在思想论争与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孕育出独特的理论形态和研究范式。虽然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自主性探索,但却未能通过追寻经典文本的原初语境、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构方式获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学术认识,更多地将之视为一种直接呼应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解固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担当意识,但在教科书体系中并未能把“中国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未能以学术的方式去加以思考和把握。
从面向社会现实方面来看,虽然对经典文本的深刻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因为这种研究首先要沉入经典文本的问题意识、原初语境和论证理路,也不背离经典文本的基本观点、内在逻辑和理想追求,但是它并不直接把经典文本的思想体系当作论证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是从思想体系中化解出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的内容。换言之,经历种种范式转换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力求从对经典文本的挖掘中开辟出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的新维度,由此加深人们对社会现实、对世界的洞察与理解。因而在学术化的反思性活动中确立起来的研究范式并不只是一种学院化论证的概念体系,还具有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实践关怀、理性关照和学术把握,甚至可以说这种对现实的学术感知与把握才是研究范式更新的原动力。
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改革开放后受到诸多深入的反思和强烈的批评。它在哲学分类的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实体性哲学的解释体系”,[注]王南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9页。属于理论哲学的研究进路;在思维方式上被认为是“相对注重本质与定性思维的哲学”,[注]韩庆祥、张健:《语言分析: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第21页。凸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与真理性;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一种迁就眼前事件的辩护工具,“实际上就成了作为改革阻力的教条主义的一大渊薮”。[注]徐长福:《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态势》,《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第5页。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学界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如何评价教科书体系的研究范式上却存在一定分歧。有学者认为,一些有教科书批判情结的人不对以往的教科书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无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而对之全盘否定、大加讨伐,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创新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注]参见汪信砚:《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27-28页。还有学者针对“体系哲学”“旧哲学思维水平”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个性化”等问题进行回应,认为对教科书体系的批评本身缺乏对教科书的准确理解,且并没有切中问题实质,以“实践本体论”等“新”思路替代传统物质本体论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注]参见郑镇:《科学扬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第45-46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回顾教科书体系研究范式的理论创构,它的确不能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面貌,但也不应忽视它在特定社会现实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种精神实质和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以及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树立文化领导权和促进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历史作用。
从诉诸经典文本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借助多元性的学术化认知来阐明经典文本的内在意蕴时,是在把对于经典文本内在意蕴的阐明方式转化为可以通过学术化分析加以理解和论证的非教科书体系的研究范式,即可以在学术化的反思性活动中确立起来的研究范式。但相对于经典文本的思想体系,这种研究范式始终是开放和未完成的。因为即便我们沿着多元性的学术化研究范式自觉走向经典文本的思想体系,经典文本中与诸研究范式不一致的内容仍将有可能被遮蔽甚至退出现代的解释系统。就此而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更新是不断丰富自身和不断逼近经典文本的过程。当人们走在“回到马克思”的道路上,试图通过多元性的学术认识去理解经典文本的思想体系时,便已不再可能形成任何一种权威性的真理体系,这是改革开放后所有研究范式与作为教科书体系研究范式的最大不同。
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需要而言,“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使得这一梦想的实现遭受了巨大挫折。面对这一历史局面,“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同样迫在眉睫,成为现代中国发展的驱动力量,也造就了全新的历史境遇。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恰切地表达了“文革”之后的国家需要。在此关键历史时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再次发挥了满足“国家需要”的精神武器作用。1978年哲学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犹如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了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18页。激起了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潮流,为打破封闭僵化的政治状态并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从真理标准讨论兴起的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学术起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能够以真诚、学术化的方式直面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增强了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取向与历史责任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回顾过去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已经由一元走向多元,由诉诸体系的权威性走向诉诸经典的现实性,由注重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走向注重对中国问题的学理论证,从而主动创构出多元的、学术化的研究范式。范式问题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问题意识、原初语境和论证理路的理解与阐释,而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学术取向和理论责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发生的范式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面对和审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学术生命力,也是7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发展的重要学术成就。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仍然面临着诸多艰巨的任务,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正在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崛起,也随之带出了各种问题。如何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如何把握并回应中国为自己、为世界带来的新问题,成了这个时代交给其思想者——无论其母语为何——的最大任务之一”。[注]丁耘:《中道之国——政治·哲学论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页。在这一新时代语境中,习近平所提出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的历史使命最充分地唤醒和表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社会的“中国问题意识”,也标明了走在范式转换途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取向与历史责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和价值理想,必然需要一种为应然的社会状态进行伦理辩护的规范性哲学理念作为支撑,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规范性取向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时代境遇使其理论取向更多是以批判社会现实的不合理之处来揭示改变世界之道,故而规范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中一定程度上受到遮蔽。但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理想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思考中国道路的超越性使命,如何为中国人寻求安身立命的正当性根据,甚至如何对具体社会实践中的物化和短视化问题予以反思和剖析,都有赖于对自身理论的规范性向度进行更深刻的揭示与阐发。据此,有论者指出:“要建立起能够真正引导、规范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政治哲学体系,一种能够切中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理论创造便是不可或缺的,而要能够做出这种创造,又必须基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张力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一种独创性的解决方案。”[注]王南湜:《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再检视》,《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1期,第22页。我们必须在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基础上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范性向度研究,从而为解决“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张力”这一根本问题提供具体的运思对象,而这种基于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的理论取向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责任。
从学术研究的现实背景来看,与近代以来国势衰落的大变局相比,当代中国正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问题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构成了文明论上的挑战。这要求研究者首先依据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实践,面向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范式转换,同时必须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来”定位和“他论”思维,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问题”之间一向表现出的主从关系,从而立足于中国道路的文明价值来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不是简单地把“中国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的本土化所产生出来的某种特殊问题,[注]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坚决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强调只有对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467页。而是通过对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重建中华民族的文明理想,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从“古今”的历史发展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是作为认识、批判和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革命学说,为解决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提供先进的理论武器。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理论武器随着中国道路的发展和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复兴,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也从“理论辩护”与“理论阐释”走向了“理论引领”。[注]参见韩庆祥:《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动态》2017年第9期,第12页。但从“中西”的文明交融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送来”的理论学说,[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其在中国的接受、传播与研究不是“单向度”的,其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意味着中国文明主体性的消泯与丧失,反而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特别是新中国70年来的系统整理与消化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文明、中国实践的融合会通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文明自觉的“中国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结合,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而造就了独特的中国道路,也改变了自身,使其开始探索基于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学术研究范式。这种学术研究范式把“中国化”提高到以文明自觉的方式走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从经典文本的丰富内蕴中汲取思想力量,但“始终本乎于当代中国语境而非经典作家来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坐标,进而以之为前提,来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不断推进”。[注]李佃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与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4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必须能为中国道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提供意义解释与价值引领,从而塑造一个具有整全性的文明世界,使得中国道路在经济空间上获得自我认同,同时在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和价值空间上获得肯定自身意志的文明主体性。
中国道路具有自身独特的文明主体性,而且在同其他国家发生历史性关系中展现出某种普遍性价值和发展道路魅力。正如有论者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拓展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实践道路达到了高度的理性自觉,具有参与和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意志,不仅能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提供全新选择,而且能够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智慧和力量。”[注]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史》,第356页。构建属于中国文明自身和体现“时代精神之精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放弃普遍性价值的界定权和对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义的揭示。恰恰相反,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以及“本土问题”与“全球问题”始终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紧密交织的社会现实,因而既需要从中国道路的文明主体性视角去透视世界历史的发展,也需要从全球化视野出发来审视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义。特别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相互的透视与审视必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责任,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要成为具有文明自觉的“中国化”范式,而且要面向全球化的实践敞开,并围绕世界历史进程中凸显的现实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哲学反思与阐释。这将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它将在“中国道路”上充分阐明和呈现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⑥Adam J.Newmark,“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olicy transfer and diffusion”,The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2012,19,pp.151 ~178;Felix Strebel,“Thomas Widmer,Visibility and facticity in policy diffusion:Going beyond the prevailing binarity”,Policy Science,2012,45,pp.385 ~398.
ProblemConsciousnessandParadigmShiftinthe70YearsofResearchandDevelopmentofMarxistPhilosophy
Chen Xiaobi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has shown a special problem awareness, which involves not only the “era problem” of the change of China's social reality, but also the “academic problem” of relating theory to civilization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paradigm shift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has gone from 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the textbook system to the reality of the classical text, and from the focus on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phenomena to the theoretical verification of Chinese problems, thus actively creating a pluralistic and academic theoretical paradigm. China's road of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as “problem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dicates the orien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the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namely, in providing the ideal of Chinese road with normative philosophy support and developing “Chinese style” research paradigm with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Key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problem awareness, paradigm shift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4-0021-08
作者简介:陈晓斌,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广州 51063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演进逻辑研究”(19YJC71001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双重逻辑及超越性研究”(GD18YMK01)、2018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思政’实现路径研究”
(责任编辑:邱 爽)
标签:范式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中国论文; 理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演进逻辑研究”(19YJC710012)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双重逻辑及超越性研究”(GD18YMK01) 2018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思政’实现路径研究”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