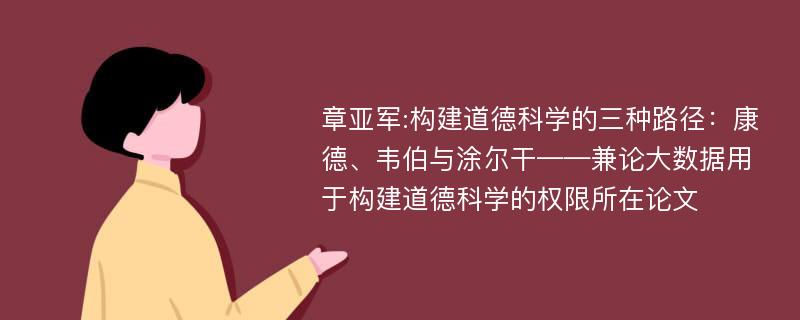
摘要:2015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出台标志着大数据的应用将从市场领域延伸到社会的其他领域。此种延伸意味着经验科学在道德领域的又一次拓展。然而,在康德祛除经验性因素以便维护道德法则普遍必然性的背景之下,这一拓展的合法性不免受到质疑。此种质疑的合法性又必须在康德之后的道德科学的思想史中予以展开。在这一思想史中,涂尔干与韦伯分别重新阐述了经验科学与道德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分别构建了各自的道德科学。与其对大数据应用于道德领域采取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不如效仿康德,进行仔细的划界。于是,本文基于三位思想家对于道德科学的构建,期望阐明大数据用于构建道德科学的权限所在。
关键词:道德科学;康德;涂尔干;韦伯;大数据
2015年,国务院接连发布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和《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两份文件。两者都涉及大数据的应用,但应用范围有所不同。前者局限于市场领域,后者则扩展到了全社会。对大数据的应用,学术界持消极和积极两种态度。持消极态度的学者认为大数据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权,在采集、运用个人信息方面可能存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安宝洋、翁建安2015;陈仕伟2016;董军、程昊2017等);持积极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大数据对伦理学来说是一种福音,它“通过将‘是’与‘应该’连接起来,……不再仅仅定位为对‘技术之是’进行批判的‘应该’”,〔1〕它意味着“认知方式与价值方式‘由分而合’”。〔2〕对前一种态度来说,保护隐私权是普遍认同的共识,我们需要做的是制定使用数据的伦理原则(邱仁宗、黄雯、翟晓梅2014)。后者则涉及伦理学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设想,持该设想的学者认为,依托于大数据,同时结合“是”与“应该”的道德科学可以被建构起来。构建道德科学的努力源远流长,有三位道德理论家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康德、韦伯和涂尔干。他们不仅构建过自己的道德科学,而且分别阐述了经验科学与道德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大数据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新运用,无疑是经验科学在道德领域的又一次拓展。借由这一新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回顾上述三位思想家的理论,阐明经验科学与道德科学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依托的基础,进而揭示大数据用于构建道德科学的权限所在。
一、康德的道德科学
1.道德科学的定义及其与经验科学的关系
康德认为,伦理学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经验性的,即实践人类学;一个是理性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同时,“理性部分实际上是道德科学”。〔3〕经验性的哲学指的是建基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哲学;而理性哲学的原则“仅仅来自于一些先天的原则”。〔4〕
虽然物理学也有上述两个部分,但两者的对象不同。物理学的对象是自然,它的法则“与事物存在的样子相一致”;而伦理学的对象是人类意志,它的法则“与事物应该存在的样子相一致”。所以道德哲学“完全建基在它的纯粹部分之上并且应用于人类,它绝不向我们对人的熟识(人类学)中借助丝毫,而是将法则先天地给予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类”。〔5〕与道德哲学不同,自然哲学涉及的是人类的思辨理性。康德认为,“在思辨理性中,如果普通理性胆敢脱离经验的法则和感性的知觉,它只能跌入各式各样的不可理解性和内在矛盾之中,或者是跌入不确定、模糊和不稳定的骚乱之中”。〔6〕因此,康德感叹道:“这里,我们不得不怀着敬佩之情观察到:在普通人类的理性之中,相比于理论性的判断力,实践性的判断力具有巨大的优势。”〔7〕理性的思辨运用与实践运用的区别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成为康德与功利主义者最为重要的分界线。
2.道德领域中理性与感觉的关系
在道德领域中,康德认为首要任务是为道德原则的普遍必然性寻求真正的根基。如果道德原则不具备普遍必然性,那么道德本身就将荡然无存。因此,所有危害道德普遍必然性的根据都不可能是其真实的根基。
基于上述理论,康德对功利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功利主义认定快乐感是善,痛苦感是恶。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这两种感觉是可以被量化的。快乐越多,善就越大。于是,功利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追求快乐的行为就是符合道德原则的行为。但是康德认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基础根本无法保障道德原则的普遍必然性。因为功利主义关注的是质料,而不是形式,“在追寻幸福之中,需要关注的不是法的形式,而是质料;也就是说,我是否能从遵循的法则中得到的满足,以及这种满足的程度”。〔8〕满足的程度依赖于人的感觉。但是人的感觉既是因人而异的,又是变动不居的。所以这样的道德原则是主观的,是无法满足道德普遍必然性的要求的,“作为法则,它们是主观必然性法则(作为一种自然的法则),客观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实践原则”。〔9〕在康德看来,在确立道德原则的基础之时,感觉是需要被排除的因素。
The first time I met Zhu Bing Ren was during an exhibition of his works in Beijing. I was a little confused by the variety of works he showed.
所以经验科学和道德科学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理性的两种不同应用与感觉的之间关系的区别。理性的实践运用只有脱离感觉方能成就自身,制定出普遍必然的法则;而理性的思辨运用一旦脱离感觉,将坠入充满矛盾的“辩证法”之中。所以理性与感觉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了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两者关系的基础。
从康德的道德理论来说,康德关注于道德原则的共相:道德原则的普遍必然性。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这种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何在?但是道德原则本身是现实存在的,它是本身,而不是它的基础,可以也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韦伯与涂尔干正是抓住这一点来构建自己的道德科学。
二、韦伯的道德科学
1.错误的道德科学与正确的道德科学
综上所述,韦伯和涂尔干的道德科学停留在“是”的领域,康德的道德科学则是“应该”的领域,并不存在一种“是”与“应该”杂糅在一起的道德科学。那么大数据到底可以帮助构建哪一种道德科学呢?我们需要从大数据的特性中寻求答案。
接下来,韦伯进一步说明了他对“科学的评论”的理解:第一步,详细阐明“根本性的、内在一致的价值原则”,〔12〕从这一根本原则中可以演化出有差异的态度。第二步,需要对次生性的现实的道德原则进行研究。这些次生性的道德原则来自于“不可还原的价值原则的含义”的演绎。演绎是两方面能力的结合,“一方面依赖于逻辑,一方面依赖于经验的观察……”。〔13〕第三步,对道德主张得到实行之后的结果进行研究,主要分成两个方面:“(1)与确定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相联系的后果;(2)不是直接期待的确定的不可避免的后果”。〔14〕
基于上述科学的定义,涂尔干认为道德原则是实在,它们是“自成一类的”,有着自己特殊的性质,“如果认为道德是不存在的,需要从别的科学中推出道德来。那么他们违反了先验的原则。我们不想从科学中推导出道德来,而是建立一种道德科学,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23〕
2.韦伯的道德科学与康德道德科学的差异
由此可见,韦伯的道德科学与康德的道德科学大相径庭。由于韦伯坚持道德科学的实然性,而不是应然性,所以他将科学方法限定为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道德领域,它要追问的是已存的道德事实何以可能?换言之,韦伯的道德科学是用康德研究自然科学的先验方法去研究道德原则、主张和生活,而不认为道德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并列但又分立的一门科学。在认清事实过程中,观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观察只能借助于感官;因此,与康德认定思辨理性无法脱离感觉相一致,感觉在韦伯的道德科学中是必不可少的。
与韦伯相一致,涂尔干认为道德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已然存在的道德事实。但是涂尔干的道德事实与韦伯的道德事实有所不同。第一,涂尔干研究的是公认的道德行为和原则,而不是被某部分人坚持的道德主张。更准确地说,涂尔干关注的是“社会的状态,而不是社会的意见”。〔30〕这些公认的道德原则,在韦伯那里被称作为“义务性的文化价值”。第二,涂尔干认为这些道德事实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张力。道德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社会结构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匹配与摩擦。
三、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1.道德科学是关于道德事实的科学
涂尔干认为,“科学是关于事物、事实的科学”。〔18〕而且这些事物必须自成一类(type),否则也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对象。此外,“……这些事物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19〕所以科学的任务是给出这种因果联系。科学不是艺术,“艺术是行动”。〔20〕行动以功用为导向。真正的“科学如此不同于艺术,……完全不管功用”。〔21〕至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涂尔干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区分越是严格,科学对于艺术就越是有用。”〔22〕
由此可见,韦伯认为经验科学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既有道德事实的手段,绝对不能替任何人作出判断,也不能产生任何道德原则。在具体实践中,面对不同的道德主张,人们都应依据自己的内心作出选择,“……这种调整是否应该发生以及从这种状况中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经验科学是无法回答的,事实上任何科学都无法回答”。〔15〕科学在当下只能使人头脑清楚(clarity)。在韦伯看来,道德主张绝对不会因为某一种学科的产生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没有哪一个学科的分支或者哪一门科学知识可以提供一种世界观,不论它们有多么的重要……”。〔16〕
因此,探究道德原则的性质构成了道德科学的第一部分内容。与违反生理原则一样,涂尔干认为违反道德原则的行为也会导致一定的后果。但是前者的后果是从其行为中直接产生的;后者的后果并不是其行为的直接结果,例如对罪犯的惩罚往往是其触犯法律的直接后果,而不是罪行的直接后果。由此可见,道德原则具有康德意义上的义务性,“我们通过严格经验的方式发现了正如康德理解的义务或者责任的概念”。〔24〕但是涂尔干认为,道德原则除了义务性之外,还有令人向往的属性(desirable)。因为“符合道德原则的行为是受到赞扬的,那些实践它们的人是高尚的”。〔25〕涂尔干认为,两种特性没有先后之别,“没有客观的理由使我们承认一种特征对另一种特征的逻辑优先性”。〔26〕道德不仅是义务性的也是令人渴望践行的。这种渴望是一种特殊的渴望,它伴随着“约束和努力(discipline and effort)”。
通过平台的运行,苏南监督检查工作做到事前有标准、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反馈,并通过大数据的分析,集中反映和整改突出问题,整体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NSTEMI患者若出现fQRS改变,则将增加MACE发生风险。fQRS可作为预测该类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接着,涂尔干将道德原则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为道德科学的第二部分内容。
道德原则为何会具有如此特殊的属性?涂尔干认为,可以从道德原则存在的目的中得到答案。涂尔干认为,“一个行动只有两个目的:自我和非我的存在”。〔27〕这里的自我是与社会相对立的个体。如果将个体作为行动的目的,那么这个行动不是道德行动,例如自我保存和自我提高。非我的存在又分为非我的其他个体和非我的集体。如果将作为个体的自我作为目标无法赋予行动以道德属性,那么作为个体的他者也不能赋予行动以道德属性,例如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情人偷东西。所以一个行动的目标只有指向集体存在,这个行动才有道德上的价值。涂尔干感叹道:“公正之所以有意义只有当其目标有高于我们作为个体们的道德价值时才有意义。”〔28〕道德是凝结社会的纽带,社会是道德原则存在的基础。
在国外,像法国的沙木尼休闲登山小镇、伦敦的温布尔登网球特色小镇、新西兰的皇后镇蹦极特色小镇以及意大利的蒙特贝卢纳体育制鞋小镇等成功的体育特色小镇的打造,大多都是在关注禀赋、借助于地缘优势、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加多元化模式的融合,进而开发利用而来的,这为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并坚定了建造的信念。
所以一方面涂尔干认为,“道德和权利的科学应该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事实的基础之上”。〔29〕另一方面他主张社会结构与道德原则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变化。……因此,道德科学的目的就是确定上述这些原因”。
2.涂尔干道德科学的特性:与前两者的比较
韦伯的道德科学以他对社会的定义为基础。他认为,社会由个人组成,祛除个人,社会也荡然无存。所有的生活都变成了经验的生活,“诸神之争”才是主角。在这一时代中,他认为我们所要守护的不是普遍必然的法则,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自己选择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重新运用了康德的“自由意志”。至此,韦伯对于道德科学的阐述看似完美落幕,可是对于社会是否只是个人之和这一点,韦伯本人的态度也存在摇摆。这种摇摆不仅体现在对国家是否是实在的犹疑上,还体现在对“义务性文化价值”存在的肯定上,“因为从一个确定的视角去看,文化价值是义务性的,即使它们与各种伦理学有着不可避免和不可调和的冲突”。〔17〕对于“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义务性的文化价值”到底能不能构成一门道德科学?“义务性的文化价值”成为了涂尔干道德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大数据主张“利用所有的数据,而不再是仅仅依靠一小部分的数据”。〔32〕推崇大数据的人认为一个事件的完整性比局部的精确性更加重要,尽管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一些不精确性会存在,但这些不精确性会随着数据量的增加而减少。
我们发现涂尔干的道德事实的双重规定并不一定与康德相对立。康德确实承认敬重感是与理性相一致的。不同的是康德强调约束性是快乐性的基础,涂尔干则认为两种特征同时存在,不分先后。康德强调约束性的基础性是为了强调理性是道德原则的基础,而涂尔干则认为社会才是真正的基础。道德原则的基础不同才是两位思想家的根本区别。
到此为止,情况变得异常复杂,上文谈到,涂尔干坚持科学的领域是“是”,也就是经验的领域。然而,从经验的研究领域,他却发现了道德基础。这一发现在康德那里完全是应然领域的研究内容,即“与应该发生的事物相一致”。尽管有此复杂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楚,涂尔干道德科学仍然在“是”的领域。只不过他认为从经验角度也可以对道德基础进行探讨。与康德为人的行动立法有所不同,涂尔干对道德原则基础的探讨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于“应该如何行动”的原则。
四、大数据对于构建道德科学的权限
韦伯在《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一文中对一种错误的道德科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种错误的道德科学认为:“一种真实的伦理科学指的是分析一个群体的伦理主张对他们生活条件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分析后者对他们前者的影响;并且这种伦理科学可以产生一种能够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的伦理学。”〔10〕韦伯认为,一种伦理科学绝不能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真正的伦理科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道德主张、原则或生活。道德主张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事实性的价值观,例如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另一类是流行的没有成为“现实”的道德主张。两者都可以作为“科学评论的对象”。〔11〕
影响边坡稳定性因素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诱发因素。其中内在因素包括边坡区地形条件、地层岩性,外在因素包括人类工程活动、降雨入渗、地震力的作用。现阶段影响边坡因素主要为地形条件、地层岩性和人类工程活动,随着雨季来临,降雨入渗将为对边坡稳定起做重要影响因素。
1.大数据的特点:追求整体性和相关关系
涂尔干认为,经验的研究远比康德想象的更加有用。他认为,我们可以从经验的角度发现道德原则的双重特征:义务性和令人向往的属性。涂尔干从这一点出发攻击功利主义和康德,前者忽视了义务性,而后者忽视了令人向往的属性。两种特性都真实存在于道德事实之中。很明显,涂尔干站在功利主义与康德的中间线上,庄严地声称道德原则是有约束的强制和令人向往的快乐的统一。换言之,感觉与理性不是必然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涂尔干认为,“根据康德的假设,义务感来源于感觉与理性的异质,这与道德目的是令人向往的特性是难以调和”。〔31〕
GTM法利用力学原理进行应力应变控制,可有效减少路面车辙,推移等剪切破坏,适用于重载交通路面。本文对比分析马歇尔法和GTM法优缺点,简要介绍GTM配合比设计方法,依托某实际工程,总结GTM沥青混合料施工工艺并对施工后路面进行性能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GTM法设计的沥青混合料路面虽然压实程度略低于传统马歇尔方法,但其泌水性能、抗车辙及高温性能优越。
大数据的提倡者认为,存在两种因果关系,一种是粗糙的因果关系,一种是精致的因果关系。前者常出现错误,后者又耗时过长。因此,他们认为相关关系比因果关系更加重要。通过去探求“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相关关系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这个世界,〔33〕“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34〕
所以大数据只是一门归纳科学,停留在“是”的领域,“大数据模型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并不具有必然性,属于归纳逻辑”。〔35〕
(2) 单边供电模式下2列AW0车测试场景如图2所示。通过该场景可以测得2列AW0车同时起动的电流波形,同时也可以考验单边供电模式下牵引供电系统的极限能力。该极限能力是牵引供电系统故障情况下提供有效运行供电的保障能力。
2.大数据与“是”的道德科学
从道德科学发展史来看,由于感觉与理性可以相一致;所以经验本身并不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没有研究的必要。现存的道德原则有着自己的规定性。它们的存在有一定的土壤。我们无法轻视作为事实的“是”。
大数据的兴起,无疑更加强调了这一点。大数据能够更好地展现道德现状,使我们对当下的道德生活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例如针对中国社会处在道德滑坡之中的论断,有人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对其予以证伪(喻丰、彭凯平2016)。但是大数据这些优势都局限于“是”的领域。
她对周暄咆哮:“咱家孩子先动的手,难道还不应该先道歉?我管不了你到处威风,但儿子现在还小,要是让他学你到处作威作福,我坚决不同意!”
3.大数据与“应该”的道德科学
道德领域的“应该”是在作为“是”的大数据科学之外的,这是康德、韦伯、涂尔干一以贯之的观点。认为大数据科学同时包含“是”与“应该”的学者忽视了这种结合的前提条件。大数据所追求的相关关系之所以能够直接给出行动准则,是因为这些大数据的应用都预设了这一应用的目的。商业公司的大数据应用以盈利为目的,国家的大数据应用以公民的福祉为前提。在这些前提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相关关系中直接得出行动的准则。只要飓风天气,蛋挞可以卖得更好,以盈利为目的的沃尔玛为何不把蛋挞和防飓风用品放在一起呢?如果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可以直接推出道德原则,无需任何前提;也就是说,一看到相关关系,就知道应该怎么做。进而认为商家在无盈利的前提下也会按照大数据相关关系显示的道德原则去行动,无疑是将商家视为道德行动的主体。这与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原则是矛盾的,与现实是矛盾的。在现实中,商家首先只能是一个寻求利益的主体。
大数据必将在展现道德事实方面大放异彩,依托大数据可以尝试建构一种“是”的道德科学。但是这种道德科学与“应该”无关。“应该”的道德科学不仅仅是数据的归纳与分析,此类道德科学的构建必须以普遍的目的为前提,以演绎为手段。
参考文献:
[1]岳瑨.大数据技术的道德意义与伦理挑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5):92.
[2]田海平.“不明所以”的人类道德进步——大数据认知旨趣从“知识域”向“道德域”拓展之可能[J].社会科学战线,2016(9):5.
[3][4][5][6][7]Immanuel Kant.Groundw 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a German-English edition).translation and edited by Mary Greg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5、5、7、37、37.
[8][9]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translation and edited by Mary Greg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23.
[10][11][12][13][14][15][17]Max Weber.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 ard A.Shils and Henry A.Finch.Illinois:Free press,1949:13、12、20、20、21、21、15.
[1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M].阎克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90.
[18][19][20][21][22]Emile Durkheim.Montesquieu and Rousseau:Forerunners of Sociology.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 ichigan press,1960:3、12、5、5、5.
[23]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6.
[24][25][26][27][28]Em ile Durkheim.Sociology and Philosophy.translation by D.F.Pocock.London:Cohen & Westltd,1953:21、21、22、25、25.
[29]Em ile Durkheim.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translated by Cornelia Brookfield.London:Routledge,1957:1.
[30][31]Em ile Durkheim.Sociology and Philosophy.translation by D.F.Pocock.London:Cohen & Westltd,1953:32、22.
[32][33][34]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著.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9、83、75.
[35]张晓强,杨君游,曾国屏.大数据方法:科学方法的变革和哲学思考[J].哲学动态,2014(8):87.
Three Roads of Constructing a Moral Science:Kant,Weber and Durkheim——Discourse the Faculty of Big Data to Constructing a Moral Science
Zhang Yajun
Abstract: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tate Council’s“Action Plan for Promoting Big Data Development”in 2015 marked the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of big data from assisting companies in formulat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assisting the government in social governance.The extension of this application actually shows that the role of empirical science is once again expanding in the field of ethics.Thus,in the context of Kant’s removal of empirical factor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universal necessity of moral laws,it is inevitable to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is extension.The legitimacy of such ques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in the history of moral science after Kant.In this history of constructing moral science,Durkheim and Weber re-examine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irical science and moral science,and also constructed their respective moral sciences.Rather than adopting a total negation or total acceptance of big data in the field of ethics,it is better to follow Kant and make a careful demarcation.Therefore,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science by three thinkers,this paper hopes to clarify the authority of big data to construct moral science.
Key words:moral science,Kant,Durkheim,Weber,big data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1-0015-07
[作者简介]章亚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严瑾
标签:道德论文; 康德论文; 科学论文; 韦伯论文; 数据论文; 《理论界》2019年第1期论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