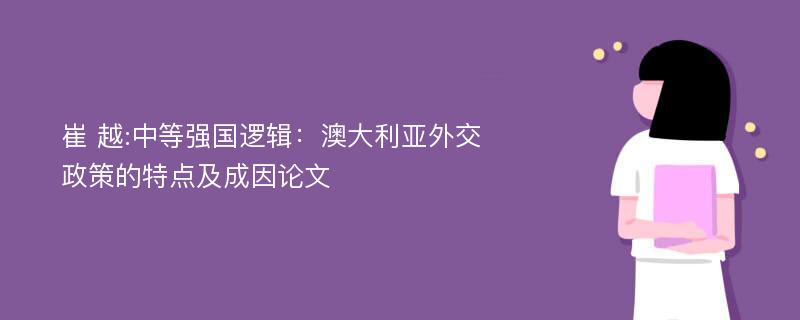
摘 要: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采取与西方强国结盟、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以及通过多边外交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结盟外交、地区外交、多边外交是澳大利亚外交的三大支柱。本文认为,澳大利亚政策的对外行为中的中等强国逻辑,可以解释这三个外交支柱并存的现象,并能够解释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关键词: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结盟外交;地区外交;多边外交
澳大利亚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形成现代外交机构,在二战过程中脱离对大英帝国的依赖,实现了外交独立。二战后,作为真正的独立主权国家,澳大利亚外交开始逐渐成型,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点。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rey Raby)指出,澳大利亚外交有三个重点:第一,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是澳大利亚国防、安全和战略安排的基础;第二,澳大利亚重视其在多边机制、特别是联合国中的地位,以期与他国协调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国际挑战;第三,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全面接触,并为这一地区的未来做出重大的贡献。① 芮捷锐(Geoffrey Raby)、毛悦:《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与中国维度》,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第6页。实际上,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时间里,澳大利亚外交都呈现出芮捷锐所概况的这三个特点。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长期保持这些特点?
一、现有研究及其不足
澳大利亚的独立外交催生于二战,是客观形势与主观意图两方面的结合的产物。② 汪诗明、王艳芬:《论澳大利亚外交机构建置的沿革》,载《学海》2003年第5期,第146-151页;张天、张静抒:《赫·维·伊瓦特与澳大利亚独立外交》,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第57-64页;Maryanne Kelton,More Than an Ally?:Contemporary Australia-Us Relations,Burlington,VT:Ashgate,2008;David McLean,“From British Colony to American Satellite? Australia and the USA During the Cold Wa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History,Vol.52,No.1,2006,pp.64-79;Alan Renouf,The Frightened Country,Melbourne:Macmillan,1979。初期,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从精英到民众普遍认同自己英国人的身份,20世纪初建国以后依然如此。但是,二战的发生使澳大利亚人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生活在欧洲边缘的英伦三岛,当澳洲大陆以及南太平洋地区出现安全危机时,让英国承担责任是不现实的。③赵昌、甘振军:《国内关于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外交研究综述》,载《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1期,第82页。二战时期出任外交部长的伊瓦特(H.V.Evatt)不认同澳大利亚只是英国的附属,主张澳大利亚实现独立的外交与国防。④ David Lee and Christopher Waters,et al,Evatt to Evans:The Labor Tradition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llen&Unwin,1997,p.12。
在结盟外交研究中,历史学家重点研究了《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缔结的背景及过程,突出冷战时代在澳大利亚外交发展中留下的印记,这一条约成为日后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战略的基础。⑤ 汪诗明:《论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复旦大学博士后论文,2006年;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W.David McIntyre,Background to the Anzus Pact:Policy-Making,Strategy and Diplomacy,1945-1955,Palgrave Macmillan,1995。从自治到独立之初,澳大利亚始终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而存在,安全上依靠英国的保护,外交上也缺乏主导权。⑥ Derek Mcdougall and Peter Shearman,Australian Security After 9/11:New and Old Agendas,Burlington,VT:Ashgate,2006,p.106。二战期间,日本在太平洋西岸的侵略威胁到澳大利亚本土的安全,在无法继续依附英国的情形之下,澳大利亚转而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美国”。⑦汪诗明、王艳芬:《论二战期间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载《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第5-10页。科勒尔·贝尔(Coral Bell)将澳大利亚描述成英语世界的一个偏远省区,其首都曾经在伦敦,后转往华盛顿,但是不太可能会在堪培拉。⑧ Coral Bell,Dependent Ally,a Study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03.历史传统成为众多国际关系学者对于澳大利亚联盟外交所采用的主要解释。
历史解释的一个分支是以澳美两国的同质性来解释澳美同盟,但存在明显缺陷。虽然两国具有相似的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⑨ Philip Bell and Roger Bell,Implicated:The United States in Australia,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持有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但这难以构成澳美同盟得以维持的主要动力。历史、文化以及价值观上的同质性仅仅是澳美结盟的有利条件而非决定性条件,因为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同质性比美国更强,而二战后澳大利亚却疏远英国、转投美国。以历史为角度和方法的研究,往往能够对具体事件条分缕析,但是不利于从宏观上把握澳大利亚外交发展的逻辑。
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依附性”被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提出来。在安全上有接受西方强国庇护的传统,在外交上习惯于协调与让步,依附强国至今仍然是澳大利亚外交最具典型意义的现象之一。新近的研究表明,澳美同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持或者增强合作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力,但是澳大利亚依旧没能摆脱对同盟的“依附性”。冷战结束后,澳美同盟并没有随着东方阵营的的瓦解而削弱,反而有所加强。澳大利亚一些决策者认为,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增加了多种不确定性因素,恐怖主义威胁、中国的崛起相继成为安全议题的新焦点。⑩喻常森:《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70-86页。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保持海上贸易航道畅通等也为澳美同盟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解释。⑪任远喆:《澳大利亚海洋战略的构建及其困境探析》,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5期,第72-78页;凌胜利、宁团辉:《冷战后美澳联盟为何依然存在?——基于海上航道安全的理解》,载《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第59-68页。另一种意见认为,冷战以后澳大利亚没有放弃澳美同盟而选择继续追随美国,是为了获得国际地位的提升,从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⑫岳小颖:《冷战后澳大利亚为何追随美国》,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38-62页。但这些解释仍然都是从澳大利亚单方面去归因澳美同盟的发展,而非从澳美双方的需要、在更广阔的国际关系中寻求对这一联盟的解释。
在众多解释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与“地理”间的“两难困境”,不仅吸收了历史研究的成果,还将地缘安全的现实视角包括起来,实用性很强。特别是在地区外交的有关问题上,它因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被众多学者所采用。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高官艾伦·雷努夫(Alan Renouf)就将地理和历史认定为澳大利亚外交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认为地理因素大大增加了澳大利亚外交的复杂性。⑬ Alan Renouf,The Frightened Country,Melbourne:Macmillan,1979,p.11.澳大利亚地处太平洋西岸的南端,并横跨太平洋与印度洋两大洋,与东南亚隔海相望。二战后亚洲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澳大利亚逐渐认识到亚洲对于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在这一大趋势之下,澳大利亚外交的重心从远在欧洲的英国转向自身所在的亚太,积极参与到地区事务中。历史则强调澳大利亚的盎格鲁-萨克逊认同对于其外交政策的影响。⑭ Alan Renouf,The Frightened Country,Melbourne:Macmillan,1979,p.14.白澳政策反映出澳大利亚对英国人身份的认同,这时候澳大利亚是大英帝国在太平洋西岸的延伸,亚洲国家是殖民和防范的对象,而不是发展友好关系的对象。当澳大利亚认识到自己的地理现实,形成独立国家的认同,亚洲才成为它真正的邻邦。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反映了这样一种转变,在二战中中国曾经是澳大利亚对日本绥靖的牺牲品,战后也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反共的主要对象,在建交30年的时间里发展为澳大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移民最重要的来源国。
同盟建立后,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澳大利亚毫无例外地出现在二战后美国组织和领导的每一次主要战争中,越南战争使其深陷泥潭,伊拉克战争充满争议,但都没能扭转澳大利亚继续向美国买保险、继续向澳美同盟续“保费”。通过战争中的合作,两国军事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融合程度之高在国际关系中堪称罕见。战后至冷战时期保守党长期执政,“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日常规范,结盟外交的地位越发难以撼动。进入21世纪,在反恐以及应对中国崛起的新形势下,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被重新发现,澳美同盟换发出新的活力。㉟喻常森:《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82页。澳大利亚颁布的《2013年国防白皮书》承诺加强两国间空军、海军的合作、允许美国海军使用澳大利亚在印度洋的海军基地。㊱ 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3,May 2013,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2016年国防白皮书》进一步表示,澳大利亚国防开支将在未来十年大幅度增长,重点用于升级达尔文港、斯特林海军基地和科科斯岛的军事设施,进一步向美国证明其战略支点的价值。㊲ 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6,February 2016,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2016-Defence-White-Paper.pdf.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牲畜是被认为很低贱的,常用来骂人,《资治通鉴·隋文帝仁寿四年》:“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胡三省注曰:“今人詈人犹曰畜生。言其无识无礼,若马牛犬豕然,待畜养而生者也。”在众多牲畜中,驴被认为比其他牲畜更为低贱,也常用来骂人,例如蠢驴、犟驴等。
流水施工具备可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应可以减少工人人数和临时设施数量,从而可以节约投资,降低成本;同时专业化施工,有助于保证工程质量的优点,具有很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虽然对澳大利亚的三个外交重点分别提出了一些解释,也有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但是这些解释却没能够将三个外交重点串联起来,这就使得学界对联盟外交、多边外交和地区外交的考察仍然呈现零散的状态。将每一种外交仅仅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来看待,而非将澳大利亚战后外交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由此形成的对澳大利亚外交的认知必定是碎片化和片面化的。而且这些解释都是从澳大利亚方面所提出的解释,并没有从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去考察。
针对索拉非尼治疗失败的二线靶向药物的研究结果继续支持瑞戈非尼可作为肝功基础及体力状态评分较好晚期肝癌患者的二线靶向治疗药物。美国西奈山医学院Llovet等(摘要270)报告了两项使用雷莫芦单抗(RAM)的全球多中心3期临床研究,提示RAM作为HCC接受索拉非尼治疗后进展或不耐受的中晚期HCC且AFP≥400 ng/mL的二线治疗药物,mOS为8.1月,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显著的临床获益。瑞戈非尼作为二线治疗有效的药物,mOS为10月。该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
一部分中等强国表现出多边主义行为倾向和特征,战后一些维和、斡旋等多边主义行为呈现出浓重的理想主义、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意味,一部分中等强国乐此不疲地参与到其中,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行为主义对此的解释是,中等强国在多边外交中更有机会将实力转化为影响力,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建立暂时性的联盟,充分发挥创造力,以获得国际信誉和国家形象的提升。这些中等强国具备独特的优势,他们与大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主导和称霸的野心,而与小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去实践和平的主张。
二、中等强国外交及其行为逻辑
中等强国是我们对一些国家人为划定的类别。中外学者对于中等强国的认定标准可以归入两个维度:(1)实力维度,即通过考察一国的物质性实力(主要指人口、领土、经济力和军事力)以及非物质性实力(主要指外交力、国内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来判定其国家实力是否处于国际体系的中间位置。㉒ 参见王逸舟:《对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一种调研》,载《欧洲》1996年第3期,第4-12页;第45页;Carsten Holbraad,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Macmillan Press,1984;冈萨雷斯著:《何谓“中等强国”?》,汤小棣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第43-44页;黄硕风:《大国的较量: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国际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马丁·怀特著:《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王诵芬主编:《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 Publishing,2004;唐纲:《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2)心理维度,即通过考察一国领导人的心理认同来判定该国是否具有中等强国的“国家心态”。㉓ Robert O.Keohane,“Lilliputians’Dilemmas: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3,No.2,1969,pp.295-296.用实力来界定中等强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而心理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对实力界定进行必要的补充。本文统合这两派的观点,认为中等强国是那些国家实力处于大国和小国中间,并具有清晰的中等强国认同的国家。㉔崔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以此为基础,本文主张中等强国所践行的外交,就是中等强国外交。首先,中等强国外交明显受到其中等强国实力的支撑以及限定。中等强国的国家实力是其外交行为的基础,并为其选择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人口与领土是这一实力的底盘和基础,经济力、军事力构成物质性实力的主体,外交力、国内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等非物质性实力则直接影响到外交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中等强国外交立足于中等规模的国家实力,在外交议题上享有一定的选择空间,但绝对无法全面铺开;同时中等强国对于外交战略的选择也需要发挥实力优势方面以及弥补弱势,从而达成一定的目标。其次,中等强国认同将中等强国外交引向特定的道路。为了在安全上保全自己、在经济上获得繁荣,中等强国可能会倾向于结盟,当可能与其所信任的军事强国结盟时尤其如此。另外一种倾向性是在多边国际机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反过来自己的国际参与也应当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与尊重。而中等强国的身份认同塑造其外交行为的意愿,为其发挥实力采取行动提供主观动机。基于以上两点,中等强国外交行为逻辑以中等强国的实力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中等强国的身份认同作为必要条件,来分析其外交行为。
(一)地缘安全与中等强国的联盟外交
结盟行为往往是应对一国在安全上的挑战,而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息息相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每个国家由于身处不同的地理位置而面临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这对国家采取何种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形成重要的制约。中等强国也不例外。中等强国在综合实力上构成仅次于大国的第二梯队,但是具体来看这些国家的各项实力,往往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一些经济发达的中等强国,军事实力可能受到军队规模的影响,与其地区大国的身份并不相称。这样的中等强国如果处于不利的地缘安全环境,会选择如何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呢?
第一种选择就是居中,但是这样做的条件是它认为自己可以在对立的大国中间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和外交空间。克劳塞维茨指出,中等国家能够在敌对紧张的大国中间起分隔作用、并具有一定自卫功能。㉕ Carsten Holbraad,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23.冷战中,加拿大力求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认为这样对自己更为有利。另一种选择则是选边,即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以应对威胁。同盟理论对结盟动机的解释中,威胁存在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威胁的水平不仅决定于实力分配,更受到地缘的毗邻性、对于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的主观认知的影响。㉖斯蒂芬·沃尔特著:《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因此,同盟行为是中等强国在面临地缘威胁时的一个重要的可选项。对威胁的认知将行为主体国的认同因素包括进来,大大增强了对结盟原因的解释力。
而另一方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大国愿意与中等强国结盟则为这种联盟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超级大国欲控制亚欧大陆,无论是心脏地带还是边缘地带,海军都是这一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海权的维护必需要相应的海外基地及战略依托,这就给中等强国提供了发挥地缘价值的可能。一个全球性大国,即使自身拥有优厚的海事条件、强大的海军军事实力,也难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在超出本国领土很远的地方去获得和维持国家利益。它的海上实力需要从本土向外延伸,而当殖民主义已不再成为选择,只有通过与盟国的战略合作才可实现。即使在“空权论”对“海权论”提出修正后,这个逻辑仍然有效,因为要保证有效的制空权,必须在合适的地点设置空军基地,不仅供飞机起降补给,也为导弹发射及拦截提供设施。
从地缘安全上来说,中等强国在认知到威胁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可信的强国作为结盟的选择,那么结盟的优越性不言而喻。也就是说,与强国结盟是符合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的选择。追随强国不仅能够规避安全风险,同时还能获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同时意味着中等强国需要为结盟付出代价。当中等强国面对安全挑战时,结盟是一种选择,但并非唯一选择,也不一定是最优选择。
(二)功能主义与中等强国的地区外交
中等强国外交受限于国家综合实力和外交资源规模,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议题上表现出更强的选择性,这正是中等强国外交聚焦于本地区的行为逻辑。功能主义中等强国理论揭示了这一行为逻辑,为中等强国选择积极参与本地区事物、在地区机制中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所谓功能主义,就是一国在参与国际治理时按照其在政治权威的功能性结构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实力,获得不同的地位和对待。㉗ For more,please see David Mitrany,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33,p.118,quoted in The Canadian Middle Power Myth,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5,No.2,2000,pp.183-195.二战后期在国际秩序重新确定、特别是联合国筹建过程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对自己的国际定位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战争功臣的身份对此提出了要求。他们依据“功能主义原则”,㉘ Adam Chapnick,“The Canadian Middle Power Myth,”pp.188-206.主张自己在某些国际事务上具有更强的利益相关性、依据其资源以及技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在这些问题领域应享有较之于其他较小国家更大发言权。
在多边机制中,中等强国可以与利益相近的国家联合起来,改变与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从而改变国际事务的进程或者走向,以实现本国的利益。澳大利亚在近几十年的多边外交实践中,特别注意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表现为在具体事务上与持有相同立场的国家协调行动而结成暂时性联盟。澳大利亚每一个多边外交的成就都是对该策略的成功运用,它也是澳大利亚从多边外交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由于这种关系没有正式的承诺作为保障,因而更加需要外交资源的投入,这却是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的优势所在。
澳大利亚外交集中于地区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地区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地区外交的内涵也随之改变。澳大利亚的地区认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呈向外扩展的趋势。西南南太平洋地区认同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范围仅限于与澳大利亚大陆最邻近的一些岛屿,包括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一些其他临近群岛。南太平洋被澳大利亚看作后花园,这个地区大国间相对实力的消涨,往往挑动澳大利亚最敏感的神经。向北延伸出去,澳洲大陆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隔海相望,这些岛屿构成澳大利亚与亚洲的连结点。地理距离上的临近和心理距离上的遥远使澳大利亚对亚洲总是存在一种矛盾心理,甚至是被亚洲国家入侵的恐惧。㊴ Rawdon Dalrymple,Continental Drift: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gional Identity,Burlington,VT:Ashgate,2003,p.6.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它从来不属于亚洲,但是与亚洲大国的关系却发展为澳地区外交的重要内容。先是日本、继而是韩国、中国,如今东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其中,成为澳大利亚举足轻重的经济伙伴。与亚洲国家交往中,澳大利亚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动机。
该异常带北部延出界外,与迪彦钦阿木大型钼多金属矿相连,具备良好的成矿潜力。根据地物化综合剖面测量,选择较好的激电异常地段,在16线布设了激电测深(图3)。
中等强国以地区外交作为重点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其国家实力所决定的。国家的综合实力越强,其利益分布的范围越广,其需要以及实际发挥影响力的范围也就越广。真正在众多议题上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国家只能是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而对于中等强国来说,地区是其外交的主战场,是其设定国家利益的主要范围,也是其发挥影响力的主要舞台。
(三)行为主义与中等强国的多边外交
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开始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舞台,因此多边外交是所有国家展示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舞台,但是它对于中等强国尤其重要。中等强国是通过多边外交迈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因此多边外交与传统的西方中等强国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联合国的建立,见证了中等强国从芸芸小国中脱颖而出,并且成为中等强国实现其国际影响的重要场所。早期研究中等强国的西方学者指出“如果联合国不存在,很难想象中等强国的功能如何发挥”。㉛ John Holmes,“Is There a Future for Middlepowermanship?”in J.King Gordon and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eds.,Canada's Role as a Middle Power:Papers Given at the Third Annual Banff Conference on World Development,August 1965,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6,p.20.
要揭示澳大利亚战后外交背后的行为逻辑,需要从澳大利亚与其主要盟国、主要的地区国家乃至更广泛国家的相对关系和互动中去寻找。对澳大利亚多边外交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显示,中等强国外交能够解释的范畴远远不止于多边外交和工党外交。这为本文指出了突破的方向,即从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强国的事实出发来分析澳大利亚战后三大外交重点的成因以及相互关系。在这里,中等强国不再是一种外交路线,而成为一个可以完整解释澳大利亚战后外交的行为逻辑。㉑关于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参见崔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从澳大利亚方面来说,与美国结盟是其护卫自身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㉝ Alan Renouf,The Frightened Country,Melbourne:Macmillan,1979,p.3.这构成澳大利亚与美国结盟的必要性。澳大利亚地广人疏、军力有限,始终对于毗邻的亚洲和自己的国家安全怀有深刻的忧虑。㉞ Rawdon Dalrymple,Continental Drift: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gional Identity,Burlington,VT:Ashgate,2003,p.6.美国远离澳大利亚,但是掌握着先进的现代军事技术,其军事能量远射到美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如前文所述,依附强国是中等强国在国家安全上的重要选择之一,美国使这一选项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对于同盟所带来的利益都是乐于接受的。在结盟的大框架下,工党主张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是因为在它的认知中,美国不一定靠得住,因此澳美同盟不见得是应对安全挑战的最佳选择。
多边外交有利于中等强国整合外交资源、投射外交能量,至今仍然是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选项。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看,中等强国似乎是在某种感召下对多边外交投射了特殊的情感,这与其中等强国认同是紧密相连的。尽管行为主义的解释并不总是站得住脚,但不可否认,它揭示出中等强国认同是好善乐施表象之下推动一些中等强国去积极践行多边外交的真正动力。
三、澳大利亚外交的中等强国逻辑
(一)结盟外交
在澳大利亚的外交史上,结盟始终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性,与美国的同盟是澳大利亚二战后外交的首要方面和第一支柱。从两党政治的角度说,澳大利亚保守党更热衷于结盟外交,总是抱着将国家安全托付于西方强国的执念。但对于澳美同盟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工党领导人也从未否认,这充分说明了结盟外交是跨越党派的共识。㉜汪诗明:《澳美依附同盟关系——二战后至越战期间澳美关系研究评述》,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第121-122页.因此仅仅从依附传统的角度去解释结盟外交是有失偏颇的。澳美同盟在二战后乃至冷战后不断向更紧密的方向发展,并不是澳大利亚依附的历史所决定的。业已成为两国政府重要外交资产的澳美同盟,是一对高度互信的大国和中等强国之间相互需要、不断互动的结果。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实力和身份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它与强国结盟是符合本国利益和现实的选择。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所表现出的“依附性”实际上是其中等强国认同的折射。
另一种分析则主张理智地看待中等强国的多边外交,不能因为某些善行过分美化和理想化中等强国。如同大国和小国一样,中等强国的多边外交同样体现着国家的私利。冷战后中等强国的多边外交更多是体现着国家利益考量的国际主义行动。
式中:x=(xS1,yS1,xS2,yS2,…,xSN,ySN)表示2N维的决策变量,y表示2维的目标向量;f1(x),f2(x)分别是节点安全连通度目标函数和节点网络覆盖率目标函数;∀i∈[1,N],∃j∈[1,N],i≠j,满足d(Si,Sj)≤Rc是节点的全连通约束,其中d(Si,Sj)表示节点Si,Sj之间的欧氏距离;为节点移动能耗约束,为节点优化后与节点最初位置之间的距离,dth是节点允许移动的最大值。
All animal procedure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and the animal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the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at the Institut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中等强国外交也是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解释,但是一般只被用来解释澳大利亚工党的多边外交政策,甚至则沦为政党政治的工具。⑮ Matthew Sussex,“The Impotence of Being Earnest? Avoiding the Pitfalls of‘Creative Middle Power Diplomacy’,”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5,No.5,2011,pp.545-62;Mark Beeson,“Can Australia Save the World?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5,No.5,2011,pp.563-577。在政党政治的外衣下,对于澳大利亚多边外交的关注多集中在工党执政时期澳大利亚对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参与。⑯ Rod Tyers,“The Cairns Group and the Uruguay Roun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Vol.101,1993,pp.49-60;汪诗明:《澳大利亚与军备控制、裁军和核不扩散机制》,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70-75页;刘樊德:《澳大利亚为何得以领军多国部队进驻东帝汶?》,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11期,第25-26页。旧金山会议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偏爱的研究主题,伊瓦特在旧金山会议上以出色的表现带领澳大利亚打破大国对联合国的垄断,这成为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起点。⑰ Daniel Mandel,“Dr H.V.Evatt at the United Nations:A Crucial Role in the 1947 Partition Resolution for Palestine,”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Vol.29,1999,pp.130-151.他以勇于表达、坚定果断、积极行动的个人风格发出了澳大利亚的声音,成为澳大利亚国际形象的可贵遗产。其他的历史学家则发现,澳大利亚保守党外交家在联合国外交中也有很突出的表现,同样应当被涵盖在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中。⑱ David Lowe,“Australia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1950s,”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1,No.2,1997,pp.171-181.工党明确将中等强国外交作为目标,而保守党为了区别于对手则倾向于避免使用这一标签。⑲ 唐小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第14-19页;Richard Leaver and David Cox,eds.,Middling,Meddling,Muddling:Issues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St.Leonards,N.S.W:Allen&Unwin,1997.但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身份并没有变;更重要的是,两个主要党派都具有中等强国认同,这一深层认同决定了两党所进行的外交都是中等强国外交。⑳崔越、牛仲君:《“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0期,第37-47页。将中等强国外交仅仅用作工党多边外交的代名词显然是不合适的,中等强国外交不应当仅仅是工党外交,也不应当仅仅是多边外交,而是澳大利亚这个中等强国所践行的外交。
从美国方面来说,与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强国结盟,是其实现全球战略的有效手段。美国身处北美,与欧亚大陆岛和非洲大陆被太平洋和大西洋所间隔,要将军力投放到全球各个地区去,需要依靠海军、航母的远洋投送,更需要依靠盟国在各战略要点提供的军事基地作为支撑。如澳前外长埃文斯所指出的,澳大利亚“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独特位置”以及“在这两洋的港口”,对于美国“维持它的全球角色”具有重要的意义。㊳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Carlton,Vic: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1,p.327.澳大利亚的战略重要性与它中等强国的实力也是分不开的,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盟友,能够更好地成为美国地理、政策乃至战略的延伸。
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将与大国结盟看作一种可获得安全保障又可节约成本投入的国际战略,从而表现出了强烈的结盟倾向。地缘安全上的忧虑形成强烈的结盟动机,而澳大利亚的地缘特性对于美国来说具有战略价值,于是两国间同盟的缔结与维持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利用自身地缘安全上的价值,在二战后与军事最强大的美国建立和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符合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实力现实和心理取向。
临床带教老师在其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选择责任心强、理论知识扎实、认真负责、热爱护理岗位的带教,并且定期进行理论及操作技能的提升,必要时还应定期外出学习以更新知识。按期召开教学方法会议,每年度进行能力测评,优胜劣汰,有利于整体带教老师资质的提高。
(二)地区外交
20世纪90年代,“优势外交”(niche diplomacy)(也译为“利基外交”)成为新时期中等强国外交的代名词。“优势外交”同样建立在中等强国以功能主义作为组织原则的行为模式的基础之上。㉙ Andrew F.Cooper,“Niche Diplomacy:a Conceptual Overview,”in Andrew F.Cooper,ed.,Niche Diplomacy: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London:Macmillan,1997,pp.3-4.“优势外交”反映了与“地区外交”同样的局限。相比于“大国能够同时下多盘棋”,㉚ John Ravenhill,“Cycles of Middle Power Activism:Constraint and Choice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ies,”p.311.中等强国外交必须有所取舍,集中于自己的优势区域和优势领域。实力与行为之间的逻辑决定了中等强国只能选择“优势”。
学生内在原因一方面体现在其自我防护意识的薄弱,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心理特点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自我防护意识受到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若在就学期间缺少相应的教育,接触社会少,思辨能力差,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改变其初心。还有很多学生在宿舍里乱用违章电器,缺少防火意识,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就无法从容应对等。心理特点的复杂和多样体现为在学习压力、生活压力或周边环境的影响下,很多学生会存在或轻或重的心理问题,承受能力不强,遇到困难就容易选择极端的处理方式。这些心理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3]。
CNNIC截至2017年12月的统计数据现显示,在线旅游用户规模已达3.76亿,在线旅游预定使用比例占48.7%,网上预定火车票占39.3%,线上预订机票酒店占23%,线上购买旅游度假产品的游客占11.5%。从数据可以看出,手机已经成为出行预定的主要渠道,通过手机订购旅行产品的用户规模已达3.40亿。
作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在地区外交中,积极追求实现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这在亚太概念的提出和推广、地区机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当融入亚洲的努力遭遇尴尬,澳国内也难以统一意见,澳转而推动亚太概念。借助亚太概念,澳大利亚希望建构一个更加符合自己利益的地区。一个包括了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必然更有利于澳大利亚,澳甚至于可以充当太平洋东、西两岸之间的桥梁。㊵崔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亚太地区外交兼顾到澳大利亚发展经贸和维护安全的双重需要,其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 的参与有效提升了它的地区影响力。
“印太”(Indo-Pacific)概念的兴起,使澳大利亚的地区认同从太平洋扩展至印度洋,实现了地缘战略空间的再界定。“印太”概念承认了澳大利亚作为两洋大陆的独特地缘战略地位,㊶ Peter Varghese,“An Australian World View: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a speech to the Lowy Institute,August 20,2017,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address-peter-varghese-aoaustralian-world-view-practitioners-perspective.而且澳大利亚将首次成为自己所在地区的中心。在这一框架下,澳大利亚也将在未来海洋权力结构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㊷任远喆:《澳大利亚海洋战略的构建及其困境探析》,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5期,第72页。因此“印太”概念的推出明显包含更多战略的考量。澳大利亚政府在《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首次重点推出了“印太”概念,《2016年国防白皮书》继续沿这一思路推进。㊸ 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3,May 2013,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6,February 2016,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2016-Defence-White-Paper.pdf.《2017年外交白皮书》以“印太”战略框架制定了具体的外交方针。㊹ 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November 2017,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
澳大利亚的“印太”版图日渐清晰,“印太”外交的走向却尚未明了。“印太”外交所应对的正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所带来的挑战。经贸关系快速发展早已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可同时对中国的不认同和不信任令澳大利亚感到焦虑。《2017年外交白皮书》中充斥着对中国改变现有秩序的焦虑。㊺ 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November 2017,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p.35,p.1,p.iii;Peter Hartcher,“How a Worried Australia Should Deal with a Mighty and Demanding China,”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November 23,2017,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opinion/how-aworried-australia-should-deal-with-a-mighty-and-demanding-china-20171122-gzqwg2.html.经济上对国有企业赴澳投资抱有疑虑,政治上控诉中国政府干涉澳大利亚政治和渗透澳大利亚社会,媒体掀起一波又一波反华浪潮,不无反映出这种焦虑。当中国的强大到足以挑战到美国的霸权地位,澳大利亚的地区外交终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如果可以选择,澳大利亚会希望澳洲大陆是在英国旁边,或者在北美大陆和欧洲之间。当然澳大利亚无法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于是它选择创造更符合自己需求的地区。这种想法推动着澳大利亚参与亚太合作,并先后成为将“亚太”、“印太”这两个地区概念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以期建立和实现更有利于本国的地缘战略空间和地区秩序。澳大利亚认识到,作为中等强国自己有实力也有可能在地区机制中发挥作用。不断创新地区概念推动地区认同,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地区行为,符合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身份特征。
(三)多边外交
澳大利亚敏锐地意识到多边机制为自己这样的中等国家所带来的好处,支持多边外交的澳大利亚政治家认同其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争端解决中所能发挥的催化剂、协助者和管理者的作用,㊻ See Andrew Fenton Cooper,Kim Richard Nossal and Richard A.Higgott,Relocating Middle Powers: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Vancouver:UBC Press,1993,pp.24-5.希望借助多边外交的方式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学者大卫·李(David Lee)在描述中等强国概念时,也认为它不仅描述了一种处于中间的国家实力,同时强调了一种行为方式,就是在国际论坛上通过多边外交的方式发挥出超过其本身实力的影响力。㊼ David Lee,“Australia as a Middle Power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a seminar paper at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p.1.
课堂上,我和孩子们玩起了“头脑风暴”的游戏,并采取“延迟评价”的课堂机制。我常常会设计一至两个开放性问题,然后让学生大胆猜测、联想、迁移。我告诉他们,答案并不是唯一的,只要是自己努力思考的结果,只要言之有理,就是最好的答案。当课堂形成接纳、支持、包容的氛围后,学生的发言变得踊跃起来。当一些学生有了答案后,我不会立刻让他们回答,而是等举手的学生多起来以后,再点名回答。这样做的目的是给更多的孩子创造思考和回答的机会。学生回答结束后,我也不急于点评,而是先让其他学生来评价。这样一来,所有学生都能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发言的尽心尽力,聆听的竖起耳朵,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容量,也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的专注力。
中等强国的问题领域很多集中在本国周边或者所在的地区,因此中等强国要求在地区事务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在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并肩战斗,有力地支持了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应给予中等强国优待的讨论。这将“功能性代表权”进一步扩大到地区代表权,从而使具有地区大国身份的中等强国在争取代表权时更具优势。结果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设定的标准,选出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与中等强国形成一个很大的交集,甚至于非常任理事国此后成为一些学者用来判定中等强国的指标之一。
澳大利亚的两个主要党派都习惯以对外联合的方式来应对安全挑战,实现外交目标。保守党支持正式的同盟,而工党更偏好非正式的、临时的、单一的“事务联盟”。,两个党派都选择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国家联合在一起,以实现其生存与发展的双重目标。这是以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实力现实为出发点的,也印证了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是跨越党派的。㊽ Carl Ungerer,“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History,vol.53,no.4(2007),p.540;崔越、牛仲君:《“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0期,第37-47页。在有所区别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保守党将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悬在依靠强国这一选项上,因此表现出“依附”或者“追随”的特征,而工党寄希望于集体安全和多边主义,因此表现出相对的“自主”特征。同时,两党轮流执政使它们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对手的外交遗产。以上两种对外联合行为进一步表明,澳大利亚结盟外交和多边外交都包含着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
如果要理解这些肿瘤的性别差异的关键在于找出性别差异的原因,而且这将有助于优化性别相关的治疗,揭示可能的保护性或者有害的性别因子,并提出新的治疗策略。尽管一些肿瘤的性别差异源于高度性别化的环境(职业、吸毒等),这使得男性和女性暴露于不同的疾病风险,但还可以寻找在细胞内关键的性别差异,从而降低肿瘤生长的可能性。性激素是主导性别差异的原因,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更关注细胞内基因组中的性别差异。
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出现“领导力真空”的情况下,有能力和抱负的中等强国还有可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冷战后期美国经济实力的绝对优势呈现下降趋势,经济以及环保等非传统安全在国际议程上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也为中等强国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可能。澳大利亚外交抓住了一次“领导力真空”的机会,80年代末、90年代初见证了澳大利亚多边外交的又一次高峰。在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召集了12个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组建了凯恩斯集团,协调彼此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的立场、统一行动,大大加强了这些较小国家在谈判中的力量。凯恩斯集团被认为是“多边谈判中最为罕见、团结和有效的国家联合”,㊾ Ann Capling,Australia and the Global Trade System:From Havana to Seattle,Cambridge,2001.也是澳大利亚在多边外交中成功发挥其中等强国领导力的经典案例。
在多边外交中,澳大利亚外交试图遵循一种“国际现实主义”,在“国际主义”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柬埔寨维和等行动都表明,澳大利亚的多边外交是有所选择的,有着明确的地区重点和领域重点。这些暗含着国家利益诉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国际主义”的行动,为澳大利亚赢得了国际声誉,是中等强国兼顾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优质选项。
澳大利亚是一个在多边领域成就卓著的中等强国,尤其是在工党执政时期,澳大利亚外交对多边主义显示出更大热情,在行动上也更为积极主动。本文认为,多边外交为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强国提供了必要的平台,通过联合立场相同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甚至领导力。
(四)关系与互动
结盟外交、地区外交和多边外交三足鼎立,共同支撑澳大利亚战后外交的基本面,不同政府、不同时期所确定的外交政策是在三者之间不同位置取得平衡的结果(见图1)。工党领导人陆克文出任总理后,提出“引领于前而不尾随于后”的“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主张,在结盟的基础上保持外交行动的独立性,在结盟外交、地区外交以及多边外交这三者之间寻求平衡,遵守《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安全原则,提升多边外交的地位;关注周边地区但绝不排斥其他地区,肯定地区外交的重要性;在多边外交上再创辉煌;高度的防务自立,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具有影响力并可信的角色。㊿ Kevin Rudd,“Leading,Not Following:The Renewal of Australian Middle Power Diplomacy,”The Sydney Papers,Vol.19,No.1,Summer 2007,p.[ii]-13(ISSN:1035-7068).
图1:澳大利亚外交的三个支柱
三种外交之间也会产生互动,外交动态往往是三种外交此消彼长的结果。首先,结盟外交在澳大利亚外交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它的主导地位对地区外交和多边外交形成制约。陆克文未能实现的抱负反映出,彼时的结盟外交已对地区外交和多边外交形成掣肘。另一个主要的例子是澳美关系日益对澳中关系造成牵制,不得不在最重要的军事盟友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选边站成为澳大利亚决策者最不想面对的可能性。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为澳经济近年来的持续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选择中国而抛弃美国是澳大利亚政治家——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完全无法想象的。于是中美关系的紧张就转化为澳中关系的紧张,澳美之间的同盟外交成为了一个妨碍澳大利亚发展其与中国关系的首要因素。
结盟外交不只有牵制的作用,也有促进的作用。是美国支持澳大利亚在地区多边外交行动以及地区多边机制创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默许下,澳大利亚成为东帝汶公民投票的主要的捐资者和主持者,以及联合国东帝汶维和部队的主导国。1989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在澳大利亚举行,1993年APEC国家首脑非正式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都是在美国支持下实现的。与澳美之间亲密的盟友关系发挥了正向的作用。在“印太”概念落地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力图通过日、印(尼)、印(度)、韩四国的所谓民主伙伴网来支撑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架构。〔51〕 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November 2017,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p.80.澳美同盟是澳推进此种多边地区安全机制内在动力。
一部分多边外交与地区外交是交织在一起的,澳大利亚参与的多边行动多集中在亚太地区。以维和行动为例,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间澳大利亚所参加的多边维和行动有122次(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数据库),其中40次是在东亚和亚太地区,而在这40次维和行动中,澳大利亚领导了27次行动,发挥着绝对的骨干作用,而在亚太地区以外,澳大利亚只领导了3次维和行动。澳大利亚还是亚太经合组织建立过程中最积极的倡导者,在有效的外交沟通下其倡议受到多国响应;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后,澳大利亚一直致力于推动它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主张APEC发展成为“亚太经济共同体”,甚至应当扩展到政治及安全领域。
相对大国来说,中等强国的外交资源更为有限,每届澳大利亚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需要决定如何分配有限的外交资源,另外就是如何在三个支柱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三种外交的互动以联盟外交为中心,联盟外交优先性,或者说美国的态度对澳大利亚所要进行的地区外交和多边外交有塑造性的影响。地区外交和多边外交有重合的部分,即地区多边外交。地区多边外交能够对新的地区以及地区认同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继而促进或影响双边层面的地区外交。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神经生理学家文森特·维莱特(Vincent Villette)利用电压传感器研究阈下电信号的周期性波动如何影响小鼠小脑神经对肌肉活动的协调。维莱特表示:有关细胞如何协同运作,我们还知之甚少。
四、结论
澳大利亚的战后外交中存在一个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因此该时期出现的三个外交重点,都可以从中等强国的角度给出合理的解释:第一,结盟外交。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希望与大国结盟从而获得安全保障,同时其地缘特性和军事条件对大国来具有可利用的战略价值,于是结盟既有主观需要又存在客观可能。第二,地区外交。由于实力所限,澳大利亚无法在全球范围或许多领域同时展开外交行动而必须有所取舍,于是它将外交政策目标更多地集中于自己所在的地区,并力求在构建地区秩序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第三,多边外交。在国际组织的平台上,澳大利亚有实力也有意愿在国际事务中充当催化剂、协助者、甚至管理者,多边外交是澳大利亚得以发挥超出其本身实力的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这些解释分别来看,不见得能够为联盟外交、地区外交和多边外交提供最充分的解释,但是它用一条逻辑线,将澳大利亚战后外交的三个重点串起来。三大外交是澳大利亚战后外交的表象,在表象之下,隐藏着促使澳大利亚做出这些外交行为的深层力量。本研究发现,三大外交的表象之下深藏着同一个根,这就是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认识这一逻辑有助于对澳大利亚战后外交形成更为宏观和完整的理解。
作者简介:崔 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澳中心讲师。
标签:澳大利亚论文; 外交论文; 强国论文; 地区论文; 美国论文; 《战略决策研究》2019年第4期论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澳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