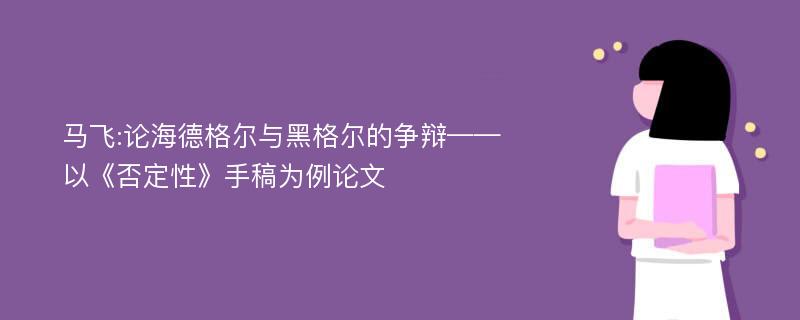
摘 要: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解释是他自己的思想转向和形而上学之克服的重要环节。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展开了本质性的哲学争辩。从形式上看,争辩(Auseinandersetzung)具有彼此分离而又相互设定的双重含义。《否定性》手稿为争辩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例子。海德格尔指认否定性为黑格尔哲学的基础规定而黑格尔哲学并没有严肃对待之。黑格尔从意识的区分出发来思考否定性,因而在某物和他物的关系中规定否定性。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差异出发来思考否定性,并且在人与存在的关联中深入否定性的根源,回到作为源始区分之位置的澄明。
关键词:海德格尔; 黑格尔; 争辩; 否定性; 差异; 澄明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一样重视历史的思想性和思想的历史性。思想建构与思想史解构是海德格尔运思的双重方式:《存在与时间》导论第二章已经讲到“厘清存在问题的双重任务”,即“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与“解构存在论历史的任务”[注]Heidegger,Seinund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2006, S.15, S.19. 中译文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1页,第26页。为统一术语、照顾文气,所引译文或有改动,下文不另注明。;《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以下简称《论稿》)则提出,“本-有”就是“原始的历史本身”[注]Heidegger,BeiträgezurPhilosophie(vomEreignis), GA65,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9, S.32(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65”);中译文参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1页。,“作为本-有的存有乃是历史”[注]GA65, S.494;《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第585页。。纵观海德格尔一生所思,“形而上学历史”(无论作为有待解构的存在论历史,还是作为争辩和对话中的“第一开端”的历史)始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形而上学历史上的那些伟大思想家的解释与批判构成了其思想工作的基本动机和任务。[注]可参见倪梁康:《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黑格尔-狄尔泰动机》,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倪梁康提到“哲学的任务”与“哲学史的任务”,前者被早期海德格尔称为“存在论的任务”,后者则可称之为“解释学的任务”,并且“在海德格尔这里与在黑格尔那里一样, 两个任务结合为一: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在海德格尔全集的目录中很容易就能看到的一串名单——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尼采等等[注]海德格尔本人在不同的地方出于不同的考虑列出过不同的名单,例如:《存在与时间》中的“解构存在论的任务”计划以时间问题为线索依次考察了康德、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参见SeinundZeit,S.40),《论稿》中列出的“历史讲座”则瞄准现代哲学,包括了莱布尼茨、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尼采(参见GA65,S.176)。,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海德格尔对这些哲学家的解释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之道,是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必经之路。
在海德格尔对这些哲学家的诸多解释中,对黑格尔的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了其与众不同之处。伽达默尔曾经指出:“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以何等的持久性围绕着黑格尔转圈子,始终在针对黑格尔进行新的划界尝试,直到如今。”[注]Hans-Georg Gadamer, Hegel,Husserl,Heidegger,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87, S.90.而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所有寻求抵御海德格尔思想格调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点,在那里海德格尔思想看上去一再与黑格尔的思辨理念论合流,这个点就是把历史引入哲学的基本问题提法。”[注] Hans-Georg Gadamer, Hegel,Husserl,Heidegger,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87, S.90.这意味着,无论从海德格尔思想的自身确认来看,还是从针对他者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在某些方面划入同一阵营的做法来看,海德格尔都不得不面对黑格尔,不得不与之展开争辩、进行对话。
早在1915年,海德格尔就在其教职论文中引用黑格尔的话,将“……就哲学的内在本质而言,既无先驱者,亦无后至者”[注]Hegel,JenaerSchriften, TW2, Suhrkamp, 1986, S.17.作为导论的箴言[注]参见Heidegger,FrüheSchriften, GA1,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8, S.193(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1”)。 ,并且在这部论文的结尾处宣称:“要同黑格尔展开一场原则性的争辩。”[注] GA1, S.411. 关于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对其黑格尔解释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解释的开端性意义,可参见张柯:《论海德格尔“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开端》,载《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但是这场争辩并未立即开启。在随后的“早期弗赖堡时期”(1919—1923)和“马堡时期”(1923—1927),海德格尔密集地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了现象学阐释,同时吸纳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历史解释学、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逐渐形成了此在的解释学—现象学—存在论。《存在与时间》中对黑格尔时间概念及其与精神之关系的解释尚未构成一种真正的争辩,而只是起到了对生存论—存在论的时间性分析的反衬作用。
原则性的争辩在海德格尔从马堡回到弗赖堡之后得到开启。首先是在1929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稿《德国理念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与当前哲学问题》中,海德格尔在与德国理念论的争辩中论及“一种将来的与黑格尔的争辩”。[注]参见Heidegger,DerDeutscheIdealismus(Fichte,Schelling,Hegel)unddiePhilosophischeProblemlagederGegenwart, GA28, Vittorio Klostermann,1997, S.208.(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28”)接着,海德格尔于1930年3月在荷兰做了题为《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难题》的报告,把争辩的战火从德国理念论烧到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域。[注]参见Heidegger,VorträgeTeilI:1915-1932, GA80.1, S.283-325. 在同年9月20日致布洛赫曼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主要的时间用来写冬天的课程讲稿了: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场解释性的争辩。如何经受这场斗争,我还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学习本质性事物的机会。”[注] Martin Heidegger,Elisabeth Blochmann, Briefwechsel1918-1969, Hg. Joachim W. Storck, 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1989, S.38.这场争辩便体现在1930—1931年冬季学期的讲座稿《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与黑格尔的争辩在这里明确地定位到了“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十字路口”。[注]Heidegger,HegelsPhänomenologiedesGeistes, GA32,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7, S.92.在短暂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之后不久,海德格尔于1934—1935年冬季学期开设了“黑格尔法哲学”讨论班,[注]参见Heidegger,SeminareHegel-Schelling, GA86, Vittorio Klostermann, 2011, S.59-184. (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86”)相应的讨论班笔记和记录见S.549-655。考虑到时代背景和海德格尔的个体处境,这一讨论班所涉及的内容更显意味深长。再往后,在写出了后来被编为全集第65卷的秘密手稿《论稿》(1936—1938)之后,即1938—1939年,海德格尔在“否定性”中寻找路径继续深入与黑格尔的争辩。[注]参见Heidegger,Hegel, GA68,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3,第一部分,《否定性:从否定性出发与黑格尔进行的一场争辩》(1938-1939,1941)。(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68”)
5.宗族恶势力或者地痞流氓阻挠土地信托流转。在农村部分地区,宗族恶势力和地痞流氓影响力不可低估,甚至已经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们早就对农村一些优质的地块和项目垂涎三尺,现在岂容别人插手?传统土地流转一般在农户之间小范围进行,他们一般不方便阻挠,现在土地大规模、长时间通过信托转让出去,当违反他们意愿时,他们就会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明的暗的都来,让你防不胜防,提心吊胆,甚至会明目张胆的动用武力,对宗族恶势力和地痞流氓不依法予以严惩,部分农村地区土地流转难以正常进行。
海德格尔在1930年的思想“转向”伴随着他与黑格尔的争辩。这场争辩为晚期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对话做了准备。[注]晚期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对话的主要文本包括《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1957)和《黑格尔与希腊人》(1958)。本文关注的则是海德格尔1930年代思想转向中与黑格尔的争辩。本文尝试在海德格尔思想范围内来理解这种争辩的意义。我们的目标不是面面俱到地呈现这场争辩,而是在对“争辩”一词的含义和翻译做出准备性的说明之后,把目光集中在海德格尔的《否定性》手稿,以之为例对争辩形成一种实质性的理解。
甲状腺肿瘤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内分泌系统肿瘤,其也是普外科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甲状腺肿瘤发病率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女性患者较多,良性肿瘤较为常见,一般无非常明显的临床症状。手术方式是治疗该病症的主要方式[1]。
一、 关于“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一词的先行说明
我们以“争辩”一词来翻译德语词“Auseinandersetzung”。这个德语词通常的意思是“分析”“阐释”“讨论”“交换意见”“争论”“辩论”等等。从构词上来看,“Auseinandersetzung”一词有“aus”(分离、出自)、“einander”(相互、彼此)和“Setzung”(设定、设置)三个构成环节,在字面上表达出彼此分离而又相互从对方得到设定的双重含义。[注]参见孙周兴:《〈尼采〉译后记》,见《尼采》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55-1156页;马琳:《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关于非性概念的交涉》,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第45页;孙冠臣:《论海德格尔“Auseinandersetzung”的多重含义》,载《现代哲学》,2014年第5期,第48页。于是,首先面对的困难就是翻译。
最后,对于海德格尔把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中的“polemes”翻译为“争辩”,我们也理解为海德格尔是从“事情本身”出发来进行“翻译”的,并非简简单单地选择了一个译名来替换通常的译名“战争”。在海德格尔看来,赫拉克利特的polemes说出的已经是作为事情本身的“争辩”。这个意义上的争辩是从作为“涌现”的physis而来得到思考的[注]参见Heidegger,EinführungindieMetaphysik, GA40, Vittorio Klostermann,1983, S.66.,源初的争辩就是“澄明”(Lichtung)[注]参见GA7,S.284.。
我们基本上认同孙周兴这里的解说:一方面,争辩乃是事情本身,解释性的争辩不应拘泥于文本,这已经超出了通常理解的“争辩”的含义;另一方面,从事情本身而来的争辩呈现出“同一与差异”的张力,表达出一种在接纳中拒斥的态度。但是,由于我们所要尝试进入的“争辩”不是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争辩,而恰恰是他与黑格尔的争辩,所以需要特别指出这种“差不多接近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的“争辩”与“扬弃”的关键差异:后者根本上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极端态度,争辩却是要在追究这种态度的根据之际与这种态度分道而行。后来在1950年代展开的与黑格尔的对话中,海德格尔在与哲学史对话的意义上更明确地把黑格尔的“扬弃”与他自己的“返回步伐”区别开来。[注] 参见Martin Heidegger, IdentitätundDifferenz, GA11,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6, S.58.
孙周兴在《〈尼采〉译后记》中强调了争辩与事情本身的内在关联:“就其尼采解释来说,海德格尔总以为,他并不是在与尼采的文字、著作辩论,而是在与‘实事’本身‘争辩’。海德格尔追溯词源,认为在古高地德语中,实事或者事情(Sache)本来就含有争执、争议的意思。在本书‘前言’中,海德格尔径直指出:‘实事,即争执,本身乃是一种争辩。’”[注]孙周兴:《〈尼采〉译后记》,见《尼采》下卷,第1155页;第1155-1156页。结合“Auseinandersetzung”一词的字面含义和前述阿佩尔关于该词不可译的论述,孙周兴指出:“从态度上讲,它可以说是一种既接纳(理解异己)又拒绝(持守本己)的姿态,差不多接近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Aufhebung)了。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一种起于‘实事’的争辩性解释不应拘执于文本,而必定要在解释中‘添加’某种来自‘实事内容’的东西。”[注]孙周兴:《〈尼采〉译后记》,见《尼采》下卷,第1155页;第1155-1156页。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海德格尔用“Auseinandersetzung”表达的也是该词通常含义中的某一个意思。但是,当涉及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时,他对词语的使用往往会超出其通常含义。例如,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讲到“悬临”时举了一些例子:“悬临在此在面前的却也可能是一次旅行,一次与他人的争辩(Auseinandersetzung)……”[注]SeinundZeit, S.250; 《存在与时间》,第309页。在这里,“争辩”显然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争论和辩论,争辩双方或者就某一陈述提出各自不同的理解,或者就某一事情各执一词。而仍然是在《存在与时间》中,一旦论及存在论问题或某个哲学家的思想,“争辩”一词就不再以那么简单的面目示人了,而是要加上“原则性的”或“批判性的”等限定语。我们可以略举几例:“后世耽误了对于‘内心’的一种以存在问题为主线并且同时与流传下来的古代存在论进行批判性争辩的专题化存在论分析”[注]⑥⑦SeinundZeit, S.25, S.98, S.398; 《存在与时间》,第32页;第127页;第479页。;“在原则性争辩的场地中,争辩不应仅仅局限于意见式的可把握的论题,而是必须以问题域的实事上的倾向为方向,即使这种方向也没有超出某种流俗的把握”⑥;“现在才在整个范围内变得可通达的对狄尔泰研究的占有,需要原则性争辩之坚持不懈与具体而微”⑦。尽管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并未做出特别的说明,但比较容易看到,这几处“争辩”的含义已然超出了通常的意见之争和观点之辩。那么,应该如何明确地理解这种超出了通常含义的“争辩”呢?
①应根据当地气候、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特点,合理规划布局集流节灌工程。集流工程、蓄水工程、输水工程和节灌工程要统一布置,相互衔接配套。
孙冠臣在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主题下讨论海德格尔的“Auseinandersetzung”。他指出了“Auseinandersetzung”在不同语境中的四种含义:(1)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中的“polemos”被翻译为“对峙”;(2)海德格尔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对置”;(3)后期海德格尔与前期海德格尔的“对质”;(4)跨文化对话意义上的Auseinandersetzung。他对这四种含义的相应译名的说明是:“‘对峙’本身带有抗争、斗争的意味,与polemos的传统翻译‘战争’相去不远;‘对置’作为相对而立的一种摆置,敞开了对话、争辩、交流的可能性;‘对质’则指示着一种澄清、表白、申辩。三个词围绕Auseinandersetzung的原初含义而构成一个家族从不同的角度言说着海德格尔的思想。至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Auseinandersetzung,通行的汉语翻译是‘对话’,但海德格尔没有使用‘Gespräch’,而是选择了带有强烈‘争’之锐气的Auseinandersetzung,明显地缺少我们心仪的‘对话’所包含的‘和’之大气。而且,在海德格尔这里,西方—欧洲与东亚之间的Auseinandersetzung尚没有开始,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Auseinandersetzung的可能性在西方—欧洲完成自我救赎之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一切都是未决的,因此,我们在这一重意义上不提供Auseinandersetzung的汉语对译词。”[注]孙冠臣:《论海德格尔“Auseinandersetzung”的多重含义》,载《现代哲学》,2014年第5期,第48-49页。
(二)教学活动形式化严重。高中音乐教学与其他学科在教学活动和形式上应该有所区别,需要大量通过对乐器的实际操作来提高学生的音乐水平。而当前高中音乐教学过程中明显存在着教学活动形式化、教学过程扁平化的现象,不利于学生音乐素养的培养。高中音乐教学过程中,许多音乐老师只是教授学生最基础的音乐知识,而没有采取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教学。
孙冠臣以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来翻译“Auseinandersetzung”,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词的丰富含义并且提升汉语哲学词汇自身表达的力度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本文的问题域来说,上述四重含义仍然可以还原为“事情”和“争辩”这两重本就共属一体的意义。
首先,可以看到,在论及东西方“对话”的时候,海德格尔实际上也使用过“Gespräch”一词。“这种[与希腊思想家及其语言的]对话还有待开始。它几乎尚未得到准备,而且对我们来说,它本身始终是那种与东亚世界无可避免的对话的先决条件。”[注]Heidegger,VorträgeundAufsätze, GA7,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0, S.41. (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7”)同时,正如孙冠臣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真正的东西方对话在海德格尔那里“尚没有开始”,因而无论是从词语的使用,还是从实际的情形来看,对于海德格尔的“Auseinandersetzung”一词,都不必强加之以“对话”的含义。
其次,海德格尔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对置”和后期海德格尔与前期海德格尔的“对质”的区别,实际上只是与之争辩的“对手”的区别。一方面,在海德格尔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争辩(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转向时期”与尼采、黑格尔的争辩)中,已然包含着一种实则针对着《存在与时间》的“自我争辩”。另一方面,只要争辩是从事情本身而来并且把我们引向事情本身的争辩,那么无论是与其他思想家争辩,还是与自己争辩,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朝向事情本身的回返。
孙周兴在海德格尔《〈尼采〉译后记》中特别谈到这个词:“这里的德文‘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一词难以完全地译成中文——阿佩尔甚至说它不能被译为外文。”[注]孙周兴:《〈尼采〉译后记》,见《尼采》下卷,第1155页。阿佩尔的说法出自其论文集《争辩:先验语用学进路的检验》(AuseinandersetzungeninErprobungdestranstzendentalpragmatischenAnsatzes)前言中就书名中的“Auseinandersetzungen”所做的“破题”说明:“德语词语‘Auseinandersetzungen’(‘与某人’或‘就某事物’)难以翻译成别的语言。因为,谁与某人(关于某物)争辩(auseinandersetzt),谁就必须同时参与两个看上去相反的活动:一方面,他必须为了与他人进行沟通而对他人所持的要求(例如某种信念、某种立场或某项计划)保持开放,而与此同时,他也必须把自己的要求保持在眼帘内,以便使自己的立场与他人的立场不断地对质,并且因此要么修正自己的立场,要么在自己的立场上与他人的立场保持距离,这样,不同的立场‘互’踩。二者——对自己立场的修正和对他人立场的疏远——通常就是一场‘争辩’的结果,尽管这当然有赖于各种论据的对质。”[注] Karl-Otto Apel,AuseinandersetzungeninErprobungdestranstzendentalpragmatischenAnsatzes, Suhrkamp, 1998. S.1.由此来看,“Auseinandersetzung”一词所表达出的“争辩”的向对方开放而又保持距离的富有张力的意味,正是一种本质性的争辩的应有之义,因此,虽然中文词语“争辩”在字面上似乎表达不出德语词“Auseinandersetzung”所具有的张力,但我们仍然选择这一译名,为的是在哲学上深入探讨该词的本质性意义时能够兼顾其通常含义。
马琳在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Auseinandersetzung”的语境中把这个词翻译为“交涉”。她在指出“Auseinandersetzung”一词同时具有“对话”“交谈”等正面含义和“争斗”“竞争”等负面含义之后,通过引证海德格尔而强调了Auseinandersetzung在哲学上的双重含义,即:“把他者与自我都带到那原初的、起源性的东西那里”[注]Heidegger,VomWesenderMenschlichenFreiheit, GA31,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2, S.292.,并且“在对方最强的威力与危险性之中把对方定立下来”[注]Heidegger,Nietzsche:DerWillezurMachtalsKunst, GA43,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5, S.279.。在海德格尔就“否定性”概念与黑格尔进行的争辩中,马琳看到了“那‘原初的、起源性的东西’最有可能是指存有之自我遮蔽或者说疏朗之镜”,亦即存在的自行遮蔽或者说澄明之境,并且她指出争辩的“最终目的在于真理之揭蔽”。[注]马琳:《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关于非性概念的交涉》,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第45页。应该说,马琳的相关讨论深入到了“争辩”的核心地带,为我们指示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进行争辩的最终朝向。
基于上述讨论,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呈现出双重意涵。一般地看,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作为一种哲学的批判性解释具有既接纳又拒斥的紧张态度;更具体地看,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哲学立场对一种“旧的”哲学立场的态度,而且是对同一事情的本质性争辩。本质性的争辩在其自身也包含一种紧张:在把争辩双方带回到问题根源处的同时,从这一根源出发给对方进行定位。这种紧张与一般意义上的争辩中的紧张在形式上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进入海德格尔的《否定性》手稿,来理解争辩的实质内容。
很明显,问题三又分为两个问题:一方面是针对黑格尔的否定性与无的关系发问,我们前面的讨论中已经给出过预先的回答,黑格尔把无理解为纯粹的无区分,因而没有从无出发来思考否定性,而是在某物和他物的区分中才出现第一个绝对的否定性。另一方面,关于无与存在的关系,这一问意在把关于否定性的讨论引回到否定性之基础或者说否定性之来源,这是争辩的要害。
二、 否定性及其根源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在分析黑格尔的时间与精神概念之关系时已经抓住了二者共同的形式结构:否定之否定。但是,那里的分析在其任务范围内仅止于此,没有对否定性概念本身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隋开皇三年(583),属敷西县隶华州。大业三年(607)改隶京兆郡。五年(609)改敷西县为华阴县,潼关属之。唐垂拱元年(685),华阴县改称仙掌县,天授二年(691)分仙掌县东部设潼津县,隶虢州。圣历二年(699)三月,改属太州。长安二年(702)撤潼津县,并入仙掌县。神龙二年,(706)复名华阴县,后至元约670余年,均属华阴县。
海德格尔在《否定性》手稿的一开始就挑明了这次争辩涉及的是《逻辑学》:“我们用谈论的方式尝试进行的这一探讨不应妨碍诸位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解释工作的进程。”[注] GA68, S.3. 从手稿开篇这句话可以看出,这份手稿是海德格尔为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讲座或座谈而准备的,但是没有记录表明他曾公开进行过这样的讲座或座谈。参见马琳:《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关于非性概念的交涉》,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第36页。手稿所涉及的《逻辑学》章节主要集中在“存在论”的开始部分,从“存在”“无”“变易”到“某物”与“他物”。
在《德国理念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与当前哲学问题》(1929)中,海德格尔已经针对黑格尔提出了后来在《否定性》手稿中才得到真正发挥的论断:“黑格尔哲思最大的和隐藏的秘密:他真正地认识了、赞许了和要求了否定性事物的积极的源初作用,但是——只是为了扬弃这种作用,并且把它吸取到绝对者的内在生活中去。”[注] GA28, S.260. 柯小刚格外看重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这一“秘密”,多次在不同的问题语境下引证这段话,参见柯小刚:《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页,第108-109页,第203页,第222页以下。到了《论稿》,海德格尔仍然感叹道:“能够理解‘否定’的人是多么少,而这些理解者中能够把握‘否定’的人又是多么稀罕。”[注] GA65, S.178;《论稿》,第207页。《论稿》作于1936—1938年,而《否定性》手稿则是作于1938—1939年,于1941年有所修订,后来收入全集第68卷。不仅《否定性》手稿的写作时间与《论稿》紧紧衔接,而且在后来的全集出版工作中,第68卷也在《论稿》之后,成为全集第三部分正式出版的第二卷著作。[注] 参见GA68, S.153,《编者后记》。
具体来看,在《否定性》手稿中,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可以展开为三个层次:首先,黑格尔的否定性的标志是意识的区分[注] 参见GA68, S.13.;而海德格尔则尝试从存在论差异来思考存在之无[注] 参见GA68, S.15.。其次,从意识的区分出发,黑格尔的否定性呈现为三重区分(直接的区分、间接的区分、无条件的区分),并且在某物与他物的关系中呈现为两种否定性(抽象的、片面的否定性和具体的、绝对的否定性);而从存在论差异出发,海德格尔那里的存在之无则标识着一个问题领域。[注] 参见GA68, S.37. 丹尼尔·达尔斯特伦(Daniel Dahlstrom)认为,海德格尔在《否定性》手稿中区分了黑格尔那里的四种否定性概念:(1)存在者的无,即脱离于一切存在者的纯粹否定性、纯粹的无;(2)存在的无,即对纯粹存在的否定、非存在;(3)有条件的抽象的否定,即在主体—客体—关系中交替出现的最初的区分和对这一区分的否定;(4)无条件的具体的否定性,即作为自身否定的否定之否定。参见Daniel Dahlstrom, “Thinking of Nothing: Heidegger’s Criticism of Hegel’s Concept of Negativity”, Stephen Houlgate and Michael Baur ed., ACompaniontoHegel, Blackwell, 2011, pp.519-536. 达尔斯特伦没有注意到,无与否定性在《否定性》手稿中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混为一谈。海德格尔在小标题为“否定性与无”的第四小节中恰恰提出,虽然看上去否定性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中就遇到了无,但问题仍然是如何理解无。实际上,由于在黑格尔那里纯粹的存在与纯粹的无是无区别的,因此在无那里否定性并未被照亮,但也正是由于纯粹的无与纯粹的有是同一的,否定性的本质或许可以显露出来。参见GA68, S.14,S.17. 马琳对达尔斯特伦所提出的“四种否定性”给出了一种批评性理解,特别指出了达尔斯特伦没有区分“无”与“非性”(否定性)。参见马琳:《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关于非性概念的交涉》,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第38-39页。最后,黑格尔哲学没有思考否定性的本源;海德格尔则力图将我们引向无之无化的发生场域:澄明(Lichtung)。[注] 与我们这里提出的三个层次类似,克里斯多夫·布顿(Christophe Bouton)指出,海德格尔在《否定性》手稿中从三个方面批评了黑格尔的否定性理解:(1)黑格尔没有严肃地对待否定性;(2)黑格尔把否定性主体化了;(3)黑格尔没有追问否定性的本源。他指出第三个方面是《否定性》手稿的主要动机。参见Christophe Bouton, ”Die helle Nacht des Nichts: Zeit und Negativität bei Hegel und Heidegger“, in: Hegel-Studien, Band45, Felix Meiner Verlag, 2011, S.103-124.
1. 意识的区分
黑格尔是从意识的区分而来思考否定性的。何谓意识的区分?“在意识中发生的我与作为我的对象的实体之间的不一致就是它们的区分,是一般的否定性事物。”[注]Hegel,PhänomenologiedesGeistes, TW3, Suhrkamp, 1986, S.39. (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TW3”)“意识把某种东西区分于自己,同时又与之关联。”[注]TW3, S.76; S.137; S.39.“意识区分出这样一个东西,它对于意识来说同时是一个没有区别的东西。”[注]TW3, S.76; S.137; S.39.这就是说,意识本身是一种区分活动,意识作为关于对象的意识,把对象与自己相区分,又在这种区分中建立了与对象的联系。
但意识的区分中的不一致不仅是我与作为对象的实体之间的不一致,“它同样也是实体自己与自己的不一致”[注]TW3, S.76; S.137; S.39.,因为这个区分实际上也是实体自身的活动。换言之,意识的区分不仅是作为自我的主体的活动,同时也是作为对象的实体的活动,实体由此表明自己实际上也是主体。因此,自身意识的区分作为否定性的标志所标明的是否定性的主体性。
主体性在这里不是某种片面地从自我出发的唯我性,而是主体在自行反射的主体—客体—关系中的存在。[注]参见Heidegger,Holzwege, GA5,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S.146.(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5”)因此,对于否定性之被标识为意识的区分,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是:“是区分取自于作为本质的意识,还是作为区分的标志被用于对意识(主体—客体—关系)的规定,抑或二者是同一个东西以及何以如此?”[注]GA68, S.13; S.22; S.23; S.29.前两个问题无疑只是虚晃一枪,因为第三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消解了前两个非此即彼的问题的可能性;这两个问题不得不预设一个没有意识的区分和一个没有区分的意识,而如果意识与区分是一回事,那么这种预设就是不可能的。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海德格尔更关心的乃是:何以如此,何以意识与区分在黑格尔那里是一回事,这意味着什么?在《否定性》手稿中海德格尔一再地提出类似的问题:“意识与区分的共同发生说的是什么?”[注]GA68, S.13; S.22; S.23; S.29.“对于黑格尔来说,意识与区分已经完全相提并论了吗?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注]GA68, S.13; S.22; S.23; S.29.“否定,即区分,比意识‘更早’——还是相反?抑或二者是同一回事?”[注]GA68, S.13; S.22; S.23; S.29.我们将会看到,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在这一问题上变得白热化。
2. 某物与他物
基于“意识”的“我表象某物”这种主体—客体—关系结构,海德格尔把黑格尔的否定性归结为三重区分:直接的意识之区分、间接的意识之区分、无条件的意识之区分。[注]参见GA68, S.37; S.17-18; S.18.这三重区分可以说是“我—表象—某物”的意识结构从“某物”经过“表象”回到“我”的过程:(1)在直接的意识中出现的“某物”已经包含一个区分,但这个区分还不是现实的;(2)在间接的意识中,“我”和“某物”的区分在表象活动中作为中介出现,我是表象着某物的我,某物是被我表象着的某物;(3)最后,在无条件的意识中,即在绝对的自身意识中,不仅作为单纯对象的某物,而且作为中介的表象活动亦即意识自身,都呈现为无区分的区分。第三种区分作为否定之否定,是具体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否定性,前两种区分则是抽象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否定性。[注]参见GA68, S.37; S.17-18; S.18.
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由于被理解为意识的区分,黑格尔的否定性不是从“无”出发得到规定,而是在“某物和他物”的关系中以“他在”(Anderssein)的形式得到说明。[注]参见GA68, S.37; S.17-18; S.18.在《逻辑学》中,纯粹的“无”本身还不构成否定性事物,只是“在其自身内的无区分性”。[注]Hegel,WissenschaftderLogikI, TW5, S.83(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TW5”);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9页。文中涉及《逻辑学》中译本的译文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动,下文不另注明。无与存在之间的差异似是而非,只是“意谓的区分”。[注] TW5, S.90;《逻辑学》上卷,第77页。在《哲学全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存在与无的区分只是一个意谓而已。”见Hegel, Enzyklopä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nI, TW8, Suhrkamp, 1986, S.186.(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TW8”)“这二者[按:存在与无]的区分只是一种意谓的区分、完全抽象的区分,这种区分同时不是区分。”(TW8, S.187.)区分只有在某物与他物的关系中才构成否定性,因为某物与他物不再是纯粹的无规定的存在,而是“此在”。“此在才包含存在与无的真实的区分,亦即包含一个某物与一个他物。”[注] TW5, S.90;《逻辑学》上卷,第76页。此在作为变易的结果,既不是退回到空洞的虚无,也不是某种脱离了无的存在,而是扬弃了存在与无的区分,成为一个有规定的东西。这样的规定性就是质。就此在作为一个存在的规定性而言,这个质就是实在性;就此在作为一个扬弃了无的非存在而言,或者说,就无也被扬弃为一个有规定的东西而言,质就是否定。[注] 参见TW5, S.118.在质这里呈现出来的区分实际上已经扬弃在此在中。实在性和否定都是此在的质,都作为此在的规定性而不与此在分离。但这样一来,此在也就不是一个无区别的东西了,而是自身包含着扬弃了的区分。作为这样的在其自身内的存在,此在就是在此存在的东西,就是某物——黑格尔强调指出,作为单纯的存在着的自身关系,某物就是第一个否定之否定。[注]参见TW5, S.123; S.128-129.
张鲁敬(1987-),男,硕士生,研究方向:生物医药和消毒剂的质量,email:453081549@qq.com;
AS临床活动性评价标准 由两名风湿免疫科医师共同判断患者的临床活动性。活动组:BASDAI评分≥6分或4分
这里已经出现了两种否定,即作为质的否定与作为某物的否定之否定。“但在这里,否定作为第一次否定,作为否定一般,当然要区别于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是具体的、绝对的否定性,而第一次否定与之相反,只是抽象的否定性。”[注] TW5, S.124;《逻辑学》上卷,第109页。但这两种否定的区分恰恰需要在对否定之否定的展开中才能得到具体的规定,而作为某物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某物与他物的关系中被进一步规定的。
(4)在做动物淋巴管灌注实验时,先解剖家兔,进行淋巴管灌注,观察活体状态下各器官淋巴管的分布及各级淋巴管之间的关系。通过本实验,充实淋巴系统解剖学实验内容,填补以往实验教学的空白点,开辟淋巴实验教学的新途径,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某物和他物首先都是某物,同时也就都是他物,或者说,哪一个是某物,哪一个是他物,还没有区别。“二者都既被规定为某物,也被规定为他物,因此是同样的,还没有出现区分。”[注] TW5, S.126;《逻辑学》上卷,第112页。在这种情况下,某物与他物的关系还是抽象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物只是抽象的他物,只是一个外在的自身关系。他在因此就是此在之外的他在,这样的他在毋宁说是非此在。但这个非此在又是被包含在某物之内的,是某物的非此在。
某物于是处在双重的自身关系中:一面是他在,即在他物的非此在中保持着自己的为他存在;一面是自在,即与在他物那里的自身不一致相对的自身一致的自在存在。最初某物和他物彼此外在的漠不相关现在被设定为为他存在和自在存在的相互区分的关系。为他存在是对此在和某物的单纯自身关系的否定,而自在存在则是在非此在和他物那里的否定关系。[注]参见TW5, S.123; S.128-129.
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为他存在和自在存在共同规定着某物。“某物是自在的,这是就其从为他存在那里返回到自己而言的。但某物也在自己那里或者说在它那里有某种规定或环境,而这是就这种环境在它那里是外在的、是一种为他存在而言的。”[注] TW5, S.129;《逻辑学》上卷,第114-115页。 为他存在和自在存在各自的区分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分都统一在某物中,而某物作为否定之否定才得到真正的规定。
否定之否定作为绝对的否定是具体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否定性,而第一次否定或者说单纯的否定则是抽象的、有条件的否定性。无论是着眼于意识的区分即主客关系的区分,还是从某物与他物的区分来看,海德格尔都是从上述两种否定的关系出发来针对绝对的否定性提出问题的:“(1)绝对的否定性是第一次抽象的否定性的上升,抑或其基础?(2)如果是基础——那么它从何而来?”[注] GA68, S.18.看上去第二个问题已然是针对第一个问题中的一种回答的追问,从而使第一个问题成为一种明知故问的设问,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第一个问题中提供的两个答案选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同时成立的,甚至应该说绝对的否定性正是以对抽象的否定性进行提升的方式而成为其基础的,或者反过来说,抽象的否定性的上升不是凭空而起,而是已经在绝对否定性之基础上的上升。因此绝对的否定性不仅是抽象的否定性的“升级版”,而且是使其升级得以可能的“平台”,在某物和他物的关系中的第一次否定也好,具体的否定之否定也罢,都是绝对否定性平台上的自行操作。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作为基础的绝对否定性的来源。如果说第一个问题还是在暗示黑格尔的否定性是从某物与他物的关系而来得到说明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已经是在直接向黑格尔的否定性发难了。如果说第一个问题黑格尔那里还可以给出两全其美的回答,那么第二个问题恰恰在对第一个问题两全其美的回答中不成问题了。如果说第一个问题的提问还处在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之内,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否定性概念的射程范围,而把我们引向了海德格尔的问题领域。
3. 否定性的根源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就否定性展开的争辩的根本朝向就在于否定性的“从何而来”,亦即否定性的本源。绝对的否定性不是对第一次抽象否定的单纯提升,也就是说,不是简单的第二次否定。在第一次否定上叠加的第二次否定仍然是相对的否定,而真正的否定之否定乃是绝对思想之“活力”。海德格尔追问道:“如果真正的否定性(即绝对的否定性)不是从一种抽象的否定性到另一种否定性的单纯的增加和丰富,而是作为绝对现实者本身的‘活力’的本质性的否定性,那么,反过来,抽象的否定性必定‘起源’于无条件的否定性。但无条件的否定性从何而来?诚然不可能有位于绝对理念之外的‘来处’;因而更加必然地必须追问绝对理念之内的‘来处’。”[注]GA68, S.22; S.22; S.26; S.27; S.24; S.41.
绝对理念之内的情形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否定性是意识的区分,而意识的区分意味着意识与区分的共同发生,意识的区分乃是进行区别的意识。因此,“在绝对理念之内也悬而不决的是,在这里什么是第一者:(简言之)作为‘我表象某物’的意识——抑或把这种表象关系标识为区分的‘区别’”[注]GA68, S.22; S.22; S.26; S.27; S.24; S.41.。在意识的区分中又存在着三重区分的否定性,于是进一步的“基础问题”就是:“(1)这里的不性事物意义上的否定性只是用来刻画绝对知识的本质性的三重区分性的一种形式上的辅助手段?……(2)抑或,绝对的我思和它的确定性的那种区分性是否定之可能性的自明基础?”[注]GA68, S.22; S.22; S.26; S.27; S.24; S.41.海德格尔指出,黑格尔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否定性的。而海德格尔接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不仅是黑格尔的问题,同时更是他自己的问题:“(3)问题一或者问题二中的不和否定性(不性和否性事物)与无之关系如何,无与存在之关系如何?”[注]GA68, S.22; S.22; S.26; S.27; S.24; S.41.
林燕玲是2018年入驻林畲村的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原是省档案局的主任科员。到任之后,他先是跑遍了全村260多户人家,了解各家存在的困难和需求,有针对性地一一加以解决。
地方政府的激励成本包括两个部分:政府激励政策有效,相应的政策法规出台和宣传所花费的成本为C1。政府激励政策有效,开发商积极建设被动房,政府对这些开发商进行奖励所花费的成本为C2。下面是使用MATLAB仿真得出的图3,图像的纵轴是政府激励政策无效的概率,横轴是推广时间,因此曲线反映了概率水平随着推广过程进行产生的变化。
基于图1所示的DPD软粒子模型,相应的相互作用参数αij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此外,键对粒子间通过简谐振动弹性力=Crij相互连接约束,其初始键长为单位长度.
讨论存在与无的关系时,海德格尔不止一次引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关于存在与无的句子,即:“纯粹的存在与纯粹的无是同一回事。”[注] TW5, S.83;《逻辑学》上卷,第70页。海德格尔的引用和相关讨论可参见:Wegmarken, GA9,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6, S.120;Seminare, GA15,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6, S.347;BeiträgezurPhilosophie(vomEreignis), GA65, S.266;Besinnung, GA66,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7, S.313;SeminareHegel-Schelling, GA86, S.729.尽管海德格尔也会认同黑格尔这个句子的表述,但双方的“根据”是根本不同的。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与无的同一说的都是二者的相互共属性;而在黑格尔那里,存在与无的同一在于二者的无区分性。而这其中的“不同”又意味着两种“区分”:存在论差异和意识的区分。“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在者”,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说出了存在的“不”,而意识的区分则在“存在与无是同一回事”的表达中无-言(Ab-sage)于根本性的区分。[注]参见GA68, S.20; S.14, S.33; S.14-15, S.39-40.
“纯粹的存在与纯粹的无是同一回事”这一表述无言于区分,这种无言来自对区分的遗忘,其本质后果是“拆-建”(Ab-bau)——《逻辑学》开端的“存在”概念所源自的一种与绝对现实性有极端区别者。[注]参见GA68, S.20; S.14, S.33; S.14-15, S.39-40.海德格尔用“无-言”和“拆-建”来标识黑格尔的绝对开端中已经“预设”了对他构不成问题的“否定性”:“拆建与无言是绝对者的‘开端’。”[注]GA68, S.22; S.22; S.26; S.27; S.24; S.41.也就是说,在绝对理念之内也没有为绝对否定性的来源留下位置,没有为否定性之根源的问题留下位置。
否定性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绝对思想的“活力”,可是黑格尔却没有严肃地对待否定性,对否定性的来源不闻不问,这意味着什么呢?作为基本概念和“活力”的否定性的不成问题意味着思想本身的不成问题。思想作为人的本质能力而把握存在者之存在,于是思想的不成问题又意味着人之本质的不成问题和存在本身的不成问题,进而言之,这意味着人与存在之关联的不成问题。[注]参见GA68, S.20; S.14, S.33; S.14-15, S.39-40.海德格尔自问自答道:“否定性在形而上学上的无疑问性作为思想之本质与作用的无疑问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仍然悬而未决的是:(1)人与存在的联系;(2)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区分。这种双重的区分共属一体,统一于唯一的问题:如果绝非从存在者而来,存在该从何处有其真而存在之真又建基于何处?”[注]GA68, S.22; S.22; S.26; S.27; S.24; S.41.这就是说,人与存在之关联藏而不显,和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区分隐而不彰,实则系于同一个问题,即存在之真的问题。
对于否定性之本源的源始区分,黑格尔无-言以对,而海德格尔则做出决-断(Ent-scheidung)。“追问那作为无条件的形而上学思想之‘活力’的否定性意味着,把那未被区分者置入决-断。首先做出一次这样的决断,可见地、可经验地做出,也就是说,使之成为急难,是一种问出存在问题的思想的唯一所思。”[注]GA68, S.41; S.43.“决-断——在这里是从先行给出者的单纯分离和区分而来做出的决断。”[注]GA68, S.41; S.43.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展开的本质性争辩是把形而上学问题夺回到其根源的斗争,这种斗争根本上乃是有所分离的决断。现在,决断所说的不是作为生存论上的本真展开性的此在之决心,而是比任何展开状态都更加源初的嵌入到此-在中去的决-断。这种嵌入着的决-断先于此在在生存论上的本真或非本真的展开并且为此在之生存的展开提供地基。向着否定性之根源的回返所朝向的就是这种决-断之渊-基(Ab-grund)。
相应地,无言的本质后果乃是对存在的拆-建,而决-断抵达的渊-基则是存在之澄明。意识在“我表象某物”的结构中对“某物作为某物”的表象是在存在(在此亦即存在者性)之光中进行的,“这种在……之光中对某物作为某物的表象已经是那种在其自身内统一地使‘对’‘作为’和‘在光中’可联结的东西的一种集结(Gefüge);那就是表象者(人)站立其中的被澄明者的‘澄明’,就是说,这种‘站立’必定预先已经一般地规定人之本质并且主导和支撑着本质的特征”[注] GA68, S.45. 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中,海德格尔在讲到显现者在其中得以显现的光亮本身又源于某个自由的敞开域时指出:“即便在像黑格尔所认为的一个在场者思辨地在另一个在场者中反映自身的地方,都已有敞开性在起支配作用,都已有自由的区域在游戏运作。也只有这一敞开性才允诺思辨思想的道路通达它所思的东西。”(Heidegger, ZurSachederDenkens, GA14, Vittorio Klostermann,2007, S.79-80;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孙周兴、陈小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2页。)。在与黑格尔的本质性争辩中,着眼于人与存在之关联,海德格尔抵达的是人之本质所处的位置:澄明(Lichtung)。
作为否定性之根源,澄明是真正的“他者”,“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处所。有一种澄明。从存在者方面来思考,这种澄明比存在者更具存在者特性。因此,这个敞开的中心并非由存在者包围着,而不如说,这个光亮中心本身就像我们所不认识的无一样,围绕着一切存在者运行”[注] GA5, S.40;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3页。译文有改动。。绽出地生存着的人就处在存在之澄明中,海德格尔在其向着存在之真回行的道路上以无蔽之名所道说的正是澄明。[注]参见Heidegger,Wegmarken, GA9,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6, S.201, S.323, S.330.
三、 结 语
澄明是黑格尔思想未经思索的否定性之根源,这一根源的被遮蔽与被遗忘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而且也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生存论解释学道路受阻、中断的原因。就此而言,《存在与时间》在抗争形而上学命运的同时又受缚于这一命运,触及了形而上学的边界但仍处于形而上学的领域之内。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的转向之思,既是从此在的生存论解释学向着存在历史之思的转向,同时也是从形而上学的领域向其根源的转向。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关于“否定性”展开的本质性争辩在这种双重转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对海德格尔《否定性》手稿的讨论,我们现在可以尝试进一步明确此前在对“争辩”一词的先行讨论中从形式上确定下来的双重紧张。
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科技不断实现与高校实际应用的深度结合,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也将走向新的发展历程。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明确提出要用“互联网+”引导我国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因此,本科教育也应该顺应其发展方向,推进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接纳在于,围绕否定性概念展开的争辩首先是跟随黑格尔的步伐进入到黑格尔的立场,而非径直地以与之不同的立场形成相互对峙。但抵达黑格尔的立场也不是为了与黑格尔同立共处,而是意在深入到这一立场的地基,把否定性问题带到其根源处。就黑格尔的立场无法把握它所出自的这一源初领域而言,争辩所朝向的根源性就意味着对黑格尔的拒斥。
但是,原则性的争辩并不止于此,而是由此才真正开始。如果海德格尔在与黑格尔的争辩中回到了问题的根源处,那么他必定不得不由此根源出发来重新确定黑格尔的位置。对一个位置的确定恰恰就要求在与该位置拉开距离的同时保持与该位置的距离。这就是说,在拒斥黑格尔的同时又保持着对他的接纳。
On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Hegel— Taking the Manuscript “Negativity” as an Example
MA Fei
(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Hegel is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both the turning of his own thought and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In 1930s, Heidegger developed an essential philosophical confrontation with Hegel. In form, confrontation (Auseinandersetzung) has two-fold meaning: apart from each other and setting for each other. The manuscript “negativity” provided a substantial example for the confrontation. Heidegger pointed out that negativity wa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t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and not treated seriously by Hegel. Hegel thought negativity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n determined negativit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mething and the other. Heidegger thought negativity from ontological difference and stepped back into the origin of negativity, into clearing (Lichtung) as the place of the original distinction, through the connection of human being with Being.
Keywords: Heidegger; Hegel; confrontation; negativity; difference; clearing
中图分类号:B516.54; 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3-0024-11
收稿日期:2019-01-08
作者简介:马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曾 静)
标签:海德格尔论文; 黑格尔论文; 否定性论文; 意识论文; 他物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