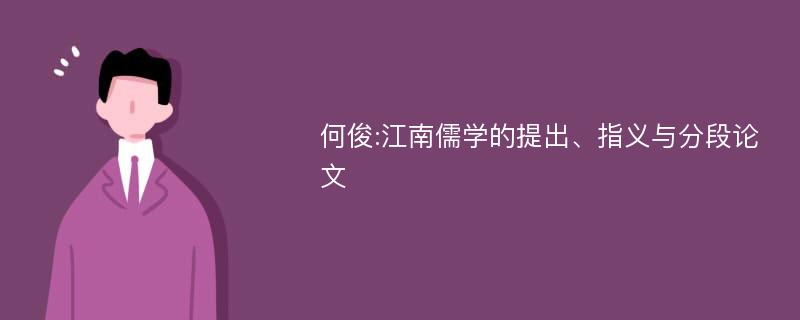
中国哲学研究
【摘 要】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中的重要现象,江南由此成为传统中国的重要区域,并在改革开放后始终引领中国发展。长期以来,江南研究是海内外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呈现出由经济研究向社会、文化研究推进的态势。儒学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为了进一步深入江南研究,提出江南儒学这样的研究领域不仅具有来自当下与未来的学术思想意义,而且具有历史的学理依据。由于江南与儒学都是内涵丰富且流变的概念,因此江南儒学研究一方面应有所聚焦,以呈现儒学的文本分析为重,以期发现与阐明那些型塑儒学的江南性质与特征的内容;另一方面则与江南儒学的历史源流相呼应,以揭示江南儒学的整体面貌与衍化方向及其动力。江南儒学在其流变过程中,虽然区域里的学术思想流派纷呈,且相对清晰,但很难由此界定江南儒学。一方面,江南儒学在整体上仍具模糊性;另一方面,内涵与边界相对清晰的区域内的学术思想流派彼此又有着密切的关联,呈现出共同的江南性。由于地理环境的改变是缓慢的,并主要由于经济活动引起,而传统时代的经济变化也是渐进的,因此对于江南儒学的分析,宜跳出朝代史,将江南儒学区分为三个长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先秦至六朝的江南儒学孕生;第二个时段是唐宋变革以后的江南儒学衍化,这个时段又以明代迁都北京,进一步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段;第三个时段是近代以降,直至今日追求现代化转型中的江南儒学探索。
【关键词】江南儒学 多样性 分段
江南研究早已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专门领域,并且呈现出从经济向社会、文化推进与展开的态势。我们提出江南儒学的研究视角,希望既能更深入地研究江南,又能为江南研究打开新的面相。然而,正如在有形的地理空间中江南还存在“何处是江南”的认识分歧,无形的精神世界中江南儒学更呈现为多样性的存在。本文就江南儒学的认识理据、内涵理解以及分析框架作一尝试性的梳理,以期获抛砖引玉之效。
一、 为什么要研究江南儒学?
江南儒学并不是一个在历史中已有的概念。在广义的江南这个历史舞台上,以区域命名的学术思想派别自宋代起可谓一直不断。如北宋的湖学、南宋的浙学、婺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明代的浙中、江右之学;清代的吴学、皖学、浙东与浙西之学,等等。这些以区域命名的学术思想派别是否具有确切的界定,另当别论,但它们仍然足以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而且在历史中乃至现代都对区域性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还作用到更广的学术思想范围,即参与到所属时代的主流学术思想的流变之中。相比较起来,江南儒学的概念并不具有这样的来自历史的依据。因此,当我们以此概念来统摄我们将要讨论的对象,自然就有一个问题需要首先予以说明,即提出这个概念的事实与学理依据是什么?
毋庸讳言,一个首要的事实是:江南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构成了提出江南儒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外部因素。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中,江南的经济社会文化不仅位居整个中国的前列,而且呈现出强劲而富有耐久性的动力;源自江南的许多理念与实践不断被上升到国家层面,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彰显了江南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性。江南所展现出的吸引力与引导性,表征着她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将极具影响。这一现实给上世纪中叶以来持久展开着的江南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促使江南提出获得更进一步的自我认知的要求。江南儒学的概念由此催生,以期江南研究获得纵深推进。
或许,来自于外部的原因还不足以构成作为学术研究的江南儒学在学理上的依据。这就需要指出,一方面如前文所言,江南儒学并不是一个历史中的概念,而完全是现代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另一方面由下文所述,江南儒学将聚焦于思想,因此,提出这个概念,虽然所将统摄而加以观照的更多是历史中的学术思想,但着眼的却是当代江南的思想表达,乃至于是关于未来的愿景。换言之,江南儒学的提出,虽然它的内容更多地涉及历史中的思想,但它的关怀与指向却是当下与未来的,江南儒学研究本身将构成当下的思想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思想活动的产生来自于外部因素的刺激,充满了学理上的正当性,因为我们认同思想史的基本观念就是以思想与环境的互动为其主题,[注]参见Benjamin Schwartz, “TheIntellectualHistoryofChina:PreliminaryReflections”, 收入J.K.Fairbank(ed.) ChineseThoughtandInstitution, Chicago, 1957. 关于“思想史”的理解,Benjamin Schwartz在他的 TheWorldofThoughtinAncient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以history of thought, history of ideas, intellectual history作有说明(参见“导言”部分及注1)。尽管对于什么是思想史还有别的界定。
2.2.1 专家的积极性 以回收应答率表示专家积极性,即专家对本研究的投入程度。本研究第1轮咨询专家应答率为93%,1名专家因出国未及时应答,第2轮咨询专家应答率为100%。
当然,强调江南儒学研究的当代与未来性,并不等于这一研究的提出完全基于此。相反,江南儒学研究的当代与未来性是基于历史本身而产生的,尽管历史上没有以此命名的思想流派,甚至没有江南儒学这样明确的自觉。因此,我们需要给予进一步的说明。
这个说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历史中的南北经济社会文化重心的转移及其衍生出的江南问题。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当然更引起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关注,相关的史料与研究汗牛充栋。这里,仅提及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梳理作一个简明的转述,以引起我们后续的讨论。《国史大纲》虽成书于上世纪前半叶,但钱穆以其纲目体,将这个长时段的重大的历史显象勾勒得极为清晰。钱穆指出,中国历史上半段的重心在北方,下半段在南方,这个转移以安史之乱为节点,转移的过程则很长,似乎直到明代才完成。[注]关于南北经济中心的转移及其完成的起点与终点,历史学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关于社会与文化的中心转移也是如此。这里的讨论且取安史之乱为起点,明代为终点,但具体到江南儒学的孕生与演化,后文将结合江南的形成具体而论。钱穆从经济的指标,比如漕运、丝织业与陶业,到文化的各部分,比如应科举的人数、宰相籍贯人口,再到社会,如户口盈缩、行政区划的大小繁简,作了系统的梳理。[注]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共用三章,即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章来梳理论证南移的问题,其中梳理南移现象与过程的部分集中在第三十八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从这个梳理与论证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不仅是毋庸置疑的史实,而且这个南移的过程最终结穴于环太湖流域的江南也是极其明确的。
也许因为这个转移过程,尤其是环太湖流域的江南成为这个转移的完成标志直至明中叶才确立,所以才会在晚明出现陈子龙(1608-1647)那样的全面论证江南地位的思想家。按照森正夫的研究,陈子龙论证的江南包括今日的江苏省南部、上海市、浙江省北部,即以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的三角洲为范畴的区域,其实就是环太湖流域。在多达七篇专文中,陈子龙不仅从综合地理条件、具体的水利与地质特征、土木建筑技术、养蚕丝织业、女性能力、水产资源、文章与艺术个性等各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江南在历史过程中所确立起来的重要性,而且更依据明朝政权本身的建立过程及其完整的政治设置,赋予了江南是明朝国家之根基的地位。换言之,陈子龙的江南论决不是就江南而论江南,而是已完全从整个中国的视野来强调江南的地位。[注]森正夫:《陈子龙的江南论》,见氏著:《“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5~149页。
不过,也正因为陈子龙的系列文章,可以反证这一个事实,即江南作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真正确立,虽然在事实上早已在形成过程中,但名位似乎要晚来很多,否则陈子龙也无必要作这样的系列文章,尤其是他也无需以自设问答的文体来作辩明。这一名位晚于实情的现象似乎在提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江南已明确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这一事实面前,还需要去辩明它对于国家的根基地位呢?可能的解释也许很多,但从陈子龙自己设定的提问,结合我们的研究对象,似乎可以聚焦在两个解释上。其一是江南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心只是一个偶然的暂时的结果,对于历史中的人而言,仍然存有重心回归的期待,因此并不认定江南已为重心,直到晚明已为定局,还需要陈子龙来论证。其二是江南固然已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心,但其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文化形态背后的思想系统不具有正当性。陈子龙在辩论中强调,作为国家根基的江南的确立,“实惟有吴风教固殊焉”。这个“风教固殊”在陈子龙的论证中当然是正面的,但在北方看来也许完全是负面的,或至少是不正统的。[注]晚清江南因太平天国战乱人口大减,有大批河南移民落户至浙江长兴与安徽广德之间(参见雷震:《我的母亲》,台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据移民至长兴的笔者父系族谱,笔者已是第八代。在改革开放以前,河南移民基本以村为聚居,语言与文化殊于当地。虽然这些移民村落基本分布在县域中相对偏僻落后之处,经济水准明显低于当地社群,但在文化上却有着某种属于集体无意识性质的代表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一个最显明的证据就是他们都把当地人称为“蛮子”。这也许不一定构成非常有力的证据,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田野性质的佐证。
这便意谓着,作为一个区域,江南能否成为国家的根基?或者,江南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的根基?或者,江南是如何成为国家的根基的?这自然便成为一个问题或者一个问题丛。由这样的问题丛出发,江南研究当然首先是一个区域研究的问题,但是由陈子龙的论证,已引发出超越区域研究的性质,关涉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及其内在动力的问题。这便意谓着江南研究不能满足于停留在经济、社会以及宽泛的文化研究上,而必须深入到作为江南的精神中去,这是江南儒学研究得以提出的重要学理所在。
3.4.4 秋季降水量各地出现异常的年份有所不同,茶卡、天峻1967年出现了异常偏多,刚察、天峻、茶卡1971年出现了异常偏多现象,天峻、共和1989年出现异常偏多现象。秋季降水量出现异常偏少的年份较少,仅海晏1991年和共和1984年出现。
如果说,中唐以前的儒学更多地呈现为“周孔之道”,那么来自江汉之间的《诗经》中的《周》《召》二《南》,似乎不宜排除在江南儒学之外,因为正如欧阳修所讲:“《周》、《召》二《南》至正之诗也。”[注]《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十《经旨·诗解八篇·王国风解》,上海:上海古籍书版社,2009年,第1602页。而诗教正是孔子行教的最基本内容,所谓“不学《诗》,无以言”。[注]《论语·季氏》。至于孔门十哲之一的吴人子游,其思想更属于孔子儒学在江南的开始。就此而言,江南儒学自始就呈现出两个源头,一个是来自长江中游的古朴原始的周召遗风,一个则是直承孔子在长江下游传播的仁学。自此以下,两个源头流向环太湖流域的江南儒学,似乎更清晰地呈现为江南的亚区域学术思想流派,而很难简单地界定谁能代表江南儒学,或者由此提炼出江南儒学是什么。此外,两个源头以下的江南儒学流变,并不是师承谱系上的学术传承,而更主要是空间地理上的思想起落。换言之,若以江南论儒学,则历史中的亚区域学术思想流派是清晰的,而作为江南的儒学却不免是模糊的。
总之,江南儒学确实是一个首先由外部因素所型塑而成的概念,同时又是基于具有坚实历史基础的学理上的。不过,江南儒学的提出虽然具有事实与学理的依据,但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其内涵仍然需要进一步界定。这个界定首先涉及到如何理解作为空间的江南,其次是作为对象的儒学。两个问题都所涉甚大,这里先处理儒学的界定。
该文拟通过对/ɝ/的声学实验,回答以下问题:贵州民族学生与美国英语母语使用者在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的数值上是否有区别;不同性别是否呈现不同的区别;以上区别是否具有显著性特征,然后在总结这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不同性别的贵州民族学生和美式英语母语使用者在/ɝ/发音上的异同,并分析造成区别的原因。
由此出发,江南儒学的研究将聚焦于儒家思想者的文本分析,以期发现与阐明那些型塑江南性质与特征的内容,但同时又会兼顾这些思想文本与它的现实境遇之间的互动。在处理后者的问题时,也许我们的研究将溢出思想文本的哲学分析,延伸到其他文献的处理,以谋取思想史研究的效果,甚至不排除田野调查,尤其在进入明清以后,前文所注即是一个例子。毫无疑问,具体的过程将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决定,不宜也难以作清晰的规定。此外,当我们对江南儒学研究中的儒学概念作经学与哲学这样的自我限定时,除了儒学本身具有这样的依据外,一个最根本的考量是源自专业的操作。“术业专攻”也许是一个逃避研究复杂问题的遁词,但的确是一个实际操作中的理由,况且专业精神终究也是现代学术分工的基础。当然,对江南儒学作这样的自我限定,决不意味着其他视角的观察就不属于儒学研究。前文对“风教”的着意强调,实际上就包含着对儒学作广义文化意义上的理解。换言之,多视角的观察不仅不应被排除,而且这正是发现与呈现儒学思想多样性的根本路径,在可能的情况下,江南儒学研究应该努力尝试。
相对于江南儒学研究中的儒学概念的自我限定,如何处理与历史中已形成的区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更难的问题,比如浙学、吴学、皖学。前文已述,江南儒学不是历史中的概念,而是今天在江南研究的学术语境中追求研究深化而提出的概念,虽然它具有来自历史的依据。当提出这一概念后,自然在认识上会以江南的视域来进行观察,在逻辑上就会涵摄江南区域内的各个学术思想流派,诸如吴学、皖学、浙学就成为江南儒学中的亚学术思想流派,整个研究应该在江南的意义上来探讨儒学,或者说是探讨儒学的江南性认识。然而,一旦在进入具体研究时,不难想象,作为子项的各个亚学术思想流派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理解江南儒学的窗口。如何与既有的各个亚学术思想流派的研究保持某种程度的间距,实乃江南儒学研究面临的难题。一方面,这个问题难以用预设的结构去框定,而是需要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去具体处理的。部分与整体之间总是存在着张力的,但是通过部分来获得对整体认识的亲切感与丰富性,借助整体来凸现部分的存在感与普遍性,则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张力就不再是冲突的,反而是必要的,不仅认识如此,实际也是如此。这同时也提醒我们,观察江南视域中的各个亚学术思想流派的互动,其实正是把握江南儒学的重要视角。另一方面,这一问题又有必要借助某种认识工具来加以化解,这个工具就是“江南”。江南儒学自始便预设了一个江南的视角,它自然地要求从江南的视域来理解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在处理哪个具体的亚学术思想流派,都足以从中跃出而见其江南性。但同样是不易解决的问题接踵而至:何谓江南?什么是作为儒学的江南?
PTEN的亚细胞定位对其在正常细胞中的功能及其抑癌作用至关重要。PTEN可在细胞质和细胞核之间转移,且均具有特定功能。在细胞质中,PTEN与细胞质靶标相互作用调节细胞增殖、细胞周期进程、细胞凋亡、细胞黏附、迁移和侵袭。在细胞核中,PTEN可维持染色体稳定性并在DNA双链断裂修复中发挥作用,从而维持基因组的完整性[2]。PTEN在细胞核和细胞质之间转移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二、 作为儒学的江南
当然,谈到江南儒学的真正孕生,无疑应以六朝为重。在江南开发史上,六朝原本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于儒学而言,晋室东渡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由于晋室是被匈奴刘汉所灭,因此晋室东渡不仅是一个朝代的替代,更是华夏文明的南移。尽管江东士族也自有文化渊源,吴地也有贺循这样的礼学名士重臣,但中原衣冠南渡却直接催生了江南儒学。一方面,东晋带来的晋室中兴复使玄风独振,另一方面,西晋的灭亡也让时人将永嘉之弊归咎于正始以来的虚荡放浊。在这种充满张力的学术思想语境中,东晋及其后的南朝儒学不仅在承续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基础上逐渐开出兼综佛道、“约简,得其英华”[注]《隋书》卷75《儒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06页。的新风格,而且培植起“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注]《南齐书》卷39《刘瓛陆澄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63页。的新风尚,江南儒学得以型塑。
儒学是一个边界很不清楚的语辞。广义上讲,即取其文化之义,则几乎涵盖传统生活的一切,尤其当研究一个区域内的儒学传统时,往往容易指向这样的广义。前述陈子龙所谓“风教”,便可以与此对应。虽然“风教”也可以作狭义的文化限定,但如果在文化的意义上来研究江南儒学,那么现有的江南文化研究就已经可以了,实在没有必要另外标举江南儒学。因此,当我们型塑江南儒学这个研究领域时,儒学的内涵指向不是广义的文化,而是狭义的“学”。借用李学勤“儒学的核心就是经学”[注]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见“光明网”2012年6月23日。的话,江南儒学的研究对象将主要是以经学为核心而展开的儒家学术思想;而置换成现代学术的分类,则是以哲学为视角的儒学研究。不过,在明确了这个基本界定后,必须马上跟进的说明是:由于江南儒学的研究是一项与地方区域具有高度相关性的研究,而无论是作为传统知识意义上的经学,还是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江南儒学不仅在知识上与其他门类具有非常粘连的关系(比如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并重几乎是江南儒学中最显著的知识现象),而且在实践上延伸到必须以其他知识门类加以分析的领域,比如陈子龙所讲的“风教”就很大程度上溢出了哲学的分析范围。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地理上,“南”似乎自始即是一个既有确定的空间所指,而又具延展性质的指向。《诗经》以《周》《召》二《南》开篇,这个“南”便是如此。程俊英在广泛征引材料而明确了二南的具体地区后,最终又引方玉润《诗经原始》以周、召为地名,南则是周、召以南的指称,从而断定:“周的西边是犬戎,北边是豳,东为列国,唯南最广,而及乎江汉之间。”[注]程俊英: 《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页。所谓“江汉之间”,似乎已是以长江、汉水为边界了。只是“唯南最广”,向南的边界仍然是可以延伸的。所以,才会出现周振鹤所讲的情况:“即使在唐代,江南一语的用法,也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故韩愈所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的江南,指的其实是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注]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概言之,就中国的自然地理而言,广义的江南可以指淮河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区域。
如前所述,大量研究发现了身体活动与成功老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研究者更倾向于做身体活动对于成功老化的促进作用这一方向的解释。但是前人研究有很多是非实验研究,因此,对于身体活动与成功老化之间关系方向的解释似乎证据不足。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成功老化者似乎有更多的锻炼参与。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和纵向追踪研究来进一步探讨身体活动与成功老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为老年人身体活动促进以及成功老化促进提供科学依据。
不过,由于历史中的具体个人似乎更多地归属于自己的所在社群,这样的归属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政区划,因此,在大致认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政区地理对于人们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江南的概念也当如此来看。按照周振鹤的梳理,作为行政区域的江南大致是沿着两条路线汇聚于环太湖流域。一条是由秦汉时期的长江中游以南的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向唐代的江南道过渡,再经由两宋的两浙路,最后集聚为明代的环太湖流域;另一条是由秦汉时期的长江下游芜湖至南京一线的江东或江左,进入环太湖流域。因为这一段的长江流向是西南往东北,由中原过江向南,给人的现场感觉更像是由西向东,故有江东之称;而古人又以面对水的来源定方位,因此江东又称江左。由长江中游与下游所构成的广义江南,实际上横跨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而最后所集聚成的狭义江南,则是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所在的环太湖流域,或者再加与此水系接壤的镇江府与杭州府,共七府。
从这个流变的江南,可以看到,一方面,江南概念的空间是在缩小。如果细加审视,则足以意识到这种缩小,即五府加二府的江南,亦是建立在巨大的共同性之上的。这个共同性首先还是基于自然地理。五府是环太湖流域,这个天然水系使得该区域在传统农业中国成为一个天然的经济共同体。而加上镇江、杭州二府,实际上是基于环太湖流域的运河水系添加,从而使得江南作为一个自组织区域获得某种开放性。其次是共同的语言系统。五府是吴语区,镇江是江淮官话,杭州因为曾经是南宋都城而使它的语言既不属于吴语,也不属于钱塘江以东的越语,而成为一个自成系统的南北混合语系,似乎成为吴语与越语的过渡。由此经济与文化的两端,可以看到,江南由一个宽泛的自然空间,经由行政区划的作用,最终形成环太湖流域,其实它完全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活动与文化认同上的。另一方面,江南概念又指向一片很大的腹地。无论是从长江中游一线,还是从长江下游一线,环太湖流域的狭义江南与荆楚、湘赣、越瓯、淮扬有着天然的沟通。这种沟通使得江南在自成一个自足系统的同时,仍然具有着开放的空间,江南也因此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多元文化的境域中。
回到我们的主题。对于我们而言,江南一方面完全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趋向极其明显的概念。那么,什么又是作为儒学的江南呢?显然,由于江南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因此处在这个变化中的江南儒学,很自然地呈现出多源与多样性。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插入略加申述,即江南开发的这种流动性的背后动力来自哪里?冀朝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提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页。这个论断在统一时代,即朝廷权力强盛时,也许是成立的,但在分裂或动荡时却未必成立。就江南的开发而言,后者显然更为重要,每一次江南开发的推进,更多地表现为人们逃离政治黑暗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的结果。[注]参见钱穆在《国史大纲》第三十九、四十章的论述。强调这一点,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江南以及江南儒学的发展的自主性或内生性。
与空间的流变相应,江南的地标也呈现出流动性。由于江南的开发在六朝就进入一个标志性时段,因此吴称建业、东晋始称建康的六朝之都南京,无疑是早期江南的地标。隋文帝统一南北,将南京夷为平地,以长江北岸的江都,即今日之扬州,作为扬州治所,因此唐以后扬州成为江南的地标。安史之乱后,江南进入继六朝之后的第二个重要开发阶段,重心向环太湖流域移动,苏州开始成为江南的地标,直至晚清太平天国。在从安史之乱至太平天国这个长时段的后半期,在整个环太湖流域中,元代所设的松江府逐渐凸显,并最终在清代太平天国严重破坏苏州之后,取苏州而代之,这便是上海的崛起。[注]上海设县以及兴学,参见赵孟頫:《大德修学记》,《赵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8页。与此同时,原本位于环太湖边缘的杭州,以及钱塘江以东的宁波、绍兴,同样因太平天国而受重创。上海作为战争的避难地,终于在苏浙皖三省的剧烈动荡中,辐聚整个地区的资源而成为江南的新地标。伴随着上海的崛起,一方面环太湖流域继续成为上海的腹地,另一方面海洋成为连接新世界的通道,江南以上海为龙头,在中国率先进入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
吕杨的故事,圈里面大家应该都听了不少,尤其是2017年8月20日,他登顶侍酒师大师的消息从伦敦传来,各个版本的报道和祝福纷至沓来,在圈中传为佳话。过去一年的各大酒展和活动中,也越来越多地见到他的身影。然而,成为大师这一年,他又有哪些变化?谁又最有机会成为我们中国热土上下的一位大师?
教学情景是学生学习的“引子”,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前奏”.生活中处处有化学,依托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开展教学工作,创设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情景,学生的学习热情会大大提升,课堂教学也会更具活力.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生活现象、社会事件、学生的生活经验等.
另一个方面则是聚焦到“有吴风教固殊”本身。既有的江南研究以经济为核心,广涉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似乎极少涉及意识层面的精神及其教化,即“风教”。这更多是属于狭义的文化,也就是本文提出的研究领域——江南儒学。中国传统的文化主流虽然存有认识上的分歧,但我们取儒家为主流的认识。从陈子龙的论证看,他虽然从自然环境一直论证到制度设计与安排,但最终却归之于“风教”,这其实就是我们提出江南儒学最直接的历史依据。在前述中,我们指出历史上没有以江南命名的思想学派,甚或没有江南儒学这样明确的自觉,但是由陈子龙的论证中所提出的“有吴风教”,其实应该承认至晚在明末,从江南的整体性上来理解“风教”的意识还是产生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陈子龙所谓的“风教”,虽然不排除各种精神系统,但显然是以儒学为基本指向的。因此,相对于江南研究范畴内的大量经济、社会,以及广义的文化研究的展开及其成果而言,聚焦于儒学的研究尚付厥如,亟待补上。需要说明的是,这样讲,并不是说关于江南区域内的具体的儒学研究没有展开,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以说始终不断,且不断在推进。这只是说从江南这一特定视角来研究此一区域的儒学的观念还没有形成。如果细细品味陈子龙的“有吴风教固殊”,则可以体会到他一方面是从江南的整体性,即“有吴”来讲的,另一方面是归结于“风教”的“固殊”,这个“固殊”正是江南儒学作为新的研究视域所需要去面对的,固殊的面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固殊性?这样的固殊性为什么会导致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以及它是否在当代仍然存活,并能否引向未来?
比如江汉以南,便有湖湘学派。在南宋儒学的整个建构中,从胡安国父子到张栻,湖湘学派不仅于当时卓有建树,而且影响及于后世。由湖南向东进入江西,赣学在北宋就已经由欧阳修引领士林,而王安石新学更是左右了北宋与南宋之际一百多年的学术思想;南宋中期以后虽然新学逐渐消歇,但象山心学与荆公新学很难完全说是没有精神上的共通。谈到浙学,虽然不能说从南宋事功学,至明代阳明心学,再到清代浙东史学,甚至到晚清民初的浙学,这其中有一个确定的学术思想谱系,但毫无疑问的是,后起的浙学代表人物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通过接续前人而加以表达,而且越往后越是明显。湘、赣、浙三省如此,苏、皖亦不例外,不待赘言。甚至可以说,在江南的各个亚区域中,越是细分的学术思想流派似乎越显得有确定性,比如章学诚分浙学为浙东与浙西之学,吴学则有推尊古文经学的扬州学派与崇尚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显然,要将整个江南的这些不同区域的学术思想流派统摄为一个清晰的江南儒学,不仅是很困难的,甚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充分认识到这样的事实的同时,另一个事实也是不应该被遮蔽的,即上述列举的这些内涵与边界相对清晰的江南亚区域学术思想派别,它们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联。有些是直接受容的,比如湖湘学派与浙学。张栻去世以后,浙学中的陈傅良到湘中,尽收张栻门人。[注]《朱子语类》卷123:“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胡季随亦从之问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61页。这样的记载,不免有夸大的成分,而且这样的尽收,诸如科举这样的外在原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难以否定湖湘学与浙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的共鸣。又如阳明学在浙中的传播与在江右的传播,恐亦难定伯仲。有些则呈现竞争性,比如章学诚区分浙东与浙西之学,便涵蓄着他与戴震的学术思想较劲;而同为吴学的扬州学派与常州学派更是显见的对抗。这样的关联不仅存在于同时代的区域性学术思想流派之间,而且存在于跨时代的区域性学术思想流派之间,比如晚清的湘学代表谭嗣同便是“夙慕宋陈同甫,故自名嗣同”。[注]参见《宋恕集》卷九《哭六烈士》之《哭谭嗣同》中“空见文章嗣同甫”及其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15页。学术思想之间的这种关联,也许在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中都能找到些许例子,但在江南的各个亚区域学术思想流派之间所普遍存在的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很难轻易否定儒学在江南存在着某种精神的一致性,即共同的精神维度、彼此相关的思想内涵,以及近似的风格与特征,等等。事实上,《中庸》所记子路问强,而孔子区分南方与北方之强,便是取精神的一致性来作答的。承认精神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与多样性截然对立。在讲到摩尼教义正是适应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所处的生态环境而获得继续存在这一历史事实时,张广达以为,“在不同的环境和语境中,历史的一致性(historical coherence)各有各自的心智、意识的投影,并通过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不同方式的叙事(narrative)体现为文化的多样性”。[注]张广达为马小鹤的《霞浦文书研究》写的序,见马小鹤:《霞浦文书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这个论断对于理解江南儒学的精神一致性与学术思想流派的多样性应该是有启发的。
当然,承认江南儒学具有精神的一致性,并不等于要对江南儒学给予某种僵硬的界定。相反,与其追求对丰富的江南儒学作出某种界定,毋宁将江南儒学视为在历史中流过不同区域的河。这不仅更符合事实,而且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要取江南儒学的视角来统摄这个极具丰富性与层次感的对象。作为儒学的江南,正与江南本身一样,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而且这一流动至今没有停止。虽然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江南儒学这条河流曾经出现过干涸与断流,但最近的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又极大地激活了她。因此,理解作为儒学的江南,在时间的维度上展开,既可以对她曾经的构成与创化把握得真切,更可以通过这样的把握对她未来的可能流向进行前瞻,表达期盼。
三、 江南儒学的分析时段
对传统中国进行研究,其分析框架普遍受制于朝代史的影响,这中间自然有某种合理处,尤其是方便于史事的陈述;而对于学术思想的衍化,政治毫无疑问又是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因此朝代更替作为理解学术思想变化的时间坐标,更具有某种难以动摇的必要性。但是,就史事的陈述而言,所有的陈述都构成为某种叙事,而叙事一旦形成为模式以后,往往会成为人们观察历史中的一切现象的预设;至于学术思想的衍化,在充分承认政治因素的外部作用的同时,还应该考虑来自学术思想自身的动力。另外,还应考虑同样属于外部作用的其他因素,比如经济方式、地理环境。事实上,对于江南儒学而言,经济方式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恰恰是很大的。
由于地理环境的改变是缓慢的,而且地理环境的改变又往往是由经济活动所引起的,而传统时代的经济变化也是渐进的,因此对于江南儒学的分段,我们更倾向于取长时段,从而尽可能地凸显江南儒学的江南性。当然,一切渐进的变化又往往因政治事件而出现拐点从而获得彰显,因此分段又总是会以政治事件而标识。当然,这与习惯于朝代史的分析框架终究已有很大的不同。
由此,江南儒学被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先秦至六朝的江南儒学孕生。前文已有述及,在先秦时期,既有江汉之间反映周代风尚的《诗经》二《南》,又有南归的子游儒学,它们都构成江南儒学最早的内容。尽管在学术思想的意义上或许还不够充分成型,但是得益于近年来郭店竹简的研究推进,结合散见于《论语》《礼记》《史记》等传世文献,子游的思想有所丰满,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孔子思想的南传,而且更有益于理解南传的儒学具有怎样的特质,这种特质对于江南儒学的意义几乎是基因似的重要。
何处是江南?这好像是一个既容易又难解的问题。容易,实乃在地理上似乎是确定的,总应该是在江的南面,尽管这江是哪一条、哪一段仍可分疏;难解,则不仅是地理上的江南指认有时代的变化,以及历史行政区划中的江南在变化,而且江南是一个包含着多方面含义的概念。由此,作为儒学的江南,无疑更难界定,因为它关乎学术思想,无形而又真实地存在;加之作为学术思想的主体的学者与思想者是流动的,许多流寓江南的北方人,他们的学术思想如果归属于江南儒学,总应该是经过说明的。
从学术思想所依赖的文本分析看,东晋虽然儒学呈现反动,但玄风仍炽,六朝江南儒学的成就更主要集中在南朝经学,前述新风格见于此,新风尚也因此而起。只是,南朝虽然经学颇为兴盛,但著述却基本散佚。除了在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书中辑佚了南朝诸位经学家如雷次宗、贺等的文献可以供综合研究外,最可称幸的是吴郡皇侃《论语义疏》完整保存了下来。综述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而提及一专书,实乃皇侃此书经历了失而复得的命运,而它对于理解此一时代的江南儒学及其在整个儒学发展中的意义又至为重要。据四库馆臣讲:“迨乾淳以后,讲学家门户日坚,羽翼日众,铲除异己,惟恐有一字之遗,遂无复称引之者,而陈氏《书录解题》亦遂不著录。知其佚在南宋时矣。惟唐时旧本流传,存于海外。”[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5《经部三十五》第一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77页。清儒对宋学多有贬斥,馆臣所讲的原因是否可靠,且存而不论。皇侃此书在南宋中晚期失传,直至清乾隆开四库馆才从日本流回,则是一个事实。这意味着从晚宋到清初的长时段内,此书已没有影响。不过,由于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都著录有此书,因此表明至南宋初,此书还为人知,对北宋,甚至对朱熹那代人,都仍然会有影响。事实上,只要稍加细审,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论语义疏》最显见的集解法在朱熹的《论语集注》得到传承,而义疏体最重要的分章句与设问答则在《朱子语类》中获得充分的呈现。此处仅举这一著述风格,以说明《论语义疏》尽管在晚宋后失传,但其实是构成了儒学从汉唐转向宋明的重要环节而为宋代儒学所吸纳。更进一步说,南朝的江南儒学对于南宋儒学的意义是存在的,隋唐的政治统一乃至学风的南北汇流,似乎并不必然阻止江南学术思想的隔代传承。
第二个时段是唐宋变革后的江南儒学衍化。这样确定第二个时段,问题接踵而至。首先,唐宋变革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起点与终点都难以精准确定。其次,如果将安史之乱作为一个起始的节点,那么在我们的分析架构里,从隋到安史之乱这段时间似乎断了。最后,所谓“唐宋变革以后”,这个“以后”又到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分析架构中,这个“以后”一直是到近代,那么这个时段就显得特别长。
(1)施工对象精准化。准确掌握施工对象的地下地质资料、周围环境、变量等因素,依托油田数据平台建成内部数据库及地层模型,形成对岩性特征的精准判断,包括渗透性、研磨性、压力系数、可钻性等。
必须承认,上述问题是存在的,而回答也确实是勉强的。唐宋变革自内藤湖南提出后,虽然成为史学界分析传统中国由中古转向近世的一个颇有意义的框架,但这个变革的起点与终点都不具有确定的时间点,而只是一个宽泛的过程;况且唐宋变革的预设也并非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我们认同唐宋变革的分析框架,因为自内藤湖南提出这一预设后,不仅大量的研究佐证了这一预设,而且也有效地推进了对近世中国的认识;至于把安史之乱作为这个变革的时间节点,固然与史学界众多的研究相关,比如前引钱穆的论述,也是因为安史之乱与永嘉之乱相似,直接导致了中原人口向江南移动,推动江南进入第二次大规模的开发,以及江南儒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的勃发。相比于晋室东渡,安史之乱虽然没有使政治中心由北南移,但经济、社会、文化的南移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即李白所谓“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注]《李白集校注》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84页。江南由此踏上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道路而不可逆转,虽至今日仍大势未改。这也是这个时段拖得很长,一直将它划在近代的原因;而所以要将近代以降另辟一个时段,不是因为江南作为中心地位的改变,而是因为此后的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江南儒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追求。
由于将安史之乱作为江南儒学第二个阶段的起点,自然就存在着如何看待从隋至安史之乱这一时期江南儒学的问题。事实上,随着隋灭陈,如前所言隋文帝夷平南京,江南至唐中期便一直处于被贬压的态势,包括儒学在内的江南文化自然首当其冲。“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注]《李白集校注》卷21《登金陵凤凰台》,第1456页。,“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注]刘禹锡:《乌衣巷》,《全唐诗》卷365,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127页。,这形象地折射了此一时期整个江南文化的衰落。这种状态一直要到唐中期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生变化时才开始改变,陈寅恪讲:“夫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之系统,而北朝之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0页。财政制度开始取用南朝旧制,南朝的旧文化也始得复苏,所谓“宣城有贤长帅以廉风俗,新安有佳山水以资胜践,为仁由己,赋禄且厚,此皆不期至而至者”。[注]《权载之文集》卷36《送歙州陆使君员外赴任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8页。总之,从六朝到唐宋变革之间,江南儒学存在着一个中断,这确是事实。
在整个第二个阶段,与江南经济社会文化定格为此一历史时期中国的中心相似,江南儒学既是江南区域性的,也代表了中国。在前一个阶段中,流寓江南的中晚唐啖助、越匡以及啖助弟子吴人陆淳的新《春秋》学与北宋湖学先后开启了宋学。此后北宋儒学的中心虽然在河洛地区,但从欧阳修、范仲淹,到王安石、周敦颐,都是来自江南,而传承与传播二程洛学的学者中,来自江南的学者构成了重要力量。南宋儒学的重镇虽称闽学,但一则朱熹的故里即今天的江西婺源在当时属于皖南的徽州,再则朱熹的活动中心主要在建阳武夷地区,与浙东金衢相邻,而金华则可以说是南宋儒学的学术中心。进入元代,金华儒学仍是学术思想的代表之一,至元末明初更成为重心。
从安史之乱到近代,这一长时段的江南儒学虽然在根本的学术思想范式上同处于一个时段,但可以进一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既为了叙述的方便,更有内容的依据。前一个时段是从安史之乱到1421年,这一年明朝迁都北京。后一个时段是此后至近代开始。选择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取自斯波义信对江南经济的考察。在考察宋代江南经济时,依据上升、平衡、下降之类的周期循环理论,斯波将考察的时段从宋朝开国一直下延到明初,分成七个时期:“第一期,960-1030年代,开拓疆土的开国期;第二期,1030年代-1060年代,上升开始发动期;第三期,1060年代-1127年,上升期;第四期,1127-1206年,实质性成长期;第五期,1207-1279年,下降始动期;第六期,1279-1367年,下降期;第七期,1368-1421年,上升始动期。”他的整个时段选择与分期划分是多方参照了政治变迁和制度框架的结构变化而作出的。[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0~82页。而对江南儒学而言,援引这一经济史的分期,一则是因为我们基本认为经济民生的关怀是江南儒学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内容,再则是从江南儒学的自身变化出发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与金华士人社群具有重要关系。朱棣发动靖难之变,于建文四年(1402年)取代建文帝登基,属于金华朱学的方孝孺殉难,可以说是启动了两浙朱子学的下降期,为后来浙中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提供了某种思想空间,而阳明心学使得包括江南儒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发生转向。
俄联邦工商会国际商业仲裁法庭的德米特里·奥格罗多夫法律博士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立法涉及交叉学科的问题,需要系统地研究人工智能系统和机器人技术的法律成熟度、管理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法律机制、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和机器人的法人资格。机器人的法律责任及其错误应该由其所属者或者使用人承担。
后一个阶段,从阳明学的崛起到清代考证学,江南儒学的版图渐由江右向两浙与皖南移动,最终集中于环太湖流域。阳明心学与清代朴学风格迥异,纳入一个阶段,似颇不类。但如果意识到清代朴学虽然与整个宋学相对立,但却是直接因阳明心学激起的反动,相反相成,适成映照,阳明心学正可以视为宋学到清学转移的环节而纳入此一阶段,是理解江南儒学的重要内容。而且,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对话乃至冲撞,正构成此一阶段江南儒学的重要形态,比如东林对阳明心学的纠弹、晚明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教西学与儒学的碰撞、章学诚对浙东与浙西之学的区分、吴学与皖学的双峰对峙、同为吴学的扬州学派与常州学派的分水竞流,其学术思想的主体性挺立未尝不是阳明心学的思想遗产。
刘婷婷,裴丽,王一群,等.基于光载波抑制调制的可调谐高倍频毫米波信号发生器[J].光子学报,2018,47(12):1206003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时段,则是近代以降,直至今日追求现代化转型中的江南儒学探索。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四十八岁的龚自珍“不携眷属傔从,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出都”,[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之4自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踏上南归之路。这年离他从学于刘逢禄,皈依常州公羊学已整二十年。[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之59自注,第81页。这位十二岁即亲炙于外祖父段玉裁,深得朴学精髓而又皈依于今文经学的敏感诗人[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之58自注,第79页。已预感动荡时代的来临,并揭开了江南儒学回应时代的篇章。
自此以下,中国便进入了三千年未遇之变局,江南儒学与整个时代一起跌宕起伏。从晚清到“五四”,“五四”到“文革”,直到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江南儒学与整个儒学一样,似乎经历了一个从勉力求变以图回应世变,到彻底污化跌至谷底,又绝处逢生再现贞下起元的过程。虽然整个时代呈现出这样的起伏波段,但细加观察,江南儒学则又因其复杂而呈现出丰富性。且举一例以见之。俞樾、章太炎、鲁迅,可谓师承清晰,而其学术思想所造迥异;师承有自,尚且如此,整个江南儒学更可想见。如果为了观察与理解此一时段复杂的江南儒学而提供某种切入,我们姑且提示两个视角,并以此结束本文。
这两个视角似乎都可以由独身南归的龚自珍身上获得呈现。一是出都。此一阶段的江南儒学似乎都自外于体制,留情于社会。晚清的孙衣言、张謇、唐文治如此,民国的章太炎、马一浮也是如此。学术思想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江南经济得力于民营也是如此。出都,离开政治,但不对抗;自外于体制,用心于社会。也许这种倾向早已在江南儒学得以孕生的六朝时期就已播下种子,因为无论是从江南士族那里,还是从南迁士族那里,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思想与行动。而且,在唐宋变革后的第二个时段的江南儒学那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六朝的种子已出苗成林;在第三个时段,这些林木已然成为起屋架房的支撑。
二是载书。此一时段虽然学术思想正在巨变之中,但江南诸儒无论各以何种形态呈现其学术思想,无不基于深厚而广博的知识,中学固不待言,西学也深涵其中,不仅经史子集,而且数理工商,儒学通经致用的精神深得贯彻。龚自珍的“载书”可谓极具象征性。在学术思想大变更的时代,江南儒学致力于旧学新知的融合创新,而其思想的新创每每基于坚实的学术中,学术与思想、知识与价值相涵共生。且引前注所及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五十八、五十九,以见此一时段江南儒学斯文有自而又微言阐扬的精神与风格:
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
在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全程中,均要严格秉持“效益至上、总量均衡、以收定支、权责对等、切实可行”的原则。预算工作以实现企业业务经营目标为基础,即获得最佳效益。针对相关的经营目标与预算指标,需进行全面解析,并强化其间的平衡性。财务人员可结合企业发展现状及战略目标,采用固定预算或弹性预算;定期预算和滚动预算等多种方法,同时选用的预算编制方法还要符合企业经济业务的特征。
导河积石归东海,一字源流奠万哗。
(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坛段先生授以许氏部目,是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始。)
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
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
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的推广让信息化走入每个家庭中,网上学校和提供教育资源的网站也逐步增多,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模式,让更多的人通过网络来进行学习,也让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有了学习的工具。新东方在线就是通过开办网校来进行网上授课,其授课主要内容是考研、英语等应试课程的学习,可以让想要继续深造的人有一个学习的平台。大学生慕课是通过上传教学视频来授课,其课程大多是大学课程,讲课教师通常是名校教授,可以让一些对于专业技术非常感兴趣的大学生了解不同顶尖人士对专业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可以与兴趣相同的人进入一个学习圈子,加强交流[4-5]。
(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
利用多媒体课件、桌面演练和应急预案演练,强化员工对每个工种、每道工序的操作方法、要领和安全要求的记忆;选拔优秀班组长、工人技师当“老师”,言传身教传授操作技能,组织现场训练;开展基层建设、基础管理、基本功训练检查,以群众性的自查互查与自纠互纠形式,查纠明显违章违纪行为、查纠不规范操作行为和管理行为,并制定纠偏措施,及时整改,筑牢了安全文化建设群众基础。
The Proposal, Content and Segmentation of Jiangnan Confucianism
He Jun
(SchoolofPhilos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southward shift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from North China to Jiangnan area is a noteworthy phenomenon in Chinese history. Jiangnan has since become a significant region and has also been a leading for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was carried out. For a long time, Jiangnan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t has become a trend to study Jiangnan’s society and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its economy.
Confucianism is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Jiangnan Confucianism has academic root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proposal of the study on Jiangnan Confucianism will be of great help to forwarding both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cademic exploration into Jiangnan area.
Since“Jiangnan” and “Confucianism” are two concepts that are rich in content and always in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of Jiangnan Confucianism should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Confucian texts, in order to discover and clarify what has shaped its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we should also investigate into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Jiangnan Confucianism to reveal its overall structure, evolution path, and its impetus.
Throughout its evolutionary process, although the division of the diverse academic schools in Jiangnan is relatively clear,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define the term, Jiangnan Confucianism. On the one hand, the complex of the schools in Jiangnan area is still ambiguous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distinctive schools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sharing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unique to Jiangnan. Since the geographical delimitation of Jiangnan changes slowly and is mainly caused by economic activities which also change in a gradual way, we should divide Jiangnan Confucianism not into dynasties, but into three longer periods: first, the birth of Jiangnan Confucianism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to the Six Dynasties; second, the unrolling of it since the revolution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change of the capital city to Bei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further divides this period into two; third, its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in recent few decades.
Keywords: Jiangnan Confucianism; diversity; segmentation
[作者简介] 何 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江南儒学的构成与创化"(项目批准号:2018XAC01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晓 诚]
标签:江南论文; 儒学论文; 思想论文; 学术论文; 时段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江南儒学的构成与创化"; (项目批准号:2018XAC011)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