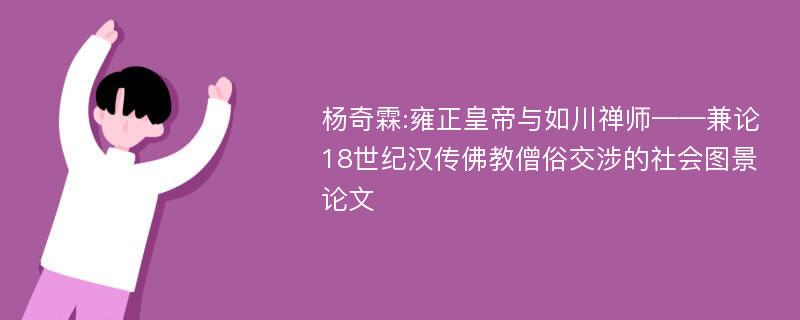
内容提要:清临济宗禅师如川超盛在雍正帝晚年振兴佛教的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凭借玉琳法嗣的身份被诏访入宫,受封无阂永觉禅师,后奉旨前往江浙看查祖庭,修葺庙宇,整肃清规,拣选僧众,并与地方社会往来密切。进入乾隆朝,超盛又总率编修《龙藏》,参与宫廷法会,与京师王公多有唱和。超盛因此而在官方档案里留下记录,这些材料史源较早、传藏有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超盛的准确生平和不见于内典的语录,可补传统佛教史料之不足,又因其颇不易见,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即以清宫档案为主,从超盛的生平考证切入,以此来展现十八世纪中前期汉传佛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影响,以及僧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细节。
关键词:如川超盛 雍正帝 社会生活 玉琳通琇 溪行森
一、前言
清世宗雍正帝与佛教渊源颇深,具有相当的佛学造诣。①如山内晋卿认为雍正之参禅优于梁武帝、唐肃宗;其著述在思想上胜过宋太宗的《秘藏诠》和《逍遥咏》,见氏著《支那佛教史之研究》,佛教大学出版部,1921年,第331-339页。而中国佛教通史类著作,大凡涉及清代佛教,多要于有限篇幅中提到雍正帝,如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9-272页。野上俊静等著,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88-190页。忽滑谷快天撰,朱谦之译:《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2年,第864-869页。此外,关于雍正帝的清史著述,亦往往要论及其与佛教之关系,如冯尔康:《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42-456页。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增订第三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0-25页。陈捷先:《雍正写真》,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37-246页。他同汉地僧人之关系,以及对待汉传佛教之态度,与其个人和大清的利益紧密相联,并伴随着身份角色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点已为不少学者所注意。①孟森注意到雍正帝“十年以后,多刻佛经,又自操语录选政”。见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第293页。冯尔康在讨论雍正帝与佛教的关系时,分成“雍邸时”和“继位后”两阶段来进行叙述,但对于继位之后的十三年未再细分,见冯尔康:《雍正传》,第442-446页。杨启樵则进一步指出:“雍正即位后十年间绝口不言佛事,仅于朱批密折中一二见。一则政务冗繁,无暇骛外;二则‘恐天下臣民不知朕心者,或起崇尚佛教,轻视政事之疑’。雍正十一年,政局大定,一再颁发佛学谕旨”。见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第22页。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13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4页也关注到潜邸时期,认为“从时间上来考察,雍正帝之好佛主要集中在他即位之前的藩邸时期,和在位期间的最后三年这两个时间段。”杨奇霖:《迦陵性音考——兼论雍正帝与藩邸汉僧之关系》,《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8-127页,则指出三个阶段似乎恰好暗合三个“十年”。雍正十一年,世宗一改此前“十年不见一僧,未尝涉禅之一字”的态度,②《御选语录》卷十八,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22 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94页下。开始依自身的好恶与意志来对佛教进行整肃和布局。时人尝谓其“晚习禅悦”、“耆年潜心释氏”③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九《前甘泉令明水龚君墓志铭》,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喻谦撰《新续高僧传四集》卷十《明中传》,慧皎等撰《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16页上。同书卷三二《福聚传》亦云:“世宗耄勤,深求梵典,延揽高僧,研味弘旨”,第875页中,,及《律宗灯谱》径云:“雍正十年以后,世宗宪皇帝振兴佛法”④源谅《律宗灯谱》卷六《实省传》,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22 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829页上-下。,皆着眼于此。其中一大举措便是对明末清初临济宗僧人玉琳通琇及其弟子溪行森法脉加以尊崇。
从空间对火山岩的密度情况进行分析,结果火山岩密度分布规律较明显,其中密度不足2.55×103kg/m3的岩石主要处在崇礼、丰宁、平泉、唐山北边区域,而密度超过2.55×103kg/m3的岩石则主要集中在南边区域。整体来看,冀北地区中生代火山岩密度较低岩石呈现半圆弧状,以高密度岩石为中心分布。
玉琳通琇是明末临济宗磬山系开山祖师天隐圆修的弟子,原主武康报恩寺。入清后,因当时寓居京师的性聪憨朴禅师推奖,⑤定明《性聪憨朴与清初北京禅学》,《佛学研究》2016 (1):285-294。于顺治十六年奉诏至内苑万善殿说法。不久,玉琳还山葬母,顺治帝又钦点玉琳座下溪行森进京。翌年,顺治帝自觉参禅有所悟,再次诏请玉琳,命其开皇坛大戒,加“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尊号。⑥超琦辑录《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禅宗全书》第64 册,影印昭庆寺本《玉林禅师语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第736-771页。玉琳是清初禅宗大德,又与顺治帝出家疑案颇有关联,故而其生平、思想已被不少佛教史和清史学者所发掘讨论,这里不再赘述。⑦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297-299页。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98-603页,该书将“磬山系”误作“盘山系”。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3卷,第208-213页。任宜敏《中国佛教史 清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6-400页。任宜敏《玉林国师禅学思想析论》,《浙江学刊》2002 (5):79-92。忽滑谷快天撰,朱谦之译《中国禅学思想史》,第851-857页。沖本克己編集委員,菅野博史編集協力《中国文化としての仏教》,《新アジア仏教史》第8 冊,東京:佼成出版社,2010年,第132-134 頁。在玉琳通琇和溪行森圆寂五十余年之后,雍正帝出于整肃佛教之需要,再次发掘出二人的价值,将其树为佛门典范。雍正帝称赞“玉琳琇父子之书,阐扬宗乘之妙旨,实能利人济世”①《御选语录》卷十一御制序,《故宫珍本丛刊》第521 册,第213页上。,而且通过与木陈道忞、骨岩行峰等人的对比,指出在二人语录之中既无私乱纪载,也不夸耀恩遇,正符合雍正帝心目中的“卓识高见”。敕谕:“玉琳琇着赐祭一次,溪森着追封明道正觉禅师,赐祭一次,以示朕礼重纯修、表扬正梵之至意。”②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谕旨,起居注册雍正十一年正月分下,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黄绫本,编号:104000275,叶16a-25b。
为了能重振“玉琳—溪”正脉,雍正帝命各地督抚寻访国师法嗣。如雍正十一年四月,谕令将康熙帝在扬州的行宫“归并高旻寺,改为庙宇,应设为玉琳国师祖庭……寻觅玉琳国师之法嗣等安住,再于其法嗣内拣选可作方丈者立为方丈”。苏州布政使白钟山覆奏云:
表5中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较慢语速的听力材料使较高听力水平班级HP-A和HP-B在长对话和短文中得到了较正常语速听力材料版本下明显高的分数(F=4.628,Sig.= .033,t=2.139,p=.034 < 0.05;F=.057,Sig.=.811,t=2.506,p=.013 <0.05)。然而,在短对话中,语速的改变并没有明显改变受试所得的平均分数(F=2.718,Sig.=.102,t=.250,p=.803 >0.05)。
(奴才) 密往各处寻觅玉琳国师法嗣,访有江宁府江宁县大慈林僧人明定,系溪行森之孙;苏州府常熟县藏海寺僧人实鉴,系洪济行演之曾孙;吴江县无碍寺僧人明旭,系古箬行卓之孙;松江府华亭县善应庵僧人超沛,系古樵行谨之徒。均系玉琳国师法嗣。奴才一经访知即密行延请,俱已陆续到苏。复询各僧宗支,尚有何人住居何地。据实鉴说出伊师明藏系洪济行演之孙,现住常州府江阴县大隐庵,奴才随又延至苏州,俱经禀明抚臣,一一验过,送往高旻寺安住。奴才又访有上江泗州属盱眙县关帝庙僧人超干,系溪行森之徒,即往延请就近入寺安住讫。但明定等初到,尚难遽定方丈,抚臣与奴才看超沛语言明白,人亦老成,现年七十一岁,精神强健,暂令在寺照管。奴才现在分路寻觅,俟续有法嗣,一并详加拣选,有无可作方丈之人,再请圣训。③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白钟山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 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22页。
苏州府的这份奏报便是当时寻访运动的一个缩影,这些主要来自江浙地区的玉琳法嗣除了被派往磬山系寺庙焚修外,还有一部分被挑选出来送入京师觐见皇帝,如川超盛便是其中之一。
二、超盛入京受封
《御选语录》称超盛为海会寺方丈,时北京有两寺名曰海会:一在东城朝阳门外,⑤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84页上。《六城寺庙清册》记其“在羊圈子……住持普顺”⑥《六城寺庙清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转引自赖惠敏、曾尧民:《雍正皇帝与北京汉传佛寺》,李天鸣主编《两岸故宫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为君难——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论文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0年,第183页。,显然与超盛无涉;一在南城左安门外,乾隆二十二年《御制海会寺诗》云:“往来久是惜零落,构筑无过葺废頺”,并自注:“此寺为南苑往来必经之路,少年时即见其零落矣”⑦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26页。又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和硕庄亲王奏报京内庙宇十应行修理,“永定门外海会寺……等庙宇三十五座,俱附近要路,有碍观瞻,其殿宇房间皆有倒坏,佛像亦有不整,今拟应行酌量修理。”(“中研院”近史所藏《内务府奏销档案》第231 册,缩微胶卷第114-116页) 应当与乾隆帝诗所指海会寺为同一寺庙,惟言及寺在永定门外,按永定门与左安门毗邻,应即一处。,若超盛于此说法,似乎不该如此零落。因此,海会寺应是超盛赴京前的驻锡之所,而非在京新居。张文良以为是南京海会寺,但并未说明依据。⑧刘雨虹编:《雍正与禅宗》,第119页。笔者认为此指荆溪海会寺,在荆溪县(今宜兴市) 均山区湖南三十里。⑨尹继善、赵国麟修,黄之隽、章士凤纂:《乾隆江南通志》卷四五,《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南4,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9页上。施惠、钱志澄修,吴景墙等纂:《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九,《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4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4页下。另陈善谟、祖福广修,周志靖纂:《光宣宜荆续志》卷一云:海会寺“雍正间赐额宝月清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40,第388页下),雍正帝常常为自己所欣赏的僧人曾经驻锡的寺院题写匾额,以示恩宠,那么海会寺得到此匾,也可能与超盛有关。然而《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六则载此匾在杭州积善海会寺:“雍正九年总督臣李卫饬属重修,十三年御书宝月清光四字额,赐悬正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5 册,第177页上)。是否为民国时宜荆县志讹误,或是同时都赐匾,暂付阙如。其一,荆溪属常州府治下,与武进相去不远;其二,玉琳之师天隐圆修寂后迁葬于此起塔,玉琳之徒全庵行进、白松行丰皆曾于此升座,①心圆拈别、火莲集梓:《揞黑豆集》卷七,《卍续藏经》第14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980页下。超琦辑录:《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卷上,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64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50页下。且行丰灵塔即“建海会寺侧”。②达珍编:《正源略集》卷四,《卍续藏经》第145 册,第333页下。故此寺可目为临济宗磬山一系,超盛也因此得以算作玉琳法嗣。
禅宗谱系《正源略集》将超盛列为“南岳下三十六世”,然而除了《御选语录》所收数则法语,以及上引方志、族谱中的零星记载之外,似乎再难见到其身影,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所幸由于超盛与雍正帝以及其他世俗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清代官方档案里反而留下不少记录,这些材料不同于传统佛教文献和民间笔记小说,不仅史源较早,且大多传藏有序、完好,正可为我们提供有关超盛的准确生平。最早在档案中注意到超盛并加以整理刊布的是张文良,只是张先生并未深入研究,仅有一篇简要的概述性导读附在资料之前。⑥张文良:《永觉禅师超盛》,刘雨虹编:《雍正与禅宗》,台北: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第119-154页。至于其迻录的档案内容,除录文有个别错简讹误之处外,主要遗憾还在于所选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雍正朝朱批奏折,对于包括起居注册、内务府奏销档等在内的其他全宗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则没有涉及。其后杨健亦曾引用一则有关超盛的朱批奏折用以论述雍正帝与僧人之关系,⑦杨健:《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6-187页。但也未对超盛本身给予过多讨论。本文即在此基础之上,对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并尝试以社会史的视角,从超盛的个案切入来展现清中前期汉传佛教僧人的生活影像。
关于超盛入宫的时间,前引县志云:“雍正元年召见,命居圆明园悟道,赐紫衣”⑧王其淦、吴康寿修,汤成烈等纂:《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九,第757页。;而汤大奎则称“雍正十二年,召对称旨,封无阂永觉禅师,赐敕印,住贤良祠”①汤大奎:《炙砚琐谈》卷上,第757页上。。按圆明园在雍正帝继位后的数年内仍在扩建营造,直至三年八月雍正帝才首次驻跸,②《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三五“雍正三年八月壬辰”条,《清实录》七,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年,第6390页下。超盛显然不可能在元年便居于其中,而应是十一年才寻访而得。又超盛名列《御选语录》当今法会之中,说明其至迟在雍正十一年初便已进入内廷,故汤书所记十二年召对云云亦稍不确。张文良认为“雍正还在藩邸时,即与超盛过从甚密,甚至有超盛参与雍正朝前期重大政治决策的说法,如年羹尧案、隆科多案,据说都是超盛暗中鼓动策划而成”③刘雨虹编:《雍正与禅宗》,第119页。,则是将《永宪录》等笔记中所记“上倚之如左右手”的文觉禅师元信误为永觉禅师超盛。④《永宪录》续编:“文觉日侍宸扆,参密勿,上倚之如左右手……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见萧奭撰,朱南铣点校:《永宪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58页。
超盛,字如川,俗名庄梁奕,本字甸山,常州武进人。④《毗陵庄氏族谱》卷四,毗陵庄氏族谱续修编纂委员会编:《毗陵庄氏族谱》第一部,常州:今日照排印务有限公司,2008年,第392页。常州毗陵庄氏为明清时期江南望族,累代科甲,家学渊源。①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41页。其曾祖有筠、祖搢、伯父清度皆进士出身,父源洁以监生考授县丞,②《毗陵庄氏族谱》卷六,《毗陵庄氏族谱》第二部,第68页。超盛生长宦门却出家为僧,乃是因为一段特殊因缘。据雍正十二年上谕,超盛“幼读儒书,秉性朴淳,赋姿颖慧,偶因堕车危殆,遇救护苏,顿悟生死梦幻之理,皈依梵教,其夙根有自来矣”③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谕旨,起居注册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分下,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黄绫本,编号:104000319,叶30b-31a。。其同乡汤大奎亦云超盛“少年不偶,披剃为缁,尝诵唐人‘春眠不觉晓’ 一绝,遂悟禅理。”④汤大奎:《炙砚琐谈》卷上,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十辑第三十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57页上。正是这次意外坠车所带来的“不偶”令庄梁奕体验到世事无常,遂由勤习儒业的家族传统转向对佛性真如的证悟。⑤《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九载其“出家西山”(见王其淦、吴康寿修,汤成烈等纂:《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57页)。武进县西寺庙颇多,未详西山所指。今常州武进区有西山寺,在旧时怀南乡,距县治西南二十里处,然而与县志及《常州府志》并无准确对应,暂不详其出家之寺。出家之后的超盛在江南一带住锡,本与政治中心无涉,直至雍正帝寻访玉琳通琇法嗣,因其绍承玉琳法脉而被召入内廷,受封无阂永觉禅师,后任编修《龙藏》的四大总率之首,一跃成为京畿佛教耆宿。虽然超盛并非僧录司的掌印僧官,却被雍正帝委以重任,在雍正朝后期的佛教规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超盛虽是磬山一系,却并非雍正帝所极力推崇的“玉琳—溪”嫡裔,加之溪法嗣凋零,能为雍正帝所赏识者更属聊聊,因此不得不从其他宗派、支系、辈分中拣选合意僧人,命其绍继正脉。由于超盛奏对称旨,深得雍正帝称许,遂成为嗣入溪正派之下的合意人选决。雍正帝曾自云:“朕遍访二师法嗣虽多,率皆知见平庸。通晓禅理者,唯明慧一人。朕实为之矜悯,欲振劳规,赖有其人,遂于禅侣之中访得僧超盛、超善、超鼎三人,亲加训示,直透重关,已命继嗣二师之下。而本派宗徒及诸山知识共相证明,莫不忻悦感服。”③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日谕旨,见陆肇域、任兆麟编纂,张维明校补:《虎阜志》,苏州:古吴轩出版社,1995年,第19页。乾隆帝亦追述此事:“昔我皇考雍正十一年八月内,以玉林、溪法嗣不昌,命超盛、超善、超鼎三人嗣溪后。”④乾隆八年闰四月谕旨,转引自陈垣《清初僧诤记》,《陈垣全集》第18 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2页。自陈垣先生引述乾隆帝谕旨始,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场由雍正帝主导的改嗣运动。遗憾的是,他们往往将之视为帝王干预宗门,难免妄参妄付,故而不予采纳和讨论。⑤任宜敏:《中国佛教史 清代》,第425-426、440页。但是,在佛教史研究中忽视政治维度和影响显然是既不现实、也不客观的。事实上,当时僧俗两界很可能已然接受了这样的法系传承,并体现在历史书写之中。⑥如张照(1691-1745) 为《莲峰(超源) 禅师语录》所作序言中有“其同门无阂永觉所请明道正觉溪禅师塔铭”云云(见震华编纂:《兴化佛教通志》卷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198页),张照视超源、超盛为同门,便是承认二人皆出溪之下;而超盛为溪请塔铭,也透露出新的法嗣为强化身份认同所做的努力。后《正源略集》,径直将超盛等列入溪法嗣,见际源、了贞辑:《正源略集目录》,《卍续藏经》第145 册,第293页上。
战士们听见命令,纷纷钻进各自的洞中。有几个胆大的,钻进洞后,又把头伸出来,想看看鬼子的轰炸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超盛对江南禅林的看视与管理,离不开地方官员的支持和参与。无论是寺庙工程的出资和施工,还是方丈人选的任命和安送,超盛都要经常与当地督抚相商,有时甚至还要以政府为主导。也正是由于政治的介入,不仅赋予超盛更多的权力,还使得其与地方社会之间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互动。
尔生长宦族,幼读儒书,秉性朴淳,赋资颖慧,偶因堕车危殆,遇救获苏,顿悟生死梦幻之理,皈依梵教,其夙根有自来矣。经朕召见,略加提持,遂能直踏三关,洞明妙义,近代禅师中之所罕遇,目今宗徒内无有出其右者。朕心嘉悦,特封尔为无阂永觉禅师,以表真僧,宣扬法器。尔其益懋进修,仔肩大道,式宏慈化,丕振宗风,以副朕接引褒嘉之意。①此谕旨笔者尝于两处觅得,一份为台北故宫藏雍正朝起居注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癸巳大学士张廷玉奉谕旨”(编号:104000319,叶30b-31a);另一份见其法侄觉生寺明寿、徒侄宝林寺广林于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在宝林寺所立诰敕碑,首云:“皇帝敕谕无阂永觉禅师超盛”,下书“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封”(录文见佟洵主编:《北京佛教石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350页)。十二年者末云:“其应行事宜,该部察例具奏”,当是初始草拟;十三年者辞气有改,字句见增,盖为发至超盛处之谕旨,本文即据此迻录。另雍正帝《御制十方普觉寺碑文》有“命无阂永觉禅师超盛往主法席”云云,落款为“大清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一级臣励宗万奉敕敬书”(《清世宗御制文集》卷十七,《故宫珍本丛刊》第548 册,第207页下。日期据今北京卧佛寺原碑补)。说明在十一月之前雍正帝便对敕封一事有所谋划,并已拟定封号,只是直至翌年二月纔正式册封。
在超盛之前,雍正帝已册封溪嫡孙楚云明慧为悟修禅师,②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一日谕旨,起居注册雍正十一年五月分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黄绫本,编号:104000282,叶1a-1b。并派往江南主持丛林事务,然而十二年下半年间,明慧因在杭州干扰世法被地方督抚参劾,不得已被召回北京。③全祖望《前甘泉令明水龚君墓志铭》:“其事竟流传上闻,世宗召明慧还京,锢不许复出。”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而此后不久雍正帝即萌生册封超盛的想法,虽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但时间上的巧合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看出雍正帝佛教政策的某种连续性。
据乾隆朝《钦定礼部则例》,册封禅师时,随敕赏给由礼部铸印局所造之银印,④德保等修:《钦定礼部则例》卷一六五,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故宫珍本丛刊》第289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01页上。虽然这只是“赐给本人,不过图章之类,非外藩喇嘛传授承用印信可比”,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 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306-307页。也与僧录司所掌之印不同,并无名义上的行政效力,但是超盛的禅师名号乃是皇帝钦命,其实际影响不容小觑,其职权甚至超越了当时的僧官。因此,就在册封禅师不久之后,超盛便被委以重任,取代明慧曾经的地位和任务,前往江南巡视。
三、超盛的“南巡”与整顿禅林
雍正帝继位之初就曾表示江浙地区“俗称僧海,乃纳子容身之要地,近十年来释子原无可取者,闻之普概丛林狼狈不堪,朕甚悯之”⑦雍正元年六月十八日浙江巡抚李馥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 辑,第350页。。直至雍正十年后“庶政渐理,然后谈及佛法”⑧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谕旨,起居注册雍正十一年正月分下,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黄绫本,编号:104000275,叶16b-17a。,决意对佛教种种积弊加以整肃,超盛便是规划中最为重要的执行者之一。一方面,超盛成为政治介入佛教的传导者,他在江南营修庙宇、整肃僧规、选任住持、考究宗派,远远超越了各级僧司的权责范围,虽无僧官之名,却行僧官之实,在佛教内部拥有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超盛又是政教角力之间的缓冲者,凭借其禅门尊宿的个人声望,试图以“出世法”来解决教内的问题,从而避免“世间法”的过多干预。这也颇为符合雍正帝整肃佛教弊症的思路,如在面对大臣所奏议的佛教治理和管控政策时,雍正帝称赞李卫“尽听方丈管辖,如有违纪驱逐出寺,押令还俗”的建议“甚是甚好”,①雍正九年正月初十日李卫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7 辑,第449-450页。却对王玑提出的通过恢复度牒制度来约束和限制汉地佛教的主张嗤之以鼻,甚至讥其“万万不可书生气乱作了”。②无年月王玑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 辑,第175-176页。
在雍正帝整肃禅林、隆兴佛教(或者说是隆兴自己所中意的玉琳一系) 的规划中,僧与寺为其两大端,故而超盛到南之后所经办之事亦围绕此展开。
实验二的词汇测试结束后,要求两组学生如实填写查阅了哪些单词,用以确定各组查阅目标词的人次,结果表明,两组学生不同程度地查阅了目标词的用法。统计结果如下:
长久以来,柴油机已成为货物运输船舶推进动力装置的主流,其运行状态直接关系着船舶安全。因此,对柴油机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测并诊断故障,提高设备的维修效率,从而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和保持最佳的运行工况,为船舶安全提供保障,又减轻船员的劳动强度。[1]
先来看寺。雍正帝崇树玉琳的手段之一便是对相关寺庙加以修葺扩建。②如雍正十二年,雍正帝亲自过问玉琳派下“实怡居住之报恩寺,实彻居住之磬山,此二处常住,现有无香火养赡? 或足用否?”海保查明奏报后,雍正帝朱批:“好! 还觉少些,汝可酌量办理,若可小敷用,则不必加增也。”见雍正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海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 辑,第267页。此外,已有不少学者指出,雍正帝所修寺庙,多属磬山一系,可见他对玉琳法嗣的偏爱。参看圣空法师《清世宗与佛教》中华佛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http:/ /www.chibs.edu.tw/ch_ html/grad-th/65/65-3.htm,2018/04/25。三月十六日,超盛抵达淮安,将“修建清江浦慈云庵之上谕”面交淮关监督年希尧,命其“照丛林款式绘图”,并“与超盛酌量办理。”③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291-292页。年希尧13-03-24,《汇》27-947年希尧随即覆奏:“与永觉禅师酌量仿照丛林规模,敬谨绘图,今特缮折恭呈御览。”④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年希尧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999页。超盛省亲结束后,自常州起身,“前往磬山、龙池等处”。⑤无年月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 辑,第226-228页。到杭州不久,又于五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间前往天目山,途径报恩、崇福、圆照诸剎。奏云:“看各处修盖,具极坚固相称,而报恩为最。惟有七堂窄浅,现与隆升商量改造。隆升面说:‘至秋间方能动工,祇恐木料采办不及,今年不能告竣’ 等语……总俟诸事料理妥后,臣僧自当一一恭折奏闻”⑥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751-752页。。隆升亦云:“再报恩寺内据禅师超盛商酌,于第五层御书楼东首另行改建敞大禅堂五间,将间架丈尺开明交与奴才。”⑦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隆升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96页。
由此可见,在其出京之前,雍正帝将自己关于南方寺庙的不少想法和决定嘱咐超盛,命其沿途经办传旨,还可与当地官员共同商酌,甚至有些具体的规划由其亲自设计。而超盛所经行之处,皆与玉琳一系相关:慈云庵为通琇舍报圆寂之所,磬山乃通琇出家受具之处,龙池山则是通琇师祖幻有正传振锡弘法之地,而报恩、崇福、圆照诸剎,亦是通琇、行森曾经主持之寺,皆与盘山系,尤其通琇行森法脉密切相关。①金车山报恩寺,明天启九年玉琳继席开法,“由此报恩法道风行海内”(《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卷上,第742页上) 大雄山崇福寺,通琇、行森、全庵行进、骨岩行峰、来云行岩,皆曾主持(任宜敏《中国佛教史 清代》,第438页。释广宾撰,释际界增订:《西天目祖山志》,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 辑第33 册,明文书局,1980年,第137、139、156页)。圆照寺《浙江通志》卷二二七:国朝顺治年间,临济正宗溪森开山,世祖章皇帝赐名圆照寺,后森归隐华严庵圆寂,建塔寺内。雍正十一年,奉勅追封明道正觉禅师,设立牌位,供奉塔院,奉旨动帑重修,十二年御书法轮弘转扁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5 册,第198页)从地理上看,后三处与天目山并不在同一方向,盖为特意绕路前往,带有查看祖庭胜迹之意。
再来看僧,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整顿禅林。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九日,超盛到达杭州圣因寺,发现“圣因常住向系官场差役、民间游玩之地,是非繁杂,竟无丛林气象,所以住持者实有难堪之任。”②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751-752页。圣因寺原为康熙帝南巡行宫,雍正五年改为佛寺,此处本就与官府纠葛,人员杂乱,屡发盗案,难以管理。③雍正五年五月十一日李卫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 辑,第196页。前文曾提及明慧禅师虽奉旨来此住持,却不安清修,不仅自己“干预地方公事”④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白钟山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 辑,第125页。,而且纵容弟子招摇生事,以致僧规不整。作为雍正帝佛教规划的执行者,超盛此来不仅是取代明慧成为江南禅林新的领袖,更要对以圣因寺僧众为代表的种种积弊加以整顿。因此,超盛“进院之后,逐项逐条分拆利弊,大小事务悉与隆升商酌,因革相宜,然后举行。而地方官僚俱极护持,此番清理,仰蒙皇上万年之福。圣因常住,自获万年清净。”⑤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751-752页。⑥ 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明慧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 辑,第236页。
其二、人事安排。前揭言及雍正帝寻觅玉琳法嗣前往高旻寺安住,曾令明慧“斟酌一与常住有益者住之……再留一二人帮助料理常住事务”⑥。明慧从中选出“明纯为方丈,明智帮扶料理常住事务”⑦雍正十二年四月初一日明慧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6 册,第100页。。超盛至此后却发现“高旻寺常住屡经更换,诸事废弛”,显然明慧的安排并不妥当,于是“竭力料理,遍访执事之人。有僧成定,系福缘庵元度之法子,看其为人,不失老诚,可充监院之任,扬城僧俗尽知其为人妥当,现在经管当家之事。”⑧无年月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 辑,第226-228页。就在超盛这份奏折上,雍正帝又就另一安排问道:“朕意秋间命超善来南,或住高旻,或住磬山,或住竹林,尚未定,据汝见与何处相宜? 若住磬山,实彻调住高旻,实源今超源来住圣因,元日来住天童。”⑨同上。超盛覆奏:“磬山乃系租庭,超善住持最为妥协”⑩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 辑,第50页。。又如圣因寺住持明永“原是隆昇去年所安”,超盛“看其为人老诚,可充主席”,遂于数日后将其“送方丈,住持圣因”①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751-752页。。
其三、检视僧众。在雍正帝对佛教的干预之下,从宗门领袖到名寺住持,难免要与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怡贤院实恒、天宁寺明章、圣月寺实彻等,或为地方官绅所选立,或为雍正帝召见后钦命,他们的言行也不仅代表着个人佛法修为,更关系到朝廷的体面以及政府对佛教事务的管理,因此超盛南行的一大目的便是检视各地僧人的信心光景。如超盛在苏州怡贤院查看后具折道:“现在常住监院僧实恒,极其妥当,原系海保向日所安,是以一切事务井井有条,殿宇房舍俱极相称……看江南僧俗,信心佛法者十有七八。如明章、实彻等,与臣僧盘桓,俱各惊异,不得不为之更加精进,即未得见地者,俱各起向上之志。而在家真信心者,亦不乏人。皆我皇上运佛慈力,逐有不期然而然之致。”②无年月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 辑,第226-228页。
其四、辨别法嗣。雍正帝晚年极为推崇永明延寿的佛学思想,③黄公元:《雍正皇帝与永明延寿禅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第3期,第89-94页。雍正十二年杭州净慈寺僧篆玉“游京师,和硕庄亲王招住海淀法界观心佛堂,十三年四月侍郎海望带领引见”④喻谦:《新续高僧传四集》卷六四,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56页下。,因其自称永明延寿法嗣,雍正帝为辨明真假,命内务府发来《凈慈寺志》五本、碑记一册,传旨隆升:“篆玉果否系大壑嫡支之处,令伊同超盛详细辨别。”⑤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隆昇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 册,第496页。超盛覆奏云:“臣僧……密考诸方,究其法派原流,自永明寿祖至大壑将及四百余年,所以继续者拈香追嗣之礼,大壑自依云栖法派:‘宗福法德义,普贤行现身,文殊广大智,成等正觉果,果与因交彻,心随境廓通,元(玄) 微机悉剖,理信妙言穷’。从大字起传至心字派,下该随字。而篆玉之师祖又另立法派:‘万法原中,峰荫子隆。常遵祖训,在世谦恭。永明后裔,远播宗风。流辉慧日,传照无穷’。所以篆玉祖师之名万瑜,房名为万峰房,传至世字派,下该谦字派,而又换作篆字,此中年代遥远,法派舛错,一时不能定其果否,臣僧再当细访,考其原由究实之后,自当恭折奏闻。”⑥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751-752页。所记谱系:“现”,《云栖法汇》作“愿”;“言”《云栖法汇》作“咸”。
技术就是生产力,而且是不可替代的生产力。长期以来,许多果农学习技术不肯下功夫,引进技术不愿付费掏钱,导致大量物资投入有去无回,别说保障收益,连基本投产都无法维系,从而导致生产种植陷入困境。与其说气候、管理和规模问题,不如说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将猕猴桃生产在种植前端和初期复杂化,而一旦正常运行,则变得简单化,最终实现高效化。对猕猴桃种植技术的漠视,实际是一种文化思维惯性的不良反应,这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这里的技术是真正有用的技术,而非不实用技术或伪技术。
雍正十二年年末,十方普觉寺(俗称卧佛寺) 重修工竣,雍正帝“命无阂永觉禅师超盛往主法席”。⑥《十方普觉寺碑文》,《清世宗御制文集》卷十七,《故宫珍本丛刊》第548 册,第207页下。而据李卫奏折内引海保赍到上谕,超盛奉旨将于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京起程,前赴江浙……十月内回京”。⑦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李卫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174页。因此,超盛很可能并未在卧佛寺驻锡太久便前去江南。至于其南下缘由,县志记载“时超盛父年高,特命回南省亲,赐赉甚厚。”①《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九,第757页。超盛后来亦将当时情形上奏:“臣僧于(十三年) 四月十二日起身前往常州,十三日到臣僧俗家。臣僧父母,先出城跪接恩赏,举家顶戴,阖郡瞻仰,老幼僧民,无不称颂皇恩浩荡,实难仰报。臣僧在俗家耽迟数日,于二十日自常州起身。”然而从其所计划的停留日期来看,超盛此往江浙也许缘起省亲,但决不止于此一目的。根据此后数月间的往来奏折及朱批,我们发现雍正帝之所以命超盛南下,实是将查看整顿江南丛林、施行自己佛教构想的重任寄托于超盛。
在这些改嗣为“玉琳—溪”正脉的僧人中,雍正帝最为欣赏且寄予厚望的,便是超盛。雍正十三年,世宗册封超盛为“无阂永觉禅师”⑦《正源略集》作“无碍永觉”。爱新觉罗永忠《延芬室集》(北京图书馆藏稿本) 乾隆三十年乙酉稿中有《题无碍永觉禅师紫竹山房小照三首》,亦作无碍。,敕谕略云:
4.休闲时间“自由化”。网络方便人们利用点滴时间,在日常工作、学习之余,冲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休闲活动。“鼠标一点”就可以在网络平台自由、平等选择休闲时间,进行各类休闲活动,突破现实休闲中的种种限制性因素,改变传统某些休闲项目被动、被支配、被监控的状态,它使人们更能切实做到解除体力上的疲劳,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更为重要的是在网络空间里人们更容易达到休闲的状态,实现工作、学习与休闲无明显界限的和谐理想状态。
四、超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超盛在奉旨南行途中,与地方社会往来密切。一方面,超盛要常常为沿途官员指点开示,提供法施;另一方面,当地士绅则纷纷向超盛贡献斋衬,进行财施。这种供施关系正可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呈现出雍正朝后期僧俗交涉的社会图景,以及说法、布施、斋僧等佛教生活细节。
首先来看超盛对官员的“法施”。直隶总督李卫在超盛出京之前便接到雍正帝谕旨,令其与禅师“约定相见接谈”。李卫称超盛为“人所不易轻见之高僧”,当即表示愿意“星夜驰往”,后经相商请示,改派属官将超盛迎至保定府相晤。③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李卫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174-175页。二人盘桓一日,李卫自言:“得与高僧相接谈论,裨益非浅”,并称赞超盛“见解高超……切近平易”。④雍正十三年三月十日李卫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233页。有趣的是,虽然李卫的态度颇为恭敬,但超盛却在奏折中直言:“臣僧看李卫虽一心诚笃,向上有志,但领会全无半点,恐一时未必能得。”⑤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291-292页。似乎并无谄谀权贵之情。
如果说李卫礼请超盛讲法,或是迫于皇帝之旨,那么还有不少官员则是因个人信仰而主动向超盛问道的。如年希尧曾于十三年正月坐禅,“疑情徒发,几不知有身者久之,适家人掀帘动有声,当下触发,如在荆棘中跃出,如失物而寻得,快活无比”,遂以为有所得。恰逢超盛于三月间到淮,于是连日听其提持开示,“方知前者之非,据禅师云比前大不相同,尚未能结实,从此再用力参去,方得干净。”①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年希尧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 册,第946页。后年希尧又于八月二十一日前往苏州探问,据超盛奏称,两人“在于织造署内日夕盘桓,臣僧问其本分之事,初犹未能清楚,至二十六日臣僧同海保互相提示他纔略觉清楚,越一晚至二十七日清早,年希尧已能看破话头……即于二十九日起身回淮去讫。”②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二日超盛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9 册,第95页。
在弯头1入口处泥浆流体产生切向分速度,二次流开始发展;在弯头1出口处可以观察到完全发展的二次流;在弯头2出口处分速度值最大,二次流强度最强;泥浆在离开弯头部分以后,不再受到离心力的作用,混合相垂直分速度逐渐减小,但由图5e)、图5f)可看出X=5D处二次流仍有一定存留,在X=20D处二次流已基本消失。爬坡管内泥浆所受到的离心力沿流动方向不断变化,当流经弯头2时与弯头1中离心力方向相反,弯头2入口面二次流强度较弯头1出口明显降低,在流过弯头2后涡流方向改变。
可是,苏东坡就是苏东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赞成大家的看法,认为米芾确实有点疯癫。这也等于说,我劝你把这个毛病改一改。好在是令人敬仰的苏东坡,米芾这样一个癫人,居然没有转身就走,甚至没有生气。否则,友谊的小船立马就翻了。
又如苏州织造海保奏报从超盛参悟的过程云:
自今年四月间,禅师来苏之始,奴才即请禅师指示,据禅师云奴才见地虽有,但尚未清楚。及禅师自杭回苏,于病体安愈时,奴才又请问,禅师云:“此番比前进些,但犹未甚清楚,总将父母未生前话头蓦直参去才好。”此八月初五日语也。是晚至初六日清早,奴才正在着实用力之际,忽然打脱话头,始知一切语句总属无用,随又请问禅师印证。禅师云:“如今纔得清楚,但本参一事,不过一小见解,往前途路甚远,须得照旧功夫做去,自有一番扩充之妙”等语。奴才敬遵禅师开示,自当着实用力,益加精进。”③雍正十三年八月十六日海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 辑,第189页。超盛也曾奏报此事:“连日海保参究本分,观其悟处,虽有见地,尚未十分清楚。现在着力精进,将来可望了明。”见无年月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27,第226-228页。
随着《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与《河北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使得互联网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各环节加速融合。现代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精准化生产、透明化管理、高效化经营、便捷化服务及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取得突破性进展,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种养加”及营销物流模式成为全省农业发展新业态。
再来看檀越向禅师的“财施”。不少官员为广种福田,还会延请超盛于寺庙升座,并出资设斋。如高斌在淮安迎接超盛时“已委就近之员先期料理妥当”,请禅师入扬州高旻寺上堂。④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291-292页。待超盛抵达扬州,京口将军王釴亦与阖郡商人又在夹山竹林寺设斋,邀超盛前往。⑤无年月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 辑,第226-228页。这些法会往往规模宏大,所费不赀,如于湛真寺斋僧一千一百余众;⑥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291-292页。高旻寺斋僧一千五百余众;⑦无年月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 辑,第226-228页。怡贤寺斋僧两千余众;⑧同上。而在圣因寺,除赴斋僧人二千余众外,“随喜僧俗,将有万数”⑨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751-752页。。短短两月间共斋僧近七千余人次,足见当时江南佛教之盛。在此过程中我们还能看到,地方社会以寺院为中心,集聚各级僧侣、官商檀越和俗家信众,通过佛教法会来辅助对基层组织管理和民间劝善教化,这亦是明清佛教政教关系的一个特点。
坐标轴和溢洪道部分的计算面积如图1所示。对断面zy进行计算。上边界设为分段连续函数yn(z)。所有的边界表面均假定无应力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应力σz达到一定值后可能形成堤坝上最危险的裂缝,同时侧向冷却对σz值和冻胀压力也有一定影响。
苏州巡抚臣高其倬谨奏为奏明事窃照常州府属荆溪县有善权寺,创于南齐时,至宋有淮东安抚使陈宗道曾捐田二百余亩于寺,时僧人为建祠寺内,奉为檀越香火。其子孙住居于寺之附近村庄,彼此往来。至康熙十三年间,议移祠于寺外,陈姓之人阻挠不移,复混携牲酒入寺祭祀。僧人以理却阻,陈姓恃族众人多,始则赴寺凶闘,继则聚众焚烧,禅林祖塔悉化灰烬。寺僧除江南语音者放出,余俱焚死,方丈和尚(划掉和尚,改为:住持僧) 白松亦同时圆寂。当时惟将首恶陈榜一人正法,又监毙者数人,余皆漏网。又闻此寺被焚复建之后,陈姓亦重建专祠,并将已正法之陈榜亦列于祠内,所有现存寺田尽被收去,山门外大路基地并收入户内。臣思陈姓杀人放火,霸产占祠,世济其恶,不法已极,虽事属年久,应查明料理,以彰天理而申国法,惩其已往,示戒将来,实人心风俗之所关。臣已行常镇道、王之锜前往善权寺,将陈姓占去田亩侵收地基松路逐一查明,悉行清还,陈榜等淫祠立即毁牌拆祠。陈宗道先经舍田有功德于寺,督令陈姓族人之良善自行移建于山门之外(此句划掉,夹批:是何心。按夹批上部残缺一二字)。案内为首之陈榜、陈永、陈复初各犯,本人虽经正法毙病故,其嫡派子孙亦难容其安居故土,并饬查明照律发遣,以示地方儆戒,(夹批:高其倬原任督抚,惟此一案察奏可嘉,该部谕奏) 至于此寺现在主持系从前寺内道人,今皆披剃,据称受法临济派下,但揆情节,不过听陈姓驱使服役,为之看守香火祠宇(夹批:似此无耻僧徒可辱逐之),并非从前常住的派。叩乞皇上另选高僧卓锡,以阐宗风,所有应建僧房,并增修殿宇。臣自当加意料理,谨绘具善权寺图并抄录饬行牌稿,恭呈御览,伏乞皇上训示。谨奏。(朱批:既欲修理,务令成一丛林规模方好。)⑤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其倬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425-426页。
表一、超盛南行所受斋衬施赠
(数据来源: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六月初一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291-292、751-752页。无年月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 辑,第226-228页。)
日期(雍正十三年) 地点官商施赠人物二月二十九日 保定 李卫(直隶总督) 斋images/BZ_267_1333_746_1375_781.png银一百两、通海缎二疋、程乡茧二疋、扇器二件、茶叶等物;侍司斋images/BZ_267_1746_812_1788_846.png银十二两。三月二十日 淮安年希尧(淮关监督) 僧斋images/BZ_267_1370_897_1413_931.png银六百两、衣屡紬缎器用物件;随行侍者斋images/BZ_267_1370_962_1413_997.png银。三月二十七日 扬州高斌(两淮盐政) 斋images/BZ_267_1333_1042_1375_1077.png银二百两、纱葛紬等礼物十余种尹会一(盐道) 斋images/BZ_267_1333_1117_1375_1152.png银一百两王之锜(江常镇道) 斋images/BZ_267_1333_1193_1375_1227.png银一百两三月二十八日三月二十九日京口商人 斋images/BZ_267_1333_1268_1375_1302.png银一千两王釴(京口将军) 斋images/BZ_267_1333_1343_1375_1377.png银五十两闰四月初四日 苏州 海保(苏州织造) 斋images/BZ_267_1332_1423_1375_1457.png银六百两、衣履紬缎器用物件;随行侍者斋images/BZ_267_1333_1489_1375_1523.png。闰四月二十九日 杭州隆升(杭州织造) 斋衬银四百两、缎疋衣拂笔墨等项二十余色;随行侍者亦有斋衬。将军、督抚等官共十二人 僧斋衬银四百两
从表中可以看出,仅地方官员赠予超盛的斋衬银便有3550 两,而当时即便是远高于全国水平的苏州粮价也不过1.3 两/石。①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页。这种尊崇除了看得见的物质施舍外,还体现在许多看不见的礼遇之上,如在苏、杭两地,隆昇、海保径将其接入织造府衙署内安住,可谓招待备至,以致雍正帝都认为有些超乎规格。②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海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 辑,第24-25页)上朱批:“钦差来南之僧,汝等相待太过。前已有谕,今命南方住持三僧,乃住南之人,非钦差便回可比,况皆平平见地,非超盛可比,不过如实彻怡辈相待可也。”此事虽是针对元日等三人而言,但从中亦可见雍正帝也认为如此招待僧人不合规制。前揭言及超盛于五、六月间至天目山等处查看祖庭庙宇,因正值盛暑,染患疟疾,遂返回苏州织造府修养。海保随即令苏州名医叶天士等相商诊治,“每日亲自看视,令医谨慎用药”③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海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880-881、903-904页。,更前后六次具折,将医药方案、调治情形、禅师病况,及饮食起居等情详细奏报,极尽关切之情。
必须指出的是,在超盛与地方官员密切互动的背后,其实有雍正帝的间接参与。海保曾希望上京聆听圣训。雍正帝却朱批道:“今岁不必着你来,不过为开示佛法,今现超盛在南,可问他如见朕一般。”①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海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 辑,第23-24页。海保接旨后随即表示“奴才惟属钝根,而仰承开导,叩感隆恩。心非木石,能无奋兴? 敬当从禅师超盛处,切问参究,务求彻底了明此事。”②无年月海保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2 册,第643页。而在年希尧参悟一事上,雍正帝也说道:“观伊自陈之奏,已至悟景,向下见处可必到也,用意提示可也。朕亦有谕,他自然向禅师说的。”③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291-292页。从这些朱批中我们不难看出,自诩为宗师的雍正帝已用帝王权威“印可”了超盛的禅学修为,并由其替代自己去向好佛臣工开示说法。反过来,不论是途经淮、扬,还是抵达苏、杭,超盛每到一处无不受到当地官员的盛情款待,或如高斌码头相候,或如高其倬出城迎迓,或如年希尧沿途护送,甚至行至杭州时,将军傅森、总督郝玉麟、巡抚程元章、副都统隆昇、穆鲁纳、金璜、萨尔哈岱,率同司道协、参、佐领等官,全部前来相迎,聆听教法。④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751-752页。表面上看是在礼遇超盛,其实是为了要“恭请圣安”——官员们请安跪拜的乃是超盛背后的皇权,那么超盛以僧人身份而受到如此尊崇也便不难理解。有了皇权的支持,超盛的影响力已不仅仅体现在僧界的管理或是寺院经济上,有时还可能影响到现实政治。
五、超盛与清初善权寺公案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海保奏报超盛“疟邪已清,酌用参药调理,约在旬日之内,可以平复。”雍正帝阅后道:“何喜如之,览奏如阅珍玩异宝,此事原与病苦寿夭无涉。而俗凡之心目,未免打退信心,今护法善神,将一番扫兴之事,翻成一则好公案。朕梦感之奇,部中颁发,想汝亦闻矣。”⑤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海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 辑,第24-25页。朱批中“一则好公案”及“梦感之奇”云云颇为有趣。张文良先生已注意到,解释为“雍正希望海保将禅师染疾,视为护法善神一则公案看。凡俗之辈一遇恶缘,即易退失信心,唯有有道之人,方能以恶缘为道场,增进功力与道行。”⑥刘雨虹编:《雍正与禅宗》,第121页。然而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公案”与“奇梦”实则另有所指。先让我们来看一份谕旨(分段为笔者所加):
吉林大学的刘国嵩等人设计了一种整体对称结构的步进型精密直线驱动器[8],该驱动器在保证位移精度和输出力的基础上,具有较好的行程稳定性,实验测得其在100 V驱动电压、10 Hz频率下,稳定步距为11.7 μm,速度达到6 mm/min,理论输出力约为291 N。华南理工大学的杜启亮等人设计了一种行走式压电驱动器,用于驱动微小型机器人[9]。中国科学院的李全松研制了一种整体结构的步进压电驱动器,如图6所示[10],试验结果表明,该驱动器行程20 mm,最大输出力38 N,步长0.02~35.15 μm。
至于火烧善权寺案,玉琳年谱中曾记:“陈氏等聚族歃血,冀图非分,遂白日火善权寺,以阻祠为名,抢攘库司方丈,发掘祖塔,纵火毁寺,杀僧众几十余人。”③《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卷下,第768页。而此事之前所发生的围绕善权常住而起的临济、曹洞之争,在清初僧诤中则更为有名。陈垣先生《清初僧诤记》“善权常住诤”一节博引洞、济两派文献,对前后纠葛有极为详细讨论,①陈垣:《清初僧诤记》,《陈垣全集》18 册,第376-381页,陈援庵虽然汲引两方史料,但因其立场、史观、目的,对陈氏宗人多有同情,直斥玉琳一系乃“藉新势力以欺压同侪”。并引《续指月录》以为“玉林之寂,实缘于此”,本文不再赘叙。此后郭朋亦有讨论,只是所据材料未出陈书范围。②郭朋:《明清佛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4-326页。张文良先生也已经注意到了善权寺一案,不同于陈、郭基于传统文献的立论(二人在相信史料及论述时都站在了曹洞及陈氏一族的立场上而对玉林有所批评),张氏则主要依据高其倬奏折,从后世官方视角出发(这一视角看似中立,实则因雍正帝对玉琳一系的尊崇而同样有所偏颇),对烧寺始末及查案经过做了详细叙述,③刘雨虹编:《雍正与禅宗》,第74-75页。笔者本无需再多着墨,只是张氏当时并未指明所据史料出处,给其他研究者的引证带来些许不便,④如圣空法师在其学位论文《清世宗与佛教》中引证此则材料时,便感慨“由于此书未注明资料出处,故引其文以陈述此事缘由,另作参考”。今笔者恰好也翻检得此份档案,故而不避繁复,将高其倬奏折并雍正帝朱批迻录如下:
向因玉琳国师具如来正法眼,实可媲从上佛祖而不媿者,朕恐宗法衰微,思为广培法嗣,数年以来,留心延访,加意提持禅僧数人,明晓性宗,可继玉琳国师之法席,而其中识解圆通、襟怀沉静者,超盛一人实为超出朕望,其将来大有成就。今年夏间,超盛奉朕差遣,前往江浙地方安插修建各寺,自浙回苏,患病甚剧。朕心深为系念,忽一夜玉琳国师见梦于朕,奏恳宽免陈氏子孙,且云皇上若不赦宥此曹,则前蒙恩赐之法嗣,臣僧亦不敢受。朕寤而惊异,实为奇特,默云超盛所患无论痊否,朕必将此案从宽,以彰玉琳国师之显应,何期一愿,方弘千里如响。昨据海保奏报超盛病已渐减矣。是知佛法慈悲,怨亲一视玉琳国师以能仁而特昭灵爽以法忍而大着威神,作平等之观,能容王法所不可容,解多生之结欲,化王法所不能化,事非出于渺茫,理合宣之朝野,俾凶顽者咸知忏悔,善良者益笃诚信,共仰国师之鸿慈,永作法门之公案,着将此案应行查究发遣之人犯及陈榜之子孙悉行宽免,其田亩地基仍照部议。经此一番灵异之后,倘各犯子孙仍有不知战栗警省者,岂但果报有在自入泥犁而国有常刑亦不可以屡幸也。①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谕旨,起居注册雍正十三年七月分下,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黄绫本,编号:104000337,叶12a-14b。
该上谕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记叙一庄发生在康熙朝的地方刑事案件:玉琳法嗣所在的宜兴善权寺与当地陈姓宗族发生矛盾,陈氏聚众纵火焚寺,死伤多人。虽然当年已将罪首陈榜等正法,但因雍正帝崇树玉琳法脉,认为彼时处罚太过疏纵,遂令江苏巡抚高其倬重审。后经部议,谕令将漏网余犯以及陈榜嫡系子孙悉数发配三姓。后一部分则讲述了自己的梦境和新的裁决:雍正帝下旨严惩陈氏族人之后,却梦到玉琳通琇向自己请求宽免陈氏,否则不敢接受雍正帝为他所挑选的法嗣。这不禁让雍正帝联想到正患恶疾的超盛,于是决心对此旧案不再追究。不意未几日便得到超盛病情好转的奏报,雍正帝因而认为两者冥冥之中必有联系,于是特下此谕,发往各处知晓。海保在八月十六日奏折中亦称:“奴才接阅邸抄,伏读上谕,并于奴才奏折内,恭绎朱批,知禅师病愈之事,适符皇上梦感之奇,竟成一则好公案,奴才不胜惊异感悦。”②雍正十三年八月十六日海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 辑,第188页。君臣二人所言“公案”与“梦”皆是指此,而所谓“部中颁发”及“上谕”即为上引谕旨。
江苏巡抚高其倬奏明从前焚烧善权寺僧之首恶陈榜等各犯子孙重建淫祠占田夺路一案,经该部议以焚烧寺庙杀伤多人之漏网余犯令该抚确查,发三姓为奴,其陈姓子孙应照例发遣等因覆奏。朕思善权寺乃六朝道场,至本朝玉琳国师曾振锡于此,弘阐宗风,而凶徒以小辄敢清天白日聚众焚烧数百僧人,毁坏丛林,目无国法,其迹等于反叛,此诚大逆之罪,允宜殃及于子孙,当年地方大臣未解此案,何得踈纵至此,今该抚所请及部议均为公当,朕已降旨允行,并将陈榜嫡派子孙亦令发三姓安插矣。
除了面向僧俗大众的施舍外,沿途官绅对超盛个人的贡献斋衬同样值得注意,笔者仅就宫中档整理如下:
雍正帝将那些依附陈氏宗族势力的僧众斥为“无耻僧徒”,皆“可辱逐之”,还把高其倬为陈氏先祖开脱之语删去,甚至责问其“是何心”。又在后来的谕旨中认为陈榜等“毁坏丛林,目无国法,其迹等于反叛,此诚大逆之罪,允宜殃及于子孙”。雍正帝对陈姓族人的切齿之恨庶几可以反衬出他对玉琳通琇一派的眷顾和尊崇。善权寺案原与超盛无关,只因一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因缘巧合而令雍正帝改变了最终的结果,相较于赏赐财物之类的恩宠,此则公案似乎更能体现雍正帝对超盛的格外关切与重视以及对于玉琳法系的眷顾,而佛教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作用亦由此可见。
六、超盛在乾隆朝的境遇
地方官员对超盛的礼敬和优待,自然有其信仰的需求;但种种超乎规格的尊奉显然更与雍正帝密不可分。从前两节所述中不难看出,能让一众督抚要员如此鞍前马后的,其实是加持在超盛背后的皇权。所谓出城五里、十里相迎逆,其目的实是要“请圣安”;对超盛讲法的踊跃赞颂之后,也都少不了一句“皆本皇上微妙之训旨”①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二日郝玉麟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 辑,第756-757页。。超盛对此也十分清楚,海保能在其病中如此尽心,多半要仰赖帝王的恩宠,如其在奏折中云:“窃思织造乃系朝廷使臣,臣僧何人,受其护持安全,实出我皇上天高地厚,格外弘恩之所致也”②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 辑,第50页。,并表示“惟有铭心矢志,益加慎重,必待真参实悟,以心印心,庶仰报皇恩高厚于万一”③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三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 辑,第141页。。因此一旦失去雍正帝的护佑,旧日的荣光也就走到了尽头。
雍正帝于八月二十三日驾崩时,此时超盛刚刚病愈不久,尚在苏州调养。四天后乾隆帝下旨:“从前法会中僧衲今分往外省者数人,恭闻皇考升遐,伊等不必来京,仍在本处虔诚讽诵。至超盛、元日二人见地明通,修持精进,深蒙皇考嘉奖,着海保等即送二人来京瞻仰梓宫。”④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2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杨健指出“乾隆帝一上台就清除宫中的道士和僧人,他令超盛等前来吊唁雍正帝,实际上是要训斥他们。”⑤杨健:《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第190-191页。然而如果相较于被派往外省的其他僧人,乾隆帝特准超盛回京奔丧,并称其“见地明通,修持精进”,仍算优待,只是在态度上已不似雍正帝那般亲昵。超盛曾于九月初二日具折请旨希望回京,此时他还并不知道雍正帝已经驾崩,仍在折中道:“臣僧远隔天颜已逾半载,衔戴圣恩,瞻依北阙,寤寐难忘。”不料乾隆帝批道:“有何难忘”,又在折末云:“相见有日,且道相见个甚么”,⑥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二日超盛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9 册,第95页。不难看出他对超盛这番望阙谢恩之言略有微词。
超盛与乾隆帝应该在“当今法会”上便已结识,而且超盛理应对当时的宝亲王甚为恭敬。雍正帝曾在朱批中与超盛闲谈道:“四阿哥二月初七得踏三关……此数月总不费心力,一些不动,几至一片矣,实不可思议,超过朕之功夫矣。”①无年月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 辑,第226-228页。超盛覆奏云:“伏绎朱批谕旨‘四阿哥工夫打一片’ 钦此。窃思四爷身居王位,即能如此绵密。”②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超盛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 辑,第50页。除称赞弘历功夫“绵密”外,还特意将原折中“几至一片”径改为“一片”(此后雍正帝又在朱批中补出“将似”二字),雍正帝是否将这些谀美之词转述给四阿哥弘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后来的事情上看,乾隆帝似乎并未领情。
乾隆帝将雍正帝留居内苑的僧道尽数逐出,命其或“还本籍”③杭世骏:《道古堂全集》卷四八《赐紫住持南屏净慈禅寺烎虚大师塔铭》:“今上御极,奉旨出居,许各还本籍。”《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7页。,或“回本山”④《武林理安寺志》卷五《实胜传》:“今上御极,奉旨着圆明园僧人回本山。”《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 辑第21 册,第270页。。并且下旨:“凡在内廷曾经行走之僧人,理应感载皇考指迷接引之深恩,放倒身心,努力参究,方不负圣慈期望之至意。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藉端夸耀,或造作言词,或招摇不法,此等之人,在国典则为匪类,在佛教则为罪人,其过犯不与平人等,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⑤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六日谕旨,《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2 册,第257-258页。又令各省督抚“凡丛林寺庙中除敕赐御书匾额、对联、碑文外,若有世祖、圣祖、皇考批谕字迹,及伊等抄录稿本与僧人所刻语录,如《北游集》《侍香纪略》《帝王明道录》等书,干涉时事,捏造言词,夸耀恩遇有一字关系世祖、圣祖、皇考者,无论刻本、写本,悉行查出,密封送部,请旨销毁,不得私藏片纸。”⑥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谕旨,《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2 册,第324-325页。不久,江南总督赵弘恩即奏:“常州府查有僧人超盛之父庄源洁刊有纪恩诗板一块,封缴到臣,随检阅诗句,实有因其子钦赐法名夸耀恩遇情由,臣于十二月初十日密封送部请旨”⑦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赵弘恩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0 册,第240页。。乾隆帝遂命“密谕属员详悉访查”。查缴先帝旧迹以免有人藉此招摇生事,本是维护帝王体面、巩固统治安定的惯用手段,这一点我们从雍正帝继位后对藩邸旧僧的打压中已窥见一斑。⑧见杨奇霖:《迦陵性音考——兼论雍正帝与藩邸汉僧之关系》,《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8-127页。当然,乾隆帝此举也是在告诫超盛等僧人,雍正帝对自己的旧日恩宠,不仅不再是其夸耀的资本,更成为一种禁忌。
(1)限制患病仔猪的饲料供给,把饲料的可消化能降到正常值的50%。增加饲料中纤维素含量达到20%~25%,以增加肠的蠕动频率,加快食物通过小肠的速度,对便秘的患猪,每头喂服硫酸钠10~25 g或碳酸氢钠2~5 g,或大黄苏打片4~8 g。在日粮中添加健胃消食药物(按说明添加)。
张文良认为超盛在乾隆帝继位后,“被逐出宫廷,并严诫其泄露宫廷秘事及‘妄夸’ 先皇恩遇,最后郁郁而终。”⑨刘雨虹编:《雍正与禅宗》,第123页。可惜并未指明史料出处,很可能仍是将其与文觉禅师相混淆。《大清重刻龙藏汇记》载超盛结衔为“敕封无阂永觉禅师赐紫沙门传临济宗钦命贤良寺住持”,①《乾隆大藏经》第1 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7年,第159页。这说明其彼时确已不在宫中,但如果就此而认为超盛郁郁而终,似乎并不合适。笔者以为,超盛在雍正帝驾崩之后虽不复荣宠,甚至受到警告和限制,但乾隆帝并未给予其过分的打压和惩罚。
据龙藏汇记,超盛回京之后应该很快便开始投入到大藏经的编撰工作之中,并位列四大“总率”之首,他不仅担任藏经馆所在地贤良寺的住持,更是唯一一个拥有“敕封”名衔的僧人,说明至少在藏经刊成的乾隆三年,超盛在佛教界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这种重要作用除了地位的尊崇外,还体现在编撰藏经的具体事务上。据《宝华山志》所载允禄、弘昼等人关于华山律宗五部入藏始末的奏折,《三坛正范》四卷因与《毗尼作持》部内重复而被从大藏中删去,便是由超盛等详加查看后所审定。②《宝华山志》卷八,杜洁祥:《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 辑第41 册,第331页。又《黔灵山志》卷十一所存《奉颁藏经原行》载乾隆四年将颁发新刊藏经,其中“直隶各省所有堪可供奉藏经之寺庙”五十六处,也是由超盛等选拟而得。③转引自王路平:《贵州佛教史》,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即便在大藏经刊刻完成之后,超盛似乎也没有遭受贬斥,而是经常出现在内廷之中。如乾隆十三年宫中法会,有“禅僧经四十八众,超盛、超成率领住持僧八人掌坛,唪法华经,拜千佛忏,每日进早晚膳,超盛等带入唪心经、往生咒”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档号:05-0091-053。。乾隆三十一年,为圆明园佛楼告成而举行开光道场,其掌坛禅师亦为超盛。⑤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奏为万善殿办理开光道场赏银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内务府奏销档案》298 册,缩微胶卷第178-179页。这也是笔者目前所见超盛行年中时代最晚者。
此外,超盛在乾隆朝与各王公大臣也多有往来,如清宗室永忠的《延芬室集》即录有作于乾隆三十年的《题无碍永觉禅师紫竹山房小照》三首,其一小注云:“丙子(笔者按:乾隆二十一) 长夏屡与禅师茶话”;又其三小注:“今春万寿寺启建龙华道场,余以随喜,适值禅师赴参升座”。⑥永忠:《延芬室集》,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0-741页。说明至少在乾隆三十年左右,超盛虽不似在雍正朝时得势,但依然以禅林耆宿的身份而活跃在京师佛教界中。
七、结语
佛教虽然以出世为终极追求,却必须在世间得到示现和展开。正如圣凯法师所论,“佛教作为宗教的社会实体,还具有社会、文化两大层面,这是佛教的外延。”⑦圣凯:《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在“整体佛教”的观照下,佛教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成为探究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关键一环。当然,佛教同社会的轇轕远非是一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所能概括的,佛教自传入汉地以来,不断调试着在传统秩序之中的位置,也一直试图在文化、社会等领域形塑宗教的神圣性、自主性与能动性,从而与现实世界互动影响。对于处在中华帝制晚期的明清汉传佛教而言,这种特征尤为显著——一方面,经过政教张力的积淀和定型,佛教最终在组织体系上被纳入皇权制度中,并成为佛教近代以来发展和转变的背景与基础;另一方面,佛教的思想、认知和生活方式等也深深融入到传统社会的各个角落,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史图景。本文所论如川超盛便主要生活于十八世纪前半叶。
如川超盛是雍正朝后期十分重要的僧人,在雍正帝整肃佛教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却因传统史料的遮蔽而一直为学界所忽视,清宫档案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探究并恢复其生平。同时,超盛的个案也为我们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出十八世纪中前期佛教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以及僧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超盛凭借玉琳法系的身份而被诏访入宫,得到雍正帝赏识,受封无阂永觉禅师,从江南的普通僧人一跃而成为当时的佛门耆宿,并奉旨前往南方巡视。在此过程中,超盛看查祖庭,修葺庙宇,整肃清规,拣选僧众,成为管理佛教事务的“钦差”,甚至还改变了世俗世界中一庄业已定案的刑事案件,由此可见其政治生活。超盛与地方社会的往来也十分密切,如在江浙为当地督抚说法开示,亦与京师王公大臣多有唱和,而所受官绅斋衬贡献则又反映出上层僧侣的经济生活和寺院经济的兴盛。超盛在乾隆朝虽不复往日的荣耀,但依然活跃于佛教界,从其名列编修《龙藏》之“总率”,出任宫中法会之“掌坛”等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其社会生活之细节。
超盛的地位和影响力来自于雍正帝的崇信,因此当雍正帝逝去,超盛昔日所受之恩宠,不仅不再是其家族夸耀的资本,更成为新君主禁忌。这实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教关系所致,虽然历代僧人都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实的矛盾作出阐释与调和,但汉传佛教终究难免受到政治的影响。正如陈垣先生感叹:“赵孟所贵,赵孟能贱……帝力果足续佛慧命乎? 续佛慧命果赖于帝力乎?”①陈垣:《清初僧诤记》,第382页。则是对中国佛教发展所提出的诘问。
作者简介:杨奇霖,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
标签:雍正论文; 奏折论文; 佛教论文; 禅师论文; 宫中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史论文; 《佛学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