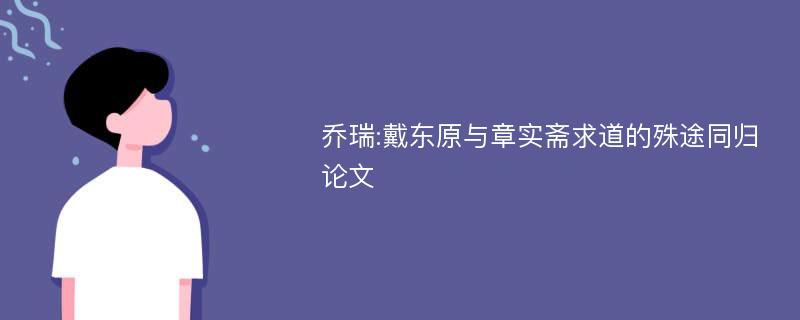
【文化研究】
摘 要:戴震与章学诚都是清代著名的学者,他们的“求道”之路相差甚远,可是最终的归宿皆为了跳出考证的局限而“求道”。戴东原从“道在六经”的基本准则出发,强调自翔实的名物考订,而实斋则对抗地提出“六经皆史”,在实斋看来学问从入之途不限于考据一端,他希冀通过文史校雠之学以通于道。虽然二者表面上在求道之法上天差地别,可是细究二人的最终终点皆是落于求道,即他们的本性其实都是“刺猬”。
关键词:戴震;章学诚;求道
一、戴、章思想矛盾的分析
提及戴震与章学诚,则鲜有人不知,作为研究清代儒学不得不提及的两位重要人物,其各自的理论与思想自近代以来自是不乏大批学者进行详细研究。想要对二者各自的学术思想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深入探究,首先必须明晰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明代晚期的程、朱和陆、王两派的义理之争,在王阳明重订《大学》后,实际上已经开启由义理之争转入校刊考订的路途,更进一步而言,儒学此时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这一过程中重新给予了“见闻之知”相当的重视。了解戴东原和章实斋理论思想出现的背景框架,将为笔者接下来进一步阐释二人思想的矛盾与联系奠定基础。
唐朝有和尚,号圆泽,与朋友李源善(一称李源)外出,见一孕妇在河边汲水,圆泽对李说:这妇人怀孕已三年,只待我去投胎,我一直避着,现在遇见没有办法了。三天之后,你到她家去看,如婴孩对你笑一笑,就是我了;再过13年(一称12年)中秋月夜,我将在杭州天竺寺等你。说罢那夜国泽圆寂,孕妇生一男孩,第三天李去探看,婴儿果然对地笑了一笑。13年后中秋夜,李源善到天竺寺,见一牧童坐在牛背上唱歌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李听了叹道国泽与这牧童真是有三生的缘分啊。
除了时代背景外,人物的心理也是我们把握他们思想的重要方面,在这里笔者借用余英时先生引入的“狐狸”与“刺猬”型人格概念说明他们是如何殊途同归的。余先生借助柏林的“狐狸”“刺猬”理论,使我们得以更清晰的理解戴、章二人的异同。刺猬型的人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中,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狐狸型的人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贯的中心系统,他们对各式各样的经验和外在对象,仅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认知态度,而不企图把它们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论点之中[1]83。证必尚博雅与分析,这种工作比较合乎“狐狸”的性情,义理则重一贯与综合,其事为“刺猬”所好,因此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实为一个“狐狸”当道的时代。
蓝蓝似有同感,点了点头,用眼睛扫描着洞壁上画着的开拓者的研发历程,以及鸣梭星、云织星、猎影星的简史。几百年来,在别人看来百无一用的机器人却把这个偌大的洞穴打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或者说是历史迷宫。橙橙拉着紫丁儿停在了一组奇怪的图案前,惊奇地打量着那上面他们所熟悉的战舰,那是地球人才拥有的战舰。小小的战舰有的飘在云上,有的在云洞里巡游,有的则底朝上挂在云下——确切地说是头朝下飘在云团下。
在理解清楚了“狐狸”与“刺猬”的区别后,我们来看一下二人表面上的冲突。戴震声名于学问最盛的阶段,他十分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重要性, 视之为求道的必由之路, 并且是唯一的途径[2]。这不得不与当时只重考证的风气有所联系,东原自乾隆甲戌入都后,长期处于“狐狸”的包围之中,受考证的影响非常之深,所以对宋儒的义理一笔抹杀,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3]168,从东原此言论观之,唯有考证才是通向义理明的正确之路。
而戴震的思想面貌与之相比就显出了一定的复杂性,由于他一开始便因为考证方面的成就被尊为“狐群之首”,这使他不得不和“狐狸”敷衍,不能像实斋那样和“狐狸”截然划清界限,也因此他有很多诸如“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着是也”[3]168的说法,在这里考证的地位被东原突出放大,这可能是他“因为正卷入了考证潮流的中心,一时之间脚步不免浮动,致有此偏颇之论”[1]130。但是东原的本性倾向于“刺猬”,论学必求“意旨所归”,他的一切考证工作最后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之中,其自述自己从十七开始便有志于闻道,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最终的终点是求道。除此之外,我们不难发现,东原时时有对一群“狐狸”的薄而寡要极为不满的言辞,“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 ”[5]143。东原在《原善》的《序》就指明自己修改本的最大特色是“比类合义,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6]61。通过绵密的训诂考证与义理探求结合,答复了时人认为他是在空说义理的批评。最后《序》末有“治经之士,莫能综贯”[6]61的话,则更显然是针对考证学家去的,可见他对考证家见树不见林的心态极为不满。同时他也有对考证学家的委婉点醒,“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不仅在诂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7]146,劝说他们最终的目的应该在于求“义理明”。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戴东原从“道在六经”的基本准则出发,强调自翔实的名物考订,而实斋则对抗地提出“六经皆史”,在实斋看来学问从入之途不限于考据一端,他希冀通过文史校雠之学以通于道。
二、二人思想联系的考证
除了在与他人的言辞中可以窥见东原间或暴露的伪装在“狐狸”之下的“刺猬”本性,细察他对于义理与考证这两门学问的不同态度,可知他内心始终偏向义理。段玉裁告诉我们:“记先生尝言‘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8]226。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东原在撰写义理文字时全副精神生命皆关注其中。东原在晚年也曾与段玉裁谈及自己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只想竭尽自己数年的努力写成一本可以明孔孟之道的书,而对于考订则仅想以余力完成。对于东原这样的想法,很难不让人将其志趣归为义理。我们了解了东原在撰述义理文字时的心理背景,即可发现 ,他虽然同时从事于义理和考证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但他对前者的重视和偏爱显然超过了后者。“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东原晚年的学术生命也归于一件大事。“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9],这是东原最确切的晚年定论。这可以说是他的“刺猬”本性所决定的。
而章实斋却不认可对于经学的考证,他自己评价自己“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结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4]335,力倡学问本乎性情之论,对于“狐狸”的博而不约表现出了反对,“足下博综十倍于仆,用力之勤,亦十倍于仆,而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也。足下于斯,岂得无意乎?”[4]292实斋反对一味追逐考证的风气,并且自己逐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最后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章实斋试图否定包括东原在内的考证学家“经学即理学”的中心观点,因而提出“六经皆史”与之抗衡,实斋提出“道”具有历史性质,是在不断发展中的,从根本上冲击了打破六经载道的见解,因为“六经中所可见者只是三代官师未分那一阶段中道的进程,三代以后的道则不可能去六经中寻找,即使六经中有可见之道,而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三者不可分,而后代经学考证家多以一隅自限,所得甚少”[1]52-53。六经既然在实斋看来不足以尽载道,他进而提出“文史不在道外”的看法。
虽然二者表面上在求道之法上天差地别,可是细究二人的最终终点皆是落于求道,即他们的本性其实都是“刺猬”。章实斋是一个十分勇敢而典型的“刺猬”,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身份,也因此他的学术面貌非常清晰,对于其最终的终点在于求道前文也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删除训练集中已有的样本时,采用减量式(或“遗忘”)算法。当样本xc在集合R中,如果它对SVR的解无作用,将其从训练集中移除时影响不大,且不需要调整。另一方面,若xc有一个非零系数,则将这个非零系数的值逐渐减少为0,同时确保训练集中的其它样本依然满足KKT条件。
三、结语
考证学占据学术主流的环境里,“支离”让一些学者不复能有超越考证进一步求道的冲动与精神了,当博学与信仰之间失去平衡,新的文献主义便代之而起[1]158-159。乾嘉时代,考证成风,学者们已然纷纷导向了天平的一端,而戴东原和章实斋则在努力平衡着两者,却遭到了“狐狸”的忽视与攻击,怎可不谓之是莫大的讽刺?
历史从来都不是过去,只因循守旧断然没有未来,而应当在旧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我们不仅仅应当着眼于东原与实斋的学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大时代下具体人物的学术观点和心路历程给我们的求学治学指明道路。
参考文献:
[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12.
[2]黄爱平.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以戴震、阮元为中心[J].清史研究,2002(03):91-98.
[3]戴震,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题惠定宇先生授径图[M].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74:168.
[4]章学诚,刘公纯点校.《文史通义》“外篇”三[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5]戴震.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答郑丈用牧书[M].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74:143.
[6]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61:61.
[7]戴震.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古经解钩沉序[M].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74:146.
[8]戴震.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附录.戴东原先生年谱[M].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74:226.
[9]戴震.戴东原手札真迹[M].台北:国立编译馆,1956.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086(2019)02-0153-02
收稿日期:2018-12-20
作者简介:乔 瑞(1999-),女,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学生,研究方向:训诂学。
标签:义理论文; 刺猬论文; 狐狸论文; 香港论文; 章学诚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清代哲学(1644~1840年)论文;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