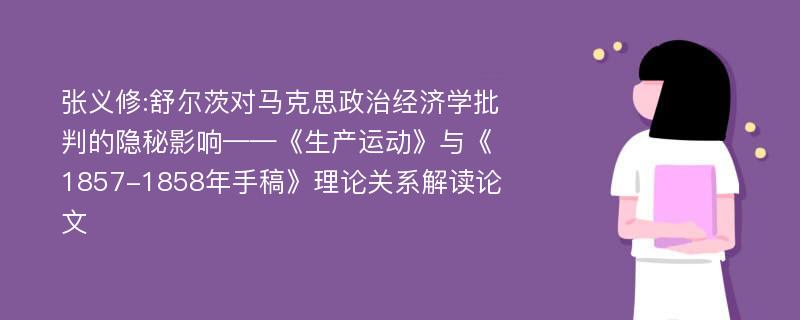
[摘 要]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产生了隐秘影响,这突出表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舒尔茨梳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史,强调斯密的“劳动一般”是劳动价值论乃至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马克思在手稿中也明确抓住了这一问题,而且阐明了“劳动一般”这一经济学出发点的现实历史基础,他对现实抽象的分析超越了舒尔茨。舒尔茨还从动力角度讨论了机器问题,认为机器的采用解放了人力,但是现实中也存在劳动单调重复的问题。马克思反对舒尔茨对机器的定性,认为机器剥夺了人在生产中的自主权,并且揭示了机器作为资本的高级物质形式对活劳动的完全占有和支配。
[关键词]马克思;舒尔茨;生产运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劳动价值论;机器
对于马克思来说,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是一部十分特别的著作,因为它不仅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启发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且在马克思伦敦时期仍然在其思想中发挥着隐秘的影响,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57-58年手稿》”)当中。本文通过《生产运动》与《1857-58年手稿》的对照分析,解读舒尔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种隐秘影响,同时阐明马克思对于舒尔茨相关思想的超越,从而更加完整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理论背景与科学性质。
马克思的《1857-58年手稿》是他为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第一份手稿,其主体部分是七个笔记本的专题手稿,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1939-1941年在莫斯科首次发表,发表时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因此也常常被称为“《大纲》”。另外,《1857-58年手稿》还包括一份马克思于1857年写作的《导言》,它写于一个标着“M”字母的笔记本上,被认为是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总的导言”。《导言》首次发表于1903出版的《新时代》第21年卷,后来一并发表在《大纲》之中。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多阶段、多层面的。而在《1857-58年手稿》中,舒尔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史与方法论的总体理解,二是对于“机器”的理解。前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导言》当中,后一方面则体现在手稿的主体部分,在后来的《资本论》中也有明确体现。以下我们也分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导言》中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作了具有经典意味的阐述。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已经触及对《导言》来说至关重要的主题,并且在具体论述上与马克思的分析有奇妙的关联性。实际上,《生产运动》两次直接提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而这两次表述都与马克思的思想有重要关联。在该书导言部分,舒尔茨将自己对物质生产规律的关注置于一个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下,并将亚当·斯密视为自己的同路人。舒尔茨在这里强调的是斯密的“分工”概念,并将“分工”理解为一种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结构,认为正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化(而非纯粹量化的生产速度提高或者财富增长)推动了历史的变革。这一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已经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不过,马克思当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史和方法论的总体态度仍然是接近于全盘否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马克思对于“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性评价。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都明确批判劳动价值论,认为这种理论特别是“劳动”概念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敌视人、将人抽象化的一种蓄意理论建构,而理想的未来社会将以人的“自主活动”来取代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这一点在《导言》中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对“劳动”概念、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学说史的重新评价,是马克思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生产运动》再次提到亚当·斯密,并对马克思产生隐秘的影响。
在书中的《精神生产·历史的角度》这一部分,舒尔茨对于包括斯密在内的政治经济学说史进行了一次梳理。他是这样说的:
在国民经济学中,是在大约16世纪中叶出现了重商主义的体系。在商业的体系中根本性的东西就在于,一个国家在和其他国家的对比中具有一定优势的生产的单个分支,被特别地强调和关心。因此它也是一个垄断的但也正因此是个别化的系统。自18世纪开始出现的重农主义的学说如今来看,是对重商主义者的反应,同时也是由特殊向普遍的一种进步,通过将原初生产作为被衍生出来的产品的普遍性来源,从而为国民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作为普遍化的更进一步发展,最终大约在18世纪末前后,工业的体系由亚当·斯密所把握,因为他将劳动一般(Arbeit überhaupt)作为生产的全部分支的共同因素,从而将其作为出发点。[1]115
社区药房应用药学服务模式,有助于用药合理性提高,帮助控制用药不良事件,且可提高患者满意率,具有可行性。
舒尔茨的这段论述,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一定已经读过,因为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大量引述《生产运动》中的其他经济学内容,作为论证工人贫困化等问题的证据。但是当时的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引述这一段。而且,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视角决定了他不会赞同舒尔茨的这种解读,因为在他当时看来,“劳动”这种抽象恰恰暴露出了政治经济学非人道的一面,而不是什么值得肯定的事情。“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2],从斯密、萨伊到李嘉图、穆勒,国民经济学越发“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的论点,然而它表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不如说是敌视人的”[2]。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说,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已经指出并承认了舒尔茨以上这段论述所指出的事实,但是他恰恰是以否定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实的。然而,到了《1857-58年手稿》的《导言》当中,马克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来看马克思在《导言》中的一段表述:
马克思为什么在分析机器时会引述舒尔茨,又为何一方面批评他的观点,一方面肯定他的这部著作“值得称赞”?想要探寻马克思和舒尔茨对机器的不同理解,还是要回到马克思的《1857-58年手稿》。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首次系统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机器”问题,相关段落常常被西方学者直接称为“机器论片断”。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并未引述舒尔茨,但是引述了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和尤尔的《工厂哲学》。马克思从这两部著作得出了以下认识:机器不是简单的工具的升级,而是多种不同功能的工具(动力、传动、完成工作)综合联动的体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经历了不同形态的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5]90此处马克思想要强调的是,机器作为劳动资料的一种新形态,在物质生产方面的特征在于能够“自行运转”,这也意味着,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5]90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具只是作为人的工具、是人的器官和功能的一种延伸;而在机器大工业阶段,人本身成为了依附于机器的一个“工具”和“器官”。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对于机器所造成的工人与劳动资料之间关系的倒转,马克思思考的灵感来自哪里呢?显然,并不来自此处他对拜比吉或尤尔的引述。追本溯源,还是与舒尔茨的《生产运动》相关。
那么,两段论述的比照,是否说明马克思在有意或无意间“抄袭”了舒尔茨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受到了许多同时代人(包括舒尔茨)的影响,这恰恰也是马克思博采众长的严谨科学精神的一种体现。但是,马克思的真正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论述虽然透露出舒尔茨的影响,但明显超越了舒尔茨的理解。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更精准、更明确地道出了“劳动一般”这一概念在经济学理论背后的哲学方法论意义,而且是因为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这一概念背后的现实历史基础:看似十分简单的范畴,却恰恰是在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最复杂的现代社会才得以出现的产物。只有在商品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各种劳动才能够现实地通约为“劳动一般”。“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3]46这样一种理论判断,不仅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才会有的观点,而且是只有到《1857-58年手稿》阶段他才形成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题中之义:从抽象范畴出发,是因为抽象本身恰是现代经济关系的真实起点。由此出发,才能在理论中重现经济体系的具体总体,实现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批判。这显然不是舒尔茨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了。相比此时的马克思,可以说,舒尔茨对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特殊与普遍关系的理解已经显得过于表面和粗糙了。
马克思在《导言》中没有提到舒尔茨的名字。但是,读一读马克思的这段表述,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舒尔茨上面的论述。在这里,马克思一改青年时代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拒斥态度,改以肯定姿态来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步。而且,他比舒尔茨更加明确地抓住了政治经济学对于“财富源泉”的理解问题:起初的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只关注个别的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而且不把这种活动视为生产性的劳动,而是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相比之下,重农主义“同这个主义相对立”(舒尔茨的说法是“对重商主义者的反应”),不再从取得货币的角度来理解财富,而是回到财富的真正的源泉,把农业劳动(舒尔茨的说法是“原初生产”)理解为创造一切物质财富的劳动,从而把一切产品理解为“产品一般”,理解为“劳动的一般成果”,这也正是舒尔茨所说的“由特殊向普遍的进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态度积极地说,“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抛开了各种特定的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将“抽象”再进一步,概括出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于是,一切财富都被理解为“产品一般”,而就其来源而言,也就有了“劳动一般(Arbeit überhaupt)”。不难发现,这个“劳动一般”正是舒尔茨所强调的概念。马克思在此无形之间与舒尔茨达成一个共识:“劳动一般”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真正出发点。
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中专门论述过机器问题。他首先将机器的应用理解为分工生产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谋生活动的不同种类分解为它们最简单的操作,外在的自然无理智的力量被运用于这种单纯机械的、简单重复的活动之中”[1]38。可见,舒尔茨正是在这里指出,机器的动力主要来自外在于工人的自然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工人的活动在利用机器的生产中,变成了最简单的操作、单纯机械的重复。如果再向前追溯,舒尔茨这里的分析也受到了亚当·斯密等人的影响。而舒尔茨之所以要突出机器的自动特征,实质上是为了延伸到分析人在机器生产中的作用,这一点被马克思继承了下来。对于人在机器大生产中的处境,舒尔茨的总体态度是颇为乐观的。他说:“人便保留了工业的更高的劳动,并且变成了这种自然力的理性的、相对物质性而言更多是以精神性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操纵者和领导者。这样,人就进入到活动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之中,因为他将服务于生产目的的材料仅仅同陌生的自然力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自然力的效果或产品,就不再依赖人自己身体的劳顿了。”[1]38在舒尔茨看来,机器用自然力代替了人力,这不仅仅意味着在狭义的发动力的意义上,人力得到了解放,而且意味着,在整个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人力都因为机器的“代劳”而得到了解放。物质生产被交给了机器,而人以精神性的方式从事的是操纵和领导的工作。与此同时,舒尔茨也发现,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机器并没有直接带来人的解放,相反,“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可以说这种连续不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1]69。
《生产运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处影响在于:如何理解“机器”问题。这是一个至今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也是对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马克思曾经明确提到舒尔茨的《生产运动》。马克思首先回顾了机器的发展,并批评过去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看不到工具和机器之间的本质区别。他指出,所谓“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的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4]。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从动力的不同来区分工具和机器,即认为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牲畜、水、风等自然力。马克思以脚注形式引述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中的相关论述:“根据这个观点也可以在工具和机器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锹、锤、凿等等,以及杠杆装置和螺旋装置,不管这些装置如何精巧,它们的动力是人……所有这些都属于工具的概念;而用畜力拉的犁,风力等推动的磨则应算作机器。”[4]不过,马克思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他犀利地反驳道:“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96000个线圈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么,机器生产事实上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4]尽管马克思不认同舒尔茨对于机器和工具的这种区分,但他仍然积极评价这部对他影响重大的著作:“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4]
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Arbeit überhaupt),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3]45
(2)平衡财政收支,弥补财政赤字。一般来说,当一国出现财政赤字时,通常采用增加税收、增发货币以及发行国债这三种方式来进行调整,但从效果和影响的角度来看,增加税收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减少赤字,但税收的增加是需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超出限度的增税会带来社会问题。同样的,增发货币在短期内缓解赤字的同时也会带来通货膨胀等问题,不利于长期财政收支的健康发展。因而,当前两种手段在一定额度内实行后效果不明显时,发行国债能够在短期内吸纳个人和组织的闲置资金,从而对财政赤字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但同样的,国债的发行也应考虑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过度的国债规模也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
在司法解释途径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放宽死缓适用条件以达到提高死缓适用率的目的。例如,有学者指出:“必须认识到,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并非易事,而在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后能否对死缓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也不见得乐观。因此,我们应该在努力推进刑法修改的同时,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为追求死缓制度在减少死刑的立即执行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寻找出路。”“因此,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要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只能通过对法律的合理解释,放宽刑法规定的死缓适用条件,使更多的原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17]
粗略来看,舒尔茨回顾了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当时他还是按照德国人的方式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的发展史。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舒尔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进展的:重商主义重视的只是生产的单个分支,重农主义则将农业生产即所谓“原初生产”视为其他产品的普遍来源。舒尔茨指出,这是一个“由特殊向普遍的进步”,即用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范畴来理解整个经济体系,而这就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作为普遍化的更进一步发展”,亚当·斯密用“劳动一般”来理解“生产的全部分支的共同因素,从而将其作为出发点”。显然,舒尔茨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史持正面评价,而且,他特别强调斯密从“劳动一般”出发来理解全部经济运作,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乃至整个方法论的核心。
舒尔茨关于机器的这两方面的论述都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因为相关段落出现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前者和他在《资本论》中的引述为同一段,后者则直接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舒尔茨自己也许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他说:“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1]69这一点,青年马克思也曾经引述过。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舒尔茨后一方面的论述才是现实,因为在工厂中,不是人主动地、自由地借助机器,而是人本身沦为了“机器”。
选择我院2016年1月-2017年12月急诊室收治的130例下肢骨折患者,将130例患者入院时护理模式不同进行分组,常规急诊护理患者设定为对照组,循证护理治疗患者为观察组,每组有患者65例,对照组:男性35例,女性30例,年龄18-78岁,平均(42.5±6.3)岁;观察组:男性36例,女性29例,年龄18-79岁,平均(41.5±6.4)岁;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有了舒尔茨的以上论述作为背景,现在我们回看《1857-58年手稿》,马克思将工人描述为机器的“肢体”,也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马克思指出:“机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5]90本来,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在劳动中起到的是中介作用;现在,工人的劳动在劳动资料即机器的运转中起中介作用。显然,马克思仍然拒绝像舒尔茨那样,认为是人在主动地、自由地操纵和领导机器。在他看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是卑微的,他们不过是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5]91。机器的到来并没有让人在生产中更加自由和主动,反而让人变得更加次要和被动。“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5]9到这里,马克思和舒尔茨观点的截然对立已经是清清楚楚了。不仅如此,马克思为什么会在后来的《资本论》中把舒尔茨的观点单独拿出来加以批判,也更加容易理解了:舒尔茨用动力来源区分机器与工具,最终是为了导引出人在有了机器这种外部动力代劳后的自由。而马克思恰恰认为,机器与工具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机器找到了外在于人的动力,而在于,在现实生产过程当中,机器剥夺了人对劳动资料的主动权。
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指出了舒尔茨在“机器”问题上对马克思的影响,这种影响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开始了,在《1857-58年手稿》以及《资本论》中有了清晰的表现。笔者也借此说明了二人理解上的截然对立之处。更重要的是,自《1857-58年手稿》开始,马克思对“机器”的理解水平已经远超舒尔茨。这主要还不是体现在以上方面,即从单纯的物质生产资料的角度来看待机器,而是体现在如下方面:马克思始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考察机器的意义,将其作为“资本”来看待。马克思在《1857-58年手稿》后续的分析中指出,机器在物质生产层面对工人的这种支配性地位,导致了资本在价值增殖层面对雇佣劳动的必然的支配性地位。马克思的论证思路如下:就价值而言,机器本身是一种已经表现为对象形式的劳动,即“对象化劳动”,雇佣工人使用机器过程中付出的则是新的“活劳动”。就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而言,活劳动总是主动利用和支配死的劳动资料。但是,在机器建构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阶段,却是机器这种死的、对象化的劳动在逼迫和支配活劳动。因此,从价值形成和增殖的角度来看,资本也就实现了对雇佣劳动真正的占有和支配。“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5]91换言之,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支配,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还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具有主观色彩的驱使和服从,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则融化在了机器运转的客观技术要求之中。“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5]91-92机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资料,作为资本的高级的物质形式,正是实现占有和支配活劳动的绝佳利器。马克思对机器的这一分析,不仅超越了舒尔茨,直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本次选取部分患者开展研究,分别给予患者硝普钠静脉滴注治疗以及酚妥拉明静脉滴注治疗,其中硝普钠治疗下的患者与接受静脉滴注治疗前比较病情改善效果更为显著,而且没有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与酚妥拉明进行比较综合应用价值更高,应当得到广泛使用。
参考文献
[1]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M]. Zürich,1843.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428.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9)02-0031-05
[收稿日期]2019-01-3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对象化”概念的思想史研究与方法论阐释(17ZXC007)
[作者简介]张义修(1988-),男,辽宁大连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奕颖)
标签:马克思论文; 机器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手稿论文; 恩格斯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对象化”概念的思想史研究与方法论阐释(17ZXC007)论文;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