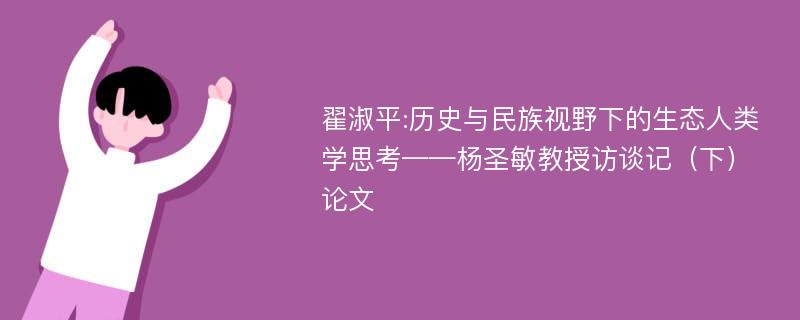
专家访谈
摘要:这部分访谈中,杨圣敏教授结合自身对于绿洲文化、干旱区文化、坎儿井等主题的田野研究,对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流派、跨学科实践、应用领域、未来走向等主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当前生态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关键词:绿洲;干旱区文化;地方性知识;生态旅游
翟淑平(以下简称翟):我有个感觉,生态人类学到中国后,总是在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框架下,和民族结合,视野就有点窄了,您是怎么看待的?
Q:雅昌的成名不仅体现在印刷界,也表现在文化艺术领域,无论技术还是商业模式均有很多特色,对此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杨圣敏(以下简称杨):对,视野就比较小。国内一些学者有这个问题,强调地方性知识,而且把这种知识完全固化,说这种知识完全都是正面作用的、不能违背,一旦违背了就不怎么好。只能说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绝对化。因为社会和文化都是变迁的,变迁的动力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出现。在科学和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时,一些地方性知识和民族传统能够帮助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生存,这些知识和传统就值得传承、保持。但是当科技和生产力提高了,旧的社会传统和知识也需要逐渐更新。如果我们不囿于个别民族,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去观察和比较,就能够更理性地去看待这些知识和传统,也能够更理性地看待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品牌”一词起源于古挪威的那维亚语“brandr”,本意是燃烧,意指生产者燃烧印章并将其烙印在产品上。在营销学理论中,品牌是能够为企业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品牌可以提升企业的资产价值,企业可以利用品牌优势减少价格弹性,稳定市场价格,同时获取同质产品的支付溢价,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对于消费者,品牌意味着高品质的产品和企业对消费者的服务承诺,以及产品所被赋予的文化等。
翟:您是要说,环境系统和文化系统、社会组织构成了一个整体,所以需要整体地、变动地理解吗?
杨:对。社会组织、文化系统、人这三者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是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与西方哲学把自然环境与人对立起来是不同的。同时中国哲学又说道可道,非恒道。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是变化不息的,没有不变的道。这个整体是会变化的,变化的原因,是由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矛盾集聚推动的。从内部来说可能是生产技术的变化、人口的增长、人际关系的变化等,从外部来说则是周围大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一般来说,大的自然环境变化很缓慢,甚至长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小环境是在不断改变的,人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小环境,小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是会不断改变的,小环境的变化会推动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逐渐变化。如果人们不去适应周围这些小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小的矛盾集聚的多了,就会形成大的矛盾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和突变。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小的变化,随时地、不断地调整人类自己的文化去适应它,也就是在人与环境的矛盾还小的时候就解决它,社会就能够平稳地发展。这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才可能,才可能知道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调整、改良。
妻子过去不说粗鲁话,现在经常说。我吃惊地望着妻子,难道皮肤病里有毒,她的身上染上毒,她的心理一样染上毒?
新疆的少数民族大多是农牧民,传统社会,其生产方式几百年、上千年没有明显变化,他们的文化也就不会变。但现在不一样了,科技发展的太快了,现代化、经济和市场全球化冲击到每一个角落,全世界都在大变、突变,不顺应形势去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怎么变,怎么调整自己,如何顺应环境的变化,以变应变,就需要借鉴一下其他民族其他地方的经验,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学者的作用在这种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因为你有更宽阔的视野,你了解的更多。如果学者也不能站得更高,仅仅龟缩在一个小的视野里发表意见,你就没有起到学者应有的作用。
1949年的时候,新疆仅有400多万人,现在已经超过2200万了。过去那些游牧民,冬天去南疆,夏天去北疆,现在不行了,没有那么多草场供你游牧了,你就要调整你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这种调整是否把旧传统一概丢掉呢?比如,新疆的老房子用生土砖砌,墙很厚,窗比较小,用砖头砌成穹隆顶,不用砍树去盖房顶。这样的建筑冬暖夏凉,又节约木材。这种建筑形式更适应干旱区的环境,就不一定要变。所以即便全球化、现代技术影响到了每一个角落,各地各民族仍有各自不同的适应方式,完全抛弃旧传统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变也是不可能的。
人和环境都在变,技术在发展,文化在变迁,所以,没有这个变化的观念,“非恒道”的观念,没有世界范围的视野,就会看不清这一点,就会和现代化有冲突。例如有的学者说,这不好,别修电站,别修水库,因为这会把我们改变了、把环境改变了。但其实需要变,只是变要有一个度,要渐变,环境和文化是一个博弈过程,有新的、更好的、可解决矛盾的、可持续的文化代替它,它就得变,而不变的,能留下来的那些传统文化都应该是可持续的,社会的进步需要的是渐变,不能突然消灭掉太多旧传统,而是要继承一部分、改造一部分;社会环境也是这样,各种亲属制度、人际关系的各种规则,不能突然都改变了,而是要渐变。渐变社会就稳定,突变容易造成动荡。
翟:所以比较的方法在生态人类学很重要,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后来,您提出一个绿洲生态人类学,包括现在新疆石河子大学他们也在提这个。
翟:那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环境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沙漠中都去争夺绿洲,那必然要引起民族的迁移啊,或者之类的人群竞争。
从调查中看到,文化课程门类多,覆盖面广,课程设置呈多元化趋势,为文化课程教师提出了挑战。教师要适应新趋势,提高知识、技能、素质的能力要素。通过适应性自我调整实现转型升级,不断更新知识,在《国标》中找到契机和生存发展空间。要尽快凝练自己的专业课程方向,教有所长,长有所教,在教学中搞研究,在研究中出成果,用成果促教学。要适应环境,调整心态和策略,通过挖掘个人及群体的潜力来改善所处的专业发展微观环境。教师要一方面系统研究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推进改革,创造性地探索融合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有效教学方法(孙有中,2016)。
杨:我对新疆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人所做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这样的例子。塔吉克自治县是新疆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县,自然灾害很多,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因此也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县。塔吉克人的一个传统,是家族内近亲通婚,一般一个村子内的人都是亲戚关系。一些学者批评他们这个风俗落后,但他们的社会很安定,是新疆犯罪率最低的县。在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只有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才能有效地对抗环境的压力。通过家族内近亲结婚,大家族不分家,内部就更团结了,人际之间的关系就更近了,灾害来了,大家互相帮助,有饭大家一起分着吃,再穷、再苦,也饿不死人。
翟:我们得站在人家的环境角度去看,而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
杨:对,还有一种对宗教的解读,认为越是落后的、环境恶劣的地方,宗教就越发达,可是我在塔吉克自治县,看到宗教在他们那里比新疆其他地方的影响都小,也就是清真寺比较少,去清真寺礼拜的人也少。为什么?因为他们用家族这个堡垒来对抗环境的压力,大家族的亲情还给他们安全感,有效纾解心理精神上的问题,因此去清真寺念经求安拉保佑的需求就小了。
翟:这是中国人类学学界的一个悖论,我们似乎总是向西方靠,但是西方把我们当成他者,人家想听我们的自己的事情。
杨:是的,他们不去做礼拜,不靠安拉,而是靠自己的家族,一个村子全是亲戚,周围上百人全是亲戚,互相来往很密切,有一点小事,都互相帮忙,有喜事就互相祝贺、送礼,联系很密切,世世代代近亲通婚,不嫁外人,家族就成了人生最可靠的保障、依靠,就是依靠这个去战胜环境的压力。
特别提示,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目录的生成,我们在新建一二三级标题样式时,必须指明它们的大纲级别,这是目录能正确生成的关键。在“一级标题”时单击“格式”按钮并选择“段落”,在打开的“段落”对话框中设置“大纲级别”为“一级”;“二级标题”设置“大纲级别”为“二级”;“三级标题”设置“大纲级别”为“三级”;“论文正文”的“大纲级别”设置为“正文”。
翟:他们那里也属于干旱区么?
杨:是干旱区,雨很少,年降水量只有100多毫米。再看新疆的维吾尔族小家庭,也能用这种逻辑解释,维吾尔族地区也是干旱区,有人做过统计,新疆南疆维吾尔地区是全国清真寺最密集的地方。[1]维吾尔人的家庭结构是小家庭,核心家庭,儿子一结婚,就分家,那怎么对抗环境的压力呢?小家庭没有那个力量,就得靠清真寺来凝聚村里人,组织村里各种活动,生老病死等各种大小事都要请阿訇来帮忙,请阿訇帮忙就要信教,就要去做礼拜,平时就要给清真寺送些财物。阿訇出面,有事的时候大家才来帮你。所有的村子都有清真寺,有的大村有两三个清真寺。所以这些事情弄明白,也就了解社会是为什么这个样子。从这个道理也能明白,那些中东的、伊斯兰国的人,不一定是为宗教信仰而战,而是为生存、为争资源而战。所以,从环境角度看问题,能让你对世界有新的更深入的理解。
翟:也就是说,环境会让视野更开阔一点,不是见宗教就是宗教,背后的东西可能会更开阔地去理解。
杨:是的。社会中宗教组织的存在不仅是因为加入者有共同的信仰,这也是一种社会认同,为了大家有个理由去抱一个团,互相支持,一起去争资源。这个时候谁不信教就可能被孤立,所以信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能够给人很多启发。怎么看边疆地区、民族地区、不发达地区,因为越是这些地区,环境影响就越大。环境影响大、压力大的地方就需要人之间有更多互相的依靠和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角度,但是要注意不要眼界太窄,只看一个小地方,别把环境跟文化的关系固定化,它是变动的。当我们进行分析的时候,就要从那个小地方跳出来,站得更高,从发展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看环境与文化的互动,从而指出对人类更有利的发展方向。
翟:所以现在就是出现了一个环境的全球史,尤其是生命共同体的看法,因为不仅是人了,它把动物,植物,也放在里边。比如我们做全球环境史的视野是够了,但是这种操作性怎么来把握呢?
杨:操作性就是在你研究的那个点上,你要弄清楚它的特点是什么,把这个特点找出来,分析哪些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这样,你必须得作对比。为什么我把新疆和海南岛作对比,还到云南去做调查?就是要把降水量差别很大的不同地方作对比。比如说对比这两个地方的回族和维吾尔族,同样信仰伊斯兰教,为什么两个地方的穆斯林风俗习惯差别很大呢?因为海南岛那边雨水特多,新疆这边降水特少,特别干旱。这种对比就能让你看出来哪些文化因素是受了环境的影响。
翟:最起码把文化这个变量控制了,来比较环境,是这个意思吗?
杨:对啊,都是穆斯林民族,比较干旱和湿润环境的影响。
江西茶叶的主要出口地区为欧盟、美国、日本等国际市场,近年来,江西省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步伐,也积极将茶叶出口至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翟:那您能具体地谈谈湿地文化中穆斯林的这种变化,表现在哪些地方吗?
杨:举个例子,对比西北和海南等地穆斯林的服饰。在西北地区,干旱风沙大、阳光强烈,夏季就穿宽松的袍子,遮挡日晒还便于通风,妇女则戴能够遮住头脸的大头巾,防风沙也防日晒。所以这种穿着最初不是宗教的要求,是环境的要求。在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人们都是这样穿着,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就是这样穿着了。而在海南、云南等地区,天气炎热又潮湿,衣着需要考虑散热的功能,服饰就比较短小,就不会像西北的穆斯林服饰那样把身体都遮蔽起来。所以,不同的服饰不是信仰上的差别,而是环境的影响。
翟:所以说穿袍子,也是跟气候有很大关系。那么,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吧?
翟:从这个角度出发,生态人类学虽然现在发展得相对一般,您认为是否还是有前景的?
翟:家族形式会有很大区别么?
杨:海南那边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资源竞争就不那么激烈,人的生存压力没有那么大,家族组织就小一些,松散一些。另外,那里的现代化水平和社会化程度高一点,家族之间、人际关系就淡一点,民族意识、宗教意识也比西北地区淡得多。福建泉州的回族在饮食上不太讲究,为什么呢?个人不必太强调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就可以维护住自己的利益。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与西北有差别。做这些对比,就能够明白他们的文化为什么有差别。
● 应急联动。从自控联动和降低安保压力的角度看,处理紧急事件仅靠视频监控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视频监控需要与报警、门禁、对讲等设备或系统根据预设的策略进行联动,实现及时响应,发现隐患、降低危害,从而提升安保水平。
杨:绿洲生态这个概念国际人类学界提了很多年了,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提了,相关的研究很多,把“绿洲”输入数据库检索,文章太多了,几千篇。其实,在干旱区、沙漠地带,人生存的地方都是一些小绿洲。中东、北非都是这样。所以绿洲生态人类学不是新的研究领域,在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的生态人类学理论创立以前,就有很多人在研究绿洲文化了。
翟:我看到您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包括民族变迁都很关注。您觉得民族关系的变迁过程,背后有没有生态、环境起的作用,它是怎么样的?
1.1.1 入组标准 ①血清总胆红素水平≥342 μmol/L;②胎龄37~42周;③日龄1~28 d;④无明确严重的围生期高危因素;⑤出生时无窒息复苏抢救史;⑥本研究的实施已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
杨: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环境中的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语言等不一样,互相之间会有误解,产生矛盾;另一个是资源的竞争,就是经济利益的争夺。资源争夺比文化差别对民族关系有更大的影响。不同文化的民族经过长时间的接触,那些误解能够逐渐消除,甚至还能在文化上互相融合;但是资源竞争就不一样了,为了一点土地、水源、矿产等资源,就能打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就为了争那点地、那点水而流血,其实他们的文化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犹太教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有好多相同之处。所以,如果民族关系不好其实往往就存在资源竞争的问题。现在好多学者从文化上说事,其实单纯从文化上说事解决不了问题。有人主张只谈文化,不要往政治上扯,出发点是好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治比文化影响大,政治就是权力,权利背后就是资源,没有权力根本保不住资源啊!要缩小贫富差距,要让社会上的资源分配公平、平等,就需要政治上的举措啊。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这样的政治举措。
翟:您的这种观点在您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有没有具体的体现?能否详细谈一谈?
杨:是的。糟糕的、恶劣的环境,战争也多,资源竞争更激烈。
整合资源,构建云平台。智慧云平台彻底解决各地融媒体建设中资金不足、技术缺乏、安全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变区域传播为全域传播,极大提升地方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
翟:那从这个方面来看,民族竞争之类的这种研究多吗?
杨:民族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太多,因为咱们总是强调民族团结,不太讲民族矛盾。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呢,过去主要用阶级分析法,从民族竞争这个角度讲的比较少。而且学者们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尤其人类学界的主流理论还是西方的,西方的主流学说还是认为文化是核心,分析什么问题都用文化说事。但是生态人类学认为经济是核心,经济问题、资源问题是核心,这是各种矛盾的本质。所以生态人类学在西方发展也不快,也比较慢,中国很多学者总跟着西方理论转,在文化里转,所以在生态人类学角度的研究就比较肤浅。
翟:现在我们中国生态人类学的一个问题,似乎在于学科的理论比较少,仍旧是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您觉得制约因素是什么?
杨:没有太大进步,还是原来西方的那点理论,没有新思想,本质上在于他们仅从文化上研究,仅关注文化。其实,环境主要是资源和经济的问题,对民族关系影响最大的也是经济和资源问题。这是中国人类学界需要明白的一点。中国人类学界很多学者都有这个倾向,一定要跟美国人讨论,不和美国人对话就觉得学问不够,不前沿。实际上他们主要是弄文化,最后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讨论了很多鸡零狗碎的文化问题,与社会焦点的大问题离得很远,解释不了伊斯兰国、解释不了新疆的这些事、西藏的这些事,就是弄文化。
杨:不一样,建筑也不一样。
杨: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前景广大。从这个角度开展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人类社会的很多事情。比如各种文化特点产生的原因、民族关系问题、民族发展道路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这个角度的理论最初是西方学者创建的,对我们很有启发,值得借鉴,但我们不能一直囿于这些既有的理论,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实证研究中去不断发展他,创新他,才可能对解决很多环境与人类之间关系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解释和思路。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也要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不仅要与西方学者对话去讨论他们的理论,更要以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去做调查和研究,从中总结规律和理论,这样做研究,这样的成果,才能够推动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也才能够得到国际学界的尊重。
进一步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法规体系。从国家层面应尽快颁布“军民融合促进法”,并结合已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制订完善促进各动员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专项法规,加快“国防勤务法”“民用资源征用法”“国民经济动员法”“信息动员条例”“装备动员条例”等立法进程,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修订工作;在企业法、金融法、基本建设法、交通法、投资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补充民营企业参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贯彻国防要求等条款,增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
翟:也就是说,他们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环境适应方式吗?
杨: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西方学者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学生,因而他们习惯于我们跟在他们后面做研究,鼓励我们去论证他们的理论。关键是我们不少学者也认为这种状况应该是常态,愿意就一直这样做研究。
翟:您说生态人类学如果走对路,就会很有前景。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走?
杨:我并没有很成熟的意见,刚才提了几条,一是要有全球的视野、历史的视野,才能看清楚方向;二是不要把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看成固定不变的。“道可道,非恒道”,世界一切都是在变化的,变化才是世界的规律,环境与人类社会、人类文化都在变化之中,人类要以变应变才是正道。生态人类学如果通过各种案例讲清楚了这种种变化的规律,就可能对人们找到以变应变的恰当方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翟:您如何看待生态人类学的应用性?
杨:就是要在具体的环境下探讨社会如何发展,考察传统文化的意义,尤其是为适应环境而具有的那些传统文化,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改,改变的度在哪里,不能把旧的全都扔了,有很多是有存在价值的。比如说在新疆的农村,很多妇女戴头巾,是因为那里风沙大,不能一概说是封建迷信。另外南疆的那些土坯砖建筑,那种穹庐顶、平顶的建筑,即经济又适合当地的环境。就不一定都要用钢筋水泥来代替。我每次去南疆农村调查,就更愿意住在土坯砖的房子里,冬暖夏凉。
翟:那这些对学者的实际调查要求会不会更加广泛一些?
杨:比如说要给政府搞现代化的时候提供参考,当地传统的人际关系准则、家族组织,不能全部都打破了。例如在帕米尔高原上,环境严酷恶劣,当地的塔吉克人为了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就要维持大家族,维持大家族的一个办法就是近亲通婚。如果塔吉克人的生产力没有很明显的提高,你认为进步的社会组织方式不能很有效地对抗环境的压力,你就不能说人家近亲通婚就是落后,不能马上要求他们改变这个风俗,只能让他逐渐改变。我看到有的塔吉克人进了城,到了喀什、乌鲁木齐居住,还是保持大家族的传统,几个兄弟不分家,上班挣的钱都交给老父亲管,家里谁花钱、包括孙子辈上学、上兴趣班,都是老父亲来分配钱,他们这种大家族很和睦,这说明有些传统保持着并没什么坏处啊,传统里边有很多正面的东西,还是有保持价值的。
翟:这里面包涵着很深、很广的生活智慧。
在对该菌实施药敏试验后,可以看出该菌对先锋霉素和培氟沙星表现出高度敏感性;对卡那霉素、土霉素、阿莫西林,表现出中度敏感性。而对青霉素和链霉素等药物表现出不敏感状态。
杨:对,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跳跃,不能跨越,要渐变、渐进。
翟:现在新疆的生态旅游搞得比较火热,比如说很多人现在到新疆、南疆旅游很好,比如说草原圈起来,房子就在这儿,人家都去看这个房子。您对生态旅游有什么看法?
杨:现在全国都很火啊。游客来几个月,圈起来的那个草原就踩坏了。新疆的旅游,不管是生态旅游,还是历史文化旅游,都是大的公司占便宜,有国企的,也有私企资本的大公司,把地方圈起来了,周围老百姓当然受影响了,土地、草原都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公司把大钱挣走了,老百姓在街边摆个小摊什么的,挣点小钱,所以肯定有意见。我去日本时,了解到京都、奈良等地方,规定外地的公司不准来搞旅游,只能是当地人自己来搞旅游业,公司也只能是当地的,这样就让当地人能够受益,也能防止外来的公司把资本卷跑。本地人搞旅游可以保持一些本地的文化,它是真的,不是假的,游客来了,我穿什么衣服、跳什么舞,这是真的,也不会制造很多社会矛盾,因为传统的地方往往都是穷地方,外来的大公司来了,去挣穷人的钱,当然就不合适了。
翟:刚才您讲到吐鲁番的研究,从干旱区文化提到了历史的视角、比较的视野,之后您在新疆研究中,关于生态环境的考虑是否依然再进行?
研究数据管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研究人员参与不足,上级机构政策缺乏,存储与保存基础设施薄弱。有文章指出,国际上不少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和英国等的研究图书馆虽然在研究数据管理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总体上仍处于宣传和培训阶段,技术服务如提供数据目录、保存实际数据等尚未展开,可见研究数据管理仍任重道远[11]。
杨:是,其实是没做完,我在当了十五、六年的民社院院长,工作比较忙,其实很多调查没有做完,我也希望能继续去做,毕竟人脉关系还在呢,村里的老乡都比较认我,关系都很好。现在有的学者看新疆问题热,都跑那去了,但不太容易进去,我可以进去,因为有我的村子,我的老乡,可以接着做,做得再细致一点,我的博士论文已完成20多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版,因为我觉得还能做得更细一点,增加一些材料。
翟:我觉得从2000年到现在,生态人类学它有一个很活跃的变化,尽管还没有奠定好基础,但是出来很多新的东西,比如有的学者探讨政治生态学,说生态背后是有政治权力的,比如说建一个国家公园,是为了有闲阶层能够回归自然,此外也包括生态补偿、生态权力之类的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考虑很多,您是如何看这种新的变化?
杨:生态人类学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然生态环境,一部分是社会生态环境。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这两部分,都是非常关键的、缺一不可的。比如社会生态环境里肯定就包括一些权力的不平衡和博弈,也包括社会变迁、民族关系的变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所以,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是很广泛的。
翟:还有一个是生态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比如说,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还有一些民族昆虫学,都归在生态人类学下边,和“民族”关联起来形成一些分支学科,您怎么理解这种跨学科?
杨:这些是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分得特别细,是没有尽头的。因为我十几年前跟日本九州大学的学者合作,在海南岛的一个村子做调查。中国学者对当地生产和生活的变化做的描述是,村民过去吃不饱饭,因为大米不够,现在粮食产量多了,稻米多了,人均产量比原来多了很多,都吃饱饭了,生活好了。日本人对此变化的看法不一样,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调查做得特别细致,那个调查团队有二十多人,有教授、有学生,他们整天跟着农民观察,农民每天去种地,此外还去打鱼、打老鼠,因为当地人也吃老鼠、吃各种虫子。日本学者就跟着去记录,也访问老年人,还把那些老鼠、虫子,反正那些杂七杂八的野果子等等,都记录下来,收集样本,然后拿回日本去化验,分析里边有多少营养成分、多少卡路里。经过一番计算,他们的结论是,过去当地人的营养也不差,非常丰富、均衡,所以生活也不错,过去大米不够吃,但是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就打老鼠、捉虫子、摘果子、挖野菜等;现在虽然米吃的多了,但营养未必有过去的丰富、均衡,所以未必像我们中国学者说的,是生活改善了。所以这个研究也是生态人类学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的分析让我们重新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角度怎么能更好,也能够很好地反思我们的进步主义。开了那么多的荒,把树林砍了,种了稻米,米是够吃了,但营养更单一了,虫子少了,小动物少了,环境破坏了,其实也未必就是好的,就是进步的。
所以我也很受他们的启发,和他们合作也很有意思。生态人类学,跨学科研究,越做越深入,所以这个研究是没有尽头的。然后,这些研究的结论确实对我们重新认识人类自己的生活、人类的社会,都会有很多启发,也让我们不断地反思发展的观念,思考什么样的发展是好的,让我们保持着清醒和警惕。我觉得,人类学对人的本性研究比较少,而最高的研究就是研究人性,其实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不论是哪个民族的人,人性都是相通的,只是因为自然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的不一样,才形成了不同的人,不同文化。而生态人类学能够对这些都有所关注,让我们更了解人性,因而很重要、很有启发。
翟:杨老师,今天的访谈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您从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个人的研究经历等角度展开的讨论,我收获良多。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再当面向您请教!
注释:
从表1可以看出,由不同位置的实测粒子速度给出的fmax随波传播距离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这反映了波传播过程中高频成分的耗散。κ和λ在不同频段内的拟合值不同,这表明α(ω)和k(ω)在不同频段内变化的快慢不同,反映了球形应力波在花岗岩中传播的复杂性。
[1]孟航:《中国穆斯林人口分布格局浅析》,《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6-0106-06
作者简介:翟淑平(1982-),女,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人类学;杨圣敏(1951-),男,回族,辽宁绥中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学、人类学。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郭 婷
标签:人类学论文; 环境论文; 文化论文; 生态论文; 新疆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三峡论坛》2019年第6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