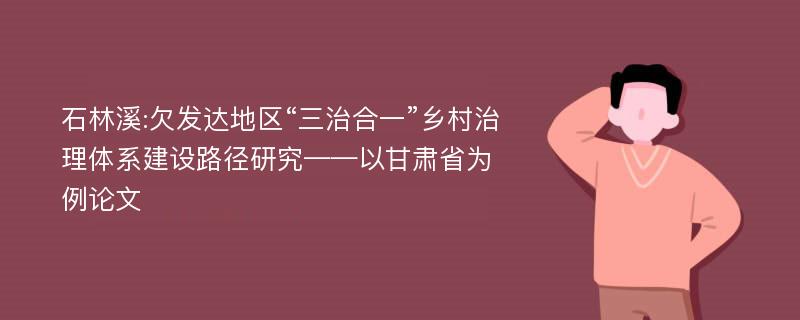
[摘 要]“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设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的实践场域。其中,自治是制度目标,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道德秉持。甘肃省等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面临德治影响相对广泛、法治较弱以及村民自治力量薄弱、建设能力有限等困境。因此,在研究“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当探究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具体情况,理清“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因地制宜地提升“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水平。
[关键词]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路径;欠发达地区
2013年,“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在浙江省桐乡市率先开展,随后全国不同地区借鉴并推广。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源自浙江省桐乡市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既是指导当前乡村治理的理论导向,也是落实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践指南。
1 自治、法治、德治的历史存续
1.1 自治:乡村治理的制度目标
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自治有其内在复杂性。长期以来,“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历史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乡村治理政治环境。乡村治理主要依靠乡风民俗、习惯规约和道德伦理等。伴随经济社会的变迁,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加剧,传统乡村内部治理结构已无法维持分化和裂变的秩序。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行政区划的设立上打破了传统,将其划分为省、县、乡三级,但是乡镇以下的行政村仍然保留着自治传统。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农民组通过公开选举正式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随后其他一些地方又出现了村民自治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监督委员会、村民组等,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明确规范了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安排和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实践证明,村民自治在推进农业发展、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安全、调解民间纠纷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村民自治自诞生以来就有其固有的内在特点。村民作为乡村发展的最终受益者,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主体作用。自治是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自治的内涵包括加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村民通过规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行为,充分发挥自治主体智慧,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摒弃影响自治有效性的过时因素,在村民自治中推陈出新,创建顺应国情和域情的村民自治秩序[1]。
1.2 法治:乡村治理的保障底线
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步伐从未停止。习近平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认为“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农村基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场域,乡村社会的基层法治建设是乡村治理的保障底线,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必须大力推进法治思想和法制化方式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运用,通过加强乡村地区法治建设来助推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2]。
[10]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11,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72.
1.3 德治:乡村治理的道德秉持
乡村秩序的良性运行和乡村生活的正常开展依托一定的规范准则。这一规范准则有2种:一种是正式制度规范,例如法律、法规、规章等形式;另一种是非正式制度规范,例如道德规范、伦理价值、习俗、文化信仰等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范[3]。这两种规范是推进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2个重要层面,对应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法治与德治,在具有广泛德治基础的中国乡村社会,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维护乡村秩序不仅需要具有强制性作用的法治来保障,还需要社会成员自觉遵守和实践公共秩序,即德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的“道德权威”对于维持乡村生活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局
2.1 德治影响相对广泛,法治较弱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的农村越来越多。2018年,甘肃省城镇化率为47.69%,远低于我国总体城镇化率59.58%。传统农村也主要集中分布于甘肃省等欠发达地区。德治是传统农村社会维护乡村秩序的最重要方式,虽然城镇化发展使城乡间人口流动加速,传统农村的人文景貌发生改变,但熟人社会的人情世故依然保留在传统农村生活现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以德治为基础,强调血缘和地缘关系,具有相对冷漠的业缘关系,德治影响相对广泛。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为乡村治理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近年来,甘肃省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乡村社会的各类问题在完善的法律体系范畴中予以规范,但农村依然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区域,法治建设仍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因此,甘肃省等欠发达地区农村法治建设整体状况不容乐观。在乡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同时,由于体制转型、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更新转变,农村社会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不断显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已超出了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范围,农村社会的各类问题必须在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的帮助下推进解决,确保农村社会秩序健康良性运行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从而调节和规范社会行为。乡村治理需要将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和具有柔性约束力的道德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地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和道德的教化作用。
(5)有色金属矿产与黑色金属矿产人均产值领先。2017年河北省持证矿山企业人均产值29.22万元。其中,第一是有色金属矿产人均产值73.63万元,第二是黑色金属矿产人均产值44.88万元,二者的人均产值明显优于其他类别。人均产值位于第三、第四、第五及第六位的分别为,能源矿产25.75万元、贵金属20.19万元、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18.48万元及建材和其它非金属矿产17.34万元。
2.2 村民自治力量薄弱
法治作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保障底线,要求任何建设方案都要依法建设,新时期“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绝对不能忽视法治作用。具体而言,国家法律必须及时有效地保障村民自治,明确村民自治的法律界限。完善农业和农村的法规体系,完善农村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农业市场规范运作。将各种与农业有关的工作纳入法治范畴,确保农村地区的改革和发展成效。开展广泛的法律教育,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村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加快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机制,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统筹各种法治力量营造农村社会法治氛围[4]。
2.3 建设能力有限
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正视中国农村差异化,坚持自治原则,有效利用法治和德治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区别对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在甘肃省等欠发达地区,应根据地方自治条件、德治基础和法治保障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最适合的治理组合、治理体系和善治类型。应从以下3个方面促进甘肃省等欠发达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构建。
3“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实现路径
“地方精英扮演关键性角色”是桐乡市实践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强而有力的建设能力作为保障,人力资源是保障建设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城镇化发展,甘肃省的农村社会结构出现了深层次的裂变和发展,农村“空心化”正成为传统农业省份甘肃省农村的“新常态”。大量劳动力资源外流和人口数量减少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许多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年轻人普遍外出务工,整个村庄的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农村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要为留守家中的老人、妇女和残障人士,而这些农村劳动力普遍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弱,人力资源质量令人担忧。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返乡潮,但返乡人员的知识能力水平和劳动实践技能较低,尚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3.1 强化法治建设
甘肃省传统农村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使村民之间普遍缺乏整体利益关系,即便存在整体性利益关系,集体行动也难以有效推行,基层村民自治作用发挥受阻。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发展,甘肃省很多地方推进了城中村改造,其中不乏巨额利益的诱惑,但因制度乏力,导致城中村改造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村民民主表决往往沦为“空投”,村干部腐败现象滋生,大规模上访或群体性事件频发。究其原因,在乡村政治中,乡镇政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等参与主体没有理顺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决策管理不民主、滥用职权等问题。村民是乡村自治的重要参与主体,自治是村民发挥自我管理作用的重要平台,而现实中普遍存在村民参与主体“缺位”和参与意识不足现象,村民主体性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不高,民主监督机制失灵。因此,“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村民自治力量相对薄弱。
3.2 完善村民自治
建设“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从村民利益出发,将村庄发展与村民利益有机统一,运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转移。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村民自治和民主监督为依托,贯彻落实乡村共建、共享、共治的要求,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政府应加强政策支持,通过完善的激励措施培育和壮大村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增强村民的凝聚力,通过合理的制度规范强化村委会服务性功能。将村民自治嵌入具体实践,发挥村民主体性作用,切实落实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本要求。落实村民的民主权利,在法治框架下依法办好自己的事务。
3.3 增强建设能力
鉴于甘肃省等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匮乏的事实,应开拓思路,打破人力资源的时空限制,广泛吸纳外来人员参与本地区乡村建设,提高乡村建设能力。此外,依靠本地区乡贤和基层政府的主要力量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乡贤参与秉承志愿精神,基层政府参与是一种职责。当代乡贤既可以是民间权威,也可以是地方精英,依靠乡贤丰富的知识和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促进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5]。政府部门可鼓励支持基层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合作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合理发挥基层政府的服务主体作用,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这是典型的民营企业“离场论”,与此类似的还有公私“合营论”、党建工会“控制论”等观点在网上流行。可以说,从下到上,都不同意这类观点。加之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民营经济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李三辉.自治、法治、德治: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三重维度[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4):37-40.
[2]何阳,孙萍.“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209-214.
[3]谢乾丰.关于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若干思考[J].社会科学动态,2018(4):16-22.
[4]袁金辉,乔彦斌.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J].行政论坛,2018(6):21-27.
[5]范和生,李三辉.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J].广西社会科学,2015(1):149-153.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19)25-47-3
基金项目:2018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甘肃省美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2018B-053)。
作者简介:石林溪(1986—),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风险社会、社会发展;李涛(1976—),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标签:乡村论文; 法治论文; 甘肃省论文; 德治论文; 村民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工人论文; 农民论文; 青年论文; 妇女运动与组织论文; 农民运动与组织论文; 中国农民运动与组织论文; 《乡村科技》2019年第25期论文; 2018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甘肃省美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2018B-053)论文; 陇东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