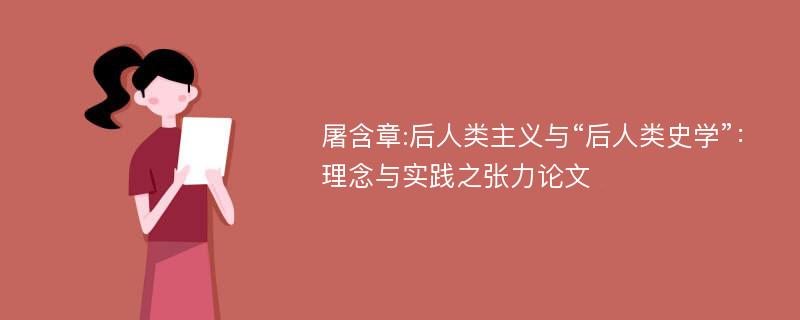
摘要:作为一个新兴的思潮,后人类主义来源颇为复杂。福柯所宣称的人类的终结及梅西会议上有关控制论的讨论,大致标志了两大渊源,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强调批判性,旨在反思人文主义(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后者则是在科技革新的刺激下产生的“后人类”议题,亦有“超人类主义”的思考。凯瑟琳·海勒对技术层面的后人类主义的回应,将科技发展中的控制论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联系到了一起,代表了两种后人类主义的交流。面对后人类主义的挑战,历史学家已经尝试突破人类中心论、人类特殊论的传统观念,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动物史),并在研究方法上力图从生命科学中汲取养分,推进了历史考掘的深度和考察的广度。简而言之,来源于科技革新和展望的后人类主义冲击了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促使史家从“后人类”的角度审视历史研究的前景,但近年“后人类史学”的实践亦表明,这一史学新潮在未来的发展仍将面临不少挑战。
关键词:后人类主义;“后人类史学”;凯瑟琳·海勒;福柯;生物学
2018年底贺建奎引发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促使人们对技术伦理做出深思。对于这两名婴儿而言,贺建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们的造物主,于是她们的身份界定便成为问题。她们可以被称作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吗?如果不是人类,又是什么?超人类,抑或后人类?在国内,与此相关的“后人类”话题随之成为热点,而在西方,有关后人类境况(posthuman condition)的讨论早在1980-1990年代便已出现。
门静脉海绵样变性属于代偿性病变,形成机制为大量侧支循环静脉在门静脉主干或其分支完全或部分阻塞后形成于其周围,形成目的为机体为了使肝脏供血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名称来源为其切面在大体标本上呈海绵状血管瘤样改变[1]。本研究对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收治的60例肝癌门静脉海绵样变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分析了128排螺旋CT诊断肝癌门静脉海绵样变的价值,现报告如下。
妊娠母猪主要表现为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突发流产,产下死胎、僵尸胎、木乃伊胎。妊娠母猪流产后,胎衣长时间不下,恶露不排,从阴道中持续排出灰色浑浊分泌物。症状消失后,妊娠母猪发情不正常,不能正常配种受孕。仔猪发病后,体温迅速升高到41 ℃,呼吸极度困难,精神状态变差,两只耳朵向后伸直,对外界刺激十分敏感,遇到声音刺激后,表现出兴奋和鸣叫。有的患病猪出现严重腹泻、呕吐症状,呕吐和腹泻物呈现黄色,从口中分泌出大量泡沫状唾液。患病猪行走无力,眼结膜发炎潮红,叫声嘶哑,共济失调,头部歪向一侧,在圈舍内作转圈运动,最终倒地死亡[2]。
那么,后人类境况会对历史学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后人类主义的挑战,历史学家尝试突破人类中心论、人类特殊论的传统观念,开拓动物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并在研究方法上力图从生命科学中汲取养分,推进历史考掘的深度和考察的广度。本文对后人类主义及后人类史学的探讨兼及两大问题:其一,后人类主义思潮由何而来?科技展望下的后人类主义与思想界所谈的后人类主义有何区别,又有何关联?其二,当我们进入后人类时代,历史学将会变成怎样?
一、后人类主义思潮的起源
“后人类”是一个听起来颇有科幻意味的词语,也许会让人联想到机器人、克隆人等科幻电影中出现的形象。但“后人类主义”却不仅仅是科幻意味的,该词的含义不是很明晰,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甚至有的解释还是对立的。“后人类主义”一词的内涵之所以如此丰富,或许与其英文构词有一定关联。在英文中,“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可作 “post-humanism”解,亦可作“posthuman-ism”解。如果是前者,有不少文学理论界的学者主张应该译为“后人文主义”,后者则是“后人类”加“主义”。[注]参见蒋怡:《西方学界的“后人文主义”》,《外国文学》,2014年第6期,第111页。国内对“后人类主义”已有一些介绍,多见于文艺界与哲学界。如蔡仲、肖雷波:《STS:从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孙绍谊:《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思潮与电影》,《文艺研究》,2011年第9期;王宁:《后人文主义与文学理论的未来》,《文艺争鸣》,2013年第9期;冉聃、蔡仲:《赛博与后人类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10期;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读书》,2015年第10期。本文以 “后人类主义”作为“posthumanism”的译名进行讨论,因为“后人文主义”难以囊括随着科技发展而带来的“后人类”议题。
批判性后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在《何为后人类主义》(WhatisPosthumanism)一书中指出,“后人类主义”一词真正进入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批判话语是在1990年代中期,而“后人类”思潮的来源则要更早一些。首先,他将“后人类”思想的系谱追溯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60年AI写作的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末段所宣称的人类的终结:“人是我们的思想考古学能轻易表明其最近日期的一个发明。并且也许该考古学还能轻易表明其迫近的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注][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92页。当然,引发思想界思考后人类的来源不止福柯一端。在尼尔·巴德明顿(Neil Badmington)看来,“后人类主义”之“后”与后结构主义有着极近的亲缘关系。[注] 参见Neil Badmington, ed., Posthuman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p.9-10. 比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动物性在,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便是引发人文学界“动物转向”(animal turn)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注] Jacques Derrida,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More to Follow),” trans.David Wills, CriticalInquiry, Vol.28, No.2 (2002), pp.369-418.“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的法语原文是“Animal que donc je suis”,直译过来是“使‘我’之存在得以成立的动物”。这里所说的动物,其实是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Cogito, ergo sum)中的“思想性”相对立的“动物性”,故译为“动物性在,故我在”。这是德里达的一个文字游戏,挑战了笛卡尔对人的定义。德里达的“动物性在,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已然成为后人类主义者的口号。由于本次笔谈有专论动物史研究的文章,故此不赘述。
这一层面的“后人类主义”在科幻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之中影响颇大,故也有人称之为“通俗的后人类主义”(“popular posthumanism”)。但由于科技发展(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革命、认知科学等)对人的中心地位的挑战,导致人与非人(动物、机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对人性造成了威胁,这促使大多数出身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者尝试捍卫古典的人文主义。比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PosthumanFuture:ConsequencesoftheBiotechnologyRevolution)一书中担忧后人类思潮之下生物技术发展的失控,提出应当以“政治锁死科技”。[注][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立志译:《我们的后人类未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卡里·沃尔夫等学者称“超人类主义”为坏的“后人类主义”,希望将此义项从“后人类主义”中排除出去,主张批判性的“后人类主义”。[注] Cary Wolfe, WhatisPosthumanism, p.xvii.
除了控制论以外,弗诺·文奇(Vernor Vinge)所提出的 “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同样推动了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发展。弗诺·文奇所说的“技术奇点”指的是,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转折点之时,人类社会将进入后人类时代,产生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如当初“地球出现人类生命”一般。[注] Vernor Vinge, “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How to Survive in the Post-human Era,” in Vision21,InterdisciplinaryScienceandEngineeringintheEraofCyberspace, NASA, 1993, p.12.不过,大卫·罗登对所谓“技术奇点”的立场非常反对,这也是促使他提出推测性的后人类主义的动力。他的理解对我们以往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学存在的意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预设之下,人类不再按部就班地沿着历史进程前进,而对未来的展望也不再需要基于对过去的回顾。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术界最常提到的技术视野下的后人类主义与批判性的后人类主义虽然用的是同一个词,但其关怀却相差甚远。技术视野之下的后人类主义的含义近乎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超人类主义”不怎么强调人类自我认知的转变,而是一种展望:畅想我们未来将如何利用技术,以及其他方式改变我们自己,不只是用其他事物代替我们自己(如人工智能),还有挖掘我们自身的潜力从而超越人类的现状(如生物技术与“赛博格”[注] 所谓“赛博格”(“cyborg”),亦即“cybernetic organism”的简称,是美国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恩斯(Manfred E.Clynes)与内森·克兰(Nathan S.Kline)在一篇题为《赛博格与空间》(Cyborgs and Space)的文章中提出的。为了克服星际旅行中人类身体的局限,他们设想可以向人体植入一种神经控制装置(也就是“赛博格”)以扩展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轻人类适应宇宙空间环境的负担,使其能有自由去做更多有创造力的事情。此后,“赛博格”的含义则扩大为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组合而成的混合生物体。参见Manfred E.Clynes and Nathan S.Kline, “Cyborgs and Space,” Astronautics (Sept.1960), pp.26-27, 74-76; Donna Haraway, Simians,CyborgsandWomen:TheReinventionof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1991.)。“超人类主义”植根于近代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继承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遗产——对于完美人类的向往。[注] 有关超人类主义的简要介绍,可参见Nick Bostrom, TheTranshumanistFAQ:AGeneralIntroduction, 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 2003, pp.4-7.
在另一条系谱之中,后人类主义的起源则被追溯到1946年到1953年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s)[注] 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s)是由梅西基金(Josiah Macy, Jr.Foundation)的弗兰克·弗里蒙特-史密斯(Frank Fremont-Smith)在美国纽约组织的一系列会议。由于资助方是梅西基金,故称“梅西会议”。梅西会议从二战开始一直到冷战时期多次举行,其中1946年到1953年的会议以控制论为主题,来自神经生理学、电气工程学、哲学、语义学、文学、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参与了讨论,可以说是一系列跨学科的盛会。参见Claus Pias,ed., Cybernetics:theMacyConferences 1946-1953, Zürich-Berlin : Diaphanes, 2016;[美]凯瑟琳·海勒著,刘宇清译:《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6-110页。上关于控制论(cybernetics)的讨论与系统理论的发明。在梅西会议上,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沃伦·麦克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等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学者经过讨论并确立了一种关于生物、机械与交流过程的新理论模型。[注] Cary Wolfe, Whatis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xii.简而言之,这是一种 “把生物视为机器,把机器视为生物”的另类方法。[注][美]凯文·凯利著,东西文库译:《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670页。由此开始,人类从思维认知上的优越地位上被移出,而被机器取而代之。
控制论的发展,将信息与它的身体剥离开来。与这种发展巧合的,是人文学科领域的话语分析,特别是由福柯创立的考古学,将身体视为话语系统的一种游戏。尽管物理学和人类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承认实体的重要性,但他们还是共同创造了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身体的实体是第二位的,而身体编码的逻辑结构(亦即符号结构)是第一位的。[注]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第257页。此处译文根据英文原文有所改动,参见 N.Katherine Hayles, HowWeBecamePosthuman:VirtualBodiesinCybernetics,Literature,and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192.
那么,如何区分这两种后人类主义呢?如何理解“后”(post)也许是二者的关键差异所在。科技后人类主义中的“后”,是时间上“后于”之义,在其语境中,“后人类”往往作为名词使用。大卫·罗登(David Roden)所命名的“推测性的后人类主义”(speculative posthumanism)属于科技后人类主义的一种,他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认知科学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种不再是人类的后人类,而作为一种新的存在形式的后人类不仅拥有智慧且强大有力。[注] David Roden, PosthumanLife:PhilosophyattheEdgeoftheHuma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18, 30. 在这里,“后人类”显然指时间上后于人类的一种存在。与此不同的是,批判性的后人类主义的“后”则在很大程度上承袭自“后结构主义”之“后”, 是对人文主义的反思。[注] Neil Badmington, ed., Posthumanism, pp.9-10.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提倡后人类主义的学者同时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提倡者。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曾是女性主义学者,近年又成为力倡后人类主义的学者。也许她认为后人类主义是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进一步突破。在她的《后人类》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达芬奇原版的维特鲁威人图被改造成女性版、小狗版、小猫版甚至机器人版。参见[意]罗西·布拉伊多蒂著,宋根成译:《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所谓“信息如何失去‘身体’”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将信息定义为一种概率,一种可能性,将其与意义剥离;[注] N.Katherine Hayles, “Situating Postmodernism With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Discourse, Vol.9 (1987), pp.24-36.到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主张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性质而非实体的表现,并提出人的意识能够从其身体中分离出来而存储到计算机中;再到梅西会议上,信息被建构成一种没有实体的媒介,而人类则被当作信息处理实体,本质上与智能机器无异。这是一个信息“如何被概念化,成为与物质形态相互分离的实体”的过程,“而物质形态曾经被认为是信息赖以栖居之地”。[注]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第2、10页。
二、控制论与考古学
把发展民生林业摆到重要的位置,采取有力的措施,下放城市园林绿地管理事权,转换森林资源管理体制,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部门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使林业工作的造、管、用、护更为有机统一。全市现有育苗单位1944家,年产值可达8490万元;森林生态旅游年接待1600万人次,年收入近3亿元;中藏药种植、林下养殖产业,年产值近2000万元,林业可持续发展有了活力源泉。
3.1.2 BCRD小鼠自主行为的检测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症组、乳腺癌组、BCRD组小鼠旷场实验跨立格子数、直立次数明显下降,除乳腺癌组直立次数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抑郁症组、乳腺癌组比较,BCRD组跨立格子数、直立次数均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0.01)。结果见表2。
凯瑟琳·海勒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一书可以说是思想界化约技术后人类的极佳案例。她在书中所讲述的“信息如何失去‘身体’”的故事颇有创造力地将控制论与福柯的考古学联系到了一起:
尽管批判性的后人类主义学者也有将“后人类”用作名词的,但如果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还是与技术后人类不同,前者所谓的“后人类”时代是一个“仍旧是人类的后人类”时代,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而后者则“预测未来将进入一个后人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将被后人类所取代。[注] Zoltán Boldizsár Simon, “Notes on Posthumanism,” p.8.此文为未刊稿,将发表在《历史与理论》(History&Theory)杂志,笔者在此感谢作者提供文稿。 比如凯瑟琳·海勒(N.Kathrine Hayles)虽以“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命名其书,但在书的末章表示:“后人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相反,它预示着某种特定的人类概念要终结。”[注]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第388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对后人类主义思想家的启发,不仅在于他关于人之消亡的预言,还有他关于身体的论述。福柯在对疯癫史、监狱史与性史的探索之中,从身体出发观察权力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的演变。他所谓的身体,已经不是属于个人的肉体,而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处在权力关系当中的身体。《规训与惩罚》里面谈到的在观众的注视中被剥去皮肉、五马分尸、烧成灰烬的达米安(Damiens), 以及在全景敞视监狱中驯顺的罪犯,他们的身体都为权力所控制与操纵。尽管呈现的形式不同,尽管后者看起来更为“文明”,但他们的身体都是展现权力的一种符号。这也正是为何凯瑟琳·海勒认为控制论与考古学具有共通之处,而其共同点正是在于二者都将身体的符号性放在首位。
尽管正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所质疑的:“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其实二者可以兼得”,[注] Ewa Domanska, “Posthumanist History,” in Peter Burke & Marek Tamm, eds., DebatingNewApproachestoHistory, p.340.多曼斯卡的说法的确有些夸张,但历史学的后人类转向确实对“历史学家的技艺”提出进一步的挑战。那么,生物学影响下的历史学如何研究人?这种新的取径和传统史学对人的一般描述有何不同?下面笔者主要围绕伦道夫·罗斯(Randolph Roth)关于美国历史上谋杀率的研究尝试探讨这一问题,他曾以此文参与美国历史学年会圆桌会议“当历史学遇上生物学”的讨论。
三、“后人类史学”的实践
爱娃·多曼斯卡(Eva Domanska)将后人类主义化约为后人类中心主义,并认为在这股潮流之下,现在的历史学应该向生命科学汲取知识,她又力倡动物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多曼斯卡接受的是卡里·沃尔夫所用的词汇“后人文学”(posthumanist)并将其理解为“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学”(post-anthropocentric humanities)。她认为后人类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体现在学界对后人类中心主义取径日益增长的兴趣,诸如动物史、生物史、环境史与神经史,以及对于人类世、气候变化、非人类力量、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与非人类中心观的时间(地理时间)的讨论。于是,多曼斯卡进一步提出:“如今历史学正在从生物学而非哲学中汲取养分。”[注] Ewa Domanska, “Posthumanist History,” in Peter Burke & Marek Tamm, eds., DebatingNewApproachesto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p.328.她的表述可能是受到美国历史学年会的圆桌会议主题 “当历史学遇上生物学” (History Meets Biology) 的启发。参见“AHR Roundtable: History Meets Biology,” 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Vol.119, No.5 (Dec.2014), pp.1492-1629.
有趣的是,卡里·沃尔夫虽然反对凯瑟琳·海勒将后人类主义理解为后人类,一种脱离实体、失去身体的状态,反对她将后人类与具象相对立,但他的治学取径却延续了凯瑟琳·海勒的探索,主张采取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旨趣与取径,考察人文主义的高贵理想是如何在被哲学与伦理学体系概念化的过程中被廉价出售的。卡里·沃尔夫说:“我们大多会同意虐待动物是不对的,还有,身患残疾者理应受到尊重与平等的对待。但是我们会看到,人文主义所用的哲学与理论体系产生了主观片面的标准——一种特殊的人类概念——构成了最初歧视非人类的动物与残疾者的基础。”[注] Cary Wolfe, WhatisPosthumanism, pp.xv-xvii.换言之,人类特殊论导致了对非人类动物与残疾者的歧视,因此卡里·沃尔夫倡导动物研究与残疾人研究。[注]残疾人研究于1980年代在欧美学术界开始兴起,使得人们看待残疾人的方式发生了范式转移:残疾被看作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现象,以及一种社会的建构,而非仅仅是个人的身体缺陷。参见Dan Goodley, DisabilityStudies:AnInterdisciplinary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2011, pp.xi-xiii.
罗斯承认,历史学家能够搜集历史资料并绘图,进而推想人们对政府与社会的看法对谋杀率有一定的影响。但他指出,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何在国家出现危机之时,因日常生活中的摩擦(比如邻里财产纠纷)而引发的命案也会相应有所增加,便不那么容易解答了。在没有借助于生物学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也能做出一些推想。比如当政治失序之时,人们感到不再受到政府的保护,于是在面临私人财产的侵犯时采取较为极端的应对方式。但是,现代神经学、内分泌学、灵长类动物学与情感心理学则能够提示另一种答案。生物学对动物行为的分析能够提供借鉴,帮助历史学家挖掘人类行为的生物性根源。在这里作者借助的是关于群居猿猴的侵略性的研究。相关研究表明,当群居猿猴的社群政治不稳定的时候,雄性猿猴血浆中的睾丸素便会上升,而血清素则会下降,猿猴的侵略性被完全激发出来。当然,由于在人体实验中难以控制无关的变量,因此还不能肯定地说人类同样如此。但有充足证据表明,在竞争性的运动比赛当中,低水平血清素的男性更冲动,更容易产生暴力倾向。并且,在竞争性的电脑游戏中,通过饮用色氨酸消耗饮料降低血清素水平会增加侵略与报复的可能性。[注] Randolph Roth, “Emotions, Facultative Adap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Homicide,” 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Vol.119, No.5 (Dec.2014), pp.1537-1546.
将人类的情绪描述转化为体内激素的升降作用,这显然超出了传统史学的认知范围。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如此追问并做出解释并无必要。但笔者认为,对这种探索性的史学实践做出价值判断似乎意义不大,关键在于这种做法背后的治史理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分析的前提是,人类相对于动物而言并没有那么特殊。唯有在突破人类特殊论的前提之下,才能运用非人类哺乳动物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人类,而借鉴生命科学相关成果解释历史中人的行为能够避免历史解释浮于表面,从而推进历史考掘的深度。
上述讨论证明,后人类主义对于人文学者具有吸引力,但如何将后人类主义的理念付诸实践,显然并不容易。《后中世纪》(Postmedieval)杂志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创建于2010年的《后中世纪》致力于前现代研究,与年鉴学派的传统有所联系,但更有可能是受到了“后人类主义”的影响,所以用“后中世纪”(postmedieval)为题。从第一期的编者艾琳·乔伊(Eileen A.Joy)与克雷格·迪昂(Craig Dionne)的导言来看,该刊的旨趣在于探索后人类史学。他们承认,“尽管前近代的过去如何阐明后人类/人类的未来仍有疑问”,但主张前近代历史的研究也许可以为后人类讨论中的种种议题提供很多宝贵的资源,包括象征、主体性、身份认同、社会性等等。[注] Eileen A.Joy, Craig Dionne, “Before the trains of thought have been laid down so firmly: The premodern post/human,” Postmedieval:AJournalofMedievalCulturalStudies, Vol.1, No.1-2 (2010), pp.1-9.
不过,《后中世纪》并不只是发表探究“后人类史学”的论文。2011年,卡里·沃尔夫受邀组织了该年第一期“动物转向”的讨论,引起了不少关注。但之后发表的论文又多与身体、性别、情感等新文化史的课题有关,可见“后人类史学”的探索,与其他新思潮有着不小的联系。显然,象征、主体性、身份认同等话题,亦非在后人类主义影响之下全新的创见。由此可见“后人类史学”尚处在探索之中,需要与其他史学探索携手共进。在《后中世纪》创刊之时,有一位名为克里斯特尔·巴托洛维奇(Crystal Bartolovich)的学者表达了与编者不同的看法。她借用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 Appiah)的“后殖民之‘后’是‘后现代’之‘后’吗?”( “Is the ‘Post-’ in ‘Postcolonial’ the ‘post-’ in ‘Postmodern’?”)这一说法,认为不应该将 “后中世纪”(postmedieval)与“后人类”(posthuman)中的“后”(post)相提并论,前者将被证实,而要确认后者还有待时日。[注] Crystal Bartolovich, “Is the Post in Posthuman the post in Postmedieval?”,Postmedieval:AJournalofMedievalCulturalStudies, Vol.1, No.1-2 (2010), pp.18-31.她的质疑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因为从《后中世纪》的发展来看,其后人类主义的旨趣已经不再是该刊唯一的主题,而是相应有所扩大。
2.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属财政拨付工资的,可考虑由财政部门每月发放工资时直接将养老保险拨付入库;或由参保单位按月申报缴纳。
电力调度信息化的主要业务为: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将控制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核心,调节流经发电、变电和输电设备的电流和电压,进行数据的监控和采集,编排电力调度计划和运行方式,以信息化和自动化为目标,实现电力调度系统相互联系、资源共享的安全、稳定、优质和经济运行。其中,要实现电力调度中心各系统间数据和信息的横向和纵向共享,就必须对电力调度信息化的措施进行优化并重新组合。
总括而言,后人类境况对人文学界的挑战普遍存在,目前史学界的回应也为史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大体说来历史学家的实践还比较落后。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从理论层面来看,思想界在消化技术性的后人类主义的思想之时,借用了许多人文学科原有的资源,比如福柯与德里达的思考,这就使得“后人类主义”,变为“后人文主义”(亦即对人文主义的修正)或者“后人类中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思想接轨。相关学者利用了人文学科内部原有的资源理解、消化新事物,自然无可厚非,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令人有“新瓶装旧酒”的印象,而不少学者也因此在性别、身体、主体性、认同等问题里打转。其二,实践“后人类史学”要求学者具备多学科的背景,而且是生命科学等理科背景,而这对目前的历史学专业培养的学者来说比较困难。再者,对于一般的文科学者来说,与技术后人类相关的书籍并不容易消化。凯瑟琳·海勒相对比较特殊,她在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化学硕士学位并工作数年之后才转而攻读文学,具有化学与文学的双重学术背景,但这样的人文学者毕竟还是少数。过去的史学尽管也强调跨学科,但涉及的学科诸如哲学、文学、社会学,大致仍旧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付诸实践相对要容易一些。与之相较,“后人类史学”对于历史工作者而言,将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挑战,但也因此而富有无穷的吸引力。
PosthumanismandPosthumanHistoriography:TheTensionbetweenTheoryandPractice
TUHan-zhang
(DepartmentofHistory,Peking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offer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osthumanism and clarif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echnological-scientific prospect of posthumanity and critical posthumanism.It is noteworthy that N.Kathrine Hayles associates cybernetic theory with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in a creative way, which is a superb example of how critics respond to the technological-scientific prospect of the posthuman futu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posthumanism, historians have also attempted to transcend the anthropocentr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experiment with new fields like animal history and borrow the methodology of biology in order to broaden and deepe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y.In a word, posthumanism challenge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which is a worthwhile undertaking.Meanwhile, it remains to be seen if posthuman historiography can attract more practitioners in the future, as it requires training and expertis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posthumanism; posthuman historiography; N.Kathrine Hayles; Michel Foucault; biology
收稿日期:2018-10-12
作者简介:屠含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宋鸥
标签:人类论文; 主义论文; 史学论文; 身体论文; 控制论论文; 《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论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