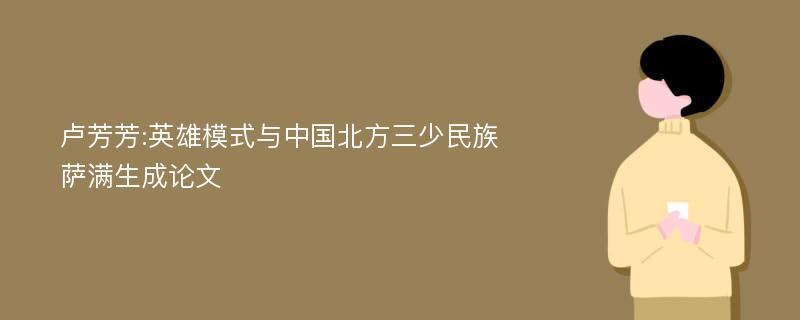
摘 要:坎贝尔提出的“分离-传授奥秘-归来”与“成为萨满-习得知识-解决问题”内在相通。英雄发现自我,发现神性的心灵之旅,是坎贝尔理论的根基所在,这也是萨满必经的心路历程。通过对时下中国北方三少民族的萨满生成过程的梳理,结合坎贝尔神话理论中的英雄模式,互相印证。“东学西学,其心莜同,南海北海,道术未裂”。
关键词:三少民族萨满;英雄原型
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 坎贝尔在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千面英雄》中,系统地提出“英雄之旅”(The hero’s journey),并总结“出发、分离-传授奥秘-回归”的具体过程与旅途中对应的各种象征阶段,这一模式被广泛地应用于当代故事创作。有学者认为:“英雄之旅不是新发明,它只是对事物的总结。它是一种对美丽结构的认识。它是一套管理人生和讲故事的原则,就像掌管着物质世界的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它就像一种永恒的真理、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形态、一种神圣的模式。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可以产生无限的和充满变化的衍生品,各个都反映着基本的精神”。[1]英雄发现自我、发现神性的心灵之旅,既是坎贝尔理论的根基所在,也是各民族萨满必经的心路历程。本文试图比较坎贝尔英雄模式与中国北方三少民族萨满生成实践,跨越时空、地域、文化,试图形成理论对话,为新时代当下萨满研究提供多维视角。
(2)建设专门性监测井,替换现有机民井。加快替换利用机民井监测的长期监测站点,避免因开采导致局部水位大幅度降落,影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消除因生产井所属权变更或报废而无法监测,造成数据中断的隐患,提升监测数据连续性和监测质量;改善监测站点管理和维护困难的现状。
对于国内萨满研究,孟慧英老师在《萨满医术:北方民族精神病学》提到:“对萨满医术,应从心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多种角度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全面而相对正确的结论”。而本文所涉及“英雄模式”的思路来自卡尔·荣格的心理学思想与约瑟夫· 坎贝尔对神话的研究,可界定为心理人类学范畴。[2](31)郭淑云老师在《中国萨满教若干问题研究述评》中指出:“既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积极汲取国外萨满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又应系统挖掘我国萨满教的历史文化资源,逐步积累能揭示本学科内在规律性的具体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建构和完善中国萨满学的理论体系”。[3](83)
一、中国北方三少民族现状
中国北方三少民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东北部,属于阿尔泰语系。根据2010 年统计数据,达斡尔族的人口数目约为131992,鄂温克族约为30875,鄂伦春族为8659 人。他们的人口、语言、居住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如图所示:
人口数目 语言 居住地 传统生产方式达斡尔族 131992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 内蒙古新疆 农业语 鄂温克语 内蒙古 狩猎驯鹿农业鄂伦春族 8659 满-通古斯语阿尔泰语系 内蒙古 狩猎阿尔泰语系 满-通古斯鄂温克族 30875
其中达斡尔语接近蒙古语,某些达斡尔语据说保留了蒙古语的古老形式。与其他民族相比,达斡尔族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较高,他们中的某些人,如Badarangaa,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前馆长,通晓8 种语言。达斡尔族与蒙古族通婚率在呼和浩特等城市的比率相当高,也有一些达斡尔族,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祖先可追溯自清政府戍边、屯垦时期。
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有三个分支,一为索伦鄂温克,以种植农作物为主,另一种被称为通古斯鄂温克人,饲养动物。三为雅库特鄂温克,也被称作使鹿鄂温克,拥有仅仅不足200 的人口,居住在根河市敖鲁古雅乡从事狩猎和饲养驯鹿,而大量的族人生活在中俄边境,俄罗斯东北侧①。鄂温克族以萨满教闻名。大约20 年前,根据国家计划,他们由政府安置,从敖鲁古雅搬迁到了根河市,以“改善生活”,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安置。第一次发生在1969 年中苏战争期间,他们从奇乾搬到敖鲁古雅,出于安全考虑,他们的许多亲戚生活在沿额尔古纳河俄罗斯边境一带。一些安置后的驯鹿牧民更乐于住在山上,并且迁回。
图2中,控制字符/R/标示一个多帧的开始;/A/,标示一个多帧的结束;/Q/,标示链路配置信息传输的开始;/C/为链路配置信息,共由1四字节组成,这些配置数据由用户在初始化时写入配置寄存器中,用于定义JESD204B系统的工作模式;/D/为用于填充多帧的数据,并无实际意义。
相传最早的鄂伦萨满是尼山(Nichan),相当健康、聪明、强大,擅长射箭,善良勤奋。经由她手治愈多位患者,甚至可以使人死而复生。然而,她的事迹激怒神灵:一个死了的人如何能复苏?死者已死!作为惩罚,她被扔进河里淹死。虽然死亡,萨满知识却传给了新的一代。根据鄂伦春的做法,在生活中成为萨满,需要一些征兆:“首先,当婴儿出生时,胎胞不破,要用刀切开取出婴儿;第二,患者长期不愈者,请萨满跳神,萨满看出患者要成为萨满。第三、患癫痫或神经错乱症”。[10](51)一个年轻人将从氏族中被挑选出来,将变得困惑、不稳定,宁愿独处。将有迹象表明他或她的灵魂是神,他或她会教各种萨满教知识带走。在启动仪式之后,他或她的灵魂将回到身体,他或她将再次成为“正常”。“新萨满学习跳神,冬天要在‘斜仁柱内举行,夏季则在外面宽阔的场地上举行,新萨满第一次学习跳神通常要进行三天。当表演者进入眩晕状态时,他或她被认为是着魔的,灵魂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10](51-53)
早在1996 年,纳日碧力戈教授曾参与由郝时远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课题组,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的鄂温克民族乡敖鲁古雅进行实地考察,因1965 年中苏冲突迫在眉睫,鄂温克驯鹿牧民早已由政府搬迁到奇乾。他的部分思考发表于《蒙古与中亚研究论文集》(1 卷,第1 篇, 1996 号),题为“失落的情感:以鄂温克族为个案”。他在文中提出:“与蒙古人不同,鄂温克族人不是那么有弹性的调整他们的情绪和重新安置他们的道德权威。他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调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改变,而在山林之间,他们可以籍由隐居或者对神灵的发现来寄托他们的情感,或者重建那些被认为是外部授权的市场化进程扰乱的事物。”②近年来,鄂伦春族的知识分子,新一代逐渐成长,陆续发出他们的声音。其中一位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白兰教授,她曾与北京大学的费孝通教授就民族文化充分商讨。据悉,因此,费教授提出“文化自觉”、呼吁少数民族文化意识,并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每年,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地区均能获得政府补贴,新的学校逐步建成,电视接收器如数分发。然而,一段时期内,由于外来的助力缺乏来自本土的观点,忽视了当地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发展的旧进化观把社会形态划分为“先进的、原始的”或“不发达的”。将少数民族和安置工程归为“文明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将不稳定的或移动的生活视作一种“落后”的象征。
二、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模式
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 坎贝尔在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千面英雄》中,提到乔伊斯的单一神话,认为所有的神话叙述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模式,最伟大的神话存在于历史叙事的表面及世界各地。他认为:当这种共同的模式穿越时空时,由于社会结构和接收环境的压力,它会转变成各种各样的地方形式。然而,其中基本的结构仍然未曾改变,它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例如召唤冒险、接受超自然的援助、与女神会面、和父亲赎罪等等系列程序,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揭示了心理层面的一整套技术。他提出:“这在他看来,这也是神话的功能所在,认为神话具有宇宙观、神秘性、社会性等功能,心灵的统一对他而言至为重要。“在欠缺普遍而有效的神话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未被认可的、初步的、但隐含强大力量之梦的众神庙。”[4](2)他提出:英雄的旅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图1
在美国人类学家、非盈利萨满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麦可·哈纳看来,萨满系统,是一组运行于灵性世界的使用方法,他整合出一套全面有效的技术,旨在保留地球上的萨满知识,透过鼓声进入著名的“萨满旅程”,展开意识之旅的旅人,会经历只可能在神话或梦境中出现的另一个宇宙。萨满的方法与技术,如观想、意识状态转换、精神分析、静心冥想、正向态度,否在协助人们“找回自己的内在医生”,在当代被证实能精准有效的恢复个人健康,并改善身心状况。
启蒙:获得某种以象征性方式表达出来的领悟;
考验:陷入险境,与命运搏斗;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卡车司机能随时随地了解行业发展动态的同时,大量货源信息被上传到智慧物流平台上,这种变化使得卡车司机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进行找货。而这些变化对于卡车司机都转化成他们最看重的指标——在工作强度不变甚至有所降低的情况下,增加了收入水平。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卡车司机选择加入智慧物流平台的原因。
归来:最后再度回到正常生活的场域。这是每一位英雄的必经之路。
鄂伦春族的萨满(yadgan)有两种:一是莫昆萨满(氏族萨满)每个氏族产只能生一个;一是“德勒库萨满”(流浪萨满),一个氏族有几个。
坎贝尔指出:“从神话到悲剧,揭示了黑暗内部道路的具体危险和技巧,是神话和童话的商业。因此,这些事件是梦幻般的和“虚幻的”:它们代表的是心理上的,而非身体上的胜利。”
在北方三少民族的萨满生成实践中,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充认萨满者,经萨满或者占卜者认定后,由其或族众者出面,请以一老师萨满为其举行领神仪式,学习到此和祭神本领,被请为师者的老萨满,达斡尔人称为‘额各雅德根’,意为母萨满,之后举行仪式;为徒者被称为‘库克雅德根,即子萨满。”[9](196)
如果英雄得到原力的祝福,他便在保护之下出发(使者),如果不是这样,他便逃跑并且会被追捕(变形逃跑、克服障碍逃跑)。在回归的阈限处,超自然的力量必然被留在后面,英雄离开可怕的王国,再次出现(归来、复活)。他带回来的恩赐则使尘世更新(万灵丹)”[5]在睡眠与清醒的重复之间,与人的一生的周期类同,坎贝尔引用了阿兹特克人的世界观:“水,土,空气,火”,宇宙的四种元素分别终结于世界的某一时期,形成重复循环之轮:水的时代在洪水中结束,土的时代在地震中结束,风的时代在飓风中结束,而“现在的时代将被火焰摧毁”。[6](224)它提醒我们的中国五行平行:金克木,木生水,水克火,火克土,当一个完整的周期结束时,地球将把金消除。
对120例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实施检验分析(统计学软件:SPSS17.0)。t检验时,将肿瘤患者的白蛋白、前白蛋白、总蛋白以及血红蛋白营养指标(计量资料)描述成均数±标准差(±s±s)的形式。P<0.05时,差异显著,符合统计学意义。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接受了人类心灵统一的思想,并非全部无视所有民族志的细节。他指出,“文化是一个系统,无论它们差异如何,其深层结构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7]通过他的分析,他证明了包括行为和思想在内的结构模式对所有社会都是普遍的,并拒绝了原始和现代意识的概念,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智力潜能。[7]
坎贝尔的英雄模式,与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理论、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有相似之处,但以上两位人类学家是从各自的田野调查观察之后形成的结论。阿诺尔德·范热内普提出“过渡仪式”,认为所有的通过仪式“转换仪式”都有着标示性的三个阶段:分离(separation)阶段、边缘(margin)阶段/阈限阶段和结合(communitas)阶段。特纳所提出的“阈限”概念更是广为人们所知。
而坎贝尔更多是从诸多类型的神话中比较、分析得出的共性总结,是偏重从神话学、心理学角度对神话功能进行的学理读解。他认为:“一旦神话的诗歌被诠释成传记、历史或科学,它就被谋杀了。栩栩如僧的意象变成遥远时空中的冷漠事实。此外,要以科学和历史证明神化的荒谬绝不困难。当文明开始以这种方式重新诠释神化时,生活便从神话中脱离出来,庙堂变成博物馆,这两个观点之间的关联也因此被消解掉了”。[4](155)坎贝尔通过他的导师海因希里·基莫讲述神话后获得了一种看待神话的态度——神话不是古人抽象的理论抑或离奇的信仰,它们其实是理解如何生活的实用模型。
根据道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开始和结束是一个周期。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阿兹特克人拥有水、土、空气和火的四种元素,而中国人拥有金、木、水、火和土的五种元素。这里有一个从三到五的光谱,我们可以在连续体中加两个。基于“地”与“天”之间的通道,在中国《尚书》和《国语》中“绝地天通”的故事,在宇宙的开始,每一个古人可以从地球,到达天堂,意味着,人人萨满时代,古人谁都能上天堂,无论何时何地。但传奇的颛顼帝王让他的大臣钟和离阻止这样的连接,和他任命的五名官员负责各自天、地、人、神和世俗生活。从此,人和神被分为不同的种类,由不同的工作人员统治。萨满被象征性地看作“专家”,在造成分裂或统一中国总扮演了某种角色,[8](237-247)他们的功能,也与位数一般为代表值为0或1的二进制工作原理雷同:绝地天通。
启程:放弃当前的处境,进入历险的领域;
三、 北方三少民族的萨满实践模式
对于英雄模式,他做出如下总结;“英雄跨越门槛的旅程,是通过陌生但却异常亲切的力量所造成的世界,有些会深刻威胁他(试炼),有些则会为他提供神奇的助力(救援者)。但他达到神话循环的最低点时,他将经历极致的痛苦并得到报偿。这种胜利可能表现为英雄与世界神母的交合(神圣婚姻),被天父兼创世者认可(与天父和解),以及他自己的神圣化(神化)来呈现。或者如果力量依然对他不友好,他就盗取他为之而来的恩赐(偷走新娘、盗取火种)。本质上,这是意识的扩展,以及随之而来存在的扩展(启示、变形、自由)。最后的任务是回归。
三少民族 祖先神 崇拜神灵鄂伦春族 ajoro Borkhan 莫昆或氏族的主神鄂温克族 hojoor 各氏族均有自己舍卧克(古老祖先)达斡尔族 hojor Barkhan 莫昆崇拜的主神
在《达尔斡族斡米南文化的观察与思考:以沃菊芬的仪式为例》中,有学者指出:“所有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祖先神崇拜的哈拉和莫昆(水平接近一个氏族)。”[9](204) 一般来说,他们认识到这些祖先神Hojor ,Barkhan。Hojor这个词来自达斡尔语意,Barkhan 是上帝的意思。[9](204)如图所示:
为便于分析,把职前教师解决数据分析问题中出现的认知错误类型分成两类:本原性错误和非本原性错误.前者主要包括数学概念理解错误和数学推理错误,而后者主要指计算错误、表征错误等不涉及数据分析本质属性的错误.从3个问题的答题情况看,存在认知错误的答卷占比46.67%,其中86.36%的认知错误属于本原性认知错误,以问题1为例,具体分析见表4.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都以哈拉或莫昆为单位供祭自己的祖先神。一般而言,在几个民族中,这种哈拉或莫昆的祖先神被成为hojor Barkhan ,其中hojodor 的意思是“根”,引申为“祖先”,Barkhan 为“神”。鄂温克人的氏族祖先神多是被雷击死的先人灵魂造成的。鄂温克人认为:人被雷击死是出于天意,而天的旨意是非常神圣的,因此死于天意的人其灵魂也非常圣洁。所以他们把有这样灵魂的人为氏族祖先神,并加以供祭。那些可以变成祖先神的还包括:鄂温克旗的保护神舍卧克,来自蛇和其他自然神的一个巫师的祖先;如祖先萨满来挑的自己的接班人。巫祖即祖先神,是这些民族祖先信仰的突出特点,是这些民族萨满教信仰对象的一个重要类别。
不同类型的规划服务于不同社会问题和规划问题,表现在规划目标、任务内容和功能均不同,即规划目标指标、影响因素不同。对其进行了梳理,汇总于表1,为在开展不同规划水资源论证时,有效建立规划与水资源论证内容的关系提供参考。
针对知识集成的目标,整理规范规程体系中的经验或者理论知识,构建煤矿安全动态诊断的专家知识库。主要建设工作包括:
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萨满生成,与坎贝尔的英雄原型的英雄,内在相通。二者都经过一个周期的分离、秘密知识的传输,之后返回所在社区服务。那些即将成为萨满的人们在为治愈向萨满寻求帮助,获得了专门传播给他们的秘密知识后,通过仪式获得了完整的萨满资格。他们通过解决问题、治疗疾病和带来其他利益而转变为为人们服务。
鄂伦春族人,曾是密林覆盖大兴安岭区域的优秀猎手。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政府要求他们以环保的名义放弃枪支。由于枪支携带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被视为比物质层面更加具有象征性和心理性的重大失落。前几年有一个表演展示了纪念放弃枪支的那一刻,演员和观众同时热泪盈眶。
从和谐美学来看,当代美学教育应把握“和”的官方与民间的符意共构,引导学生辨析并区别同与异的人伦关系,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在自我与他者关系中考虑生存的意义,培养他们对他者的宽容与理解品质,并意识到个体的生存存在于共在中。
这种精神之旅通常被描述为以痛苦的疾病的开始,找到主人并许愿、经过仪式、学习过程、再为氏族服务,其心理模式与坎贝尔的完全一致:主人公离开尘世,踏上冒险之旅,获得知识,回到原属社区。三少民族的萨满生成即是此模式的证明。然而,有些细节值得一提:
萨满生成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是来自外部力量。例如,达斡尔族萨满斯琴卦认为:成为萨满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许多人年纪轻轻就体弱多病,没有人能治疗他们。他们不得不寻求从萨满处连接曾许诺的祖先神,病人会成为萨满或得到帮助,祖先神灵承诺其成为一个萨满或为其愈疗。[11](22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者曾在访谈中问及鄂温克族萨满沃菊芬如何传承萨满文化,对方回答:“这不是传承的事;神抓了谁就是谁。你也死不成,这是一种使命。[11](25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会要忠诚党的事业,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把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落实到广大职工群众中去;要把执行党的意志的坚定性和为职工服务的实效性统一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到工会各项工作中去,把党的意志和主张落实到广大职工中去。这些重要指示,明确了工会工作的政治定位和工会组织的政治属性,为做好新时代工会工作指明了正确政治方向。各级工会要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根本政治原则,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信息传递的保密性。笔者同意许多学者所持的观点:梦境传承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30 年间斯琴卦患病期间,她反复做同样的梦:一位老人前去看望她。无论唤起神灵或是治疗疾病的经历、技术手段,都是通过梦境实现的。这并非孤例,在诸多萨满口述史中都有涉及。
恰如坎贝尔的英雄原型所示,历经各种身体体验的试炼,鄂伦春族尼山萨满的灵魂无所不在,萨满将克服各种各样的身体试炼,由救人性命到治愈疾病,灵魂将克服所有物理界限,会飞升或向下。
四、讨论
通过对中国北方三少民族的生成过程进行梳理,结合坎贝尔神话理论中的英雄模式,二者互相印证。坎贝尔提出的“启程-传授奥秘-归来”与“成为萨满-习得知识-解决问题”内在相通,英雄得到召唤、发现自我意识、发现神性的心灵之旅,是坎贝尔理论的根基所在,也是萨满必经的心路历程。该模式与萨满通过“突发疾病、知识获取的异常体验、解决问题”之间,存在维特根斯坦所提到的“家族相似性”,值得进一步分析。坎贝尔的理论强调英雄的自我发现和超自然援助的精神之旅,它从理论上呼应着萨满通过仪式的迷幻体验。英雄意识到召唤,踏上精神之旅,通过试炼获得了部分心理经验,与感到“神圣病痛”、心理上肢解成为萨满,同属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在此,人类深层心理的一致性成为连接西方与东方学术的共同纽带,由此它被赋予超文化内涵。“东学西学,其心莜同,南海北海,道术未裂”。
考虑到坎贝尔在印度的经历和他对梵文的钻研,他的原型英雄应是平行对应的男萨满或女萨满,生活在一个“东方社会”并不奇怪。笔者并不急于发表一个关于这种“家族相似性”[12]的陈述,从而得出一个判断结论。格尔茨拒绝在普世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站在一边,宁愿致力于“浓描”。[12]在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思想、正确把握自己的立场之前,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田野,提出更多的“浓描”。
注释:
①According to Mihály Hoppál and Lajos Nádorfi, with a population as many as 985 528(2010), the Saha are also known as Yakut who speak a language that belongs to the Turkic branch of the Altaic family. Cf. Mihály Hoppál and Lajos Nádorfi,2016, Shamans, Images and Rituals, p. 30. Budapest:Hungarian Academy of Arts.
实验组症状缓解的患者有48例,治疗缓解有效率为96.0%;对照组症状缓解的患者有40例,治疗缓解有效率为87.0%,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缓解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18,P=0.218)。详见表1。
②英文原文如下:“Unlike the Mongols, the Ewenki are not so resilient in restructuring their emotion and relocating moral authority. Both time and space are short for them. They are not yet prepared for change while the spaces in mountains and forests,where they could have substantialized their emotions by finding gods ji or reconstructing some, have been disturbed and re-attributed by the marketing process empowered from outside. ” 《Emotion Gets Lost: An Ewenki Case》Mongolia and Inner Asia Studies Unit Occasional Papers (Volume 1, Number 1, 1996)
参考文献:
[1](美)Cristopher Vogler.作家之旅:源自神话的写作要义[M].第三版,第二版前言。
[2]孟慧英.萨满医术:北方民族精神病学[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1.
[3]郭淑云.中国萨满教若干问题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1(3)
[4] (美)约瑟夫·坎贝尔著. 朱侃如译, 千面英雄[M].金城出版社, 2012.2.
[5]Joseph Campbell, 200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Third Edition, p. 211. Novato,California: New World Library.
[6]Joseph Campbell, 200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 224.
[7]http://www.philosophers.co.uk/claude-levistrauss.html,accessed on April 24, 2017.
[8]Naran Bilik, 2015,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 Potentials for Our Future, pp. 237-247. Dagmar Eigner & Jüren Kremer (eds), Kathmandu:Vajra Books.
[9]萨敏娜 吴凤玲.达尔斡族斡米南文化的观察与思考:以沃菊芬的仪式为例[M].民族出版社,2011,
[10]关小云 王宏刚 编著.鄂伦春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M].民族出版社, 2010.9.
[11]Ding Shiqing and Sain-tana, 2011,Investigation into the Shamanic Heritage among the Daur (Dawoer zu saman wenhua yicun diaocha), p. 223,Beijing: The Minzu Press.
[12]Clifford Geertz, Available Light: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e Making of Shaman among the Three Northern Minorities in China and the Study of the Hero’s Theme
LU Fangf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CASS Beijing 200433)
Abstract: After briefly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three small Altaic language speaking minorities in North China, the Daur, the Evenk, and the Oroqen, who are well known for their shamanic practices both in the past and at present, I compare their shaman-making processes with an eye to the Hero’s theme developed by Joseph Campbell in his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I argue that there is a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ampbell’s processual model of departure - initiation - the ultimate boon and that of Transformation into a shaman - Knowledge acquisition - problem solving among the three small minorities in North China. While the core of Campbell’s theory centers on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hero’s self-discovery and receiving supernatural aid, it parallels with the psychedelic path that a shaman must go through at a rite held for the occasion. Psychic unity of the human kind is a common tie that binds the scholarship of the West and the East. Despite diversified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local features, there is a metaconnection that overrides all these traits.
I believe that such comparison is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hamanic studies in China and can possibly shed a new light on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deadlock in theoretic study of shamanism in China. No doubt, all this has to rely on ethnographic ‘thick description’ and intense theoretic discussion.
Key words: three small minorities;shamanic;hero’s self-discovery ;
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19)03-124-06
收稿日期:2019-08-30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批准号 17ZDA152)论文之一。
作者简介:卢芳芳(1982-),女,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责任编辑 黄隽瑾】
标签:萨满论文; 坎贝尔论文; 鄂温克族论文; 达斡尔族论文; 英雄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批准号17ZDA152)论文之一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