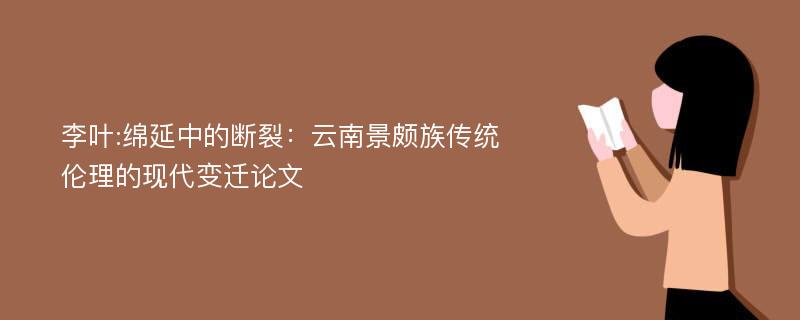
摘 要:云南景颇族传统伦理与其原始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原始宗教信仰作为景颇族传统伦理绝对、至高的外在他律,赋予景颇族传统伦理在社会道德实践过程具有神圣的权威,从而对景颇族传统社会进行有效规范与控制。景颇族原始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之变化,自然也影响着景颇族传统伦理的现代变迁,并主要以传统的整体绵延与局部断裂为主要变迁形式,具体反映在景颇族传统伦理与鬼、神、人的三维关系之中。
关键词:绵延;断裂;景颇族;传统伦理;现代变迁
云南景颇族传统伦理,是指基于原始鬼魂崇拜的观念架构,并以氏族——部落的血缘群体关系为社会依托,建构起来的一套带有鲜明景颇族民族特性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体系。由于景颇族传统伦理本身就以全民性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为基质,而“原始人的宗教信仰不但是整个人类宗教的发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形式的源泉。”[1]因此,景颇族传统伦理不可避免地天然携带着原始宗教的文化因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将景颇族的传统伦理视为原始宗教伦理在景颇族原始社会生活中的延展与泛化。
在初民社会中,不仅伦理与宗教没有明确的概念分割,而且 “宗教与道德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相反,在原始人类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生活的认识尚未获得充分自律的情况下,原始道德与原始宗教几乎无法区分。”[2]换而言之,即景颇族先民所信仰的原始宗教与原始道德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难以割裂、混而为一的紧密联系。由此,对于尚处于原始氏族——部落时期,且并未形成成熟、系统的抽象思维的传统景颇族而言,其传统伦理与原始道德实践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也难以区分,两者几乎合二为一、互相融合、彼此渗透,共同维系着景颇族传统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维关系,并具体通过风俗习惯、宗教仪礼、文学艺术、禁忌规避、习惯法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与表达。
原始宗教作为景颇族传统伦理与道德的意义根据,实则也是传统伦理得以走向原始道德实践的神圣可能与保障。因此,景颇族传统伦理的现代变迁主要讨论的是在社会生存方式发生变迁的过程,随着原始宗教的逐渐抽离,景颇族传统伦理是如何在新的社会文化生态之中找到平衡的驻点,在延续传统意义表达的同时适应新的道德诉求,进而发挥道德效用。而原始宗教在景颇族传统伦理中的抽离则具体表现为“鬼”、神、人三者在其传统伦理与道德实践中的功能与地位变迁。因此,围绕景颇族传统伦理与“鬼”、神、人的三维关系来展开论述,足以一窥景颇族传统伦理的现代变迁之状貌。
景颇族先民经漫长而艰辛的南迁之旅,最终逐渐定居于地势陡峻、山川纵横、河谷相间的高海拔山区或半山区,据史料所载“但山则悬崖峭壁,河则黑水弱流。遥见隔崖,粉墙庐舍,俨然车马往来,而世莫能通焉。亦不知为何地也。”①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生产资料严重匮乏,景颇族先民时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严酷的环境是宗教信仰产生的基础……”[3]帮助景颇族先民突破困境、拯救自我的原始宗教应运而生。景颇族全民所信仰的原始宗教认为万物皆有鬼魂,除人之外,自然界的草木山石、日月星辰等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鬼魂,如山鬼、树鬼、风鬼、雷鬼、虹鬼、太阳鬼、月亮鬼等。而信仰乃是指“特定社会文化群体和生活于该社群文化下的个体,基于一种共同价值目标期待之基础上,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4]因此,初民社会中的每一个景颇族,犹如基因遗传一般,从一出生开始便已分有着原始鬼魂观,并成为他们认识并解释自然、社会的知识储备库。不言而喻,纷繁多样的“鬼”自然也就成了景颇族传统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要素。由此,作为长期在这一文化生态中协调各种关系以凝聚血缘群体的经验性积累与沉淀的传统伦理,又怎会不给“鬼”留有一席。
一、传统伦理与“鬼”
景颇族传统伦理孕育于氏族——部落时期,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是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下,人们维持自身生存消费的能力也越低下,人口生产的水平和质量也低下,而对自然的依赖和畏惧则随之增大。”[5]由此,人与自然之间就形成了一股张力,张力越大,人就越无力把握自己的行为,从而越依赖于自然,甚至是臣服于自然,最终便只能诉诸于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对自然、图腾、祖先的崇拜以及禁忌的规避中寻求自我表达、掌控自身行为,以缓解自然施与的压迫感。由此,在景颇族先民对“自身行为向规范化发展的感知和意识”[6]尚未明晰与成熟之时,“鬼”作为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具象化代表就成了规范氏族血缘群间的权利与义务,指导人们进行善恶判断、行为选择,协调社会关系的权威依据。因此,景颇族传统伦理是以“鬼”作为绝对、神圣的外在他律来实现道德实践,维持社会秩序,而过度关注生存需求以期从自然界获得充足物质保障的景颇族先民,则更多的是被动服从且完全依赖这一神圣他律,个体性的主体价值完全湮没于“鬼”所统摄的与生俱来、别无选择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这在景颇族家庭伦理、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生态伦理之中皆有体现。
(一)家庭伦理
民族传统家庭伦理指的是 “各民族过去发生的、一以贯之的、在现实家庭生活中仍发生作用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7]不言而喻,景颇族传统伦理中的家庭伦理就是代代沿传下来,在景颇族传统家庭生活之中“调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8]具体包括夫妻间的伦理关系、父母与子女间的伦理关系、邻里之间的伦理关系。
3.邻里之间的伦理关系
第一,恋爱自由,婚姻包办。景颇族地区传统的婚恋方式是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景颇族传统社会中的男女青年一般在十六七岁就能开始恋爱,每家都会为达到婚恋年龄的女儿单独准备一间房,以方便自家女儿与到访男青年接触与交流,同时每个村寨都设有专供景颇族男女青年 “干脱总”②的公房。在“干脱总”过程中,全村寨的男女青年同居一室,通过对唱情歌、玩游戏等方式来增进了解,以确定心仪对象,若彼此互有好感,则进一步发展;若姑娘不回应,男方就会主动放弃,绝不强求。景颇族男女青年在恋爱之时,享有很大自由,但不能未婚先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被视为触犯了女方所在村寨的“鬼”,是不吉利的,男方家必须杀牛“洗寨”,即祭献女方村寨的“鬼”以求得“鬼”的宽恕,如此方能得到女方村寨中的村民的谅解。相对于婚前恋爱的自由,传统社会的景颇族婚姻则几乎没有自由可言,主要由父母包办,父母往往通过指腹为婚和买卖婚来为子女选定结婚对象,子女到结婚年龄就遵照父母的意愿,与父母选定的对象完婚。
第二,“血不倒流”。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景颇族传统社会,舅权制发挥着重要作用。景颇族传统婚恋严格恪守“血不能倒流”的信条,即“姑母家男子必须娶舅家女子为妻,但舅家男子绝不能娶姑母家女子”[9],“姑爷种”、“丈人种”之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姑家三代以内的所有亲戚都是“姑爷种”,与之相对的则是舅家三代以内的所有亲戚皆为“丈人种”。同时,姨表婚也是被禁止的。因此,无论是在日常生产生活及节庆活动中,或者是在“干脱总”的过程中,“丈人种”一方的小伙子是不允许对“姑爷种”一方的姑娘乱开玩笑、嬉戏调情的,姨表关系间的男女青年亦是如此,否则将被视为不合礼节。此外,景颇族传统社会认为“同姓之内,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绝对禁止发生婚姻关系”[10]若有违反,将在山官和董萨的主持下,按照习惯法接受严厉惩罚。无论是礼节,还是习惯法,其合法性都由“鬼”来赋予的。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老师讲,学生听,学生预习听课复习考试的过程,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授课工作。研究组合理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采用PBL理念,分为三段式教学模式,其中分为设问、讨论、总结,5人为1组,推选1名组长进行讨论以及记录过程[3]。具体措施如下。
(2)气孔 气孔是指在焊接过程中,电弧周围的空气、母材和焊材表面的杂质燃烧分解产生的气体溶在熔池中,且在熔化金属冷却前未能及时逸出而残留在焊缝中形成的孔穴。
在父母包办的婚姻中,无论是指腹为婚,还是买卖婚,其实质都是一种婚姻交易,都是通过对女性进行估价,以判定其大致能与多少头牛的价值相等。同时,在景颇族传统婚姻中实行的“转房制”、“妻姊妹婚”都是将女性作为一种财产来进行 “转让”。丈夫去世的年轻女子,不得外嫁,因夫家之前已经付过聘礼,女子就相当于变成了夫家的私有财产,并且董萨已经将女子的“鬼”念到了夫家,所以只能转嫁给夫家的哥哥或弟弟,甚至丧偶的年轻侄媳妇也会被转嫁给夫家的叔伯。若妻子去世,而妻妹又尚未出嫁,则必须嫁给自己的姐夫。
此外,笔者还利用中国知网(CNKI)的检索发现,截至2014年4月,以“生态文明”为篇名的检索结果有23556篇,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为篇名的文献检索结果有182篇。通过文献数量可以发现,研究生态文明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针对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对照教材,可将所需文字、图片等内容通过手动计算机编辑和拍照、摄像等方式保存为电子资料,利用powerpoint软件完成内容编排。结合EV录屏录屏软件,可支持选区录制、插入多摄像头并添加多种图片、文字内容,可在线直播,也可通过窗口穿透预览录制内容,且画面不受干扰。
2.父母与子女间的伦理关系
伦理是“人类完善发展自身的活动。”[31]体现着人的个体内在需求。同时,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是社会客观需求的表达。由此,伦理兼具有内在主体性与外在他律性,在社会道德实践中,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运行需求的变化常会引起两者间的关系调整。
幼子继承制是景颇族传统伦理中“爱幼”的重要体现。长子结婚以后就分家独立出去,父母则一直跟随幼子生活,父母去世之后,财产主要由幼子继承,幼子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与责任。而父母早亡的孩子则会得到同一宗族家庭的抚养。因此,在景颇族传统社会,很少出现老无所养,幼无所教的情况。此外,景颇族传统家庭十分重视子嗣传承,如果某一家没有儿子,那么就被认为是没了后人,这也是与父系氏族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紧密相连的。
1.夫妻间的伦理关系
处于原始社会早期的景颇族先民主要以采集、狩猎、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生产,对自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血缘群体只有通过互助协作才能获得生存所需。因此,邻里之间形成了农忙或有事的时候就互相帮忙,农闲的时候互相串门,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若遇到像婚丧嫁娶、起房建屋、拉事复仇这样的大事,则整个村寨的人都要来帮忙。由于担心自家有事没人来帮忙,所以没有人敢坏了这样的规矩。既然邻里之间需要互助协作,那么和睦相处就是必不可少的。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并非指的是从不产生摩擦与纠纷,而是产生纠纷时,经村里山官、德高望重的老人、董萨的调解协商结束之后,当场喝酒以示重归于好,双方都不可再提。
景颇族传统的家庭伦理看似与“鬼”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主要是依靠习俗惯制来维持和规范着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整个村寨之间的关系。然而,正是“鬼”使这些口耳相传的习俗获得了合法性与有效性,“鬼”或直接,或间接都全程参与了景颇族传统家庭的构建,就连判定一对新人是否为真正的合法夫妻,主要是通过繁琐习俗规范背后的“鬼”的认可,如结婚时要将新娘的“鬼”以及新娘娘家的“鬼”念到新郎家,并告知自家“家堂鬼”,新娘才能真正算得上是新郎家的人,才会得到“家堂鬼”的庇佑。换而言之,未经“鬼”认可的家庭是不能称之为家庭的。“鬼”将景颇族先民现实的道德诉求与理想的伦理观念连接起来,无力把握自己的景颇族先民依附于这一神圣力量,来获取世俗道德实践的可能性。
(10)状态10(t8~t9):在t8时刻,uC1减小至零,此刻开通S1,可实现零电压开通.从t8时刻开始,Lr释放剩余电能,iLr处于恒速减小状态,iLr在t9时刻变化为零时,关断Sa4,可实现零电流关断,本状态结束.然后电路返回状态1,进入下一个开关周期的工作.
(二)政治伦理
景颇族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是伴随着山官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社会规范体系。由于山官制度产生于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的原始社会末期,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因此,景颇族传统政治伦理既有民主性,又有专制性。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采取简易计税方法,即应纳增值税税额=不含税销售额×税率。为了更好地分析“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影响,现做以下前提假设:假设1,企业的应税销售额为R,成本为C且企业“营改增”前后销售额保持不变;假设2:“营改增”前后企业不存在混合销售及兼营行为,即“营改增”前企业就其应税行为缴纳营业税,“营改增”后企业就其应税行为缴纳增值税;假设3:企业不存在营业外收入与营业外支出,仅就其销售收入、成本与相关税费计算其所得。表1为适用3%征收率的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化情况,表2为“营改增”前后适用5%征收率的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变动情况。
所谓民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最开始的山官一般是由选举产生,至少在景颇族的民间传说中是如此。另一方面,指在决定辖区事务之时,山官“必须与辖区内的‘苏温’④、老人、大‘董萨’等组成领导核心,尊重本民族的习惯法,按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12]同时,山官还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保护辖区内百姓不被其他村寨欺负,为辖区内百姓调解纠纷,组织祭祀与生产,“招待客人食宿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孤寡的生活”[13]等。专制性则主要体现在山官作为某一区域的最高政治、军事领袖,享有一定的阶级特权。如辖区内的百姓每年都要去山官家义务帮工几天,要祭献山官家的家堂鬼,“百姓杀牛祭神或猎获野兽时,必须送一条后腿给山官”[14]。同时,山官与百姓间有着较为严格的等级界限。官种高于百姓,官种只与官种婚配,百姓不能娶山官家的女儿。但这种“等级内婚”也并不是绝对的,一些没落的山官也会将女儿嫁给百姓。
此外,景颇族传统政治伦理并不一味提倡百姓对山官的服从,还提倡自由反抗。如果山官没有德行,欺压剥削辖区百姓,那么百姓是可以废除山官的。这体现在景颇族民间传说之中,如《山官发火》讲的就是百姓阶层的孤儿变成山官,山官变成奴隶的故事。在景颇族传统社会也的确会出现村寨内的百姓,重新推选山官的现象。而影响最大的,则要属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借“鬼”之名推翻山官制度的“贡龙”⑤起义,也正是“鬼”的意志的介入,才使这次起义变得名正言顺。
(三)制度伦理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5]顾名思义,制度伦理则是这些制约得以设立的原则与规范。景颇族传统社会的制度伦理,主要蕴含在习俗、习惯法、禁忌之中,从而以道德实践的方式实现“法”的表达。
各个接头做无缝处理。先进行侧墙顶部和底部的碳纤维布粘贴,粘贴完成后在外侧进行碳纤维布环形箍的粘贴,碳纤维布环形箍在侧墙外侧底部重叠后,在外侧采用不锈钢压条和膨胀螺栓进行加固。
景颇族传统习俗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祭鬼,是景颇族生产、生活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习俗,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先祭“鬼”,出远门要祭“鬼”,上山烧地之前要祭“鬼”,春耕秋收也要祭“鬼”,就连喝酒的时候都要用手指蘸酒祭“鬼”,祭“鬼”几乎贯穿于所有习俗之中。除此之外,景颇族传统习俗还有:
“吃白食”,亦即在景颇族村寨,你可以在走进任何一家去吃饭,主人都会热情招待,绝不会让客人饿着离开。即使贫困百姓走到山官家,山官也必须好好招待。
数学的产生,来源于实践和科学实验,反过来为其服务,并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不断发展提高。君子教育理念下的智慧课堂,更强调学以致用。教师要依据学生个体差异,有的放矢,设计有弹性、开放性及不同层次的练习,让全体学生得到发展、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教师在此过程中要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以“礼貌”“睿智”的君子形象展示给学生,以耐心、诚恳的积极态度去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
(102)尖齿羽苔 Plagiochila pseudorenitens Schiffn.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
平均共享,在景颇族传统社会,主要表现在食物分配上,杀牲献鬼之后,要请全村寨的人一起分享祭献所宰杀的鸡、牛等,狩猎所得,则是见着有份,平均分配。以酒待客,客人到访进门就要给客人敬上一杯进门酒,以示欢迎。走亲访友都要带着竹筒酒,景颇族男子随身携带的“筒帕”⑥里随时都要放着竹筒酒,遇人就递上一杯酒。
尊重私有财产,景颇族传统社会有“号地”的习俗,每到砍草烧地的时节,景颇族就会在自己看中的田地或提前砍光一片草地,或挖一条沟等作为记号,表示此地已所属他人,其他人看到标记也就不会去开垦。同样,被别人做过记号的树,其他人也不会去砍。不仅田地、树木,在景颇族村寨,只要是有人做过记号的东西,其他人都不会去拿,因为盗窃在景颇族传统社会要受到很严厉的惩罚,因此,真正可以称得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拉事”⑦,是景颇族传统社会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通常是因个人或家族之间的人命、债务、婚姻等纠纷经调解无效之后,整个村寨的人就一起到对方家里或对方村寨任意一家拉牛以作补偿和报复,因此,“拉事”经常演变和扩大为村寨与村寨之间,甚至是山官辖区⑧与辖区之间的冲突,某一群体内的扶弱抑强,最终变成了民族内部的以暴制暴。
习惯法作为法律与道德的混合体,“是维系和调整某一社会组织或群体及成员之间关系的习惯约束力量的总和,是由该组织或群体的成员出于维护生产和生活需要而约定俗成,适用于一定区域的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16]因此,它既有法律的强制性,又兼有道德的习惯性。景颇族习惯法又称“通德拉”是景颇族传统社会调解纠纷的重要依据,详细规定着惩罚或赔偿方式、赔偿数额等,主要调解“财产、土地、债务纠纷,凶杀、偷窃、奸淫、诬陷、劫牛、触犯禁忌等等。”[17]一般都是在山官、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董萨主持下,当事人经过协商,最终按习惯法的条例来执行。若依然无法解决,则诉诸于神判,主要通过闷水、捞开水锅等方式,借助“鬼”的意志来判定是非善恶,解决纠纷。
在脚手架施工工程管理中很多施工单位还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安全管理,采用的管理方法是传统的线性顺序法,这种方法不仅会延长施工工期,而且对施工安全管理没有太大的作用,管理人员只是根据硬性制度进行工作,没有形成安全管理的意识,对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禁忌是“一种原始民族对魔鬼力量信仰的表现和延伸”[18],是原始民族“道德和法的最初雏形”。[19]景颇族传统社会中禁忌在衣食住行等一切方面规范着景颇族的言行举止。如,不能随便出入别人家的“鬼门”,不能在别人家里久站不坐,不能从火塘上跨过去,别人家进新房的时候,不能说不吉利的话等等。同时,由于禁忌融于一切伦理体系,因此,“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一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20]从而,禁忌强化着其他伦理体系的道德实践效用。如景颇族禁忌中的,严禁同姓婚、姨表婚、“血倒流”,严禁在没有人去世的时候跳丧葬舞,严禁盗窃等,这些都与景颇族传统伦理中的其他内容相重合,禁忌则赋予了它们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制性。
(四)生态伦理
生态伦理,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与原则。生活在原始社会的景颇族先民并未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万物有灵观虽然的确孕育着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生命平等之意蕴,但他们的生态伦理更多的只是建基在面对自然的手足无措,畏惧自然,同时又依赖自然的无力感之上,与现代人的生态伦理有所区别。“对于现代人的“思维习惯来说,‘自然界’组成了一个不变的客观体系。但是,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界’是不存在的。社会集体把它周围的实在感觉成神秘的实在在这种实在中的一切不是受规律的支配,而是受神秘的联系和互渗的支配。”[21]因此,他们的生态伦理,更多的是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崇拜,仅在客观上,非常有限的程度上保护了生态。如景颇族传统伦理中禁止砍伐“能尚”附近的树木,以免触犯了庇佑村寨的“鬼”,给村民带来灾难。狩猎、烧地、砍树之前都要通过祭献,告知鬼灵。
不难看出,在人的主体自觉性十分欠缺的原始时期,人对自身行为的掌握只能借助于外力,而原始宗教则正好“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22]在帮助人们消解人与自然间的张力的同时,也为人类观念世界的构建提供着合理性依据。“原始的宗教形式,使人们朴素的道德观念转化成内心神秘的道德诫律,形成了对崇拜对象的道德敬畏心理情感,从而大大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关系。”[23]纵观景颇族传统伦理的整个体系,原始宗教中的“鬼”从未缺席任何一种伦理向道德实践转化的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多维关系,其根本上都是以景颇族先民对“鬼”的绝对服从来进行协调,这也是人的主体自觉意识对神圣集体主义的完全绝对依附。
二、传统伦理与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开始从缅甸传入景颇族地区,打破了景颇族原始宗教与景颇族传统文化之间的一致性。由于“宗教中无论任何方面,也无论任何信条,都不能没有其伦理方面的相配部分。”[24]因此,随着基督教在景颇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以至上神——上帝为核心的基督教伦理在景颇族社会社会中也逐渐争得生存空间,多元伦理在景颇族社会生活的参与,为景颇族的价值取向、道德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进而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动摇着“鬼”在景颇族传统伦理中的绝对控制,在群体共享价值基础上形成的集体向心力遭到削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景颇族个体自觉意识的萌生。同时,伴随着基督教在景颇族生产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加深,景颇族传统社会中的 “经济习惯、饮食、卫生习惯、婚姻家庭关系、集体互助精神、文化、教育”[25]等都发生了变迁,景颇族传统伦理的传播方式及表达手段或被改变,或被彻底切断,基督教宗教伦理在客观上促进景颇族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景颇族传统伦理体系发生断裂。
基督教传入景颇族地区之初,面对景颇族原始宗教在景颇族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采取了妥协的策略,主要通过施与恩惠的方式,如免费医治、分发礼物等以此来获得景颇族的认同。而在教义内容上则仅是在称呼上将景颇族原始宗教中的 “鬼”用“上帝”来代替,并未在内容上进行过多改动。这一时期,针对景颇族的陈俗陋习,基督教提出了十条教规“(一)不调戏妇女,不淫乱;(二)不说谎,不作伪证;(三)礼拜日要休息做礼拜;(四)不偷盗;(五)不杀人;(六)不抽烟,不饮酒;(七)不跳民族民间舞蹈,不唱山歌;(八)靠拢支持传教人,并协助传教;(九)尊敬父母,守国法;(十)爱人如已,互相帮助,不可嫉妒。”[26]由此,以基督教信仰体系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开始在景颇族地区推行,但由于信教人数较少且不稳定,其规范性与约束性仅在较小区域内有效,景颇族传统伦理依然具有普遍性,发挥着指导和管理景颇族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
然而,由于景颇族原始宗教所赖于生存的氏族——部落社会渐趋衰落与瓦解,加之,基督教的强势入侵,并随之在景颇族地区不断发展、壮大,景颇族原始宗教的滞后性日益凸显,进而逐渐丧失了“基于宇宙论的世界论说的有效性,丧失了对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的社会法权,丧失了为社会的沟通语义系统提供元叙述的能力。”[27]作为原始宗教与道德混合体的景颇族传统伦理,自然也就开始丧失对景颇族现实世界的普遍性控制力。与此同时,基督教在景颇族地区推行的教规戒律的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景颇族生产生活领域的渗透也越来越广泛。如十条戒律里的“不调戏妇女,不淫乱”、“不说谎,不作伪证”、“不偷盗”、“不杀人”以及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这些教规皆因具有上帝的权威,由此,便在信教景颇族群体之中同样具有了法的效力,规范和引导着信教景颇族的社会行为。从而出现景颇族传统伦理与基督教宗教伦理“分而治之”社会文化局面。
此外,景颇族传统伦理教育主要依靠言传身教,董萨在各种祭献活动中的祭词,各种节庆活动中的舞蹈、歌曲等,都是景颇族传统伦理的表达与传播方式。比如在婚嫁祭词中有对“丈人种”与“姑爷种”婚嫁礼俗的叙述“远古从宁贯杜娶龙女开始,就有了丈人种家,就有了姑爷种家。丈人种家女儿,嫁给姑爷家儿子,姑爷家儿子,娶丈人家女儿。”[28]在景颇族的大型祭祀活动目瑙纵戈中董萨所诵念的景颇族的创世史诗——目瑙斋瓦,其中包含着景颇族一切伦理规范的起源与发展。同时,由集体歌舞所带来的“欢乐的感受总是与道德的赞许行为联系在一起。”[29]然而,基督教宗教伦理中的诸多内容,如不允许祭鬼,也不能参与祭鬼活动,只能进行礼拜祷告;不允许抽烟、喝酒;不允许唱山歌,跳民族舞等,都是在为景颇族改风易俗的同时,改变着景颇族传统伦理言传身教的教育模式,进而切断传统伦理的传播途径,导致口耳相传、代代相沿的景颇族传统伦理出现断裂。
完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中国图书的知识产权,严厉打击国外盗版和非法渠道。制定激励企业出口的相关优惠政策,扶持出口企业的发展。
第三,男尊女卑。传统景颇族家庭一般都实行一夫一妻制,男性在家里及家族里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女性,家庭事务由男性决定,同时也享有参与家族事务的权利。女性除了要分担大部分生产劳动之外,还要承担全部家务,而男性则从不做女性的事情,否则将被人取笑。结婚过后,男性依然可以出去“串姑娘”,但不能与已婚妇女私通。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之科技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民族地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在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32]云南景颇族地区也被动地卷入了全球性的多元文化竞争与交流之中,并对景颇族社会的公共价值与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挑战着景颇族传统伦理的绝对化、神圣化,从而使群体性的价值取向丧失力量支撑,景颇族个体从传统伦理的“绝对”控制中挣脱出来,获得个体自觉意识与主体价值,并反过来对传统伦理进行着挑拣,以建构“正合时宜”的普适性的公共准则与规范。景颇族传统伦理中有诸多内容都是具有普适性的,如团结互助、友好睦邻、以礼相待、自由平等、尊重私有、扶弱济贫,再如习惯法中对婚外通奸的禁止、对赡养父母的规定以及传统伦理中所蕴含的万物平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等都与我国当前的社会道德建设内容相契合,并且能够以一种先天的习惯力量来推动着社会道德的建设。这既是景颇族传统伦理与社会的适应,同时也是景颇族个体从被动服从向主动选择的具体体现。
三、传统伦理与人
尊老爱幼在景颇族传统伦理的重要内容。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老人掌握着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而家庭教育又是重要的教育模式,从而也就决定了老人在景颇族传统社会的重要地位。子女、晚辈在父母、长辈面前要十分恭敬,家里的大小事务都要征得家里老人的同意,无论外出劳动还是走村串寨都要告知老人,而家族事务则主要由山官、董萨和有威望的老人来主持和处理。日常吃饭、喝酒、嚼烟等都要先给在场的老人,上座都是留给老人的,年轻人不得随便坐。景颇族传统伦理中对老人的尊重,在丧葬习俗中体现的较为明显。景颇族村寨的老人去世,葬礼都比较隆重,“凡是有子孙的年长者死,都要跳丧葬舞。”[11]若死者为村寨中德高望重、儿孙满堂的老人,附近各村寨的人都会来送葬,除了跳丧葬舞之外,还要在送魂的时候跳专门的“金再再”。③此外,无人照顾的孤寡老人由血缘宗亲赡养。
景颇族传统伦理与人的关系,指的是人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价值需求与传统伦理的群体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景颇族传统伦理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一直贯穿于传统伦理与“鬼”、传统伦理与神的关系之中,但受所处的群体血缘的氏族——部落社会结构限制,人的主体价值需求一直服从于“鬼”的神圣性控制下整体主义价值取向。即使在基督教宗教伦理与传统伦理“分而治之”的原始社会末期到“文革”前这一时期,景颇族的主体意识虽有苏醒,但依然未能挣脱群体需求的制约,相反“鬼”与神对根源于传统伦理的民族道德的共同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强化着传统伦理所蕴含的整体意识。简而言之,从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到“文革”开始之前,人的内在主体性都是服从于神圣化、绝对化的外在他律性。
基督教宗教伦理并非完全否定景颇族的传统伦理,景颇族传统伦理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共享、互助协作、尊老爱幼、尊重私有等内容都是为基督教宗教伦理所推崇和认可的,并将诸如此类的宗教色彩较淡的伦理规范列入了教规之中,从而使原本由“鬼”赋予合法性与神圣性的行为规范,同时也被赋予了上帝意志。“一般的生活习俗经过民族群体的整体评价和指引,会把其中某些部分演变上升成民德,特别严格的民德也就固定为民族禁忌,这样从一般社会习俗到民德,再到禁忌的认识、评价、遵守、传承等过程,实现了对民族的制约作用。”[30]因此,经过非信教群体与信教群体共同认可的伦理规范,则自然成为了景颇族社会中的公共道德与准则,并以民族道德的形式在景颇族社会中保留与延续。此外,基督教传入景颇族地区之后,为景颇族创制了文字,文字的出现使原本口耳相传的景颇族传统伦理道德得以记述,从而使其更具系统性与规范性,有益于保存与传承。
景颇族个体对传统伦理的选择是从当代的社会需求出发,由此,自然要对传统伦理所赖于存在的合理性根据进行新的阐释与注解。虽然对景颇族传统伦理起到了“祛魅”的作用,将传统伦理中的落后因素进行了剔除,如杀牲献鬼、宗教禁忌、习惯法中的神判等,但是这也切断了传统伦理的传播途径,掐断了景颇族传统伦理传承的外在可能。同时,也使景颇族传统伦理丢失其文化意蕴,失去原有文化内涵的传统伦理,也就丧失了传承的内在动因。由此,外在约束力,内在凝聚力都遭到破坏的景颇族传统伦理,在景颇族年轻一代人群中的认同感也大为削弱,从而出现传承主体的断裂。
景颇族传统伦理与“鬼”、神、人的三维关系,最为直观地反映出在景颇族社会生存方式发生变迁的过程,随着原始宗教在景颇族社会中的元叙述能力的丧失,景颇族传统伦理的社会控制力与约束力由“绝对”到相对的转变。相伴而来的则是个体主体意识与价值观念对整体价值目标的依附性逐渐减弱,人从被动接受与服从转向了主动选择,转而从个体道德需求出发来思量、判断传统伦理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自觉建构“正合时宜”的新的社会伦理。而这些新建构起来的社会伦理,也并非是完全外来的,对景颇族传统伦理的彻底否定与摧毁,而是立足整个景颇族群体所共享的民族道德之上的,以寻求传统伦理与新的社会生存方式之间的契合点、平衡点,形成公共领域的共享准则。
不得不提的是,基督教宗教伦理在景颇族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建构公共道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作为西方现代文化重要代表的基督教宗教伦理既有现代社会的文化因子,同时又在与景颇族传统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吸收了景颇族传统伦理的要素,从而当景颇族由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之时,由于基督教宗教伦理在公共领域道德建设的前期铺垫,使景颇族并未遭遇毁灭性的文化震惊,进而造成传统的彻底断裂。由此,云南景颇族传统伦理方能在社会生存方式产生重大变迁的过程中,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过渡,在绵延中发生断裂。
注释:
①参见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
②亦叫“串姑娘”,男女青年在一起喝酒聊天、唱歌跳舞、谈情说爱.
③一种送魂、驱鬼的舞蹈。
③施工期间槽内泥浆必须高于地下水水位1.0 m以上,且不低于导墙面0.5 m,当发生泥浆渗漏时必须及时堵漏和补浆。
④各村寨的头人,笔者注。
总的来说,反讽修辞,既不能完全直译,也不能完全意译,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语言效果不同,一定要具体情形具体对待。
⑤景颇族语,有起义、翻身建立新制度之意。
⑥装东西的挎包。
⑦报复、复仇。
⑧一个山官辖区通常包括一个或几个村寨。
参考文献:
[1]吕大吉.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
[2]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8.
[3]朱普选.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地理基础[J].贵州民族研究,1997,(2).
[4]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43.
[5][6]高力.原始宗教与民族道德[J].思想战线,1994,(3).
[7]李资源.文明的呼唤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1~2.
[8]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5.
[9][11][13][14]赵学先,岳坚.景颇族文化大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92.68.193.193.
[10]祁德川.景颇族风情[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46.
[12]龚佩华.景颇族山官制社会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28.
[15]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3.
[16]俞荣根.习惯法与羌族习惯法[A]//谢晖,陈金钊.民间法(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20.
[17]周兴渤.景颇族文化[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31.
[18][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杨康,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9.
[19]谢青松.傣族传统道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69.
[20][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70.
[21]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237-238.
[22][24]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78.78.
[23]高力.试述德宏地区民族伦理道德的特点及功能[J].思想战线,1989,(3).
[25]游斌,王爱国,宫玉宽.多元民族文化中的基督教教:“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报告”[A]//牟钟鉴.宗教与民族(第三辑)[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226~229.
[26]张建章.德宏宗教——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宗教志[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275.
[27][德]卢曼.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M].刘锋,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2.
[28]石锐.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505~506.
[29][德]莫里茨·石里克.伦理学问题[M].孙美堂,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90.
[30]徐海柱.傈僳族的婚俗仪式及功能分析[J].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7,(2).
[31]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54.
[3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5.
Partial Fracture in the Whole:The Changes of the Traditional Ethics of Jingpo Ethnic Group in Yunnan in Modern Society
LI Ye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ethics of Jingpo in Yunna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imitive religion.The primitive religious as the absolute and the high external heteronomy of the traditional ethics of Jingpo,it gives the traditional ethics moral practice process in society with divine authority,so it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and control.In the change of the survival situation of modern society,the primitive religious also changed,So it must affects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ethics and mainly in the traditional integral stretching and local fracture as the main form of change,and specific reflecte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relationshipin of traditional ethics and ghosts,gods and people.
Key words:Stretching;Fracture;The Jingpo Ethnic;Traditional Ethics;Modern Changes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3-0222-07
收稿日期 :2019-02-12
作者简介:李 叶(1989—),女,云南曲靖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宗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 先 巴]
[责任校对 徐长菊]
标签:景颇族论文; 伦理论文; 传统论文; 社会论文; 宗教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