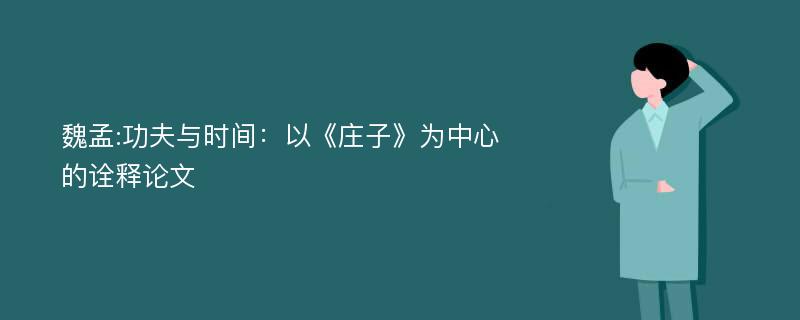
摘要:功夫论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色,而“时间”又是“功夫”的基础性含义,因此从“时间”视角诠释“功夫”能拓展功夫论的研究视野。中国古代的时间观不是线性的纯粹数值序列,而是螺旋演进的、随境域因缘而生成着的、注重时机时势的时间观。这一时间观是以时空一体的原初时间体验即“原发时间”为前提的。以《庄子》为例,其功夫论即是顺应时机时势、超越日常时间观、进入“原发时间”,从而通达自由无碍之境的过程。庄子中的体道功夫境界是“真人”之“游”,而实现“游”的功法则是“忘”。无论是静修体道中的“忘”还是技艺实践过程中的“忘”,都意在脱开现成化和凝固化的存在形态,超越世俗常人的时间观念,从而进入原初发生着的时间境域。
关键词:功夫;时间;庄子;真人
功夫(工夫)①功夫与工夫含义略有差别,但在古代亦常常通用。为行文方便,如不专门强调,笔者在下文中所言“功夫”,皆包含“工夫”的含义与用法。,其本义为做某事所花费的时间与努力,以及做事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技巧和效果。宋明儒学家将“功夫”用在德性修养实践的领域,遂有功夫论之说。事实上,功夫论非儒门专利,道家、佛家皆有自身的功夫论,扩而言之,武术、书画、茶艺、烹饪、表演等各种技艺门类,也都有各自的功夫体系。倪培民先生认为,“功夫论”可以很好地概括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修炼、践行以及生活方式的关注,因为“功夫”一词很好地统摄了功能(功力)、功法、功用(功效)、工夫(努力)等内涵,功夫视角的哲学不是对世界进行事实描述或者理论建构,而是意在使人最终达到艺术人生的实践能力②参见倪培民:《将“功夫”引入哲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倪培民:《中国哲学的功夫视角和功夫视角下的世界哲学》,《周易研究》2015年第3期;倪培民:《什么是对儒家学说进行功夫的诠释?》,《哲学分析》2013年第4期。。而在“功夫”所内蕴的诸种含义中,“时间”内涵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功夫修炼者在生命实践不断施行、体验世界不断展开的共同过程中,超越主客的对立,克服实体化、现成化的观念,在时境、时遇、时气的动态生成构建中不断提升自己审时度势、应机而变的能力,并在原初发生着的时间境域中达成对天道或良知的体悟。功夫的时间性过程体现出功力的动态构成、功法的灵活使用、功效的不断更新。本文将在分析时间与功夫之关系的基础上,以《庄子》为例来诠释时间视角下的道家功夫论。
一、功夫与时间
从“时间”的视角诠释“功夫”,首先需要说明什么意义上的“时间”是“功夫”所本具的内涵,然后才能说明这种意义上的“时间”在“功夫”的三大面向,即功力、功法、功效上如何得以体现。
学者们也一直在探索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对于企业经营效益的影响。Chu和Keh(2006)在研究中发现,广告投入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要大于研发投入。黄晓波、张丽云、黄硕(2018)的研究指出,研发费用和营销费用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同时研发费用和营销费用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第一,与西方发展出的抽象的、单向线性的“测度时间”观念不同,中国古代的主流时间观活跃在提示时机、时势的“标度时间”经验中,“时”是随境域、因缘所生成的“时域”,而非抽象的、数学化的“时刻点”,“时”的运动方式不是单向线性,而是呈现出螺旋演进的周期性。吴国盛认为,“测度时间”从出于“标度时间”经验,是“标度时间”经验脱离具体境遇后被精确计量的结果,但通过测量而获得的数值体系被当作时间的本质以后,标度时间的原初目的(即把握时机)也就被遮蔽了[1](P19)。所以,“功夫”的时间内涵不是指抽象化、数学化、客观化、线性化、去时机化、去境域化的“测度时间”,而是指随具体境遇生成的、不断展开着的“时境、时遇、时气”,以及其所显现着的时机、时势。当我们说“一顿饭的工夫”、“一炷香的工夫”、“一眨眼的工夫”时,我们用来测量时段的单位都是非常具体的生活经验,而非完全脱离生活境遇的纯粹数值。当我们说“花工夫”做某事时,“工夫”的时间内涵则完全体现在具体的做事过程中,而非意指某种量值意义上的时段。
无涂层和有涂层样品在80 ℃模拟海水中浸泡6 h的照片如图9所示.图9显示,无涂层样品的表面是发亮的[图9(a)], 在80 ℃模拟海水中浸泡6 h后样品表面腐蚀,出现黑色锈斑[图9(c)],所浸泡的模拟海水由无色变成黄色.有涂层样品的表面是银白色的(图9(b)),在80 ℃模拟海水中浸泡6 h后表面仍呈银白色,没有出现裂纹(图9(d)),所浸泡的模拟海水仍是无色透明的,说明有涂层样品没有被腐蚀.这表明所制备的涂层具有较好的抗80 ℃模拟海水腐蚀的能力.
第二,中国古代所注重的“标度时间”经验还可被还原为“原发时间”的境域,功夫的时间内涵主要体现在进入“原发时间”的存在境域。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标度时间”经验,还是肇始于西方、现已影响世界的“测度时间”观念,都是人类理性的创造,都还有更为原初的时间体验作为创制时间体系的基础。先于时间测量活动、“前—概念表象”的时间体验本身,被张祥龙先生称为“原发天时”或者“原发时间”:“所谓‘原发’(originally happening),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合或发生”,原发时间的体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预存着的当场呈现”[2](P209-210)。在柏格森看来,时间(西方的测度时间)本质上是空间化的时间。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标度时间”尚有对时间进行空间化测量的成分,那么“原发时间”则是真正的时间性过程。
当我们讲“原发时间”时,即已超越了“空间”之“间”以及“时间”之“间”,而通达无“间”的“时—空”统一境域①笔者所说的“时—空”统一境域与相对论所发展出的四维“空—时”(space-time)连续统不同,后者本质上是更为精致的四维空间,仍是对原初时空境域的抽象化和数学化。孙铁骑、鞠曦认为:“在本在(本然而在)的层面上,‘时空本无间,无间时空自生生’,‘时就是空,空就是时’,时空就是万有不分的混沌,就是宇宙生生的开始,就是生生不息的本体。”参见孙铁骑:《内道外儒:鞠曦思想述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第91页。。科学世界的“时间”与“空间”是两个对立统一的范畴,“空间”是从万物中抽象出来的纯一的、现成化的场所,而通过仿效“空间”抽象出来的纯一的、供事件在其中先后展开的现成化的媒介即是“时间”。而当我们将时间或空间还原到原初发生着的状态,时间与空间即融合为“无间时空”②以《庄子》为例,庄子所谓“六通四辟”、“六极五常”、“天地”、“宇宙”、“阴阳”、“气”等都是融时空为一体的表述,都是指万物化生演变的总体性境域。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世界整体的“道”也就可以被诠释为“原发时间”,即时间与空间未分的原初境域、彼此融合的无数事件的总体、阴阳气化的氤氲摩荡、生生不已的自在绵延。作为“原发时间”的“道”不是能以“概念—表象”思维认知的对象,而是只能通过无知无欲的浑朴真心来体悟和契入的化生境域。然而,人类由自我意识所开展出来的对象化认知方式分别出了“物”的世界,并通过对由“万物”构成的世界进行抽象化与数学化操作产生了“空间”和“时间”的观念。道家的“体道功夫”即在于超越被“时间”和“空间”规定着的“物”的世界,从而领悟到“原发时间”层面的“物化”世界。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体道功夫中实现“游”的功法,那就是“忘”。西方哲学强调记忆、回忆而非遗忘,柏拉图认为,认识就是回忆,就是回忆起心灵已经遗忘的东西[6](P76)。柏格森也以“记忆”作为其“绵延”学说的基础,他认为:“对于现在的感受来说,没有不附加对于过去的时刻的回忆的状态的连续。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绵延。内在的绵延就是一种记忆的连续的生命。”[5](P20)然而,庄子却格外钟情于“忘”。
第三,从时间哲学的视角看,“功夫”中的“功力”、“功法”、“功效”等面向可以被诠释为顺应时机时势、超越“标度之时”进入“原发时间”从而通达自由无碍之境的过程。中国古代的标度时间体系是通过阴阳气化的思维方式展开的。阴阳相交互构,从而具有某种“机(几)”或“势”,乘机得势也就成为古人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易传》力倡“与时偕行”,老子强调“动善时”(《老子·第八章》),庄子则说“与时俱化”(《庄子·山木》)。可见,儒道皆以顺应和利用时机时势为功夫之要。例如,在古代,围绕“四时”所构建起来的囊括天象、物候、方位、政令、祭祀、礼仪、伦理、音律、颜色、嗅味、术数、衣食、医药等各个方面的全息天人体系,成为修炼时机化生存功夫的重要知识内容。然而,上述“标度时间”体系仍然具有外在的性质,在功夫修炼主体的具体存在过程中,体悟天道或良知的时境瞬息万变,因此儒道两家的功夫修炼还需超越外在性的标度时间体系,进入“原发时间”的存在境域,在原初发生着的第一现场达成对“仁”、“诚”、“良知”的自觉,或者对“天道”、“自然”的领悟。人不仅在“时”之中,而且人的生命存在即是“时”本身,如何在领悟、利用标度时间所暗示的时机、时势的基础上,超越具有外在性的“标度时间”并最终进入“原发时间”的动态境域,这是功夫论中的“功法”问题;而在知时、察时、用时并最终与时偕行、与时俱化的过程中,则展现出功夫的不同境界、层次和效用。
二、“真人”之“游”:庄子体道功夫境界的时间诠释
如果说儒家功夫论的重心是在“原发时间”境域中达成对自心德性的自觉,那么道家功夫论的重心则是在“原发时间”的整体境域中领悟万物化生的自然之性。下面我们就以《庄子》①本文所引《庄子》原文均依据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下文凡引《庄子》仅夹注篇名。为例,从时间哲学的视角对庄子的功夫论进行分析。
庄子的体道功夫论所要追求的理想人格形态是“真人”。“真人”存在于“原发时间”的整体性境域(即庄子所谓“一”)中,“其一与天为徒”(《大宗师》),真人从符号与观念的人化世界中跳脱出来,从而能够与原初的自然浑然共在。“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大宗师》),即在事态初露征兆时不嫌逆,“事之既成,不自雄以为能”[3](P132),即不对未来之事进行谋划。也就是说,真人能够以“虚待之心”(因“时”境而构成着的心,而不是现成化的主体之心)对不断前来的“时”(构成性境域)保持最大的开放性,从而不把自身固化在现成的情境状态里,他也不期待、想象和谋划未来,因为如果对未来有所期待,那么就一定在期待着某种“什么”发生,而这种对尚未发生之事所作的限定一定与因缘汇聚所构成的将来有所不符。在真人的视域里,“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大宗师》),即错过时机和得到时机都应该平等地对待,而不是后悔和自得。“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大宗师》),做梦总有要梦见的“什么”,而真人虚无恬淡、和于天德,他从不滞留在任何现成化的意识内容之上,故无梦;忧虑总是对尚未发生的“什么”感到忧虑,而真人不会从当下时境中先行到未来的某个预期境域之中,他只是以虚待的方式向未来之“时”的可能性全然敞开,故无忧。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讠斤,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大宗师》)死生现象是从人的视角对生命过程所作的时间区分。若从超越个别事物之时间性进程的整个宇宙的大生命(即原发时间境域)来看,死生就不再是限定生命时段的两个端点,而是在“原发时间”的化生境域中“出入”、“往来”着的事件过程。真人超越了常人的生死分别,而以不悦不恶、不欣不拒的虚待之心对待生命之“时”的到场与退场,从而能够翛然往来、自在无碍。真人“不忘其所始”,他能够时时与原发时境相应而不溢出那缘构生成着的变化时气,从而不停驻于某种现成化的状态中。真人还“不求其所终”,即不赋予生命任何外在性的目的,只是随顺自然尽其天年。当生命之时不断前来时,真人以虚待之心“受而喜之”,当生命之时退场时,真人仍以无碍之心“忘而复之”,即忘掉作为现象的死亡事件,复归于原发时境的大化洪流中。
柏格森采用直觉而非分析的方法,在自我意识的深处发现了彼此外在的观念之间原本存在着一种流动,即“绵延”,绵延之流是意识中各种观念与状态之间彼此渗透与交融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生命力,“意识所觉到的内在绵延不是旁的,而只是意识状态的互相融化以及自我的逐渐成长”[4](P79);“当绵延流走时,我们虽可通过想像的努力而能不加怀疑地把它固定下来,将它分割为并列的各个部分并将所有这些部分加以调配,但这种活动之完成所根据的仍然是对于绵延的冻结的记忆、绵延的可动性所留下的静止的痕迹,而不是绵延本身”[5](P10)。我们只有通过“回顾”该绵延流动的“痕迹”(即记忆中的事物,它们事实上已经不再存在、而是融化入绵延的最新进展之中)才能区分出不同的状态,才能在意识中确定彼此有别的“物”的存在。每一“物”都是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例如价值、意义、用途以及所唤起的行动等)的东西,自然形物、道德伦常、身体情绪、思想观念,所有这些有所“是”的“物”彼此外在,从而形成了一个静态的固体世界,这是常人无法“游”于自由之境的原因。
静修体道的核心功法在于对意识建立在“记忆”能力基础上的心念活动采取反向操作,即通过“忘”的方法获得超越性的内在体验。此外,庄子为我们塑造了大量手工艺人或技艺实践者的形象,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梓庆为鐻、佝偻承蜩、工倕旋指、津人操舟、丈夫游水等。他们通过精熟的技艺来实现“忘”的境界,而与手头之事物打交道的构成性境域其实就是人生在世的隐喻,这构成了庄子体道功夫论的又一重要面向。
⑩ 刘 译 :Pleased that he can practice the ancient Way...[4]38
总之,庄子笔下的真人超越了世俗时间观念中三种时态彼此外在的看法,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相以本真的方式相互缘构、统一到时,从而交媾出活泼泼的当下时气、时域。真人以虚待之心向前来之“时”开放,从而维持住了一个无物常驻于心的活态境域,真人即以生命存在的方式领悟着“原发时间”这一终极的构成性境域。常人以非本真的方式存在于世,因为常人生活在“物”的世界中,对于“物”的记忆构成了“过去”,对于“物”的注意构成了“当下”,对于“物”的期待构成了“将来”。真人“游心于物之初”(《田子方》)、“游乎万物之所终始”(《达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田子方》),故真人没有关于“物”的“知”以及因对“物”之好恶所生之“欲”与“情”。真人不固着于过去之记忆,因为无所可记,真人之“记”乃是对“物化”这一缘构本性的领会,故真人“其寝无梦”、“过而弗悔”;真人也不期望未来,因为无所可期,真人之“期待”方式是“虚待”(虚而待物),即对尚未到来之“时”的可能性报以最大的敞开态度,故真人“不谟士”、“其觉无忧”、“不求其所终”;无所“记”之“过去”与无所“期”之“未来”共同交媾生出的“当下”自然也是不断地化生与流通着的时境,真人(或者至人、圣人、神人等)对于发生着的“物化”进程只是如镜照物般地“应而不藏”:“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钟泰先生的解释是:“‘不将’,则已去者不随之去。‘不迎’,则未来者不逆其来。‘不藏’,则现在者亦不与之俱住。”[3](P179)
在超越了“物”与“物”之不可入性、间断性的“绵延之流”或“原发时间”里,各种状态交融渗透,从而形成一个没有断裂和外在性的流体世界,体道之“真人”即“游”于此“物化”或“气化”着的原初境域。“游”的功夫境界是对“物”的超越,故庄子常说“游”于“物之祖”、“物之初”、“物之所终始”;这是“无物”的绵延之流,故庄子说“游”于“天地之一气”、“无何有之乡”;像庖丁这样的匠人,因为超越了固化观念和方法,故可臻至“游刃有余”之境界;而体道之“真人”也因超越了人世毁誉穷达的分别而可以“游”于人间世。那么实现“游”的“功夫”境界,又该采用什么“功法”呢?
三是定主题。主题党日活动通常以“规定动作+”的模式开展,“+”的部分就是结合实际确定的“自选动作”。设计好党日活动主题,做好“自选动作”,是开展好“主题党日”活动的关键之一。在设计党日活动主题时,一是要紧紧围绕党的建设“5+2”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突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三、忘:庄子体道功法的时间诠释
(一)“时间”视域下的“忘”
陶小西睡得死,鼾声震天响,完全没察觉到温衡在身旁,她不舍得把这样的温暖错过,趴在一旁的凳子上浅眠,到破晓时分又悄悄回去客房。
《庄子》中的“忘”出现高达80多次,如“忘年忘义”(《齐物论》)、“其心忘”(《大宗师》)、“坐忘”(《大宗师》)、“忘适之适”(《达生》)、“忘言”(《外物》)等。此外,还有大量与“忘”含义相近的词,如“遗其耳目”(《达生》)、“遗万物”(《天道》)中的“遗”;“外天下”、“外物”、“外生”(《大宗师》)中的“外”;“吾丧我”(《齐物论》)中的“丧”;“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大宗师》)中的“堕”、“黜”、“离”、“去”,等等。
在现代汉语中,“记忆”的含义更偏重于“记”,而表达“忆”则会使用“回忆”。实际上,“记—忆”一词原本表达的便是我们意识的绵延方式:“记”使感知在意识中滞留并逐渐降低其强度,从而形成我们关于“过去”的经验——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而“忆”使感知的滞留与新的感知综合起来,从而将存在于“过去”的“记忆”带向“当前”,然后新的“当前”感知再次滞留并逐渐减弱其强度,并进而成为新的“过去”……如此循环往复地推动整个意识的绵延发展。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此外,庄子还格外强调“忘言”。在具体的功夫实践中,“忘言”与“忘物”是同时发生的,正如陈霞教授所言:“‘名’也是‘实’得以完成和能被思考的场所,没有被语言说出来的自然万物无法被思考”,所以,“名”和“实”是“同时共在、互相成全的”[9]。当然,与“忘言”共在的“忘物”并不是让“物”归于绝对空无,而是让“物”以其自身方式存在,即以“前‘概念-表象’”的方式如如自在。在庄子看来,“道”是不能用语言表象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如果可用语言概念来表象,那就一定是“物”的世界;反之,只有“忘言”,才能超越“物”的世界而“让”作为“原发时间”的“道”显发出来。
(二)“忘”与静修功夫
《庄子》功夫论中有关静修体道的内容有“心斋”、“坐忘”、“朝彻”、“见独”、“守一”等。在《大宗师》中,颜回通过“忘仁义”、“忘礼乐”、“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而达到了“坐忘”之境,颜回谓之“同于大通”。颜回所忘者包括形体、知见、伦常礼教,这些其实都是藉由语言所分别出的现成化的“物”,是记忆所存留的“绵延”或“原发时间”的静态痕迹,它们从原发情境的势域中凝固下来而丧失了时机性,所以成为“游”的障碍和阻力。通过“忘”的功夫,颜回最终通达“坐忘”之境,所有的记忆之“物”似乎都融化为一,从而呈现出彼此渗透的流通景象。在这种自由流通的“当下”时境中,颜回关于自我身体和外物的观念认知都被超越了,自身也融入在大化之中,此谓“同于大通”。
《大宗师》篇还有一个南伯子葵向女偊问道的故事,女偊所领悟到的是“朝彻”、“见独”、“无古今”、“不死不生”:
程序设计方面,Arduino兼容C/C++语言,用户通过C/C++语言对输出模块(电机、灯、蜂鸣器等)进行程序化控制,从而实现各部分的搭配工作,达到预期避障目标。通常对于全地形越野竞赛,设计者需要就实际赛道、障碍设计独有的程序,有时甚至需要设计一些特殊的程序,例如:现有一条赛道,设计要求在发车后三秒直行且屏蔽循迹功能且在通电25秒后停下,故可定义宏常量t=0,使其在loop循环中if(t=0){t++;直行程序},这样就可以避免无限循环三秒直行程序,再利用Millis函数控制停止时间,一整套的特殊要求程序就完成了。电子控制程序设计应力求简洁、易读懂、功能性强。
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
女偊通过“外”(忘)的功法,经过“外天下”、“外物”、“外生”的修炼,将社会关系、有形之物乃至身体之生死都层层剥离、统统“忘”掉,最后的剩余者不能是任何还可以被“忘”的现成者,而只能是化生着的构成性境域,是个体“当下”生命的原初发生过程本身。在这种原初的发生进程中,处在构成中的“我”所领悟到的是照彻全体的智慧之光明,是与对象化认知的“小知”不同的“洞见”与“觉知”,故谓之“朝彻”;所有有形的现成化观念都消融于大化之流的自在绵延中,这是无待之“独”境,故谓之“见独”;“道无终始,物有死生”,在原发时间的境域中,自然没有古今之分、生死之别,所以女偊有时间(常人的时间感)消失之感,故谓之“无古今”、“不死不生”。
《在宥》篇广成子向黄帝问道以及《知北游》篇啮缺问道乎被衣,都讲到了收视反听、静心守神的功夫方法,我们依然可以从“忘”的角度来进行解读:
“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在宥》)
“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知北游》)
秦明月习惯性地掏出手套戴在手上,去拉车门,只轻轻一拉,车门即开。虽然车身外一层尘土,但车内却一点杂物也没有,只在驾驶台前摆着一张卡片,是进停车场时的停车卡。他轻轻拿起来一看,记录着进场时间正是三天前的晚上8时过3分。
梓庆削木为鐻……“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达生》)
这两段引文中的功夫论内容亦常见于流传至今的许多道家修炼功法中,其核心要领在于调正身形、收视反听、止息思虑、心神守身等。其中“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无摇女精”、“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闭女外”、“摄汝知”等要求,都与“忘”的功法有关,即“忘”掉耳目感官与外境相接所产生的见闻,从而止息精神因追逐外物所产生的动摇。需要注意的是,“守形”、“守汝身”、“守其一”等所“守”的并非现成化之身形,亦非固化之整体,而是以虚待之心“让”生命现象本身自发地“发生”出来,这里的“守”相当于“观化”(《至乐》)中的“观”,是无预设的虚心静候之意。“守其一”、“一汝视”、“一汝度”等所强调的“一”也不是具体的数目“一”,而是指绝待无二之“独”境,是化生着的“原发时间”境域;体道工夫并非是将心思专一至某处,而是观照于整体性的发生进程本身。所以,像“守其一”等体道要领可能导致这样的误解,即执着地“守”某“一”现成化之物,这就需要“守其一”包含对“守”和“一”本身的“忘”。原初的发生境域整体(“道”)只有在“忘”的功法不断地去蔽下,才会自发地显现。这一点在“心斋”功夫中被表达地最为清楚:
“忘”即是“亡心”,但所“亡”的又是什么意义上的“心”呢?《说文》曰:“忘,不识也。”也就是说,“忘”意味着不能再识别,而再识别的前提是有所记忆。所以“忘”所否定的只能是产生对象化意识内容(记忆之物)的“成心”。“忘”离不开“记忆”,“没有先在的‘记’,也就没有后来的‘忘’可言”,“庄子之‘忘’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遗忘,不是完全地抹去过去事件的痕迹,而是一种超越、去蔽和解构”[7]。人要完全抹去记忆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无记忆的意识”[5](P20),庄子所谓“忘”只能是超越、去蔽和解构意义上的“忘”,通过对具体所“记”(意识中“物”的延迟与滞留)的超越,让柏格森所谓的“绵延”(即“原发时间”)更顺畅地得以发生:“心”一旦停留在记忆中的某处,就意味着将过去的某物放在了现在感知状态的旁边,这样就偷偷引入了空间化的时间观念,意识内的记忆之“物”便呈现出彼此外在、并排置列的关系,意识的自在绵延也就无法顺畅地进行下去了。通过“忘”,感知内容在意识中的滞留便以“前概念-表象”的方式、“是其所是”的方式参与到绵延过程中,“我”并不在感知的滞留中“识别”(忆)出任何“物”,从而解蔽出“前语言”(庄子谓之“忘言”)的纯粹发生本身。最后,“忘”还意味着对“主客对待”意义上的“主体”的消解,个体生命实质上就是“原发时间”进程本身,实体化的“我”是不存在的。“我”只是“我”的历史,是“我”所有的过去,是“我”的所作所为本身,是连续的自我创造[8](P11-12)。因此,“忘”还包含对“身”、“形”、“我”、“己”之实体性的解构。
“听之以耳”和“听之以心”所听到的仍是对象化之“物”。只有“听之以气”,主体以无任何预设的虚待之心迎接“时”的不断前来,“道”才会显发出来。“气”所象征的原发构成性建立在“忘”“物”的基础上,对“听之以耳”和“听之以心”的否定其实就是对“忘”的肯定。而“听之以气”事实上已经暗含了“忘”的功法,因为“气”为“虚而待物者”,通过“忘”,“心”才能变“虚”,才能以“气”的方式发挥作用,如此才能“以气听气”。这样的气化境域就是因“虚待”之心而通流为一的“道”。
(三)“忘”与技艺功夫
庄子功夫论所追求的最高功夫境界可以用“游”字来概括。《庄子》中“游”字共出现80余次,“游”所描绘的乃是存在着的个体生命突破种种限制与束缚所通达的自由境界。导致个体生命存在之不自由的种种限制与束缚,归根结底在于“成心”(或“机心”)对“物”的分别与执取。一切“经验我”所生成的对象化的意识内容,如自然形物、道德伦常、身体情绪、思想观念等,都可被纳入广义上的“物”的范畴。“物”只有被当作现成的存在者才能借助于语言名号被确定下来,而与现成之“物”相对应的即是“成心”。“成心”使“物”从原初混沌中显露出来,而作为意识内容的“物”又构成着“成心”。由“成心”所固化下来的“物”存在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定之中,具有广延量值上的大小多少以及时间限度上的死生终始。因为度量死生终始、长短久暂的时间在本质上是空间化的时间,所以由“物”构成的世界也就遮蔽了世界原初的时间性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空间化的世界。拥有“成心”的常人会认为,自身之外的万物是彼此有别的;而在自身的意识之内,藉由语言建立起来的种种观念之间也是彼此外在的。正如柏格森所说:“语言要求我们在我们的观念之间,如同在物质对象之间一样,树立种种同样明晰而准确的区别,产生同样的无连续性。”[4](序,P1)这种形物和观念之物所固有的间断性、不可入性,构成了自由之“游”的最大障碍。
技艺实践之不同于收视反听的专门性修炼,在于技艺实践的动态情境要求实践者时时对“当下”情境做出回应。“‘艺’意味着灵巧、机变、有尺度感,在适时应和之中让‘阴阳’或‘相异者’相交,从而当场引发出某种事物和情境,因而能养成人的分寸感和对时机的领会。”[2](P218)所以技艺活动的展开越是能够顺畅无碍地流通,它就越是呼唤主体处身于“当下”境域中。
“当下”不同于测度时间中的“现在”,它是由人、物、事所缘构生成的动态势域,是毫无阻滞的流通之“时”,是生生不已的原初发生。一切现成化的东西,诸如主体、客体、方法、技巧、目的、价值等,都会阻碍“当下”之“时”的绵延流通,而这些现成化、凝固化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仍是人类所本具的“记忆”能力的副产品。没有记忆,我们就无从与世界打交道,但对记忆所提供给我们的现成化的观念和方法的执着,却又常常成为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障碍。记忆所存留的毕竟是绵延所遗留下来的不动影像,是已经丧失时机时势的现成之物。所以,用现成化的观念和方法去框限生动发生着的“当下”往往招致挫败。庄子笔下的技艺实践所维持的原初发生的现场则能够帮助实践者超越现成化的前设,从而让生命随生存境域之态势自发地做出回应。以下所录就是《庄子》中一些相应的案例。
自2002年启动引江济太以来,实践证明,将长江清水引入太湖,并向太湖周边及下游地区增加供水,可增加流域水资源有效供给,加快河湖水体流动,提高水体自净能力,改善太湖及地区河网水质。同时,作为流域供水安全应急保障的重要手段,引江济太在应对2003年黄浦江上游燃油水污染事故、2007年无锡市供水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为保障青草沙原水系统切换期间供水安全而实施的引江济太应急调水的成功实践进一步表明,引江济太对保障流域供水安全作用明显。
工作流程管理主要实现产品设计与修改过程的跟踪与控制,包括审批流程和更改流程,实现工程数据的提交与修改、管理和监督、文档的分布控制、自动通知等。企业在实施PLM系统前梳理了工作流程,并建立工作流程模型存放到PLM系统中,相关人员根据PLM系统的工作流程完成工作。PLM系统采用电子签审,有权限的审批人员对工作进行签审,并将该次操作作为文档的一部分,系统永久保存,以备查询。PLM系统的会签功能可实现多人同时审阅一张图纸或文档,避免了纸质文件流转造成的时间延误,提高了审批流程的效率。
大梁张了张嘴,还是冇言语。我又缓缓地说:“我是个女人,再么样他们不会打我,更不会杀我吧。好男不跟女斗,这老话都说了。”我站起身,转过脸对着大梁,“只能这样了。我明朝一大早就去。早点儿困吧。”
庖丁释刀对曰:“……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髋,因其固然……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养生主》)
轮扁曰:“……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天道》)
津人操舟若神……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达生》)
“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达生》)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蹶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达生》)
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达生》)
二是通过活动提升综合素质。举办“学思践悟,与你分享”主题交流分享会,交融心灵、取长补短;组织青年员工分组采访整理10位劳模代表的先进事迹,形成学习劳模、崇尚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氛围。定期召开青年员工座谈会,及时了解掌握其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深入交流,互相探讨,共同提高。现今,公司8个部门中已任用了4名80后中层副职以上干部。
《达生》篇中,梓庆为鐻的过程是专门性修炼与技艺实践的有机结合。在入山林寻找合适的木材之前,梓庆需斋戒三日、五日、七日,分别“忘”掉“庆赏爵禄”、“非誉巧拙”、“四枝形体”,即超越财利、名声、形体,这是属于专门性静修的功夫,这为他专注于“当下”的制作过程创造了条件。然后他入山林、寻树木,当感到成品已了然于胸时,他才开始加工生产,非如此则不冒然开始。梓庆认为“器”可以“凝神”,也就是可以将自己的生命聚合在域状的“当下”中,此时的整个制作过程可被称为“以天合天”,即以自己的自然之性与木材的自然之性相契相合。“以天合天”即是藉由前期的“忘”所达至的“天然”、“自然”状态,精神不滞于任何外在性的现成者,而是与在手材料的磨合中让物我的原初本性共在于整体性的原发境域。
与梓庆还有一个前期的静修准备不同,《养生主》篇的庖丁则是在纯粹的技艺操作中“道进乎技”。刚开始解牛时,庖丁仍未摆脱对象化认知的束缚,“所见无非全牛”,三年以后则能够“未尝见全牛”,最终能够“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目视”所见者是流动之绵延的凝固化影像,所谓“牛”也是通过记忆之“滞留”所截取的静态之“物”。而通过“为学日益”的技艺积累,庖丁因“手熟”而“心忘”,即“忘”了对象化的被操作者以及现成化的操作方法,从而任由意识的内在绵延自由地流动。超越“目视”的“神遇”即是以非固着化的开放之心与被解之牛的自然纹理相遇合,从而生出活泼灵动的解牛时境。感官(尤其是眼目)所生成的多是绵延的陈迹,而“神”的自发流动则超越了所有具体的记忆之物,超越了感官留存的瞬时影像,在所有意识内容彼此渗透融通的整体性中涌现出自发性的流淌,从而使庖丁臻至“游刃有余”的化境。
与庖丁解牛类似的故事还有《天道》篇的轮扁斫轮。轮扁认为,圣人之书已是糟粕陈迹,因为“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书中所言已经丧失了原初时境的时机与时势,所留存下来的只是凝固化、现成化、没有生机的东西。他以自己斫轮为例进行说明,其“不徐不疾”的功夫火候“有数存焉于其间”,然而他却“口不能言”,只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轮扁所说的“数”即是所斫车轮时时变化着的状态对斫轮者力道、节奏等功夫的动态呼唤。这“原发时间”的境域自然是离言绝象的,因为可言说者会遮蔽语言所指对象的原发构成性而将其简化为某种静态的、均质化的东西。所以轮扁的技艺是“忘言”状态下的“得手应心”——我们现代汉语中的“得心应手”恰恰是对“得手应心”原初意味的遮蔽。手对车轮的触摸象征着人与世界“相刃相靡”(《齐物论》)的交互,“手”先行于“心”正是为了以“直觉”而非“分析”的思维方式契入“原初发生”的时间境域。“手”有所得,“心”便“应”之,这里的“心”是无任何现成化预设的虚待之心,此心不驻留于任何记忆定格下来的现成之物,因而能够以整体性的构成境域去回应每一个来临之“时”——例如所斫车轮的某一状态——的呼唤。当“我”不再是主体之“我”而是与构生着“我”的整体性境域相符相契时,“我”对于“当下时境”的回应就是整体性的势域之“道”因“时”任“势”的自发流动与涌现。轮扁的“得之于手而应于心”中的“应”乃是超越记忆对于个别之物的执着后,集合所有记忆信息的自由融合所生发出来的适应性智能。
对于这种我们今人称之为本能或直觉的适应性智能,再没有比对“水”的适应更形象的譬喻了。《达生》篇中“津人操舟”和“丈夫游水”的故事就与水有关。水是最具形变的意象之一,它就像人生在世的时境一样,任何固着化的前设都是无效的,而只能“感而后应,迫而后动”(《刻意》),津人操舟若神,因为他是善游者,而善游者已然“忘水”;丈夫游水有道,是因为他“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和旋涡一起没入,和涌流一起浮出,顺水势而为,而不自作主张。水的动态变化使得游水者只能安住于“当下”的动态时境,并以虚待之心对之做出回应。
安住于“当下”的缘构境域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达生》篇“佝偻丈人承蜩”的故事能给我们很好的说明。经过“累丸二”、“累三”、“累五”的渐进式练习,佝偻丈人在承蜩之时可以做到处身“若蹶株拘”、执臂“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以万物易蜩之翼”,孔子对此的评价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佝偻丈人承蜩时的境况有点像收视反听的静修状态,即通过“凝神”的工夫契入那原初的动态境域。只是,佝偻丈人的忘记“天下之大、万物之多”是通过粘住蜩翼的实践活动呼唤出来的,而不是像静修体道者那样对内在意识直接进行“忘”的主动操作。佝偻丈人的承蜩境界容易给我们造成守心一处的静止感,其实,这种用志不分的凝神状态恰恰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冥合境域中显发出更加动人心魄的原初构成性,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佝偻丈人深沉的呼吸以及蜩翼的微动所带来的情势的变化。所以佝偻丈人藉由对承蜩活动的凝神恰恰使自身进入到终极境域的原初统一性之中。
这种在技艺实践中突破物我二分的融合之境,用庄子的话讲就是“化”。《达生》篇中工倕旋指的技艺能够超过规矩所画出来的,因为他“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手指已经和所用之物融合为一、因而不必用心思来计量,这使他的心灵专一而无有窒碍:“其灵台一而不桎”。“化”的境界是藉由“忘”的功夫实现的。庄子说,“忘足”是“履之适也”,“忘要(腰)”是“带之适也”,“忘是非”是“心之适也”,而最后还要超越为了“适”而“忘”的目的性,以及作为现成方法的“忘”本身,所以还要达到“忘适之适”。通过“忘”达到“适”,再通过“忘适”达到原初的“适”,即物我无碍地共在于混冥融契的“原发时间”境域之中。
四、结语
庄子所推崇的真人即真实的人、真正的人,以无知无欲的浑朴真心存在于世的真人,超越了被现成化的时间和空间规定着的“物”的世界,从而能够“游”于“通天下一气”的“原发时间”境域中。实现“游”这一功夫境界的功法是“忘”,无论是静修体道中的“忘”还是技艺实践过程中的“忘”,都意在脱开现成化和凝固化的存在形态、超越世俗常人的时间观念,从而进入“原发时间”的化生境域。本文仅仅是对庄子体道功夫的时间诠释,而从更宏观的视域对中国古代的功夫论进行时间视角的诠释,仍然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煌绿乳糖胆盐肉汤(BGLB)、结晶紫中性红胆盐琼脂(VRBA):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氢氧化钠(粒)、无水碳酸钠、硫酸铜:天津市东丽区天大化学试剂厂;酒石酸钾钠: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福林酚: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
参考文献:
[1]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M].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陈霞.“相忘”与“自适”:论庄子之“忘”[J].哲学研究,2012,(8).
[8][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9]陈霞.庄子与麦克道尔语言观比较研究[J].哲学动态,2015,(4).
Kung Fu and Time: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ChuangTzu
WEI Meng-fei
(DepartmentofManagement,Henan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Zhengzhou450046,China)
Abstract:Kung Fu theory,which means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remains one of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philosophy.Apart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effort,labor and skill,the primary meaning of Kung Fu is time.Therefore,interpreting Kung Fu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has the potential of expanding the range of studies.In ancient China,time is not understood as a linear or pure mathematical thing.Instead,it is a spiral evolution continuously formed by specific situations to which special attention had been paid.This idea of time actually is based on the primordial time experience which takes time and space as an inseparable whole.Taking Chuang Tzu as an example,his Kung Fu theory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process of follow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tendencies of various time-situations,aprocess of transcending ordinary concept of time and entering the free situation which can be called primordial time.In Chuang Tzu,the wandering Ture Man represents the Taoist Kung Fu,and the method for Authentic Person to wander freely is by forgetting.Whether being the forgetting in meditation or the forgetting in workmanship,the key point lies in going beyond the established and fixed state of being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linear time,until one enters the primordial state of becoming.
Key words:Kung Fu;time;Chuang Tzu;Ture Man
中图分类号:B2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3-0012-09
收稿日期:2018-04-22
作者简介:魏孟飞,男,哲学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春梅
标签:时间论文; 境域论文; 功夫论文; 庄子论文; 真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道家论文; 《齐鲁学刊》2019年第3期论文; 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