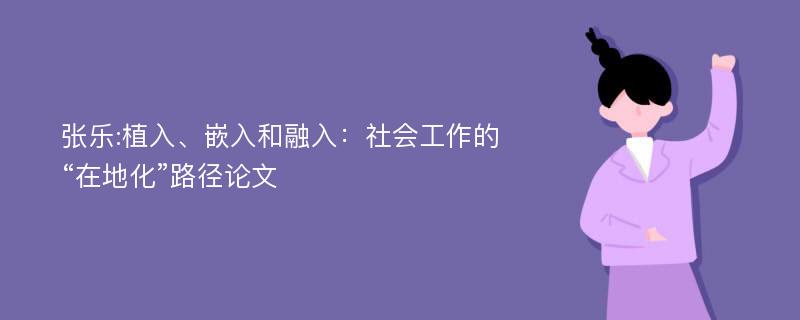
摘 要: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在地化”的过程。期间社会工作经历了生硬植入和深度嵌入的发展阶段,而地方性隔离与权力规训让社会工作的“在地化”变得困难重重。但是,专业社会工作先天具有“扎根倾向和落地特质”,即便面对困境,其也从未抛弃“提高人民福祉”的价值原则,反而是凭借“促进社会公平”的使命感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专业能力,在基层治理场域中不断进行着适应、调整和改变。通过根植于基层,立足于服务的策略方式,社会工作正逐步迈向与基层治理体系日益融合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社会工作 在地化 植入 嵌入 融入
一、引 言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走符合国情的本土化道路早已是各界共识,而本土化实现路径主要有四种主张:一是嵌入说(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王思斌,2011;史柏年,2013;尹阿雳等,2016),二是内生转型说(李迎生,方舒,2010;张昱,孙志丽,2010;卫小将,2014),三是分立说(刘威,2011;殷妙仲,2011),四是融合说(李伟,张昱,2015)。无论哪一派观点都没有完全排除政府的作用去单纯地谈社会工作发展。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大陆当前“政—社”关系下,依靠政府结合既有体制来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政府强势主导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也有弊端,这表现在专业社会工作者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和内部治理官僚化等问题,社会工作在街区权力体系中逐渐式微,失去了影响力(朱健刚等,2013:43),甚至出现了“道德实践的商品化”和“政治实践的工具化”现象(肖小霞等,2013:151),社会工作追求社会正义的使命也被扭曲了(郑广怀,王小姬,2014:31),以至于社会工作自身陷入了身份焦虑(张超,2017:73)和看似难以解脱的发展困局之中(宋言奇、余力,2016:126)。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在寻求自我发展的道路上难道真的如以往研究所言的那样变得愈加保守和悲观了吗?以专业性和自主性自诩的社会工作在面对国家强势主导的框架里真的毫无“招架还手”之力了吗?本文以笔者长期积累的观察笔记、学生实习报告与跟追访谈资料为依据,通过介绍W市社会工作及其核心社会组织的“在地化”过程,揭示社会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的细节,尝试性地回答上述问题。
之所以讨论专业社会工作的“在地化”而不是通常所言的“本土化”,有其独特的考量。本文认可季乃礼的观点:本土化与国际化相对应,不仅强调研究重点是中国的现象,而且根据中国实践概括出能够对中国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季乃礼,2018:1)①季乃礼,2018,《推动我国政治学研究“在地化”》,《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zx/bwyc/201807/t20180704_4494787.shtml.。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基本路径是本土化,将全球社会工作知识融入中国架构之中重新进行诠释,最终将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性知识与中国的特色异质性演化相结合。而“在地化”除了具有宏大的“全球视野”层面的中国化的涵义之外,更强调较小范围内的社会工作在地方上的“落地生根”的过程,突出地方乃至基层街区场域中的社会工作根植的过程及其结果。换言之,“在地化”更能体现带有“舶来性”的社会工作的“扎根倾向”与“落地特征”。
二、植入:社会工作的主动介入与政府的被动接纳
植入一词多用在医学和生物工程领域,医学上将可植入物(人工晶体、人工关节、人造心脏瓣膜等)通过外科手术放置于人的体腔中的过程称之为植入。受此启发,本文将社会工作在本地发展的初始阶段也叫做“植入期”,也即是作为“外物”的进入,以一种近乎物理性的方式开始其“在地化”的进程。
(一)主动接触与形式化安排
1.高校办专业与主动“在地化”意愿
W市的社会工作的建立源自S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开办与招生。2004年,该校正式招收了第一届社会工作本科班,规模为60人。是S省最早举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之一,更是W市第一家开设社会工作本科教育的学校。在时间上占有先机,以“先发优势”获取各种支持和资源,使社会工作的萌芽依托驻地高校的力量顺利完成了。
在高校里“诞生”的社会工作,却不脱离地方社会独自发展。S高校最初的社会工作课程体系基本借鉴了欧美国家和港台地区社会工作院系的课程设置,贯彻国际通行800标准学时的要求。高标准的办学目标和对新办专业的热情推动着社会工作必须主动寻求“在地化”。但是,由于高校兴办社会工作专业存在路径依赖(王思斌,2013:117),学校层面关注的是招生规模和生源质量,在“校地合作”方面投入的资源较少,各个专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地方社会开展交流与合作。于是,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只好动用各自的社会资源,寻求能为学生实习提供场所、机构和督导的社会帮助。S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最早的负责人是一位具有本地籍贯的具有社会学方向的资深教授,其所掌握的地方资源颇多,与市政府多名高层官员有着同学之谊,区县一级的领导干部又多是其学生晚辈,多重身份的专业负责人让社会工作与地方的初步接洽成为可能。
2.地方社会治理的需求与工作压力的促动
2004年前后,W市及其下属各级治理单位虽然并不十分了解社会工作,但其对高校主动“上门求助”的反应态度是“欢迎”。由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长期存在“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组织架构特征(马跃,2011:183),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提供社会福利的事业单位,都缺乏高素质的人才为其分担不断加码的服务性工作。高校师生的到来无疑称得上是“久旱甘霖”。
“我们既需要专家学者们的真知灼见,也需要大学生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服务工作中……下面的活很多,我们人手很缺,你们肯定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想,更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基层社区工作就是社会工作,学生们来这里实习就对了。”(访谈资料012,H区民政局原副局长C先生)
本文基于空间外差光谱技术的基本特性,将多重信号分类算法应用于空间外差干涉图功率谱估计,采用CAT准则对影响MUSIC算法谱估计结果的信号空间维数p进行自适应定维研究.结果表明改进的CAT准则结合MUSIC算法能很好地实现空间外差干涉图的光谱复原,提高光谱信噪比与复原效果.
“在地化”早期,一方是以专业建设和寻求实践平台为主要目标的接触性行动;另一方则是以疏解日常工作压力和获取智力、人力支持为目标的欢迎性行动。尽管双方的需求及出发点各不相同,但这些差异性没有妨碍双方建立联系,反而促成了“彼此的试探性接触”。很快,学校与镇街等基层政府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街区欢迎师生来实习,却没有明确实习的具体机构(基层当时也没有社会工作机构可以选择),提供实习机会,却没有明确具体的岗位,安排实习接洽人员,却没有安排专业实习督导(也更没有专业督导)。整体而言,这是一种有实习的形式,没有明确的实习内容,有实践的外表,却没有社会工作专业的精神内核的“在地化”。但无论如何,主动接触和形式化安排为实质的“在地化”奠定了基础性,积累了经验。
《史记》:“始皇三十七年,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刻石颂德……”。《水经注》云:“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在山侧”。
(二)社会工作的刻板化介入与街区的排异反应
1.社会工作的刻板介入
高等院校兴办社会工作专业初期大多都存在简单移植的现象,S学校也不例外。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专业“该如何办”没有太多现成经验可以借鉴,有的只是对欧美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社会工作教育和服务体系的教科书式的生搬硬套。如何让源自市民社会悠久历史传统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专业在东方文化传统影响深厚的现代中国落地生根,尤其是让西式的社会工作实践被当地的街区社会治理体制与福利系统所认可乃至接受,并非易事。
“教科书都明确规定社会工作的标准流程是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和结案6个步骤,我们以反家暴为主题,期待在社区带着学生走完这个流程。可根本没有社区女性居民参加我们的活动,甚至有好心居民劝诫我们,要明白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居委会工作人员还警告我们,在社区宣传这类主题,有违和谐社区建设的精神。”(访谈记录002,个案社会工作任课教师Z老师)
尽管从事一线教学专业课教师很早就发现将西式社会工作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做简单复制存在诸多弊端。但是专业已经开办,学生已经入校,实务课程需要本地机构提供实践基地,这些现实问题又迫使反思性教学探索不得不暂时让位于进入社区和服务机构开展“服务实习”的现实需求。不过,由于当时社会工作专业师生都没有前期的工作积累,就只能按照西式教材和参考书上的要求去摸索,难免会出现“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事实也证明,以西方价值导向和工作方法介入中国地方事务的时候,刻板化的单纯模仿无法实现最初设定的专业目标,甚至适得其反,容易引起基层社会的反弹,让专业介入变得困难重重。
2.街区的排异反应
与社会工作师生的生硬植入方式相对应,作为被植入对象的基层治理单位对这种方式同样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排异反应。
首先,街区原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于社会工作的到来显然没有做好准备,无论是心理上的接受度还是制度安排上的接纳度都明显不足。21世纪初,社会工作这个概念对于中小城市的街区管理者而言还是个新鲜词。由于街区管理者对此毫无头绪,加之他们在主观上也没有兴趣和精力去认真了解社会工作,自然无法与社会工作师生产生认知上的共鸣。
社会工作,我最初以为它就是社会上的基础工作,是政府管理工作和经济工作之外的工作。……这不就是咱们居委会正在做的事情吗?这也能办成了专业,真了不起哈!(访谈资料021,H社区主任J女士)
这番言论表明,街区管理者并不真正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含义,而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工作”又带有很大程度的想象成分。这种陌生夹带着想象的内心感受产生了对社会工作的轻视感。
其二,街区原有的治理制度安排自成体系,日常的运作机制早已成为“惯性运转”的常态。新生的社会工作不是这个基层治理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外来感带来的排斥也在所难免。
与你们学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接洽都是上级领导的安排。……你也知道,我们基层的事情很多,事务繁忙,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见谅啊!(访谈资料033,J街道办事处L副主任)
可见,由于街区基层政权与社会工作院系之间的合作协议是粗线条的,缺乏制度化的保障,这使得街区管理机构和实际管理者有了自由裁量的余地。在行政化的街居制管理方式下,街道和居委会实际上占据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主导地位,拥有几乎全部事权,且这些赋权具有法律和行政权威(葛道顺,2012:88)。既然是上级安排来实习的大学师生,那么自己的街区“听命”接待就是,至于如何落实双方合作的细节,则全凭本街区的需求和领导者个人的偏好来决定。
其三,可以说,社会工作是被高校师生“带到”地方上来的。地方原本指望借用高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本为自己增添帮手,但是他们发现这些冠之以“专业社工”的人与以往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完全不一样。
在基层,街区治理体系主要负责落实上级政府的政策,他们对于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态度也会随着上级政府文件的出台而发生了明显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基层政府开始把自己掌控的工作场域有限地让渡给社会工作。这包括有形工作地点(物理空间)的腾挪和无形的工作领域、服务对象的转接。
“你们这些大学生更愿意接触居民,问东问西。”“有时我们安排他们做一些上级交代的工作,他们却说自己的老师布置了任务,需要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配合他们开展活动。哈哈!我哪有时间配合他们啊。……后来,这帮子学生就自己在社区拉起横幅,主动给居民发宣传单,讲起反家暴的事情来了。影响多不好啊!”(访谈资料011,X社区主任W女士)
社区产生这样的抵触是有原因的:心怀专业使命的社会工作师生的行动方式和行动效果同街区原有的治理体系的目标、方式和他们对社会工作的期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让二者早期的互动显得不太融洽。
(三)礼节性隔离与仪式化表现
当然,社会工作与街区不和谐状态让双方都感到不舒服,而且这种尴尬局面也让各自的工作目标及其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既然合作还要继续,双方也就开始寻求沟通与协调。街区治理机构希望从高校得到支援,同时,又不想被社会工作主导街区的实际工作方向和内容。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事先了解学校教学实习安排的方式,对实习进行干预,以便重新掌控社会工作“在地化”进程。
咱们就是合作关系,彼此照顾对方的感受和利益也是应该的。……以后你们的学校计划要和我们协商一下,最好有个时间安排和内容简介,我们街道办分管社区的主任需要知道学校的目标和具体内容,这样方便协调嘛!”(访谈资料012,H街道办事处主任X女士)
社会工作与基层行政系统没有隶属关系,教学和专业实践有自己的规律性,加之高校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先天诉求,让街区治理部门的策略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街区又不好完全拒绝专业社会工作的“在地化”要求,所以采取了“礼节性隔离”的方式加以应对。所谓礼节性隔离,就是街区系统表面上接受社会工作进入自己的工作场域,口头答应为其提供教学实习甚至科学研究的便利,但这些都是礼节性的,态度客气却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落实。更为重要的是街区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决策过程并不会通知社会工作参与,他们无意将高校社会工作师生看成是“社会治理的实干家”,也无意让其提供决策建议,形成了实质上的隔离。
这就意味着,S组织在政治生活方面既要受到校内党组织的监督,同时也要向业务主管部门的党组织汇报工作。双重政治领导成为这类社会工作组织的一大特征。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时,政治管理的力度也随之加深加强。H区组织部在落实“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党建工作要求时,提出“党建引领的基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选择了S组织所在的J街道试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依托S社会工作组织,将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合并,将辖区内不同层次、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的党务群众工作和传统行政性社会工作(民政、文化服务和计生管理)统一纳入服务中心,并把辖区内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整合起来,由党群服务中心统筹资源合理调配。如此一来,无论是传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还是新兴的专业社会组织服务,都被纳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以党建为抓手,以民生服务为核心,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力量对社会工作的组织化控制。
我们的教学实践得想法子迎合居委会的喜好,他们才愿意为我们提供更多机会和实在的支持。居委会喜欢办活动,需要我们学生去撑场面,不同居委会之间还明争暗斗,因为街道办对他们有考核,活动声势越大,仪式感越强,他们的宣传效果就越好。(访谈资料001,社会工作系G老师)
3)提钻阻力及提钻行程:钻进机构在某些工况下,如在岩石中钻进,需采用抬钻的钻进策略,因此要求限幅机构能实现的提钻行程lu≥10 mm,且提钻阻力Fu<20 N。
当然,社会工作努力的效果是有限的:一方面,基层社会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居民对社会工作的认知都还不够深入,更谈不上诚心接纳和发自内心的需要。所以,社会工作想要在街区扎根的行动就缺少了社会基础,社会工作一厢情愿的努力效果必然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以投街区所好的形式进行的策略调整,使得其促进社会变革、实现社会公平的使命被暂时抑制。虽然,社会工作迎合街区日常工作的仪式性表现得到了街区一定程度的重视。但社会工作仪式化的努力是以牺牲专业价值诉求和专业技能含量为代价的,换来的只是取街区治理部门对社会工作的暂时性支持和有限接纳。可以说,这一时期社会工作的“在地化”是浅层次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三、嵌入:社会工作的依附性自主与政府的有限性管控
外来植入体(专业社会工作)和接受体(街区治理系统)在情感上都难以接受,再度调整成为双方的一种理性选择。当然,这一调整既是彼此的内在需求,也是外部环境使然。当国家与社会以一种并非平等的关系互动时,国家在这一关系中所处的主导性控制地位就会发挥更为重要的影响(管兵,2015:88)。只有当国家从中央开始力推各级政府职能转变时,社会组织的发展才会被“松绑”。外部环境的变化让社会工作嵌入到原有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成为可能。本文认同王思斌教授对嵌入概念的界定:“社会工作是嵌入原来的社会服务领域之中并谋求发展的”,或者说是“社会工作实际上是进入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原有领地,前者嵌入后者之中”(王思斌,2011:210)。这里所说的“原来的社会服务领域”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属于同一所指,即行政性、非专业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的‘嵌入’指的是它必须进入行政性社会工作占主导地位或基本覆盖的社会空间发挥作用”(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6)。
图中Rk和Xk分别表示等值内电阻及内电抗;PakQak和Pdk分别表示交流有功、交流无功和直流有功;Vak和θak分别表示交流侧的电压幅值和相位;Vck和θck分别表示等值内电势的幅值和相位;Vdk表示直流侧电压幅值。潮流方程如下:
嵌入与植入的区别在于,植入带有强烈的外来性质,没有与原有系统发生“有机”联系。社会工作在植入阶段只是在原有社会治理体系外部围观,做一些非核心的辅助性工作,而嵌入则是二者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直接联系,并在功能机制上建立了协作性关系,社会工作从外围开始逐步渗入到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内部发挥作用。在此时期,社会工作“在地化”不仅有了落地的实践,而且拓展出生根的机会空间。
(一)空间让渡与依附性自主
以上管理规定一方面让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更加规范化,另一方面,也让政府对社会工作组织的监管变得更加直接:政府制定准入门槛让那些符合政府需求的社会组织才有机会与其合作、为其服务。固定拨款让社会组织依赖其经济支持,短期合同期迫使社会工作组织尽可能地围绕政府短期执政目标设计自己的服务计划,从而诱导社会服务的短视性行为泛滥。近乎苛刻的财会制度让分散性、公益性和不易量化的社会服务难以充分体现其价值。计时和数人头的工作量核算方式让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服务存在“变质”的风险。繁杂的档案记录整理工作让社会工作者不胜其烦,填报政府要求的各类报表和宣传材料耗费了社会工作者大量本应该用于提高社会服务质量的时间和精力。整体而言,当项目制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体制(渠敬东,2012:114),并能为国家提供一种有效的总体性的控制机制的时候(黄晓春、嵇欣,2016:76),它则会更多地体现政府监管的需求与刚性规定,其细致的操作规范突出了行政管理的可视化、量化和效率提升的目标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工作类组织应有的社会性和公益性目标的实现。
不可否认,社会工作嵌入原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寻求发展机会是自身需求所激发的主动行为。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工作的嵌入也是行政管理体系逐步“松绑”的结果(肖小霞、张兴杰,2012:118)。在中国大陆,政府掌握主要资源,其他社会要素想要以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面貌出现并发挥作用时,首先需要得到它的认可和授权。社会工作“在地化”也不例外。S省传统政治意识较强,在对待社会组织地位与功能的定位上远落后于北上广深等发达省市,其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民间社会服务力量的壮大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一直到2015年前后,S省W市H区三级政府的民政和财政部门才单独或联合发布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施办法》《关于加快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修订)》等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了社会工作类服务组织的地位、作用和扶持细则,才给社会工作“在地化”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制度空间,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终于获得合法性授权,并在发展资金和资源上获得鼓励性扶持。
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需从问题开始;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启发式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独立思考,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初社会工作站办公场所就是在居委会一间大屋子里增加了一张桌子,不要小看这么一张桌子,它代表着位置,象征着政府对社会工作的合法性认可。后来,社会工作站的业务种类和范围都在扩展,居委会在办公场所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是给社工站匀出了一小间房。”“2016年,我们搬到了这里来,整个三层,1000平方米都是机构的办公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访谈资料010,社会组织孵化园总干事Z先生)
按行政村分,全县种植核桃的行政村共272个。其中种植面积6.7hm2以上的行政村105个,33.3hm2以上的行政村13个,66.7hm2以上的行政村2个,栽植面积最大的是段家镇李家垣村106.7hm2。
工作面积的扩大和办公环境的改善,是社会工作得到基层政府接纳的一个重要标志。伴随着物理空间的腾挪,基层治理单位在工作领域和管理服务对象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社会工作组织的正式“入场”。街区管理者把各类民生入户调查、慰老服务、托幼服务等任务繁杂的社会服务转交给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甚至希望社会工作组织接手社区的纠纷调解、上访户安抚和流动人口管理等令基层社会管理者都倍感棘手的问题领域。这类工作劳动强度大、服务时间长、投入成本高,同时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街区治理部门对于这些工作领域和服务对象虽然长期关注,但缺乏人手、精力和专业技巧。S机构的专业性强,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高,处理基层社会矛盾的能力较强,J街道办事处很快就与该机构达成合作协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让社会工作进入并逐步接手了传统的社区工作。
2.社会工作的依附性自主:体制依附与专业独立性保持
为了让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接更多的社会服务与管理职责,政府购买社会工作组织的服务成为各地普遍的做法。在市民社会算不上发达的W市,其社会工作组织自主筹措发展资金的能力严重不足。包括S机构在内,他们都不得不依赖于基层政府购买自己的服务来获取必要的活动经费和运营开支。很长一段时期,政府购买成为社会工作机构主要甚至是惟一资金来源。政府通常与社会工作机构签订购买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签),约定服务目标、服务对象和领域、服务达标与绩效考核等条款(多数情况下由政府决定这些条款的内容),进行项目化管理和招投标。从以上政府购买服务的三个特征来看,政府可以最大化地控制社会工作机构,让社会工作依附于政府来谋求发展。有研究指出,虽然用服务换经费的做法备受诟病,但广大社会服务从业机构也实属无奈。面对此等窘境,学者们在对策建议上只能呼吁式地提出“让政府主动放弃控制”的期待(赵一红,2012;张兴杰等,2013;管兵,2015;林磊,2017)。
本次研究发现,虽然在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中,社会工作对政府的依附不可避免。但是,某些比如具备高校背景的社会工作机构在处理“去边界化情境压力①2007年之后,国家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的建设,在党政机关办公空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专门给社会工作等社会组织划拨工作场所和办公空间实属难得。”时,并非毫无办法。他们凭借自身的优势,也在积极地寻求自主发展的空间。具体表现为:其一,依托高校背景注册成立的社会工作机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其骨干成员的体制内身份让基层政府无法将其归为“草根”。其二,高校背景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营运的先进且不断更新的专业理念、理论以及与实践结合的能力、娴熟的服务技巧是一般社会组织不具备的,也是基层政府最为需要的,这些特征让该类机构在功能属性上具有了不可替代性。其三,高校背景的社会工作机构的主要从业者视野宽、合作伙伴分布广泛,他们与境内外社会工作研究机构和实务部门的联系紧密,尤其与各类基金会联系紧密,具备了其他社会组织和基层政府无法企及的资源链接能力,这些合法的基金会在国内致力于中国公益和慈善事业的推动工作,同样在寻求本地的合作伙伴。很多基金会通过项目资助的形式向本地社会工作组织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让此类机构的资金来源变得更加多元化。凡此种种,都让高校背景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有了相对的自主性。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各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生理健康、情感职能、生理职能和生理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生理健康、情感职能、生理职能和生理功能评分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直到这时,周教授方才明白一切都是那个当导演的朋友搞的恶作剧。周教授心情一下颇不舒畅起来,气极败坏地走到院外拨通了那个导演朋友的电话,大声说,你怎么能这样么,玩笑开得太大了么。说完,像怀了深仇大恨似的,猛地摁了关机键。
可见,在嵌入发展阶段,社会工作对政府的依附不可或缺,这是由现存的社会治理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可以这么认为,社会工作依附式自主是组织对其所面对的“制度复杂性”的能动回应(王诗宗、宋程成,2013:50)。依附与自主之间的二律背反式的作用,促使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限制中主动寻求自主的生存空间,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扬长避短,在体制内外努力拓展相对独立发展的机会。
(二)政治规训与专业化纠偏
1.政治引导:掌控合法性的原生冲动
基层政府出于政治行政等方面考虑,在允许社会工作嵌入到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其的政治规训和管理。
组织控制是政府规训社会工作的基本形式。在国内,社会工作组织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后才具备合法开展工作的资格。在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文件出台之前,民政部门规定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类组织开展工作,必须登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要有挂靠单位和业务主管单位,且在同一行政区域内不能同时存在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民办非企业。S组织因为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挂靠单位而无法注册。寻找到单位愿意让其挂靠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先期在辖区内注册了民非企业,因此,S组织的成立又被拖后了几年。一直等到国家要求地方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类社会组织,专门出台指导性意见后,W市和H区才跟随出台了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配套文件。S组织终于得以正式在W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在国家没有完全赋予社会组织发展空间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已经通过“登记准入”的方式掌控着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当准入条件放宽,有资质和能力的社会工作类组织大量涌入社会福利服务领域,政治权力机关又制定了新的管理形式: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政治号召下,各类社会组织都要成立党支部。
我们跟民政局声明在校内已经成立了教工支部,有正常的组织生活的时候,民政局答复S组织依然需要成立支部,要把党的建设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访谈资料024,S组织支部书记H先生)
针对街区治理部门看似接纳实则隔离行动方式,社会工作也发展出了应对措施。考虑到最初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专业努力在现实的街区场域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社会工作采取仪式化的表现来努力地争取街区的支持。
政治规训的第二种形式是嵌入性监管。嵌入最初特指社会工作为了自身发展不得不寻求原有行政性社会工作体系的帮助,在现有社会福利体制内谋求生存空间,获得合法性的过程。等到社会工作日益嵌入原有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并获得民众认可后,国家力量的基层代理人又以有序发展和规范发展为由,开始谋求反向嵌入到社会工作和服务类社会组织之中,以便加强监管(尹阿雳等,2016:53)。一个时期内,社会工作的业务主管机关以孵化和帮助为理由,要求辖区内的社会工作组织,通过法定选举程序,让某些行政人员进入组织的决策层,成为其组织核心成员。
“社会组织孵化园的总干事开始一直是由区民政科的一名Y姓副科长兼任的,总干事的职责就是拟定机构的发展目标和规划,统筹管理机构日常事务,定期召开管理层会议并未机构拓展发展空间谋求发展资源。Y总干事在民政局工作,他能为机构初创时期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访谈资料010,社会组织孵化园总干事Z先生)
表面上看,社会工作类组织主要负责人由政府工作人员兼任,可以为社会组织在发展起步阶段带来一些和实惠,但这种过于密切的联结形式在实质上却依然是一种政治规训:业务主管机关派驻工作人员,是其对民间组织的信任缺乏的表现。尽管这类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时已经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但还是不如派遣自己的工作人员介入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和决策中来的更为直接。
“影子主任”是嵌入性监管的另外一种形式。在基层,居委会主任对社会工作类组织的运作及成效至关重要,被社会组织称为自己社会工作组织的“影子主任”。①根据组织社会学的观点,边界是指一个组织终止的地方和该组织所处环境开始的地方。边界存在于组织与环境之间,是组织生存的基础。边界描述了不同组织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与其根深蒂固的生长土壤密不可分。原则上,社会服务组织在开展服务过程中要求其与政府部门之间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及清晰的职能边界。但是,在公共服务合约外包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极不对称,从而使社会组织在界定自身和建构同政府关系时存在规则运作空间,产生了“去边界化的情景”。参见黄晓星,杨杰《社会服务组织的边界生产——基于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社会工作如果完全脱离居委会主任的支持,社会工作组织则无法驻扎社区,无法调动社区资源,无法有效组织居民参与活动。而社会工作组织获得居委会的支持,则需要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居委会的既定任务相结合,这时居委会主任对社会工作组织的决策就具有足够话语权。很多时候,居委会主任会把社区日常管理和行政工作任务交由社会工作组织协助完成,而这些工作与社会直接服务和公益活动的联系不太紧密,甚至会打乱社会工作组织的工作计划,拖延其日常服务的进度。社区主任一旦成为社会工作组织的影子主任②影子主任,某些社区居委会为主作为其辖区内社区服务中心实际“控制人”的戏称。参见尹阿雳,赵环,徐选国.双向嵌入: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新视角[J].社会工作,2016(3):54.,那么社会工作组织的实际控制权也会无形中发生转移。社区主任行使了社会工作组织负责人的“职权”,也就意味着传统行政工作和基层管理的“返场与再生产”。行政管理与专业社会服务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行政力量有了深度管理社会组织的机会。
政治引领的第三种形式是对社会工作组织管理的项目化和考核的行政化。正如前文所述,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在财务上“控制”社会工作组织。在这一考核形式中,政府专门针对此类财政支出制定了绩效考核体系。其中,最关键的也是最能体现政治引领的方式就是购买服务的项目化管理。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治理技术,社会服务项目化具有公开透明化、合同化、绩效可评价化等特征(侯利文,徐选国,2017:50-51)。在W市及H区的实践中,一般性社会工作组织想要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首先要具备资质(除了一些必须的法定资质条件外,社会组织还需获得业务主管部门评定3A以上级别才可以参与竞标);一旦社会工作类组织获得政府购买其服务的资格,则需与政府签订合同(合同里详细规定专款专用、核算和配套资金数额、受益保证以及合同有效期等内容);在履行合同期间,社会工作组织需要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制度并接受政府定期检查(支付审批制度、资金的公益服务类使用范围、资金使用的银行票据业务形式以及严格的会计核算制度等);绩效考核的可视化与量化(要填写受益人、监护人以及两名以上的证明人的身份信息与联系方式备查、救助方式和救助金额、回访记录、项目评估报告、项目收支细目和文宣材料等)。
1.发展空间的让渡:政策空间松绑与物理空间腾挪
2.社会工作专业化纠偏:基于知识与能力的能动反应
心怀社会革新使命的社会工作在被“引领”的同时,从没放弃专业化“纠偏”的努力。在社会工作领域,“专业化”的讲法挺多,被广泛认同的一种说法是格林伍德在其《专业的特质》中提到“专业”的五个条件——理论体系、专业权威、专业认可、专业价值和专业文化。一个成熟的专业应该具有完整且系统的、能够支撑其行动的理论体系;社会对其专业活动充分接受并给予高度认可和评价;在其内部上述活动已经建立起专业的权威,公认的专业能力成为该领域活动的重要评价标准;从事该活动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行业内部对其成员有明确的约束性、系统化伦理准则;以上所述在社会和行业内部都已经形成亚文化共识,从业者有高度认同的价值观和较为一致的专业行为模式(格林伍德,2012:14)。社会工作面对各种带来的困扰与挑战,不断调整策略,努力地进行着“专业回归”的纠偏行动。
此外,电视新闻记者还应当积极步入到“VR、AR、人工智能+新闻”的试水队列中,利用创新技术,提高新闻节目的感染力和现场感。移动直播就是高新科技引入电视新闻传播的一种大胆的尝试,在文字、图片等普通信息载体之外,移动还汇集了H5、直播流等多种播报形式,采用现场报道与“碎片化”上传相结合的工作流程,使受众通过界面更新不断获取新鲜资讯,既提高了用户参与感,也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高效性。
汉朝有个叫“乐府”的机构,派出官员到各地搜集乐曲民谣,并且培训专业的乐舞演员进行演出。乐府既搜集、整理民间“俗乐舞”,也创作宫廷“雅乐舞”,朝廷常举办盛大的乐舞演出。
科学化包装。在科学主义深入人心的今天,专业性与科学性密不可分。凡是被冠之以科学的事物,都自然具有了理论权威性,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接受。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论调:任何“非科学”都是非理性的,是很容易被归结为“愚昧迷信甚至是反动”的行列遭到广泛抵制和打击。因此,专业社会工作立足现实,迫切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体系的科学化”。科学化一方面以系统化、抽象化、高度学术化的理论面貌呈现自身,另一方面充分借鉴传统学科专业的话语体系和实践形态宣传自己的应有价值。
“现在的基层治理官员和社会管理者的文化水平较高,给他们介绍社会工作是什么、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你得有哲学的思辨与深度,法学的规范尺度和权威性,还得有类似经济学的数据模型做支撑,更要有临床心理学洞察人心和系统治疗的能力。……总之,得让社会工作听起来相当科学才行。”(访谈资料016,社工系C老师兼S组织督导)
高校背景的社会工作组织成员大多受过正规和长期的学术训练,学养根基扎实,善于将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概括。同时,教师的素养让又其长于将理论文本转化为话语演说,进行通俗化传播。通过给政府官员和行政业务主管、基层治理负责人座谈、授课和日常交流,向上述官僚群体介绍社会工作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构架、基本概念、学术名词,以展示社会工作“深厚”的理论底蕴,努力改变着管理者眼中社会工作不够专业的“草根与民间底色”。当然,理论的抽象和枯燥性决定了社会工作者不能一味向政府官员灌输,而是需要从科学性与趣味性的结合上下功夫。社会工作的理论范式可分为三大类型: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和批评主义范式(文军,2012:125)。出于“包装”的考虑,多数时候,专业社会工作宣讲的理论以实证主义居多。这就造成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危机干预学说大行其道。现场心理小测验往往成为社会工作宣讲惯用的开场白,用来“暖场”“破冰”,而复杂的心理测量表则能起到“知识炫技”的作用,最终则是为专业的科学性做注脚。
本刊研究与试验报告的印刷版一般为3~4页,约5000~6000字;综述与评论的印刷版一般为4~8页,不超过8000字。
专业反渗透。尽管在基层治理部门看来,他们较为有效地掌控着社会工作的发展节奏。随着嵌入时间的推移,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政权的接触越来越多,彼此的了解也日益加深,高校资源与地方资源的结合点变多了,彼此的“互嵌”的成分也就越多。当基层政府看到因社会工作的参与而提高的社会治理实效时,他们愿意并希望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项目。这就为社会工作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树立专业权威提供了政治机遇。
2017年以来,H区逐步推广社会组织孵化工作,需要对全区的镇街进行规划,制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行业标准,并对社会组织孵化、出壳和独立运作进行评估,这一切都需要有经验有能力的机构辅助其完成。作为本地唯一拥有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S高校,其社会工作系注册兴办的S社会工作组织就成为不二之选。基于以往的经验,社会工作组织及其成员的研究者和咨询专家的身份一旦被基层治理政权接受,那么社会工作就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在合适的时候还能进入政府规划的决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有关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制定与评价。
“参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内部讨论会时,我们争取发出社会工作的声音。当政府提出的要求和设想超出我们自身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轻易推辞,我们会将省外、甚至境外的合法优质资源链接过来,给地方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建议……只有让政府看到实效,才有机会更多的进言。”(访谈资料001,社会工作系G老师兼S社会工作研究与服务中心总干事)
这表明,社会工作反渗透策略并不与政治引领做直接、面对面的对抗,而是采取迂回式路径,用政府的政策和资金发展壮大自己,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政府对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认可,逐步将自己对政府的资金政策依赖转化为政府对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和技术的依赖。“政治依赖与专业依赖”并存让社会工作同基层治理政权的力量呈现出微妙的“均衡态”。
专业区隔与统领。仅仅依托高校的社会工作组织依然无法与强大的基层治理体系建立对等的伙伴关系。社会工作需要在专业文化和专业价值层面寻求“同盟者”。一般的民间机构缺少专业知识和技能,更没有太多外部资源,整体上处于原子化状态,更加难以与行政力量博弈。加之现有的行政监管和市场竞争机制让原本就缺乏合力的民间社会组织变得越发疏离。他们由于在业务、资源、甚至骨干精英等方面存在同质化情况,导致社会组织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甚至一段时间内社会组织为了一个政府购买项目发生相互诋毁、拆台等“同行相互倾扎”现象。随着S社会工作组织的出现,上述不利于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事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改变民间社会组织“一盘散沙”的局面第一步就是树立社会工作在行业内部的权威性。社会工作在多个场合不断重申“社工、义工和志愿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向社会组织宣讲社会工作与一般性助人活动和慈善活动之间的区别。从而在行业内部营造出“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分,衬托出社会工作专业性。当然,一味的区分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并不能整合民间力量。社会工作还需要对其进行组织文化和能力建设,以实效吸引社会组织。民政部门委托S组织对全区社会服务类组织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特别是社会工作师的职业资格考试辅导,让社会工作者能近距离接触社会组织从业者。高校教师出身的社会工作系统化的知识讲解和深入浅出的价值阐释,让社会组织从业者耳目一新,而接地气的案例分析和颇具技巧的现场教学更是让社会组织佩服。社会工作还为不同类型的社会服务组织设计其发展目标、实施计划或免费培训工作人员,和为其申报政府购买项目服务低收费出谋划策。这些做法让社会工作的权威逐步形成并得到不断巩固。社会组织的整体力量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改变,逐步形成围绕S组织的自发社工组织联盟。S组织的核心骨干成为了社会组织的精神导师和实践导师。社会工作的理念在社会组织中得以传播,社会工作的技能在社会组织手中得以转化,社会工作的愿景目标通过专业联盟得以更好的实现。一旦社会服务力量的联盟和统领关系得到确定和维持,社会工作的嵌入也就变得更加深入和稳固。
四、融入:在地化的完善与发展
融入,在汉语中被解释为融合、混入、混合,是指一类事物融合到另一类事物中成为一体,最终共同发挥优势、承担职能的过程(陆士桢,漆光鸿,2017:25)。以此为标准,W市社会工作“在地化”程度尚未进入到融入阶段。换言之,以S组织为代表社会工作还没有与本地社会治理与服务体系完成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本文在此只是对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服务体系能从“深度嵌入”走向体制、机制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出探讨。
(一)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长期以来,基层治理意识落后、治理能力低下、治理方式单一、治理效果差强人意,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魏来、胡莉,2016;刘建平、陈文琼,2016;吴永红、梁波,2017)。究其原因,基层治理主体体系中的社会主体虚化(虚置)和基层治理能力弱化是两个根本所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工作等关键社会性主体未能充分融合到现有治理体系并发挥应有作用的负面后果。对此,中央有着清晰地认识,不断提出关于加强和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主张。党的十八大提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党的十九大则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针对社会治理水平给出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具体标准。党的纲领性文件逐步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路线图清晰地呈现出来。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真正的多元参与,社会工作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参与主体。以社会工作组织为代表的社会服务组织以其专业理念和专业服务为支撑,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依法依规开展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它们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主体参与进来是治理现代化对必然要求。
针对富集物酸泥中杂质含量较高,本文探讨了酸泥中碲的分析测定方法,通过硝酸溶解试样,经过硫酸冒烟、加入亚铁氰化钾溶液、静置过滤消除干扰元素,滤液直接测定,减少和优化了分离条件,建立了溴化碲分光光度法测定碲的分析方法,该方法简便快速,不需要特殊昂贵的试剂和仪器,测定结果准确可靠,便于普通实验室使用。
(二)融入的可能性分析
想要实现社会工作真正意义上的“在地化”,让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体系充分融合,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包括价值理念目标上的亲和、角色定位上的耦合及目标功能上的匹配等。
价值理念上的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治理的核心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为人民谋福利初心不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价值承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要求。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的目标自然也是一切为了人民。对于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基层治理权力来说更是如此。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历经百余的发展,对自身的核心价值也从未改变:社会工作一直以倡导社会变革为目标、以推动社会公平为己任、以实现人民福祉为价值原则(沈黎,2009:46)。在中国,社会工作作为最通俗的“助人事业”,始终“以人为本”关注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于由此产生的困境给予最大的同情和洞察。尤其是当这些困境导致社会不公的时候,社会工作以提供专业化服务形式积极介入,试图通过提升人的能力和改善环境的方式,帮助陷入困境中的人们脱离困境并增进其福祉。社会工作价值源自基层社会,其价值践行更是扎根于基层社会,服务基层的民众是社会工作从未改变过的价值诉求。可见,以“助人”为使命的专业社会工作完全融入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治理体系中,这在彼此的核心理念上不存在任何障碍。
本文利用轴压屈曲试验平台进行了圆柱壳、开孔圆柱壳、含补强件圆柱壳轴压屈曲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轴压屈曲临界载荷开孔圆柱壳最小,含补强件圆柱壳次之,圆柱壳最大,与模拟结果规律一致。圆柱壳开孔导致轴压临界载荷下降,可通过补强方法提高临界载荷。可为壳体屈曲设计分析提供参考价值。
角色定位上的耦合。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政权在彼此的角色认知和定位上越接近,二者的越有可能进行深度融合。二者在角色关系上存在三对耦合关联。一是政策执行者与问题发现者。以镇街和社区为代表的基层治理单元是社会治理政策的最直接执行者。他们履行着把握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和防范风险的职责。与之相对应,社会工作组织及其从业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首先扮演的是特定社会问题发现者的角色。社会问题的洞察、梳理和归纳分析需要既能扎根基层,贴近民众,又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组织和人员,而社会工作者恰恰擅长此道。社会工作发现的问题,大多都是基层社会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问题。二是服务的提供者与服务过程的监督者。社会工作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服务提供者,可以为社区中有需要的个人或群体提供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等直接服务,也可以为其提供资源链接和政策咨询等间接服务。这些服务都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也最能体现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服务宗旨。当然,基层治理单位将众多为民服务工作交给社会工作组织开展,它持续承担服务与治理过程的监督者角色,通过制定标准流程、中期考核等形式严把社会服务的质量关口。三是,政策倡导者与效果评估者。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和提供社会服务时还会将其所接触的大量案例进行归纳整理,把这些在基层社会发现的、凭借一己之力又无力解决的难题及时向基层组织反馈,积极向决策机构建议建言,做政策的倡导者。同时,基层社会治理单位通过对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评估,检验服务项目的治理效果;通过征集社会工作的建议,及时向上级反馈政策建议,以便在治理体制、机制乃至法制上有所改进。
目标与功能上的匹配。随着中国社会变迁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城市社区中利益主体的异质性程度越来越高,居民之间、居民和基层组织之间、居民与驻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都难免产生纠纷和冲突。而现实中,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单纯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了基层治理效果差强人意。民众需求的强烈性和基层治理目标任务的紧迫性都呼唤新的治理主体的参与并发挥功能。基层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工作的根本目标就是解决基层的各种社会矛盾,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效性。引导社会工作等服务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让其发挥社会协同的功能效应,则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打造“社会化和专业化”社会治理新格局核心内容。社会工作致力于推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此促进社会公平的事业,就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工作以其充满人文关怀的专业化实践,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教育,动员了社区居民,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居民个体的权利意识、互助意识和归属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通过扎根基层的社会组织培育和孵化工作,以引领、示范和增能的方式,扶持公益慈善和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让他们逐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最为关键的是,社会工作直接进入基层社会,面向广大居民开展直接的专业化服务,通过心理咨询、行为矫治、家庭辅导、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等形式,帮助居民疏导不良情绪、改善生活状况、增进理解和互助,这又在功能效果上为基层社会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营造和谐社会氛围、提供民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可见,二者在目标和功能上的匹配性同样明显。这些都为社会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五、余论
社会工作想要真正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落地生根并开枝散叶”,还需要克服其在植入和嵌入阶段已经出现的障碍和困境才行。从内部看,首先要克服的困境是如何妥善处理“活命与使命”的矛盾。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即便是背靠高等院校“这颗大树”,社会工作也不得不暂时搁置或者策略性的改变自己的“社会公平正义推动者的使命”,向权力、市场和技术等强大力量妥协和低头。刻意装扮的“科学化”有让社会工作迷失自我,存在变成医务工作者或者心理咨询师等个体主义的倾向。而为了获取政府购买的支持而日益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做派,让社会工作组织存在蜕变成“二政府”而不再是基层民众代言人的危险。至于项目化的管理主义偏好,更是让社会工作服务有深陷市场化的盈利逻辑所主导的泥潭不能自拔的风险。更遑论,过于重视可视化的绩效考评还让社会工作进入一种慢慢忘记“服务民众、推动公平”的初心而不自知的险境。从外部看,社会工作的“在地化”需要理顺“国家—社会”的关系,从法律和政治体制上明确和保障政社关系的协同性。目前,无论是学界讨论还是地方实践,对于社会工作是追求与政府平等的地位还是作为政府的隶属存在,依旧没有定论。一味地照搬欧美国家的“政—社平等模式”甚至倡导“大社会小政府治理模式”的论调只会加重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这也会让社会工作无奈地停留在“依附和嵌入”阶段,难有进一步的发展。目前看,在体制上应该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制,在机制上应该落实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由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较为现实的发展路径。而这一切都需要有法律的规制和确认,才能让社会工作的融入和完全“在地化”置于制度和法律的保护下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葛道顺,2012,《社会工作制度建构:内涵、设置与嵌入》,《学习与实践》第10期.
管兵,2015,《竞争性与反向嵌入性: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公共管理学报》第3期.
侯利文、徐选国,2017,《社会、历史与制度:迈向社会工作发展的新阶段》,《社会工作与管理》第17卷第6期.
黄晓春、嵇欣,2016,《技术治理的极限及其超越》,《社会科学》第11期.
李靖、李春生,2017,《强社区抑或弱社区: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反思——以A省多地撤销街道办改革为例》,《学习论坛》第11期.
李迎生、方舒,2010,《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4卷第3期.
林磊,2017,《治理语境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研究的再思考》,《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刘建平、陈文琼,2016,《“最后一公里”困境与农民动员——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第2期.
刘威,2011,《“一个中心”与“三种主义”——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再出发》,《中州学刊》第3期.
陆士桢、漆光鸿,2017,《融入——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探析(下)》,《中国社会工作》第31期.
马跃,2011,《宏观工作体制和乡镇应对策略——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解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
欧内斯特·格林伍德,2012,《专业的特质》,张剑、罗晓辉、秦晓峰译,载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渠敬东,2012,《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沈黎,2009,《社会工作国际定义的文本诠释》,《社会福利》第5期.
史柏年,2012,《如何填补?社会工作教育先行之缺!》,《中国社会工作》第30期。
史柏年,2013,《教师领办服务机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理性选择》,《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宋言奇、余力,2016,《“嵌入”视角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2期。
王诗宗、宋程成,2013,《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王思斌,2011,《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王思斌,2013,《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跨域实践》,《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卫小将,2014,《土生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之构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魏来、胡莉,2016,《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特征、发展困境与化解之策》,《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
文军,2012,《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及其发展趋势》,《江海学刊》第4期。
吴永红、梁波,2017,《制度结构、非均衡依赖与基层治理困境的再生产——以居委会减负悖论为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肖小霞、张兴杰,2012,《社工机构的生成路径与运作困境分析》,《江海学刊》第5期。
肖小霞、张兴杰、张开云,2013,《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异化》,《理论月刊》第7期。
殷妙仲,2011,《专业、科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十年的三个迷思》,《社会科学》第1期。
尹阿雳、赵环、徐选国,2016,《双向嵌入: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新视角》,《社会工作》第3期。
张超,2017,《身份焦虑:社会工作机构的合法性困境及其突破》,《社会工作》第1期。
张兴杰、肖小霞、张开云,2013,《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检视与未来政策选项》,《浙江学刊》第5期。
张昱、孙志丽,2010,《社会工作的社会建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2期。
赵一红,2012,《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分析》,《社会工作》第4期。
郑广怀、向羽,2016,《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及启示》,《社会工作》第5期。
朱健刚、陈安娜,2013,《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项目基金:山东省教学改革研究面上资助项目“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多中心协同培养模式研究”(B2016M011)的中期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9)02-0003-15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9.02.001
张乐,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博士生导师(威海 264209)。
编辑/程渔朗
标签:社会工作论文; 社会论文; 组织论文; 基层论文; 政府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社会工作》2019年第2期论文; 山东省教学改革研究面上资助项目“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多中心协同培养模式研究”(B2016M011)的中期成果论文; 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论文;
